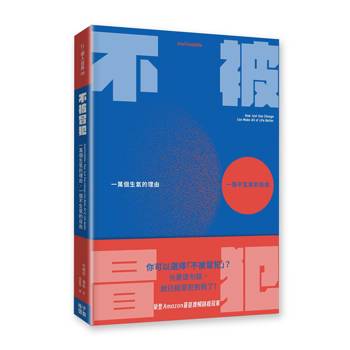第一章:不被冒犯——荒唐的想法
好的,這可能是你聽過最愚蠢的事情,但我還是要說:
你可以選擇「不被冒犯」。
我其實是在一次商務會議上聽到有人這麼說的。這讓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有幾個:(1)我之前從未這樣想過;(2)我到現在還記得一些會議的內容;(3)我竟然被邀請參加商務會議。
我記得那個人說,不被冒犯是我們可以做的一個選擇。
對啊,當然啦,選擇不被冒犯。你知道的,選擇嘛,說得好像這真的是由我們決定的一樣。
光是這句話就已經冒犯到我了。
我查了「冒犯」這個詞的定義,所有字典都提到憤怒、怨恨相關的概念。因此,當我在這本書寫到這個詞時,就是這個意思。
冒犯還有另一個定義,是指感官上的衝擊和不舒服,例如我們前幾天剛嘗試自製燒烤醬,結果大家一致認同這味道非常冒犯人……但這不是我們在這本書要討論的。
我想談的是被得罪,以及自以為有權對某人生氣的想法。當然,有時候對某人發「義怒」也不為過,對吧?有時我們的憤怒是有正當理由的……
那個人在商務會議上的一席話確實引發我去思考,因為他顯然錯得離譜。而且,既然我身為一個基督徒,不就理應為了某些事情對人感到憤怒嗎?被冒犯不也是基督徒的日常嗎?
所以,當時我做了任何一個理性、公正、靈性成熟的人會做的事情:我仔細查考聖經,找出可以駁倒他的經文,在邏輯上擊敗他,讓他屈服,然後—你懂的—講贏他!
問題來了:如今我認為他說得對。不被冒犯不只是我們可以做的選擇,更是我們應該做的選擇。
我們應該放棄被冒犯的權利,這意味著放棄憤怒的權利。當我們這樣做,是一種非常討神喜悅的犧牲。它一拳擊倒我們的驕傲,不僅迫使我們在思想上謙卑,更使我們實際上變得謙卑。
我曾經認為基督徒感到被冒犯是必須的,現在我認為我們應該成為這個繞著冒犯旋轉的星球上最令人耳目一新、最不容易被冒犯的人。放棄我們憤怒的權利能使我們脫離自我中心,反而以他人為中心。當我們開始這樣生活時,一切都會改變。
事實上,這甚至不是「放棄」權利,因為這種權利本來就不存在。我們被教導要饒恕,就意味著憤怒必須消失,無論我們是否認為自己的憤怒是「正義」的。
我知道,這個想法在很多人聽來可能有點荒唐,甚至難以認同。彷彿我已經聽見有人在心裡嘀咕:「這也太蠢了吧,我真的無法接受。」我對這種微妙的心聲有敏銳的雷達,我都感覺到了。
也有不少基督教文章說我錯了。典型的例子是像這篇來自一個線上靈修材料的文章,談到憤怒這件事,作者給了一個符合主流的觀點:憤怒有時正是我們「應該有」的情緒!
憤怒其實也有它正面的價值,甚至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少了那股怒氣當推力,我會很懷疑我們能否完成任何有果效的事。
沒有憤怒,我們就無法完成任何有果效的事?包括,寫靈修心得?
以下是另一個例子,說明我們如何用現在流行的「憤怒文化」,來重新解讀原本的聖經經文: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以弗所書4:26,和合本)
去吧,發怒吧。你生氣是對的—但不要用你的憤怒作為復仇的燃料。(以弗所書4:26,MSG譯本直翻)
你注意到了嗎?我很喜歡尤金.畢德生(Eugene Peter¬son,英文信息本聖經的作者),但是……「你生氣是對的」?天啊大家,原文中可沒有這樣寫。這是新版本,我猜你搞不好更喜歡這版。
保羅在幾節之後就寫道:「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以弗所書4:31)畢德生的翻譯方式真是令人驚訝,我們竟然看到「你生氣是對的」?
為什麼涉及這個問題時,我們用這種方式解讀聖經?
為什麼當我在我的廣播節目中談到憤怒時,這麼多信徒立即引用「生氣卻不要犯罪」這句經文,卻跳過這段的其餘部分?為什麼要忽略後面那句「除掉一切惱怒和苦毒」?
保羅很清楚地說,是的,我們會生氣,在所難免,畢竟我們是人類,但我們必須除掉它。所以現在就處理它吧,我們沒有憤怒的權利。
你可能會問一個很合理的問題:但神不是也會發怒嗎?耶穌不也會生氣嗎?
對此,我經過深思且具有神學素養的回答是:嗯,當然。
是的,神可以憤怒。不只這個,還有其他神可以做但我們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說:報仇,那是祂的專屬權利。祂不准許我們報仇也很合理,原因在於:我們與我們發怒的對象一樣有罪。但是神呢?祂沒有。
此外,神也有權柄審判人,但我們沒有。祂的判決是可信的,因為祂與我們很不一樣,祂完美無罪。祂的憤怒也是可靠的,因祂的性情跟我們很不一樣。
神愛你,在祂眼中你很特別,但抱歉……你不是神。
我們不太願意承認一件事:就是我們其實蠻喜歡生氣的。當然,我們不喜歡那些讓人生氣的事本身,但我們很喜歡那種「逮到別人出錯」的感覺。當某某做錯了什麼,假設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憤怒給了我們一種道德優越感。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稱之為「正義的憤怒」。我們認為這是道德的、好的。
問題是,指向某人的「義怒」相當狡猾。事實證明,我往往認為我的憤怒比其他人的憤怒更正義。這是因為我認為自己非常正確。我支持我自己,我的論點在我看來特別有說服力。
不巧的是,有句箴言說:「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箴言16:2)
不只是我,顯然所有的人都覺得自己很有道理。我的憤怒是義怒,因為我很明顯是對的,而別人是錯的。我看自己所行的都很純正,永遠都是。
這時候,每個人的憤怒似乎都是對的。憤怒是一種席捲而來、看似合理的情緒,讓我們覺得自己被剝奪了應有的東西。但是情緒就是情緒,並不是理智的批判性思維。憤怒不會停下來,但我們必須停下來,並且質疑它。
我們人類非常擅長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並改寫故事,把自己放在不公不義的中心(之後會有更多討論)。我們可以將對某人(例如任何威脅我們的人)的憤怒或仇恨重新描繪成一幅看起來正義的藝術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耶穌的教導中,沒有任何「好吧,如果某人真的是個混蛋,那麼你很有資格覺得被冒犯」的容許。耶穌直接告訴我們要饒恕,甚至—尤其是!—那些很合理的不滿,以及真的會令人反感的事情。
這正是重點所在:你認為有充分理由發怒的那件事,正是你被呼召去饒恕的。恩典不是給那些配得的人;饒恕意味著不再懷有怨恨,放下怒氣。
憤怒非常容易,它是我們的預設模式。
愛非常困難,愛根本是一個神蹟。
今天我在《Inc.》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憤怒和馬丁.路德.金恩的文章。作者引用了金恩的自傳中寫的:「你不能心懷憤怒。」但還不只這樣,即使在受到攻擊時,金恩也說,我們應該愛我們的敵人。2
作者像往常一樣,將金恩這番話轉成某種程度對憤怒的認可,說我們應該確保以有建設性的方式使用憤怒。這樣說無可厚非,但我不同意作者的觀點。這篇文章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中一個是作者聲稱同意馬丁.路德.金恩的觀點,卻說出了幾乎相反的話。他把金恩的話稀釋得不那麼極端,也不那麼美了。
金恩說:「我不能心懷憤怒」,而作者說:「我同意。讓我們以有建設性的方式使用憤怒!」
我覺得我們常常也會這樣解讀耶穌的教導。像是祂說「要愛你的仇敵」、「為逼迫你的人禱告」,我們表面上點頭,心裡卻默默加一句:「但說真的,生氣是有道理的啦。」
我們對使徒雅各也是如此,他明明在聖經中清楚表示,憤怒不會產生神希望我們具備的那種義:「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1:20)
我們在讀保羅的教導時也會這麼做,像是他列出的那些罪,比如歌羅西書3章8節:「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
我們對「憤怒」這段其實不太買單。當保羅說要把怒氣從生命中除去時,我們照常會默默補上一句:「當然啦,除非那是有建設性的憤怒。」
但說真的,我沒聽過有人把同樣邏輯套在這節經文的其他教導。誰會說:「要除掉污言穢語—除非罵得很合理」或是「別說傷人的話—除非他真的活該」?
說穿了,我們其實還蠻喜歡自己在生氣的感覺,因為在某個程度上,我們覺得自己超有道理。
當聽到我對憤怒的觀點時,一位廣播聽眾告訴我:「我不懂,難道我們不應該對那些在新聞裡毆打遊民的人感到憤怒嗎?」
鑒於我們應該「除去一切的憤怒」,我的看法是:憤怒會發生,畢竟我們是人類,但我們不該一直懷有它。像金恩牧師一樣,我們看到不公不義之事,應該為之悲傷,並採取行動反對它—但不能懷抱怨氣、惡意和憤慨。我希望我們有足夠的動力去保護無辜者和弱勢群體,但不應該是由憤怒來驅動我們。
尋求公義,愛好憐憫,是不必懷著憤怒也能做到的。人們說我們必須憤怒才能對抗不公正,但我發現,最棒的警察不會在憤怒中行使職權,最好的士兵也不會在憤怒中執行勤務。
憤怒無法增加判斷力。
是的,只有神有能力做到公正又憤怒。如果我在一位人類法官面前受審,我肯定會希望他在判決時沒有挾帶怒氣。
當我說我們沒有權利懷有憤怒的時候,有些人認為我瘋了。也許我是瘋了。起初,我也很討厭這種想法。問題是,現在我希望我是對的,因為這樣會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而我好像也更能理解耶穌的心了。
好的,這可能是你聽過最愚蠢的事情,但我還是要說:
你可以選擇「不被冒犯」。
我其實是在一次商務會議上聽到有人這麼說的。這讓我印象深刻的原因有幾個:(1)我之前從未這樣想過;(2)我到現在還記得一些會議的內容;(3)我竟然被邀請參加商務會議。
我記得那個人說,不被冒犯是我們可以做的一個選擇。
對啊,當然啦,選擇不被冒犯。你知道的,選擇嘛,說得好像這真的是由我們決定的一樣。
光是這句話就已經冒犯到我了。
我查了「冒犯」這個詞的定義,所有字典都提到憤怒、怨恨相關的概念。因此,當我在這本書寫到這個詞時,就是這個意思。
冒犯還有另一個定義,是指感官上的衝擊和不舒服,例如我們前幾天剛嘗試自製燒烤醬,結果大家一致認同這味道非常冒犯人……但這不是我們在這本書要討論的。
我想談的是被得罪,以及自以為有權對某人生氣的想法。當然,有時候對某人發「義怒」也不為過,對吧?有時我們的憤怒是有正當理由的……
那個人在商務會議上的一席話確實引發我去思考,因為他顯然錯得離譜。而且,既然我身為一個基督徒,不就理應為了某些事情對人感到憤怒嗎?被冒犯不也是基督徒的日常嗎?
所以,當時我做了任何一個理性、公正、靈性成熟的人會做的事情:我仔細查考聖經,找出可以駁倒他的經文,在邏輯上擊敗他,讓他屈服,然後—你懂的—講贏他!
問題來了:如今我認為他說得對。不被冒犯不只是我們可以做的選擇,更是我們應該做的選擇。
我們應該放棄被冒犯的權利,這意味著放棄憤怒的權利。當我們這樣做,是一種非常討神喜悅的犧牲。它一拳擊倒我們的驕傲,不僅迫使我們在思想上謙卑,更使我們實際上變得謙卑。
我曾經認為基督徒感到被冒犯是必須的,現在我認為我們應該成為這個繞著冒犯旋轉的星球上最令人耳目一新、最不容易被冒犯的人。放棄我們憤怒的權利能使我們脫離自我中心,反而以他人為中心。當我們開始這樣生活時,一切都會改變。
事實上,這甚至不是「放棄」權利,因為這種權利本來就不存在。我們被教導要饒恕,就意味著憤怒必須消失,無論我們是否認為自己的憤怒是「正義」的。
我知道,這個想法在很多人聽來可能有點荒唐,甚至難以認同。彷彿我已經聽見有人在心裡嘀咕:「這也太蠢了吧,我真的無法接受。」我對這種微妙的心聲有敏銳的雷達,我都感覺到了。
也有不少基督教文章說我錯了。典型的例子是像這篇來自一個線上靈修材料的文章,談到憤怒這件事,作者給了一個符合主流的觀點:憤怒有時正是我們「應該有」的情緒!
憤怒其實也有它正面的價值,甚至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少了那股怒氣當推力,我會很懷疑我們能否完成任何有果效的事。
沒有憤怒,我們就無法完成任何有果效的事?包括,寫靈修心得?
以下是另一個例子,說明我們如何用現在流行的「憤怒文化」,來重新解讀原本的聖經經文: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以弗所書4:26,和合本)
去吧,發怒吧。你生氣是對的—但不要用你的憤怒作為復仇的燃料。(以弗所書4:26,MSG譯本直翻)
你注意到了嗎?我很喜歡尤金.畢德生(Eugene Peter¬son,英文信息本聖經的作者),但是……「你生氣是對的」?天啊大家,原文中可沒有這樣寫。這是新版本,我猜你搞不好更喜歡這版。
保羅在幾節之後就寫道:「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以弗所書4:31)畢德生的翻譯方式真是令人驚訝,我們竟然看到「你生氣是對的」?
為什麼涉及這個問題時,我們用這種方式解讀聖經?
為什麼當我在我的廣播節目中談到憤怒時,這麼多信徒立即引用「生氣卻不要犯罪」這句經文,卻跳過這段的其餘部分?為什麼要忽略後面那句「除掉一切惱怒和苦毒」?
保羅很清楚地說,是的,我們會生氣,在所難免,畢竟我們是人類,但我們必須除掉它。所以現在就處理它吧,我們沒有憤怒的權利。
你可能會問一個很合理的問題:但神不是也會發怒嗎?耶穌不也會生氣嗎?
對此,我經過深思且具有神學素養的回答是:嗯,當然。
是的,神可以憤怒。不只這個,還有其他神可以做但我們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說:報仇,那是祂的專屬權利。祂不准許我們報仇也很合理,原因在於:我們與我們發怒的對象一樣有罪。但是神呢?祂沒有。
此外,神也有權柄審判人,但我們沒有。祂的判決是可信的,因為祂與我們很不一樣,祂完美無罪。祂的憤怒也是可靠的,因祂的性情跟我們很不一樣。
神愛你,在祂眼中你很特別,但抱歉……你不是神。
我們不太願意承認一件事:就是我們其實蠻喜歡生氣的。當然,我們不喜歡那些讓人生氣的事本身,但我們很喜歡那種「逮到別人出錯」的感覺。當某某做錯了什麼,假設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憤怒給了我們一種道德優越感。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稱之為「正義的憤怒」。我們認為這是道德的、好的。
問題是,指向某人的「義怒」相當狡猾。事實證明,我往往認為我的憤怒比其他人的憤怒更正義。這是因為我認為自己非常正確。我支持我自己,我的論點在我看來特別有說服力。
不巧的是,有句箴言說:「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清潔;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箴言16:2)
不只是我,顯然所有的人都覺得自己很有道理。我的憤怒是義怒,因為我很明顯是對的,而別人是錯的。我看自己所行的都很純正,永遠都是。
這時候,每個人的憤怒似乎都是對的。憤怒是一種席捲而來、看似合理的情緒,讓我們覺得自己被剝奪了應有的東西。但是情緒就是情緒,並不是理智的批判性思維。憤怒不會停下來,但我們必須停下來,並且質疑它。
我們人類非常擅長將自己塑造成受害者,並改寫故事,把自己放在不公不義的中心(之後會有更多討論)。我們可以將對某人(例如任何威脅我們的人)的憤怒或仇恨重新描繪成一幅看起來正義的藝術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耶穌的教導中,沒有任何「好吧,如果某人真的是個混蛋,那麼你很有資格覺得被冒犯」的容許。耶穌直接告訴我們要饒恕,甚至—尤其是!—那些很合理的不滿,以及真的會令人反感的事情。
這正是重點所在:你認為有充分理由發怒的那件事,正是你被呼召去饒恕的。恩典不是給那些配得的人;饒恕意味著不再懷有怨恨,放下怒氣。
憤怒非常容易,它是我們的預設模式。
愛非常困難,愛根本是一個神蹟。
今天我在《Inc.》雜誌上讀到一篇關於憤怒和馬丁.路德.金恩的文章。作者引用了金恩的自傳中寫的:「你不能心懷憤怒。」但還不只這樣,即使在受到攻擊時,金恩也說,我們應該愛我們的敵人。2
作者像往常一樣,將金恩這番話轉成某種程度對憤怒的認可,說我們應該確保以有建設性的方式使用憤怒。這樣說無可厚非,但我不同意作者的觀點。這篇文章有幾點值得注意,其中一個是作者聲稱同意馬丁.路德.金恩的觀點,卻說出了幾乎相反的話。他把金恩的話稀釋得不那麼極端,也不那麼美了。
金恩說:「我不能心懷憤怒」,而作者說:「我同意。讓我們以有建設性的方式使用憤怒!」
我覺得我們常常也會這樣解讀耶穌的教導。像是祂說「要愛你的仇敵」、「為逼迫你的人禱告」,我們表面上點頭,心裡卻默默加一句:「但說真的,生氣是有道理的啦。」
我們對使徒雅各也是如此,他明明在聖經中清楚表示,憤怒不會產生神希望我們具備的那種義:「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各書1:20)
我們在讀保羅的教導時也會這麼做,像是他列出的那些罪,比如歌羅西書3章8節:「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
我們對「憤怒」這段其實不太買單。當保羅說要把怒氣從生命中除去時,我們照常會默默補上一句:「當然啦,除非那是有建設性的憤怒。」
但說真的,我沒聽過有人把同樣邏輯套在這節經文的其他教導。誰會說:「要除掉污言穢語—除非罵得很合理」或是「別說傷人的話—除非他真的活該」?
說穿了,我們其實還蠻喜歡自己在生氣的感覺,因為在某個程度上,我們覺得自己超有道理。
當聽到我對憤怒的觀點時,一位廣播聽眾告訴我:「我不懂,難道我們不應該對那些在新聞裡毆打遊民的人感到憤怒嗎?」
鑒於我們應該「除去一切的憤怒」,我的看法是:憤怒會發生,畢竟我們是人類,但我們不該一直懷有它。像金恩牧師一樣,我們看到不公不義之事,應該為之悲傷,並採取行動反對它—但不能懷抱怨氣、惡意和憤慨。我希望我們有足夠的動力去保護無辜者和弱勢群體,但不應該是由憤怒來驅動我們。
尋求公義,愛好憐憫,是不必懷著憤怒也能做到的。人們說我們必須憤怒才能對抗不公正,但我發現,最棒的警察不會在憤怒中行使職權,最好的士兵也不會在憤怒中執行勤務。
憤怒無法增加判斷力。
是的,只有神有能力做到公正又憤怒。如果我在一位人類法官面前受審,我肯定會希望他在判決時沒有挾帶怒氣。
當我說我們沒有權利懷有憤怒的時候,有些人認為我瘋了。也許我是瘋了。起初,我也很討厭這種想法。問題是,現在我希望我是對的,因為這樣會讓生活變得更加美好,而我好像也更能理解耶穌的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