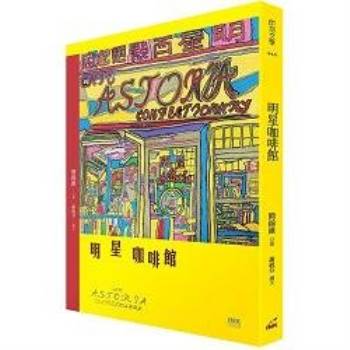俄羅斯股東的異國辛酸淚
落難的俄國皇族
艾斯尼的年紀足以當阿錐的父親,阿錐也一直稱他為Uncle。一起改建飛虎隊屋舍時,艾斯尼並未明白向他表明出身,只透露自己曾經在上海法租界擔任過建築工程師,協助軍方蓋房子。但是相識久了,鄉愁越來越濃了,艾斯尼還是忍不住從老皮箱裡翻出一張張從俄羅斯帶來的照片,以及一張寫滿俄國名字的同學錄,一點一滴訴說自己的人生。
「這些是俄羅斯貴族學校的同學,圈起來的是已經過世或是已經聯絡不上了。」「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互相聯絡,修改自己的聯絡方式,改好以後再將資料寄到下一個國家,給下一個同學。上一次在法國的同學以為我住在中國的武昌,還把信給寄到那兒去了……」艾斯尼慢慢說,阿錐靜靜聽。第一次聽到艾斯尼提起自己的貴族身分,他並不驚訝,因為早在哥哥的店裡第一眼看到這位外國人時,就知道他定是出身不凡。
艾斯尼身上流著俄國皇族的血統,本名為George Elsner ConStanIII ENobche,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親戚,也是負責保護沙皇安全的皇家侍衛團長。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發動革命,尼古拉二世家族連同親近僕人遭到布爾什維克軍隊集體殺害;一九二二年,保皇派與革命的戰火持續蔓延,英、美、法、日都派兵前往支援,但美國突然間撤兵,連帶其他國家也跟著退出戰場,導致俄國皇軍節節敗退。最後,艾斯尼只能率領部屬逃入中國東北的哈爾濱,隨後輾轉到上海的法租界協助法軍進行新建房屋的檢驗。
曾經,艾斯尼還拿出尼古拉二世家族照片,一一指著影中人告訴阿錐,這位是皇后,這三位是女大公,還有這位小皇儲總是讓尼古拉二世很擔心,稍微碰撞一下就腫得嚇人,身上總是輕一塊紫一塊。後來一位中下層階級的農夫治好小皇儲的病,沙皇和皇后變得非常寵愛這位農夫,引起軍官、百官和資本官的不滿,但中下階層卻又起身聲援那名農夫……。
艾斯尼閉上眼睛,記憶越過時空回到當時的殺戮戰場,他痛苦回憶:「農民拿著鐮刀圍住皇宮,軍隊竟然拿著槍枝掃射農民,這樣的統治階級怎麼會不滅亡呢?」俄國的歷史,阿錐不懂,但他可以感受艾斯尼對於戰爭的深惡痛絕。一次阿錐帶全家陪他到海邊出遊,艾斯尼抓起一大把沙,捏得手掌爆起青筋,沙土從指縫中留了下來。他搖搖頭:「沙子一定要雙手好好一起捧,用力捏只會得到越少;政府對人民也不能用武力,否則人民一定會反抗的。」
逃到中國那年,艾斯尼才二十二歲。烽火起起落落,他從青年變成壯年、再從壯年變成中年,離開上海來到台灣時,已經將近五十歲了。動盪的大時代將他與故鄉的距離拉得越來越遠,但思鄉的心情就像一甕苦酒,越陳越烈。他從烽火中隨身攜帶的一只小木箱,彷彿一個通往故鄉的隧道,每到夜深人靜,他便靜靜地翻出木箱內一張張泛黃又斑駁的照片,靜靜地、細細地端詳……
這一切,阿錐都看在眼裡。早些年為了讓艾斯尼有個穩定的棲身之處,他在林森北路(當時名為中山北路七條通)買下兩間比鄰的房舍,安排艾斯尼與自己、家人住在隔壁,方便就近照顧。但是住處可以安排,心裡的空洞卻難以填滿。自己又能為他做點什麼呢?
一九五六年,知名影星尤伯連納與英格麗褒曼主演的《真假公主》在台灣上演,阿錐聽聞故事內容正是末代真假俄羅斯公主的故事,便與妻子帶著艾斯尼前去觀賞,希望聊慰他的思鄉之情。但是當故事透過放映機的光束一幕一幕映在銀幕上,阿錐就一點一點地後悔了,因為他在艾斯尼的臉上,見不到任何欣喜,反而只有難以言喻的悲傷。
走出戲院,艾斯尼悲憤難平地說:「亂演!這戲根本是亂演!這世界上哪裡還找得到安娜塔西雅公主呢?」三人由西門町走回武昌街,走著走著,艾斯尼彷彿再度被記憶的獠牙刺傷,痛苦地說道:「如果我沒有中彈,如果我能早一點趕到,也許沙皇一家人就不會死了……」望著他臉上的傷痛,阿錐和妻子的喉頭像是被什麼東西卡住了,一時全說不出話來。
那天,阿錐才知道原來艾斯尼頸上的舊傷,是通往時代劇變的一個深淵。布爾什維克軍人抓走尼古拉二世一家人的那一夜,曾對皇軍瘋狂掃射,艾斯尼因而頸部中彈失去意識。當他從血泊中醒來,帶著部屬趕到西伯利亞的烏拉山區,布爾什維克軍人已經離去,但所留下殘暴的殺戮畫面卻讓他無法克制地對著天空嚎啕大哭。「沙皇一家人全被射殺了,一個都不留,他們的遺體甚至都被潑了鹽酸……。」如何走出那片出森林?艾斯尼已經不記得了,但尼古拉二世全家遺體蜷縮焦黑的模樣,多年來始終難以自他腦海中抹滅。
在ASTORIA股東糾紛之後,艾斯尼陷入抑鬱寡歡。被同鄉友人背叛的憤怒以及無法離開台灣、與親友重逢的失落,讓他積鬱成疾而中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艾斯尼倒臥在明星二樓的廁所內,被緊急送往醫院。儘管如此,他始終離不開明星。住院三天之後,他坐著公車從醫院來到武昌街,一步一步拄著柺杖,沿著階梯爬到二樓靠窗的老位置。
此後的十二年當中,中風七度來襲,但直到最後一次住進醫院之前,艾斯尼到明星報到的習慣不曾改變。別人老勸他留在家中休養,但阿錐卻天天幫他在明星二樓保留一處「專屬特別座」。他和艾斯尼雖然都沒有說,但他們彼此都清楚,對艾斯尼而言,明星不止是一間西點咖啡屋,更是異鄉的另一個「家」。遠在北國的家回不去,至少也要回到飄著故鄉味道的地方!
五、六十年前,和外國人來往密切,在台灣人眼中似乎是件怪事。特別是在幫飛虎隊改建住處賺了一點錢之後,很多人都在背後笑我:「伊要去乎外國人做子。」甚至就連我的婚禮,大哥所請來的證婚人也在致詞中介紹我是「乎外國人做子」的那個少年郎,讓我當場不知如何回應。事後,我的母親相當不能諒解地質問我:「你要乎外國人做子,為啥米攏沒講?你好歹嘛要講一聲!」
我常常想,還好艾斯尼不懂中文,否則對於這些反應,應該也會感到不自在吧!我與艾斯尼可謂忘年之交,即使剛認識時,我只有十八歲,但在他眼裡,我不是一個毛頭小子,而是一個值得信賴且可以獨當一面的好朋友。而他之於我,不只是帶領我走上一條特殊的人生道路,更在潛移默化中給了我許多深刻的影響。
艾斯尼中風前,我特地買了一棟房子讓他居住;艾斯尼中風後的十二年裡,我為他請看護,並把他當成親人一樣陪伴照顧。在別人眼中,我為他所做的已經不亞於一個孩子對父親的關懷。但比起他的言行帶給我的種種影響,我總覺得這些回報不算什麼。
可能是因為出身皇族的關係,自幼接受過系統皇家禮儀教育,艾斯尼不管是言行或舉止,都展現出充分的得體與氣度。平日的生活節儉卻不失品味,偶爾麵包和濃湯就是一餐,但用餐的禮儀與優雅的步調卻不曾因此而減少;經常穿著的西裝不脫那兩、三套,有的甚至已經穿了許多年,但即使是在生病之後,他始終保持一身的潔淨與筆挺。
最讓我難忘的,還是他不輕易接受他人好處的堅持。那一年,朋友聽說我們將一同到西門町的萬國戲院看《真假公主》,好意送來電影票,到了戲院門口,艾斯尼卻掏出三塊半,堅持自己要負擔電影票費用。平常看慣了搶著付帳而拉拉扯扯的畫面,本以為自己會為那三塊半與他在戲院門口僵持,但他只是輕輕地說道:「Archie,不管那是不是朋友送給你的,我都應該付自己的費用。」頓時,我看到的不是一個落難的俄羅斯人,而是一個將自尊擺在最前頭的白俄貴族!在他篤定的神情與不急不徐的語氣中,我只能默默地從他手中接過錢。
整建飛虎隊屋舍過程中,我一直認為這些生意是因他而上門,我和許多台灣人都是因為他才能找到頭路。那幾年,我們一邊合作開設ASTORIA,一邊繼續改建宿舍工程,但我幾次想要將獲利與他均分都遭到拒絕,我只能私底下將那些錢用來為ASTORIA買器具和材料,讓他不需要為了張羅資金而傷腦筋。有一回,一位美國駐台高官對改建成果大為滿意,付了一大筆錢當作工程款。當天我送了一半金額到他面前,但經濟狀況不甚理想的他卻再度拒絕,強調自己無功不受祿,並要我別再提起這些事。這份情義和風骨,讓我永誌於心,幾年之後,我特別在中山北路一段(現今林森北路)買下兩棟相鄰的房子,一棟作為我和妻小的住處,另一棟則安排作為他的養老居所,也算是我回報給他的禮物。
咱台灣人說「吃人一口,還人一斗」。我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受到一個落難異域的俄羅斯人提攜,怎能不知恩圖報呢?這段長達二十多年的異國友誼,又豈是金錢或是物質所能取代呢?
台灣文學作家的窩
樓下擺攤的周夢蝶
一九五○年代起,台灣文化界總算擺脫戰後的青黃不接,開始有人辦雜誌、有人搞出版,重慶南路一帶因鄰近火車站和眾多政府機關,成為多數出版社落腳處,書店隨之聚集,騎樓下也出現一個個賣雜誌、書報的小書攤。一九五九年,明星的騎樓多了一攤小小的書報攤,書報攤的老闆長得瘦骨嶙峋,有時將攤子擺在明星門口左邊,有時擺在右邊。有客人時,他會陪客人聊聊;沒客人時,一張板凳坐、一張板凳翹腳,就打起盹。
當時艾斯尼等人正盤算如何將明星脫手,屋內股東糾紛方興未艾,對屋外的攤子根本無心過問,於是就這麼任由小書攤擺著,彼此相安無事,明星找明星的買主,書攤找書攤的顧客。隔年(1960),阿錐成為明星唯一的老闆,仍不知道門前坐的是作品散見各報章的一位詩人。
有天,阿錐在廚房裡指導新進的師傅如何製作俄羅斯風味的麵包,突然一樓麵包店的員工跑進來,「老闆,老闆,門口那個賣書的昏過去了!」阿錐和妻子衝到門前一看,果見賣書人倒在地上,原本瘦小的身子顯得更加單薄。「快叫救護車,快把他送到醫院。」眾人七嘴八舌幫著想辦法,賣書人卻逐漸恢復意識,阿錐問:「是不是身體不舒服,要不要送你到醫院?」但對方一再強調自己沒事,不需要勞駕救護車,便又坐回書攤忙了。
眾人見他如此堅持,漸漸散去。阿錐朝屋內走了幾步,想了想停下腳步又轉回騎樓,「你真的沒事嗎?」他心想這人臉色蒼白如紙,怎可能沒事?對方被他這麼一問,神色變得怪異,一會兒才壓低聲音說:「我真的沒病,只是三天連一本書都賣不掉,沒吃東西,餓得受不了。」阿錐感覺這人有些風骨,若是堅持請客,肯定不被接受,於是改口說:「我等會請太太拿些麵包和熱牛奶,如果你有錢就給我錢,如果沒錢就算我招待,有緣才能在同一個屋簷下做生意,大家交個朋友。」
兩人從此有了正式的交集,阿錐問他:「怎麼稱呼?」賣書人回:「就叫我老周吧!」
一段時日後,阿錐注意到老周攤前總有幾位文化氣息濃厚的客人,經常提著一落落的舊書讓他賣,偶爾也會請老周上明星二樓去喝喝咖啡;阿錐還注意到每天明星還未開店,老周就已在騎樓下張羅。阿錐好奇問:「老周,你住哪兒?怎麼這麼早?」老周說:「我住三重,坐第一班公車過來,比較不擠!」書就這麼搬來搬去嗎?阿錐很好奇,老周翻著書說,有時會找個地方寄放,有時搬回牯嶺街的書商那寄放,完全找不到地方,就布包一包扛著走囉!阿錐心想這老周個子瘦小、三餐看起來也不正常,如此折騰豈不累壞?當天下午,阿錐又來到書報攤,「老周,以後收攤就把書寄放在武昌街五號的茶莊(確認一下行業)裡,別再搬了!我已經跟茶莊老闆說好了。」老周有點驚訝,點了點頭表示謝意。原來當時阿錐已將武昌街七號、五號店面買回,並將五號租給茶莊,為了讓老周比較方便,因而情商茶莊主人在打烊後釋出一點空間讓他寄放書刊。
時光約莫又過半載,茶莊老闆在閒聊中提到,「那老周真是勤奮,每天一大早就來等我們開門。」阿錐已對老周有些認識,也從其他客人口中得知這位賣書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詩人周夢蝶,猜想他有讀書人風骨,定是不願意影響到別人做生意,所以才每天一早到門口等茶莊開門,在店家正式營業前就把書搬出來。阿錐又跟老闆商量了一會,才走到書報攤。
「老周,你每天得等茶莊開門才能搬書,又得等茶莊打烊才能收攤。這樣好了,你以後就進茶莊找個地方睡,我已經跟老闆說好了,你就不必再天天往返三重和台北了。」
周夢蝶聽了不語。阿錐怕自己說錯話,趕緊表示:「我沒其他意思,你還是可以隨時回三重,只是如果收攤得晚,就住著比較方便。」那之後,偶爾周夢蝶會在茶莊留宿,但仍小心翼翼不干擾茶莊做生意,一早五、六點就起床刷牙洗臉,先到旁邊的豆漿攤吃個饅頭、喝甜豆漿,再於茶莊營業前將書刊全部搬出來。
一方面,慕名來看周夢蝶的人越來越多,從大學生、文人、軍人都有,每隔一、兩天就有人請他上樓去談論文學,漸漸演變成固定在每週三晚間七點到九點半聚會。阿錐見每次至少五、六個人圍著他,他多半是聽而不答,直到最後才動筆將想說的話寫在紙上;這一寫不得了,連鄰座的客人也都湊過來爭睹他的筆札,甚至曾有過兩桌人為此爭執,「周先生又不是你一人的,怎麼可以霸著不放?」
阿錐看了覺得有趣,私下問:「老周,你都說些什麼、寫些什麼呢?怎麼有這麼多人來聽你說話、看你寫字?」周夢蝶十分困窘,急忙揮手道:「沒沒沒,不就是聽聽彼此的想法,我還真怕自己說錯話呢。每次覺得自己說錯話,回去的公車上就開始煩惱,有時還煩惱一整個星期,晚上都睡不好呢!」書報攤的生意維持二十一年,星期三的聚會也持續十多年。一九八○年的某一天,阿錐一進門就聽門市員工說:「老闆,今天老周又在門口昏倒,後來被送進榮總了。」周夢蝶在門前昏倒已經不只一次了,此次聽起來似乎格外嚴重,阿錐上樓問其他認識周夢蝶的作家客人,對方告訴他:「不太清楚,可能是貧血和胃出血。」聽完,阿錐嘆了一口氣,「他每天就吃那麼點饅頭、喝那麼點豆漿,怎能不生病?」
後來聽說周夢蝶同時罹患四種疾病: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胃出血、高度貧血,開刀切除四分之三個胃才救回一命。自此明星門前不再有小書攤,周三晚間的聚會也停止,但前來詢問的客人不曾少過,幾乎隔幾天就有人上門問:「周先生呢?他不來了嗎?」
「他要先休息一陣子,暫時不會再來了。」雖然每次阿錐都這樣告訴客人,心底卻和他們一樣期待老周儘速恢復健康,早點回到明星來。
落難的俄國皇族
艾斯尼的年紀足以當阿錐的父親,阿錐也一直稱他為Uncle。一起改建飛虎隊屋舍時,艾斯尼並未明白向他表明出身,只透露自己曾經在上海法租界擔任過建築工程師,協助軍方蓋房子。但是相識久了,鄉愁越來越濃了,艾斯尼還是忍不住從老皮箱裡翻出一張張從俄羅斯帶來的照片,以及一張寫滿俄國名字的同學錄,一點一滴訴說自己的人生。
「這些是俄羅斯貴族學校的同學,圈起來的是已經過世或是已經聯絡不上了。」「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互相聯絡,修改自己的聯絡方式,改好以後再將資料寄到下一個國家,給下一個同學。上一次在法國的同學以為我住在中國的武昌,還把信給寄到那兒去了……」艾斯尼慢慢說,阿錐靜靜聽。第一次聽到艾斯尼提起自己的貴族身分,他並不驚訝,因為早在哥哥的店裡第一眼看到這位外國人時,就知道他定是出身不凡。
艾斯尼身上流著俄國皇族的血統,本名為George Elsner ConStanIII ENobche,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親戚,也是負責保護沙皇安全的皇家侍衛團長。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發動革命,尼古拉二世家族連同親近僕人遭到布爾什維克軍隊集體殺害;一九二二年,保皇派與革命的戰火持續蔓延,英、美、法、日都派兵前往支援,但美國突然間撤兵,連帶其他國家也跟著退出戰場,導致俄國皇軍節節敗退。最後,艾斯尼只能率領部屬逃入中國東北的哈爾濱,隨後輾轉到上海的法租界協助法軍進行新建房屋的檢驗。
曾經,艾斯尼還拿出尼古拉二世家族照片,一一指著影中人告訴阿錐,這位是皇后,這三位是女大公,還有這位小皇儲總是讓尼古拉二世很擔心,稍微碰撞一下就腫得嚇人,身上總是輕一塊紫一塊。後來一位中下層階級的農夫治好小皇儲的病,沙皇和皇后變得非常寵愛這位農夫,引起軍官、百官和資本官的不滿,但中下階層卻又起身聲援那名農夫……。
艾斯尼閉上眼睛,記憶越過時空回到當時的殺戮戰場,他痛苦回憶:「農民拿著鐮刀圍住皇宮,軍隊竟然拿著槍枝掃射農民,這樣的統治階級怎麼會不滅亡呢?」俄國的歷史,阿錐不懂,但他可以感受艾斯尼對於戰爭的深惡痛絕。一次阿錐帶全家陪他到海邊出遊,艾斯尼抓起一大把沙,捏得手掌爆起青筋,沙土從指縫中留了下來。他搖搖頭:「沙子一定要雙手好好一起捧,用力捏只會得到越少;政府對人民也不能用武力,否則人民一定會反抗的。」
逃到中國那年,艾斯尼才二十二歲。烽火起起落落,他從青年變成壯年、再從壯年變成中年,離開上海來到台灣時,已經將近五十歲了。動盪的大時代將他與故鄉的距離拉得越來越遠,但思鄉的心情就像一甕苦酒,越陳越烈。他從烽火中隨身攜帶的一只小木箱,彷彿一個通往故鄉的隧道,每到夜深人靜,他便靜靜地翻出木箱內一張張泛黃又斑駁的照片,靜靜地、細細地端詳……
這一切,阿錐都看在眼裡。早些年為了讓艾斯尼有個穩定的棲身之處,他在林森北路(當時名為中山北路七條通)買下兩間比鄰的房舍,安排艾斯尼與自己、家人住在隔壁,方便就近照顧。但是住處可以安排,心裡的空洞卻難以填滿。自己又能為他做點什麼呢?
一九五六年,知名影星尤伯連納與英格麗褒曼主演的《真假公主》在台灣上演,阿錐聽聞故事內容正是末代真假俄羅斯公主的故事,便與妻子帶著艾斯尼前去觀賞,希望聊慰他的思鄉之情。但是當故事透過放映機的光束一幕一幕映在銀幕上,阿錐就一點一點地後悔了,因為他在艾斯尼的臉上,見不到任何欣喜,反而只有難以言喻的悲傷。
走出戲院,艾斯尼悲憤難平地說:「亂演!這戲根本是亂演!這世界上哪裡還找得到安娜塔西雅公主呢?」三人由西門町走回武昌街,走著走著,艾斯尼彷彿再度被記憶的獠牙刺傷,痛苦地說道:「如果我沒有中彈,如果我能早一點趕到,也許沙皇一家人就不會死了……」望著他臉上的傷痛,阿錐和妻子的喉頭像是被什麼東西卡住了,一時全說不出話來。
那天,阿錐才知道原來艾斯尼頸上的舊傷,是通往時代劇變的一個深淵。布爾什維克軍人抓走尼古拉二世一家人的那一夜,曾對皇軍瘋狂掃射,艾斯尼因而頸部中彈失去意識。當他從血泊中醒來,帶著部屬趕到西伯利亞的烏拉山區,布爾什維克軍人已經離去,但所留下殘暴的殺戮畫面卻讓他無法克制地對著天空嚎啕大哭。「沙皇一家人全被射殺了,一個都不留,他們的遺體甚至都被潑了鹽酸……。」如何走出那片出森林?艾斯尼已經不記得了,但尼古拉二世全家遺體蜷縮焦黑的模樣,多年來始終難以自他腦海中抹滅。
在ASTORIA股東糾紛之後,艾斯尼陷入抑鬱寡歡。被同鄉友人背叛的憤怒以及無法離開台灣、與親友重逢的失落,讓他積鬱成疾而中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艾斯尼倒臥在明星二樓的廁所內,被緊急送往醫院。儘管如此,他始終離不開明星。住院三天之後,他坐著公車從醫院來到武昌街,一步一步拄著柺杖,沿著階梯爬到二樓靠窗的老位置。
此後的十二年當中,中風七度來襲,但直到最後一次住進醫院之前,艾斯尼到明星報到的習慣不曾改變。別人老勸他留在家中休養,但阿錐卻天天幫他在明星二樓保留一處「專屬特別座」。他和艾斯尼雖然都沒有說,但他們彼此都清楚,對艾斯尼而言,明星不止是一間西點咖啡屋,更是異鄉的另一個「家」。遠在北國的家回不去,至少也要回到飄著故鄉味道的地方!
五、六十年前,和外國人來往密切,在台灣人眼中似乎是件怪事。特別是在幫飛虎隊改建住處賺了一點錢之後,很多人都在背後笑我:「伊要去乎外國人做子。」甚至就連我的婚禮,大哥所請來的證婚人也在致詞中介紹我是「乎外國人做子」的那個少年郎,讓我當場不知如何回應。事後,我的母親相當不能諒解地質問我:「你要乎外國人做子,為啥米攏沒講?你好歹嘛要講一聲!」
我常常想,還好艾斯尼不懂中文,否則對於這些反應,應該也會感到不自在吧!我與艾斯尼可謂忘年之交,即使剛認識時,我只有十八歲,但在他眼裡,我不是一個毛頭小子,而是一個值得信賴且可以獨當一面的好朋友。而他之於我,不只是帶領我走上一條特殊的人生道路,更在潛移默化中給了我許多深刻的影響。
艾斯尼中風前,我特地買了一棟房子讓他居住;艾斯尼中風後的十二年裡,我為他請看護,並把他當成親人一樣陪伴照顧。在別人眼中,我為他所做的已經不亞於一個孩子對父親的關懷。但比起他的言行帶給我的種種影響,我總覺得這些回報不算什麼。
可能是因為出身皇族的關係,自幼接受過系統皇家禮儀教育,艾斯尼不管是言行或舉止,都展現出充分的得體與氣度。平日的生活節儉卻不失品味,偶爾麵包和濃湯就是一餐,但用餐的禮儀與優雅的步調卻不曾因此而減少;經常穿著的西裝不脫那兩、三套,有的甚至已經穿了許多年,但即使是在生病之後,他始終保持一身的潔淨與筆挺。
最讓我難忘的,還是他不輕易接受他人好處的堅持。那一年,朋友聽說我們將一同到西門町的萬國戲院看《真假公主》,好意送來電影票,到了戲院門口,艾斯尼卻掏出三塊半,堅持自己要負擔電影票費用。平常看慣了搶著付帳而拉拉扯扯的畫面,本以為自己會為那三塊半與他在戲院門口僵持,但他只是輕輕地說道:「Archie,不管那是不是朋友送給你的,我都應該付自己的費用。」頓時,我看到的不是一個落難的俄羅斯人,而是一個將自尊擺在最前頭的白俄貴族!在他篤定的神情與不急不徐的語氣中,我只能默默地從他手中接過錢。
整建飛虎隊屋舍過程中,我一直認為這些生意是因他而上門,我和許多台灣人都是因為他才能找到頭路。那幾年,我們一邊合作開設ASTORIA,一邊繼續改建宿舍工程,但我幾次想要將獲利與他均分都遭到拒絕,我只能私底下將那些錢用來為ASTORIA買器具和材料,讓他不需要為了張羅資金而傷腦筋。有一回,一位美國駐台高官對改建成果大為滿意,付了一大筆錢當作工程款。當天我送了一半金額到他面前,但經濟狀況不甚理想的他卻再度拒絕,強調自己無功不受祿,並要我別再提起這些事。這份情義和風骨,讓我永誌於心,幾年之後,我特別在中山北路一段(現今林森北路)買下兩棟相鄰的房子,一棟作為我和妻小的住處,另一棟則安排作為他的養老居所,也算是我回報給他的禮物。
咱台灣人說「吃人一口,還人一斗」。我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受到一個落難異域的俄羅斯人提攜,怎能不知恩圖報呢?這段長達二十多年的異國友誼,又豈是金錢或是物質所能取代呢?
台灣文學作家的窩
樓下擺攤的周夢蝶
一九五○年代起,台灣文化界總算擺脫戰後的青黃不接,開始有人辦雜誌、有人搞出版,重慶南路一帶因鄰近火車站和眾多政府機關,成為多數出版社落腳處,書店隨之聚集,騎樓下也出現一個個賣雜誌、書報的小書攤。一九五九年,明星的騎樓多了一攤小小的書報攤,書報攤的老闆長得瘦骨嶙峋,有時將攤子擺在明星門口左邊,有時擺在右邊。有客人時,他會陪客人聊聊;沒客人時,一張板凳坐、一張板凳翹腳,就打起盹。
當時艾斯尼等人正盤算如何將明星脫手,屋內股東糾紛方興未艾,對屋外的攤子根本無心過問,於是就這麼任由小書攤擺著,彼此相安無事,明星找明星的買主,書攤找書攤的顧客。隔年(1960),阿錐成為明星唯一的老闆,仍不知道門前坐的是作品散見各報章的一位詩人。
有天,阿錐在廚房裡指導新進的師傅如何製作俄羅斯風味的麵包,突然一樓麵包店的員工跑進來,「老闆,老闆,門口那個賣書的昏過去了!」阿錐和妻子衝到門前一看,果見賣書人倒在地上,原本瘦小的身子顯得更加單薄。「快叫救護車,快把他送到醫院。」眾人七嘴八舌幫著想辦法,賣書人卻逐漸恢復意識,阿錐問:「是不是身體不舒服,要不要送你到醫院?」但對方一再強調自己沒事,不需要勞駕救護車,便又坐回書攤忙了。
眾人見他如此堅持,漸漸散去。阿錐朝屋內走了幾步,想了想停下腳步又轉回騎樓,「你真的沒事嗎?」他心想這人臉色蒼白如紙,怎可能沒事?對方被他這麼一問,神色變得怪異,一會兒才壓低聲音說:「我真的沒病,只是三天連一本書都賣不掉,沒吃東西,餓得受不了。」阿錐感覺這人有些風骨,若是堅持請客,肯定不被接受,於是改口說:「我等會請太太拿些麵包和熱牛奶,如果你有錢就給我錢,如果沒錢就算我招待,有緣才能在同一個屋簷下做生意,大家交個朋友。」
兩人從此有了正式的交集,阿錐問他:「怎麼稱呼?」賣書人回:「就叫我老周吧!」
一段時日後,阿錐注意到老周攤前總有幾位文化氣息濃厚的客人,經常提著一落落的舊書讓他賣,偶爾也會請老周上明星二樓去喝喝咖啡;阿錐還注意到每天明星還未開店,老周就已在騎樓下張羅。阿錐好奇問:「老周,你住哪兒?怎麼這麼早?」老周說:「我住三重,坐第一班公車過來,比較不擠!」書就這麼搬來搬去嗎?阿錐很好奇,老周翻著書說,有時會找個地方寄放,有時搬回牯嶺街的書商那寄放,完全找不到地方,就布包一包扛著走囉!阿錐心想這老周個子瘦小、三餐看起來也不正常,如此折騰豈不累壞?當天下午,阿錐又來到書報攤,「老周,以後收攤就把書寄放在武昌街五號的茶莊(確認一下行業)裡,別再搬了!我已經跟茶莊老闆說好了。」老周有點驚訝,點了點頭表示謝意。原來當時阿錐已將武昌街七號、五號店面買回,並將五號租給茶莊,為了讓老周比較方便,因而情商茶莊主人在打烊後釋出一點空間讓他寄放書刊。
時光約莫又過半載,茶莊老闆在閒聊中提到,「那老周真是勤奮,每天一大早就來等我們開門。」阿錐已對老周有些認識,也從其他客人口中得知這位賣書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詩人周夢蝶,猜想他有讀書人風骨,定是不願意影響到別人做生意,所以才每天一早到門口等茶莊開門,在店家正式營業前就把書搬出來。阿錐又跟老闆商量了一會,才走到書報攤。
「老周,你每天得等茶莊開門才能搬書,又得等茶莊打烊才能收攤。這樣好了,你以後就進茶莊找個地方睡,我已經跟老闆說好了,你就不必再天天往返三重和台北了。」
周夢蝶聽了不語。阿錐怕自己說錯話,趕緊表示:「我沒其他意思,你還是可以隨時回三重,只是如果收攤得晚,就住著比較方便。」那之後,偶爾周夢蝶會在茶莊留宿,但仍小心翼翼不干擾茶莊做生意,一早五、六點就起床刷牙洗臉,先到旁邊的豆漿攤吃個饅頭、喝甜豆漿,再於茶莊營業前將書刊全部搬出來。
一方面,慕名來看周夢蝶的人越來越多,從大學生、文人、軍人都有,每隔一、兩天就有人請他上樓去談論文學,漸漸演變成固定在每週三晚間七點到九點半聚會。阿錐見每次至少五、六個人圍著他,他多半是聽而不答,直到最後才動筆將想說的話寫在紙上;這一寫不得了,連鄰座的客人也都湊過來爭睹他的筆札,甚至曾有過兩桌人為此爭執,「周先生又不是你一人的,怎麼可以霸著不放?」
阿錐看了覺得有趣,私下問:「老周,你都說些什麼、寫些什麼呢?怎麼有這麼多人來聽你說話、看你寫字?」周夢蝶十分困窘,急忙揮手道:「沒沒沒,不就是聽聽彼此的想法,我還真怕自己說錯話呢。每次覺得自己說錯話,回去的公車上就開始煩惱,有時還煩惱一整個星期,晚上都睡不好呢!」書報攤的生意維持二十一年,星期三的聚會也持續十多年。一九八○年的某一天,阿錐一進門就聽門市員工說:「老闆,今天老周又在門口昏倒,後來被送進榮總了。」周夢蝶在門前昏倒已經不只一次了,此次聽起來似乎格外嚴重,阿錐上樓問其他認識周夢蝶的作家客人,對方告訴他:「不太清楚,可能是貧血和胃出血。」聽完,阿錐嘆了一口氣,「他每天就吃那麼點饅頭、喝那麼點豆漿,怎能不生病?」
後來聽說周夢蝶同時罹患四種疾病: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胃出血、高度貧血,開刀切除四分之三個胃才救回一命。自此明星門前不再有小書攤,周三晚間的聚會也停止,但前來詢問的客人不曾少過,幾乎隔幾天就有人上門問:「周先生呢?他不來了嗎?」
「他要先休息一陣子,暫時不會再來了。」雖然每次阿錐都這樣告訴客人,心底卻和他們一樣期待老周儘速恢復健康,早點回到明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