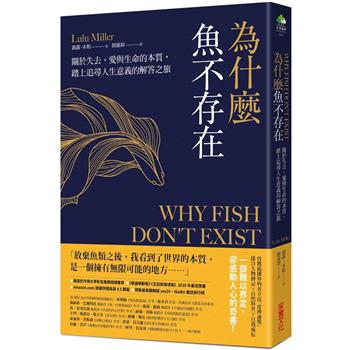第三章 無神論間奏
位在麻州東南部的一座半島──鱈魚角(Cape Cod),說不定是一片催生存在主義的沃土,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因為那裡的沙質土壤中,含有能催化形而上學的金屬,我只知道我也是在那裡改變了我的世界觀。事情發生在我七歲的時候,說來奇怪,我對大衛.斯塔爾.喬丹的痴迷,似乎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而且他還成了日後我的人生陷入低潮時,想要求助的那個人。
那是個初夏的清晨,我們全家在麻州的韋爾弗利特(Wellfleet)度假,它與佩尼克塞島的直線距離僅約八十公里。
我跟我爸站在露台上,輪流用一副笨重的黑色望遠鏡,看著前方一望無際的黃綠色沼澤,試圖辨識遠處蘆葦叢中的一個小白點。我爸個子很高,留著鬍子,頂著一頭黑髮,穿著一條牛仔短褲,沒穿襯衫,挺著一個毛茸茸的可愛肚皮。我媽、兩個姐姐和貓咪都還在睡覺。我一直沒法讓鏡片聚焦在那個小白點上,只好把望遠鏡還給我爸,我用肉眼繼續盯著蘆葦叢中的那個白點,那到底是隻天鵝,還是一個浮標呢?難不成是什麼更有趣的東西?但不知怎的,我突然脫口而出問我爸:「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或許是因為眼前的沼澤好大一片,一直綿延到海邊,而海又綿延到哪裡呢?應該是海洋的盡頭吧,我的腦中出現船隻航行到那裡便掉下去的畫面,下一秒,我突然想知道,我們究竟在這裡做什麼。
我爸並沒有立刻回答我,只是挑高了一邊的眉毛,然後轉過身來笑著對我說:「沒有任何意義!」
我感覺自從我出生後,我爸就一直熱切地等著我問這個問題,而此刻他終於有機會告訴我:生命沒有任何意義,不必自尋煩惱;世間沒有上帝,沒有人在看著你,也沒有人在乎你;沒有來世,沒有命運,沒有計畫,不管是誰告訴你生命有意義,都不要相信。這些全都是人們為了安慰自己而幻想出來的東西,目的是為了驅散那令人害怕的感覺:一切都不重要、你這個人也無關緊要。但這就是事實,一切都不重要、你這個人也無關緊要。
然後我爸拍了拍我的頭。
我不知道當時我露出什麼樣的表情,嚇到一臉蒼白嗎?我感覺天地間有條巨大的羽絨被突然被扯開了。
接著他告訴我,混亂是世間唯一的統治者,這股力量形成的巨大漩渦在無意間創造了人類,但很快就會毀滅我們。我們的夢想、目標和最崇高的行為,混亂全都不在乎。我爸指著露台下方布滿松針的土壤,對我說:「你一定要記住,雖然你可能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但你其實和一隻螞蟻沒什麼區別,除了個頭比較大一些,但你依舊無關緊要。」他停頓了一下,確認他腦中的等級圖:「除非,我見過你幫忙鬆土?還是你曾啃食木頭來加快它的分解過程?」
我聳了聳肩,不置可否。
「我從沒見過你做這些事情,所以我可以說,你對地球的重要性還不如一隻螞蟻呢。」
然後,為了讓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張開了雙臂,我還以為他要抱我並對我說:「開玩笑的啦,你當然很重要!」沒想到他竟然是說:「想像這是所有的時間,人類存在的時間只有這麼長!」他在胸前比劃著一條巨大而無形的時間線,說到「這麼長」一詞時,他還誇張地把手指捏在一起,「而且我們可能很快就會消失了!如果你放眼地球之外……」他喟嘆道:「那我們真的不算什麼,因為宇宙中還有其他行星,之外還有更多的太陽系……」
我不確定這段內容是否跟我爸當年說的話一字不差,不過在將近二十年後,我聽到天文學家尼爾.德格拉斯.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那句家喻戶曉的名言:「我們只是一顆微粒上的一顆微粒上的一顆微粒。」簡直跟我爸的說法遙相呼應。
當時才七歲的我,根本沒能力用語言精確表達出我心裡湧起的寒意:「那這一切有什麼意義呢?幹麼要去上學?幹麼要用通心麵黏在紙上做美勞?」
童年的我只能靜靜地觀察我爸的行為,想從中找出答案。他是個充滿活力的生化學家,用顫抖的雙手研究離子,這種帶電的微粒,能為所有生命活動提供動力,包括心跳、閃電,甚至是離子本身的活動。我爸開車時不綁安全帶、寫信從不留回信地址,還會在禁止戲水的地方游泳。有一天他回家後宣布,他再也受不了袖子了,因為袖子經常打翻他的試管,他拿起剪刀,氣沖沖地把衣櫃裡的衣服剪了個遍。接下來的好幾年,他上班時的穿著簡直像個學術界的海盜。
他很寵我家那隻淘氣的狗,從不按照食譜餵牠,雖然我媽已經表明她頂多只同意讓狗吃小白鼠的肝臟,其他一率不准,但我爸還是會用實驗室剩下的青蛙腿或電鰩的內臟,試做各種新料理。有次我跟他去養老院探視奶奶,剛要走進大門時,一位坐輪椅的老太太不小心擋到我們,我爸立刻對她大喊:「慢一點!」而且故意摔倒在地上,臉上還做出齜牙咧嘴的表情,裝作被撞得不輕。我當時覺得尷尬極了,也很擔心他會嚇到這位可憐的阿嬤,但老奶奶卻被我爸逗笑了,我這才明白,她開得起玩笑,也巴不得別人跟她開玩笑,她很樂於當個開得起玩笑的人。
我爸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似乎都在實踐他的人生哲學:你不是什麼重要的大人物,所以想怎麼活就怎麼活吧。他常年以摩托車代步,喝大量的啤酒,一逮著機會就下水游泳,而且一定要用搞笑的方式跳水──肚子先觸水。但為了避免自己淪為一名享樂主義者,他不得不拿一個謊言當成他的道德準則:雖然其他人也不是重要人士,但你得把他們當成重要人士來對待。
所以,他幾乎每天早上都會泡咖啡給我媽喝,而且五十年如一日。他也沒拿學生當外人,過節時總會邀他們來我家聚餐,他們有時還會住在我家。我家廚房的餐桌上刻滿了數字,那是他用顫抖的手刻出來的,那是他在無數個夜晚,辛苦教我們姐妹三人領略數學之美所留下的紀錄。
他用充沛的活力應對嚴峻的現實,並活出了精采的一生,我這輩子一直努力想要學我爸那樣活著,抱著我們是「不重要的小人物」的想法,腳蹬小丑鞋,踏著歡快的步伐,慢慢地走向幸福。
但我經常畫虎不成反類犬。
「你不重要」這句話,往往從我身上引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巨大的誘惑
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要我們別為此心煩意亂,他認為大多數人會在任何時刻動過這個念頭,這個解除痛苦的方法如此誘人,甚至被十八世紀的詩人威廉.古柏(William Cowper)稱為「巨大的誘惑」。
從我五年級它就開始向我招手了,當時我大姐遭到嚴重霸凌而從高中輟學。我可愛的姐姐遺傳了我爸的黑髮,她戴著一副栗色框的眼鏡,一笑就露出閃亮的牙套。她不太會察言觀色,而且很容易感到焦慮,只要一有壓力就會開始拔眉毛和睫毛。我痛恨她的同學們不善待她、不放過她,只要一想到整間學校連一個同情她的人都沒有,我就非常心痛,有時候,我必須逼自己完全不去想這件事,我的心情才會好一點。
我試著像我爸那樣,從田野間找到安慰:捏泥餅、抓螢火蟲、築雨水壩,我是築雨水壩的高手,有次甚至引來一隻鴨子!但是等我上了中學後,我也開始遭到「走廊霸凌」,男生會用力拉扯我木工褲的褲環,譏笑說:「你的錘子呢?」我壓低棒球帽不想引人注意,卻還是逃不過他們的嘲笑,甚至叫我「傑瑞」,我根本搞不懂為什麼。九年級時,我經過一群男生,他們大聲喊著:「七!」顯然是在幫經過的女生評分,我心想七分還不錯嘛;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的意思是說要喝下七罐啤酒,才有辦法和我發生關係。七罐啤酒就爛醉如泥了,表示他們完全不想碰我。
我明白一個擁有堅強靈魂的勇敢女孩,會對那些臭男生反脣相譏。我明白自己遇到的情況真的不算什麼,但我內心沒有那樣東西,雖然我也說不清楚那是什麼。總之,在我需要骨氣的時候,我卻只能找到一盤散沙。
等我再長大一些,我大姐的情況仍未見改變,她雖然上了社區大學,卻和室友處不來,鬧翻後只好搬回家。她雖然拿到了學位,工作卻總是做不長久,當收銀員嘛,太緊張;當圖書館員嘛,又太健談。她晚上回到家時,既要面對我媽的擔心,還要面對我爸的失望,只能躲在臥室門後大吼大叫,我想像我大姐變成了一個淚眼婆娑的孤獨龍捲風。當我看到大姐臉上的眉毛和睫毛全被拔光時,我真的嚇到了,倒不是因為這副模樣看起來很詭異,而是因為我知道自己心裡同樣潛藏著巨大的悲傷,只不過,我比較喜歡用小刀在皮膚上劃下一些小傷口,用這樣的方式來發洩。
但我爸似乎已經忍無可忍,他迫切希望我倆趕快振作起來,並在生命結束之前盡情享受人生。我爸在實驗室的辦公桌上,掛了一幅用棕色的花體字書寫而成的格言,裱在一個上了清漆的木質畫框裡,那是達爾文的一句名言:「生命如是之觀,何等壯麗恢弘!」(Ther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這是他寫的《物種起源》中的最後一句話,這也是達爾文對上帝說的「情話」,為自己抹去了上帝的存在而表達歉意,這同時也是達爾文給的承諾,只要你看得夠仔細,就會發現生命的壯麗恢弘。但有時,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一種指責──如果你看不到生命的壯麗恢弘,你應該感到羞愧。
每當我爸心情不好,或是工作了一整天、灌了一肚子酒時,他就會拖著沉重的步伐上樓,說他受夠了我們姐妹倆的胡鬧,他會用力甩門或搖晃我們,完全忘了他給自己定下的道德鐵律:把別人當成重要人士對待。有幾次,他還狠狠搧了我姐幾記耳光,在她臉上留下了紅印子。看著父女對立的緊張氣氛,我媽都急哭了,而身為全家精神支柱的二姐,後來也毅然離開家裡,在我升上十年級的時候,去了非洲的馬利(Mali)求學。
當時,我感覺天下之大竟無自己容身之處,外面只有充滿惡意的學校走廊,和看不見任何東西的地平線,家裡也只有大力甩上的門。一九九九年四月八日,那天是星期天,也是我的十六歲生日,我在日記中寫道:「我看不見一絲光亮。」隔天放學後,我開車去了沃爾格林連鎖藥局,找到擺放安眠藥的貨架,它們的外包裝分成淺藍色、深藍色和紫色,但都用白色星星許諾你一夜好眠,我快速拿了幾盒紫色的安眠藥塞在大衣裡,不想讓人起疑。
待我回到家吃完晚飯,整個人覺得輕鬆多了,我靜靜等待全家都睡著,爸媽縮著身子睡著了,只有這個時候他們才不會吵架;大姐的眼皮也難得闔上了;二姐在某個比自家更好的非洲家庭裡睡著了;小白狗查理也睡著了。我躡手躡腳地走到地下室,當時我還不知道動物死前會挖個洞躲進去,我只是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那裡。我給自己搞了個儀式,鄭重其事地把每粒藥丸從它的小塑膠泡泡中擠出來,一分鐘擠一顆,看來就算是無神論者也喜歡儀式。
我在亮晃晃的燈光中醒來,聽到了護理師的羞辱,我媽憂心地坐在醫院的椅子上,我的屁股下面墊著保潔墊。放眼望去是用一片片塑膠磁磚拼成的格子狀天花板,我心想它們看起來好像蘇打餅乾啊,呃,其實更像長方形的石磨全麥薄片。隔天,醫生開了抗憂鬱的帕羅西汀(Paxil)給我,但我拉不下臉來吃。學校出於擔心,禁止我參加這次的校外教學活動,我服藥的事已經悄悄地在學校走廊裡傳開來。
我特意買了支粉色的脣蜜,並努力笑得燦爛,但心裡暗暗發誓下次一定要成功。我腦中浮現一個閃閃發光的金屬物件,它肯定比藥丸更管用,保證能順利完成任務,在高中結束前,我滿腦子都是那個巨大的誘惑。
光亮的出現與消逝
不過,等我進了大學以後,我的世界終於出現了一絲光亮。某天,我跟一個肩膀寬闊、憨態可掬的捲髮男在走廊上擦肩而過,他有一雙泰迪熊般的棕色眼睛,身上散發出一股肉桂香。他是即興表演社團的成員,而且是最出色的那一個,他說話時的手勢很大,總是從充滿善意的角度講出異想天開的笑話,在這個冷酷無情的世界裡激起歡笑的漣漪。我經常坐在觀眾席看他表演,並為之驚嘆不已,這樣的暖男怎麼可能到手。
我花了好多年的時間,透過雙方都認識的朋友慢慢結識他,之後便經常扣應他主持的深夜即興饒舌節目,放大膽子試著……饒它一回舌!我甚至加入了即興表演社團,然後在某個晚上,我鼓起勇氣向他告白,他居然沒有像我猜想的那樣溜之大吉,走廊上那些男生的冷嘲熱諷讓我以為他肯定會那麼做,但他居然吻了我。
大學畢業後,我們搬到布魯克林同居,這個小公寓雖然只有一間臥室,以及一張紅色的富美家餐桌,但門廊倒是挺漂亮的。我找到一份工作,幫忙製作廣播電台的科學奇觀節目。他則繼續從事喜劇方面的工作──單口喜劇、即興表演和編劇,並兼差開計程車來養活自己。我們經常坐在門廊上,喝啤酒徹夜長聊,聊各自的白天生活,吐槽自己又幹了哪些蠢事。我覺得我找到了本以為不可能存在的至寶──一間庇護所,況且它還有股肉桂香,雖然它的牆壁是用不甚高明的諧音梗和韻文砌成的,但日益加高的牆還是能幫我擋掉現實世界的寒冷。
我滿腦子都是對未來的憧憬──當電視節目的編劇,一起搭建樹屋,在院子裡追著孩子玩。但這樣美好的生活卻在七年後被我親手毀了,某個深夜,在離他八百公里外的某個海灘上,我被月光、紅酒和篝火沖昏了頭,忍不住勾搭上那個我一整晚都不敢直視的金髮女郎。剛從海裡游罷歸來的她渾身溼透,身上起了無數的雞皮疙瘩,我想伸出舌頭把它們舔平。當我的手摟住她的腰肢,當我的脣吻上她的頸子,她開懷地笑了,我倆沐浴在星光下,身上的氣息也融為一體。事後,當我向捲髮哥和盤托出這一切,他對我說:「我們分手吧。」
但我不相信他,我不相信我倆這麼多年來攜手建立的一切,竟然如此不堪一擊。我求他重新考慮,我向他保證,那晚的事只是一時的意亂情迷,是一個無心之過,絕不會再發生。但他真的很生氣,也很受傷,無法再跟我這麼隨便的人在一起。失去了他,世界跟著變得黯淡無光,我們的朋友都知道我幹了什麼好事,全都疏遠我了。我因為不想解釋,所以躲著家人;我曾經頗為投入的工作,如今也一敗塗地,過去我認真追尋的那些科學故事,如今看來只不過是從各個方面──化學、神經學、昆蟲學──證明這一切的努力是多麼悲涼且毫無意義。
那巨大的誘惑又慢慢開始浮現在我的腦中,它的槍管在向我招手,說它想為我獻上一份最棒的禮物:一了百了。
但這時候,我的內心深處竟出現了一樣東西,那是我的脊椎骨嗎?我終究還是有點骨氣的,抑或只是我腦中某個痴心妄想的角落,想出了一個備案──只要我持續展現出夠強的悔意,說不定捲髮哥就會明白我有多後悔,並重新接納我。於是,我拿起了我最強的武器──一枝筆,給他寫了一封又一封信,我等待著、盼望著。我偶爾會開個蹩腳的玩笑,發出我倆才懂的求饒示好暗號。我曾在二○一二年的第一天寄一封電郵給他:「交往十二週年快樂。」但沒有任何回應,日子一天天過去,轉眼間我倆已分手三年,我仍故作開朗,可惜我的窗外越來越寂靜,熱力學第二定律向我展示它的威力,但我仍不肯死心。
這就是大衛.斯塔爾.喬丹引起我注意的原因,我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東西,讓他能無視於永遠不會成功的警告,不斷舉起縫衣針對抗混沌之力。他是否無意間發現了什麼訣竅,或是拿到了一帖藥方,能在冷酷的世界裡燃起希望?再加上他是個科學家,令我多了分想像,讓他堅持下去的東西,說不定跟我爸的世界觀不謀而合。也許他悟出了其中的關鍵,知道如何在沒有未來的世界裡懷抱希望、如何在黑暗的日子裡繼續前進、如何在沒有上帝的垂憐下保有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