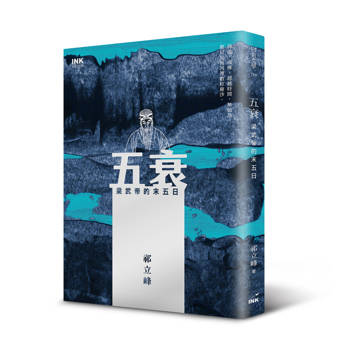一 倒數五日:亂臣侯景(關鍵字:異族)
1.
只要閉上眼睛,我就會看到一整爿無際無邊的蒼茫雪白。
即便已經很多年過去了,但如今早已長大成人的我,依舊時常想起懷朔鎮的冬天。那種鋪天蓋地而來的凜冽冷風,彷彿要將世間的一切生靈活物全都化成冰霰霜雪般的決絕,是我來到江南之後始終難以忘懷的。
後來我在臺城內殿的庫房裡,找到一只他州進貢的冰裂白玉瓷瓶。一旁的舍人告訴我—要能塑造出這般天然如冰層罅隙的裂紋,極其難得,極其珍貴,得仰賴上千名的工匠日夜窯燒,爐火不歇,打鑿不停,砸碎槌毀數百件失敗品之後,方足以製作出一只這樣渾然天成的傑作。
但我撫摸那只瓷瓶,固然白皙澄澈、卻始終感覺不到那冰層風雪般的冷。在我少數讀過的詩歌裡,好像曾有過這樣的形容與意象──「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就像不可語冰的夏蟲,奢言風、奢言雪那般,他們這些個南方詩人,哪裡懂什麼叫做冷、什麼才是真正的冰呢?
我向來不喜歡南方士人那種附庸風雅、吟詩作賦,所以讀過的詩並不多。但只有在懷朔鎮感受到的那種冷,會讓我想起古詩裡的句子—「朔風動勁草,邊馬有歸心」。離家幾萬里遠了,草木禽獸,誰能無情而不思歸呢?
記憶不斷回到剛剛從軍的那幾年—身材高壯、滿臉鬍髯,虎軀十圍的爾朱榮將軍,似乎也禁不起凍寒,在他那身明裲襠鎧之外,還另外裹上一襲獸皮大氅。然而我們這些底下兄弟就只剩下鎧甲穿,鐵衣縫接處都給覆雪結霜了。
相較前一個追隨的將軍鮮于氏,爾朱將軍已經稱得上是體恤軍士了。我們士卒營帳裡,冬夜裡還能燒柴取暖。那鮮于老賊根本不管麾下士兵的死活。每兩三天就有身體撐不住了的鎮兵被送離營區,不知流落何處。
但我雖怕冷但卻耐著住,可能從小習慣了。越過河北,冬天就顯得異常漫長,從九月一直到來年的三、四月,山路的霜雪沒有片刻解凍過。
這麼一說起來,我這才發現記憶裡的少年時代,好像經常感覺到冷。不只是身體的,也是心靈的,或說形而上的。寒冷讓我雙腿觳觫,牙根發顫。就像童年時那個如夢似真的場景—雪地裡成群的狼群,圍著一條野狗,要將牠給生吞啃囓,屍骨不全。
而我就是那條野狗。吃不飽身不暖,明知道狼牙利齒,還是義無反顧捨身一搏──不過大梁朝根本不是狼群,不過是群毫無反應力的呆騃木雞。
許多年過去了,屬下也開始喊我將軍。我據鞍跨馬,刀鐔舐血,征戰江湖,別人都說我侯景什麼都不怕。但我其實最怕的還是冷。就像後來的百姓經常說我殘忍,史家總是稱我暴虐,但暴力與文明本質上是相對的。就像愛與恨,恩怨與諒解,寒冷與溫暖也總是相對的。
人們常說真正懂黑暗的人,才能理解光明的可貴。但我卻覺得你必須真正懂得冷,才知道何謂溫暖。冷並不是一瞬間,而是緩慢的過程,如同凌遲這般的刑罰。從手指腳趾開始,褪去血色,接著是麻,再來是凍到發痛,如萬蟻囓咬那麼錐心刺骨,然後就無感了,麻木了。
要逆轉這個過程則需要更漫長的療癒。爾朱將軍允許士卒們燒柴燃爐的夜晚,大夥一擁到了炕沿爐前,將手指伸向篝火邊,發紫的肌膚慢慢褪成粉櫻般的顏色,再來是原本暫停的血液終於開始奔騁,從心臟汩汩流向四肢末梢,然後手指才終於有了知覺,緩慢的熱流在周身溫柔地流淌著。到此時身為人類的機能好像才真正活轉過來。
兵營大帳裡幾百兵卒就這麼貼緊在一起,烤火取暖。也就是這樣的時刻讓我體會到────人只有將自己的身體與心靈和另外一個人重疊在一起的時刻,才能全然理解對方的感情、思考、美麗與哀傷。
但大多數的時候,人們彼此之間距離很遠。就像我跟梁主之間。他是江南人,我是北方人。直到我軍攻陷建康,入主臺城,我才開始試著去理解眼前的這個老人。只是會不會太遲了呢?在大梁經歷了如此大規模、大毀滅的叛亂之後,在國家陷入這樣的凍寒之際,還有沒有回暖的可能呢?
本事: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雁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為北鎮戍兵,稍立功效︙︙天柱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弒胡氏,并誅其親屬。景始以私眾見榮,榮甚奇景,即委以軍事。(《梁書.侯景傳》)
2.
但若未來的史家重新檢視這場軍事行動,要將罪愆完全推賴於個人之一身,我也是要卻之不恭的。
你們可別忘了,我並非傳統士族出身,而是六鎮子弟,是鮮卑化的胡人,我從祖上到自己這一代,始終就只是一個小小的鎮兵家族。
如果你勤奮一些,如前朝漢代經師窮經皓首、願意前往中祕苑或翰林院,調閱輿地或地理方志的筆記,就會知道六鎮最初指的是「懷朔鎮」、「武川鎮」、「撫冥鎮」、「柔玄鎮」、「沃野鎮」、「懷荒鎮」這六個邊地鄉城。如今別說是江南了,就算中原人士,也鮮少人記得六鎮真正的名字,因為後來的「六鎮」往往成了一個統稱。朝廷在六鎮屯兵屯田,我就像涼州、冀州一帶的二十萬軍民一樣,說好聽是我們身為大魏的臣妾子民,實則是在魏國與柔然族之間的餘地。
兩國之間的餘地,在司馬遷的《史記》裡,將這樣的餘地稱為「甌脫」:「(大漢)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甌本來是陶器,但後來當成國家的代稱。某一年梁主北伐時的詔令甚至這麼寫—「我國家猶如金甌,不得損傷」。
把國家當成自己家,當成金甌玉徽般珍貴,這可真是荒唐。但金甌之外還有釉面、還有皮殼還有包漿,那就是六鎮,就是我的家鄉。在世界之外,在金貴珍寶的器皿之外的世界,談判的籌碼,軍事家的棋子,大國博弈之間的犧牲品。
很難想像吧。上古三代以來的賢君聖王,總是把什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掛在嘴邊。但就是偏偏就是有某些地方,有某一群人,某個場所,某個無人知曉的甌脫之地,沒辦法被接納成為這金匱寶匣的國家之一。
我實在不願意如此定義自己的家鄉,但它確實如此。每當柔然乾旱或大疫,草枯馬衰之時,六鎮就是首先被掠奪的目標。而大魏若鐵了心要針對草原民族報復,六鎮也是首先被徵召入伍的最前線。
到了我的父祖那一輩時,他們逕自決定要武裝村落以守護自己的身家性命,或許對大國來說我們只是散兵游勇,但人只有在捍衛自己珍愛之物時,才會凶狠發狂地跟人家拚命。也因此,我幼年就被帶到雪山裡作軍事訓練。當其他地方的孩童還在成群結隊、歡快玩耍的年紀,我們懷朔鎮孩子的世界裡,就剩下健身習武,保家衛國。
當然,你問我家在哪裡我知道,就是六鎮。就是冬夜裡大雪紛飛、草木銀白的淒冷世界。
但你問我衛的是哪一國,我就當真不確切要怎麼回答了。
即便如此,每次大魏與柔然的爭鬥,我們六鎮子弟總是有人犧牲。家家有寡婦獨悲、戶戶有孤兒垂淚。夜裡的懷朔鎮,我總是伴隨著如絡緯如蟬鳴、又如詩人低吟的啜泣聲入眠。
聽久了之後,我忽然覺得哭泣的聲音,哀號的聲音,很動人,很柔美,很悅耳。所以我有時在想,史家總是說我偏激殘暴,說我好殺戮。那都是一種誤解,我就喜歡聆聽人在死前,斬斷手腳,割舌劓鼻,卻將死不能的痛哭與嚎叫。
聽說人之將死,最後喪失的器官會是聽覺。我其實不太相信《禮記》說的那些什麼—「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怒」這一套。然而人之將亡,鳥之將死,確實會將喉嚨裡僅存的空氣,透過逼仄的聲道擠裂而出,像氣泡膨脹到了如晶球般的弧面。那種悶嗆、窒塞的聲音,最後一絲對生之欲望與掙扎都被壓縮到了無限小值。
那是最後的生存本能。疼痛,寒冷,後悔,怨恨,就是仰賴這些強烈的感情,人才算是活著。
本事:
……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皆擣殺之,其慘虐如此。(《梁書.侯景傳》)
3.
在一次行軍訓練演習時,我在雪山裡迷了路。我用粗短而凍傷發紅的手指,不斷刨挖著雪地,終於找到覆在層層厚雪底下的草根,簡直食不下嚥。你很難想像吧,那時我才只有六歲。
但也是那次迷路,我遇見了那條野狗。我在鎮上市集就看過牠幾次。總是流連於食攤之間,搖尾乞憐,討要到一點殘羹冷飯,就心滿意足地汪汪亂叫著。
但野狗畢竟是野狗,餐風露宿,很快地牠瘸了腿,毛皮上長了癩痢。孩童或攤商連餵養牠都不願意了。只剩下我偶爾還是會拿著家裡的碎骨試著餵食牠,但我沒給牠取名。
我阿娘曾經對我說:若給貍奴狗崽這些畜生取了名認了人,你就會錯把牠們當成對等的存在。所以我只換牠作「狗子」。
入冬之後,那條野狗就在鎮裡從此消失了蹤跡。我沒想到如今我跟牠一樣,陷入了雪山的絕境。
夜幕低垂,狼群嚎叫聲像呼群保義的將軍,登高一喊,此起彼落。就算僅六歲的我心裡也明白,得要先想辦法活得過今晚,才有可能獲救。狼群躡起利爪、悄然無聲接近,在漆黑裡,只剩兇殘眼瞳裡如鬼火般的煢煢亮光。我收斂起矮短的身體四肢,瑟縮在淺洞裡,將野狗擁入懷中,汲取最後的溫暖。
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當狼群圍上來時,野狗掙脫我的懷抱,狠狠地咬著領頭狼的脖頸。
惡狼當場鮮血噴濺,山谷裡迴盪著野獸搏鬥與臨死之際的怒吼。
那一刻我才真正體貼到,再怎麼孱弱怎麼無力的野獸,終究是一頭野獸。當牠被逼到了絕境,困進了牆角,再無退縮之餘地,牠也有可能奮力一搏、拚死求生。
也因此,我後來進入爾朱榮將軍的麾下,在練兵大操場上,初次自報家門時,我大聲說了自己的綽號——「狗子」。當作紀念那條野狗吧。我其實沒想過自己的名字被記載史冊圖
籙裡。但我讀過兵書史書,我太清楚那些自以為繼聖絕志的造作史家們,會怎麼去建構那些
傳記裡的汙名—「亂臣傳」、「奸凶傳」,「倖逆傳」。
詩人把我的起義寫成「一日朝市異」,將朝市傾淪的大罪過安在我身上;賦家描繪我成「野心之貪狼」,用非人非獸的動物來譬喻我的出身與族群。但你不需要用那些耽溺於故紙堆裡的史學家或文學家的定義來定義我。
我與你之間的差別在於、你不曾親眼見識過那個場景:滿身癩痢、前腳跛行,凍到站都站不穩的野狗,憑著半條爛命,發狠往狼的要害去咬的那股狠勁──也就是靠著這股狠勁,讓我一路撐到了現在。
當我第二次歸返江南之際,我就聽梁主,不,聽蕭衍老兒的侍從提到過一件超自然的怪事──天監初年,當時已經高齡八九十幾歲的釋寶誌和尚,有天忽然念出了一首讖詩。只是在當時的南方,一時沒人聽得懂這首詩,只管將它給謄抄了下來:
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
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
幾乎沒有南朝人知曉我給自己取的這個「狗子」的綽號。這太低俗,太惡趣,太不風雅。
但寶誌僧卻將它給預言了出來。就連我童年時受困於雪山,差點命絕於斯,當死未死之際的往事,都說得一清二楚。我甚至不確定,那時候這些事情已經發生了嗎?
不該發生的都發生了,該發生的卻又終究會發生。這到底是歷史還是預言,似乎也很難分得清了。就好像人們常說的那句格言—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它不會給人們留下任何教訓。
到了天監十三年(西元五一四年),寶誌和尚就圓寂了,如今他的金身供奉在定林寺。
我攻入建康城的前夕,還特別要求部隊,經寺廟地界時須繞道而行,不得進犯定林寺方圓十里。我侯景半生戎馬,軍旅倥傯,從來沒有真心服過誰,更不信梁主魏主鍾情服膺的佛理輪迴。但這位素未謀面的寶誌神僧,還當真有幾分意思。
南方人自始至終都不能理解六鎮子弟的心態。我們是徹頭徹尾的邊緣人。不是鮮卑人,不是柔然人,更不是南方漢人。我的阿爺那邊有羌族的血統,根據史家的記載、後世學者的研究筆記,說我們是經過鮮卑化或漢化的羌族。
不過哪一族也不重要。反正漢人總是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到底族類是什麼,異心又是什麼?最關鍵的問題是,你要怎麼定義「邊緣人」呢?
我在六鎮長大那幾年,跟著爾朱榮將軍叛服有時的那幾年,從來不曾用過「邊緣人」這個詞彙。直到來到洛陽,後來又到了江南,才真正懂得這個詞的指涉。它是指介於人的定義邊緣。是人也不是人,端看他做了什麼事,以及後來的歷史怎麼定義他。
多麼荒唐啊。人類本自有階級,社會本自有階級。士農工商,男女僧俗,四部四眾各司其職,這個我懂。但六鎮子弟始終不被當成真正的人那樣對待。很不公平不對嗎?南方的漢人做出什麼樣奸邪凶險的齷齪事,他都還是人。但我們出身在塞外,就成了人與野獸的混種。
如果要當野獸也無所謂,至少我要像當時救命的那條野狗。狗子的貪狂與狠勁,將讓我在這亂世繼續苟延殘喘。
本事:
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狗子,景小字。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梁書.侯景傳》)
1.
只要閉上眼睛,我就會看到一整爿無際無邊的蒼茫雪白。
即便已經很多年過去了,但如今早已長大成人的我,依舊時常想起懷朔鎮的冬天。那種鋪天蓋地而來的凜冽冷風,彷彿要將世間的一切生靈活物全都化成冰霰霜雪般的決絕,是我來到江南之後始終難以忘懷的。
後來我在臺城內殿的庫房裡,找到一只他州進貢的冰裂白玉瓷瓶。一旁的舍人告訴我—要能塑造出這般天然如冰層罅隙的裂紋,極其難得,極其珍貴,得仰賴上千名的工匠日夜窯燒,爐火不歇,打鑿不停,砸碎槌毀數百件失敗品之後,方足以製作出一只這樣渾然天成的傑作。
但我撫摸那只瓷瓶,固然白皙澄澈、卻始終感覺不到那冰層風雪般的冷。在我少數讀過的詩歌裡,好像曾有過這樣的形容與意象──「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就像不可語冰的夏蟲,奢言風、奢言雪那般,他們這些個南方詩人,哪裡懂什麼叫做冷、什麼才是真正的冰呢?
我向來不喜歡南方士人那種附庸風雅、吟詩作賦,所以讀過的詩並不多。但只有在懷朔鎮感受到的那種冷,會讓我想起古詩裡的句子—「朔風動勁草,邊馬有歸心」。離家幾萬里遠了,草木禽獸,誰能無情而不思歸呢?
記憶不斷回到剛剛從軍的那幾年—身材高壯、滿臉鬍髯,虎軀十圍的爾朱榮將軍,似乎也禁不起凍寒,在他那身明裲襠鎧之外,還另外裹上一襲獸皮大氅。然而我們這些底下兄弟就只剩下鎧甲穿,鐵衣縫接處都給覆雪結霜了。
相較前一個追隨的將軍鮮于氏,爾朱將軍已經稱得上是體恤軍士了。我們士卒營帳裡,冬夜裡還能燒柴取暖。那鮮于老賊根本不管麾下士兵的死活。每兩三天就有身體撐不住了的鎮兵被送離營區,不知流落何處。
但我雖怕冷但卻耐著住,可能從小習慣了。越過河北,冬天就顯得異常漫長,從九月一直到來年的三、四月,山路的霜雪沒有片刻解凍過。
這麼一說起來,我這才發現記憶裡的少年時代,好像經常感覺到冷。不只是身體的,也是心靈的,或說形而上的。寒冷讓我雙腿觳觫,牙根發顫。就像童年時那個如夢似真的場景—雪地裡成群的狼群,圍著一條野狗,要將牠給生吞啃囓,屍骨不全。
而我就是那條野狗。吃不飽身不暖,明知道狼牙利齒,還是義無反顧捨身一搏──不過大梁朝根本不是狼群,不過是群毫無反應力的呆騃木雞。
許多年過去了,屬下也開始喊我將軍。我據鞍跨馬,刀鐔舐血,征戰江湖,別人都說我侯景什麼都不怕。但我其實最怕的還是冷。就像後來的百姓經常說我殘忍,史家總是稱我暴虐,但暴力與文明本質上是相對的。就像愛與恨,恩怨與諒解,寒冷與溫暖也總是相對的。
人們常說真正懂黑暗的人,才能理解光明的可貴。但我卻覺得你必須真正懂得冷,才知道何謂溫暖。冷並不是一瞬間,而是緩慢的過程,如同凌遲這般的刑罰。從手指腳趾開始,褪去血色,接著是麻,再來是凍到發痛,如萬蟻囓咬那麼錐心刺骨,然後就無感了,麻木了。
要逆轉這個過程則需要更漫長的療癒。爾朱將軍允許士卒們燒柴燃爐的夜晚,大夥一擁到了炕沿爐前,將手指伸向篝火邊,發紫的肌膚慢慢褪成粉櫻般的顏色,再來是原本暫停的血液終於開始奔騁,從心臟汩汩流向四肢末梢,然後手指才終於有了知覺,緩慢的熱流在周身溫柔地流淌著。到此時身為人類的機能好像才真正活轉過來。
兵營大帳裡幾百兵卒就這麼貼緊在一起,烤火取暖。也就是這樣的時刻讓我體會到────人只有將自己的身體與心靈和另外一個人重疊在一起的時刻,才能全然理解對方的感情、思考、美麗與哀傷。
但大多數的時候,人們彼此之間距離很遠。就像我跟梁主之間。他是江南人,我是北方人。直到我軍攻陷建康,入主臺城,我才開始試著去理解眼前的這個老人。只是會不會太遲了呢?在大梁經歷了如此大規模、大毀滅的叛亂之後,在國家陷入這樣的凍寒之際,還有沒有回暖的可能呢?
本事: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雁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為北鎮戍兵,稍立功效︙︙天柱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弒胡氏,并誅其親屬。景始以私眾見榮,榮甚奇景,即委以軍事。(《梁書.侯景傳》)
2.
但若未來的史家重新檢視這場軍事行動,要將罪愆完全推賴於個人之一身,我也是要卻之不恭的。
你們可別忘了,我並非傳統士族出身,而是六鎮子弟,是鮮卑化的胡人,我從祖上到自己這一代,始終就只是一個小小的鎮兵家族。
如果你勤奮一些,如前朝漢代經師窮經皓首、願意前往中祕苑或翰林院,調閱輿地或地理方志的筆記,就會知道六鎮最初指的是「懷朔鎮」、「武川鎮」、「撫冥鎮」、「柔玄鎮」、「沃野鎮」、「懷荒鎮」這六個邊地鄉城。如今別說是江南了,就算中原人士,也鮮少人記得六鎮真正的名字,因為後來的「六鎮」往往成了一個統稱。朝廷在六鎮屯兵屯田,我就像涼州、冀州一帶的二十萬軍民一樣,說好聽是我們身為大魏的臣妾子民,實則是在魏國與柔然族之間的餘地。
兩國之間的餘地,在司馬遷的《史記》裡,將這樣的餘地稱為「甌脫」:「(大漢)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甌本來是陶器,但後來當成國家的代稱。某一年梁主北伐時的詔令甚至這麼寫—「我國家猶如金甌,不得損傷」。
把國家當成自己家,當成金甌玉徽般珍貴,這可真是荒唐。但金甌之外還有釉面、還有皮殼還有包漿,那就是六鎮,就是我的家鄉。在世界之外,在金貴珍寶的器皿之外的世界,談判的籌碼,軍事家的棋子,大國博弈之間的犧牲品。
很難想像吧。上古三代以來的賢君聖王,總是把什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掛在嘴邊。但就是偏偏就是有某些地方,有某一群人,某個場所,某個無人知曉的甌脫之地,沒辦法被接納成為這金匱寶匣的國家之一。
我實在不願意如此定義自己的家鄉,但它確實如此。每當柔然乾旱或大疫,草枯馬衰之時,六鎮就是首先被掠奪的目標。而大魏若鐵了心要針對草原民族報復,六鎮也是首先被徵召入伍的最前線。
到了我的父祖那一輩時,他們逕自決定要武裝村落以守護自己的身家性命,或許對大國來說我們只是散兵游勇,但人只有在捍衛自己珍愛之物時,才會凶狠發狂地跟人家拚命。也因此,我幼年就被帶到雪山裡作軍事訓練。當其他地方的孩童還在成群結隊、歡快玩耍的年紀,我們懷朔鎮孩子的世界裡,就剩下健身習武,保家衛國。
當然,你問我家在哪裡我知道,就是六鎮。就是冬夜裡大雪紛飛、草木銀白的淒冷世界。
但你問我衛的是哪一國,我就當真不確切要怎麼回答了。
即便如此,每次大魏與柔然的爭鬥,我們六鎮子弟總是有人犧牲。家家有寡婦獨悲、戶戶有孤兒垂淚。夜裡的懷朔鎮,我總是伴隨著如絡緯如蟬鳴、又如詩人低吟的啜泣聲入眠。
聽久了之後,我忽然覺得哭泣的聲音,哀號的聲音,很動人,很柔美,很悅耳。所以我有時在想,史家總是說我偏激殘暴,說我好殺戮。那都是一種誤解,我就喜歡聆聽人在死前,斬斷手腳,割舌劓鼻,卻將死不能的痛哭與嚎叫。
聽說人之將死,最後喪失的器官會是聽覺。我其實不太相信《禮記》說的那些什麼—「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怒」這一套。然而人之將亡,鳥之將死,確實會將喉嚨裡僅存的空氣,透過逼仄的聲道擠裂而出,像氣泡膨脹到了如晶球般的弧面。那種悶嗆、窒塞的聲音,最後一絲對生之欲望與掙扎都被壓縮到了無限小值。
那是最後的生存本能。疼痛,寒冷,後悔,怨恨,就是仰賴這些強烈的感情,人才算是活著。
本事:
……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皆擣殺之,其慘虐如此。(《梁書.侯景傳》)
3.
在一次行軍訓練演習時,我在雪山裡迷了路。我用粗短而凍傷發紅的手指,不斷刨挖著雪地,終於找到覆在層層厚雪底下的草根,簡直食不下嚥。你很難想像吧,那時我才只有六歲。
但也是那次迷路,我遇見了那條野狗。我在鎮上市集就看過牠幾次。總是流連於食攤之間,搖尾乞憐,討要到一點殘羹冷飯,就心滿意足地汪汪亂叫著。
但野狗畢竟是野狗,餐風露宿,很快地牠瘸了腿,毛皮上長了癩痢。孩童或攤商連餵養牠都不願意了。只剩下我偶爾還是會拿著家裡的碎骨試著餵食牠,但我沒給牠取名。
我阿娘曾經對我說:若給貍奴狗崽這些畜生取了名認了人,你就會錯把牠們當成對等的存在。所以我只換牠作「狗子」。
入冬之後,那條野狗就在鎮裡從此消失了蹤跡。我沒想到如今我跟牠一樣,陷入了雪山的絕境。
夜幕低垂,狼群嚎叫聲像呼群保義的將軍,登高一喊,此起彼落。就算僅六歲的我心裡也明白,得要先想辦法活得過今晚,才有可能獲救。狼群躡起利爪、悄然無聲接近,在漆黑裡,只剩兇殘眼瞳裡如鬼火般的煢煢亮光。我收斂起矮短的身體四肢,瑟縮在淺洞裡,將野狗擁入懷中,汲取最後的溫暖。
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當狼群圍上來時,野狗掙脫我的懷抱,狠狠地咬著領頭狼的脖頸。
惡狼當場鮮血噴濺,山谷裡迴盪著野獸搏鬥與臨死之際的怒吼。
那一刻我才真正體貼到,再怎麼孱弱怎麼無力的野獸,終究是一頭野獸。當牠被逼到了絕境,困進了牆角,再無退縮之餘地,牠也有可能奮力一搏、拚死求生。
也因此,我後來進入爾朱榮將軍的麾下,在練兵大操場上,初次自報家門時,我大聲說了自己的綽號——「狗子」。當作紀念那條野狗吧。我其實沒想過自己的名字被記載史冊圖
籙裡。但我讀過兵書史書,我太清楚那些自以為繼聖絕志的造作史家們,會怎麼去建構那些
傳記裡的汙名—「亂臣傳」、「奸凶傳」,「倖逆傳」。
詩人把我的起義寫成「一日朝市異」,將朝市傾淪的大罪過安在我身上;賦家描繪我成「野心之貪狼」,用非人非獸的動物來譬喻我的出身與族群。但你不需要用那些耽溺於故紙堆裡的史學家或文學家的定義來定義我。
我與你之間的差別在於、你不曾親眼見識過那個場景:滿身癩痢、前腳跛行,凍到站都站不穩的野狗,憑著半條爛命,發狠往狼的要害去咬的那股狠勁──也就是靠著這股狠勁,讓我一路撐到了現在。
當我第二次歸返江南之際,我就聽梁主,不,聽蕭衍老兒的侍從提到過一件超自然的怪事──天監初年,當時已經高齡八九十幾歲的釋寶誌和尚,有天忽然念出了一首讖詩。只是在當時的南方,一時沒人聽得懂這首詩,只管將它給謄抄了下來:
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
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
幾乎沒有南朝人知曉我給自己取的這個「狗子」的綽號。這太低俗,太惡趣,太不風雅。
但寶誌僧卻將它給預言了出來。就連我童年時受困於雪山,差點命絕於斯,當死未死之際的往事,都說得一清二楚。我甚至不確定,那時候這些事情已經發生了嗎?
不該發生的都發生了,該發生的卻又終究會發生。這到底是歷史還是預言,似乎也很難分得清了。就好像人們常說的那句格言—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它不會給人們留下任何教訓。
到了天監十三年(西元五一四年),寶誌和尚就圓寂了,如今他的金身供奉在定林寺。
我攻入建康城的前夕,還特別要求部隊,經寺廟地界時須繞道而行,不得進犯定林寺方圓十里。我侯景半生戎馬,軍旅倥傯,從來沒有真心服過誰,更不信梁主魏主鍾情服膺的佛理輪迴。但這位素未謀面的寶誌神僧,還當真有幾分意思。
南方人自始至終都不能理解六鎮子弟的心態。我們是徹頭徹尾的邊緣人。不是鮮卑人,不是柔然人,更不是南方漢人。我的阿爺那邊有羌族的血統,根據史家的記載、後世學者的研究筆記,說我們是經過鮮卑化或漢化的羌族。
不過哪一族也不重要。反正漢人總是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到底族類是什麼,異心又是什麼?最關鍵的問題是,你要怎麼定義「邊緣人」呢?
我在六鎮長大那幾年,跟著爾朱榮將軍叛服有時的那幾年,從來不曾用過「邊緣人」這個詞彙。直到來到洛陽,後來又到了江南,才真正懂得這個詞的指涉。它是指介於人的定義邊緣。是人也不是人,端看他做了什麼事,以及後來的歷史怎麼定義他。
多麼荒唐啊。人類本自有階級,社會本自有階級。士農工商,男女僧俗,四部四眾各司其職,這個我懂。但六鎮子弟始終不被當成真正的人那樣對待。很不公平不對嗎?南方的漢人做出什麼樣奸邪凶險的齷齪事,他都還是人。但我們出身在塞外,就成了人與野獸的混種。
如果要當野獸也無所謂,至少我要像當時救命的那條野狗。狗子的貪狂與狠勁,將讓我在這亂世繼續苟延殘喘。
本事:
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狗子,景小字。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梁書.侯景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