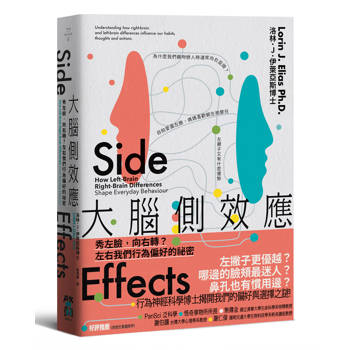序言(節錄)
人類行為是傾向一側的。我們的身體是對稱的,至少外觀上如此,但我們的行為卻不是這樣。左右手看起來區別不大,但幾乎90%的人慣用右手寫字和丟東西,從事技巧性活動時,也會經常使用右手。然而,多數人抱嬰兒時,通常會將其抱在左側。一般人擺姿勢讓別人畫肖像或拍照時,無論是16世紀的繪畫或者IG自拍照,都習慣露出左臉頰。而我們親吻愛人時,經常將頭向右歪斜。為何我們的行為會如此左右不對稱?我們又如何從這些現象去理解大腦呢?當我們將自拍照上傳到約會網站的個人簡介時,該如何運用這些資訊讓我們的自拍照得更好看?或者,我們該如何使用Photoshop處理政治廣告,讓候選人更能吸引某些選民?了解左右腦差異如何改變我們的觀點、傾向和態度,可以幫助我們在藝術、建築、廣告甚至運動方面,表現得更好嗎?讀完本書後,你將會了解大腦的側偏向(lateral bias)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行為,以及該如何善用這些資訊讓自己表現得更好。
在科學實驗室、醫院的腦部掃描儀上,或者從有單側腦損傷或進行腦部手術後的個人行為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左右腦的功能差異。然而,我們從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能輕易觀察到這類左右差異。人的失衡行為就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
我們的某些左右差異非常一致,而且由來已久。例如,無論男性或女性,無論來自馬來西亞或法國,90%的人都喜歡用右手。此外,根據對古代文物和藝術品的分析,人類這個物種在五十多個世紀裡一直偏好使用右手。其他強烈的側偏好(lateral preference)是近世才出現,只有數百年的歷史,好比肖像畫中擺姿勢的偏好。如果仔細觀察描繪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宗教藝術作品,便會發現在90%的畫作中,耶穌都是向右轉頭,露出左臉。我們抱嬰兒時的側向姿勢偏好也由來已久,但遠遠沒有像我們在群體層面上慣用右手的強烈偏好,大約70%的人抱嬰兒時都是抱在左側。
本書檢視的不平衡行為與我們潛在的左右腦差異有關。每個人的大腦都是獨一無二的。雖然每個人的臉龐外觀各不相同,但多數人的頭骨內都有相同的構造,具有同樣的整體形狀、位置和功能。然而,每個大腦卻是不一樣的。本書分析的左右差異都是「基於群體層面」。換句話說,這裡討論的偏好適用於一大群人的趨勢,但不一定適用於群體中的每一個人。以慣用手為例,從群體層面來看,一般人習慣使用右手,但有些人就是左撇子。我們知道90%的人都是右撇子,但這不表示左撇子有什麼問題,或者他們和右撇子大不相同。其他大腦偏側化(lateralization)的個體差異也是如此。對於90%的人來說,左腦主導語言,但這並不表示10%以右腦主導語言的人,在口說或書寫方面表現會比較差。
失衡行為的個體差異偶爾可能揭露了某些問題。例如,新手媽媽通常會朝左邊抱嬰兒,但患有憂鬱症的母親可能更常把嬰兒抱在右邊。如果你喜歡將孩子抱在右邊,是否表示你得了憂鬱症?絕對不是。然而,如果將喜歡朝右抱嬰兒的群體與朝左抱小孩的人相比,憂鬱症在前面那個群體中更為常見。本書探討群體層面和群體的趨勢,而非診斷或分析個人情況。
⋯⋯
當你閱讀本書時,有時會搞混左邊和右邊,但這不是你的錯。你沒有什麼問題。我有時會要你做一些奇特的腦力體操,我認為借助一、兩張圖片就可以克服左右混亂的難題。上頁圖2顯示了視覺系統的交叉作用,看起來很簡單:左側的空間進入右腦,反之亦然。右腦專門負責臉部辨識,導致我們自拍時習慣左臉對著鏡子。當我開始描述這種現象時,你必須想像一個人的臉位於視野中心,再想像兩個人面對面時,哪半張臉位於哪個空間,然後在你的腦海中再次顛倒左右,因為我們討論的場景是有人在照鏡子!
本書的編排方式是一次討論一種側偏好,這可能會給人一種印象,感覺側偏好通常是相互獨立的,但其實並非如此。例如,用手偏好(請參閱第一章)與我們對腳、耳朵和眼睛的側偏好(請參閱第二章)密切相關。擺姿勢偏好(請參閱第六章),也與我們在同一件藝術品中看到的光源方向偏好(請參閱第七章)有關。這並不表示某種偏好必然導致另一種偏好。我在不同章節討論不同的偏好,並不表示它們是離散和獨立的現象,許多偏好是相互關聯的。等我們單獨檢視過每項側偏好以後,我會在〈後記〉將這些偏好串聯起來。
第1章 慣用手:左撇子更優越嗎?(節錄)
最著名和最明顯的側效應就是慣用手。從群體層面來看,多數人偏好使用右手,從中便可輕易看出人腦是失衡的。慣用手並非新發現或新發展的側偏好,連《聖經》等古代文獻也曾提及。然而,不知何故,這種用手習慣卻成了被人研究最多但也最神祕的側偏好,人人都會注意到這種左右差異。專門探討慣用手的書籍有數十本,即便你沒有讀過其中一本,我猜你也曾想過自己為何會習慣使用某一隻手。一旦慣用手輕微受傷,我們便會深刻發現,另一隻手竟然如此無用,進而感到尷尬無比。
因此,本書最好先分析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左右手的習慣,但如此開篇也是最糟糕的。然而,我真的別無選擇。各位將在後續章節中發現,慣用手會影響(不是導致,而是影響)書中討論的其他多數側偏好。慣用手的影響錯綜複雜且無所不在,我研究別種側偏好時根本無法擺脫它。為了與其他章節的重點保持一致,我討論慣用手時會局限於日常生活,然後透過這個角度去描繪其他的側偏好。
右撇子占人口的比例有多少?我可以簡短回答,也能給出冗長的答案。簡短的答案是,大約90%的人習慣使用右手。那冗長的回答呢?右撇子占比多少,得看一個人的出生地,也取決於這個人的出生時間,還端賴他成長的文化和環境,以及他的性取向。這個比例甚至取決於一個人的(胚胎)發展軌跡,以及在出生過程中或者之前是否出了什麼差錯。這還取決於一個人的性別。話雖如此,取決的因素就只有這麼多。這些因素可能會將大約10%的比例推高一點,但也很有限。除了左撇子大會(儘管有左撇子的虛擬聚會,甚至還有一些面對面的集會,特別在8月13號的國際左撇子日﹝International Left Handers Day﹞),你永遠不會在某個時間、某個場所或某個文化中,找到一個超過50%的人偏好使用左手的龐大群體。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歷史。現代的圖像檔案中有大量關於慣用手的資料。我們可以查看一些圖片,譬如檢視重要文件的簽名照片,甚至查看數十年前的棒球卡背面,從中推斷某個去世已久之人的用手習慣。然而,這類紀錄只能追溯到這麼久以前。如果要問人類習慣用右手有多久了,該在哪裡找出答案呢?早期的文字紀錄非常罕見。例如,《舊約.士師記》第二十章第15–16節,描述了一場由700名左撇子或善用雙手者和26,000名右撇子戰鬥的場景。從這個比例(97%)來看,人類非常愛用右手。
然而,如果我們可以追溯到比《聖經》更久遠的時代,甚至回到數百萬年之前。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的狩獵方式顯示出慣用右手的跡象!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提供了有力證據,顯示當時的工具製造者是以右手旋轉石芯。從北京猿人製造的石器也能看到類似的模式。此外,幾乎每一種早期文化都會繪製人們從事狩獵之類的各種活動圖像。在某些圖像中(請參閱上圖3),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某個人只用一隻手投擲武器或手執物體。從克魯馬儂人(Cro-Magnon people)的手繪圖畫、對北美原住民藝術的考察,以及西元前2500年至1500年的埃及貝尼.哈桑(Beni Hasan)和希臘底比斯(Thebes)墳墓中,描繪人物用手從事技巧性活動的繪畫,便可看出人類對右手的強烈偏好。
有人調查過西元前15000年至西元1950年,繪製的一萬二千多件清楚描繪人類用單手做動作的藝術品,發現其中92.6%的作品都讓人物使用右手。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側偏好顯得非常穩定。舉例來說,在西元前3000年以前的圖像中,這個比例為90%;在西元500∼1700年的圖像中,這個比例則介於89∼94%。我們使用這種公認的不尋常研究技術,便可知道偏好使用右手的習慣,在過去五十個世紀裡基本上沒有改變!
然而,事情可沒那麼簡單。在出生於西元1900年左右的人之中,大約3%是左撇子,但在此之前和之後,左撇子的占比約為五十個世紀以來10%的平均水平。最棒的一組慣用手資料,基本上是偶然產生的。1986年,我那時還小,我的父母是《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的忠實訂閱者,就在那年9月,該雜誌最不尋常的一期版本寄到了我家信箱。它裡面有一張「刮一下、聞一下」(scratch-and-sniff)卡,超過1,100萬訂戶被要求辨識卡片上的氣味,回答一些人口統計的問題,然後將卡片寄回雜誌社。在人口統計的問題中,有兩題和慣用手有關,要求讀者填寫他們寫字和投擲時習慣使用哪隻手。調查結果令人難以置信。超過140萬人寄回填好的卡片,儘管慣用手似乎與嗅覺辨別(olfactory discrimination,這是最初啟發這項調查的問題之一)無關,但人口統計變量之間的相互關係足以透露某些訊息,尤其這組資料量十分龐大。
這批資料的原始報告指出了兩個關鍵情況。一個非常有趣,另一個則令人費解,還讓人有點擔憂。有趣的發現是,男性自稱是左撇子的可能性比女性高出約25%。第二項發現引起了多數人關注。在1950年後出生的受訪者中,左撇子相對普遍(請記住,這項調查是在1986年做的,因此1950年之後出生的人當時只有36歲以下)。但在出生較早的老年人之中,左撇子則愈來愈少,人數直線下降,在出生於1920 年或之前的受訪者之中,只有3%或4%是左撇子。第二組涵蓋同一時期的資料規模比較小(這次的抽樣對象是英國公民,不是美國公民),也透露出相同模式。1800年代末至1920年間出生的左撇子跑去哪裡了?在這個群體中,左撇子比率是否真的如此低,或者更糟的是,左撇子的死亡率是否比較高,因此年老的左撇子占比才這麼低?
人類行為是傾向一側的。我們的身體是對稱的,至少外觀上如此,但我們的行為卻不是這樣。左右手看起來區別不大,但幾乎90%的人慣用右手寫字和丟東西,從事技巧性活動時,也會經常使用右手。然而,多數人抱嬰兒時,通常會將其抱在左側。一般人擺姿勢讓別人畫肖像或拍照時,無論是16世紀的繪畫或者IG自拍照,都習慣露出左臉頰。而我們親吻愛人時,經常將頭向右歪斜。為何我們的行為會如此左右不對稱?我們又如何從這些現象去理解大腦呢?當我們將自拍照上傳到約會網站的個人簡介時,該如何運用這些資訊讓我們的自拍照得更好看?或者,我們該如何使用Photoshop處理政治廣告,讓候選人更能吸引某些選民?了解左右腦差異如何改變我們的觀點、傾向和態度,可以幫助我們在藝術、建築、廣告甚至運動方面,表現得更好嗎?讀完本書後,你將會了解大腦的側偏向(lateral bias)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行為,以及該如何善用這些資訊讓自己表現得更好。
在科學實驗室、醫院的腦部掃描儀上,或者從有單側腦損傷或進行腦部手術後的個人行為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左右腦的功能差異。然而,我們從正常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能輕易觀察到這類左右差異。人的失衡行為就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
我們的某些左右差異非常一致,而且由來已久。例如,無論男性或女性,無論來自馬來西亞或法國,90%的人都喜歡用右手。此外,根據對古代文物和藝術品的分析,人類這個物種在五十多個世紀裡一直偏好使用右手。其他強烈的側偏好(lateral preference)是近世才出現,只有數百年的歷史,好比肖像畫中擺姿勢的偏好。如果仔細觀察描繪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宗教藝術作品,便會發現在90%的畫作中,耶穌都是向右轉頭,露出左臉。我們抱嬰兒時的側向姿勢偏好也由來已久,但遠遠沒有像我們在群體層面上慣用右手的強烈偏好,大約70%的人抱嬰兒時都是抱在左側。
本書檢視的不平衡行為與我們潛在的左右腦差異有關。每個人的大腦都是獨一無二的。雖然每個人的臉龐外觀各不相同,但多數人的頭骨內都有相同的構造,具有同樣的整體形狀、位置和功能。然而,每個大腦卻是不一樣的。本書分析的左右差異都是「基於群體層面」。換句話說,這裡討論的偏好適用於一大群人的趨勢,但不一定適用於群體中的每一個人。以慣用手為例,從群體層面來看,一般人習慣使用右手,但有些人就是左撇子。我們知道90%的人都是右撇子,但這不表示左撇子有什麼問題,或者他們和右撇子大不相同。其他大腦偏側化(lateralization)的個體差異也是如此。對於90%的人來說,左腦主導語言,但這並不表示10%以右腦主導語言的人,在口說或書寫方面表現會比較差。
失衡行為的個體差異偶爾可能揭露了某些問題。例如,新手媽媽通常會朝左邊抱嬰兒,但患有憂鬱症的母親可能更常把嬰兒抱在右邊。如果你喜歡將孩子抱在右邊,是否表示你得了憂鬱症?絕對不是。然而,如果將喜歡朝右抱嬰兒的群體與朝左抱小孩的人相比,憂鬱症在前面那個群體中更為常見。本書探討群體層面和群體的趨勢,而非診斷或分析個人情況。
⋯⋯
當你閱讀本書時,有時會搞混左邊和右邊,但這不是你的錯。你沒有什麼問題。我有時會要你做一些奇特的腦力體操,我認為借助一、兩張圖片就可以克服左右混亂的難題。上頁圖2顯示了視覺系統的交叉作用,看起來很簡單:左側的空間進入右腦,反之亦然。右腦專門負責臉部辨識,導致我們自拍時習慣左臉對著鏡子。當我開始描述這種現象時,你必須想像一個人的臉位於視野中心,再想像兩個人面對面時,哪半張臉位於哪個空間,然後在你的腦海中再次顛倒左右,因為我們討論的場景是有人在照鏡子!
本書的編排方式是一次討論一種側偏好,這可能會給人一種印象,感覺側偏好通常是相互獨立的,但其實並非如此。例如,用手偏好(請參閱第一章)與我們對腳、耳朵和眼睛的側偏好(請參閱第二章)密切相關。擺姿勢偏好(請參閱第六章),也與我們在同一件藝術品中看到的光源方向偏好(請參閱第七章)有關。這並不表示某種偏好必然導致另一種偏好。我在不同章節討論不同的偏好,並不表示它們是離散和獨立的現象,許多偏好是相互關聯的。等我們單獨檢視過每項側偏好以後,我會在〈後記〉將這些偏好串聯起來。
第1章 慣用手:左撇子更優越嗎?(節錄)
最著名和最明顯的側效應就是慣用手。從群體層面來看,多數人偏好使用右手,從中便可輕易看出人腦是失衡的。慣用手並非新發現或新發展的側偏好,連《聖經》等古代文獻也曾提及。然而,不知何故,這種用手習慣卻成了被人研究最多但也最神祕的側偏好,人人都會注意到這種左右差異。專門探討慣用手的書籍有數十本,即便你沒有讀過其中一本,我猜你也曾想過自己為何會習慣使用某一隻手。一旦慣用手輕微受傷,我們便會深刻發現,另一隻手竟然如此無用,進而感到尷尬無比。
因此,本書最好先分析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左右手的習慣,但如此開篇也是最糟糕的。然而,我真的別無選擇。各位將在後續章節中發現,慣用手會影響(不是導致,而是影響)書中討論的其他多數側偏好。慣用手的影響錯綜複雜且無所不在,我研究別種側偏好時根本無法擺脫它。為了與其他章節的重點保持一致,我討論慣用手時會局限於日常生活,然後透過這個角度去描繪其他的側偏好。
右撇子占人口的比例有多少?我可以簡短回答,也能給出冗長的答案。簡短的答案是,大約90%的人習慣使用右手。那冗長的回答呢?右撇子占比多少,得看一個人的出生地,也取決於這個人的出生時間,還端賴他成長的文化和環境,以及他的性取向。這個比例甚至取決於一個人的(胚胎)發展軌跡,以及在出生過程中或者之前是否出了什麼差錯。這還取決於一個人的性別。話雖如此,取決的因素就只有這麼多。這些因素可能會將大約10%的比例推高一點,但也很有限。除了左撇子大會(儘管有左撇子的虛擬聚會,甚至還有一些面對面的集會,特別在8月13號的國際左撇子日﹝International Left Handers Day﹞),你永遠不會在某個時間、某個場所或某個文化中,找到一個超過50%的人偏好使用左手的龐大群體。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歷史。現代的圖像檔案中有大量關於慣用手的資料。我們可以查看一些圖片,譬如檢視重要文件的簽名照片,甚至查看數十年前的棒球卡背面,從中推斷某個去世已久之人的用手習慣。然而,這類紀錄只能追溯到這麼久以前。如果要問人類習慣用右手有多久了,該在哪裡找出答案呢?早期的文字紀錄非常罕見。例如,《舊約.士師記》第二十章第15–16節,描述了一場由700名左撇子或善用雙手者和26,000名右撇子戰鬥的場景。從這個比例(97%)來看,人類非常愛用右手。
然而,如果我們可以追溯到比《聖經》更久遠的時代,甚至回到數百萬年之前。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的狩獵方式顯示出慣用右手的跡象!舊石器時代的石器提供了有力證據,顯示當時的工具製造者是以右手旋轉石芯。從北京猿人製造的石器也能看到類似的模式。此外,幾乎每一種早期文化都會繪製人們從事狩獵之類的各種活動圖像。在某些圖像中(請參閱上圖3),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某個人只用一隻手投擲武器或手執物體。從克魯馬儂人(Cro-Magnon people)的手繪圖畫、對北美原住民藝術的考察,以及西元前2500年至1500年的埃及貝尼.哈桑(Beni Hasan)和希臘底比斯(Thebes)墳墓中,描繪人物用手從事技巧性活動的繪畫,便可看出人類對右手的強烈偏好。
有人調查過西元前15000年至西元1950年,繪製的一萬二千多件清楚描繪人類用單手做動作的藝術品,發現其中92.6%的作品都讓人物使用右手。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側偏好顯得非常穩定。舉例來說,在西元前3000年以前的圖像中,這個比例為90%;在西元500∼1700年的圖像中,這個比例則介於89∼94%。我們使用這種公認的不尋常研究技術,便可知道偏好使用右手的習慣,在過去五十個世紀裡基本上沒有改變!
然而,事情可沒那麼簡單。在出生於西元1900年左右的人之中,大約3%是左撇子,但在此之前和之後,左撇子的占比約為五十個世紀以來10%的平均水平。最棒的一組慣用手資料,基本上是偶然產生的。1986年,我那時還小,我的父母是《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的忠實訂閱者,就在那年9月,該雜誌最不尋常的一期版本寄到了我家信箱。它裡面有一張「刮一下、聞一下」(scratch-and-sniff)卡,超過1,100萬訂戶被要求辨識卡片上的氣味,回答一些人口統計的問題,然後將卡片寄回雜誌社。在人口統計的問題中,有兩題和慣用手有關,要求讀者填寫他們寫字和投擲時習慣使用哪隻手。調查結果令人難以置信。超過140萬人寄回填好的卡片,儘管慣用手似乎與嗅覺辨別(olfactory discrimination,這是最初啟發這項調查的問題之一)無關,但人口統計變量之間的相互關係足以透露某些訊息,尤其這組資料量十分龐大。
這批資料的原始報告指出了兩個關鍵情況。一個非常有趣,另一個則令人費解,還讓人有點擔憂。有趣的發現是,男性自稱是左撇子的可能性比女性高出約25%。第二項發現引起了多數人關注。在1950年後出生的受訪者中,左撇子相對普遍(請記住,這項調查是在1986年做的,因此1950年之後出生的人當時只有36歲以下)。但在出生較早的老年人之中,左撇子則愈來愈少,人數直線下降,在出生於1920 年或之前的受訪者之中,只有3%或4%是左撇子。第二組涵蓋同一時期的資料規模比較小(這次的抽樣對象是英國公民,不是美國公民),也透露出相同模式。1800年代末至1920年間出生的左撇子跑去哪裡了?在這個群體中,左撇子比率是否真的如此低,或者更糟的是,左撇子的死亡率是否比較高,因此年老的左撇子占比才這麼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