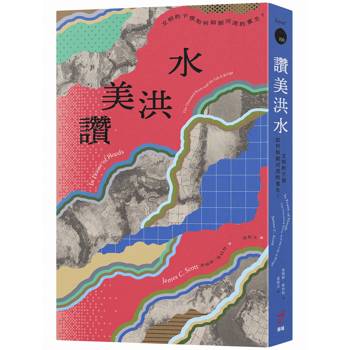導論:談談河流
把時間拉長來看,河流是活的。它們誕生、它們變化、它們改變河道、它們創造通往大海的新水路;它們緩慢流淌,也急速奔流;它們(通常)蘊含著豐富的生命;它們會類似自然死亡一樣步入生命終點;它們會受到傷害變成殘廢,甚至遭到謀殺。河流雖然必須遵循水力法則,但每一條河流都有自己的性格與歷史。因此,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每一條河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命歷程與生態傳記。任何河流,如奧利諾科河(Orinoco)、尚比西河(Zambesi)、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黃河、恆河、亞馬遜河(Amazon)、多瑙河(Danube)、伊洛瓦底江,從各方面來說都是獨特的,就像生活在河邊的薩滿、哲人、漁夫、哲學家、暴君、叛亂者與聖人一樣,有著自己獨特的一生。當然,河流的預期壽命遠比個人生命長得多。但這種預期壽命已經被人類發明的火藥、挖土機與鋼筋混凝土改變;此外還有厚人類世(thick Anthropocene)的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人類的干預已經大大提高河流的死亡率與發病率。
談到人的一生,我們會從人的壽命來思考,那麼談到河流的一生,我們就應該擴大我們的時間透鏡,從「河流的時間」來思考。我們預設的時間單位理應是河流的生命。一旦採取這種時間尺度,我們的視角將完全不同於智人的思維模式,因為智人的時間尺度頂多只有三個世代(我們的父母、自己與我們的子女)。其他的實體,例如我們要談的河流,運作的時間尺度往往遠比人類漫長,我們唯有採用它們的時間尺度才能了解。如果我們研究的是其他生物的生命長度,例如魚類、昆蟲或鳥類,那麼我們的時間感也會成比例地縮短,除非我們研究的是整個物種的生命長度。
因此,我們採取的時間透鏡往往取決於我們想了解的對象。在地球長達長達四、五十億年的地質時間裡,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只是個嬰兒。如果我們依照尼爾‧舒賓(Neil Shubin)的圖表,把地球的歷史成比例縮減到只有一年,一月一日代表大霹靂(Big Bang),而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午夜代表現在,那麼直到六月為止,地球上只有單細胞微生物,如藻類、細菌與變形蟲。2最初的人類出現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多數河流直到末次冰盛期由盛轉衰之時,才轉變成我們今日熟悉的面貌,時間大概距今二萬年前。在那之前,地球上絕大多數的水都鎖在極地冰帽裡,海平面也比現在低得多(大約低一百二十公尺),許多河流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不過是涓滴細流。之後,伴隨而來長達六千年的劇烈融水脈動(meltwater pulse)讓海平面上升大約一百公尺,形成巨大的海灣或湖泊,淹沒了許多低窪的河流三角洲,包括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隨後陸地因為不再負擔冰河的重量而隆起,加上沉積物的沉積與海平面稍微下降,產生了我們今日熟悉的河流樣貌。另一個判斷的例子是北美洲的聖羅倫斯河(St. Lawrence River)。聖羅倫斯河今日的形式,源自於冰封的阿格西湖(Lake Agassiz)與勞倫泰冰蓋(Laurentide ice sheet)迅速融化,導致原本被冰川重壓的陸地反彈上升。大約一萬年前,冰川融冰產生的巨大脈動往東沿著地質斷層線傾洩而下,這條斷層線就是今日聖羅倫斯河的河道。一些地質學家認為,這場重大的氣候學事件導致海平面驟升一到三公尺,造成史無前例的洪水,也讓北大西洋氣候更加嚴寒。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重點是,從地質學來說,此時許多河流仍處於萌芽階段。與人類的生命相比,這些河流幾乎是長生不老,然而與整個物種相比,河流卻遠比我們年輕許多。
那麼,究竟什麼是河流?對絕大多數讀者來說,包括我在內,提到一條河的名字,例如密西西比河與尼羅河,總會想到地圖上標示的河流河道,從源頭開始,穿過陸地,最後注入大海,前提是如果這條河「乖巧」的話。透過不同專家的透鏡,我們會會發現一條河擁有不同的特定利益。對水文工程師來說,河流代表可以興建水壩發電,或應該興建堤防與溢洪道來保護有價值的地產。對公衛專家來說,河流代表可以提供飲用水給沿岸居民。對於在氾濫平原耕種的農民來說,河流除了是重要的灌溉水源,也能帶來有養分的沉積物。對商人與船運公司來說,河流代表可以航行的通衢大道,使人可以運送貨物到上下游。對製革廠、水泥廠或化學工業來說,河流可能只是一個方便而且免費的汙水排放系統。上述這些說法,或多或少都把流動的河水當成一種可以用來獲利的資源,或者說得好聽一點,可以為全人類帶來好處。
本書拒絕採取這種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主張用更寬廣的角度理解河流。首先,我們堅持把河流視為各種生命形式的集合體,有無數的生命仰賴河流存在並獲益。在這些生命形式中,智人也是其中之一──或者說,智人只是其中之一。河流中還存在數百萬種其他生命,包括生命短暫的昆蟲、水鳥、貽貝、魚類、氾濫平原上的植物與樹木、長壽的淡水豚與斑真鮰。所以,如果我們想像河流的所有公民組織議會,針對河流的狀況與命運進行辯論,那麼人類將只是少數黨。3(我將在第五章試圖想像這樣的場景,讓其他公民也有發聲的機會。)傳統上,我們對絕大多數河流的理解,總是局限在河流的幹流上,也就是源頭以下的地區,以及三角洲與分流以上的地區。這種習慣似乎來自於地圖繪製人員的通行做法,他們總是將「河流」最大的流動部分標示出來,接著上溯直到冰川、湖泊或泉水為止,然後將此地標示為河源。為了追溯尼羅河、湄公河或亞馬遜河的源頭而死亡的帝國探險家人數,幾乎與率先攀登世界最高峰而死亡的人數不相上下。此外,在河源的判定上,不僅長度最長的上流支流可以成為河源,連水量最大的上流支流也可以成為河源。簡單地說,河流從哪裡「開始」,完全是主觀判斷。
如果我們認為河流是所有仰賴流水、淤泥、黏土與砂礫(所有這些元素我們都稱之為河流)的生命形式的集合體,那麼我們對於河流的概念,就必須包含河流的所有上流支流與三角洲分流。這些支流分流構成了整個流水與氾濫平原系統,許多仰賴河流的生命形式也在眾多水路之間遷徙,並且依賴洪水脈動取得營養與進行繁殖。這些事實需要一個有系統的觀點。河流不能當成樹幹來理解,而應該當成植物,我們要了解植物,就必須考慮植物的葉子與根,還有植物所需的養分,養分在植物內部流動,使植物各部分連繫成一個整體。
從生物的角度來看,河流整體包含了支流、濕地、氾濫平原、回水區、漩渦、週期性的沼澤地,這意味著貨真價實的生物形式走廊。距離河流與氾濫平原愈遠,生物的生命濃度下降得愈劇烈。這種下跌的現象不僅發生在生活在水裡或水邊的魚類、雙殼貝類、水鳥與烏龜身上,也發生在仰賴生物多樣性以獲取營養的河流鳥類(例如猛禽與蒼鷺)、哺乳動物與爬蟲類身上。不只動物,連植物也是如此:生活在水中的植物(藻類、草與水生植物)與生活在水邊的植物,都仰賴季節性的洪水脈動提供的養分維生。植物繁盛會吸引草食性動物(如加拿大馬鹿與鹿)前來,之後肉食性動物(狼與大型貓科動物)則緊隨而至獵食草食性動物。
如果流動的水代表「河流性質」中不可或缺的養分,那麼或許我們的觀點還是太狹隘。人們也許會問,為什麼我們不重視那些地圖上從未標明的微型流動,難道只因為這些流動太微小或屬於季節性?每條支流都有自己的支流,而支流的支流當然也有更小的涓滴細流源源不斷地提供水源。同樣的,在地圖上繪製河流的人決定在那裡停筆,也是獨斷的判斷。因此,恰當而言,只有「水景」(waterscape)一詞才能涵蓋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河流。這也是(或理應是)我們對「流域」(watershed)一詞的理解。如果我們把流域想成循環系統,那麼雨水、露水、只在春天形成的池塘、泉水,這些微型水路就成了支撐整個系統的毛細管,或者更好的說法是微型支流。這些微型支流提供的不只是水。由於它們布滿整個流域,因此絕大部分河流生態系需要的養分都由它們收集運送。如果排除掉這些微型支流與洪水脈動,那麼剩餘的河道根本無法維持豐富的生命形式。
我覺得可以把河流的運作方式想像成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只是兩者的運作方式是相反的。植物是藉由毛細現象來對抗重力,但流域的運作完全仰賴重力。植物的根部靠著數百萬根菌根連結,收集必需的養分供植物生長與繁殖。從功能來看,這些菌根就像流域中的數百萬個潮濕地,緩慢地聚集與傳送蘊涵養分的水到溪流與支流,然後匯入幹流、分流,最終注入大海。植物的葉子與果實也像豐饒而肥沃的氾濫平原(無論有沒有被開墾),將整個流域的養分匯聚,支撐起河流生命的豐富性。
*
河流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很多事」。對人類中心論與大加速感興趣的人,河流是醒目的例證,顯示人類試圖控制與馴化自然過程將造成什麼結果。事實上,我們至今仍無法完全理解自然的複雜與多變。十九世紀中葉,喬治‧伯金斯‧馬許(George Perkins Marsh)在他的作品《人與自然》(Man and Nature)中提出了非常有先見之明地提出河流是人類影響自然系統的第一個例證。4各地的氾濫平原是人類早期文明的生產中心。管理氾濫平原、提升灌溉水利、控制洪水與運送貨物(特別是木材),成為治理國家的首要之務。因此,當人類最初努力馴服這個野蠻的自然世界時,他們的焦點就是河流。從羅馬的輸水道,到漢朝的水利專家,再到十七世紀晚期歐洲的運河泡沫,為了政治與經濟利益,人類投入龐大的資源管理河流。因此,如果我們想要了解人類干預複雜自然系統使其符合人類與國家目的的歷史,那麼河流管理的故事,將是用來衡量人類中心論的理想指標。
把時間拉長來看,河流是活的。它們誕生、它們變化、它們改變河道、它們創造通往大海的新水路;它們緩慢流淌,也急速奔流;它們(通常)蘊含著豐富的生命;它們會類似自然死亡一樣步入生命終點;它們會受到傷害變成殘廢,甚至遭到謀殺。河流雖然必須遵循水力法則,但每一條河流都有自己的性格與歷史。因此,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每一條河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命歷程與生態傳記。任何河流,如奧利諾科河(Orinoco)、尚比西河(Zambesi)、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黃河、恆河、亞馬遜河(Amazon)、多瑙河(Danube)、伊洛瓦底江,從各方面來說都是獨特的,就像生活在河邊的薩滿、哲人、漁夫、哲學家、暴君、叛亂者與聖人一樣,有著自己獨特的一生。當然,河流的預期壽命遠比個人生命長得多。但這種預期壽命已經被人類發明的火藥、挖土機與鋼筋混凝土改變;此外還有厚人類世(thick Anthropocene)的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人類的干預已經大大提高河流的死亡率與發病率。
談到人的一生,我們會從人的壽命來思考,那麼談到河流的一生,我們就應該擴大我們的時間透鏡,從「河流的時間」來思考。我們預設的時間單位理應是河流的生命。一旦採取這種時間尺度,我們的視角將完全不同於智人的思維模式,因為智人的時間尺度頂多只有三個世代(我們的父母、自己與我們的子女)。其他的實體,例如我們要談的河流,運作的時間尺度往往遠比人類漫長,我們唯有採用它們的時間尺度才能了解。如果我們研究的是其他生物的生命長度,例如魚類、昆蟲或鳥類,那麼我們的時間感也會成比例地縮短,除非我們研究的是整個物種的生命長度。
因此,我們採取的時間透鏡往往取決於我們想了解的對象。在地球長達長達四、五十億年的地質時間裡,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只是個嬰兒。如果我們依照尼爾‧舒賓(Neil Shubin)的圖表,把地球的歷史成比例縮減到只有一年,一月一日代表大霹靂(Big Bang),而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午夜代表現在,那麼直到六月為止,地球上只有單細胞微生物,如藻類、細菌與變形蟲。2最初的人類出現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大多數河流直到末次冰盛期由盛轉衰之時,才轉變成我們今日熟悉的面貌,時間大概距今二萬年前。在那之前,地球上絕大多數的水都鎖在極地冰帽裡,海平面也比現在低得多(大約低一百二十公尺),許多河流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不過是涓滴細流。之後,伴隨而來長達六千年的劇烈融水脈動(meltwater pulse)讓海平面上升大約一百公尺,形成巨大的海灣或湖泊,淹沒了許多低窪的河流三角洲,包括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隨後陸地因為不再負擔冰河的重量而隆起,加上沉積物的沉積與海平面稍微下降,產生了我們今日熟悉的河流樣貌。另一個判斷的例子是北美洲的聖羅倫斯河(St. Lawrence River)。聖羅倫斯河今日的形式,源自於冰封的阿格西湖(Lake Agassiz)與勞倫泰冰蓋(Laurentide ice sheet)迅速融化,導致原本被冰川重壓的陸地反彈上升。大約一萬年前,冰川融冰產生的巨大脈動往東沿著地質斷層線傾洩而下,這條斷層線就是今日聖羅倫斯河的河道。一些地質學家認為,這場重大的氣候學事件導致海平面驟升一到三公尺,造成史無前例的洪水,也讓北大西洋氣候更加嚴寒。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重點是,從地質學來說,此時許多河流仍處於萌芽階段。與人類的生命相比,這些河流幾乎是長生不老,然而與整個物種相比,河流卻遠比我們年輕許多。
那麼,究竟什麼是河流?對絕大多數讀者來說,包括我在內,提到一條河的名字,例如密西西比河與尼羅河,總會想到地圖上標示的河流河道,從源頭開始,穿過陸地,最後注入大海,前提是如果這條河「乖巧」的話。透過不同專家的透鏡,我們會會發現一條河擁有不同的特定利益。對水文工程師來說,河流代表可以興建水壩發電,或應該興建堤防與溢洪道來保護有價值的地產。對公衛專家來說,河流代表可以提供飲用水給沿岸居民。對於在氾濫平原耕種的農民來說,河流除了是重要的灌溉水源,也能帶來有養分的沉積物。對商人與船運公司來說,河流代表可以航行的通衢大道,使人可以運送貨物到上下游。對製革廠、水泥廠或化學工業來說,河流可能只是一個方便而且免費的汙水排放系統。上述這些說法,或多或少都把流動的河水當成一種可以用來獲利的資源,或者說得好聽一點,可以為全人類帶來好處。
本書拒絕採取這種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觀點,主張用更寬廣的角度理解河流。首先,我們堅持把河流視為各種生命形式的集合體,有無數的生命仰賴河流存在並獲益。在這些生命形式中,智人也是其中之一──或者說,智人只是其中之一。河流中還存在數百萬種其他生命,包括生命短暫的昆蟲、水鳥、貽貝、魚類、氾濫平原上的植物與樹木、長壽的淡水豚與斑真鮰。所以,如果我們想像河流的所有公民組織議會,針對河流的狀況與命運進行辯論,那麼人類將只是少數黨。3(我將在第五章試圖想像這樣的場景,讓其他公民也有發聲的機會。)傳統上,我們對絕大多數河流的理解,總是局限在河流的幹流上,也就是源頭以下的地區,以及三角洲與分流以上的地區。這種習慣似乎來自於地圖繪製人員的通行做法,他們總是將「河流」最大的流動部分標示出來,接著上溯直到冰川、湖泊或泉水為止,然後將此地標示為河源。為了追溯尼羅河、湄公河或亞馬遜河的源頭而死亡的帝國探險家人數,幾乎與率先攀登世界最高峰而死亡的人數不相上下。此外,在河源的判定上,不僅長度最長的上流支流可以成為河源,連水量最大的上流支流也可以成為河源。簡單地說,河流從哪裡「開始」,完全是主觀判斷。
如果我們認為河流是所有仰賴流水、淤泥、黏土與砂礫(所有這些元素我們都稱之為河流)的生命形式的集合體,那麼我們對於河流的概念,就必須包含河流的所有上流支流與三角洲分流。這些支流分流構成了整個流水與氾濫平原系統,許多仰賴河流的生命形式也在眾多水路之間遷徙,並且依賴洪水脈動取得營養與進行繁殖。這些事實需要一個有系統的觀點。河流不能當成樹幹來理解,而應該當成植物,我們要了解植物,就必須考慮植物的葉子與根,還有植物所需的養分,養分在植物內部流動,使植物各部分連繫成一個整體。
從生物的角度來看,河流整體包含了支流、濕地、氾濫平原、回水區、漩渦、週期性的沼澤地,這意味著貨真價實的生物形式走廊。距離河流與氾濫平原愈遠,生物的生命濃度下降得愈劇烈。這種下跌的現象不僅發生在生活在水裡或水邊的魚類、雙殼貝類、水鳥與烏龜身上,也發生在仰賴生物多樣性以獲取營養的河流鳥類(例如猛禽與蒼鷺)、哺乳動物與爬蟲類身上。不只動物,連植物也是如此:生活在水中的植物(藻類、草與水生植物)與生活在水邊的植物,都仰賴季節性的洪水脈動提供的養分維生。植物繁盛會吸引草食性動物(如加拿大馬鹿與鹿)前來,之後肉食性動物(狼與大型貓科動物)則緊隨而至獵食草食性動物。
如果流動的水代表「河流性質」中不可或缺的養分,那麼或許我們的觀點還是太狹隘。人們也許會問,為什麼我們不重視那些地圖上從未標明的微型流動,難道只因為這些流動太微小或屬於季節性?每條支流都有自己的支流,而支流的支流當然也有更小的涓滴細流源源不斷地提供水源。同樣的,在地圖上繪製河流的人決定在那裡停筆,也是獨斷的判斷。因此,恰當而言,只有「水景」(waterscape)一詞才能涵蓋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河流。這也是(或理應是)我們對「流域」(watershed)一詞的理解。如果我們把流域想成循環系統,那麼雨水、露水、只在春天形成的池塘、泉水,這些微型水路就成了支撐整個系統的毛細管,或者更好的說法是微型支流。這些微型支流提供的不只是水。由於它們布滿整個流域,因此絕大部分河流生態系需要的養分都由它們收集運送。如果排除掉這些微型支流與洪水脈動,那麼剩餘的河道根本無法維持豐富的生命形式。
我覺得可以把河流的運作方式想像成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只是兩者的運作方式是相反的。植物是藉由毛細現象來對抗重力,但流域的運作完全仰賴重力。植物的根部靠著數百萬根菌根連結,收集必需的養分供植物生長與繁殖。從功能來看,這些菌根就像流域中的數百萬個潮濕地,緩慢地聚集與傳送蘊涵養分的水到溪流與支流,然後匯入幹流、分流,最終注入大海。植物的葉子與果實也像豐饒而肥沃的氾濫平原(無論有沒有被開墾),將整個流域的養分匯聚,支撐起河流生命的豐富性。
*
河流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很多事」。對人類中心論與大加速感興趣的人,河流是醒目的例證,顯示人類試圖控制與馴化自然過程將造成什麼結果。事實上,我們至今仍無法完全理解自然的複雜與多變。十九世紀中葉,喬治‧伯金斯‧馬許(George Perkins Marsh)在他的作品《人與自然》(Man and Nature)中提出了非常有先見之明地提出河流是人類影響自然系統的第一個例證。4各地的氾濫平原是人類早期文明的生產中心。管理氾濫平原、提升灌溉水利、控制洪水與運送貨物(特別是木材),成為治理國家的首要之務。因此,當人類最初努力馴服這個野蠻的自然世界時,他們的焦點就是河流。從羅馬的輸水道,到漢朝的水利專家,再到十七世紀晚期歐洲的運河泡沫,為了政治與經濟利益,人類投入龐大的資源管理河流。因此,如果我們想要了解人類干預複雜自然系統使其符合人類與國家目的的歷史,那麼河流管理的故事,將是用來衡量人類中心論的理想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