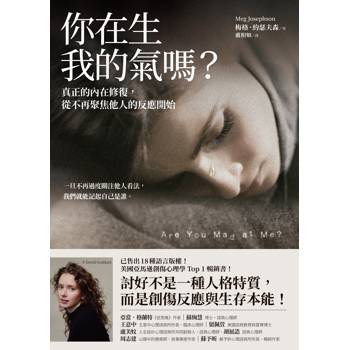〈第1章 創傷反應──什麼是「討好反應」?它如何保護你?〉
▍討好反應
大腦的主要工作是帶給我們安全感,就這麼簡單。這個原始的求生本能自古便已存在,至少有幾十萬年歷史。它專注於人類的基本生存,比如避免受傷、維持溫飽與繁衍後代,並負責在我們感到不安全時進入備戰模式。當大腦感受到威脅時,神經系統會出現四種反應:戰、逃、僵和討好。
本書聚焦的「討好反應」是最少被討論,卻也最常見的創傷反應。「討好反應」是近十年才出現的詞彙,最初是由心理治療師佩特.沃克於二○一三年出版的《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中所提出的。其他三種威脅反應則較為人熟知:「戰」是對威脅採取攻擊,以使其消失(例如大聲斥責或動手毆打);「逃」是指身體離開當前的環境或關係(例如直接逃走或消失不見);「僵」則發生在身體無法離開時退而求其次,透過心理防衛機制脫離正在發生的一切(例如解離、麻木、沉溺於白日夢)。
「討好」是什麼呢?它是指變得對威脅來說更有吸引力、被威脅所喜歡、讓威脅滿意、對威脅表示贊同或提供協助……如此一來,就能讓自己感到安全。在社會中,這種反應往往遭到忽略,因為它經常受到讚賞。我們因討好他人而獲得升遷;我們因忽視自己的需求而得到「無私」的讚美;當我們放棄自己的需求、提前察覺他人的渴望時,往往能獲得肯定。對許多人──尤其是女性來說,討好是我們從小就開始學習,並被整個社會不斷強化的;我們自幼便被灌輸「人生的主要任務就是取悅、安撫他人,並為他人的舒適犧牲自己的需求」。討好,是一種求生工具,是一種讓人即使身在被剝奪了權力的社會中,仍能下意識覺得自己還握有一點掌控權的方式。
這四種反應並不是固定的特質,也不是我們的命運。我們可能會在不同的時機採取其中任何一種或所有反應,一切取決於大腦與身體覺得哪一種最有效。
討好不是有意識的選擇,而是天生的求生機制。
沃克指出,討好反應是在混亂的家庭環境中發展出來的。當一個孩子發現,「戰鬥」只會讓局勢或施虐的緊張關係升高、「僵住」無法帶來真正的安全感,而「逃跑」也並非總是可行時,「討好」便成為另一種求生策略。孩子「學會透過討好,獲得相對安全的協助者角色」。這些壓力反應本身都是有用、具適應性、且在當時是必要的;但這種反應本該只是短暫啟動,持續個幾分鐘或幾小時,而不是連續數年。然而對許多人來說,長期的討好反應已如同呼吸般自然。
在生命大部分的時間裡,我曾以為討好是自己的天性,甚至曾引以為傲,覺得自己就是個隨和、沒有太多偏好或意見的酷女孩。在那些我根本不想參與的社交圈裡,我能像變色龍般調整自己的性格,讓自己變得討人喜歡。
這種變色龍式的酷女孩氣質,曾保護我很長一段時間。我會密切觀察父親的情緒,在對的時候說對的話,或是在不對的時候選擇沉默。當我察覺到父親開始出現失控的行為時,我會用盡一切方法避免他的怒火爆發。老實說,讓他開心,總比處理他不開心造成的後果要來得容易。
也許只要我快樂、完美又乖巧,他也會快樂;也許只要我討人喜歡,他就不會對我生氣。這些都不是出於意識、經過深思熟慮的想法──討好已成為一種潛意識反應。
的確,討好對當時的我確實有保護作用,然而當那段日子過去,我卻發現自己離「自我」十分遙遠,彷彿從未真正遇見那個稱為「我」的人。我看著別人的雙眼,心裡想著:「他們想聽我說什麼?」然後說出他們想聽的話。
▍討好不叫「善意」
當你察覺到自己出現討好反應時,你可以想想:「我什麼時候是在討好,什麼時候只是單純在當個好人?」身為人類,我們天生渴望與他人連結、具有社會性、嚮往和諧與歸屬感。療癒討好反應並不會阻礙這種與生俱來的欲望,反而能讓我們更親近它。如果我們不與自己建立連結,就無法真正與他人建立連結。
在討好他人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放棄自我,才能達到取悅的目的。別人的舒適感比我們自己的更重要,除非他人安好,否則我們無法安心。為了獲得安全感,我們學會不惜一切代價,都要維持和平,卻因此與自我失去連結,不去思考「我需要什麼?我有什麼想法?我想要的是什麼?」等問題。
透過本書,我們將學到「善意」(nice)與「慈悲」(compassionate)之間的真正差異。表現出善意,是因為在乎他人如何看待我們—為了被視為「好人」而去做某件事;慈悲,則是出於真誠地去做一件能讓內心踏實安穩的事。在人際關係中不斷放棄自我,並不是慈悲的展現。善意經常被拿來避免衝突,但如果我們不斷犧牲自己的需求,只為了迎合他人,長此以往,將導致內心的匱乏。
動機很重要。「我為什麼要這麼做?我之所以說『好』,是因為我真心願意,還是害怕對方會因為我說『不』而生氣?我讚美對方,是因為我打從心裡這麼想,還是想讓對方喜歡我?」當我們能在習慣性的行為發生前暫停一下,就有機會看清背後真正的動機。
▍過度警覺
討好反應的關鍵,正是所謂的「過度警覺」。當神經系統處在過度敏感的狀態下,無論是否有實際威脅,都會對潛在危險保持極度警戒。這時,大腦會持續掃描周遭環境,尋找可能的威脅。短暫的過度警覺是正常的反應,比方說,當你正準備入睡時,突然聽見樓下傳來奇怪的聲音,於是你心跳加速、大腦迅速規畫逃生路線。不久後,你發現那個聲音是烘衣機的運轉聲。警戒模式解除。
對於長期處於討好模式的人而言,過度警覺已成每天的常態,令人筋疲力盡,不但將所有事物視為潛在的威脅,而且這種過度警覺還會延伸到對情緒的監控—我們不斷確認他人的情緒狀態,試圖揣測他們的感受,好讓自己能立刻調整應對。當然,這是大腦某個區域自然產生的功能,而且在許多情境中都非常有用。但對那些困在討好反應中的人而言,這種過度警覺就像打開了過強的電源,即使身處安全的環境,身心依然不肯放鬆,進而陷入過度分析、反覆思索,以及擔心焦慮的漩渦: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氣?
▍持續警戒的大腦與身體
接下來說明我們的「新」大腦。這是使我們成為人類,並在演化過程中發展出的區域,它賦予我們許多全新的能力,例如計畫、分析、思考、想像;而在討好反應的情境中,這部分會讓我們不斷反芻、苦苦思索:朋友們明明看過我的IG限時動態,為什麼都沒回我訊息?為了說明人類的大腦有多狡猾複雜,我想引用「慈悲焦點治療」(Compassion-Focused Therapy, CFT)理論創始者──心理學家保羅.吉伯特(Paul Gilbert)所舉的例子來說明。首先登場的,是一隻草原動物:
一隻斑馬正沐浴在陽光下,愉快地咀嚼青草,享受牠美味的午餐。忽然,牠的眼角瞥見了一頭獅子,於是血液開始加速流動,心跳加快,身體立刻進入備戰狀態,準備為生存做出下一步行動。千鈞一髮之際,斑馬做出朝反方向衝刺的決定,時間開始倒數……。
就在此時,獅子竟慢慢轉身離開,被下一個獵物吸引了注意力。斑馬立刻平靜下來,危機解除。牠的神經系統回到正常的穩定狀態,繼續無憂地吃著草。
若能做一隻斑馬,多好。
但對人類而言,生活沒那麼簡單。我們擁有和斑馬一樣的生存本能,但多虧了「新」大腦,我們另外具備了重複播放事件、過度分析,甚至是持續關注的能力。因此,當威脅消失後,斑馬能立刻回到內在的安全感之中,人類卻會在心裡反覆播放剛剛那一幕,在心裡無數次想著:那頭獅子會不會回來?萬一牠打算趁我睡著時偷襲怎麼辦?獅子對我是不是有什麼意見?還是我剛才說錯了什麼?
這意味著我們的身體能停留在過度警覺的狀態,彷彿那頭獅子仍近在眼前。對人類而言,不論威脅是真實發生的、存在於記憶之中,或只是想像出來的,我們都可能進入生存模式。我們明明身處安全狀態,反應卻如同受到威脅時一樣,而這種狀態有可能持續數年、數十年,甚至一輩子。
從這層意義上來說,焦慮就像是一個警報系統。你的身體聰明地學會了留意某些可能觸發警報的信號(例如情緒變化或肢體語言),當它察覺到這些線索時,就會警鈴大作,不論威脅是否存在。即使身處安全狀態,身體仍會做出生理反應,彷彿你正處於危險之中,隨時準備迎接獅子的攻擊。
▍這算是創傷嗎?
伊莎貝爾,四十三歲,坐在我的正對面,伸手拿取另一張面紙,用完後往左手邊放,只見面紙堆得越來越高。這是我們的第五次晤談。她告訴我,從外人看來,她似乎成長在一個充滿支持的家庭裡,擁有一切:父母結縭多年,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還有一隻毛茸茸的狗,吠叫聲比牠的體型大得多。但關起門來,父母總是爭吵不休,空氣中彌漫著緊張的氣氛。伊莎貝爾大部分的童年記憶裡,她都是孤單一人,總是讀著從圖書館借來的奇幻小說,藉此獲得安慰,期盼讀到最後一頁時,父母會和好如初。
她自稱一輩子都是個討好型的人,心中總藏有一股深層的恐懼,總覺得自己有問題。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可怕,但有時候我很希望自己能遭遇一些『大事』,至少這樣能讓我覺得自己的這些感受並非毫無來由。人們會因為我的遭遇而相信我的話,我也會相信自己這樣的反應其來有自。」
當我向她解釋討好反應是四種創傷反應之一,也是許多個案常有的感覺時,伊莎貝爾卻對「創傷」一詞感到困惑:「創傷不是要遭遇某個重大事件才會出現嗎?」
創傷可能是由許多微小的日常瞬間累積而成的,但對身體來說,這些瞬間並非微不足道。 創傷是指神經系統如何感知某個事件或特定時間的經歷,以及身體如何處理它的反應(這就是為什麼即使是手足,即使經歷了同樣的事,其中一人會覺得受創,另一人卻毫無所傷)。
創傷,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所引發的內在反應,是內心深處的傷口在隱隱作痛,例如覺得被拋棄、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對親密關係的恐懼……這些內在傷痛可能來自各式各樣的經驗,不只包括經常在主流媒體中看到的「重大」事件;此外,日常生活中不斷累積的「微小」創傷所帶來的破壞力和痛苦,並不亞於一次性的「重大」創傷。
當那些本該給予我們安全感的人,反倒令我們覺得不安、被忽視、不被愛或視而不見時,這種影響就稱為「複雜性創傷」(complex trauma)。複雜性創傷經常發生在家庭或照顧系統中,因為這些環境理應是讓我們感到安全與穩定的來源。
討好反應通常來自於持續存在複雜性創傷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們感受不到應有的滋養與支持,而這種創傷也會以多種形式出現,包括情緒、言語、身體、性等方面,或是忽視與疏離。複雜性創傷之所以令人難以理解和處理,是因為它們多半來自於長期且重複的經歷,而且一直以來都被視為「正常」,是我們熟悉的一切。
複雜性創傷同時也包括了「未發生的事」,也就是自己在創傷發生的過程中及事後未能獲得的支持與關懷。壓力事件發生後,你是否獲得了所需要的照料?還是被獨自留下,甚至被告知要「自己想辦法撐下去」?身體如何消化壓力事件,會深受事件發生後處理方式的影響,因為創傷的本質更多是關於那道內在的傷口,而不只是事件本身,也因此,療癒永遠是有可能的。我們無法改寫歷史,也無法改變過去的外在境遇,但我們總是能改變自己的內在經驗。
▍有時確實免不了討好
有時我們必須討好,無論是為了確保自身安全,還是為了領到薪水。將討好視為一種生存反應來討論的同時,也必須承認外部世界與體制對我們的影響。畢竟討好反應就是一種潛意識裡讓自己努力符合父權體制、白人主導社會所定義的「好人」典範,不是嗎?
在男性主導的社會中,討好曾是女性賴以生存的必要手段。無論公開或私下,女性必須在家庭、職場、社會等層面取悅與安撫男性。以美國為例,直到一九七四年,女性才終於獲准以自己的名義申請並擁有信用卡,身處在這樣的社會裡,女性倘若不懂察言觀色、追求男性的認可,該如何立足?除了基本生存需求,女性更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被訓練去討好:發脾氣會被說是「瘋子」,提出異議會被認為「難搞」,堅定個人立場就會被貼上「婊子」的標籤。
我也有一些正與身心障礙症狀共處的個案,無論這些障礙對他人來說是否明顯可見,他們都逐漸意識到,「討好」對自己而言是種不得不為的生存策略。為了融入多數,他們或是克制自己的口吃,或是在社交場合掩飾情緒或心理方面的疾病,或是穿著厚重的毛衣遮蓋脊髓損傷的痕跡,甚至為了不讓朋友知道自己有慢性疾病,耗盡精力勉強跟上大家的腳步。
你的種族、族裔、性別、性別認同、性傾向、階級、文化背景、宗教成長經驗和/或身心障礙,都可能使你為了在充滿壓迫的社會體系中生存下來、獲得接納,而產生根本性的討好需求。請試著思考一下,這些多重身分的交織重疊,與你渴望被視為「好人」的需求、害怕惹麻煩的焦慮,以及習以為常的過度警覺之間有何關聯。
請記得:討好反應是一種必須且具有適應性的生存機制。有時,我們的確需要去討好。
這項療癒工作的重點,是以一種現實且可行的方式來修復討好反應—當你不需要的時候,在你感到安全的情況下,學會放下討好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