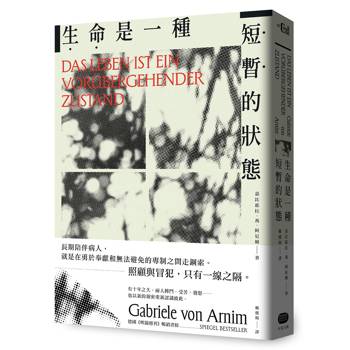第二章 該如何述說(節錄)
「我們述說故事是為了活下去」,瓊.蒂蒂安寫道,那是一九六八年,在她那本《白色專輯》散文集裡。憑著這本書,她奠定了自己在文壇的地位,在美國知識分子的抗議合唱中成為一個獨特的聲音。四十多年後,七十八歲的蒂蒂安為了活下去而述說故事──或許應該說得更正確一點:是為了忍受「活下去」這件事。她在短期之內接連失去了丈夫和女兒,於是她用寫作來對抗遺忘與回憶,對抗死亡與恐懼。她病了,老了,形單影隻。她愈來愈消瘦,愈來愈單薄,愈來愈沒有安全感。留下的只有誠實。毫不留情地揭發由於生命短暫易逝所帶來的打擊。作家安媞耶.拉維克.施圖伯爾多年來把瓊.蒂蒂安的作品譯成德文,曾經稱她為「現實的解剖師」。
我們為了活下去而述說故事。我們需要故事來了解生活。或許我該對妳述說的也是一個故事。
妳說:把它說出來,說出那是怎麼回事,說出那對你們造成了什麼影響,對妳造成了什麼影響。如果我要把「它」說出來,就也得要述說我自己。鄭重地脫下褲子,袒露自己。因為妳想知道一個人在危機時期如何生活,會變成什麼樣的人,會發現自己的哪一面,從何處汲取所需要的力量與耐心,在自己身上有何欠缺,在哪些事情上一敗塗地,在何處變得支離破碎,急需用黏膠把自己重新拼湊起來。哪一種黏膠黏得最牢?
危機就像嗜血的蚊子一樣追趕著我們。我們必須一再逃離死亡。在這種時候還有餘裕來反省、來思考、來改變自己嗎?還是會變得毫無知覺?在有如鯊魚嘴的生活中要如何存活,隨時可能「啪」地合攏的鯊魚嘴。
我該向妳述說這些。
要如何應付如影隨形的恐懼。要如何取得平衡,既在疾病中,同時也留在生活裡。生活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當一個向來只想要獨立自主的狂暴鬥士忽然變得完全無法自主。照顧與冒犯只有一線之隔,關懷在何時會變成專橫,試圖拯救生命在何時會以令對方感到屈辱的侮辱收場。犧牲奉獻在何時會變得殘忍無情。要如何去愛一個男人,去守護他,當他就在她對他說無法再跟他一起生活的那一天倒下。該怎麼做,當那可憎的命運兩度落在同一個人身上。當她也病了,就愈來愈難不去怨天尤人。與其他人的關係起了什麼變化,要如何學會不要感到難過,當一些曾經自稱為朋友的人由於軟弱和對疾病的恐懼而不再出現。在這樣的生活中,現實與個人的感知如何愈離愈遠。
那張照片多麼如詩如畫,妳戴著紅色遮陽帽,穿過草原上長得高高的草,走向妳寫作之處。但我當然會暗忖:那裡有蛇嗎?當妳讀到這幾行字,妳會想:她總是懷疑會有危險。而妳這樣想也沒錯。過去這些年的災厄蟄伏在我心裡,等待著被喚醒,成為黑羽烏鴉拍動翅膀掠過我心頭。妳帽子的紅色就跟妳寫作小屋前面那兩根細長的紅柱一樣,在高高的黃草之間,在乳藍色的炙熱天空下,紅得多麼美。美麗的事物所帶來的安慰。這一點我將一再提起。當我把恰好合適的檯燈擺在家中恰到好處的位置,我心中那種奇妙的快樂低語,然後我就忍不住一再跑過去看,並且感到一絲幸福。他說我在與審美有關的事情上是個獨裁者。最近,我曾想找一支顏色與我身上穿的毛衣一樣的湯匙來吃水煮蛋……不,現在我寧可別對此事發表任何看法。
我一邊寫下這幾行字,一邊看向一束飽滿的鬱金香,有橙色、紅色和白色的花朵。花萼張開了,幾支花莖昂然向上生長,另幾支則慵懶地向下捲曲。這有一種誘人的性感。彷彿這些花朵正朝著未來的幸福伸展身體,其實卻只是逐漸接近終將凋萎的生命盡頭。只是?在感知上,美麗與短暫易逝本來不就是一體的嗎?倘若不是明知其短暫易逝,有生命的美麗事物還會令我們感到欣喜嗎?
最近我們通電話時,妳稍微催促了我,說我該著手了。於是今天我把裝著弔唁信函的木箱拿出來,整理了箱中信件,並且把木箱擱在水龍頭底下刷洗。它不該沾滿灰塵,當我把那些紙條和這些年來寫滿的那許多大大小小的筆記本全都放進去。只有在我書寫時,當我把所經歷的事訴諸文字,才能製造出一種距離,在所發生的事與我之間才能產生空間。當我隔著由文字築起的牆去窺視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就能比較平靜地接受那些事。文字保護了我。裹在由字句、紙頁、句點和驚嘆號織成的大衣裡,我就比較不害怕。隔著一段距離望向所發生的事,消除了事件本身的戲劇性,把現實化為一則故事,我讀著這則故事,在閱讀的當下並未活在其中。
現在我果真把自己手寫的日記整理出來,也把這些年來打字儲存在筆電裡的隨筆列印出來。有好幾百頁。明天我將拿去裝訂。等著瞧吧,看它們將會凝視我多久,等到我終於去讀。威廉.格納齊諾曾經讓他小說中一個陰鬱的主角這麼說:「我因為內心的深不見底而備受煎熬。」
「它」──是去看見所發生的事,也是對所發生的事視而不見;是去理解所發生的事,也是對所發生的事不能理解。我抓住了最微渺的希望,彷彿那是一條繩索,而非一條細線,浪費力氣去無視那顯而易見的事實:如果他活下來,就會是個重殘之人。
「它」──那是我的耐心,以及我的不耐煩。由於吞嚥障礙,他經常得要咳嗽,弄得我神經緊張。從他嘴角流出的口水常使我失去食慾。當他再度能夠稍微自己進食,老是把衣服弄髒,我的反應也很煩躁。當他以為他得要小便,擔心自己說得太遲,而我不得不一再跳起來去拿尿壺,我不耐煩地嘆了口氣。
也就是說,現在我得要正視自己在這些年裡可能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不是我本來可以成為的那個模樣。假如我們曾在任何時候有可能是自己本來可以成為的那個模樣。
假如他還在,此刻就會咧嘴笑著說:有這份心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理查.費納根曾在他的一本小說裡寫道:「過去總是難以預料。」如果臉頰胖嘟嘟的小天使擠進畫面來粉飾過去或掩蓋過去呢?如果騙人的記憶早已把我變成了我想要成為的那個模樣?佛洛伊德把這個過程稱為「屏幕記憶」,當次要的記憶把真正重要的記憶推擠到邊緣,加以掩蓋。而對難堪時刻的抗拒,對折磨人的真相的抗拒,則會導致記憶缺口與記憶錯誤。
於是我坐在這裡,像一件扣子扣歪了的雨衣,等待著自己鼓起勇氣去讀我當時寫下的文字。「該如何談論疾病?」曾有人這麼問,然後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談得太多很可怕,但是根本不談卻更糟。」
要如何敘述一個情況,當一個人在譫妄中,顯然感覺到自己有生命危險,上百次、上千次地一再地說:不要中斷,請不要中斷,不要中斷,不要結束,不要結束,不要結束,請不要結束。
「它」──是持續不斷的恐懼所帶來的痛苦,像一種水狀的溶液傾瀉到全身。有十年之久,這份恐懼與我同桌而坐──或是它的小表親「不安」、「擔心」、「憂慮」與我同坐在沙發上、書桌旁,在爐台前站在我旁邊,和我一起躺在床上。懂得恐懼是件好事,是合情合理的,可是當恐懼控制了我們,我們就完了。假如不懂得恐懼,我們可能早就從教堂的高塔上摔落,被馬路上的車流輾碎,被黑夜吞噬,被愛情毀滅。可是當恐懼耗盡了我們的心力,當我們在驚慌失措的夜裡幾乎想打電話叫救護車或是報警,因為心臟跳得太快,因為腦袋陣陣作痛,使人把嗡嗡耳鳴聽成正一步步逼近的陌生腳步聲,這時恐懼就握有了權力與決定權,能夠恣意折磨我們。
我曾在某處讀到:自由在恐懼終止之處出現。當時我心想:當然,所以右翼分子才會在此地與各處激起眾人的恐懼,好讓民眾任由自己被操控。因此,偉大的抗議文化理論家吉恩.夏普才會說:要使一個社會朝著自由的方向改變,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要提倡希望而非散播恐懼。然而,恐懼在我渺小的日常生活中扎了根,使我不再自由。恐懼乃是摧毀生活勇氣的特務。「一旦你開始感到恐懼,就再也停不下來了」,這是最近報紙上引用一位北韓異議人士所說的話。我無法停止感到恐懼。那些年裡都沒辦法。當我轉進我住的那條街,看見一輛救護車閃著紅光,我就會想像他在救護車上。一切尚未發生的事都隨時可能發生。也許讓恐懼之火熊熊燃燒的就是這種種可能性。恐懼是籠統的,害怕是具體的。恩斯特.布洛赫在他那本《希望的原理》中寫道:「地面在搖晃,他們不知道是為什麼,不知道原因何在。他們的這種狀態就是恐懼。如果這種狀態更加確定,就成了害怕。」有時恐懼與害怕合而為一,害怕擴大成為恐懼。而害怕的人就也會感到恐懼。
在加護病房,當醫生問他是否寧可別人不要管他,他好幾次用力點頭。比起中風、心肌炎、肺炎,他的拒絕幾乎更讓醫生擔心。
我在他床邊低語:你要是死了,我會殺了你。
他的摯友在電話裡說:下一次我來,我們就在地毯上躺個半小時,我會緊緊抱著你,我們只要躺在地毯上半小時就好。
「我們述說故事是為了活下去」,瓊.蒂蒂安寫道,那是一九六八年,在她那本《白色專輯》散文集裡。憑著這本書,她奠定了自己在文壇的地位,在美國知識分子的抗議合唱中成為一個獨特的聲音。四十多年後,七十八歲的蒂蒂安為了活下去而述說故事──或許應該說得更正確一點:是為了忍受「活下去」這件事。她在短期之內接連失去了丈夫和女兒,於是她用寫作來對抗遺忘與回憶,對抗死亡與恐懼。她病了,老了,形單影隻。她愈來愈消瘦,愈來愈單薄,愈來愈沒有安全感。留下的只有誠實。毫不留情地揭發由於生命短暫易逝所帶來的打擊。作家安媞耶.拉維克.施圖伯爾多年來把瓊.蒂蒂安的作品譯成德文,曾經稱她為「現實的解剖師」。
我們為了活下去而述說故事。我們需要故事來了解生活。或許我該對妳述說的也是一個故事。
妳說:把它說出來,說出那是怎麼回事,說出那對你們造成了什麼影響,對妳造成了什麼影響。如果我要把「它」說出來,就也得要述說我自己。鄭重地脫下褲子,袒露自己。因為妳想知道一個人在危機時期如何生活,會變成什麼樣的人,會發現自己的哪一面,從何處汲取所需要的力量與耐心,在自己身上有何欠缺,在哪些事情上一敗塗地,在何處變得支離破碎,急需用黏膠把自己重新拼湊起來。哪一種黏膠黏得最牢?
危機就像嗜血的蚊子一樣追趕著我們。我們必須一再逃離死亡。在這種時候還有餘裕來反省、來思考、來改變自己嗎?還是會變得毫無知覺?在有如鯊魚嘴的生活中要如何存活,隨時可能「啪」地合攏的鯊魚嘴。
我該向妳述說這些。
要如何應付如影隨形的恐懼。要如何取得平衡,既在疾病中,同時也留在生活裡。生活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當一個向來只想要獨立自主的狂暴鬥士忽然變得完全無法自主。照顧與冒犯只有一線之隔,關懷在何時會變成專橫,試圖拯救生命在何時會以令對方感到屈辱的侮辱收場。犧牲奉獻在何時會變得殘忍無情。要如何去愛一個男人,去守護他,當他就在她對他說無法再跟他一起生活的那一天倒下。該怎麼做,當那可憎的命運兩度落在同一個人身上。當她也病了,就愈來愈難不去怨天尤人。與其他人的關係起了什麼變化,要如何學會不要感到難過,當一些曾經自稱為朋友的人由於軟弱和對疾病的恐懼而不再出現。在這樣的生活中,現實與個人的感知如何愈離愈遠。
那張照片多麼如詩如畫,妳戴著紅色遮陽帽,穿過草原上長得高高的草,走向妳寫作之處。但我當然會暗忖:那裡有蛇嗎?當妳讀到這幾行字,妳會想:她總是懷疑會有危險。而妳這樣想也沒錯。過去這些年的災厄蟄伏在我心裡,等待著被喚醒,成為黑羽烏鴉拍動翅膀掠過我心頭。妳帽子的紅色就跟妳寫作小屋前面那兩根細長的紅柱一樣,在高高的黃草之間,在乳藍色的炙熱天空下,紅得多麼美。美麗的事物所帶來的安慰。這一點我將一再提起。當我把恰好合適的檯燈擺在家中恰到好處的位置,我心中那種奇妙的快樂低語,然後我就忍不住一再跑過去看,並且感到一絲幸福。他說我在與審美有關的事情上是個獨裁者。最近,我曾想找一支顏色與我身上穿的毛衣一樣的湯匙來吃水煮蛋……不,現在我寧可別對此事發表任何看法。
我一邊寫下這幾行字,一邊看向一束飽滿的鬱金香,有橙色、紅色和白色的花朵。花萼張開了,幾支花莖昂然向上生長,另幾支則慵懶地向下捲曲。這有一種誘人的性感。彷彿這些花朵正朝著未來的幸福伸展身體,其實卻只是逐漸接近終將凋萎的生命盡頭。只是?在感知上,美麗與短暫易逝本來不就是一體的嗎?倘若不是明知其短暫易逝,有生命的美麗事物還會令我們感到欣喜嗎?
最近我們通電話時,妳稍微催促了我,說我該著手了。於是今天我把裝著弔唁信函的木箱拿出來,整理了箱中信件,並且把木箱擱在水龍頭底下刷洗。它不該沾滿灰塵,當我把那些紙條和這些年來寫滿的那許多大大小小的筆記本全都放進去。只有在我書寫時,當我把所經歷的事訴諸文字,才能製造出一種距離,在所發生的事與我之間才能產生空間。當我隔著由文字築起的牆去窺視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就能比較平靜地接受那些事。文字保護了我。裹在由字句、紙頁、句點和驚嘆號織成的大衣裡,我就比較不害怕。隔著一段距離望向所發生的事,消除了事件本身的戲劇性,把現實化為一則故事,我讀著這則故事,在閱讀的當下並未活在其中。
現在我果真把自己手寫的日記整理出來,也把這些年來打字儲存在筆電裡的隨筆列印出來。有好幾百頁。明天我將拿去裝訂。等著瞧吧,看它們將會凝視我多久,等到我終於去讀。威廉.格納齊諾曾經讓他小說中一個陰鬱的主角這麼說:「我因為內心的深不見底而備受煎熬。」
「它」──是去看見所發生的事,也是對所發生的事視而不見;是去理解所發生的事,也是對所發生的事不能理解。我抓住了最微渺的希望,彷彿那是一條繩索,而非一條細線,浪費力氣去無視那顯而易見的事實:如果他活下來,就會是個重殘之人。
「它」──那是我的耐心,以及我的不耐煩。由於吞嚥障礙,他經常得要咳嗽,弄得我神經緊張。從他嘴角流出的口水常使我失去食慾。當他再度能夠稍微自己進食,老是把衣服弄髒,我的反應也很煩躁。當他以為他得要小便,擔心自己說得太遲,而我不得不一再跳起來去拿尿壺,我不耐煩地嘆了口氣。
也就是說,現在我得要正視自己在這些年裡可能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不是我本來可以成為的那個模樣。假如我們曾在任何時候有可能是自己本來可以成為的那個模樣。
假如他還在,此刻就會咧嘴笑著說:有這份心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理查.費納根曾在他的一本小說裡寫道:「過去總是難以預料。」如果臉頰胖嘟嘟的小天使擠進畫面來粉飾過去或掩蓋過去呢?如果騙人的記憶早已把我變成了我想要成為的那個模樣?佛洛伊德把這個過程稱為「屏幕記憶」,當次要的記憶把真正重要的記憶推擠到邊緣,加以掩蓋。而對難堪時刻的抗拒,對折磨人的真相的抗拒,則會導致記憶缺口與記憶錯誤。
於是我坐在這裡,像一件扣子扣歪了的雨衣,等待著自己鼓起勇氣去讀我當時寫下的文字。「該如何談論疾病?」曾有人這麼問,然後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談得太多很可怕,但是根本不談卻更糟。」
要如何敘述一個情況,當一個人在譫妄中,顯然感覺到自己有生命危險,上百次、上千次地一再地說:不要中斷,請不要中斷,不要中斷,不要結束,不要結束,不要結束,請不要結束。
「它」──是持續不斷的恐懼所帶來的痛苦,像一種水狀的溶液傾瀉到全身。有十年之久,這份恐懼與我同桌而坐──或是它的小表親「不安」、「擔心」、「憂慮」與我同坐在沙發上、書桌旁,在爐台前站在我旁邊,和我一起躺在床上。懂得恐懼是件好事,是合情合理的,可是當恐懼控制了我們,我們就完了。假如不懂得恐懼,我們可能早就從教堂的高塔上摔落,被馬路上的車流輾碎,被黑夜吞噬,被愛情毀滅。可是當恐懼耗盡了我們的心力,當我們在驚慌失措的夜裡幾乎想打電話叫救護車或是報警,因為心臟跳得太快,因為腦袋陣陣作痛,使人把嗡嗡耳鳴聽成正一步步逼近的陌生腳步聲,這時恐懼就握有了權力與決定權,能夠恣意折磨我們。
我曾在某處讀到:自由在恐懼終止之處出現。當時我心想:當然,所以右翼分子才會在此地與各處激起眾人的恐懼,好讓民眾任由自己被操控。因此,偉大的抗議文化理論家吉恩.夏普才會說:要使一個社會朝著自由的方向改變,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要提倡希望而非散播恐懼。然而,恐懼在我渺小的日常生活中扎了根,使我不再自由。恐懼乃是摧毀生活勇氣的特務。「一旦你開始感到恐懼,就再也停不下來了」,這是最近報紙上引用一位北韓異議人士所說的話。我無法停止感到恐懼。那些年裡都沒辦法。當我轉進我住的那條街,看見一輛救護車閃著紅光,我就會想像他在救護車上。一切尚未發生的事都隨時可能發生。也許讓恐懼之火熊熊燃燒的就是這種種可能性。恐懼是籠統的,害怕是具體的。恩斯特.布洛赫在他那本《希望的原理》中寫道:「地面在搖晃,他們不知道是為什麼,不知道原因何在。他們的這種狀態就是恐懼。如果這種狀態更加確定,就成了害怕。」有時恐懼與害怕合而為一,害怕擴大成為恐懼。而害怕的人就也會感到恐懼。
在加護病房,當醫生問他是否寧可別人不要管他,他好幾次用力點頭。比起中風、心肌炎、肺炎,他的拒絕幾乎更讓醫生擔心。
我在他床邊低語:你要是死了,我會殺了你。
他的摯友在電話裡說:下一次我來,我們就在地毯上躺個半小時,我會緊緊抱著你,我們只要躺在地毯上半小時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