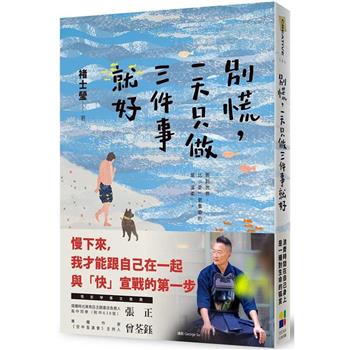〈塞席爾群島的一日三事〉
焦慮不是來自於想到未來,而是來自於想要控制未來。
魚比人還多的國度,潛水者的天堂
期待了好幾年,我終於去了塞席爾(Seychelles)群島,一個魚比人還要多的國家。
塞席爾是個位於非洲東南、馬達加斯加島北方一千多公里處的西印度洋島嶼國家,人口不到十萬人,要不是因為到了這裡,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遇見一位真正的塞席爾人。
塞席爾人顯然知道自己是「稀有動物」,也以自己的國家為榮,到處都看得到獨特的國旗,他們確實也有充足的理由覺得光榮,因為這個在大海當中靠海為生的小國,竟然可以成為全非洲人均所得GDP最高、也最安全的國家。這面由五種鮮豔的顏色呈放射狀排列的國旗,由象徵海洋的藍色、象徵太陽的黃色、象徵人民及人們在愛與團結中奮鬥的心的紅色、象徵社會正義與和諧的白色、象徵土地與自然的綠色共同組成的旗幟,在島上的半個月,這面原本我從來沒見過的旗幟,突然變得像老朋友那樣熟悉。
我之所以會千里迢迢到這個東非外海默默無聞的小島,其實是因為久聞這裡是個潛水者的天堂,而我喜歡潛水,所以抱著朝聖的心情而來。不用說,作為一個熱愛海洋的潛水員,既然來了這個被稱作世界十大知名潛水點之一的地區,每天最重要的事情,當然就是潛水。
至於朋友抱著羨慕的目光,強調這是歐洲貴族鍾愛的度假勝地,英國威廉王子跟凱特王妃的蜜月島、比爾‧蓋茲的私人別墅什麼的,對我來說就像餵豬吃珍珠一樣。
我來塞席爾就是要潛水!
我住宿的地點在馬埃(Mahé)島人煙稀少的西南部,一個叫做「芒果之家」的旅館,是一棟義大利建築師的老宅改建的,連桌子都是芒果形狀。
首都城市維多利亞(Victoria)在島嶼東北方,而芒果之家在安靜的島嶼之南,這裡晚上沒有路燈,入夜後就只有滿天星斗和夜行性野生動物活動的聲音。每天早上陽光在海平面升起,有時細雨濛濛。頭幾天我都在島的南方海域潛水,但是季風一起,風向便改變,南方風浪變大。
「這風要多久才會停呢?」
「要五個月吧!」酷似巴布‧馬利(Bob Marley)的潛水嚮導聳聳肩。
「什麼!」忽然,潛水季節就結束了。
最期待的潛水時刻
還好,島的北方因為地形的關係,一年到頭都可以潛水,唯一的問題是芒果之家距離潛水中心地點,有相當的距離,必須要繞大半個島,開陡峭的山路經過國家公園才能抵達。而且大多數的路段都只容一台車經過,在山路會車的時候需要相當好的開車技術,還有彼此謙讓等待的耐心,光是開車到集合地點的時間,就要一個小時以上。這也是為什麼我每天早上必須設定鬧鐘在六點的原因,我會坐在陽台面對著海洋,一面喝著來自當地有芒果香味的黑咖啡,慢慢醒來,一面看著夕陽從山的背後冉冉升起,喝完咖啡後,清點準備所有的潛水裝備,吃一點早餐後出發,開蜿蜒的山路到島的另一頭,正好可以趕上八點半的集合時間。有時候抵達的時間已經將近九點鐘,負責潛水中心的荷蘭女士也不介意,因為她知道我一定會在潛水船出發之前抵達,而且我裝備齊全,不需要她操心。
就像很多島嶼的潛水慣例,每天早上出發的潛水船,會先移動比較長的距離,到比較遠、挑戰度也比較高的潛水地點,進行第一潛。潛水員都完成潛水回到船上以後,中間為了安全因素,至少間隔一個小時,才能進行第二潛,會趁這個空檔,移動到難度比較低,或是水域比較淺、也比較靠近岸上基地的潛水點。船長會拿出保溫瓶,他的妻子事先準備好的熱紅茶讓大家喝著取暖,那是我第一次喝到塞席爾島上茶園栽種的紅茶,是跟香草莢一起烘焙的,泡茶的時候加了很多島嶼自己種植的蔗糖。那味道讓我聯想到小時候在南台灣的高雄,時常跟大麥、決明子、糖粉一起炒製的紅茶,極為相似;加上塞席爾的植被生態,跟南台灣海濱非常相像,有種回到了童年的錯覺,也成了兩次潛水之間最讓我期待的片刻。
是什麼環節讓我焦慮?
跟世界上大多有名的潛水點不同,塞席爾的海底不是由珊瑚礁組成,而是巨大的花崗岩地形,對潛水來說是個相當獨特的經驗。運氣好的時候,水中的可見度高達水下三十米,水溫也差不多維持在攝氏二十九度左右。所以到達水深四十米的Aldebaran看見沉沒在海底的日本漁船,和跟我身體一般大的蝙蝠鯧,一起緩緩下潛到繞著沉船桅杆、數以萬計的黃色四線笛鯛之間,我被密密麻麻包圍著,到了甚至看不見身邊搭檔的程度,還有成群的巨大燕魟像大雁般遨遊,讓我一整個大感動。但是下一個小時,天候卻瞬息萬變,風浪變得很大,海流強烈,能見度也只剩下不到眼前兩米。即便如此,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這就是自然,而面對自然的時候,我總是用同樣的原則面對,那就是抱持著「敬畏」和「接受」的態度,而不是自大地試圖去「征服」自然。
通常兩只氣瓶的潛水,會在下午一點半左右結束,回到岸上。
即使我人在旅行的時候,每天仍然都有一場到兩場由我帶領的線上哲學工作坊。這幾年來,由於工作型態的改變,大多數的工作都可以透過網路進行。無論我人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都要預先計算好時差,也要確認網路的順暢,才能順利進行日常的工作。
由於位在東非外海的塞席爾群島,和北京、台北都有著四個小時的時差,對我的工作時間來說,這簡直是太完美的安排了。這意味著每週三天晚上七點開始的哲學工作坊,是塞席爾的下午三點鐘、而每週四天晚上八點開始的工作坊,則是塞席爾時間下午四點。原本在馬埃島南方潛水的我,上岸後剛好有足夠的時間清洗我的潛水裝備,把身上的鹽分沖掉,還可以在沿路山坡頂一家叫做「三朵玫瑰花」(3 Roses)的胖卡餐車小店稍停留,我會選擇米飯或薯條,搭配兩個菜,其中一樣通常是塞席爾傳統的章魚咖哩或螃蟹咖哩,另外一樣可能是風乾的紅鯛魚,也可能是鹽烤的鱸魚。對於喜歡吃海鮮的我來說,塞席爾的路邊料理是很完美的,反正島上除了雞之外,沒有飼養動物,所以基本上不大會吃到肉類。另外,我希望每天的日常生活能夠盡量環保,每天會隨身帶著自己準備的飯盒,請老闆裝在我的飯盒裡,米飯的分量也會按照我的食量斟酌減半,確保不會造成食物的浪費。另外一個飯盒則會裝甜點,有時候是焦糖布丁,有時候是裡面抹了果醬的甜甜圈,完全看當天老闆做了什麼。這是一個沒有菜單,也沒有任何造作的純樸島國,我覺得這樣很好。
但自從必須到馬埃島的東北角才能潛水,每次上岸後,就意味著必須多花一個多小時才能回到島上西南角的旅館。
經過了兩三天之後,我發現下午四點的線上課還好,但是如果當天有下午三點開始的線上課,會讓我上午的潛水變得焦慮。
因為開車至少要一小時的時間,所以每到下午一點半,如果潛水船還沒有靠岸的時候,我就會開始緊張,擔心時間不夠。
即使一點半前準時靠岸,一面在清洗潛水用具的時候,也會忍不住開始產生焦慮。因為我又想仔細地清洗乾淨,確認裝備沒有殘留沙粒或是鹽分,又想趕快上路離開,以免在路上被接送孩子放學的家長堵在狹窄的山路上。
洗完潛水裝備上路,我並沒有覺得放鬆,反而開始新的憂慮。因為我擔心會不會在半路上,突然像前兩天那樣遇到前方車子引擎突然自燃的交通事故,造成唯一的聯通道路封閉,或是其他的意外。
雖然潛水上岸之後,肚子餓得嘰哩咕嚕叫,但我擔心萬一停下來買飯盒,會不會耽誤了路程?買了飯盒,會不會沒有時間吃?回到住宿的地方,停車場在山坡底下,我還要步行走回山坡最頂上的住處,會不會因此趕不及?
萬一回到房間,才發現無線網路突然不通的話,是不是有足夠的時間,立刻改用手機漫遊上網應變?
調整好做下一件事的狀態
每一堂哲學工作坊,通常我都會布置課前作業,讓參加者在上課之前,先針對主題思考,從每一個人的課前作業中,我就可以了解參加者的思考狀態。可是如果只能勉強趕在上課前五分鐘慌亂衝回書房,意味著我根本沒有時間閱讀參加者的課前作業,沒有辦法充分掌握每一個參與者獨特的思路。
這種種的焦慮,與我潛水時在深水之下專注呼吸的狀態,有著天壤之別。我並不喜歡自己那種慌亂、憂慮的狀態,覺察到這點之後,我做了一個決定:如果當天下午的線上課是塞席爾時間三點開始的,那天就不潛水,如果是四點開始的話,才可以潛水。
「差一個小時,有差這麼多嗎?」或許有人會這麼說。
我知道應該是可以趕在最後一刻準時上線的,而且如果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辦法準時上線的話,也有三位常態配置的助教可以協助我先進行一開始的討論。雖然如此,我仍然寧可在一個小時之前,調整好做下一件事的最佳狀態。意思就是,在開始正式工作的一個小時之前,我可以喝咖啡、散個步,或是做點別的事情。但不能是會將我帶離那個最適狀態的事。比如回覆郵件、上網看無關的新聞或視頻,或是整理文件,就會形成太大的干擾,開車在隨時可能出現狀況的陌生國度山路上趕路,就更不用說了。但在陽台上喝咖啡或洗洗碗盤這種事卻不會造成干擾,因為我的思考狀態不會被這些彷彿禪修般重複性高的小動作影響。
就這樣,我在塞席爾群島的旅行,出現了新的規律。
一個禮拜四天潛水,因為這四天都是下午四點鐘開始線上工作,我會在下午三點前悠閒地結束午餐,回到房間,有足夠的時間備課。就像我在哲學思考的教師培訓課上,常常提醒老師的,我也用同樣的話來提醒自己:「作為老師,最好的備課,就是準備好自己。」
至於另外三天,因為下午三點鐘要開始工作,我可以允許自己不設定鬧鐘,奢侈地睡到自然醒,奢侈地慢慢喝咖啡,慢慢吃早餐,然後找一條登山步道、一個沒有去過的海灘,或是什麼都不做,在住處的沙灘上,躺在吊床看書。但無論如何,都會在下午兩點以前回到房間,給自己在工作以前有完整一個小時的時間,沉靜下來,調整自己到最合適的狀態。所以從上線登入的那一分鐘開始,我就是準備好的狀態。
「那不是很可惜嗎?」或許有人會說。
(節錄)
〈第三件重要的事:成為一個同伴〉
「同伴」是一種職人的哲學,跟一個同伴一起工作和學習,永遠會是一種樂趣。
最大的讚美:成為真誠的「同伴」
無論在NGO的領域、寫作的領域,還是哲學諮商的領域,我希望跟我在一起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跟我的「同伴」關係。
因此只要有人在各種培力的課程、評審會議或工作坊上尊稱我為「老師」,過去的我可能會因此感到被重視的虛榮,偷偷高興一下,但是現在的我卻一點都高興不起來,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如果是在哲學思考工作坊上,我甚至會特別停下來強調,在邏輯思考裡,我們沒有「師生」的關係,我們都是思考的「夥伴」。
對我來說,那才是最大的讚美。
我清楚感受到這種關係的轉換,為我和世界建立起一個安全和信任的環境。我慢慢地學會如何在同行的路上,與和我一起的人,成為真誠的「同伴」。
「同伴」的概念,是從哪裡來的呢?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在收音機上聽到美國手工烘焙大師丹尼爾‧立德(Daniel Leader)在接受採訪時,說了一段對他人生重要的往事。
四十多年前,他還是一個很年輕、但被認為有天賦,也已經頗有經驗的麵包師,法語說得不錯的他到了烘焙的聖地法國去拜師學藝。他遇到一個麵包師傅,跟其他師傅教他的時候很不一樣,這個師傅不但很有耐心,而且可以透過手指的觸碰,評估麵粉的狀態,很有自信地對食譜進行微小調整,達到心目中想要的結果。
比如給麵團加水的時後,他不會拿量杯,也不會按照食譜,而是一滴一滴地慢慢加,不斷觀察、評估和計算,尋找麵團的微妙變化,直到完美地融合為止。
丹尼爾說,光是看著師傅如何決定兩種麵粉的混合比例,以及揉麵團的過程,就像一個震撼人心的大師講堂。整個指導的過程有如行雲流水,不著痕跡,他的動作很快、溫柔,卻毫不費力。
他小心翼翼地處理麵團,不去損壞麵包內部的結構,創造出形狀完美的麵包。即使像丹尼爾這樣有經驗的麵包師,也因此能夠用新鮮的眼光,來重新看待烘焙這門手藝。
有一次,丹尼爾為了把一桶發酵中的麵團倒在麵包檯,按照他在美國的習慣,用手用力敲打著桶子邊緣,讓麵團跟桶子分開,重重掉到麵包檯上。
師傅看了一眼,在不批評丹尼爾的習慣下,只是淡淡地說他有一個更好的方式,接著拿出一把抹刀,輕輕地、溫柔地用抹刀鬆開容器兩側的麵團,讓麵團完美無聲地滑到正方形的麵包檯上。
在將麵團放回容器之前,師傅又輕輕拍打麵團,彷彿在鼓勵它。
把你學會的技術交給「同伴」
在這些細微的動作中,丹尼爾說他看到極大的尊重和良好的能量轉移—雖然丹尼爾在訪談當中,並沒有明說是在他和師傅之間,還是師傅和麵團之間,但我猜測是兩者兼具。
在學習結束以後,丹尼爾忍不住問這位師傅,為什麼他跟其他麵包師相比,令人感受到一種說不出的與眾不同?
這位麵包師傅慎重地說:「因為我是Compagnons du Devoir et du Tour de France的成員。」
這是丹尼爾第一次聽說這個起源於中世紀行會的法國工匠組織,而這個師傅原來是Minoterie Suire這個古老家族麵粉廠的創新和研究總監,法國烘焙界的大師法布里斯‧庫里(Fabrice Cuéry)。
作為一名已經訓練有素的烘焙師,法布里斯當年為了要成為一名這個組織認證的Compagnon(同伴),除了必須參加烘焙術科考試,更重要的是參加像是人格測驗的評估考試,看他有沒有成為一個好師傅的性格和潛力。
一旦通過嚴格的考驗被選上之後,會得到腰帶和儀式手杖,正式成為「有抱負的人」(aspirant),標誌著未來的旅程。接下來,就要進行五年的學徒(stagiaire)修業期。
每一年,學徒會被分派到一個法國境內不同的地點,跟著一位烘焙大師,接受一年的指導。他在南方的普羅旺斯學會了烤福加斯(Fougasse Aux Herbes De Provence)這種特別的香草麵包後,又到東北的亞爾薩斯去學了咕咕霍夫(kougelhopf)麵包,這種用裸麥、黑麥、小胚芽麥所做成的麵粉,將麵包做成圓邊帽的形狀,然後加入啤酒酵母,是專門用來搭配生蠔、鵝肝的重口味麵包。
這個古老的法國工匠組織想要做的,遠遠不只是讓年輕麵包師,到處去學習製作不同麵包的技術,更重要的是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要把之前學會的技術,立刻交給新的同伴。也就是說,他從普羅旺斯到了亞爾薩斯,不只要學習亞爾薩斯的麵包技術,也要把在普羅旺斯學習的麵包技術,毫不藏私地帶給亞爾薩斯的麵包師們。這是一種道德承諾,不僅要傳遞他的烘焙訣竅,還要傳遞他作為一個好匠人、甚至一個好人的生活方式。
我想要成為這樣的人
「compagnon」(同伴)這個詞,來自於古法語「compaignon」,意思就是「一個與人一起吃麵包的人」,他被帶入社群,與其他學徒一起住在同一間房子裡。成為一名同伴,意味著必須學習與跟自己背景很不同的人一起同行,並且幫助對方以他們自己選擇的方式蓬勃發展。
實際上,這個環法的古老行會,在中世紀時期建造了法國的教堂和城堡,並受到國王和天主教會的迫害,因為他們拒絕在任何一個機構的規則下生活,而開始了自己的制度。
除了麵包師、甜點烘焙師之外,養成的專業還包括編輯、石匠、木匠、屋頂工、水暖工、鎖匠、金屬匠、木工雕刻家、泥水匠、畫家、裝潢師傅、櫥櫃製造商、園丁景觀設計師、製桶師傅、車身修理工、鍋爐製造工、機械師、電工、精密機械師、鐵匠、馬蹄鐵匠、皮匠、鞍具製造工、鞋匠、釀酒師等,而養成的方式都是一樣的:這些原本就已經有法國政府頒發的 Certificat d’aptitude professionhelle(專業資質證書)證照的工匠,在持續多年的工作和旅行中學習。在法國有八十多個這行會的據點,規模大小不等,有小到只能容納五個人的小房子,也有大到可容納一百多人住在一起的大房子。學徒學習的不只是技術,還包括這個行業的經營,以及高尚的職人道德。這是一個傳統師徒制的指導網絡,透過這樣的身教可以學習一門手藝,同時透過體驗社區生活和旅行來培養性格。完成修學的旅程後,「有抱負的人」必須提交一件結業作品(稱為「傑作」,travail de réception 或 chef-d’œuvre)給行會接受評鑑,如果被接受,才可以正式成為一名「同伴」,獲得一個同伴的專屬名字,並獲得一根能達到心臟高度的新手杖。這還沒有結束,接下來這個剛得到「同伴」認證的職人,必須繼續巡迴三年後,選擇在一個地方穩定地生活和工作,成為compagnon sédentaire(久坐不動的同伴),開始教導自己的學徒。
當來自美國的丹尼爾遇見他的師傅法布里斯時,法布里斯已經選擇大西洋羅亞爾省一個小城市布賽(Boussay)的Minoterie Suire百年麵粉廠作為他的基地,並且二十年來在那裡傳遞給他的「同伴」各種技能和準則;當了數百名麵包師的「同伴」,建立的不是以自己為名的品牌,分享的也不只是他對麵包烘焙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他對烘焙的熱情,以及傳達對職人的期許。
丹尼爾說的這個故事,讓我深受啟發。
「這就是我想要成為的人啊!」當時年輕的我跟自己這麼說,雖然我一點都不知道未來的我具體想要做什麼。但在那一刻,我意識到這正是我想要成為的人。
(節錄)
焦慮不是來自於想到未來,而是來自於想要控制未來。
魚比人還多的國度,潛水者的天堂
期待了好幾年,我終於去了塞席爾(Seychelles)群島,一個魚比人還要多的國家。
塞席爾是個位於非洲東南、馬達加斯加島北方一千多公里處的西印度洋島嶼國家,人口不到十萬人,要不是因為到了這裡,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遇見一位真正的塞席爾人。
塞席爾人顯然知道自己是「稀有動物」,也以自己的國家為榮,到處都看得到獨特的國旗,他們確實也有充足的理由覺得光榮,因為這個在大海當中靠海為生的小國,竟然可以成為全非洲人均所得GDP最高、也最安全的國家。這面由五種鮮豔的顏色呈放射狀排列的國旗,由象徵海洋的藍色、象徵太陽的黃色、象徵人民及人們在愛與團結中奮鬥的心的紅色、象徵社會正義與和諧的白色、象徵土地與自然的綠色共同組成的旗幟,在島上的半個月,這面原本我從來沒見過的旗幟,突然變得像老朋友那樣熟悉。
我之所以會千里迢迢到這個東非外海默默無聞的小島,其實是因為久聞這裡是個潛水者的天堂,而我喜歡潛水,所以抱著朝聖的心情而來。不用說,作為一個熱愛海洋的潛水員,既然來了這個被稱作世界十大知名潛水點之一的地區,每天最重要的事情,當然就是潛水。
至於朋友抱著羨慕的目光,強調這是歐洲貴族鍾愛的度假勝地,英國威廉王子跟凱特王妃的蜜月島、比爾‧蓋茲的私人別墅什麼的,對我來說就像餵豬吃珍珠一樣。
我來塞席爾就是要潛水!
我住宿的地點在馬埃(Mahé)島人煙稀少的西南部,一個叫做「芒果之家」的旅館,是一棟義大利建築師的老宅改建的,連桌子都是芒果形狀。
首都城市維多利亞(Victoria)在島嶼東北方,而芒果之家在安靜的島嶼之南,這裡晚上沒有路燈,入夜後就只有滿天星斗和夜行性野生動物活動的聲音。每天早上陽光在海平面升起,有時細雨濛濛。頭幾天我都在島的南方海域潛水,但是季風一起,風向便改變,南方風浪變大。
「這風要多久才會停呢?」
「要五個月吧!」酷似巴布‧馬利(Bob Marley)的潛水嚮導聳聳肩。
「什麼!」忽然,潛水季節就結束了。
最期待的潛水時刻
還好,島的北方因為地形的關係,一年到頭都可以潛水,唯一的問題是芒果之家距離潛水中心地點,有相當的距離,必須要繞大半個島,開陡峭的山路經過國家公園才能抵達。而且大多數的路段都只容一台車經過,在山路會車的時候需要相當好的開車技術,還有彼此謙讓等待的耐心,光是開車到集合地點的時間,就要一個小時以上。這也是為什麼我每天早上必須設定鬧鐘在六點的原因,我會坐在陽台面對著海洋,一面喝著來自當地有芒果香味的黑咖啡,慢慢醒來,一面看著夕陽從山的背後冉冉升起,喝完咖啡後,清點準備所有的潛水裝備,吃一點早餐後出發,開蜿蜒的山路到島的另一頭,正好可以趕上八點半的集合時間。有時候抵達的時間已經將近九點鐘,負責潛水中心的荷蘭女士也不介意,因為她知道我一定會在潛水船出發之前抵達,而且我裝備齊全,不需要她操心。
就像很多島嶼的潛水慣例,每天早上出發的潛水船,會先移動比較長的距離,到比較遠、挑戰度也比較高的潛水地點,進行第一潛。潛水員都完成潛水回到船上以後,中間為了安全因素,至少間隔一個小時,才能進行第二潛,會趁這個空檔,移動到難度比較低,或是水域比較淺、也比較靠近岸上基地的潛水點。船長會拿出保溫瓶,他的妻子事先準備好的熱紅茶讓大家喝著取暖,那是我第一次喝到塞席爾島上茶園栽種的紅茶,是跟香草莢一起烘焙的,泡茶的時候加了很多島嶼自己種植的蔗糖。那味道讓我聯想到小時候在南台灣的高雄,時常跟大麥、決明子、糖粉一起炒製的紅茶,極為相似;加上塞席爾的植被生態,跟南台灣海濱非常相像,有種回到了童年的錯覺,也成了兩次潛水之間最讓我期待的片刻。
是什麼環節讓我焦慮?
跟世界上大多有名的潛水點不同,塞席爾的海底不是由珊瑚礁組成,而是巨大的花崗岩地形,對潛水來說是個相當獨特的經驗。運氣好的時候,水中的可見度高達水下三十米,水溫也差不多維持在攝氏二十九度左右。所以到達水深四十米的Aldebaran看見沉沒在海底的日本漁船,和跟我身體一般大的蝙蝠鯧,一起緩緩下潛到繞著沉船桅杆、數以萬計的黃色四線笛鯛之間,我被密密麻麻包圍著,到了甚至看不見身邊搭檔的程度,還有成群的巨大燕魟像大雁般遨遊,讓我一整個大感動。但是下一個小時,天候卻瞬息萬變,風浪變得很大,海流強烈,能見度也只剩下不到眼前兩米。即便如此,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這就是自然,而面對自然的時候,我總是用同樣的原則面對,那就是抱持著「敬畏」和「接受」的態度,而不是自大地試圖去「征服」自然。
通常兩只氣瓶的潛水,會在下午一點半左右結束,回到岸上。
即使我人在旅行的時候,每天仍然都有一場到兩場由我帶領的線上哲學工作坊。這幾年來,由於工作型態的改變,大多數的工作都可以透過網路進行。無論我人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都要預先計算好時差,也要確認網路的順暢,才能順利進行日常的工作。
由於位在東非外海的塞席爾群島,和北京、台北都有著四個小時的時差,對我的工作時間來說,這簡直是太完美的安排了。這意味著每週三天晚上七點開始的哲學工作坊,是塞席爾的下午三點鐘、而每週四天晚上八點開始的工作坊,則是塞席爾時間下午四點。原本在馬埃島南方潛水的我,上岸後剛好有足夠的時間清洗我的潛水裝備,把身上的鹽分沖掉,還可以在沿路山坡頂一家叫做「三朵玫瑰花」(3 Roses)的胖卡餐車小店稍停留,我會選擇米飯或薯條,搭配兩個菜,其中一樣通常是塞席爾傳統的章魚咖哩或螃蟹咖哩,另外一樣可能是風乾的紅鯛魚,也可能是鹽烤的鱸魚。對於喜歡吃海鮮的我來說,塞席爾的路邊料理是很完美的,反正島上除了雞之外,沒有飼養動物,所以基本上不大會吃到肉類。另外,我希望每天的日常生活能夠盡量環保,每天會隨身帶著自己準備的飯盒,請老闆裝在我的飯盒裡,米飯的分量也會按照我的食量斟酌減半,確保不會造成食物的浪費。另外一個飯盒則會裝甜點,有時候是焦糖布丁,有時候是裡面抹了果醬的甜甜圈,完全看當天老闆做了什麼。這是一個沒有菜單,也沒有任何造作的純樸島國,我覺得這樣很好。
但自從必須到馬埃島的東北角才能潛水,每次上岸後,就意味著必須多花一個多小時才能回到島上西南角的旅館。
經過了兩三天之後,我發現下午四點的線上課還好,但是如果當天有下午三點開始的線上課,會讓我上午的潛水變得焦慮。
因為開車至少要一小時的時間,所以每到下午一點半,如果潛水船還沒有靠岸的時候,我就會開始緊張,擔心時間不夠。
即使一點半前準時靠岸,一面在清洗潛水用具的時候,也會忍不住開始產生焦慮。因為我又想仔細地清洗乾淨,確認裝備沒有殘留沙粒或是鹽分,又想趕快上路離開,以免在路上被接送孩子放學的家長堵在狹窄的山路上。
洗完潛水裝備上路,我並沒有覺得放鬆,反而開始新的憂慮。因為我擔心會不會在半路上,突然像前兩天那樣遇到前方車子引擎突然自燃的交通事故,造成唯一的聯通道路封閉,或是其他的意外。
雖然潛水上岸之後,肚子餓得嘰哩咕嚕叫,但我擔心萬一停下來買飯盒,會不會耽誤了路程?買了飯盒,會不會沒有時間吃?回到住宿的地方,停車場在山坡底下,我還要步行走回山坡最頂上的住處,會不會因此趕不及?
萬一回到房間,才發現無線網路突然不通的話,是不是有足夠的時間,立刻改用手機漫遊上網應變?
調整好做下一件事的狀態
每一堂哲學工作坊,通常我都會布置課前作業,讓參加者在上課之前,先針對主題思考,從每一個人的課前作業中,我就可以了解參加者的思考狀態。可是如果只能勉強趕在上課前五分鐘慌亂衝回書房,意味著我根本沒有時間閱讀參加者的課前作業,沒有辦法充分掌握每一個參與者獨特的思路。
這種種的焦慮,與我潛水時在深水之下專注呼吸的狀態,有著天壤之別。我並不喜歡自己那種慌亂、憂慮的狀態,覺察到這點之後,我做了一個決定:如果當天下午的線上課是塞席爾時間三點開始的,那天就不潛水,如果是四點開始的話,才可以潛水。
「差一個小時,有差這麼多嗎?」或許有人會這麼說。
我知道應該是可以趕在最後一刻準時上線的,而且如果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辦法準時上線的話,也有三位常態配置的助教可以協助我先進行一開始的討論。雖然如此,我仍然寧可在一個小時之前,調整好做下一件事的最佳狀態。意思就是,在開始正式工作的一個小時之前,我可以喝咖啡、散個步,或是做點別的事情。但不能是會將我帶離那個最適狀態的事。比如回覆郵件、上網看無關的新聞或視頻,或是整理文件,就會形成太大的干擾,開車在隨時可能出現狀況的陌生國度山路上趕路,就更不用說了。但在陽台上喝咖啡或洗洗碗盤這種事卻不會造成干擾,因為我的思考狀態不會被這些彷彿禪修般重複性高的小動作影響。
就這樣,我在塞席爾群島的旅行,出現了新的規律。
一個禮拜四天潛水,因為這四天都是下午四點鐘開始線上工作,我會在下午三點前悠閒地結束午餐,回到房間,有足夠的時間備課。就像我在哲學思考的教師培訓課上,常常提醒老師的,我也用同樣的話來提醒自己:「作為老師,最好的備課,就是準備好自己。」
至於另外三天,因為下午三點鐘要開始工作,我可以允許自己不設定鬧鐘,奢侈地睡到自然醒,奢侈地慢慢喝咖啡,慢慢吃早餐,然後找一條登山步道、一個沒有去過的海灘,或是什麼都不做,在住處的沙灘上,躺在吊床看書。但無論如何,都會在下午兩點以前回到房間,給自己在工作以前有完整一個小時的時間,沉靜下來,調整自己到最合適的狀態。所以從上線登入的那一分鐘開始,我就是準備好的狀態。
「那不是很可惜嗎?」或許有人會說。
(節錄)
〈第三件重要的事:成為一個同伴〉
「同伴」是一種職人的哲學,跟一個同伴一起工作和學習,永遠會是一種樂趣。
最大的讚美:成為真誠的「同伴」
無論在NGO的領域、寫作的領域,還是哲學諮商的領域,我希望跟我在一起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跟我的「同伴」關係。
因此只要有人在各種培力的課程、評審會議或工作坊上尊稱我為「老師」,過去的我可能會因此感到被重視的虛榮,偷偷高興一下,但是現在的我卻一點都高興不起來,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如果是在哲學思考工作坊上,我甚至會特別停下來強調,在邏輯思考裡,我們沒有「師生」的關係,我們都是思考的「夥伴」。
對我來說,那才是最大的讚美。
我清楚感受到這種關係的轉換,為我和世界建立起一個安全和信任的環境。我慢慢地學會如何在同行的路上,與和我一起的人,成為真誠的「同伴」。
「同伴」的概念,是從哪裡來的呢?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在收音機上聽到美國手工烘焙大師丹尼爾‧立德(Daniel Leader)在接受採訪時,說了一段對他人生重要的往事。
四十多年前,他還是一個很年輕、但被認為有天賦,也已經頗有經驗的麵包師,法語說得不錯的他到了烘焙的聖地法國去拜師學藝。他遇到一個麵包師傅,跟其他師傅教他的時候很不一樣,這個師傅不但很有耐心,而且可以透過手指的觸碰,評估麵粉的狀態,很有自信地對食譜進行微小調整,達到心目中想要的結果。
比如給麵團加水的時後,他不會拿量杯,也不會按照食譜,而是一滴一滴地慢慢加,不斷觀察、評估和計算,尋找麵團的微妙變化,直到完美地融合為止。
丹尼爾說,光是看著師傅如何決定兩種麵粉的混合比例,以及揉麵團的過程,就像一個震撼人心的大師講堂。整個指導的過程有如行雲流水,不著痕跡,他的動作很快、溫柔,卻毫不費力。
他小心翼翼地處理麵團,不去損壞麵包內部的結構,創造出形狀完美的麵包。即使像丹尼爾這樣有經驗的麵包師,也因此能夠用新鮮的眼光,來重新看待烘焙這門手藝。
有一次,丹尼爾為了把一桶發酵中的麵團倒在麵包檯,按照他在美國的習慣,用手用力敲打著桶子邊緣,讓麵團跟桶子分開,重重掉到麵包檯上。
師傅看了一眼,在不批評丹尼爾的習慣下,只是淡淡地說他有一個更好的方式,接著拿出一把抹刀,輕輕地、溫柔地用抹刀鬆開容器兩側的麵團,讓麵團完美無聲地滑到正方形的麵包檯上。
在將麵團放回容器之前,師傅又輕輕拍打麵團,彷彿在鼓勵它。
把你學會的技術交給「同伴」
在這些細微的動作中,丹尼爾說他看到極大的尊重和良好的能量轉移—雖然丹尼爾在訪談當中,並沒有明說是在他和師傅之間,還是師傅和麵團之間,但我猜測是兩者兼具。
在學習結束以後,丹尼爾忍不住問這位師傅,為什麼他跟其他麵包師相比,令人感受到一種說不出的與眾不同?
這位麵包師傅慎重地說:「因為我是Compagnons du Devoir et du Tour de France的成員。」
這是丹尼爾第一次聽說這個起源於中世紀行會的法國工匠組織,而這個師傅原來是Minoterie Suire這個古老家族麵粉廠的創新和研究總監,法國烘焙界的大師法布里斯‧庫里(Fabrice Cuéry)。
作為一名已經訓練有素的烘焙師,法布里斯當年為了要成為一名這個組織認證的Compagnon(同伴),除了必須參加烘焙術科考試,更重要的是參加像是人格測驗的評估考試,看他有沒有成為一個好師傅的性格和潛力。
一旦通過嚴格的考驗被選上之後,會得到腰帶和儀式手杖,正式成為「有抱負的人」(aspirant),標誌著未來的旅程。接下來,就要進行五年的學徒(stagiaire)修業期。
每一年,學徒會被分派到一個法國境內不同的地點,跟著一位烘焙大師,接受一年的指導。他在南方的普羅旺斯學會了烤福加斯(Fougasse Aux Herbes De Provence)這種特別的香草麵包後,又到東北的亞爾薩斯去學了咕咕霍夫(kougelhopf)麵包,這種用裸麥、黑麥、小胚芽麥所做成的麵粉,將麵包做成圓邊帽的形狀,然後加入啤酒酵母,是專門用來搭配生蠔、鵝肝的重口味麵包。
這個古老的法國工匠組織想要做的,遠遠不只是讓年輕麵包師,到處去學習製作不同麵包的技術,更重要的是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就要把之前學會的技術,立刻交給新的同伴。也就是說,他從普羅旺斯到了亞爾薩斯,不只要學習亞爾薩斯的麵包技術,也要把在普羅旺斯學習的麵包技術,毫不藏私地帶給亞爾薩斯的麵包師們。這是一種道德承諾,不僅要傳遞他的烘焙訣竅,還要傳遞他作為一個好匠人、甚至一個好人的生活方式。
我想要成為這樣的人
「compagnon」(同伴)這個詞,來自於古法語「compaignon」,意思就是「一個與人一起吃麵包的人」,他被帶入社群,與其他學徒一起住在同一間房子裡。成為一名同伴,意味著必須學習與跟自己背景很不同的人一起同行,並且幫助對方以他們自己選擇的方式蓬勃發展。
實際上,這個環法的古老行會,在中世紀時期建造了法國的教堂和城堡,並受到國王和天主教會的迫害,因為他們拒絕在任何一個機構的規則下生活,而開始了自己的制度。
除了麵包師、甜點烘焙師之外,養成的專業還包括編輯、石匠、木匠、屋頂工、水暖工、鎖匠、金屬匠、木工雕刻家、泥水匠、畫家、裝潢師傅、櫥櫃製造商、園丁景觀設計師、製桶師傅、車身修理工、鍋爐製造工、機械師、電工、精密機械師、鐵匠、馬蹄鐵匠、皮匠、鞍具製造工、鞋匠、釀酒師等,而養成的方式都是一樣的:這些原本就已經有法國政府頒發的 Certificat d’aptitude professionhelle(專業資質證書)證照的工匠,在持續多年的工作和旅行中學習。在法國有八十多個這行會的據點,規模大小不等,有小到只能容納五個人的小房子,也有大到可容納一百多人住在一起的大房子。學徒學習的不只是技術,還包括這個行業的經營,以及高尚的職人道德。這是一個傳統師徒制的指導網絡,透過這樣的身教可以學習一門手藝,同時透過體驗社區生活和旅行來培養性格。完成修學的旅程後,「有抱負的人」必須提交一件結業作品(稱為「傑作」,travail de réception 或 chef-d’œuvre)給行會接受評鑑,如果被接受,才可以正式成為一名「同伴」,獲得一個同伴的專屬名字,並獲得一根能達到心臟高度的新手杖。這還沒有結束,接下來這個剛得到「同伴」認證的職人,必須繼續巡迴三年後,選擇在一個地方穩定地生活和工作,成為compagnon sédentaire(久坐不動的同伴),開始教導自己的學徒。
當來自美國的丹尼爾遇見他的師傅法布里斯時,法布里斯已經選擇大西洋羅亞爾省一個小城市布賽(Boussay)的Minoterie Suire百年麵粉廠作為他的基地,並且二十年來在那裡傳遞給他的「同伴」各種技能和準則;當了數百名麵包師的「同伴」,建立的不是以自己為名的品牌,分享的也不只是他對麵包烘焙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他對烘焙的熱情,以及傳達對職人的期許。
丹尼爾說的這個故事,讓我深受啟發。
「這就是我想要成為的人啊!」當時年輕的我跟自己這麼說,雖然我一點都不知道未來的我具體想要做什麼。但在那一刻,我意識到這正是我想要成為的人。
(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