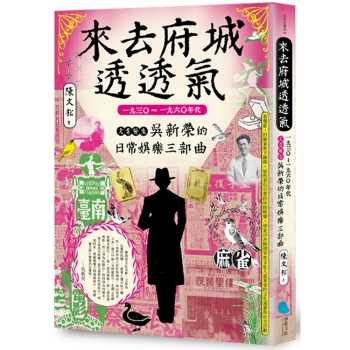二、吳新榮打麻雀到下圍棋的心境
從日記中我們所看到的吳新榮日常,頗具曲折的戲劇性與深刻的時代感,如實傳達出傳主在不同時期生活的心理轉折。麻雀如此,圍棋亦然。
論者常以吳新榮自稱「醫業是我正妻,文學是我情婦。」來探究他對文學創作的投入與成就。筆者卻在首次讀完吳新榮日記並且以他的娛樂活動為研究主題時,往往情不自禁地以現代流行語「小三」來比附、戲稱。實在是因為這「小三」不但會影響正妻和情婦,而且還不只一個。它們的地位時常流動,時而麻雀居上,時而圍棋當道,有時更不惜出遠門,化身「文化人」到府城去喫茶店或カ—フェ風流、看電影、吃小吃來「透透氣」。
有趣的是,這些不同的「小三」在傳主的日常生活經營過程當中,都有其「適時」、「適所」和「適人」的立意和權變。從麻雀到圍棋,轉折點剛好落在吳新榮人生最具活力的青壯年期到逐漸邁入中晚年的階段。圍棋更是兼跨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從日常生活到國家認同,臺灣人都面臨最為難熬且動輒得咎的艱困局勢。今日我們何其有幸得以從這整部日記裡,直接閱讀和仔細吟味當一個人面臨著瞬息萬變的時局變遷下,體會傳主內心的轉折和甘苦之處。
然而,不管是正妻、情婦抑或是「眾小三」,都是傳主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為了讓傳主生活及生命的詮釋更為多元、更能與不同時代相呼應,適當的裁切是有其必要的。日記雖有上述之重大意義,但傳主吳新榮在寫作當下,未必有公諸於世的想法。所以,觀其所思,察其所言,究竟他是一時興起或有周密安排,以至是否言出必行,這些我們在今天去理解時,應具備同情的理解和細緻的觀察,始能設身處地,不會強加不當的批判到傳主身上。(一)從下五子棋到下圍棋
如上所述,吳新榮正式學下圍棋始於一九四○年。不過有趣的是,不管麻雀或圍棋,吳新榮都跟他臺南高等商業學校時的啟蒙師林茂生有著亦步亦趨的巧妙雷同。當他在一九三六年加入南洲俱樂部之後,吳新榮曾在該處所舉辦的麻雀大會上,兩度成為林茂生的手下敗將。到了一九四○年的下半年吳新榮才開始學下圍棋,之後經過兩年的不斷苦練,雖然已經可跟伙伴一較高下,實力依舊未成氣候。吳新榮甚至在一九四二年的日記中戲稱自己的圍棋才只是「十六、十七、十八級前後」。反觀林茂生早在一九三五年即位居七級,兩者棋力相差不可「以道里計」。
撇開段位制不談,吳新榮在愛下圍棋之前除了沉迷麻將,偶爾也會與伙伴玩起與圍棋原理類似的「五子棋」。例如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日,適逢三子吳南圖出生,吳新榮當天在飯後便與友好下五子棋取樂:
雪芬昨夜開始有了異狀,早上起床馬上打電話到六甲請岳母趕快來。到了下午開始初期陣痛,又趕快請產婆吳氏繡來。正好下午六點十分生下了個男嬰,我的第四個孩子,即第三個男孩。骨格和南星、南河同型。只有朱里畢竟是女孩,骨架與兄弟不同。以岳母和產婆為主,在晚餐時,安排了小宴。飯後到酒配銷所,和周約典、陳振鼓兩位玩五子棋,一勝一敗,連戰數十回合,沒有勝負。返家後開始想新生兒的命名問題,寫信告訴昭川義兄、奇珍兄和雪金報喜。
吳新榮等人玩五子棋或日後下圍棋的地方,和打麻雀時一樣,主要是佳里街酒配銷所和自宅小雅園。
晚上到酒配銷所玩五子棋。對手是徐清吉、周約典兩位,他們都不是我的對手。黃大友君將在佳里開業當代書,我和徐君商談舉辦歡迎會,決定邀請的人有謝得宜、郭水潭、黃淵和其他幾位朋友。
昨夕開始舉行第二種防空演習,到金唐殿報到。和徐清吉君去拜訪石錫純氏,不在家。回程拜訪鄭國湞氏,看看他的新建築,並談些組合和街政的話。傍晚到佳里興外診,之後拜訪郭水潭君,談了些話。晚和黃大友君一起去找徐清吉兄,玩五子棋。
由此可知,吳新榮在學下圍棋以前,除了麻雀以外就是五子棋,而與打麻雀不同的是,對手和場所相當固定,就是黃大友、徐清吉兩人,地點主要在酒配銷所,因為該配銷所是由方沁和其女婿徐清吉擔任酒類經銷商,所以該處幾乎成了鹽分地帶集團的附屬俱樂部。
文中所稱防空演習,自然與戰時體制有關。為了提高國防意識,臺灣軍司令部早於一九三一年就特地選在陸軍記念日當天,以大臺北地區為主,進行全臺首次的防空演習暨燈火管制。當日本對中國發動滿洲事變,日本本土和殖民地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後,更是不時在全臺各地舉行各種規模和時間長短不一的防空演習暨夜間燈火管制措施,尤其一九三七年中日全面開戰之後更是如此,臺南地區也不例外。不過,因為是演習,過程中不會真的出現敵機來襲,這段「躲空襲警報」的時間吳新榮仍是經常和伙伴一起玩五子棋。
一九四○年三月,吳新榮將麻雀牌投入糞坑後不久,即決定開始正式學下圍棋而。從後來的日記觀察,圍棋幾乎完全取代麻雀的地位。因此,這一年可說是吳新榮的室內社交娛樂從麻雀過渡到圍棋的分水嶺。這樣的轉變除了工具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因為兩者性質差異,其目的和對象也出現極大的轉變。在殖民政策與時局上,麻雀既是賭具,打麻雀自然視為「非國民」的行為。反之,下圍棋則是符合戰時「國策」的正當娛樂。也許,這也是對時局異常敏感的吳新榮後來之所以幾乎禁絕打麻雀而改下圍棋的最主要因素。
從日記中我們所看到的吳新榮日常,頗具曲折的戲劇性與深刻的時代感,如實傳達出傳主在不同時期生活的心理轉折。麻雀如此,圍棋亦然。
論者常以吳新榮自稱「醫業是我正妻,文學是我情婦。」來探究他對文學創作的投入與成就。筆者卻在首次讀完吳新榮日記並且以他的娛樂活動為研究主題時,往往情不自禁地以現代流行語「小三」來比附、戲稱。實在是因為這「小三」不但會影響正妻和情婦,而且還不只一個。它們的地位時常流動,時而麻雀居上,時而圍棋當道,有時更不惜出遠門,化身「文化人」到府城去喫茶店或カ—フェ風流、看電影、吃小吃來「透透氣」。
有趣的是,這些不同的「小三」在傳主的日常生活經營過程當中,都有其「適時」、「適所」和「適人」的立意和權變。從麻雀到圍棋,轉折點剛好落在吳新榮人生最具活力的青壯年期到逐漸邁入中晚年的階段。圍棋更是兼跨日治末期到戰後初期,從日常生活到國家認同,臺灣人都面臨最為難熬且動輒得咎的艱困局勢。今日我們何其有幸得以從這整部日記裡,直接閱讀和仔細吟味當一個人面臨著瞬息萬變的時局變遷下,體會傳主內心的轉折和甘苦之處。
然而,不管是正妻、情婦抑或是「眾小三」,都是傳主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為了讓傳主生活及生命的詮釋更為多元、更能與不同時代相呼應,適當的裁切是有其必要的。日記雖有上述之重大意義,但傳主吳新榮在寫作當下,未必有公諸於世的想法。所以,觀其所思,察其所言,究竟他是一時興起或有周密安排,以至是否言出必行,這些我們在今天去理解時,應具備同情的理解和細緻的觀察,始能設身處地,不會強加不當的批判到傳主身上。(一)從下五子棋到下圍棋
如上所述,吳新榮正式學下圍棋始於一九四○年。不過有趣的是,不管麻雀或圍棋,吳新榮都跟他臺南高等商業學校時的啟蒙師林茂生有著亦步亦趨的巧妙雷同。當他在一九三六年加入南洲俱樂部之後,吳新榮曾在該處所舉辦的麻雀大會上,兩度成為林茂生的手下敗將。到了一九四○年的下半年吳新榮才開始學下圍棋,之後經過兩年的不斷苦練,雖然已經可跟伙伴一較高下,實力依舊未成氣候。吳新榮甚至在一九四二年的日記中戲稱自己的圍棋才只是「十六、十七、十八級前後」。反觀林茂生早在一九三五年即位居七級,兩者棋力相差不可「以道里計」。
撇開段位制不談,吳新榮在愛下圍棋之前除了沉迷麻將,偶爾也會與伙伴玩起與圍棋原理類似的「五子棋」。例如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日,適逢三子吳南圖出生,吳新榮當天在飯後便與友好下五子棋取樂:
雪芬昨夜開始有了異狀,早上起床馬上打電話到六甲請岳母趕快來。到了下午開始初期陣痛,又趕快請產婆吳氏繡來。正好下午六點十分生下了個男嬰,我的第四個孩子,即第三個男孩。骨格和南星、南河同型。只有朱里畢竟是女孩,骨架與兄弟不同。以岳母和產婆為主,在晚餐時,安排了小宴。飯後到酒配銷所,和周約典、陳振鼓兩位玩五子棋,一勝一敗,連戰數十回合,沒有勝負。返家後開始想新生兒的命名問題,寫信告訴昭川義兄、奇珍兄和雪金報喜。
吳新榮等人玩五子棋或日後下圍棋的地方,和打麻雀時一樣,主要是佳里街酒配銷所和自宅小雅園。
晚上到酒配銷所玩五子棋。對手是徐清吉、周約典兩位,他們都不是我的對手。黃大友君將在佳里開業當代書,我和徐君商談舉辦歡迎會,決定邀請的人有謝得宜、郭水潭、黃淵和其他幾位朋友。
昨夕開始舉行第二種防空演習,到金唐殿報到。和徐清吉君去拜訪石錫純氏,不在家。回程拜訪鄭國湞氏,看看他的新建築,並談些組合和街政的話。傍晚到佳里興外診,之後拜訪郭水潭君,談了些話。晚和黃大友君一起去找徐清吉兄,玩五子棋。
由此可知,吳新榮在學下圍棋以前,除了麻雀以外就是五子棋,而與打麻雀不同的是,對手和場所相當固定,就是黃大友、徐清吉兩人,地點主要在酒配銷所,因為該配銷所是由方沁和其女婿徐清吉擔任酒類經銷商,所以該處幾乎成了鹽分地帶集團的附屬俱樂部。
文中所稱防空演習,自然與戰時體制有關。為了提高國防意識,臺灣軍司令部早於一九三一年就特地選在陸軍記念日當天,以大臺北地區為主,進行全臺首次的防空演習暨燈火管制。當日本對中國發動滿洲事變,日本本土和殖民地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後,更是不時在全臺各地舉行各種規模和時間長短不一的防空演習暨夜間燈火管制措施,尤其一九三七年中日全面開戰之後更是如此,臺南地區也不例外。不過,因為是演習,過程中不會真的出現敵機來襲,這段「躲空襲警報」的時間吳新榮仍是經常和伙伴一起玩五子棋。
一九四○年三月,吳新榮將麻雀牌投入糞坑後不久,即決定開始正式學下圍棋而。從後來的日記觀察,圍棋幾乎完全取代麻雀的地位。因此,這一年可說是吳新榮的室內社交娛樂從麻雀過渡到圍棋的分水嶺。這樣的轉變除了工具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因為兩者性質差異,其目的和對象也出現極大的轉變。在殖民政策與時局上,麻雀既是賭具,打麻雀自然視為「非國民」的行為。反之,下圍棋則是符合戰時「國策」的正當娛樂。也許,這也是對時局異常敏感的吳新榮後來之所以幾乎禁絕打麻雀而改下圍棋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