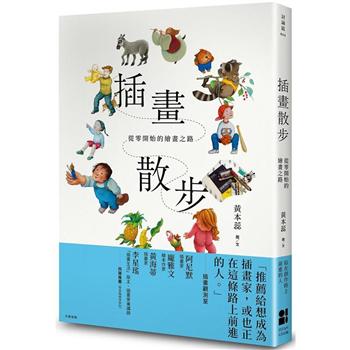卷一 從台北到紐約
從前從前——我的童年與童話
我愛畫畫,是無庸置疑的。從三、四歲人人稱我黃毛ㄚ頭開始,之後上了幼稚園、入了小學、中學……,每一個相處過的老師,都不時地向我的母親保證:我將會成為一個畫家,多麼籠統的預言啊!但他們似乎多少言中了我一生與畫筆為伍的命運。
從小在城市長大,生活在那個年代並無特別可去之處,只有家門口的一方水泥地,玩耍的對象也總是妹妹,我們要不抓支粉筆,或拾一塊炭,隨處塗鴉。說旅行呢,去過最遠的地方只是板橋的外婆家。但是,我很愛幻想,愛做白日夢,不分時與地,只要有這麼一扇小窗,我準可以對著外面景物編起一串故事—天上雲彩的消息,或地上的風吹草動,總有無數的戲在我與它們之間上演著。
有一次,爸爸不知如何弄來了一套「世界童話全集」,啊!那些美好的故事,為我的幻想插上了翅膀,我從此便——起飛了!回想那一本本的童話書,灰色的平裝書皮,用小小的鉛字體,印了一排簡簡單單的書名——《盧森堡童話》。最遠只去過板橋外婆家的我,在那個年紀就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叫做盧森堡,還有丹麥、智利、格陵蘭。每本童話書內的妝點也不比書皮精彩,總是清一色報紙質地的書頁加上套了一色的鉛體印刷;但一個個故事,卻自有它華美的彩衣。讀著它們時,感覺自己也披上了那彩衣,鼓動著雙翼,飛向一個個古老的王國,神祕的鄉城無遠弗屆。
「那裡的屋子長什麼樣子?」「人們穿什麼服裝?」「公主哭出珍珠來是什麼光景?」我常有這些好奇,所以好想把想像中的童話世界畫出來。孩童時期的想像,直接又逼真,一個個美好的童話城堡,早在小小腦袋裡築妥,只待彩筆一揮,就呼之欲出了。想畫畫,當時家裡現有的,是大我六歲的姐姐教我做紙娃娃剩下來的紙,和一盒「利百代」牌子的蠟筆,在當時這已經是很豐富的材料了!我就這麼一張張地把單色鉛字地故事畫出色彩……
上了中學,更是惡習難改,課堂上的每一本課本,凡有空白之處,都被畫滿了故事,《傲慢與偏見》《戰火孤女淚》《西廂記》……,故事不分國界,沒有限制。慢慢的,進入了青春期的尷尬年紀,書讀多了,涉獵廣了,人也自認深沉了。除了風花雪月的故事總在我的十大排行榜上之外,對於那些充滿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文章,漸漸衷情起來,人好像就這麼地成熟了。在此同時,我決定就讀美術科系,雖然和童話世界漸行漸遠,但那些振翅翱翔的童年經驗,長久駐紮在我的體內,到現在,我還不時與那鼓動著大大的翅膀、身披斑斕彩衣的小女孩,四處翱翔著……
故事繼續——成長與繪畫
在開始接觸藝術創作的年紀,對很多事都有很多疑問。對自己的存在有疑問、對人生有疑問、對國家、世界都有疑問。把這些疑問強行放入創作裡,再用年輕人特有的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努力刻劃他們所認知的人性與世界,然後為它們正名為「藝術」—那就是我青年期的重心。讀的書也不同了。除了許多藝術史的書、理論的書之外,有的人偏愛哲學思考,有的人瘋狂參與政治,又有些人埋首精研繪畫理論—期待自己成為一種新的繪畫風潮的獨領風騷者。
那一段日子裡,我大抵是很勤懇的在習畫的,整個藝術領域在我眼前拓展,各種畫派、各種主義、各種可能性,令人眼花撩亂。而超現實主義那種帶著寂寞的晦澀詩意,尤其吸引我。「超現實主義」是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詩人與畫家利用不同創作的方式,相互激勵而成的畫派。我喜歡這種內容的創作,因為這種表現方式,讓我對文字的濃厚情感與繪畫的表達技巧上,可以同時得到滿足。
我一方面像剛開了眼界似地興奮著,要把這眼前的景致盡收眼底,另一方面卻被一種未曾經驗的無聊漸漸襲上身,這是一種寂寞的感覺。我常常想,這無聊與寂寞是怎麼來的?雖然這樣想著,卻也不特別去追究,日子就這麼過去,後來也因為忙了,無聊彷彿減少了,但寂寞,卻一日日坐大起來……
一個新的章節——成為一個插畫家
人生的變數既難掌握,卻又那麼地宿命。二十幾歲初出大學校園的我,一路走來,幾經波折跌宕,再回顧時,我已坐在紐約家裡的書桌前,二十年的光陰也已飛逝。初離校門,父親驟逝,母親罹癌,我離開了生長的地方,來到美國,一個陌生的國土,陪伴在美國就醫的母親。沒有了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語言,像拔了根似的,也讓自己飛離了軌。母親過世後,孑然一身。原有的那日漸坐大的寂寞感,更是盤據了一身。沒有一個窩心的住處,也沒有足夠的畫具與空間,每日只能以簡單的紙筆寫點感覺,畫點心境,聊以寄情。直到某些日子裡,在不經意的冥想中,偶然與那個小小的自己不期而遇—身披五彩繽紛的羽裳,飛著四處造訪的小女孩。猛然意識到:原來自己多麼懷念那些拾著短短蠟筆,大膽又盡興地畫著童話世界的日子啊!於是我又開始畫起一個個小小的故事——在這裡,我接觸到自己生命的源頭,看到幼小年輕的自己,對陌生的世界感到新鮮與好奇……。我彷彿也看見自己在縮小……縮小……對這片新踏上的國土開始感覺新鮮與好奇。
我喜歡畫畫、喜歡故事、喜歡用畫來說故事、喜歡文字與繪畫結合時剎那間蹦出的火花。是什麼力量不斷驅使我去尋找故事,並且去把它畫出來,大概就是這個火花迸裂時的驚艷吧!
八○年代中期,我抱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傻勁隻身飛赴紐約——這個全美最大的都市,也是世界經濟、貿易、文化、藝術的中心。我有一個夢想要落實,想要成為一個童書插畫家。我感覺自己正披上那張斑斕的彩衣,細心地整理著羽翼,等待振翅而飛。
雖是初生之犢,但也不能忘記先做功課——尋找一個插畫經紀人,是我當前的課題。
我提著大大的作品夾,穿梭在曼哈段高樓林立的市區內。紐約這個大都會,雖不如巴黎的浪漫、羅馬的古趣盎然,但它有一股朝氣,像是一塊磁鐵,不僅吸引了來訪的旅客,更讓年輕人蜂擁雲集,只為了在這塊試金石之上,把自己的理想磨出光芒來。我在短短的數週內,拜訪了幾家經紀公司,與幾位經紀人在晤談後,順利地獲得一位有二十多年經紀人經驗的女士的青睞。在她的公司裡,經營了二十多位名氣大小不一的插畫家,她邀請我加入她的行列,我們隨後便開始迄今第十八年的合作關係。
故事至此,我好像順利地開啟了「童書插畫家」之鑰,一路走來也似乎順理成章、毫無坎坷,其實這一切,多要歸功在事前的充分準備,市場的接受力,再加上一點運氣。八○年中期以後,美國市場經濟保持景氣,童書出版業也日益蓬勃,但投入的創作者人數尚未激增。當時我二十幾歲的年輕生命,一心嚮往投入這個創作的行列,成為出版事業的一員。
在事前準備方面,當然「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既然志在出版業,對出版事業就要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幾十年前,在網際網路完全不發達的年代,藝術家尋找資訊的地方,大概只有靠圖書館、書店或報章雜誌了!那時一個小小故事,至今記憶猶新:記得仍每天翻閱報紙的年代嗎?我就是在那個年代,不經意在一份華人報紙上讀到一則很有意思的啟事,大致上說,市民們如有「任何」問題,可以致電市立圖書館員詢問,這不禁讓我想到一部老電影,裡面的男女主角分別由凱薩琳‧赫本和史賓賽‧區賽飾演,他們是兩名天才圖書館員,專門接聽市民電話,解答任何疑難雜症,不記得電影名稱了,但是那則新聞讓我好奇地拿起電話,試想會不會有個天才圖書館員在聽筒的另一端,能否解答我的疑難雜症……對啦!那是中文專線,沒有凱薩琳‧赫本,而是一位溫柔如母親的女性回覆了我的需求,感謝她,因為就是她告知,一本在美國各個市立圖書館都可參閱的資料書籍《文學市場》(Literary Market Place,簡稱LMP),刊登了有所有美國出版社的名稱、地址、電話,以及編輯的姓名。年輕人想要尋找適合的出版社,可從這裡去察訪、聯繫,因為儘管每個出版社的行事風格不一,但一般而言,「編輯」是想入行的插畫家及作家該去聯繫的對象。本書並刊登有一些經紀公司的資料供參考,我當時正是完全拜此書之賜。另一本名為《Writer’s Market》的書,也有類似的參考價值。
當然今天的年輕人,哪需要打電話詢問?哪需要溫柔如母親般的建議?綜上至下所述,都是一個上個世代的退休插畫家的喃喃自語。然而我是這麼想的,這本書,也不是一本工具書,更不涉及理論,所以也不是一本理論專書,輕輕鬆鬆地,只是我的經驗分享罷了!
在此一提美國的經紀人制度:
在出版業的經紀人代表插畫家,是與出版社溝通的橋梁,他們了解出版業的趨勢,和出版社也有一定的良好關係。所以在商談合約時,經紀人通常能為畫家爭取到較好的條件,當然經紀人會索取一定比例的費用,一般合理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在此要打破一個迷思,就是編輯或許會多花心思瀏覽較有威望的經紀人所推薦的畫家,但這並不必然是工作到手的保證。一切結果仍取決於這個畫家作品本身的好壞,以及作品風格是否契合編輯的喜好。
再談一談美國的出版社如何尋找一位理想的插畫家:
當出版社有新書出版的計畫時,編輯部門會率先考慮一位他們喜歡的,或熟悉其作品的畫家,並與他(或她)聯繫出版的可能性。有時候編輯會參考藝術指導的意見,啟用一位新人(出版社常會有不少年輕畫家的作品影印資料存檔)。當候選人的範圍縮小到二、三人時,編輯或許會要求畫家們提供一張針對這個故事而作的小畫(sample),然後再進行最後的挑選。一旦決定了一位插畫家,合作關係便從此開始——包括合約的討論,工作進度的安排,以及正式工作內容的進行等等。
再囉嗦一下:出版事業畢竟是人際合作的事業,當編輯選擇一個畫家時,此人的個性人格特質有時也是他們考慮合作與否的部分因素,假若是一個新人,編輯們自然會多花一些時間指引與開導,但畫家本身也該儘早吸收專業知識,以便應付這個極其專業的領域。
從前從前——我的童年與童話
我愛畫畫,是無庸置疑的。從三、四歲人人稱我黃毛ㄚ頭開始,之後上了幼稚園、入了小學、中學……,每一個相處過的老師,都不時地向我的母親保證:我將會成為一個畫家,多麼籠統的預言啊!但他們似乎多少言中了我一生與畫筆為伍的命運。
從小在城市長大,生活在那個年代並無特別可去之處,只有家門口的一方水泥地,玩耍的對象也總是妹妹,我們要不抓支粉筆,或拾一塊炭,隨處塗鴉。說旅行呢,去過最遠的地方只是板橋的外婆家。但是,我很愛幻想,愛做白日夢,不分時與地,只要有這麼一扇小窗,我準可以對著外面景物編起一串故事—天上雲彩的消息,或地上的風吹草動,總有無數的戲在我與它們之間上演著。
有一次,爸爸不知如何弄來了一套「世界童話全集」,啊!那些美好的故事,為我的幻想插上了翅膀,我從此便——起飛了!回想那一本本的童話書,灰色的平裝書皮,用小小的鉛字體,印了一排簡簡單單的書名——《盧森堡童話》。最遠只去過板橋外婆家的我,在那個年紀就知道有這麼一個地方,叫做盧森堡,還有丹麥、智利、格陵蘭。每本童話書內的妝點也不比書皮精彩,總是清一色報紙質地的書頁加上套了一色的鉛體印刷;但一個個故事,卻自有它華美的彩衣。讀著它們時,感覺自己也披上了那彩衣,鼓動著雙翼,飛向一個個古老的王國,神祕的鄉城無遠弗屆。
「那裡的屋子長什麼樣子?」「人們穿什麼服裝?」「公主哭出珍珠來是什麼光景?」我常有這些好奇,所以好想把想像中的童話世界畫出來。孩童時期的想像,直接又逼真,一個個美好的童話城堡,早在小小腦袋裡築妥,只待彩筆一揮,就呼之欲出了。想畫畫,當時家裡現有的,是大我六歲的姐姐教我做紙娃娃剩下來的紙,和一盒「利百代」牌子的蠟筆,在當時這已經是很豐富的材料了!我就這麼一張張地把單色鉛字地故事畫出色彩……
上了中學,更是惡習難改,課堂上的每一本課本,凡有空白之處,都被畫滿了故事,《傲慢與偏見》《戰火孤女淚》《西廂記》……,故事不分國界,沒有限制。慢慢的,進入了青春期的尷尬年紀,書讀多了,涉獵廣了,人也自認深沉了。除了風花雪月的故事總在我的十大排行榜上之外,對於那些充滿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的文章,漸漸衷情起來,人好像就這麼地成熟了。在此同時,我決定就讀美術科系,雖然和童話世界漸行漸遠,但那些振翅翱翔的童年經驗,長久駐紮在我的體內,到現在,我還不時與那鼓動著大大的翅膀、身披斑斕彩衣的小女孩,四處翱翔著……
故事繼續——成長與繪畫
在開始接觸藝術創作的年紀,對很多事都有很多疑問。對自己的存在有疑問、對人生有疑問、對國家、世界都有疑問。把這些疑問強行放入創作裡,再用年輕人特有的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努力刻劃他們所認知的人性與世界,然後為它們正名為「藝術」—那就是我青年期的重心。讀的書也不同了。除了許多藝術史的書、理論的書之外,有的人偏愛哲學思考,有的人瘋狂參與政治,又有些人埋首精研繪畫理論—期待自己成為一種新的繪畫風潮的獨領風騷者。
那一段日子裡,我大抵是很勤懇的在習畫的,整個藝術領域在我眼前拓展,各種畫派、各種主義、各種可能性,令人眼花撩亂。而超現實主義那種帶著寂寞的晦澀詩意,尤其吸引我。「超現實主義」是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詩人與畫家利用不同創作的方式,相互激勵而成的畫派。我喜歡這種內容的創作,因為這種表現方式,讓我對文字的濃厚情感與繪畫的表達技巧上,可以同時得到滿足。
我一方面像剛開了眼界似地興奮著,要把這眼前的景致盡收眼底,另一方面卻被一種未曾經驗的無聊漸漸襲上身,這是一種寂寞的感覺。我常常想,這無聊與寂寞是怎麼來的?雖然這樣想著,卻也不特別去追究,日子就這麼過去,後來也因為忙了,無聊彷彿減少了,但寂寞,卻一日日坐大起來……
一個新的章節——成為一個插畫家
人生的變數既難掌握,卻又那麼地宿命。二十幾歲初出大學校園的我,一路走來,幾經波折跌宕,再回顧時,我已坐在紐約家裡的書桌前,二十年的光陰也已飛逝。初離校門,父親驟逝,母親罹癌,我離開了生長的地方,來到美國,一個陌生的國土,陪伴在美國就醫的母親。沒有了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語言,像拔了根似的,也讓自己飛離了軌。母親過世後,孑然一身。原有的那日漸坐大的寂寞感,更是盤據了一身。沒有一個窩心的住處,也沒有足夠的畫具與空間,每日只能以簡單的紙筆寫點感覺,畫點心境,聊以寄情。直到某些日子裡,在不經意的冥想中,偶然與那個小小的自己不期而遇—身披五彩繽紛的羽裳,飛著四處造訪的小女孩。猛然意識到:原來自己多麼懷念那些拾著短短蠟筆,大膽又盡興地畫著童話世界的日子啊!於是我又開始畫起一個個小小的故事——在這裡,我接觸到自己生命的源頭,看到幼小年輕的自己,對陌生的世界感到新鮮與好奇……。我彷彿也看見自己在縮小……縮小……對這片新踏上的國土開始感覺新鮮與好奇。
我喜歡畫畫、喜歡故事、喜歡用畫來說故事、喜歡文字與繪畫結合時剎那間蹦出的火花。是什麼力量不斷驅使我去尋找故事,並且去把它畫出來,大概就是這個火花迸裂時的驚艷吧!
八○年代中期,我抱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傻勁隻身飛赴紐約——這個全美最大的都市,也是世界經濟、貿易、文化、藝術的中心。我有一個夢想要落實,想要成為一個童書插畫家。我感覺自己正披上那張斑斕的彩衣,細心地整理著羽翼,等待振翅而飛。
雖是初生之犢,但也不能忘記先做功課——尋找一個插畫經紀人,是我當前的課題。
我提著大大的作品夾,穿梭在曼哈段高樓林立的市區內。紐約這個大都會,雖不如巴黎的浪漫、羅馬的古趣盎然,但它有一股朝氣,像是一塊磁鐵,不僅吸引了來訪的旅客,更讓年輕人蜂擁雲集,只為了在這塊試金石之上,把自己的理想磨出光芒來。我在短短的數週內,拜訪了幾家經紀公司,與幾位經紀人在晤談後,順利地獲得一位有二十多年經紀人經驗的女士的青睞。在她的公司裡,經營了二十多位名氣大小不一的插畫家,她邀請我加入她的行列,我們隨後便開始迄今第十八年的合作關係。
故事至此,我好像順利地開啟了「童書插畫家」之鑰,一路走來也似乎順理成章、毫無坎坷,其實這一切,多要歸功在事前的充分準備,市場的接受力,再加上一點運氣。八○年中期以後,美國市場經濟保持景氣,童書出版業也日益蓬勃,但投入的創作者人數尚未激增。當時我二十幾歲的年輕生命,一心嚮往投入這個創作的行列,成為出版事業的一員。
在事前準備方面,當然「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既然志在出版業,對出版事業就要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幾十年前,在網際網路完全不發達的年代,藝術家尋找資訊的地方,大概只有靠圖書館、書店或報章雜誌了!那時一個小小故事,至今記憶猶新:記得仍每天翻閱報紙的年代嗎?我就是在那個年代,不經意在一份華人報紙上讀到一則很有意思的啟事,大致上說,市民們如有「任何」問題,可以致電市立圖書館員詢問,這不禁讓我想到一部老電影,裡面的男女主角分別由凱薩琳‧赫本和史賓賽‧區賽飾演,他們是兩名天才圖書館員,專門接聽市民電話,解答任何疑難雜症,不記得電影名稱了,但是那則新聞讓我好奇地拿起電話,試想會不會有個天才圖書館員在聽筒的另一端,能否解答我的疑難雜症……對啦!那是中文專線,沒有凱薩琳‧赫本,而是一位溫柔如母親的女性回覆了我的需求,感謝她,因為就是她告知,一本在美國各個市立圖書館都可參閱的資料書籍《文學市場》(Literary Market Place,簡稱LMP),刊登了有所有美國出版社的名稱、地址、電話,以及編輯的姓名。年輕人想要尋找適合的出版社,可從這裡去察訪、聯繫,因為儘管每個出版社的行事風格不一,但一般而言,「編輯」是想入行的插畫家及作家該去聯繫的對象。本書並刊登有一些經紀公司的資料供參考,我當時正是完全拜此書之賜。另一本名為《Writer’s Market》的書,也有類似的參考價值。
當然今天的年輕人,哪需要打電話詢問?哪需要溫柔如母親般的建議?綜上至下所述,都是一個上個世代的退休插畫家的喃喃自語。然而我是這麼想的,這本書,也不是一本工具書,更不涉及理論,所以也不是一本理論專書,輕輕鬆鬆地,只是我的經驗分享罷了!
在此一提美國的經紀人制度:
在出版業的經紀人代表插畫家,是與出版社溝通的橋梁,他們了解出版業的趨勢,和出版社也有一定的良好關係。所以在商談合約時,經紀人通常能為畫家爭取到較好的條件,當然經紀人會索取一定比例的費用,一般合理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在此要打破一個迷思,就是編輯或許會多花心思瀏覽較有威望的經紀人所推薦的畫家,但這並不必然是工作到手的保證。一切結果仍取決於這個畫家作品本身的好壞,以及作品風格是否契合編輯的喜好。
再談一談美國的出版社如何尋找一位理想的插畫家:
當出版社有新書出版的計畫時,編輯部門會率先考慮一位他們喜歡的,或熟悉其作品的畫家,並與他(或她)聯繫出版的可能性。有時候編輯會參考藝術指導的意見,啟用一位新人(出版社常會有不少年輕畫家的作品影印資料存檔)。當候選人的範圍縮小到二、三人時,編輯或許會要求畫家們提供一張針對這個故事而作的小畫(sample),然後再進行最後的挑選。一旦決定了一位插畫家,合作關係便從此開始——包括合約的討論,工作進度的安排,以及正式工作內容的進行等等。
再囉嗦一下:出版事業畢竟是人際合作的事業,當編輯選擇一個畫家時,此人的個性人格特質有時也是他們考慮合作與否的部分因素,假若是一個新人,編輯們自然會多花一些時間指引與開導,但畫家本身也該儘早吸收專業知識,以便應付這個極其專業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