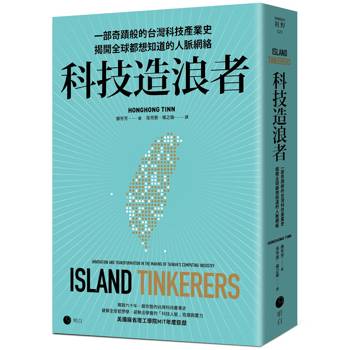第一章 「再續前緣」──交通大學在台復校
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的那個夜晚, 在台北的「鐵路招待所」(Taiwan Railway Club),三百名交通大學的校友一同慶祝他們母校五十五年校慶。一九五二年的這次聚會是交大校友在台灣的第三次聚會,會中大家喝著茶、吃著點心,接待櫃台則覆蓋了一張大大的宣紙,上面印了一個壽字,來賓紛紛在紙上簽名。來賓中年紀最大的是一九○三年入校的七十歲校友,將他的名字簽在壽字上,象徵他眼中這所大學偉大的歷史,以及校友們歷經戰火仍得平安。當天的聚會邀請也刊登在兩大報上。恰好其中一家報紙的副董事長正是交大校友。其他出席的校友包括來自工程界的各個工程師,例如鐵路、電訊、煉油、銅礦開採、肥料、鋼鐵與電力。除了這些工程師,來賓還有位居中華民國政府重要位置的官員,以及一位前杭州市長(杭州是中國千年來最富庶的城市之一)。1這次聚會頗為轟動。
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一八九六年成立於上海,是清朝時期最早成立的大學,負有改造並現代化教育系統的任務。初期南洋公學還有中學。而其教學則著重於鐵道、郵政與電報,希望藉由引進現代科技教育,讓中國能與西方、日本帝國主義列強對抗。一九一一年清朝結束,中華民國成立,十年後南洋公學合併了唐山、北京、上海幾所新的高校,成為交通大學。而中華民國交通部,因為「交通」一詞與道路交通、傳播、運輸有關,故而得名。另外,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也常被認作交大校友,由於他自幼畢業於南洋模範中學,而且這所學校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一度隸屬於南洋公學,因此張忠謀與交通大學的淵源很深。
以「東方MIT」著稱的交通大學,在二次大戰前的中國,是少數專注於訓練關鍵工程領域專家的高等教育機構。根據一九三○年七月一日的《中國報》(China Press)的報導,交大上海校區有四十一位鐵道管理畢業生、二十二位機械工程畢業生,還有五十二位從工程學院畢業。在此同時,交大的北平小區有六十一位學生畢業於鐵道管理學院,三十二位自唐山的土木工程學院取得學位。這些畢業生都在「著名的工廠」、「顯要公司」大展鴻圖。那時候,交大的董事長與副董事長就是當時鐵路部的部長與副部長。這兩位促成交大的畢業生到各個通訊與工業機構,進行學士後的訓練或直接任職。
後來有上千位交大校友在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跟著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到了台灣。
當時國民政府被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打得節節敗退,約有一百二十萬的中國民眾與軍人隨著蔣介石撤退到台灣,這批交大校友也在其中。台灣在一九四五年時人口只約六百二十萬人,大部分只會說台語和日語,這一百二十萬新移民湧入,無論在人數上或文化上都帶來極大衝擊。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領了交大各學院,將之變成共產中國高等教育中樞。在台灣的交大校友失去與母校的聯繫,他們既無法再拜訪母校各地校園,或在其中舉行任何活動。同時因為大陸政權與蔣介石政府處於交戰狀態,台灣的交大校友也不被允許與留在中國的交大教職人員或校友聯繫。
在台灣安居落戶後,台灣的交大校友開始建立彼此的聯繫。這些人都是在政府擔任行政要員與科技官僚,或各領域的工程師與科學家。從一九四九年開始,校友會的執行委員會就開始固定聚會。而第一次校友大會可能在一九五○年就舉行了。除了台灣,在美國、日本與其他地區的校友聚會也很快展開。一九五二年四月,交大校友刊物《友聲》創刊,這是一份每月或每兩月固定發行於台灣和其他地區的校友通訊。當中會分享個別校友動態,回顧他們在逃離中國之前的生活。那些二次大戰前的校園生活回憶,尤其是運動、人際間的聯繫,對於移民來到台灣展開新生活的校友,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塊。日子久了,他們也開始交換他們在科學或工程專業領域的想法,對於科技計畫與工程教育發表看法,同時對於他們拜訪過的其他國家的物質建設與工業發展提出觀察心得。
一九五三年校友會規模更為擴大,又在同一個場地舉辦了活動,參與人數多了一倍,大家一起大啖豬排飯。校友受邀觀賞好幾場表演同樂,也有許多室內小組活動,鐵路招待所的戶外花園還有古箏表演。花園中點亮了多盞燈籠,裝飾了美麗的季節花朵。一位衣冠楚楚的校友還表演了單口相聲。相聲表演結束還在現場販售男女胸花,為一位剛失去視力的校友募款。晚上八點鐘,校友們齊聚猜燈謎,有十位盛裝的女校友與校友的女性家屬,舉著燈籠「妝點」舞台,帶動節慶的氣氛。所謂「妝點」,是校友刊物編輯的用詞。這樣的性別組合,恰好呼應了另一個場景:當晚稍早,所有的女性校友都被要求擔任櫃台接待,在俱樂入口處登記到場的來賓。為了當晚的紀念品與猜燈謎的禮物,有些校友先前也負責去找有錢的企業來贊助。這些紀念品和禮物,由一台五噸卡車載到會場,裡頭有牛肉、海鮮、鳳梨罐頭,醬油、茶葉、肥皂、攜帶型煤油爐、蠟燭、打火機丁浣填充液、殺蟲劑DDT與BHC、雜誌、鋁凳、男性內衣、橡膠鞋……都是一九五○年代台灣人眼中珍貴的民生物資。
這場為散落在外的交大校友所舉辦的盛會,校友們只要一想到已遠離的母校與家園,心裡不由得一陣鼻酸。而當校友們在策畫這場盛會之時,有一位校友樂觀認為下一年的校友會將在中國舉辦。因為蔣介石在一九五三年宣稱,他將反攻大陸、收復失土。令校友們失望的是,接下來一年,以及之後的幾十年,校友會舉辦的地點都不曾是中國而是台灣。大部分的校友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政府允許人民回大陸探親,才有機會再訪故土。也許有人會把這跟東德居民做類比,當初東德人在冷戰時期也是無法自由旅行去西德探親。而南北韓之間的旅行,直到今日仍然嚴格受限。
校友會也成為交大校友發展個人與專業連結的重要場合,他們對於貢獻台灣發展鐵路、電訊、礦業與其他公共建設的興趣,也在當中找到出口。散落各地的交大校友最終在台灣建立起母校的榮光,致力於工程與電信的發展。他們促成電子計算機運算技術與電腦產業的建立,又帶動產業的興盛。一九六○年代透過聯合國科技支援計畫贊助的台灣首兩台主機電腦,就設置在復校的交大裡面。國營事業的工程師、大學的學者、軍方人員,以及台灣各地即將成為電腦使用者的人,都被吸引到交通大學的校園內,來學習電子數位運算。那些選修了相關課程的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成為台灣第一代電腦工程師與學者。
本章要解析交大校友如何在冷戰的環境中找到機會,促進他們的專業與工業發展。台灣交大校友動員了他們在島上的政治關係,也從在美國校園與企業的海外校友引進資源,於一九五八年重開校園,成為一個訓練冷戰時期電訊工程師的「新場所」。他們為交大的「有用之處」找到兩種說法:首先,這些校友表示他們熱切想參與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對抗的戰爭準備。他們聲稱新的交大對於訓練將來「抵抗」中共的工程專家非常重要。不過後來當他們想要推動政府撥款讓交大在台灣復校,卻沒有辦法從蔣介石政府得到足夠的財力支持,因為蔣把大部分的經費都投入到直接的軍事建設計畫中,覺得這樣對於光復大陸比較有實質的助益。這群校友後來槓桿出足夠的資源,透過設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成功吸引了復校所需的資源。他們能夠做成,是因為強調「電子」研究來凸顯學校的重要性,把電子工程領域的重要性跟原能相提並論,高倡這兩個領域在台灣國防與捍衛冷戰下「自由世界」資本陣營,具有關鍵角色。一九五六年的校友年會刻意創造了電子科學與原能科學領域的雙強對話。
這群校友想要復校的動機有好幾重。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效忠蔣介石,所以他們才會隨他來到台灣。這群人覺得他們有義務保護台灣免受敵人的滲透。除了愛國情懷,這些工程師與技術官僚在投入冷戰期國防的同時,也逐步提升了台灣的電訊專業能力。他們能成功讓一所成立於中國大陸的大學在台灣復校,反映了他們能重新定位台灣的戰略地位,又能夠連結台灣與海外校友的關係,在島內與海外都建立起專家網絡。
細說往事,重現交大過去榮光的挑戰
從交大校友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母校在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到台灣」時就「停止」運作,而政府應該盡快讓交大在台「復校」。一九五二年四十七歲的水運專家與官員王洸指出:交大若能復校,對於收復中國大陸將有極大的貢獻,對後續的國家重建也有利。復校後的大學可以為國家目標訓練許多專家。王認為,校友會應該準備在台灣重啟交大,因為敵對的「共匪」已開始在高等教育注重通訊科技。中國共產黨就在不久前接收交大上海校區,又擴張了北京與唐山分部,並且將武昌的海軍學校從職校升格為大專學院。王的倡議可比擬一九四○年代美國協助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在西柏林重建。自由大學的設立是為了要抗衡著名的腓特烈─威廉大學(Frederick WilliamUniversity,該校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被稱為柏林洪堡大學),當時位於東柏林的腓特烈─威廉大學戰後已落入共產黨控制。不過,交大又經過好一段時間,直到一九五八年六月才復校,比德國自由大學的設立慢了許多。
雖然王的倡議得到交大校友的熱烈回響,但是政府當下認為財政困難而作罷。然而,一九五三年交大校友會的執行委員會,受到王提議的鼓舞,熱烈討論了在台灣復校的方案。委員會中有多位政府菁英,他們指出,既然交通部正在對鐵路局、通訊與海關人員進行訓練,
也可以考慮把目前的訓練課程從政府人員擴大到大專院校。受完訓練教育的學子可透過交大的名義授予學位。交通部與教育部負責交大復校頭幾年的經費。在中華民國的政府架構中,教育部監督各大學的運作,並分配立院通過的經費給學校。交大校友會的執行委員會提交了一項議案到該年的中國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與立法院。不過立法院拒絕了項法案,因為可能負擔不起長期的經費。錢不夠用,是因為要支應軍方重新奪回大陸的布局。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這段期間,交大校友知道有戰爭準備,也知道他們在對抗中共這場戰事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校友們強調,如果蔣介石要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收復中國大陸,交通通訊領域的工程師,包括鐵路、公路、電力、郵政、水利輸送等等的需求量都會很大。要發展這些領域,交通大學在台灣運營、訓練更多工程師,就很重要。一九五三年八月,當時交通部次長錢其琛,評估了工程師未來幾年可能面臨短缺。他表示,對於通訊交通工程師的需求,很快就會超越當時台灣所能提供四萬八千三百名的工程師職缺。根據他的數據,每年每千名工程師中會有三人因為退休或死亡離開職位,另外會有三人自請離職或因為合約到期而離開。到戰時還有部分工程人員要入伍。雖然雇主可以提升他們還在崗位上的工程師的表現,要增加相關領域工程師的人數,仍然需要依靠教育系統。
一九五三年五月,交大校友會執委會再度碰頭。他們開了會議集思廣益,討論如何說服政府來支持交大復校。錢其琛認為校友會應該可以從教育部要到所需要的支持。當時新生日報的副社長也呼籲,要提高公眾對於訓練通訊交通領域專家與管理人才的意識。任職於鐵路局的校友葉佩蘭則呼籲,復校後可招收更多女性。到了九月,校友執委會再度聚首,提議三個在中國石油、台電與交通部任職高階主管的校友,去找立法院院長和副院長,重申培育更多工程人員的重要性。
從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八年,有三所大學各持不同理由在台灣復校。一九五四年,東吳大學(成立於蘇州的衛理教派私立大學),說服教育部讓東吳在台灣復校,因為他們已經籌到足夠復校的款項。該校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就以開設公開短期訓練課程來籌足自己的經費。復校後就設立法律、政治、經濟、會計、外語的大學部學位。
一九五四年六月,經由政治大學校友的陳情,教育部也得到立法院同意讓政大復校。政治大學的前身是由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七年建立於南京的中央黨校,培育出不少黨國菁英。蔣介石是第一任校長。該校在一九三二年開設大學部。一九四九年四月,五百位中央黨校校友在台北團聚。龐大的與會人數顯示該校許多校友都跟隨蔣到了台灣。蔣在一九五四年七月指派了一個委員會,其中包括他兒子蔣經國,準備復校事宜。該年,國立政治大學先設立了公共行政、公民教育、新聞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政大對於國民黨政府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而其正統性也是復校的關鍵。
除了著重社會科學的教育,蔣介石對於發展核能也很有興趣,認為有望發展核子武器。於是他下令清華大學復校,以便在相關領域進行研究。清華大學是二次大戰前著名的中國大學,其前身是清華學堂,設立於一九一一年。當時美國退回庚子賠款,清廷便把這筆款項用來興辦教育,故而設立該學堂。另外,二戰前的清華大學也設置了社會科學、人文、自然科學與工程等學位。一九五四年,台灣立法院通過立法,設立原子能委員會。一九五五年,蔣介石簽定了一項雙邊條約,內容是與美國共同為和平用途發展核能。蔣接著面見國防部長,決定要購入一台核能反應爐,並將之設置在清華大學裡面。物理學家梅貽琦,曾經擔任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清大校長,這次從美國被徵召回台,負責購買教學與研究用的反應爐,並且規劃大學部的核能系。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立法院設立了委員會,正式著手準備清大復校。參與清大復校的交大校友中還有李熙謀。一九一八年,他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獲得電子工程碩士學位,也是對日抗戰時期交大的院長之一。一九五五年,他成為立法院核能委員會的一員,並在八月出席了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屆核能和平使用國際年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Atomic Energy)。
在蔣介石來到台灣之前,台灣其實已經有提供電子工程教育的大學了。甲午戰爭後,清廷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就被日本統治,從一八九五年開始,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而在日治時期,有三間學校提供電子工程教育的課程:台北帝國大學、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以及台北工業學校。
一九二八年,日本在台設立了台北帝國大學,這是日本設立九所帝國大學當中的一所。
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把台北帝大改名成為國立台灣大學,在此之前,台大是日治台灣時期唯一的一所大學。台大的師資遍及各領域,包含文理、科學、醫學等。台灣大學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工程方面的科系才開始招收學生,包含電子工程的大學生。根據歷史學者葉碧苓的說法,台灣之所以遲遲無法設立工程方面的科系,是因為日本在一九三○年代以前,只想利用殖民地台灣來對日本本土提供農業方面的資源。
一九五二年四月八日的那個夜晚, 在台北的「鐵路招待所」(Taiwan Railway Club),三百名交通大學的校友一同慶祝他們母校五十五年校慶。一九五二年的這次聚會是交大校友在台灣的第三次聚會,會中大家喝著茶、吃著點心,接待櫃台則覆蓋了一張大大的宣紙,上面印了一個壽字,來賓紛紛在紙上簽名。來賓中年紀最大的是一九○三年入校的七十歲校友,將他的名字簽在壽字上,象徵他眼中這所大學偉大的歷史,以及校友們歷經戰火仍得平安。當天的聚會邀請也刊登在兩大報上。恰好其中一家報紙的副董事長正是交大校友。其他出席的校友包括來自工程界的各個工程師,例如鐵路、電訊、煉油、銅礦開採、肥料、鋼鐵與電力。除了這些工程師,來賓還有位居中華民國政府重要位置的官員,以及一位前杭州市長(杭州是中國千年來最富庶的城市之一)。1這次聚會頗為轟動。
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一八九六年成立於上海,是清朝時期最早成立的大學,負有改造並現代化教育系統的任務。初期南洋公學還有中學。而其教學則著重於鐵道、郵政與電報,希望藉由引進現代科技教育,讓中國能與西方、日本帝國主義列強對抗。一九一一年清朝結束,中華民國成立,十年後南洋公學合併了唐山、北京、上海幾所新的高校,成為交通大學。而中華民國交通部,因為「交通」一詞與道路交通、傳播、運輸有關,故而得名。另外,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也常被認作交大校友,由於他自幼畢業於南洋模範中學,而且這所學校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一度隸屬於南洋公學,因此張忠謀與交通大學的淵源很深。
以「東方MIT」著稱的交通大學,在二次大戰前的中國,是少數專注於訓練關鍵工程領域專家的高等教育機構。根據一九三○年七月一日的《中國報》(China Press)的報導,交大上海校區有四十一位鐵道管理畢業生、二十二位機械工程畢業生,還有五十二位從工程學院畢業。在此同時,交大的北平小區有六十一位學生畢業於鐵道管理學院,三十二位自唐山的土木工程學院取得學位。這些畢業生都在「著名的工廠」、「顯要公司」大展鴻圖。那時候,交大的董事長與副董事長就是當時鐵路部的部長與副部長。這兩位促成交大的畢業生到各個通訊與工業機構,進行學士後的訓練或直接任職。
後來有上千位交大校友在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跟著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到了台灣。
當時國民政府被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打得節節敗退,約有一百二十萬的中國民眾與軍人隨著蔣介石撤退到台灣,這批交大校友也在其中。台灣在一九四五年時人口只約六百二十萬人,大部分只會說台語和日語,這一百二十萬新移民湧入,無論在人數上或文化上都帶來極大衝擊。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領了交大各學院,將之變成共產中國高等教育中樞。在台灣的交大校友失去與母校的聯繫,他們既無法再拜訪母校各地校園,或在其中舉行任何活動。同時因為大陸政權與蔣介石政府處於交戰狀態,台灣的交大校友也不被允許與留在中國的交大教職人員或校友聯繫。
在台灣安居落戶後,台灣的交大校友開始建立彼此的聯繫。這些人都是在政府擔任行政要員與科技官僚,或各領域的工程師與科學家。從一九四九年開始,校友會的執行委員會就開始固定聚會。而第一次校友大會可能在一九五○年就舉行了。除了台灣,在美國、日本與其他地區的校友聚會也很快展開。一九五二年四月,交大校友刊物《友聲》創刊,這是一份每月或每兩月固定發行於台灣和其他地區的校友通訊。當中會分享個別校友動態,回顧他們在逃離中國之前的生活。那些二次大戰前的校園生活回憶,尤其是運動、人際間的聯繫,對於移民來到台灣展開新生活的校友,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塊。日子久了,他們也開始交換他們在科學或工程專業領域的想法,對於科技計畫與工程教育發表看法,同時對於他們拜訪過的其他國家的物質建設與工業發展提出觀察心得。
一九五三年校友會規模更為擴大,又在同一個場地舉辦了活動,參與人數多了一倍,大家一起大啖豬排飯。校友受邀觀賞好幾場表演同樂,也有許多室內小組活動,鐵路招待所的戶外花園還有古箏表演。花園中點亮了多盞燈籠,裝飾了美麗的季節花朵。一位衣冠楚楚的校友還表演了單口相聲。相聲表演結束還在現場販售男女胸花,為一位剛失去視力的校友募款。晚上八點鐘,校友們齊聚猜燈謎,有十位盛裝的女校友與校友的女性家屬,舉著燈籠「妝點」舞台,帶動節慶的氣氛。所謂「妝點」,是校友刊物編輯的用詞。這樣的性別組合,恰好呼應了另一個場景:當晚稍早,所有的女性校友都被要求擔任櫃台接待,在俱樂入口處登記到場的來賓。為了當晚的紀念品與猜燈謎的禮物,有些校友先前也負責去找有錢的企業來贊助。這些紀念品和禮物,由一台五噸卡車載到會場,裡頭有牛肉、海鮮、鳳梨罐頭,醬油、茶葉、肥皂、攜帶型煤油爐、蠟燭、打火機丁浣填充液、殺蟲劑DDT與BHC、雜誌、鋁凳、男性內衣、橡膠鞋……都是一九五○年代台灣人眼中珍貴的民生物資。
這場為散落在外的交大校友所舉辦的盛會,校友們只要一想到已遠離的母校與家園,心裡不由得一陣鼻酸。而當校友們在策畫這場盛會之時,有一位校友樂觀認為下一年的校友會將在中國舉辦。因為蔣介石在一九五三年宣稱,他將反攻大陸、收復失土。令校友們失望的是,接下來一年,以及之後的幾十年,校友會舉辦的地點都不曾是中國而是台灣。大部分的校友一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政府允許人民回大陸探親,才有機會再訪故土。也許有人會把這跟東德居民做類比,當初東德人在冷戰時期也是無法自由旅行去西德探親。而南北韓之間的旅行,直到今日仍然嚴格受限。
校友會也成為交大校友發展個人與專業連結的重要場合,他們對於貢獻台灣發展鐵路、電訊、礦業與其他公共建設的興趣,也在當中找到出口。散落各地的交大校友最終在台灣建立起母校的榮光,致力於工程與電信的發展。他們促成電子計算機運算技術與電腦產業的建立,又帶動產業的興盛。一九六○年代透過聯合國科技支援計畫贊助的台灣首兩台主機電腦,就設置在復校的交大裡面。國營事業的工程師、大學的學者、軍方人員,以及台灣各地即將成為電腦使用者的人,都被吸引到交通大學的校園內,來學習電子數位運算。那些選修了相關課程的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成為台灣第一代電腦工程師與學者。
本章要解析交大校友如何在冷戰的環境中找到機會,促進他們的專業與工業發展。台灣交大校友動員了他們在島上的政治關係,也從在美國校園與企業的海外校友引進資源,於一九五八年重開校園,成為一個訓練冷戰時期電訊工程師的「新場所」。他們為交大的「有用之處」找到兩種說法:首先,這些校友表示他們熱切想參與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對抗的戰爭準備。他們聲稱新的交大對於訓練將來「抵抗」中共的工程專家非常重要。不過後來當他們想要推動政府撥款讓交大在台灣復校,卻沒有辦法從蔣介石政府得到足夠的財力支持,因為蔣把大部分的經費都投入到直接的軍事建設計畫中,覺得這樣對於光復大陸比較有實質的助益。這群校友後來槓桿出足夠的資源,透過設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成功吸引了復校所需的資源。他們能夠做成,是因為強調「電子」研究來凸顯學校的重要性,把電子工程領域的重要性跟原能相提並論,高倡這兩個領域在台灣國防與捍衛冷戰下「自由世界」資本陣營,具有關鍵角色。一九五六年的校友年會刻意創造了電子科學與原能科學領域的雙強對話。
這群校友想要復校的動機有好幾重。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效忠蔣介石,所以他們才會隨他來到台灣。這群人覺得他們有義務保護台灣免受敵人的滲透。除了愛國情懷,這些工程師與技術官僚在投入冷戰期國防的同時,也逐步提升了台灣的電訊專業能力。他們能成功讓一所成立於中國大陸的大學在台灣復校,反映了他們能重新定位台灣的戰略地位,又能夠連結台灣與海外校友的關係,在島內與海外都建立起專家網絡。
細說往事,重現交大過去榮光的挑戰
從交大校友的角度來看,他們的母校在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到台灣」時就「停止」運作,而政府應該盡快讓交大在台「復校」。一九五二年四十七歲的水運專家與官員王洸指出:交大若能復校,對於收復中國大陸將有極大的貢獻,對後續的國家重建也有利。復校後的大學可以為國家目標訓練許多專家。王認為,校友會應該準備在台灣重啟交大,因為敵對的「共匪」已開始在高等教育注重通訊科技。中國共產黨就在不久前接收交大上海校區,又擴張了北京與唐山分部,並且將武昌的海軍學校從職校升格為大專學院。王的倡議可比擬一九四○年代美國協助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在西柏林重建。自由大學的設立是為了要抗衡著名的腓特烈─威廉大學(Frederick WilliamUniversity,該校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被稱為柏林洪堡大學),當時位於東柏林的腓特烈─威廉大學戰後已落入共產黨控制。不過,交大又經過好一段時間,直到一九五八年六月才復校,比德國自由大學的設立慢了許多。
雖然王的倡議得到交大校友的熱烈回響,但是政府當下認為財政困難而作罷。然而,一九五三年交大校友會的執行委員會,受到王提議的鼓舞,熱烈討論了在台灣復校的方案。委員會中有多位政府菁英,他們指出,既然交通部正在對鐵路局、通訊與海關人員進行訓練,
也可以考慮把目前的訓練課程從政府人員擴大到大專院校。受完訓練教育的學子可透過交大的名義授予學位。交通部與教育部負責交大復校頭幾年的經費。在中華民國的政府架構中,教育部監督各大學的運作,並分配立院通過的經費給學校。交大校友會的執行委員會提交了一項議案到該年的中國國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與立法院。不過立法院拒絕了項法案,因為可能負擔不起長期的經費。錢不夠用,是因為要支應軍方重新奪回大陸的布局。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這段期間,交大校友知道有戰爭準備,也知道他們在對抗中共這場戰事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校友們強調,如果蔣介石要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收復中國大陸,交通通訊領域的工程師,包括鐵路、公路、電力、郵政、水利輸送等等的需求量都會很大。要發展這些領域,交通大學在台灣運營、訓練更多工程師,就很重要。一九五三年八月,當時交通部次長錢其琛,評估了工程師未來幾年可能面臨短缺。他表示,對於通訊交通工程師的需求,很快就會超越當時台灣所能提供四萬八千三百名的工程師職缺。根據他的數據,每年每千名工程師中會有三人因為退休或死亡離開職位,另外會有三人自請離職或因為合約到期而離開。到戰時還有部分工程人員要入伍。雖然雇主可以提升他們還在崗位上的工程師的表現,要增加相關領域工程師的人數,仍然需要依靠教育系統。
一九五三年五月,交大校友會執委會再度碰頭。他們開了會議集思廣益,討論如何說服政府來支持交大復校。錢其琛認為校友會應該可以從教育部要到所需要的支持。當時新生日報的副社長也呼籲,要提高公眾對於訓練通訊交通領域專家與管理人才的意識。任職於鐵路局的校友葉佩蘭則呼籲,復校後可招收更多女性。到了九月,校友執委會再度聚首,提議三個在中國石油、台電與交通部任職高階主管的校友,去找立法院院長和副院長,重申培育更多工程人員的重要性。
從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八年,有三所大學各持不同理由在台灣復校。一九五四年,東吳大學(成立於蘇州的衛理教派私立大學),說服教育部讓東吳在台灣復校,因為他們已經籌到足夠復校的款項。該校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就以開設公開短期訓練課程來籌足自己的經費。復校後就設立法律、政治、經濟、會計、外語的大學部學位。
一九五四年六月,經由政治大學校友的陳情,教育部也得到立法院同意讓政大復校。政治大學的前身是由中國國民黨於一九二七年建立於南京的中央黨校,培育出不少黨國菁英。蔣介石是第一任校長。該校在一九三二年開設大學部。一九四九年四月,五百位中央黨校校友在台北團聚。龐大的與會人數顯示該校許多校友都跟隨蔣到了台灣。蔣在一九五四年七月指派了一個委員會,其中包括他兒子蔣經國,準備復校事宜。該年,國立政治大學先設立了公共行政、公民教育、新聞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政大對於國民黨政府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而其正統性也是復校的關鍵。
除了著重社會科學的教育,蔣介石對於發展核能也很有興趣,認為有望發展核子武器。於是他下令清華大學復校,以便在相關領域進行研究。清華大學是二次大戰前著名的中國大學,其前身是清華學堂,設立於一九一一年。當時美國退回庚子賠款,清廷便把這筆款項用來興辦教育,故而設立該學堂。另外,二戰前的清華大學也設置了社會科學、人文、自然科學與工程等學位。一九五四年,台灣立法院通過立法,設立原子能委員會。一九五五年,蔣介石簽定了一項雙邊條約,內容是與美國共同為和平用途發展核能。蔣接著面見國防部長,決定要購入一台核能反應爐,並將之設置在清華大學裡面。物理學家梅貽琦,曾經擔任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清大校長,這次從美國被徵召回台,負責購買教學與研究用的反應爐,並且規劃大學部的核能系。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立法院設立了委員會,正式著手準備清大復校。參與清大復校的交大校友中還有李熙謀。一九一八年,他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獲得電子工程碩士學位,也是對日抗戰時期交大的院長之一。一九五五年,他成為立法院核能委員會的一員,並在八月出席了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屆核能和平使用國際年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Atomic Energy)。
在蔣介石來到台灣之前,台灣其實已經有提供電子工程教育的大學了。甲午戰爭後,清廷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就被日本統治,從一八九五年開始,到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而在日治時期,有三間學校提供電子工程教育的課程:台北帝國大學、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以及台北工業學校。
一九二八年,日本在台設立了台北帝國大學,這是日本設立九所帝國大學當中的一所。
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把台北帝大改名成為國立台灣大學,在此之前,台大是日治台灣時期唯一的一所大學。台大的師資遍及各領域,包含文理、科學、醫學等。台灣大學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工程方面的科系才開始招收學生,包含電子工程的大學生。根據歷史學者葉碧苓的說法,台灣之所以遲遲無法設立工程方面的科系,是因為日本在一九三○年代以前,只想利用殖民地台灣來對日本本土提供農業方面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