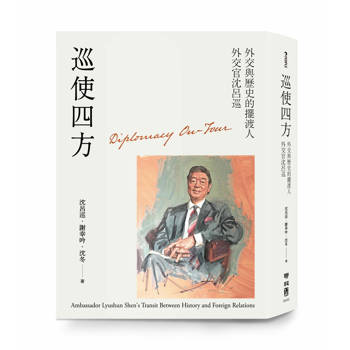第二章 揚帆啟航、北美時期
沈呂巡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外交。
一生只牽掛一個地方,就是外交部。
一生最在乎一種關係,就是外交關係,其中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又是他心頭重中之重,臺北與華府的風吹草動,沈呂巡絕不錯過。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是沈呂巡外交生涯第一天,他向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報到,擔任諮議。第二章〈揚帆啟航、北美時期〉,我們看外交教父錢復破格拔擢的沈呂巡,全心投入對美國國會外交與臺美關係,也看沈呂巡追尋國父的足跡,從美國丹佛到英國倫敦,一路熱血澎湃。
我們專注於沈呂巡關注國家主權、解讀臺美關係脈絡。重點包括:
一、美國對臺灣法律地位的認定;
二、美國國務卿或總統,在不同時空稱呼我國為「占領當局」或「自治實體」;
三、被視為最反共的美國總統雷根,對於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設立「聯絡處」的模式,也因中共反對而退讓;
四、認清三十年來最友我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本質是「外交現實主義者」;
五、與美國斷交後的中華民國,如何繼續保有相當多的法理空間與相當的國際法人資格;
六、美國對臺灣主權問題「不採立場」(takes no position on the question of Taiwan’s sovereignty.)。
從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一直到沈呂巡二○二三年一月六日病逝,老沈無時無刻都在關注美國與我關係如何突破,如何能夠在沒有邦交的情況下,爭取主權象徵的、官方意義的、實質關係的進展。
位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駐美代表處,是老沈三十五年外交生涯的起點與終點,從諮議到駐美代表、從《八一七公報》的損害控管到我與美國斷交三十六年後首次在雙橡園升旗,沈呂巡為外交戮力穿梭的身影,不只華府,也包括了臺北、堪薩斯、日內瓦、布魯塞爾、倫敦等地,各自繽紛,精采非凡。
呂巡時論、回憶外交
由當年杜勒斯秘密證詞看中美協防條約——兼談條約即將失效時我們應有的認識和做法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聯合報》二版
《中美協防條約》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由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及我國外長葉公超簽字訂定,翌年元月由美政府提交參院審議,二月七日杜勒斯親赴參院外交委員會祕密院會作證,並接受質詢。此一證詞及答問紀錄一直列為機密,至去年四月始予公開,載於參院《外交委員會歷史文獻集》(Historical Series)第七集三○九至三五六頁。我們雖不敢說杜氏當時對參議員們完全直言無隱,但在祕密院會中,尤其被許多大牌議員追問之下,杜氏所作的陳述應較其他官方文件更為坦白可信,是則我們可進一步了解美國當初締結此約的各項考慮及對我政府之觀感等等,對探討近三十年中美關係之癥結當不無助益,尤其在此約即將終止的今天,此種了解或對今後對美外交工作亦有所啟發。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那次祕密會議出席議員共十三人,其中有我們熟知的大牌議員傅爾布萊特、史巴克曼、後擔任過副總統的韓福瑞、現任美駐日大使的曼斯菲德等等。可異者當時最支持我們的諾蘭參議員(亦外委會委員,當時被人戲稱為「來自臺灣的參議員」)卻未出席。由於原紀錄頗長,本文將先就杜氏對下列題目之看法摘要記述,再作一綜合評論。
訂約之經過及原因
依據杜氏陳述,此約之締結乃由我方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主動提出草案,杜氏認為原則可行,但由於牽涉國共紛爭,問題複雜,故一再往返磋商,翌年九月杜氏親自訪臺與故總統蔣公晤談,返美後乃積極推動此約,主要交涉在華府進行,中間一度並遣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再往臺北磋商,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約成初簽,十二月二日正式簽字。
杜氏稱美國簽此約之主要原因,在臺澎為西太平洋阻遏共黨擴張的鏈島防線之一環,而美國與其他防線上的國家如日、韓、菲等都已有防衛條約,若對臺灣獨缺不但有礙防線完整,危及東亞各盟國之安全,美國亦將被誤為欲以臺灣作與中共交易之犧牲,並可能鼓勵中共犯臺等等。大部議員對此均無異議,但因參院在一月底剛通過《臺灣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授權總統可以用兵保衛臺澎及相關外島區域,部份議員乃以此約與決議案作用有何不同為問,杜氏答稱條約為一雙方行為,置防衛關係於一莊嚴之基礎上,不似決議案只是美國片面行為,其並透露訪臺晤先總統蔣公時曾問是否願以美總統對第七艦隊所下的防衛臺澎命令為協防之法律基礎,蔣公堅決答否。此外杜氏並強調條約可消除臺灣軍民疑慮,鼓舞士氣,並贏得對美國的好感等等,皆非決議案可比,又稱美國簽約的目的絕非「利他」(Altruistic),所著眼仍是美國的利益。
臺灣法律地位問題
所謂臺灣「法律地位」問題,是關於此約爭議最多的問題之一。杜氏所持為地位未定論,蓋以臺灣在歷史上曾遭葡、荷、日人統治過,不同於中國大陸,戰後盟國對日及《中日和約》中均只規定日本放棄對臺主權,未定其歸屬,故法律地位仍是未定,並稱此約亦不影響此一未定狀態,蓋美國亦不對臺澎擁有主權,何能藉此約對臺澎作主權之移轉。韓福瑞議員以蘇俄是否可對臺澎提出主權要求為問,杜氏之答覆為肯定,因蘇俄曾對日參戰,但認為蘇俄若作此要求其基礎殊薄弱,因蘇俄對日宣戰時日本已快投降了。杜氏又指出中華民國對臺澎之主權雖不完備(Perfect),但無一國可以比擬,且可引用國際法的「時效」原則,即經有效治理一段時間後其主權趨於完備,亦不否認此約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此一趨勢。自由派議員傅爾布萊特、史巴克曼等仍以我政府對臺澎之主權既不完備,美國何能以臺澎為條約標的與我政府逕行締約為問,杜氏答我政府目下為一「占領當局」(Occupying Power),如同美政府之於琉球與巴拿馬運河區一般。又稱條約中所規定的美方「領土」(按:即美國轄下的西太平洋島嶼)乃指琉球、關島等,美國只「占領當局」而已,並不擁有主權,但在該約第六條中與臺澎同列於有關「領土」之規定中,可見其屬同級。又稱條約中「領土」(Territories)一字乃經慎選使用,蓋此字並不一定意含「主權」(Sovereignty)在內。
史巴克曼議員又問是否反對參院作一聲明稱該約不影響臺澎法律地位之未定狀態,杜氏答原則不反對,但仍要考慮一下,因此時正值我大陳撤退,其必須考慮此種聲明是否對我軍民有不良之心理影響(按:後外交委員會對該約之審議報告書中有此聲明)。
反攻大陸問題及對我政府之觀感
自由派議員們亦極關切美國可否干涉我反攻大陸問題,杜氏答此條約的目的並非限制我政府於臺澎,條約正文中亦無規定可據以干涉我反攻行動,但約後的換文可限制我政府不得美國協議不能逕行反攻(按即反攻行動屬「共同協議事項」),傅氏乃以換文的法律效力為問,是否對蔣公以後的政府有拘束力?杜氏答謂換文雖非條約的一部份,但因附於條約,故較一般外交上的換文更具「神聖性」(Solemnity)。傅氏又問為何不將此列於條約之中,杜氏答蔣公將永不會與美國締一限制他反攻行動的條約。對美國助我反攻之可能,杜氏答吾人願見共產黨有朝一日在中國大陸消失,但吾人不準備以軍事行動促此實現。又該約第六條中規定協防條款可依據未來雙方協議而擴張適用於其他領土,摩斯議員乃問此規定是否暗示協防金馬外島之可能,杜氏答否,又稱若有此種擴張適用之協議將視為修約,將提交參院同意。摩斯又問為何加入此擴張規定,杜氏答因美國與韓國之協防條約有此款,中華民國不願受差別待遇,否則將被誤為放棄反攻大陸的目標。
摩斯議員似對我政府是否民主,臺籍人士有無參政機會等至為關切,其並當場引述某臺獨領袖給他的信件及前臺省主席吳國楨在美攻擊我政府不民主的言論為佐證。杜氏對此等問題之答覆為不能以美式民主標準評判東方國家,否則吾人將無東方國家可以為友。又我政府中雖無非國民黨人士存在,國會又在大陸選出,在接收臺灣之初確也與地方人士有若干衝突,但目前一般臺灣人民對政府並無重大不滿或反對,對吳氏言論因其從未與其接觸亦無從評論(後史密斯議員介入稱彼與吳氏甚稔,願詳告摩斯吳氏的情形)。摩斯又問是否可能將臺灣置於聯合國託管之下,杜氏認為臺灣人民對此不會接受,故不可能。格林議員問是否可能承認一獨立的「臺灣國」則可化解許多問題,杜氏答或可化解一些但也會製造許多新問題,首先必須製造一「臺灣國」,如此則須與四、五十萬美國所訓練裝備的我國軍為敵,又可能使聯合國中國席位拱手讓於中共。杜氏又認為我政府雖享有美國之法律承認,但理論上是一位於「外國土地」(alien land)上的「流亡政府」(gov’t in exile),不過承認流亡政府的例子歷史上亦殊多,不足為怪。史巴克曼議員乃問歷史上承認流亡政府的時間均甚暫,非長久之計,但美國對臺澎究竟有何長遠打算,是否將來會一朝放手不管(Turn those loose)?杜氏只簡短答「是」,史要杜再詳說,杜氏詞窮,只得承認目前整個情況確不正常(abnormality),但美國必須接受現實,不能因此不正常妨礙到確保美國在該地區的安全利益,蓋臺灣若落入共黨手中,整個西太平洋鏈島防線均會瓦解,是則美國將面臨蘇俄、中共、日本三結合的巨大敵對力量,美國的防衛線也只好撤回本土了,故與我政府訂此約,實有必要。
綜合評論
從杜氏證詞看來,《中美協防條約》應是當時我外交上的一項勝利,我們得到了所須要的安全保障,也儘量避免了對我們的束縛。國人似常批評我們的外交不夠主動,但此約由我主動提出,應是主動外交最好的例子。約中有關反攻大陸問題對我們有利的列為正文(即協防區域可予擴張),不利的列在約外換文(即反攻行動屬「共同協議事項」),更屬難得。雙方交涉期間幾達一年之久,可見折衝之不易。杜氏所說蔣公將永不會締結一限制其反攻行動的條約,可見蔣公處斯時惡劣的局勢下,對美交涉仍是大義凜然,不受其挾制。但換文的法律效力杜氏似未說清楚,蓋據一般國際法,約後換文雖非條約之一部,但與條約有同等法律效力。杜氏乃律師出身,對此自應知曉,卻僅以「神聖性」向素難對付的傅爾布萊特為言,似亦可怪(傅氏質詢,語多鋒利,如逕指杜氏為《中日和約》之導演,使美國如此約之「教父」一般)。然或許杜氏原意為換文可以隨時由一方片面廢棄,但因此換文附於條約較為「神聖」,不得如此。若照杜氏言,協防區域的擴張協議皆須提交參院同意,而今日卡特逕行廢約將整個協防區域減至零,反無須參院同意,在法理邏輯上似亦有說不通之處。今日引起極大爭議的廢約問題當時並未見若何討論,蓋此本為美國憲法上總統與國會權限之爭,與此約本身無涉,但巧合者,巴克萊議員原要問杜氏一問題卻一下忘記了,至最後才提出,赫然是《臺灣決議案》之存廢是否影響此約存廢的問題,杜氏答兩者無關連,但此約可經一年的通知而終止,此竟為杜氏答覆整個質詢的最後一句話。
杜氏對我政府是否民主,是否得人民擁護的印象似尚持平,對臺獨領導人與吳國楨氏似乏興趣。海外「臺獨分子」與「民主人士」在此類節骨眼的關頭「幫倒忙」的現象似乎今昔皆然,日前若干自稱有心致力臺灣民主化的人士,卻要求美國以人權問題為口實對臺禁運武器,則安全受危害者寧非臺灣一千七百萬同胞?
有關臺灣法律地位問題,杜氏雖也認為未定,但其「不完備」論及可依國際法「時效」原則使之完備等等,似較一般「未定論」為公允,但將我政府治理臺澎之地位比諸美國之於琉球、巴拿馬運河區,則屬不倫不類之至。關於條約中「領土」一詞之解釋及在約中之安排,更可見杜氏心機之深,亦可見吾人嘗謂美國人辦外交「天真」之天真。但就一般習用的國際法名詞言,「領土」一詞無論在中英文中均含有「主權」之意,然就杜氏解釋以觀,卻近似中文「領地」之意。
綜而言之,從證詞中可看出這位我們認為三十年來對我們最友好的美國國務卿乃一外交現實主義者(Realist)。其所說的訂約原因雖無甚新義,但可注意者其中無一句提到我們一向論中美關係時所習用的「悠久盟邦」、「道義之交」、「共同理想」、「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類的詞句,議員中亦無一人提及。若以「道義」考慮為出發,則杜氏認為以美式民主標準相責,東方國家中尚乏人可以為友,故只得遷就「現實」了。現實是什麼,現實是一「不正常」狀態,因為臺澎島上有一「位於外國土地上的流亡政府」,而因為美國防堵共黨擴張危及本土之鏈島防線不可缺臺澎(但可缺金馬),也因為再去製造一個「臺灣國」太費事,且有將聯合國中國席位讓予中共的危險,故只得因利乘便與這個「占領當局」締約了。或許最初連締約都不熱中,只想以第七艦隊防衛臺澎的命令為協防之法律基礎,故才有杜氏對蔣公試探性之一問。當初若非我政府主動堅持,則此約能否締結或亦不無疑問。在此種種考慮下,美國對臺澎長遠之計更非所計及了。
中美「共同利益」之處仍多
以上評述,並非危言聳聽,史料俱在,可以覆按。美國當初所以與我締此約,不過著眼臺灣戰略地位及利用我箝制中共,其出於一時權宜之利害考慮,於杜氏證詞中極為顯見,絕非有厚愛於吾人(如杜氏所說的絕非「利他」),更非有些人一廂情願的以為「為大陸淪陷贖罪」,故一旦戰略情勢改觀,則全盤俱去。三十年來我們未能突破現有格局,則今日中美關係之變化,也許老早即註定無可避免。中美雙方同床異夢,本不自今日始,吾人對此亦不必作過分情緒式之反應,各國本有其各各不同之自身利益,國與國間關係亦究非戀愛婚姻可比,好在今後中美雙方有「共同利益」之處仍多,則何妨互為「利用」,少投擲無謂的感情或作自以為是、一廂情願的寄望。國際關係史上,本多一時利害之結合,但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我們,似對「道義」總有一份執著。放眼今日天下,若謂禮失而求諸野,似也只有尋之於「第三世界」的沙烏地阿拉伯了。
沈呂巡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外交。
一生只牽掛一個地方,就是外交部。
一生最在乎一種關係,就是外交關係,其中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又是他心頭重中之重,臺北與華府的風吹草動,沈呂巡絕不錯過。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是沈呂巡外交生涯第一天,他向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報到,擔任諮議。第二章〈揚帆啟航、北美時期〉,我們看外交教父錢復破格拔擢的沈呂巡,全心投入對美國國會外交與臺美關係,也看沈呂巡追尋國父的足跡,從美國丹佛到英國倫敦,一路熱血澎湃。
我們專注於沈呂巡關注國家主權、解讀臺美關係脈絡。重點包括:
一、美國對臺灣法律地位的認定;
二、美國國務卿或總統,在不同時空稱呼我國為「占領當局」或「自治實體」;
三、被視為最反共的美國總統雷根,對於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設立「聯絡處」的模式,也因中共反對而退讓;
四、認清三十年來最友我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本質是「外交現實主義者」;
五、與美國斷交後的中華民國,如何繼續保有相當多的法理空間與相當的國際法人資格;
六、美國對臺灣主權問題「不採立場」(takes no position on the question of Taiwan’s sovereignty.)。
從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一直到沈呂巡二○二三年一月六日病逝,老沈無時無刻都在關注美國與我關係如何突破,如何能夠在沒有邦交的情況下,爭取主權象徵的、官方意義的、實質關係的進展。
位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駐美代表處,是老沈三十五年外交生涯的起點與終點,從諮議到駐美代表、從《八一七公報》的損害控管到我與美國斷交三十六年後首次在雙橡園升旗,沈呂巡為外交戮力穿梭的身影,不只華府,也包括了臺北、堪薩斯、日內瓦、布魯塞爾、倫敦等地,各自繽紛,精采非凡。
呂巡時論、回憶外交
由當年杜勒斯秘密證詞看中美協防條約——兼談條約即將失效時我們應有的認識和做法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聯合報》二版
《中美協防條約》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由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及我國外長葉公超簽字訂定,翌年元月由美政府提交參院審議,二月七日杜勒斯親赴參院外交委員會祕密院會作證,並接受質詢。此一證詞及答問紀錄一直列為機密,至去年四月始予公開,載於參院《外交委員會歷史文獻集》(Historical Series)第七集三○九至三五六頁。我們雖不敢說杜氏當時對參議員們完全直言無隱,但在祕密院會中,尤其被許多大牌議員追問之下,杜氏所作的陳述應較其他官方文件更為坦白可信,是則我們可進一步了解美國當初締結此約的各項考慮及對我政府之觀感等等,對探討近三十年中美關係之癥結當不無助益,尤其在此約即將終止的今天,此種了解或對今後對美外交工作亦有所啟發。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那次祕密會議出席議員共十三人,其中有我們熟知的大牌議員傅爾布萊特、史巴克曼、後擔任過副總統的韓福瑞、現任美駐日大使的曼斯菲德等等。可異者當時最支持我們的諾蘭參議員(亦外委會委員,當時被人戲稱為「來自臺灣的參議員」)卻未出席。由於原紀錄頗長,本文將先就杜氏對下列題目之看法摘要記述,再作一綜合評論。
訂約之經過及原因
依據杜氏陳述,此約之締結乃由我方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主動提出草案,杜氏認為原則可行,但由於牽涉國共紛爭,問題複雜,故一再往返磋商,翌年九月杜氏親自訪臺與故總統蔣公晤談,返美後乃積極推動此約,主要交涉在華府進行,中間一度並遣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再往臺北磋商,至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約成初簽,十二月二日正式簽字。
杜氏稱美國簽此約之主要原因,在臺澎為西太平洋阻遏共黨擴張的鏈島防線之一環,而美國與其他防線上的國家如日、韓、菲等都已有防衛條約,若對臺灣獨缺不但有礙防線完整,危及東亞各盟國之安全,美國亦將被誤為欲以臺灣作與中共交易之犧牲,並可能鼓勵中共犯臺等等。大部議員對此均無異議,但因參院在一月底剛通過《臺灣決議案》(Formosa Resolution)授權總統可以用兵保衛臺澎及相關外島區域,部份議員乃以此約與決議案作用有何不同為問,杜氏答稱條約為一雙方行為,置防衛關係於一莊嚴之基礎上,不似決議案只是美國片面行為,其並透露訪臺晤先總統蔣公時曾問是否願以美總統對第七艦隊所下的防衛臺澎命令為協防之法律基礎,蔣公堅決答否。此外杜氏並強調條約可消除臺灣軍民疑慮,鼓舞士氣,並贏得對美國的好感等等,皆非決議案可比,又稱美國簽約的目的絕非「利他」(Altruistic),所著眼仍是美國的利益。
臺灣法律地位問題
所謂臺灣「法律地位」問題,是關於此約爭議最多的問題之一。杜氏所持為地位未定論,蓋以臺灣在歷史上曾遭葡、荷、日人統治過,不同於中國大陸,戰後盟國對日及《中日和約》中均只規定日本放棄對臺主權,未定其歸屬,故法律地位仍是未定,並稱此約亦不影響此一未定狀態,蓋美國亦不對臺澎擁有主權,何能藉此約對臺澎作主權之移轉。韓福瑞議員以蘇俄是否可對臺澎提出主權要求為問,杜氏之答覆為肯定,因蘇俄曾對日參戰,但認為蘇俄若作此要求其基礎殊薄弱,因蘇俄對日宣戰時日本已快投降了。杜氏又指出中華民國對臺澎之主權雖不完備(Perfect),但無一國可以比擬,且可引用國際法的「時效」原則,即經有效治理一段時間後其主權趨於完備,亦不否認此約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此一趨勢。自由派議員傅爾布萊特、史巴克曼等仍以我政府對臺澎之主權既不完備,美國何能以臺澎為條約標的與我政府逕行締約為問,杜氏答我政府目下為一「占領當局」(Occupying Power),如同美政府之於琉球與巴拿馬運河區一般。又稱條約中所規定的美方「領土」(按:即美國轄下的西太平洋島嶼)乃指琉球、關島等,美國只「占領當局」而已,並不擁有主權,但在該約第六條中與臺澎同列於有關「領土」之規定中,可見其屬同級。又稱條約中「領土」(Territories)一字乃經慎選使用,蓋此字並不一定意含「主權」(Sovereignty)在內。
史巴克曼議員又問是否反對參院作一聲明稱該約不影響臺澎法律地位之未定狀態,杜氏答原則不反對,但仍要考慮一下,因此時正值我大陳撤退,其必須考慮此種聲明是否對我軍民有不良之心理影響(按:後外交委員會對該約之審議報告書中有此聲明)。
反攻大陸問題及對我政府之觀感
自由派議員們亦極關切美國可否干涉我反攻大陸問題,杜氏答此條約的目的並非限制我政府於臺澎,條約正文中亦無規定可據以干涉我反攻行動,但約後的換文可限制我政府不得美國協議不能逕行反攻(按即反攻行動屬「共同協議事項」),傅氏乃以換文的法律效力為問,是否對蔣公以後的政府有拘束力?杜氏答謂換文雖非條約的一部份,但因附於條約,故較一般外交上的換文更具「神聖性」(Solemnity)。傅氏又問為何不將此列於條約之中,杜氏答蔣公將永不會與美國締一限制他反攻行動的條約。對美國助我反攻之可能,杜氏答吾人願見共產黨有朝一日在中國大陸消失,但吾人不準備以軍事行動促此實現。又該約第六條中規定協防條款可依據未來雙方協議而擴張適用於其他領土,摩斯議員乃問此規定是否暗示協防金馬外島之可能,杜氏答否,又稱若有此種擴張適用之協議將視為修約,將提交參院同意。摩斯又問為何加入此擴張規定,杜氏答因美國與韓國之協防條約有此款,中華民國不願受差別待遇,否則將被誤為放棄反攻大陸的目標。
摩斯議員似對我政府是否民主,臺籍人士有無參政機會等至為關切,其並當場引述某臺獨領袖給他的信件及前臺省主席吳國楨在美攻擊我政府不民主的言論為佐證。杜氏對此等問題之答覆為不能以美式民主標準評判東方國家,否則吾人將無東方國家可以為友。又我政府中雖無非國民黨人士存在,國會又在大陸選出,在接收臺灣之初確也與地方人士有若干衝突,但目前一般臺灣人民對政府並無重大不滿或反對,對吳氏言論因其從未與其接觸亦無從評論(後史密斯議員介入稱彼與吳氏甚稔,願詳告摩斯吳氏的情形)。摩斯又問是否可能將臺灣置於聯合國託管之下,杜氏認為臺灣人民對此不會接受,故不可能。格林議員問是否可能承認一獨立的「臺灣國」則可化解許多問題,杜氏答或可化解一些但也會製造許多新問題,首先必須製造一「臺灣國」,如此則須與四、五十萬美國所訓練裝備的我國軍為敵,又可能使聯合國中國席位拱手讓於中共。杜氏又認為我政府雖享有美國之法律承認,但理論上是一位於「外國土地」(alien land)上的「流亡政府」(gov’t in exile),不過承認流亡政府的例子歷史上亦殊多,不足為怪。史巴克曼議員乃問歷史上承認流亡政府的時間均甚暫,非長久之計,但美國對臺澎究竟有何長遠打算,是否將來會一朝放手不管(Turn those loose)?杜氏只簡短答「是」,史要杜再詳說,杜氏詞窮,只得承認目前整個情況確不正常(abnormality),但美國必須接受現實,不能因此不正常妨礙到確保美國在該地區的安全利益,蓋臺灣若落入共黨手中,整個西太平洋鏈島防線均會瓦解,是則美國將面臨蘇俄、中共、日本三結合的巨大敵對力量,美國的防衛線也只好撤回本土了,故與我政府訂此約,實有必要。
綜合評論
從杜氏證詞看來,《中美協防條約》應是當時我外交上的一項勝利,我們得到了所須要的安全保障,也儘量避免了對我們的束縛。國人似常批評我們的外交不夠主動,但此約由我主動提出,應是主動外交最好的例子。約中有關反攻大陸問題對我們有利的列為正文(即協防區域可予擴張),不利的列在約外換文(即反攻行動屬「共同協議事項」),更屬難得。雙方交涉期間幾達一年之久,可見折衝之不易。杜氏所說蔣公將永不會締結一限制其反攻行動的條約,可見蔣公處斯時惡劣的局勢下,對美交涉仍是大義凜然,不受其挾制。但換文的法律效力杜氏似未說清楚,蓋據一般國際法,約後換文雖非條約之一部,但與條約有同等法律效力。杜氏乃律師出身,對此自應知曉,卻僅以「神聖性」向素難對付的傅爾布萊特為言,似亦可怪(傅氏質詢,語多鋒利,如逕指杜氏為《中日和約》之導演,使美國如此約之「教父」一般)。然或許杜氏原意為換文可以隨時由一方片面廢棄,但因此換文附於條約較為「神聖」,不得如此。若照杜氏言,協防區域的擴張協議皆須提交參院同意,而今日卡特逕行廢約將整個協防區域減至零,反無須參院同意,在法理邏輯上似亦有說不通之處。今日引起極大爭議的廢約問題當時並未見若何討論,蓋此本為美國憲法上總統與國會權限之爭,與此約本身無涉,但巧合者,巴克萊議員原要問杜氏一問題卻一下忘記了,至最後才提出,赫然是《臺灣決議案》之存廢是否影響此約存廢的問題,杜氏答兩者無關連,但此約可經一年的通知而終止,此竟為杜氏答覆整個質詢的最後一句話。
杜氏對我政府是否民主,是否得人民擁護的印象似尚持平,對臺獨領導人與吳國楨氏似乏興趣。海外「臺獨分子」與「民主人士」在此類節骨眼的關頭「幫倒忙」的現象似乎今昔皆然,日前若干自稱有心致力臺灣民主化的人士,卻要求美國以人權問題為口實對臺禁運武器,則安全受危害者寧非臺灣一千七百萬同胞?
有關臺灣法律地位問題,杜氏雖也認為未定,但其「不完備」論及可依國際法「時效」原則使之完備等等,似較一般「未定論」為公允,但將我政府治理臺澎之地位比諸美國之於琉球、巴拿馬運河區,則屬不倫不類之至。關於條約中「領土」一詞之解釋及在約中之安排,更可見杜氏心機之深,亦可見吾人嘗謂美國人辦外交「天真」之天真。但就一般習用的國際法名詞言,「領土」一詞無論在中英文中均含有「主權」之意,然就杜氏解釋以觀,卻近似中文「領地」之意。
綜而言之,從證詞中可看出這位我們認為三十年來對我們最友好的美國國務卿乃一外交現實主義者(Realist)。其所說的訂約原因雖無甚新義,但可注意者其中無一句提到我們一向論中美關係時所習用的「悠久盟邦」、「道義之交」、「共同理想」、「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類的詞句,議員中亦無一人提及。若以「道義」考慮為出發,則杜氏認為以美式民主標準相責,東方國家中尚乏人可以為友,故只得遷就「現實」了。現實是什麼,現實是一「不正常」狀態,因為臺澎島上有一「位於外國土地上的流亡政府」,而因為美國防堵共黨擴張危及本土之鏈島防線不可缺臺澎(但可缺金馬),也因為再去製造一個「臺灣國」太費事,且有將聯合國中國席位讓予中共的危險,故只得因利乘便與這個「占領當局」締約了。或許最初連締約都不熱中,只想以第七艦隊防衛臺澎的命令為協防之法律基礎,故才有杜氏對蔣公試探性之一問。當初若非我政府主動堅持,則此約能否締結或亦不無疑問。在此種種考慮下,美國對臺澎長遠之計更非所計及了。
中美「共同利益」之處仍多
以上評述,並非危言聳聽,史料俱在,可以覆按。美國當初所以與我締此約,不過著眼臺灣戰略地位及利用我箝制中共,其出於一時權宜之利害考慮,於杜氏證詞中極為顯見,絕非有厚愛於吾人(如杜氏所說的絕非「利他」),更非有些人一廂情願的以為「為大陸淪陷贖罪」,故一旦戰略情勢改觀,則全盤俱去。三十年來我們未能突破現有格局,則今日中美關係之變化,也許老早即註定無可避免。中美雙方同床異夢,本不自今日始,吾人對此亦不必作過分情緒式之反應,各國本有其各各不同之自身利益,國與國間關係亦究非戀愛婚姻可比,好在今後中美雙方有「共同利益」之處仍多,則何妨互為「利用」,少投擲無謂的感情或作自以為是、一廂情願的寄望。國際關係史上,本多一時利害之結合,但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我們,似對「道義」總有一份執著。放眼今日天下,若謂禮失而求諸野,似也只有尋之於「第三世界」的沙烏地阿拉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