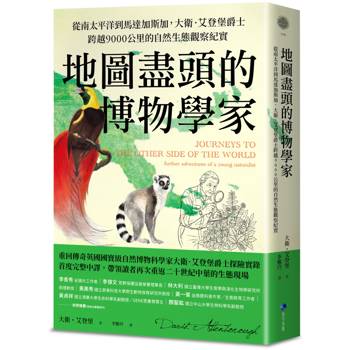引言
一九五四到六四年的十年間,我非常幸運,每年都得以去熱帶地區製作自然歷史影片,起初我們的探險考察計畫,是由BBC電視台和倫敦動物園聯合組織,目標不僅是拍攝動物,還要捕捉其中一些動物,因此該電視節目命名為《動物園尋奇》(Zoo Quest)這個籠統的名稱。但非常悲傷的是,由於身體欠佳,動物園方的代表傑克・萊斯特(Jack Lester)無法參加第三次旅程,此後動物園方的參與度降低到,僅接受電視節目中我們試圖帶回的生物,因此在野外拍攝動物而非捕捉動物,成為旅程的首要任務。我們的興趣與日俱增,旅途中遇見的部落人民開始在影片中占據了愈來愈引人注目的地位,因此《動物園尋奇》這個節目名稱似乎已不適合做為這本選集的書名。我所撰寫關於這幾段旅程的前三本書,在一九八○年以微濃縮的形式重新出版,然後在二○一七年又以增修的版本再次出版,書名是「年輕博物學家的深層冒險」(Adventures of a Young Naturalist)。這是第二版的三篇選集,同樣經過略微修訂。
從這幾段旅程的最後一次賦歸以來,已過去六十多年,毫不令人驚訝的是,這個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新幾內亞東部當初由澳洲管理,現已獨立為巴布亞新幾內亞;吉米谷(Jimi Valley)當年還是個剛有人探索的處女地,如今不僅有道路行經,且擁有自己的國會議員。我們造訪時由薩洛特女王統治東加,她於一九六五年去世後,由王儲繼任為陶法阿豪・圖普四世,隨後又由喬治・圖普五世繼任。新赫布里底群島曾以一種奇異又獨特的殖民地政府形式管理,即英法共管地,而今已獨立為萬那杜共和國。澳洲的達爾文小鎮現已成為一座城市,卡卡杜國家公園(Kakadu National Park)諾蘭基岩(Nurlangie)周圍的土地,有了旅館和道路,以符合當地的需要。我們造訪時,所見那些狂野奔跑的亞洲水牛今已滅絕,使這個奇妙而脆弱的生態系統回復到接近原始狀態。我們是最早拍攝諾蘭基岩畫作的團隊,如今該地享譽國際,並出現在澳洲郵票上。馬加尼(Magani)曾告訴我們,許多關於他如何創作的故事,如今他的樹皮畫作已被列為澳洲國家美術館館藏。在雲都姆附近岩石上作畫的人,其精神由使用現代繪畫技巧的藝術家繼承,他們的油畫現以數十萬美元(甚至數百萬美元)的價格出售。某些澳洲原住民的原始版本儀式細節已縮減,目的是不冒犯現今澳洲原住民的敏感神經。
當然,電視製作技術已發生不可估量的變化,錄音機不再使用磁帶,也不會拒絕在熱帶陽光下運作,與我們當年所使用的巨大怪獸相比,電視攝影機已電子化,體積又小,因此不再需要包裹特殊襯墊讓機器保持安靜,更有甚者,是他們現在可以立即重播所拍攝的影片,不必再等待好幾個月,才能知道我們是否拍到希望的片段。
儘管如此,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本質上是在為地方和事件留下記述。
大衛・艾登堡,寫於二○一八年五月
第一部 天堂探索
第一章 瓦吉谷
維多利亞號首航全世界,於一五二二年九月六日到達西班牙,從船上帶下的奇觀異事中,有五張鳥皮,鳥皮上的羽毛,尤其從鳥皮側面生長出薄紗似的長羽,形態是無與倫比地光彩壯麗,完全不同於以往所見。其中兩張鳥皮是由摩鹿加(Moluccas)一座島上的巴占國王(King of Batchian),贈送給探險隊長麥哲倫(Magellan),做為贈與西班牙國王的贈禮。探險史家皮加費蒂(Pigafetti)以文字記錄這份贈禮,他寫道,「這些鳥像歌鶇一樣大;頭小喙長,有如筆般細長的腿,就像一支書寫筆,跨度很長。鳥沒有翅膀,取而的時才飛行。他們告訴我們這些鳥來自人間天堂,稱這種鳥為『bolon dinata』,意即神聖之鳥。」
這些華麗的生物因此被稱之為天堂鳥,是紀錄上有史以來最早輸入歐洲的標本,皮加費蒂對牠們的描述相對不那麼聳人聽聞。毫無疑問,當地的剝皮者將這種鳥剪斷翅膀,以強調長羽的壯觀,但牠們驚人的美麗、極端的稀有性、與「人間天堂」的聯想,都賦予這些鳥類神祕又魔幻的光環,很快地,關於牠們的傳說就和牠們的美麗一樣充滿神奇。約翰內斯・于根・凡・林斯科滕(Johannes Huygen van Linschoten)描述自己於七十年後在摩鹿加群島的航程,他寫道,「在這些群島上,只發現一隻被葡萄牙人稱之為passeros de sol的鳥,意即『太陽鳥』,義大利人稱之為Manu codiatas,拉丁語學家稱為Paradiseas,我們則稱之為天堂鳥,這是因為牠們的羽毛比其他鳥類更美;從來沒有人活生生目睹過這些鳥,而是看見牠們死後落在島嶼上:牠們飛行,據說總是飛向陽光,持續飛在空中,因為既沒有腳也沒有翅膀,所以無法停落在地面上,但牠們僅有頭部和身體,身體的大部分都是尾巴。」
林斯科滕描述這種鳥類缺乏腿部,這個狀態很容易解釋,即使在今日,當地人還是習慣除去鳥的腿部,從而使他們更容易幫鳥剝皮。皮加費蒂曾表示,天堂鳥擁有雙腿,此一事實遭人們輕易遺忘,或遭後世的作家強力反駁,因為這些人亟欲維持圍繞這種鳥類的浪漫傳說,但是林斯科滕對牠們生活方式的描述,卻為一名有思想能力的博物學家帶來許多問題,如果鳥類始終處於飛行狀態,牠們要如何築巢和孵蛋,牠們要吃什麼?很快就得出答案了,而這些答案與他們試圖合理化的幻想,一樣不合常理。
一位作家曾描述,「在雄性後部有一個特定的空腔,雌性的腹部也是中空的,雌性會在當中產卵,因此在兩個空腔的幫助下,鳥坐在蛋上將蛋孵化出來」。另一位作家解釋,這種鳥類在長期飛行狀態中僅靠露水和空氣維生,然後補充說明這種鳥沒有胃部和腸部,因為這些器官對於如此出色的一種動物來說沒有用處,取而代之的是腹腔中充滿了脂肪。第三位作家希望增加牠們所謂無腳故事的可信度,同時他留意到在某些物種的羽毛中有成對捲曲的堅韌翮羽,便寫道:「牠們並非坐在地上,而是靠自己身上的細絲或羽毛靠在大樹枝上來休憩,就像蒼蠅或空氣中的小生物一樣。」
即便在第一批鳥皮輸入歐洲後的兩百年,這種鳥類確切的生息地(即「人間天堂」)仍然未知,直到十八世紀,才發現牠們生活在新幾內亞及其近海島嶼。當歐洲博物學家首度在自然環境中看到活生生的鳥時,圍繞牠們的大部分神話都被消散無蹤。然而自皮加費蒂時代以來,圍繞此種鳥類的浪漫氛圍從未受世人遺忘,當瑞典偉大的博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想要幫最可能是皮加費蒂所描述的物種取一個科學名稱時,他稱之為Paradisea apoda,即無腿天堂鳥。
但近兩百年來,科學發現所揭露關於天堂鳥的真實事實,幾乎與早期傳說一樣奇妙,因為這些鳥擁有整個鳥類世界中最為燦爛且不可思議的羽飾,現在已識別出多達五十多種不同物種,其形體和大小差異極大。有些物種就像「無腿天堂鳥」一樣,翅膀下面有瀑布狀華麗的細絲長羽,其他種類的胸部則帶有巨大虹彩色的胸羽,有些則是有長形光滑的黑色尾巴,當中閃爍著紫色的陰影,其他種類的尾羽減少成翮羽。威爾森氏麗色天堂鳥(Wilson’s Bird)頭禿,有亮藍色頭皮;薩克森國王天堂鳥(King of Saxony’s Bird)有兩道頭羽,其長度是其身體的兩倍,每道頭羽上都飾有珐瑯般淺珍珠藍的羽片,最大的物種可達烏鴉的大小;最小的王風鳥(King Bird of Paradise),體型比知更鳥大一些。事實上,天堂鳥間的相似之處,不過是全身羽毛幾可說是驚人地奢華,且會沉迷於狂野的求偶舞,求偶期間,牠們會向黃褐色的雌鳥展示一身輝煌的羽毛。
這樣美麗而浪漫的生物,肯定值得飛越千里去一睹其風采,多年來我一直懷抱著去看天堂鳥的執念,倫敦動物園已有好多年沒有展出標本,而當時我正考慮從事一次遠征之旅來尋找標本,完全沒有這種鳥類的標本。更有甚者,至少在英國從未播映過野生鳥類表演舞蹈的影片,我決定去新幾內亞嘗試拍攝牠們,並捕捉幾隻活體帶回倫敦。
新幾內亞的國土無邊無際,那裡是全世界最大的非大陸島嶼,首尾綿延超過一千英里,此地有高至阿爾卑斯山的山脈連綿起伏,山坡上並非覆蓋著萬年雪和冰川,而是長滿青苔的巨樹森林。在這些山脈間是滿布叢林的巨大山谷,其中許多實際上處於未開發狀態,向海岸蔓延的則是面積達數百平方英里布滿蚊蚋的沼澤。
在政治上,該島幾乎可均分為兩部分,我們旅途期間,西半部由荷蘭統治,東半部則由澳洲統治。在最近期的領土範圍中,靠近整座島嶼中心的一處高地上,坐落著一處高地山谷,在那裡有個名為農都格(Nondugl)的小型聚落,那裡是澳洲百萬富翁兼慈善家愛德華・霍斯壯爵士(Sir Edward Hallstrom)所建立的一座實驗農場暨動物群落。他建造出巨大的鳥舍,當中所容納的天堂鳥,比全世界所有動物園的總和還要多,居住在該處的人是最偉大的動物收藏家之一、同時也是天堂鳥專家弗雷德・蕭・梅耶(Fred Shaw Mayer),因此如果可以獲得許可,農都格是我們造訪的理想之地。
愛德華爵士多年來一直是倫敦動物園的支持者兼贊助者,當我寫信給他並告訴他,我們的雄心壯志時,他回覆並建議我們,以該聚落為基地,進行為期四個月的探險歷程。
***
查爾斯・拉格斯(Charles Lagus)和我,已經在熱帶地區執行過三次動物搜奇暨拍攝之旅,當我們坐在一架向東奔赴第四段旅程的大型客機上,兩人都陷入新旅程開始之初一直無止盡困擾我們的憂慮——他在腦中確認自己的攝影器材,擔心遺漏了一些重要物品,而我則試圖預期我們到達農都格之前,會面對到的所有官僚障礙,並企圖安慰自己,其中大多數的狀況都已經預見,並且做好萬全準備。
三天內我們抵達澳洲,從雪梨出發,向北飛往新幾內亞,在該島東北岸的萊城,從舒適的四引擎客機下機,然後登上一架不甚豪華的飛機,該班機每週會將補給品運往中部高地的瓦吉谷(Wahgi valley)。
我們坐在形似貨架的鋁製座位上,座位沿著機艙單側設置,長度有飛機全長的一半。前面擺著長長一堆沿著機艙排列的貨物,並用繩索環綁在艙面上,當中包含有信件袋、扶手椅、柴油引擎的大量鑄鐵零件,紙箱裝滿年齡只有一天大的小雞,還有大量塊狀麵包,全部貨物當中還有十六件我們的行李和設備。
同行乘客是七名半裸的巴布亞人,他們僵硬而緊張地坐定,閉口不言又面無表情,目不轉睛盯著堆在他們前方幾英寸的貨物。至少對他們其中幾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搭飛機——起飛前,我還得向他們示範如何繫上安全帶——他們流淌著幾滴汗水,讓皮膚反射出光芒。
雨水灑在飛機的小窗戶上,雨聲被引擎的轟鳴聲淹沒,往外一看,舉目所及,除了一片灰濛濛外什麼都看不見,當我們向上攀升越過看不見的山巒,飛機開始搖晃抖動。因為天氣很冷,我微微發起抖來,皮膚仍因汗水感到濕黏,萊城的悶熱天氣讓我爆了一身汗。
飛機穩步攀升,直到外面的灰雲開始崩解成疾速飄逝的幻影迷霧,此時機艙突然變亮,好像電燈打開了般。我從其中一扇窗戶望出去,陽光照射在飛機光滑顫抖的機翼上,幾英里外是黑暗的峰頂,如島嶼般在不動的波浪狀雲層中突起。很快地,下方的白色雲層上出現了裂隙,每道裂隙中的景觀都像一幅奇異不真實的風景照,有時露出一條蜿蜒曲折的粼粼河水,有時只是頃刻看到幾幢小屋,但最常見的是平凡的木頭小路。我驚鴻一瞥下方的土地,面積愈來愈大,數量愈來愈多。我們飛過一排排此起彼落、山背如剃刀般的山丘,茂密叢生的樹木,有些光禿但整片褐色的草叢之後,最終融合成一幅連續畫面。一座接著一座山峰從下方掠過,直到高度陡然下降,我們不再飛越蠻荒的絕壁,而是沿著寬闊的綠色山谷飛行,瓦吉谷到了。
這片地面間的許多區域清除成飛機跑道,其中一個降落點即是農都格的實驗農場。我們的班機下降,飛越機場的建築物,有輛小型卡車從一間車庫中駛出,緩慢沿著紅色細線移動,明顯損害了連接房屋和飛機跑道的景觀。我們顛簸著著陸,查爾斯和我硬著頭皮爬出飛機,那輛卡車繞著彎道行駛,駛向蔓草叢生的簡易機場,並發出尖聲,停妥在機翼下方。有兩個男人跳了出來,一人結實魁梧,戴著頂寬邊、沾滿汗水的帽子,穿著卡其色工作服,他自我介紹自己是機場經理法蘭克・彭伯-史密斯(Frank Pemble-Smith),另一位老而瘦的男子則是弗雷德・蕭・梅耶。
我們一起從飛機上卸下攜帶的物品,法蘭克一邊隱隱咒罵,自家農場機械的部分零件並不在這批貨物當中,他花了幾分鐘時間與飛行員交換八卦。然後飛機的引擎重新啟動,在跑道上咆哮著飛向空中,前往下一個停靠站。下一站距離此地僅有四分鐘的飛行時間。法蘭克安排他在巴布亞機場的人手,將我們的裝備裝載到在附近等待的牽引機拖車上,然後他用卡車將我們載離,與他的妻子見面,並到他的屋子裡喝杯茶。
我們坐在他整潔的客廳裡享用司康時,我看見有一個高大、留著濃密鬍鬚的半裸男子,驚人身影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外頭,他棕色的手臂和長滿毛髮的胸膛被煤煙燻黑,臉上塗有紅色、黃色和綠色的斑點和條紋,腰部圍著編織纖維製成的寬闊硬質腹帶,其正面懸掛著一小段羊毛狀織物,一直延伸到小腿上,他的身後就像古時婦女的裙撐一樣,塞滿了濃密的葉片飾物。他身上裝飾有大量的珍珠貝殼珠寶:由小飾物組成的皮帶以一條細繩繫在腰間;一個巨大的珍珠裝飾胸甲,懸掛在圍繞脖子的繩索上;下巴圍著一塊寬大的新月狀裝飾物,部分隱藏在鬍鬚裡;他身上鑲嵌一根細長的鐮刀狀物,這個物體從珍珠貝殼的邊緣切下,穿過鼻子穿孔的中隔。然而他最令人讚嘆的個人裝飾,既不是珍珠貝殼也並非顏料,而是巨大的羽毛頭飾,頭飾包含至少出自五種不同品種的三十隻天堂鳥羽,有紅寶石色、翡翠色、天鵝絨黑和珐瑯藍,這些驚人的鳥羽構成一頂不可置信的輝煌冠冕。
一九五四到六四年的十年間,我非常幸運,每年都得以去熱帶地區製作自然歷史影片,起初我們的探險考察計畫,是由BBC電視台和倫敦動物園聯合組織,目標不僅是拍攝動物,還要捕捉其中一些動物,因此該電視節目命名為《動物園尋奇》(Zoo Quest)這個籠統的名稱。但非常悲傷的是,由於身體欠佳,動物園方的代表傑克・萊斯特(Jack Lester)無法參加第三次旅程,此後動物園方的參與度降低到,僅接受電視節目中我們試圖帶回的生物,因此在野外拍攝動物而非捕捉動物,成為旅程的首要任務。我們的興趣與日俱增,旅途中遇見的部落人民開始在影片中占據了愈來愈引人注目的地位,因此《動物園尋奇》這個節目名稱似乎已不適合做為這本選集的書名。我所撰寫關於這幾段旅程的前三本書,在一九八○年以微濃縮的形式重新出版,然後在二○一七年又以增修的版本再次出版,書名是「年輕博物學家的深層冒險」(Adventures of a Young Naturalist)。這是第二版的三篇選集,同樣經過略微修訂。
從這幾段旅程的最後一次賦歸以來,已過去六十多年,毫不令人驚訝的是,這個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新幾內亞東部當初由澳洲管理,現已獨立為巴布亞新幾內亞;吉米谷(Jimi Valley)當年還是個剛有人探索的處女地,如今不僅有道路行經,且擁有自己的國會議員。我們造訪時由薩洛特女王統治東加,她於一九六五年去世後,由王儲繼任為陶法阿豪・圖普四世,隨後又由喬治・圖普五世繼任。新赫布里底群島曾以一種奇異又獨特的殖民地政府形式管理,即英法共管地,而今已獨立為萬那杜共和國。澳洲的達爾文小鎮現已成為一座城市,卡卡杜國家公園(Kakadu National Park)諾蘭基岩(Nurlangie)周圍的土地,有了旅館和道路,以符合當地的需要。我們造訪時,所見那些狂野奔跑的亞洲水牛今已滅絕,使這個奇妙而脆弱的生態系統回復到接近原始狀態。我們是最早拍攝諾蘭基岩畫作的團隊,如今該地享譽國際,並出現在澳洲郵票上。馬加尼(Magani)曾告訴我們,許多關於他如何創作的故事,如今他的樹皮畫作已被列為澳洲國家美術館館藏。在雲都姆附近岩石上作畫的人,其精神由使用現代繪畫技巧的藝術家繼承,他們的油畫現以數十萬美元(甚至數百萬美元)的價格出售。某些澳洲原住民的原始版本儀式細節已縮減,目的是不冒犯現今澳洲原住民的敏感神經。
當然,電視製作技術已發生不可估量的變化,錄音機不再使用磁帶,也不會拒絕在熱帶陽光下運作,與我們當年所使用的巨大怪獸相比,電視攝影機已電子化,體積又小,因此不再需要包裹特殊襯墊讓機器保持安靜,更有甚者,是他們現在可以立即重播所拍攝的影片,不必再等待好幾個月,才能知道我們是否拍到希望的片段。
儘管如此,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本質上是在為地方和事件留下記述。
大衛・艾登堡,寫於二○一八年五月
第一部 天堂探索
第一章 瓦吉谷
維多利亞號首航全世界,於一五二二年九月六日到達西班牙,從船上帶下的奇觀異事中,有五張鳥皮,鳥皮上的羽毛,尤其從鳥皮側面生長出薄紗似的長羽,形態是無與倫比地光彩壯麗,完全不同於以往所見。其中兩張鳥皮是由摩鹿加(Moluccas)一座島上的巴占國王(King of Batchian),贈送給探險隊長麥哲倫(Magellan),做為贈與西班牙國王的贈禮。探險史家皮加費蒂(Pigafetti)以文字記錄這份贈禮,他寫道,「這些鳥像歌鶇一樣大;頭小喙長,有如筆般細長的腿,就像一支書寫筆,跨度很長。鳥沒有翅膀,取而的時才飛行。他們告訴我們這些鳥來自人間天堂,稱這種鳥為『bolon dinata』,意即神聖之鳥。」
這些華麗的生物因此被稱之為天堂鳥,是紀錄上有史以來最早輸入歐洲的標本,皮加費蒂對牠們的描述相對不那麼聳人聽聞。毫無疑問,當地的剝皮者將這種鳥剪斷翅膀,以強調長羽的壯觀,但牠們驚人的美麗、極端的稀有性、與「人間天堂」的聯想,都賦予這些鳥類神祕又魔幻的光環,很快地,關於牠們的傳說就和牠們的美麗一樣充滿神奇。約翰內斯・于根・凡・林斯科滕(Johannes Huygen van Linschoten)描述自己於七十年後在摩鹿加群島的航程,他寫道,「在這些群島上,只發現一隻被葡萄牙人稱之為passeros de sol的鳥,意即『太陽鳥』,義大利人稱之為Manu codiatas,拉丁語學家稱為Paradiseas,我們則稱之為天堂鳥,這是因為牠們的羽毛比其他鳥類更美;從來沒有人活生生目睹過這些鳥,而是看見牠們死後落在島嶼上:牠們飛行,據說總是飛向陽光,持續飛在空中,因為既沒有腳也沒有翅膀,所以無法停落在地面上,但牠們僅有頭部和身體,身體的大部分都是尾巴。」
林斯科滕描述這種鳥類缺乏腿部,這個狀態很容易解釋,即使在今日,當地人還是習慣除去鳥的腿部,從而使他們更容易幫鳥剝皮。皮加費蒂曾表示,天堂鳥擁有雙腿,此一事實遭人們輕易遺忘,或遭後世的作家強力反駁,因為這些人亟欲維持圍繞這種鳥類的浪漫傳說,但是林斯科滕對牠們生活方式的描述,卻為一名有思想能力的博物學家帶來許多問題,如果鳥類始終處於飛行狀態,牠們要如何築巢和孵蛋,牠們要吃什麼?很快就得出答案了,而這些答案與他們試圖合理化的幻想,一樣不合常理。
一位作家曾描述,「在雄性後部有一個特定的空腔,雌性的腹部也是中空的,雌性會在當中產卵,因此在兩個空腔的幫助下,鳥坐在蛋上將蛋孵化出來」。另一位作家解釋,這種鳥類在長期飛行狀態中僅靠露水和空氣維生,然後補充說明這種鳥沒有胃部和腸部,因為這些器官對於如此出色的一種動物來說沒有用處,取而代之的是腹腔中充滿了脂肪。第三位作家希望增加牠們所謂無腳故事的可信度,同時他留意到在某些物種的羽毛中有成對捲曲的堅韌翮羽,便寫道:「牠們並非坐在地上,而是靠自己身上的細絲或羽毛靠在大樹枝上來休憩,就像蒼蠅或空氣中的小生物一樣。」
即便在第一批鳥皮輸入歐洲後的兩百年,這種鳥類確切的生息地(即「人間天堂」)仍然未知,直到十八世紀,才發現牠們生活在新幾內亞及其近海島嶼。當歐洲博物學家首度在自然環境中看到活生生的鳥時,圍繞牠們的大部分神話都被消散無蹤。然而自皮加費蒂時代以來,圍繞此種鳥類的浪漫氛圍從未受世人遺忘,當瑞典偉大的博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想要幫最可能是皮加費蒂所描述的物種取一個科學名稱時,他稱之為Paradisea apoda,即無腿天堂鳥。
但近兩百年來,科學發現所揭露關於天堂鳥的真實事實,幾乎與早期傳說一樣奇妙,因為這些鳥擁有整個鳥類世界中最為燦爛且不可思議的羽飾,現在已識別出多達五十多種不同物種,其形體和大小差異極大。有些物種就像「無腿天堂鳥」一樣,翅膀下面有瀑布狀華麗的細絲長羽,其他種類的胸部則帶有巨大虹彩色的胸羽,有些則是有長形光滑的黑色尾巴,當中閃爍著紫色的陰影,其他種類的尾羽減少成翮羽。威爾森氏麗色天堂鳥(Wilson’s Bird)頭禿,有亮藍色頭皮;薩克森國王天堂鳥(King of Saxony’s Bird)有兩道頭羽,其長度是其身體的兩倍,每道頭羽上都飾有珐瑯般淺珍珠藍的羽片,最大的物種可達烏鴉的大小;最小的王風鳥(King Bird of Paradise),體型比知更鳥大一些。事實上,天堂鳥間的相似之處,不過是全身羽毛幾可說是驚人地奢華,且會沉迷於狂野的求偶舞,求偶期間,牠們會向黃褐色的雌鳥展示一身輝煌的羽毛。
這樣美麗而浪漫的生物,肯定值得飛越千里去一睹其風采,多年來我一直懷抱著去看天堂鳥的執念,倫敦動物園已有好多年沒有展出標本,而當時我正考慮從事一次遠征之旅來尋找標本,完全沒有這種鳥類的標本。更有甚者,至少在英國從未播映過野生鳥類表演舞蹈的影片,我決定去新幾內亞嘗試拍攝牠們,並捕捉幾隻活體帶回倫敦。
新幾內亞的國土無邊無際,那裡是全世界最大的非大陸島嶼,首尾綿延超過一千英里,此地有高至阿爾卑斯山的山脈連綿起伏,山坡上並非覆蓋著萬年雪和冰川,而是長滿青苔的巨樹森林。在這些山脈間是滿布叢林的巨大山谷,其中許多實際上處於未開發狀態,向海岸蔓延的則是面積達數百平方英里布滿蚊蚋的沼澤。
在政治上,該島幾乎可均分為兩部分,我們旅途期間,西半部由荷蘭統治,東半部則由澳洲統治。在最近期的領土範圍中,靠近整座島嶼中心的一處高地上,坐落著一處高地山谷,在那裡有個名為農都格(Nondugl)的小型聚落,那裡是澳洲百萬富翁兼慈善家愛德華・霍斯壯爵士(Sir Edward Hallstrom)所建立的一座實驗農場暨動物群落。他建造出巨大的鳥舍,當中所容納的天堂鳥,比全世界所有動物園的總和還要多,居住在該處的人是最偉大的動物收藏家之一、同時也是天堂鳥專家弗雷德・蕭・梅耶(Fred Shaw Mayer),因此如果可以獲得許可,農都格是我們造訪的理想之地。
愛德華爵士多年來一直是倫敦動物園的支持者兼贊助者,當我寫信給他並告訴他,我們的雄心壯志時,他回覆並建議我們,以該聚落為基地,進行為期四個月的探險歷程。
***
查爾斯・拉格斯(Charles Lagus)和我,已經在熱帶地區執行過三次動物搜奇暨拍攝之旅,當我們坐在一架向東奔赴第四段旅程的大型客機上,兩人都陷入新旅程開始之初一直無止盡困擾我們的憂慮——他在腦中確認自己的攝影器材,擔心遺漏了一些重要物品,而我則試圖預期我們到達農都格之前,會面對到的所有官僚障礙,並企圖安慰自己,其中大多數的狀況都已經預見,並且做好萬全準備。
三天內我們抵達澳洲,從雪梨出發,向北飛往新幾內亞,在該島東北岸的萊城,從舒適的四引擎客機下機,然後登上一架不甚豪華的飛機,該班機每週會將補給品運往中部高地的瓦吉谷(Wahgi valley)。
我們坐在形似貨架的鋁製座位上,座位沿著機艙單側設置,長度有飛機全長的一半。前面擺著長長一堆沿著機艙排列的貨物,並用繩索環綁在艙面上,當中包含有信件袋、扶手椅、柴油引擎的大量鑄鐵零件,紙箱裝滿年齡只有一天大的小雞,還有大量塊狀麵包,全部貨物當中還有十六件我們的行李和設備。
同行乘客是七名半裸的巴布亞人,他們僵硬而緊張地坐定,閉口不言又面無表情,目不轉睛盯著堆在他們前方幾英寸的貨物。至少對他們其中幾人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搭飛機——起飛前,我還得向他們示範如何繫上安全帶——他們流淌著幾滴汗水,讓皮膚反射出光芒。
雨水灑在飛機的小窗戶上,雨聲被引擎的轟鳴聲淹沒,往外一看,舉目所及,除了一片灰濛濛外什麼都看不見,當我們向上攀升越過看不見的山巒,飛機開始搖晃抖動。因為天氣很冷,我微微發起抖來,皮膚仍因汗水感到濕黏,萊城的悶熱天氣讓我爆了一身汗。
飛機穩步攀升,直到外面的灰雲開始崩解成疾速飄逝的幻影迷霧,此時機艙突然變亮,好像電燈打開了般。我從其中一扇窗戶望出去,陽光照射在飛機光滑顫抖的機翼上,幾英里外是黑暗的峰頂,如島嶼般在不動的波浪狀雲層中突起。很快地,下方的白色雲層上出現了裂隙,每道裂隙中的景觀都像一幅奇異不真實的風景照,有時露出一條蜿蜒曲折的粼粼河水,有時只是頃刻看到幾幢小屋,但最常見的是平凡的木頭小路。我驚鴻一瞥下方的土地,面積愈來愈大,數量愈來愈多。我們飛過一排排此起彼落、山背如剃刀般的山丘,茂密叢生的樹木,有些光禿但整片褐色的草叢之後,最終融合成一幅連續畫面。一座接著一座山峰從下方掠過,直到高度陡然下降,我們不再飛越蠻荒的絕壁,而是沿著寬闊的綠色山谷飛行,瓦吉谷到了。
這片地面間的許多區域清除成飛機跑道,其中一個降落點即是農都格的實驗農場。我們的班機下降,飛越機場的建築物,有輛小型卡車從一間車庫中駛出,緩慢沿著紅色細線移動,明顯損害了連接房屋和飛機跑道的景觀。我們顛簸著著陸,查爾斯和我硬著頭皮爬出飛機,那輛卡車繞著彎道行駛,駛向蔓草叢生的簡易機場,並發出尖聲,停妥在機翼下方。有兩個男人跳了出來,一人結實魁梧,戴著頂寬邊、沾滿汗水的帽子,穿著卡其色工作服,他自我介紹自己是機場經理法蘭克・彭伯-史密斯(Frank Pemble-Smith),另一位老而瘦的男子則是弗雷德・蕭・梅耶。
我們一起從飛機上卸下攜帶的物品,法蘭克一邊隱隱咒罵,自家農場機械的部分零件並不在這批貨物當中,他花了幾分鐘時間與飛行員交換八卦。然後飛機的引擎重新啟動,在跑道上咆哮著飛向空中,前往下一個停靠站。下一站距離此地僅有四分鐘的飛行時間。法蘭克安排他在巴布亞機場的人手,將我們的裝備裝載到在附近等待的牽引機拖車上,然後他用卡車將我們載離,與他的妻子見面,並到他的屋子裡喝杯茶。
我們坐在他整潔的客廳裡享用司康時,我看見有一個高大、留著濃密鬍鬚的半裸男子,驚人身影一動也不動地站在外頭,他棕色的手臂和長滿毛髮的胸膛被煤煙燻黑,臉上塗有紅色、黃色和綠色的斑點和條紋,腰部圍著編織纖維製成的寬闊硬質腹帶,其正面懸掛著一小段羊毛狀織物,一直延伸到小腿上,他的身後就像古時婦女的裙撐一樣,塞滿了濃密的葉片飾物。他身上裝飾有大量的珍珠貝殼珠寶:由小飾物組成的皮帶以一條細繩繫在腰間;一個巨大的珍珠裝飾胸甲,懸掛在圍繞脖子的繩索上;下巴圍著一塊寬大的新月狀裝飾物,部分隱藏在鬍鬚裡;他身上鑲嵌一根細長的鐮刀狀物,這個物體從珍珠貝殼的邊緣切下,穿過鼻子穿孔的中隔。然而他最令人讚嘆的個人裝飾,既不是珍珠貝殼也並非顏料,而是巨大的羽毛頭飾,頭飾包含至少出自五種不同品種的三十隻天堂鳥羽,有紅寶石色、翡翠色、天鵝絨黑和珐瑯藍,這些驚人的鳥羽構成一頂不可置信的輝煌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