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皇朝風雲實錄:文字血淚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字字珠璣,隱藏殺機;多字少字,驚動天地;
隻字片語,望文生義;寫者無心,讀者有意;
文字可以鼓勵人心,卻也是奸臣、皇帝的迫害手段!
歷史上的文人寫出許多千古留名的文章,然而這些文字背後,有時卻潛藏著可怕的危機——鉤索羅織的冤獄。
因烏台詩案而被貶到黃州的大文豪蘇東坡,曾在詩中提到:「平生文字為吾累」
連蘇東坡都有這樣的感嘆,可見文字獄是多麼可怕!
文字不只是作為溝通的工具,也能變成害人的依據。
一字一句可能讓自己成功,也有可能因此受到殘酷的迫害、刑罰。
這些因文字所造成的牢獄之災,有的是權臣、朋黨間鬥爭的結果,但大多是來自皇帝的猜疑多忌,所以皇帝才是大興文字獄的元凶。
目錄
前言
「種豆」的收穫——楊惲被腰斬
他並非詩人,卻惹下了中國第一樁詩禍!
「《廣陵散》於今絕矣」——嵇康之死
至於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魯迅
史碑之悲
北朝一代名臣,在滿頭尿液的屈辱中被砍頭,這是為什麼?
「平生文字為吾累」——烏台詩案
文字構築了他博大精深的世界,也成了他命運的災星!
《車蓋亭》詩——蔡確的厄運
詩文箋注,並非僅是學者的專利,也成了「文倀」製造他人罪狀的法寶!
詩人皇后——生命在詩禍中凋謝
縊殺一代契丹女傑的素練,竟然是用文字獄的毒藤編織而成。
「罪己」與殺人
一面下「罪己詔」,一面殺人,絕妙的諷刺!
文字獄,權奸的武器
賣國和弄文字獄,是秦檜的兩項「特長」!
朱元璋的「文字學」
明太祖朱元璋竟然成了「文字學家」,可他的「文字學」,卻是殺人的把戲!
波瀾迭起的萬曆文禍
大風起於青萍之末,文禍起於國本之爭。
一代思想家的慘遇
「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叛逆者,用自己的生命,點燃了啟蒙之火!
鮮血飛濺的《明史輯略》案
觸忤了統治者的忌諱,換來的是血肉橫飛!
血染《南山集》
為了修史的念頭,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飄零的大樹——年大將軍得禍於文字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雍正的「出奇料理」
活著的「現行犯」寬免,死了的思想犯戮屍,出奇料理,奇而又奇!
「獨抒己見」的後患
皇上讓你「獨抒己見」,你就敢「獨抒己見」嗎?
「堅磨生」的血光之災
如此荒謬的「賞析」,何往而不「悖逆」!
瘋子逃不脫文字獄的屠刀
有的是魯莽,有的是發瘋……而命運大概很悲慘,不是凌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魯迅《隔膜》
序/導讀
前言
在整個中國封建時代,文字之禍像一條綿延不絕的毒線,從秦朝一直到晚清。它雖然時隱時現、時緩時烈,卻是無法根除的,因為它是封建專制制度的必然產物。作為統治者來說,以文字罪人既是整肅統治階級內部異己力量的法寶,也是消弭平民百姓中異端思想的工具;既是進一步加強皇權的需要,也是鞏固王朝統治的強化劑。
這裡所說的「文字之禍」,概念的內涵基本上同於「文字獄」。所謂「文字獄」,就是封建統治者鎮壓知識分子反抗、加強思想文化專制,從其著作詩文中摘取所謂違礙字句,羅織罪狀,稱為「文字獄」。中國文化史中,不時可見「文字獄」受害者的斑斑紫血!
「文字獄」是因文字得禍的一個統稱,細緻分來,還有一些具體的種類。如因為撰寫史書而忤逆統治者的,可稱為「史禍」;因創作詩詞曲文被挑出「譏謗」、羅織罪名的,可稱為「詩禍」。舉子或考官因考試的文字而罹禍的可稱為「科場案」;而像明初一批因寫賀表謝箋而遭殺身之禍的,可稱為「表箋禍」;因為撰寫私人著作被統治者找出所謂「悖逆文字」的,可稱為「逆書案」……等等。當然,因文字而得禍的情況是多種多樣的,以上所說,是主要的幾種。
文字獄是個歷史性的範疇,它是隨著封建專制制度的產生、強化及衰亡而發生、發展變化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字獄有不同的特點。這是由當日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特殊背景以及君主的個性、心態等諸多因素決定的。因而,對於文字獄的考察研究,離不開對當時社會的整體觀照,尤其是對意識形態特點的了解。
我們不妨就幾例文字獄作一點簡略的分析。
先看春秋時期的齊太史「直筆」事件。
魯襄公二十五年(西元前五四八年),齊莊公與大夫崔杼的夫人棠姜私通,崔杼設計捉姦,包圍了莊公,莊公跳牆逃跑,被崔杼手下的人射死。齊國的太史便記錄道:「崔杼弒其君。」崔杼對這個記載既惱怒又害怕,於是,便把這個史官殺了。太史的弟弟接著寫,還是寫「崔杼弒其君」,也被崔杼殺了;太史的另一個弟弟又接著寫:「崔杼弒其君」,崔杼無可奈何,只得作罷。
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第一例史禍。它反映了春秋時期史官文化的背景。春秋時期,史官的地位非常重要,史官也都以「良史」自期。而「良史」最起碼的要求就是「直筆」,客觀、準確地記載歷史事件,「不虛美,不隱惡」。而要做一個「良史」,就難免與統治者發生衝突。統治者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害怕遺臭萬年,便不許史家直書其事。史家受良心和史德的支配,堅持秉筆直書,結果是與統治者發生衝突,統治者憑藉手中的權勢迫害史家,於是產生了史禍。
北魏崔浩《國書》案,是南北朝時期一起著名的史禍,(本書有較詳的披載)。它的發生就不是「文字」的原因所能範圍的,而是有著深刻的政治、文化、民族的背景。崔浩受命撰寫三十卷卷的編年體《國書》,記載了北魏統治者立國前後的一些史實,後來又將《國書》全書內容都刻在石碑上,立於通衢大道之側,一些鮮卑貴族看到了史碑上刻著鮮卑族統治者的一些不光彩之事,大為惱火,到太武帝那裡告崔浩「暴揚國惡」,結果崔浩受盡屈辱後被太武帝處死,與其聯姻的幾家北方士族也都被滅族。
這件史禍實際涉及到北魏初期鮮卑貴族集團和北方漢人士族集團在利益上、文化上的衝突。崔浩作為漢族士族的代表人物,是處處維護土族利益的,而且在文化上自然是輕視鮮卑人的,鮮卑貴族作為北魏的統治階級,對於漢族士族的自貴自重不能容忍,於是早就把崔浩視為眼中釘,久欲除之。太武帝本來是很欣賞、器重崔浩的才幹的,但他作為鮮卑貴族的最大代表,當然首先要從本民族統治集團的利益出發,恐怕也很難避免崔浩的死。
因詩詞而得禍的詩禍事件,在文字獄中恐怕是數量最多的,很難進行量化的統計分析,因為因詩罹禍者實在太多,而且詩禍最為典型地體現出文字獄的特點:牽強附會,深文周納,妄猜「言外之意」,而定「言內」之罪。
「詩言志」、「詩緣情」,這兩個詩學的基本命題都是非常古老的,概括了詩歌抒情達意的最主要的功能。對於中國古代的士人來說,詩(也包括後起的詞、曲)是最主要的抒情手段。宋人嚴羽對詩所下的定義是很精當的:「詩者,吟詠情性也。」(《滄浪詩話.詩辨》)有的時候,詩可以作為中國古代士大夫實現功利目的的工具,如科舉中的詩賦取士,而詩賦取士也是產生於社會上普遍為詩的風尚之中的。科舉中詩賦取士作為一種導向,和社會上普遍尚詩是互為因果的,詩在更多的情形下,是士人們吟詠情性渲洩內心的最重要的渠道。
人們的情感是複雜的、豐富的、瞬息萬變的,這種情感的豐富性,造成了詩的內涵的豐富性。而在諸種類型的情感中,哀怨、悲憤之情,尤易撥動人們心弦。因而,外國有「憤怒出詩人」的說法,中國有「詩窮而易工」的命題,都是大量創作實踐的總結。南朝詩論家鐘嶸就特別重視怨情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他說:
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詩品序》)
鐘嶸所評價的五言詩中,也多為哀怨之作,如其評《古詩》云:「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評李陵詩「文多淒愴,怨者之流」,評班婕妤詩「詞旨清捷,怨深文綺」;評曹植詩「詞采華茂,情兼雅怨」,等等,此類甚多。這固然有鐘嶸的評詩標準,眼光在其中,但同時也是詩歌創作中的客觀存在。
詩中有這麼多怨艾之情,如果生逢文網嚴密的時代,再有人存心找你的岔子,還不是很容易的事嗎?
詩與政治的聯繫又是密切的,中國士人又有很強的干政意識,「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一入仕途,就勢必關心當朝時政,寫作詩賦,也免不了直接或間接地議論政治。這在唐、宋詩人中尤為普遍,而到明清時期,則被文字獄的血腥嚇怕了,對於時政避之如恐不及。而在直接或間接地表達對某些時政的詩中找出「罪證」來——只要你的政敵盯上了你的作品,也是不難辦到的。
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特徵與闡釋方法,也給文字獄的製造者提供了方便。中國的古詩,講究「弦外之音」、「韻外之致」,推崇「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感。因而古代詩人們作詩,力求意境的朦朧含蓄者多,在極為有限的文字形式中創造更為廣闊的審美時空。而對於詩歌的闡釋則主張「詩無達詁」,也就是說,對於同一首詩可以作全然不同的闡釋。這也為某些文字獄製造者提供了「斷章取義」、曲解其詩的方便。
我們可以從幾樁詩禍中來看這類文字獄的特點。
遼道宗時,懿德皇后蕭觀音生下皇子浚,浚被立為太子,太子長大後參與政事,成為權奸耶律乙辛的障礙。於是,耶律乙辛便設計陷害蕭觀音和太子。他指使別人寫了誨淫的《十香詞》,說是宋朝皇后所為,騙取蕭觀音的墨跡,同時蕭觀音還針對《十香詞》寫了一首《懷古》詩,針砭趙飛燕一類以媚入寵、干政敗國的行為。耶律乙辛卻舉以為蕭觀音與宮中伶人趙惟一的「罪證」,因為在詩中找出了「趙」、「惟」、「一」三個字,這當然就激怒了道宗,蕭觀音被賜自盡,趙惟一被滿門抄斬,禍滅九族。
再如北宋《車蓋亭詩》案。元豐時期宰相蔡確被貶出朝,調知安州,在車蓋亭寫下十首絕句,與他早有嫌隙的吳處厚得到此詩後,為了搆陷他進行了「箋注」,如對第三首絕句的箋注,詩是這樣寫的:
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
睡覺莞爾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
本是一首抒寫閒適心情的作品,吳處厚箋注為:「方今朝廷清明,不知確笑何事?」再有第六首,原詩是這樣的:
風搖熟果時聞落,雨滴余花亦自香。
葉底出巢黃口鬧,波間逐隊小魚忙。
這首詩本是寫夏日景物的,別無深意,吳處厚則箋注為「譏新進用事之人」。蔡確的一組抒寫夏日閒適情懷的絕句,就被曲解為有政治含義的「謗訕朝政」之作。吳處厚以此進行告訐,結果蔡確被再度遠貶嶺南。
詩禍中也有確有譏謗之意的,像蘇軾的《吳中田婦嘆》等作對王安石新法的諷刺,但更多的是這類靠曲解來陷人以罪。
表箋禍是明太祖朱元璋時期一種特有的文字獄。明初制定:凡遇正旦、冬至、萬壽聖節等節日以及其他節日慶典,官府必須上表祝賀,遇有恩典賞賜也須依例上謝恩表。太祖朱元璋文化不高疑心卻大,對表箋中的字句亂加猜疑,妄作附會。他當過和尚,對於「僧」、「髮髡」、「光」等一律忌諱,他參加過農民起義軍,怕被人說成盜賊,對於「盜」、「賊」一律忌諱,而且有些音近的字也都觸犯了他。如表箋中的「則」字,他附會為音近的「賊」,於是本來是一些陳言套語的「作則垂憲」、「建中作則」、「儀則天下」等,都犯了大忌,作者不是被殺頭,就是被腰斬。其他如「法坤」、「天下有道」等等,也都犯忌,作者被殺。一大批表箋禍形成了明代文字獄的第一個高潮。
科場案中不全都是文字獄,有
試閱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瓊州。」這是大詩人蘇軾對自己貶謫生涯的寫照。黃州、惠州、瓊州,是蘇軾後半生的主要貶所。黃州,是他貶謫生涯的「第一站」!
貶謫黃州,與其說是不幸,毋寧說是萬幸。因為,他是從殺頭之罪中又撿回了一條命。摸摸腦袋,恍如再生。
黃州貶謫,是「烏台詩案」的處理結果。而這「烏台詩案」,卻是北宋第一號的文字獄!
「烏台詩案」的背景牽涉到「王安石變法」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很明顯,蘇軾是變法的反對派。蘇軾被捕入獄的罪名即是作詩譏諷新法,謗訕朝廷。但是,「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評價是非常複雜的,遠非可以一概而論,而且也並非本書力所能及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變法與反變法、新黨與舊黨之爭,已逐漸蛻變為權力傾軋的朋黨之爭。「烏台詩案」發生的元豐二年(西元一○七九年),王安石已經第二次罷相,退居於鐘山。而朝中的「新黨」,多是一些已經蛻化的「變法派」。因為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中一些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對,只能起用一班新進之人,這些人資淺位卑,現在有了升進的機會,於是拚命表現,他們不管新法推行的實效如何,總是望風承旨,說新法如何如何受百姓歡迎,王安石是個個性十分倔強、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政治家,他當然只願意聽這些「讚歌」。因此,當時的新黨之中,頗有一些品行不端、為士林所鄙薄的人。譬如呂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拔擢起來的,後來為了攫取權勢,竟不惜出賣王安石,把王安石排擠出朝,自己占據了相位。一手製造「烏台詩案」的李定、舒亶等人,也都是聲名狼藉、為士大夫所不齒的小人。
「烏台」也就是御史台。所謂御史台,是朝廷的糾察機構,權力甚大。當時任御史中丞的是李定,這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長官,李定原是王安石的門生,中了進士以後當過定遠尉、秀州判官等地方官。當王安石推行新法正需要人才的時候,孫覺把他推薦出來,因善於逢迎而很得王安石信任。李定的母親去世,按封建禮制,為人子的應辭去官職,守喪三年,而李定貪戀官位,匿喪不報,這在封建社會尤其是禮教盛行的宋代,可以說是很卑鄙的行為,因而當時議論紛紛。另一個和李定一起羅織蘇軾罪名的御史台官員是舒亶,時任監察御史裡行,此人也以善於深文周納、置人於罪而著稱。他們在蘇軾的詩文中找到了許多譏諷新法的內容,於是萬分興奮,具本參奏,彈劾蘇軾侮慢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參本上奏後,神宗皇帝下詔逮問蘇軾,一場文字獄由此而興。
離開京師已是八、九年了。從杭州到密州,從密州又到徐州,這一年(元豐二年即西元一○七九年)三月,東坡奉調為湖州知州,遠離了政治鬥爭漩渦中心的朝廷,身為太守的東坡並未全然超脫。當年,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和司馬光等人堅決反對,兩派人物政見不同,朝中充滿危機,蘇軾兩次給神宗皇帝上書,力辯新政之不可行,措辭十分激烈,現在想來,都不禁滿身冷汗。「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並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平生文字為吾累」——烏台詩案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事業,黃州、惠州、瓊州。」這是大詩人蘇軾對自己貶謫生涯的寫照。黃州、惠州、瓊州,是蘇軾後半生的主要貶所。黃州,是他貶謫生涯的「第一站」!
貶謫黃州,與其說是不幸,毋寧說是萬幸。因為,他是從殺頭之罪中又撿回了一條命。摸摸腦袋,恍如再生。
黃州貶謫,是「烏台詩案」的處理結果。而這「烏台詩案」,卻是北宋第一號的文字獄!
「烏台詩案」的背景牽涉到「王安石變法」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很明顯,蘇軾是變法的反對派。蘇軾被捕入獄的罪名即是作詩譏諷新法,謗訕朝廷。但是,「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評價是非常複雜的,遠非可以一概而論,而且也並非本書力所能及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變法與反變法、新黨與舊黨之爭,已逐漸蛻變為權力傾軋的朋黨之爭。「烏台詩案」發生的元豐二年(西元一○七九年),王安石已經第二次罷相,退居於鐘山。而朝中的「新黨」,多是一些已經蛻化的「變法派」。因為王安石推行新法,遭到朝中一些元老重臣的激烈反對,只能起用一班新進之人,這些人資淺位卑,現在有了升進的機會,於是拚命表現,他們不管新法推行的實效如何,總是望風承旨,說新法如何如何受百姓歡迎,王安石是個個性十分倔強、聽不得不同意見的政治家,他當然只願意聽這些「讚歌」。因此,當時的新黨之中,頗有一些品行不端、為士林所鄙薄的人。譬如呂惠卿,本是王安石一手拔擢起來的,後來為了攫取權勢,竟不惜出賣王安石,把王安石排擠出朝,自己占據了相位。一手製造「烏台詩案」的李定、舒亶等人,也都是聲名狼藉、為士大夫所不齒的小人。「烏台」也就是御史台。所謂御史台,是朝廷的糾察機構,權力甚大。當時任御史中丞的是李定,這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長官,李定原是王安石的門生,中了進士以後當過定遠尉、秀州判官等地方官。當王安石推行新法正需要人才的時候,孫覺把他推薦出來,因善於逢迎而很得王安石信任。李定的母親去世,按封建禮制,為人子的應辭去官職,守喪三年,而李定貪戀官位,匿喪不報,這在封建社會尤其是禮教盛行的宋代,可以說是很卑鄙的行為,因而當時議論紛紛。另一個和李定一起羅織蘇軾罪名的御史台官員是舒亶,時任監察御史裡行,此人也以善於深文周納、置人於罪而著稱。他們在蘇軾的詩文中找到了許多譏諷新法的內容,於是萬分興奮,具本參奏,彈劾蘇軾侮慢朝廷,甚至有不臣之心。參本上奏後,神宗皇帝下詔逮問蘇軾,一場文字獄由此而興。
離開京師已是八、九年了。從杭州到密州,從密州又到徐州,這一年(元豐二年即西元一○七九年)三月,東坡奉調為湖州知州,遠離了政治鬥爭漩渦中心的朝廷,身為太守的東坡並未全然超脫。當年,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和司馬光等人堅決反對,兩派人物政見不同,朝中充滿危機,蘇軾兩次給神宗皇帝上書,力辯新政之不可行,措辭十分激烈,現在想來,都不禁滿身冷汗。「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並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上書的時候,東坡甚至懷了必死的決心,「俯伏引領,以待誅殛」。但皇上是寬厚的,並沒有把東坡治罪,但王安石的親戚謝景溫(當時任侍御史知雜事),藉機彈劾蘇軾,說他丁憂歸蜀的途中,濫用政府的衛兵乘舟商販。王安石於是派人窮究此事,但終無所得,只好不了了之。東坡心裡明白,這場風波,當然是因他反對新法的態度引起的。他覺得在朝廷裡很難乾下去,於是便自請外放,熙寧四年(西元一○七一年),他被派做杭州通判,於是帶著眷屬來到了人間麗都——杭州。
杭州也好,密州也好,徐州也好,東坡改變不了他那外向的性格,也改變不了對朝政的關心。他時常把酒臨風,夜泛西湖,笑聲朗朗地吟誦著新作的詩篇,西子湖畔,望湖樓上,他留下了多少千古傳誦的秀句佳什: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飲湖上初晴後雨》)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這些詩作幾乎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作為一個詩人,杭州給了他那麼多揮之不去、寫之不竭的詩材,而東坡也沒有辜負這上蒼的賜予。
然而,東坡並非僅是一個詩酒流連的文人,並不是我們印象中那個總是舉著酒杯,吟著「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謫仙人」,他還是一個深切關心民生疾苦的地方官,在幾任知州的位上,他為百姓辦了許多實事。在徐州,他組織軍民抗洪搶險,修建防洪堤壩,深受百姓愛戴。
作為父母官,他不時地深入鄉村,考察百姓的生計與生產狀況。「青苗法」等新法的一些政策,由於有關官員為了邀功請賞,爭取政績,在推行中採取了強行分配的硬性規定,給百姓造成了很多痛苦。和著對新法的不滿,蘇軾在他的詩中屢屢排遣這種情緒。如果說「諷刺新法」,像《吳中田婦嘆》這樣一些詩是並不冤枉的。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風霜來幾時。
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
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
汗流肩赪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
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
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這裡不僅描繪出青苗法、免役法所造成的流弊,而且用漢朝的龔遂、黃霸這樣恤民寬政的好官來反語譏刺推行新法的官員,這自然難免使新黨諸人如芒刺在背了。
蘇軾是天下聞名的大詩人,他的詩一寫出來便不脛而走,很快便傳到京師。新黨人物對蘇軾的詩文中的「刺」深為不滿,也多方留意。於是他們一天天在收集蘇軾的材料。
蘇軾的口沒有遮攔,蘇軾的筆也沒有遮攔,他對胞弟蘇轍說過:「我如果覺得某件事情不對,就像飯菜裡發現一隻蒼蠅,非吐出來不可。」而且,他經常大開玩笑,語涉譏刺,常常使用雙關語,使一些謹慎的人聽了都覺得提心吊膽!
剛到湖州任上,他就給神宗皇帝上了一份謝表,表中寫道:「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這份謝表也惹出了麻煩,謝表中所說的「新進」,就是指李定這類新黨中的得勢新貴。這個字眼當然不無嘲諷之意,李定得知,甚為惱火。「這不明擺著是罵我們嗎?豈可忍之!不除此人,不解我心頭之恨!」於是,李定、舒亶、何正臣這幾個御史台官員,便摘出謝表中的幾句,還有蘇軾所作《靈璧張氏園亭記》中「古云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等語,鍛成罪狀,說蘇軾「侮慢聖上」,奏請逮捕治罪。
御史台的差吏,奉了皇帝的詔命,策馬飛奔,直往湖州。而湖州太守蘇軾,還在書房裡吟詩,哪裡知道大禍即將臨頭!
七月上旬,剛剛下過幾場暴雨,壓住了暑熱;現在天氣轉晴,太陽出來,轉眼間又熱了起來。蘇軾想起來自己珍藏的那些字畫,自從到了湖州以後,從未拿出來曬過,只恐連日陰雨,使書畫受潮,於是,便命人把它們都拿出來,放在院子裡曝曬。
眼前這幅墨竹,是文與可的手跡。文與可即文同是當朝著名的大畫家,湖州畫派的開創者。這位名畫家是蘇軾的表兄,兩人情誼甚篤。蘇軾也善畫墨竹,老師恰正是文與可。文與可不僅是一位畫家,在為官任上也是一位體察民瘼的好官。在政治傾向上,和蘇軾是相同的,不過文與可不像蘇軾那樣外溢,所以表面看來較為超脫。文與可也以蘇軾為知己,他說:「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蘇軾一邊看著文與可的墨竹,一邊想起先前的趣事。文與可畫竹,開始時不自貴重,無論誰請他作畫,他都馬上給人家畫;後來求畫的人太多,都拿著縑素求他的墨竹。文與可畫得太累了,便把這些縑素扔在地上,罵道:「乾脆拿這些東西做襪子吧!」後來文與可從洋州太守任上罷職回來,蘇軾正在徐州當太守,文與可給東坡寫信告訴他:「我近來告訴那些士大夫:『墨竹一派,徐州蘇軾所作甚佳,可往求之。』這些襪材,這回可要堆到你那裡去了。」又在信尾題詩一首,其中有「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蘇軾覆信說:「竹長萬尺,應當用絹兩百五十匹,知兄倦於筆硯,就把這些素絹給我吧!」文與可看了以後,笑道:「我是隨便寫的,真有二百五十匹絹,我就用它來買田歸老了。」可是,就在當年的正月二十日,文與可病逝於陳州,蘇軾想到此處,手撫畫卷,有淚如傾。
上書的時候,東坡甚至懷了必死的決心,「俯伏引領,以待誅殛」。但皇上是寬厚的,並沒有把東坡治罪,但王安石的親戚謝景溫(當時任侍御史知雜事),藉機彈劾蘇軾,說他丁憂歸蜀的途中,濫用政府的衛兵乘舟商販。王安石於是派人窮究此事,但終無所得,只好不了了之。東坡心裡明白,這場風波,當然是因他反對新法的態度引起的。他覺得在朝廷裡很難乾下去,於是便自請外放,熙寧四年(西元一○七一年),他被派做杭州通判,於是帶著眷屬來到了人間麗都——杭州。
杭州也好,密州也好,徐州也好,東坡改變不了他那外向的性格,也改變不了對朝政的關心。他時常把酒臨風,夜泛西湖,笑聲朗朗地吟誦著新作的詩篇,西子湖畔,望湖樓上,他留下了多少千古傳誦的秀句佳什: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飲湖上初晴後雨》)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這些詩作幾乎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作為一個詩人,杭州給了他那麼多揮之不去、寫之不竭的詩材,而東坡也沒有辜負這上蒼的賜予。
然而,東坡並非僅是一個詩酒流連的文人,並不是我們印象中那個總是舉著酒杯,吟著「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的「謫仙人」,他還是一個深切關心民生疾苦的地方官,在幾任知州的位上,他為百姓辦了許多實事。在徐州,他組織軍民抗洪搶險,修建防洪堤壩,深受百姓愛戴。
作為父母官,他不時地深入鄉村,考察百姓的生計與生產狀況。「青苗法」等新法的一些政策,由於有關官員為了邀功請賞,爭取政績,在推行中採取了強行分配的硬性規定,給百姓造成了很多痛苦。和著對新法的不滿,蘇軾在他的詩中屢屢排遣這種情緒。如果說「諷刺新法」,像《吳中田婦嘆》這樣一些詩是並不冤枉的。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風霜來幾時。
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
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
汗流肩赪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
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
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這裡不僅描繪出青苗法、免役法所造成的流弊,而且用漢朝的龔遂、黃霸這樣恤民寬政的好官來反語譏刺推行新法的官員,這自然難免使新黨諸人如芒刺在背了。
蘇軾是天下聞名的大詩人,他的詩一寫出來便不脛而走,很快便傳到京師。新黨人物對蘇軾的詩文中的「刺」深為不滿,也多方留意。於是他們一天天在收集蘇軾的材料。
蘇軾的口沒有遮攔,蘇軾的筆也沒有遮攔,他對胞弟蘇轍說過:「我如果覺得某件事情不對,就像飯菜裡發現一隻蒼蠅,非吐出來不可。」而且,他經常大開玩笑,語涉譏刺,常常使用雙關語,使一些謹慎的人聽了都覺得提心吊膽!
剛到湖州任上,他就給神宗皇帝上了一份謝表,表中寫道:「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這份謝表也惹出了麻煩,謝表中所說的「新進」,就是指李定這類新黨中的得勢新貴。這個字眼當然不無嘲諷之意,李定得知,甚為惱火。「這不明擺著是罵我們嗎?豈可忍之!不除此人,不解我心頭之恨!」於是,李定、舒亶、何正臣這幾個御史台官員,便摘出謝表中的幾句,還有蘇軾所作《靈璧張氏園亭記》中「古云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等語,鍛成罪狀,說蘇軾「侮慢聖上」,奏請逮捕治罪。
御史台的差吏,奉了皇帝的詔命,策馬飛奔,直往湖州。而湖州太守蘇軾,還在書房裡吟詩,哪裡知道大禍即將臨頭!
七月上旬,剛剛下過幾場暴雨,壓住了暑熱;現在天氣轉晴,太陽出來,轉眼間又熱了起來。蘇軾想起來自己珍藏的那些字畫,自從到了湖州以後,從未拿出來曬過,只恐連日陰雨,使書畫受潮,於是,便命人把它們都拿出來,放在院子裡曝曬。
蘇軾正在怔怔地想著心事,家人忽來報說弟弟子由派人來了。東坡把他請進客廳,那個人氣喘吁吁,身上沾滿了灰塵,急急地向蘇軾報告說御史台派人來逮他,請他速作準備。原來蘇軾的好友王詵駙馬先在朝廷聽到了消息,連忙派人到南京找到子由,請他設法通知蘇軾,於是,子由派來的信使提前一步趕到了。
聽了這個消息,蘇軾愕然,半天說不出話來。李定那些人的敵意,蘇軾是知道的,可沒有想到災禍來得如此之速。家裡人勸他:「老爺,還是暫避一時為好,收拾一下,趕快走吧。」蘇軾長嘆一聲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縱使躲到天涯海角也無濟於事,徒然連累家人和朋友,不如泰然受之吧。」
不到兩個時辰,御史台的差吏到了。根本不容通報,這位御史台的官差皇甫遵帶著士兵便闖了進來。登時庭院裡充滿了緊張、恐怖的氣氛,四個士兵分立兩旁,手裡握著腰刀,真是如臨大敵一般。蘇軾身穿太守的官服迎了出來。因為有了思想準備,他的臉色很鎮定。皇甫遵當堂宣布了皇帝的詔命,要蘇軾跟他即刻動身。
蘇軾說:「我知道我冒犯了朝廷,早晚有此一劫,恐怕難逃一死,請允許我同我的家人告別。」
老爺被朝廷逮捕,全家人驚懼萬分,無不哭泣,蘇太太哭得最是傷心,看到官差如此凶悍,大家都感到老爺此一去是凶多而吉少,恐怕成了永別了。
蘇軾自有蘇軾的幽默,即便是在如此嚴峻的時刻,他仍然不失這種幽默的性格。他用手為太太拭去眼淚,笑著說:「夫人,臨別我給你講個掌故聽吧。宋真宗東封泰山,歸來途中,遍訪天下隱者,得到杞人楊朴,楊朴本以能詩著名。真宗召見楊朴,問他能否作詩,他回答說:『不能。』真宗又問他:『臨行有人作詩送你嗎?』楊朴又回答說:『也沒有。惟有臣妻寫了一首絕句:且休落拓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大笑,賜還歸山,並且給其一子官做,以為養資。那麼現在夫人難道不能也像楊處士妻子一樣,寫一首詩送我嗎?」聽了丈夫的趣話,蘇太太忍俊不禁,破涕為笑了。
長子蘇邁,陪同父親一起隨押解的官差到京師去,父子踏上這凶險的路程,家人望著他們的背影,止不住又哭聲一片……。
剛剛行到宿州,御史台的命令又下,搜查蘇軾家中文稿。於是,州郡長官望風希旨,派遣如狼似虎的吏人。到了蘇府,團團圍住,把蘇府上下翻了個底朝天,將所有詩稿、文稿盡行搜去。蘇軾家人幾乎被嚇死。差人走後,蘇太太氣得哭罵:「就是因為好著書,才惹出來這些災難,把人嚇得這樣!」於是,把書燒了大半。待案件結束後,蘇軾回到家中,搜尋整理,已經損失了十之七八了,詩人禁不住跌足嘆息。
押解赴京的路上,蘇軾以為這次自己必死無疑了,便起了自殺的念頭,過揚子江時,便要自投江中,一死了之,但是差吏看管甚緊,使他沒有死成。到了御史台的監獄裡,他又要以絕食求死,後來神宗派使者到獄中,對獄吏有所叮囑約束,獄吏對蘇軾較為客氣,才使蘇軾打消了這個念頭。
聽到這位大詩人被朝廷逮捕拿問,湖州、徐州、杭州一帶百姓無不憂慮。於是,他們為蘇軾作解厄齋一個多月。
蘇軾從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關進御史台監獄,然後便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天時間的審訊。
昔為太守,今為囚徒。李定看著坐在被告席上的蘇軾,心中不禁一陣得意,不過表面上裝得十分嚴肅。
李定拿出蘇軾在杭州時期前後的詩作百餘首,要詩人承認是在惡意攻擊朝廷,最明顯的要數寫在杭州的《山村五絕》了。如第二首: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
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催耕。
御史們指摘這是諷刺朝廷鹽法峻刻,不便於民,當時販私鹽者多帶刀仗,詩中取西漢時龔遂故事,意謂但使鹽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劍而買牛買犢,則自力耕耘不勞勸督。這不是嘲諷鹽法之苛嗎?
如第三首: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御史們指出,這首詩的諷意更為明顯。詩中意謂: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當時鹽法太峻,僻遠地區沒有鹽吃,動經數月。古之聖人,能夠聞韶樂而忘味,山中小民,又怎可淡而無鹽?其實,蘇軾所寫,乃是當時實錄。蘇軾曾記述說:「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有數月食無鹽者。」(《上文侍中論榷鹽書》)這是當時朝廷鹽法峻刻所致。
如第四首:
杖黎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御史們指出,這是諷刺青苗法、助役法之不便。詩中說農民得了青苗錢,馬上就在城中胡亂花了。
再如《游風水洞二首》中「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之句,是誹謗朝中大臣為小人爭進;《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其四有句:「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戲子由》詩中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諷刺新法之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前後所摘,有七八十處。
蘇軾渾身有口也無法辯解,只好承認詩中多有批評譏刺新法之意。
眼前這幅墨竹,是文與可的手跡。文與可即文同是當朝著名的大畫家,湖州畫派的開創者。這位名畫家是蘇軾的表兄,兩人情誼甚篤。蘇軾也善畫墨竹,老師恰正是文與可。文與可不僅是一位畫家,在為官任上也是一位體察民瘼的好官。在政治傾向上,和蘇軾是相同的,不過文與可不像蘇軾那樣外溢,所以表面看來較為超脫。文與可也以蘇軾為知己,他說:「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蘇軾一邊看著文與可的墨竹,一邊想起先前的趣事。文與可畫竹,開始時不自貴重,無論誰請他作畫,他都馬上給人家畫;後來求畫的人太多,都拿著縑素求他的墨竹。文與可畫得太累了,便把這些縑素扔在地上,罵道:「乾脆拿這些東西做襪子吧!」後來文與可從洋州太守任上罷職回來,蘇軾正在徐州當太守,文與可給東坡寫信告訴他:「我近來告訴那些士大夫:『墨竹一派,徐州蘇軾所作甚佳,可往求之。』這些襪材,這回可要堆到你那裡去了。」又在信尾題詩一首,其中有「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蘇軾覆信說:「竹長萬尺,應當用絹兩百五十匹,知兄倦於筆硯,就把這些素絹給我吧!」文與可看了以後,笑道:「我是隨便寫的,真有二百五十匹絹,我就用它來買田歸老了。」可是,就在當年的正月二十日,文與可病逝於陳州,蘇軾想到此處,手撫畫卷,有淚如傾。
蘇軾正在怔怔地想著心事,家人忽來報說弟弟子由派人來了。東坡把他請進客廳,那個人氣喘吁吁,身上沾滿了灰塵,急急地向蘇軾報告說御史台派人來逮他,請他速作準備。原來蘇軾的好友王詵駙馬先在朝廷聽到了消息,連忙派人到南京找到子由,請他設法通知蘇軾,於是,子由派來的信使提前一步趕到了。
聽了這個消息,蘇軾愕然,半天說不出話來。李定那些人的敵意,蘇軾是知道的,可沒有想到災禍來得如此之速。家裡人勸他:「老爺,還是暫避一時為好,收拾一下,趕快走吧。」蘇軾長嘆一聲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縱使躲到天涯海角也無濟於事,徒然連累家人和朋友,不如泰然受之吧。」不到兩個時辰,御史台的差吏到了。根本不容通報,這位御史台的官差皇甫遵帶著士兵便闖了進來。登時庭院裡充滿了緊張、恐怖的氣氛,四個士兵分立兩旁,手裡握著腰刀,真是如臨大敵一般。蘇軾身穿太守的官服迎了出來。因為有了思想準備,他的臉色很鎮定。皇甫遵當堂宣布了皇帝的詔命,要蘇軾跟他即刻動身。
蘇軾說:「我知道我冒犯了朝廷,早晚有此一劫,恐怕難逃一死,請允許我同我的家人告別。」
老爺被朝廷逮捕,全家人驚懼萬分,無不哭泣,蘇太太哭得最是傷心,看到官差如此凶悍,大家都感到老爺此一去是凶多而吉少,恐怕成了永別了。
蘇軾自有蘇軾的幽默,即便是在如此嚴峻的時刻,他仍然不失這種幽默的性格。他用手為太太拭去眼淚,笑著說:「夫人,臨別我給你講個掌故聽吧。宋真宗東封泰山,歸來途中,遍訪天下隱者,得到杞人楊朴,楊朴本以能詩著名。真宗召見楊朴,問他能否作詩,他回答說:『不能。』真宗又問他:『臨行有人作詩送你嗎?』楊朴又回答說:『也沒有。惟有臣妻寫了一首絕句:且休落拓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大笑,賜還歸山,並且給其一子官做,以為養資。那麼現在夫人難道不能也像楊處士妻子一樣,寫一首詩送我嗎?」聽了丈夫的趣話,蘇太太忍俊不禁,破涕為笑了。
長子蘇邁,陪同父親一起隨押解的官差到京師去,父子踏上這凶險的路程,家人望著他們的背影,止不住又哭聲一片……。
剛剛行到宿州,御史台的命令又下,搜查蘇軾家中文稿。於是,州郡長官望風希旨,派遣如狼似虎的吏人。到了蘇府,團團圍住,把蘇府上下翻了個底朝天,將所有詩稿、文稿盡行搜去。蘇軾家人幾乎被嚇死。差人走後,蘇太太氣得哭罵:「就是因為好著書,才惹出來這些災難,把人嚇得這樣!」於是,把書燒了大半。待案件結束後,蘇軾回到家中,搜尋整理,已經損失了十之七八了,詩人禁不住跌足嘆息。
押解赴京的路上,蘇軾以為這次自己必死無疑了,便起了自殺的念頭,過揚子江時,便要自投江中,一死了之,但是差吏看管甚緊,使他沒有死成。到了御史台的監獄裡,他又要以絕食求死,後來神宗派使者到獄中,對獄吏有所叮囑約束,獄吏對蘇軾較為客氣,才使蘇軾打消了這個念頭。聽到這位大詩人被朝廷逮捕拿問,湖州、徐州、杭州一帶百姓無不憂慮。於是,他們為蘇軾作解厄齋一個多月。
蘇軾從七月二十八日被捕,八月十八日關進御史台監獄,然後便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天時間的審訊。
昔為太守,今為囚徒。李定看著坐在被告席上的蘇軾,心中不禁一陣得意,不過表面上裝得十分嚴肅。
李定拿出蘇軾在杭州時期前後的詩作百餘首,要詩人承認是在惡意攻擊朝廷,最明顯的要數寫在杭州的《山村五絕》了。如第二首: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
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催耕。
御史們指摘這是諷刺朝廷鹽法峻刻,不便於民,當時販私鹽者多帶刀仗,詩中取西漢時龔遂故事,意謂但使鹽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劍而買牛買犢,則自力耕耘不勞勸督。這不是嘲諷鹽法之苛嗎?
如第三首: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御史們指出,這首詩的諷意更為明顯。詩中意謂: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當時鹽法太峻,僻遠地區沒有鹽吃,動經數月。古之聖人,能夠聞韶樂而忘味,山中小民,又怎可淡而無鹽?其實,蘇軾所寫,乃是當時實錄。蘇軾曾記述說:「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有數月食無鹽者。」(《上文侍中論榷鹽書》)這是當時朝廷鹽法峻刻所致。
如第四首:
杖黎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御史們指出,這是諷刺青苗法、助役法之不便。詩中說農民得了青苗錢,馬上就在城中胡亂花了。
再如《游風水洞二首》中「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之句,是誹謗朝中大臣為小人爭進;《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其四有句:「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戲子由》詩中有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諷刺新法之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前後所摘,有七八十處。
蘇軾渾身有口也無法辯解,只好承認詩中多有批評譏刺新法之意。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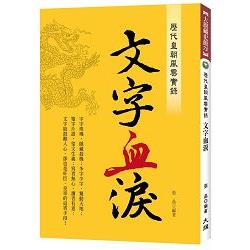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