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搭車去柏林:在路上的頹廢壯遊,給自己的成人禮。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這是一趟受經典文學《在路上》啟發而展開的旅程──
★88個陌生司機,100天的未知旅行,16000公里的搭便車路途,從北京到柏林。
★旅遊衛視《行者》電視專題創下最高收視率,豆瓣史上評分最高的中國公路紀錄片圖文全紀錄。
★當當網網友五顆星滿分評價!
「我們離年輕這一詞彙越來越遠,去搭車旅行、去在路上,更像一場遲來的成人禮。完全沒人知道我們的生命,除了不可避免地趨向衰老外,還將有何遭遇……。」(《在路上》)
美籍中國小伙子谷岳是搭車計畫的始作俑者,紀錄片導演劉暢陪著在路上不斷傻樂。在2009年夏天,兩人一路只依靠陌生人的幫助,從北京出發,用招手搭車的方式前進,穿越中國、中亞和歐洲,耗時100天、行進16000公里,最終抵達德國柏林,完成了一次史無前例、艱辛又浪漫的旅程。而在那裡,等待他們的是谷岳的女友伊卡。
出發前,谷岳說:「有些事情現在不去做,就永遠不會做了。」
抵達終點後,劉暢說:「我在想,無論多麼難的事,如果你當一個旁觀者,就覺得肯定很難,但如果身體力行,多麼難的事情都會慢慢過去。」
◎踏出最艱難的第一步
每片土地的風都是不同的,因為味道,因為心情,因為一切都是未知。
雖然十年的拍片生涯中也經常出門,足跡基本上踏遍了大半個中國,但一直有著團隊的支持和精心的計畫。這次和谷岳一起,行程中太多要靠自己去解決和完成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恨不得把家也一起背走。沒錯,對背包客來講,這兩個歪歪扭扭的包就是家了。這種隨意旅行的方式,我一直嚮往很久,我痛恨充滿計畫的行程,彷彿一眼就可以看到結局的電影。然而,真的要上路時,我可以聽到來自遙遠內心的咚咚鼓聲。
◎從北京到柏林
在三個月的旅途中,他們遇到各種問題,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在他們的車裡、家裡,遭遇不同的人生。有的是社會底層的卡車司機,有的是閒適自得的農村居民,有裡海邊獨臂豪飲的俄羅斯水手,有年輕小情侶,也有土耳其豪放熱誠的富二代。
※ 搭車之最慢:從吐魯番到庫車的一輛大貨車,620公里花了18個小時。
※ 搭車之最快:從布達佩斯到布拉格,530公里耗時3小時。那是一輛德國老闆的豪華款輝騰,時速200公里。
※ 搭車等待時間最長:兩天。在羅馬尼亞離匈牙利邊境只有19公里的地方,等了兩天。
◎旅行可以與年紀無關,可以與收入無關,你關不住心裡對世界的好奇心,就關不住對旅行的渴望。
旅程就是發現別人怎麼生活,你會感覺到他們的努力,體會到他們面對生活的勇氣。到國外以後看看另外一些人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看他們怎麼去排除生活中的壓力,追尋生活中的美好,你發現得越多,你的心情也會越來越開朗。旅行和行走是特別鼓舞人的,而且非常簡單,只要你肯去做就行了。你不需要失去所有,只要有追求原來自我的勇氣就夠了。
★88個陌生司機,100天的未知旅行,16000公里的搭便車路途,從北京到柏林。
★旅遊衛視《行者》電視專題創下最高收視率,豆瓣史上評分最高的中國公路紀錄片圖文全紀錄。
★當當網網友五顆星滿分評價!
「我們離年輕這一詞彙越來越遠,去搭車旅行、去在路上,更像一場遲來的成人禮。完全沒人知道我們的生命,除了不可避免地趨向衰老外,還將有何遭遇……。」(《在路上》)
美籍中國小伙子谷岳是搭車計畫的始作俑者,紀錄片導演劉暢陪著在路上不斷傻樂。在2009年夏天,兩人一路只依靠陌生人的幫助,從北京出發,用招手搭車的方式前進,穿越中國、中亞和歐洲,耗時100天、行進16000公里,最終抵達德國柏林,完成了一次史無前例、艱辛又浪漫的旅程。而在那裡,等待他們的是谷岳的女友伊卡。
出發前,谷岳說:「有些事情現在不去做,就永遠不會做了。」
抵達終點後,劉暢說:「我在想,無論多麼難的事,如果你當一個旁觀者,就覺得肯定很難,但如果身體力行,多麼難的事情都會慢慢過去。」
◎踏出最艱難的第一步
每片土地的風都是不同的,因為味道,因為心情,因為一切都是未知。
雖然十年的拍片生涯中也經常出門,足跡基本上踏遍了大半個中國,但一直有著團隊的支持和精心的計畫。這次和谷岳一起,行程中太多要靠自己去解決和完成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恨不得把家也一起背走。沒錯,對背包客來講,這兩個歪歪扭扭的包就是家了。這種隨意旅行的方式,我一直嚮往很久,我痛恨充滿計畫的行程,彷彿一眼就可以看到結局的電影。然而,真的要上路時,我可以聽到來自遙遠內心的咚咚鼓聲。
◎從北京到柏林
在三個月的旅途中,他們遇到各種問題,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在他們的車裡、家裡,遭遇不同的人生。有的是社會底層的卡車司機,有的是閒適自得的農村居民,有裡海邊獨臂豪飲的俄羅斯水手,有年輕小情侶,也有土耳其豪放熱誠的富二代。
※ 搭車之最慢:從吐魯番到庫車的一輛大貨車,620公里花了18個小時。
※ 搭車之最快:從布達佩斯到布拉格,530公里耗時3小時。那是一輛德國老闆的豪華款輝騰,時速200公里。
※ 搭車等待時間最長:兩天。在羅馬尼亞離匈牙利邊境只有19公里的地方,等了兩天。
◎旅行可以與年紀無關,可以與收入無關,你關不住心裡對世界的好奇心,就關不住對旅行的渴望。
旅程就是發現別人怎麼生活,你會感覺到他們的努力,體會到他們面對生活的勇氣。到國外以後看看另外一些人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看他們怎麼去排除生活中的壓力,追尋生活中的美好,你發現得越多,你的心情也會越來越開朗。旅行和行走是特別鼓舞人的,而且非常簡單,只要你肯去做就行了。你不需要失去所有,只要有追求原來自我的勇氣就夠了。
名人推薦
小鵬(《背包十年》作者)、何(南犬)瑞(背包客棧站長)、唐宏安(旅遊作家、旅遊廣播節目主持人)、陳岳賢(自助旅遊達人、《我愛背包客》作者)、褚士瑩(國際NGO工作者)、劉航(《行者》電視專題創辦人、蔡景暉(Lonely Planet 中國市場代表)。
生活是一條長河,奔走流轉。對旅行者來說,這條河的歸宿是海洋,因為那裡的自由無邊無際。很幸運,我和劉暢都找到了正確的出口。──小鵬(《背包十年》作者)
一段由北京的記錄片導演寫下,由北京搭車至柏林的經歷,筆觸生動、真實。閱讀本書,除了能和作者一同經歷所遇到的人物和事件外,更能發現旅人眼中的相同與不同。──何(南犬)瑞(背包客棧站長)
看到最後我發現這本書不只是個流浪的故事,而是個三十歲失去夢想的紀錄片導演找回自己熱情靈魂的故事。──唐宏安(旅遊作家、旅遊廣播節目主持人。)
其實做搭便車的旅行,並不是要證明自己有多行,只是要藉由這樣子的方式,凸顯出「自助旅行」可以是多元化、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陳岳賢(自助旅遊達人、《我愛背包客》作者)
憑著對於世界的想像,跟一本過期好幾年的旅行指南書,一路從北京搭車去柏林,亂七八糟、顛顛倒倒,以為這一路會看清世界,結果看得最清的是自己。──褚士瑩(國際NGO工作者)
一次只有終點確定,其餘所有的一切都充滿未知與期待的旅行是不是就是人生的縮影,每個人都應該去尋找自己的成人禮。──劉航(《行者》電視專題創辦人)
對於年輕人來說,人生到底有幾種可能?其實人生就是一次旅行,你期待怎樣的旅行,就會有怎樣的人生。──蔡景暉(Lonely Planet 中國市場代表)
生活是一條長河,奔走流轉。對旅行者來說,這條河的歸宿是海洋,因為那裡的自由無邊無際。很幸運,我和劉暢都找到了正確的出口。──小鵬(《背包十年》作者)
一段由北京的記錄片導演寫下,由北京搭車至柏林的經歷,筆觸生動、真實。閱讀本書,除了能和作者一同經歷所遇到的人物和事件外,更能發現旅人眼中的相同與不同。──何(南犬)瑞(背包客棧站長)
看到最後我發現這本書不只是個流浪的故事,而是個三十歲失去夢想的紀錄片導演找回自己熱情靈魂的故事。──唐宏安(旅遊作家、旅遊廣播節目主持人。)
其實做搭便車的旅行,並不是要證明自己有多行,只是要藉由這樣子的方式,凸顯出「自助旅行」可以是多元化、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陳岳賢(自助旅遊達人、《我愛背包客》作者)
憑著對於世界的想像,跟一本過期好幾年的旅行指南書,一路從北京搭車去柏林,亂七八糟、顛顛倒倒,以為這一路會看清世界,結果看得最清的是自己。──褚士瑩(國際NGO工作者)
一次只有終點確定,其餘所有的一切都充滿未知與期待的旅行是不是就是人生的縮影,每個人都應該去尋找自己的成人禮。──劉航(《行者》電視專題創辦人)
對於年輕人來說,人生到底有幾種可能?其實人生就是一次旅行,你期待怎樣的旅行,就會有怎樣的人生。──蔡景暉(Lonely Planet 中國市場代表)
目錄
推薦序
.反著活,倒著走∕國際NGO工作者 褚士瑩
.不是「旅行」,而是「流浪」∕旅遊作家 唐宏安
.因為無法預期,讓回憶更美好∕自助旅遊達人 陳岳賢
前言 為了「在路上」而展開的冒險旅程∕劉暢
第一章 因為孤獨,所以旅行
清晨五點半的地鐵五號線
穀嶽的三分鐘
第二章 只要邁出最艱難的第一步
6月8日,從后海出發
大雨中的第一次搭車
搭車4小時
搭車10小時
搭車16小時
搭車20小時
搭車24小時
行駛在公路上的水手
坐卡車一路向西
穿越茫茫戈壁
中途返京
新疆重逢,再次出發
涉險過關
第三章 MY WAY
心中的馬國
住在集裝箱房子裡的人
赤身跳湖
可愛的吉爾吉斯斯坦胖大媽
簡單而幸福的牧馬人
24小時夜奔
有豔沒有遇
世界盡頭
俄羅斯獨臂水手
幽靈夜車
消失了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
飛車驚魂
忐忑土耳其
英俊善良的富二代
又一次小別
第四章 青年的世界
從雪山穿越到羅馬尼亞
在孤兒院做義工
五星級的搭車客
三十歲以後才感覺年輕
和吉普賽女郎共舞
遇上了搭車的競爭對手
無法融入的布達佩斯
布拉格,傻子才悲傷
第五章 三十歲的成人禮
寫在後面:2010年,一路向南
.反著活,倒著走∕國際NGO工作者 褚士瑩
.不是「旅行」,而是「流浪」∕旅遊作家 唐宏安
.因為無法預期,讓回憶更美好∕自助旅遊達人 陳岳賢
前言 為了「在路上」而展開的冒險旅程∕劉暢
第一章 因為孤獨,所以旅行
清晨五點半的地鐵五號線
穀嶽的三分鐘
第二章 只要邁出最艱難的第一步
6月8日,從后海出發
大雨中的第一次搭車
搭車4小時
搭車10小時
搭車16小時
搭車20小時
搭車24小時
行駛在公路上的水手
坐卡車一路向西
穿越茫茫戈壁
中途返京
新疆重逢,再次出發
涉險過關
第三章 MY WAY
心中的馬國
住在集裝箱房子裡的人
赤身跳湖
可愛的吉爾吉斯斯坦胖大媽
簡單而幸福的牧馬人
24小時夜奔
有豔沒有遇
世界盡頭
俄羅斯獨臂水手
幽靈夜車
消失了的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
飛車驚魂
忐忑土耳其
英俊善良的富二代
又一次小別
第四章 青年的世界
從雪山穿越到羅馬尼亞
在孤兒院做義工
五星級的搭車客
三十歲以後才感覺年輕
和吉普賽女郎共舞
遇上了搭車的競爭對手
無法融入的布達佩斯
布拉格,傻子才悲傷
第五章 三十歲的成人禮
寫在後面:2010年,一路向南
序/導讀
前言
因《在路上》而開始的冒險旅程
如果你在百度上搜尋「搭車去柏林」,你可能會得到幾十萬條資訊:二○○九年,兩個北京小伙子──谷岳、劉暢用一個夏天,以舉手搭便車的方式途經十幾個國家,一萬六千公里的旅程到達德國柏林,看望一個女孩。這個幸福的女孩叫伊卡,是谷岳相戀三年的女友,這種極富浪漫色彩的苦行見證了普通人愛情裡的閃光點。那麼,兩個旅行者中的另一個人,劉暢,總是會遇到朋友們各種各樣的疑問,你,又是為什麼而去的呢?我想,寫這本書也許可以表達出我含混不清的旅行目的,以及為了逃離我們庸庸碌碌的人生而作的一切努力。
一開始,我認為一切都跟一本書有關。那就是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書中兩個年輕人不斷瘋狂地穿行美洲:搭車、自駕、不能抑制地無目的地旅行。「這種離經叛道的行為儘管幾乎不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卻具有相當的迷人之處。」
二十世紀五○年代,《在路上》出版後,《紐約時報》刊登的書評這樣寫道:「在極度的時尚使人們的注意力變得支離破碎,敏感性變得遲鈍薄弱的時代,如果說一件真正的藝術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義的話,該書的出版就是一個歷史性事件。」
《在路上》讓無數的年輕人拿起簡單的行囊上路,開始了一代又一代人沒有目的地的旅途。他們害怕鏡子中的自我,最終丟失在物質洪流裡,或僅僅是表演著為尋找自我所做的逃離。去哪裡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做出反抗現實的姿態來,這些年輕人表演、鞠躬,之後就往後一躍,跳進舞臺的側幕裡,五十多年來重複上演著這樣一幕幕鬧劇。這一文化轟轟烈烈繁衍至今天,從文學、從音樂、從電影,成為主流消費文化之外的另一體系。說到這裡,我們為什麼選擇搭車旅行已經表示得很清楚:我和谷岳很快就會離「年輕」這一辭彙越來越遠,我們長年如同螞蟻一般的努力奮鬥在時代洪流面前,漸漸變得微不足道,物質的家園早已褪色,精神的家園形單影隻,搭車旅行,在路上,更像一場遲來的成人禮。
作為一名微不足道的導演,在搭車旅行之前,我曾設想過拍一部公路電影,一男一女,兩段截然不同的旅程,目的地相同卻永遠沒有相遇。男主角路過生命的孤獨與割捨,女主角路過生命的迷惘與歡愉。寫作劇本是漫長艱辛的過程,我發現,公路片只能在公路上完成。在漫長的煎熬和等待中,好友谷岳的邀請彷彿是從天而降的禮物。三個多月的旅程,我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他們的車裡、家裡,遭遇不同人的人生:在新疆廣袤的沙漠,慷慨地搭每一位路人同行的石油卡車司機;在吉爾吉斯酒後遭遇牧民熱騰騰的馬油大餐;烏茲別克沙漠船隻墓地的守墓老人;裡海邊獨臂豪飲的俄羅斯水手;土耳其豪放熱誠的富二代;伊斯坦堡雄渾壯觀的歐亞兩岸;羅馬尼亞堅強的孤兒院志願者;匈牙利布達佩斯青年旅館的韓國老闆;布拉格的CROSS重金屬俱樂部;東柏林的藝術家貧民窟……親自體驗並拍攝一部公路紀錄片,是我這些年來最大的夢想。我相信公路電影的製作者們都經歷著這樣在路上的日子,思想的巡遊也必然伴隨著身體的遊歷。
《在路上》這本書從二○○○年一直陪伴我到現在,四次閱讀都沒有翻到最終章,命中注定它要留給這次旅程。在搭車旅途的某輛大卡車上,我在顛簸的駕駛室的臥鋪上讀完了最後一頁。車窗外是何時何地的風景,都已不再重要。
《在路上》的結尾這樣寫道:
我知道在愛荷華州,在人們允許孩子們哭泣的地方,孩子們在大聲地哭泣著。今夜,星星就要出來,你可知道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今夜金星一定低垂,在祝福大地的黑夜完全降臨之前,把它熠熠的光輝灑落在草原上,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隱沒掉最後一片海灘,然而完全沒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地趨向衰老外,還將有何遭遇。
這本小書是我個人的小小旅行隨想,有些旅程段落詳細,有些只是一筆帶過。這趟旅程我和谷岳約定好一人寫一本書,同樣的旅行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生命體驗與收穫。我偏執於一個普通北京人的視角,偶然的機緣巧合,展開搭車去十餘個國家的夢想之旅,我沒有超於常人的意志品質,也沒有職業旅行家的豐富經驗,更沒有超凡脫俗的個人魅力。我只是因為想要追求一些自己以為需要的東西而與朋友踏上旅途。旅途終結的時候,每個人的內心都因為這段路而得到了某種圓滿,於是那個原來執著的目標也許就不再重要。
劉暢推薦序1
反著活,倒著走
許多中國人的父母過度強調孩子的早熟早慧,孩子從小到大因此活得規規矩矩,少年老成,三十多歲扛起背包旅行才第一次感覺年輕,五十多歲功成名就後才開始泡夜店,就像好萊塢電影《班傑明的奇幻旅程》裡描述那個出生時是老頭,臨終前終於變成嬰孩的男主角那樣,生命是反著活的。西方人眼裡看來滑稽甚至有點恐怖,但大多數這一代的中國人都能理解。
也有一種人,老是在上班族一大早爭先恐後上班的時候,才跟別人反方向搭著地鐵回家睡覺,我們無法理解這種人的生活方式,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壞人,正好留長髮,又有辦法維生,就一律管叫「藝術家」。這樣性格的人,會選擇跟從歐洲出發一路往亞洲前進的旅行者背道而馳,從北京的後海喝杯啤酒後就搭便車出發去德國, 想必也沒有人覺得太訝異,反正就是喜歡把路倒過來走的那種人,要是能像黃明正那樣倒立著過日子、看世界的話,恐怕也會這麼幹。
有意思的是,這種特立獨行的人,不分種族國籍排成一列擺在一起,看起來無論穿著打扮、神采、態度都很像,不信的話去隨便一家標榜地下音樂的酒館混一個晚上。
因為這個時代,就連不一樣,都不一樣得很相似。
《出走,搭車去柏林──在路上的頹廢壯遊,給自己的成人禮。》的作者,是來自北京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劉暢,跟他的哥兒們谷岳, 一個這輩子只在十多年前正式上過一個月班的朋友,兩個藝術家,一個沒什麼存款卻有氣喘,另一個活到三十多歲沒出國自助旅行也沒住過青年旅館,卻憑著對於世界的想像,跟一本過期好幾年的旅行指南書,一路從北京搭車去柏林,亂七八糟、顛顛倒倒,以為這一路會看清世界,結果看得最清的是自己。
他們這趟旅行的過程,雖然跟許多背包客、驢友的路線不同,但是得到的結論,老實說跟世界上古今中外任何一個背起背包出國三個月的年輕人,都差不多。
以為這是一輩子一次的壯遊,但到達目的地以後,才發現真正的旅行才要開始,這點也不怎麼稀奇,父子檔自編自導自演,描述老來喪子的醫師父親,背起亡兒的背包代替兒子完成庇里牛斯山朝聖之旅《The Way》,就是這麼演的,挺主流的,所以這兩人接著不久又籌劃起從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旅行,也是意料中事。
本書整個故事真正特別的,在於故事的主角,是兩個中國的中年男人。
中國這一代都會男人的世界觀,跟世界是有距離的,基於種種內外在因素,在亞洲比起韓國、日本、港台的男女,海外壯遊或自我放逐的經驗是少的,所以看到這兩個無論是自我期許或是社會評價都很高的北京文化人,能夠放下身段,走進地圖上沒有多少著墨的機場與機場之間的虛線,用搭車的方式,用誠實的態度和開放的心胸填滿知識的空白,走上個人派的朝聖之路,用慢遊的方式來表達對世界的敬意,真誠的欣賞中亞的吉爾吉斯與土耳其鄉間無法第一眼看到的美好,虛心體驗勤勉的韓國人在世界盡頭的競爭力,並且回頭反思這一代中國人(主要是漢人)對陌生人的冷漠與不信任,以及中國有車的中產階級對於明明是舉手之勞,所表現出來的卻是近乎可恥的功利與吝嗇,這些外頭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一旦來自外人就會被當成耳邊風的批評,如今出於菁英分子的親身經歷,或許就能形成一股內省的力量。
譬如,在這趟旅行的回憶中,劉暢說到在吉爾吉斯出乎意外的美好生活經驗,讓他重新思考現代人最在意的「幸福」這檔事兒。
他說:「簡單並快樂,就是幸福感,就好像生活盡在掌控中,哪怕天公不做美,下雪了,遇到什麼災害了,他們也能應付。如果風調雨順,他們可能會多養點兒羊,再多養點兒馬,他們的生活小富即安,有自己固定的房子,在山上有放牧點,有自己的車,子女也在大城市裡工作,小兒子在身邊服侍,人與人之間關係簡單,那種和睦感滿足感特別讓人羡慕。」
這種描述,跟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裡面描繪的世外桃源其實是極度類似的。
當然,指著開著名車,戴著名錶,住在豪宅裡的山西煤老闆富二代的鼻子說:「你眼前所擁有的一切所帶來的快樂,還不如吉爾吉斯的一窮二白的一介牧民。」是愚蠢的,但是對介於富二代跟窮牧人光譜的兩個極端之間,占據這一代中國人絕大比例的中產階級來說,卻是一個極好的提醒,提醒我們中年男人也可以去旅行,提醒我們可以路反著走,偶爾生命可以倒著活,就算沒有豔遇的旅程也可以很不錯。
國際NGO工作者 褚士瑩
推薦序2
不是「旅行」,而是「流浪」
我一直想「流浪」!
我說的不是「旅行」,而是「流浪」。在我的定義中,流浪不該有行程,甚至不該有明確的路線,簡單來說,流浪就該讓命運決定把你帶到哪兒去。《出走,搭車去柏林──在路上的頹廢壯遊,給自己的成人禮。》就是這樣的「流浪」故事。
作者劉暢和伙伴谷岳的搭車計畫──從北京一路搭便車到柏林。搭便車充滿不確定性,搭上誰的車,走哪一條路線,遇見什麼人、什麼事,都由命運決定。我看到這兒,就熱血了起來,完全是我心中夢幻的「流浪」。才看完前言,我的心跳已經加速,已經迫不及待跟著他的文字回到搭車上路的那一天。
「谷岳是搭車計畫的始作俑者,我陪著在路上不斷傻樂。」劉暢的這段文字,我特愛「傻樂」這個詞。這段交給命運決定的流浪旅程,就像人生一樣,遇到什麼都該用這傻樂的心情去面對。他們用傻樂與每個接觸過的人交心,也因為這樣,旅程中所經歷的片段,說起來似乎都有那麼點相同的青年旅館種種、與當地人共舞……等,有了劉暢與谷岳參與其中,就變得不同。
除了「流浪」這回事,更打動我的是作者劉暢的心境轉折。畢竟我們同是三十歲,這個青春所剩無幾,夢想被時間與現實擠壓的年紀。工作了幾年,人生已經不再新鮮,充滿了「不得不」的感嘆,不敢想自己哪一天可以達成別人的期待,而自我的期待已經消失很久了。三十歲就是這麼一個讓人想嘆氣,卻仍有點不甘心的年紀。我才紮紮實實的掙扎了一回,看到劉暢筆下的感嘆,更有種同是天涯人的心情。值得開心的是,我們同樣的掙扎了,也同樣透過流浪找回了自己年輕的靈魂。
他在旅行中點點滴滴地突破自我,極度內向的他學著谷岳至少也成為三星半的搭車人。從第一次比出搭車國際標準姿勢,第一天就想放棄回城裡吃涮羊肉,到最後旅程結束時「怎麼就這樣結束了?」的失落心情,這三個月的旅程確實改變了他,也改變了許多看過紀錄片的年輕人,更改變了即將在半個月後踏上流浪旅程的我。
看到旅程的終點即將到達,我也跟著有點感傷了!這精彩的旅程就要畫下句點了。「搭上最後一輛車,駛進終點時,我在想,無論多麼難的事,如果你當一個旁觀者,就覺得肯定很難,但如果身體力行,多麼難的事情都會慢慢過去。」我在心中默念了兩遍劉暢最後寫下的心情。
所有流浪過的人都知道,流浪從不會真正結束。「這只是一個歇腳的時刻。」劉暢說。流浪過程中得到的養分會在心中滋養出另一段流浪,每個句點都是下一個章節的開始。看到最後我發現這本書不只是個流浪的故事,而是個三十歲失去夢想的紀錄片導演找回自己熱情靈魂的故事。
我有幸在流浪啟程之前看完本書。劉暢與谷岳因著《在路上》這本書而上路,我的流浪旅程也必定因《出走,搭車去柏林》這本書而會有不同的化學變化。至於搭車流浪會出現在我旅程的哪一個章節?就交給命運決定吧!這才叫流浪嘛!
旅遊作家 唐宏安
推薦序3
因為無法預期,讓回憶更美好
「一趟旅程,永遠是無法預期的;但也就因為無法預期,更能誘發出回憶的美好!」這是我每次結束旅程之後,浮現在腦海中的一段話。
我也曾經在過往的旅遊中,花一個月搭便車旅行。雖然聽起來感覺很厲害,但我卻覺得這絕對是旅遊行為中最具備挑戰性的事。因為在過程中,真的會發生太多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情況,往往事發突然,完全無法控制。
像書中〈遇上了搭車的競爭對手〉該篇提到,本來以為是會越來越順的旅程,怎知會半路殺出程咬金,出現了搭便車同好,重點又是一位女性,兩個大男人搭便車的優勢頓時消失了。也就因為如此,會衍生出一個搭便車的不成文公式,那就是「單身辣妹最容易搭上車,三人以上(尤指男性)困難度是難上加難」,藉由這句話,也讓我回想到當初那如苦行僧的旅程。
再者,這樣的旅遊行徑是最挑戰中國人傳統觀念的。作者在書中也提到,在中國願意搭載他們倆的司機真是太少了,但到了歐洲,舉起手來搭車,感覺上似乎是簡單多了。這讓我想到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總是將「陌生人」三個字冠上惡名昭彰的罪名,避之猶恐不及。
而事實上真是如此嗎?相信藉由本書可以了解到很多情況並不是如此。因為在他們的旅行過程中,曾遇到小女孩主動幫忙帶路、也遇到富二代不但讓他們搭便車,還幫忙代訂四星級飯店,重點是連住宿費都付了等等,種種經歷聽起來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卻在他們的旅程中上演。而我也曾遇過相同的情形,剎那間真的會讓人覺得疑惑,為何在我們熟悉的國度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疏遠呢?彼此之間都有戒心,不願意去幫助陌生人,深怕會招來麻煩。
我曾經在旅程中,遇到一位十八歲的外國女孩在荒郊野外讓我上車。我當時的造型和土匪沒兩樣,而她竟然敢讓我上車,各位試想,在這種情形中,到底誰比較危險呢?
說實話,換做是以前的我,我是不可能搭載陌生人的,但現在的想法卻全然不同,也是因為一句話感動了我。當年我在搭便車的過程中,曾經有一位搭載我的司機對我說:「保護來我國
因《在路上》而開始的冒險旅程
如果你在百度上搜尋「搭車去柏林」,你可能會得到幾十萬條資訊:二○○九年,兩個北京小伙子──谷岳、劉暢用一個夏天,以舉手搭便車的方式途經十幾個國家,一萬六千公里的旅程到達德國柏林,看望一個女孩。這個幸福的女孩叫伊卡,是谷岳相戀三年的女友,這種極富浪漫色彩的苦行見證了普通人愛情裡的閃光點。那麼,兩個旅行者中的另一個人,劉暢,總是會遇到朋友們各種各樣的疑問,你,又是為什麼而去的呢?我想,寫這本書也許可以表達出我含混不清的旅行目的,以及為了逃離我們庸庸碌碌的人生而作的一切努力。
一開始,我認為一切都跟一本書有關。那就是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書中兩個年輕人不斷瘋狂地穿行美洲:搭車、自駕、不能抑制地無目的地旅行。「這種離經叛道的行為儘管幾乎不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卻具有相當的迷人之處。」
二十世紀五○年代,《在路上》出版後,《紐約時報》刊登的書評這樣寫道:「在極度的時尚使人們的注意力變得支離破碎,敏感性變得遲鈍薄弱的時代,如果說一件真正的藝術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義的話,該書的出版就是一個歷史性事件。」
《在路上》讓無數的年輕人拿起簡單的行囊上路,開始了一代又一代人沒有目的地的旅途。他們害怕鏡子中的自我,最終丟失在物質洪流裡,或僅僅是表演著為尋找自我所做的逃離。去哪裡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做出反抗現實的姿態來,這些年輕人表演、鞠躬,之後就往後一躍,跳進舞臺的側幕裡,五十多年來重複上演著這樣一幕幕鬧劇。這一文化轟轟烈烈繁衍至今天,從文學、從音樂、從電影,成為主流消費文化之外的另一體系。說到這裡,我們為什麼選擇搭車旅行已經表示得很清楚:我和谷岳很快就會離「年輕」這一辭彙越來越遠,我們長年如同螞蟻一般的努力奮鬥在時代洪流面前,漸漸變得微不足道,物質的家園早已褪色,精神的家園形單影隻,搭車旅行,在路上,更像一場遲來的成人禮。
作為一名微不足道的導演,在搭車旅行之前,我曾設想過拍一部公路電影,一男一女,兩段截然不同的旅程,目的地相同卻永遠沒有相遇。男主角路過生命的孤獨與割捨,女主角路過生命的迷惘與歡愉。寫作劇本是漫長艱辛的過程,我發現,公路片只能在公路上完成。在漫長的煎熬和等待中,好友谷岳的邀請彷彿是從天而降的禮物。三個多月的旅程,我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他們的車裡、家裡,遭遇不同人的人生:在新疆廣袤的沙漠,慷慨地搭每一位路人同行的石油卡車司機;在吉爾吉斯酒後遭遇牧民熱騰騰的馬油大餐;烏茲別克沙漠船隻墓地的守墓老人;裡海邊獨臂豪飲的俄羅斯水手;土耳其豪放熱誠的富二代;伊斯坦堡雄渾壯觀的歐亞兩岸;羅馬尼亞堅強的孤兒院志願者;匈牙利布達佩斯青年旅館的韓國老闆;布拉格的CROSS重金屬俱樂部;東柏林的藝術家貧民窟……親自體驗並拍攝一部公路紀錄片,是我這些年來最大的夢想。我相信公路電影的製作者們都經歷著這樣在路上的日子,思想的巡遊也必然伴隨著身體的遊歷。
《在路上》這本書從二○○○年一直陪伴我到現在,四次閱讀都沒有翻到最終章,命中注定它要留給這次旅程。在搭車旅途的某輛大卡車上,我在顛簸的駕駛室的臥鋪上讀完了最後一頁。車窗外是何時何地的風景,都已不再重要。
《在路上》的結尾這樣寫道:
我知道在愛荷華州,在人們允許孩子們哭泣的地方,孩子們在大聲地哭泣著。今夜,星星就要出來,你可知道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今夜金星一定低垂,在祝福大地的黑夜完全降臨之前,把它熠熠的光輝灑落在草原上,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隱沒掉最後一片海灘,然而完全沒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地趨向衰老外,還將有何遭遇。
這本小書是我個人的小小旅行隨想,有些旅程段落詳細,有些只是一筆帶過。這趟旅程我和谷岳約定好一人寫一本書,同樣的旅行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生命體驗與收穫。我偏執於一個普通北京人的視角,偶然的機緣巧合,展開搭車去十餘個國家的夢想之旅,我沒有超於常人的意志品質,也沒有職業旅行家的豐富經驗,更沒有超凡脫俗的個人魅力。我只是因為想要追求一些自己以為需要的東西而與朋友踏上旅途。旅途終結的時候,每個人的內心都因為這段路而得到了某種圓滿,於是那個原來執著的目標也許就不再重要。
劉暢推薦序1
反著活,倒著走
許多中國人的父母過度強調孩子的早熟早慧,孩子從小到大因此活得規規矩矩,少年老成,三十多歲扛起背包旅行才第一次感覺年輕,五十多歲功成名就後才開始泡夜店,就像好萊塢電影《班傑明的奇幻旅程》裡描述那個出生時是老頭,臨終前終於變成嬰孩的男主角那樣,生命是反著活的。西方人眼裡看來滑稽甚至有點恐怖,但大多數這一代的中國人都能理解。
也有一種人,老是在上班族一大早爭先恐後上班的時候,才跟別人反方向搭著地鐵回家睡覺,我們無法理解這種人的生活方式,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壞人,正好留長髮,又有辦法維生,就一律管叫「藝術家」。這樣性格的人,會選擇跟從歐洲出發一路往亞洲前進的旅行者背道而馳,從北京的後海喝杯啤酒後就搭便車出發去德國, 想必也沒有人覺得太訝異,反正就是喜歡把路倒過來走的那種人,要是能像黃明正那樣倒立著過日子、看世界的話,恐怕也會這麼幹。
有意思的是,這種特立獨行的人,不分種族國籍排成一列擺在一起,看起來無論穿著打扮、神采、態度都很像,不信的話去隨便一家標榜地下音樂的酒館混一個晚上。
因為這個時代,就連不一樣,都不一樣得很相似。
《出走,搭車去柏林──在路上的頹廢壯遊,給自己的成人禮。》的作者,是來自北京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劉暢,跟他的哥兒們谷岳, 一個這輩子只在十多年前正式上過一個月班的朋友,兩個藝術家,一個沒什麼存款卻有氣喘,另一個活到三十多歲沒出國自助旅行也沒住過青年旅館,卻憑著對於世界的想像,跟一本過期好幾年的旅行指南書,一路從北京搭車去柏林,亂七八糟、顛顛倒倒,以為這一路會看清世界,結果看得最清的是自己。
他們這趟旅行的過程,雖然跟許多背包客、驢友的路線不同,但是得到的結論,老實說跟世界上古今中外任何一個背起背包出國三個月的年輕人,都差不多。
以為這是一輩子一次的壯遊,但到達目的地以後,才發現真正的旅行才要開始,這點也不怎麼稀奇,父子檔自編自導自演,描述老來喪子的醫師父親,背起亡兒的背包代替兒子完成庇里牛斯山朝聖之旅《The Way》,就是這麼演的,挺主流的,所以這兩人接著不久又籌劃起從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旅行,也是意料中事。
本書整個故事真正特別的,在於故事的主角,是兩個中國的中年男人。
中國這一代都會男人的世界觀,跟世界是有距離的,基於種種內外在因素,在亞洲比起韓國、日本、港台的男女,海外壯遊或自我放逐的經驗是少的,所以看到這兩個無論是自我期許或是社會評價都很高的北京文化人,能夠放下身段,走進地圖上沒有多少著墨的機場與機場之間的虛線,用搭車的方式,用誠實的態度和開放的心胸填滿知識的空白,走上個人派的朝聖之路,用慢遊的方式來表達對世界的敬意,真誠的欣賞中亞的吉爾吉斯與土耳其鄉間無法第一眼看到的美好,虛心體驗勤勉的韓國人在世界盡頭的競爭力,並且回頭反思這一代中國人(主要是漢人)對陌生人的冷漠與不信任,以及中國有車的中產階級對於明明是舉手之勞,所表現出來的卻是近乎可恥的功利與吝嗇,這些外頭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一旦來自外人就會被當成耳邊風的批評,如今出於菁英分子的親身經歷,或許就能形成一股內省的力量。
譬如,在這趟旅行的回憶中,劉暢說到在吉爾吉斯出乎意外的美好生活經驗,讓他重新思考現代人最在意的「幸福」這檔事兒。
他說:「簡單並快樂,就是幸福感,就好像生活盡在掌控中,哪怕天公不做美,下雪了,遇到什麼災害了,他們也能應付。如果風調雨順,他們可能會多養點兒羊,再多養點兒馬,他們的生活小富即安,有自己固定的房子,在山上有放牧點,有自己的車,子女也在大城市裡工作,小兒子在身邊服侍,人與人之間關係簡單,那種和睦感滿足感特別讓人羡慕。」
這種描述,跟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裡面描繪的世外桃源其實是極度類似的。
當然,指著開著名車,戴著名錶,住在豪宅裡的山西煤老闆富二代的鼻子說:「你眼前所擁有的一切所帶來的快樂,還不如吉爾吉斯的一窮二白的一介牧民。」是愚蠢的,但是對介於富二代跟窮牧人光譜的兩個極端之間,占據這一代中國人絕大比例的中產階級來說,卻是一個極好的提醒,提醒我們中年男人也可以去旅行,提醒我們可以路反著走,偶爾生命可以倒著活,就算沒有豔遇的旅程也可以很不錯。
國際NGO工作者 褚士瑩
推薦序2
不是「旅行」,而是「流浪」
我一直想「流浪」!
我說的不是「旅行」,而是「流浪」。在我的定義中,流浪不該有行程,甚至不該有明確的路線,簡單來說,流浪就該讓命運決定把你帶到哪兒去。《出走,搭車去柏林──在路上的頹廢壯遊,給自己的成人禮。》就是這樣的「流浪」故事。
作者劉暢和伙伴谷岳的搭車計畫──從北京一路搭便車到柏林。搭便車充滿不確定性,搭上誰的車,走哪一條路線,遇見什麼人、什麼事,都由命運決定。我看到這兒,就熱血了起來,完全是我心中夢幻的「流浪」。才看完前言,我的心跳已經加速,已經迫不及待跟著他的文字回到搭車上路的那一天。
「谷岳是搭車計畫的始作俑者,我陪著在路上不斷傻樂。」劉暢的這段文字,我特愛「傻樂」這個詞。這段交給命運決定的流浪旅程,就像人生一樣,遇到什麼都該用這傻樂的心情去面對。他們用傻樂與每個接觸過的人交心,也因為這樣,旅程中所經歷的片段,說起來似乎都有那麼點相同的青年旅館種種、與當地人共舞……等,有了劉暢與谷岳參與其中,就變得不同。
除了「流浪」這回事,更打動我的是作者劉暢的心境轉折。畢竟我們同是三十歲,這個青春所剩無幾,夢想被時間與現實擠壓的年紀。工作了幾年,人生已經不再新鮮,充滿了「不得不」的感嘆,不敢想自己哪一天可以達成別人的期待,而自我的期待已經消失很久了。三十歲就是這麼一個讓人想嘆氣,卻仍有點不甘心的年紀。我才紮紮實實的掙扎了一回,看到劉暢筆下的感嘆,更有種同是天涯人的心情。值得開心的是,我們同樣的掙扎了,也同樣透過流浪找回了自己年輕的靈魂。
他在旅行中點點滴滴地突破自我,極度內向的他學著谷岳至少也成為三星半的搭車人。從第一次比出搭車國際標準姿勢,第一天就想放棄回城裡吃涮羊肉,到最後旅程結束時「怎麼就這樣結束了?」的失落心情,這三個月的旅程確實改變了他,也改變了許多看過紀錄片的年輕人,更改變了即將在半個月後踏上流浪旅程的我。
看到旅程的終點即將到達,我也跟著有點感傷了!這精彩的旅程就要畫下句點了。「搭上最後一輛車,駛進終點時,我在想,無論多麼難的事,如果你當一個旁觀者,就覺得肯定很難,但如果身體力行,多麼難的事情都會慢慢過去。」我在心中默念了兩遍劉暢最後寫下的心情。
所有流浪過的人都知道,流浪從不會真正結束。「這只是一個歇腳的時刻。」劉暢說。流浪過程中得到的養分會在心中滋養出另一段流浪,每個句點都是下一個章節的開始。看到最後我發現這本書不只是個流浪的故事,而是個三十歲失去夢想的紀錄片導演找回自己熱情靈魂的故事。
我有幸在流浪啟程之前看完本書。劉暢與谷岳因著《在路上》這本書而上路,我的流浪旅程也必定因《出走,搭車去柏林》這本書而會有不同的化學變化。至於搭車流浪會出現在我旅程的哪一個章節?就交給命運決定吧!這才叫流浪嘛!
旅遊作家 唐宏安
推薦序3
因為無法預期,讓回憶更美好
「一趟旅程,永遠是無法預期的;但也就因為無法預期,更能誘發出回憶的美好!」這是我每次結束旅程之後,浮現在腦海中的一段話。
我也曾經在過往的旅遊中,花一個月搭便車旅行。雖然聽起來感覺很厲害,但我卻覺得這絕對是旅遊行為中最具備挑戰性的事。因為在過程中,真的會發生太多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情況,往往事發突然,完全無法控制。
像書中〈遇上了搭車的競爭對手〉該篇提到,本來以為是會越來越順的旅程,怎知會半路殺出程咬金,出現了搭便車同好,重點又是一位女性,兩個大男人搭便車的優勢頓時消失了。也就因為如此,會衍生出一個搭便車的不成文公式,那就是「單身辣妹最容易搭上車,三人以上(尤指男性)困難度是難上加難」,藉由這句話,也讓我回想到當初那如苦行僧的旅程。
再者,這樣的旅遊行徑是最挑戰中國人傳統觀念的。作者在書中也提到,在中國願意搭載他們倆的司機真是太少了,但到了歐洲,舉起手來搭車,感覺上似乎是簡單多了。這讓我想到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總是將「陌生人」三個字冠上惡名昭彰的罪名,避之猶恐不及。
而事實上真是如此嗎?相信藉由本書可以了解到很多情況並不是如此。因為在他們的旅行過程中,曾遇到小女孩主動幫忙帶路、也遇到富二代不但讓他們搭便車,還幫忙代訂四星級飯店,重點是連住宿費都付了等等,種種經歷聽起來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卻在他們的旅程中上演。而我也曾遇過相同的情形,剎那間真的會讓人覺得疑惑,為何在我們熟悉的國度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如此疏遠呢?彼此之間都有戒心,不願意去幫助陌生人,深怕會招來麻煩。
我曾經在旅程中,遇到一位十八歲的外國女孩在荒郊野外讓我上車。我當時的造型和土匪沒兩樣,而她竟然敢讓我上車,各位試想,在這種情形中,到底誰比較危險呢?
說實話,換做是以前的我,我是不可能搭載陌生人的,但現在的想法卻全然不同,也是因為一句話感動了我。當年我在搭便車的過程中,曾經有一位搭載我的司機對我說:「保護來我國
試閱
◎為了「在路上」而展開的旅程
如果你在百度上搜尋「搭車去柏林」,你可能會得到幾十萬條資訊:二○○九年,兩個北京小伙子──谷岳、劉暢用一個夏天,以舉手搭便車的方式途經十幾個國家,一萬六千公里的旅程到達德國柏林,看望一個女孩。這個幸福的女孩叫伊卡,是谷岳相戀三年的女友,這種極富浪漫色彩的苦行見證了普通人愛情裡的閃光點。那麼,兩個旅行者中的另一個人,劉暢,總是會遇到朋友們各種各樣的疑問,你,又是為什麼而去的呢?我想,寫這本書也許可以表達出我含混不清的旅行目的,以及為了逃離我們庸庸碌碌的人生而作的一切努力。
一開始,我認為一切都跟一本書有關。那就是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書中兩個年輕人不斷瘋狂地穿行美洲:搭車、自駕、不能抑制地無目的地旅行。「這種離經叛道的行為儘管幾乎不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卻具有相當的迷人之處。」
二十世紀五○年代,《在路上》出版後,《紐約時報》刊登的書評這樣寫道:「在極度的時尚使人們的注意力變得支離破碎,敏感性變得遲鈍薄弱的時代,如果說一件真正的藝術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義的話,該書的出版就是一個歷史性事件。」
《在路上》讓無數的年輕人拿起簡單的行囊上路,開始了一代又一代人沒有目的地的旅途。他們害怕鏡子中的自我,最終丟失在物質洪流裡,或僅僅是表演著為尋找自我所做的逃離。去哪裡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做出反抗現實的姿態來,這些年輕人表演、鞠躬,之後就往後一躍,跳進舞臺的側幕裡,五十多年來重複上演著這樣一幕幕鬧劇。這一文化轟轟烈烈繁衍至今天,從文學、從音樂、從電影,成為主流消費文化之外的另一體系。說到這裡,我們為什麼選擇搭車旅行已經表示得很清楚:我和谷岳很快就會離「年輕」這一辭彙越來越遠,我們長年如同螞蟻一般的努力奮鬥在時代洪流面前,漸漸變得微不足道,物質的家園早已褪色,精神的家園形單影隻,搭車旅行,在路上,更像一場遲來的成人禮。
作為一名微不足道的導演,在搭車旅行之前,我曾設想過拍一部公路電影,一男一女,兩段截然不同的旅程,目的地相同卻永遠沒有相遇。男主角路過生命的孤獨與割捨,女主角路過生命的迷惘與歡愉。寫作劇本是漫長艱辛的過程,我發現,公路片只能在公路上完成。在漫長的煎熬和等待中,好友谷岳的邀請彷彿是從天而降的禮物。三個多月的旅程,我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他們的車裡、家裡,遭遇不同人的人生:在新疆廣袤的沙漠,慷慨地搭每一位路人同行的石油卡車司機;在吉爾吉斯酒後遭遇牧民熱騰騰的馬油大餐;烏茲別克沙漠船隻墓地的守墓老人;裡海邊獨臂豪飲的俄羅斯水手;土耳其豪放熱誠的富二代;伊斯坦堡雄渾壯觀的歐亞兩岸;羅馬尼亞堅強的孤兒院志願者;匈牙利布達佩斯青年旅館的韓國老闆;布拉格的CROSS重金屬俱樂部;東柏林的藝術家貧民窟……親自體驗並拍攝一部公路紀錄片,是我這些年來最大的夢想。我相信公路電影的製作者們都經歷著這樣在路上的日子,思想的巡遊也必然伴隨著身體的遊歷。
《在路上》這本書從二○○○年一直陪伴我到現在,四次閱讀都沒有翻到最終章,命中注定它要留給這次旅程。在搭車旅途的某輛大卡車上,我在顛簸的駕駛室的臥鋪上讀完了最後一頁。車窗外是何時何地的風景,都已不再重要。
《在路上》的結尾這樣寫道:
我知道在愛荷華州,在人們允許孩子們哭泣的地方,孩子們在大聲地哭泣著。今夜,星星就要出來,你可知道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今夜金星一定低垂,在祝福大地的黑夜完全降臨之前,把它熠熠的光輝灑落在草原上,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隱沒掉最後一片海灘,然而完全沒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地趨向衰老外,還將有何遭遇。
這本小書是我個人的小小旅行隨想,有些旅程段落詳細,有些只是一筆帶過。這趟旅程我和谷岳約定好一人寫一本書,同樣的旅行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生命體驗與收穫。我偏執於一個普通北京人的視角,偶然的機緣巧合,展開搭車去十餘個國家的夢想之旅,我沒有超於常人的意志品質,也沒有職業旅行家的豐富經驗,更沒有超凡脫俗的個人魅力。我只是因為想要追求一些自己以為需要的東西而與朋友踏上旅途。旅途終結的時候,每個人的內心都因為這段路而得到了某種圓滿,於是那個原來執著的目標也許就不再重要。
◎清晨五點半的地鐵五號線
你可曾見過北京地鐵五號線清晨五點半的月臺?它華而不實地被設計成海洋動物曬乾後的軀殼的樣子,乾巴巴地,等待著早班的地下鐵從這邊來再從那邊走,等待著面無表情的人們前來重複命中注定的日子。我經常會在清晨,趕最早的一班地鐵回家,因為工作通常需要熬夜,我便有了這樣一種機會,體會與人群相反的軌跡,體會身體在極度透支後的某種亢奮,身體是軟的,而心底卻清明一片,靜逸安詳。你會發現夜與晝的更替是隨鳥的叫聲來臨,天知道北京竟有這麼多種鳥,在你不知道的遠方喧鬧。
鳥的聲音會被對面月臺漸漸匯聚的人聲終結,列車會把他們帶往市中心,而我的方向相反,等候在回家的路上,獨自擁有這一半的月臺,以一種旁觀的心態默默注視著對面越聚越多的人群。那些人雖然陌生,卻都是再熟悉不過的陌生人,我們都從五環外的新建高樓裡醒來,或是十幾個人擠在兩室一廳分割的公寓裡,因為搶洗手間而爭吵,因為左鄰右舍的梳洗打扮而詛咒著為什麼不能再睡上十幾分鐘。找到熟悉的早點攤,排隊買著熟悉的糊弄肚子的食物,然後強打起精神隨擁擠的地鐵奔赴一個小時後另一個屬於自己的格子間。
熟悉這樣的世界,這樣的陌生人,這樣的生活,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紋一樣。常常問自己,三十多歲了,如果有機會和別人交換各自的生活,那麼,我會選擇和誰交換?瀟灑地開寶馬(BMW)車的,還是在地鐵車廂裡啃油條的?沒有,熟悉的生活僅有這一點點差別,我們擁有同樣的苦難,僅靠可憐的一點點財富來顯示彼此的差別。三十多歲了,人生不再新鮮,多少對未知的探求也泯滅在這許許多多的「不得不」裡。不得不去向看板上成功的人生靠近:一家三口,穿著一塵不染的夏裝,跑向以外國風景地命名的美好社區,女人很滿足,男人很得意,孩子的頭髮很整齊。雖然覺得這一切很可笑,但是,開往城郊的地鐵來了,我也只能低頭走進車廂裡。每天,我們在地鐵五號線裡路過路人甲,再路過路人乙,看別人看自己,沒有一絲絕望。因為五號線代表我每天的旅程,無可選擇。
這僅是我二○○九年年初的想法 ,六個月後,我和一個叫谷岳的傢伙去了一萬多公里外的城市,那裡有他的姑娘,也有無數條血管般蓬勃的地鐵線,喧鬧地在每一個清晨流過城市的龐大身軀,那裡叫柏林。
◎谷岳的三分鐘
「三分鐘內可以發生許多事,欣賞一段不錯的音樂,吃一頓倉促的速食,經歷一場感情變故,改變一個人的某種世界觀,獲得或失去一筆財富,也可能失去親人,或離開一片你摯愛的熱土,再或踏上一段征途,很多很多……」
在北京南鑼鼓巷的一家小酒館,我把自己的三分鐘給了對面這個叫谷岳的傢伙,他用三分鐘和我說明了他的計畫:他想尋找一個旅伴,拍攝經驗豐富,能各自負擔費用,花三個月的時間,一起從北京出發,搭車旅行去德國首都柏林。用他的話講,去看女朋友的旅程也要給自己留下些什麼,這裡借用他的演講文稿:
「一直崇拜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再加上電影《摩托車日記》(台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和《荒野生存》(台譯:阿拉斯加之死)的啟發,我要去找伊卡,也要親自體驗一下『在路上』的自由精神。如果我是坐飛機去見她,那麼舷窗下的原野,我就無法用腳步去丈量,我和伊卡也就沒有更多的收穫,我想慢慢去感受與她距離越來越近所帶來的影響,對我生命的影響。
以前我也上過班,在二○○一年的時候,我在美國的通用電氣做金融(工作),算風險評估吧。工作了一個月後,突然有一天有一個深省,我就想我從小學就努力好好學習,上中學、上大學、找著一份好工作,要買房子、買車、結婚生孩子,這一輩子的東西都已經知道了,我覺得有點兒太遺憾了。所以二○○三年我把工作辭掉了,把我的家當都賣了,開始環球世界旅行。二○○六年認識我現在的女朋友伊卡,她是德國人。我跟她相處兩年後,她說她要回德國一段時間,想家了,這又給我再次上路的動力。另外我覺得社會越來越實際了,所有的東西都建立在金錢和互利的關係上,所以我想用這種搭車的方式,來尋找不是在金錢,不是在互利的關係上創建的一種友誼。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搭車,要搭陌生人的車。」
其實在這以前兩年我們就通過旅遊衛視的朋友認識,那時他就已經是職業的旅行家了。而我,一個拍紀錄片的小小導演,雖然也經歷過諸如雅魯藏布江大峽谷、長江源、柴達木、可哥西裡等地的探險拍攝,但旅行一直不是我的直接目的。而這次,更是沒有任何理由,只是要走,要出發,要一直走在路上。
十年前在電影學院讀書的時候,我拚命看《麥田裡的守望者》(台譯:麥田捕手)這樣的小說,聽《涅槃》,去中戲小劇場蹭話劇《盜版浮士德》,和同學們聊著某大師艱澀難懂的電影,憧憬著將來一起拍充滿新銳氣息的片子,唾棄著所謂俗氣的生活,那時候覺得這肯定就是自己將來的人生。但是慢慢地從畢業開始,我也進入了一種大家都會進入的生活。去掙錢,去過一種世俗人眼中你應該過的那種生活。谷岳用三分鐘說了他的想法後,問我能不能走,感覺言語中還要給我一些時間去思考。但我內心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定要走,雖然當時搭車對我來說還只是天空上飄著的一種概念。那時我正處於人生的低潮,感慨自己十多年的時間在北京這個城市裡做了很多莫名的事情,表面上熱熱鬧鬧,內心卻無比空虛。我的故鄉,這座巨大而喧鬧的城市,時常讓我害怕失去僅有的一點兒歸屬感,失去掙扎生存的勇氣。
我的生活像是在莫比斯環(Mobius band)上爬的螞蟻一樣,螞蟻一直以為能從紙的開端爬到紙的末端,爬到末端才發現其實又到了開始的地方。一直原地打轉,缺少生活的新鮮和激情。所以一定要走。決定的同時,隨之而來的是很多的顧慮:我的存款不多,這三個月走了,生活來源就沒有了,雖然我是自由職業,沒有固定工作,沒有辭職的問題,但是同樣面臨生存的壓力。房租怎麼交?以後怎麼辦?長期合作拍片的客戶這次拒絕了,以後人家還會不會來找你合作?很多的機會就因此失去了。但是能促使我把這些都拋下而毅然決定走的主要原因,還是對這個城市的感覺,有時候我會覺得整個城市已離棄了我,我從城市的中心漂流到了城市的周邊──記得小時候是在長安街沿線長大,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遷徙,到三環外,四環外,過了這麼多年,甚至置身五環以外,從二十三樓的出租房眺望環內,曾經的核桃樹與梧桐依然蒼翠,但已物是人非。我很想笑,既然生活已把自己趕得越來越遠,為何不乾脆痛快點兒走得更遠?去看看真正想看的東西,「在路上」這三個字,一下子跳出來,在腦海裡閃著神聖的光輝。
「有些事情現在不去做,就永遠不會做了。」對面拿著啤酒的谷岳沒來由地說了一句。
十年前,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科學新聞,至今想起仍會發冷。
一九九九年情人節那天,旅行者二號在掠過冥王星後,飛向沒有盡頭的宇宙深淵。它的孤獨讓人不寒而慄,在調整方向奔赴這一命運時,一個女科學家,遙控它做了最後一件事情:緩緩轉過身,將鏡頭朝向我們這個行星系,眨了最後一下眼睛。那張最孤獨的照片,遠沒有想像中宏偉,地球只是一粒可以拂去的塵沙。藍色的塵沙,與沙漠中任何一粒沙子一樣寂寞。
我無比羡慕旅行者二號,溫暖地告別後,一頭扎入冰冷的沒有盡頭的宇宙荒漠,飄蕩在充滿無盡可能性的虛空裡。
這次去柏林的旅程的紀錄片播出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感謝觀眾對我們的支持和厚愛。更令人鼓舞的是無數中國年輕人正拿起行囊,搭車奔走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去探索去收穫屬於自己的精彩旅程,完成自己的成人禮。
歡迎讀者能到網上或旅遊衛視收看我們的紀錄片《搭車去柏林》。
◎六月八日,從后海出發
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家裡把背包打了好幾遍,很少臨出門前會這麼仔細地準備行李。把東西拿出來又放進去,放進去又拿出來,反覆幾次都無從知道究竟要帶多少東西才能夠這三個月的旅行。這種心情有點兒像小學去郊遊的前一天晚上,興奮得睡不著覺,一直檢查自己包裡的糖果巧克力是不是夠吃一樣。愣愣地看著撐得滿滿的大包小包,它們靜靜地像在問我,到底準備好了麼?
雖然十年的拍片生涯中也經常出門,足跡基本上踏遍了大半個中國,但一直有著團隊的支持和精心的計畫。這次和谷岳一起,行程中太多要靠自己去解決和完成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恨不得把家也一起背走。沒錯,對背包客來講,這兩個歪歪扭扭的包就是家了。這種隨意旅行的方式,我一直嚮往很久,我痛恨充滿計畫的行程,彷彿一眼就可以看到結局的電影。然而,真的要上路時,我可以聽到來自遙遠內心的咚咚鼓聲。
六月八日,我們兩人在后海的一個酒吧裡面碰頭,就像平常一樣。我們把出發的地點定在后海,因為那曾經是少年時代的樂園,游泳,滑冰,刷夜(編按:不回家,在外面過夜)。中學時也會每天放學騎車專門到湖邊轉一圈,不為了什麼,只是單純地發呆,坐到太陽落山,水邊晚風吹來,聽著湖對面生澀的薩克斯,很舒服,也許這就是故鄉的感覺。與其說從后海的某一地出發,不如說是從我心裡的某一塊地兒出發。碰巧谷岳也有后海情結。他對北京許多快樂的記憶也是在后海沿岸發生的。但我們去了以後才發現,那天下了北京乾旱許久後的第一場大雨,我們被困在那兒了。
酒吧裡一個客人都沒有,早上十點,我們聚齊,外面雲霧濛濛,湖面平靜。拍了第一張合影照片,換上衝鋒衣(編按:透氣防水的登山服),各自背起四十公斤的負重。包裡除了衣服、帳篷、睡袋外,還有兩部攝影機和照相機、三角架、筆記本、各種充電器、電池,甚至一人還有一瓶防狼噴霧劑。把包一背,好像真是要遠行了。這時雨突然就大起來了,越等越大,中午了,不能再等下去,我們冒著大雨放棄了坐公車去公路邊的想法,攔了一輛出租車,趕赴六里橋京石高速入口,開始我們三個半月的搭車旅行……
如果你在百度上搜尋「搭車去柏林」,你可能會得到幾十萬條資訊:二○○九年,兩個北京小伙子──谷岳、劉暢用一個夏天,以舉手搭便車的方式途經十幾個國家,一萬六千公里的旅程到達德國柏林,看望一個女孩。這個幸福的女孩叫伊卡,是谷岳相戀三年的女友,這種極富浪漫色彩的苦行見證了普通人愛情裡的閃光點。那麼,兩個旅行者中的另一個人,劉暢,總是會遇到朋友們各種各樣的疑問,你,又是為什麼而去的呢?我想,寫這本書也許可以表達出我含混不清的旅行目的,以及為了逃離我們庸庸碌碌的人生而作的一切努力。
一開始,我認為一切都跟一本書有關。那就是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書中兩個年輕人不斷瘋狂地穿行美洲:搭車、自駕、不能抑制地無目的地旅行。「這種離經叛道的行為儘管幾乎不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卻具有相當的迷人之處。」
二十世紀五○年代,《在路上》出版後,《紐約時報》刊登的書評這樣寫道:「在極度的時尚使人們的注意力變得支離破碎,敏感性變得遲鈍薄弱的時代,如果說一件真正的藝術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義的話,該書的出版就是一個歷史性事件。」
《在路上》讓無數的年輕人拿起簡單的行囊上路,開始了一代又一代人沒有目的地的旅途。他們害怕鏡子中的自我,最終丟失在物質洪流裡,或僅僅是表演著為尋找自我所做的逃離。去哪裡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做出反抗現實的姿態來,這些年輕人表演、鞠躬,之後就往後一躍,跳進舞臺的側幕裡,五十多年來重複上演著這樣一幕幕鬧劇。這一文化轟轟烈烈繁衍至今天,從文學、從音樂、從電影,成為主流消費文化之外的另一體系。說到這裡,我們為什麼選擇搭車旅行已經表示得很清楚:我和谷岳很快就會離「年輕」這一辭彙越來越遠,我們長年如同螞蟻一般的努力奮鬥在時代洪流面前,漸漸變得微不足道,物質的家園早已褪色,精神的家園形單影隻,搭車旅行,在路上,更像一場遲來的成人禮。
作為一名微不足道的導演,在搭車旅行之前,我曾設想過拍一部公路電影,一男一女,兩段截然不同的旅程,目的地相同卻永遠沒有相遇。男主角路過生命的孤獨與割捨,女主角路過生命的迷惘與歡愉。寫作劇本是漫長艱辛的過程,我發現,公路片只能在公路上完成。在漫長的煎熬和等待中,好友谷岳的邀請彷彿是從天而降的禮物。三個多月的旅程,我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陌生人,在他們的車裡、家裡,遭遇不同人的人生:在新疆廣袤的沙漠,慷慨地搭每一位路人同行的石油卡車司機;在吉爾吉斯酒後遭遇牧民熱騰騰的馬油大餐;烏茲別克沙漠船隻墓地的守墓老人;裡海邊獨臂豪飲的俄羅斯水手;土耳其豪放熱誠的富二代;伊斯坦堡雄渾壯觀的歐亞兩岸;羅馬尼亞堅強的孤兒院志願者;匈牙利布達佩斯青年旅館的韓國老闆;布拉格的CROSS重金屬俱樂部;東柏林的藝術家貧民窟……親自體驗並拍攝一部公路紀錄片,是我這些年來最大的夢想。我相信公路電影的製作者們都經歷著這樣在路上的日子,思想的巡遊也必然伴隨著身體的遊歷。
《在路上》這本書從二○○○年一直陪伴我到現在,四次閱讀都沒有翻到最終章,命中注定它要留給這次旅程。在搭車旅途的某輛大卡車上,我在顛簸的駕駛室的臥鋪上讀完了最後一頁。車窗外是何時何地的風景,都已不再重要。
《在路上》的結尾這樣寫道:
我知道在愛荷華州,在人們允許孩子們哭泣的地方,孩子們在大聲地哭泣著。今夜,星星就要出來,你可知道那大熊星座就是上帝?今夜金星一定低垂,在祝福大地的黑夜完全降臨之前,把它熠熠的光輝灑落在草原上,藏起河流,裹住山峰,隱沒掉最後一片海灘,然而完全沒有人知道,自己除了可悲地趨向衰老外,還將有何遭遇。
這本小書是我個人的小小旅行隨想,有些旅程段落詳細,有些只是一筆帶過。這趟旅程我和谷岳約定好一人寫一本書,同樣的旅行不同的視角,不同的生命體驗與收穫。我偏執於一個普通北京人的視角,偶然的機緣巧合,展開搭車去十餘個國家的夢想之旅,我沒有超於常人的意志品質,也沒有職業旅行家的豐富經驗,更沒有超凡脫俗的個人魅力。我只是因為想要追求一些自己以為需要的東西而與朋友踏上旅途。旅途終結的時候,每個人的內心都因為這段路而得到了某種圓滿,於是那個原來執著的目標也許就不再重要。
◎清晨五點半的地鐵五號線
你可曾見過北京地鐵五號線清晨五點半的月臺?它華而不實地被設計成海洋動物曬乾後的軀殼的樣子,乾巴巴地,等待著早班的地下鐵從這邊來再從那邊走,等待著面無表情的人們前來重複命中注定的日子。我經常會在清晨,趕最早的一班地鐵回家,因為工作通常需要熬夜,我便有了這樣一種機會,體會與人群相反的軌跡,體會身體在極度透支後的某種亢奮,身體是軟的,而心底卻清明一片,靜逸安詳。你會發現夜與晝的更替是隨鳥的叫聲來臨,天知道北京竟有這麼多種鳥,在你不知道的遠方喧鬧。
鳥的聲音會被對面月臺漸漸匯聚的人聲終結,列車會把他們帶往市中心,而我的方向相反,等候在回家的路上,獨自擁有這一半的月臺,以一種旁觀的心態默默注視著對面越聚越多的人群。那些人雖然陌生,卻都是再熟悉不過的陌生人,我們都從五環外的新建高樓裡醒來,或是十幾個人擠在兩室一廳分割的公寓裡,因為搶洗手間而爭吵,因為左鄰右舍的梳洗打扮而詛咒著為什麼不能再睡上十幾分鐘。找到熟悉的早點攤,排隊買著熟悉的糊弄肚子的食物,然後強打起精神隨擁擠的地鐵奔赴一個小時後另一個屬於自己的格子間。
熟悉這樣的世界,這樣的陌生人,這樣的生活,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紋一樣。常常問自己,三十多歲了,如果有機會和別人交換各自的生活,那麼,我會選擇和誰交換?瀟灑地開寶馬(BMW)車的,還是在地鐵車廂裡啃油條的?沒有,熟悉的生活僅有這一點點差別,我們擁有同樣的苦難,僅靠可憐的一點點財富來顯示彼此的差別。三十多歲了,人生不再新鮮,多少對未知的探求也泯滅在這許許多多的「不得不」裡。不得不去向看板上成功的人生靠近:一家三口,穿著一塵不染的夏裝,跑向以外國風景地命名的美好社區,女人很滿足,男人很得意,孩子的頭髮很整齊。雖然覺得這一切很可笑,但是,開往城郊的地鐵來了,我也只能低頭走進車廂裡。每天,我們在地鐵五號線裡路過路人甲,再路過路人乙,看別人看自己,沒有一絲絕望。因為五號線代表我每天的旅程,無可選擇。
這僅是我二○○九年年初的想法 ,六個月後,我和一個叫谷岳的傢伙去了一萬多公里外的城市,那裡有他的姑娘,也有無數條血管般蓬勃的地鐵線,喧鬧地在每一個清晨流過城市的龐大身軀,那裡叫柏林。
◎谷岳的三分鐘
「三分鐘內可以發生許多事,欣賞一段不錯的音樂,吃一頓倉促的速食,經歷一場感情變故,改變一個人的某種世界觀,獲得或失去一筆財富,也可能失去親人,或離開一片你摯愛的熱土,再或踏上一段征途,很多很多……」
在北京南鑼鼓巷的一家小酒館,我把自己的三分鐘給了對面這個叫谷岳的傢伙,他用三分鐘和我說明了他的計畫:他想尋找一個旅伴,拍攝經驗豐富,能各自負擔費用,花三個月的時間,一起從北京出發,搭車旅行去德國首都柏林。用他的話講,去看女朋友的旅程也要給自己留下些什麼,這裡借用他的演講文稿:
「一直崇拜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再加上電影《摩托車日記》(台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和《荒野生存》(台譯:阿拉斯加之死)的啟發,我要去找伊卡,也要親自體驗一下『在路上』的自由精神。如果我是坐飛機去見她,那麼舷窗下的原野,我就無法用腳步去丈量,我和伊卡也就沒有更多的收穫,我想慢慢去感受與她距離越來越近所帶來的影響,對我生命的影響。
以前我也上過班,在二○○一年的時候,我在美國的通用電氣做金融(工作),算風險評估吧。工作了一個月後,突然有一天有一個深省,我就想我從小學就努力好好學習,上中學、上大學、找著一份好工作,要買房子、買車、結婚生孩子,這一輩子的東西都已經知道了,我覺得有點兒太遺憾了。所以二○○三年我把工作辭掉了,把我的家當都賣了,開始環球世界旅行。二○○六年認識我現在的女朋友伊卡,她是德國人。我跟她相處兩年後,她說她要回德國一段時間,想家了,這又給我再次上路的動力。另外我覺得社會越來越實際了,所有的東西都建立在金錢和互利的關係上,所以我想用這種搭車的方式,來尋找不是在金錢,不是在互利的關係上創建的一種友誼。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搭車,要搭陌生人的車。」
其實在這以前兩年我們就通過旅遊衛視的朋友認識,那時他就已經是職業的旅行家了。而我,一個拍紀錄片的小小導演,雖然也經歷過諸如雅魯藏布江大峽谷、長江源、柴達木、可哥西裡等地的探險拍攝,但旅行一直不是我的直接目的。而這次,更是沒有任何理由,只是要走,要出發,要一直走在路上。
十年前在電影學院讀書的時候,我拚命看《麥田裡的守望者》(台譯:麥田捕手)這樣的小說,聽《涅槃》,去中戲小劇場蹭話劇《盜版浮士德》,和同學們聊著某大師艱澀難懂的電影,憧憬著將來一起拍充滿新銳氣息的片子,唾棄著所謂俗氣的生活,那時候覺得這肯定就是自己將來的人生。但是慢慢地從畢業開始,我也進入了一種大家都會進入的生活。去掙錢,去過一種世俗人眼中你應該過的那種生活。谷岳用三分鐘說了他的想法後,問我能不能走,感覺言語中還要給我一些時間去思考。但我內心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定要走,雖然當時搭車對我來說還只是天空上飄著的一種概念。那時我正處於人生的低潮,感慨自己十多年的時間在北京這個城市裡做了很多莫名的事情,表面上熱熱鬧鬧,內心卻無比空虛。我的故鄉,這座巨大而喧鬧的城市,時常讓我害怕失去僅有的一點兒歸屬感,失去掙扎生存的勇氣。
我的生活像是在莫比斯環(Mobius band)上爬的螞蟻一樣,螞蟻一直以為能從紙的開端爬到紙的末端,爬到末端才發現其實又到了開始的地方。一直原地打轉,缺少生活的新鮮和激情。所以一定要走。決定的同時,隨之而來的是很多的顧慮:我的存款不多,這三個月走了,生活來源就沒有了,雖然我是自由職業,沒有固定工作,沒有辭職的問題,但是同樣面臨生存的壓力。房租怎麼交?以後怎麼辦?長期合作拍片的客戶這次拒絕了,以後人家還會不會來找你合作?很多的機會就因此失去了。但是能促使我把這些都拋下而毅然決定走的主要原因,還是對這個城市的感覺,有時候我會覺得整個城市已離棄了我,我從城市的中心漂流到了城市的周邊──記得小時候是在長安街沿線長大,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遷徙,到三環外,四環外,過了這麼多年,甚至置身五環以外,從二十三樓的出租房眺望環內,曾經的核桃樹與梧桐依然蒼翠,但已物是人非。我很想笑,既然生活已把自己趕得越來越遠,為何不乾脆痛快點兒走得更遠?去看看真正想看的東西,「在路上」這三個字,一下子跳出來,在腦海裡閃著神聖的光輝。
「有些事情現在不去做,就永遠不會做了。」對面拿著啤酒的谷岳沒來由地說了一句。
十年前,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科學新聞,至今想起仍會發冷。
一九九九年情人節那天,旅行者二號在掠過冥王星後,飛向沒有盡頭的宇宙深淵。它的孤獨讓人不寒而慄,在調整方向奔赴這一命運時,一個女科學家,遙控它做了最後一件事情:緩緩轉過身,將鏡頭朝向我們這個行星系,眨了最後一下眼睛。那張最孤獨的照片,遠沒有想像中宏偉,地球只是一粒可以拂去的塵沙。藍色的塵沙,與沙漠中任何一粒沙子一樣寂寞。
我無比羡慕旅行者二號,溫暖地告別後,一頭扎入冰冷的沒有盡頭的宇宙荒漠,飄蕩在充滿無盡可能性的虛空裡。
這次去柏林的旅程的紀錄片播出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感謝觀眾對我們的支持和厚愛。更令人鼓舞的是無數中國年輕人正拿起行囊,搭車奔走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去探索去收穫屬於自己的精彩旅程,完成自己的成人禮。
歡迎讀者能到網上或旅遊衛視收看我們的紀錄片《搭車去柏林》。
◎六月八日,從后海出發
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家裡把背包打了好幾遍,很少臨出門前會這麼仔細地準備行李。把東西拿出來又放進去,放進去又拿出來,反覆幾次都無從知道究竟要帶多少東西才能夠這三個月的旅行。這種心情有點兒像小學去郊遊的前一天晚上,興奮得睡不著覺,一直檢查自己包裡的糖果巧克力是不是夠吃一樣。愣愣地看著撐得滿滿的大包小包,它們靜靜地像在問我,到底準備好了麼?
雖然十年的拍片生涯中也經常出門,足跡基本上踏遍了大半個中國,但一直有著團隊的支持和精心的計畫。這次和谷岳一起,行程中太多要靠自己去解決和完成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恨不得把家也一起背走。沒錯,對背包客來講,這兩個歪歪扭扭的包就是家了。這種隨意旅行的方式,我一直嚮往很久,我痛恨充滿計畫的行程,彷彿一眼就可以看到結局的電影。然而,真的要上路時,我可以聽到來自遙遠內心的咚咚鼓聲。
六月八日,我們兩人在后海的一個酒吧裡面碰頭,就像平常一樣。我們把出發的地點定在后海,因為那曾經是少年時代的樂園,游泳,滑冰,刷夜(編按:不回家,在外面過夜)。中學時也會每天放學騎車專門到湖邊轉一圈,不為了什麼,只是單純地發呆,坐到太陽落山,水邊晚風吹來,聽著湖對面生澀的薩克斯,很舒服,也許這就是故鄉的感覺。與其說從后海的某一地出發,不如說是從我心裡的某一塊地兒出發。碰巧谷岳也有后海情結。他對北京許多快樂的記憶也是在后海沿岸發生的。但我們去了以後才發現,那天下了北京乾旱許久後的第一場大雨,我們被困在那兒了。
酒吧裡一個客人都沒有,早上十點,我們聚齊,外面雲霧濛濛,湖面平靜。拍了第一張合影照片,換上衝鋒衣(編按:透氣防水的登山服),各自背起四十公斤的負重。包裡除了衣服、帳篷、睡袋外,還有兩部攝影機和照相機、三角架、筆記本、各種充電器、電池,甚至一人還有一瓶防狼噴霧劑。把包一背,好像真是要遠行了。這時雨突然就大起來了,越等越大,中午了,不能再等下去,我們冒著大雨放棄了坐公車去公路邊的想法,攔了一輛出租車,趕赴六里橋京石高速入口,開始我們三個半月的搭車旅行……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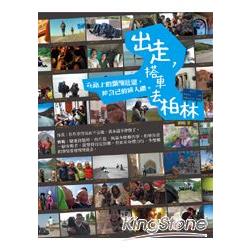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