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巴塔哥尼亞快車(旅行文學名家保羅‧索魯經典作紀念版):一個旅人X從北美到南美X 22種火車旅遊風情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一個旅人。從北美到南美。 22種火車旅遊風情
抱著流浪的情懷,我踏上第一班火車,一般人搭這班車是為了上班。
他們下車——他們的火車之旅已然終結;
我留在車廂,我的火車之旅,才剛開始。
「索魯的風格就是那種穿透世俗虛偽的銳利,毫不留情,也絕不隨俗。」
——詹宏志
「我感興趣的是在晨光清醒後的故事:從熟悉到有點陌生、到頗為新奇、到全然不識,最後到置身於奇鄉異地。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達;是旅行,而非降落……。我於是決定做個實驗,隻身隨著火車,從麻薩諸塞州的梅德福向南奔到不能再遠的地方……。」
單單是為了一個再單純不過的「實驗」的念頭,作者保羅‧索魯不設定旅行目的,也不預期行旅的心情,只帶著一副沾沾自喜的如逃犯般落魄的模樣,展開一場從北美到南美別出心裁的漫長旅程。
在旅程的起點,保羅‧索魯選擇湖岸快車與他一同登場。平穩前行的列車上,他讓別人的終點站成為自己的起始,晃晃盪盪地揭開與空間的對話之旅。整個旅程由二十二種火車接力式地串聯而成,且以不同風貌呈現奇麗多變的旅行情味。如橫跨美國六州的孤星號,像櫥窗般透視出墨西哥的衰頹與肉慾的阿茲提克之鷹,橫越重山駛往秘魯的山脈列車;還有穿行國界、路程長達一千哩以上的泛美特快車……最後,為旅程畫下句點的,則是有百年歷史、速度也如年邁老牛的老巴塔哥尼亞「特快」車。
一場孤獨的旅程,二十二種不同風情的火車,隨著悠長的汽笛鳴聲,讓一幕幕真實上演的旅遊過程,有情有味地在《老巴塔哥尼亞快車》一書中重現。
【書評讚譽】
★索魯的風格就是那種穿透世俗虛偽的銳利,豪不留情,也絕不隨俗。……我曾說索魯是「反省『旅行』本身的旅行者」。——詹宏志
★無庸置疑地,……這是一本有史以來,書寫火車之旅最傑出的著作。——珍.莫里斯(Jan Morris)
★就像絕妙的對話,一本傑出的旅行書包含兩個要素:敘述與評論……索魯的評論總是藉精簡的散文形式來表現。有趣的是,在本書的每一段旅程中,敘事的技法更加突出——尤以描寫聖薩爾瓦多的足球賽及其騷動場面最為精采出色——書中對話體的敘述手法,堪稱索魯所有作品之最。——保羅.弗謝爾(Paul Fusell)
★旅遊書寫的極致表現……即便連瑣碎乏味也充滿興味與人情味;對於無家可歸的孩童的描述,更是令人滿心悲淒,難以忘懷。——每日電訊報
★當代最迷人的旅行書之一。——金融時報
抱著流浪的情懷,我踏上第一班火車,一般人搭這班車是為了上班。
他們下車——他們的火車之旅已然終結;
我留在車廂,我的火車之旅,才剛開始。
「索魯的風格就是那種穿透世俗虛偽的銳利,毫不留情,也絕不隨俗。」
——詹宏志
「我感興趣的是在晨光清醒後的故事:從熟悉到有點陌生、到頗為新奇、到全然不識,最後到置身於奇鄉異地。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達;是旅行,而非降落……。我於是決定做個實驗,隻身隨著火車,從麻薩諸塞州的梅德福向南奔到不能再遠的地方……。」
單單是為了一個再單純不過的「實驗」的念頭,作者保羅‧索魯不設定旅行目的,也不預期行旅的心情,只帶著一副沾沾自喜的如逃犯般落魄的模樣,展開一場從北美到南美別出心裁的漫長旅程。
在旅程的起點,保羅‧索魯選擇湖岸快車與他一同登場。平穩前行的列車上,他讓別人的終點站成為自己的起始,晃晃盪盪地揭開與空間的對話之旅。整個旅程由二十二種火車接力式地串聯而成,且以不同風貌呈現奇麗多變的旅行情味。如橫跨美國六州的孤星號,像櫥窗般透視出墨西哥的衰頹與肉慾的阿茲提克之鷹,橫越重山駛往秘魯的山脈列車;還有穿行國界、路程長達一千哩以上的泛美特快車……最後,為旅程畫下句點的,則是有百年歷史、速度也如年邁老牛的老巴塔哥尼亞「特快」車。
一場孤獨的旅程,二十二種不同風情的火車,隨著悠長的汽笛鳴聲,讓一幕幕真實上演的旅遊過程,有情有味地在《老巴塔哥尼亞快車》一書中重現。
【書評讚譽】
★索魯的風格就是那種穿透世俗虛偽的銳利,豪不留情,也絕不隨俗。……我曾說索魯是「反省『旅行』本身的旅行者」。——詹宏志
★無庸置疑地,……這是一本有史以來,書寫火車之旅最傑出的著作。——珍.莫里斯(Jan Morris)
★就像絕妙的對話,一本傑出的旅行書包含兩個要素:敘述與評論……索魯的評論總是藉精簡的散文形式來表現。有趣的是,在本書的每一段旅程中,敘事的技法更加突出——尤以描寫聖薩爾瓦多的足球賽及其騷動場面最為精采出色——書中對話體的敘述手法,堪稱索魯所有作品之最。——保羅.弗謝爾(Paul Fusell)
★旅遊書寫的極致表現……即便連瑣碎乏味也充滿興味與人情味;對於無家可歸的孩童的描述,更是令人滿心悲淒,難以忘懷。——每日電訊報
★當代最迷人的旅行書之一。——金融時報
目錄
導讀 只有旅程,沒有目的地 / 詹宏志
楔子
第1章 湖岸快車
第2章 孤星號
第3章 阿茲提克之鷹
第4章 搭莽夫號前往韋拉克魯斯
第5章 通往塔帕丘拉的客車
第6章 往瓜地馬拉城的七點半班車
第7章 往薩卡帕的七點整班車
第8章 往聖薩爾瓦多的單節小火車
第9章 往庫圖克的慢車
第10章 大西洋線:往利蒙的十二點班車
第11章 太平洋線:往蓬塔雷納斯的十點班車
第12章 到科隆的巴波亞子彈列車
第13章 到波哥大的太陽號特快車
第14章 卡利馬特快車
第15章 往瓜亞基爾的自動火車
第16章 山脈列車
第17章 開往麻丘比丘的火車
第18章 泛美號
第19章 往布宜諾賽利斯的北極星號
第20章 布宜諾賽利斯地下鐵
第21章 南湖特快車
第22章 老巴塔哥尼亞特快車
楔子
第1章 湖岸快車
第2章 孤星號
第3章 阿茲提克之鷹
第4章 搭莽夫號前往韋拉克魯斯
第5章 通往塔帕丘拉的客車
第6章 往瓜地馬拉城的七點半班車
第7章 往薩卡帕的七點整班車
第8章 往聖薩爾瓦多的單節小火車
第9章 往庫圖克的慢車
第10章 大西洋線:往利蒙的十二點班車
第11章 太平洋線:往蓬塔雷納斯的十點班車
第12章 到科隆的巴波亞子彈列車
第13章 到波哥大的太陽號特快車
第14章 卡利馬特快車
第15章 往瓜亞基爾的自動火車
第16章 山脈列車
第17章 開往麻丘比丘的火車
第18章 泛美號
第19章 往布宜諾賽利斯的北極星號
第20章 布宜諾賽利斯地下鐵
第21章 南湖特快車
第22章 老巴塔哥尼亞特快車
序/導讀
只有旅程,沒有目的地
──我讀索魯的《老巴塔哥尼亞快車》 / 詹宏志
把地圖打開來,你會看到密密麻麻的交通網路,有很多路途是相通的,只是真實生活上你不一定用得到或想到要用,譬如說,理論上你可以從香港搭乘火車一路(經過許許多多奇怪的目的地)通往倫敦,但很少人實際上這麼做,他3.們多數是選擇搭乘一趟毫無風景也毫無過程的飛機,睡眼惺忪地到達了地球的另一端。
有一位旅行作家卻在他新英格蘭的家中看著牆上地圖,看出了從他家通往波士頓城裡的通勤火車可以接上開往芝加哥的火車,而芝加哥又有長途火車可以抵達德州,在德州你又能找到火車通過邊境前往墨西哥,這個時候你已經離開北美洲了;墨西哥又有火車前往瓜地馬拉和宏都拉斯,然後再通向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如果還要繼續往南,那火車還能帶你再通往哥斯大黎加和巴拿馬,然後你離開中美洲進入了南美;這火車線繼續接往哥倫比亞再進厄瓜多,還可以通往秘魯,從秘魯往南你可以 選擇往狹長的智利,還是東折經玻利維亞前往阿根廷,阿根廷一路向南,我們就來到阿根廷南部高地,也就是所謂的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火車的終點在高原上一個小鎮叫伊斯奎(Esquel),按照阿根廷大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說法,「那裡雖不是撒哈拉,但卻是阿根廷最像撒哈拉的地方,那裡什麼都沒有。」
打開地圖用放大鏡仔細看,的確有一條代表鐵路的彎曲綿延細線,讓你可以從波士頓一路搭乘火車,直到這「什麼都沒有」的阿根廷南部高地,穿過十三個國家和無數個城鎮,穿過一萬公里和各形各色的地景地理以及無數種文化歷史。是的,你從波士頓出發,最後終將到達老巴塔哥尼亞,問題是,你會瘋狂到想要這樣做嗎?
有一位旅行作家確實想到這麼做,也真的做了。否則我們將如何有今天這本奇書可茲閱讀討論?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1941- )是當今文壇一位特立獨行的作家,寫小說與旅行文學,兩者都舉世矚目。他的小說也充滿了旅行,代表作《蚊子海岸》(The Mosquito Coast, 1981)曾拍攝成電影,描寫的就是一位美國作家棄絕文明,攜家帶眷前往南美洲宏都拉斯,想在叢林蠻荒建造理想家園的故事。《蚊子海岸》的故事描寫的不是浪漫詩意,而是大自然的殘酷,滿懷理想的作家真正面對的是人類孤獨自賴的艱難,甚至連累他的親人紛紛受難;這是一個自我發現與理想幻滅的故事,可說是另種角度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也因此他的作品常常被拿來和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6)作比較。
保羅.索魯自己則是另一個瘋狂的旅行者,在他另一部有意思的旅行作品《大洋洲的快樂島嶼》(The Happy Isles of Oceania, 1992)中,他本來只是要應邀到紐西蘭作一個幾天的新書宣傳,但他的行李包括了一張帳篷、一個睡袋,以及一艘可折疊的獨木舟,結果他流浪在太平洋裡,一共划遊了五十一個島,最後停在夏威夷,直到書本結束時還沒有回家。
索魯的旅行作品常常發人深省,但不一定是來自旅程中的觀察;事實上他對旅行過程中的地方與人物的觀察有時尖銳得令人不快。有一次我甚至看到一篇書評說:「如果他這麼不喜歡他在路上所看到的人與事,他又何必勞煩去寫一本旅行作品。」保羅.索魯也許是太世故也太犬儒了,他常常一下子視破許多人間的虛偽,對凡夫俗子的愚言愚行尤其有敏感的了解與記錄,我們不要忘了他的另一個身分是小說家,日常生活的荒謬有時是比壯麗景觀更值得記錄的事。
索魯最銳不可當的反省在於他對「旅行書寫」的觀察,譬如說多數的旅遊作品的「美滿結局」是回家,他就寫下了一本「旅行者沒回家」的奇特旅行書(《大洋洲的快樂島嶼》);又譬如說,多數的旅行作品的重心在一個獨特的「旅遊地」,索魯就刻意創造一個沒有旅遊地的旅程,也就是我們即將要閱讀的這部《老巴塔哥尼亞快車》(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1979),這本書從一開始就乘坐火車,一直坐到鐵路的盡頭,從波士頓郊外社區坐到阿根廷南部高原,走到無路可走,旅行就結束了,這場旅行沒有目的地,只有旅程。
在《大洋洲的快樂島嶼》裡,作者離家時忍受不住離婚的痛苦(「當我獨自一人,基於習慣,我只睡在床的左側,醒來時看到旁邊的空曠,加倍覺得孤單。」),書本結束時他親吻著身旁的女孩,並寫道:「當你快樂時就像是回家了。」索魯不是不知道旅行作品是要回家的,只是他自覺地用了另一種回家的概念,一場旅行連結了兩個婚姻(或關係),一個人在旅行中變身並且治療,以另一個新的自己出現,旅行就該結束了。
在《老巴塔哥尼亞快車》裡,索魯一開始就短暫提到另一本旅行經典《察沃的食人魔》(The Man-eaters of Tsavo, 1907),抱怨作者沒有提到離家時的細節,書本一開始人已經來到非洲,彷彿一切為英雄事蹟作準備,但你總得離開家呀,也總得和行李作一番狼狽的搏鬥。可是沒有,多數的旅行書不寫這些瑣事。《察沃的食人魔》其實是一本「狩獵旅行」經典,記錄的是上個世紀末,英國政府計畫從肯亞海港蒙巴薩(Mombasa)建造一條鐵路直入烏干達境內,更從印度運來三萬五千名建築工人,結果有兩頭獅子「做到了德國人做不到的事」,把整個大英帝國鐵路建築工程完全停擺了下來,因為這兩頭神出鬼沒的獅子一共吃了(或咬死了)超過一百個工人,引發工人們的恐慌性罷工。一位工程師、業餘的獵人帕特森(J. H. Patterson, 1867-1947)以他的謹慎和毅力,和兩隻「察沃的食人魔」周旋,最後獵殺了這兩頭獅子,也寫下這部史上最驚險的狩獵傳奇,最近才被拍成好萊塢電影,而那兩頭獅子的標本也還放在芝加哥的博物館裡。
《老巴塔哥尼亞快車》則有意識地把離家作為起點,作者索魯搭上郊區前往市區的通勤火車,車內多數人是要去上班的,人群中只有一個人的終點在遙遠得無法想像的地方,到了市區換上長途火車,但這「長途」比起旅行者的旅途還微不足道,車上也沒有其他旅客了解或相信他的終點在更遠的地方。火車更迭,景觀變換,熟悉的場景逐漸陌生,終究完全陌生;最後你走到盡頭,那裡空曠無涯,大片草原滿布野花,對很多執意的旅行者也許旅行才要開始,但索魯卻說:「這是我的終點。」
因為他是反省「旅行」本身的旅行者。
──我讀索魯的《老巴塔哥尼亞快車》 / 詹宏志
把地圖打開來,你會看到密密麻麻的交通網路,有很多路途是相通的,只是真實生活上你不一定用得到或想到要用,譬如說,理論上你可以從香港搭乘火車一路(經過許許多多奇怪的目的地)通往倫敦,但很少人實際上這麼做,他3.們多數是選擇搭乘一趟毫無風景也毫無過程的飛機,睡眼惺忪地到達了地球的另一端。
有一位旅行作家卻在他新英格蘭的家中看著牆上地圖,看出了從他家通往波士頓城裡的通勤火車可以接上開往芝加哥的火車,而芝加哥又有長途火車可以抵達德州,在德州你又能找到火車通過邊境前往墨西哥,這個時候你已經離開北美洲了;墨西哥又有火車前往瓜地馬拉和宏都拉斯,然後再通向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如果還要繼續往南,那火車還能帶你再通往哥斯大黎加和巴拿馬,然後你離開中美洲進入了南美;這火車線繼續接往哥倫比亞再進厄瓜多,還可以通往秘魯,從秘魯往南你可以 選擇往狹長的智利,還是東折經玻利維亞前往阿根廷,阿根廷一路向南,我們就來到阿根廷南部高地,也就是所謂的巴塔哥尼亞(Patagonia);火車的終點在高原上一個小鎮叫伊斯奎(Esquel),按照阿根廷大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說法,「那裡雖不是撒哈拉,但卻是阿根廷最像撒哈拉的地方,那裡什麼都沒有。」
打開地圖用放大鏡仔細看,的確有一條代表鐵路的彎曲綿延細線,讓你可以從波士頓一路搭乘火車,直到這「什麼都沒有」的阿根廷南部高地,穿過十三個國家和無數個城鎮,穿過一萬公里和各形各色的地景地理以及無數種文化歷史。是的,你從波士頓出發,最後終將到達老巴塔哥尼亞,問題是,你會瘋狂到想要這樣做嗎?
有一位旅行作家確實想到這麼做,也真的做了。否則我們將如何有今天這本奇書可茲閱讀討論?
保羅.索魯(Paul Theroux,1941- )是當今文壇一位特立獨行的作家,寫小說與旅行文學,兩者都舉世矚目。他的小說也充滿了旅行,代表作《蚊子海岸》(The Mosquito Coast, 1981)曾拍攝成電影,描寫的就是一位美國作家棄絕文明,攜家帶眷前往南美洲宏都拉斯,想在叢林蠻荒建造理想家園的故事。《蚊子海岸》的故事描寫的不是浪漫詩意,而是大自然的殘酷,滿懷理想的作家真正面對的是人類孤獨自賴的艱難,甚至連累他的親人紛紛受難;這是一個自我發現與理想幻滅的故事,可說是另種角度的《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1899),也因此他的作品常常被拿來和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6)作比較。
保羅.索魯自己則是另一個瘋狂的旅行者,在他另一部有意思的旅行作品《大洋洲的快樂島嶼》(The Happy Isles of Oceania, 1992)中,他本來只是要應邀到紐西蘭作一個幾天的新書宣傳,但他的行李包括了一張帳篷、一個睡袋,以及一艘可折疊的獨木舟,結果他流浪在太平洋裡,一共划遊了五十一個島,最後停在夏威夷,直到書本結束時還沒有回家。
索魯的旅行作品常常發人深省,但不一定是來自旅程中的觀察;事實上他對旅行過程中的地方與人物的觀察有時尖銳得令人不快。有一次我甚至看到一篇書評說:「如果他這麼不喜歡他在路上所看到的人與事,他又何必勞煩去寫一本旅行作品。」保羅.索魯也許是太世故也太犬儒了,他常常一下子視破許多人間的虛偽,對凡夫俗子的愚言愚行尤其有敏感的了解與記錄,我們不要忘了他的另一個身分是小說家,日常生活的荒謬有時是比壯麗景觀更值得記錄的事。
索魯最銳不可當的反省在於他對「旅行書寫」的觀察,譬如說多數的旅遊作品的「美滿結局」是回家,他就寫下了一本「旅行者沒回家」的奇特旅行書(《大洋洲的快樂島嶼》);又譬如說,多數的旅行作品的重心在一個獨特的「旅遊地」,索魯就刻意創造一個沒有旅遊地的旅程,也就是我們即將要閱讀的這部《老巴塔哥尼亞快車》(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 1979),這本書從一開始就乘坐火車,一直坐到鐵路的盡頭,從波士頓郊外社區坐到阿根廷南部高原,走到無路可走,旅行就結束了,這場旅行沒有目的地,只有旅程。
在《大洋洲的快樂島嶼》裡,作者離家時忍受不住離婚的痛苦(「當我獨自一人,基於習慣,我只睡在床的左側,醒來時看到旁邊的空曠,加倍覺得孤單。」),書本結束時他親吻著身旁的女孩,並寫道:「當你快樂時就像是回家了。」索魯不是不知道旅行作品是要回家的,只是他自覺地用了另一種回家的概念,一場旅行連結了兩個婚姻(或關係),一個人在旅行中變身並且治療,以另一個新的自己出現,旅行就該結束了。
在《老巴塔哥尼亞快車》裡,索魯一開始就短暫提到另一本旅行經典《察沃的食人魔》(The Man-eaters of Tsavo, 1907),抱怨作者沒有提到離家時的細節,書本一開始人已經來到非洲,彷彿一切為英雄事蹟作準備,但你總得離開家呀,也總得和行李作一番狼狽的搏鬥。可是沒有,多數的旅行書不寫這些瑣事。《察沃的食人魔》其實是一本「狩獵旅行」經典,記錄的是上個世紀末,英國政府計畫從肯亞海港蒙巴薩(Mombasa)建造一條鐵路直入烏干達境內,更從印度運來三萬五千名建築工人,結果有兩頭獅子「做到了德國人做不到的事」,把整個大英帝國鐵路建築工程完全停擺了下來,因為這兩頭神出鬼沒的獅子一共吃了(或咬死了)超過一百個工人,引發工人們的恐慌性罷工。一位工程師、業餘的獵人帕特森(J. H. Patterson, 1867-1947)以他的謹慎和毅力,和兩隻「察沃的食人魔」周旋,最後獵殺了這兩頭獅子,也寫下這部史上最驚險的狩獵傳奇,最近才被拍成好萊塢電影,而那兩頭獅子的標本也還放在芝加哥的博物館裡。
《老巴塔哥尼亞快車》則有意識地把離家作為起點,作者索魯搭上郊區前往市區的通勤火車,車內多數人是要去上班的,人群中只有一個人的終點在遙遠得無法想像的地方,到了市區換上長途火車,但這「長途」比起旅行者的旅途還微不足道,車上也沒有其他旅客了解或相信他的終點在更遠的地方。火車更迭,景觀變換,熟悉的場景逐漸陌生,終究完全陌生;最後你走到盡頭,那裡空曠無涯,大片草原滿布野花,對很多執意的旅行者也許旅行才要開始,但索魯卻說:「這是我的終點。」
因為他是反省「旅行」本身的旅行者。
試閱
第一章 湖岸快車
那輛平穩前進的火車上,有一個人顯然不是去上班的。從他袋子的尺寸,你一眼就瞧得出來。一如你總是可以從那副沾沾自喜的落魄相,嗅出逃犯的氣味;他的嘴裡似乎含著祕密——好像馬上要吹出泡泡來。唉,算了吧,幹嘛要吞吞吐吐的呢?我在自己的老臥房裡醒來,一生絕大多數歲月,我都是在這棟屋子度過的。冰雪深埋屋宇周圍,凍結的足跡穿越後院,直達垃圾桶。暴風雪才剛造訪過此地,預料不久後另一場即將颳起。我比平常更加小心翼翼地整裝、綁鞋帶,放過嘴唇上方的鬍渣不刮,以便蓄鬍留鬚。拍拍口袋,確定原子筆和護照安然無恙,我下了樓,與母親那只老在打呃的咕咕鐘擦肩而過,然後前往威靈頓圓環(Wellington Circle)搭火車去。今早是一個凍得教人麻痺的霜雪天,好一個前往南美洲的良辰吉日。
對某些人來說,這班列車是通往蘇利文廣場(Sullivan Square)或是米爾克街(Milk Street),抑或終點站東方高地(Orient Heights);但對我而言,這班車將帶領我前往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兩個男人用外國語低聲交談著;有的人攜著午餐盒、小旅行袋與公事包;一位小姐拿著一只縐巴巴的百貨公司用袋,顯然是要去退還或是交換不要的商品(舊袋子把這趟尷尬之旅更襯托得栩栩如生)。嚴寒改變了車內多種族乘客的容顏,白人的臉頰好似灑滿了粉紅粉筆灰,中國人全無血色,黑人面色呈灰白或灰黃。曙光初露時是華氏十二度,等到九、十點左右卻降到了九度,且在持續下降中。行經秣市(Haymarket),車門一開,冷風便呼呼吹進車廂,兩位絮語不斷的外國人也噤了口,看上去是地中海人吧,迎面的冷風繃緊了他們的面部肌肉。乘客大多縮成一團,手肘貼緊了身體兩側,手擱在膝蓋上,半瞇著眼,努力保藏著自個兒的溫度。
他們在城裡有事待辦——工作、購物、上銀行,或是到百貨公司退物處辦理尷尬差事兒。有兩人膝蓋上擱著厚重的教科書,一個背向我的身影正讀著《社會學導論》(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一個男人嚴肅地掃瞄過《環球報》(Globe)的標題,還有一個人,正用拇指翻弄著公事包內的文件。一位女士告誡她的小女兒腳不要亂踢,身子坐正些。四站過後,車子原已坐得半滿——但現在,人全湧入了狂風大作的月台。他們會在傍晚時分返家,一整天都在高談闊論天氣的種種。然而,他們為此而全副武裝,辦公服之外還罩著愛斯基摩大衣,戴著五指手套、圓形手套、羊毛帽。決心懸在他們的臉龐而疲憊的表情,已漸露端倪。沒有半絲興奮的痕跡,一切都再普通平常不過。搭火車,早就是他們的例行公事。
沒人望向窗外,他們從前就瞧過港口、邦克山(Bunker Hill)與沿路的看板了。他們也不注視彼此,視線就僵在眼睛前數吋不動。可縱使他們對頭上的廣告視若未睹,後者仍對前者訴說著訊息。這些傢伙是當地人,他們舉足輕重,而廣告公司也知道他們旳銷售對象是誰。需要聯邦直接稅表格嗎?其下,一個身著厚呢水手上衣的年輕人正對著報紙露齒而笑,吞嚥口水。兌現您的支票,行遍麻省。一位面色灰黃如南非哈藤塔特族(Hottentot)的女士,緊緊抱著她的購物袋。請自動自發贊助波士頓的公立學校。對於那位頭戴俄式小帽、檢視公事包文件的無聊仁兄而言,倒也不賴。想抵押借款嗎?找我們就對了!沒有人往上瞧。修理屋頂與排水溝。利用閒暇時間取得大學學位。一家餐廳。一家廣播電台。一則宣導戒菸的告示。上述標語的宣傳對象不是我,它們管的是當地事,但今早我將遠離。當你遠離之際,廣告所蘊涵的許諾便不再有實質的意涵。金錢、學校、房屋、廣播:我將一切拋諸腦後。這段從威靈頓圓環到史泰特街(State Street)的短短路程上,廣告變成了一連串哀懇的呢喃,有如某種不知名語言的胡扯瞎談。我大可聳肩以對,因為我正坐著車遠離家園。除了酷寒及落雪反照出的刺眼亮光,其餘事對我的旅程一無影響。除了一件事之外,一切都不再重要:當列車緩緩駛進南站(South Station)時,我離巴塔哥尼亞又近了一英里。
一趟火車之旅的序幕
旅行是一幕消逝的場景,一場孤獨的旅程,沿著變形的地理線,進入全然的遺忘。
流浪變成何種模樣?
既然它逃開了我們所有人。
然而旅行書恰恰相反,孤獨者回歸日常生活,繪聲繪影地描述他與空間的這樁實驗物語。旅行書是最簡單明瞭的一種敘述,它是一項解釋,自個兒為出現和消失的理由自圓其說。它是一種律動,規律來自於字詞的堆積重複。印象的消褪是銳不可擋的,但少有完全不存於記憶者。然而,傳統上卻會濃縮旅行書寫,從中間起頭(一如許多小說),猛地就把讀者放在奇鄉異國,卻不先領他前往該處。一本書的開頭可能如下:「白蟻把我的吊床當點心吃掉了」;抑或,「從巴塔哥尼亞的山谷往下深入,盡是灰色奇岩,滿載著洪水所遺留的千古刻痕及裂縫。」乾脆從伸手可及的距離隨機取出三本書,查看一下開頭句好了:
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近正午時分,我首次發現,自己進入了非洲東岸蒙巴薩(Mombasa)那險象橫生的狹灣。(《察沃的食人魔》[The Man-Eaters of Tsavo],帕特森[J. H. Patterson]著)
「歡迎光臨!」路邊碩大的廣告牌如是說。此時,車子已完成了螺絲狀的登高之旅,從南印度平原的酷熱,一下子躍入近乎天賜的涼爽。(《保護下的烏迪》[Ooty Preserved],龐特-道恩斯[Mollie Panter-Downes]著)
從房間的陽台上,我可以一覽加納(Ghana)首都阿克拉(Accra)的全景。(《你屬於何家部落?》[Which Tribe Do You Belong To?],莫拉微亞[Alberto Moravia]著)
可是,我向來的疑問,在這幾本旅行書(大多數旅行書)裡卻避而不答:你是怎麼抵達那兒的?連動機都不提,歡迎的序幕就已然揭起。前去的過程其實往往與抵達一樣繽紛多彩。不過,由於好奇心本身已蘊涵著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又被視為一項奢侈品(可是,反正有什麼好急的呢?),我們已習慣生活就是一連串的到達與道別、成功與失敗,而中間種種是不值一顧的。帕爾納索斯山(Mount Parnassus,位於希臘中部,希臘神話中為祭祀太陽神阿波羅之地--譯註)的頂峰是眾所矚目的焦點,但較低的斜坡呢? 我們並非對離家的過程全無信心,但相關文字卻少得可憐。離別被形容成恐慌的一刻,在機場大廳驗票的瞬間,舷梯旁笨拙的親吻;然後一切寂靜無聲,直到,「從房間的陽台上,我可以一覽加納首都阿克拉的全景……」
旅行,其實是兩碼子事。打從醒來的那一瞬間,你就在往一個陌生的地方邁進,每一段路程(譬如和咕咕鐘擦肩而過,順著富爾頓[Fulton]進入費斯威[Fellsway]等等),都領你更近了目的地一步。《察沃的食人魔》一書的背景是本世紀初的肯亞,描寫獅子吞食印地安鐵路工人。但我敢打賭,一本更加細膩精彩的書原本大有可能誕生,內容則是從南安普頓(Southampton,位於美國紐約州東南部--譯註)到蒙巴薩的海上之旅。只不過,帕特森上校基於種種個人因素,並未著手撰寫。
旅遊文學已變成細微小道不足觀矣。典型的開場是,從飛機傾斜的機身,鬧劇似把鼻子緊貼著舷窗往下望。這種逗笑的開場,這種特意加強的效果,已太為人熟悉,連諧仿(parody)都幾近毫無可能。他們是怎麼說的?「下方,橫著熱帶草原、洪水沒頂的山谷、宛如百衲被的農田。當飛機穿過雲層時,我可瞧見蜿蜒攀往山丘的泥巴路,以及小得近似玩具的車輛。我們繞著機場飛,當飛機降低準備著地,我看見了雄壯威武的棕櫚樹、收成的農田、襤褸人家的屋頂、用簡陋柵欄綴在一起的方形田野、宛如螻蟻的人類、五彩繽紛的……」
我從不以為這種臆測有任何說服力可言。我則每當飛機降落時,一顆心早懸到了喉嚨口。我擔心——難道你們不會嗎?——下一秒鐘大夥兒即將墜機。我一生的片段在眼前迅速閃過,錯失與傷感的種種枝節小事,短促地浮現心頭。然後,某個聲音響起,告訴我請留在座位,直到飛機完全降落。等到飛機抵達停機坪,播音器會放出電影《月河》(Moon River)的交響組曲。我猜想,如果我有勇氣四處張望的話,也許可看到一個旅行文學作家在振筆直書:「下方,橫著熱帶草原……」
話說到這兒,到底旅行是怎生風貌?也許確實沒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搭飛機的經驗大多無事可說。值得一提的事件顯然跟災難脫不了關係,所以人們才會以否定句來定義「愉快的搭機經驗」:你沒碰上劫機,你沒遇到墜機,你沒嘔吐,你沒遲到,機上的食物不會讓你皺眉頭。基於以上種種,你心懷感激,感激使你鬆了一口氣,導致內心一片空白。這也滿說得通的,因為,搭機的乘客等於是時空旅人。他爬入內鋪地毯、散發強烈消毒味兒的通道,把繫好皮帶,準備返鄉或離家。時間變短了,或者該說時間扭曲變形了,使他從一個時間區離開,在另一個時間區出現。打從他踏入通道,把膝蓋緊靠在前座,僵直身子的那一刻起——打從他離去的那一刻起,他的心思就只專注於抵達。當然囉,前提是,如果他還有任何感覺的話。就算他凝睇窗外,所見除了如北極凍原般的雲層外,絕無他物,上方則是寬曠的空間。時間被閃耀地遮蒙住了:沒有任何景物值得一瞧。因此,許多人對搭飛機一事感到歉意滿懷。他們說:「其實我真的很想把那隻塑膠怪獸拋到腦後,改去搭三桅帆船。我要站在船尾甲板上,好讓海風吹拂我的頭髮。」
其實無需抱歉。搭飛機也許並非一般定義的旅行,但確實是項奇蹟。只要付得起機票,搭上正確的電扶梯(以波士頓的洛根機場[Logan Airport]為例好了),任何人都可以變出德拉千非(Drachenfels)的峭壁,或伊尼斯弗綠(Innisfree)的島湖(Lake Isle)——不過,有一點必須聲明清楚:搭電扶梯上行的短短一段路,也許比整趟航行加起來,更能豐富心靈且富有旅行的風味。其餘的,外國異地,也就是構成抵達的種種,只剩下那條連結飛機與惡臭機場的上下活動梯。如果搭機客把這類型的轉乘視為旅行,而寫入書中呈現大眾,讀者遇見的第一個外國人,不是搜身的海關人員,就是移民入境檢查處裡蓄有鬍鬚的惡魔。儘管,搭飛機已躍為世界的流行,我們仍必須哀嘆下列事實:飛機使我們對空間不再敏銳;我們遭受束縛,一如身著盔甲的戀侶。
顯而易見,我感興趣的是於晨光清醒之後的故事:從熟悉到有點陌生、到頗為新奇、到全然不識。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達;是旅行,而非降落。我自覺上了旅行書籍的當,並懷疑自己抗拒的事物到底是什麼。我決定做個實驗:親身前往旅行書上提到的國家,隨著火車,從麻州的梅德福(Medford)向南奔到不能再遠的地方;在一般旅行書開始的地方,劃下本書的句點。
反正我沒別的事好做。我的寫作生涯漸受肯定,才剛寫完一部小說,兩年足不出戶了。我尋覓著別的寫作題材,卻發現非但沒有走上正途,反而在曲路上不停徘徊。我痛恨嚴寒的天氣,我需要陽光,而且我目前沒有工作——所以,還有什麼能阻住我的腳步?在研究地圖之後,發現從梅德福的家園,到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亞大草原之間,似乎有條絡繹不絕的絲線。火車可直通到伊斯奎小鎮(Esquel,位於巴塔哥尼亞北側--譯註),其後便毫無鐵軌蹤跡。而若想前往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火車是不得其門而入,但在梅德福和伊斯奎之間,鐵路繁似星斗。
抱著流浪的情懷,我踏上第一班火車,一般人搭這班車是為了上班。他們下車——他們的火車之旅已然終結;我留在車廂,我的火車之旅,才剛開始。
那輛平穩前進的火車上,有一個人顯然不是去上班的。從他袋子的尺寸,你一眼就瞧得出來。一如你總是可以從那副沾沾自喜的落魄相,嗅出逃犯的氣味;他的嘴裡似乎含著祕密——好像馬上要吹出泡泡來。唉,算了吧,幹嘛要吞吞吐吐的呢?我在自己的老臥房裡醒來,一生絕大多數歲月,我都是在這棟屋子度過的。冰雪深埋屋宇周圍,凍結的足跡穿越後院,直達垃圾桶。暴風雪才剛造訪過此地,預料不久後另一場即將颳起。我比平常更加小心翼翼地整裝、綁鞋帶,放過嘴唇上方的鬍渣不刮,以便蓄鬍留鬚。拍拍口袋,確定原子筆和護照安然無恙,我下了樓,與母親那只老在打呃的咕咕鐘擦肩而過,然後前往威靈頓圓環(Wellington Circle)搭火車去。今早是一個凍得教人麻痺的霜雪天,好一個前往南美洲的良辰吉日。
對某些人來說,這班列車是通往蘇利文廣場(Sullivan Square)或是米爾克街(Milk Street),抑或終點站東方高地(Orient Heights);但對我而言,這班車將帶領我前往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兩個男人用外國語低聲交談著;有的人攜著午餐盒、小旅行袋與公事包;一位小姐拿著一只縐巴巴的百貨公司用袋,顯然是要去退還或是交換不要的商品(舊袋子把這趟尷尬之旅更襯托得栩栩如生)。嚴寒改變了車內多種族乘客的容顏,白人的臉頰好似灑滿了粉紅粉筆灰,中國人全無血色,黑人面色呈灰白或灰黃。曙光初露時是華氏十二度,等到九、十點左右卻降到了九度,且在持續下降中。行經秣市(Haymarket),車門一開,冷風便呼呼吹進車廂,兩位絮語不斷的外國人也噤了口,看上去是地中海人吧,迎面的冷風繃緊了他們的面部肌肉。乘客大多縮成一團,手肘貼緊了身體兩側,手擱在膝蓋上,半瞇著眼,努力保藏著自個兒的溫度。
他們在城裡有事待辦——工作、購物、上銀行,或是到百貨公司退物處辦理尷尬差事兒。有兩人膝蓋上擱著厚重的教科書,一個背向我的身影正讀著《社會學導論》(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一個男人嚴肅地掃瞄過《環球報》(Globe)的標題,還有一個人,正用拇指翻弄著公事包內的文件。一位女士告誡她的小女兒腳不要亂踢,身子坐正些。四站過後,車子原已坐得半滿——但現在,人全湧入了狂風大作的月台。他們會在傍晚時分返家,一整天都在高談闊論天氣的種種。然而,他們為此而全副武裝,辦公服之外還罩著愛斯基摩大衣,戴著五指手套、圓形手套、羊毛帽。決心懸在他們的臉龐而疲憊的表情,已漸露端倪。沒有半絲興奮的痕跡,一切都再普通平常不過。搭火車,早就是他們的例行公事。
沒人望向窗外,他們從前就瞧過港口、邦克山(Bunker Hill)與沿路的看板了。他們也不注視彼此,視線就僵在眼睛前數吋不動。可縱使他們對頭上的廣告視若未睹,後者仍對前者訴說著訊息。這些傢伙是當地人,他們舉足輕重,而廣告公司也知道他們旳銷售對象是誰。需要聯邦直接稅表格嗎?其下,一個身著厚呢水手上衣的年輕人正對著報紙露齒而笑,吞嚥口水。兌現您的支票,行遍麻省。一位面色灰黃如南非哈藤塔特族(Hottentot)的女士,緊緊抱著她的購物袋。請自動自發贊助波士頓的公立學校。對於那位頭戴俄式小帽、檢視公事包文件的無聊仁兄而言,倒也不賴。想抵押借款嗎?找我們就對了!沒有人往上瞧。修理屋頂與排水溝。利用閒暇時間取得大學學位。一家餐廳。一家廣播電台。一則宣導戒菸的告示。上述標語的宣傳對象不是我,它們管的是當地事,但今早我將遠離。當你遠離之際,廣告所蘊涵的許諾便不再有實質的意涵。金錢、學校、房屋、廣播:我將一切拋諸腦後。這段從威靈頓圓環到史泰特街(State Street)的短短路程上,廣告變成了一連串哀懇的呢喃,有如某種不知名語言的胡扯瞎談。我大可聳肩以對,因為我正坐著車遠離家園。除了酷寒及落雪反照出的刺眼亮光,其餘事對我的旅程一無影響。除了一件事之外,一切都不再重要:當列車緩緩駛進南站(South Station)時,我離巴塔哥尼亞又近了一英里。
一趟火車之旅的序幕
旅行是一幕消逝的場景,一場孤獨的旅程,沿著變形的地理線,進入全然的遺忘。
流浪變成何種模樣?
既然它逃開了我們所有人。
然而旅行書恰恰相反,孤獨者回歸日常生活,繪聲繪影地描述他與空間的這樁實驗物語。旅行書是最簡單明瞭的一種敘述,它是一項解釋,自個兒為出現和消失的理由自圓其說。它是一種律動,規律來自於字詞的堆積重複。印象的消褪是銳不可擋的,但少有完全不存於記憶者。然而,傳統上卻會濃縮旅行書寫,從中間起頭(一如許多小說),猛地就把讀者放在奇鄉異國,卻不先領他前往該處。一本書的開頭可能如下:「白蟻把我的吊床當點心吃掉了」;抑或,「從巴塔哥尼亞的山谷往下深入,盡是灰色奇岩,滿載著洪水所遺留的千古刻痕及裂縫。」乾脆從伸手可及的距離隨機取出三本書,查看一下開頭句好了:
一八九八年三月一日近正午時分,我首次發現,自己進入了非洲東岸蒙巴薩(Mombasa)那險象橫生的狹灣。(《察沃的食人魔》[The Man-Eaters of Tsavo],帕特森[J. H. Patterson]著)
「歡迎光臨!」路邊碩大的廣告牌如是說。此時,車子已完成了螺絲狀的登高之旅,從南印度平原的酷熱,一下子躍入近乎天賜的涼爽。(《保護下的烏迪》[Ooty Preserved],龐特-道恩斯[Mollie Panter-Downes]著)
從房間的陽台上,我可以一覽加納(Ghana)首都阿克拉(Accra)的全景。(《你屬於何家部落?》[Which Tribe Do You Belong To?],莫拉微亞[Alberto Moravia]著)
可是,我向來的疑問,在這幾本旅行書(大多數旅行書)裡卻避而不答:你是怎麼抵達那兒的?連動機都不提,歡迎的序幕就已然揭起。前去的過程其實往往與抵達一樣繽紛多彩。不過,由於好奇心本身已蘊涵著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又被視為一項奢侈品(可是,反正有什麼好急的呢?),我們已習慣生活就是一連串的到達與道別、成功與失敗,而中間種種是不值一顧的。帕爾納索斯山(Mount Parnassus,位於希臘中部,希臘神話中為祭祀太陽神阿波羅之地--譯註)的頂峰是眾所矚目的焦點,但較低的斜坡呢? 我們並非對離家的過程全無信心,但相關文字卻少得可憐。離別被形容成恐慌的一刻,在機場大廳驗票的瞬間,舷梯旁笨拙的親吻;然後一切寂靜無聲,直到,「從房間的陽台上,我可以一覽加納首都阿克拉的全景……」
旅行,其實是兩碼子事。打從醒來的那一瞬間,你就在往一個陌生的地方邁進,每一段路程(譬如和咕咕鐘擦肩而過,順著富爾頓[Fulton]進入費斯威[Fellsway]等等),都領你更近了目的地一步。《察沃的食人魔》一書的背景是本世紀初的肯亞,描寫獅子吞食印地安鐵路工人。但我敢打賭,一本更加細膩精彩的書原本大有可能誕生,內容則是從南安普頓(Southampton,位於美國紐約州東南部--譯註)到蒙巴薩的海上之旅。只不過,帕特森上校基於種種個人因素,並未著手撰寫。
旅遊文學已變成細微小道不足觀矣。典型的開場是,從飛機傾斜的機身,鬧劇似把鼻子緊貼著舷窗往下望。這種逗笑的開場,這種特意加強的效果,已太為人熟悉,連諧仿(parody)都幾近毫無可能。他們是怎麼說的?「下方,橫著熱帶草原、洪水沒頂的山谷、宛如百衲被的農田。當飛機穿過雲層時,我可瞧見蜿蜒攀往山丘的泥巴路,以及小得近似玩具的車輛。我們繞著機場飛,當飛機降低準備著地,我看見了雄壯威武的棕櫚樹、收成的農田、襤褸人家的屋頂、用簡陋柵欄綴在一起的方形田野、宛如螻蟻的人類、五彩繽紛的……」
我從不以為這種臆測有任何說服力可言。我則每當飛機降落時,一顆心早懸到了喉嚨口。我擔心——難道你們不會嗎?——下一秒鐘大夥兒即將墜機。我一生的片段在眼前迅速閃過,錯失與傷感的種種枝節小事,短促地浮現心頭。然後,某個聲音響起,告訴我請留在座位,直到飛機完全降落。等到飛機抵達停機坪,播音器會放出電影《月河》(Moon River)的交響組曲。我猜想,如果我有勇氣四處張望的話,也許可看到一個旅行文學作家在振筆直書:「下方,橫著熱帶草原……」
話說到這兒,到底旅行是怎生風貌?也許確實沒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搭飛機的經驗大多無事可說。值得一提的事件顯然跟災難脫不了關係,所以人們才會以否定句來定義「愉快的搭機經驗」:你沒碰上劫機,你沒遇到墜機,你沒嘔吐,你沒遲到,機上的食物不會讓你皺眉頭。基於以上種種,你心懷感激,感激使你鬆了一口氣,導致內心一片空白。這也滿說得通的,因為,搭機的乘客等於是時空旅人。他爬入內鋪地毯、散發強烈消毒味兒的通道,把繫好皮帶,準備返鄉或離家。時間變短了,或者該說時間扭曲變形了,使他從一個時間區離開,在另一個時間區出現。打從他踏入通道,把膝蓋緊靠在前座,僵直身子的那一刻起——打從他離去的那一刻起,他的心思就只專注於抵達。當然囉,前提是,如果他還有任何感覺的話。就算他凝睇窗外,所見除了如北極凍原般的雲層外,絕無他物,上方則是寬曠的空間。時間被閃耀地遮蒙住了:沒有任何景物值得一瞧。因此,許多人對搭飛機一事感到歉意滿懷。他們說:「其實我真的很想把那隻塑膠怪獸拋到腦後,改去搭三桅帆船。我要站在船尾甲板上,好讓海風吹拂我的頭髮。」
其實無需抱歉。搭飛機也許並非一般定義的旅行,但確實是項奇蹟。只要付得起機票,搭上正確的電扶梯(以波士頓的洛根機場[Logan Airport]為例好了),任何人都可以變出德拉千非(Drachenfels)的峭壁,或伊尼斯弗綠(Innisfree)的島湖(Lake Isle)——不過,有一點必須聲明清楚:搭電扶梯上行的短短一段路,也許比整趟航行加起來,更能豐富心靈且富有旅行的風味。其餘的,外國異地,也就是構成抵達的種種,只剩下那條連結飛機與惡臭機場的上下活動梯。如果搭機客把這類型的轉乘視為旅行,而寫入書中呈現大眾,讀者遇見的第一個外國人,不是搜身的海關人員,就是移民入境檢查處裡蓄有鬍鬚的惡魔。儘管,搭飛機已躍為世界的流行,我們仍必須哀嘆下列事實:飛機使我們對空間不再敏銳;我們遭受束縛,一如身著盔甲的戀侶。
顯而易見,我感興趣的是於晨光清醒之後的故事:從熟悉到有點陌生、到頗為新奇、到全然不識。重要的是旅程,而非抵達;是旅行,而非降落。我自覺上了旅行書籍的當,並懷疑自己抗拒的事物到底是什麼。我決定做個實驗:親身前往旅行書上提到的國家,隨著火車,從麻州的梅德福(Medford)向南奔到不能再遠的地方;在一般旅行書開始的地方,劃下本書的句點。
反正我沒別的事好做。我的寫作生涯漸受肯定,才剛寫完一部小說,兩年足不出戶了。我尋覓著別的寫作題材,卻發現非但沒有走上正途,反而在曲路上不停徘徊。我痛恨嚴寒的天氣,我需要陽光,而且我目前沒有工作——所以,還有什麼能阻住我的腳步?在研究地圖之後,發現從梅德福的家園,到阿根廷南部的巴塔哥尼亞大草原之間,似乎有條絡繹不絕的絲線。火車可直通到伊斯奎小鎮(Esquel,位於巴塔哥尼亞北側--譯註),其後便毫無鐵軌蹤跡。而若想前往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火車是不得其門而入,但在梅德福和伊斯奎之間,鐵路繁似星斗。
抱著流浪的情懷,我踏上第一班火車,一般人搭這班車是為了上班。他們下車——他們的火車之旅已然終結;我留在車廂,我的火車之旅,才剛開始。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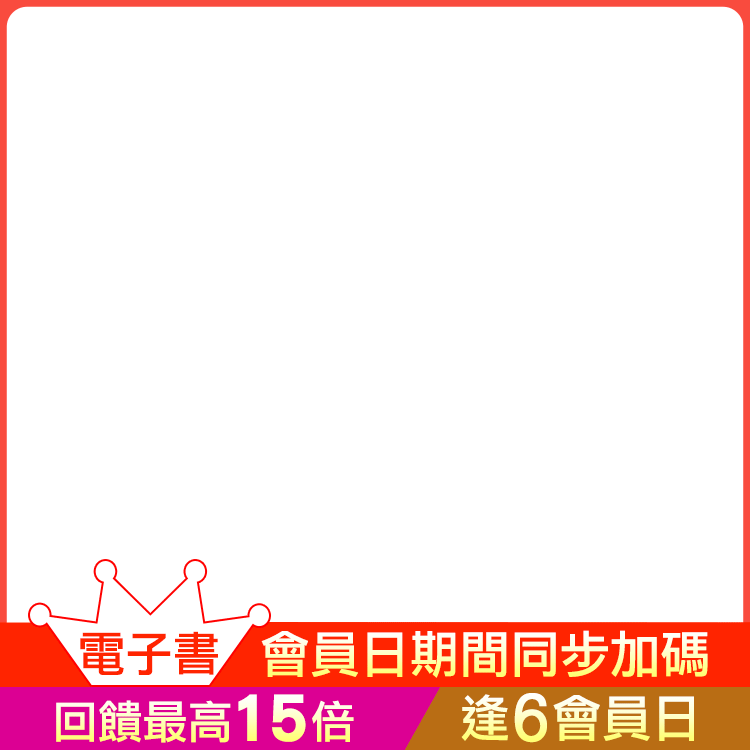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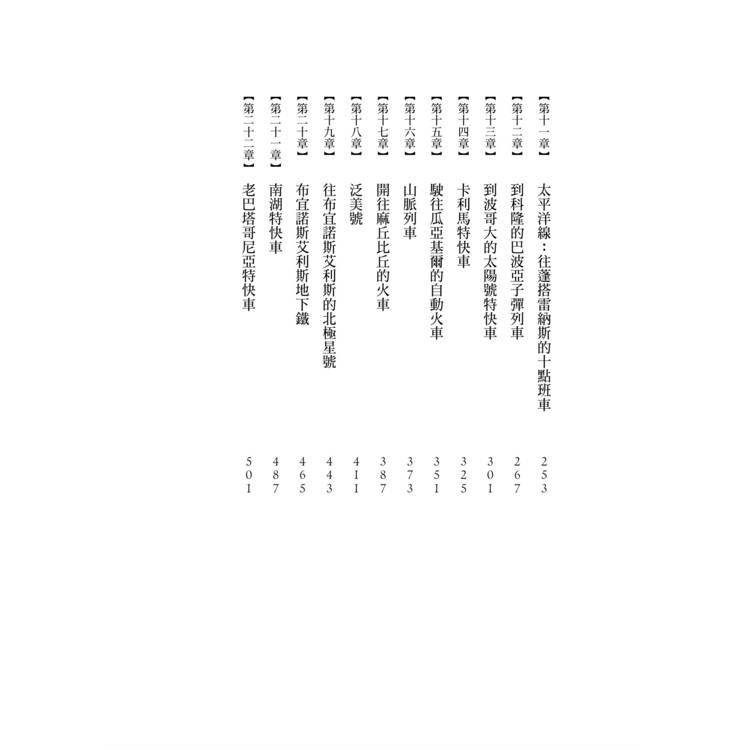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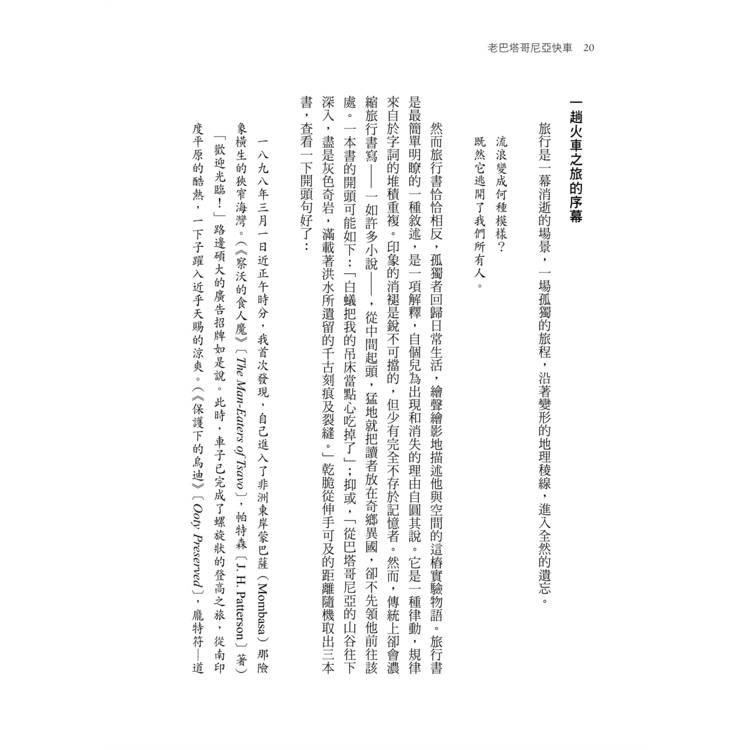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