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跑的路,已經跑過:民主英烈傳第二卷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本書《當跑的路,已經跑過》為《民主英烈傳》之第二卷,收入1990 年之後辭世的50 名民主英烈,以不同的世代排序,時間跨度長達90 年。
本書所選之人物,生前皆以不同形式挺身反抗中共極權暴政,幾乎都受到過中共政權不同形式之迫害。其中,曾被流放、拘押和判刑者占一半以上,有多位人物慘死在監獄中或被釋放後不久就因健康被嚴酷的牢獄之災摧毀而病逝。他們的生命歷程即是對中共極權體制之強烈控訴和批判。
本書所寫之人物,其生活區域涵蓋中國本土、香港、台灣及海外,亦包括外籍人士與圖博人、滿人、蒙古人等少數族裔。作者深切期盼,本書成為一座看不見的橋梁,將中國和海外的抗爭者及抗爭運動連接起來,促進不同環境下的抗爭者增加了解、交流、信任及彼此支持,並延續離世的抗爭者生前所積累的精神資源。
本書所選之人物,生前皆以不同形式挺身反抗中共極權暴政,幾乎都受到過中共政權不同形式之迫害。其中,曾被流放、拘押和判刑者占一半以上,有多位人物慘死在監獄中或被釋放後不久就因健康被嚴酷的牢獄之災摧毀而病逝。他們的生命歷程即是對中共極權體制之強烈控訴和批判。
本書所寫之人物,其生活區域涵蓋中國本土、香港、台灣及海外,亦包括外籍人士與圖博人、滿人、蒙古人等少數族裔。作者深切期盼,本書成為一座看不見的橋梁,將中國和海外的抗爭者及抗爭運動連接起來,促進不同環境下的抗爭者增加了解、交流、信任及彼此支持,並延續離世的抗爭者生前所積累的精神資源。
目錄
凡例與致謝
自序:丈夫九死千刀雪,一笑全無百莽煙
1900年代人
01|龔品梅(1901-2000): 一品寒梅雪中傲立,獨擋風霜春撒人間
02|劉景文(1909-1992):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1910年代人
03|湯戈旦(1911-1993):誰知肉市存真佛,應信污池有白蓮
04|欽本立(1918-1991):為新聞自由拚死一搏
05|趙紫陽(1919-2005):小朝廷何足道哉,大丈夫無所謂了
06|李志綏(1919-1995):只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1920年代人
07|劉賓雁(1925-2005): 人生最應該探求和堅持的是真相和真理
08|林牧(1927-2006):何日黎民能作主,也將白鐵鑄元兇
09|戴煌(1928-2016):即便被殺頭,也要說真話
10|許醫農(1929-2024): 我把自己當做火炬,至少照亮一個角落
1930年代人
11|司徒華(1931-2011): 我永遠與大家在風雨崎嶇的民主道路上前進
12|流沙河(1931-2019):文人,寫下去即是勝利
13|梅兆贊(1932-2021): 我的兄弟姐妹是那些為自由獻身的中國人
14|李.愛德華茲(1932-2024): 美國的保守主義是建立在反共基礎上的
15|班旦加措(1933-2018): 人對自由的珍愛,就如雪下暗藏的火苗
16|周素子(1933-2022):耐得霜寒若許,瘦影還如故
17|譚蟬雪(1934-2018):雪中之蟬,長鳴不已
18|林希翎(1935-2009): 我將身上的十字架背負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19|周淑莊(1936-2023):我要為死去的親人討回公道
20|方勵之(1936-2012):民主不是賜予的,是自己爭取來的
1940年代人
21|賀星寒(1941-1995): 我從此就站在了共產主義體系的外面
22|王在京(1943-2000):赴火蛾翎焚,當車螳臂掊
23|尹敏(1944-2021):做堅定的守靈人,做堅定的守望者!
24|嚴正學(1944-2024):余心之所善,九死猶未悔
25|黃春榮(1944-2024): 一個真男人不畏強權,只會為了正義發聲
26|羅宇(1944-2020):中國最大的禍害就是共產黨
27|曹思源(1946-2014):人間正道私有化,憲政春潮永不休
28|李贊民(1948-2018):胸中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陸沉?
29|楊小凱(1948-2004):我會再像獅子一樣咆哮回來
30|羅海星(1949-2010):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31|王策(1949-2021):以基督精神再造共和
32|紀斯尊(1949-2019):君子抱仁義,不懼天地傾
1950年代人
33|胡踐(1951-1995):一種有冤猶可報,不如銜石疊滄溟
34|吳學燦(1951-2015):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35|周倫佐(1952-2016):一支蠟燭就這樣點燃,直到熄滅
36|鄧麗君(1953-1995):我絕不向暴政低頭,絕不對壓力妥協
37|高玉蓮(1954-2016):壯志若鐵石,頑直未易摧
38|趙品潞(1956-2004):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
39|劉士賢(1956-2020):我是民主道路上的一顆鋪路石
1960年代人
40|孟浪(1961-2018):我們的血必須替他們洶湧
41|梅艷芳(1963-2003):我是民主運動的忠貞分子
42|華春輝(1963-2024):言論無罪,自由萬歲
43|李金鴻(1963-2020):墮入深淵的人,仍然可以是行進者!
44|郭洪偉(1964-2021):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
45|丁建強(1965-2020): 如果我的生命能換來中共倒台,我願意明天就死
46|鄭艾欣(1967-2012):清清不染淤泥水,我與荷花同日生
1970年代人
47|張六毛(1972-2015):摶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錐擊暴秦
48|毛黎惠(1978-2022): 我不會自殺,我要與黑社會組織鬥爭到底
1980年代人
49|梁凌杰(1984-2019): 對不仁不義的香港政府的最後一聲咆哮
1990年代人
50|才旺羅布(1996-2022):我是一棵焚而不毀的樹
附錄 《當代英雄》(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一卷)人物名單
《勇者無懼》(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二卷)人物名單
《美好的仗,已經打過》(民主英烈傳,第一卷)人物名單
《永不屈服》(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三卷)人物名單
自序:丈夫九死千刀雪,一笑全無百莽煙
1900年代人
01|龔品梅(1901-2000): 一品寒梅雪中傲立,獨擋風霜春撒人間
02|劉景文(1909-1992):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1910年代人
03|湯戈旦(1911-1993):誰知肉市存真佛,應信污池有白蓮
04|欽本立(1918-1991):為新聞自由拚死一搏
05|趙紫陽(1919-2005):小朝廷何足道哉,大丈夫無所謂了
06|李志綏(1919-1995):只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
1920年代人
07|劉賓雁(1925-2005): 人生最應該探求和堅持的是真相和真理
08|林牧(1927-2006):何日黎民能作主,也將白鐵鑄元兇
09|戴煌(1928-2016):即便被殺頭,也要說真話
10|許醫農(1929-2024): 我把自己當做火炬,至少照亮一個角落
1930年代人
11|司徒華(1931-2011): 我永遠與大家在風雨崎嶇的民主道路上前進
12|流沙河(1931-2019):文人,寫下去即是勝利
13|梅兆贊(1932-2021): 我的兄弟姐妹是那些為自由獻身的中國人
14|李.愛德華茲(1932-2024): 美國的保守主義是建立在反共基礎上的
15|班旦加措(1933-2018): 人對自由的珍愛,就如雪下暗藏的火苗
16|周素子(1933-2022):耐得霜寒若許,瘦影還如故
17|譚蟬雪(1934-2018):雪中之蟬,長鳴不已
18|林希翎(1935-2009): 我將身上的十字架背負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19|周淑莊(1936-2023):我要為死去的親人討回公道
20|方勵之(1936-2012):民主不是賜予的,是自己爭取來的
1940年代人
21|賀星寒(1941-1995): 我從此就站在了共產主義體系的外面
22|王在京(1943-2000):赴火蛾翎焚,當車螳臂掊
23|尹敏(1944-2021):做堅定的守靈人,做堅定的守望者!
24|嚴正學(1944-2024):余心之所善,九死猶未悔
25|黃春榮(1944-2024): 一個真男人不畏強權,只會為了正義發聲
26|羅宇(1944-2020):中國最大的禍害就是共產黨
27|曹思源(1946-2014):人間正道私有化,憲政春潮永不休
28|李贊民(1948-2018):胸中有誓深於海,肯使神州竟陸沉?
29|楊小凱(1948-2004):我會再像獅子一樣咆哮回來
30|羅海星(1949-2010):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31|王策(1949-2021):以基督精神再造共和
32|紀斯尊(1949-2019):君子抱仁義,不懼天地傾
1950年代人
33|胡踐(1951-1995):一種有冤猶可報,不如銜石疊滄溟
34|吳學燦(1951-2015):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35|周倫佐(1952-2016):一支蠟燭就這樣點燃,直到熄滅
36|鄧麗君(1953-1995):我絕不向暴政低頭,絕不對壓力妥協
37|高玉蓮(1954-2016):壯志若鐵石,頑直未易摧
38|趙品潞(1956-2004):位卑未敢忘憂國,事定猶須待闔棺
39|劉士賢(1956-2020):我是民主道路上的一顆鋪路石
1960年代人
40|孟浪(1961-2018):我們的血必須替他們洶湧
41|梅艷芳(1963-2003):我是民主運動的忠貞分子
42|華春輝(1963-2024):言論無罪,自由萬歲
43|李金鴻(1963-2020):墮入深淵的人,仍然可以是行進者!
44|郭洪偉(1964-2021):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
45|丁建強(1965-2020): 如果我的生命能換來中共倒台,我願意明天就死
46|鄭艾欣(1967-2012):清清不染淤泥水,我與荷花同日生
1970年代人
47|張六毛(1972-2015):摶沙有願興亡楚,博浪無錐擊暴秦
48|毛黎惠(1978-2022): 我不會自殺,我要與黑社會組織鬥爭到底
1980年代人
49|梁凌杰(1984-2019): 對不仁不義的香港政府的最後一聲咆哮
1990年代人
50|才旺羅布(1996-2022):我是一棵焚而不毀的樹
附錄 《當代英雄》(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一卷)人物名單
《勇者無懼》(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二卷)人物名單
《美好的仗,已經打過》(民主英烈傳,第一卷)人物名單
《永不屈服》(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三卷)人物名單
序/導讀
自序/
丈夫九死千刀雪,一笑全無百莽煙
一生歷盡苦難的詩人聶甘弩晚年曾寫下這樣的詩句:「丈夫九死千刀雪,一笑全無百莽煙。」這句詩正可概括本卷《民主英烈傳》中所寫到的五十位人物。
本書中所記述的五十位在1990年之後辭世的民主英烈,以出生日期而論,從1900年代至1990年代,橫亙了九十年的漫長光陰。他們的生命歷程各不相同,卻具有兩個共同點:其一,他們都是民主、共和、自由、憲政價值的求索者、捍衛者,同時也必然是中共極權主義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反對者(這種反對,發生在他們各自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有的人覺悟較早,有的人到了晚年才大徹大悟)。其二,因為他們的反對,他們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招致了來自中共政權的種種迫害與摧殘,乃至於家破人亡,但他們如屈原一樣「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反叛以及對反叛的反叛
在本書所記述的人物中,在1930年代末之前出生的,也就是在民國時代度過其中年、青年或少年時代人物,絕大多數都有過左傾、親共、參加共產黨乃至在共產黨內擔任要職的經歷。他們不惜背叛原有的階層和家族,青春熱血地投入到中共革命之中。比如:出生地主家庭卻帶頭供了自家的家產、後來擔任總理及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在中共文宣部門任職的欽本立、劉賓雁、林牧、戴煌,中共在香港布設的草蛇灰線般的地下黨組織成員的司徒華,從海外趕回「新中國」服務並成為毛澤東御醫的李志綏,出身「敵對階級」的流沙河、林希翎,作為中學生的更年少的譚蟬雪、方勵之,甚至作為「天然左」的美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梅兆贊和李.愛德華茲,無不如此。
20世紀中葉的中國,左禍何以掀起滔天巨浪?這一方面是中共的宣傳和統戰工作做得十分成功。中共更多地宣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而非共產主義、馬列主義,輕而易舉地俘獲了絕大多數年輕人的心靈。另一方面則表明,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崩解,中國變成一處廣袤空曠的「跑馬場」,在英美清教徒秩序和民主、共和、自由、憲政價值尚未進入中國之際,包括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內的各種左派思潮卻更迅速地搶占了思想觀念之高地,將中國帶往萬劫不復之深淵。
近年來,關於一群晚年覺悟的前輩,有一種頗為流行的「兩頭真」的說法,即早年投共是出於真誠的理想主義,晚年反共也是出於真誠的理想主義。然而,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因為真理只有一個,只能有「一頭真」,不可能有「兩頭真」,如果「兩頭真」,就不必「以晚年之我反對早年之我」了。據傳愛因斯坦說過一句名言:「一個人青年時代不是左派,則沒有良心;中年之後還是左派,則沒有理性。」這句話也是不成立的(愛因斯坦本人的思想就左傾)。那些青年時代親共、投共的人物,往好了說是「純真」,但實事求是地說乃是「愚蠢」—「愚蠢」可以勉強予以諒解,但不值得讚美。更何況,「愚蠢」的結果往往是參與中共的作惡—趙紫陽參與過血腥的土改,其他那些左派學生賣力地替中共散播謊言。不能美化他們早年的錯誤選擇,也正因為他們身上有早年的原罪,他們晚年的反叛才尤為可貴。
反之,那些青年時代就不是左派的人,既有良心,又有理性。在那個赤禍滔天、人人唯恐不左的時代,仍有人以火眼金睛看透中共的本質,持守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咬定青山、巋然不動。比如,本書中寫到的天主教的主教龔品梅、基督教獨立教會的師母劉景文(王明道的妻子),都是從基督信仰和聖經真理中找到戳破共產黨謊言和抵禦共產黨暴力的武器。藏傳佛教的僧侶班旦加措,則是從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遺囑中認識到一個不言自明的真相:共產黨就是其預言中邪惡的「大紅龍」。他們從未被共產黨所蠱惑,他們的先見之明和擇善固執更值得後人效仿和標舉。
本書的人物中,還有另一群反叛者,乃是「對反叛的反叛」。他們出身於中共政權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家庭,卻義無反顧地成為其反叛者。比如,中共開國大將、權傾一時的羅瑞卿的兒子羅宇,中共幹部家庭出身的楊小凱、胡踐、華春輝、丁建強,以及中共派駐香港的左派文人領袖羅孚之子羅海星,如果他們承襲父輩之蔭蔽,完全可以過上錦衣玉食的好日子,但他們「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飢渴」,毅然與可讓他們點石成金的體制決裂,寧願孤獨地流亡,寧願淪為階下囚,寧願被羞辱與踐踏,寧願付出生命代價。他們的背叛可歌可泣,正所謂「烈士之所以異於恒人,以其仗節以配誼也」。
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
慕義不分先後,反共也不分先後。本書所記述的人物,在不同的歷史時刻選擇站在中共的對立面,亦即站在正義與自由一邊。
最早的反對,是在1950年代的鎮反運動和宗教迫害中,龔品梅身陷「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案」坐牢三十一年、劉景文身陷「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坐牢二十年,他們寧願將牢底坐穿也要持守純正信仰,但主流社會和知識界對他們的遭遇幾乎視而不見。
隨後,在反右運動中,大批自以為是「第二種忠誠」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或準右派)、淪為賤民,包括欽本立、劉賓雁、戴煌、許醫農、流沙河、周素子、譚蟬雪、林希翎、方勵之、賀星寒等人。苦難之始,亦是反思之始。
在文革中覺醒的,是後來成為世界頂級經濟學家的楊小凱以及毛的御醫李志綏。楊小凱在牢獄中目睹了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自由精靈,李志綏則在毛的深宮中看到了「打天下的光棍」的幽暗真相。
在西單民主牆時代步入反對陣營行列的,則有湯戈旦、李贊民、劉士賢等人。而鄧小平對民主牆的始亂終棄,表明鄧與毛乃一丘之貉。
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展開帶有異議色彩的文學藝術創作和思想探索的,包括嚴正學、周倫佐、孟浪等人。他們將各自的工作延續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給後世留下豐厚的文學、藝術、思想遺產。
將更多國民推向中共之敵對陣營的,則是六四槍聲。六四是當代中國史的轉折點,也是很多人生命的轉折點,幾乎所有抗爭者都與六四存有某種特別的關聯—因為反對開槍殺人,趙紫陽從中共總書記淪為「國家的囚徒」;曾經的「毛粉」梅兆贊在天安門廣場被軍人打掉牙齒、打斷手臂,從此成為西方觀察家中對中共暴政最嚴厲的批判者;原本是普通家庭主婦的周淑莊和尹敏,因痛失愛兒,加入「風雨雞鳴」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影響一代青年學子的方勵之,先遁入美國使館,再踏上終身的流亡路;原本是香港貴公子的羅海星挺身而出,參與「黃雀行動」,為朋友捨命⋯⋯為六四坐牢的良心犯還包括:王在京、曹思源、胡踐、吳學燦、李金鴻等人;為六四而流亡異國他鄉的還有趙品潞、丁建強等人。他們的人生被定格在那個血腥的夜晚,正如詩人孟浪在一首記念六四的詩歌中所說:「他們的血,停在那裡/我們的血,驟然流著。//哦,是他們的血靜靜地流在我們身上/而我們的血必須替他們洶湧。//他們的聲音,消失在那裡/我們的聲音,繼續高昂地喊出。//哦,那是他們的聲音發自我們的喉嚨/我們的聲音,是他們的聲音的嘹亮回聲。//在這裡—/沒有我們,我們只是他們!//在這裡—/沒有他們,他們就是我們!」
在1990年代以來的維權運動中,湧現出更多草根維權人士,如黃春榮、紀斯尊、華春輝、郭洪偉、張六毛、毛黎惠、梁凌杰等人。他們或死於看守所和監獄,或死於酷刑和折磨,或死於困苦和疾病,或死於孤獨和絕望,他們較少被外界關注和報導,公共領域關於他們的資料相當有限,有些人甚至找不到一張清晰的照片。在中南海獨夫民賊眼中,他們是螻蟻,是韭菜,是人礦,是奴隸。但實際上,他們是頂橡樹的牛犢,是填海的精衛,是移山的愚公,是逐日的夸父,是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是盜火的普羅米修斯,是被中共竊取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中「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無論是「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還是「民主英烈傳」系列,我們都將用更多篇幅來記載這些籍籍無名的英雄和烈士。
他們是微弱的少數,卻是可以改變歷史的關鍵少數
一如既往,本卷特別關注那些看似微弱的卻也是能夠改變這個國家未來的「少數派」,正如聖經中所說,一點點酵母能使整個麵團發酵。
以性別而論,本卷中的女性包括:劉景文、許醫農、周素子、譚蟬雪、林希翎、周淑莊、尹敏、鄧麗君、梅艷芳、鄭艾欣、毛黎惠等十一位。魯迅的感慨,亦可用在她們身上—她們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正是「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
以族裔而論,少數族裔的人物有:湯戈旦(滿族)、欽本立(蒙古族)、班旦加措(藏族)、高玉蓮(蒙古族)、才旺羅布(藏族)等人。他們當中,有人為普世的民主自由吶喊,有人為本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抗爭,最終亦是殊途同歸。
以宗教信仰而論,廣義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為數眾多:龔品梅、劉景文、許醫農、司徒華、李.愛德華茲、林希翎、嚴正學、曹思源、楊小凱、王策、紀斯尊、趙品潞、劉士賢、李金鴻、丁建強等人。其中,楊小凱和王策對基督教憲政主義研究頗深,其著述對未來中國的民主化和憲政轉型極具標竿意義。本卷還收入兩位藏傳佛教信徒—作為僧侶的班旦加措和作為世俗信徒的才旺羅布—的故事,從他們的人生經歷可以透視,藏傳佛教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抵禦能力遠比漢傳佛教強。本卷中也記載了作為法輪功信徒的鄭艾欣的故事,儘管作者本人對作為龐大的新興宗教體系的法輪功的很多做法持懷疑和批評態度,但作者肯定和表彰那些甘願為其信仰和信念受苦、獻身的普通法輪功修煉者。
以職業而論,本書特別記述作為藝人的鄧麗君、梅艷芳、才旺羅布的故事。他們身處如同染缸的演藝界,卻「修身絜行,言必由繩墨」,跟今天那些爭先恐後地跪舔當權者的無良藝人相比,宛如雲泥之別。
以國籍而論,本書收入梅兆贊與李.愛德華茲兩位美國人。中共政權以無孔不入的統戰術縱橫國際社會,將若干親共、媚共的西方政商文化名流冊封為所謂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其實,他們只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真正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應當是梅兆贊和李.愛德華茲這樣的人:前者以筆為投槍,揭露出中共蹂躪中國人民的真相;後者創立「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終身以反共為志業。
反共不是職業,而是志業。反共不是爭名奪利的舞台,而是「一簑煙雨任平生」的義路。反共不是「皇帝輪流做,今日到我家」,而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看今日中共政權之橫征暴斂、無法無天,看今日反共陣營之種種怪現狀,更覺發掘民主英烈之精神遺產殊為重要與必要。比如,本書中所記述之王在京,是一位以裁縫剪刀謀生的殘障人士,是青島第一批腰纏萬貫的商人,卻衝冠一怒為六四,入獄多年,出獄後貧病交加、潦倒而逝。本書中所記述之趙品潞,是曾被學生領袖輕視和排斥的工自聯領袖,流亡美國後,不取嗟來之食,幹搬家和裝修的重體力活,自食其力且慷慨助人。「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他們比檯面上那些長袖善舞、誇誇其談者更讓人尊重和懷念。
我們弘揚少數派的可貴,也期待少數能發酵成多數,總有一日,民主、共和、自由、憲政將「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丈夫九死千刀雪,一笑全無百莽煙
一生歷盡苦難的詩人聶甘弩晚年曾寫下這樣的詩句:「丈夫九死千刀雪,一笑全無百莽煙。」這句詩正可概括本卷《民主英烈傳》中所寫到的五十位人物。
本書中所記述的五十位在1990年之後辭世的民主英烈,以出生日期而論,從1900年代至1990年代,橫亙了九十年的漫長光陰。他們的生命歷程各不相同,卻具有兩個共同點:其一,他們都是民主、共和、自由、憲政價值的求索者、捍衛者,同時也必然是中共極權主義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反對者(這種反對,發生在他們各自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有的人覺悟較早,有的人到了晚年才大徹大悟)。其二,因為他們的反對,他們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招致了來自中共政權的種種迫害與摧殘,乃至於家破人亡,但他們如屈原一樣「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反叛以及對反叛的反叛
在本書所記述的人物中,在1930年代末之前出生的,也就是在民國時代度過其中年、青年或少年時代人物,絕大多數都有過左傾、親共、參加共產黨乃至在共產黨內擔任要職的經歷。他們不惜背叛原有的階層和家族,青春熱血地投入到中共革命之中。比如:出生地主家庭卻帶頭供了自家的家產、後來擔任總理及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在中共文宣部門任職的欽本立、劉賓雁、林牧、戴煌,中共在香港布設的草蛇灰線般的地下黨組織成員的司徒華,從海外趕回「新中國」服務並成為毛澤東御醫的李志綏,出身「敵對階級」的流沙河、林希翎,作為中學生的更年少的譚蟬雪、方勵之,甚至作為「天然左」的美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梅兆贊和李.愛德華茲,無不如此。
20世紀中葉的中國,左禍何以掀起滔天巨浪?這一方面是中共的宣傳和統戰工作做得十分成功。中共更多地宣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而非共產主義、馬列主義,輕而易舉地俘獲了絕大多數年輕人的心靈。另一方面則表明,近代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崩解,中國變成一處廣袤空曠的「跑馬場」,在英美清教徒秩序和民主、共和、自由、憲政價值尚未進入中國之際,包括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內的各種左派思潮卻更迅速地搶占了思想觀念之高地,將中國帶往萬劫不復之深淵。
近年來,關於一群晚年覺悟的前輩,有一種頗為流行的「兩頭真」的說法,即早年投共是出於真誠的理想主義,晚年反共也是出於真誠的理想主義。然而,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因為真理只有一個,只能有「一頭真」,不可能有「兩頭真」,如果「兩頭真」,就不必「以晚年之我反對早年之我」了。據傳愛因斯坦說過一句名言:「一個人青年時代不是左派,則沒有良心;中年之後還是左派,則沒有理性。」這句話也是不成立的(愛因斯坦本人的思想就左傾)。那些青年時代親共、投共的人物,往好了說是「純真」,但實事求是地說乃是「愚蠢」—「愚蠢」可以勉強予以諒解,但不值得讚美。更何況,「愚蠢」的結果往往是參與中共的作惡—趙紫陽參與過血腥的土改,其他那些左派學生賣力地替中共散播謊言。不能美化他們早年的錯誤選擇,也正因為他們身上有早年的原罪,他們晚年的反叛才尤為可貴。
反之,那些青年時代就不是左派的人,既有良心,又有理性。在那個赤禍滔天、人人唯恐不左的時代,仍有人以火眼金睛看透中共的本質,持守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咬定青山、巋然不動。比如,本書中寫到的天主教的主教龔品梅、基督教獨立教會的師母劉景文(王明道的妻子),都是從基督信仰和聖經真理中找到戳破共產黨謊言和抵禦共產黨暴力的武器。藏傳佛教的僧侶班旦加措,則是從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遺囑中認識到一個不言自明的真相:共產黨就是其預言中邪惡的「大紅龍」。他們從未被共產黨所蠱惑,他們的先見之明和擇善固執更值得後人效仿和標舉。
本書的人物中,還有另一群反叛者,乃是「對反叛的反叛」。他們出身於中共政權的既得利益集團和家庭,卻義無反顧地成為其反叛者。比如,中共開國大將、權傾一時的羅瑞卿的兒子羅宇,中共幹部家庭出身的楊小凱、胡踐、華春輝、丁建強,以及中共派駐香港的左派文人領袖羅孚之子羅海星,如果他們承襲父輩之蔭蔽,完全可以過上錦衣玉食的好日子,但他們「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飢渴」,毅然與可讓他們點石成金的體制決裂,寧願孤獨地流亡,寧願淪為階下囚,寧願被羞辱與踐踏,寧願付出生命代價。他們的背叛可歌可泣,正所謂「烈士之所以異於恒人,以其仗節以配誼也」。
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
慕義不分先後,反共也不分先後。本書所記述的人物,在不同的歷史時刻選擇站在中共的對立面,亦即站在正義與自由一邊。
最早的反對,是在1950年代的鎮反運動和宗教迫害中,龔品梅身陷「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案」坐牢三十一年、劉景文身陷「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坐牢二十年,他們寧願將牢底坐穿也要持守純正信仰,但主流社會和知識界對他們的遭遇幾乎視而不見。
隨後,在反右運動中,大批自以為是「第二種忠誠」的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或準右派)、淪為賤民,包括欽本立、劉賓雁、戴煌、許醫農、流沙河、周素子、譚蟬雪、林希翎、方勵之、賀星寒等人。苦難之始,亦是反思之始。
在文革中覺醒的,是後來成為世界頂級經濟學家的楊小凱以及毛的御醫李志綏。楊小凱在牢獄中目睹了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自由精靈,李志綏則在毛的深宮中看到了「打天下的光棍」的幽暗真相。
在西單民主牆時代步入反對陣營行列的,則有湯戈旦、李贊民、劉士賢等人。而鄧小平對民主牆的始亂終棄,表明鄧與毛乃一丘之貉。
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展開帶有異議色彩的文學藝術創作和思想探索的,包括嚴正學、周倫佐、孟浪等人。他們將各自的工作延續到生命的最後時刻,給後世留下豐厚的文學、藝術、思想遺產。
將更多國民推向中共之敵對陣營的,則是六四槍聲。六四是當代中國史的轉折點,也是很多人生命的轉折點,幾乎所有抗爭者都與六四存有某種特別的關聯—因為反對開槍殺人,趙紫陽從中共總書記淪為「國家的囚徒」;曾經的「毛粉」梅兆贊在天安門廣場被軍人打掉牙齒、打斷手臂,從此成為西方觀察家中對中共暴政最嚴厲的批判者;原本是普通家庭主婦的周淑莊和尹敏,因痛失愛兒,加入「風雨雞鳴」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影響一代青年學子的方勵之,先遁入美國使館,再踏上終身的流亡路;原本是香港貴公子的羅海星挺身而出,參與「黃雀行動」,為朋友捨命⋯⋯為六四坐牢的良心犯還包括:王在京、曹思源、胡踐、吳學燦、李金鴻等人;為六四而流亡異國他鄉的還有趙品潞、丁建強等人。他們的人生被定格在那個血腥的夜晚,正如詩人孟浪在一首記念六四的詩歌中所說:「他們的血,停在那裡/我們的血,驟然流著。//哦,是他們的血靜靜地流在我們身上/而我們的血必須替他們洶湧。//他們的聲音,消失在那裡/我們的聲音,繼續高昂地喊出。//哦,那是他們的聲音發自我們的喉嚨/我們的聲音,是他們的聲音的嘹亮回聲。//在這裡—/沒有我們,我們只是他們!//在這裡—/沒有他們,他們就是我們!」
在1990年代以來的維權運動中,湧現出更多草根維權人士,如黃春榮、紀斯尊、華春輝、郭洪偉、張六毛、毛黎惠、梁凌杰等人。他們或死於看守所和監獄,或死於酷刑和折磨,或死於困苦和疾病,或死於孤獨和絕望,他們較少被外界關注和報導,公共領域關於他們的資料相當有限,有些人甚至找不到一張清晰的照片。在中南海獨夫民賊眼中,他們是螻蟻,是韭菜,是人礦,是奴隸。但實際上,他們是頂橡樹的牛犢,是填海的精衛,是移山的愚公,是逐日的夸父,是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是盜火的普羅米修斯,是被中共竊取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中「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無論是「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系列,還是「民主英烈傳」系列,我們都將用更多篇幅來記載這些籍籍無名的英雄和烈士。
他們是微弱的少數,卻是可以改變歷史的關鍵少數
一如既往,本卷特別關注那些看似微弱的卻也是能夠改變這個國家未來的「少數派」,正如聖經中所說,一點點酵母能使整個麵團發酵。
以性別而論,本卷中的女性包括:劉景文、許醫農、周素子、譚蟬雪、林希翎、周淑莊、尹敏、鄧麗君、梅艷芳、鄭艾欣、毛黎惠等十一位。魯迅的感慨,亦可用在她們身上—她們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正是「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祕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
以族裔而論,少數族裔的人物有:湯戈旦(滿族)、欽本立(蒙古族)、班旦加措(藏族)、高玉蓮(蒙古族)、才旺羅布(藏族)等人。他們當中,有人為普世的民主自由吶喊,有人為本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抗爭,最終亦是殊途同歸。
以宗教信仰而論,廣義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為數眾多:龔品梅、劉景文、許醫農、司徒華、李.愛德華茲、林希翎、嚴正學、曹思源、楊小凱、王策、紀斯尊、趙品潞、劉士賢、李金鴻、丁建強等人。其中,楊小凱和王策對基督教憲政主義研究頗深,其著述對未來中國的民主化和憲政轉型極具標竿意義。本卷還收入兩位藏傳佛教信徒—作為僧侶的班旦加措和作為世俗信徒的才旺羅布—的故事,從他們的人生經歷可以透視,藏傳佛教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抵禦能力遠比漢傳佛教強。本卷中也記載了作為法輪功信徒的鄭艾欣的故事,儘管作者本人對作為龐大的新興宗教體系的法輪功的很多做法持懷疑和批評態度,但作者肯定和表彰那些甘願為其信仰和信念受苦、獻身的普通法輪功修煉者。
以職業而論,本書特別記述作為藝人的鄧麗君、梅艷芳、才旺羅布的故事。他們身處如同染缸的演藝界,卻「修身絜行,言必由繩墨」,跟今天那些爭先恐後地跪舔當權者的無良藝人相比,宛如雲泥之別。
以國籍而論,本書收入梅兆贊與李.愛德華茲兩位美國人。中共政權以無孔不入的統戰術縱橫國際社會,將若干親共、媚共的西方政商文化名流冊封為所謂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其實,他們只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真正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應當是梅兆贊和李.愛德華茲這樣的人:前者以筆為投槍,揭露出中共蹂躪中國人民的真相;後者創立「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終身以反共為志業。
反共不是職業,而是志業。反共不是爭名奪利的舞台,而是「一簑煙雨任平生」的義路。反共不是「皇帝輪流做,今日到我家」,而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看今日中共政權之橫征暴斂、無法無天,看今日反共陣營之種種怪現狀,更覺發掘民主英烈之精神遺產殊為重要與必要。比如,本書中所記述之王在京,是一位以裁縫剪刀謀生的殘障人士,是青島第一批腰纏萬貫的商人,卻衝冠一怒為六四,入獄多年,出獄後貧病交加、潦倒而逝。本書中所記述之趙品潞,是曾被學生領袖輕視和排斥的工自聯領袖,流亡美國後,不取嗟來之食,幹搬家和裝修的重體力活,自食其力且慷慨助人。「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他們比檯面上那些長袖善舞、誇誇其談者更讓人尊重和懷念。
我們弘揚少數派的可貴,也期待少數能發酵成多數,總有一日,民主、共和、自由、憲政將「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
試閱
鄧麗君:我絕不向暴政低頭,絕不對壓力妥協
鄧麗君:出生於台灣雲林縣褒忠鄉田洋村。父親鄧樞是河北大名縣大街鎮鄧台村人,是因國共戰爭而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國軍軍官,母親趙素桂是山東東平縣人。
早在小學時,鄧麗君就已展現出歌唱天賦,並經常登台表演。1964年,年僅十一歲的鄧麗君參加中華廣播電台舉辦的黃梅調歌唱比賽,以一曲〈訪英台〉奪得冠軍;翌年以〈採紅菱〉在金馬獎唱片公司舉辦的歌唱比賽奪冠。其後,鄧麗君利用課餘時間參加正聲廣播公司舉辦的歌唱訓練班,學習歌唱技巧,以第一名成績結業。
1967年,鄧麗君加盟宇宙唱片,發行個人第一張專輯《鄧麗君之歌第一集.鳳陽花鼓》。1968年,於台北中山堂參加賑濟菲律賓震災的演出,捐款新台幣一萬一千元。1969年,中國電視公司啟播,鄧麗君獲邀主持晚間黃金時間播出的節目《每日一星》,並為中視首部電視連續劇《晶晶》主唱同名主題曲,成為她演唱的第一首影視主題歌曲,令她家傳戶曉。同年,參演首部電影—由謝君儀執導的《謝謝總經理》,飾演能歌善舞的女大學生,片中她唱了十首曲風青春活潑的歌曲,正式成為「歌、影、視」三棲的歌手。
1960年代末,鄧麗君開始赴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地巡迴演出,並頻繁參與慈善。1971年,為籌設香港保良中學、救濟香港水災義演;7月,在越南海南醫院看望孤寡老人;6月,參加新加坡「歌樂飄飄慈善晚會」,為殘障兒童救濟基金募款;1973年,於新加坡國家劇場出席遠東十大巨星慈善晚會。
1974年,鄧麗君在母親陪同下,前往日本發展。同年7月1日,她的日語單曲〈空港〉在一個月內以七十萬餘張總銷量進入全日本流行榜前十五名,因此榮獲日本唱片大獎新人獎。她在東京、川崎等地舉辦個人演唱會,大受歡迎。
1979年,鄧麗君又赴美國發展,先到舊金山落腳,然後到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進修英文,之後轉學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日文、生物及數學。期間完成了〈甜蜜蜜〉和〈小城故事〉的錄製,並在舊金山、洛杉磯和溫哥華舉行演唱會。
1980年10月4日,鄧麗君返回台灣舉行演唱會,捐所得新台幣一百五十萬零六百元予「自強救國基金」。在演唱會中,主持人田文仲向鄧麗君求證關於中國邀約她前往演唱之事,她表示曾在報紙上看見相關訊息但無人前來接洽,並手握拳頭、溫柔而堅定地說:「如果,我去大陸演唱的話,那麼,當我在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們三民主義在大陸實行的那一天。」話畢,台下響起如雷貫耳的掌聲,主持人也讚嘆鼓掌。
1981年1月,鄧麗君被行政院新聞局授予「愛國藝人」獎牌。8月,鄧麗君花了一個多月,跑遍台灣各地軍營勞軍演唱,深受國軍將士追捧,被稱作「永遠的軍中情人」。她說:「我生長在一個軍人家庭,我老爸曾參加過台兒莊、營口等戰役,所以,我從小看到軍人就有一份說不出的親切感。在面對國軍弟兄們表演時,陌生感就會一掃而空,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像美國的鮑勃.霍伯一樣,年年風塵僕僕的為自己國家的阿兵哥盡心盡力。」
在勞軍演出期間,鄧麗君在清晨5點起床,與金門守軍弟兄一起晨跑,包括幾程很難跑的坡度。她沒有喊累,汗水從她沒有化妝的臉上不斷淌下,她只是帥氣的用手背抹去,就像任何一個阿兵哥會做的舉動一樣。據部隊指揮官說,「鄧麗君效應」延續了好長一段時間,往後晨跑再沒有人敢摸魚、脫隊,部隊長往往會抬出鄧麗君來激勵大家,她的行動勞軍果然達到效果,不但提升了士氣,而且加強了心防,這不是唱唱跳跳、瘋狂一宵的勞軍活動所能比擬。
在鄧麗君成千上萬歌迷當中,有一位身分很特殊的人物,就是在1981年11月26日下午,駕著米格機投誠來歸的反共義士吳榮根。當記者紛紛問及他今後個人的心願時,誰也料不到,他竟然誠懇而靦腆說:「非常想見鄧麗君一面。」
透過新聞局安排,鄧麗君應邀在台中清泉崗和吳榮根見面,吳榮根初見鄧麗君,紅著臉,大半天說不出話來,鄧麗君不斷以輕言細語引導他。吳榮根談到她的歌被禁聽、禁錄,大陸人民仍然想盡辦法偷偷的聽。她感慨地表示,在自由地區生活的人,能隨意選擇愛聽的歌曲,在大陸卻不能,說著、聽著,忍不住哭了,不斷以搭在右肩上的圍巾拭淚。她送給吳榮根兩張唱片—《別把眉兒皺》和《原鄉情濃》,讓身在台灣的自由人能夠自在的聽個夠。
鄧麗君平復情緒之後,應基地飛行軍官要求,清唱了《何日君再來》和《小城故事》,吳榮根在旁靜靜的聽著她清唱,這比他在中國的部隊裡偷偷聽那種拷貝了又拷貝的錄音帶要清晰太多太多,好聽得不能再好聽。他覺得自己實在幸福極了,幸福到說不出適當的話來表達。鄧麗君落落大方的邀吳榮根一起唱《小城故事》,空軍官兵們熱切的鼓掌,打拍子應和。直到下午3點,鄧麗君才離開空軍基地,吳榮根送到基地門口,握手、目送她離去,內心的感動和興奮無法形容。
不久之後,海峽對岸又有孫天勤、李天慧等人投奔自由,同樣表明非常想見鄧麗君。鄧麗君在十五週年演唱會上與他們相見,並親切問好。那晚的表演,徹底滿足了反共義士們此生最想聽她唱歌的心願。
多年後,孫天勤在台北病逝。在追悼會上,其遺孀、音樂家李天慧特別提及,先生生前最愛聽的就是鄧麗君的歌。追悼會上最後放映孫天勤的追思影片,配樂就是孫天勤最愛的鄧麗君的代表作《月亮代表我的心》。
1985年2月9日,鄧麗君在新加坡接受香港記者長途電話訪問時表示:「身為一個藝人,有這麼多中國人喜歡聽自己的歌,心裡難免會有點兒想面對面唱給他們聽的衝動,但是我生長在台灣,我一定會堅持我的立場,不可能去大陸演唱⋯⋯」
1970年代後期,鄧麗君的歌聲開始傳入中國並受到熱烈歡迎,但官方主流文化一直批評其「黃色」、「反動」、「靡靡之音」。1980年,中國音樂協會召開「西山會議」予以嚴厲批判,指責《何日君再來》是「漢奸歌曲」。會上有一名文革中倖存下來的原左翼文聯工作者厲聲譴責說:「這首歌我熟悉,1937年就唱出來了。那時日本人還占著上海呢,上海灘都知道。說這君再來呀,是希望國民黨回來收復失地的。現在唱,那不就等於要等跟國民黨『反攻大陸』搞裡應外合嘛。」
然而,官方越是批判和查禁,民間越是喜歡。鄧麗君的盜版卡帶充斥市面,擄獲無數民眾的心,《何日君再來》、《小城故事》、《路邊的野花不要採》在大街小巷中傳唱,人們開玩笑地說:「白天聽老鄧(鄧小平)、晚上聽小鄧」、「只愛小鄧,不愛老鄧」。
劉曉波曾在幾篇文章中談及大學時代聽到鄧麗君歌曲時的巨大震撼:「在我的記憶中,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對中國人的觀念轉變產生最深刻影響的文化事件,絕不是官方發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而是一波接一波的民間思潮,特別是鄧麗君的歌和《今天》的詩,對我們這代大學生的深遠影響,不但遠遠超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超過當時頗為時髦的『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正是這種來自民間的『靡靡之音』和『反叛之聲』,讓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性堅冰融化為人性的春風,讓革命化審美裂變為現代性審美。」
劉曉波還寫道:「我常常想起1977年我剛上大學的時候,我第一次聽到了港台歌星鄧麗君那種纏綿的、非常富有人情色彩的、帶有內心獨白式的歌曲。這種從唱法和歌詞所表達出來的竊竊私語式的,傾訴個人內心痛苦、哀傷和生活小感覺的歌聲,給我的靈魂造成強烈的震撼。⋯⋯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第一次聽鄧麗君歌聲的時候,它確實喚起了我們這一代人心中一種本能的、對溫暖的人性的嚮往。我記得在大學裡聽這些歌的時候,同學們都非常興奮。但是,由於當時剛剛改革開放,聽這種歌在某種程度上還有禁忌,所以很多人是回到家裡,幾個同學拿著答錄機偷著聽。但是,這種歌聲的傳播面非常之廣、非常之快,迅速普及了全國。」
劉曉波寫出了那一代中國年輕大學生對鄧麗君的癡迷:「1970年代末,鄧麗君的歌征服了大陸的年輕一代,喚醒了國人生命中最柔軟的部分。她用氣嗓唱出的情歌,唱垮了我們用鋼鐵旋律鑄造的革命意志,唱軟了我們用殘酷鬥爭錘煉出的冷酷心腸,也喚醒了我們身上被擠壓到生命黑暗處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壓抑的柔軟和溫情得到了釋放。儘管,官方禁止這類『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廣播裡聽到,第一個學著鄧麗君氣嗓的李谷一被多次開會批判。但在私下裡,大家都圍著一台俗稱『磚頭』的收錄機反覆聽,在寢室裡、走廊裡、飯堂裡一遍遍地唱。那時,誰擁有那塊日本產的『磚頭』,誰就會得到眾星捧月般的簇擁。」
1989年5月,北京及中國各地爆發民主運動。5月27日,戒嚴令下的北京情勢越發危急,近二百位香港演藝界人士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持續十二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將近三十萬市民入場參加,歌聲響徹整個馬場。十二小時的馬拉松演唱會,共籌得一千三百萬港元,全部用以支援北京民運。
鄧麗君不顧周遭親友反對,表態支持學生,並親赴現場演唱〈家在山的那一邊〉,身上懸掛「反對軍管」的牌子。在演講前,她對聽眾說:「非常謝謝大家這麼熱心,在香港,大家聚在一起,努力爭取民主。我練習了一首歌,從來沒唱過,我想也沒多少人聽過,希望大家聽了以後,就知道我心裡想說的是什麼。」這首歌的歌詞是: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那兒有茂密的森林,那兒有無邊的草原
春天播種稻麥的種子,秋天收割等待著新年
張大叔從不發愁,李大嬸永遠樂觀
自從窯洞裡鑽出了厲鼠,一切都改變了
它嚼食了深埋的枯骨,侵毒了人性的良善……
(未完)
鄧麗君:出生於台灣雲林縣褒忠鄉田洋村。父親鄧樞是河北大名縣大街鎮鄧台村人,是因國共戰爭而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國軍軍官,母親趙素桂是山東東平縣人。
早在小學時,鄧麗君就已展現出歌唱天賦,並經常登台表演。1964年,年僅十一歲的鄧麗君參加中華廣播電台舉辦的黃梅調歌唱比賽,以一曲〈訪英台〉奪得冠軍;翌年以〈採紅菱〉在金馬獎唱片公司舉辦的歌唱比賽奪冠。其後,鄧麗君利用課餘時間參加正聲廣播公司舉辦的歌唱訓練班,學習歌唱技巧,以第一名成績結業。
1967年,鄧麗君加盟宇宙唱片,發行個人第一張專輯《鄧麗君之歌第一集.鳳陽花鼓》。1968年,於台北中山堂參加賑濟菲律賓震災的演出,捐款新台幣一萬一千元。1969年,中國電視公司啟播,鄧麗君獲邀主持晚間黃金時間播出的節目《每日一星》,並為中視首部電視連續劇《晶晶》主唱同名主題曲,成為她演唱的第一首影視主題歌曲,令她家傳戶曉。同年,參演首部電影—由謝君儀執導的《謝謝總經理》,飾演能歌善舞的女大學生,片中她唱了十首曲風青春活潑的歌曲,正式成為「歌、影、視」三棲的歌手。
1960年代末,鄧麗君開始赴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地巡迴演出,並頻繁參與慈善。1971年,為籌設香港保良中學、救濟香港水災義演;7月,在越南海南醫院看望孤寡老人;6月,參加新加坡「歌樂飄飄慈善晚會」,為殘障兒童救濟基金募款;1973年,於新加坡國家劇場出席遠東十大巨星慈善晚會。
1974年,鄧麗君在母親陪同下,前往日本發展。同年7月1日,她的日語單曲〈空港〉在一個月內以七十萬餘張總銷量進入全日本流行榜前十五名,因此榮獲日本唱片大獎新人獎。她在東京、川崎等地舉辦個人演唱會,大受歡迎。
1979年,鄧麗君又赴美國發展,先到舊金山落腳,然後到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進修英文,之後轉學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日文、生物及數學。期間完成了〈甜蜜蜜〉和〈小城故事〉的錄製,並在舊金山、洛杉磯和溫哥華舉行演唱會。
1980年10月4日,鄧麗君返回台灣舉行演唱會,捐所得新台幣一百五十萬零六百元予「自強救國基金」。在演唱會中,主持人田文仲向鄧麗君求證關於中國邀約她前往演唱之事,她表示曾在報紙上看見相關訊息但無人前來接洽,並手握拳頭、溫柔而堅定地說:「如果,我去大陸演唱的話,那麼,當我在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們三民主義在大陸實行的那一天。」話畢,台下響起如雷貫耳的掌聲,主持人也讚嘆鼓掌。
1981年1月,鄧麗君被行政院新聞局授予「愛國藝人」獎牌。8月,鄧麗君花了一個多月,跑遍台灣各地軍營勞軍演唱,深受國軍將士追捧,被稱作「永遠的軍中情人」。她說:「我生長在一個軍人家庭,我老爸曾參加過台兒莊、營口等戰役,所以,我從小看到軍人就有一份說不出的親切感。在面對國軍弟兄們表演時,陌生感就會一掃而空,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像美國的鮑勃.霍伯一樣,年年風塵僕僕的為自己國家的阿兵哥盡心盡力。」
在勞軍演出期間,鄧麗君在清晨5點起床,與金門守軍弟兄一起晨跑,包括幾程很難跑的坡度。她沒有喊累,汗水從她沒有化妝的臉上不斷淌下,她只是帥氣的用手背抹去,就像任何一個阿兵哥會做的舉動一樣。據部隊指揮官說,「鄧麗君效應」延續了好長一段時間,往後晨跑再沒有人敢摸魚、脫隊,部隊長往往會抬出鄧麗君來激勵大家,她的行動勞軍果然達到效果,不但提升了士氣,而且加強了心防,這不是唱唱跳跳、瘋狂一宵的勞軍活動所能比擬。
在鄧麗君成千上萬歌迷當中,有一位身分很特殊的人物,就是在1981年11月26日下午,駕著米格機投誠來歸的反共義士吳榮根。當記者紛紛問及他今後個人的心願時,誰也料不到,他竟然誠懇而靦腆說:「非常想見鄧麗君一面。」
透過新聞局安排,鄧麗君應邀在台中清泉崗和吳榮根見面,吳榮根初見鄧麗君,紅著臉,大半天說不出話來,鄧麗君不斷以輕言細語引導他。吳榮根談到她的歌被禁聽、禁錄,大陸人民仍然想盡辦法偷偷的聽。她感慨地表示,在自由地區生活的人,能隨意選擇愛聽的歌曲,在大陸卻不能,說著、聽著,忍不住哭了,不斷以搭在右肩上的圍巾拭淚。她送給吳榮根兩張唱片—《別把眉兒皺》和《原鄉情濃》,讓身在台灣的自由人能夠自在的聽個夠。
鄧麗君平復情緒之後,應基地飛行軍官要求,清唱了《何日君再來》和《小城故事》,吳榮根在旁靜靜的聽著她清唱,這比他在中國的部隊裡偷偷聽那種拷貝了又拷貝的錄音帶要清晰太多太多,好聽得不能再好聽。他覺得自己實在幸福極了,幸福到說不出適當的話來表達。鄧麗君落落大方的邀吳榮根一起唱《小城故事》,空軍官兵們熱切的鼓掌,打拍子應和。直到下午3點,鄧麗君才離開空軍基地,吳榮根送到基地門口,握手、目送她離去,內心的感動和興奮無法形容。
不久之後,海峽對岸又有孫天勤、李天慧等人投奔自由,同樣表明非常想見鄧麗君。鄧麗君在十五週年演唱會上與他們相見,並親切問好。那晚的表演,徹底滿足了反共義士們此生最想聽她唱歌的心願。
多年後,孫天勤在台北病逝。在追悼會上,其遺孀、音樂家李天慧特別提及,先生生前最愛聽的就是鄧麗君的歌。追悼會上最後放映孫天勤的追思影片,配樂就是孫天勤最愛的鄧麗君的代表作《月亮代表我的心》。
1985年2月9日,鄧麗君在新加坡接受香港記者長途電話訪問時表示:「身為一個藝人,有這麼多中國人喜歡聽自己的歌,心裡難免會有點兒想面對面唱給他們聽的衝動,但是我生長在台灣,我一定會堅持我的立場,不可能去大陸演唱⋯⋯」
1970年代後期,鄧麗君的歌聲開始傳入中國並受到熱烈歡迎,但官方主流文化一直批評其「黃色」、「反動」、「靡靡之音」。1980年,中國音樂協會召開「西山會議」予以嚴厲批判,指責《何日君再來》是「漢奸歌曲」。會上有一名文革中倖存下來的原左翼文聯工作者厲聲譴責說:「這首歌我熟悉,1937年就唱出來了。那時日本人還占著上海呢,上海灘都知道。說這君再來呀,是希望國民黨回來收復失地的。現在唱,那不就等於要等跟國民黨『反攻大陸』搞裡應外合嘛。」
然而,官方越是批判和查禁,民間越是喜歡。鄧麗君的盜版卡帶充斥市面,擄獲無數民眾的心,《何日君再來》、《小城故事》、《路邊的野花不要採》在大街小巷中傳唱,人們開玩笑地說:「白天聽老鄧(鄧小平)、晚上聽小鄧」、「只愛小鄧,不愛老鄧」。
劉曉波曾在幾篇文章中談及大學時代聽到鄧麗君歌曲時的巨大震撼:「在我的記憶中,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對中國人的觀念轉變產生最深刻影響的文化事件,絕不是官方發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而是一波接一波的民間思潮,特別是鄧麗君的歌和《今天》的詩,對我們這代大學生的深遠影響,不但遠遠超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超過當時頗為時髦的『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正是這種來自民間的『靡靡之音』和『反叛之聲』,讓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性堅冰融化為人性的春風,讓革命化審美裂變為現代性審美。」
劉曉波還寫道:「我常常想起1977年我剛上大學的時候,我第一次聽到了港台歌星鄧麗君那種纏綿的、非常富有人情色彩的、帶有內心獨白式的歌曲。這種從唱法和歌詞所表達出來的竊竊私語式的,傾訴個人內心痛苦、哀傷和生活小感覺的歌聲,給我的靈魂造成強烈的震撼。⋯⋯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第一次聽鄧麗君歌聲的時候,它確實喚起了我們這一代人心中一種本能的、對溫暖的人性的嚮往。我記得在大學裡聽這些歌的時候,同學們都非常興奮。但是,由於當時剛剛改革開放,聽這種歌在某種程度上還有禁忌,所以很多人是回到家裡,幾個同學拿著答錄機偷著聽。但是,這種歌聲的傳播面非常之廣、非常之快,迅速普及了全國。」
劉曉波寫出了那一代中國年輕大學生對鄧麗君的癡迷:「1970年代末,鄧麗君的歌征服了大陸的年輕一代,喚醒了國人生命中最柔軟的部分。她用氣嗓唱出的情歌,唱垮了我們用鋼鐵旋律鑄造的革命意志,唱軟了我們用殘酷鬥爭錘煉出的冷酷心腸,也喚醒了我們身上被擠壓到生命黑暗處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壓抑的柔軟和溫情得到了釋放。儘管,官方禁止這類『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廣播裡聽到,第一個學著鄧麗君氣嗓的李谷一被多次開會批判。但在私下裡,大家都圍著一台俗稱『磚頭』的收錄機反覆聽,在寢室裡、走廊裡、飯堂裡一遍遍地唱。那時,誰擁有那塊日本產的『磚頭』,誰就會得到眾星捧月般的簇擁。」
1989年5月,北京及中國各地爆發民主運動。5月27日,戒嚴令下的北京情勢越發危急,近二百位香港演藝界人士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持續十二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將近三十萬市民入場參加,歌聲響徹整個馬場。十二小時的馬拉松演唱會,共籌得一千三百萬港元,全部用以支援北京民運。
鄧麗君不顧周遭親友反對,表態支持學生,並親赴現場演唱〈家在山的那一邊〉,身上懸掛「反對軍管」的牌子。在演講前,她對聽眾說:「非常謝謝大家這麼熱心,在香港,大家聚在一起,努力爭取民主。我練習了一首歌,從來沒唱過,我想也沒多少人聽過,希望大家聽了以後,就知道我心裡想說的是什麼。」這首歌的歌詞是: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那兒有茂密的森林,那兒有無邊的草原
春天播種稻麥的種子,秋天收割等待著新年
張大叔從不發愁,李大嬸永遠樂觀
自從窯洞裡鑽出了厲鼠,一切都改變了
它嚼食了深埋的枯骨,侵毒了人性的良善……
(未完)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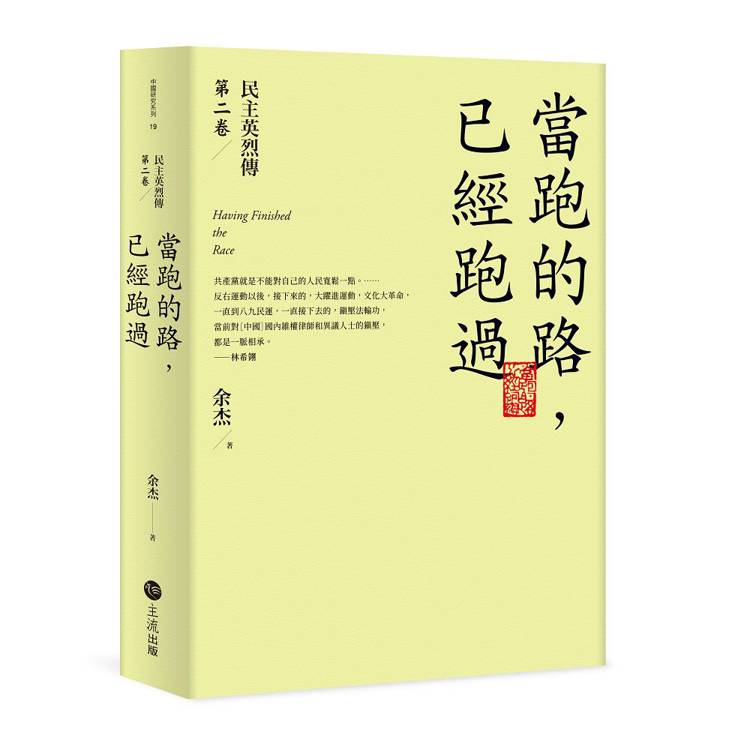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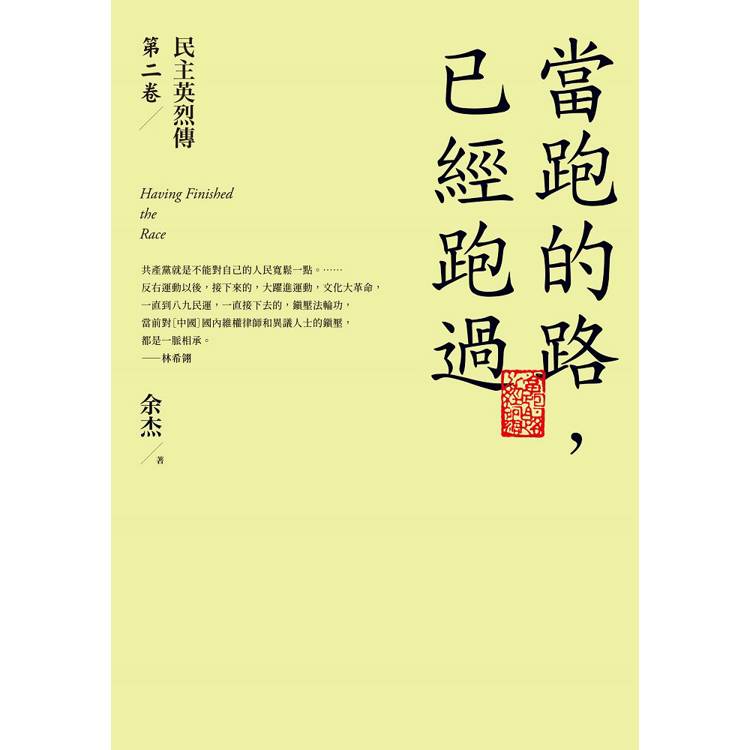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