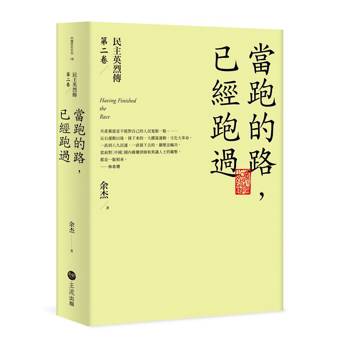鄧麗君:我絕不向暴政低頭,絕不對壓力妥協
鄧麗君:出生於台灣雲林縣褒忠鄉田洋村。父親鄧樞是河北大名縣大街鎮鄧台村人,是因國共戰爭而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國軍軍官,母親趙素桂是山東東平縣人。
早在小學時,鄧麗君就已展現出歌唱天賦,並經常登台表演。1964年,年僅十一歲的鄧麗君參加中華廣播電台舉辦的黃梅調歌唱比賽,以一曲〈訪英台〉奪得冠軍;翌年以〈採紅菱〉在金馬獎唱片公司舉辦的歌唱比賽奪冠。其後,鄧麗君利用課餘時間參加正聲廣播公司舉辦的歌唱訓練班,學習歌唱技巧,以第一名成績結業。
1967年,鄧麗君加盟宇宙唱片,發行個人第一張專輯《鄧麗君之歌第一集.鳳陽花鼓》。1968年,於台北中山堂參加賑濟菲律賓震災的演出,捐款新台幣一萬一千元。1969年,中國電視公司啟播,鄧麗君獲邀主持晚間黃金時間播出的節目《每日一星》,並為中視首部電視連續劇《晶晶》主唱同名主題曲,成為她演唱的第一首影視主題歌曲,令她家傳戶曉。同年,參演首部電影—由謝君儀執導的《謝謝總經理》,飾演能歌善舞的女大學生,片中她唱了十首曲風青春活潑的歌曲,正式成為「歌、影、視」三棲的歌手。
1960年代末,鄧麗君開始赴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地巡迴演出,並頻繁參與慈善。1971年,為籌設香港保良中學、救濟香港水災義演;7月,在越南海南醫院看望孤寡老人;6月,參加新加坡「歌樂飄飄慈善晚會」,為殘障兒童救濟基金募款;1973年,於新加坡國家劇場出席遠東十大巨星慈善晚會。
1974年,鄧麗君在母親陪同下,前往日本發展。同年7月1日,她的日語單曲〈空港〉在一個月內以七十萬餘張總銷量進入全日本流行榜前十五名,因此榮獲日本唱片大獎新人獎。她在東京、川崎等地舉辦個人演唱會,大受歡迎。
1979年,鄧麗君又赴美國發展,先到舊金山落腳,然後到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進修英文,之後轉學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日文、生物及數學。期間完成了〈甜蜜蜜〉和〈小城故事〉的錄製,並在舊金山、洛杉磯和溫哥華舉行演唱會。
1980年10月4日,鄧麗君返回台灣舉行演唱會,捐所得新台幣一百五十萬零六百元予「自強救國基金」。在演唱會中,主持人田文仲向鄧麗君求證關於中國邀約她前往演唱之事,她表示曾在報紙上看見相關訊息但無人前來接洽,並手握拳頭、溫柔而堅定地說:「如果,我去大陸演唱的話,那麼,當我在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們三民主義在大陸實行的那一天。」話畢,台下響起如雷貫耳的掌聲,主持人也讚嘆鼓掌。
1981年1月,鄧麗君被行政院新聞局授予「愛國藝人」獎牌。8月,鄧麗君花了一個多月,跑遍台灣各地軍營勞軍演唱,深受國軍將士追捧,被稱作「永遠的軍中情人」。她說:「我生長在一個軍人家庭,我老爸曾參加過台兒莊、營口等戰役,所以,我從小看到軍人就有一份說不出的親切感。在面對國軍弟兄們表演時,陌生感就會一掃而空,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像美國的鮑勃.霍伯一樣,年年風塵僕僕的為自己國家的阿兵哥盡心盡力。」
在勞軍演出期間,鄧麗君在清晨5點起床,與金門守軍弟兄一起晨跑,包括幾程很難跑的坡度。她沒有喊累,汗水從她沒有化妝的臉上不斷淌下,她只是帥氣的用手背抹去,就像任何一個阿兵哥會做的舉動一樣。據部隊指揮官說,「鄧麗君效應」延續了好長一段時間,往後晨跑再沒有人敢摸魚、脫隊,部隊長往往會抬出鄧麗君來激勵大家,她的行動勞軍果然達到效果,不但提升了士氣,而且加強了心防,這不是唱唱跳跳、瘋狂一宵的勞軍活動所能比擬。
在鄧麗君成千上萬歌迷當中,有一位身分很特殊的人物,就是在1981年11月26日下午,駕著米格機投誠來歸的反共義士吳榮根。當記者紛紛問及他今後個人的心願時,誰也料不到,他竟然誠懇而靦腆說:「非常想見鄧麗君一面。」
透過新聞局安排,鄧麗君應邀在台中清泉崗和吳榮根見面,吳榮根初見鄧麗君,紅著臉,大半天說不出話來,鄧麗君不斷以輕言細語引導他。吳榮根談到她的歌被禁聽、禁錄,大陸人民仍然想盡辦法偷偷的聽。她感慨地表示,在自由地區生活的人,能隨意選擇愛聽的歌曲,在大陸卻不能,說著、聽著,忍不住哭了,不斷以搭在右肩上的圍巾拭淚。她送給吳榮根兩張唱片—《別把眉兒皺》和《原鄉情濃》,讓身在台灣的自由人能夠自在的聽個夠。
鄧麗君平復情緒之後,應基地飛行軍官要求,清唱了《何日君再來》和《小城故事》,吳榮根在旁靜靜的聽著她清唱,這比他在中國的部隊裡偷偷聽那種拷貝了又拷貝的錄音帶要清晰太多太多,好聽得不能再好聽。他覺得自己實在幸福極了,幸福到說不出適當的話來表達。鄧麗君落落大方的邀吳榮根一起唱《小城故事》,空軍官兵們熱切的鼓掌,打拍子應和。直到下午3點,鄧麗君才離開空軍基地,吳榮根送到基地門口,握手、目送她離去,內心的感動和興奮無法形容。
不久之後,海峽對岸又有孫天勤、李天慧等人投奔自由,同樣表明非常想見鄧麗君。鄧麗君在十五週年演唱會上與他們相見,並親切問好。那晚的表演,徹底滿足了反共義士們此生最想聽她唱歌的心願。
多年後,孫天勤在台北病逝。在追悼會上,其遺孀、音樂家李天慧特別提及,先生生前最愛聽的就是鄧麗君的歌。追悼會上最後放映孫天勤的追思影片,配樂就是孫天勤最愛的鄧麗君的代表作《月亮代表我的心》。
1985年2月9日,鄧麗君在新加坡接受香港記者長途電話訪問時表示:「身為一個藝人,有這麼多中國人喜歡聽自己的歌,心裡難免會有點兒想面對面唱給他們聽的衝動,但是我生長在台灣,我一定會堅持我的立場,不可能去大陸演唱⋯⋯」
1970年代後期,鄧麗君的歌聲開始傳入中國並受到熱烈歡迎,但官方主流文化一直批評其「黃色」、「反動」、「靡靡之音」。1980年,中國音樂協會召開「西山會議」予以嚴厲批判,指責《何日君再來》是「漢奸歌曲」。會上有一名文革中倖存下來的原左翼文聯工作者厲聲譴責說:「這首歌我熟悉,1937年就唱出來了。那時日本人還占著上海呢,上海灘都知道。說這君再來呀,是希望國民黨回來收復失地的。現在唱,那不就等於要等跟國民黨『反攻大陸』搞裡應外合嘛。」
然而,官方越是批判和查禁,民間越是喜歡。鄧麗君的盜版卡帶充斥市面,擄獲無數民眾的心,《何日君再來》、《小城故事》、《路邊的野花不要採》在大街小巷中傳唱,人們開玩笑地說:「白天聽老鄧(鄧小平)、晚上聽小鄧」、「只愛小鄧,不愛老鄧」。
劉曉波曾在幾篇文章中談及大學時代聽到鄧麗君歌曲時的巨大震撼:「在我的記憶中,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對中國人的觀念轉變產生最深刻影響的文化事件,絕不是官方發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而是一波接一波的民間思潮,特別是鄧麗君的歌和《今天》的詩,對我們這代大學生的深遠影響,不但遠遠超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超過當時頗為時髦的『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正是這種來自民間的『靡靡之音』和『反叛之聲』,讓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性堅冰融化為人性的春風,讓革命化審美裂變為現代性審美。」
劉曉波還寫道:「我常常想起1977年我剛上大學的時候,我第一次聽到了港台歌星鄧麗君那種纏綿的、非常富有人情色彩的、帶有內心獨白式的歌曲。這種從唱法和歌詞所表達出來的竊竊私語式的,傾訴個人內心痛苦、哀傷和生活小感覺的歌聲,給我的靈魂造成強烈的震撼。⋯⋯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第一次聽鄧麗君歌聲的時候,它確實喚起了我們這一代人心中一種本能的、對溫暖的人性的嚮往。我記得在大學裡聽這些歌的時候,同學們都非常興奮。但是,由於當時剛剛改革開放,聽這種歌在某種程度上還有禁忌,所以很多人是回到家裡,幾個同學拿著答錄機偷著聽。但是,這種歌聲的傳播面非常之廣、非常之快,迅速普及了全國。」
劉曉波寫出了那一代中國年輕大學生對鄧麗君的癡迷:「1970年代末,鄧麗君的歌征服了大陸的年輕一代,喚醒了國人生命中最柔軟的部分。她用氣嗓唱出的情歌,唱垮了我們用鋼鐵旋律鑄造的革命意志,唱軟了我們用殘酷鬥爭錘煉出的冷酷心腸,也喚醒了我們身上被擠壓到生命黑暗處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壓抑的柔軟和溫情得到了釋放。儘管,官方禁止這類『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廣播裡聽到,第一個學著鄧麗君氣嗓的李谷一被多次開會批判。但在私下裡,大家都圍著一台俗稱『磚頭』的收錄機反覆聽,在寢室裡、走廊裡、飯堂裡一遍遍地唱。那時,誰擁有那塊日本產的『磚頭』,誰就會得到眾星捧月般的簇擁。」
1989年5月,北京及中國各地爆發民主運動。5月27日,戒嚴令下的北京情勢越發危急,近二百位香港演藝界人士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持續十二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將近三十萬市民入場參加,歌聲響徹整個馬場。十二小時的馬拉松演唱會,共籌得一千三百萬港元,全部用以支援北京民運。
鄧麗君不顧周遭親友反對,表態支持學生,並親赴現場演唱〈家在山的那一邊〉,身上懸掛「反對軍管」的牌子。在演講前,她對聽眾說:「非常謝謝大家這麼熱心,在香港,大家聚在一起,努力爭取民主。我練習了一首歌,從來沒唱過,我想也沒多少人聽過,希望大家聽了以後,就知道我心裡想說的是什麼。」這首歌的歌詞是: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那兒有茂密的森林,那兒有無邊的草原
春天播種稻麥的種子,秋天收割等待著新年
張大叔從不發愁,李大嬸永遠樂觀
自從窯洞裡鑽出了厲鼠,一切都改變了
它嚼食了深埋的枯骨,侵毒了人性的良善……
(未完)
鄧麗君:出生於台灣雲林縣褒忠鄉田洋村。父親鄧樞是河北大名縣大街鎮鄧台村人,是因國共戰爭而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國軍軍官,母親趙素桂是山東東平縣人。
早在小學時,鄧麗君就已展現出歌唱天賦,並經常登台表演。1964年,年僅十一歲的鄧麗君參加中華廣播電台舉辦的黃梅調歌唱比賽,以一曲〈訪英台〉奪得冠軍;翌年以〈採紅菱〉在金馬獎唱片公司舉辦的歌唱比賽奪冠。其後,鄧麗君利用課餘時間參加正聲廣播公司舉辦的歌唱訓練班,學習歌唱技巧,以第一名成績結業。
1967年,鄧麗君加盟宇宙唱片,發行個人第一張專輯《鄧麗君之歌第一集.鳳陽花鼓》。1968年,於台北中山堂參加賑濟菲律賓震災的演出,捐款新台幣一萬一千元。1969年,中國電視公司啟播,鄧麗君獲邀主持晚間黃金時間播出的節目《每日一星》,並為中視首部電視連續劇《晶晶》主唱同名主題曲,成為她演唱的第一首影視主題歌曲,令她家傳戶曉。同年,參演首部電影—由謝君儀執導的《謝謝總經理》,飾演能歌善舞的女大學生,片中她唱了十首曲風青春活潑的歌曲,正式成為「歌、影、視」三棲的歌手。
1960年代末,鄧麗君開始赴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地巡迴演出,並頻繁參與慈善。1971年,為籌設香港保良中學、救濟香港水災義演;7月,在越南海南醫院看望孤寡老人;6月,參加新加坡「歌樂飄飄慈善晚會」,為殘障兒童救濟基金募款;1973年,於新加坡國家劇場出席遠東十大巨星慈善晚會。
1974年,鄧麗君在母親陪同下,前往日本發展。同年7月1日,她的日語單曲〈空港〉在一個月內以七十萬餘張總銷量進入全日本流行榜前十五名,因此榮獲日本唱片大獎新人獎。她在東京、川崎等地舉辦個人演唱會,大受歡迎。
1979年,鄧麗君又赴美國發展,先到舊金山落腳,然後到洛杉磯的南加州大學進修英文,之後轉學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習日文、生物及數學。期間完成了〈甜蜜蜜〉和〈小城故事〉的錄製,並在舊金山、洛杉磯和溫哥華舉行演唱會。
1980年10月4日,鄧麗君返回台灣舉行演唱會,捐所得新台幣一百五十萬零六百元予「自強救國基金」。在演唱會中,主持人田文仲向鄧麗君求證關於中國邀約她前往演唱之事,她表示曾在報紙上看見相關訊息但無人前來接洽,並手握拳頭、溫柔而堅定地說:「如果,我去大陸演唱的話,那麼,當我在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們三民主義在大陸實行的那一天。」話畢,台下響起如雷貫耳的掌聲,主持人也讚嘆鼓掌。
1981年1月,鄧麗君被行政院新聞局授予「愛國藝人」獎牌。8月,鄧麗君花了一個多月,跑遍台灣各地軍營勞軍演唱,深受國軍將士追捧,被稱作「永遠的軍中情人」。她說:「我生長在一個軍人家庭,我老爸曾參加過台兒莊、營口等戰役,所以,我從小看到軍人就有一份說不出的親切感。在面對國軍弟兄們表演時,陌生感就會一掃而空,我希望有一天能夠像美國的鮑勃.霍伯一樣,年年風塵僕僕的為自己國家的阿兵哥盡心盡力。」
在勞軍演出期間,鄧麗君在清晨5點起床,與金門守軍弟兄一起晨跑,包括幾程很難跑的坡度。她沒有喊累,汗水從她沒有化妝的臉上不斷淌下,她只是帥氣的用手背抹去,就像任何一個阿兵哥會做的舉動一樣。據部隊指揮官說,「鄧麗君效應」延續了好長一段時間,往後晨跑再沒有人敢摸魚、脫隊,部隊長往往會抬出鄧麗君來激勵大家,她的行動勞軍果然達到效果,不但提升了士氣,而且加強了心防,這不是唱唱跳跳、瘋狂一宵的勞軍活動所能比擬。
在鄧麗君成千上萬歌迷當中,有一位身分很特殊的人物,就是在1981年11月26日下午,駕著米格機投誠來歸的反共義士吳榮根。當記者紛紛問及他今後個人的心願時,誰也料不到,他竟然誠懇而靦腆說:「非常想見鄧麗君一面。」
透過新聞局安排,鄧麗君應邀在台中清泉崗和吳榮根見面,吳榮根初見鄧麗君,紅著臉,大半天說不出話來,鄧麗君不斷以輕言細語引導他。吳榮根談到她的歌被禁聽、禁錄,大陸人民仍然想盡辦法偷偷的聽。她感慨地表示,在自由地區生活的人,能隨意選擇愛聽的歌曲,在大陸卻不能,說著、聽著,忍不住哭了,不斷以搭在右肩上的圍巾拭淚。她送給吳榮根兩張唱片—《別把眉兒皺》和《原鄉情濃》,讓身在台灣的自由人能夠自在的聽個夠。
鄧麗君平復情緒之後,應基地飛行軍官要求,清唱了《何日君再來》和《小城故事》,吳榮根在旁靜靜的聽著她清唱,這比他在中國的部隊裡偷偷聽那種拷貝了又拷貝的錄音帶要清晰太多太多,好聽得不能再好聽。他覺得自己實在幸福極了,幸福到說不出適當的話來表達。鄧麗君落落大方的邀吳榮根一起唱《小城故事》,空軍官兵們熱切的鼓掌,打拍子應和。直到下午3點,鄧麗君才離開空軍基地,吳榮根送到基地門口,握手、目送她離去,內心的感動和興奮無法形容。
不久之後,海峽對岸又有孫天勤、李天慧等人投奔自由,同樣表明非常想見鄧麗君。鄧麗君在十五週年演唱會上與他們相見,並親切問好。那晚的表演,徹底滿足了反共義士們此生最想聽她唱歌的心願。
多年後,孫天勤在台北病逝。在追悼會上,其遺孀、音樂家李天慧特別提及,先生生前最愛聽的就是鄧麗君的歌。追悼會上最後放映孫天勤的追思影片,配樂就是孫天勤最愛的鄧麗君的代表作《月亮代表我的心》。
1985年2月9日,鄧麗君在新加坡接受香港記者長途電話訪問時表示:「身為一個藝人,有這麼多中國人喜歡聽自己的歌,心裡難免會有點兒想面對面唱給他們聽的衝動,但是我生長在台灣,我一定會堅持我的立場,不可能去大陸演唱⋯⋯」
1970年代後期,鄧麗君的歌聲開始傳入中國並受到熱烈歡迎,但官方主流文化一直批評其「黃色」、「反動」、「靡靡之音」。1980年,中國音樂協會召開「西山會議」予以嚴厲批判,指責《何日君再來》是「漢奸歌曲」。會上有一名文革中倖存下來的原左翼文聯工作者厲聲譴責說:「這首歌我熟悉,1937年就唱出來了。那時日本人還占著上海呢,上海灘都知道。說這君再來呀,是希望國民黨回來收復失地的。現在唱,那不就等於要等跟國民黨『反攻大陸』搞裡應外合嘛。」
然而,官方越是批判和查禁,民間越是喜歡。鄧麗君的盜版卡帶充斥市面,擄獲無數民眾的心,《何日君再來》、《小城故事》、《路邊的野花不要採》在大街小巷中傳唱,人們開玩笑地說:「白天聽老鄧(鄧小平)、晚上聽小鄧」、「只愛小鄧,不愛老鄧」。
劉曉波曾在幾篇文章中談及大學時代聽到鄧麗君歌曲時的巨大震撼:「在我的記憶中,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對中國人的觀念轉變產生最深刻影響的文化事件,絕不是官方發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而是一波接一波的民間思潮,特別是鄧麗君的歌和《今天》的詩,對我們這代大學生的深遠影響,不但遠遠超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超過當時頗為時髦的『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正是這種來自民間的『靡靡之音』和『反叛之聲』,讓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性堅冰融化為人性的春風,讓革命化審美裂變為現代性審美。」
劉曉波還寫道:「我常常想起1977年我剛上大學的時候,我第一次聽到了港台歌星鄧麗君那種纏綿的、非常富有人情色彩的、帶有內心獨白式的歌曲。這種從唱法和歌詞所表達出來的竊竊私語式的,傾訴個人內心痛苦、哀傷和生活小感覺的歌聲,給我的靈魂造成強烈的震撼。⋯⋯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第一次聽鄧麗君歌聲的時候,它確實喚起了我們這一代人心中一種本能的、對溫暖的人性的嚮往。我記得在大學裡聽這些歌的時候,同學們都非常興奮。但是,由於當時剛剛改革開放,聽這種歌在某種程度上還有禁忌,所以很多人是回到家裡,幾個同學拿著答錄機偷著聽。但是,這種歌聲的傳播面非常之廣、非常之快,迅速普及了全國。」
劉曉波寫出了那一代中國年輕大學生對鄧麗君的癡迷:「1970年代末,鄧麗君的歌征服了大陸的年輕一代,喚醒了國人生命中最柔軟的部分。她用氣嗓唱出的情歌,唱垮了我們用鋼鐵旋律鑄造的革命意志,唱軟了我們用殘酷鬥爭錘煉出的冷酷心腸,也喚醒了我們身上被擠壓到生命黑暗處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壓抑的柔軟和溫情得到了釋放。儘管,官方禁止這類『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廣播裡聽到,第一個學著鄧麗君氣嗓的李谷一被多次開會批判。但在私下裡,大家都圍著一台俗稱『磚頭』的收錄機反覆聽,在寢室裡、走廊裡、飯堂裡一遍遍地唱。那時,誰擁有那塊日本產的『磚頭』,誰就會得到眾星捧月般的簇擁。」
1989年5月,北京及中國各地爆發民主運動。5月27日,戒嚴令下的北京情勢越發危急,近二百位香港演藝界人士在跑馬地馬場舉行持續十二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將近三十萬市民入場參加,歌聲響徹整個馬場。十二小時的馬拉松演唱會,共籌得一千三百萬港元,全部用以支援北京民運。
鄧麗君不顧周遭親友反對,表態支持學生,並親赴現場演唱〈家在山的那一邊〉,身上懸掛「反對軍管」的牌子。在演講前,她對聽眾說:「非常謝謝大家這麼熱心,在香港,大家聚在一起,努力爭取民主。我練習了一首歌,從來沒唱過,我想也沒多少人聽過,希望大家聽了以後,就知道我心裡想說的是什麼。」這首歌的歌詞是: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那兒有茂密的森林,那兒有無邊的草原
春天播種稻麥的種子,秋天收割等待著新年
張大叔從不發愁,李大嬸永遠樂觀
自從窯洞裡鑽出了厲鼠,一切都改變了
它嚼食了深埋的枯骨,侵毒了人性的良善……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