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與彼岸:一個社會運動者的身心之旅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從金門到南臺灣
從藝術到社會運動
從身心耗損到自我修復
一個環境運動者的「兩岸」備忘錄
這是一本結合自傳與社運經歷思考的書寫,記錄李根政從金門農家子弟、小學美術老師,後來落腳南臺灣成為環境運動者的歷程及反思。
金門古寧頭是國共對峙前線,八二三炮戰打響名號,然而戰爭的殘酷只有當地人才能感同身受。李根政在「前線」也是「邊陲」的古寧頭出生,小時候撿拾炮彈碎片換零嘴,青年時到臺灣本島學習美術,栽進藝術的世界。然而保守的家鄉關不住他嚮往自由的心靈,離開被宗族人際綑綁的金門來到高雄後,因緣際會從柴山展開對環境的省思,投入環境運動。
三十歲和友人創辦第一個環境組織,帶著教職身分從事環境運動;四十歲辭去教職,全心投入經營環境組織。從原本手握畫筆的文藝青年,轉為手握油漆刷寫抗議布條的社會運動者,穿梭在柴山公園設立、汞汙泥、臺塑及日月光水汙染、反高屏大湖、後勁反五輕等運動中。「棄文從武」的選擇,潛藏著對於環境深刻的思考,以及受南方社會運動啟蒙的初心。然而,在投入社會運動理想與實踐時,又該如何安頓耗損的身心?
「此岸」與「彼岸」,象徵著在金門與臺灣之間,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運動者志業與日常生活追尋之間,來來回回的多重對話,也在時代的矛盾衝突中,看見運動者生命的真實滋味。
【專文推薦】
吳介民 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
林生祥 音樂人
邱花妹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黃文龍 前柴山公園促進會會長、眼科醫師
【真誠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列)
何欣潔 離島出版總編輯
邱毓斌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阿潑 文字工作者
許恩恩 作家
廖瞇 文字工作者
賴偉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常務理事
從藝術到社會運動
從身心耗損到自我修復
一個環境運動者的「兩岸」備忘錄
這是一本結合自傳與社運經歷思考的書寫,記錄李根政從金門農家子弟、小學美術老師,後來落腳南臺灣成為環境運動者的歷程及反思。
金門古寧頭是國共對峙前線,八二三炮戰打響名號,然而戰爭的殘酷只有當地人才能感同身受。李根政在「前線」也是「邊陲」的古寧頭出生,小時候撿拾炮彈碎片換零嘴,青年時到臺灣本島學習美術,栽進藝術的世界。然而保守的家鄉關不住他嚮往自由的心靈,離開被宗族人際綑綁的金門來到高雄後,因緣際會從柴山展開對環境的省思,投入環境運動。
三十歲和友人創辦第一個環境組織,帶著教職身分從事環境運動;四十歲辭去教職,全心投入經營環境組織。從原本手握畫筆的文藝青年,轉為手握油漆刷寫抗議布條的社會運動者,穿梭在柴山公園設立、汞汙泥、臺塑及日月光水汙染、反高屏大湖、後勁反五輕等運動中。「棄文從武」的選擇,潛藏著對於環境深刻的思考,以及受南方社會運動啟蒙的初心。然而,在投入社會運動理想與實踐時,又該如何安頓耗損的身心?
「此岸」與「彼岸」,象徵著在金門與臺灣之間,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運動者志業與日常生活追尋之間,來來回回的多重對話,也在時代的矛盾衝突中,看見運動者生命的真實滋味。
【專文推薦】
吳介民 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
林生祥 音樂人
邱花妹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黃文龍 前柴山公園促進會會長、眼科醫師
【真誠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列)
何欣潔 離島出版總編輯
邱毓斌 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阿潑 文字工作者
許恩恩 作家
廖瞇 文字工作者
賴偉傑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常務理事
目錄
【推薦序】帶著鄉愁運動的人 吳介民
【推薦序】一位走得遠、走得久的運動者 邱花妹
【推薦序】和解之路 林生祥
【推薦序】小我、大我、無我 黃文龍
序
輯一 花崗岩島
戰火連天
矛盾的黨國奶水
沒有祕密的甜蜜
古寧頭灣
海埔地的鳥
美軍航照圖
三年大旱
染紅的鋼鐵與和平
輯二 南方的土地
十三號碼頭
柴山
看見犧牲之所
工業喝好水 農業喝毒水
神明與環保運動
與汙染共存或者出走
大河的浸潤
輯三 社會運動者
這是一份工作嗎
改變自己
毛筆與油漆刷
輯四 日常之味
身與心
媽媽的神明
喜歡吃還是喜歡煮飯
飲食偏好,是一種家庭銘印
後記 此岸與彼岸
致謝
附錄:李根政經歷
【推薦序】一位走得遠、走得久的運動者 邱花妹
【推薦序】和解之路 林生祥
【推薦序】小我、大我、無我 黃文龍
序
輯一 花崗岩島
戰火連天
矛盾的黨國奶水
沒有祕密的甜蜜
古寧頭灣
海埔地的鳥
美軍航照圖
三年大旱
染紅的鋼鐵與和平
輯二 南方的土地
十三號碼頭
柴山
看見犧牲之所
工業喝好水 農業喝毒水
神明與環保運動
與汙染共存或者出走
大河的浸潤
輯三 社會運動者
這是一份工作嗎
改變自己
毛筆與油漆刷
輯四 日常之味
身與心
媽媽的神明
喜歡吃還是喜歡煮飯
飲食偏好,是一種家庭銘印
後記 此岸與彼岸
致謝
附錄:李根政經歷
序/導讀
序
動念寫這本書正處於五十五歲這個門檻,老婆怡賢和許多同學都陸續進入退休生活,而我還在第一線的環境運動工作,心中不免也開始盤算著什麼時候要退休。
但是看到企業界、政治界的人士,在這正有社會影響力的年齡,不會輕言退休,況且作為非營利組織的共同創辦人,總有難以割捨的責任,心中有許多拉扯和矛盾。
在有點不上不下的生命階段,想了很多事,所以決定把它寫下來,做一個階段性的梳理。
有了第一本書《臺灣山林百年紀》的經驗,發現書寫下來往往可以好好告別過去,找到再出發的動力和方向,探尋生命新的可能性。
我常常想起日本國民畫家東山魁夷在唐招提寺御影堂的障壁畫,包含〈揚州薰風〉、〈濤聲〉、〈山雲〉三部曲。描繪著鑑真和尚六次從中國東渡到日本傳法,所遇到的艱難險阻。自古以來求法傳道者的精神,猶如一道道的光芒,總是激勵著我們這樣的凡人。
我也常會想起我的祖父,一個下南洋討生活的人,二十年才能回鄉一趟的磨難;我的父母經過了戰爭的洗禮和流離,都是我輩難以理解的辛苦。
相較而言,我是如此的幸運,有機會持續追尋著夢想。
我被歸類為環保人士或社運分子,但這本書並不打算喋喋不休分享環境問題,而是想要分享社會運動帶給我生命的轉變。
世界如潮水般正在劇烈變動著,作為一個臺灣人、金門人、環境運動工作者,如同一艘海上失去動力的船隨著潮水擺動,有時以為自己正在前進,但不時又被打回了岸上。每當生命要往前跨一步時,總是得從過往的生命去尋找內在的動力與勇氣。
我發現,每個人終究得面對自己的出身與銘印;每個人總有某些追尋,而我的追尋是從小島到了大島,在出世與入世之間拉扯。
從金門到臺灣,我在三十歲那年放下熱愛的藝術創作,四十歲辭去教職,從事環境運動,年近半百投身參選搞政黨,妄想開創新政治,在這個翻騰的社會與環境中,學習和成長。
從一個追求自我實現的原子個體,成了投入公共事務的環境運動者。在許多場合常常被問到,你是受到什麼樣的啟蒙或者影響而從事環境運動?你為什麼可以堅持這麼久?
這樣的提問代表的是對這份工作或志業的肯定,而站在對立面的人,則常把從事環境運動的組織或個人,視為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們。
這本書回溯我出生與成長的銘印,嘗試回答自己也不太清楚的這些問題。
在國際局勢愈加動盪,中國對臺灣併吞威脅持續升級之際,社會的分裂日益加劇,「我們」這樣的一群人們,因為監督或批判時政,則常被抹紅為中共同路人;或者因為支持與執政的民進黨接近的政策,而被抹為綠營側翼。
但事實上,被歸類為同一群人的「我們」,異質性很高,不應該也不適合被這樣貼標籤。
世界紛歧而多元,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這樣的一群人,很可能只有在「關心環境」的某一些角度有所交集,但其他領域則未必。
社會運動雖被認為是對公共事務和社會關懷的付出,但對我來說,更像是生命的學習和成長的歷程。包含了學習各種議題知識,精進改變社會的方法,處理自我的身心平衡,而最難的往往是後者。
我是一個來自偏鄉離島的人,處在兩個島嶼相異的歷史背景中,從戰爭與農村的背景,走到了臺灣的經濟成長,現世安穩、消費主義無所不存的世道。半世紀之後,再逢中國意圖併吞臺灣,處於戰爭邊緣的新情境。想要全盤瞭解自己身處的時代,再怎麼知識淵博與經驗豐富的人都無法做到。
兩年多來,我書寫著生命中的重要主題,金門、南方、社會運動、藝術與書法,起初想寫一本結構嚴謹的書,反覆改了好幾個版本,但實在做不到,只好妥協。生命之流是一個沒有中斷的連續體,生命中發生的事情和思緒總是交織、交雜、纏繞著,如同神經元構成的立體網絡,而寫作終究只是生命行旅和所思所想的切片、有限的記憶。
因為承認自己的有限,打破線性時間序的寫作邏輯之後,才豁然開朗。這不是自傳也不是小說,這是關於我在老家金門與臺灣之間,兩種身分的矛盾與追尋;社會運動的啟蒙;以及我的創作與生活,如微塵般的生命經歷。
但即使寫出來了,內心很仍然掙扎,這樣的一本書到底有沒有出版的價值?這些念頭在我腦海裡反覆出現。
最後,說服自己的理由是,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特的,無分孰輕孰重;每個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分享的目的不在於彰顯個人,而是在廣大世界中留下痕跡,如果對某些人和社會有些許影響和幫助,即有意義。
這是一本自我探尋的書寫,對於這個渡海的旅程,我內心充滿感恩,特別是人生半百之後,看見自己生命正處於縫合的新狀態,重溫寫字的單純喜悅。
謹以本書感謝生養我的金門、臺灣這兩個島嶼土地的滋養,及接納並允許我投入的社會,許多前輩友伴、後輩的啟蒙與幫助,以及親愛的家人的支持。
致與我同樣關心社會與小我實現,在大島與小島,在我們與他們之間,從此岸努力追尋彼岸的人們。
動念寫這本書正處於五十五歲這個門檻,老婆怡賢和許多同學都陸續進入退休生活,而我還在第一線的環境運動工作,心中不免也開始盤算著什麼時候要退休。
但是看到企業界、政治界的人士,在這正有社會影響力的年齡,不會輕言退休,況且作為非營利組織的共同創辦人,總有難以割捨的責任,心中有許多拉扯和矛盾。
在有點不上不下的生命階段,想了很多事,所以決定把它寫下來,做一個階段性的梳理。
有了第一本書《臺灣山林百年紀》的經驗,發現書寫下來往往可以好好告別過去,找到再出發的動力和方向,探尋生命新的可能性。
我常常想起日本國民畫家東山魁夷在唐招提寺御影堂的障壁畫,包含〈揚州薰風〉、〈濤聲〉、〈山雲〉三部曲。描繪著鑑真和尚六次從中國東渡到日本傳法,所遇到的艱難險阻。自古以來求法傳道者的精神,猶如一道道的光芒,總是激勵著我們這樣的凡人。
我也常會想起我的祖父,一個下南洋討生活的人,二十年才能回鄉一趟的磨難;我的父母經過了戰爭的洗禮和流離,都是我輩難以理解的辛苦。
相較而言,我是如此的幸運,有機會持續追尋著夢想。
我被歸類為環保人士或社運分子,但這本書並不打算喋喋不休分享環境問題,而是想要分享社會運動帶給我生命的轉變。
世界如潮水般正在劇烈變動著,作為一個臺灣人、金門人、環境運動工作者,如同一艘海上失去動力的船隨著潮水擺動,有時以為自己正在前進,但不時又被打回了岸上。每當生命要往前跨一步時,總是得從過往的生命去尋找內在的動力與勇氣。
我發現,每個人終究得面對自己的出身與銘印;每個人總有某些追尋,而我的追尋是從小島到了大島,在出世與入世之間拉扯。
從金門到臺灣,我在三十歲那年放下熱愛的藝術創作,四十歲辭去教職,從事環境運動,年近半百投身參選搞政黨,妄想開創新政治,在這個翻騰的社會與環境中,學習和成長。
從一個追求自我實現的原子個體,成了投入公共事務的環境運動者。在許多場合常常被問到,你是受到什麼樣的啟蒙或者影響而從事環境運動?你為什麼可以堅持這麼久?
這樣的提問代表的是對這份工作或志業的肯定,而站在對立面的人,則常把從事環境運動的組織或個人,視為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們。
這本書回溯我出生與成長的銘印,嘗試回答自己也不太清楚的這些問題。
在國際局勢愈加動盪,中國對臺灣併吞威脅持續升級之際,社會的分裂日益加劇,「我們」這樣的一群人們,因為監督或批判時政,則常被抹紅為中共同路人;或者因為支持與執政的民進黨接近的政策,而被抹為綠營側翼。
但事實上,被歸類為同一群人的「我們」,異質性很高,不應該也不適合被這樣貼標籤。
世界紛歧而多元,每個人都是獨特的,這樣的一群人,很可能只有在「關心環境」的某一些角度有所交集,但其他領域則未必。
社會運動雖被認為是對公共事務和社會關懷的付出,但對我來說,更像是生命的學習和成長的歷程。包含了學習各種議題知識,精進改變社會的方法,處理自我的身心平衡,而最難的往往是後者。
我是一個來自偏鄉離島的人,處在兩個島嶼相異的歷史背景中,從戰爭與農村的背景,走到了臺灣的經濟成長,現世安穩、消費主義無所不存的世道。半世紀之後,再逢中國意圖併吞臺灣,處於戰爭邊緣的新情境。想要全盤瞭解自己身處的時代,再怎麼知識淵博與經驗豐富的人都無法做到。
兩年多來,我書寫著生命中的重要主題,金門、南方、社會運動、藝術與書法,起初想寫一本結構嚴謹的書,反覆改了好幾個版本,但實在做不到,只好妥協。生命之流是一個沒有中斷的連續體,生命中發生的事情和思緒總是交織、交雜、纏繞著,如同神經元構成的立體網絡,而寫作終究只是生命行旅和所思所想的切片、有限的記憶。
因為承認自己的有限,打破線性時間序的寫作邏輯之後,才豁然開朗。這不是自傳也不是小說,這是關於我在老家金門與臺灣之間,兩種身分的矛盾與追尋;社會運動的啟蒙;以及我的創作與生活,如微塵般的生命經歷。
但即使寫出來了,內心很仍然掙扎,這樣的一本書到底有沒有出版的價值?這些念頭在我腦海裡反覆出現。
最後,說服自己的理由是,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特的,無分孰輕孰重;每個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分享的目的不在於彰顯個人,而是在廣大世界中留下痕跡,如果對某些人和社會有些許影響和幫助,即有意義。
這是一本自我探尋的書寫,對於這個渡海的旅程,我內心充滿感恩,特別是人生半百之後,看見自己生命正處於縫合的新狀態,重溫寫字的單純喜悅。
謹以本書感謝生養我的金門、臺灣這兩個島嶼土地的滋養,及接納並允許我投入的社會,許多前輩友伴、後輩的啟蒙與幫助,以及親愛的家人的支持。
致與我同樣關心社會與小我實現,在大島與小島,在我們與他們之間,從此岸努力追尋彼岸的人們。
試閱
戰火連天【節錄】
「一戰古寧頭,再戰大二膽,同仇敵愾,消滅匪黨,光輝的八二三!」這是一九七七年三臺聯播連續劇《風雨生信心》同名主題曲。
古寧頭是我的老家,是一個以戰爭聞名,被炮彈洗禮最慘烈的村莊。村子裡大抵都是閩式建築,即使到了今天仍是如此。
沿著家裡的周圍繞一圈,每棟舊房子都可以看到戰爭的印記。村莊裡留著許多戰後重建或修補的建築樣式,用海砂和稀薄的水泥粗糙翻模印製的屋瓦和空心磚,窗戶用上木頭和鋼筋,或者水泥印的花磚,大小補丁和堆疊各種材質的牆面,視覺上很美,但每道牆都是悲傷的故事。
村莊裡除了房子,最突兀的是為了躲炮彈用的防空洞。 許多金門人家裡就有防空洞,或者幾戶人家共同使用一個防空洞。
我家的防空洞已在二十多年前房子改建時填掉,如今沒法再進入重新感受。有一天,我和阿母、三叔、哥哥重新推敲家裡的防空洞,討論兩個晚上後,拼湊出這樣的故事。
防空洞開挖的時間應是在一九五四年九三炮戰 後,這個克難的防空洞,讓家人挺過了八二三炮戰 及之後延續二十年的「單打雙不打」。
防空洞長約一.五公尺、寬約一.一公尺,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要擠上八、九個或者更多人,不僅擁擠而且十分潮溼,常常要頻繁地把地下湧水舀出去,在那個年代每逢單日就要躲進這個安全的避難所。
每一個島嶼都有屬於它的命運,但是島嶼的命運通常不由自主,像是大洋中的小船,常常被大船駛過的巨浪攪得翻天覆地。
金門,距離臺灣島最近的距離是兩百一十公里,而距離中國最近的距離僅一.八公里。關於這個島嶼,最深的烙印是戰爭,以及最堅硬的花崗岩,最貧瘠的沙地與紅赤土。我的老家在金門西北角的古寧頭,已有六百多年歷史,村子分為南山、北山、林厝三個聚落,絕大部分都姓李,彼此都有血緣關係。從明朝以來,村子外海就上演大規模海戰,清朝出武將打海盜,子民除了務農,也擅於操舟航海,近代則是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的交戰區。
第二次國共戰爭,奠下臺海兩岸分治的一九四九年古寧頭大戰, 共軍指揮所就在古寧頭北山村,距離我家僅約兩百公尺,村子裡曾發生了激烈的巷戰,如今滿是彈孔的古厝已成觀光景點。當年不滿二十歲的父親和許多金門的男性一樣,被軍隊拉夫協助挖壕溝、埋屍體,後來共產黨打輸了,金門成為國民黨軍隊──中華民國的統治區,古寧頭成了一個被軍營包圍的村莊,古老的閩南建築牆上,到處是「殺朱拔毛」、「反共抗俄」的口號。
古寧頭大戰之後,金門開始實施「戰地政務」, 這意味人們所有的日常生活都軍事化了。
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是集軍、政、國民黨部的最高領導人,金門人形容是「皇帝」。縣長是少將或上校擔任,沒有地方議會;人民和軍人犯了罪都是接受軍法審判,晚上實施宵禁,燈火管制,往來臺灣和金門比照出國要入出境管制;臺灣和金門之間實施電信管制,只能寫信和發電報,沒有電話;金門、馬祖地區發行專用的貨幣,實施金融管制;五戶連保,互相監視;電器、攝影器材、球類等都是違禁品。
國民黨為什麼在金門實施全面的軍事化?回顧國際局勢和兩岸關係,發現並非中共的軍事威脅增加,而是蔣中正要透過在金門大量駐軍,提升臺灣在國際冷戰局勢中的地位,尤其是爭取美國的支持。然而,事實證明這個策略並沒有效果,一九七一年臺灣退出聯合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的唯一代表,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逐漸不被國際承認,一九七九年美國和中共建交。此意味著,在金門實施的軍事化,使得金門人做出無謂的犧牲,連作為工具的效果都沒有達成。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對金門炮擊,連續六個星期的猛烈炮擊,大約五十萬發炮彈落在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島嶼上,造成一百四十名平民死亡,數百人受傷,數千棟民房損毀。根據史學家的研究,毛澤東發動戰爭的原因可能是「向美國警告、向蘇聯示威,或是動員中國人民」,但很確定並不是想拿下金門,因為金門是臺灣與中國大陸相連的象徵,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占領金門,就是邁向兩個中國的第一步。
因為中國一個獨裁者的意志,金門成為炮火蹂躪的戰區,古寧頭是被炮擊最嚴重的村莊,我家大廳毀於炮火,家人堆置蚵殼於防空洞上方試圖阻隔炮火,冒死去沙崗的田裡撿拾地瓜勉強存活。母親說,炮彈落在雙鯉湖的聲音好像在舂麥(tsing-be̍h)。我只有一位姑姑,只聽過卻沒見過。從小聽父母口述,八二三炮戰期間,新婚才三個月的姑丈和懷有身孕的姑姑在田裡工作,姑丈中炮後,姑姑前去相救而雙亡。
八二三炮戰後到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之前,國、共又維持了長達二十一年「單打雙不打」的交戰狀態,只要是日曆上的單號日,共軍會在傍晚時刻打炮彈過來,國軍隨後回擊,在這個島嶼的人們,也被迫配合戰爭狀態。那段期間實施的是獨立於臺灣的「戰地政務」,生活裡有許多禁忌。
一九六八年,我出生在什麼樣的時刻?前一年北山播音站完工, 後一年慈堤完工,古寧頭灣成了慈湖,國民黨軍隊在古寧頭的軍事布署已經完備。
當時,村莊四周都是軍營。最高峰時,島嶼上住著六至十萬名軍人,人數足足是原有金門人口的二至三倍。
我們當小孩的,家裡不可以有球類,不能放風箏,當然也不能亂說話,大人不斷告誡亂說話會被抓去關。但很「炫」的是,從小我們的玩具槍就是真槍,因為年滿十八歲以上的男人就要當民防隊員,會分配到一把步槍隨時放在家中,我們會幫忙爸爸保養那把木頭柄單發射擊子彈的三○步槍,當然也會拿來練習扣扳機。我讀國中時,所有男同學都被編入「幼獅隊」, 在全島發布雷霆演習的時候負責巡邏和守路口,和同學一起抓逃兵。
十歲以前,我和島上的居民一同過著「單打雙不打」的炮彈人生,每逢日曆上印著一、三、五、七、九單日號碼的傍晚,我和家人就得點上蠟燭,進入父母親臥室裡的地下防空洞躲炮彈,等國共雙方的炮火結束,我和許多小朋友一樣,會依據當晚炮彈可能的落點,拿著手電筒去找炮彈破片,賣給雜貨店換取一點零嘴。
戰爭炮火成了日常,當時的我並不知道什麼是恐懼,但每次母親到廚房裡祭拜姑姑的牌位時,心裡總有莫名的感覺,也不曉得是恨或者痛。中年之後想到這件事,卻不由自主地流淚。
戰爭改變的,還有白馬。我家有一隻白馬,但在八二三炮戰時被炮彈傷到肚子,痛苦哀鳴,爸爸只好委託鄰居結束牠的生命,然後和鄰居分食。我家還有一隻白沙驢,被阿兵哥(國民黨軍隊)牽走(說好聽是徵召)載彈藥。於是,白馬和驢子成了家裡的傳說。
父親名李沃沛,一九三二年生,是古寧村子裡少數念過私塾的「知識分子」。家裡除了《金門日報》,還訂了《中國時報》。農忙回家後,父親每天都戴著老花眼鏡在大廳前的石砛上,靠著天井的自然光讀報。在這時刻裡,常見鄰居捧著來自臺灣的孩子或南洋親戚的來信,請父親讀信、回信。但是,父親對於當時由黨國掌控的宗族活動,只是被動的參與,鮮少與地方上鑽營的頭人來往。正直的父親所展現的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綜合的形象,成了我畢生的典範。
母親名為蔡白雪,與父親同年出生於金門瓊林,一個出了三位進士而被清朝皇帝賜名的村莊。為了給弟弟念書,母親沒有去上學,成了一輩子務農持家不識字的女性,二十一歲因媒婆牽線嫁給了父親。
婚前他們在各自的村子,經歷了「日本手」、古寧頭大戰,婚後則一起挺過了八二三炮戰。在老家大廳全毀、新婚小姑及其夫婿在炮火身亡後,為躲避戰禍,那一年,一家七口老小逃難到臺灣,從高雄、麻豆、豐原,最後落腳三重埔。
八二三炮戰隔年,二叔續留三重埔,身為長子的父親,帶著一家老小返回老家古寧頭,繼續上山下海養活一家人。在流離和醫療資源匱乏下,我的大姊和二哥因病早逝,父母很少流露他們的傷悲,直到晚年才跟我們說──夢到衣衫襤褸的孩子,拉著父親的衣角要東西吃。從那年起,在父親的指引下,我們找到當年村子外一處無主之地,當初草草掩埋兄姊的可能地點,為從未謀面的兄姊掃墓。
我是在戰後十年出生,排名第八的孩子。金門人說的「戰後」並不是指二戰之後,而是八二三炮戰之後。
古寧頭人有山有海,山指的是貧瘠的旱田,海指的是蚵田。我家的「山」田分散於沙崗、宮口、埔頭邊,約莫有一甲多的貧瘠旱田,這是祖父下南洋到呂宋島當餐廳服務生所掙得的農地;而「海」指的是祖先以花崗石條矗立於潮間帶的石蚵田,是我們主要的蛋白質來源。
戒嚴的海,只有持「下海證」的村民才能通過崗哨下海。氣候尚未劇變的當年,金門的冬天又溼又冷,大人小孩常生凍瘡,冷冽的日子蚵仔最肥美,為配合潮水,父母常常天未亮便得使喚起長著凍瘡的手腳,走過長長的泥灘地,用蚵擎把石蚵敲下來清洗、裝袋,再挑上岸。蚵仔以肩挑或牛車運回家之後,剖蚵是母親、姊姊、奶奶等家中婦女的主要工作,往往剖蚵到很晚,隔天父親才能去市場販賣,那是一種勞動時間很長的生活。
父母的勞動很少可以轉換為金錢,要供應孩子上學的經濟壓力龐大,往往到註冊時還得設法借錢繳孩子的學費。我一直記得父親每天記錄著賣菜、賣蚵的所得,盤算著如何支應一家的生活。那雙粗糙的手、歷經風霜的臉孔及溼透的汗衫,是已過世父親最鮮明的形象之一。待自己當了老師領了薪水,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每次購物時,總是在內心換算,這樣要剖多少斤的蚵仔。
多年之後,我因為見證了臺南七股反濱南工業區、雲林台西反臺塑煉鋼廠 的開發案,才看到臺灣蚵仔的養殖方式,不論是平掛、垂吊或浮棚式,其採收方式比起金門的石蚵要省力多了。在那些時刻,往往更加想起父母的辛勞。
下海的勞務告個段落,父母親接著往旱田𥚃挑水、拔草、抓蟲;下午再下一次田,或者拉著牛車蒐集木麻黃枯枝落葉當燃料,煮豬食。
這些收穫提供了家中基本的食物來源。中、晚餐吃的是地瓜、地瓜籖,偶爾會和著屯放數年的戰備米,配上早上海裡順便抓到的小魚、蟹、自家種的蔬菜。
家中所有孩子都得分擔一些勞動,那是個重男輕女的年代,兩位雙胞胎姊姊,除了山海家務勞動,還要照顧弟妹,因此被迫減少去學校上學的時間。
我不是最懂事、會主動幫忙家務的孩子,但放學後協助農務是基本工作。平日下課後,和哥哥一起去割草餵牛、切牛皮菜、野菜、削地瓜煮豬食,假日在田裡拔草、抓蟲(不太敢抓)。務農是個看天(自然)吃飯,但又是與天對抗的工作,尤其是那拔不盡的野草。
播種季節到了,孩子就跟在父親和耕牛後方,挖個洞播玉米、高粱或者花生的種子;地瓜則是用插技的,等藤蔓長了,需要翻地瓜藤,以避免太多根系長出很多小地瓜;如果是種西瓜和蔬菜,則要從井裡打水,在熱天裡挑個數十擔灌溉在貧瘠的沙地。
為了製作高粱酒而種植的高粱,是家裡每年主要的農事收入,金門軍政府提供了保價收購。當時金門的農業完全沒有機械化,農民靠黃牛犁田,手工播種和收割,然後將收成的高粱穗鋪在馬路上,讓來往的車輛輾壓脫殼。當時的民用車子不多,許多是軍車,對於騎機車的人來說,輪胎輾過高粱很容易打滑,相當危險,直到九○年代才禁止這種做法。
小時候協助務農的辛勞,如今回想,相較於和土地脫節的都市生活,反而是豐富的生命經驗。高粱之外,旱田裡的地瓜是主食,此外還種植著多樣的蔬菜和瓜果,春天種花生、芝麻,夏天是大西瓜、小玉西瓜、香瓜,冬天種大小白菜、牛皮菜……這些務農和種植經驗,讓我每天的飲食和土地之間有很強的連結感。
至今,我記得和父母親相處的幸福時光,是農務勞動後,在傍晚斜照的溫暖陽光下,父親走路牽著牛車,讓母親坐牛車上一起走回家,臉上洋溢著笑容的畫面。
往往在工作繁重或面對困頓之時,都會想到父母歷經戰亂貧苦、艱苦辛勞地持家,就覺得自己的狀態不算什麼。久而久之,成了我在困境中最大的內在支持。
「一戰古寧頭,再戰大二膽,同仇敵愾,消滅匪黨,光輝的八二三!」這是一九七七年三臺聯播連續劇《風雨生信心》同名主題曲。
古寧頭是我的老家,是一個以戰爭聞名,被炮彈洗禮最慘烈的村莊。村子裡大抵都是閩式建築,即使到了今天仍是如此。
沿著家裡的周圍繞一圈,每棟舊房子都可以看到戰爭的印記。村莊裡留著許多戰後重建或修補的建築樣式,用海砂和稀薄的水泥粗糙翻模印製的屋瓦和空心磚,窗戶用上木頭和鋼筋,或者水泥印的花磚,大小補丁和堆疊各種材質的牆面,視覺上很美,但每道牆都是悲傷的故事。
村莊裡除了房子,最突兀的是為了躲炮彈用的防空洞。 許多金門人家裡就有防空洞,或者幾戶人家共同使用一個防空洞。
我家的防空洞已在二十多年前房子改建時填掉,如今沒法再進入重新感受。有一天,我和阿母、三叔、哥哥重新推敲家裡的防空洞,討論兩個晚上後,拼湊出這樣的故事。
防空洞開挖的時間應是在一九五四年九三炮戰 後,這個克難的防空洞,讓家人挺過了八二三炮戰 及之後延續二十年的「單打雙不打」。
防空洞長約一.五公尺、寬約一.一公尺,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要擠上八、九個或者更多人,不僅擁擠而且十分潮溼,常常要頻繁地把地下湧水舀出去,在那個年代每逢單日就要躲進這個安全的避難所。
每一個島嶼都有屬於它的命運,但是島嶼的命運通常不由自主,像是大洋中的小船,常常被大船駛過的巨浪攪得翻天覆地。
金門,距離臺灣島最近的距離是兩百一十公里,而距離中國最近的距離僅一.八公里。關於這個島嶼,最深的烙印是戰爭,以及最堅硬的花崗岩,最貧瘠的沙地與紅赤土。我的老家在金門西北角的古寧頭,已有六百多年歷史,村子分為南山、北山、林厝三個聚落,絕大部分都姓李,彼此都有血緣關係。從明朝以來,村子外海就上演大規模海戰,清朝出武將打海盜,子民除了務農,也擅於操舟航海,近代則是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的交戰區。
第二次國共戰爭,奠下臺海兩岸分治的一九四九年古寧頭大戰, 共軍指揮所就在古寧頭北山村,距離我家僅約兩百公尺,村子裡曾發生了激烈的巷戰,如今滿是彈孔的古厝已成觀光景點。當年不滿二十歲的父親和許多金門的男性一樣,被軍隊拉夫協助挖壕溝、埋屍體,後來共產黨打輸了,金門成為國民黨軍隊──中華民國的統治區,古寧頭成了一個被軍營包圍的村莊,古老的閩南建築牆上,到處是「殺朱拔毛」、「反共抗俄」的口號。
古寧頭大戰之後,金門開始實施「戰地政務」, 這意味人們所有的日常生活都軍事化了。
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是集軍、政、國民黨部的最高領導人,金門人形容是「皇帝」。縣長是少將或上校擔任,沒有地方議會;人民和軍人犯了罪都是接受軍法審判,晚上實施宵禁,燈火管制,往來臺灣和金門比照出國要入出境管制;臺灣和金門之間實施電信管制,只能寫信和發電報,沒有電話;金門、馬祖地區發行專用的貨幣,實施金融管制;五戶連保,互相監視;電器、攝影器材、球類等都是違禁品。
國民黨為什麼在金門實施全面的軍事化?回顧國際局勢和兩岸關係,發現並非中共的軍事威脅增加,而是蔣中正要透過在金門大量駐軍,提升臺灣在國際冷戰局勢中的地位,尤其是爭取美國的支持。然而,事實證明這個策略並沒有效果,一九七一年臺灣退出聯合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的唯一代表,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逐漸不被國際承認,一九七九年美國和中共建交。此意味著,在金門實施的軍事化,使得金門人做出無謂的犧牲,連作為工具的效果都沒有達成。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對金門炮擊,連續六個星期的猛烈炮擊,大約五十萬發炮彈落在面積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島嶼上,造成一百四十名平民死亡,數百人受傷,數千棟民房損毀。根據史學家的研究,毛澤東發動戰爭的原因可能是「向美國警告、向蘇聯示威,或是動員中國人民」,但很確定並不是想拿下金門,因為金門是臺灣與中國大陸相連的象徵,一旦中華人民共和國占領金門,就是邁向兩個中國的第一步。
因為中國一個獨裁者的意志,金門成為炮火蹂躪的戰區,古寧頭是被炮擊最嚴重的村莊,我家大廳毀於炮火,家人堆置蚵殼於防空洞上方試圖阻隔炮火,冒死去沙崗的田裡撿拾地瓜勉強存活。母親說,炮彈落在雙鯉湖的聲音好像在舂麥(tsing-be̍h)。我只有一位姑姑,只聽過卻沒見過。從小聽父母口述,八二三炮戰期間,新婚才三個月的姑丈和懷有身孕的姑姑在田裡工作,姑丈中炮後,姑姑前去相救而雙亡。
八二三炮戰後到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之前,國、共又維持了長達二十一年「單打雙不打」的交戰狀態,只要是日曆上的單號日,共軍會在傍晚時刻打炮彈過來,國軍隨後回擊,在這個島嶼的人們,也被迫配合戰爭狀態。那段期間實施的是獨立於臺灣的「戰地政務」,生活裡有許多禁忌。
一九六八年,我出生在什麼樣的時刻?前一年北山播音站完工, 後一年慈堤完工,古寧頭灣成了慈湖,國民黨軍隊在古寧頭的軍事布署已經完備。
當時,村莊四周都是軍營。最高峰時,島嶼上住著六至十萬名軍人,人數足足是原有金門人口的二至三倍。
我們當小孩的,家裡不可以有球類,不能放風箏,當然也不能亂說話,大人不斷告誡亂說話會被抓去關。但很「炫」的是,從小我們的玩具槍就是真槍,因為年滿十八歲以上的男人就要當民防隊員,會分配到一把步槍隨時放在家中,我們會幫忙爸爸保養那把木頭柄單發射擊子彈的三○步槍,當然也會拿來練習扣扳機。我讀國中時,所有男同學都被編入「幼獅隊」, 在全島發布雷霆演習的時候負責巡邏和守路口,和同學一起抓逃兵。
十歲以前,我和島上的居民一同過著「單打雙不打」的炮彈人生,每逢日曆上印著一、三、五、七、九單日號碼的傍晚,我和家人就得點上蠟燭,進入父母親臥室裡的地下防空洞躲炮彈,等國共雙方的炮火結束,我和許多小朋友一樣,會依據當晚炮彈可能的落點,拿著手電筒去找炮彈破片,賣給雜貨店換取一點零嘴。
戰爭炮火成了日常,當時的我並不知道什麼是恐懼,但每次母親到廚房裡祭拜姑姑的牌位時,心裡總有莫名的感覺,也不曉得是恨或者痛。中年之後想到這件事,卻不由自主地流淚。
戰爭改變的,還有白馬。我家有一隻白馬,但在八二三炮戰時被炮彈傷到肚子,痛苦哀鳴,爸爸只好委託鄰居結束牠的生命,然後和鄰居分食。我家還有一隻白沙驢,被阿兵哥(國民黨軍隊)牽走(說好聽是徵召)載彈藥。於是,白馬和驢子成了家裡的傳說。
父親名李沃沛,一九三二年生,是古寧村子裡少數念過私塾的「知識分子」。家裡除了《金門日報》,還訂了《中國時報》。農忙回家後,父親每天都戴著老花眼鏡在大廳前的石砛上,靠著天井的自然光讀報。在這時刻裡,常見鄰居捧著來自臺灣的孩子或南洋親戚的來信,請父親讀信、回信。但是,父親對於當時由黨國掌控的宗族活動,只是被動的參與,鮮少與地方上鑽營的頭人來往。正直的父親所展現的勞動者和知識分子綜合的形象,成了我畢生的典範。
母親名為蔡白雪,與父親同年出生於金門瓊林,一個出了三位進士而被清朝皇帝賜名的村莊。為了給弟弟念書,母親沒有去上學,成了一輩子務農持家不識字的女性,二十一歲因媒婆牽線嫁給了父親。
婚前他們在各自的村子,經歷了「日本手」、古寧頭大戰,婚後則一起挺過了八二三炮戰。在老家大廳全毀、新婚小姑及其夫婿在炮火身亡後,為躲避戰禍,那一年,一家七口老小逃難到臺灣,從高雄、麻豆、豐原,最後落腳三重埔。
八二三炮戰隔年,二叔續留三重埔,身為長子的父親,帶著一家老小返回老家古寧頭,繼續上山下海養活一家人。在流離和醫療資源匱乏下,我的大姊和二哥因病早逝,父母很少流露他們的傷悲,直到晚年才跟我們說──夢到衣衫襤褸的孩子,拉著父親的衣角要東西吃。從那年起,在父親的指引下,我們找到當年村子外一處無主之地,當初草草掩埋兄姊的可能地點,為從未謀面的兄姊掃墓。
我是在戰後十年出生,排名第八的孩子。金門人說的「戰後」並不是指二戰之後,而是八二三炮戰之後。
古寧頭人有山有海,山指的是貧瘠的旱田,海指的是蚵田。我家的「山」田分散於沙崗、宮口、埔頭邊,約莫有一甲多的貧瘠旱田,這是祖父下南洋到呂宋島當餐廳服務生所掙得的農地;而「海」指的是祖先以花崗石條矗立於潮間帶的石蚵田,是我們主要的蛋白質來源。
戒嚴的海,只有持「下海證」的村民才能通過崗哨下海。氣候尚未劇變的當年,金門的冬天又溼又冷,大人小孩常生凍瘡,冷冽的日子蚵仔最肥美,為配合潮水,父母常常天未亮便得使喚起長著凍瘡的手腳,走過長長的泥灘地,用蚵擎把石蚵敲下來清洗、裝袋,再挑上岸。蚵仔以肩挑或牛車運回家之後,剖蚵是母親、姊姊、奶奶等家中婦女的主要工作,往往剖蚵到很晚,隔天父親才能去市場販賣,那是一種勞動時間很長的生活。
父母的勞動很少可以轉換為金錢,要供應孩子上學的經濟壓力龐大,往往到註冊時還得設法借錢繳孩子的學費。我一直記得父親每天記錄著賣菜、賣蚵的所得,盤算著如何支應一家的生活。那雙粗糙的手、歷經風霜的臉孔及溼透的汗衫,是已過世父親最鮮明的形象之一。待自己當了老師領了薪水,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每次購物時,總是在內心換算,這樣要剖多少斤的蚵仔。
多年之後,我因為見證了臺南七股反濱南工業區、雲林台西反臺塑煉鋼廠 的開發案,才看到臺灣蚵仔的養殖方式,不論是平掛、垂吊或浮棚式,其採收方式比起金門的石蚵要省力多了。在那些時刻,往往更加想起父母的辛勞。
下海的勞務告個段落,父母親接著往旱田𥚃挑水、拔草、抓蟲;下午再下一次田,或者拉著牛車蒐集木麻黃枯枝落葉當燃料,煮豬食。
這些收穫提供了家中基本的食物來源。中、晚餐吃的是地瓜、地瓜籖,偶爾會和著屯放數年的戰備米,配上早上海裡順便抓到的小魚、蟹、自家種的蔬菜。
家中所有孩子都得分擔一些勞動,那是個重男輕女的年代,兩位雙胞胎姊姊,除了山海家務勞動,還要照顧弟妹,因此被迫減少去學校上學的時間。
我不是最懂事、會主動幫忙家務的孩子,但放學後協助農務是基本工作。平日下課後,和哥哥一起去割草餵牛、切牛皮菜、野菜、削地瓜煮豬食,假日在田裡拔草、抓蟲(不太敢抓)。務農是個看天(自然)吃飯,但又是與天對抗的工作,尤其是那拔不盡的野草。
播種季節到了,孩子就跟在父親和耕牛後方,挖個洞播玉米、高粱或者花生的種子;地瓜則是用插技的,等藤蔓長了,需要翻地瓜藤,以避免太多根系長出很多小地瓜;如果是種西瓜和蔬菜,則要從井裡打水,在熱天裡挑個數十擔灌溉在貧瘠的沙地。
為了製作高粱酒而種植的高粱,是家裡每年主要的農事收入,金門軍政府提供了保價收購。當時金門的農業完全沒有機械化,農民靠黃牛犁田,手工播種和收割,然後將收成的高粱穗鋪在馬路上,讓來往的車輛輾壓脫殼。當時的民用車子不多,許多是軍車,對於騎機車的人來說,輪胎輾過高粱很容易打滑,相當危險,直到九○年代才禁止這種做法。
小時候協助務農的辛勞,如今回想,相較於和土地脫節的都市生活,反而是豐富的生命經驗。高粱之外,旱田裡的地瓜是主食,此外還種植著多樣的蔬菜和瓜果,春天種花生、芝麻,夏天是大西瓜、小玉西瓜、香瓜,冬天種大小白菜、牛皮菜……這些務農和種植經驗,讓我每天的飲食和土地之間有很強的連結感。
至今,我記得和父母親相處的幸福時光,是農務勞動後,在傍晚斜照的溫暖陽光下,父親走路牽著牛車,讓母親坐牛車上一起走回家,臉上洋溢著笑容的畫面。
往往在工作繁重或面對困頓之時,都會想到父母歷經戰亂貧苦、艱苦辛勞地持家,就覺得自己的狀態不算什麼。久而久之,成了我在困境中最大的內在支持。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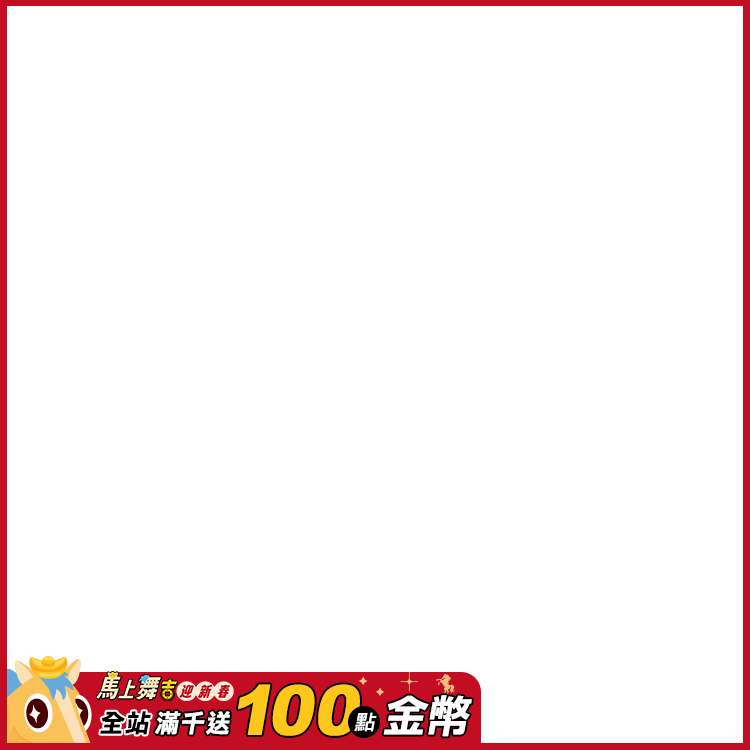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