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奧義:解碼家族書寫的16種視角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 每一種敘事、每一部作品,都可能纏繞家族書寫的幽魂 ★
★ Openbook年度好書獎得主 黃宗潔 洞澈真情之作 ★
「在各種類型的作品中,看見家族線索如何如影隨形地纏繞著我們。
一個人的原生家庭,可以是祝福,也或許是詛咒,
但無論何者,都有從不同眼光去看待的可能。」
——黃宗潔
▌ 家,無所不在
在著重身分認同、心靈療癒等時代趨勢下,家族書寫與相關議題愈受矚目,作品或意在自我追尋,或以建構家族圖像為用心,或處理親緣關係並療癒創傷,或勾勒移民等多元族群處境……。然除了傳統定義下的家族書寫,在許多跨越類型的作品中,亦往往能一窺「家」在生命軌跡中所留下的深淺刻度。
而一旦家族書寫被視為無非「傷口的挖掘」、「親情綑綁的背反」或「闡述議題的方式」,停留在僅是自我揭露寫作型態的認知,亦可能限制了作品與讀者對話的更多可能性。長期關注此領域的黃宗潔,意欲超越文類框架,在多部主題各異、風格多樣的著作中,揭示「家」這個精神與物質單位,無所不在的影響。
▌ 首部脈絡性梳理家族書寫的專書
本書以「鬆動讀者對家族書寫的既定想像,擴大對家的定義與理解」為核心,透過姓名、性別、飲食、歷史、物件、非典型家庭、動物、科幻、教養、失智、創傷、犯罪、自然、空間、城市、跨域等十六個面向,以及貫穿每篇意旨的關鍵詞,剖析備受討論且擁有廣大讀者的中外經典著作。
談及的作品包括:韓江《永不告別》、吳明益《單車失竊記》、蜜雪兒.桑娜《沒有媽媽的超市》、陳思宏《鬼地方》、是枝裕和《小偷家族》、洪愛珠《老派少女購物路線》、石黑一雄《克拉拉與太陽》、廖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李潔珂《山與林的深處》、馬尼尼為《今生好好愛動物》等三十二部核心文本,進而廣及數十部延伸書籍,橫跨小說、散文、自然、藝術、社會紀實等多元主題類型。
▌ 透過他人的心湖,看見自己的倒影
黃宗潔犀敏捕捉個人成長經歷,以及與親愛之人的記憶,如何層層疊疊地沉積在生命中,進而化為語言文字。而透過這些觸動人心的曲折故事,引起共感的經驗,我們得以「看見自己的倒影」,同時重整記憶,安頓靈魂,進而對自身、對家族、對他人有更多的理解,以及寬容。
此書不是單向書評、不是學術論文、不只是作品導讀,也並非評述合集。本書可以是主題閱讀的指南,尋求情感撫慰的依憑;同時,亦可以是開啟對話的起點,思辨諸多文化與社會議題的專書。
內容選錄
★〔姓名篇〕 「幾位司武家族成員對原生家庭的感受,卻足以讓我們看到姓氏作為『家』這個單位的辨識符號,可以是凝聚認同感的來源,也可能是『如怪物般吞噬成員』的深淵。」(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
★〔性別篇〕 「『與父親在性取向上的重疊, 此刻讓我感到羞愧,可恥,甚至憤怒。』令他羞愧的不是同志身分,而是與父親成為同類人。」(白樵《風葛雪羅》)
★〔飲食篇〕 「洪愛珠的飲食書寫,是從個人層面出發,想盡辦法在當下,把日子算上親愛之人的份額繼續過下去的方式。」(洪愛珠《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歷史篇〕 「小說家保存了一整座森林的記憶,保存了樹與大象的記憶,當然,也包括了無數家庭的記憶。」(吳明益《單車失竊記》)
★〔非典型家庭篇〕 「廖瞇並非試著剝除滌身上的繭,相反地,她是在整理纏繞在自身與家人身上的絲線。」(廖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動物篇〕 「這些無家的貓與狗故事,某部分其實埋藏著,她難以梳理清楚的,關於家、故鄉、情感的答案。」(馬尼尼為《今生好好愛動物》)
★〔教養篇〕 「對身為天文學家的他來說,『我的兒子是一個我想都不敢想要看透的袖珍宇宙』。沒有任何一個疾病標籤可以涵蓋他獨一無二的人格特質。」(理察・鮑爾斯《困惑的心》)
★〔失智篇〕 「井上靖回頭看見母親努力想將和服衣襟拉正的身影。就算所有經驗記憶都沉沒在冰凍的記憶湖沼,身而為人的自尊心,依然會是他們緊緊懷揣的珍貴物事。這個需求很容易被周遭的人所遺忘。」(井上靖《我的母親手記》)
★〔自然篇〕 「難以解釋的身分,讓她意識到自己承繼的不是臉孔,也不是語言能力,而是流離的感受。」(李潔珂《山與林的深處》)
★〔空間篇〕 「唯有透過象徵性的送機,讓父親『再死一次』,才能真正地讓他在文字中安息。(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
★〔跨域篇〕 「『無法處處是家』和『處處可以為家』,都是我們在生命的動態演變中,疊加新變異的過程,在祖先或留下或離開的故土,加上新的足跡。」(阿馬蒂亞.沈恩《家在世界的屋宇下》)
★ Openbook年度好書獎得主 黃宗潔 洞澈真情之作 ★
「在各種類型的作品中,看見家族線索如何如影隨形地纏繞著我們。
一個人的原生家庭,可以是祝福,也或許是詛咒,
但無論何者,都有從不同眼光去看待的可能。」
——黃宗潔
▌ 家,無所不在
在著重身分認同、心靈療癒等時代趨勢下,家族書寫與相關議題愈受矚目,作品或意在自我追尋,或以建構家族圖像為用心,或處理親緣關係並療癒創傷,或勾勒移民等多元族群處境……。然除了傳統定義下的家族書寫,在許多跨越類型的作品中,亦往往能一窺「家」在生命軌跡中所留下的深淺刻度。
而一旦家族書寫被視為無非「傷口的挖掘」、「親情綑綁的背反」或「闡述議題的方式」,停留在僅是自我揭露寫作型態的認知,亦可能限制了作品與讀者對話的更多可能性。長期關注此領域的黃宗潔,意欲超越文類框架,在多部主題各異、風格多樣的著作中,揭示「家」這個精神與物質單位,無所不在的影響。
▌ 首部脈絡性梳理家族書寫的專書
本書以「鬆動讀者對家族書寫的既定想像,擴大對家的定義與理解」為核心,透過姓名、性別、飲食、歷史、物件、非典型家庭、動物、科幻、教養、失智、創傷、犯罪、自然、空間、城市、跨域等十六個面向,以及貫穿每篇意旨的關鍵詞,剖析備受討論且擁有廣大讀者的中外經典著作。
談及的作品包括:韓江《永不告別》、吳明益《單車失竊記》、蜜雪兒.桑娜《沒有媽媽的超市》、陳思宏《鬼地方》、是枝裕和《小偷家族》、洪愛珠《老派少女購物路線》、石黑一雄《克拉拉與太陽》、廖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李潔珂《山與林的深處》、馬尼尼為《今生好好愛動物》等三十二部核心文本,進而廣及數十部延伸書籍,橫跨小說、散文、自然、藝術、社會紀實等多元主題類型。
▌ 透過他人的心湖,看見自己的倒影
黃宗潔犀敏捕捉個人成長經歷,以及與親愛之人的記憶,如何層層疊疊地沉積在生命中,進而化為語言文字。而透過這些觸動人心的曲折故事,引起共感的經驗,我們得以「看見自己的倒影」,同時重整記憶,安頓靈魂,進而對自身、對家族、對他人有更多的理解,以及寬容。
此書不是單向書評、不是學術論文、不只是作品導讀,也並非評述合集。本書可以是主題閱讀的指南,尋求情感撫慰的依憑;同時,亦可以是開啟對話的起點,思辨諸多文化與社會議題的專書。
內容選錄
★〔姓名篇〕 「幾位司武家族成員對原生家庭的感受,卻足以讓我們看到姓氏作為『家』這個單位的辨識符號,可以是凝聚認同感的來源,也可能是『如怪物般吞噬成員』的深淵。」(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
★〔性別篇〕 「『與父親在性取向上的重疊, 此刻讓我感到羞愧,可恥,甚至憤怒。』令他羞愧的不是同志身分,而是與父親成為同類人。」(白樵《風葛雪羅》)
★〔飲食篇〕 「洪愛珠的飲食書寫,是從個人層面出發,想盡辦法在當下,把日子算上親愛之人的份額繼續過下去的方式。」(洪愛珠《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歷史篇〕 「小說家保存了一整座森林的記憶,保存了樹與大象的記憶,當然,也包括了無數家庭的記憶。」(吳明益《單車失竊記》)
★〔非典型家庭篇〕 「廖瞇並非試著剝除滌身上的繭,相反地,她是在整理纏繞在自身與家人身上的絲線。」(廖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動物篇〕 「這些無家的貓與狗故事,某部分其實埋藏著,她難以梳理清楚的,關於家、故鄉、情感的答案。」(馬尼尼為《今生好好愛動物》)
★〔教養篇〕 「對身為天文學家的他來說,『我的兒子是一個我想都不敢想要看透的袖珍宇宙』。沒有任何一個疾病標籤可以涵蓋他獨一無二的人格特質。」(理察・鮑爾斯《困惑的心》)
★〔失智篇〕 「井上靖回頭看見母親努力想將和服衣襟拉正的身影。就算所有經驗記憶都沉沒在冰凍的記憶湖沼,身而為人的自尊心,依然會是他們緊緊懷揣的珍貴物事。這個需求很容易被周遭的人所遺忘。」(井上靖《我的母親手記》)
★〔自然篇〕 「難以解釋的身分,讓她意識到自己承繼的不是臉孔,也不是語言能力,而是流離的感受。」(李潔珂《山與林的深處》)
★〔空間篇〕 「唯有透過象徵性的送機,讓父親『再死一次』,才能真正地讓他在文字中安息。(郝譽翔《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
★〔跨域篇〕 「『無法處處是家』和『處處可以為家』,都是我們在生命的動態演變中,疊加新變異的過程,在祖先或留下或離開的故土,加上新的足跡。」(阿馬蒂亞.沈恩《家在世界的屋宇下》)
目錄
目次
前言 成為自己生命的讀者
【輯一.記憶刻度】
〔姓名篇〕禮物——《同名之人》《姓司武的都得死》
〔性別篇〕角色——《我的蟻人父親》《暗房裡的男人》
〔飲食篇〕軌跡——《老派少女購物路線》《沒有媽媽的超市》
〔歷史篇〕金繼——《永不告別》《單車失竊記》
【輯二.心之倒影】
〔物件篇〕意義之堆——《收藏無物》《物盡其用》
〔非典型家庭篇〕選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小偷家族》
〔動物篇〕我們——《摯友》《今生好好愛動物》
〔科幻篇〕情感價值——《人工少女》《克拉拉與太陽》
【輯三.背離親緣】
〔教養篇〕語言——《困惑的心》《母愛有多難》
〔失智篇〕迷路——《我的母親手記》《病非如此》
〔創傷篇〕經驗詮釋——《家鎖》《隱谷路》
〔犯罪篇〕崩壞時刻——《我的孩子是兇手》《鬼地方》
【輯四.沿途行跡】
〔自然篇〕共棲——《雲山》《山與林的深處》
〔空間篇〕出境——《奶奶的夏威夷祭祀》《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
〔城市篇〕地差感——《想像一座城市》《廢墟的故事》
〔跨域篇〕歸屬——《無國籍》《入境大廳》
前言 成為自己生命的讀者
【輯一.記憶刻度】
〔姓名篇〕禮物——《同名之人》《姓司武的都得死》
〔性別篇〕角色——《我的蟻人父親》《暗房裡的男人》
〔飲食篇〕軌跡——《老派少女購物路線》《沒有媽媽的超市》
〔歷史篇〕金繼——《永不告別》《單車失竊記》
【輯二.心之倒影】
〔物件篇〕意義之堆——《收藏無物》《物盡其用》
〔非典型家庭篇〕選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小偷家族》
〔動物篇〕我們——《摯友》《今生好好愛動物》
〔科幻篇〕情感價值——《人工少女》《克拉拉與太陽》
【輯三.背離親緣】
〔教養篇〕語言——《困惑的心》《母愛有多難》
〔失智篇〕迷路——《我的母親手記》《病非如此》
〔創傷篇〕經驗詮釋——《家鎖》《隱谷路》
〔犯罪篇〕崩壞時刻——《我的孩子是兇手》《鬼地方》
【輯四.沿途行跡】
〔自然篇〕共棲——《雲山》《山與林的深處》
〔空間篇〕出境——《奶奶的夏威夷祭祀》《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
〔城市篇〕地差感——《想像一座城市》《廢墟的故事》
〔跨域篇〕歸屬——《無國籍》《入境大廳》
試閱
內文精摘
〔姓名篇〕
禮物
◎《同名之人》,鍾芭.拉希莉著,彭玲嫻譯,天培,二○○四
◎《姓司武的都得死》,譚劍著,蓋亞,二○二三
二○二一年,台灣某間連鎖壽司店推出限時優惠方案,若名字與鮭魚同音即可享有折扣,名為「鮭魚」則全桌免費招待。業者顯然預期一般人不會以鮭魚為名,免費僅是招徠顧客與製造話題的行銷手法,不料卻有三百多名消費者前往戶政事務所改名,一時之間各種姓氏的鮭魚盡出,還有高價鮭魚、大口吃鮭魚、同鮭魚盡、鮭魚之夢等創意姓名,命名彷彿成了一場「鮭魚遊戲」。此一被稱為「鮭魚之亂」的事件不只登上國際新聞版面,後續也引發了對命名權、改名權的討論。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們既然擁有自己的姓名,那麼姓名的「使用方式」自然也應該完全操之在我,「鮭魚之亂」中動輒將名字改為四、五十個字,字數多到身分證幾乎塞不下的案例,想必抱著這樣的態度。改名對他們而言,形同在網路世界的不同平台取暱稱。然而,我們可以擁有無數個代號來維護自己的網路匿名性,現實世界卻無法如此,否則法律也無須對改名次數進行規範。至於利用免費吃到飽的福利,以數百元的價格組團用餐再收取餐費的少數「鮭魚」,將改名一事轉化為商業行為,名字在此模式中形同可以獲利的「商品」。從這個角度來看,「鮭魚之亂」不僅僅是一場令廠商始料未及的風波,或茶餘飯後的有趣話題,而是隱含著我們看待姓名的態度,以及一個深層的提問:我們的名字,屬於我們自己嗎?
無論法律如何規定改名的次數與程序,或是不同國家對姓名看法的文化差異,一個跨文化的事實是,我們日後想幫自己取多少筆名、藝名、小名都好,人生的第一個名字必然是被決定的。因此,它是一份禮物,而且是生命中第一份禮物。名字承載著命名者對新生兒的期盼與祝福,但它也一如所有的禮物,送禮者與收受者之間,對價值的認知、喜好與感受都未必相同。與其他禮物唯一的差異,或許在於就算不喜歡,它也無法轉贈。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同名之人》(The Namesake)與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儘管在故事風格與小說類型上都大相逕庭,卻同樣能帶我們看到姓名在生命中,作為一份禮物(或負資產?)的角色與意義。
——
●名字是一道咒語或一個祝福
「這世上最短的咒正是『名』。所謂咒,簡單說來就是束縛。要知道,名稱正是束縛事物本質的一種東西。」《同名之人》裡的主角果戈理,若是讀到夢枕獏在《陰陽師》中透過安倍晴明之口說出的這段話,想必深有同感。這部處理兩代印裔美籍移民人生的小說,深刻細膩地透過一個糾結一生的名字,突顯出姓名作為符號,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遠比我們意識到的更重要。
果戈理這個名字,原是一場文化衝擊下的意外產物。年輕的移民夫婦阿碩可與愛希瑪依照傳統,將新生兒的命名權交託給愛希瑪的外婆。在那個仍然依賴電報與信件往返的年代,寫上小嬰兒名字的信,卻未能及時在他出生前抵達。儘管如此,他們並不焦慮,因為根據孟加拉的命名規則,每個人都有兩個名字,一個乳名,一個學名。學名是長大之後在正式場合使用,對於襁褓中的嬰兒來說,他只需要父母長輩表達親暱與祝福的乳名。問題是,在美國,嬰兒若沒有名字,就無法開立出生證明,也無法出院。
情急之下,阿碩可想起一個無懈可擊的名字——在火車事故時,從他緊握的手中掉落,讓他得以被搜救人員發現,救了他一命的那本小說,作者的名字,果戈理。愛希瑪同意了,因為她知道,「這名字代表的不只是她兒子的生命,也是她丈夫的生命。」那是一個父親送給兒子的第一份禮物。
對於這份禮物,年幼的果戈理並非一開始就感受到它的特別之處,卻也並不排斥。儘管他從來不曾在那些印著名字的紀念品上找到自己的名字,但他會在路牌上看到GO LEFT、GO RIGHT,遇見這些「Gogol 的片段」是種樂趣,也讓他得以指認自己的一部分。名字所帶來的種種認同困惑與困擾,是從進入學校這個小型社會才出現的。
好不容易選定了一個完美的孟加拉學名「倪克熙爾」,果戈理的父母卻再次在命名這件事情上,意識到移民生活是一場永恆的,文化與文化之間折衝磨合的過程。幼稚園無法理解父母為何要使用一個不存在於出生證明上,既非中間名也不是暱稱的名字。愛希瑪與阿碩可只能無奈接受父母的意願被學校無視的現實。至於果戈理,那卻是他與這個名字磨合的真正起點。他不明白人為何需要兩個名字,因此在幼稚園校長詢問時,斷然放棄了陌生的「倪克熙爾」之名,但慢慢地,他發現除了自己之外,沒有人叫做果戈理。他討厭老師點名時對自己名字的遲疑,更無法想像追求女孩時在浪漫氛圍中說出「嗨,我是果戈理。」名字這個沒有形體的東西甚至「會對他的身體造成不適,像襯衫上扎著皮膚的標籤,永恆不能褪下。」
●藉以指認「我是誰」與「我不是誰」
對於許多動輒「撞名」的人來說,果戈理的煩惱看似「奢侈」,更何況,獨一無二的名字,不是更能滿足我們期待與眾不同的心理需求?但自我認同其實是不斷在獨特性與歸屬感的天平間擺盪挪移、尋找位置的過程。果戈理這個過度特別的名字,反而令他在同儕中感到格格不入。更困擾的是,為此他必須不斷解釋:這個字在印度文中沒有任何意義,而是與他毫無關係的俄文。相對於那些連結著美好語意的傳統名字,姓名對他的意義與其說指認了「我是誰」,不如說是「我不是誰」——不是印度人,也不是美國人,當然更不可能是俄國人。甚至連他的姓名來源,那位同名之人,作家果戈理,也不叫果戈理——那是他的姓而非名。
身為移民後裔的認同困惑與孤獨感,被果戈理這個獨一無二的名字,徹底地具象化了。果戈理決定成為他童年時拒絕的那個名字,倪克熙爾。這並未讓他的生活顯得比較輕易,他依然在旁人討論姓名時感到不自在,更諷刺的是,他最後選擇的婚姻對象,是從小就認識,因此知道他本名的茉淑蜜——一個同樣苦於自己名字既罕見又難以發音的女孩。
鍾芭.拉希莉既未簡化,也未誇大姓名的重要性。果戈理的婚姻當然不只是基於名字的相似性,但他確實在某次朋友聚會後,意識到「吸引他倆結合的奇特情愫」,與這孤單的,未能輕易找到同名之人的認同感有關,一如他童年時總會留意墓園裡那些古怪又古老的名字,並且被那些擁有「過時的,無法想像的名字的人」深深吸引。他所依附的認同對象,從來不是印度人或美國人這樣的族群劃分,而是那些與他一樣,落單的、無法被妥善安放在群體中的,畸零者。
這世界上並不存在「完美的名字」,認同自己的姓名,當然也不至於就能擁有「完美的人生」。當父親終於告訴果戈里命名的源由,同樣不會讓彆扭、厭棄了一輩子的名字,搖身一變成為帶著光圈的名牌。果戈理三個字依然如同某個應該被隱藏的汙點,一場災難的分身與見證,但他對這個被自己放棄的名字,從此多了一份歉疚感。
當歉疚感悄悄萌芽,當他明白了這個在印度文與英文裡都沒有任何意義的名字,在父親的字典裡,卻意味著重生與祝福,他看待自己、看待父親、看待果戈理三個字的眼光都已不同。禮物之為禮物,也唯有在收禮者意識到那作為一份禮物時,意義才得以被指認。
●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進一步來說,姓名這個符號,可能是所有身分標籤中,最複雜的一種。在公開與隱匿之間,它以全稱、敬稱、暱稱、化名等各式各樣的形式,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名字作為禮物的意義,不僅止於命名者與被命名的關係,在某些文化或情境中,分享自己的名字,亦具有託付信任與交出一部分自己的象徵意義。韓劇《魷魚遊戲》裡,在殘酷的生存遊戲中一步步踏入死亡陷阱的參賽者,就被剝奪了姓名,只以去人性化的編號受到掌控。女主角姜曉與她編號240的同伴智英,在死亡面前,最後唯一能交換的珍貴物事,僅僅剩下彼此的姓名。這令人動容的一幕,可說是姓名作為禮物的最好彰顯。
至於村上春樹《東京奇譚集》裡那隻愛偷名字的「品川猴」,更說出「在這同時,也把附著在名字上的負面要素,多少也帶走一些」的話,同樣暗示名字既是「身分」,也作為某種「分身」的意義。
〈品川猴〉裡另一個有趣的細節,是主角婚後覺得一一向客戶通知自己改姓太麻煩了,在職場上仍保留婚前的姓名,發現有時會突如其來地遺忘姓名之後,她去珠寶店訂購了一個刻上「安藤(大澤)美月」的銀手鐲來提醒自己,就像寵物項圈的概念一樣。「安藤(大澤)」的身分,突顯出婚後冠上夫姓的情況,讓女性需要經歷一段重新適應自己新姓名的過程。儘管未必每個人都會為此困擾,卻提醒我們鑲嵌在身分符號之中的姓氏,作為「家庭/家族單位」的意義遠大於代表「個人」。這是何以傳統婚宴場合,餐廳往往會掛上「X府喜宴」或「XX聯姻」標語,而非新人的名字,隱然標誌著婚姻作為兩個家族而非兩個個體結合的現實。
正因姓氏作為一個集體符號,雖說同姓三分親,但除了罕見姓氏,一般人對於「同姓之人」通常不會產生特別親近的感受。姓氏帶來的苦惱除非特殊狀況(例如傳統社會對同姓婚姻的反對),否則不會像名字這種更具個別性的符號一般讓人念茲在茲。但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這部小說,卻透過一個虛構的滅族式謀殺案,對姓氏背後所連結的,「家」與「家族」的概念進行了反思。
●姓氏是斬斷不了的親緣束縛
「姓司武的都得死」是個奇特的謀殺委託案,雖然不少人在結怨時會以對方全家作為咒罵的對象,但真要實際執行,即使以「全世界加起來只有五十多個成員」來說,也是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暗殺任務。但譚劍賦予這個虛構姓氏一個「香港限定」的獨特設定——他們是居住在大嶼山圍村的原居民。四散的家族成員有一個合理與必要的聚集契機,就是三年一次的家祭。這讓職業殺手的「工作難度」瞬間減輕不少。一場大規模的集體毒殺案,就成為小說驚人的開場序曲。
香港的圍村有其非常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傳統,相對也更父權中心。根據「丁屋政策」,新界原居民的男丁只要年滿十八歲,即可申請建造一間三層以下、每層七百平方呎的丁屋,無須向政府繳付地價。小說裡的司武家族成員,單是這被動收入已可不愁吃穿,每個月都有豐厚的生活津貼。姓氏對他們來說,確實如同一份權利與禮物,尤其是男性成員。當然,對那些只因同姓就莫名枉死的人來說,司武這個姓氏卻是不折不扣的負資產。
既然是推理小說,故事最後自然解釋了兇手要殺掉整個家族的動機,但謎團的設計並非本文要討論的重點,這部小說最吸引人之處,事實上也不在於那關鍵的動機與解謎的趣味,而是作者在〈後記〉提到的,「活在一個丁權家族裡各成員的感受。」幾位倖存者多半在情感上或生活上與家族疏離,卻又在經濟上或心理上被這個姓氏束縛著。
活得像個浪子的志義,自嘲名字中英夾雜、不中不西:「志」來自族譜輩分,「義」是家族天主教信仰的影響,「justice」、「faith」、「charity」這些單字被直接當成正式英文名,印在身分證上。但當他說出:「名字取得亂七八糟,反映那些人的想法也亂七八糟。有時我懷疑我這種人生過得亂七八糟的基因也是遺傳。」卻又隱然在自棄的情緒中流露出無法斬斷親緣的體悟。表妹志愛身為女性,對封建保守的家族從無好感,集體毒殺案發生後,她甚至覺得他們死了也不可惜,因為,「那些人包括雙親就算沒死,活下去也是行屍走肉,除了消費以外,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但她同樣清楚自己「一輩子不必出來工作的人生,是司武家賜與的。」他們的處境,就如同與司武家早已斷絕往來,卻因為案情重新被捲入家族糾葛,並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不得不積極參與查案的私家偵探志信形容的,是一個開放式監獄,囚友每個月都可以領到生活費,靈魂卻被禁錮著。
●家也可能如怪物般吞噬成員
在推理小說的框架下,血緣關係的感受與思考,並不只是感性的惆悵,更是務實的「誰會是加害者/受害者」之考量。外嫁的女兒不姓司武,卻同樣被納入謀殺名單,因為無論父系或母系,他們都擁有司武家的基因。但基因作為看似科學又可靠的線索,除了外貌上的相似特徵、隱藏的遺傳疾病,甚至志義形容的,性格與生活方式,足以作為辨識「一家人」的條件,那接受骨髓移植而擁有受贈者基因的人,也算是一家人嗎?當事者顯然並不這麼認為。於是,血緣、法律、同居,再加上「把事情變複雜」的科技,沒有一個能充分回答「什麼是家人?」這個問題。
對志愛和志信來說,更能給他們「家人」感受的,從來不是形同陌路的原生家庭。相較於親生父親,志愛覺得指導教授給她的關懷和啟發,更足以勝任父親這個角色,「即使教授是為天主教不容的同性戀者。誰說同性戀者不會給人父愛?」至於志信,更在警方質疑他「寧願陪狗也不去和家人共聚」時,理直氣壯地回覆:「家人的定義並不限於人,只要一起生活又有感情交流就是家人。我的狗當然是我家人,而且比姓司武的親近得多。」在釐清案情的過程中,這些司武家的成員們,無非也在澄清家與家人的定義。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可以視為家的地方」,但即使身處同一屋簷下,對家的樣貌也未必有共識。其中的歧異既受到世代觀念遞嬗的影響,自然也有個別差異。儘管司武這個姓氏是虛構的,圍村家族的處境即使對應在現實香港社會也屬少數,幾位司武家族成員對原生家庭的感受,卻足以讓我們看到姓氏作為「家」這個單位的辨識符號,可以是凝聚認同感的來源,也可能是「如怪物般吞噬成員」的深淵。原生家庭給予的是禮物還是負資產,儘管全憑運氣,但我們仍然擁有以自由意志去動搖無形禁錮的力量。如何找出那個可以視為家的所在,重新描摩自己心中家的形貌,或許才是小說留待讀者破譯的,真正謎團。
(未完待續)
〔姓名篇〕
禮物
◎《同名之人》,鍾芭.拉希莉著,彭玲嫻譯,天培,二○○四
◎《姓司武的都得死》,譚劍著,蓋亞,二○二三
二○二一年,台灣某間連鎖壽司店推出限時優惠方案,若名字與鮭魚同音即可享有折扣,名為「鮭魚」則全桌免費招待。業者顯然預期一般人不會以鮭魚為名,免費僅是招徠顧客與製造話題的行銷手法,不料卻有三百多名消費者前往戶政事務所改名,一時之間各種姓氏的鮭魚盡出,還有高價鮭魚、大口吃鮭魚、同鮭魚盡、鮭魚之夢等創意姓名,命名彷彿成了一場「鮭魚遊戲」。此一被稱為「鮭魚之亂」的事件不只登上國際新聞版面,後續也引發了對命名權、改名權的討論。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們既然擁有自己的姓名,那麼姓名的「使用方式」自然也應該完全操之在我,「鮭魚之亂」中動輒將名字改為四、五十個字,字數多到身分證幾乎塞不下的案例,想必抱著這樣的態度。改名對他們而言,形同在網路世界的不同平台取暱稱。然而,我們可以擁有無數個代號來維護自己的網路匿名性,現實世界卻無法如此,否則法律也無須對改名次數進行規範。至於利用免費吃到飽的福利,以數百元的價格組團用餐再收取餐費的少數「鮭魚」,將改名一事轉化為商業行為,名字在此模式中形同可以獲利的「商品」。從這個角度來看,「鮭魚之亂」不僅僅是一場令廠商始料未及的風波,或茶餘飯後的有趣話題,而是隱含著我們看待姓名的態度,以及一個深層的提問:我們的名字,屬於我們自己嗎?
無論法律如何規定改名的次數與程序,或是不同國家對姓名看法的文化差異,一個跨文化的事實是,我們日後想幫自己取多少筆名、藝名、小名都好,人生的第一個名字必然是被決定的。因此,它是一份禮物,而且是生命中第一份禮物。名字承載著命名者對新生兒的期盼與祝福,但它也一如所有的禮物,送禮者與收受者之間,對價值的認知、喜好與感受都未必相同。與其他禮物唯一的差異,或許在於就算不喜歡,它也無法轉贈。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同名之人》(The Namesake)與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儘管在故事風格與小說類型上都大相逕庭,卻同樣能帶我們看到姓名在生命中,作為一份禮物(或負資產?)的角色與意義。
——
●名字是一道咒語或一個祝福
「這世上最短的咒正是『名』。所謂咒,簡單說來就是束縛。要知道,名稱正是束縛事物本質的一種東西。」《同名之人》裡的主角果戈理,若是讀到夢枕獏在《陰陽師》中透過安倍晴明之口說出的這段話,想必深有同感。這部處理兩代印裔美籍移民人生的小說,深刻細膩地透過一個糾結一生的名字,突顯出姓名作為符號,在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遠比我們意識到的更重要。
果戈理這個名字,原是一場文化衝擊下的意外產物。年輕的移民夫婦阿碩可與愛希瑪依照傳統,將新生兒的命名權交託給愛希瑪的外婆。在那個仍然依賴電報與信件往返的年代,寫上小嬰兒名字的信,卻未能及時在他出生前抵達。儘管如此,他們並不焦慮,因為根據孟加拉的命名規則,每個人都有兩個名字,一個乳名,一個學名。學名是長大之後在正式場合使用,對於襁褓中的嬰兒來說,他只需要父母長輩表達親暱與祝福的乳名。問題是,在美國,嬰兒若沒有名字,就無法開立出生證明,也無法出院。
情急之下,阿碩可想起一個無懈可擊的名字——在火車事故時,從他緊握的手中掉落,讓他得以被搜救人員發現,救了他一命的那本小說,作者的名字,果戈理。愛希瑪同意了,因為她知道,「這名字代表的不只是她兒子的生命,也是她丈夫的生命。」那是一個父親送給兒子的第一份禮物。
對於這份禮物,年幼的果戈理並非一開始就感受到它的特別之處,卻也並不排斥。儘管他從來不曾在那些印著名字的紀念品上找到自己的名字,但他會在路牌上看到GO LEFT、GO RIGHT,遇見這些「Gogol 的片段」是種樂趣,也讓他得以指認自己的一部分。名字所帶來的種種認同困惑與困擾,是從進入學校這個小型社會才出現的。
好不容易選定了一個完美的孟加拉學名「倪克熙爾」,果戈理的父母卻再次在命名這件事情上,意識到移民生活是一場永恆的,文化與文化之間折衝磨合的過程。幼稚園無法理解父母為何要使用一個不存在於出生證明上,既非中間名也不是暱稱的名字。愛希瑪與阿碩可只能無奈接受父母的意願被學校無視的現實。至於果戈理,那卻是他與這個名字磨合的真正起點。他不明白人為何需要兩個名字,因此在幼稚園校長詢問時,斷然放棄了陌生的「倪克熙爾」之名,但慢慢地,他發現除了自己之外,沒有人叫做果戈理。他討厭老師點名時對自己名字的遲疑,更無法想像追求女孩時在浪漫氛圍中說出「嗨,我是果戈理。」名字這個沒有形體的東西甚至「會對他的身體造成不適,像襯衫上扎著皮膚的標籤,永恆不能褪下。」
●藉以指認「我是誰」與「我不是誰」
對於許多動輒「撞名」的人來說,果戈理的煩惱看似「奢侈」,更何況,獨一無二的名字,不是更能滿足我們期待與眾不同的心理需求?但自我認同其實是不斷在獨特性與歸屬感的天平間擺盪挪移、尋找位置的過程。果戈理這個過度特別的名字,反而令他在同儕中感到格格不入。更困擾的是,為此他必須不斷解釋:這個字在印度文中沒有任何意義,而是與他毫無關係的俄文。相對於那些連結著美好語意的傳統名字,姓名對他的意義與其說指認了「我是誰」,不如說是「我不是誰」——不是印度人,也不是美國人,當然更不可能是俄國人。甚至連他的姓名來源,那位同名之人,作家果戈理,也不叫果戈理——那是他的姓而非名。
身為移民後裔的認同困惑與孤獨感,被果戈理這個獨一無二的名字,徹底地具象化了。果戈理決定成為他童年時拒絕的那個名字,倪克熙爾。這並未讓他的生活顯得比較輕易,他依然在旁人討論姓名時感到不自在,更諷刺的是,他最後選擇的婚姻對象,是從小就認識,因此知道他本名的茉淑蜜——一個同樣苦於自己名字既罕見又難以發音的女孩。
鍾芭.拉希莉既未簡化,也未誇大姓名的重要性。果戈理的婚姻當然不只是基於名字的相似性,但他確實在某次朋友聚會後,意識到「吸引他倆結合的奇特情愫」,與這孤單的,未能輕易找到同名之人的認同感有關,一如他童年時總會留意墓園裡那些古怪又古老的名字,並且被那些擁有「過時的,無法想像的名字的人」深深吸引。他所依附的認同對象,從來不是印度人或美國人這樣的族群劃分,而是那些與他一樣,落單的、無法被妥善安放在群體中的,畸零者。
這世界上並不存在「完美的名字」,認同自己的姓名,當然也不至於就能擁有「完美的人生」。當父親終於告訴果戈里命名的源由,同樣不會讓彆扭、厭棄了一輩子的名字,搖身一變成為帶著光圈的名牌。果戈理三個字依然如同某個應該被隱藏的汙點,一場災難的分身與見證,但他對這個被自己放棄的名字,從此多了一份歉疚感。
當歉疚感悄悄萌芽,當他明白了這個在印度文與英文裡都沒有任何意義的名字,在父親的字典裡,卻意味著重生與祝福,他看待自己、看待父親、看待果戈理三個字的眼光都已不同。禮物之為禮物,也唯有在收禮者意識到那作為一份禮物時,意義才得以被指認。
●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進一步來說,姓名這個符號,可能是所有身分標籤中,最複雜的一種。在公開與隱匿之間,它以全稱、敬稱、暱稱、化名等各式各樣的形式,標誌著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名字作為禮物的意義,不僅止於命名者與被命名的關係,在某些文化或情境中,分享自己的名字,亦具有託付信任與交出一部分自己的象徵意義。韓劇《魷魚遊戲》裡,在殘酷的生存遊戲中一步步踏入死亡陷阱的參賽者,就被剝奪了姓名,只以去人性化的編號受到掌控。女主角姜曉與她編號240的同伴智英,在死亡面前,最後唯一能交換的珍貴物事,僅僅剩下彼此的姓名。這令人動容的一幕,可說是姓名作為禮物的最好彰顯。
至於村上春樹《東京奇譚集》裡那隻愛偷名字的「品川猴」,更說出「在這同時,也把附著在名字上的負面要素,多少也帶走一些」的話,同樣暗示名字既是「身分」,也作為某種「分身」的意義。
〈品川猴〉裡另一個有趣的細節,是主角婚後覺得一一向客戶通知自己改姓太麻煩了,在職場上仍保留婚前的姓名,發現有時會突如其來地遺忘姓名之後,她去珠寶店訂購了一個刻上「安藤(大澤)美月」的銀手鐲來提醒自己,就像寵物項圈的概念一樣。「安藤(大澤)」的身分,突顯出婚後冠上夫姓的情況,讓女性需要經歷一段重新適應自己新姓名的過程。儘管未必每個人都會為此困擾,卻提醒我們鑲嵌在身分符號之中的姓氏,作為「家庭/家族單位」的意義遠大於代表「個人」。這是何以傳統婚宴場合,餐廳往往會掛上「X府喜宴」或「XX聯姻」標語,而非新人的名字,隱然標誌著婚姻作為兩個家族而非兩個個體結合的現實。
正因姓氏作為一個集體符號,雖說同姓三分親,但除了罕見姓氏,一般人對於「同姓之人」通常不會產生特別親近的感受。姓氏帶來的苦惱除非特殊狀況(例如傳統社會對同姓婚姻的反對),否則不會像名字這種更具個別性的符號一般讓人念茲在茲。但譚劍《姓司武的都得死》這部小說,卻透過一個虛構的滅族式謀殺案,對姓氏背後所連結的,「家」與「家族」的概念進行了反思。
●姓氏是斬斷不了的親緣束縛
「姓司武的都得死」是個奇特的謀殺委託案,雖然不少人在結怨時會以對方全家作為咒罵的對象,但真要實際執行,即使以「全世界加起來只有五十多個成員」來說,也是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暗殺任務。但譚劍賦予這個虛構姓氏一個「香港限定」的獨特設定——他們是居住在大嶼山圍村的原居民。四散的家族成員有一個合理與必要的聚集契機,就是三年一次的家祭。這讓職業殺手的「工作難度」瞬間減輕不少。一場大規模的集體毒殺案,就成為小說驚人的開場序曲。
香港的圍村有其非常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傳統,相對也更父權中心。根據「丁屋政策」,新界原居民的男丁只要年滿十八歲,即可申請建造一間三層以下、每層七百平方呎的丁屋,無須向政府繳付地價。小說裡的司武家族成員,單是這被動收入已可不愁吃穿,每個月都有豐厚的生活津貼。姓氏對他們來說,確實如同一份權利與禮物,尤其是男性成員。當然,對那些只因同姓就莫名枉死的人來說,司武這個姓氏卻是不折不扣的負資產。
既然是推理小說,故事最後自然解釋了兇手要殺掉整個家族的動機,但謎團的設計並非本文要討論的重點,這部小說最吸引人之處,事實上也不在於那關鍵的動機與解謎的趣味,而是作者在〈後記〉提到的,「活在一個丁權家族裡各成員的感受。」幾位倖存者多半在情感上或生活上與家族疏離,卻又在經濟上或心理上被這個姓氏束縛著。
活得像個浪子的志義,自嘲名字中英夾雜、不中不西:「志」來自族譜輩分,「義」是家族天主教信仰的影響,「justice」、「faith」、「charity」這些單字被直接當成正式英文名,印在身分證上。但當他說出:「名字取得亂七八糟,反映那些人的想法也亂七八糟。有時我懷疑我這種人生過得亂七八糟的基因也是遺傳。」卻又隱然在自棄的情緒中流露出無法斬斷親緣的體悟。表妹志愛身為女性,對封建保守的家族從無好感,集體毒殺案發生後,她甚至覺得他們死了也不可惜,因為,「那些人包括雙親就算沒死,活下去也是行屍走肉,除了消費以外,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但她同樣清楚自己「一輩子不必出來工作的人生,是司武家賜與的。」他們的處境,就如同與司武家早已斷絕往來,卻因為案情重新被捲入家族糾葛,並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不得不積極參與查案的私家偵探志信形容的,是一個開放式監獄,囚友每個月都可以領到生活費,靈魂卻被禁錮著。
●家也可能如怪物般吞噬成員
在推理小說的框架下,血緣關係的感受與思考,並不只是感性的惆悵,更是務實的「誰會是加害者/受害者」之考量。外嫁的女兒不姓司武,卻同樣被納入謀殺名單,因為無論父系或母系,他們都擁有司武家的基因。但基因作為看似科學又可靠的線索,除了外貌上的相似特徵、隱藏的遺傳疾病,甚至志義形容的,性格與生活方式,足以作為辨識「一家人」的條件,那接受骨髓移植而擁有受贈者基因的人,也算是一家人嗎?當事者顯然並不這麼認為。於是,血緣、法律、同居,再加上「把事情變複雜」的科技,沒有一個能充分回答「什麼是家人?」這個問題。
對志愛和志信來說,更能給他們「家人」感受的,從來不是形同陌路的原生家庭。相較於親生父親,志愛覺得指導教授給她的關懷和啟發,更足以勝任父親這個角色,「即使教授是為天主教不容的同性戀者。誰說同性戀者不會給人父愛?」至於志信,更在警方質疑他「寧願陪狗也不去和家人共聚」時,理直氣壯地回覆:「家人的定義並不限於人,只要一起生活又有感情交流就是家人。我的狗當然是我家人,而且比姓司武的親近得多。」在釐清案情的過程中,這些司武家的成員們,無非也在澄清家與家人的定義。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可以視為家的地方」,但即使身處同一屋簷下,對家的樣貌也未必有共識。其中的歧異既受到世代觀念遞嬗的影響,自然也有個別差異。儘管司武這個姓氏是虛構的,圍村家族的處境即使對應在現實香港社會也屬少數,幾位司武家族成員對原生家庭的感受,卻足以讓我們看到姓氏作為「家」這個單位的辨識符號,可以是凝聚認同感的來源,也可能是「如怪物般吞噬成員」的深淵。原生家庭給予的是禮物還是負資產,儘管全憑運氣,但我們仍然擁有以自由意志去動搖無形禁錮的力量。如何找出那個可以視為家的所在,重新描摩自己心中家的形貌,或許才是小說留待讀者破譯的,真正謎團。
(未完待續)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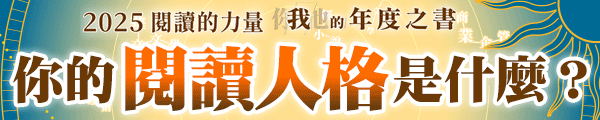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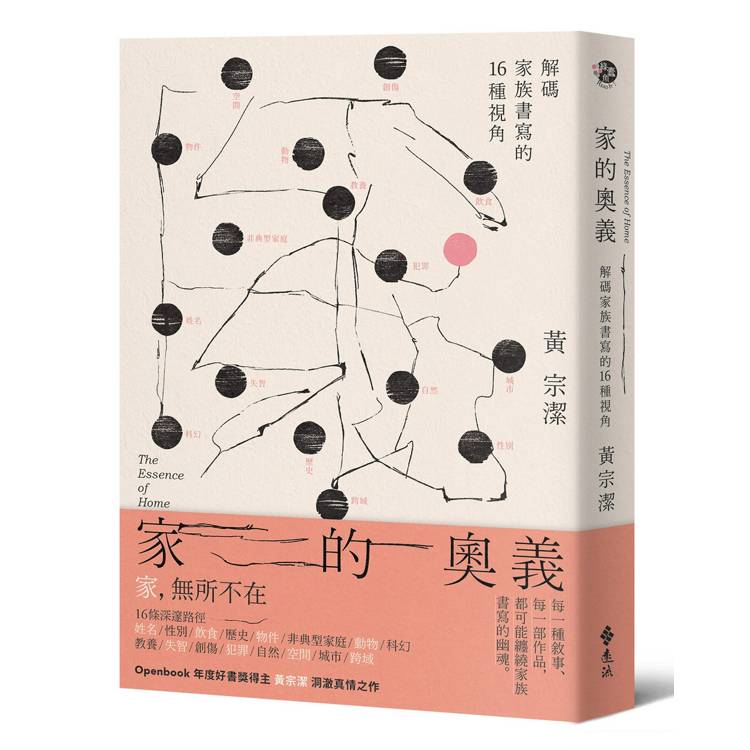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