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靜的巨大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我不知道是什麼在護持著這「寧靜的巨大」,
我卻越來越相信它還在護持著我們。
──席慕蓉
寫《七里香》時的席慕蓉,是清澈的溪流,在年輕時涓涓地流著。那時我不認識她。等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奔忙在故鄉路上的席慕蓉了……她這時發現,自己的生命中居然還有一個浩淼的大海。
我為她感到幸運,不是每個作家都可以遇到溪流,也遇到大海的。
──陳丹燕〈讀書記〉
置身在多種源流的文化之間,席慕蓉以札記和書信的方式來詮釋她的探尋、反省及發現。這本新書中有她不變的「本我」與「初心」,更讓讀者以全新角度來看待「他者」與「他方」的存在,領悟生命個體的流轉,其實還有更幽微與更遼闊的牽連。
【本書特色】
1. 「生命裡有些特別的質素在吸引著我,我渴望能把它們用文字挽留下來。」──席慕蓉。當代散文大家之一,文壇重量級作家席慕蓉最新散文集。
2. 題材優美動人,有幸福的時刻、有對原鄉的感人情懷,一本就像好友時時在
身邊陪伴我們的隨身書。
3. 作者有別於科技時代許多人不再用手寫信給友人,她與朋友魚雁往返的情
誼,是一切講求快速的現代人值得學習的。
我卻越來越相信它還在護持著我們。
──席慕蓉
寫《七里香》時的席慕蓉,是清澈的溪流,在年輕時涓涓地流著。那時我不認識她。等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是奔忙在故鄉路上的席慕蓉了……她這時發現,自己的生命中居然還有一個浩淼的大海。
我為她感到幸運,不是每個作家都可以遇到溪流,也遇到大海的。
──陳丹燕〈讀書記〉
置身在多種源流的文化之間,席慕蓉以札記和書信的方式來詮釋她的探尋、反省及發現。這本新書中有她不變的「本我」與「初心」,更讓讀者以全新角度來看待「他者」與「他方」的存在,領悟生命個體的流轉,其實還有更幽微與更遼闊的牽連。
【本書特色】
1. 「生命裡有些特別的質素在吸引著我,我渴望能把它們用文字挽留下來。」──席慕蓉。當代散文大家之一,文壇重量級作家席慕蓉最新散文集。
2. 題材優美動人,有幸福的時刻、有對原鄉的感人情懷,一本就像好友時時在
身邊陪伴我們的隨身書。
3. 作者有別於科技時代許多人不再用手寫信給友人,她與朋友魚雁往返的情
誼,是一切講求快速的現代人值得學習的。
目錄
〈代序〉蒙文課
輯一:短歌
琴聲
邂逅
偶遇
畫筆
孕婦
伴侶
哀傷的時代
冬日的午後
麻葉繡球
百合花及其他
誘惑
陰山下
草原騙局
洛陽李家營
輯二:線索
關於揮霍
追尋之歌
如花的綻放
寄友人書
線索
舞者‧阿月
初老
詩人與寫詩的人
秋月
謝函
輯三:對照集
童年物件
對照集
長路迢遙
天穹低處盡吾鄉
聖誕夜
百合花及其他
一如天唱
走馬
三匹狼
芨芨草
輯四:高原札記
查干蘇魯德
斡難河畔
普氏野馬
闕特勤碑
刻痕──寫給海日汗的第二封信
神聖的人
諾門罕戰爭
鷹笛
瑪麗亞‧索
輯五:北方書簡
永世的渴慕
書寫的意義
悲傷輔導
繁華舊夢
星空下的神話
無知的慈悲
花訊
生活‧在他方
寧靜的巨大
曼德拉山岩畫
【附錄】
長城之外的草香——讀《席慕蓉和她的內蒙古》所記觀感 鮑爾吉‧原野
讀書記 陳丹燕
輯一:短歌
琴聲
邂逅
偶遇
畫筆
孕婦
伴侶
哀傷的時代
冬日的午後
麻葉繡球
百合花及其他
誘惑
陰山下
草原騙局
洛陽李家營
輯二:線索
關於揮霍
追尋之歌
如花的綻放
寄友人書
線索
舞者‧阿月
初老
詩人與寫詩的人
秋月
謝函
輯三:對照集
童年物件
對照集
長路迢遙
天穹低處盡吾鄉
聖誕夜
百合花及其他
一如天唱
走馬
三匹狼
芨芨草
輯四:高原札記
查干蘇魯德
斡難河畔
普氏野馬
闕特勤碑
刻痕──寫給海日汗的第二封信
神聖的人
諾門罕戰爭
鷹笛
瑪麗亞‧索
輯五:北方書簡
永世的渴慕
書寫的意義
悲傷輔導
繁華舊夢
星空下的神話
無知的慈悲
花訊
生活‧在他方
寧靜的巨大
曼德拉山岩畫
【附錄】
長城之外的草香——讀《席慕蓉和她的內蒙古》所記觀感 鮑爾吉‧原野
讀書記 陳丹燕
序/導讀
蒙文課 代序
去上蒙文課。
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
在燈下,才剛寫了上面這兩行,忽覺悚然。這樣簡短的兩行字,這樣簡單的事實,如果是發生在六歲那年,是極為歡喜的大事,也值得父母大書特書,把這一天定為孩子啟蒙的紀念日。
可是,如果是發生在孩子已經六十多歲的這一年,父母都已逝去,她一個人在燈下,在日記本裡鄭重地寫下這兩行字的時候,還值得慶賀嗎?
或許,還是值得慶賀的吧。
在南國的燈下,在不斷滴落的熱淚裡,我一個人靜靜地自問自答。
或許,還是值得慶賀的吧。
去上蒙文課。
學會了寫自己的名字。
在燈下,才剛寫了上面這兩行,忽覺悚然。這樣簡短的兩行字,這樣簡單的事實,如果是發生在六歲那年,是極為歡喜的大事,也值得父母大書特書,把這一天定為孩子啟蒙的紀念日。
可是,如果是發生在孩子已經六十多歲的這一年,父母都已逝去,她一個人在燈下,在日記本裡鄭重地寫下這兩行字的時候,還值得慶賀嗎?
或許,還是值得慶賀的吧。
在南國的燈下,在不斷滴落的熱淚裡,我一個人靜靜地自問自答。
或許,還是值得慶賀的吧。
試閱
追尋之歌
有些詩人,可以把自己的創作經驗和作品分析,寫成一本又一本有系統可循的書,宛如明鏡,是一種清楚的自我認知和詮譯。
有些詩人,則是除了他的詩作之外,從不多發一言。那面明鏡,總是孤獨地懸掛在自己的心中。
而我呢?我當然絕對做不成前者,但是,也更做不成後者。
創作的熱情反覆前來,心中是懷著一些模糊的憧憬。可是,在創作的過程裡,也充滿了困惑,所有的線索好像都在,卻是混亂、矛盾,甚至是互相否定的。
每次都是只有在終於寫成了一首詩的那一瞬間,好像才能恍然於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究竟是些什麼。
創作的熱情反覆前來,卻始終難以辨識那深藏在我心中的憧憬的全貌。
要更清楚的看見自己,我需要的是一種激發和觸動。
如果眼前有個比較具象的畫面,我應該就是那個在無星無月的夜裡,在山林中艱難尋路的旅人,期盼天際能不時出現明亮的閃電,只為,那瞬間的光耀,就足夠讓我審視自己的置身之處與目的地之間的距離,以及方位的差異,從而可以在其後的黑暗裡,再摸索出一小段的路程來。
由於腳步比較慢,詩因此也寫得不算多。這幾天,我的第六本詩集出版了,自己好奇地去數了一數,六本中發表的詩作總數,也不過是三百三十多首而已。可是,如果從其中年代最早的那一首算起,一九五九年的春日到此刻二○○五年的春天,這時間卻是長長的四十多年!
好友其楣剛剛才對我說過一句話:
「你啊!你是個糊里糊塗就寫了四、五十年的詩人!」
她的意思是說,我既不曾立下什麼大志,也沒有什麼周詳的寫作計畫,可是,卻也一直一直沒有離開。
是因為那深藏著的始終不曾向我完整顯現的憧憬嗎?
所以,我對「錢南章樂展──一棵開花的樹」這場音樂會是充滿期待的。
音樂會全場的二十首曲子都是以我的詩作入歌,由女高音徐以琳教授獨唱,鋼琴家王美齡教授伴奏。
而作曲家說,他想要以這二十首的獨唱曲來詮釋我這個人,以及我作為一個詩人的一生。
有這種可能嗎?
在過往的生活中我們互不相涉,除了我偶爾聽過他的音樂,他偶爾讀到我的詩之外,幾乎就等於是兩個陌生人。但是,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對我來說,那又將是何等強烈炫目的閃電,何等令我戰慄的激發和觸動呢?
這三位音樂家在開始練習的時候,不希望我在場。等到終於准我去聆聽的那日,是個又冷又濕的雨天,從淡水到關渡,車窗上一直有層薄薄的霧氣,像我心裡輕微的忐忑。
可是,第一首歌,就讓我驚呆住了。
〈出岫的憂愁〉原詩寫成於一九八二年:
驟雨之後
就像雲的出岫 你一定要原諒
一定要原諒啊 一個女子的
無端的憂愁
只有四行的詩,卻重複了兩次相同的請求。在詩成的當時,甚至一直到此刻之前,我都認為這「請求」是謙卑的表達。可是,為什麼在錢南章的歌裡,卻讓我聽到了一個生命深藏著的堅持,甚至可以說是驕傲?
這首歌彷彿在沉緩而又平靜地宣示:是的,我是在請求你的原諒。不過,即使你不能原諒,我還是要保有我生命裡那必然會出現的無端的憂傷。
在楊宗翰先生的一篇論文裡曾經引用朱雙一先生對我早期詩作的見解:「……『因你而生的一切苦果/我都要親嘗』(〈苦果〉)。這種心態看似謙卑,實乃現代女性自主意識的產物……把自己對愛的追求和奉獻,當作自我價值的實現,而非把自己託付給男性的傳統女性式的企望,也非受封建禮教壓迫的一種被動行為。即使同樣寫苦苦的等待,它亦非古代閨怨詩中那種婦女從一而終、依仗夫婿的心態投射,而是對愛和美的等待和追求。這種區別所顯示的,正是現代女性對自身價值的自覺。」
這兩位學者我都不認識,並且前者好像並不同意後者的論點。我多麼希望他們二位都能前來聆聽這場音樂會。
在詩裡隱藏了這麼多年的質素,為什麼此刻在歌中卻昭然若揭?是因為錢南章那深沉獨特的詮釋嗎?還是因為徐以琳那飽滿醇厚、充滿了生命能量的美麗歌聲?
我心戰慄,不敢多言,只想聆聽。
是多麼美好的時刻!
窗外,細雨輕輕落下,窗內,美麗的歌聲與琴音彼此呼應,一首又一首地接著唱下去。歌中是我的青春,在樂音中正頻頻追問「一定有些什麼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不然 草木怎麼都會/循序生長/而候鳥都能飛回故鄉」。
在不斷的追問之中,時光那條大河已波瀾壯闊地從我眼前流過,青春轉瞬間就遠在彼岸……然後,故鄉這個主題逐漸靠近。
錢南章教授說:「如果只是要寫一首歌,我會挑一首我最喜歡的詩來譜曲。但是今天我所面對的,是一整場藝術歌曲的作品發表會。」
所以,「無論是全場音樂會的長度、樂曲的多樣性、每一組歌曲或上下半場在音樂上是否能累積達到高潮,都在設計範圍之內。」
因此,〈風景〉〈戲子〉〈在黑暗的河流上〉及〈高高的騰格里〉這四首歌,對他來說,「都希望在音樂上達到高潮,作為每組歌曲的結束。」
然而,對我而言,我卻並沒有感受到這種「設計」。只覺得生命裡的許多情境在歌中比在詩裡以更為強烈的力量迎面逼來,尤其在最後一組以蒙古高原為主題的四首歌裡,每一首都直刺我心。
作曲家在歌中用了許多疊句,不斷延展,彷彿是追問,又像是高原的回音。我心戰慄,含淚聆聽,聆聽我生命深處始終不曾變易的,對愛和美的等待與追尋。
詩人與寫詩的人──我讀《新詩五十問》之後
這幾天,拜讀了向明先生的新書《新詩五十問》,好像心思也跟著活潑了起來。
這本書以一問一答的方式,來闡釋詩人對詩的種種看法。五十篇短文旁敲側擊,不知不覺地就把讀者帶到詩的世界裡去了。
當然,對詩的看法,言人人殊,各有妙處,原本就不必一定要完全相同。不過,對於書中的第二問「詩人還是詩匠?」我有些疑點,很想在這裡提出來就教於向明先生。
為了敘述方便,我必須先節錄部分原文:
問:去年秋天的一次「詩的星期五」聚會上,台上的兩位詩人發表完自己的作品之後,輪到聽眾發問。有一位年輕詩人很小心的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問:「詩人和寫詩的人到底有什麼區別?」您當時的看法如何?
答:這個問題一下觸及大部分詩人的隱痛,年輕人的問題絕對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深思後的有意一問。當時台上的詩人白靈無奈的作了答覆。他說:「剛剛開始學寫的人祇能稱作寫詩的人,一直寫到有點年紀,有些成就才能算是詩人。詩人與寫詩的人區別大概就在此。」
白靈的答覆顯然沒有獲得多少掌聲。此後便沒有人再作解釋,直到主持人洛夫上台作結論時,他才補充了他的看法。他強作笑顏的說:「詩集賣得好的人才算是詩人,詩集沒有人要的便是寫詩的人。」這次台下的掌聲仍然不多,但笑聲盈耳。
當時我也在場,也很想提出我的看法,但一時思緒不能集中,而時間也不允許,祇好作罷。但我對白靈和洛夫兩人的解釋卻是不敢敬同的。(中略)
最近讀詩很多,寫詩很少。越讀越覺得詩是一種天真的表現,好詩必定天真無邪,詩人越天真寫出來的詩越可貴。(中略)
但天真最容易變質,會腐蝕天真的便是世故。普通人一世故,就會自我墮落,沒有自己的理想。詩人一旦世故就會比庸俗的人更庸俗,各種欲望便會隨之而生。(中略)天真的詩人變得世故以後,一切均是有所為而為,(中略)這時實際他已降格為一個詩匠,專為某種目的而寫,或不得不寫的寫詩的人。
詩人與寫詩的人或詩匠最大的分野便是一個一味天真的去寫,不忮不求,每寫必有創意;一個是被世俗牽著鼻子去寫,常常自作應聲之蟲。
以上是原文的主要內容,現在,我要開始發問了。我的第一個疑點是:也許向明誤會了發問者的原意?
因為,如果「詩人」和「寫詩的人」在向明的答覆中,前者是被肯定的,後者是被否定的話,那麼,發問者的問題應該修改成這樣:
「寫詩的人和自以為在寫詩的人到底有什麼區別?」
不過,這樣一來,答案早就明白地擺在問題裡,恐怕也就不需要發問了。
因為,詩,只能有一種:就是具備了「詩質」的文字。這種本質,深藏在詩人的心裡,有如美玉深藏在山中或水底一樣,是一種天賦,只能發掘和激發,卻絕對不能無中生有。要在文字裡發揮出這種「詩質」,才能稱為「詩」,要在被稱為是「詩」之後,才能再分為「好詩」與「壞詩」。就像再有瑕疵的玉,依舊是玉,而無論怎麼染色怎麼去用功打磨的石頭,它的本質永遠也只能是一塊石頭而已。
所以,那位發問者在提問題時,也許前提是先肯定了「詩人」與「寫詩的人」寫的都是「詩」,兩者的資質完全相同。
如果是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那麼,白靈和洛夫兩位先生的回答其實也言之成理。
白靈的回答可以解釋成是一種外在的附加價值。社會對這兩個名詞有不同的認定,如果要成為眾所公認的詩人,寫詩的人確實是需要一些時間和作品的累積的。
而洛夫的回答,則可以解釋成是一種內在的心理狀態,是因際遇不同所造成的區別。寂寞的詩人就是一個在沒有人要他的詩集的時候,依舊堅持地寫著詩的人。
當然,這兩種回答,仍然必須要在那位發問者的原意是對這兩個名詞都抱持肯定的態度時,才能算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我們假定,在他發問之前,對於「詩」這個字,是曾經謹慎地考慮過的。
不過,我們此刻無法找到他再來一問究竟,所以,也有可能,他的原意是比較接近向明所了解的意思──他對「詩人」比較肯定,而對「寫詩的人」隱含了否定的價值觀。
如果是這樣,向明的答覆才能算是正確。不過,在其中,我又有些不同的意見。
向明說:「詩人越天真寫出來的詩越可貴。」這點我完全同意。但是,「天真無邪」如夏日初發的芙蓉,可貴的就在那一瞬間的冰清玉潔,不過,人生能有幾次那樣的幸福?只要是不斷在成長著的人,心中就會不斷地染上塵埃。讀詩、寫詩,其實就是個體在無可奈何的沉淪中對潔淨的「初心」的渴望。我總覺得,這「渴望」本身,也能成為詩質,飽經世故之後的詩人,如果能夠在滄桑無奈之中還不失他的天真,恐怕是更為可貴的吧。
另外,向明認為,當詩人成為專為某種目的,或不得不寫的寫詩的人時,他已經降格為一個詩匠了。
對於「匠」這個名詞,我總覺得,中國傳統文人,實在是錯用了這個「匠」字。因為,一個能夠真正把他的工作做好的工匠,也需要才情。我們故宮所藏的那麼多或者精緻或者樸素的美麗器物,都是一些了不起的工匠聚精會神地做出來的。我想,大部分的文人即使你讓他去學三輩子,可能也做不到。所以,把「匠氣」拿來當作次等的文章或者書畫的形容詞,好像是很貼切,而其實又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我又回到先前的問題上來。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當一個詩人淪落到專為某種目的,或不得不寫的時候,他就已經不能再是詩人了。
「被世俗牽著鼻子去寫」的東西,就不能再稱為詩,詩人降格之後,便只能成為「自以為還在寫詩的人」。
當一位詩人變成了自以為還在寫詩的人之後,會因為每個人不同的性格,而讓他此後的生活變成了一場悲劇、喜劇,或者甚至是鬧劇。不過,如果他自己不會發現的話,也不會有什麼嚴重的傷害,頂多是他周圍的朋友有點「鬱卒」罷了。
比較恐怖的是那些從來不是詩人,但是一直以為自己是在寫詩評的人。因為萬一他又非常用功,幾十年下來著作等身,每一座圖書館裡都有他的書,那可真是讀者的大災難啊!
話扯遠了,再回到原處來吧。今天晚上,我把想到的種種先在電話裡說給曉風聽,像繞口令似的解釋了半天之後,她的回答是:
「我聽得都累死了!不過,我倒覺得,『詩人』只是個名詞,而『寫詩的人』裡有個動詞。名詞是別人給你的稱呼,是空的,固定的,遠不如『寫詩的人』裡這個動詞是自己可以控制,可以一直自由自在地寫詩。當然,最好的狀況是:又能是別人心中的詩人,又能不受影響地繼續做個寫詩的人。否則的話,如果只能二選一,我倒寧願做個可以一直寫下去的寫詩的人,而不是只有一個固定的空空的稱呼──詩人。」
好!這又來了一種精采說法!我當即徵求了同意把這段話放在最後。其實,仔細比較一下,她的意見和向明的結論非常相似,只是肯定與否定的對象互換了而已。
不知道那位當初發問的年輕詩人現在在什麼地方?會不會看到我們這些意見?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他要在創作的長路上面臨選擇,他到底是選擇名詞呢還是動詞?
一如天唱──再迎騰格爾
讀完騰格爾的自傳《天唱》,印象最深的是他父母的幾張相片。只有幾張,散置在書頁間,從黑白到彩色,從年輕到年老,當然逐漸受到歲月滄桑的改變,可是,卻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無邪、真誠與靜定的特質,始終如一地從他們身上顯現,是整個人、整個身體舉止的神態。
這應該就是孟馳北先生所說的「隱性文化」在游牧民族身上的具體顯現了。
孟馳北先生在他的《草原文化與人類歷史》上下兩冊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人們對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出土文物都看作價值連城的瑰寶,哪怕是一塊碎陶片都有人嘔心瀝血地研究,而對原始初民在數十萬年中對人類心理世界的塑造,卻鮮有人傾注探索的心血。人的心理世界原來也是一片蠻荒,或者說是一片空白,今天被人們稱之為『勇敢』『進取』『冒險』等心理現象,都是原始初民在時間長河中塑造出來的。」
在時間的長河中塑造出來的種種美德,是一種「隱性文化」,普遍表現在今天人類的身上,而在游牧民族身上表現得特別鮮明,所以,孟馳北先生說:「這種隱性文化可以說是草原文化的內核。」
時間的長河是綿延不絕的,同時也是流動著的,騰格爾,這位極為獨特的歌者,身為草原之子,當然也是從這樣深沉的文化中走出來的。
然而,我相信台灣的聽眾在他一九九二年首次來台的演唱現場上所受到的強烈感動,除了歌聲中素樸渾厚的生命之力外,還有一種驚訝和讚嘆,就是騰格爾能夠如此自由和自如地游走於傳統和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卻還能保有那種特質。就如樂評所說的:「一種嶄新的風格、一種淳樸、從未聽到過,甚至從未想到過的淳樸。」
而那年,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演唱會是第二場,那天晚上,據朋友告訴我聽,來來去去的聽眾足足有三萬人次,現場的氣氛極為熱烈,騰格爾自己也記得:
「節目單上的唱完,翻唱了兩首不能再唱,觀眾就手拉手圍著台子,這邊喊『騰格爾騰格爾』,那邊嚷『再來一個再來一個』,真是山呼海嘯啊!」
對騰格爾來說是難忘的鼓勵,對當晚的聽眾來說,也是難忘的「鼓勵」,就好像是有什麼可以從歌聲裡走出來,鼓舞你、激勵你,提醒你原來一直深藏在心裡的竟然有那麼多美好的質素。
一九六○年一月十五日生在內蒙古鄂爾多斯鄂托克旗額爾和圖蘇木,騰格爾的家鄉曾經是豐饒美麗的。「那是一種天地人和的美,純自然的大美,語言無法描述。現在已經看不到這樣的大美了,可是它完整地保留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影響著並且將繼續影響我的一生。」
影響著他一生的應該還有鄂爾多斯的民歌。在這一處高原上,民歌多如海洋中的波光,而騰格爾的父母都唱,「年輕的時候特別會唱,現在也還唱。我父親知道的民歌之多,在我們那兒是數一數二的。」
騰格爾曾經寫過一首〈古老的歌〉,在其中就插進去一段父親最愛唱的民歌。每當他抱起吉他唱這首歌的時候,還特別努力模仿父親吟唱時的風格,讓有時會在座的父親,覺得特別歡喜。
騰格爾的父親還喜歡他寫的另一首歌,就是〈父親和我〉。
但是,騰格爾的父親也就喜歡這兩首歌,其他的都不怎麼在意。
騰格爾的母親就更不在意了,因為,她唱的是道地的民歌。
騰格爾說:「民歌就是這樣,記錄著、積淀著從古至今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相似的、共通的、永恆的人類情感。由此決定了它天長地久、不可抗拒的魅力。」
騰格爾唱的,和他父母唱的並不一樣,然而,在心底,他其實是羨慕的--因為他們不表演、不作秀,只在乎自己的內心感受,整個人沉浸在自己的歌聲裡,如此的專注與虔誠。
騰格爾說:「這就是民歌,這樣唱歌的人,那才叫真正的歌手。我知道現在我做不了這樣的歌手,但我心裡有一個這樣的歌手,總有一天我會成這樣的歌手──在我不再是一個『歌手』的時候。」
現在的騰格爾,還有許許多多的夢想與試驗在等待實現。
一九九三年成立迄今的「蒼狼樂隊」就是其中之一。
帶著「蒼狼樂隊」,騰格爾走遍國內外,一首又一首的新歌不斷唱出來,一張又一張的唱片不斷發行,也不斷得到許多獎項的鼓勵。
同時,在草原的深處,你也可以聽到有人在騎馬橫渡的時候遠遠地唱著〈蒙古人〉〈蒼狼大地〉〈父親和我〉以及〈天堂〉……
我就常常遇到這樣的時刻,在內蒙古阿拉善盟荒漠化了的草原上,在鄂爾多斯成陵一處無人的階梯之下,在新疆阿爾泰山麓邊一座小旅舍裡,總有人會在忽然間唱起了騰格爾的歌:「……駿馬失去了主人/獵狗失去了駿馬/蒼狼大地一片黃沙/豐美草原幾度寂寞/啊哈呼……」
騰格爾啊,騰格爾,你可知道,其實民歌就是這樣。記錄著、積淀著從古至今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這不就是你自己說的嗎?
每一代都不是一池死水,每一代都是有從四方八面奔湧過來的不同的源泉,今天你所寫出來的歌,將會有一部分成為明天的民歌,因為,正是你,充滿了夢想,充滿了勇氣往世界各地走去,才有可能讓你的歌終於成為一種共通的,永恆的人類情感,由此決定了它天長地久、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知道你很喜歡自己的名字「騰格爾」,在蒙文裡是指「天」、「天神」以及「廣大無邊」之意。所以,祝福你有一日終於會達到你的願望:「一如天唱。」
有些詩人,可以把自己的創作經驗和作品分析,寫成一本又一本有系統可循的書,宛如明鏡,是一種清楚的自我認知和詮譯。
有些詩人,則是除了他的詩作之外,從不多發一言。那面明鏡,總是孤獨地懸掛在自己的心中。
而我呢?我當然絕對做不成前者,但是,也更做不成後者。
創作的熱情反覆前來,心中是懷著一些模糊的憧憬。可是,在創作的過程裡,也充滿了困惑,所有的線索好像都在,卻是混亂、矛盾,甚至是互相否定的。
每次都是只有在終於寫成了一首詩的那一瞬間,好像才能恍然於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究竟是些什麼。
創作的熱情反覆前來,卻始終難以辨識那深藏在我心中的憧憬的全貌。
要更清楚的看見自己,我需要的是一種激發和觸動。
如果眼前有個比較具象的畫面,我應該就是那個在無星無月的夜裡,在山林中艱難尋路的旅人,期盼天際能不時出現明亮的閃電,只為,那瞬間的光耀,就足夠讓我審視自己的置身之處與目的地之間的距離,以及方位的差異,從而可以在其後的黑暗裡,再摸索出一小段的路程來。
由於腳步比較慢,詩因此也寫得不算多。這幾天,我的第六本詩集出版了,自己好奇地去數了一數,六本中發表的詩作總數,也不過是三百三十多首而已。可是,如果從其中年代最早的那一首算起,一九五九年的春日到此刻二○○五年的春天,這時間卻是長長的四十多年!
好友其楣剛剛才對我說過一句話:
「你啊!你是個糊里糊塗就寫了四、五十年的詩人!」
她的意思是說,我既不曾立下什麼大志,也沒有什麼周詳的寫作計畫,可是,卻也一直一直沒有離開。
是因為那深藏著的始終不曾向我完整顯現的憧憬嗎?
所以,我對「錢南章樂展──一棵開花的樹」這場音樂會是充滿期待的。
音樂會全場的二十首曲子都是以我的詩作入歌,由女高音徐以琳教授獨唱,鋼琴家王美齡教授伴奏。
而作曲家說,他想要以這二十首的獨唱曲來詮釋我這個人,以及我作為一個詩人的一生。
有這種可能嗎?
在過往的生活中我們互不相涉,除了我偶爾聽過他的音樂,他偶爾讀到我的詩之外,幾乎就等於是兩個陌生人。但是,如果他真的做到了,對我來說,那又將是何等強烈炫目的閃電,何等令我戰慄的激發和觸動呢?
這三位音樂家在開始練習的時候,不希望我在場。等到終於准我去聆聽的那日,是個又冷又濕的雨天,從淡水到關渡,車窗上一直有層薄薄的霧氣,像我心裡輕微的忐忑。
可是,第一首歌,就讓我驚呆住了。
〈出岫的憂愁〉原詩寫成於一九八二年:
驟雨之後
就像雲的出岫 你一定要原諒
一定要原諒啊 一個女子的
無端的憂愁
只有四行的詩,卻重複了兩次相同的請求。在詩成的當時,甚至一直到此刻之前,我都認為這「請求」是謙卑的表達。可是,為什麼在錢南章的歌裡,卻讓我聽到了一個生命深藏著的堅持,甚至可以說是驕傲?
這首歌彷彿在沉緩而又平靜地宣示:是的,我是在請求你的原諒。不過,即使你不能原諒,我還是要保有我生命裡那必然會出現的無端的憂傷。
在楊宗翰先生的一篇論文裡曾經引用朱雙一先生對我早期詩作的見解:「……『因你而生的一切苦果/我都要親嘗』(〈苦果〉)。這種心態看似謙卑,實乃現代女性自主意識的產物……把自己對愛的追求和奉獻,當作自我價值的實現,而非把自己託付給男性的傳統女性式的企望,也非受封建禮教壓迫的一種被動行為。即使同樣寫苦苦的等待,它亦非古代閨怨詩中那種婦女從一而終、依仗夫婿的心態投射,而是對愛和美的等待和追求。這種區別所顯示的,正是現代女性對自身價值的自覺。」
這兩位學者我都不認識,並且前者好像並不同意後者的論點。我多麼希望他們二位都能前來聆聽這場音樂會。
在詩裡隱藏了這麼多年的質素,為什麼此刻在歌中卻昭然若揭?是因為錢南章那深沉獨特的詮釋嗎?還是因為徐以琳那飽滿醇厚、充滿了生命能量的美麗歌聲?
我心戰慄,不敢多言,只想聆聽。
是多麼美好的時刻!
窗外,細雨輕輕落下,窗內,美麗的歌聲與琴音彼此呼應,一首又一首地接著唱下去。歌中是我的青春,在樂音中正頻頻追問「一定有些什麼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不然 草木怎麼都會/循序生長/而候鳥都能飛回故鄉」。
在不斷的追問之中,時光那條大河已波瀾壯闊地從我眼前流過,青春轉瞬間就遠在彼岸……然後,故鄉這個主題逐漸靠近。
錢南章教授說:「如果只是要寫一首歌,我會挑一首我最喜歡的詩來譜曲。但是今天我所面對的,是一整場藝術歌曲的作品發表會。」
所以,「無論是全場音樂會的長度、樂曲的多樣性、每一組歌曲或上下半場在音樂上是否能累積達到高潮,都在設計範圍之內。」
因此,〈風景〉〈戲子〉〈在黑暗的河流上〉及〈高高的騰格里〉這四首歌,對他來說,「都希望在音樂上達到高潮,作為每組歌曲的結束。」
然而,對我而言,我卻並沒有感受到這種「設計」。只覺得生命裡的許多情境在歌中比在詩裡以更為強烈的力量迎面逼來,尤其在最後一組以蒙古高原為主題的四首歌裡,每一首都直刺我心。
作曲家在歌中用了許多疊句,不斷延展,彷彿是追問,又像是高原的回音。我心戰慄,含淚聆聽,聆聽我生命深處始終不曾變易的,對愛和美的等待與追尋。
詩人與寫詩的人──我讀《新詩五十問》之後
這幾天,拜讀了向明先生的新書《新詩五十問》,好像心思也跟著活潑了起來。
這本書以一問一答的方式,來闡釋詩人對詩的種種看法。五十篇短文旁敲側擊,不知不覺地就把讀者帶到詩的世界裡去了。
當然,對詩的看法,言人人殊,各有妙處,原本就不必一定要完全相同。不過,對於書中的第二問「詩人還是詩匠?」我有些疑點,很想在這裡提出來就教於向明先生。
為了敘述方便,我必須先節錄部分原文:
問:去年秋天的一次「詩的星期五」聚會上,台上的兩位詩人發表完自己的作品之後,輪到聽眾發問。有一位年輕詩人很小心的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問:「詩人和寫詩的人到底有什麼區別?」您當時的看法如何?
答:這個問題一下觸及大部分詩人的隱痛,年輕人的問題絕對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深思後的有意一問。當時台上的詩人白靈無奈的作了答覆。他說:「剛剛開始學寫的人祇能稱作寫詩的人,一直寫到有點年紀,有些成就才能算是詩人。詩人與寫詩的人區別大概就在此。」
白靈的答覆顯然沒有獲得多少掌聲。此後便沒有人再作解釋,直到主持人洛夫上台作結論時,他才補充了他的看法。他強作笑顏的說:「詩集賣得好的人才算是詩人,詩集沒有人要的便是寫詩的人。」這次台下的掌聲仍然不多,但笑聲盈耳。
當時我也在場,也很想提出我的看法,但一時思緒不能集中,而時間也不允許,祇好作罷。但我對白靈和洛夫兩人的解釋卻是不敢敬同的。(中略)
最近讀詩很多,寫詩很少。越讀越覺得詩是一種天真的表現,好詩必定天真無邪,詩人越天真寫出來的詩越可貴。(中略)
但天真最容易變質,會腐蝕天真的便是世故。普通人一世故,就會自我墮落,沒有自己的理想。詩人一旦世故就會比庸俗的人更庸俗,各種欲望便會隨之而生。(中略)天真的詩人變得世故以後,一切均是有所為而為,(中略)這時實際他已降格為一個詩匠,專為某種目的而寫,或不得不寫的寫詩的人。
詩人與寫詩的人或詩匠最大的分野便是一個一味天真的去寫,不忮不求,每寫必有創意;一個是被世俗牽著鼻子去寫,常常自作應聲之蟲。
以上是原文的主要內容,現在,我要開始發問了。我的第一個疑點是:也許向明誤會了發問者的原意?
因為,如果「詩人」和「寫詩的人」在向明的答覆中,前者是被肯定的,後者是被否定的話,那麼,發問者的問題應該修改成這樣:
「寫詩的人和自以為在寫詩的人到底有什麼區別?」
不過,這樣一來,答案早就明白地擺在問題裡,恐怕也就不需要發問了。
因為,詩,只能有一種:就是具備了「詩質」的文字。這種本質,深藏在詩人的心裡,有如美玉深藏在山中或水底一樣,是一種天賦,只能發掘和激發,卻絕對不能無中生有。要在文字裡發揮出這種「詩質」,才能稱為「詩」,要在被稱為是「詩」之後,才能再分為「好詩」與「壞詩」。就像再有瑕疵的玉,依舊是玉,而無論怎麼染色怎麼去用功打磨的石頭,它的本質永遠也只能是一塊石頭而已。
所以,那位發問者在提問題時,也許前提是先肯定了「詩人」與「寫詩的人」寫的都是「詩」,兩者的資質完全相同。
如果是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那麼,白靈和洛夫兩位先生的回答其實也言之成理。
白靈的回答可以解釋成是一種外在的附加價值。社會對這兩個名詞有不同的認定,如果要成為眾所公認的詩人,寫詩的人確實是需要一些時間和作品的累積的。
而洛夫的回答,則可以解釋成是一種內在的心理狀態,是因際遇不同所造成的區別。寂寞的詩人就是一個在沒有人要他的詩集的時候,依舊堅持地寫著詩的人。
當然,這兩種回答,仍然必須要在那位發問者的原意是對這兩個名詞都抱持肯定的態度時,才能算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我們假定,在他發問之前,對於「詩」這個字,是曾經謹慎地考慮過的。
不過,我們此刻無法找到他再來一問究竟,所以,也有可能,他的原意是比較接近向明所了解的意思──他對「詩人」比較肯定,而對「寫詩的人」隱含了否定的價值觀。
如果是這樣,向明的答覆才能算是正確。不過,在其中,我又有些不同的意見。
向明說:「詩人越天真寫出來的詩越可貴。」這點我完全同意。但是,「天真無邪」如夏日初發的芙蓉,可貴的就在那一瞬間的冰清玉潔,不過,人生能有幾次那樣的幸福?只要是不斷在成長著的人,心中就會不斷地染上塵埃。讀詩、寫詩,其實就是個體在無可奈何的沉淪中對潔淨的「初心」的渴望。我總覺得,這「渴望」本身,也能成為詩質,飽經世故之後的詩人,如果能夠在滄桑無奈之中還不失他的天真,恐怕是更為可貴的吧。
另外,向明認為,當詩人成為專為某種目的,或不得不寫的寫詩的人時,他已經降格為一個詩匠了。
對於「匠」這個名詞,我總覺得,中國傳統文人,實在是錯用了這個「匠」字。因為,一個能夠真正把他的工作做好的工匠,也需要才情。我們故宮所藏的那麼多或者精緻或者樸素的美麗器物,都是一些了不起的工匠聚精會神地做出來的。我想,大部分的文人即使你讓他去學三輩子,可能也做不到。所以,把「匠氣」拿來當作次等的文章或者書畫的形容詞,好像是很貼切,而其實又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我又回到先前的問題上來。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當一個詩人淪落到專為某種目的,或不得不寫的時候,他就已經不能再是詩人了。
「被世俗牽著鼻子去寫」的東西,就不能再稱為詩,詩人降格之後,便只能成為「自以為還在寫詩的人」。
當一位詩人變成了自以為還在寫詩的人之後,會因為每個人不同的性格,而讓他此後的生活變成了一場悲劇、喜劇,或者甚至是鬧劇。不過,如果他自己不會發現的話,也不會有什麼嚴重的傷害,頂多是他周圍的朋友有點「鬱卒」罷了。
比較恐怖的是那些從來不是詩人,但是一直以為自己是在寫詩評的人。因為萬一他又非常用功,幾十年下來著作等身,每一座圖書館裡都有他的書,那可真是讀者的大災難啊!
話扯遠了,再回到原處來吧。今天晚上,我把想到的種種先在電話裡說給曉風聽,像繞口令似的解釋了半天之後,她的回答是:
「我聽得都累死了!不過,我倒覺得,『詩人』只是個名詞,而『寫詩的人』裡有個動詞。名詞是別人給你的稱呼,是空的,固定的,遠不如『寫詩的人』裡這個動詞是自己可以控制,可以一直自由自在地寫詩。當然,最好的狀況是:又能是別人心中的詩人,又能不受影響地繼續做個寫詩的人。否則的話,如果只能二選一,我倒寧願做個可以一直寫下去的寫詩的人,而不是只有一個固定的空空的稱呼──詩人。」
好!這又來了一種精采說法!我當即徵求了同意把這段話放在最後。其實,仔細比較一下,她的意見和向明的結論非常相似,只是肯定與否定的對象互換了而已。
不知道那位當初發問的年輕詩人現在在什麼地方?會不會看到我們這些意見?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他要在創作的長路上面臨選擇,他到底是選擇名詞呢還是動詞?
一如天唱──再迎騰格爾
讀完騰格爾的自傳《天唱》,印象最深的是他父母的幾張相片。只有幾張,散置在書頁間,從黑白到彩色,從年輕到年老,當然逐漸受到歲月滄桑的改變,可是,卻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無邪、真誠與靜定的特質,始終如一地從他們身上顯現,是整個人、整個身體舉止的神態。
這應該就是孟馳北先生所說的「隱性文化」在游牧民族身上的具體顯現了。
孟馳北先生在他的《草原文化與人類歷史》上下兩冊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人們對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出土文物都看作價值連城的瑰寶,哪怕是一塊碎陶片都有人嘔心瀝血地研究,而對原始初民在數十萬年中對人類心理世界的塑造,卻鮮有人傾注探索的心血。人的心理世界原來也是一片蠻荒,或者說是一片空白,今天被人們稱之為『勇敢』『進取』『冒險』等心理現象,都是原始初民在時間長河中塑造出來的。」
在時間的長河中塑造出來的種種美德,是一種「隱性文化」,普遍表現在今天人類的身上,而在游牧民族身上表現得特別鮮明,所以,孟馳北先生說:「這種隱性文化可以說是草原文化的內核。」
時間的長河是綿延不絕的,同時也是流動著的,騰格爾,這位極為獨特的歌者,身為草原之子,當然也是從這樣深沉的文化中走出來的。
然而,我相信台灣的聽眾在他一九九二年首次來台的演唱現場上所受到的強烈感動,除了歌聲中素樸渾厚的生命之力外,還有一種驚訝和讚嘆,就是騰格爾能夠如此自由和自如地游走於傳統和現代、東方與西方之間,卻還能保有那種特質。就如樂評所說的:「一種嶄新的風格、一種淳樸、從未聽到過,甚至從未想到過的淳樸。」
而那年,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的演唱會是第二場,那天晚上,據朋友告訴我聽,來來去去的聽眾足足有三萬人次,現場的氣氛極為熱烈,騰格爾自己也記得:
「節目單上的唱完,翻唱了兩首不能再唱,觀眾就手拉手圍著台子,這邊喊『騰格爾騰格爾』,那邊嚷『再來一個再來一個』,真是山呼海嘯啊!」
對騰格爾來說是難忘的鼓勵,對當晚的聽眾來說,也是難忘的「鼓勵」,就好像是有什麼可以從歌聲裡走出來,鼓舞你、激勵你,提醒你原來一直深藏在心裡的竟然有那麼多美好的質素。
一九六○年一月十五日生在內蒙古鄂爾多斯鄂托克旗額爾和圖蘇木,騰格爾的家鄉曾經是豐饒美麗的。「那是一種天地人和的美,純自然的大美,語言無法描述。現在已經看不到這樣的大美了,可是它完整地保留在我童年的記憶中,影響著並且將繼續影響我的一生。」
影響著他一生的應該還有鄂爾多斯的民歌。在這一處高原上,民歌多如海洋中的波光,而騰格爾的父母都唱,「年輕的時候特別會唱,現在也還唱。我父親知道的民歌之多,在我們那兒是數一數二的。」
騰格爾曾經寫過一首〈古老的歌〉,在其中就插進去一段父親最愛唱的民歌。每當他抱起吉他唱這首歌的時候,還特別努力模仿父親吟唱時的風格,讓有時會在座的父親,覺得特別歡喜。
騰格爾的父親還喜歡他寫的另一首歌,就是〈父親和我〉。
但是,騰格爾的父親也就喜歡這兩首歌,其他的都不怎麼在意。
騰格爾的母親就更不在意了,因為,她唱的是道地的民歌。
騰格爾說:「民歌就是這樣,記錄著、積淀著從古至今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相似的、共通的、永恆的人類情感。由此決定了它天長地久、不可抗拒的魅力。」
騰格爾唱的,和他父母唱的並不一樣,然而,在心底,他其實是羨慕的--因為他們不表演、不作秀,只在乎自己的內心感受,整個人沉浸在自己的歌聲裡,如此的專注與虔誠。
騰格爾說:「這就是民歌,這樣唱歌的人,那才叫真正的歌手。我知道現在我做不了這樣的歌手,但我心裡有一個這樣的歌手,總有一天我會成這樣的歌手──在我不再是一個『歌手』的時候。」
現在的騰格爾,還有許許多多的夢想與試驗在等待實現。
一九九三年成立迄今的「蒼狼樂隊」就是其中之一。
帶著「蒼狼樂隊」,騰格爾走遍國內外,一首又一首的新歌不斷唱出來,一張又一張的唱片不斷發行,也不斷得到許多獎項的鼓勵。
同時,在草原的深處,你也可以聽到有人在騎馬橫渡的時候遠遠地唱著〈蒙古人〉〈蒼狼大地〉〈父親和我〉以及〈天堂〉……
我就常常遇到這樣的時刻,在內蒙古阿拉善盟荒漠化了的草原上,在鄂爾多斯成陵一處無人的階梯之下,在新疆阿爾泰山麓邊一座小旅舍裡,總有人會在忽然間唱起了騰格爾的歌:「……駿馬失去了主人/獵狗失去了駿馬/蒼狼大地一片黃沙/豐美草原幾度寂寞/啊哈呼……」
騰格爾啊,騰格爾,你可知道,其實民歌就是這樣。記錄著、積淀著從古至今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這不就是你自己說的嗎?
每一代都不是一池死水,每一代都是有從四方八面奔湧過來的不同的源泉,今天你所寫出來的歌,將會有一部分成為明天的民歌,因為,正是你,充滿了夢想,充滿了勇氣往世界各地走去,才有可能讓你的歌終於成為一種共通的,永恆的人類情感,由此決定了它天長地久、不可抗拒的魅力。
我知道你很喜歡自己的名字「騰格爾」,在蒙文裡是指「天」、「天神」以及「廣大無邊」之意。所以,祝福你有一日終於會達到你的願望:「一如天唱。」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執筆的欲望
9折
特價441元
加入購物車
英雄時代
9折
特價360元
加入購物車
胡馬依北風
9折
特價333元
加入購物車
當夏夜芳馥:席慕蓉畫作精選集
9折
特價495元
加入購物車
我給記憶命名
9折
特價360元
加入購物車
除你之外
9折
特價315元
加入購物車
寫給海日汗的 21 封信
9折
特價342元
加入購物車
金色的馬鞍
9折
特價306元
加入購物車
回顧所來徑
9折
特價252元
加入購物車
給我一個島
9折
特價288元
加入購物車
晨讀10分鐘:青春無敵早點詩—中學生新詩選
9折
特價252元
貨到通知
大師說故事:蝸牛先生的名言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以詩之名
9折
特價315元
加入購物車
席慕蓉精選集
9折
特價342元
停售
寧靜的巨大
9折
特價261元
加入購物車
2006/席慕蓉(足本)
9折
特價405元
停售
2006/席慕蓉(7月-12月)
9折
特價288元
加入購物車
邊緣光影
9折
特價243元
加入購物車
迷途詩冊(32開)
9折
特價198元
加入購物車
時光九篇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我摺疊著我的愛
9折
特價216元
加入購物車
百年遊記II山.水.樓.園
9折
特價261元
貨到通知
席慕蓉.世紀詩選
9折
特價162元
加入購物車
無怨的青春
9折
特價189元
加入購物車
七里香
9折
特價189元
加入購物車
評論十家(第二集)
9折
特價162元
加入購物車
寫生者
9折
特價162元
加入購物車
江山有待
9折
特價198元
加入購物車
看更多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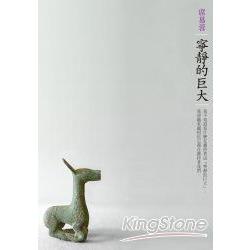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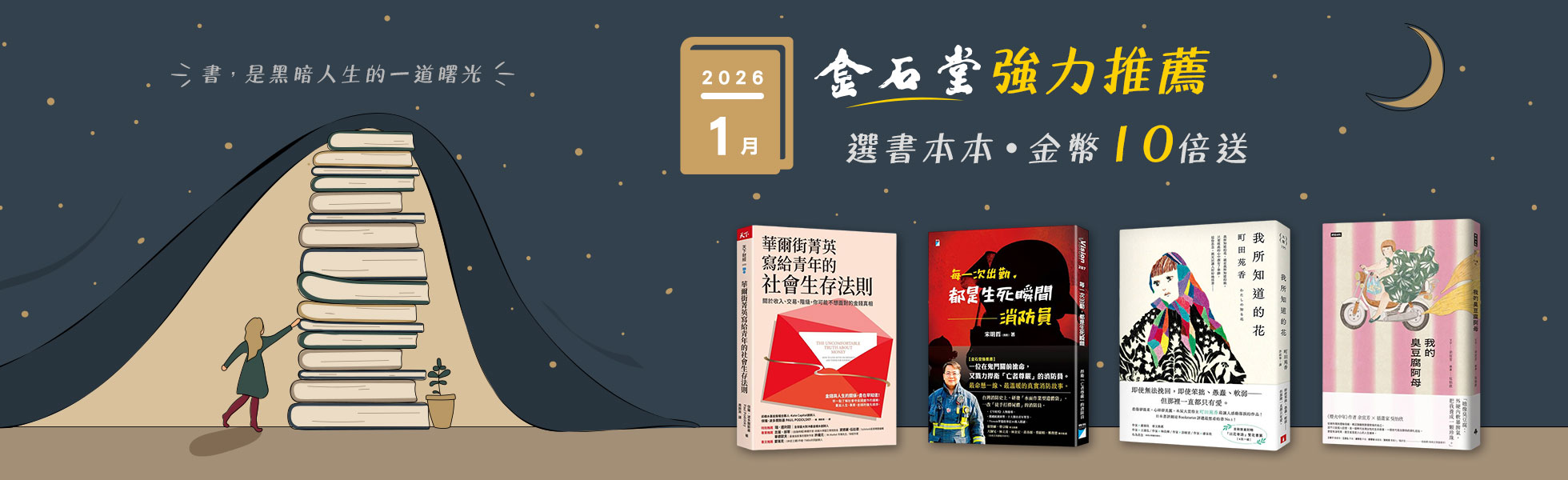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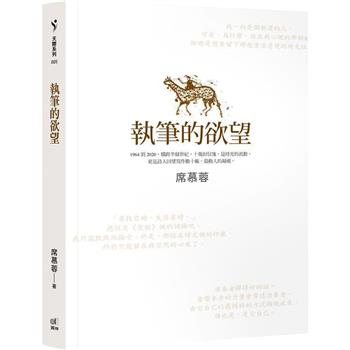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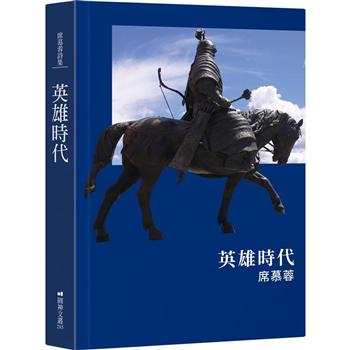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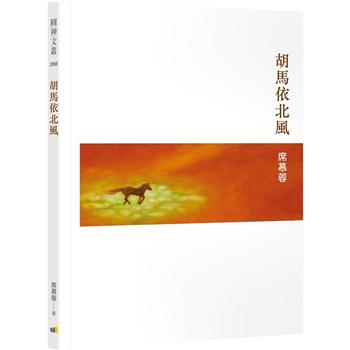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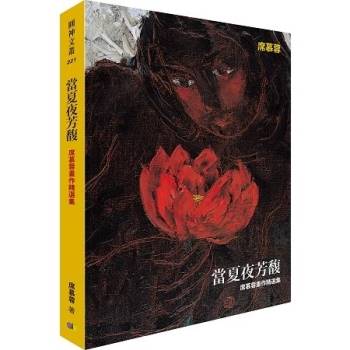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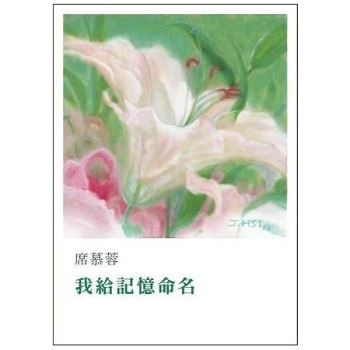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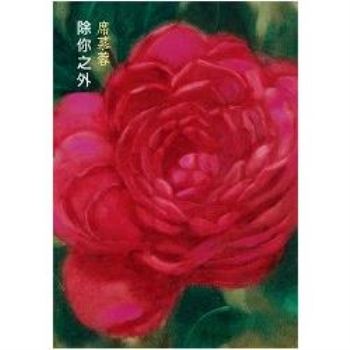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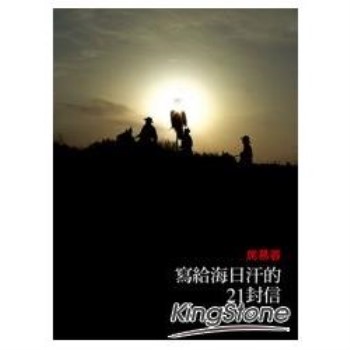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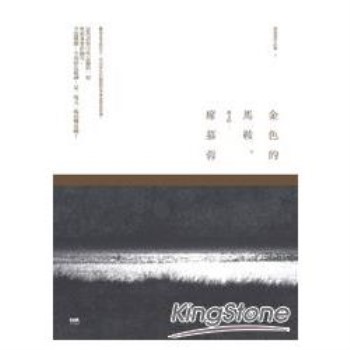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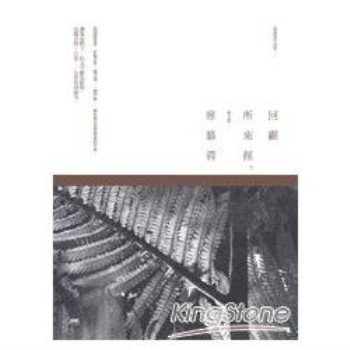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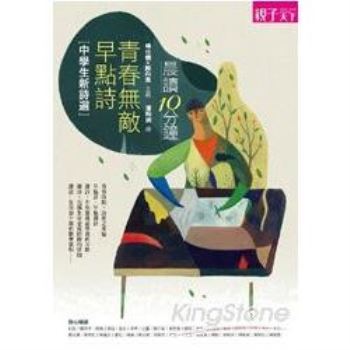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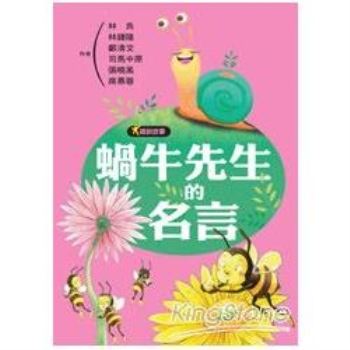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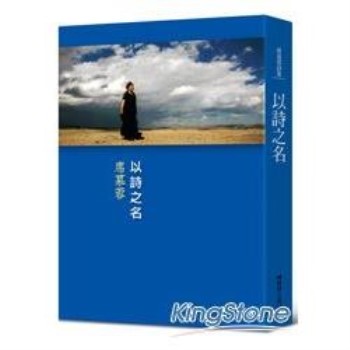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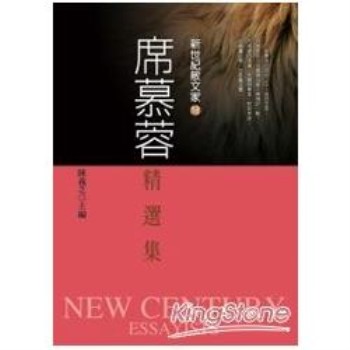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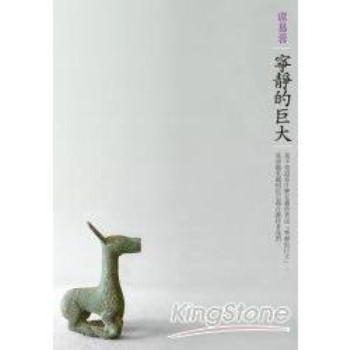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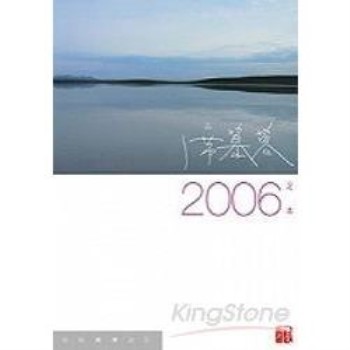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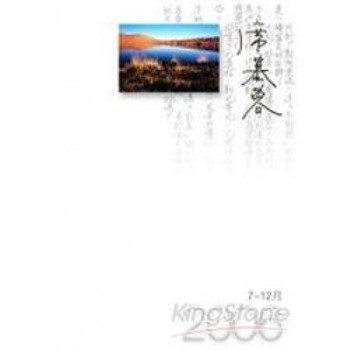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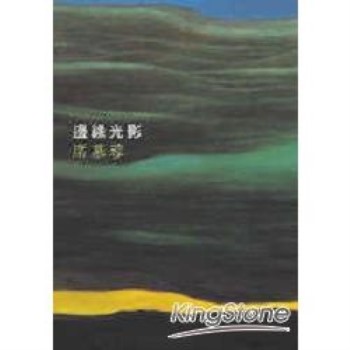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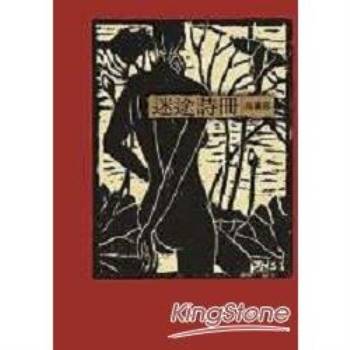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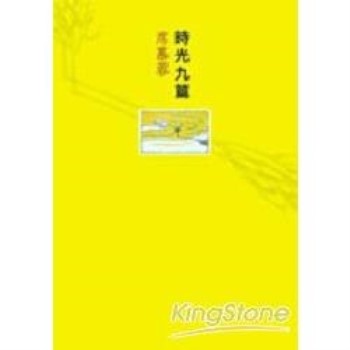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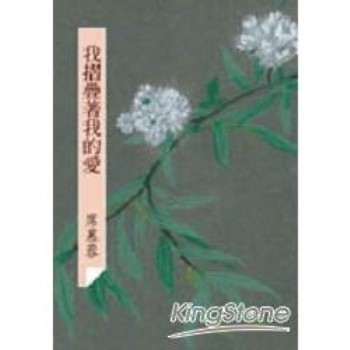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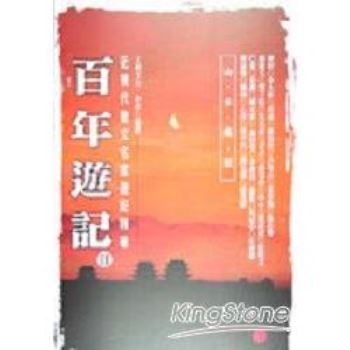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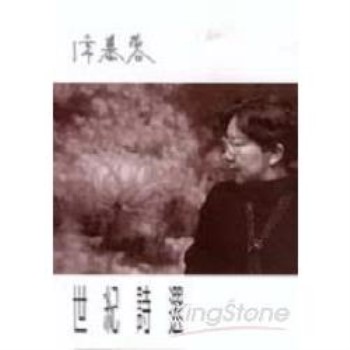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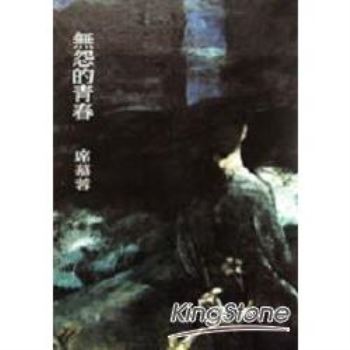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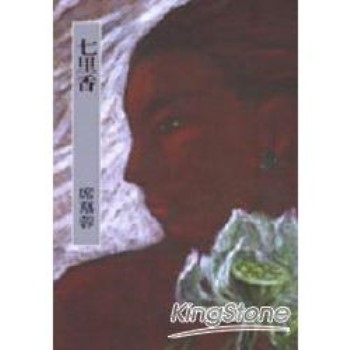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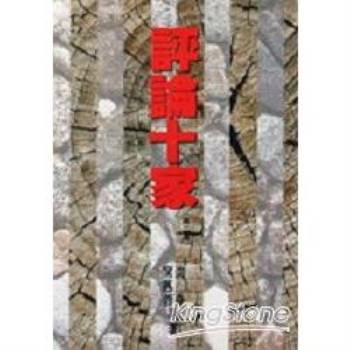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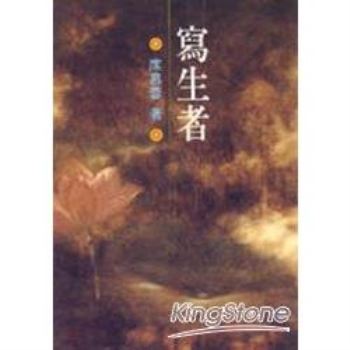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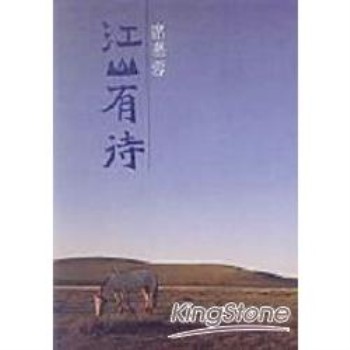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