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消息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小說家怎麼讀書?讀些什麼書?不同的讀物如何在作家的心上啟動不同的化學變化?
張亦絢第一本非小說創作,點名一百多本引她在思索間或發笑、或落淚的書,類別不拘,上至天文地理數學哲學,下至文學偵探心靈勵志。來看看小說家的書單和你有何不同!
如果我是小學生,我可以這樣寫我的讀書心得報告嗎?
史上最用心、最任性的讀書心得報告135篇!
張亦絢第一本非小說創作,點名一百多本引她在思索間或發笑、或落淚的書,類別不拘,上至天文地理數學哲學,下至文學偵探心靈勵志。來看看小說家的書單和你有何不同!
如果我是小學生,我可以這樣寫我的讀書心得報告嗎?
史上最用心、最任性的讀書心得報告135篇!
名人推薦
蔡珠兒、孫梓評、徐玫怡、神小風 搖頭不已推薦
「哇哇哇,太放肆了,怎麼可以這樣?好一個文字頑童,歡恣奔放,生猛鬼馬,總是趁虛欺近,挨過來呵口癢,捏一下,踩一腳,打了火速就跑,輕功一跳三丈高,你追也追不到,防也防不著。她那打法又無賴,輕輕一下,卻能點穴挑筋,讓你或者酥麻,或者爆笑,或者癢不可耐,或者,癱在那裡,無語問蒼天。」——蔡珠兒
「偷窺自己喜愛的小說家平常都讀些什麼,心裡愉快,但腦子很忙,首先要暗中比對讀過的書所殘餘的印象,隨即得迎接那些扔擲而來的發亮話語,其『重點之所不在』們,究竟聲東擊西了什麼?在藏得剛剛好的聰明之中,煙火般綻開的,有閱讀者的脾氣,生活者的關心,書寫者的氣勢,觀察者的細膩……偶爾夾帶一點純情者的天真,不知怎的,總使我想起那句,『精緻的淘氣』。」——孫梓評
「和她說話;忍不住想追問更多;看她寫書,免不了想一路讀下去,這是小說家張亦絢的強大魅力,叫人心甘情願的跟隨。更重要的是,她喚醒了閱讀的「自由」--這個在學校課堂裡可能從未被人想起來,卻多麼寶貴的字眼。歪路往往最迷人,也真沒那麼好走;但張亦絢走得那麼快活、那麼精神,那是她對書理直氣壯的愛意。愛有很多、很多,但本著讀書人的義氣,她總會〈非常貼心的〉留下點空白,讓你自己去懂。」——神小風
「我看了張亦絢的新書了,很快的瀏覽!心中一直跑出一個聲音:我不能推薦張亦絢,我不能 ~ 應該是拜託她推薦我吧!這個女生太奇異了,她提到的太多書我都沒看過,我只是二十年前認識她就知道她是個腦袋裡裝了特別大量聰慧敏感奇妙內容的孩子,但憑這樣實在沒有資格推薦她。張亦絢,妳的作品很好,但要我推薦,我會覺得:徐玫怡,妳怎麼好意思ㄌㄟ!!」——徐玫怡
「哇哇哇,太放肆了,怎麼可以這樣?好一個文字頑童,歡恣奔放,生猛鬼馬,總是趁虛欺近,挨過來呵口癢,捏一下,踩一腳,打了火速就跑,輕功一跳三丈高,你追也追不到,防也防不著。她那打法又無賴,輕輕一下,卻能點穴挑筋,讓你或者酥麻,或者爆笑,或者癢不可耐,或者,癱在那裡,無語問蒼天。」——蔡珠兒
「偷窺自己喜愛的小說家平常都讀些什麼,心裡愉快,但腦子很忙,首先要暗中比對讀過的書所殘餘的印象,隨即得迎接那些扔擲而來的發亮話語,其『重點之所不在』們,究竟聲東擊西了什麼?在藏得剛剛好的聰明之中,煙火般綻開的,有閱讀者的脾氣,生活者的關心,書寫者的氣勢,觀察者的細膩……偶爾夾帶一點純情者的天真,不知怎的,總使我想起那句,『精緻的淘氣』。」——孫梓評
「和她說話;忍不住想追問更多;看她寫書,免不了想一路讀下去,這是小說家張亦絢的強大魅力,叫人心甘情願的跟隨。更重要的是,她喚醒了閱讀的「自由」--這個在學校課堂裡可能從未被人想起來,卻多麼寶貴的字眼。歪路往往最迷人,也真沒那麼好走;但張亦絢走得那麼快活、那麼精神,那是她對書理直氣壯的愛意。愛有很多、很多,但本著讀書人的義氣,她總會〈非常貼心的〉留下點空白,讓你自己去懂。」——神小風
「我看了張亦絢的新書了,很快的瀏覽!心中一直跑出一個聲音:我不能推薦張亦絢,我不能 ~ 應該是拜託她推薦我吧!這個女生太奇異了,她提到的太多書我都沒看過,我只是二十年前認識她就知道她是個腦袋裡裝了特別大量聰慧敏感奇妙內容的孩子,但憑這樣實在沒有資格推薦她。張亦絢,妳的作品很好,但要我推薦,我會覺得:徐玫怡,妳怎麼好意思ㄌㄟ!!」——徐玫怡
編輯推薦
讀書像遠足快樂聊天吃零食,觀點又靚又犀利!
本書是小說家張亦絢的135篇讀書心得報告,也是第一本非小說創作,點名一百多本引她在思索間或發笑、或落淚的書,類別不拘,上至天文地理數學哲學,下至文學偵探心靈勵志。書中有段寫到:「比如很久以前看的佛斯特的《小說面面觀》,多好的一本書,但是我在跟朋友聊到時,總忍不住千叮萬囑:『這是很好的一本書,但作者說小說不常處理到睡眠這個主題,這是不對的,他怎麼可以忘記《織工馬南傳》呢?』」小編覺得實在詼諧有趣,透過本書,讀者將一窺小說家怎麼讀書?讀些什麼書?不同的讀物如何在作家的心上啟動不同的化學變化?趕快來瞧瞧小說家的書單和你有何不同吧!
序/導讀
前言
寫在前面一
小道消息 厚此薄彼
《愛的不久時》出版後,大家都很捧場地贊同我:對對對,這真的是一本冬天可以放進大衣口袋的書--但各位捧場歸捧場,也太不嚴謹了吧?你們誰的冬大衣口袋那麼大呀?我拿到《愛》的成書時,有點意外:原來還是一本有厚度的書啊。捲不起來。我原本的願望是出一本特薄的,就是那種在書架上一不小心就會被擠到看不見,再一不小心才會又突然被發現--生於夾縫,獨木難支卻要支,羊腸小道、一縷幽魂,永遠介於被遺忘與掉下來之間的--狀況緊急時還可以一口吞進肚子裡--好了,我說夠了。
大學時代有學姐給我們做心理測驗,要我們選一個飲料罐,我選了窄的可以圈在手掌虎口裡的那種罐子。「這就是妳選情人的態度!」算命仙慈悲微笑,彷彿見到什麼天機:「妳需要一個可以握在手裡的情人。」握壽司情人?這是什麼樣子?我看電影看話劇都不怕長,八九小時的東西也一定要看,還吵鬧別人也得去看。獨書一厚就惹我生氣--不是內容長度的問題,而是它的大體形令我感到如同死亡的威脅。像揮舞的狼牙棒什麼的。德州電鋸。
電影系有些教科書,印了大量照片又不肯分冊出,光是從架上拿出來都讓我覺得有引發內外傷的可能。每次看到負責出版的教授,我都暗忖:這個人把書出成了可以斷手斷腳的東西耶。恨。但是,對薄書的戀戀是怎麼回事啊?我自己偷偷精神分析了一下,有了答案。
不過這可不關各位讀者的事。重要的是我「出本小書」的心願得償,這並非我的理想書架,我只是隨著情緒寫它,有衝動就寫,沒有就不寫。在小小的完美的衝動中寫它。如同小孩時代在地上快樂地滾兩下的那種衝動。目的不明,原因更不明,只有身體,身體它是高高興興的。
寫在前面二
親愛的書,所有的壞脾氣,與一切的好情緒
我在看書這事上有十足的壞脾氣與好情緒。一知道有人下筆有了我感覺上的差池,我往往深印腦海,永生不忘。比如很久以前看的佛斯特的《小說面面觀》,多好的一本書,但是我在跟朋友聊到時,總忍不住千叮萬囑:「這是很好的一本書,但作者說小說不常處理到睡眠這個主題,這是不對的,他怎麼可以忘記《織工馬南傳》呢?這個小說睡眠就佔有很大的重要性。如果妳讀到這的時候,不要忘記《織工馬南傳》。」我朋友是一個正常不已的人,她立刻嘆口氣說:「這位佛斯特先生真可憐,只不過是忘了提《織工馬南傳》,就被小姐妳碎碎唸到今天。」我這才有點回過神來,發現自己有多偏執與可笑。
不過這種對書反常的記憶與愛好,也有它溫柔可人的一面地。話說我曾經覺得某些作者不對我脾胃,可是只要發現他/她們讀過某書,我在心理馬上就對他/她們前嫌盡釋,在心中不斷跟對方握手:「我雖然不喜歡你/妳,但只要想到你/妳連赫爾岑的書都唸過,嗯,或許你/妳也是不錯的人吧。」或是對某某我也一向有意見,但之後又會在心裡道:想到某某某連某某書也讀過,我對於他/她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原諒!當然,偶而我也會有「什麼!沒看過這書,我難以原諒!」這種完全自我中心的不當譴責。我就是這樣一個不近人情的傢伙啊。
看書這件事嘛,是這樣豐富人生地:年輕時讀亨利米勒的《南迴歸線》等書,覺得沒多大意思。後來得知他是楚浮很喜歡的作者,他的書曾是楚浮反覆閱讀的案頭書,因為我很看重楚浮,便一面想像「楚浮究竟看到了些什麼」那樣去重讀亨利米勒,雖然不到因此就喜歡上亨利米勒的地步,但總也是有了另一番體會。覺得彷彿一口氣走過三個人的人生:楚浮的、米勒的、我自己的。所以看書這件事,真可以是綿延一生,不斷增補的一個過程。
小時候,我有每隔一陣子就去檢查書中我喜愛的段落是否在書中安好無恙的,幾乎是動物性的習慣。我阿嬤老來喜歡把曾經愛過的衣服不時攤出來,不要穿,只是看一看;那種感情就是完全無關實用性了,是種類似戀物的繾綣與打開記憶寶盒的動作。在法國多年,最痛苦的,當然就是幾乎沒有足夠的中文書可看,也不可能重覆我從小養成的定期檢閱活動。想到喜歡的段落,只能空想著。當然也有另個原因,就是覺得要把握一切時間看那裡的法文書,中文書是用來治感冒的,等閒時間不碰。巴黎原來有個服務華僑的大型中文圖書館,我原來拿它一月犒賞自己一次異國的辛苦生活,但它後來也關閉了。
開始還偶爾拜託朋友寄,可我看書的習慣冷僻,有次想要一本台灣史料的書,都跟我說找不到,可我在心裡清清楚楚記得它在唐山書店的那個方位,可是人在遠方,不可能飛回來從架中把書抽出來給對方看,那股難過勁,真是沒法說。回台灣沒多久,我去唐山,十年過去了,那本書確實仍在我記憶中方位所在。不偏不倚,多麼幸福。在大學讀書時,電影藝術那兩大排是走慣了的,我就像身體裡有一個反射鏡般在身體裡用拍照法把它們都在敝人體中直接歸了位,可以憑感覺立刻摸到它們,也覺得它們就駐守在我身體裡似的。有一次或許是因為大批新書來到的關係吧,圖書館把書的次序換了方式排列,這就實實在在令我感到生理上的嚴重不適,頭昏眼花了好幾天,好像積木被推倒在我身體裡面亂成一團,又像有人趁我不注意竄改了我的染色體密碼一般。
二十歲,我就開始一定程度的居無定所與四處漂泊。再喜歡的書,都不留。為了保持高度的機動性,除了工具書教科書留著外,就算是愛書,也都養成看完就送人送社福送圖書館的習慣。禁止感情用事。有時候,我對自己說:這麼好的書,一定會再版,想看就去圖書館或去書店翻就好。但是後來發現這想法錯得厲害。送掉的好書往往沒有再版或是連圖書館都找不到,我於是迫不得已養成筆記習慣;這倒不是人們以為的小說家的閱讀摘要,坦白說是相當形而下的存證動作,好比臉書上有人給自己的三餐菜色拍照留念。對我來說,既然我原以為可以倚靠的出版業或圖書館未必與我對書的評價意見一致,為了我個人健康或是不健康--神經質的需求,我總抄一點寫一點書的什麼,以備有天該書在這世上滅絕之際,我還留有我私人的一個「抄本」。我是極端極端自私的,圖書館或出版業有什麼走向,我只有興致來時才關心一下,這個對書的記念,主要的功能乃是維持我個人身心的平衡。有天我發現我的日記裡實在不成比例有著太多對書的好發議論了,為了校正自己--不要問我為什麼校正,我就是那種沒事就會興起校正自己想法的那種人-- 我規定自己對書的喜好要有節制,最初好像是規定對一本書只可寫三行吧?可這實在太痛苦,沒講幾句就得收尾,所以後來寬容到六行,就像有人自己規定一天一根煙,固然可以過癮,但癮頭也不可以太大。
這個習慣便是《小道消息》的前身。到了真正動筆,又做了一點調整,一度我想叫它《關於書的幸福八卦書》。只因我覺得八卦這個東西是很有趣的,早年早年的時候,我曾注意到一兩位影藝版的記者,會以很巧妙的八卦,把一些就當時來說前衛的觀念散播出去,使我一度興起研究「有益社會的八卦」這樣的念頭。但要說「營養的八卦」可也不太對勁,八卦的趣味還是在它看似沒營養的樣貌上。
正常情況下,寫書評要針對一本書的要旨說話,要評估讀者所需要的背景輔助,種種考慮下,書評能夠寫的,有很多限制,但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像我這樣,一本書只取對我有意義的一段甚至一句話,或是,有如個人備忘錄般地叫出不同書中的片段一起說嘴,可說完完全全是種旁門左道之法。不過我本是有些邪僻之人,年紀漸長,對自己之外任何人任何物所加的限制,更以「吾生也有涯」為由,眼睛一閉就繞過了。讀書時繳報告,法國教授喜歡用的嘉許評語之一是「高度個人化的作品」,現下我這本書的唯一一個優點大概也就是這了,除了個人化之外,身無長物呢。小說固然有類型名為「私小說」,我這種寫法大概可稱為「私筆記」了。蘇珊.宋塔有本書的書名叫《重點所在》,我在龐畢度中心下頭的書店看到封面上的書名,馬上想,如是我,可要來寫一本書叫《重點之所不在》,所以輯一輯二就用上這個老想法;後來想另起一輯把法文書的部份集中起來,名為〈昨日巴黎〉;之後又寫〈地球觀光客〉與〈一言難盡點唱機〉兩輯,真是為寫得高興,雖然偶爾會想「應該要寫這應該要寫那」,但後來真的放自己很多馬地決定,應該就不寫,想寫才要寫。
至於書名《小道消息》,大概是我書名中最不奇怪的一個了,我自己非常喜歡。從小到大,不論是課堂上的老師或遇見的人們,一有人一臉愧意害羞猶豫地聲明:我有幾句不太重要的題外話要說......--每回這話一到,總是有些真正有味道的話可以聽的時刻來了-- 如果有讀者是張迷,這裡也就借用〈姑姑語錄〉中「有意思的話」 的典故,但願,對各位讀者,這本書可以是獻給你/妳們的一些,「有意思的話」。但願你/妳們可以跟我一起享受--《小道消息》。
後記
記我最愛的電影,我最愛的電影對話:
他問:「妳最近做些什麼?」
她答:「我在好好照顧我自己,我把我自己照顧得很好。」
寫在前面一
小道消息 厚此薄彼
《愛的不久時》出版後,大家都很捧場地贊同我:對對對,這真的是一本冬天可以放進大衣口袋的書--但各位捧場歸捧場,也太不嚴謹了吧?你們誰的冬大衣口袋那麼大呀?我拿到《愛》的成書時,有點意外:原來還是一本有厚度的書啊。捲不起來。我原本的願望是出一本特薄的,就是那種在書架上一不小心就會被擠到看不見,再一不小心才會又突然被發現--生於夾縫,獨木難支卻要支,羊腸小道、一縷幽魂,永遠介於被遺忘與掉下來之間的--狀況緊急時還可以一口吞進肚子裡--好了,我說夠了。
大學時代有學姐給我們做心理測驗,要我們選一個飲料罐,我選了窄的可以圈在手掌虎口裡的那種罐子。「這就是妳選情人的態度!」算命仙慈悲微笑,彷彿見到什麼天機:「妳需要一個可以握在手裡的情人。」握壽司情人?這是什麼樣子?我看電影看話劇都不怕長,八九小時的東西也一定要看,還吵鬧別人也得去看。獨書一厚就惹我生氣--不是內容長度的問題,而是它的大體形令我感到如同死亡的威脅。像揮舞的狼牙棒什麼的。德州電鋸。
電影系有些教科書,印了大量照片又不肯分冊出,光是從架上拿出來都讓我覺得有引發內外傷的可能。每次看到負責出版的教授,我都暗忖:這個人把書出成了可以斷手斷腳的東西耶。恨。但是,對薄書的戀戀是怎麼回事啊?我自己偷偷精神分析了一下,有了答案。
不過這可不關各位讀者的事。重要的是我「出本小書」的心願得償,這並非我的理想書架,我只是隨著情緒寫它,有衝動就寫,沒有就不寫。在小小的完美的衝動中寫它。如同小孩時代在地上快樂地滾兩下的那種衝動。目的不明,原因更不明,只有身體,身體它是高高興興的。
寫在前面二
親愛的書,所有的壞脾氣,與一切的好情緒
我在看書這事上有十足的壞脾氣與好情緒。一知道有人下筆有了我感覺上的差池,我往往深印腦海,永生不忘。比如很久以前看的佛斯特的《小說面面觀》,多好的一本書,但是我在跟朋友聊到時,總忍不住千叮萬囑:「這是很好的一本書,但作者說小說不常處理到睡眠這個主題,這是不對的,他怎麼可以忘記《織工馬南傳》呢?這個小說睡眠就佔有很大的重要性。如果妳讀到這的時候,不要忘記《織工馬南傳》。」我朋友是一個正常不已的人,她立刻嘆口氣說:「這位佛斯特先生真可憐,只不過是忘了提《織工馬南傳》,就被小姐妳碎碎唸到今天。」我這才有點回過神來,發現自己有多偏執與可笑。
不過這種對書反常的記憶與愛好,也有它溫柔可人的一面地。話說我曾經覺得某些作者不對我脾胃,可是只要發現他/她們讀過某書,我在心理馬上就對他/她們前嫌盡釋,在心中不斷跟對方握手:「我雖然不喜歡你/妳,但只要想到你/妳連赫爾岑的書都唸過,嗯,或許你/妳也是不錯的人吧。」或是對某某我也一向有意見,但之後又會在心裡道:想到某某某連某某書也讀過,我對於他/她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原諒!當然,偶而我也會有「什麼!沒看過這書,我難以原諒!」這種完全自我中心的不當譴責。我就是這樣一個不近人情的傢伙啊。
看書這件事嘛,是這樣豐富人生地:年輕時讀亨利米勒的《南迴歸線》等書,覺得沒多大意思。後來得知他是楚浮很喜歡的作者,他的書曾是楚浮反覆閱讀的案頭書,因為我很看重楚浮,便一面想像「楚浮究竟看到了些什麼」那樣去重讀亨利米勒,雖然不到因此就喜歡上亨利米勒的地步,但總也是有了另一番體會。覺得彷彿一口氣走過三個人的人生:楚浮的、米勒的、我自己的。所以看書這件事,真可以是綿延一生,不斷增補的一個過程。
小時候,我有每隔一陣子就去檢查書中我喜愛的段落是否在書中安好無恙的,幾乎是動物性的習慣。我阿嬤老來喜歡把曾經愛過的衣服不時攤出來,不要穿,只是看一看;那種感情就是完全無關實用性了,是種類似戀物的繾綣與打開記憶寶盒的動作。在法國多年,最痛苦的,當然就是幾乎沒有足夠的中文書可看,也不可能重覆我從小養成的定期檢閱活動。想到喜歡的段落,只能空想著。當然也有另個原因,就是覺得要把握一切時間看那裡的法文書,中文書是用來治感冒的,等閒時間不碰。巴黎原來有個服務華僑的大型中文圖書館,我原來拿它一月犒賞自己一次異國的辛苦生活,但它後來也關閉了。
開始還偶爾拜託朋友寄,可我看書的習慣冷僻,有次想要一本台灣史料的書,都跟我說找不到,可我在心裡清清楚楚記得它在唐山書店的那個方位,可是人在遠方,不可能飛回來從架中把書抽出來給對方看,那股難過勁,真是沒法說。回台灣沒多久,我去唐山,十年過去了,那本書確實仍在我記憶中方位所在。不偏不倚,多麼幸福。在大學讀書時,電影藝術那兩大排是走慣了的,我就像身體裡有一個反射鏡般在身體裡用拍照法把它們都在敝人體中直接歸了位,可以憑感覺立刻摸到它們,也覺得它們就駐守在我身體裡似的。有一次或許是因為大批新書來到的關係吧,圖書館把書的次序換了方式排列,這就實實在在令我感到生理上的嚴重不適,頭昏眼花了好幾天,好像積木被推倒在我身體裡面亂成一團,又像有人趁我不注意竄改了我的染色體密碼一般。
二十歲,我就開始一定程度的居無定所與四處漂泊。再喜歡的書,都不留。為了保持高度的機動性,除了工具書教科書留著外,就算是愛書,也都養成看完就送人送社福送圖書館的習慣。禁止感情用事。有時候,我對自己說:這麼好的書,一定會再版,想看就去圖書館或去書店翻就好。但是後來發現這想法錯得厲害。送掉的好書往往沒有再版或是連圖書館都找不到,我於是迫不得已養成筆記習慣;這倒不是人們以為的小說家的閱讀摘要,坦白說是相當形而下的存證動作,好比臉書上有人給自己的三餐菜色拍照留念。對我來說,既然我原以為可以倚靠的出版業或圖書館未必與我對書的評價意見一致,為了我個人健康或是不健康--神經質的需求,我總抄一點寫一點書的什麼,以備有天該書在這世上滅絕之際,我還留有我私人的一個「抄本」。我是極端極端自私的,圖書館或出版業有什麼走向,我只有興致來時才關心一下,這個對書的記念,主要的功能乃是維持我個人身心的平衡。有天我發現我的日記裡實在不成比例有著太多對書的好發議論了,為了校正自己--不要問我為什麼校正,我就是那種沒事就會興起校正自己想法的那種人-- 我規定自己對書的喜好要有節制,最初好像是規定對一本書只可寫三行吧?可這實在太痛苦,沒講幾句就得收尾,所以後來寬容到六行,就像有人自己規定一天一根煙,固然可以過癮,但癮頭也不可以太大。
這個習慣便是《小道消息》的前身。到了真正動筆,又做了一點調整,一度我想叫它《關於書的幸福八卦書》。只因我覺得八卦這個東西是很有趣的,早年早年的時候,我曾注意到一兩位影藝版的記者,會以很巧妙的八卦,把一些就當時來說前衛的觀念散播出去,使我一度興起研究「有益社會的八卦」這樣的念頭。但要說「營養的八卦」可也不太對勁,八卦的趣味還是在它看似沒營養的樣貌上。
正常情況下,寫書評要針對一本書的要旨說話,要評估讀者所需要的背景輔助,種種考慮下,書評能夠寫的,有很多限制,但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像我這樣,一本書只取對我有意義的一段甚至一句話,或是,有如個人備忘錄般地叫出不同書中的片段一起說嘴,可說完完全全是種旁門左道之法。不過我本是有些邪僻之人,年紀漸長,對自己之外任何人任何物所加的限制,更以「吾生也有涯」為由,眼睛一閉就繞過了。讀書時繳報告,法國教授喜歡用的嘉許評語之一是「高度個人化的作品」,現下我這本書的唯一一個優點大概也就是這了,除了個人化之外,身無長物呢。小說固然有類型名為「私小說」,我這種寫法大概可稱為「私筆記」了。蘇珊.宋塔有本書的書名叫《重點所在》,我在龐畢度中心下頭的書店看到封面上的書名,馬上想,如是我,可要來寫一本書叫《重點之所不在》,所以輯一輯二就用上這個老想法;後來想另起一輯把法文書的部份集中起來,名為〈昨日巴黎〉;之後又寫〈地球觀光客〉與〈一言難盡點唱機〉兩輯,真是為寫得高興,雖然偶爾會想「應該要寫這應該要寫那」,但後來真的放自己很多馬地決定,應該就不寫,想寫才要寫。
至於書名《小道消息》,大概是我書名中最不奇怪的一個了,我自己非常喜歡。從小到大,不論是課堂上的老師或遇見的人們,一有人一臉愧意害羞猶豫地聲明:我有幾句不太重要的題外話要說......--每回這話一到,總是有些真正有味道的話可以聽的時刻來了-- 如果有讀者是張迷,這裡也就借用〈姑姑語錄〉中「有意思的話」 的典故,但願,對各位讀者,這本書可以是獻給你/妳們的一些,「有意思的話」。但願你/妳們可以跟我一起享受--《小道消息》。
後記
記我最愛的電影,我最愛的電影對話:
他問:「妳最近做些什麼?」
她答:「我在好好照顧我自己,我把我自己照顧得很好。」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感情百物 (限量簽名版)
9折
特價405元
停售
感情百物
9折
特價405元
加入購物車
九歌109年小說選
9折
特價378元
加入購物車
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9折
特價288元
加入購物車
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錄(2020我行我素版)
9折
特價315元
加入購物車
我討厭過的大人們 ( 限量簽名版 )
9折
特價288元
停售
性意思史:張亦絢短篇小說集
9折
特價306元
貨到通知
性意思史:張亦絢短篇小說集(限量簽名版)
9折
特價306元
停售
看電影的慾望
9折
特價297元
加入購物車
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
9折
特價252元
加入購物車
小道消息
9折
特價252元
貨到通知
愛的不久時:南特/巴黎回憶錄
9折
特價270元
貨到通知
看更多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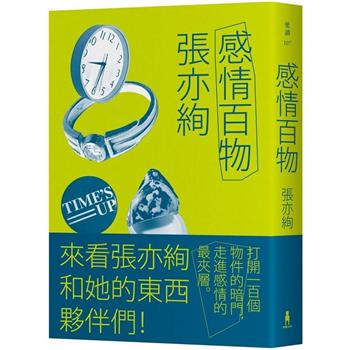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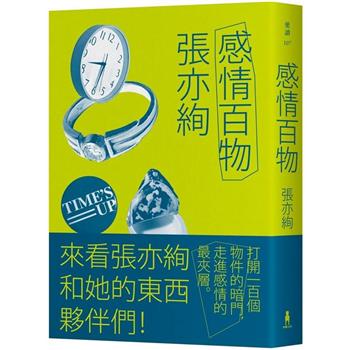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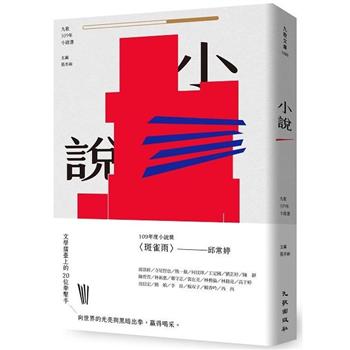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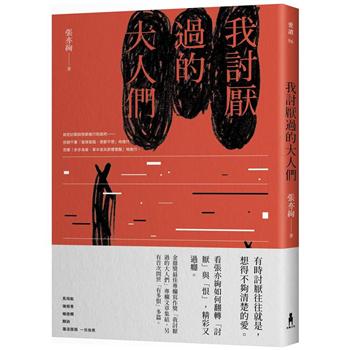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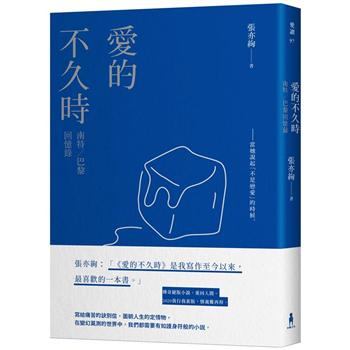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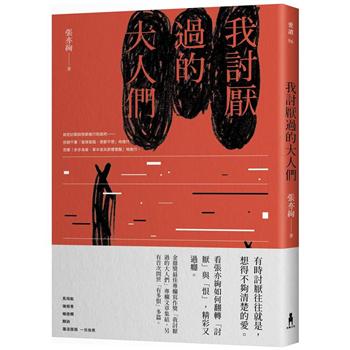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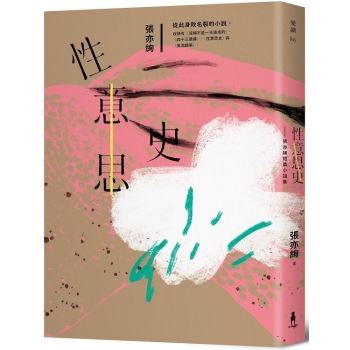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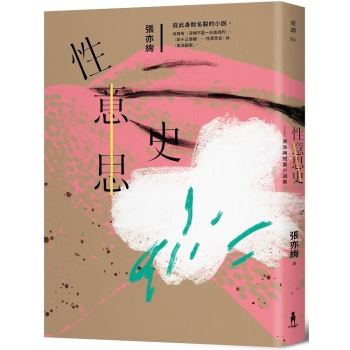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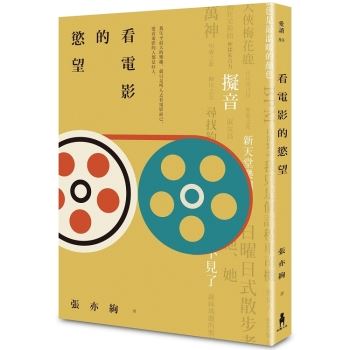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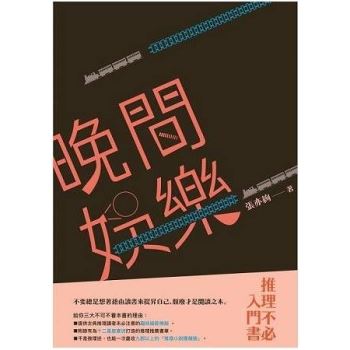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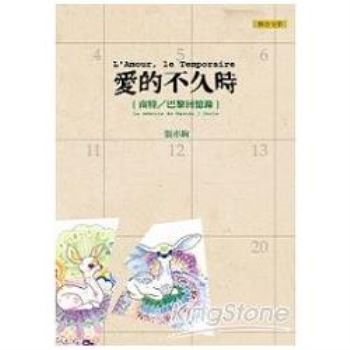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