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著:張翎中篇小說集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原來你就是我。
或者說,我就是你。
而你,不是還活著,你其實是還在死著。
慢慢的,一分一秒的……
本書收錄四則中篇小說:
〈死著〉
一起車禍,導致茶葉公司經理路思銓腦死,卻因為交警業績、醫病妥協與妻子的愛怨嗔痴等各方人馬的諸種算計與俗世念想,使他求死不能。最後,靠著盲女茶妹拔掉急救系統的電源,終結了他「死著」的悲慘命運。
〈雁過藻溪〉
移居加拿大久不回國的末雁,因母親過世,與女兒靈靈帶著母親的骨灰,回到家鄉藻溪安葬。三代女性,在鬼影幢幢的故土,見證了土改引發的一場暴行,突如其來的欲望、親情與身世隱情,竟摧毀了三個世代女子的生活。
〈戀曲三重奏〉
無論是大學時的初戀張敏,後來成為丈夫的許韶峰,到加拿大坐移民監認識的打包工人章亞龍,在女主角王曉楠的情愛三重奏裡,總帶著另一個人的影子。於是愛或不愛、背叛與被背叛,每一個人都寂寞,每一個樂章都寫滿了孤獨。
〈陪讀爹娘〉
項媽媽與李伯伯在國內原各是醫生、建築師,為了照顧在海外攻讀博士學位的下一代,遠赴多倫多幫忙帶孫子、燒飯菜,成為當今社會面目全無的人,也帶出三代在教養與溝通的摩擦與衝突。
名人推薦
有情推薦
書寫時代的荒謬、乖危與殘酷,主角無一不奮力掙扎,勇於對抗,不畏流俗,雖無法擺脫悲劇,但生命力的湧現超越了哀傷的基調。……這本選集彷彿是小說技藝的實驗室,展示出她不斷超越既有關心的題材、創作的風格與語言的特質。
──須文蔚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系主任
祕密的包藏往往是張翎小說裡的重要引線,作家且善於將懸念保持到最後。這些捂著祕密過日子的人,生命或許隨波逐流,但也充滿翻騰的可能性,正是在宿命的巧合與偶然的轉機裡,小說家提示了關於人性與際遇的多元思考。
──石曉楓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目錄
推薦序 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張翎小說中令人驚嘆的想像力 須文蔚
推薦序 未完待續:故事後的故事 石曉楓
臺灣版序 關於《死著》的一番閒話
死著
雁過藻溪
戀曲三重奏
陪讀爹娘
序/導讀
臺灣版序
關於《死著》的一番閒話
自《金山》(二○○九)問世以來,我似乎進入了長篇小說的「狂熱期」,不到八年的時間裡,先後發表了《睡吧,芙洛,睡吧》(二○一二)、《唐山大地震》(二○一三)、《陣痛》(二○一四)、《流年物語》(二○一六)、《勞燕》(二○一七)。而中篇小說的寫作速度,卻明顯緩慢了下來,八年裡總共才出了五部。這部小說集收集了包括《死著》在內的四部中篇小說,從時間順序來說,《死著》(也是集名)則是我最近的一部中篇。
和我從前的小說創作過程一樣,《死著》也是靈感偶發之物。二○一四年回國在上海逗留時,我和復旦大學的幾位學者一起吃了一頓飯。席間的話題從某位知名教授的去世,不知怎地就轉到了非必要搶救上。一位朋友說起了一樁「欲死不能」的事件,我深受觸動,《死著》的最初萌想,就是在那一刻發生的。
《死著》講述的是一起車禍導致腦死亡的病人的搶救事件。出於各種原因,車禍中牽扯到的各方都不願讓此人在年底以前死去,於是就動用了最先進的醫學手段來維繫著他的心臟搏動。只要還有心跳,此人就還能維持著身邊許多人的利益,於是死就不再是他個人的事,死就成了很多人共謀的一件事。
靈感是曇花一現的美麗幻象,而小說創作卻是要把每一個細節落到實處的枯燥過程。我面臨的第一個困難就是對急救過程的一知半解。幸好我在北京和溫州的幾家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裡有幾個熟人,在向他們討教的過程裡,有人提起了艾克膜技術──一種體外心肺循環支持系統。正好不久前我讀到了柯文哲先生關於艾克膜技術(臺灣稱葉克膜)的一篇演講──他在就任臺北市長之前是臺大醫院的急救科醫生,人稱「亞洲葉克膜之父」,我對這個搶救方案立刻產生了興趣。把這項先進而極為昂貴的急救技術應用在一個腦死亡病人身上,正好構成了小說所需的黑色幽默元素,也順勢造就了小說中「誰來承擔費用」的矛盾衝突,使得劉醫生在利益和良心之間的糾結變得合理。
創作過程裡的另一困難是對公路交通管理規則、勞動法規和工傷事故賠償法規的無知。調研有些枯燥費時,但相對簡單,真正的挑戰是把一則則法規移植在同一起案例上,使故事情節的推進既不至於出現太過明顯的破綻,而又保持了適當的峰谷起伏。這是一個走平衡木的過程,令人提心吊膽,忐忑不安。
其實最大的糾結都還不是這些。一直到小說將近尾聲,我還沒有想好由誰來充當結束這場鬧劇的「上帝」角色。盲女茶妹是天上掉下來的「神來之筆」,在我最初的設想裡,她只是陸經理在妻子和逢場作戲的情人之間的一個緩衝物。在某一個電閃雷鳴的時刻她突然從隱祕之地現身,朝我伸出手來大聲說出主動請纓的意願。驚詫之餘,我開始覺得她其實就是我一直找尋的那個人選。一個盲女靠著直覺找到並且拔掉急救系統的電源,給小說增添了一絲神祕感。她是一片荒謬陰晦之中的唯一一絲光亮和溫暖。故事裡的明眼人都看不見隱藏在現象之下的真相脈絡,唯一一個能參透真相的人卻是醫學意義上的瞎子──這個嘲諷的原版來自《聖經》。
一直到小說完成之後,名字依舊懸而未決。我原先想到的一個名字是《哈姆雷特》中最經典的一句台詞:「To Be or Not To Be。」這個名字在英文裡顯得極為貼切,但中文的各種翻譯,如「生存還是毀滅」、「活著還是死亡」,都無法傳神地揭示小說的真正寓意。後來,在一次聚會中,我隨意提起了這部已經完工卻還在等待著上天賜名的小說,一位在一所加拿大大學任教的朋友突然說:「為何不叫《死著》呢?」我不禁拍案叫絕。這個題目所指向的死亡不是一個瞬間的動作,而是一個時段模糊的過程──這正是我想通過小說所表述的深意。《死著》發表後,很多讀者不約而同地聯想到了余華的《活著》。雖然在起名的時候沒有想到過《活著》,但把《死著》看成是對《活著》的一種致意,卻是我內心的意外之喜。
我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談論《死著》,是因為它與我從前中篇小說涉及的題材全然不同,它涉及了中國的當下。近年來我雖然頻繁地回國,而且時常會待上一陣子,可是我畢竟是過客,我的文化土壤是在東西方之間的那塊邊緣地帶,當下的中國題材對我來說是一個尷尬的挑戰。《死著》的創作過程突然給了我一個從未有過的信念:局外人也是可以有看法的,局外人的看法和局內人具有平等的價值。
本集子所選的四部中篇小說,按照時間順序來梳理的話,《雁過藻溪》應該排在《死著》之前。藻溪是地名,也是一條河流的名字,在浙江省蒼南縣境內。藻溪是我母親出生長大的地方,那裡有她童年少年乃至青春時期的許多印跡,那裡埋葬著她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伯父伯母,還有許多她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親戚。藻溪發生的一切故事,對我來說都是史前的。我尚未記事時就隨父母來到溫州,一直在那裡居住到上大學為止。我對藻溪的最初印象,來自我父母在家講的那種節奏很快,音節很短,音量很大的方言。他們告訴我那是藻溪礬山一帶的方言,是閩南話。隔一兩個週末,母親就會帶我去身為明礬石研究專家的外公家裡做客,我常常會看見一些藻溪來的鄉人,帶著各樣土產乾貨,坐在我外婆的病榻前和我外婆說話。到城裡找工作,看病,借錢──常常是這一類的事情。外公和他已經成年的子女年復一年盡心盡力地為鄉人幫著這樣那樣的忙,而我外婆和一位長住在她家的表姑婆則用方言和鄉人們說著一些她們熟悉的人和事,在敘述的過程中臉上便漸漸浮現出一種迷茫柔和而快樂的神情。
當我長大成人遠離故土,長久地生活在他鄉時,我才明白,其實我的外婆和表姑婆,一直到死也沒有真正適應在城市的生活。她們的身體早就來到了城市,可是她們的心卻長久地留在了藻溪。如果把她們的一生比喻作樹的話,她們不過是被生硬地移植過來的殘幹斷枝,浮浮地落在城市的表土之上,而她們的根,卻長久地留在了藻溪。
我和藻溪第一次真正的對視,發生在一九八六年初夏。那是在即將踏上遙遠的留學旅程之時,遵照母親的吩咐我回了一趟她的老家,為兩年前去世的外婆掃墓。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到母親的出生地。族親們領我去了一個破舊不堪的院落,對我說:這原來是你外公家族的宅院,後來成為糧食倉庫,又被一場大火燒毀,只剩下這個門。我走上台階,站在那扇很有幾分歲月痕跡的大門前,用指甲摳著門上的油漆。斑駁之處,隱隱露出幾層不同的顏色。每一層顏色,大約都是一個年代。每一個年代大約都有一個故事。我發現我開始有了好奇。
一個叫藻溪的地方。一些陌生的墓碑。一段在土改年月裡成就的婚緣。這就是我在開始書寫《雁過藻溪》時對藻溪的全部認識。這些印象是鮮活卻凌亂的,似乎無法組成一個延續到今天的故事。於是我想到了一個載體,一個可以把過去現在未來聯結起來的人物,在他(她)身上我可以把那些零散的印象聚集成一條意向明確的線。構思的過程猶如布置聖誕樹,各樣的飾物原本是凌亂沒有主題的,然而一旦把它們一一掛在一棵青蔥的樹上,主題突然就呼之欲出了。
這棵樹就是末雁。末雁是我在加拿大生活中常常見到的知識女性。在有的方面她們具有非凡的聰明睿智,完全能獨當一面,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卻異常的天真無知無能。她們久不回國,思維方式由於多年時空的隔絕還基本停留在八十年代文革剛過的那個模式裡。她們對中國的設想也還停留在那個時期的印象上。末雁的藻溪之行是一個發掘自我的旅程。在五十歲的年紀上一程一程地回到人生的起點上,她發現的不僅僅是一個關於自己身世的碩大祕密,她其實也經歷了錯失在青春歲月裡的成熟過程。在那個叫藻溪的狹小世界裡,她遭遇了她的大世界裡所不曾遭遇過的東西,比如欲望,比如親情,比如真相。震驚過後,猛一睜眼,她才真正長大了──儘管遲了三十年。
《雁過藻溪》無疑是四部小說中影響最大的,它進入了二○○五年中國小說學會的年度排行榜,獲得十月文學獎,並被選入多種年度精選本。我至今仍然會忍不住感慨:這部以土改中發生的慘烈故事為背景的小說,居然在當年能夠引起如此的關注──無論是原發期刊還是選刊的編輯們,都是具有何等勇氣值得敬佩的人。
順著時間的線條一路擼下去,《戀曲三重奏》和《陪讀爹娘》應該是這本集子中最早的作品,在它們身上依稀還能看得出留學生和新移民的身分轉換過程中留下的印記。兩部小說只相隔一年,雖然故事情節相差極大,前者講述的是一位被富商安置於加拿大以換取移民身分的中年女子的情感經歷,後者是關於兩位陪子女來多倫多讀書的老人家的惺惺相惜,但兩部小說卻共享著一個極為鮮明的主題:孤獨。無論是《戀曲三重奏》中的王曉楠,還是《陪讀爹娘》中的項媽媽,他們需要面對的不僅是感情世界的孤獨,還有失去熟悉的社會文化背景、身處異鄉的孤獨。
對《戀曲三重奏》裡的王曉楠來說,張敏是她的初戀,是激情和青春相撞時迸發的璀璨煙火。煙火是美麗但卻瞬間即逝的,除了死亡,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將其定格。失去了張敏之後,王曉楠的翅膀折了,從天空墜落,而許韶峰是她落下時腳尖碰觸到的第一片地。她順理成章地投靠了許韶峰。他們大概也是相愛過的,只是對兩個各有私心的都市男女來說,那樣的愛是不夠讓他們拿來抵擋大千世界的欲望和野
試閱
關於《死著》的一番閒話
自《金山》(二○○九)問世以來,我似乎進入了長篇小說的「狂熱期」,不到八年的時間裡,先後發表了《睡吧,芙洛,睡吧》(二○一二)、《唐山大地震》(二○一三)、《陣痛》(二○一四)、《流年物語》(二○一六)、《勞燕》(二○一七)。而中篇小說的寫作速度,卻明顯緩慢了下來,八年裡總共才出了五部。這部小說集收集了包括《死著》在內的四部中篇小說,從時間順序來說,《死著》(也是集名)則是我最近的一部中篇。
和我從前的小說創作過程一樣,《死著》也是靈感偶發之物。二○一四年回國在上海逗留時,我和復旦大學的幾位學者一起吃了一頓飯。席間的話題從某位知名教授的去世,不知怎地就轉到了非必要搶救上。一位朋友說起了一樁「欲死不能」的事件,我深受觸動,《死著》的最初萌想,就是在那一刻發生的。
《死著》講述的是一起車禍導致腦死亡的病人的搶救事件。出於各種原因,車禍中牽扯到的各方都不願讓此人在年底以前死去,於是就動用了最先進的醫學手段來維繫著他的心臟搏動。只要還有心跳,此人就還能維持著身邊許多人的利益,於是死就不再是他個人的事,死就成了很多人共謀的一件事。
靈感是曇花一現的美麗幻象,而小說創作卻是要把每一個細節落到實處的枯燥過程。我面臨的第一個困難就是對急救過程的一知半解。幸好我在北京和溫州的幾家醫院的重症監護室裡有幾個熟人,在向他們討教的過程裡,有人提起了艾克膜技術──一種體外心肺循環支持系統。正好不久前我讀到了柯文哲先生關於艾克膜技術(臺灣稱葉克膜)的一篇演講──他在就任臺北市長之前是臺大醫院的急救科醫生,人稱「亞洲葉克膜之父」,我對這個搶救方案立刻產生了興趣。把這項先進而極為昂貴的急救技術應用在一個腦死亡病人身上,正好構成了小說所需的黑色幽默元素,也順勢造就了小說中「誰來承擔費用」的矛盾衝突,使得劉醫生在利益和良心之間的糾結變得合理。創作過程裡的另一困難是對公路交通管理規則、勞動法規和工傷事故賠償法規的無知。調研有些枯燥費時,但相對簡單,真正的挑戰是把一則則法規移植在同一起案例上,使故事情節的推進既不至於出現太過明顯的破綻,而又保持了適當的峰谷起伏。這是一個走平衡木的過程,令人提心吊膽,忐忑不安。
其實最大的糾結都還不是這些。一直到小說將近尾聲,我還沒有想好由誰來充當結束這場鬧劇的「上帝」角色。盲女茶妹是天上掉下來的「神來之筆」,在我最初的設想裡,她只是陸經理在妻子和逢場作戲的情人之間的一個緩衝物。在某一個電閃雷鳴的時刻她突然從隱祕之地現身,朝我伸出手來大聲說出主動請纓的意願。驚詫之餘,我開始覺得她其實就是我一直找尋的那個人選。一個盲女靠著直覺找到並且拔掉急救系統的電源,給小說增添了一絲神祕感。她是一片荒謬陰晦之中的唯一一絲光亮和溫暖。故事裡的明眼人都看不見隱藏在現象之下的真相脈絡,唯一一個能參透真相的人卻是醫學意義上的瞎子──這個嘲諷的原版來自《聖經》。
一直到小說完成之後,名字依舊懸而未決。我原先想到的一個名字是《哈姆雷特》中最經典的一句台詞:「To Be or Not To Be。」這個名字在英文裡顯得極為貼切,但中文的各種翻譯,如「生存還是毀滅」、「活著還是死亡」,都無法傳神地揭示小說的真正寓意。後來,在一次聚會中,我隨意提起了這部已經完工卻還在等待著上天賜名的小說,一位在一所加拿大大學任教的朋友突然說:「為何不叫《死著》呢?」我不禁拍案叫絕。這個題目所指向的死亡不是一個瞬間的動作,而是一個時段模糊的過程──這正是我想通過小說所表述的深意。《死著》發表後,很多讀者不約而同地聯想到了余華的《活著》。雖然在起名的時候沒有想到過《活著》,但把《死著》看成是對《活著》的一種致意,卻是我內心的意外之喜。我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談論《死著》,是因為它與我從前中篇小說涉及的題材全然不同,它涉及了中國的當下。近年來我雖然頻繁地回國,而且時常會待上一陣子,可是我畢竟是過客,我的文化土壤是在東西方之間的那塊邊緣地帶,當下的中國題材對我來說是一個尷尬的挑戰。《死著》的創作過程突然給了我一個從未有過的信念:局外人也是可以有看法的,局外人的看法和局內人具有平等的價值。
本集子所選的四部中篇小說,按照時間順序來梳理的話,《雁過藻溪》應該排在《死著》之前。藻溪是地名,也是一條河流的名字,在浙江省蒼南縣境內。藻溪是我母親出生長大的地方,那裡有她童年少年乃至青春時期的許多印跡,那裡埋葬著她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伯父伯母,還有許多她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親戚。藻溪發生的一切故事,對我來說都是史前的。我尚未記事時就隨父母來到溫州,一直在那裡居住到上大學為止。我對藻溪的最初印象,來自我父母在家講的那種節奏很快,音節很短,音量很大的方言。他們告訴我那是藻溪礬山一帶的方言,是閩南話。隔一兩個週末,母親就會帶我去身為明礬石研究專家的外公家裡做客,我常常會看見一些藻溪來的鄉人,帶著各樣土產乾貨,坐在我外婆的病榻前和我外婆說話。到城裡找工作,看病,借錢──常常是這一類的事情。外公和他已經成年的子女年復一年盡心盡力地為鄉人幫著這樣那樣的忙,而我外婆和一位長住在她家的表姑婆則用方言和鄉人們說著一些她們熟悉的人和事,在敘述的過程中臉上便漸漸浮現出一種迷茫柔和而快樂的神情。
當我長大成人遠離故土,長久地生活在他鄉時,我才明白,其實我的外婆和表姑婆,一直到死也沒有真正適應在城市的生活。她們的身體早就來到了城市,可是她們的心卻長久地留在了藻溪。如果把她們的一生比喻作樹的話,她們不過是被生硬地移植過來的殘幹斷枝,浮浮地落在城市的表土之上,而她們的根,卻長久地留在了藻溪。我和藻溪第一次真正的對視,發生在一九八六年初夏。那是在即將踏上遙遠的留學旅程之時,遵照母親的吩咐我回了一趟她的老家,為兩年前去世的外婆掃墓。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到母親的出生地。族親們領我去了一個破舊不堪的院落,對我說:這原來是你外公家族的宅院,後來成為糧食倉庫,又被一場大火燒毀,只剩下這個門。我走上台階,站在那扇很有幾分歲月痕跡的大門前,用指甲摳著門上的油漆。斑駁之處,隱隱露出幾層不同的顏色。每一層顏色,大約都是一個年代。每一個年代大約都有一個故事。我發現我開始有了好奇。
一個叫藻溪的地方。一些陌生的墓碑。一段在土改年月裡成就的婚緣。這就是我在開始書寫《雁過藻溪》時對藻溪的全部認識。這些印象是鮮活卻凌亂的,似乎無法組成一個延續到今天的故事。於是我想到了一個載體,一個可以把過去現在未來聯結起來的人物,在他(她)身上我可以把那些零散的印象聚集成一條意向明確的線。構思的過程猶如布置聖誕樹,各樣的飾物原本是凌亂沒有主題的,然而一旦把它們一一掛在一棵青蔥的樹上,主題突然就呼之欲出了。
這棵樹就是末雁。末雁是我在加拿大生活中常常見到的知識女性。在有的方面她們具有非凡的聰明睿智,完全能獨當一面,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卻異常的天真無知無能。她們久不回國,思維方式由於多年時空的隔絕還基本停留在八十年代文革剛過的那個模式裡。她們對中國的設想也還停留在那個時期的印象上。末雁的藻溪之行是一個發掘自我的旅程。在五十歲的年紀上一程一程地回到人生的起點上,她發現的不僅僅是一個關於自己身世的碩大祕密,她其實也經歷了錯失在青春歲月裡的成熟過程。在那個叫藻溪的狹小世界裡,她遭遇了她的大世界裡所不曾遭遇過的東西,比如欲望,比如親情,比如真相。震驚過後,猛一睜眼,她才真正長大了──儘管遲了三十年。
《雁過藻溪》無疑是四部小說中影響最大的,它進入了二○○五年中國小說學會的年度排行榜,獲得十月文學獎,並被選入多種年度精選本。我至今仍然會忍不住感慨:這部以土改中發生的慘烈故事為背景的小說,居然在當年能夠引起如此的關注──無論是原發期刊還是選刊的編輯們,都是具有何等勇氣值得敬佩的人。順著時間的線條一路擼下去,《戀曲三重奏》和《陪讀爹娘》應該是這本集子中最早的作品,在它們身上依稀還能看得出留學生和新移民的身分轉換過程中留下的印記。兩部小說只相隔一年,雖然故事情節相差極大,前者講述的是一位被富商安置於加拿大以換取移民身分的中年女子的情感經歷,後者是關於兩位陪子女來多倫多讀書的老人家的惺惺相惜,但兩部小說卻共享著一個極為鮮明的主題:孤獨。無論是《戀曲三重奏》中的王曉楠,還是《陪讀爹娘》中的項媽媽,他們需要面對的不僅是感情世界的孤獨,還有失去熟悉的社會文化背景、身處異鄉的孤獨。
對《戀曲三重奏》裡的王曉楠來說,張敏是她的初戀,是激情和青春相撞時迸發的璀璨煙火。煙火是美麗但卻瞬間即逝的,除了死亡,沒有其他方式可以將其定格。失去了張敏之後,王曉楠的翅膀折了,從天空墜落,而許韶峰是她落下時腳尖碰觸到的第一片地。她順理成章地投靠了許韶峰。他們大概也是相愛過的,只是對兩個各有私心的都市男女來說,那樣的愛是不夠讓他們拿來抵擋大千世界的欲望和野心的。於是,他和她的心裡都有了空隙,章亞龍就是在這個空隙裡鑽了進來。章亞龍的結局是一個謎,沒有人知道確切的答案。王曉楠和章亞龍都經過了太多的事,沒有人(包括我)知道他們是否還有愛的能力,所以結局只能是一個懸念。這部小說裡的每一個人都是寂寞的,愛的時候,不愛的時候,都一樣;在家的時候,遠離故土的時候,也是一樣。沒有一種寂寞可以代替另外一種寂寞,他們都得一一熬過。所以王曉楠的情愛三重奏裡,每一個樂章都寫滿了孤獨。《陪讀爹娘》裡的項媽媽,和王曉楠一樣,也是寂寞的。她千里迢迢來到多倫多,為獨生女兒照看孩子。在那個住滿了國際留學生的查爾斯大街五十三號宿舍樓裡,她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人,沒有人知道她曾經是出色的醫生,也沒有人知道她曾經有過轟轟烈烈的愛情,甚至沒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所有認識她的人都理所當然地以她女兒的姓氏和她與女兒的關係來稱呼她項媽媽,她失去了一切曾經獨立存在過的佐證和痕跡。當她認識了李伯伯,一個和她一樣來多倫多照顧兒子的老人時,她才猛然從他的身上看見了自己的影子──她驚訝於自己竟然如此安然地接受了命運的改變和侵蝕。她和李伯伯由惺惺相惜開始的溫情,幾乎在還未完全展開時就面臨結束了:由於兒子的未婚妻要搬來和兒子同住,李伯伯不得不提前回國。就在他們的萍水相逢猝然進入尾聲時,他們卻依稀看見了一段或許可以持久的感情正在悄悄開始。
《死著》裡收集的四部中篇小說,從最早的《陪讀爹娘》(二○○一)到最近的《死著》(二○一五),中間相隔了十四年。希望臺灣的讀者能從這十四年的軌跡裡,看到一個作家在思想視角以及寫作風格上的漸變過程。
是為序。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多倫多
死著
我,抑或是你?
柳絮,楊花,雪,羽毛,飛塵……
我想到了世界上一切輕盈的物體,可是我比它們還輕。我不具體積,缺乏形狀,所以,我也沒有重量。
我沒有四肢,沒有軀幹,甚至也沒有頭顱,我卻依舊能看,能聽,能聞。我的感官失去了承載它們的器皿,如丟了鞘的刀,自由,尖銳,所向披靡。我不僅掙脫了身體的羈束,我還掙脫了萬有引力這根巨大繩索的捆綁,現在再也沒有一樣東西可以限制我的行蹤,把我拉回地面。我是風,是雲,我可以抵達任意一個高度,穿越任何一條哪怕比頭髮絲還細的縫。
然而,我還不太習慣這份突然獲得的自由。我總覺得萬有引力是在和我玩著某種規則掌握在它自己手裡的惡作劇遊戲,短暫地鬆了鬆它的掌控,只是為了讓我在享有片刻虛妄的快活之後,再把我鎖入那個萬劫不復的囚籠。我戰戰兢兢忐忑不安地探測著我的邊界,不敢輕舉妄動。我漂浮在天花板上由兩面牆夾築而成的一個角落裡,四下觀看。我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看過世界,所以每一樣撞進我視野的東西,都讓我產生嬰孩第一次睜開眼睛猝然看見萬物時的那種好奇和驚訝。從高往下看,房間的線條是斜的,牆壁白得割眼,牆上掛的那幅畫,有點像一片上窄下寬的裙擺。其實那也不能算是畫,它只是一幅加了注解的人體器官剖視圖。我不知道房間所在的樓層,從視窗顯露出來的那片樹梢來判斷,這裡至少是四樓。此刻所有關於時間和季節的記憶,似乎都已經像牆壁一樣被刷白了,我只能根據視窗射進來的那抹光線來推測,現在大概在下午四點半到五點之間。至於季節,那倒相對簡單:樹枝上的葉子已經落盡,露出了一只黑糊糊的鳥巢,所以只能是冬天。一群灰頭土臉的雀子在光禿禿的樹枝之間竄來竄去,用毛糙尖利的嗓音吱吱呀呀地唱著歌。我聽不懂,卻也知道那是哀怨──關於饑餓和蕭肅的哀怨。街上的人流很濃稠,從高處望下去,我看不見他們的身子,因為他們的身子已經被他們的頭所遮蔽。他們像一顆顆棋子,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推搡著,在街市的棋盤上來來回回地挪動。
當然,這些都不是我視野裡的中心內容。牆不是,窗不是,樹不是,陽光不是,雀兒更不是。甚至連街景和行人也不是。他們太光滑,身上沒長毛刺,我的目光短暫地掃過他們時,他們沒能鉤住我的眼睛。真正鉤住我眼睛的,是屋子中間那件貌似水母的龐然大物。它周身長滿了吸管,每一根吸管都扎進一個躺臥在它肚腹上的長條物件中,窸窸窣窣地吸吮著那物件體內的汁液。過了一會兒,等我的目光終於找到了聚焦點,我才明白過來那水母原來是一張病床,而那長條物件,原來是你。你的大部分身子都掩蓋在一張白床單底下,露出來的那張臉,被紗布和管子分割完畢之後,只剩下兩爿山嶺一樣陡峭的顴骨。你大概剛剛在這個姿勢裡固定下來,你的身子,身下的床單和枕頭,甚至還有房間裡的空氣,都還彼此認著生,正在試試探探地進行著第一輪關於空間和地盤的談判。
屋裡還有兩個人,是一老一小兩個護士。小護士一邊看著儀錶上的數字,一邊在一個紙夾上作著紀錄。老護士站在小護士身後,目光越過小護士的肩膀,蛇似地在小護士的紙上爬行。
「仔細點,這份病歷將來一定會有人盯著。」老護士叮囑道。我漂浮在天花板上由兩面牆夾築而成的一個角落裡,四下觀看。我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看過世界,所以每一樣撞進我視野的東西,都讓我產生嬰孩第一次睜開眼睛猝然看見萬物時的那種好奇和驚訝。從高往下看,房間的線條是斜的,牆壁白得割眼,牆上掛的那幅畫,有點像一片上窄下寬的裙擺。其實那也不能算是畫,它只是一幅加了注解的人體器官剖視圖。我不知道房間所在的樓層,從視窗顯露出來的那片樹梢來判斷,這裡至少是四樓。此刻所有關於時間和季節的記憶,似乎都已經像牆壁一樣被刷白了,我只能根據視窗射進來的那抹光線來推測,現在大概在下午四點半到五點之間。至於季節,那倒相對簡單:樹枝上的葉子已經落盡,露出了一只黑糊糊的鳥巢,所以只能是冬天。一群灰頭土臉的雀子在光禿禿的樹枝之間竄來竄去,用毛糙尖利的嗓音吱吱呀呀地唱著歌。我聽不懂,卻也知道那是哀怨──關於饑餓和蕭肅的哀怨。街上的人流很濃稠,從高處望下去,我看不見他們的身子,因為他們的身子已經被他們的頭所遮蔽。他們像一顆顆棋子,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推搡著,在街市的棋盤上來來回回地挪動。
當然,這些都不是我視野裡的中心內容。牆不是,窗不是,樹不是,陽光不是,雀兒更不是。甚至連街景和行人也不是。他們太光滑,身上沒長毛刺,我的目光短暫地掃過他們時,他們沒能鉤住我的眼睛。真正鉤住我眼睛的,是屋子中間那件貌似水母的龐然大物。它周身長滿了吸管,每一根吸管都扎進一個躺臥在它肚腹上的長條物件中,窸窸窣窣地吸吮著那物件體內的汁液。過了一會兒,等我的目光終於找到了聚焦點,我才明白過來那水母原來是一張病床,而那長條物件,原來是你。你的大部分身子都掩蓋在一張白床單底下,露出來的那張臉,被紗布和管子分割完畢之後,只剩下兩爿山嶺一樣陡峭的顴骨。你大概剛剛在這個姿勢裡固定下來,你的身子,身下的床單和枕頭,甚至還有房間裡的空氣,都還彼此認著生,正在試試探探地進行著第一輪關於空間和地盤的談判。
屋裡還有兩個人,是一老一小兩個護士。小護士一邊看著儀錶上的數字,一邊在一個紙夾上作著紀錄。老護士站在小護士身後,目光越過小護士的肩膀,蛇似地在小護士的紙上爬行。
「仔細點,這份病歷將來一定會有人盯著。」老護士叮囑道。小護士大概是個新畢業生,連白色的帽角上都掛著著一絲初出校門的緊張和拘謹。小護士的指尖覺出了老護士目光的重量,顫了一顫,筆就從手裡掉了下去。筆落在了你的枕頭上,順著你頭壓出來的那塊凹痕,滾到了你的脖子底下。
小護士輕輕地托起你的頭,取出了那只不聽使喚的筆。突然,她發出了一聲壓抑了的驚叫,捏著筆的手在空中凝固成一朵半開的蘭花。
你插著管子的鼻孔裡,突然湧出了一股液體。那液體清清亮亮的,中間夾雜了幾抹桃紅,像生著氣的蛋清。
「腦脊液。」老護士輕描淡寫地說。
老護士在醫院工作了十幾年,老護士見過了從生到死過程中間的所有稀奇,神經網路早已經被磨成一張滿是褶皺的牛皮紙。
「要取樣化驗嗎?」小護士問。
「用不著。腦子心肺都成那樣了,不可逆。」老護士說。
「要不要,去問一聲,劉主任?」小護士猶猶豫豫地問。
「劉主任交代過了,維持著就行。今天這幾個病人累得他夠嗆,讓他歇一歇。」老護士說。
護士做老了,就做成了精。成了精的護士通曉科室裡的每一根筋絡,知道什麼時候該捏哪一根。成了精的護士不僅調派得了護士,甚至也可以調派醫生──是不動聲色的那種調派法。
小護士用棉球小心翼翼地擦去了你鼻孔插管四周的黏液。小護士其實還有問題想問,可是小護士的問題被老護士的一個哈欠給堵了回去。小護士知道劉主任站了多久,老護士就陪了多久;劉主任有多累,老護士就有多累。小護士不懂的事情還很多,她還有半輩子的時間可以慢慢地體會,她用不著一次問清。
小護士堵在嗓子眼裡的那個問題是:「既然不可逆,為什麼還要上葉克膜*?」(*葉克膜是ECMO的音譯,指體外心肺支援系統,是一種先進的急救設施,俗稱「人工心肺」。)
小護士終於仔仔細細地作完了紀錄,在合上夾子之前,又核實了一遍病人資訊。小護士湊過身去核對你病床上方的那塊名牌時,我看見了你的名字。
路思銓。
我吃了一大驚,因為那也是我的名字。
過了一會兒,我才終於醒悟過來,原來你就是我。
或者說,我就是你。
眼睛,抑或是鼻子──一件七個月前發生的事
茶妹坐在門前的樹蔭裡,一邊揉撚剛剛殺過青的茶葉,一邊抬頭聞天。今年的天時很順。梅雨按著時令來了,把茶樹上的灰塵洗得乾乾淨淨。雨水多,卻沒有多到讓人著急上火的地步,連綿的雨天裡總能擠進一兩個有太陽的好日子,讓人搶上幾個鐘點採茶,攤晒,殺青。
今天就是這樣一個好天。空氣裡的味道很雜,茶妹聞到了日頭烘烤著土坡的泥塵味,茶葉在她手指的揉搓下滲出來的清澀味,還有雞走過她家門前屙下的一灘稀屎味。茶妹不僅聞得著氣味,茶妹還聞得出顏色。篩子裡的茶葉不如去年的鮮綠,興許是雨水的緣故,興許是日頭,興許是殺青的火候。茶是一樣古靈精怪的物件,每一季都有每一季的性情脾氣,季季不同。不過顏色只是秀給人看的,茶妹知道這一季的茶和上一季的味道一樣清香。村裡的家家戶戶都靠茶葉吃飯,茶妹家也是。只是阿爸年年收茶時都會留一小部分茶葉,送給城裡的親戚朋友。這些茶阿爸總是要手工製作,阿爸信不過機器。
其實那天茶妹還聞著了另外一樣味道,一樣她這輩子都沒聞過的味道。她說不出那是什麼味道,只覺得帶著隱隱一絲的鐵腥味,也帶著隱隱一絲鐵一樣的重量。那味道不知道是從哪個方向過來的,沉沉地彌漫在空中,壓得她腦瓜仁子發緊。那味道在幾個月後的某一天裡,還會再次出現,那時茶妹才會醒悟,原來這是老天爺變著法子在給她遞話,告訴她日子要有變故。
茶妹今年虛歲十九,實歲十八,算不上細皮嫩肉,眉眼也長得尋常。可是茶妹的嘴角,卻生著兩個淺淺的坑。用不著笑,只要臉上的任何一根筋肉輕輕一扯,就能扯得那兩個坑一陣亂顫。這一顫,茶妹的臉面上便再也掛不住一絲陰雲。
可惜茶妹看不見自己的模樣,因為茶妹是個瞎子。
茶妹並不是生下來就瞎的。在六歲以前,她看得清蝴蝶翅膀上的每一條紋路,天邊雲彩裡最細的那條皺褶。六歲那年,顏色開始一樣一樣走失,先是紅,再是藍,再是綠,再是黃。後來世界變成了一片混沌的灰暗。再後來,連灰色也消失了。等到有一天,茶妹在正午時分問阿媽天為什麼還沒亮,阿媽才覺出了不對勁,可那時事情已經進入了一條不可逆轉的死胡同。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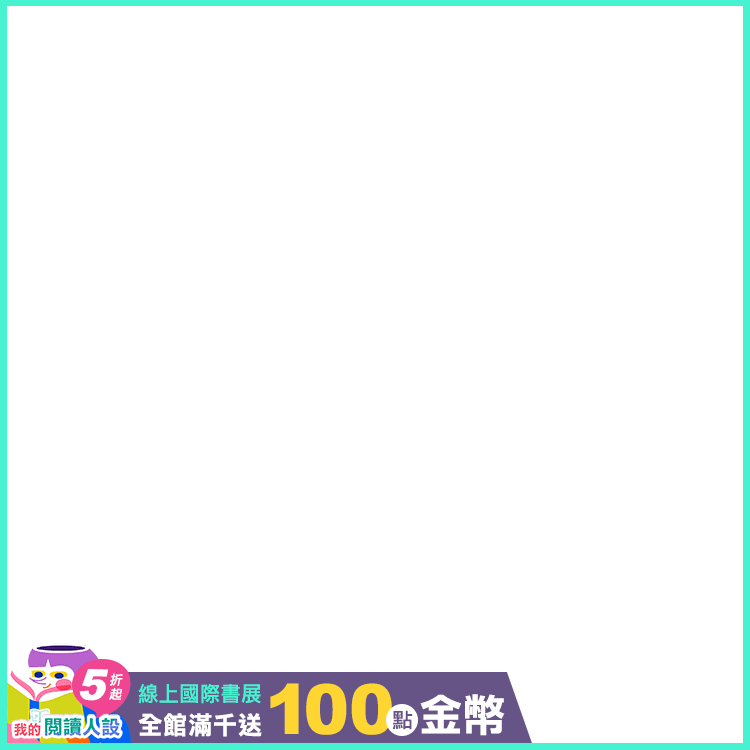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