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用閱讀開啟視野,讓書成為照亮你人生的光
【金石堂選書】本月推薦您這些好書👉 快來看看
內容簡介
春燈公子大宴江湖人物是一年一度的盛事,此會行之有年,幾與尋常歲時典祀無二,但設宴人出身成謎,設宴地點更是直似桃花源,在現實空間裡以及曾與會者的記憶中都不復尋覓。
唯一存世的證據,是輾轉流傳的二十則詩、詞「題品」(儒行、藝能、機慎、洞見、俠智、巧慧、運會、奇報、憨福、勇力、義盜、練達、聰明、詭飾、狡詐、薄倖、褊急、頑懦、貪癡……)——這些題品據聞正出自春燈宴中的高潮:由與宴諸客之中秘密地被挑選出來的說話人,傾一年時光琢磨,務求能令聽者咋舌稱奇、公子青眼品論的故事。
唯一存世的證據,是輾轉流傳的二十則詩、詞「題品」(儒行、藝能、機慎、洞見、俠智、巧慧、運會、奇報、憨福、勇力、義盜、練達、聰明、詭飾、狡詐、薄倖、褊急、頑懦、貪癡……)——這些題品據聞正出自春燈宴中的高潮:由與宴諸客之中秘密地被挑選出來的說話人,傾一年時光琢磨,務求能令聽者咋舌稱奇、公子青眼品論的故事。
試閱
春燈宴
春燈公子大宴江湖人物是一年一度的盛事,此會行之有年,幾與尋常歲時典祀無二。雖然說是例行,然而本年與會的是些甚麼樣的人物?又在甚麼地方舉行,行前一向是不傳之秘。直到應邀之人依柬赴約,到了地頭兒,自有知客人前來迎迓,待得與眾賓客相見,才知究竟。
這個一年一度的飯局,總在歲暮年初之間,應邀者感於春燈公子盛情,往往排除萬難,千里間關,無論跋涉如何辛苦,總期能與當世之豪傑人物一晤,把酒相談是幸。據說首會之地是在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簡直是海內第一水榭,古稱天花寺的所在。相傳呂文靖嘗題詩於寺,云:
「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等閒能有幾人來。」
到南宋年間,天花寺仍然完好如初,陸務觀也有〈東關二首〉,云: 「天華寺西艇子橫/白蘋風細浪紋平/移家祇欲東關住/夜夜湖中看月生。」
「煙水蒼茫西復東/扁舟又繫柳陰中/三更酒醒殘燈在/臥聽瀟瀟雨打篷。」
不過,到了放翁作詩那時,天花寺三面皆是民間廬舍,前臨一支港,景觀大異於前。有人說是寺本在湖中,後遷徙於草市通衢之上云云。春去秋來,星移物換,到了春燈公子首會天下英雄的那一年,去放翁作詩之歲,又不免過了數百載,天花寺居然又給修蕺完好,依樣軒窗向水,綽影浮光,端的是一座莊嚴、清靜又雅潔的蘭若,誰也說不上來算不算是恢復了呂文靖題詩之時的舊觀,可誰都說相去非唯不遠,而輝煌璧麗,怕不猶有過之?當年此會盛況非凡,時時有人說起,總道輾轉識得與會者某某,又聞聽人說起某人自陳與會之事如何;總而言之,街談巷議,蜚短流長,一直不曾斷絕。
這春燈公子究竟是個怎樣出身?甚麼家世?籍隸何處?資歷如何?有些甚麼事功著述?彷彿誰也說不清楚。有說他是王公貴冑之後的,有說他是達官顯宦之子的,有說他祖上有范蠡、鄧通之流的人物,家道殷實,卻一向禁絕子孫涉足於名利之場,是以積數十代之財貨,富可敵國,卻鮮有忌之、害之甚或知之者。由於大會江湖豪傑之事甚秘,外人往往無從得窺情實,祇能任人謠傳訛說,也就沒有誰能考辨精詳,加之以聚會之地忽南忽北、徂東徂西,令人難以捉摸,一旦宴罷,人去樓空,原先的繁花盛景、燈火樓台,居然在轉瞬之間就空曠蕭索起來。即使讓參與過盛會的人物追述回憶,亦皆惘然,故而連春燈公子的祖居家宅究竟何在,都是個謎了。 天花寺一會之後,春燈公子暴得大名,人人爭相問訊:此君如何能將這麼些了不得的大人物相邀共至、齊聚一堂?給問到的與會之人不覺茫然,竊喜一念:原來我也算是個了不得的大人物了?大人物不常見,幾年例會下來,反而形成了另一個局面;自凡是有頭有臉的江湖大萬,不論是管領著一幫一派、或者傳承著某家某學,甚或精通一藝而能聞達於百里之境者,乃至偶發一事而能知名於三山五城之外者,多有到處探聽春燈公子行蹤的。打從年頭直到年尾,總有這麼樣的話語在口耳之間飄盪盤桓:「可知今年『春燈宴』邀了些甚麼人哪?」
「春燈宴」成了個現成的名目,這應該是天花寺之會後五、六年間的事。雖說春燈公子本人從來沒用過這個名目招徠賓客,可它畢竟是喊響了。傳聞之中,「春燈宴」上還有相當動人的花樣兒。
風聞打從「春燈宴」初開之歲,就沿襲了成例,每會當天自辰時起迎賓,無何道遠路近,客人們總在前一日都齊聚於館舍了。相識不識一照上面,對於彼此皆為春燈公子座上之客的身份都已經了然於胸,自然相互禮遇,一團和氣。即使偶有些人物,曾經鬧過大小尷尬,一旦在這場合上相見,也往往收拾起意氣,待宴罷之後,相揖別過,有甚麼過節,也祇能等後會之時再算了。正因如此,有許多江湖上礙於情面,不好相商的人物,往往還巴望著能在「春燈宴」上不期而遇,以便排難解紛。可這還不能算是人人期盼於「春燈會」上的花樣兒。真正的花樣兒,叫「立題品」。
總在開宴當日申牌時分,春燈公子的一十六童男女侍從就會引出這麼一個人物,此人或老或少,或男或女,年年不同。一亮相,不必多言,眾人自然都明白了:這位一定就是今年「立題品」的說話人。這位說話人究竟有些甚麼能為?是怎麼從眾賓客之中揀選出來的?其事甚秘,近二十年來,謠諑紛紜,沒有能說準的。然而無論如何,應邀與會之人都不免發些想頭:說不得今年到會之日,給那一十六位童男同女給請上台去「立題品」的就是我呢。是以人人來到「春燈宴」之前,總不免琢磨著要說一個足以令人咋舌稱奇的故事。於是,但見蟻躦蠅聚之人莫不晃腦搖頭,挺腰踮腳,滿心巴望著有那童男女來請移駕登台──自然,失望的多。
「立題品」之所以成了江湖中人參與「春燈會」的一個想頭,自然是有緣故的;但凡是登台說出一則首尾俱全的故事來的,春燈公子登時濡墨揮毫,或吟以詩、或填以詞,為這故事所述的人物下一個題品,書成一卷,發付裱褙匠人收了,究竟裝裱之後如何庋藏?如何展示?也無人詳其下落。倒是有那麼一闋詞,因為江左裱聖左彥奎不慎丟失,原件輾轉淪落,居然在數十年之後給誤植進茗畹堂重刻的納蘭詞(容若)詞集之中,亦殊可怪──這是岔話,就不多說了。 回頭說待春燈公子將詩、詞題品一揮而就,當下就給這說話人也奉上赤金萬兩,號曰「喉潤」。潤喉之資,竟過於中人之家一生一世的開銷,手筆之大,教人最是嘖嘖稱奇。奉上銀票之際,往往就是每年「春燈宴」熱鬧到極點的一刻。
春燈公子最早流傳於世的詩詞,就是這二十則題品。此乃斯人斯文首度問世,謹先臚列其一至十九品於左:
方觀承——儒行品;七古一首
代有文豪忽一發/ 偏如野草爭奇突/ 鋪張咫尺掬清英/ 肯向風塵申討伐/ 吾輩非今兼妒古/ 疑他李杜笑屈父/ 驚聞舉世不觀書/ 卻對燈灰吹寂苦/ 寧不知樽前幾度竟成懽/ 且樂鯨吸化羽翰/ 一飲三吟羞夢囈/ 百年九死悔儒餐/ 狼毫颯颯攀銀壁/ 龍墨殷殷伏玉盤/ 再約明朝看筆跡/ 猶知波磔愧蹣跚/ 悄賦留仙曲/ 忍聽錄鬼簿/ 臨老見真章/ 平生欣然託。
達六合——藝能品;瀟湘夜雨一闋: 醉捲洋流/ 怒酣雲氣/ 暑天一夜清颸。 挾山排闥送淋漓。 敲瓦疾/ 飄零劍影/ 翻帖亂/ 寥落蛇碑。 凝神處/ 揮馳不礙/ 遍掃新詞。 墨無濃淡/ 妝非深淺/ 耐得經時。 倩狂風稍息/ 留月斜窺。 才一瞬/ 驚波破紙/ 儘幾筆/ 卓磔凝思。 誇神武/ 何須電母/ 毫末到高枝。 朱祖謀──機慎品;滿庭芳一闋: 漸入春山/ 泥塗花信/ 蝶去朝夢留遲。 夜涼蒸透/ 雲在最高枝。 何若揚州蘇軾/ 憔悴裡、偷鑄新詞。 吟哦處/ 青衫竹杖/ 冷落到天涯。 寧知遊興老/ 三分宿醉/ 一片歸思。 想獨雕殘句/ 閒賦新題。 古道西風瘦馬/ 也不過、些許情癡。 爭如我/ 閉門讀史/ 開口變傳奇。
李純颩──洞見品;水龍吟一闋: 斜眉笑看英雄/ 十方風雨闌幹淚。 危樓慢倚/ 紅塵流盼/ 無情如此。 羈旅江湖/ 斷魂魏闕/ 暗銷王氣。 想驚弓斷戟/ 殘山剩水/ 音書絕、人歸未? 淺嘗蓴羹鱸燴。 趁烽煙、寄蒼茫意。 綢繆萬裏/ 向黃昏處/ 目無餘子。 痛快恩仇/ 沉酣歌舞/ 飄搖天際。 教漁樵看了/ 閒言碎語/ 幾番滋味。
黃八子──俠智品;鷓鴣天一闋: 擊缺銀壺趁醉驕。 繁華看盡最無聊。 蓬山不應殷勤喚/ 濁酒還愁寂寞消。 塵劫外/ 怨歌遙。 客船今夜共聽潮。 殘詩草罷燈焚過/ 獨送相思上九霄。 雙刀張—─巧慧品,七律一首: 逐客風塵逐客遊/ 蓬飛到處不堪留/ 憐螢暑夜曾捐扇/ 掛劍寒窗慣夢鷗/ 莫笑癡人書咄咄/ 寧知野趣鹿呦呦/ 鄰翁勸進樽中月/ 仰盡初霜白滿頭。
張天寶──運會品;沁園春一闋: 帳捲殘風/ 夢碎珠簾/ 抖擻暗塵。 漸清明雲月/ 蒼茫蘆雪/ 匆匆聚散/ 往往隨人。 佐讀青燈/ 臨書白素/ 一向消磨差似貧。 吹煙看/ 念山餘斷樹/ 雨急飄蓴。 紛紜、 國破無痕/ 更不忍無椎虛刺秦。 算年華辜負/ 豪情棖觸/ 稍嫌厭氣/ 未便灰心。 馳騁飛涎/ 誅伐碩鼠/ 墨染閒池驚莠民。 吾何憾/ 幸詩翁解飲/ 帖字銷魂。
史茗楣──奇報品;夜半樂一闋: 幾時別過重聚。 稍經點染/ 仍似胭脂駐。 數玉兔盈虧/ 喚郎依據。 淺深怎地/ 殷勤照拂/ 卻聞幾番憐惜嬌呼/ 失神無語。 更哪見、蟾枝滴零雨。 隔簾裡外見識/ 面撫芳茵/ 魂飛煙樹。 離恨久、良宵當然虛度。 欲聽消息/ 難說氣候/ 泊時短短長長/ 不知朝暮。 待潮退、闌干拍千處。 豈有他故/ 簟竹吹涼/ 繡衾抱住。 恨祇恨殘紅唾香褥。 也依依、誰教匝月才傾吐。 休懊惱、待掃花邊霧。 落英仍濕君歸路。
荊道士──憨福品;七律二首: 便上秋山伴酒壺/ 盤空影細似飄鬚/ 瀟瀟雨過舒長醉/ 疾疾風來試腐儒/ 敢向新亭誇志氣/ 猶哀故國肆貍奴/ 叢林深處誰相喚/ 一酹江關有鷓鴣。 深垂絳帳倖垂名/ 願效鴻鵠向古行/ 野筆何須沾聖露/ 荒墳幸自掩清英/ 常從典籍知風力/ 近事權謀遠庶情/ 搦管稍嫌毫末冷/ 誰憐卅載一揮輕。 韓鐵棍——勇力品;七律一首: 風橫在野蔽天低/ 力拔殘雲迫日西/ 忍道相思霜不冷/ 猶驚作別劍先啼/ 重逢又近重陽節/ 爛斧爭如爛醉泥/ 與爾同懽須趁酒/ 能催咳唾作征鼙。
靴子李──義盜品;七律二首: 冷月沉竿雨在蓑/ 蠻煙處處壓漁歌/ 灘頭拍急苔痕淺/ 甕底傾空怨望多/ 餌誘生涯渾拙計/ 魚藏心事付清波/ 閒情愛道江湖遠/ 十載江湖一劍磨。 英雄惜命遺相知/ 忍看夷門執轡時/ 晉鄙勘符應合節/ 侯嬴計死更離奇/ 屠家已慣鉛刀割/ 貴冑難酬壯士癡/ 此詠非關忠與義/ 古來忠義不全屍。
范明儒──練達品;七律一首: 霧失羊碑渾歲暮 茶餘猴栗愧生涯 經年乏味療飢字 此夜添香快意詩 一律清吟初賦懶 常懷得意老成癡 聽燃爆竹三千個 但覺聲聲送舊遲。
金巧僧──聰明品;七律一首: 亂葉息風聲弄鐵/ 寒棲忍看輅摧花/ 江湖賞識塵衣客/ 殿閣笙歌錦笛家/ 野望京門孤鶩遠/ 恩遷嶺店夕陽斜/ 幽居不到人間世/ 怕聽郵鞭喝樹鴉。
九麻子—─詭飾品;七律二首: 不信甘泉路不平/ 積憂立解賴蘇瓊/ 步乒廚下凝天祿/ 飲馬窟邊臥戍卿/ 栗瀑空懸荒徑隱/ 秫田任熟老淵明/ 呼來共席非袁燦/ 睏覺春殘一杖橫。 一石猶應添五斗/ 八仙不必論三停/ 途窮逕向鄰姬臥/ 意適常依麴院聽 披髮踞床高阮籍/ 揚褌謝客效劉伶/ 裁詩便作仙泉頌/ 顛倒人居太白星。
插天飛──狡詐品;七律一首: 松風夜引萬刀橫/ 雨後淅零淬劍聲/ 有酒頻催詩意老/ 無絃更覺客心清/ 吟追律細敲壺缺/ 歎看煙輕拂月明/ 莫笑憂懷思伏莽/ 初涼天氣已涼情。 潘鼓皮──薄倖品;金縷曲一闋: 哭笑紅塵耳。 縱分離一時來去/ 天涯長記。 看破深情真偶得/ 未便花箋密意。 任詞裡充填翻悔。 人比疏花還寂寞/ 更歸時月落涼如水。 誰領略/ 生滋味。 芳菲散漫無時已。 奈何聽絲絃錯落/ 一般彈淚。 難學潘郎消擲果/ 怎料佳人知己。 獨難捨幾番新醉。 也似愁春非病酒/ 豈貪歡教說香衾裏。 思念否/ 常相憶。
獅子頭──褊急品;七律一首: 染翰輕盈憤世深/ 神思到紙氣森森/ 揮毫如將三千士/ 打鬼能安百萬心/ 板蕩偏懷孤節久/ 蜩螗更見異聲沉/ 愁腸不為新醅醉/ 獨有騷詩對古吟。
菖蒲花──頑懦品;青玉案一闋: 尋常寂寞歸南浦。 更幾棹、輕舟渡。 夢得猿啼催客句。 三聲離別/ 五夜零雨。 魂飛慣到遊山處。 踏盡芳華不知暮。 肯向雲深尋去路。 忽然寒意/ 悄然私語。 簾外春如許。
李仲梓——貪癡品;瑞鶴仙一闋: 黯然銷魂矣。 便萬里飛來/ 共此沈醉。 蕭蕭在深蕊。 肆風流纏祟╱ 又懽何事。 蜂情蝶意。 到春霖、絲絲是淚。 潤高枝/ 幾點迢遞。 望斷斜陽蔭裡。 無計。 一天涯遠/ 趕算程途/ 抱衾而已。 該忘得/ 艱難記。 對紅顏趁早/ 遲傷粉褪/ 畢竟年華容易。 看詩情老/ 咏聲哀/ 浮生如水。
不知不覺之間,「春燈會」已經二十年了;之前十九春秋,一年一度一會的十九則題品盡在於是。到了第二十年上,會於福島北灣東郭百級樓。這一日捱到黃昏,眾賓客正嘈嘈嚷嚷、紛紛紜紜地猜測:今回不知又輪到甚麼人物、說些甚麼樣兒的故事。忽然,樓外坊巷裡傳來一陣吆喝,聽聲彷彿是教賣零食菓子的小販──此等人物,自然是不足以言與會的了──孰料這小販也忒膽大,一聲霹靂也似地叫喚,道:「世上風流都叫他春燈公子品論遍了,但不知公子自個兒又算得哪一品呢?」
眾賓客怕失了禮儀,未便嘖聲,不意春燈公子卻聞言大笑,道:「說話人不是說話人,問得倒是在行。請教樓外這位:十九年來,天下人閒話天下事,你都聽說過了?」
十九年來,天下人閒話天下事,確乎不可不知………… 方觀承
乾隆十三年三月,方恪敏公觀承由直隸藩司升任浙撫,在撫署二門上題了一聯:「湖上劇清吟,吏亦稱仙,始信昔人才大;海邊銷霸氣,民還喻水,願看此日潮平」。這是有清一代督撫中文字最稱「奇逸」者。
嘉慶十八年,也是三月,方觀承的侄兒方受疇亦由直隸藩司升浙撫。這個時候,方觀承的兒子方維甸已經是直隸總督了。早在嘉慶十四年七月,方維甸也就以以閩浙總督暫護浙撫篆。數十年之間,父子叔姪兄弟三持使節,真是無比的殊遇,於是方維甸在父親當年題聯的楹柱旁邊的牆上又補了寫一聯:「兩浙再停驂,有守無偏,敬奉丹豪遵寶訓/一門三秉節,新猷舊政,勉期素志紹家聲」還在聯後寫了一段長跋,記敘了這樁家門幸事。人稱方觀承是「老宮保」,方維甸是「小宮保」。
方氏一門三大臣,要從一個人的故事說起。一個人,一枝筆,其餘全無依傍。
話說杭州西湖東南邊有座吳山,不知打從甚麼時候起,出了個賣卜的寒士,人稱方先生。方先生年歲不大,可是相術極準,頗得地頭兒上的父老敬重;也因為相術準,外地遊人不乏衝他去的,地方上的父老就敬重得更起勁兒了。
約當此際,杭州地界上有個姓周的大鹽商,生平亦好風鑒之術,遇上能談此道的人,無不虛懷延攬,專程求教,搞到後來,由於求速效,沒有時間和精力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祇好跟一個「五百年來一布衣」──號稱賴布衣嫡傳的第十六代徒孫學技。賴布衣是宋徽宗時代的風水大師,實為天下名卜,一脈師承到了清初,算算真有五百年。傳到這不知名姓的徒孫,宣稱保有有賴布衣的一身布衣。這身破布衣,也是五百年前古物──可見人要是出了名,就連死後,身上的東西也會多起來。
且說這周大鹽商殫銀三萬兩,跟著賴布衣的十六代徒孫學成「隨機易」──看了甚麼,無論動靜,祇消心頭有靈感,都能卜,人們稱道他門檻精到,未必是要巴結他有錢。他真算出過一件事,據說救了一整條船隊的鹽貨,還有幾百條人命,功德極大。
周大鹽商有個女兒,作父親的從小看她的相,怎麼看,怎麼看出個「一品夫人」的命來,於是自凡有上門來議婚的,一定左相右相、上下打量,總一句話打發:「此子同小女匹配不上。」如此延宕多年,女兒已經二十多歲了,卻沒有一個凡夫俗子有一品大員之相,能入得了周大鹽商之法眼的。
有那麼一回,鹽商們一同到廟裡行香,遇上大雨,來時雇的沒頂的轎子行不得也,祇好盤桓於寺廟左右,正遇見方先生的卜攤。周大鹽商自然不必花錢問卜,可他一眼瞧出這賣卜郎中骨骼非凡,又見他轉身走出去一段路,更覺此人奇偉俊逸──原來方先生每一步踏出,那留在地上的腳印都是扎扎實實的「中滿」之局;也就是今天人稱的「扁平足」了。 周大鹽商大樂,確信為貴人,上前問了年庚籍貫,知道方先生中過秀才,入過泮,有個生員的資歷在身,而且未婚,年紀也同自己的女兒相彷彿,益覺這是老天爺賞賜的機會,而且秀才是「宰相根苗」,豈能不禮重?遂道:「先生步武嚴君平後塵,自然是一樁風雅之事,不過大丈夫年富力強,還是該銳意進取,起碼教教書,啟蒙幾個佳子弟,教學相長,不也是一樁樂事?」
「步武嚴君平後塵」,說的是漢代蜀郡的嚴遵,漢成帝的時候在成都市上賣卜,每天得錢百文,足敷衣食所需,就收起卜攤,回家閉門讀《老子》。後來著有《道德真經指歸》,是大文學家揚雄的老師,終其一生不肯做官,活到九十幾歲。
周大鹽商用嚴遵來捧這方先生的場,可以說是極其推重了;方先生也知音感德,謙詞道謝了一陣,才說:「我畢竟是個外鄉人,此地也沒有相熟的戚友,就算想開館授業,也沒有代為引薦的人哪!」
周大鹽商即道:「方先生果然有意教書嗎?我正有兩個年紀少小的兒子,能請方先生來為我的兩個孩子開蒙嗎?」餘話休說,方先生欣然接受了。周大鹽商親自備辦了衣冠什物和一些簡單的家具,很快地就把方先生延聘到家裡來住下了。過了半年,發現這方先生性情通達,學問書法俱佳,周大鹽商便展開了他早已預謀的第二步計畫──重金禮聘了媒妁,納方先生為贅婿。
儘管風鑒之術有準頭可說,周大鹽商卻怎麼也沒料到自己的命理也該照看一下──這一對新人才合巹不多久,他自己就得急病死了。偌大一份產業,全由長子繼承下來。
周家的長子生小就是個膏糧子弟,根本看不起讀書人。父親一死,就不許兩個弟弟唸書了,還說:「學這套『丐術』做甚麼?」方先生在房裡讀書,新娘子也數落他:「大丈夫不能自作振發,全仗著親戚接濟也不是辦法。連我這個做老婆的也著實沒有顏面見人呢!」
方先生脾氣挺大,一聽這話就過意不去了,轉身要走人;聽他老婆又道:「我是奉了先府君之命,必得終身相隨侍,這樣說哪裡是有甚麼別的意思呢?祇不過是要勸夫子你自立;今天你就這麼一走了之,又能上哪兒去呢?」方先生仍止不住忿忿,說道:「饑餒寒苦是我的命,然而即便是饑餒寒苦,也不能仰人鼻息;如今不過是還我一個本來面目。至於上哪兒去麼──天地之大,何處不能容身?」儘管他的妻子苦苦哀求,方先生還是負氣,竟然脫了華服,穿上當初賣卜的舊衣裳,一文錢不拿,就把來時隨身攜帶的一套筆硯取走上路,可謂絕塵而去,去不復顧也!
身上沒有半文錢,就真是要行乞了。方先生打從杭州出發,也無計東洛西關、也不知南越北胡,走到山窮水盡,連乞討也無以自立的時候,已經來到了湖南嘉禾縣的境內。面前一座三塔寺,讓他興起了重操舊業的念頭──還是賣卜。
賣卜的這一行門道多、品類雜,遇有行客商旅稠密之處,便自成聚落,大家都是通天地鬼神的高人,很少會因為搶生意而彼此起釁的,方先生在三塔寺就結交了一個看八字的郎中,叫離虛子的。這離虛子與方先生往來,彼此都感覺到對方的人品不凡,特別來得投契。 有一天,離虛子趁四下無人,要了方先生的八字去,稍一推演,便道:「閣下當得一品之官,若往北去,不久就可以上達公卿了。我推過的命多了,閣下這個命格是十分清楚的,決計不會有錯謬。」方先生應道:「承君美意,可是沒有盤纏,我哪兒也去不了啊!」離虛子道:「這不難。自從我來到此地,多少年積累所得,也有十幾兩銀子,都交付閣下了罷!十年之後,可別忘了兄弟我,到那時閣下稍稍為我一揄揚,我就有吃喝不盡的生意了。」方先生道:「真能如公所言,方某如何敢忘了這大恩大德呢?」
方先生有了川資,搭上一條走漕的糧船來到了天津。錢又快用光了,聽說保定府有個賣茶的方某人,生意作得極大,方先生想起了這人還是個族親,就盤算著:何不暫時上保定去投靠、先混它個一時溫飽,再作打算呢?沒想到他後首剛到保定,就聽說那族親已然先一步歇了生意,回南方去了。方先生於是栖栖然如喪家之犬,遇見三兩個同鄉,人人都是措大,誰也沒有餘裕能幫助他。所幸有人看他入過學,能寫幾筆字,給薦了個在藩署(布政使司衙門)當「帖寫」的差事。
藩署是個公署,掌管一省之中吏、戶、刑、工各科的幕僚都在這一個衙門裡辦事。而所謂「帖寫」,不過就是個抄寫員,替衙門裡掌管案牘文書的書吏謄錄檔案而已。一天辛苦揮毫,賺不上幾十個制錢,僅敷餬口而已。
屋漏偏逢連夜雨──才寫了幾個月的字,方先生又染上了瘧疾──這個病,在當時的北方人眼中是個絕症,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倒虧得他那小小的上司書辦憐恤,拿了幾百枚制錢搋在他懷裡,趁他發熱昏睡之際,雇了幾個工人給扛出署去。工人們也懶得走遠,一見路邊有座古剎,便把方先生給扔在廊廡之下了。
當時大雪壓身,熱氣逢雪而解,方先生燒一退,人也清醒過來。一摸懷裡有銅錢,知道自己這又是叫人給擲棄了,歎了口大氣,不免又懷著一腔忿忿,勉強向北踽踽而行。
不多時,已經來到了漕河邊兒上,雪又下大了。方先生腳下認不清道路,偏在此時又發起寒來。祇一個沒留神,竟撲身掉下河裡去,眼見就要凍僵。也是他命不該絕──此際河邊一座小廟裡有個老僧,正擁坐在火爐邊打瞌睡,夢見殿前的神佛告訴他:「貴人有難,速往救之!」老僧睜開眼,赫然瞧見遠處河心之中蹲伏著一頭全身乍亮精白的老虎。老僧揉揉眼,再走出廟門幾步,發現河口上那白虎早已經沒了蹤跡,河沿兒上不過是趴著個看來已經凍餒不堪的貧民。
由於不知此人是生是死,老僧也猶豫著該不該出手相救。未料這時殿上的神佛又說話了:「出家人以慈悲為本,見死不救,你大禍就要臨頭了;可要是救了他呢,你這破廟的香火就快要興旺起來了。」老僧聽見這話,還有甚麼好猶豫的?當下有了精神,便將方先生扛進廟裡,脫去濕衣,溫以棉被,燒上一大鍋薑湯灌餵,方先生終於醒了。老和尚自然不會把神佛的指示說給方先生聽,卻殷殷地向他打聽來處和去向,弄清楚這是個落魄的儒生,益發地尊敬了,又給換上一套好衣裳,算是收留了他。
到了春暖花開的時節,老僧對方先生說:「先生畢竟是功名中人,而此地卻無可發跡。老衲有個師弟,是京師隆福寺的方丈,與王公大人們時相往來,那兒倒是個有機緣的去處。老衲且修書一封,另外再奉上兩吊錢的盤纏,送先生登程,還望先生能在彼處得意。」
春燈公子大宴江湖人物是一年一度的盛事,此會行之有年,幾與尋常歲時典祀無二。雖然說是例行,然而本年與會的是些甚麼樣的人物?又在甚麼地方舉行,行前一向是不傳之秘。直到應邀之人依柬赴約,到了地頭兒,自有知客人前來迎迓,待得與眾賓客相見,才知究竟。
這個一年一度的飯局,總在歲暮年初之間,應邀者感於春燈公子盛情,往往排除萬難,千里間關,無論跋涉如何辛苦,總期能與當世之豪傑人物一晤,把酒相談是幸。據說首會之地是在會稽鏡湖之東,地名東關,簡直是海內第一水榭,古稱天花寺的所在。相傳呂文靖嘗題詩於寺,云:
「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等閒能有幾人來。」
到南宋年間,天花寺仍然完好如初,陸務觀也有〈東關二首〉,云: 「天華寺西艇子橫/白蘋風細浪紋平/移家祇欲東關住/夜夜湖中看月生。」
「煙水蒼茫西復東/扁舟又繫柳陰中/三更酒醒殘燈在/臥聽瀟瀟雨打篷。」
不過,到了放翁作詩那時,天花寺三面皆是民間廬舍,前臨一支港,景觀大異於前。有人說是寺本在湖中,後遷徙於草市通衢之上云云。春去秋來,星移物換,到了春燈公子首會天下英雄的那一年,去放翁作詩之歲,又不免過了數百載,天花寺居然又給修蕺完好,依樣軒窗向水,綽影浮光,端的是一座莊嚴、清靜又雅潔的蘭若,誰也說不上來算不算是恢復了呂文靖題詩之時的舊觀,可誰都說相去非唯不遠,而輝煌璧麗,怕不猶有過之?當年此會盛況非凡,時時有人說起,總道輾轉識得與會者某某,又聞聽人說起某人自陳與會之事如何;總而言之,街談巷議,蜚短流長,一直不曾斷絕。
這春燈公子究竟是個怎樣出身?甚麼家世?籍隸何處?資歷如何?有些甚麼事功著述?彷彿誰也說不清楚。有說他是王公貴冑之後的,有說他是達官顯宦之子的,有說他祖上有范蠡、鄧通之流的人物,家道殷實,卻一向禁絕子孫涉足於名利之場,是以積數十代之財貨,富可敵國,卻鮮有忌之、害之甚或知之者。由於大會江湖豪傑之事甚秘,外人往往無從得窺情實,祇能任人謠傳訛說,也就沒有誰能考辨精詳,加之以聚會之地忽南忽北、徂東徂西,令人難以捉摸,一旦宴罷,人去樓空,原先的繁花盛景、燈火樓台,居然在轉瞬之間就空曠蕭索起來。即使讓參與過盛會的人物追述回憶,亦皆惘然,故而連春燈公子的祖居家宅究竟何在,都是個謎了。 天花寺一會之後,春燈公子暴得大名,人人爭相問訊:此君如何能將這麼些了不得的大人物相邀共至、齊聚一堂?給問到的與會之人不覺茫然,竊喜一念:原來我也算是個了不得的大人物了?大人物不常見,幾年例會下來,反而形成了另一個局面;自凡是有頭有臉的江湖大萬,不論是管領著一幫一派、或者傳承著某家某學,甚或精通一藝而能聞達於百里之境者,乃至偶發一事而能知名於三山五城之外者,多有到處探聽春燈公子行蹤的。打從年頭直到年尾,總有這麼樣的話語在口耳之間飄盪盤桓:「可知今年『春燈宴』邀了些甚麼人哪?」
「春燈宴」成了個現成的名目,這應該是天花寺之會後五、六年間的事。雖說春燈公子本人從來沒用過這個名目招徠賓客,可它畢竟是喊響了。傳聞之中,「春燈宴」上還有相當動人的花樣兒。
風聞打從「春燈宴」初開之歲,就沿襲了成例,每會當天自辰時起迎賓,無何道遠路近,客人們總在前一日都齊聚於館舍了。相識不識一照上面,對於彼此皆為春燈公子座上之客的身份都已經了然於胸,自然相互禮遇,一團和氣。即使偶有些人物,曾經鬧過大小尷尬,一旦在這場合上相見,也往往收拾起意氣,待宴罷之後,相揖別過,有甚麼過節,也祇能等後會之時再算了。正因如此,有許多江湖上礙於情面,不好相商的人物,往往還巴望著能在「春燈宴」上不期而遇,以便排難解紛。可這還不能算是人人期盼於「春燈會」上的花樣兒。真正的花樣兒,叫「立題品」。
總在開宴當日申牌時分,春燈公子的一十六童男女侍從就會引出這麼一個人物,此人或老或少,或男或女,年年不同。一亮相,不必多言,眾人自然都明白了:這位一定就是今年「立題品」的說話人。這位說話人究竟有些甚麼能為?是怎麼從眾賓客之中揀選出來的?其事甚秘,近二十年來,謠諑紛紜,沒有能說準的。然而無論如何,應邀與會之人都不免發些想頭:說不得今年到會之日,給那一十六位童男同女給請上台去「立題品」的就是我呢。是以人人來到「春燈宴」之前,總不免琢磨著要說一個足以令人咋舌稱奇的故事。於是,但見蟻躦蠅聚之人莫不晃腦搖頭,挺腰踮腳,滿心巴望著有那童男女來請移駕登台──自然,失望的多。
「立題品」之所以成了江湖中人參與「春燈會」的一個想頭,自然是有緣故的;但凡是登台說出一則首尾俱全的故事來的,春燈公子登時濡墨揮毫,或吟以詩、或填以詞,為這故事所述的人物下一個題品,書成一卷,發付裱褙匠人收了,究竟裝裱之後如何庋藏?如何展示?也無人詳其下落。倒是有那麼一闋詞,因為江左裱聖左彥奎不慎丟失,原件輾轉淪落,居然在數十年之後給誤植進茗畹堂重刻的納蘭詞(容若)詞集之中,亦殊可怪──這是岔話,就不多說了。 回頭說待春燈公子將詩、詞題品一揮而就,當下就給這說話人也奉上赤金萬兩,號曰「喉潤」。潤喉之資,竟過於中人之家一生一世的開銷,手筆之大,教人最是嘖嘖稱奇。奉上銀票之際,往往就是每年「春燈宴」熱鬧到極點的一刻。
春燈公子最早流傳於世的詩詞,就是這二十則題品。此乃斯人斯文首度問世,謹先臚列其一至十九品於左:
方觀承——儒行品;七古一首
代有文豪忽一發/ 偏如野草爭奇突/ 鋪張咫尺掬清英/ 肯向風塵申討伐/ 吾輩非今兼妒古/ 疑他李杜笑屈父/ 驚聞舉世不觀書/ 卻對燈灰吹寂苦/ 寧不知樽前幾度竟成懽/ 且樂鯨吸化羽翰/ 一飲三吟羞夢囈/ 百年九死悔儒餐/ 狼毫颯颯攀銀壁/ 龍墨殷殷伏玉盤/ 再約明朝看筆跡/ 猶知波磔愧蹣跚/ 悄賦留仙曲/ 忍聽錄鬼簿/ 臨老見真章/ 平生欣然託。
達六合——藝能品;瀟湘夜雨一闋: 醉捲洋流/ 怒酣雲氣/ 暑天一夜清颸。 挾山排闥送淋漓。 敲瓦疾/ 飄零劍影/ 翻帖亂/ 寥落蛇碑。 凝神處/ 揮馳不礙/ 遍掃新詞。 墨無濃淡/ 妝非深淺/ 耐得經時。 倩狂風稍息/ 留月斜窺。 才一瞬/ 驚波破紙/ 儘幾筆/ 卓磔凝思。 誇神武/ 何須電母/ 毫末到高枝。 朱祖謀──機慎品;滿庭芳一闋: 漸入春山/ 泥塗花信/ 蝶去朝夢留遲。 夜涼蒸透/ 雲在最高枝。 何若揚州蘇軾/ 憔悴裡、偷鑄新詞。 吟哦處/ 青衫竹杖/ 冷落到天涯。 寧知遊興老/ 三分宿醉/ 一片歸思。 想獨雕殘句/ 閒賦新題。 古道西風瘦馬/ 也不過、些許情癡。 爭如我/ 閉門讀史/ 開口變傳奇。
李純颩──洞見品;水龍吟一闋: 斜眉笑看英雄/ 十方風雨闌幹淚。 危樓慢倚/ 紅塵流盼/ 無情如此。 羈旅江湖/ 斷魂魏闕/ 暗銷王氣。 想驚弓斷戟/ 殘山剩水/ 音書絕、人歸未? 淺嘗蓴羹鱸燴。 趁烽煙、寄蒼茫意。 綢繆萬裏/ 向黃昏處/ 目無餘子。 痛快恩仇/ 沉酣歌舞/ 飄搖天際。 教漁樵看了/ 閒言碎語/ 幾番滋味。
黃八子──俠智品;鷓鴣天一闋: 擊缺銀壺趁醉驕。 繁華看盡最無聊。 蓬山不應殷勤喚/ 濁酒還愁寂寞消。 塵劫外/ 怨歌遙。 客船今夜共聽潮。 殘詩草罷燈焚過/ 獨送相思上九霄。 雙刀張—─巧慧品,七律一首: 逐客風塵逐客遊/ 蓬飛到處不堪留/ 憐螢暑夜曾捐扇/ 掛劍寒窗慣夢鷗/ 莫笑癡人書咄咄/ 寧知野趣鹿呦呦/ 鄰翁勸進樽中月/ 仰盡初霜白滿頭。
張天寶──運會品;沁園春一闋: 帳捲殘風/ 夢碎珠簾/ 抖擻暗塵。 漸清明雲月/ 蒼茫蘆雪/ 匆匆聚散/ 往往隨人。 佐讀青燈/ 臨書白素/ 一向消磨差似貧。 吹煙看/ 念山餘斷樹/ 雨急飄蓴。 紛紜、 國破無痕/ 更不忍無椎虛刺秦。 算年華辜負/ 豪情棖觸/ 稍嫌厭氣/ 未便灰心。 馳騁飛涎/ 誅伐碩鼠/ 墨染閒池驚莠民。 吾何憾/ 幸詩翁解飲/ 帖字銷魂。
史茗楣──奇報品;夜半樂一闋: 幾時別過重聚。 稍經點染/ 仍似胭脂駐。 數玉兔盈虧/ 喚郎依據。 淺深怎地/ 殷勤照拂/ 卻聞幾番憐惜嬌呼/ 失神無語。 更哪見、蟾枝滴零雨。 隔簾裡外見識/ 面撫芳茵/ 魂飛煙樹。 離恨久、良宵當然虛度。 欲聽消息/ 難說氣候/ 泊時短短長長/ 不知朝暮。 待潮退、闌干拍千處。 豈有他故/ 簟竹吹涼/ 繡衾抱住。 恨祇恨殘紅唾香褥。 也依依、誰教匝月才傾吐。 休懊惱、待掃花邊霧。 落英仍濕君歸路。
荊道士──憨福品;七律二首: 便上秋山伴酒壺/ 盤空影細似飄鬚/ 瀟瀟雨過舒長醉/ 疾疾風來試腐儒/ 敢向新亭誇志氣/ 猶哀故國肆貍奴/ 叢林深處誰相喚/ 一酹江關有鷓鴣。 深垂絳帳倖垂名/ 願效鴻鵠向古行/ 野筆何須沾聖露/ 荒墳幸自掩清英/ 常從典籍知風力/ 近事權謀遠庶情/ 搦管稍嫌毫末冷/ 誰憐卅載一揮輕。 韓鐵棍——勇力品;七律一首: 風橫在野蔽天低/ 力拔殘雲迫日西/ 忍道相思霜不冷/ 猶驚作別劍先啼/ 重逢又近重陽節/ 爛斧爭如爛醉泥/ 與爾同懽須趁酒/ 能催咳唾作征鼙。
靴子李──義盜品;七律二首: 冷月沉竿雨在蓑/ 蠻煙處處壓漁歌/ 灘頭拍急苔痕淺/ 甕底傾空怨望多/ 餌誘生涯渾拙計/ 魚藏心事付清波/ 閒情愛道江湖遠/ 十載江湖一劍磨。 英雄惜命遺相知/ 忍看夷門執轡時/ 晉鄙勘符應合節/ 侯嬴計死更離奇/ 屠家已慣鉛刀割/ 貴冑難酬壯士癡/ 此詠非關忠與義/ 古來忠義不全屍。
范明儒──練達品;七律一首: 霧失羊碑渾歲暮 茶餘猴栗愧生涯 經年乏味療飢字 此夜添香快意詩 一律清吟初賦懶 常懷得意老成癡 聽燃爆竹三千個 但覺聲聲送舊遲。
金巧僧──聰明品;七律一首: 亂葉息風聲弄鐵/ 寒棲忍看輅摧花/ 江湖賞識塵衣客/ 殿閣笙歌錦笛家/ 野望京門孤鶩遠/ 恩遷嶺店夕陽斜/ 幽居不到人間世/ 怕聽郵鞭喝樹鴉。
九麻子—─詭飾品;七律二首: 不信甘泉路不平/ 積憂立解賴蘇瓊/ 步乒廚下凝天祿/ 飲馬窟邊臥戍卿/ 栗瀑空懸荒徑隱/ 秫田任熟老淵明/ 呼來共席非袁燦/ 睏覺春殘一杖橫。 一石猶應添五斗/ 八仙不必論三停/ 途窮逕向鄰姬臥/ 意適常依麴院聽 披髮踞床高阮籍/ 揚褌謝客效劉伶/ 裁詩便作仙泉頌/ 顛倒人居太白星。
插天飛──狡詐品;七律一首: 松風夜引萬刀橫/ 雨後淅零淬劍聲/ 有酒頻催詩意老/ 無絃更覺客心清/ 吟追律細敲壺缺/ 歎看煙輕拂月明/ 莫笑憂懷思伏莽/ 初涼天氣已涼情。 潘鼓皮──薄倖品;金縷曲一闋: 哭笑紅塵耳。 縱分離一時來去/ 天涯長記。 看破深情真偶得/ 未便花箋密意。 任詞裡充填翻悔。 人比疏花還寂寞/ 更歸時月落涼如水。 誰領略/ 生滋味。 芳菲散漫無時已。 奈何聽絲絃錯落/ 一般彈淚。 難學潘郎消擲果/ 怎料佳人知己。 獨難捨幾番新醉。 也似愁春非病酒/ 豈貪歡教說香衾裏。 思念否/ 常相憶。
獅子頭──褊急品;七律一首: 染翰輕盈憤世深/ 神思到紙氣森森/ 揮毫如將三千士/ 打鬼能安百萬心/ 板蕩偏懷孤節久/ 蜩螗更見異聲沉/ 愁腸不為新醅醉/ 獨有騷詩對古吟。
菖蒲花──頑懦品;青玉案一闋: 尋常寂寞歸南浦。 更幾棹、輕舟渡。 夢得猿啼催客句。 三聲離別/ 五夜零雨。 魂飛慣到遊山處。 踏盡芳華不知暮。 肯向雲深尋去路。 忽然寒意/ 悄然私語。 簾外春如許。
李仲梓——貪癡品;瑞鶴仙一闋: 黯然銷魂矣。 便萬里飛來/ 共此沈醉。 蕭蕭在深蕊。 肆風流纏祟╱ 又懽何事。 蜂情蝶意。 到春霖、絲絲是淚。 潤高枝/ 幾點迢遞。 望斷斜陽蔭裡。 無計。 一天涯遠/ 趕算程途/ 抱衾而已。 該忘得/ 艱難記。 對紅顏趁早/ 遲傷粉褪/ 畢竟年華容易。 看詩情老/ 咏聲哀/ 浮生如水。
不知不覺之間,「春燈會」已經二十年了;之前十九春秋,一年一度一會的十九則題品盡在於是。到了第二十年上,會於福島北灣東郭百級樓。這一日捱到黃昏,眾賓客正嘈嘈嚷嚷、紛紛紜紜地猜測:今回不知又輪到甚麼人物、說些甚麼樣兒的故事。忽然,樓外坊巷裡傳來一陣吆喝,聽聲彷彿是教賣零食菓子的小販──此等人物,自然是不足以言與會的了──孰料這小販也忒膽大,一聲霹靂也似地叫喚,道:「世上風流都叫他春燈公子品論遍了,但不知公子自個兒又算得哪一品呢?」
眾賓客怕失了禮儀,未便嘖聲,不意春燈公子卻聞言大笑,道:「說話人不是說話人,問得倒是在行。請教樓外這位:十九年來,天下人閒話天下事,你都聽說過了?」
十九年來,天下人閒話天下事,確乎不可不知………… 方觀承
乾隆十三年三月,方恪敏公觀承由直隸藩司升任浙撫,在撫署二門上題了一聯:「湖上劇清吟,吏亦稱仙,始信昔人才大;海邊銷霸氣,民還喻水,願看此日潮平」。這是有清一代督撫中文字最稱「奇逸」者。
嘉慶十八年,也是三月,方觀承的侄兒方受疇亦由直隸藩司升浙撫。這個時候,方觀承的兒子方維甸已經是直隸總督了。早在嘉慶十四年七月,方維甸也就以以閩浙總督暫護浙撫篆。數十年之間,父子叔姪兄弟三持使節,真是無比的殊遇,於是方維甸在父親當年題聯的楹柱旁邊的牆上又補了寫一聯:「兩浙再停驂,有守無偏,敬奉丹豪遵寶訓/一門三秉節,新猷舊政,勉期素志紹家聲」還在聯後寫了一段長跋,記敘了這樁家門幸事。人稱方觀承是「老宮保」,方維甸是「小宮保」。
方氏一門三大臣,要從一個人的故事說起。一個人,一枝筆,其餘全無依傍。
話說杭州西湖東南邊有座吳山,不知打從甚麼時候起,出了個賣卜的寒士,人稱方先生。方先生年歲不大,可是相術極準,頗得地頭兒上的父老敬重;也因為相術準,外地遊人不乏衝他去的,地方上的父老就敬重得更起勁兒了。
約當此際,杭州地界上有個姓周的大鹽商,生平亦好風鑒之術,遇上能談此道的人,無不虛懷延攬,專程求教,搞到後來,由於求速效,沒有時間和精力窮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祇好跟一個「五百年來一布衣」──號稱賴布衣嫡傳的第十六代徒孫學技。賴布衣是宋徽宗時代的風水大師,實為天下名卜,一脈師承到了清初,算算真有五百年。傳到這不知名姓的徒孫,宣稱保有有賴布衣的一身布衣。這身破布衣,也是五百年前古物──可見人要是出了名,就連死後,身上的東西也會多起來。
且說這周大鹽商殫銀三萬兩,跟著賴布衣的十六代徒孫學成「隨機易」──看了甚麼,無論動靜,祇消心頭有靈感,都能卜,人們稱道他門檻精到,未必是要巴結他有錢。他真算出過一件事,據說救了一整條船隊的鹽貨,還有幾百條人命,功德極大。
周大鹽商有個女兒,作父親的從小看她的相,怎麼看,怎麼看出個「一品夫人」的命來,於是自凡有上門來議婚的,一定左相右相、上下打量,總一句話打發:「此子同小女匹配不上。」如此延宕多年,女兒已經二十多歲了,卻沒有一個凡夫俗子有一品大員之相,能入得了周大鹽商之法眼的。
有那麼一回,鹽商們一同到廟裡行香,遇上大雨,來時雇的沒頂的轎子行不得也,祇好盤桓於寺廟左右,正遇見方先生的卜攤。周大鹽商自然不必花錢問卜,可他一眼瞧出這賣卜郎中骨骼非凡,又見他轉身走出去一段路,更覺此人奇偉俊逸──原來方先生每一步踏出,那留在地上的腳印都是扎扎實實的「中滿」之局;也就是今天人稱的「扁平足」了。 周大鹽商大樂,確信為貴人,上前問了年庚籍貫,知道方先生中過秀才,入過泮,有個生員的資歷在身,而且未婚,年紀也同自己的女兒相彷彿,益覺這是老天爺賞賜的機會,而且秀才是「宰相根苗」,豈能不禮重?遂道:「先生步武嚴君平後塵,自然是一樁風雅之事,不過大丈夫年富力強,還是該銳意進取,起碼教教書,啟蒙幾個佳子弟,教學相長,不也是一樁樂事?」
「步武嚴君平後塵」,說的是漢代蜀郡的嚴遵,漢成帝的時候在成都市上賣卜,每天得錢百文,足敷衣食所需,就收起卜攤,回家閉門讀《老子》。後來著有《道德真經指歸》,是大文學家揚雄的老師,終其一生不肯做官,活到九十幾歲。
周大鹽商用嚴遵來捧這方先生的場,可以說是極其推重了;方先生也知音感德,謙詞道謝了一陣,才說:「我畢竟是個外鄉人,此地也沒有相熟的戚友,就算想開館授業,也沒有代為引薦的人哪!」
周大鹽商即道:「方先生果然有意教書嗎?我正有兩個年紀少小的兒子,能請方先生來為我的兩個孩子開蒙嗎?」餘話休說,方先生欣然接受了。周大鹽商親自備辦了衣冠什物和一些簡單的家具,很快地就把方先生延聘到家裡來住下了。過了半年,發現這方先生性情通達,學問書法俱佳,周大鹽商便展開了他早已預謀的第二步計畫──重金禮聘了媒妁,納方先生為贅婿。
儘管風鑒之術有準頭可說,周大鹽商卻怎麼也沒料到自己的命理也該照看一下──這一對新人才合巹不多久,他自己就得急病死了。偌大一份產業,全由長子繼承下來。
周家的長子生小就是個膏糧子弟,根本看不起讀書人。父親一死,就不許兩個弟弟唸書了,還說:「學這套『丐術』做甚麼?」方先生在房裡讀書,新娘子也數落他:「大丈夫不能自作振發,全仗著親戚接濟也不是辦法。連我這個做老婆的也著實沒有顏面見人呢!」
方先生脾氣挺大,一聽這話就過意不去了,轉身要走人;聽他老婆又道:「我是奉了先府君之命,必得終身相隨侍,這樣說哪裡是有甚麼別的意思呢?祇不過是要勸夫子你自立;今天你就這麼一走了之,又能上哪兒去呢?」方先生仍止不住忿忿,說道:「饑餒寒苦是我的命,然而即便是饑餒寒苦,也不能仰人鼻息;如今不過是還我一個本來面目。至於上哪兒去麼──天地之大,何處不能容身?」儘管他的妻子苦苦哀求,方先生還是負氣,竟然脫了華服,穿上當初賣卜的舊衣裳,一文錢不拿,就把來時隨身攜帶的一套筆硯取走上路,可謂絕塵而去,去不復顧也!
身上沒有半文錢,就真是要行乞了。方先生打從杭州出發,也無計東洛西關、也不知南越北胡,走到山窮水盡,連乞討也無以自立的時候,已經來到了湖南嘉禾縣的境內。面前一座三塔寺,讓他興起了重操舊業的念頭──還是賣卜。
賣卜的這一行門道多、品類雜,遇有行客商旅稠密之處,便自成聚落,大家都是通天地鬼神的高人,很少會因為搶生意而彼此起釁的,方先生在三塔寺就結交了一個看八字的郎中,叫離虛子的。這離虛子與方先生往來,彼此都感覺到對方的人品不凡,特別來得投契。 有一天,離虛子趁四下無人,要了方先生的八字去,稍一推演,便道:「閣下當得一品之官,若往北去,不久就可以上達公卿了。我推過的命多了,閣下這個命格是十分清楚的,決計不會有錯謬。」方先生應道:「承君美意,可是沒有盤纏,我哪兒也去不了啊!」離虛子道:「這不難。自從我來到此地,多少年積累所得,也有十幾兩銀子,都交付閣下了罷!十年之後,可別忘了兄弟我,到那時閣下稍稍為我一揄揚,我就有吃喝不盡的生意了。」方先生道:「真能如公所言,方某如何敢忘了這大恩大德呢?」
方先生有了川資,搭上一條走漕的糧船來到了天津。錢又快用光了,聽說保定府有個賣茶的方某人,生意作得極大,方先生想起了這人還是個族親,就盤算著:何不暫時上保定去投靠、先混它個一時溫飽,再作打算呢?沒想到他後首剛到保定,就聽說那族親已然先一步歇了生意,回南方去了。方先生於是栖栖然如喪家之犬,遇見三兩個同鄉,人人都是措大,誰也沒有餘裕能幫助他。所幸有人看他入過學,能寫幾筆字,給薦了個在藩署(布政使司衙門)當「帖寫」的差事。
藩署是個公署,掌管一省之中吏、戶、刑、工各科的幕僚都在這一個衙門裡辦事。而所謂「帖寫」,不過就是個抄寫員,替衙門裡掌管案牘文書的書吏謄錄檔案而已。一天辛苦揮毫,賺不上幾十個制錢,僅敷餬口而已。
屋漏偏逢連夜雨──才寫了幾個月的字,方先生又染上了瘧疾──這個病,在當時的北方人眼中是個絕症,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倒虧得他那小小的上司書辦憐恤,拿了幾百枚制錢搋在他懷裡,趁他發熱昏睡之際,雇了幾個工人給扛出署去。工人們也懶得走遠,一見路邊有座古剎,便把方先生給扔在廊廡之下了。
當時大雪壓身,熱氣逢雪而解,方先生燒一退,人也清醒過來。一摸懷裡有銅錢,知道自己這又是叫人給擲棄了,歎了口大氣,不免又懷著一腔忿忿,勉強向北踽踽而行。
不多時,已經來到了漕河邊兒上,雪又下大了。方先生腳下認不清道路,偏在此時又發起寒來。祇一個沒留神,竟撲身掉下河裡去,眼見就要凍僵。也是他命不該絕──此際河邊一座小廟裡有個老僧,正擁坐在火爐邊打瞌睡,夢見殿前的神佛告訴他:「貴人有難,速往救之!」老僧睜開眼,赫然瞧見遠處河心之中蹲伏著一頭全身乍亮精白的老虎。老僧揉揉眼,再走出廟門幾步,發現河口上那白虎早已經沒了蹤跡,河沿兒上不過是趴著個看來已經凍餒不堪的貧民。
由於不知此人是生是死,老僧也猶豫著該不該出手相救。未料這時殿上的神佛又說話了:「出家人以慈悲為本,見死不救,你大禍就要臨頭了;可要是救了他呢,你這破廟的香火就快要興旺起來了。」老僧聽見這話,還有甚麼好猶豫的?當下有了精神,便將方先生扛進廟裡,脫去濕衣,溫以棉被,燒上一大鍋薑湯灌餵,方先生終於醒了。老和尚自然不會把神佛的指示說給方先生聽,卻殷殷地向他打聽來處和去向,弄清楚這是個落魄的儒生,益發地尊敬了,又給換上一套好衣裳,算是收留了他。
到了春暖花開的時節,老僧對方先生說:「先生畢竟是功名中人,而此地卻無可發跡。老衲有個師弟,是京師隆福寺的方丈,與王公大人們時相往來,那兒倒是個有機緣的去處。老衲且修書一封,另外再奉上兩吊錢的盤纏,送先生登程,還望先生能在彼處得意。」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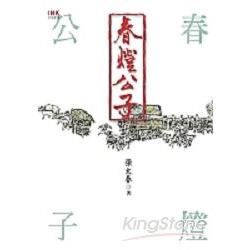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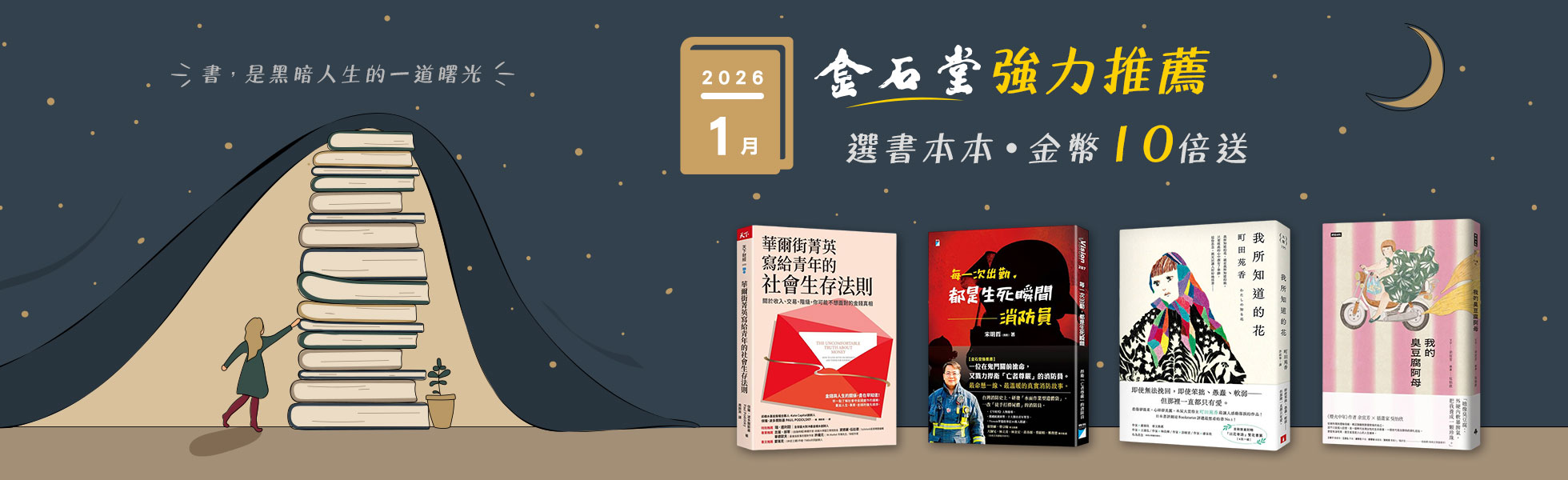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