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堂
一場穿越讓他被冒牌貨霸占身體~父母情人都沒發現異樣,偏偏是他的仇敵一眼看穿那不是他!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一場莫名其妙的靈魂穿越,一段刻骨銘心的深沉暗戀
別人穿越總是越活越好,他就是那個被取代的倒楣鬼
千萬讀者敲碗期待!最想知道結局的斷頭大坑!
晉江原創網人氣懸疑耽美小說
獨家完整版精彩結局,收錄特別加筆番外篇〈主角們〉
愛得再深,混得再好又能怎樣?
一場莫名其妙的靈魂穿越,沈意成了孤魂野鬼,只能困在家中,眼睜睜地看著那個冒牌貨號稱失憶,霸占他的身體、他的家人、朋友與情人,卻過得比他好。
五年來,沒有人發現沈意不是沈意。
他被全世界狠狠遺忘,曾經的張揚銳氣一點點困在虛無之地消磨殆盡。
直到那一天,死對頭陸嘉澤出現在他面前,在「沈意」周遭展開調查。
沈意幻想過無數次,有人能揪出冒牌貨,找回真正的他。
父母情人死黨都沒發現異樣,偏偏是他的仇敵一眼看穿。
沈意有點興奮,有點期待,卻又想不透,怎麼會是那個陸嘉澤呢?
目錄
第一章 虛無之地
第二章 同學少年多不賤
第三章 亡者歸來
第四章 遙不可及
第五章 北雁南飛
第六章 現出原形
第七章 抽絲剝繭
第八章 噬罪者
第九章 唯有時間
第十章 繪夢之章
第十一章 絕地反攻
第十二章 骨血相融
終章 類似愛情
番外 主角們
後記
試閱
第一章 虛無之地
於是我與那輛車漸離漸遠,我回家做飯。
沈意花了三、四年才把這本書看完,倒不是他看書慢,實在是書的主人拖拖拉拉,一週才翻那麼一、兩頁,於是他每週的消遣就是把那一、兩頁反覆誦讀,以保證自己還記得住怎麼發音。
他有好些年沒有跟人說話了,他不太記得清具體的時間,可能是四年也可能是五年,剛開始他還一天天地數著,後來他就數糊塗了。儘管他曾經算是個高材生,但是日復一日的重複,總會把那些耐心都磨掉的,現在他連春夏秋冬都懶得算了。
現在應該算是春天了吧,他往窗外看了看,恍惚看到小區裡的桃花開了,但是他不確定,他記得他入住的那一年小區裡還沒有桃花的,都是討人厭的香樟樹,一到春夏季節,就滿地羊屎蛋子一樣的果實,踩起來咯吱咯吱的。
他似乎還記得當時他的車停在香樟樹下,每次都落滿了果實,然後他就會大聲抱怨,再然後那個人就會安慰地拍拍他,要他不要激動。
他這一年記憶有些壞了,所以也分不清這到底是記憶還是他意淫出來的,於是想了想也就算了。
「於是我與那輛車漸離漸遠,我回家做飯。」他又把結尾讀了一遍,關於這個結尾他已經讀了三天了,但是他還是讀下去了,看書的時候他才能勉強確認自己曾經是一個人,真實活過的人。
他再次把結尾讀了七、八遍,陽台上發出了微弱的汪汪聲,他小跑著過去,看到後勤部蜷縮在窩裡,小小聲地叫著,似乎是在壓抑什麼,極其不安。
「怎麼了?」他輕輕問,蹲下去查看,後勤部是一條老狗,很老很老了,沈意覺得應該有七、八年了,也可能更長點,九年什麼的,他只記得他把後勤部帶回來的那一年,他才剛剛畢業。
那時他剛找了工作,忙著出櫃忙著跟父母吵架忙著和情人甜蜜,後勤部被照顧得一塌糊塗,但是他跟後勤部關係還算不錯,他是牠的主人,於是在他消失前,牠都一直很聽話。
牠哀哀地叫著,皮毛都皺起來了,他不知道牠是不是要死了,但是他並不難過。
他伸出手,很想摸摸牠。在他是人的時候,他很少做這個動作。因為他很忙,忙著賺錢,忙著跟情人甜蜜,忙著和對手攀比,忙著對朋友神氣,他總是在各種衣香鬢影觥籌交錯裡穿梭,他天生是屬於交際場的。
世界是公平的,以前他不摸牠,現在他就摸不到牠,他的手指在碰到牠的頭顱時,跟以前一樣,輕飄飄地穿過去了,像是立體的影像,能看,卻只是薄薄的光影。
「怎麼了?」他伸著手在虛空裡,有個跟他一樣的聲音漸漸靠近了,沈意聽到後勤部的喉嚨裡吐出了呵呵的咕嚕聲,像是在撒嬌又像是在討好。
他不用抬頭都知道來的是誰,好幾年了,他都聽習慣了,更正確的說,三十多年了,他都聽習慣了。
「是不是病了?」另外一個聲音也跟了過來,還是一樣的熟悉,沈意轉過頭去,看到兩個男人站在陽台外面,前面那個皺著眉頭,後面那個一臉不耐,兩人半半拉拉地抱在一起,一大早就甜蜜得一塌糊塗。
兩個熟悉的人,一個是他的身體,一個是他情人。
三、四年前,他一直在想這是為什麼,三、四年後,他終於想通了。
大概這世界上真有狗血劇這種東西,或者因果報應什麼的,他只知道有一天,他突然就變成了一個不知道是鬼還是魂魄的虛無物體,然而自己的身體還活著。
他還記得那件事,因為實在記憶太深刻,他想忘都忘不了。
他記得那是他從父母家回來的第二天。他出櫃了二年,他父母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那一天他爸媽終於讓他回去了,他興奮得一塌糊塗,喝了點小酒,回來如常地跟情人親密了,然後早上起來就發現自己飄在了天花板上。
他分不清是自己死了還是別的什麼,但是他千真萬確地看到自己的身體活了,後來他反覆琢磨,只能挫敗地承認,這世界估計真有什麼靈魂穿越之類的事情,因為那個身體醒了之後,說失憶了。
他在家裡轉來轉去,試圖講話,試圖出門,試圖寫字,但是他什麼都碰不了,於是他就眼睜睜地看著他的身體號稱失憶之後成為了他,一寸一寸地入侵了他的領地,先是他的情人,然後是他的父母,之後是他的朋友。
他不太清楚應該叫他的身體什麼,後來第一次看到情人與他的身體做愛的時候,他決定管那個身體叫冒牌貨,再後來他慢慢地看到情人與冒牌貨感情日濃之後,他已經只想管冒牌貨叫正牌貨了。
冒牌貨其實過得比他好,他想,他脾氣有點暴躁,跟情人在一起,雖然不吵架但是也有摩擦;可冒牌貨很溫順,所以三、四年的時間,他困在這裡,慢慢地看了一部名為愛情的生活劇,那麼纏綿那麼感人。 「是要死了吧?」冒牌貨或者正牌貨說,被他情人抱著腰,眼眸明亮,笑容燦爛,「要不要找個地方把牠埋了?」
他情人其實是個好情人,跟他在一起的時候也是脾氣溫順的,他還記得冒牌貨剛醒來的時候說失憶了,他情人就接受了,一天一天照顧,耐心又……刻意。
沈意其實是不太相信他情人看不出來冒牌貨跟他不一樣,就算是有那個失憶的藉口也不成立。失憶是忘了一些事情,又不是去換心了,從頭到尾都不同,怎麼會這麼容易讓人相信呢?
他喜歡吃辣的,這個冒牌貨喜歡吃甜的,他性格招搖,這個冒牌貨溫順,他從來不會一覺睡到接近十點才起床,但是冒牌貨喜歡睡懶覺,他一直負責賺錢,在社交場上縱橫,但是這個冒牌貨連出門都懶。
差太多了,但是他情人相信得太自然了,以至於他這一年有事沒事都開始琢磨,是不是其實他情人潛意識裡更希望他是冒牌貨那樣的人。
不過這種事只能偶爾琢磨了當消遣,深處他是絕對不敢想的。
人,總要有點希望。
「死了再埋吧。」他情人低低地說,一張小白臉蹭在冒牌貨的脖子上,沈意還記得他情人的名字也與小白臉一樣的娘娘腔,叫雲默。
他仰起頭,冒牌貨與雲默離他只有幾十厘米,那兩人抱在一起,臉頰廝磨,迎著太陽特別的燦爛,他記得以前有人誇過他和情人長得好的,帥哥與美人組合。
後勤部還在哀哀地叫著,大概是真的要死了,但是無論是冒牌貨還是雲默都不感興趣了,牠活得夠久了,即使死也是理所當然的,於是他們在討論回家的事情,商量著要不要帶點酒回去。
酒是他從小一起長大的死黨送的。送的那天,他還在讀著結尾,蹲在虛空裡咬著舌頭一字一頓,他死黨送了特產酒過來,還親切地拍了拍冒牌貨。
冒牌貨失憶之後,與家裡關係就好多了,不像他那時候,因為出櫃,跟父母就差點成仇敵了,要不是冒牌貨性格實在太悶,說不定生意做得都會比他好。
他不想再聽他們討論了,蹲下去繼續看後勤部,牠蜷縮成一團,皮毛都鬆弛了,他想如果牠死了,能看見他就好了。
其實他也不知道自己死了沒有,他只知道自己出不了這棟房子,也碰不了任何物質,他記得以前上學的時候,老師說,一個人一生中會死三次,第一次是腦死亡,意味著身體死了;第二次是葬禮,意味著在社會中死了;第三次是遺忘,這世上再也沒有人想起你了,那就是完完全全地死透了。
他覺得自己的第一次死亡還沒有到,但是又好像確確實實地到了第三次死得透透的地步了。
他的情人他的父母他的朋友,再也沒有任何人記得他了,他們甚至都不能發現他和冒牌貨有任何不同。
那對小情人的討論到了高潮,一者堅持要帶,一者堅持說喝酒傷身,兩人小小聲地爭執了一會,結果不知道怎麼就激烈地吻了起來,他偏著頭看著陽光,罵了一聲狗男男,然後才發現其實自己已經麻木了。
四、五年了啊,他想,看著太陽,以前他對著太陽眼睛很疼,現在他什麼感覺都沒有,只是覺得那種光亮讓人瘋狂,讓他劇烈地渴望把後勤部勒死了。
於是我與那輛車漸離漸遠,我回家做飯。他再背了一次結尾,站起來回書房,他打算把最後一頁再讀十遍,因為那對狗男男親到情難自已,已經在地毯上滾起來了。
沈意是個人的時候,就不太喜歡週末,一到週末他可能比平時都要忙,各種邀請聚會堆積在一起,端的是腳不點地,現在他成了鬼魂的時候,倒是特別喜歡週末。
他分不清日日月月,卻記得住週末,因為到了週末那兩個人就會出門,讓他一個人清靜清靜。
他在無人的房子裡轉了三圈,這房子是他買的,買的時候託人內定,位置是最好的,採光也是一等一的棒,開窗便見人工湖,夏天的時候涼風習習蓮香隱隱,冬天在飄窗上坐一坐,渾身都暖洋洋的。
他從客廳走到臥室,又穿越到廚房,最後又繞回陽台。好幾年了,他的領地只有這棟房子,於是他已經熟悉了每一寸土地。
後勤部還在哀哀叫著,他不知道牠是不是病了,但是他摸不到牠,於是只好坐在牠身邊看著牠。其實他有點討厭牠,都說狗是靈敏的生物,但是後勤部一點也沒有發現冒牌貨和他有什麼不同,每天都開開心心地蹭著冒牌貨。 「你要是能看見我就好了。」只要有一個生物能看見他就行了,狗也好貓也罷,哪怕是一隻蟑螂都行啊,這一年他感覺自己已經慢慢地垮掉了,開始的時候還憎恨情人、憎恨父母看不出他的區別,現在他已經什麼都不恨了,他只想跟一個生物說說話。
哪怕是死了呢,死了也好啊,變成鬼,只要有東西跟他在一起都好。
人總到了失去的時候才會珍惜,以前,他身邊總是圍繞著一堆人,那時候他是大家公子,事業有成,哪怕是出櫃跟父母鬧翻了,那些狐朋狗友也會豎著大拇指說沈少爺,夠爺們,來,為你們偉大的愛情,我敬你一杯。
偉大的愛情。他懶洋洋地想,以前他和雲默在一起的時候,愛得死去活來,不顧一切地出櫃,發誓海枯石爛山崩地裂不分開,但是四、五年之後,他看著雲默和別人親熱,已經麻木了。
時間這玩意兒能把一切都消磨了,你的意志你的感情你的過去,它一寸一寸地前進著,你無奈看著陽光下的光線,就被它一點一點抹殺了。
後勤部哀哀的聲音漸漸低了了下去,似乎是要睡著了,他偏著頭,看到牠的眼睛濕漉漉的,像是哭了。
這麼多年,他目睹了自己逐漸死去,現在他又要目睹另外一個生物死去了,雖然前者是社會上的死亡,後者是物理上的死亡,但是其實本質都一樣,最終消失。
大概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死了沒有人惦記,而後勤部將要死了,他還惦記著。
他伸出手把手放在牠頭上,陽光穿透下來,他的手只是在虛空裡,但是他還是覺得有點高興,好像真摸到了什麼。
他玩了一會,聽到了門鎖的聲音,估計是那對小情人是忘了拿東西,於是也懶得去看。
他盤算著晚上怎麼玩窗口進出遊戲,這是他少有的樂趣,他不允許自己一大早就把這樂趣享受了。
客廳裡聲音斷斷續續的,似乎是有人在找什麼,一會輕一會重,翻得嘩嘩啦啦,他漫不經心地聽了一會才發現不對。冒牌貨和雲默的腳步聲他都聽到熟悉了,雲默走路是輕輕的,而冒牌貨喜歡拖著鞋子走路,嗤啦嗤啦的,但是今天這個是那種沉穩的、重重的步調。
難道是小偷?他突然有點興奮,忙竄出去,這大概是他現在唯一的好處了,想走路的時候走路,不想走路的時候,倒掛在房頂也沒問題。
客廳裡空無一人,他聽見書房裡有著微弱的翻書聲,忙奔過去,一看之下,簡直大喜,真的是個小偷啊,背對著他,穿了一身黑色的大衣,彎著腰正在翻他之前看了四、五年的書。
他有一瞬間激動得快哭了,這麼多年,除了那對狗男男和偶爾過來的死黨與父母,他就再也沒有看過任何一個人了。
他輕手輕腳地走過去,其實這是多餘的,哪怕他現在大聲唱歌,這個賊也不會發現的,但是他還是想輕一點,假裝自己有可能被發現。
那個賊一直在看那本書,過了一會才抬起頭來,沈意這兩年的記憶裡衰退,很多事情已經記不清了,但是等這個賊抬起頭來的時候,他還是想「啊」一聲。
這個賊,他認識!
更準確地說,這可能就不是一個賊。他想,困惑地看著對方直起身,又去翻他的抽屜,他情人是個小職員,幾乎不用書房,而那個冒牌貨號稱失憶了,壓根就不工作,於是這書房其實還是保持著他生前的樣子,他看到那個賊把他抽屜裡好多書都翻出來,然後一本一本地弄整齊了。
他這才看到,這個賊還拖著一個巨大的行李箱,就放在腳邊,那裡面現在已經放了許多東西,有客廳裡的相框,還有臥室裡的一些小零碎,他甚至覺得那些東西都是很古老的了,基本都是他在的時候就有的,而不是後來冒牌貨添加的。
「陸嘉澤,你想幹什麼?」他問,但是知道對方壓根聽不到,也就只能笑了笑。
這個賊……不,應該說這個人,其實他很熟悉。他們一起長大的,之所以沒有發展成死黨,實在是因為他們倆性格不太相投,陸嘉澤跟他一樣囂張,從小就跟他打架,上學拚成績,後來又拚工作與業績,他們一直就互相傾軋著,那些年偶爾在酒會上相逢,他們都假裝看不見對方。
他現在記不清的事情很多,但是對陸嘉澤印象深刻。畢竟二十幾年兩人一直暗暗較勁。他還記得他出櫃那年,那些朋友們都鼓勵他或者誇獎他爺們,只有陸嘉澤在某個酒會上不冷不熱地看他說,把眼睛擦亮些,看看值不值得。
他那時把酒都倒在了陸嘉澤的頭上,他們互相諷刺,他說陸嘉澤嫉妒他有個好情人,陸嘉澤說誰會把那種貨色當個寶啊,然後兩人在廁所裡還互相甩了對方幾拳。 陸嘉澤是個小白臉,長得比雲默還要秀氣,卻非要喊雲默是個小白臉,把他氣得不行,趁著互毆的時候還狠狠地把陸嘉澤的臉揍成了爛番茄。
不過他倒是記得,那之後陸嘉澤就出國了,他還高興了好幾天,跟情人說,終於送走瘟神了,可以放鞭炮慶祝之類的弱智話。
陸嘉澤確實是個瘟神,走了幾個月後他父母就突然向他妥協了,讓他回家,再然後他就突然變成了現在的樣子。
他圍著陸嘉澤繞了幾圈,後者這幾年居然沒有變化,依舊是一張冷得能見冰雪的小白臉,好像被人欠了八百萬並且討不回來似的,太陽這麼好的日子還戴著手套,站姿筆直如標槍。
他繞來繞去,看著陸嘉澤把他的書房翻得一塌糊塗,把許多莫名其妙的東西都帶走了。比如他的一本相冊,那裡面的照片都是剪綵或者什麼重要酒會胡亂拍的,都是工作上的,所以便一直扔在書房。
陸嘉澤拿這些東西幹什麼呢?他想,眼睜睜地看著後者把東西都搜刮到了行李箱裡,然後開始搞破壞。先是把電腦砸了,然後是把抽屜裡面不要的全部倒出來,甚至還把書櫥給推翻了,像是神經病發作。
書房裡亂得一塌糊塗,破壞狂卻好像滿意了,拍拍手拖著箱子走了出去。又按照書房的套路,把臥室和客廳裡所有的東西也都給破壞了,能砸的砸,不能砸的全部扔地上,還踩了幾腳。他跟著陸嘉澤晃了好幾個房間,終於醒悟過來,陸嘉澤應該是在模擬偷竊現場。
因為陸嘉澤把抽屜裡零碎的現金與一些玉石裝飾品也拿走了。
難道他書房裡有什麼重要東西,值得陸嘉澤來偷嗎?沈意饒有趣味地想,他現在一點都不在乎有人偷東西,他都死了那麼多年了,還有什麼好在乎的,他只希望這個賊多待一會,他喜歡看到人的感覺。
可惜陸嘉澤聽不到他的心聲,在把客廳毀完了之後,就拖著行李箱走了,他一步一步跟著陸嘉澤,心裡無端地淒涼起來。
一個人,得有多貧瘠,才會見到敵人都渴望抱著他說親愛的你不要走。
陸嘉澤開門出去,後勤部在陽台上哀哀地又叫了起來,前者的腳步聲頓了頓,似乎聽到了,然後居然就又折回來了。
「他連你也不要了嗎?」陸嘉澤在亂成一鍋粥的客廳裡開闢出一條路,他不像沈意,想摸後勤部就摸到了,後勤部在他手上低低地哀鳴著,沈意驚訝地看到陸嘉澤居然紅了眼睛,「我帶你回家吧。」
瘟神陸嘉澤大概是翻身了,這次倒做了點好事,那對小情人一回來就報了警,在客廳裡走來走去,激烈地討論著到底是小偷呢還是報復呢,熱鬧得不得了。
沈意在邊上聽得嗤之以鼻,如果是他以前做生意時,還勉強可能得罪人,遭到報復什麼的,冒牌貨這幾年什麼都不懂,都是宅在家裡的,到哪去樹敵啊?
他飄到門口去,那裡落著那對狗男男留下的袋子,他把頭埋過去看了看,才發現裡面都是食物,應該是他父母那裡帶回來的。
他母親是個標準的貴夫人,十指不沾陽春水,這幾年倒是頻繁下廚了,冒牌貨好幾次還跟雲默調笑說燒得太難吃了,只有一道蜜汁豆腐能入口,於是每次吃飯只好拚命吃豆腐,弄得他媽媽以為他喜歡,每次去都燒不說,還要給他弄好了帶回來。
於是我與那輛車漸離漸遠,我回家做飯。
沈意花了三、四年才把這本書看完,倒不是他看書慢,實在是書的主人拖拖拉拉,一週才翻那麼一、兩頁,於是他每週的消遣就是把那一、兩頁反覆誦讀,以保證自己還記得住怎麼發音。
他有好些年沒有跟人說話了,他不太記得清具體的時間,可能是四年也可能是五年,剛開始他還一天天地數著,後來他就數糊塗了。儘管他曾經算是個高材生,但是日復一日的重複,總會把那些耐心都磨掉的,現在他連春夏秋冬都懶得算了。
現在應該算是春天了吧,他往窗外看了看,恍惚看到小區裡的桃花開了,但是他不確定,他記得他入住的那一年小區裡還沒有桃花的,都是討人厭的香樟樹,一到春夏季節,就滿地羊屎蛋子一樣的果實,踩起來咯吱咯吱的。
他似乎還記得當時他的車停在香樟樹下,每次都落滿了果實,然後他就會大聲抱怨,再然後那個人就會安慰地拍拍他,要他不要激動。
他這一年記憶有些壞了,所以也分不清這到底是記憶還是他意淫出來的,於是想了想也就算了。
「於是我與那輛車漸離漸遠,我回家做飯。」他又把結尾讀了一遍,關於這個結尾他已經讀了三天了,但是他還是讀下去了,看書的時候他才能勉強確認自己曾經是一個人,真實活過的人。
他再次把結尾讀了七、八遍,陽台上發出了微弱的汪汪聲,他小跑著過去,看到後勤部蜷縮在窩裡,小小聲地叫著,似乎是在壓抑什麼,極其不安。
「怎麼了?」他輕輕問,蹲下去查看,後勤部是一條老狗,很老很老了,沈意覺得應該有七、八年了,也可能更長點,九年什麼的,他只記得他把後勤部帶回來的那一年,他才剛剛畢業。
那時他剛找了工作,忙著出櫃忙著跟父母吵架忙著和情人甜蜜,後勤部被照顧得一塌糊塗,但是他跟後勤部關係還算不錯,他是牠的主人,於是在他消失前,牠都一直很聽話。
牠哀哀地叫著,皮毛都皺起來了,他不知道牠是不是要死了,但是他並不難過。
他伸出手,很想摸摸牠。在他是人的時候,他很少做這個動作。因為他很忙,忙著賺錢,忙著跟情人甜蜜,忙著和對手攀比,忙著對朋友神氣,他總是在各種衣香鬢影觥籌交錯裡穿梭,他天生是屬於交際場的。
世界是公平的,以前他不摸牠,現在他就摸不到牠,他的手指在碰到牠的頭顱時,跟以前一樣,輕飄飄地穿過去了,像是立體的影像,能看,卻只是薄薄的光影。
「怎麼了?」他伸著手在虛空裡,有個跟他一樣的聲音漸漸靠近了,沈意聽到後勤部的喉嚨裡吐出了呵呵的咕嚕聲,像是在撒嬌又像是在討好。
他不用抬頭都知道來的是誰,好幾年了,他都聽習慣了,更正確的說,三十多年了,他都聽習慣了。
「是不是病了?」另外一個聲音也跟了過來,還是一樣的熟悉,沈意轉過頭去,看到兩個男人站在陽台外面,前面那個皺著眉頭,後面那個一臉不耐,兩人半半拉拉地抱在一起,一大早就甜蜜得一塌糊塗。
兩個熟悉的人,一個是他的身體,一個是他情人。
三、四年前,他一直在想這是為什麼,三、四年後,他終於想通了。
大概這世界上真有狗血劇這種東西,或者因果報應什麼的,他只知道有一天,他突然就變成了一個不知道是鬼還是魂魄的虛無物體,然而自己的身體還活著。
他還記得那件事,因為實在記憶太深刻,他想忘都忘不了。
他記得那是他從父母家回來的第二天。他出櫃了二年,他父母沒有跟他說過一句話,那一天他爸媽終於讓他回去了,他興奮得一塌糊塗,喝了點小酒,回來如常地跟情人親密了,然後早上起來就發現自己飄在了天花板上。
他分不清是自己死了還是別的什麼,但是他千真萬確地看到自己的身體活了,後來他反覆琢磨,只能挫敗地承認,這世界估計真有什麼靈魂穿越之類的事情,因為那個身體醒了之後,說失憶了。
他在家裡轉來轉去,試圖講話,試圖出門,試圖寫字,但是他什麼都碰不了,於是他就眼睜睜地看著他的身體號稱失憶之後成為了他,一寸一寸地入侵了他的領地,先是他的情人,然後是他的父母,之後是他的朋友。
他不太清楚應該叫他的身體什麼,後來第一次看到情人與他的身體做愛的時候,他決定管那個身體叫冒牌貨,再後來他慢慢地看到情人與冒牌貨感情日濃之後,他已經只想管冒牌貨叫正牌貨了。
冒牌貨其實過得比他好,他想,他脾氣有點暴躁,跟情人在一起,雖然不吵架但是也有摩擦;可冒牌貨很溫順,所以三、四年的時間,他困在這裡,慢慢地看了一部名為愛情的生活劇,那麼纏綿那麼感人。 「是要死了吧?」冒牌貨或者正牌貨說,被他情人抱著腰,眼眸明亮,笑容燦爛,「要不要找個地方把牠埋了?」
他情人其實是個好情人,跟他在一起的時候也是脾氣溫順的,他還記得冒牌貨剛醒來的時候說失憶了,他情人就接受了,一天一天照顧,耐心又……刻意。
沈意其實是不太相信他情人看不出來冒牌貨跟他不一樣,就算是有那個失憶的藉口也不成立。失憶是忘了一些事情,又不是去換心了,從頭到尾都不同,怎麼會這麼容易讓人相信呢?
他喜歡吃辣的,這個冒牌貨喜歡吃甜的,他性格招搖,這個冒牌貨溫順,他從來不會一覺睡到接近十點才起床,但是冒牌貨喜歡睡懶覺,他一直負責賺錢,在社交場上縱橫,但是這個冒牌貨連出門都懶。
差太多了,但是他情人相信得太自然了,以至於他這一年有事沒事都開始琢磨,是不是其實他情人潛意識裡更希望他是冒牌貨那樣的人。
不過這種事只能偶爾琢磨了當消遣,深處他是絕對不敢想的。
人,總要有點希望。
「死了再埋吧。」他情人低低地說,一張小白臉蹭在冒牌貨的脖子上,沈意還記得他情人的名字也與小白臉一樣的娘娘腔,叫雲默。
他仰起頭,冒牌貨與雲默離他只有幾十厘米,那兩人抱在一起,臉頰廝磨,迎著太陽特別的燦爛,他記得以前有人誇過他和情人長得好的,帥哥與美人組合。
後勤部還在哀哀地叫著,大概是真的要死了,但是無論是冒牌貨還是雲默都不感興趣了,牠活得夠久了,即使死也是理所當然的,於是他們在討論回家的事情,商量著要不要帶點酒回去。
酒是他從小一起長大的死黨送的。送的那天,他還在讀著結尾,蹲在虛空裡咬著舌頭一字一頓,他死黨送了特產酒過來,還親切地拍了拍冒牌貨。
冒牌貨失憶之後,與家裡關係就好多了,不像他那時候,因為出櫃,跟父母就差點成仇敵了,要不是冒牌貨性格實在太悶,說不定生意做得都會比他好。
他不想再聽他們討論了,蹲下去繼續看後勤部,牠蜷縮成一團,皮毛都鬆弛了,他想如果牠死了,能看見他就好了。
其實他也不知道自己死了沒有,他只知道自己出不了這棟房子,也碰不了任何物質,他記得以前上學的時候,老師說,一個人一生中會死三次,第一次是腦死亡,意味著身體死了;第二次是葬禮,意味著在社會中死了;第三次是遺忘,這世上再也沒有人想起你了,那就是完完全全地死透了。
他覺得自己的第一次死亡還沒有到,但是又好像確確實實地到了第三次死得透透的地步了。
他的情人他的父母他的朋友,再也沒有任何人記得他了,他們甚至都不能發現他和冒牌貨有任何不同。
那對小情人的討論到了高潮,一者堅持要帶,一者堅持說喝酒傷身,兩人小小聲地爭執了一會,結果不知道怎麼就激烈地吻了起來,他偏著頭看著陽光,罵了一聲狗男男,然後才發現其實自己已經麻木了。
四、五年了啊,他想,看著太陽,以前他對著太陽眼睛很疼,現在他什麼感覺都沒有,只是覺得那種光亮讓人瘋狂,讓他劇烈地渴望把後勤部勒死了。
於是我與那輛車漸離漸遠,我回家做飯。他再背了一次結尾,站起來回書房,他打算把最後一頁再讀十遍,因為那對狗男男親到情難自已,已經在地毯上滾起來了。
沈意是個人的時候,就不太喜歡週末,一到週末他可能比平時都要忙,各種邀請聚會堆積在一起,端的是腳不點地,現在他成了鬼魂的時候,倒是特別喜歡週末。
他分不清日日月月,卻記得住週末,因為到了週末那兩個人就會出門,讓他一個人清靜清靜。
他在無人的房子裡轉了三圈,這房子是他買的,買的時候託人內定,位置是最好的,採光也是一等一的棒,開窗便見人工湖,夏天的時候涼風習習蓮香隱隱,冬天在飄窗上坐一坐,渾身都暖洋洋的。
他從客廳走到臥室,又穿越到廚房,最後又繞回陽台。好幾年了,他的領地只有這棟房子,於是他已經熟悉了每一寸土地。
後勤部還在哀哀叫著,他不知道牠是不是病了,但是他摸不到牠,於是只好坐在牠身邊看著牠。其實他有點討厭牠,都說狗是靈敏的生物,但是後勤部一點也沒有發現冒牌貨和他有什麼不同,每天都開開心心地蹭著冒牌貨。 「你要是能看見我就好了。」只要有一個生物能看見他就行了,狗也好貓也罷,哪怕是一隻蟑螂都行啊,這一年他感覺自己已經慢慢地垮掉了,開始的時候還憎恨情人、憎恨父母看不出他的區別,現在他已經什麼都不恨了,他只想跟一個生物說說話。
哪怕是死了呢,死了也好啊,變成鬼,只要有東西跟他在一起都好。
人總到了失去的時候才會珍惜,以前,他身邊總是圍繞著一堆人,那時候他是大家公子,事業有成,哪怕是出櫃跟父母鬧翻了,那些狐朋狗友也會豎著大拇指說沈少爺,夠爺們,來,為你們偉大的愛情,我敬你一杯。
偉大的愛情。他懶洋洋地想,以前他和雲默在一起的時候,愛得死去活來,不顧一切地出櫃,發誓海枯石爛山崩地裂不分開,但是四、五年之後,他看著雲默和別人親熱,已經麻木了。
時間這玩意兒能把一切都消磨了,你的意志你的感情你的過去,它一寸一寸地前進著,你無奈看著陽光下的光線,就被它一點一點抹殺了。
後勤部哀哀的聲音漸漸低了了下去,似乎是要睡著了,他偏著頭,看到牠的眼睛濕漉漉的,像是哭了。
這麼多年,他目睹了自己逐漸死去,現在他又要目睹另外一個生物死去了,雖然前者是社會上的死亡,後者是物理上的死亡,但是其實本質都一樣,最終消失。
大概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死了沒有人惦記,而後勤部將要死了,他還惦記著。
他伸出手把手放在牠頭上,陽光穿透下來,他的手只是在虛空裡,但是他還是覺得有點高興,好像真摸到了什麼。
他玩了一會,聽到了門鎖的聲音,估計是那對小情人是忘了拿東西,於是也懶得去看。
他盤算著晚上怎麼玩窗口進出遊戲,這是他少有的樂趣,他不允許自己一大早就把這樂趣享受了。
客廳裡聲音斷斷續續的,似乎是有人在找什麼,一會輕一會重,翻得嘩嘩啦啦,他漫不經心地聽了一會才發現不對。冒牌貨和雲默的腳步聲他都聽到熟悉了,雲默走路是輕輕的,而冒牌貨喜歡拖著鞋子走路,嗤啦嗤啦的,但是今天這個是那種沉穩的、重重的步調。
難道是小偷?他突然有點興奮,忙竄出去,這大概是他現在唯一的好處了,想走路的時候走路,不想走路的時候,倒掛在房頂也沒問題。
客廳裡空無一人,他聽見書房裡有著微弱的翻書聲,忙奔過去,一看之下,簡直大喜,真的是個小偷啊,背對著他,穿了一身黑色的大衣,彎著腰正在翻他之前看了四、五年的書。
他有一瞬間激動得快哭了,這麼多年,除了那對狗男男和偶爾過來的死黨與父母,他就再也沒有看過任何一個人了。
他輕手輕腳地走過去,其實這是多餘的,哪怕他現在大聲唱歌,這個賊也不會發現的,但是他還是想輕一點,假裝自己有可能被發現。
那個賊一直在看那本書,過了一會才抬起頭來,沈意這兩年的記憶裡衰退,很多事情已經記不清了,但是等這個賊抬起頭來的時候,他還是想「啊」一聲。
這個賊,他認識!
更準確地說,這可能就不是一個賊。他想,困惑地看著對方直起身,又去翻他的抽屜,他情人是個小職員,幾乎不用書房,而那個冒牌貨號稱失憶了,壓根就不工作,於是這書房其實還是保持著他生前的樣子,他看到那個賊把他抽屜裡好多書都翻出來,然後一本一本地弄整齊了。
他這才看到,這個賊還拖著一個巨大的行李箱,就放在腳邊,那裡面現在已經放了許多東西,有客廳裡的相框,還有臥室裡的一些小零碎,他甚至覺得那些東西都是很古老的了,基本都是他在的時候就有的,而不是後來冒牌貨添加的。
「陸嘉澤,你想幹什麼?」他問,但是知道對方壓根聽不到,也就只能笑了笑。
這個賊……不,應該說這個人,其實他很熟悉。他們一起長大的,之所以沒有發展成死黨,實在是因為他們倆性格不太相投,陸嘉澤跟他一樣囂張,從小就跟他打架,上學拚成績,後來又拚工作與業績,他們一直就互相傾軋著,那些年偶爾在酒會上相逢,他們都假裝看不見對方。
他現在記不清的事情很多,但是對陸嘉澤印象深刻。畢竟二十幾年兩人一直暗暗較勁。他還記得他出櫃那年,那些朋友們都鼓勵他或者誇獎他爺們,只有陸嘉澤在某個酒會上不冷不熱地看他說,把眼睛擦亮些,看看值不值得。
他那時把酒都倒在了陸嘉澤的頭上,他們互相諷刺,他說陸嘉澤嫉妒他有個好情人,陸嘉澤說誰會把那種貨色當個寶啊,然後兩人在廁所裡還互相甩了對方幾拳。 陸嘉澤是個小白臉,長得比雲默還要秀氣,卻非要喊雲默是個小白臉,把他氣得不行,趁著互毆的時候還狠狠地把陸嘉澤的臉揍成了爛番茄。
不過他倒是記得,那之後陸嘉澤就出國了,他還高興了好幾天,跟情人說,終於送走瘟神了,可以放鞭炮慶祝之類的弱智話。
陸嘉澤確實是個瘟神,走了幾個月後他父母就突然向他妥協了,讓他回家,再然後他就突然變成了現在的樣子。
他圍著陸嘉澤繞了幾圈,後者這幾年居然沒有變化,依舊是一張冷得能見冰雪的小白臉,好像被人欠了八百萬並且討不回來似的,太陽這麼好的日子還戴著手套,站姿筆直如標槍。
他繞來繞去,看著陸嘉澤把他的書房翻得一塌糊塗,把許多莫名其妙的東西都帶走了。比如他的一本相冊,那裡面的照片都是剪綵或者什麼重要酒會胡亂拍的,都是工作上的,所以便一直扔在書房。
陸嘉澤拿這些東西幹什麼呢?他想,眼睜睜地看著後者把東西都搜刮到了行李箱裡,然後開始搞破壞。先是把電腦砸了,然後是把抽屜裡面不要的全部倒出來,甚至還把書櫥給推翻了,像是神經病發作。
書房裡亂得一塌糊塗,破壞狂卻好像滿意了,拍拍手拖著箱子走了出去。又按照書房的套路,把臥室和客廳裡所有的東西也都給破壞了,能砸的砸,不能砸的全部扔地上,還踩了幾腳。他跟著陸嘉澤晃了好幾個房間,終於醒悟過來,陸嘉澤應該是在模擬偷竊現場。
因為陸嘉澤把抽屜裡零碎的現金與一些玉石裝飾品也拿走了。
難道他書房裡有什麼重要東西,值得陸嘉澤來偷嗎?沈意饒有趣味地想,他現在一點都不在乎有人偷東西,他都死了那麼多年了,還有什麼好在乎的,他只希望這個賊多待一會,他喜歡看到人的感覺。
可惜陸嘉澤聽不到他的心聲,在把客廳毀完了之後,就拖著行李箱走了,他一步一步跟著陸嘉澤,心裡無端地淒涼起來。
一個人,得有多貧瘠,才會見到敵人都渴望抱著他說親愛的你不要走。
陸嘉澤開門出去,後勤部在陽台上哀哀地又叫了起來,前者的腳步聲頓了頓,似乎聽到了,然後居然就又折回來了。
「他連你也不要了嗎?」陸嘉澤在亂成一鍋粥的客廳裡開闢出一條路,他不像沈意,想摸後勤部就摸到了,後勤部在他手上低低地哀鳴著,沈意驚訝地看到陸嘉澤居然紅了眼睛,「我帶你回家吧。」
瘟神陸嘉澤大概是翻身了,這次倒做了點好事,那對小情人一回來就報了警,在客廳裡走來走去,激烈地討論著到底是小偷呢還是報復呢,熱鬧得不得了。
沈意在邊上聽得嗤之以鼻,如果是他以前做生意時,還勉強可能得罪人,遭到報復什麼的,冒牌貨這幾年什麼都不懂,都是宅在家裡的,到哪去樹敵啊?
他飄到門口去,那裡落著那對狗男男留下的袋子,他把頭埋過去看了看,才發現裡面都是食物,應該是他父母那裡帶回來的。
他母親是個標準的貴夫人,十指不沾陽春水,這幾年倒是頻繁下廚了,冒牌貨好幾次還跟雲默調笑說燒得太難吃了,只有一道蜜汁豆腐能入口,於是每次吃飯只好拚命吃豆腐,弄得他媽媽以為他喜歡,每次去都燒不說,還要給他弄好了帶回來。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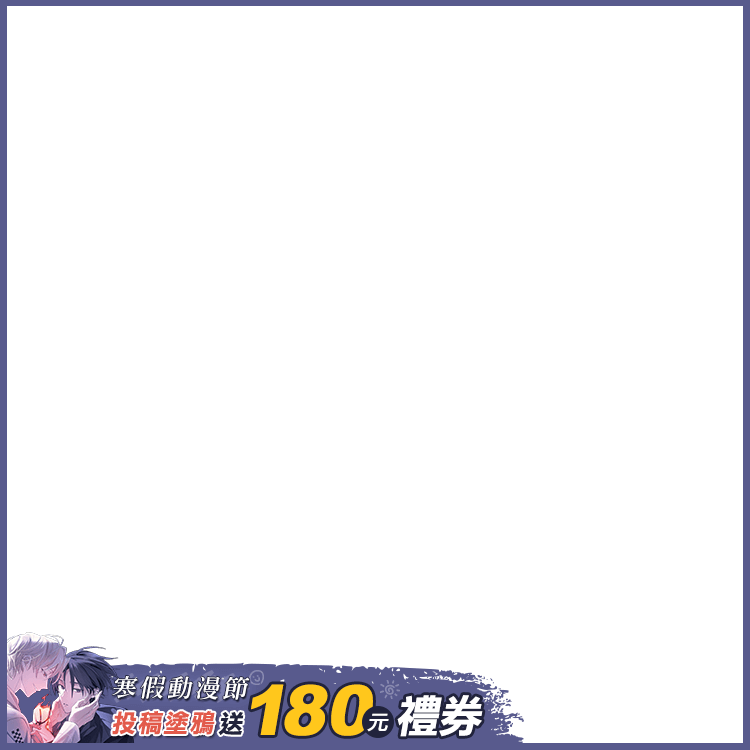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