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故事裡:現在即過去,過去即現在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從「物語」理解人生,看見超越意志、跨越時空的靈魂奧祕
★探索日本王朝文學中的情愛、趣味、美學、主體意識與生命追尋
★從經典文學,理解日本人的「經典」思維
每個人一生當中
都活在他特有的「故事」裡
人要將經驗到的事化做自己的一部分,必須將這些經驗組合進自己的世界觀中,也就是化為自己可以接受的故事。──河合隼雄
心理治療是一門無法以科學方法進行觀察、診斷的工作,它重視「人際關係」,是在關係的進展中,幫助人「創造他們的故事」。因此如果要理解「人」,「故事」顯然是一門顯學,而追溯久遠前的故事,更能看見人類上下千年的樣貌,獲得跨越時間、地域的洞察。
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平安時代是日本文學的黃金時期,許多作品都對人們的生活型態與思想有精彩深刻的描繪。本書將討論平安至鎌倉時代的多部經典,從中探索人類靈魂與意識的發展變遷,看見隱藏在故事中「貫穿古今」的奧祕:
§ 竹取物語 §
作為日本最古老的物語,絕世美女「輝夜姬」何以未與男性共結連理,並轉身離去?
§ 宇津保物語 §
這部以「琴」為主軸的作品,有著不可思議的政爭情節,這和日本的民族性有什麼關係?以及當人經歷了「非人世」的體驗,該如何將那樣的經驗以某種形式帶回到現世中,與之共存?
§ 落窪物語 §
作為現存最古老的日本灰姑娘故事,這是一場喜劇收尾的「女性成年禮」,彰顯了復仇與孝養也可以毫不牴觸的智慧。
§ 平中物語 §
這部以和歌貫穿全文的作品,宛如「打嘴鼓」般你來我往、針鋒相對。這些透過講究的紙質、筆跡、文字,搭配精心挑選的花材傳遞的「情書」,除了暗通款曲、互相調侃,更充滿了現今日本少見的詼諧。
§ 更級日記 §
為什麼有些外表看起來不怎麼幸福的人生裡,其實蘊藏著偌大的安心?到底「夢」對人有什麼樣的意義?
§ 濱松中納言物語 §
作為《更級日記》的對照組,作者彷彿在不可思議的情節中,演繹著循「夢」而活的人生將會走到哪裡去。
§ 追溯自身身世的公主 §
「欲想方設法,釐清己身世,只因宿世緣,使我煩且憂。」身世不明的故事常常傳達出「探求自身主體性」的議題,但這部作品卻有全然不同的啟發?
★探索日本王朝文學中的情愛、趣味、美學、主體意識與生命追尋
★從經典文學,理解日本人的「經典」思維
每個人一生當中
都活在他特有的「故事」裡
人要將經驗到的事化做自己的一部分,必須將這些經驗組合進自己的世界觀中,也就是化為自己可以接受的故事。──河合隼雄
心理治療是一門無法以科學方法進行觀察、診斷的工作,它重視「人際關係」,是在關係的進展中,幫助人「創造他們的故事」。因此如果要理解「人」,「故事」顯然是一門顯學,而追溯久遠前的故事,更能看見人類上下千年的樣貌,獲得跨越時間、地域的洞察。
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平安時代是日本文學的黃金時期,許多作品都對人們的生活型態與思想有精彩深刻的描繪。本書將討論平安至鎌倉時代的多部經典,從中探索人類靈魂與意識的發展變遷,看見隱藏在故事中「貫穿古今」的奧祕:
§ 竹取物語 §
作為日本最古老的物語,絕世美女「輝夜姬」何以未與男性共結連理,並轉身離去?
§ 宇津保物語 §
這部以「琴」為主軸的作品,有著不可思議的政爭情節,這和日本的民族性有什麼關係?以及當人經歷了「非人世」的體驗,該如何將那樣的經驗以某種形式帶回到現世中,與之共存?
§ 落窪物語 §
作為現存最古老的日本灰姑娘故事,這是一場喜劇收尾的「女性成年禮」,彰顯了復仇與孝養也可以毫不牴觸的智慧。
§ 平中物語 §
這部以和歌貫穿全文的作品,宛如「打嘴鼓」般你來我往、針鋒相對。這些透過講究的紙質、筆跡、文字,搭配精心挑選的花材傳遞的「情書」,除了暗通款曲、互相調侃,更充滿了現今日本少見的詼諧。
§ 更級日記 §
為什麼有些外表看起來不怎麼幸福的人生裡,其實蘊藏著偌大的安心?到底「夢」對人有什麼樣的意義?
§ 濱松中納言物語 §
作為《更級日記》的對照組,作者彷彿在不可思議的情節中,演繹著循「夢」而活的人生將會走到哪裡去。
§ 追溯自身身世的公主 §
「欲想方設法,釐清己身世,只因宿世緣,使我煩且憂。」身世不明的故事常常傳達出「探求自身主體性」的議題,但這部作品卻有全然不同的啟發?
名人推薦
河合隼雄這本《活在故事裡》從聲音、異世界、場所、夢等多角度,帶領讀者閱讀、解析平安朝的物語世界,由於其心理學的專業,每每見到純文學者看不到的地方,讓人驚嘆連連,或擊掌叫好!──林水福(日本文學研究者、作家)
對於河合隼雄而言,活在日本的社會構造之外,不知道日本人的「故事」,也不知道日本人的「神話」的外國人,不可能理解日本人,更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心。但是,相反地,河合隼雄也指出了一條幫助外國人理解日本,理解日本人的正道。毫無疑問,那就是接近日本人的「故事」,接近日本人的「神話」,接近日本人的「世間」。──陳永峰(東海大學跨領域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他並不一定把故事往他專門的臨床心理學拉攏,而是慎重地維持著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中間立場。故事與臨床心理學公平地拿著透明的鏡子,相互映照、反射,最後散發出透亮到人類心底的光芒。──小川洋子(知名日本作家)
共同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林水福|日本文學研究者、作家
洪素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IAAP榮格分析師
陳文玲|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教授、X書院@創意實驗室尋獸師
陳永峰│東海大學跨領域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賴振南|天主教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魏宏晉|心靈工坊成長學苑「現代大歷史」授課講師
對於河合隼雄而言,活在日本的社會構造之外,不知道日本人的「故事」,也不知道日本人的「神話」的外國人,不可能理解日本人,更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心。但是,相反地,河合隼雄也指出了一條幫助外國人理解日本,理解日本人的正道。毫無疑問,那就是接近日本人的「故事」,接近日本人的「神話」,接近日本人的「世間」。──陳永峰(東海大學跨領域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他並不一定把故事往他專門的臨床心理學拉攏,而是慎重地維持著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中間立場。故事與臨床心理學公平地拿著透明的鏡子,相互映照、反射,最後散發出透亮到人類心底的光芒。──小川洋子(知名日本作家)
共同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林水福|日本文學研究者、作家
洪素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IAAP榮格分析師
陳文玲|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教授、X書院@創意實驗室尋獸師
陳永峰│東海大學跨領域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賴振南|天主教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魏宏晉|心靈工坊成長學苑「現代大歷史」授課講師
目錄
【推薦序一】今天是過去,過去是今天/陳永峰
【推薦序二】一說再說:靈魂活在故事裡/魏宏晉
【導讀】河合隼雄如何看日本物語/林水福
第一章 為什麼是故事?
心理治療的世界
故事的特性
「もの」的意思
故事和現代
王朝物語
第二章 殞滅之美
故事的鼻祖
殞滅之美
不可以偷看的禁忌
對另一個世界的憧憬
老翁和女兒
輝夜姬的系譜
第三章 沒有殺戮的戰爭
故事與殺人
《宇津保物語》和爭戰
如何對戰?
征戰與對話
日本人的美學意識
依靠自然現象解決
第四章 聲音的不可思議
聲音與氣味
《宇津保物語》和琴
音樂的傳承
音樂與異世界
第五章 繼子的幸福
《落窪物語》
繼子故事的種種樣貌
母親和女兒
復仇的方式
阿漕的觀點
第六章 冗句.定句.疊句──《平中物語》的和歌
歌物語
文雅的戰役
喚起意象的力道
具備美學概念的搗蛋鬼
和歌的傳統
第七章 物語中的Topos
「場所」的份量
《換身物語》的情形
《濱松中納言物語》
日本與唐土
轉世
故事要說的是什麼?
第八章 紫曼陀羅試行方案
閱讀《源氏物語》
女性與男性
女性的物語
紫曼陀羅
做為獨立個體的女性
第九章 《濱松中納言物語》和《更級日記》的夢
夢的價值
《濱松中納言物語》的夢
《更級日記》的夢
夢與現實
夢的體驗和故事
事情的演變趨勢
第十章 設計在故事情節裡的惡
《追溯自身身世的公主》
族譜的意義
私通
《理查三世》
恨的故事
原罪與原悲
後記
【解說】串聯起所有一切/小川洋子
「故事與日本人的心」選輯 發刊詞/河合俊雄
【附錄】延伸閱讀
【推薦序二】一說再說:靈魂活在故事裡/魏宏晉
【導讀】河合隼雄如何看日本物語/林水福
第一章 為什麼是故事?
心理治療的世界
故事的特性
「もの」的意思
故事和現代
王朝物語
第二章 殞滅之美
故事的鼻祖
殞滅之美
不可以偷看的禁忌
對另一個世界的憧憬
老翁和女兒
輝夜姬的系譜
第三章 沒有殺戮的戰爭
故事與殺人
《宇津保物語》和爭戰
如何對戰?
征戰與對話
日本人的美學意識
依靠自然現象解決
第四章 聲音的不可思議
聲音與氣味
《宇津保物語》和琴
音樂的傳承
音樂與異世界
第五章 繼子的幸福
《落窪物語》
繼子故事的種種樣貌
母親和女兒
復仇的方式
阿漕的觀點
第六章 冗句.定句.疊句──《平中物語》的和歌
歌物語
文雅的戰役
喚起意象的力道
具備美學概念的搗蛋鬼
和歌的傳統
第七章 物語中的Topos
「場所」的份量
《換身物語》的情形
《濱松中納言物語》
日本與唐土
轉世
故事要說的是什麼?
第八章 紫曼陀羅試行方案
閱讀《源氏物語》
女性與男性
女性的物語
紫曼陀羅
做為獨立個體的女性
第九章 《濱松中納言物語》和《更級日記》的夢
夢的價值
《濱松中納言物語》的夢
《更級日記》的夢
夢與現實
夢的體驗和故事
事情的演變趨勢
第十章 設計在故事情節裡的惡
《追溯自身身世的公主》
族譜的意義
私通
《理查三世》
恨的故事
原罪與原悲
後記
【解說】串聯起所有一切/小川洋子
「故事與日本人的心」選輯 發刊詞/河合俊雄
【附錄】延伸閱讀
序/導讀
【推薦序一】今天是過去,過去是今天 / 陳永峰(東海大學跨領域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本書,《活在故事裡》的作者是河合隼雄,編者是河合俊雄。譯自日本岩波書店二○一六年重新編輯出版的岩波現代文庫「故事與日本人的心選輯II」『物語を生きる—今は昔、昔は今』一書(初版,小學館,二○○二年)。
筆者還在京都大學留學之時,曾經在會議現場同時見過河合隼雄和河合俊雄這對同為京大教授的父子檔。雖然一次都沒有交談過,但是單從身影來看,一者爽颯,一者憂沉。在畫面上,與其說是父與子,不如說是開創者與追隨者,說不定更為恰當。這樣唐突的來自一個外國人的「日本人觀察」,如果河合隼雄知道的話,一定不會反對,說不定還會啟動他一貫的冷笑話裝置,開玩笑地說:「哦、吼吼!你這個外國人,太危險了吧!不行,不行。」然後再追加一句,「沒辦法,這就是日本社會裡的組織支配原理,連臨床心理學家也『超克』不了啊!」
也就是說,對於河合隼雄而言,活在日本的社會構造之外,不知道日本人的「故事」,也不知道日本人的「神話」的外國人,不可能理解日本人,更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心。但是,相反地,河合隼雄也指出了一條幫助外國人理解日本,理解日本人的正道。毫無疑問,那就是接近日本人的「故事」,接近日本人的「神話」,接近日本人的「世間」。
不過,只看本書的話,讀者們可能無法想像,河合隼雄年輕時重度著迷於西洋文化,相對地,對於日本的傳統文化則是憎惡不已。根據河合俊雄的證言,年輕時吸引河合隼雄的都是西洋的故事,戰爭的經驗使他極度厭惡日本的故事與神話,但是後來他之所以不得不面對它們,和他經由夢來分析自身的經驗有關。同時,在日本從事心理治療工作的經驗,也迫使他認識到日本故事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對日本人而言,日本的故事就像來自遠古的歷史沉積。這樣的認識,促使他完成了許多關於日本故事的著作。(河合隼雄著,河合俊雄編,《神話心理學──來自眾神的處方箋》,心靈工坊出版,二○一八年,頁二○八。)
本書從只要是日本人就沒有人不知道的《竹取物語》寫起,再到《宇津保物語》、《落窪物語》、《源氏物語》等等,日本民間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河合隼雄發現這些故事幾乎都沒有直接衝突的情節,並且從中指出日本人的美學意識是盡可能避免直接的爭端,比起為了勝利、利益、慾望而衝突,日本人更重視努力維持體面與格調。因此,為求勝利而不擇手段的人,經常被塑造成「反面角色」,而貫徹遁世美學的那一邊則被視為「正面角色」。這也使得「離開」、「消失」,成為日本型故事中永遠的不是結局的結局。
依照河合隼雄的解釋,Nothing has happened,什麼也沒有發生,留下來的只有「空」跟「無」正是日本型故事的重要特徵。例如,有名傳說的主角浦島太郎既沒有跟龍王打了起來,也沒有帶走龍王的女兒,說走就走,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
如果不明瞭這件事的話,確實非常難理解日本人的歷史觀。也就是說,日本人明顯地可以從「無」的場所(Topos)出發,這種特徵在其他文明則不明顯。本書第七章「物語中的 Topos」就提到了此一文化特徵。
對基督教文明以及中華文明而言,歷史的主軸是「時間」,相對地,日本文化的主軸是「空間」。所以,日本人只要「空間=場所=Topos」一變,行動準則就變。
例如,二○一五年末,日韓慰安婦問題在「外部的場所」的韓國首爾達成和解的同一天,日本第一夫人安倍昭惠在「內部的場所」的日本東京參拜靖國神社。
二○一六年底,同樣的劇本再度演出,安倍首相與當時的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剛在「外部」的美國珍珠港悼念完太平洋戰爭的犧牲者,一回到「內部」,稻田朋美就出現在東京靖國神社祭拜擴大戰端,遂行戰爭的A級戰犯。
讀者讀到這裡,大概多少可以理解日本人在「空間=場所」之間,縱橫無盡,自由穿梭的文化能力了吧。至於哪邊是真,哪邊是假;哪邊是「表」,哪邊是「裏」;哪邊是「本音」(編按:真心話),哪邊是「建前」(編按:表面話),就一點都不重要了。
河合隼雄在戰後日本學術界中的地位,就在於創造了以研究「故事」為主的學術流派,並且不斷強調日本社會的母性意識。母性意識包容一切,追求全體性,無可避免充滿了必須被容忍的內在矛盾。京都學派哲學家西田幾多郎也直指這就是日本人最重要的文化特徵,言之為「絕對矛盾下的自我同一」。
說不定在潛意識裡,戰後京都學派的重要繼承者河合隼雄,利用對日本型「故事」的整理和解說,替祖師爺西田幾多郎的「絕對矛盾」在日本型的「故事」裡完成了「自我同一=identity」。
「故事發想的起點不在於『個人』,而是把自己當作是委身在整個『事情的演變趨勢』(組織)之中的人物,用這樣的形式來找到主體性。而我,不也讓人感覺是偉大的『演變趨勢』中極小的一部分嗎?」(本書第十章「追溯自身身世的公主」)
毫無疑問,河合隼雄身為一個受到西方文化強烈影響的日本人,透過本書以及對日本型「故事」的研究,說明「我」該怎麼做才能不失去自我認同。
也就是說,筆者認為如果台灣的讀者想要正確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話,本書非讀不可,當然河合隼雄的其他著作,也不能放過。
【推薦序二】一說再說:靈魂活在故事裡 / 魏宏晉(心靈工坊成長學苑「現代大歷史」授課講師)
作為出身日本的榮格學派精神分析師,河合隼雄不僅精通深度心理學,更善於深入文化思想,他在《活在故事裡》中的論述,是兩條脈絡的精彩淬煉,熔鑄出「靈魂」與「關係」的心理與文化的關鍵議題。
「靈魂」(psyche)是榮格心理學裡重中之重的議題,所謂「個體化」(individuation),可說就是自我(ego)朝靈魂邁進的過程。然而,於此之際,靈魂必然出現岐義。就榮格主張的目的性認識論(teleology)而言,靈魂本質也許就是大寫的「Self」,或可暫借佛教術語,擬之為「自性」,也彰顯人的存在的價值意義。不過,這樣的論調,卻碰觸到形而上的本體論問題,而這是榮格本人所明確拒斥的。因此,靈魂一說,或許是心理實存(psychological authencity),與自我的自由意志有關。惟此為「靈」(spirit)之「他者」?亦或是「魂」(soul)的「本我」?卻也難說。連榮格都承認自己無法用語言文字說清楚。這些字眼不管是在哪種文化系統中,都是多重多義,彼此糾纏不清,論述者只能各據立場,著力發揮。
就古典學派而言,常見以「烘雲托月」之法分析個體化過程的象徵,比如,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談永恆少年時,是運用與母親關係的連結,藉以論證永恆少年原型本身;而部分可能受到榮格古典學派影響的客體關係理論,走的也是類似的路數。理論上,儘管避談本體,通過主客辯證向上的過程,心靈也必然提升,朝核心慢慢逼近。
然而對於被譽為分析心理學最具創造力的後繼者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來說,靈魂的問題若侷限在原型的個別型態與互相作用的理論分析是沒有意義的。靈魂是人的整體,他的「原型心理學」(archetypal psychology)主張以靈魂為基礎的內在敘事,說的是生命的完整故事,是一種關係的整然呈現,而非個別原型象徵的隻字片語。
希爾曼自稱是榮格學派的離經叛道者,他要「從治療室出走,更廣泛地與西方文化意象連結起來」。不過,這種看似叛逆的主張,卻也是在積極地回歸精神分析的浪漫主義思想源頭,回到文化中,找尋心靈的根本。
河合隼雄從事心理治療研究時,受希爾曼的啟發,領悟到:當治療進入故事的關係與脈絡中,故事「敘說的」,便是個案靈魂「想講的」的道理。他進行日本文學研究,是把包括許多華人讀者也熟悉的《源氏物語》、《竹取物語》等日本古典文學當作「個案」進行「治療」,以希爾曼為師,強調「故事在說話」的方法論;於認識的層面,則突出日本的「物之哀」(物の哀れ)思想,說出特屬日本人的心靈物語。
物之哀思想出現在西元十一世紀左右的日本文學作品中,時處平安時代。到了十八世紀時,思想家本居宣長宣揚反對中國儒家外加的倫理觀,倡導以內在價值自我省視的物之哀代之。這樣的思想革命,除了讓日本脫離中國這個政治與文化他者的制約,確立了自我的主體性外;價值觀的判定標準,也從外審轉為內視,就如稍早發生在歐洲的那場文學革命一般,日本也出現了一場專屬日本的浪漫主義變革。
物之哀經常以感物傷時的方式表達,在視覺意象上,類於中國元朝文學家馬致遠《天淨沙》的描寫,「孤藤、小橋、瘦馬」,托襯出「斷腸人在天涯」的孤寂;情緒則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但,這些都無法完整說明日本特有的物之哀美學。那是一種主、客二者在衰敗的必然性中,卻於最完美的一刻偶遇,完成了共時性的美的極致。櫻花落下,亦當隨死,物與我一起脫離了醜惡,未必成神,但也能在柏拉圖神學與哲學交界的宇宙靈魂(Ames universelles)處相融,重回本來一體的靈魂關係中。
《活在故事裡》的論述本身就是個故事,一個日本文化靈魂所自我敘說,與深度心理學確立關係的故事,河合先生說得真精彩呀!然紙過短,也拙於筆力,於此卻只能對背後的理論脈絡稍加拈提。關於其中故事的美麗與哀愁,就有待讀者您自行品味,自我再加敘說了。
本書,《活在故事裡》的作者是河合隼雄,編者是河合俊雄。譯自日本岩波書店二○一六年重新編輯出版的岩波現代文庫「故事與日本人的心選輯II」『物語を生きる—今は昔、昔は今』一書(初版,小學館,二○○二年)。
筆者還在京都大學留學之時,曾經在會議現場同時見過河合隼雄和河合俊雄這對同為京大教授的父子檔。雖然一次都沒有交談過,但是單從身影來看,一者爽颯,一者憂沉。在畫面上,與其說是父與子,不如說是開創者與追隨者,說不定更為恰當。這樣唐突的來自一個外國人的「日本人觀察」,如果河合隼雄知道的話,一定不會反對,說不定還會啟動他一貫的冷笑話裝置,開玩笑地說:「哦、吼吼!你這個外國人,太危險了吧!不行,不行。」然後再追加一句,「沒辦法,這就是日本社會裡的組織支配原理,連臨床心理學家也『超克』不了啊!」
也就是說,對於河合隼雄而言,活在日本的社會構造之外,不知道日本人的「故事」,也不知道日本人的「神話」的外國人,不可能理解日本人,更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心。但是,相反地,河合隼雄也指出了一條幫助外國人理解日本,理解日本人的正道。毫無疑問,那就是接近日本人的「故事」,接近日本人的「神話」,接近日本人的「世間」。
不過,只看本書的話,讀者們可能無法想像,河合隼雄年輕時重度著迷於西洋文化,相對地,對於日本的傳統文化則是憎惡不已。根據河合俊雄的證言,年輕時吸引河合隼雄的都是西洋的故事,戰爭的經驗使他極度厭惡日本的故事與神話,但是後來他之所以不得不面對它們,和他經由夢來分析自身的經驗有關。同時,在日本從事心理治療工作的經驗,也迫使他認識到日本故事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對日本人而言,日本的故事就像來自遠古的歷史沉積。這樣的認識,促使他完成了許多關於日本故事的著作。(河合隼雄著,河合俊雄編,《神話心理學──來自眾神的處方箋》,心靈工坊出版,二○一八年,頁二○八。)
本書從只要是日本人就沒有人不知道的《竹取物語》寫起,再到《宇津保物語》、《落窪物語》、《源氏物語》等等,日本民間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河合隼雄發現這些故事幾乎都沒有直接衝突的情節,並且從中指出日本人的美學意識是盡可能避免直接的爭端,比起為了勝利、利益、慾望而衝突,日本人更重視努力維持體面與格調。因此,為求勝利而不擇手段的人,經常被塑造成「反面角色」,而貫徹遁世美學的那一邊則被視為「正面角色」。這也使得「離開」、「消失」,成為日本型故事中永遠的不是結局的結局。
依照河合隼雄的解釋,Nothing has happened,什麼也沒有發生,留下來的只有「空」跟「無」正是日本型故事的重要特徵。例如,有名傳說的主角浦島太郎既沒有跟龍王打了起來,也沒有帶走龍王的女兒,說走就走,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
如果不明瞭這件事的話,確實非常難理解日本人的歷史觀。也就是說,日本人明顯地可以從「無」的場所(Topos)出發,這種特徵在其他文明則不明顯。本書第七章「物語中的 Topos」就提到了此一文化特徵。
對基督教文明以及中華文明而言,歷史的主軸是「時間」,相對地,日本文化的主軸是「空間」。所以,日本人只要「空間=場所=Topos」一變,行動準則就變。
例如,二○一五年末,日韓慰安婦問題在「外部的場所」的韓國首爾達成和解的同一天,日本第一夫人安倍昭惠在「內部的場所」的日本東京參拜靖國神社。
二○一六年底,同樣的劇本再度演出,安倍首相與當時的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剛在「外部」的美國珍珠港悼念完太平洋戰爭的犧牲者,一回到「內部」,稻田朋美就出現在東京靖國神社祭拜擴大戰端,遂行戰爭的A級戰犯。
讀者讀到這裡,大概多少可以理解日本人在「空間=場所」之間,縱橫無盡,自由穿梭的文化能力了吧。至於哪邊是真,哪邊是假;哪邊是「表」,哪邊是「裏」;哪邊是「本音」(編按:真心話),哪邊是「建前」(編按:表面話),就一點都不重要了。
河合隼雄在戰後日本學術界中的地位,就在於創造了以研究「故事」為主的學術流派,並且不斷強調日本社會的母性意識。母性意識包容一切,追求全體性,無可避免充滿了必須被容忍的內在矛盾。京都學派哲學家西田幾多郎也直指這就是日本人最重要的文化特徵,言之為「絕對矛盾下的自我同一」。
說不定在潛意識裡,戰後京都學派的重要繼承者河合隼雄,利用對日本型「故事」的整理和解說,替祖師爺西田幾多郎的「絕對矛盾」在日本型的「故事」裡完成了「自我同一=identity」。
「故事發想的起點不在於『個人』,而是把自己當作是委身在整個『事情的演變趨勢』(組織)之中的人物,用這樣的形式來找到主體性。而我,不也讓人感覺是偉大的『演變趨勢』中極小的一部分嗎?」(本書第十章「追溯自身身世的公主」)
毫無疑問,河合隼雄身為一個受到西方文化強烈影響的日本人,透過本書以及對日本型「故事」的研究,說明「我」該怎麼做才能不失去自我認同。
也就是說,筆者認為如果台灣的讀者想要正確理解日本和日本人的話,本書非讀不可,當然河合隼雄的其他著作,也不能放過。
【推薦序二】一說再說:靈魂活在故事裡 / 魏宏晉(心靈工坊成長學苑「現代大歷史」授課講師)
作為出身日本的榮格學派精神分析師,河合隼雄不僅精通深度心理學,更善於深入文化思想,他在《活在故事裡》中的論述,是兩條脈絡的精彩淬煉,熔鑄出「靈魂」與「關係」的心理與文化的關鍵議題。
「靈魂」(psyche)是榮格心理學裡重中之重的議題,所謂「個體化」(individuation),可說就是自我(ego)朝靈魂邁進的過程。然而,於此之際,靈魂必然出現岐義。就榮格主張的目的性認識論(teleology)而言,靈魂本質也許就是大寫的「Self」,或可暫借佛教術語,擬之為「自性」,也彰顯人的存在的價值意義。不過,這樣的論調,卻碰觸到形而上的本體論問題,而這是榮格本人所明確拒斥的。因此,靈魂一說,或許是心理實存(psychological authencity),與自我的自由意志有關。惟此為「靈」(spirit)之「他者」?亦或是「魂」(soul)的「本我」?卻也難說。連榮格都承認自己無法用語言文字說清楚。這些字眼不管是在哪種文化系統中,都是多重多義,彼此糾纏不清,論述者只能各據立場,著力發揮。
就古典學派而言,常見以「烘雲托月」之法分析個體化過程的象徵,比如,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談永恆少年時,是運用與母親關係的連結,藉以論證永恆少年原型本身;而部分可能受到榮格古典學派影響的客體關係理論,走的也是類似的路數。理論上,儘管避談本體,通過主客辯證向上的過程,心靈也必然提升,朝核心慢慢逼近。
然而對於被譽為分析心理學最具創造力的後繼者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來說,靈魂的問題若侷限在原型的個別型態與互相作用的理論分析是沒有意義的。靈魂是人的整體,他的「原型心理學」(archetypal psychology)主張以靈魂為基礎的內在敘事,說的是生命的完整故事,是一種關係的整然呈現,而非個別原型象徵的隻字片語。
希爾曼自稱是榮格學派的離經叛道者,他要「從治療室出走,更廣泛地與西方文化意象連結起來」。不過,這種看似叛逆的主張,卻也是在積極地回歸精神分析的浪漫主義思想源頭,回到文化中,找尋心靈的根本。
河合隼雄從事心理治療研究時,受希爾曼的啟發,領悟到:當治療進入故事的關係與脈絡中,故事「敘說的」,便是個案靈魂「想講的」的道理。他進行日本文學研究,是把包括許多華人讀者也熟悉的《源氏物語》、《竹取物語》等日本古典文學當作「個案」進行「治療」,以希爾曼為師,強調「故事在說話」的方法論;於認識的層面,則突出日本的「物之哀」(物の哀れ)思想,說出特屬日本人的心靈物語。
物之哀思想出現在西元十一世紀左右的日本文學作品中,時處平安時代。到了十八世紀時,思想家本居宣長宣揚反對中國儒家外加的倫理觀,倡導以內在價值自我省視的物之哀代之。這樣的思想革命,除了讓日本脫離中國這個政治與文化他者的制約,確立了自我的主體性外;價值觀的判定標準,也從外審轉為內視,就如稍早發生在歐洲的那場文學革命一般,日本也出現了一場專屬日本的浪漫主義變革。
物之哀經常以感物傷時的方式表達,在視覺意象上,類於中國元朝文學家馬致遠《天淨沙》的描寫,「孤藤、小橋、瘦馬」,托襯出「斷腸人在天涯」的孤寂;情緒則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但,這些都無法完整說明日本特有的物之哀美學。那是一種主、客二者在衰敗的必然性中,卻於最完美的一刻偶遇,完成了共時性的美的極致。櫻花落下,亦當隨死,物與我一起脫離了醜惡,未必成神,但也能在柏拉圖神學與哲學交界的宇宙靈魂(Ames universelles)處相融,重回本來一體的靈魂關係中。
《活在故事裡》的論述本身就是個故事,一個日本文化靈魂所自我敘說,與深度心理學確立關係的故事,河合先生說得真精彩呀!然紙過短,也拙於筆力,於此卻只能對背後的理論脈絡稍加拈提。關於其中故事的美麗與哀愁,就有待讀者您自行品味,自我再加敘說了。
試閱
【內文試閱】
1-1 心理治療的世界
我接下來將以「活在故事裡」為題,舉日本的王朝物語為例進行討論。我想我既非日本文學也非日本史學專家,卻特意要針對日本的物語加以論述,應該在文章的最開始稍微說明一下是什麼緣故。
我的專門領域是臨床心理學,一心為心理治療竭盡心力。一開始,我強烈希望可以將自己執行的工作盡可能「科學化」,讓它成為可信賴的職業,也一直朝著這個目標努力。但此同時,我在工作上最重要的目的依然是─探究怎麼做才能為前來諮商的人提供最大幫助。在持續以後者為中心的執業過程中,我漸漸自覺到,自己的工作是一份不得不異於以往科學方法的工作。
讓我這樣思考的機緣很多,我舉一個例子。在我們的領域中有學會,大家都期望在學會裡見到科學的、客觀的研究發表。因此在初期,清一色都是這樣的成果發表。然而在反覆舉辦的過程中,我逐漸了解比起這樣的內容,徹底追究一個實際案例的「個案研究」對聽眾更有幫助。我從經驗中清楚知道,這和其他「科學」領域中的「專案報告」(a case report)意義並不相同。也就是說,一般而言,專案報告是為了指出有這樣特別的案例存在,因此今後在這樣特殊的案例出現之時便可以派上用場。但我卻了解到,我們所進行的「個案研究」在更加廣泛的意義上會有幫助。
例如,當某個人發表「焦慮症」的個案研究時,聽者會感覺這可以運用在自己所負責的拒學學生心理治療上。就算是女性的個案,在男性個案上一樣可以派上用場。因為這雖然是「個案」,卻能夠普遍地造福其他案例。這種時候,我不僅會想要自己也來如法炮製,更會湧現出想要從頭開始重新整理研究發表內容的欲望。
這是為什麼呢?最直接了當的回答就是:在心理治療中「人際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自然科學領域中,一直以來,研究者都必須和他所研究的對象切斷關係。因為是從彼此沒有關聯的立場來客觀地進行研究,所以研究結果具有普遍性。然而,心理治療師如果和前來諮商的案主「切斷關係」,用這樣的態度來聽對方說話,諮商是無法進行的吧。這樣說起來,這個「關係」是什麼樣的關係?這段關係又會如何變化呢?治療師與案主的關係雖然重要,案主自己不是也置身在家人、朋友、同事等的關係網絡中嗎?再加上,即使說是兩個人「交談」,在這個過程中,治療師的心理狀態、身體狀態都會發生變化,如果像深層心理學家說的無意識也會產生關聯的話,治療師與案主的關係將變得極其複雜。
治療師一邊全盤考慮這樣的關係,一邊在這關係的整體之中找出條理,和案主朝著治癒的方向邁進。對聽者而言,在聆聽這類發表的時候,心裡會對於種種關係的樣貌進行反省、發現,而這些反省、發現,會超越該個案的具體事實,成為有用的東西。在明白會有這樣的效益之後,我們的學會便開始十分重視個案研究。順帶一提,就在我們開始這麼做之後,帶著熱情來聆聽發表的參加者變得非常多。因為內容可以立即派上用場,有這樣的反應也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雖然我從經驗上得知個案研究的重要性,但讀到榮格學派的心理分析學者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主張個案研究的本質是 story telling 的時候,我才茅塞頓開,這就是說故事啊!人類要將自己所經驗的事情化做自己的一部分,或是放在自己心裡,必須要將這些經驗善加組合在自己的世界觀或是人生觀中。這項作業也就是將這些經驗化為自己可以接受的故事,並從中梳理出脈絡。有情節,是故事的特徵。在「報告」個案的時候,報告者認為自己只是在敘述事實,但因為其中具備了已經被收藏到治療師內心裡的脈絡,就這一點而言,個案報告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變成了 story telling。
如果以這樣的邏輯來思考,我想我們也可以說心理治療這份工作,本來就是要幫助前來諮商的人創造適合他們自己的故事。例如,對於為神經衰弱症狀所困擾的人而言,他們的症狀是不是可以視做「沒辦法放進自己故事裡的材料」?又例如焦慮症患者,他們是因為不曉得這些焦慮是從何而來、為什麼會出現,所以才會焦慮。他們無法將這些不安編進自己的故事裡,用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說出來。因此,為了使創造自己的故事成為可能,我們必須進行各式各樣的調查,像是自己過去或是現在的狀況、從前自己未曾意識到的內心運作等等,在進行這些調查的過程中,會有新的發現,獲得新的觀點。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可以透過一覽全貌得知「原來如此」,藉此能夠把自己的人生「當做故事來述說」。這時,這些症狀應該就消失了。
如果採取「我的人生故事」這樣的思考方式,每個人應該都是不一樣的,但在某個程度上卻又可以類型化。也因為如此,我們心理治療師在一定程度上必須知道各式各樣的故事以及其類
型。這是我之所以對故事抱持興趣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人,喜歡故事。人類從獲得語言能力的那一刻開始,或許神話就已經誕生了。伴隨著神話,人們的對話內容也以「民間故事」或「傳說」的型態流傳下來,而它們的共同特徵是「作者」不詳。說不定,它們是某個天賦異稟的個人所創造的作品,卻透過了共同擁有這些故事的人們,以「我們的故事」的形式存續了下來。藉由這些故事,人們得以強化與過去的連結、與土地的連結,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連結。如果用現代的詞彙來說,我們可以說「故事」在建立某個部落民族或是家族的主體認同上幫了大忙。
心理治療師的工作之一,便是幫助前來諮商的人探索自己的主體認同。這項工作和前文中提到的創造「自己的故事」,可以說是同義詞。就我目前為止所論述的幾個點來看,讀者應該可以認同這樣的說法吧。
1-2 故事的特性
在上一節中,談到了身為一個心理治療師,之所以意識到故事重要性的思考歷程。在本節中,我想針對故事的特性再多加思考。在故事的特性中,首先我想強調的是「建立雙方關係」的作用。或者也可以說,故事是從想要為某些事物「建立關係」的意圖中產生的。
我們來思考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杯子中插著一朵野花,如果事情只是這樣,或許沒有誰會特別注意這朵花。可是,一旦知道這是一個十歲的小女孩為了替臥病在床的母親打氣而在放學的時候摘來的,這朵花就不單單只是一朵花了。透過這朵花,我們對這個女孩有了親近感,也能體會她們母女之間的親情。這個時候,「關係的建立」便形成了。當我們受到這件事感動,便會想要向人訴說。當我們跟朋友聊到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說,小女孩本來是想買花的,可是對她來說太貴了,當她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突然看見了一朵野花......,故事稍微有了改變。聽到這件事的人再去對其他人述說的時候,可能又會加油添醋:她的母親看到這朵花覺得很開心,高燒一下子便退了......。
所以有人說「故事」不可信,這就是原因之一。雖然把故事內容完全當真,是愚蠢的,可是如果因為這樣就說故事是毫無意義的,這也不對。透過敘說故事,我們得知了母女關係的樣貌。透過對於母女親情的感動,說者與聽者之間產生了關係,「關係的圓」範圍漸漸擴大,從而故事有了它的意義。關係中的真實,會像這樣漸漸傳遞出去。
關於事物的本質,如同眾所周知的,紫式部早在將近一千年以前就在《源氏物語》中論述過,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螢〉的這一卷中,光源氏一開始給了故事相當低的評價,他說「故事很少說出真正的事實」。可是到後來他說,比起敘述單純的事實,故事傳遞了更多的真實。此時,源氏所說的「《日本書紀》等史書都只是片面之詞」,可說是「一語中的」的一句話。他的意思是,只記載事實的《日本書紀》等正史史書,寫的都不過只是極少的一部分而已。賭上性命創作故事的紫式部自視之高,藉光源氏的口說了出來。
曾經擁有高度評價的故事,在近代之後急遽失去其價值。其中,自然科學占了很重要的角色。自然科學雖然致力於找出外在事實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因果關係」,但前提卻是把這些外在事實當做是和觀察者(研究者)沒有關係的東西。因此,從中發現的事實具備了超越單一個人的普遍性,而這個「普遍性」擁有非常強大的力量。也就是說,如果巧妙地結合透過自然科學所發現的結果和技術,人類就得以立於現象的「外側」來進行控制、操作。或許是因為這個方法太過有效,人類才會因此以為科學知識可以化一切為可能,或是誤解科學知識才是唯一的真理。
因為這樣的誤解,許多現代人因此切斷了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變得像是無根的浮萍一樣。雖然生活變得方便而有效率,但自己到底為何而活?這個「活著的意義」感覺似乎急速地變得薄弱。所謂「意義」,就像是整體關係的應有樣貌。如果人活著,卻不知道自己和圍繞著自己的世界有著什麼樣的關係,當然也就感覺不到「意義」。
可是,許多人在察覺這個道理之前,就已經否定了自然科學以外的知識,或是嗤之以鼻。而人們也假設很多的學問研究是「科學的」,他們嘗試將十八世紀的物理學方法論適用在自己的領域中,無論他們的專業範疇是社會科學還是人文科學。他們獲得了一定的成果,這是事實。可是如果他們以為僅僅如此就是做學問,或是只有這個方法才是獲知真正事實的方法,那就錯了。
現代人被迫從種種不同的觀點反省「自然科學是全知全能的」這樣的想法,其中一個相當大的主題應該可以說是「死亡」。無論醫學再如何進步,人類都無法對死亡說不。人們希望至少可以盡可能長壽,所以延命醫學愈來愈進步,近代人的平均壽命也因此增加。可是,這個現象反而讓「死亡」成了更深化的課題。
如同前文所述,關於「人類的死」,我們或許可以把它當做是和自己無關的事情,用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可是關於「我自己的死」,要當做是和自己無關的事情,卻是不可能的。不只是我自己的死,連和我關係親近的人的死也是一樣,不是嗎?經歷了家人、情人、對自己而言重要的人的死亡,人們有時候會罹患抑鬱症而來找我們心理治療師尋求諮商。「為什麼他會死?」對於這些人這樣的提問,用科學的方式來說明,是沒有意義的。這些人想知道的是,「第二人稱的死(近親者的死)」代表了什麼意義。換句話說,他們是想針對「為什麼他會死?」這個問題,找出自己也能夠接受的「故事」。
這麼一想,你或許會察覺在故事裡提到「死亡」的例子有很多。「第一人稱的死」、「第二人稱的死」,對人類而言是永遠的課題。也因為如此,它們很容易就在故事裡成為主題。在後文將舉出的王朝時代的物語裡也是一樣,沒有一個故事是完全不提及死亡的,只是各故事的說法各不相同而已。
故事具有創造兩者關係的作用,這一點我們不能忘記,故事除了建構自他之間的關係之外,也會在我們的內在建構連結。如果以深層心理學的思考方式來說的話,就是我們必須要認知到故事所扮演的,連結意識與無意識的這個角色。在人的內在,除了平常就在運作的意識之外,還會產生我們無法輕易意識到的內心運作。人們稱之為「我」的存在,到底具有多大的廣度和深度,這是無法測量的,可是一般人都相信,「我」知道我自己的事情。然而,試著去想想我們的身體,你就能馬上明白,「我」對於我的身體是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儘管如此,身體一樣運作得很好。身體中有「我」可以控制、能夠認知到其運作的部分。而關於內心,好像也是如此。雖然有些我們不知道的內心運作會發生,但是它們會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妥善運作。
如果這個整體性的統合出了差錯,這樣的人便會尋訪我們心理治療師。為神經衰弱所困擾的人,就是這一類的典型。例如,當一個人罹患不潔恐懼症,他在摸了東西之後就必須洗好幾次手。他在正常的意識中雖然知道沒有必要,可是不洗手他就覺得不痛快。無意識的內心運作為了和正常的意識達成妥協,不斷洗手這樣的強迫行為便成了必要。
如果事情沒有這麼嚴重,又會是怎麼樣的情形呢?例如,在正常的意識裡,一個人會充分明白自己擔任某家企業課長的這個事實,在一般人的觀念裡具有多高的地位。可是在無意識中,他會希望能夠大大強調自己是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存在,無論他的地位高低或是財產多寡,他都擁有絕對的存在價值。此時,聯結這兩種意識的「故事」就有了必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法,舉例來說,某個課長在喝醉之後一定會自吹自擂,編造自己指正部長的過失,給了對方沉重一擊的「故事」─事實可能沒有這麼了不起─這個「故事」便扮演了統合他的人格的角色。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他是在清醒而且部長也在場的時候說這個「故事」,或是他周圍的人聯合起來,當他又要開始說一樣的故事時就說「知道了啦」,阻止他繼續說下去,他就會陷入相當程度的危機裡。「故事」在維繫一個人的意識整合上,發揮了它的功能。所有的人應該都擁有這樣的「故事」,雖然也有人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5-2 繼子故事的種種樣貌
《落窪物語》幾乎可以說是繼子故事的典型,不過我們可以說,全世界都有這樣的繼子故事。我在研究日本人的領域方面,首先以日本的神話、民間故事為對象,對於日本民間故事中的繼子故事,尤其感興趣。這是因為,如同在第二章〈殞滅之美〉中稍微提及的,在日本的民間故事中,就如同「黃鶯之居」,年輕男女雖然相遇(有時候會結婚),結局卻多是勞燕分飛。相對於此,在繼子的故事裡,很多到最後都迎向了幸福婚姻。這在一般而言,悲劇結局較多的日本民間故事裡,尤其是與歐洲的故事相較之下,甚至讓人感覺是特例。然而在日本的民間故事中,繼子故事所占的份量相當大。在關敬吾所編纂的《日本民間故事大成》第五卷中,收錄了將繼子故事分類而成的二十種故事類型。接下來,我將敘述其中一則「米福粟福」極其簡單的故事概要。
從前從前,有兩個名為米福、粟福的姊妹。米福是前一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因此後母無時無刻都在找機會霸凌她,不過妹妹粟福卻性情良善,總是護著姊姊。有一次,後母要去參加廟會,她只帶粟福,要米福看家。這個時候雖然她給米福出了種種難題,不過都在路過的和尚和麻雀的幫助之下解決了。鄰居的女孩來約米福一起去廟會,但米福沒有可以穿出門的衣服。她想起山中的老婆婆曾經給她一個藏寶箱,打開一看,裡面有一件美麗的和服,於是她穿著和服前往廟會。粟福察覺到姊姊來了,母親卻說那不是米福,因為她穿的和服太漂亮了。米福先回家換回髒衣服,當她正在工作的時候,後母和粟福回來了。後來,有個人來提親,希望能夠迎娶米福。米福從山中老婆婆給的藏寶箱中拿出了新娘子的禮服,並穿上它坐上轎子嫁過去了。粟福說她也想坐上轎子嫁人,卻沒有人要娶她。母親讓粟福乘坐在石臼上拖著她走,結果摔了一跤,兩個人都滾進田裡。她們一邊說著:「啊,好羨慕,好羨慕啊!」然後便咕嘟咕嘟地沉入水底,變成了田螺。
這則故事中,繼女被後母霸凌,但是最後有了幸福婚姻的這一點和《落窪物語》是相同的。只是,後母在這一則故事裡,因為自己的失誤丟了性命,而在《落窪物語》中說的則是有意識的復仇。在民間故事的繼子故事中,只敘述繼子的幸福結局,而不特別提及後母下場的作品相當多,其中幾乎沒有復仇的故事,後母是以某種形式受到懲罰,大概是這樣的模式。不過,在民間故事中有許多像這樣遭受後母霸凌的女兒,最後步入幸福婚姻的故事,這一點值得注目。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物語作品。先前提過《落窪物語》是現存最早獨立描寫「霸凌繼子的故事」的物語作品,不過在當時,同樣以霸凌繼子為主題來傳述的作品,還有《住吉物語》。只不過,這部物語只剩下在鎌倉時代改寫的作品流傳至今日。(全文未完)
1-1 心理治療的世界
我接下來將以「活在故事裡」為題,舉日本的王朝物語為例進行討論。我想我既非日本文學也非日本史學專家,卻特意要針對日本的物語加以論述,應該在文章的最開始稍微說明一下是什麼緣故。
我的專門領域是臨床心理學,一心為心理治療竭盡心力。一開始,我強烈希望可以將自己執行的工作盡可能「科學化」,讓它成為可信賴的職業,也一直朝著這個目標努力。但此同時,我在工作上最重要的目的依然是─探究怎麼做才能為前來諮商的人提供最大幫助。在持續以後者為中心的執業過程中,我漸漸自覺到,自己的工作是一份不得不異於以往科學方法的工作。
讓我這樣思考的機緣很多,我舉一個例子。在我們的領域中有學會,大家都期望在學會裡見到科學的、客觀的研究發表。因此在初期,清一色都是這樣的成果發表。然而在反覆舉辦的過程中,我逐漸了解比起這樣的內容,徹底追究一個實際案例的「個案研究」對聽眾更有幫助。我從經驗中清楚知道,這和其他「科學」領域中的「專案報告」(a case report)意義並不相同。也就是說,一般而言,專案報告是為了指出有這樣特別的案例存在,因此今後在這樣特殊的案例出現之時便可以派上用場。但我卻了解到,我們所進行的「個案研究」在更加廣泛的意義上會有幫助。
例如,當某個人發表「焦慮症」的個案研究時,聽者會感覺這可以運用在自己所負責的拒學學生心理治療上。就算是女性的個案,在男性個案上一樣可以派上用場。因為這雖然是「個案」,卻能夠普遍地造福其他案例。這種時候,我不僅會想要自己也來如法炮製,更會湧現出想要從頭開始重新整理研究發表內容的欲望。
這是為什麼呢?最直接了當的回答就是:在心理治療中「人際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自然科學領域中,一直以來,研究者都必須和他所研究的對象切斷關係。因為是從彼此沒有關聯的立場來客觀地進行研究,所以研究結果具有普遍性。然而,心理治療師如果和前來諮商的案主「切斷關係」,用這樣的態度來聽對方說話,諮商是無法進行的吧。這樣說起來,這個「關係」是什麼樣的關係?這段關係又會如何變化呢?治療師與案主的關係雖然重要,案主自己不是也置身在家人、朋友、同事等的關係網絡中嗎?再加上,即使說是兩個人「交談」,在這個過程中,治療師的心理狀態、身體狀態都會發生變化,如果像深層心理學家說的無意識也會產生關聯的話,治療師與案主的關係將變得極其複雜。
治療師一邊全盤考慮這樣的關係,一邊在這關係的整體之中找出條理,和案主朝著治癒的方向邁進。對聽者而言,在聆聽這類發表的時候,心裡會對於種種關係的樣貌進行反省、發現,而這些反省、發現,會超越該個案的具體事實,成為有用的東西。在明白會有這樣的效益之後,我們的學會便開始十分重視個案研究。順帶一提,就在我們開始這麼做之後,帶著熱情來聆聽發表的參加者變得非常多。因為內容可以立即派上用場,有這樣的反應也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雖然我從經驗上得知個案研究的重要性,但讀到榮格學派的心理分析學者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主張個案研究的本質是 story telling 的時候,我才茅塞頓開,這就是說故事啊!人類要將自己所經驗的事情化做自己的一部分,或是放在自己心裡,必須要將這些經驗善加組合在自己的世界觀或是人生觀中。這項作業也就是將這些經驗化為自己可以接受的故事,並從中梳理出脈絡。有情節,是故事的特徵。在「報告」個案的時候,報告者認為自己只是在敘述事實,但因為其中具備了已經被收藏到治療師內心裡的脈絡,就這一點而言,個案報告在不知不覺中已經變成了 story telling。
如果以這樣的邏輯來思考,我想我們也可以說心理治療這份工作,本來就是要幫助前來諮商的人創造適合他們自己的故事。例如,對於為神經衰弱症狀所困擾的人而言,他們的症狀是不是可以視做「沒辦法放進自己故事裡的材料」?又例如焦慮症患者,他們是因為不曉得這些焦慮是從何而來、為什麼會出現,所以才會焦慮。他們無法將這些不安編進自己的故事裡,用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說出來。因此,為了使創造自己的故事成為可能,我們必須進行各式各樣的調查,像是自己過去或是現在的狀況、從前自己未曾意識到的內心運作等等,在進行這些調查的過程中,會有新的發現,獲得新的觀點。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可以透過一覽全貌得知「原來如此」,藉此能夠把自己的人生「當做故事來述說」。這時,這些症狀應該就消失了。
如果採取「我的人生故事」這樣的思考方式,每個人應該都是不一樣的,但在某個程度上卻又可以類型化。也因為如此,我們心理治療師在一定程度上必須知道各式各樣的故事以及其類
型。這是我之所以對故事抱持興趣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人,喜歡故事。人類從獲得語言能力的那一刻開始,或許神話就已經誕生了。伴隨著神話,人們的對話內容也以「民間故事」或「傳說」的型態流傳下來,而它們的共同特徵是「作者」不詳。說不定,它們是某個天賦異稟的個人所創造的作品,卻透過了共同擁有這些故事的人們,以「我們的故事」的形式存續了下來。藉由這些故事,人們得以強化與過去的連結、與土地的連結,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連結。如果用現代的詞彙來說,我們可以說「故事」在建立某個部落民族或是家族的主體認同上幫了大忙。
心理治療師的工作之一,便是幫助前來諮商的人探索自己的主體認同。這項工作和前文中提到的創造「自己的故事」,可以說是同義詞。就我目前為止所論述的幾個點來看,讀者應該可以認同這樣的說法吧。
1-2 故事的特性
在上一節中,談到了身為一個心理治療師,之所以意識到故事重要性的思考歷程。在本節中,我想針對故事的特性再多加思考。在故事的特性中,首先我想強調的是「建立雙方關係」的作用。或者也可以說,故事是從想要為某些事物「建立關係」的意圖中產生的。
我們來思考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杯子中插著一朵野花,如果事情只是這樣,或許沒有誰會特別注意這朵花。可是,一旦知道這是一個十歲的小女孩為了替臥病在床的母親打氣而在放學的時候摘來的,這朵花就不單單只是一朵花了。透過這朵花,我們對這個女孩有了親近感,也能體會她們母女之間的親情。這個時候,「關係的建立」便形成了。當我們受到這件事感動,便會想要向人訴說。當我們跟朋友聊到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說,小女孩本來是想買花的,可是對她來說太貴了,當她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時候,突然看見了一朵野花......,故事稍微有了改變。聽到這件事的人再去對其他人述說的時候,可能又會加油添醋:她的母親看到這朵花覺得很開心,高燒一下子便退了......。
所以有人說「故事」不可信,這就是原因之一。雖然把故事內容完全當真,是愚蠢的,可是如果因為這樣就說故事是毫無意義的,這也不對。透過敘說故事,我們得知了母女關係的樣貌。透過對於母女親情的感動,說者與聽者之間產生了關係,「關係的圓」範圍漸漸擴大,從而故事有了它的意義。關係中的真實,會像這樣漸漸傳遞出去。
關於事物的本質,如同眾所周知的,紫式部早在將近一千年以前就在《源氏物語》中論述過,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螢〉的這一卷中,光源氏一開始給了故事相當低的評價,他說「故事很少說出真正的事實」。可是到後來他說,比起敘述單純的事實,故事傳遞了更多的真實。此時,源氏所說的「《日本書紀》等史書都只是片面之詞」,可說是「一語中的」的一句話。他的意思是,只記載事實的《日本書紀》等正史史書,寫的都不過只是極少的一部分而已。賭上性命創作故事的紫式部自視之高,藉光源氏的口說了出來。
曾經擁有高度評價的故事,在近代之後急遽失去其價值。其中,自然科學占了很重要的角色。自然科學雖然致力於找出外在事實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因果關係」,但前提卻是把這些外在事實當做是和觀察者(研究者)沒有關係的東西。因此,從中發現的事實具備了超越單一個人的普遍性,而這個「普遍性」擁有非常強大的力量。也就是說,如果巧妙地結合透過自然科學所發現的結果和技術,人類就得以立於現象的「外側」來進行控制、操作。或許是因為這個方法太過有效,人類才會因此以為科學知識可以化一切為可能,或是誤解科學知識才是唯一的真理。
因為這樣的誤解,許多現代人因此切斷了與這個世界的「關係」,變得像是無根的浮萍一樣。雖然生活變得方便而有效率,但自己到底為何而活?這個「活著的意義」感覺似乎急速地變得薄弱。所謂「意義」,就像是整體關係的應有樣貌。如果人活著,卻不知道自己和圍繞著自己的世界有著什麼樣的關係,當然也就感覺不到「意義」。
可是,許多人在察覺這個道理之前,就已經否定了自然科學以外的知識,或是嗤之以鼻。而人們也假設很多的學問研究是「科學的」,他們嘗試將十八世紀的物理學方法論適用在自己的領域中,無論他們的專業範疇是社會科學還是人文科學。他們獲得了一定的成果,這是事實。可是如果他們以為僅僅如此就是做學問,或是只有這個方法才是獲知真正事實的方法,那就錯了。
現代人被迫從種種不同的觀點反省「自然科學是全知全能的」這樣的想法,其中一個相當大的主題應該可以說是「死亡」。無論醫學再如何進步,人類都無法對死亡說不。人們希望至少可以盡可能長壽,所以延命醫學愈來愈進步,近代人的平均壽命也因此增加。可是,這個現象反而讓「死亡」成了更深化的課題。
如同前文所述,關於「人類的死」,我們或許可以把它當做是和自己無關的事情,用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可是關於「我自己的死」,要當做是和自己無關的事情,卻是不可能的。不只是我自己的死,連和我關係親近的人的死也是一樣,不是嗎?經歷了家人、情人、對自己而言重要的人的死亡,人們有時候會罹患抑鬱症而來找我們心理治療師尋求諮商。「為什麼他會死?」對於這些人這樣的提問,用科學的方式來說明,是沒有意義的。這些人想知道的是,「第二人稱的死(近親者的死)」代表了什麼意義。換句話說,他們是想針對「為什麼他會死?」這個問題,找出自己也能夠接受的「故事」。
這麼一想,你或許會察覺在故事裡提到「死亡」的例子有很多。「第一人稱的死」、「第二人稱的死」,對人類而言是永遠的課題。也因為如此,它們很容易就在故事裡成為主題。在後文將舉出的王朝時代的物語裡也是一樣,沒有一個故事是完全不提及死亡的,只是各故事的說法各不相同而已。
故事具有創造兩者關係的作用,這一點我們不能忘記,故事除了建構自他之間的關係之外,也會在我們的內在建構連結。如果以深層心理學的思考方式來說的話,就是我們必須要認知到故事所扮演的,連結意識與無意識的這個角色。在人的內在,除了平常就在運作的意識之外,還會產生我們無法輕易意識到的內心運作。人們稱之為「我」的存在,到底具有多大的廣度和深度,這是無法測量的,可是一般人都相信,「我」知道我自己的事情。然而,試著去想想我們的身體,你就能馬上明白,「我」對於我的身體是如何運作,其實一無所知。儘管如此,身體一樣運作得很好。身體中有「我」可以控制、能夠認知到其運作的部分。而關於內心,好像也是如此。雖然有些我們不知道的內心運作會發生,但是它們會以一個整體的形式妥善運作。
如果這個整體性的統合出了差錯,這樣的人便會尋訪我們心理治療師。為神經衰弱所困擾的人,就是這一類的典型。例如,當一個人罹患不潔恐懼症,他在摸了東西之後就必須洗好幾次手。他在正常的意識中雖然知道沒有必要,可是不洗手他就覺得不痛快。無意識的內心運作為了和正常的意識達成妥協,不斷洗手這樣的強迫行為便成了必要。
如果事情沒有這麼嚴重,又會是怎麼樣的情形呢?例如,在正常的意識裡,一個人會充分明白自己擔任某家企業課長的這個事實,在一般人的觀念裡具有多高的地位。可是在無意識中,他會希望能夠大大強調自己是獨一無二、無可取代的存在,無論他的地位高低或是財產多寡,他都擁有絕對的存在價值。此時,聯結這兩種意識的「故事」就有了必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法,舉例來說,某個課長在喝醉之後一定會自吹自擂,編造自己指正部長的過失,給了對方沉重一擊的「故事」─事實可能沒有這麼了不起─這個「故事」便扮演了統合他的人格的角色。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他是在清醒而且部長也在場的時候說這個「故事」,或是他周圍的人聯合起來,當他又要開始說一樣的故事時就說「知道了啦」,阻止他繼續說下去,他就會陷入相當程度的危機裡。「故事」在維繫一個人的意識整合上,發揮了它的功能。所有的人應該都擁有這樣的「故事」,雖然也有人並未意識到這一點。
5-2 繼子故事的種種樣貌
《落窪物語》幾乎可以說是繼子故事的典型,不過我們可以說,全世界都有這樣的繼子故事。我在研究日本人的領域方面,首先以日本的神話、民間故事為對象,對於日本民間故事中的繼子故事,尤其感興趣。這是因為,如同在第二章〈殞滅之美〉中稍微提及的,在日本的民間故事中,就如同「黃鶯之居」,年輕男女雖然相遇(有時候會結婚),結局卻多是勞燕分飛。相對於此,在繼子的故事裡,很多到最後都迎向了幸福婚姻。這在一般而言,悲劇結局較多的日本民間故事裡,尤其是與歐洲的故事相較之下,甚至讓人感覺是特例。然而在日本的民間故事中,繼子故事所占的份量相當大。在關敬吾所編纂的《日本民間故事大成》第五卷中,收錄了將繼子故事分類而成的二十種故事類型。接下來,我將敘述其中一則「米福粟福」極其簡單的故事概要。
從前從前,有兩個名為米福、粟福的姊妹。米福是前一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因此後母無時無刻都在找機會霸凌她,不過妹妹粟福卻性情良善,總是護著姊姊。有一次,後母要去參加廟會,她只帶粟福,要米福看家。這個時候雖然她給米福出了種種難題,不過都在路過的和尚和麻雀的幫助之下解決了。鄰居的女孩來約米福一起去廟會,但米福沒有可以穿出門的衣服。她想起山中的老婆婆曾經給她一個藏寶箱,打開一看,裡面有一件美麗的和服,於是她穿著和服前往廟會。粟福察覺到姊姊來了,母親卻說那不是米福,因為她穿的和服太漂亮了。米福先回家換回髒衣服,當她正在工作的時候,後母和粟福回來了。後來,有個人來提親,希望能夠迎娶米福。米福從山中老婆婆給的藏寶箱中拿出了新娘子的禮服,並穿上它坐上轎子嫁過去了。粟福說她也想坐上轎子嫁人,卻沒有人要娶她。母親讓粟福乘坐在石臼上拖著她走,結果摔了一跤,兩個人都滾進田裡。她們一邊說著:「啊,好羨慕,好羨慕啊!」然後便咕嘟咕嘟地沉入水底,變成了田螺。
這則故事中,繼女被後母霸凌,但是最後有了幸福婚姻的這一點和《落窪物語》是相同的。只是,後母在這一則故事裡,因為自己的失誤丟了性命,而在《落窪物語》中說的則是有意識的復仇。在民間故事的繼子故事中,只敘述繼子的幸福結局,而不特別提及後母下場的作品相當多,其中幾乎沒有復仇的故事,後母是以某種形式受到懲罰,大概是這樣的模式。不過,在民間故事中有許多像這樣遭受後母霸凌的女兒,最後步入幸福婚姻的故事,這一點值得注目。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物語作品。先前提過《落窪物語》是現存最早獨立描寫「霸凌繼子的故事」的物語作品,不過在當時,同樣以霸凌繼子為主題來傳述的作品,還有《住吉物語》。只不過,這部物語只剩下在鎌倉時代改寫的作品流傳至今日。(全文未完)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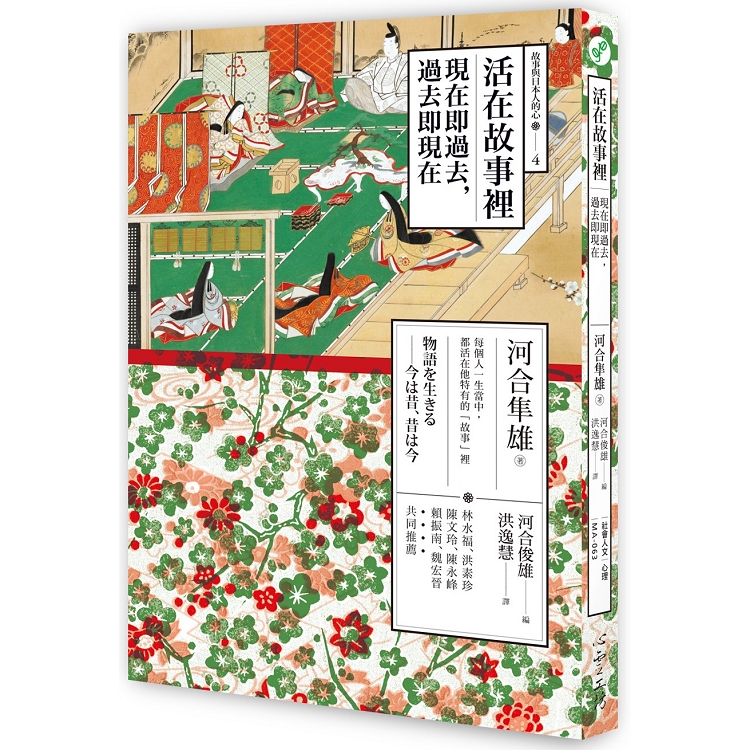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