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呼吸的罪:直木賞得獎作!一穂ミチ:我希望把所謂的「罪」描繪成一種──人人身上多少都有過的感覺。
第171屆直木賞得獎作!一穂ミチ把那些變形的日常瑣碎,說給你聽。超值合購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第171屆直木賞得獎作
一穂ミチ:我希望把所謂的「罪」描繪成一種──
人人身上多少都有過的感覺。
(《VERY》訪談)
獨家收錄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只要活著,就會犯錯。
▍但犯了錯的人,一定有罪嗎?
#罪與同類
十五歲的優斗,肯定沒想到二十歲的自己會活得如此不堪。大學中輟,在居酒屋攬客打工勉強過活。某天,一個濃妝豔抹的女子向他搭訕,優斗沉浸在豔遇的愉悅中,直到女子說她也是大阪人,名叫「井上渚」。不可能。只是同名同姓而已。畢竟,那個井上渚已經……
#罪與孤獨
疫情之下扛起家計的丈夫是很辛苦沒錯,但我只要看起來輕鬆一點,他就覺得我在偷懶。百合偷偷打開Meets Deli,今天來送餐的外送員不是他。這種期待感,是轉蛋。每次等待外送員頭像出現時,她有種近似電流通過的酥麻感,感覺自己真的「活著」。
#罪與憐憫
啊,我已經死了。似乎是在十五年前的豪雨中死亡,最近骨頭才被發現,不過我什麼都不記得了。我回到家裡,無意間聽到媽媽對著電話大吼:「我被那孩子偷走的錢都還找不回來!」什麼意思?我打算逃家?每當回想起什麼,不明白的事情不減反增,我好害怕,但我已經無處可去了。
#罪與羈絆
自從被餐廳裁掉後,恭一就一直繭居在家。某天兒子玩耍回來,拿著附近獨居老人給他的「符咒」,沒想到是張一萬圓舊鈔。兒子說那個爺爺抱怨管家煮的味噌湯太鹹,還說他的抽屜裡有很多張符咒。恭一久違地開始熬湯……
#罪與祝福
母親很擔心隔壁的太太,可能是新生兒過世了。比起這個,達郎更煩惱的是母親疑似出現失智症狀,還有讀高中的女兒懷孕,堅持要生下來。這種時候,達郎又接到母親跌下樓梯的消息。母親說是她自己跌的,監視器卻拍到一個女人匆忙跑離公寓……
#罪與希望
萬里無雲的星期六,我們約在郊外車站,「動物園的冬天」開車來接我們。後車廂載著剛從賣場買來的七輪爐與炭火,還真是輛適合露營的車呢。我們邊朝著山林駛去,邊七嘴八舌地聊天──明明我們就要去死了。
▍一穂ミチ筆下的「罪」就像感冒──
▍每個人都一定得過。
「小說的角色之一,正是看見那些從社會規範與常識中掉落的東西。就像手心捧水時,不管怎麼捧,都會漏出的一滴水——我想在作品裡描寫的就是那一滴。」
──一穂ミチ(《VERY》訪談)
想消失的人彼此成全。主婦沉迷於邂逅外送帥哥。拿走控制狂母親的錢離家。
覬覦獨居老人積蓄而照顧他。未成年懷孕堅持生下孩子。幫助不想活的人自殺。
落下的那一滴水,是外遇、詐欺或見死不救?或者孤獨、羈絆與希望?
「錯」的發生,未必帶著惡意,也許只是,在幸與不幸之間起伏,仍試圖前進。
而在那些難以定義的罪名裡,我們也許都──看見了自己。
▍一穂ミチ非寫不可的故事
「作家是種奇怪的生物,越痛苦、越煎熬的回憶,越覺得非寫不可,強迫症似的。或許是我自己斤斤計較的本性使然,總覺得不寫下來不划算,老是忍不住翻來覆去舔舐那些最苦澀的糖球。因為活著這件事,就是為了從中求取一滴甘露苦苦掙扎──那甘露也許是希望,也許是人情,也許是人與人之間相繫的紐帶。」
(摘自繁體中文版序)
▍台灣作家、各大書店工作者、愛書人一致推薦
書中的沉重命題不少,但作家厲害的地方在於,她把那些「為了生存而犯下的罪」寫得如此輕盈且具備溫度,彷彿剛剛才從我們身上取下似的。……這是讓人一邊讀一邊感嘆「人生真荒謬」,卻又忍不住想給這個世界一個擁抱的溫暖傑作。即使是有罪的靈魂,在找到同類的那一刻,也能重新學會呼吸。──小說家|劉芷妤
嗚哇,直木賞真不是拿假的。在狡猾的喜劇中,隱約透出子宮脫垂般的疲憊,我願稱它為住在精神病院的女性主義。──作家|盧郁佳
一穂老師不炫技,不多餘,清清淡淡地把疫情過後的世界,那些人,那些鬼,那些變形的日常瑣碎,說給你聽。
如此輕巧,又如此親密。很輕,卻能直擊人心。
⋯⋯疫情前的日子早已成為歷史,失去的東西不會再回來。
但我們還有故事,我們還有自己。
我們還有罪惡,足以支撐我們走完人生。──作家|蕭瑋萱
每讀完一篇都值得停下來思考,若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結局會如何?⋯⋯我們都曾經想犯罪,但最後阻止我們的或許是心中的那股名為人性的氣,或許是生活中某個人的善舉,亦或許是不經意抬頭看的天空。──**書店店員|Chun
讀到最後一篇實在是太精采。⋯⋯六則故事雖貫穿在被疫情毀掉的人生,但作者筆下的每個人物卻又是如此貼近生活且鮮明,敘事中沒有過多的跌宕起伏,彷若此刻日常且持續發生,正是如此讀起來特別精采過癮,更有同感。會讓人忍不住想著原來是這樣啊,如果是這樣……──**書店工|小喵
書中人物都是普通人,都有自己的遺憾、心事,有些傷痕不是要被原諒,是希望有人理解,有人能安慰⋯⋯人生雖然不盡完美,但還是有希望。這是一本讓人讀完意猶未盡的好書,值得閱讀。──墊腳石採購|孟儒
作者用了短篇小故事,述說人們後疫情時代的行為,內容詳述當下背景及每個角色的想法,顯示那最醜陋的一面,雖然改變不是壞事,但仍要朝好的地方發展,不然無法在多變的環境中適應。──墊腳石中壢店副店長|職業媽媽雅鈴
私心很喜歡一穂ミチ的文字,讀完都有種明亮感。如果說上本著作《請待在有光的地方》是雨過天晴的陽光普照,清新透明;《會呼吸的罪》則像是身處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直到眼睛適應了黑暗,才驚覺遠處正閃爍著一絲微弱卻堅定的光芒,帶著希望。──政大書城台南店 書店店員|胖達
明明是短篇故事卻讓人讀到欲罷不能!這六個故事都狠狠踩在道德缺失與罪證確鑿的灰色地帶上,除了探討日常生活中的小罪小惡之外,劇情的安排讓人像在搭雲霄飛車,故事前段慢慢爬升的過程中先埋下一些懸疑的種子,後段急轉直下的結局又令人瞠目結舌、驚呼連連,讀來實在太過癮了!──書食家
那些深藏在角色們內心底層的想法,也許你我都曾興起過,卻沒能與他人說出口,作者將這些「想法」撰寫成小說,沒想到如此令我感到毛骨悚然,然而,繼續閱讀下去卻產生了另一種深層的感受——巨大的悲傷。──閱讀書帳.愛書人|陳子楹
短篇主角們宛如現實生活中的小人物縮影,經由他們的視角去揭露那些未必能被法律清楚界定、卻真實存在的「罪」,讀來格外耐人尋味。
闔上書本才發現首篇一句平凡的對白深深留在心底:「就是覺得,大家都滿不容易的。」──書際探險家|蛙蛙
編輯推薦
有些罪就像感冒,每個人都得過
文/黃雅群(皇冠文化編輯)
一穂ミチ的《會呼吸的罪》榮獲第171屆直木賞,她在日本《VERY》雜誌專訪時這麼說:「我希望把所謂的『罪』描繪成一種──人人身上多少都有過的感覺。」
六篇故事的背景都是新冠疫情,日文書名「ツミデミック」,取「tsu-mi(「罪」的日文發音)」+「pandemic(疫情/大流行)」的結合,起初理解為「當罪成為流行性傳染病」,直到讀完整本書才恍然大悟,並不是「罪」正在大流行,是一穂ミチ筆下的「罪」像感冒,每個人一定都得過。
不過如此的巧思在中文語境裡較難呈現出同等的效果,因此繁體中文版書名從「活著就會犯錯」切入──在那段黑暗時期,我們確實連呼吸都像是有罪;在其他任何時候,只要會呼吸,就會犯錯,但犯了錯的人,一定有罪嗎?於是《會呼吸的罪》定罪,不對,是定名。
扛起家計的丈夫總是對自己嫌言嫌語,只要看起來輕鬆一點,他就覺得我在偷懶。主婦百合偷偷打開Meets Deli,期待那個外送員接單。這種期待感,是轉蛋。每次等待頭像出現時,她有種近似電流通過的酥麻感,感覺自己真的「活著」──這是外遇,還是孤獨?
被餐廳裁掉的繭居男恭一,無意間從兒子那得知,附近獨居老人家裡有很多「符咒」,是一萬圓舊鈔。他順便得知老人對管家煮的料理很不滿意,於是恭一久違地拿出食材,開始熬湯──這是詐欺,還是羈絆?
萬里無雲的星期六,一群人相約在郊外車站,其中一人開著適合露營的車來接他們。車上載著剛買來的炭火和爐子,一行人七嘴八舌,邊朝著山林駛去。明明他們就要去死了──這是見死不救,還是希望?
一穂ミチ說:「小說的角色之一,正是看見那些從社會規範與常識中掉落的東西。就像手心捧水時,不管怎麼捧,都會漏出的一滴水——我想在作品裡描寫的就是那一滴。」每一篇故事結束後心中浮現的問號,以及背後那份熟悉又曖昧的心情,我想就是落下的那一滴水,以及所謂「人人身上多少都有過的感覺」。「錯」的發生,未必帶著惡意,也許只是,在幸與不幸之間起伏,仍試圖前進。而在那些難以定義的罪名裡,我們也許都看見了自己。
在繁體中文版序中,作者寫下:「作家是種奇怪的生物,越痛苦、越煎熬的回憶,越覺得非寫不可,強迫症似的。或許是我自己斤斤計較的本性使然,總覺得不寫下來不划算,老是忍不住翻來覆去舔舐那些最苦澀的糖球。因為活著這件事,就是為了從中求取一滴甘露苦苦掙扎──那甘露也許是希望,也許是人情,也許是人與人之間相繫的紐帶。」全人類共同的黑暗記憶,成為直木賞得主非寫下不可的故事,對於讀者來說,也是一滴珍貴的甘露吧。
序/導讀
繁體中文版序
猶記得二○一九年年底,在報上看見「中國出現新型肺炎」的新聞那天。它只占據了國際版上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塊,我還和公司裡的同事聊著,要是擴散到日本來就不好了。當時那還只是幾句毫無危機感,氣氛和睦的日常閒談,誰也沒想過它真的會在轉眼間成為現實中的威脅。
《會呼吸的罪》,我非常喜歡臺灣版的這個書名。那段時期,真的好像連呼吸都是罪過一樣令人害怕。吸一口氣說不定就會把病毒吸進體內,自己呼出的氣息說不定會把病毒傳染給別人──那幾年間,我們就連獨處時都忘不了這種緊張感,各位讀者想必也一樣吧。在那個隔絕與不寬容如野草般瘋長的世界,唯有這份痛苦與不安彷彿能成為眾人心照不宣的共鳴,說來何其諷刺。
說到底,有些人從來不受病毒感染,有些人即使感染了,也能靠著自己的免疫系統戰勝病毒,只經歷輕微咳嗽和低燒就順利康復;另一方面,卻也有人患上嚴重肺炎因此喪命,也有人至今仍然苦於看不見盡頭的長新冠症狀⋯⋯我經歷的一切只屬於我,你經歷的一切也只屬於你,每個人各有各的「新冠疫情」體驗。
在這些經驗當中,或許也潛藏著這樣的故事──我懷抱這種想法,寫下了這六篇小說。每一篇都沒有特定原型,字裡行間卻都摻雜了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裡,我所嘗到的各式各樣的感受。重讀一遍,有些部分惹人發笑,也有些橋段令我胸口發緊。那段生活在物品滿溢的都市,卻連明天的口罩都沒有著落的日子。看見新聞上說臺灣透過優秀的行政系統,平等、高效率地將口罩分配給民眾,當時我不知道有多羨慕啊。直到今天,在便利商店或藥局看見貨架上成排的口罩,我仍不由得想起當時的心情。
作家是種奇怪的生物,越痛苦、越煎熬的回憶,越覺得非寫不可,強迫症似的。或許是我自己斤斤計較的本性使然,總覺得不寫下來不划算,老是忍不住翻來覆去舔舐那些最苦澀的糖球。因為活著這件事,就是為了從中求取一滴甘露苦苦掙扎──那甘露也許是希望,也許是人情,也許是人與人之間相繫的紐帶。
生活在日本的我,透過許多人的協助,得以將故事呈現給生活在臺灣的你,這也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滴甘露。
由衷感謝。
試閱
漣漪之旅
聽說,在全世界都屏住氣息的那段時期,連大氣污染的情況都有所改善。我原本想著要趁機到燈火熄滅的鬧區悠閒地看看星空,結果一次也沒有行動,明明有著大把的時間才對。發著呆吹著五月的風,無關緊要的心事從右至左流過腦海。如果討厭的回憶也能像這樣全部拋開,讓它們乘著風飛走就好了。正當我這麼想,下一班列車便到站了。
三名乘客分別從不同車廂走下來,一定就是他們了。我猶豫了一瞬間是否該向他們搭話,不過萬一認錯人就太丟臉了,我於是決定走向剪票口外,那是我們正式的碰面地點。
走出剪票口,剛才那三人果然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裡。一個是比我年輕一些,貌似二十歲後段的女人,一個是更年輕的少女,還有一個中年男人。女人沒戴口罩,脖子上圍著淺薰衣草色的披肩,一副初夏出遊的裝扮,但另外兩人除了下半臉都被口罩遮住之外,還戴了鴨舌帽,少女戴著眼鏡,男人戴的甚至是深色太陽眼鏡,幾乎看不出相貌。口罩一直到不久前還是象徵「安心」的指標,此刻卻感覺像一種可疑配件,肯定是因為它和今天晴朗明媚的風光一點也不相稱吧。
「啊,你該不會是推特上的……?」
我正猶豫該怎麼開口,披肩女便主動向我搭話了。
「是的,沒錯。」
「可以請教一下你的暱稱嗎?」
「……討厭小黃瓜。」
講出自己隨便取的暱稱實在太難為情,我以細如蚊蚋的聲音回答,她卻絲毫不放在心上,「噢」地點點頭:「你就是討厭小黃瓜。」
拜託不要再複誦一次。
「你好,我是萬壽菊。這邊這位男性是紅豆金時,女生是凱特毛絲。」
兩人只是把脖子往前伸似的微微點頭,冷淡的反應對我來說反而比較自在。考量到接下來的行程,這也是合適的態度。
「還有一個人,也就是動物園的冬天,會開車來接我們……但他好像還沒到。這一站也只有這個出口。」
車站前除了公車站、開設在車站建築內的便利商店,就只看得到拉下鐵捲門的居酒屋了。
「你們和動物園的冬天私訊聊過嗎?」
聽見萬壽菊這麼問,我們三人都搖搖頭。「動物園的冬天」是今天這場集會的發起人,約定見面的細節也由他主導安排,除了這個網名之外,我對他的年齡、性別都一概不知。他在推特上的用字遣詞很有禮貌,也認真回覆訊息,給人一種值得信任的印象。我明白網路上營造的印象根本靠不住,不過我猜其他幾位參與者大概也都是同樣想法。過了約定的時間,主辦人還沒現身,眾人之間彌漫起略顯不安的氛圍。
「我現在私訊他看看。」
我拿出智慧型手機,傳了一則簡短的訊息給動物園的冬天:「我們到了,全員到齊。」萬壽菊看著車道,喃喃說:「還是我們被騙了?」
「咦,討厭……」
凱特毛絲以細小的聲音抗議:「我們都特地跑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了。」
「就是說呀。不過,萬一他真的放我們鴿子怎麼辦?」
一個試探般的問題──實際上也是試探沒錯,萬壽菊在探問我們的意志、決心和覺悟。誰也沒答腔,我們偷偷窺探著彼此的反應,過半晌,紅豆金時開口:
「在問別人之前,妳呢?妳自己打算怎麼辦?」
那是道低沉又有磁性的美聲,與他可疑的打扮一點也不相稱,我嚇了一跳,總覺得好像在哪裡聽過這聲音。是我想太多了嗎,可是……我剛陷入沉思,萬壽菊便微微舉起一隻手,說:
「你們看,會不會是那輛車?」
一輛色彩莫名清新的萊姆綠休旅車朝這裡駛近。車子在我們面前停下,一個男人一走出駕駛座,便頻頻鞠著躬說:「不好意思,讓你們久等了。」男人一頭花白的頭髮,髮際線已經後退到靠近髮旋,戴著銀框眼鏡(可能是老花眼鏡),鏡片底下兩粒西瓜籽一樣的小眼睛畏畏縮縮地游移。他肯定是這群人裡面最年長的一位,恭敬到堪稱卑微的舉止卻顯得相當熟練。我推測,這個人大概吃過不少苦吧。如果在公所的櫃檯窗口看到他,這副碌碌無為的模樣說不定反而令人安心,感覺他會親切又仔細地告訴民眾該找哪個部門辦事,文件又該如何填寫。
他無從得知我失禮的想像,只是保持著卑躬屈膝的態度說「在推特上受各位關照了」。萬壽菊俐落地向他介紹:
「你就是動物園的冬天嗎?你好,我是萬壽菊,這幾位分別是討厭小黃瓜、紅豆金時和凱特毛絲,我們剛做完自我介紹。」
這個人的工作能力一定很強吧,活潑開朗,感覺溝通能力不錯,服裝和妝容也無可挑剔。為什麼她今天會出現在這種地方?儘管一瞬間感到疑惑,但她當然也有她的隱情,我立刻打消了這個想法。
「這樣啊,大家都到了。哎呀,真沒想到能全員到齊,這麼說或許也不太恰當,但我有點驚訝。身為發起人也不知道該不該高興,心情有點複雜……啊,各位請上車、請上車。」
動物園的冬天依然坐進了休旅車的駕駛座,我和紅豆金時坐在中央座椅,後排坐的則是萬壽菊和凱特毛絲。
「路上沒什麼車,可是五金百貨賣場人好多啊。」
明明也沒遲到多久,動物園的冬天卻持續解釋道:
「賣場有夠大,我找不到東西放在哪裡,但店裡店員又少,找不到人問路,真是急死我了。」
「政府第一次發布緊急事態宣言的時候,聽說大家無處可去,全都跑到五金賣場去採購家用品嘛。現在也還很多人嗎?」
萬壽菊友善地接話。
「聽說很多人會去戶外活動啦、露營什麼的,去買那些用品的人也不少。」
「這輛車感覺也很適合車上露營,真是輛好車。」
「已經是中古車囉。我本來想好了,假如今天誰也沒赴約,我就一個人漫無目的地開著車隨便轉轉,四處兜風。」
「這感覺也很好玩呢。對了,『動物園的冬天』真是個好名字,有種寂寞的感覺。」
「哎呀,真不好意思……妳說得沒錯,我啊,喜歡冬天的動物園。不是像上野那種大型的動物園,我更喜歡偏鄉平凡無奇的小動物園。遊客本來就不多,冬天平日的人煙更加稀少,動物們也冷得縮成一團,有種淡淡的哀愁。然後,該說再稍微加點巧思嗎,把兩個詞順序對調……啊,不好意思,光顧著自己說話。」
他說得興致勃勃,好像無論出於再怎麼瑣碎的原因,只要有人對自己感興趣、向自己提問就讓他高興得不得了。我對這態度有點煩躁,這是同類相斥,他表現得太過明顯,教人看不下去。同時卻也感受到一種親近感,畢竟他也是跑來參加這種集會的人嘛。
「那萬壽菊,妳是因為喜歡萬壽菊才取這個暱稱嗎?」
「對呀,很單純吧。紅豆金時喜歡紅豆嗎?」
紅豆金時冷淡地回答「還好」,他可能害羞吧。
「至於凱特毛絲,應該是喜歡那個模特兒吧?凱特.摩絲?」
我沒聽過這個名字,是知名人物嗎?凱特毛絲點頭說「超喜歡」。「我收集了好多她的剪報,手機裡大概存了一千張她的照片吧。」
「哇,真厲害。然後,討厭小黃瓜,就是很討厭小黃瓜吧。」
「……對。」
萬壽菊蘊含笑意的嗓音,聽得我臉頰發熱。我很清楚她沒有嘲笑我的意思,但儘管是用過即丟的帳號,多數人還是取了與「喜歡的東西」相關的名字,只有我一個人率先想到「討厭的東西」。這好像突顯出了我這個人的某種本質,教我無地自容。
「不過話說回來,雖然暱稱都是自己取的,用代號彼此稱呼還是有點那個啊,該說是難為情呢,還是有點肉麻呢……」動物園的冬天說。
「代號不是什麼好東西吧,像間諜一樣。」
「說得也對。」
聽見紅豆金時的吐槽,動物園的冬天迎合地笑了笑,報上自己的名字:
「敝姓毛利。聽說在網路上不能使用本名,我只是為了方便稱呼才取了個暱稱,還是用習慣的名字稱呼我比較自在。哎,不過我們也沒什麼機會喊彼此的名字就是了。」
「咦,那我要不要也說出我的名字呢……還是叫我萬壽菊就好了。話說回來,我們七嘴八舌地聊著這種話題,感覺也滿好笑的。」
萬壽菊說到這裡頓了頓,車裡的氣氛忽然沉重起來。
「明明我們現在就要去死了。」
年齡、特質都各不相同的我們,為了同一個目的在推特聯絡上彼此,聚在一塊,那就是一起自殺。我無法忍受自己繼續活著,渴望尋死,卻又沒有勇氣一個人實行,想找人作伴。一搜尋「自殺」,搜尋引擎就會多管閒事地將人導向求助專線,然而在女高中生跳樓直播也能登上趨勢的法外地帶,要找到同類卻易如反掌。我從那些標籤瀏覽各式各樣的帳號,找到「動物園的冬天」,成功加入了這個五人團體,人數對我來說不多不少剛剛好。我想我很幸運,成功篩選掉那些天天發文說「好想去死、好想去死」,只想引起別人注意的討拍仔,順利與一群有執行力的夥伴會合。休旅車從冷清的車站出發,朝著更加人跡罕至的山中林道駛去,後車廂堆著毛利買來的煉炭和七輪爐。
「只不過,天氣還真好啊。」
後照鏡裡,毛利笑得眼睛都埋進了皺紋裡:
「雖然我也不知道這到底該感激,還是該覺得可惜。」
接下來,我們真的都會死嗎?我仍然沒有任何現實感,拿手機嘗試搜尋「凱特.摩絲」。畫面上跳出一個女人的照片,她目光銳利、身材瘦削,是個美女,但我不明白那種「超喜歡」她,狂熱到把她的名字當成網名的心情。女孩子的喜好充滿了謎團。
「對了,各位,說好的東西都帶來了嗎?」
「帶來了。沒想到遺書這麼難寫,有些地方寫得太多了需要刪除,寫得太簡單又像在裝帥……簡直跟小學寫讀書心得的時候一樣辛苦。」
「萬壽菊的遺書,感覺會寫得很開朗呢。」毛利說。
「那我不是像個傻瓜一樣嗎。」
「不、不,我不是那個意思。」
前方出現隧道,萬壽菊從後排座椅把身體往前探,薄披肩輕輕掠過我的耳垂,搔得我有點癢。
「哎,你們看,山上開著好多紫藤花。」
確實,裸露的山地各處都濺上了淡紫色彩,與公園裡自藤棚規規矩矩垂下的紫藤花不同,能感受到野性的生命力。
「噢,真的耶,都到了這季節啦。跟萬壽菊的,呃,圍巾?是同一個顏色。」
「請你叫它披肩。」
「抱歉,我對時尚一竅不通。」
「如果開得滿山遍野,一定更漂亮吧。」
毛利和萬壽菊和睦地聊著,這時紅豆金時咕噥著潑了他們一盆冷水:
「少開玩笑了。」
休旅車駛進隧道,紅豆金時戴太陽眼鏡的側臉映在黑暗的車窗上,與水泥牆面形成二重曝光的畫面。
「紫藤一旦繁殖,被藤蔓纏上的樹木便會枯萎,它是所謂的『植物殺手』,處理起來非常麻煩。這是樹木沒受到良好保護,山林受傷的證據。我家老爸做的是林業,看紫藤都像看到眼中釘。」
紅豆金時突然滔滔不絕地說起話來,因此我和萬壽菊都盯著他瞧,凱特毛絲也從手機螢幕上抬起臉來,無法回頭的毛利在後照鏡中瞪大眼睛,像在說「哇」。紅豆金時的聲音果然很好聽,而且莫名耳熟。也許是受人矚目感到不自在了,紅豆金時補上一句「雖然這也不重要」,壓下鴨舌帽的帽簷。車子轉眼間穿過了隧道,五月明朗的日光再一次灑落擋風玻璃。
「不會、不會,我們也學到了一課。」
毛利一個人兀自點著頭,接著話鋒一轉。「話說回來……」他換上嚴肅幾分的語氣開口:
「我也不太好意思問這個,但要是一直掛心這件事,死也不能瞑目的話就傷腦筋了……所以還是請教一下,紅豆金時,你該不會就是演戲的那個遠藤三雄吧?」
我腦中模糊不清的思考回路瞬間連通,頓時有種撥雲見日般的暢快感,萬壽菊也輕輕「啊」了一聲。沒錯,就是那個演員,遠藤三雄。他常在連續劇和兩小時懸疑劇裡飾演戲份排行第四、第五的角色,雖然不起眼,但無論出現在什麼樣的作品都沒有突兀感,是個靈活稱職的配角,例如主角朋友的爸爸,或主角常去的居酒屋的老闆。
「真的耶,是遠藤三雄!我看過你的《地下搜查官》系列!」
萬壽菊興高采烈地說道,多半有點客套話的成分。反之,她隔壁的凱特毛絲也許是沒聽過這號人物,低下頭又開始滑起手機來。紅豆金時輕輕嘖了一聲,卻沒有否認,看來被說中了。
「哎呀,終於消除了我心裡一個疙瘩。這還是我生來第一次親眼見到藝人啊。」毛利說。
「不好意思喔,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的卻是這種二流藝人。」
「哪裡的話。說到底,像遠藤先生這樣的人,怎麼會來參加這種聚會……」
紅豆金時,也就是遠藤三雄,煩躁地扯下鴨舌帽和口罩啐道:
「這個問題的答案,你們比我更清楚吧。」
車內氣氛一陣尷尬,外頭傳來鳥鳴聲,像精心製作的環境音。誰也沒料到,下一個開口的竟然是凱特毛絲。
「遠藤三雄,炎上。」
看來她是在手機上搜尋相關報導。聽見「炎上」一詞,遠藤的嘴角扭曲。
三年前,政府頒布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期間,遠藤三雄在朋友經營的酒吧裡辦酒會,被週刊雜誌拍到他喝得爛醉,腳步搖搖晃晃地從店裡出來。照片和報導以〈密閉空間內密切接觸!知名演員酒吧內群聚開趴〉的標題登上網路新聞頭條,立刻引起無法自由外出、積鬱已久的大眾猛烈抨擊,「#要求撤換遠藤三雄」的標籤野火燎原般在社群媒體上擴散。遠藤三雄固定出演的系列連續劇以不自然的劇情發展讓他強制退場,舞臺劇以及電影工作也陸續遭到撤銷。在那段時期,這種獵巫般的譴責都稀鬆平常,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娛樂吧。只是回鄉下老家一趟、與一群人集體行動,就被視作重刑犯,公開姓名、學校或任職公司,遠藤三雄身為知名人物,火燒得特別旺。內容相差無幾的批判報導反覆出現在網路上,連他過去所有的一言一行都被放大檢視,類似的批評留言大量湧現。過不久,世人看膩了這場火刑,但他燒成灰燼的事業卻再也回不來。在這一刻之前,我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他在炎上之後一直被業界排擠在外。當然,我沒有加入抨擊他的行列,但罪惡感仍然一陣陣刺痛我的胃。記得有一說是,對霸凌視而不見的人也該當同罪。
「我的確違反了規定,我很抱歉,這我認罪。」
拿下口罩之後,遠藤身上傳出一股酒味,是打算這輩子最後一次喝個痛快嗎?我可是為了盡可能乾乾淨淨地死去,從昨天晚上就開始絕食了耶。
「可是,這種事有必要被抨擊到那種地步嗎?我並不是想辦什麼宴會,只是從新人時期就常常關照我的酒吧快倒閉了,我希望多少能幫上一點忙。我的經紀公司和老家都收到誹謗中傷的信件,甚至收到殺人預告,工作全部取消。你們記得當時的感染人數嗎?一天不到一千人。就為了那一千人提心吊膽,彼此監視,愚蠢也該有個限度。何況再過不久,即使每天幾萬人確診,所有人也當作沒看見了,反而還呼籲要讓社會運作、經濟流通。」
明明在這種時刻,演員現場的「獨白」卻讓我聽得有點入迷。他的咬字、聲量都和外行人完全不一樣,肯定得投注許多時間與努力才能習得這種技藝。他沒有偷竊東西,也沒有傷害別人,累積的一切卻只因為一次酒宴化為泡影,這劇本未免太殘酷了。
「我要讓那些一臉事不關己,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的傢伙知道,這就是你們瘋狂的正義感招來的結果。雖然這也同樣馬上就會被世人忘記,但反正我也沒什麼好失去了,所以我今天才決定參加。毛利先生是吧,怎麼樣,我的理由很符合主旨吧?」
「啊,是的,那當然,該說是無可挑剔嗎……」
毛利被他的氣勢壓倒,吞吞吐吐地回答。毛利以「動物園的冬天」身分募集死亡伙伴時,開出的條件是「人生被疫情毀掉的人」。
「各位,如果你們也不是被病毒本身,而是被這場疫情和疫情下的社會殺死了靈魂,要不要一起上路?在這一切被當作『過去』輕易淡忘之前,讓我們賭上性命,為自己發聲。向這個為了疫後新生活歡欣鼓舞的社會投下一顆震撼彈,告訴他們,失去的東西不會再回來。」
我不太確定自己是否符合條件,但受到這則推文吸引,我還是註冊了帳號,與動物園的冬天聯絡。近來自殺相關的報導容易受到規範,但只要我們所有人都帶來遺書,寫上各自尋死的理由,週刊雜誌肯定不會錯過這則新聞,人們會視之為疫情下的悲劇,在社群媒體上大量轉發──這是毛利的計畫。坦白說,我很懷疑事情是否真能這麼順利,不過如今有了遠藤,成功的可能性一下子提升不少。哎,不過死後人們的反應,我們也看不到了。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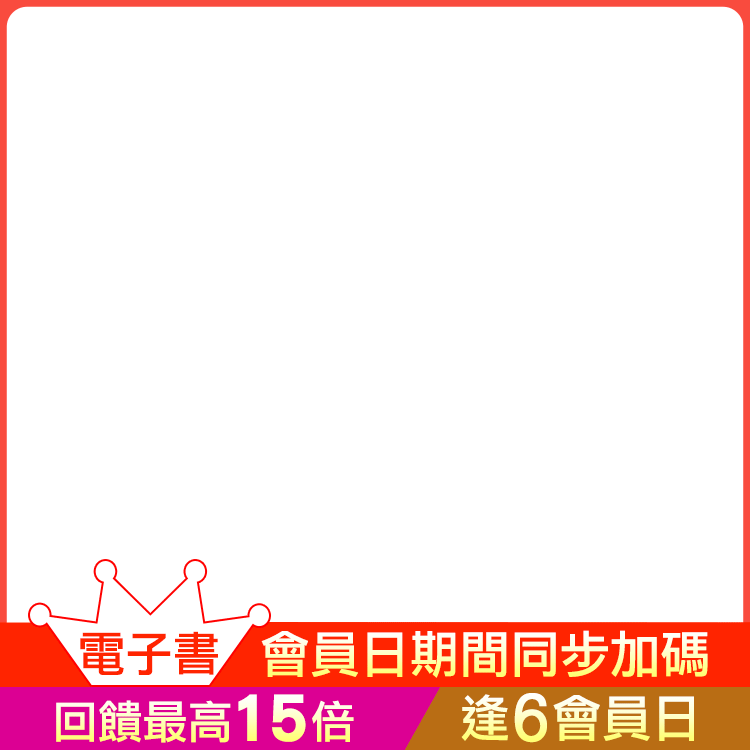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