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馬依北風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我可以這樣說嗎?
在這條創作的長路上,自己一直是個心懷感激的寫生者,
以親身的感受和行走作為基礎。
是的,是生命在激發我,
而我怎樣也不捨得忘記……如此而已。
三十年前,《信物》以荷花為題,書寫創作;三十年後,席慕蓉以游牧文化為題,回首凝望。
三十年的時間就在行走和追索探問之間慢慢地過去,曾痴心描摹的蓮荷,一夕之間對象轉為馬與原鄉。創作的描述不同,但本質沒有絲毫改變,都是生命的見證。
越過光陰長河,《胡馬依北風》除了見證創作長路迢遙,並同時紀念著創作者與出版社之間合作三十年的美好時光,依舊波光粼粼。
本書特色
◆ 從蓮荷到駿馬,三十年創作長路迢遙,這本書是生命的見證,更是一位作家與出版社共同銘刻,慶賀深厚情誼的芬芳信物。
目錄
代序:長路迢遙
海馬迴
輾轉的陳述
記憶或將留存
普氏野馬
溜圓白駿
後記:如此厚賜
附錄:出版書目
試閱
【內文連載】
後記:如此厚賜 在二○○五年四月十一日的日記裡,曾記下和齊邦媛老師的一段對話: 今天近中午時分,和齊老師通了一次電話,老師剛好在臺北家中,談興很高。這之間她引用了一句英詩,大意是:「現在的我,只想在路邊坐下,細細地回想我的一生。」 齊老師當時曾說了詩人的名字,但我沒記住。只是非常喜歡這句詩,就在晚上寫日記的時候,把這種感覺記下來。原來,一句詩,可以如此具象地呈現了創作源頭的那種渴望。 原來,從很幼小的時候開始,我就是自己的旁觀者。遇見不捨得忘記的時刻,就會叮囑再三:「不要忘記,不要忘記!」於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就常常喜歡在路邊或者桌前坐下,以畫面與文字,來細細回想剛才經過的一切……但是,怎麼會那麼剛好?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關鍵時刻裡,前前後後,圓神出版社竟然幫我出版了四本書,作為最精確的見證。 一九八八年三月出版的《在那遙遠的地方》,是住在香港的攝影家林東生經由曉風的介紹,自告奮勇在一九八七年夏季,以四十天的時間去內蒙古為我尋找並拍攝我父親故鄉附近的景象,再加上我曾經寫下的與自己鄉愁有關的散文,合成一冊,由圓神出版。 那時的我,並沒有察覺到周遭也在變化。是的,僅僅是一年多的時間之後,自出生到四十多歲都被隔絕在外的我,這個遠離原鄉的蒙古女子,竟然可以親自前去探訪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底,我站在父親的草原上,是整整前半生總是遙不可及的大地啊!如今卻就在我的眼前,我的腳下,等著我,等著我開始一步一步地走過去…… 雖然只有十幾天的行程,只去探看了父親的草原和母親的河。但是,那奔湧前來的強烈觸動如眼前的草原一樣無邊無際,如身旁的河流一樣不肯止息。於是,一九九○年七月,《我的家在高原上》出版了。除了我的文字之外,還有同行好友王行恭為我拍攝的更多的極為難得的現場畫面,並且還由他擔任美術編輯的工作。 怎麼會那麼剛好?這封面一綠一紅的兩本書,《在那遙遠的地方》和《我的家在高原上》見證的,是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因為世事的突變,身為當局者的我所生發的百感交集……而也由於這兩本書,我終於可以得到了臺灣朋友的同情,以及,蒙古高原上的族人的接納。這樣的情節如果寫在小說裡,讀者一定會認為太過牽強。可是,在真實的世界裡一切就是如此,有書為證,感謝圓神。 現在再來說另外兩本書,《信物》與《胡馬依北風》吧。 《信物》一書,出版於一九八九年一月,其實還早於我的還鄉,是在圓神出版的第二本書。 我想,從一九八八年第一本《在那遙遠的地方》合作開始,簡志忠和我這個作者之間,就有了一種「默契」。是的,在這裡,出版者和作者都還保有一些比較天真的願望。我們兩人都經歷過困苦的童年和少年時期,許多累積著的對「美」的想望,總是在被壓制或者被勸誡的狀態下,難以成形。 可是,生命本身有些質素卻極為頑強,一有可能,它們就萌發、成長。這本《信物》,或許就是出版者和作者共同的心願,以表達出自身長久以來對單純的「美」的想望吧。 這本《信物》,在當時的臺灣可以說是少見又有些奢侈的新書。精裝本全球限量兩百五十冊,由作者親自編號、簽名,並且還附贈一張以版畫方式精印的藏書票。 書的主題是蓮荷。文字只有一篇六千多字的散文,敘述我多年以來傾心於描寫蓮荷這種植物的起因,以及,種種與此有關的學習和創作過程的心情。貫穿全書的則是我在前一年(一九八八年)夏天,剛好獨自一人遠赴峇里島上的小鎮烏布,在當地的荷池旁,以兩個星期的時間寫生而成的素描,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多張。是清晨速寫回來之後,整個下午,再在旅舍房間的露臺上,重新以針筆和水彩筆構成的單色素描。 以下是書中的一段文字: ……住在我對面,隔著一大叢花樹,有時候只聽其聲不見其人的是一對德國夫婦,大概注意我很久了。終於有一天,在院子裡互道了日安和交換了天氣出奇的好之類的寒喧之後,金髮嬌小的妻子忍不住問我,是不是在寫小說? 我笑著否認了,並且邀她到我屋前的平臺上來,給她看我的速寫和素描,告訴她說,我是來這裡畫荷花的。 她轉過身來興奮地向她的丈夫說:「你聽過這樣的事嗎?一個人跑到這麼遠的島上來只是為了畫一朵荷花?」 她這句話說出來之後,我好像才忽然間從別人的眼睛裡看到我自己,原來是這樣的荒謬而又奢侈— 整整一個夏天,只為了畫一朵荷。 可是,整個事情,果真是像它表面所顯示的那樣嗎?我回來了之後,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荒謬的意思就是不合理,奢侈的意思就是浪費。可是,要怎樣的生活方式才能是合理而又不浪費的呢? 我們的生命,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不都是一件奢侈品嗎? 要怎樣用它,才能算是不浪費呢? 這些是一九八八年深秋之後,寫在《信物》裡的一段文字。其實,前幾個月在峇里島上速寫蓮荷之時,並沒預想到這些畫作會單獨成為一冊精裝限量版本的主題。而等到一九八九年一月書成之時,和朋友們歡喜慶祝的時候,也完全不能預知,還有更歡喜和更奢侈的道路就在不遠的前方。 是的,僅僅只在《信物》書成的幾個月之後,我就從前半生這小小安靜的世界裡突然跨入蒙古高原那時空浩瀚的故土之上了。 三十年的時間就在行走和追索探問之間慢慢地過去…… 今天,正在為《胡馬依北風》這本新書寫後記的我,身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十年的盛夏,端午剛過兩天。前幾日才知道簡志忠還是堅持要再出版一本限量版的精裝新書,以紀念和慶賀我們合作三十年的美好時光。 真的啊!怎麼可能一合作就是歡歡喜喜的三十年了呢? 這一次,新書所有稿件都已齊備,只差我筆下這篇後記。 新書的主要內容是五篇散文中的幾匹蒙古馬,再加上幾幅我畫的與原鄉有關的畫作,還有我的幾張攝影作為記錄,書名是《胡馬依北風》。 感謝圓神,怎麼會那樣剛好?前面有兩本相距只有兩年時間的書,為我留下歸返原鄉之前《在那遙遠的地方》的萬般惆悵,和《我的家在高原上》初見原鄉時的狂喜和憂傷,甚至還有憤怒…… 那曾經坐在路邊細細回想的一切,圓神都讓它成書,成為生命的見證。 而今天,兩本相隔超過三十年的《信物》與《胡馬依北風》所要見證的,卻幾乎是比三十年更為加倍長久的時光裡,我在稱為「創作」這條長路上的變與不變了。 在《信物》中以二十多年的痴心去描摹的蓮荷,可以在之後的一夕之間棄而不顧,這變動從表面上看來不可說不大。 而在三十年後的《胡馬依北風》裡,除了描摹和敘述的對象改變了以外,而在我四周,那無論是時間上的深遠和空間裡的巨大都是無可否認的改變。 但是,我可不可以這樣說?是生命在激發這些變化,我創作的本質卻依然沒有絲毫改變。 我可以這樣說嗎?在這條創作的長路上,自己一直是個心懷感激的寫生者,以親身的感受和行走作為基礎。是的,是生命在激發我,而我只是怎樣也不捨得忘記……如此而已。 三十多年來出版的書目,會放在這本新書的後頁。而三十年裡,能有這樣的四本書作為創作初心的見證,是簡志忠,以及所有工作伙伴給我的厚賜。 在圓神的美編團隊裡,早先是和正弦合作,這幾年則是和鳳剛一起工作。兩人的風格不同,卻都是才情充沛的年輕人,有好幾本詩集的封面都各有特色。我尤其喜歡散文集《寧靜的巨大》封面的感覺。在工作中,他們好像也能寬諒我的猶疑不決,知道我正在一個新的世紀裡努力去學習和適應呢。 最知道我的這種掙扎的是近幾年的主編靜怡。在電話裡,她的聲音總是平和舒緩。可是,在討論的時候,她卻常常會激發出我對創作的熱情而快樂起來,很溫暖的感覺,好像剛才曾經面對的困難已經不再是困難了。 想一想,在這超過三十年的時光裡,無論是畫一朵荷或者敘述幾匹馬,整個出版社都來給你護持和加持,卻從來沒給你任何壓力,總是任由你安靜而又緩慢地繼續寫下去,這是多麼難得的情誼啊! 如此厚賜,我深深感激。 輾轉的陳述 一九九二年五月下旬,蒙藏委員會在臺北的政治大學校區,舉行了一場「蒙古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中,哈勘楚倫教授以〈蒙古馬與馬文化〉為題,發表了一篇論文。 在談到蒙古馬特別強烈的方向感,以及眷戀故土的優異性向之時,他舉了一個真實的例子,讓我非常感動,會後不久就寫了一篇散文〈胡馬依北風〉。四年之後,又在一篇範圍比較大的散文裡加進了這匹馬的故事作為其中的一段。 現在,我想摘錄上面兩篇散文裡的不同段落,重新組合成我今天要敘述的「前篇」: 這則真「馬」真事,發生在六○年代中期的蒙古國(那時還叫做「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的政府送了幾匹馬給南方的友邦越南政府作為禮物。 這幾匹馬是用專人專車護送到了目的地。可是,第二天早上,發現其中的一匹騸馬不見了,在附近搜尋了一陣也毫無所獲,只好向上級報告。幸好贈禮儀式已經舉行完畢,也就沒有再深加追究了。 半年之後,一匹又瘦又髒,蹄子上還帶著許多舊傷新痕的野馬,來到了烏蘭巴托城郊之外的牧場上。牧場主人一早起來,就看到了牠在遠遠的草地上站著,心想這到底是誰家走失了的馬,在那裡踟躕流連…… 想不到,靠近了之後,才發現這匹馬竟然在對著他流淚,大滴大滴的熱淚不斷滾落下來。雖然是又瘦又髒,不過,一個蒙古牧人是絕對會認出自己的馬來的。 驚詫激動的主人,在想明白了之後,更是忍不住抱著牠放聲大哭了。 想一想,這是多麼令人心疼的馬兒啊! 想一想,牠要走過多遠的路?要經過多少道關卡?不但要渡過長江,渡過黃河,還有那大大小小許多數不清的河道支流;不但要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峻嶺,還要在連綿起伏的丘陵間辨識方向;不但要經過江南阡陌縱橫的水田,還要獨自跋涉荒寒的戈壁;還有,最最不可思議的是,牠要如何躲過人類的好奇與貪欲? 在牠經過的這條不知有幾千幾萬里的長路上,難道從來沒遇到過任何的村鎮和城市?難道從來沒有人攔阻或是捕捉過牠嗎? 不可思議!牠是怎麼走回來的?半年的時間裡,在這條長路上,這匹馬受過多少磨難?牠是怎麼堅持下來的? 驚喜稍定,主人開始大宴賓客,向眾人展示這剛從天涯歸來的遊子。並且鄭重宣布,從此以後,這匹馬永遠不會離開家園,離開主人的身邊,再也不須工作,任何人都不可以騎乘牠,更不可讓牠受一丁點兒的委曲。 據說,這匹馬又活了許多年,才在家鄉的草原上老病而逝,想牠的靈魂一定能夠快樂地安息了吧。 故事到了這裡,算是有了個完美的結局。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反而會常常想起另外的那幾匹留在越南的馬兒來。會後,我再去追問了哈勘楚倫教授,到底是什麼在引導著蒙古馬往家鄉的方向走去?他回答我說: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總覺得應該是一種北方的氣息從風裡帶過來的吧?」 也許是這樣。 就像古詩裡的「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每個生命,都有他不同的選擇與不同的嚮往,有連他自己也無從解釋和抗拒的鄉愁。 因此,我就會常常想起那幾匹羈留在越南的蒙古馬來,當牠們年復一年在冬季迎著北風尋索著一種模糊的訊息時,心裡會有怎樣的悵惘和悲傷呢? 以上是我的「前篇」,從一九九二與一九九六兩個年分裡的兩篇散文摘錄而成的。 是的,時間已經過去很多年了,我從小喚他叔叔,向他問過很多問題的哈勘楚倫教授也已經逝去。可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他用「風中帶來的氣息」作為回答時那微帶歉意的笑容好像還在我眼前。 是的,生命的奧秘是難以解釋的。我想,他心中真正的回答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吧? 今天的我,要寫的「後續」,也並非找到了答案,我只是在陳述事實而已。 我是從一九九三年夏天就認識了恩和教授的,他是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的教授,這兩年,我常常有機會向他請益。 去年(二○一四)秋天,我去呼和浩特的內蒙古博物院演講,然後和兩位朋友一起去拜訪他。他給我們講述游牧文化的歷史以及他在草原生活裡的親身感受,我們三個聽得都入迷了。 在這之間,他也談及蒙古馬的特殊稟賦,還舉了一個例子,他說: 我是從一本書裡讀到的。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蒙古的遊牧人》,作者是特木爾扎布先生,他是蒙古國的畜牧學家,也是科學院的院士。 在這本書裡,他引用了蒙古國一位頗負盛名,有著「人民畫家」封號的藝術家,貢布蘇榮先生的回憶錄中的一段。 貢布蘇榮在一九七一年,曾經應邀去越南參加了一次會議。那個時代,在共產國家裡,常有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藝術家召開的例會,每次輪流在一個不同的國家舉行,那年是在越南。 在會議之前,主辦單位邀請各國的代表先去一處海港城市散心。在這個城市的郊區,藝術家們隨意徜徉在空曠的草地上,有的就聚在一起閒聊,好增進彼此的認識。 遠遠看見一匹白馬在吃草,貢布蘇榮也沒特別在意。 他和幾位藝術家聚成一個小群體,其中有從俄羅斯來的,由於通俄語的緣故,聊得還很熱鬧。 但是,聊著聊著,有人就注意到了,那匹白馬忽然直直地朝向他們這群人走來,而且,目標似乎是對著貢布蘇榮。 再近前一些的時候,貢布蘇榮也看清楚了,這是一匹蒙古馬。毛色雖說是白,卻已髒汙,失去了光亮,馬身可說是骨瘦如柴。 這樣的一匹馬正對著他落淚。 儘管已經有人過來攔阻,白馬還是努力邁步往前,想要靠近貢布蘇榮。畫家那天穿著一身筆挺的西服,打著領帶,是以鄭重的心情來參與盛會的。可是,這匹馬好像也是下定了決心,非要來見貢布蘇榮不可。牠的力氣超乎尋常,眾人幾次攔阻都擋不住,終於給牠走到貢布蘇榮面前的時候,白馬的眼淚和鼻涕都沾到畫家的衣服上了。 不過,這時候的貢布蘇榮完全沒有在意,他的心中只有滿滿的疼惜,對眼前這匹傷心涕泣的蒙古馬,除了撫摸和輕拍牠的頸背,不知道要怎麼安慰牠才好。 「你是怎麼把我認出來的?你怎麼知道,我是從蒙古來的人呢?」 一九九五年,二十四年之後,貢布蘇榮在提筆寫這一段回憶之時,也是流著熱淚追想的。 是多麼令人疼惜的一匹好馬啊! 那天,恩和教授關於這個例子的講述就到此為止。我急著向他說出多年前哈勘楚倫教授舉出的那一個例子,不過,他告訴我,在上世紀六○年代裡,蒙古支援共產主義的越南,「贈馬」這樣的行動,應該有過好幾次。 所以,我並不能知道,這匹白馬,是否就是哈勘楚倫教授所說的那幾匹馬中的一匹。可是,牠的出現,卻可以讓我們明白,當年所有被送到越南,從此羈留在異鄉的每一匹蒙古馬兒的心情。 從牠身上,我們可以看見,一匹蒙古馬的大腦裡,藏著多麼深厚的感情與記憶,能把貢布蘇榮從人群之中辨認出來。 而這匹白馬如此奮力地向貢布蘇榮靠近,是希望這個從故鄉來的人,或許能帶自己回家嗎? 貢布蘇榮心中的疼痛與歉疚,想是因為他已完全明白了這匹馬的悲傷與冀望。可是,在當時的環境裡,他是怎麼也不可能把這匹馬帶回蒙古家鄉的。 所以,這種疼痛與歉疚始終沉在心底,使他在多年之後也不得不拿起筆來寫下這一次的相遇。是的,他沒能把白馬帶回來,可是,他還是可以把這一匹以及其他許多匹流落在異鄉的蒙古馬的悲傷,傳回到牠們的故鄉。 從六○年代中期到今天,已是整整的五十年了,無論是那匹回到家的馬,還是那些回不了家的,都早已不在人間。可是,在蒙古高原上,牠們的故事還一直在被眾人輾轉陳述,我想,轉述者的動機應該只有一種吧,那就是對如此高貴和勇敢的生命懷著極深的疼惜。 此刻,我也以同樣的心情和手中的這支筆,進入了這輾轉陳述者的行列,成為其中的一人了。
後記:如此厚賜 在二○○五年四月十一日的日記裡,曾記下和齊邦媛老師的一段對話: 今天近中午時分,和齊老師通了一次電話,老師剛好在臺北家中,談興很高。這之間她引用了一句英詩,大意是:「現在的我,只想在路邊坐下,細細地回想我的一生。」 齊老師當時曾說了詩人的名字,但我沒記住。只是非常喜歡這句詩,就在晚上寫日記的時候,把這種感覺記下來。原來,一句詩,可以如此具象地呈現了創作源頭的那種渴望。 原來,從很幼小的時候開始,我就是自己的旁觀者。遇見不捨得忘記的時刻,就會叮囑再三:「不要忘記,不要忘記!」於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就常常喜歡在路邊或者桌前坐下,以畫面與文字,來細細回想剛才經過的一切……但是,怎麼會那麼剛好?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個關鍵時刻裡,前前後後,圓神出版社竟然幫我出版了四本書,作為最精確的見證。 一九八八年三月出版的《在那遙遠的地方》,是住在香港的攝影家林東生經由曉風的介紹,自告奮勇在一九八七年夏季,以四十天的時間去內蒙古為我尋找並拍攝我父親故鄉附近的景象,再加上我曾經寫下的與自己鄉愁有關的散文,合成一冊,由圓神出版。 那時的我,並沒有察覺到周遭也在變化。是的,僅僅是一年多的時間之後,自出生到四十多歲都被隔絕在外的我,這個遠離原鄉的蒙古女子,竟然可以親自前去探訪了! 一九八九年八月底,我站在父親的草原上,是整整前半生總是遙不可及的大地啊!如今卻就在我的眼前,我的腳下,等著我,等著我開始一步一步地走過去…… 雖然只有十幾天的行程,只去探看了父親的草原和母親的河。但是,那奔湧前來的強烈觸動如眼前的草原一樣無邊無際,如身旁的河流一樣不肯止息。於是,一九九○年七月,《我的家在高原上》出版了。除了我的文字之外,還有同行好友王行恭為我拍攝的更多的極為難得的現場畫面,並且還由他擔任美術編輯的工作。 怎麼會那麼剛好?這封面一綠一紅的兩本書,《在那遙遠的地方》和《我的家在高原上》見證的,是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因為世事的突變,身為當局者的我所生發的百感交集……而也由於這兩本書,我終於可以得到了臺灣朋友的同情,以及,蒙古高原上的族人的接納。這樣的情節如果寫在小說裡,讀者一定會認為太過牽強。可是,在真實的世界裡一切就是如此,有書為證,感謝圓神。 現在再來說另外兩本書,《信物》與《胡馬依北風》吧。 《信物》一書,出版於一九八九年一月,其實還早於我的還鄉,是在圓神出版的第二本書。 我想,從一九八八年第一本《在那遙遠的地方》合作開始,簡志忠和我這個作者之間,就有了一種「默契」。是的,在這裡,出版者和作者都還保有一些比較天真的願望。我們兩人都經歷過困苦的童年和少年時期,許多累積著的對「美」的想望,總是在被壓制或者被勸誡的狀態下,難以成形。 可是,生命本身有些質素卻極為頑強,一有可能,它們就萌發、成長。這本《信物》,或許就是出版者和作者共同的心願,以表達出自身長久以來對單純的「美」的想望吧。 這本《信物》,在當時的臺灣可以說是少見又有些奢侈的新書。精裝本全球限量兩百五十冊,由作者親自編號、簽名,並且還附贈一張以版畫方式精印的藏書票。 書的主題是蓮荷。文字只有一篇六千多字的散文,敘述我多年以來傾心於描寫蓮荷這種植物的起因,以及,種種與此有關的學習和創作過程的心情。貫穿全書的則是我在前一年(一九八八年)夏天,剛好獨自一人遠赴峇里島上的小鎮烏布,在當地的荷池旁,以兩個星期的時間寫生而成的素描,大大小小共有二十多張。是清晨速寫回來之後,整個下午,再在旅舍房間的露臺上,重新以針筆和水彩筆構成的單色素描。 以下是書中的一段文字: ……住在我對面,隔著一大叢花樹,有時候只聽其聲不見其人的是一對德國夫婦,大概注意我很久了。終於有一天,在院子裡互道了日安和交換了天氣出奇的好之類的寒喧之後,金髮嬌小的妻子忍不住問我,是不是在寫小說? 我笑著否認了,並且邀她到我屋前的平臺上來,給她看我的速寫和素描,告訴她說,我是來這裡畫荷花的。 她轉過身來興奮地向她的丈夫說:「你聽過這樣的事嗎?一個人跑到這麼遠的島上來只是為了畫一朵荷花?」 她這句話說出來之後,我好像才忽然間從別人的眼睛裡看到我自己,原來是這樣的荒謬而又奢侈— 整整一個夏天,只為了畫一朵荷。 可是,整個事情,果真是像它表面所顯示的那樣嗎?我回來了之後,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荒謬的意思就是不合理,奢侈的意思就是浪費。可是,要怎樣的生活方式才能是合理而又不浪費的呢? 我們的生命,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不都是一件奢侈品嗎? 要怎樣用它,才能算是不浪費呢? 這些是一九八八年深秋之後,寫在《信物》裡的一段文字。其實,前幾個月在峇里島上速寫蓮荷之時,並沒預想到這些畫作會單獨成為一冊精裝限量版本的主題。而等到一九八九年一月書成之時,和朋友們歡喜慶祝的時候,也完全不能預知,還有更歡喜和更奢侈的道路就在不遠的前方。 是的,僅僅只在《信物》書成的幾個月之後,我就從前半生這小小安靜的世界裡突然跨入蒙古高原那時空浩瀚的故土之上了。 三十年的時間就在行走和追索探問之間慢慢地過去…… 今天,正在為《胡馬依北風》這本新書寫後記的我,身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十年的盛夏,端午剛過兩天。前幾日才知道簡志忠還是堅持要再出版一本限量版的精裝新書,以紀念和慶賀我們合作三十年的美好時光。 真的啊!怎麼可能一合作就是歡歡喜喜的三十年了呢? 這一次,新書所有稿件都已齊備,只差我筆下這篇後記。 新書的主要內容是五篇散文中的幾匹蒙古馬,再加上幾幅我畫的與原鄉有關的畫作,還有我的幾張攝影作為記錄,書名是《胡馬依北風》。 感謝圓神,怎麼會那樣剛好?前面有兩本相距只有兩年時間的書,為我留下歸返原鄉之前《在那遙遠的地方》的萬般惆悵,和《我的家在高原上》初見原鄉時的狂喜和憂傷,甚至還有憤怒…… 那曾經坐在路邊細細回想的一切,圓神都讓它成書,成為生命的見證。 而今天,兩本相隔超過三十年的《信物》與《胡馬依北風》所要見證的,卻幾乎是比三十年更為加倍長久的時光裡,我在稱為「創作」這條長路上的變與不變了。 在《信物》中以二十多年的痴心去描摹的蓮荷,可以在之後的一夕之間棄而不顧,這變動從表面上看來不可說不大。 而在三十年後的《胡馬依北風》裡,除了描摹和敘述的對象改變了以外,而在我四周,那無論是時間上的深遠和空間裡的巨大都是無可否認的改變。 但是,我可不可以這樣說?是生命在激發這些變化,我創作的本質卻依然沒有絲毫改變。 我可以這樣說嗎?在這條創作的長路上,自己一直是個心懷感激的寫生者,以親身的感受和行走作為基礎。是的,是生命在激發我,而我只是怎樣也不捨得忘記……如此而已。 三十多年來出版的書目,會放在這本新書的後頁。而三十年裡,能有這樣的四本書作為創作初心的見證,是簡志忠,以及所有工作伙伴給我的厚賜。 在圓神的美編團隊裡,早先是和正弦合作,這幾年則是和鳳剛一起工作。兩人的風格不同,卻都是才情充沛的年輕人,有好幾本詩集的封面都各有特色。我尤其喜歡散文集《寧靜的巨大》封面的感覺。在工作中,他們好像也能寬諒我的猶疑不決,知道我正在一個新的世紀裡努力去學習和適應呢。 最知道我的這種掙扎的是近幾年的主編靜怡。在電話裡,她的聲音總是平和舒緩。可是,在討論的時候,她卻常常會激發出我對創作的熱情而快樂起來,很溫暖的感覺,好像剛才曾經面對的困難已經不再是困難了。 想一想,在這超過三十年的時光裡,無論是畫一朵荷或者敘述幾匹馬,整個出版社都來給你護持和加持,卻從來沒給你任何壓力,總是任由你安靜而又緩慢地繼續寫下去,這是多麼難得的情誼啊! 如此厚賜,我深深感激。 輾轉的陳述 一九九二年五月下旬,蒙藏委員會在臺北的政治大學校區,舉行了一場「蒙古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中,哈勘楚倫教授以〈蒙古馬與馬文化〉為題,發表了一篇論文。 在談到蒙古馬特別強烈的方向感,以及眷戀故土的優異性向之時,他舉了一個真實的例子,讓我非常感動,會後不久就寫了一篇散文〈胡馬依北風〉。四年之後,又在一篇範圍比較大的散文裡加進了這匹馬的故事作為其中的一段。 現在,我想摘錄上面兩篇散文裡的不同段落,重新組合成我今天要敘述的「前篇」: 這則真「馬」真事,發生在六○年代中期的蒙古國(那時還叫做「蒙古人民共和國」)。當時的政府送了幾匹馬給南方的友邦越南政府作為禮物。 這幾匹馬是用專人專車護送到了目的地。可是,第二天早上,發現其中的一匹騸馬不見了,在附近搜尋了一陣也毫無所獲,只好向上級報告。幸好贈禮儀式已經舉行完畢,也就沒有再深加追究了。 半年之後,一匹又瘦又髒,蹄子上還帶著許多舊傷新痕的野馬,來到了烏蘭巴托城郊之外的牧場上。牧場主人一早起來,就看到了牠在遠遠的草地上站著,心想這到底是誰家走失了的馬,在那裡踟躕流連…… 想不到,靠近了之後,才發現這匹馬竟然在對著他流淚,大滴大滴的熱淚不斷滾落下來。雖然是又瘦又髒,不過,一個蒙古牧人是絕對會認出自己的馬來的。 驚詫激動的主人,在想明白了之後,更是忍不住抱著牠放聲大哭了。 想一想,這是多麼令人心疼的馬兒啊! 想一想,牠要走過多遠的路?要經過多少道關卡?不但要渡過長江,渡過黃河,還有那大大小小許多數不清的河道支流;不但要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峻嶺,還要在連綿起伏的丘陵間辨識方向;不但要經過江南阡陌縱橫的水田,還要獨自跋涉荒寒的戈壁;還有,最最不可思議的是,牠要如何躲過人類的好奇與貪欲? 在牠經過的這條不知有幾千幾萬里的長路上,難道從來沒遇到過任何的村鎮和城市?難道從來沒有人攔阻或是捕捉過牠嗎? 不可思議!牠是怎麼走回來的?半年的時間裡,在這條長路上,這匹馬受過多少磨難?牠是怎麼堅持下來的? 驚喜稍定,主人開始大宴賓客,向眾人展示這剛從天涯歸來的遊子。並且鄭重宣布,從此以後,這匹馬永遠不會離開家園,離開主人的身邊,再也不須工作,任何人都不可以騎乘牠,更不可讓牠受一丁點兒的委曲。 據說,這匹馬又活了許多年,才在家鄉的草原上老病而逝,想牠的靈魂一定能夠快樂地安息了吧。 故事到了這裡,算是有了個完美的結局。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反而會常常想起另外的那幾匹留在越南的馬兒來。會後,我再去追問了哈勘楚倫教授,到底是什麼在引導著蒙古馬往家鄉的方向走去?他回答我說: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總覺得應該是一種北方的氣息從風裡帶過來的吧?」 也許是這樣。 就像古詩裡的「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每個生命,都有他不同的選擇與不同的嚮往,有連他自己也無從解釋和抗拒的鄉愁。 因此,我就會常常想起那幾匹羈留在越南的蒙古馬來,當牠們年復一年在冬季迎著北風尋索著一種模糊的訊息時,心裡會有怎樣的悵惘和悲傷呢? 以上是我的「前篇」,從一九九二與一九九六兩個年分裡的兩篇散文摘錄而成的。 是的,時間已經過去很多年了,我從小喚他叔叔,向他問過很多問題的哈勘楚倫教授也已經逝去。可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他用「風中帶來的氣息」作為回答時那微帶歉意的笑容好像還在我眼前。 是的,生命的奧秘是難以解釋的。我想,他心中真正的回答應該就是這個意思吧? 今天的我,要寫的「後續」,也並非找到了答案,我只是在陳述事實而已。 我是從一九九三年夏天就認識了恩和教授的,他是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的教授,這兩年,我常常有機會向他請益。 去年(二○一四)秋天,我去呼和浩特的內蒙古博物院演講,然後和兩位朋友一起去拜訪他。他給我們講述游牧文化的歷史以及他在草原生活裡的親身感受,我們三個聽得都入迷了。 在這之間,他也談及蒙古馬的特殊稟賦,還舉了一個例子,他說: 我是從一本書裡讀到的。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蒙古的遊牧人》,作者是特木爾扎布先生,他是蒙古國的畜牧學家,也是科學院的院士。 在這本書裡,他引用了蒙古國一位頗負盛名,有著「人民畫家」封號的藝術家,貢布蘇榮先生的回憶錄中的一段。 貢布蘇榮在一九七一年,曾經應邀去越南參加了一次會議。那個時代,在共產國家裡,常有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藝術家召開的例會,每次輪流在一個不同的國家舉行,那年是在越南。 在會議之前,主辦單位邀請各國的代表先去一處海港城市散心。在這個城市的郊區,藝術家們隨意徜徉在空曠的草地上,有的就聚在一起閒聊,好增進彼此的認識。 遠遠看見一匹白馬在吃草,貢布蘇榮也沒特別在意。 他和幾位藝術家聚成一個小群體,其中有從俄羅斯來的,由於通俄語的緣故,聊得還很熱鬧。 但是,聊著聊著,有人就注意到了,那匹白馬忽然直直地朝向他們這群人走來,而且,目標似乎是對著貢布蘇榮。 再近前一些的時候,貢布蘇榮也看清楚了,這是一匹蒙古馬。毛色雖說是白,卻已髒汙,失去了光亮,馬身可說是骨瘦如柴。 這樣的一匹馬正對著他落淚。 儘管已經有人過來攔阻,白馬還是努力邁步往前,想要靠近貢布蘇榮。畫家那天穿著一身筆挺的西服,打著領帶,是以鄭重的心情來參與盛會的。可是,這匹馬好像也是下定了決心,非要來見貢布蘇榮不可。牠的力氣超乎尋常,眾人幾次攔阻都擋不住,終於給牠走到貢布蘇榮面前的時候,白馬的眼淚和鼻涕都沾到畫家的衣服上了。 不過,這時候的貢布蘇榮完全沒有在意,他的心中只有滿滿的疼惜,對眼前這匹傷心涕泣的蒙古馬,除了撫摸和輕拍牠的頸背,不知道要怎麼安慰牠才好。 「你是怎麼把我認出來的?你怎麼知道,我是從蒙古來的人呢?」 一九九五年,二十四年之後,貢布蘇榮在提筆寫這一段回憶之時,也是流著熱淚追想的。 是多麼令人疼惜的一匹好馬啊! 那天,恩和教授關於這個例子的講述就到此為止。我急著向他說出多年前哈勘楚倫教授舉出的那一個例子,不過,他告訴我,在上世紀六○年代裡,蒙古支援共產主義的越南,「贈馬」這樣的行動,應該有過好幾次。 所以,我並不能知道,這匹白馬,是否就是哈勘楚倫教授所說的那幾匹馬中的一匹。可是,牠的出現,卻可以讓我們明白,當年所有被送到越南,從此羈留在異鄉的每一匹蒙古馬兒的心情。 從牠身上,我們可以看見,一匹蒙古馬的大腦裡,藏著多麼深厚的感情與記憶,能把貢布蘇榮從人群之中辨認出來。 而這匹白馬如此奮力地向貢布蘇榮靠近,是希望這個從故鄉來的人,或許能帶自己回家嗎? 貢布蘇榮心中的疼痛與歉疚,想是因為他已完全明白了這匹馬的悲傷與冀望。可是,在當時的環境裡,他是怎麼也不可能把這匹馬帶回蒙古家鄉的。 所以,這種疼痛與歉疚始終沉在心底,使他在多年之後也不得不拿起筆來寫下這一次的相遇。是的,他沒能把白馬帶回來,可是,他還是可以把這一匹以及其他許多匹流落在異鄉的蒙古馬的悲傷,傳回到牠們的故鄉。 從六○年代中期到今天,已是整整的五十年了,無論是那匹回到家的馬,還是那些回不了家的,都早已不在人間。可是,在蒙古高原上,牠們的故事還一直在被眾人輾轉陳述,我想,轉述者的動機應該只有一種吧,那就是對如此高貴和勇敢的生命懷著極深的疼惜。 此刻,我也以同樣的心情和手中的這支筆,進入了這輾轉陳述者的行列,成為其中的一人了。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執筆的欲望
9折
特價441元
加入購物車
英雄時代
9折
特價360元
加入購物車
胡馬依北風
9折
特價333元
加入購物車
當夏夜芳馥:席慕蓉畫作精選集
9折
特價495元
加入購物車
我給記憶命名
9折
特價360元
加入購物車
除你之外
9折
特價315元
加入購物車
寫給海日汗的 21 封信
9折
特價342元
加入購物車
金色的馬鞍
9折
特價306元
加入購物車
回顧所來徑
9折
特價252元
加入購物車
給我一個島
9折
特價288元
加入購物車
晨讀10分鐘:青春無敵早點詩—中學生新詩選
9折
特價252元
貨到通知
大師說故事:蝸牛先生的名言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以詩之名
9折
特價315元
加入購物車
席慕蓉精選集
9折
特價342元
停售
寧靜的巨大
9折
特價261元
加入購物車
2006/席慕蓉(足本)
9折
特價405元
停售
2006/席慕蓉(7月-12月)
9折
特價288元
加入購物車
邊緣光影
9折
特價243元
加入購物車
迷途詩冊(32開)
9折
特價198元
加入購物車
時光九篇
9折
特價234元
加入購物車
我摺疊著我的愛
9折
特價216元
加入購物車
百年遊記II山.水.樓.園
9折
特價261元
貨到通知
席慕蓉.世紀詩選
9折
特價162元
加入購物車
無怨的青春
9折
特價189元
加入購物車
七里香
9折
特價189元
加入購物車
評論十家(第二集)
9折
特價162元
加入購物車
寫生者
9折
特價162元
加入購物車
江山有待
9折
特價198元
加入購物車
看更多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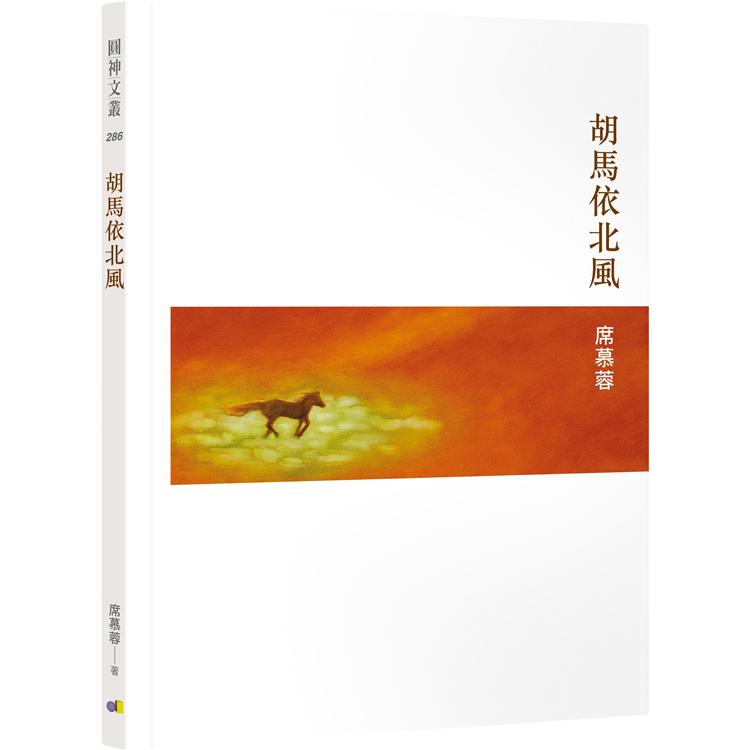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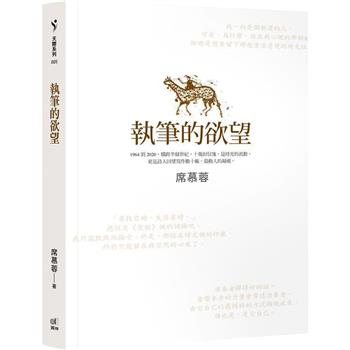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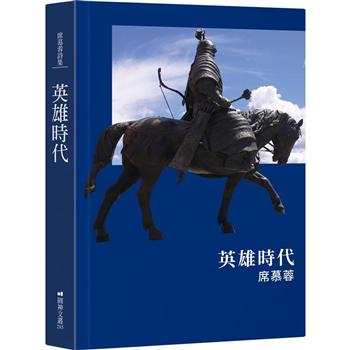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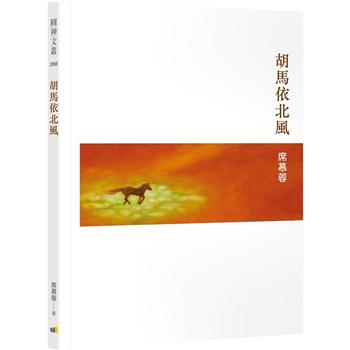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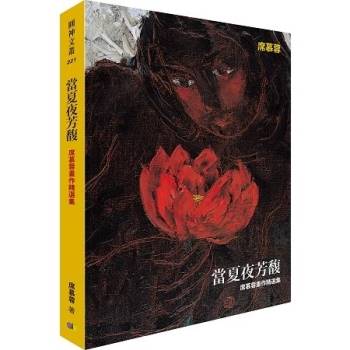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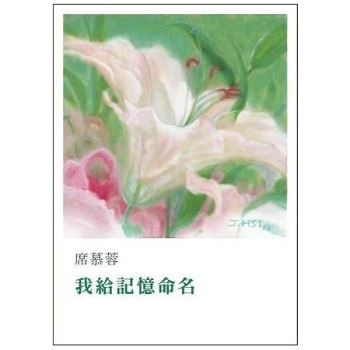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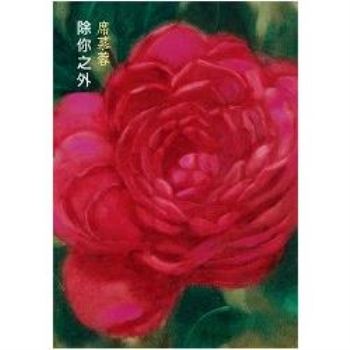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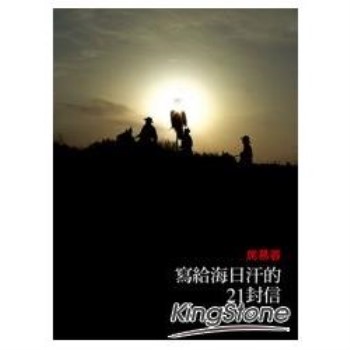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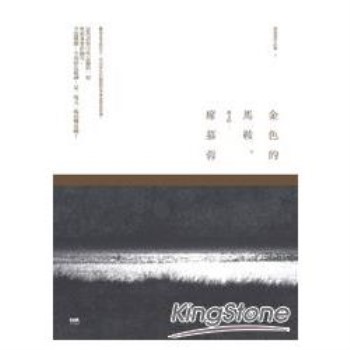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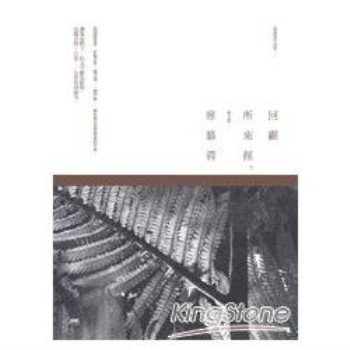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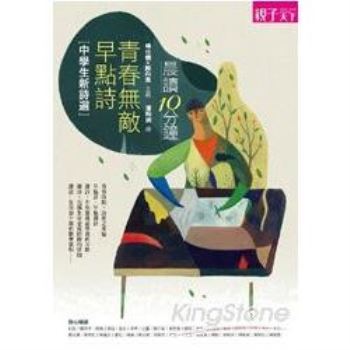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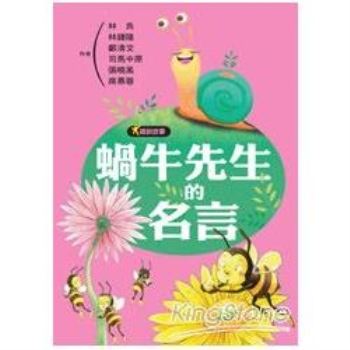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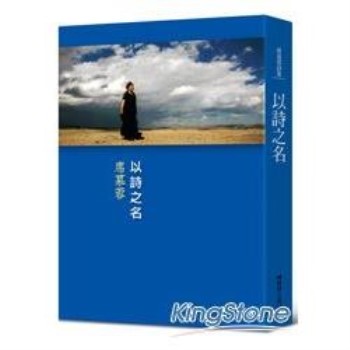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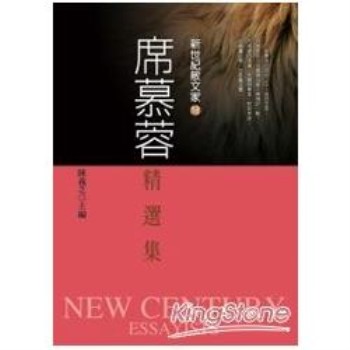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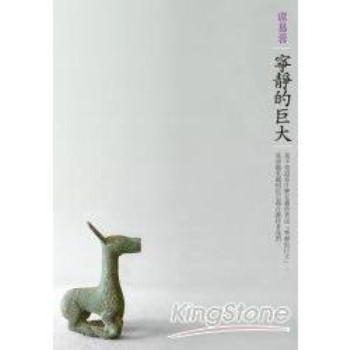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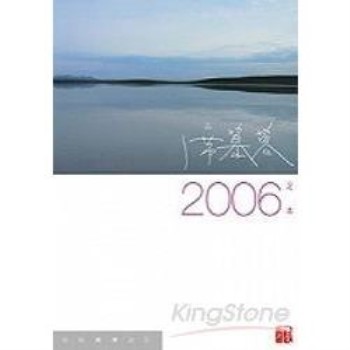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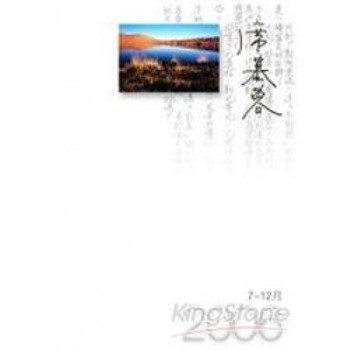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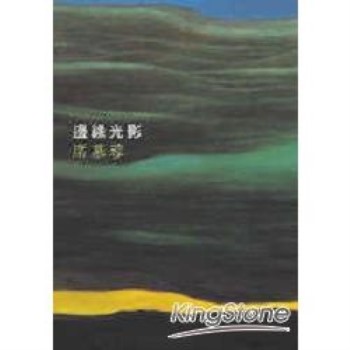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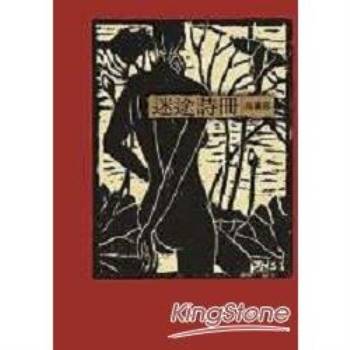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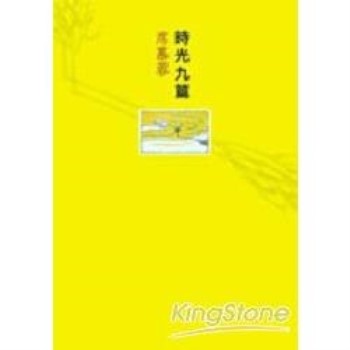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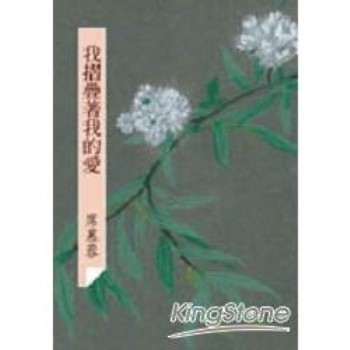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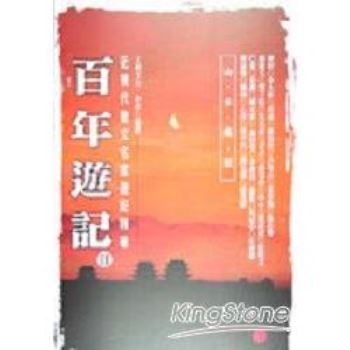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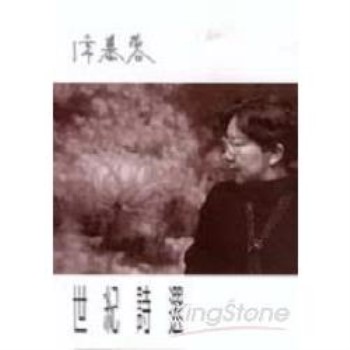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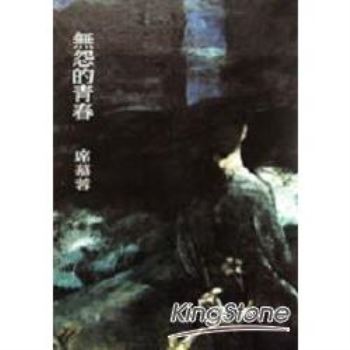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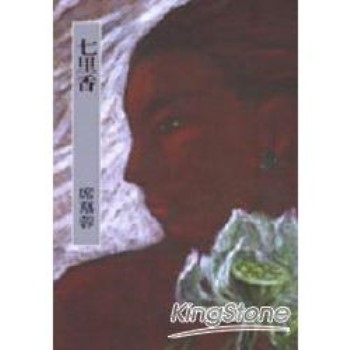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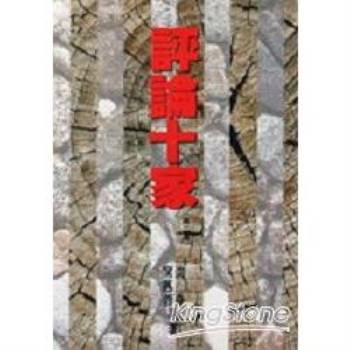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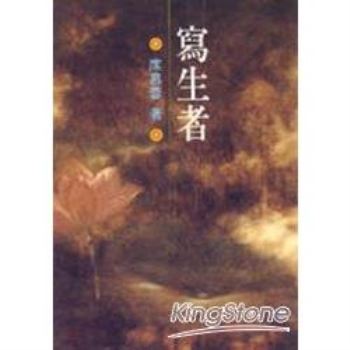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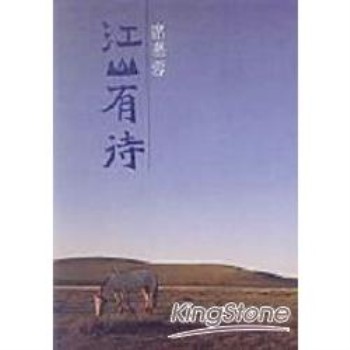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