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還有攝影家三叔公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他們的闖蕩與日常瑣碎,有時比大師傳奇更觸動人心
家族書寫 ╳ 攝影逸史 ╳ 李鳴鵰寫真 ╳ 沖印產業田野調查
★台北文學獎年金大奬★台灣文學金典獎 得主廖瞇
繼《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後,睽違五年,又見獨樹一幟之作
「對我爸媽來說,照相沖印是他們一輩子的工作,
而這一輩子的工作剛好也是沖印業的歷史。」——廖瞇
▌ 靠彩色沖印技術養大的女兒
▌ 竟對爸媽做了一輩子的工作一無所知
「在晚餐過後客人少的時候,一邊聽收音機一邊修片。他不急,一張一張慢慢來,眼角的皺紋,臉上的法令紋,那些細紋需要銳利的眼,穩當的手。阿美就沒法修片,她的手會抖。一張底片,小廖要修五到十分鐘,遇上畢業季,有時一天拍五十個,光是修片就得花上六、七小時。打烊後小廖拉下鐵門,繼續修,直到晚間十二點。」
一九七○年代,甫退伍的台北西門町青年小廖,與就讀大學夜校的宜蘭女孩阿美,同在天母的菱天大樓上班,兩人結識、相戀、結婚成家。之後憑藉在菱天習得的彩色沖印技術,闖南走北,開設手工放大的小工廠,頂下高雄的沖印店,趕上台灣彩色快速沖印連鎖店興盛時期;其間一度轉行種植香菇,遠赴中美洲多明尼加試身手……
小廖與阿美一路闖蕩拚搏,養活一雙子女。廖瞇透過訪談田調,記錄爸媽胼手胝足的歷程,寫下自己的歷史。當年燈下修片的身影,打相片機器嗡嗡嗡的聲響,俱化作女兒筆下文字的骨血與靈魂。
▌ 與張才、鄧南光並稱「攝影三劍客」
▌ 從少年修片師到創立沖印王國的李鳴鵰
「一九四六年,李鳴鵰在衡陽路上開設中美行時,本名鄧騰煇的鄧南光,也在同一條路上開了照相器材行,名為『南光』。張才的『影心』照相館則是在延平北路上。看著『南光』『影心』,再看『中美』,名字似乎反映了老闆的背景與性格。」
三叔公李鳴鵰原是從學徒做起的修片師,並因此接觸攝影。之後經過戰亂,遊歷於廣東、香港九龍,積累豐厚閱歷。戰後返台,李鳴鵰以〈牧羊童〉等作為人熟知,與張才、鄧南光並稱「攝影三劍客」。同時憑藉敏銳商業嗅覺,創立新中美,代理日本三菱相紙、軟片,之後設立菱天,再於快速沖印機引進後擴展為擁有兩百多家連鎖門市的「三上彩色沖印」。
橫跨攝影創作與照相沖印產業的李鳴鵰,是回溯小廖阿美生涯時一枚輝亮的名字,是台灣照相沖印產業的時代印記。李鳴鵰與小廖阿美參差對照,拼貼照映出產業的發展軌跡。
▌ 還記得消失在巷口的彩色沖印店嗎?
▌ 記述台灣照相沖印產業興衰史
「以前洗照片沒有門市,只有工廠,全台灣的底片都要寄到台北沖洗。『不急的坐火車,急的坐飛機,洗成照片再寄回來。』從前沒有快速沖印機,那時洗照片分成好幾台機器,每台機器都很大,一家公司有好幾個部門,上百人。」
柯達、富士、柯尼卡等多家軟片廠牌爭鳴;「它抓得住我」廣告宣傳詞響亮;照相館裡,一卷三十六張底片洗出後,小心翼翼一張張裝進附贈的小相本;加洗時,用蠟筆畫正字……。彩色沖印曾經如此深入我們的日常,數位時代來臨後卻又迅速消失,留下一段滿載共同記憶卻未曾被細究的逸史。
攝影不只是創作,更是生活記錄。本書訪談對象,除了小廖阿美,還涵括照相沖印產業不同時期、上下游各環節相關從業者,這些人大多不擁有攝影專業,大量沖洗的照片不屬於藝術殿堂,「但這些對他人不一定有意義的照片,我們卻會看著它笑、看著它哭。」
本書特色
✸ 平實中見深摯情感的家族書寫
✸ 記述時代夾縫間的庶民拚搏史
✸ 勾勒歷史洪流下的攝影家身影
✸ 爬梳台灣沖印產業的發展軌跡
名家推薦
朱和之 │ 作家
阮鳳儀 │ 導演
許俐葳 │ 小說家
陳佳琦 │ 嘉義市立美術館館長、攝影評論者
陳珊妮 │ 音樂人
黃宗潔 │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鄧九雲 │ 作家
盧郁佳 │ 作家
簡永彬 │ 攝影文化工作者
(按姓氏筆畫排序)
家族書寫 ╳ 攝影逸史 ╳ 李鳴鵰寫真 ╳ 沖印產業田野調查
★台北文學獎年金大奬★台灣文學金典獎 得主廖瞇
繼《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後,睽違五年,又見獨樹一幟之作
「對我爸媽來說,照相沖印是他們一輩子的工作,
而這一輩子的工作剛好也是沖印業的歷史。」——廖瞇
▌ 靠彩色沖印技術養大的女兒
▌ 竟對爸媽做了一輩子的工作一無所知
「在晚餐過後客人少的時候,一邊聽收音機一邊修片。他不急,一張一張慢慢來,眼角的皺紋,臉上的法令紋,那些細紋需要銳利的眼,穩當的手。阿美就沒法修片,她的手會抖。一張底片,小廖要修五到十分鐘,遇上畢業季,有時一天拍五十個,光是修片就得花上六、七小時。打烊後小廖拉下鐵門,繼續修,直到晚間十二點。」
一九七○年代,甫退伍的台北西門町青年小廖,與就讀大學夜校的宜蘭女孩阿美,同在天母的菱天大樓上班,兩人結識、相戀、結婚成家。之後憑藉在菱天習得的彩色沖印技術,闖南走北,開設手工放大的小工廠,頂下高雄的沖印店,趕上台灣彩色快速沖印連鎖店興盛時期;其間一度轉行種植香菇,遠赴中美洲多明尼加試身手……
小廖與阿美一路闖蕩拚搏,養活一雙子女。廖瞇透過訪談田調,記錄爸媽胼手胝足的歷程,寫下自己的歷史。當年燈下修片的身影,打相片機器嗡嗡嗡的聲響,俱化作女兒筆下文字的骨血與靈魂。
▌ 與張才、鄧南光並稱「攝影三劍客」
▌ 從少年修片師到創立沖印王國的李鳴鵰
「一九四六年,李鳴鵰在衡陽路上開設中美行時,本名鄧騰煇的鄧南光,也在同一條路上開了照相器材行,名為『南光』。張才的『影心』照相館則是在延平北路上。看著『南光』『影心』,再看『中美』,名字似乎反映了老闆的背景與性格。」
三叔公李鳴鵰原是從學徒做起的修片師,並因此接觸攝影。之後經過戰亂,遊歷於廣東、香港九龍,積累豐厚閱歷。戰後返台,李鳴鵰以〈牧羊童〉等作為人熟知,與張才、鄧南光並稱「攝影三劍客」。同時憑藉敏銳商業嗅覺,創立新中美,代理日本三菱相紙、軟片,之後設立菱天,再於快速沖印機引進後擴展為擁有兩百多家連鎖門市的「三上彩色沖印」。
橫跨攝影創作與照相沖印產業的李鳴鵰,是回溯小廖阿美生涯時一枚輝亮的名字,是台灣照相沖印產業的時代印記。李鳴鵰與小廖阿美參差對照,拼貼照映出產業的發展軌跡。
▌ 還記得消失在巷口的彩色沖印店嗎?
▌ 記述台灣照相沖印產業興衰史
「以前洗照片沒有門市,只有工廠,全台灣的底片都要寄到台北沖洗。『不急的坐火車,急的坐飛機,洗成照片再寄回來。』從前沒有快速沖印機,那時洗照片分成好幾台機器,每台機器都很大,一家公司有好幾個部門,上百人。」
柯達、富士、柯尼卡等多家軟片廠牌爭鳴;「它抓得住我」廣告宣傳詞響亮;照相館裡,一卷三十六張底片洗出後,小心翼翼一張張裝進附贈的小相本;加洗時,用蠟筆畫正字……。彩色沖印曾經如此深入我們的日常,數位時代來臨後卻又迅速消失,留下一段滿載共同記憶卻未曾被細究的逸史。
攝影不只是創作,更是生活記錄。本書訪談對象,除了小廖阿美,還涵括照相沖印產業不同時期、上下游各環節相關從業者,這些人大多不擁有攝影專業,大量沖洗的照片不屬於藝術殿堂,「但這些對他人不一定有意義的照片,我們卻會看著它笑、看著它哭。」
本書特色
✸ 平實中見深摯情感的家族書寫
✸ 記述時代夾縫間的庶民拚搏史
✸ 勾勒歷史洪流下的攝影家身影
✸ 爬梳台灣沖印產業的發展軌跡
名家推薦
朱和之 │ 作家
阮鳳儀 │ 導演
許俐葳 │ 小說家
陳佳琦 │ 嘉義市立美術館館長、攝影評論者
陳珊妮 │ 音樂人
黃宗潔 │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鄧九雲 │ 作家
盧郁佳 │ 作家
簡永彬 │ 攝影文化工作者
(按姓氏筆畫排序)
目錄
目次
推薦序 攝影如此庶民,故事不必偉大 陳佳琦
代自序
1 雖然李鳴鵰是我的三叔公
2 西門町的小廖,羅東的阿美
3 少年修片師李鳴鵰
4 「三菱彩色」那棟樓 〔BOX:沖印廠作業流程與生態〕
5 李鳴鵰在做什麼? 〔BOX:「攝影三劍客」傳說〕
6 小廖開「洋洋」,阿美當老闆娘 〔BOX:家庭工廠起家的器材師傅〕
7 他們還不知道,彩色沖印就要飛起來了 〔BOX:「抓得住我」的軟片們〕
8 小廖種菇
9 小廖繞了一圈後回台灣 〔BOX:小相本的祕密〕
10 小廖阿美終於開了自己的店
後記 跟小廖去暗房
註釋
附錄 李鳴鵰、小廖與阿美、彩色沖印發展對照年表
謝辭
推薦序 攝影如此庶民,故事不必偉大 陳佳琦
代自序
1 雖然李鳴鵰是我的三叔公
2 西門町的小廖,羅東的阿美
3 少年修片師李鳴鵰
4 「三菱彩色」那棟樓 〔BOX:沖印廠作業流程與生態〕
5 李鳴鵰在做什麼? 〔BOX:「攝影三劍客」傳說〕
6 小廖開「洋洋」,阿美當老闆娘 〔BOX:家庭工廠起家的器材師傅〕
7 他們還不知道,彩色沖印就要飛起來了 〔BOX:「抓得住我」的軟片們〕
8 小廖種菇
9 小廖繞了一圈後回台灣 〔BOX:小相本的祕密〕
10 小廖阿美終於開了自己的店
後記 跟小廖去暗房
註釋
附錄 李鳴鵰、小廖與阿美、彩色沖印發展對照年表
謝辭
序/導讀
代自序
先是聲音,而後是畫面。
媽媽坐在一台機器前,她左手拿底片,右手在鍵盤上按啊按,此時會聽到啪嗒一聲,然後閃光,啪嗒,閃光,左手的底片就這樣一秒一下移動到右邊。接著是一條長長的照片,像河一樣從機器的尾巴吐出,然後喀嚓、喀嚓,變成一張張照片掉落。
這是我對洗照片最早的記憶。一九八六年,我九歲。我在媽媽上班的彩色沖印店,盯著那台機器吐出照片。才九歲的我還沒想到要問,機器裡面發生了什麼魔法,可以把底片的影像變成照片,但有著另一個疑惑。
店門口貼著「彩色快速沖印」「四十分鐘快速交件」的字樣。我覺得很奇怪,四十分鐘很久啊,是一堂課的時間,四十分鐘明明沒有很快,為什麼要叫做「快速」沖印?
讀高中時,爸媽終於開了自己的店,門口仍有著「快速沖印」四個大字。店開了十二年,最終不敵數位沖印,爸媽決定退休將店面頂讓出去。我看著快速沖印那四個字,第一次問了擺在心裡許久的疑問。
「四十分鐘有很快嗎?」
「喔,因為以前要花更久的時間啊。」
以前洗照片沒有門市,只有工廠,全台灣的底片都要寄到台北沖洗。爸爸說得很輕鬆,我卻有點聽不懂。從前沒有門市?底片全都寄到台北沖洗?那不就要好幾天?
「對啊,不急的坐火車,急的坐飛機,洗成照片再寄回來。」媽媽說。
爸爸繼續說,從前沒有快速沖印機,那時洗照片分成好幾台機器,沖洗底片的一台,打相片的一台,沖洗相紙的一台,烘乾的一台,再人工裁切。「每台機器都很大,一家公司有好幾個部門,上百人。」爸爸翻開相簿指著一張團照。我看著照片,找著爸爸媽媽,他們的臉在團照中變得很小,但仍舊能夠分辨。公司員工在大樓前合影,大大的字寫著「菱天大樓」。
突然意識到,我是他們用洗照片養大的,卻對他們的工作一無所知。
◎
有記憶以來,媽媽就在洗照片,她一直坐在沖印機前打相片。而爸爸是拍照、修片、設定沖印機、換相紙、換藥水補充藥水、跑外務收件送件。一家沖印店只要兩個人就能撐起來,我沒想過在三十年前,洗照片是以工廠的形式存在。在某件專業上,從年輕做到老,在日文中稱為職人。但若用職人來稱呼我媽,她可能會說,什麼職人不職人,有一份工作可以做到老,很好啊。媽媽從讀大學夜校時進入菱天打工,到自己開店,一做三十四年。她的手拿過多少支底片?打過多少張照片呢?彩色沖印的黃金期,一天至少可以沖一百支底片,一支底片三十六張,一天是三千六百張。這樣乘一乘加一加,媽媽的一生,說是打過上千萬張照片並不為過。
而爸爸是高工畢業,進菱天打工,後來成為手工沖洗組的組長。快速沖印機出現後,傳統大型沖印廠逐漸轉型成連鎖快速沖印店,他被派駐各家門市協助機器設定。曾因想自己創業,三進三出,也跟過堂哥去到多明尼加開店。我看著爸爸的一生,他不使用手機,不會用手機拍照,這個曾經一天拍五十組證件照的他,「啵!」一聲就能抓住最佳表情的他,當我拿著手機請他幫忙拍照,他總是說,「我是手機白癡」「不要不要」。
看著菱天大樓的團照,看著照片中的爸爸與媽媽,第一次,我對這張泛黃的照片有了好奇。我仔細端詳,第一排的中位,是個西裝筆挺的長輩。爸爸指著他說,這是爸爸的老闆,也是你的三叔公。
「你三叔公叫李鳴鵰,是個攝影家。」
爸爸的老闆就是我們的親戚?而且是個攝影家?等等,為什麼我們姓廖,三叔公姓李?
◎
「你的阿祖姓李,他給姓廖的『招』。阿祖生的第一個兒子要跟廖家姓廖,就是你阿公。第二個兒子跟你阿祖姓李。」爸爸說。
我一邊聽爸爸說,一邊 Google「李鳴鵰」:
「一九二二年出生於桃園縣大溪鎮的李鳴鵰,與鄧南光、張才是台灣攝影史中最為人稱道的光影先行者,三人以不同的寫實風格在四、五○年代獨領風騷,他們經常參與展覽與評審,提攜後進不遺餘力,被攝影界尊稱為『快門三劍客』。」
接著是一張名為〈牧羊童〉的照片,然後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我盯著那張臉,覺得有點眼熟。
「我認得這個人耶,這個人買過書給我。」
◎
我見過李鳴鵰一面。
為什麼會在李鳴鵰家住一晚,我已經忘了,好像是祖母帶我們去。雖然不記得原因,但記得他家很大,獨棟的別墅。媽媽說怎麼可能,她怎麼都不知道?「你會不會記錯了?」媽媽說,我們很少跟親戚往來,「而且我們住高雄,三叔公住天母,你們是什麼時候去的?」我說我跟弟弟真的去過他家,「我還記得隔天他帶我們去書店,說要買書給我們。」
三叔公說,一個人可以挑兩本。我心想這個人好好喔。不知是否是日後的腦補,腦袋裡有著三叔公站在書架前彎著腰,推開眼鏡瀏覽書籍的畫面。我繞了書架一圈,挑了《野性的呼喚》。雖然想再挑一本,可是不好意思,一時也不知道該怎麼挑。最後,三叔公自己選了一本書給我,是賽珍珠的《大地》。至今我還記得那本書的封面,一個中年女子畫像的鉛筆素描。
問弟弟對這件事有印象嗎?他從書架取了本書:「我的是《拍案驚奇》。」
有弟弟的佐證,我確定這記憶不是杜撰。而當時還是國中生的我並不知道,眼前的三叔公是個攝影家,他對我來說就是個和藹可親的長輩。
「你三叔公很喜歡攝影,後來他叫你五叔公去日本學沖印技術。那台快速沖印機就是他們公司代理的。」爸爸說。
三叔公是因為喜歡攝影,所以跨足沖印業?可是印象中我的父系家族並不富有,三叔公是在什麼情況下接觸攝影?
我對這個只見過一次面,現已不在世的三叔公,起了興趣。
先是聲音,而後是畫面。
媽媽坐在一台機器前,她左手拿底片,右手在鍵盤上按啊按,此時會聽到啪嗒一聲,然後閃光,啪嗒,閃光,左手的底片就這樣一秒一下移動到右邊。接著是一條長長的照片,像河一樣從機器的尾巴吐出,然後喀嚓、喀嚓,變成一張張照片掉落。
這是我對洗照片最早的記憶。一九八六年,我九歲。我在媽媽上班的彩色沖印店,盯著那台機器吐出照片。才九歲的我還沒想到要問,機器裡面發生了什麼魔法,可以把底片的影像變成照片,但有著另一個疑惑。
店門口貼著「彩色快速沖印」「四十分鐘快速交件」的字樣。我覺得很奇怪,四十分鐘很久啊,是一堂課的時間,四十分鐘明明沒有很快,為什麼要叫做「快速」沖印?
讀高中時,爸媽終於開了自己的店,門口仍有著「快速沖印」四個大字。店開了十二年,最終不敵數位沖印,爸媽決定退休將店面頂讓出去。我看著快速沖印那四個字,第一次問了擺在心裡許久的疑問。
「四十分鐘有很快嗎?」
「喔,因為以前要花更久的時間啊。」
以前洗照片沒有門市,只有工廠,全台灣的底片都要寄到台北沖洗。爸爸說得很輕鬆,我卻有點聽不懂。從前沒有門市?底片全都寄到台北沖洗?那不就要好幾天?
「對啊,不急的坐火車,急的坐飛機,洗成照片再寄回來。」媽媽說。
爸爸繼續說,從前沒有快速沖印機,那時洗照片分成好幾台機器,沖洗底片的一台,打相片的一台,沖洗相紙的一台,烘乾的一台,再人工裁切。「每台機器都很大,一家公司有好幾個部門,上百人。」爸爸翻開相簿指著一張團照。我看著照片,找著爸爸媽媽,他們的臉在團照中變得很小,但仍舊能夠分辨。公司員工在大樓前合影,大大的字寫著「菱天大樓」。
突然意識到,我是他們用洗照片養大的,卻對他們的工作一無所知。
◎
有記憶以來,媽媽就在洗照片,她一直坐在沖印機前打相片。而爸爸是拍照、修片、設定沖印機、換相紙、換藥水補充藥水、跑外務收件送件。一家沖印店只要兩個人就能撐起來,我沒想過在三十年前,洗照片是以工廠的形式存在。在某件專業上,從年輕做到老,在日文中稱為職人。但若用職人來稱呼我媽,她可能會說,什麼職人不職人,有一份工作可以做到老,很好啊。媽媽從讀大學夜校時進入菱天打工,到自己開店,一做三十四年。她的手拿過多少支底片?打過多少張照片呢?彩色沖印的黃金期,一天至少可以沖一百支底片,一支底片三十六張,一天是三千六百張。這樣乘一乘加一加,媽媽的一生,說是打過上千萬張照片並不為過。
而爸爸是高工畢業,進菱天打工,後來成為手工沖洗組的組長。快速沖印機出現後,傳統大型沖印廠逐漸轉型成連鎖快速沖印店,他被派駐各家門市協助機器設定。曾因想自己創業,三進三出,也跟過堂哥去到多明尼加開店。我看著爸爸的一生,他不使用手機,不會用手機拍照,這個曾經一天拍五十組證件照的他,「啵!」一聲就能抓住最佳表情的他,當我拿著手機請他幫忙拍照,他總是說,「我是手機白癡」「不要不要」。
看著菱天大樓的團照,看著照片中的爸爸與媽媽,第一次,我對這張泛黃的照片有了好奇。我仔細端詳,第一排的中位,是個西裝筆挺的長輩。爸爸指著他說,這是爸爸的老闆,也是你的三叔公。
「你三叔公叫李鳴鵰,是個攝影家。」
爸爸的老闆就是我們的親戚?而且是個攝影家?等等,為什麼我們姓廖,三叔公姓李?
◎
「你的阿祖姓李,他給姓廖的『招』。阿祖生的第一個兒子要跟廖家姓廖,就是你阿公。第二個兒子跟你阿祖姓李。」爸爸說。
我一邊聽爸爸說,一邊 Google「李鳴鵰」:
「一九二二年出生於桃園縣大溪鎮的李鳴鵰,與鄧南光、張才是台灣攝影史中最為人稱道的光影先行者,三人以不同的寫實風格在四、五○年代獨領風騷,他們經常參與展覽與評審,提攜後進不遺餘力,被攝影界尊稱為『快門三劍客』。」
接著是一張名為〈牧羊童〉的照片,然後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我盯著那張臉,覺得有點眼熟。
「我認得這個人耶,這個人買過書給我。」
◎
我見過李鳴鵰一面。
為什麼會在李鳴鵰家住一晚,我已經忘了,好像是祖母帶我們去。雖然不記得原因,但記得他家很大,獨棟的別墅。媽媽說怎麼可能,她怎麼都不知道?「你會不會記錯了?」媽媽說,我們很少跟親戚往來,「而且我們住高雄,三叔公住天母,你們是什麼時候去的?」我說我跟弟弟真的去過他家,「我還記得隔天他帶我們去書店,說要買書給我們。」
三叔公說,一個人可以挑兩本。我心想這個人好好喔。不知是否是日後的腦補,腦袋裡有著三叔公站在書架前彎著腰,推開眼鏡瀏覽書籍的畫面。我繞了書架一圈,挑了《野性的呼喚》。雖然想再挑一本,可是不好意思,一時也不知道該怎麼挑。最後,三叔公自己選了一本書給我,是賽珍珠的《大地》。至今我還記得那本書的封面,一個中年女子畫像的鉛筆素描。
問弟弟對這件事有印象嗎?他從書架取了本書:「我的是《拍案驚奇》。」
有弟弟的佐證,我確定這記憶不是杜撰。而當時還是國中生的我並不知道,眼前的三叔公是個攝影家,他對我來說就是個和藹可親的長輩。
「你三叔公很喜歡攝影,後來他叫你五叔公去日本學沖印技術。那台快速沖印機就是他們公司代理的。」爸爸說。
三叔公是因為喜歡攝影,所以跨足沖印業?可是印象中我的父系家族並不富有,三叔公是在什麼情況下接觸攝影?
我對這個只見過一次面,現已不在世的三叔公,起了興趣。
試閱
2 西門町的小廖,羅東的阿美
問媽媽寫到她,要叫她什麼呢?阿美好了,「阿bí。」台語發音。阿美,一九五三年生,「小時候大家都叫我阿美。」家裡有五個小孩,她是中間那一個,「連我弟都叫我阿美。」阿美出生在宜蘭羅東,小時習舞,獲獎無數,這是後來我看照片才知道的,如果沒有照片,我大概不會相信媽媽以前跳舞。
「我跳舞很認真啊,常常跳主角。」阿美說。認真就可以跳到主角?我還以為跳舞比較看天分。我看著媽媽跳舞時的裝扮,「這是跳民俗舞蹈嗎?」「可以這樣講吧。」阿美說。
家裡的阿美相本,有小時候的,上台北讀書工作的。小時照片都是黑白照,尺寸不一,不像後來彩色沖印時期都是三乘五或四乘六那樣整齊。阿美真的很會整理東西,想想她小時住羅東,大學上台北,後來跟我爸結婚,搬到高雄,生我時回台北,沒多久去羅東,之後又下高雄工作,再跟著我爸去台南種菇,最後搬回高雄。這樣前前後後奔奔波波,她小時候的照片都還留得好好的,不僅還在,且全數整理到精裝大相本裡。
而小廖幾乎沒有小時照片。我爸說可以叫他「小廖」,「我們家四個男生嘛,我最小,大家就叫我小廖。」小廖,一九五○年生,老家在台北西門町,近今日紅樓。原本以為小廖有個開設照相材料行的三叔李鳴鵰,洗照片容易也便宜,他的照片應該不少,但並沒有。
從前對小廖的想像是:因為喜歡拍照,所以走上沖洗照片這途。結果小廖說,他去三叔的公司上班之前,沒有拿過相機,他是先學會了沖洗照片,才開始拍照。原來小廖跟李鳴鵰一樣,李鳴鵰是先學會了修片,開始賺錢存到錢之後,才為自己買了台雙眼相機。
「以前相機很貴啊。」小廖說他第一台相機也是雙眼,一台三千多,牌子忘了。一九七○年代的三千多,大約是小廖一個月的薪水。單眼相機就更貴了,他的第一台單眼是奇農(Chinon),一台要一萬多塊錢。
不是因為喜歡拍照,才去學沖洗,而是先學會了沖洗,對拍照有了一點興趣,有經濟能力後才買相機來拍。但也不是接觸沖洗這行的人,都會對拍照感興趣。像阿美,印象中沒看過她拍照,阿美雖然洗了一輩子的照片,但她會使用單眼相機嗎?我以為阿美不會,結果一問,阿美說,有學過,但不熟練。我太小看阿美了,畢竟阿美年輕時還沒有傻瓜相機,想拍照只能用單眼。既然都在沖印公司工作了,就算平常沒拿相機,但對相機的基本概念還是有的,我怎麼會覺得阿美不會用單眼相機呢?
阿美去沖印公司上班前,打過許多工。她大學讀夜間部,白天工作,晚上讀書。阿美跟同鄉的國中同學在外租屋,房間很小,是房間裡的房間,要爬木梯子上去,「我才一百五十五公分,但上去之後也只能彎腰,不然會頂到天花板。」阿美說的時候,一種媽媽以前好辛苦你知道嗎的感覺,學費生活費都要自己來,只能住在連腰都站不直的閣樓。
一九七二年,政府推動「客廳即工廠」政策,阿美和幾個蘭陽女中畢業的同學,也做過這種家庭代工,「做清潔液分裝,大家在業主的一間空房,把一大桶成品分裝成小瓶小瓶。工作很單調,但一起打工聊天很有趣。」後來外公幫忙牽線,阿美到貿易公司當小妹,可是主管會毛手毛腳,阿美又不敢講,「做了一陣子之後,我說做不習慣,你阿公就再幫我問別的工作,最後到菱天上班。」
菱天,就是三叔公李鳴鵰的沖印公司。安排媽媽到菱天上班的,是五叔公廖名雁。五叔公跟外公是師專同學。
廖名雁,一九二六年生。師專畢業後當小學老師,兩年後被派到台北市教育局做教育行政。過沒多久,李鳴鵰對廖名雁說,「你做公務員賺不到錢啦,賺不到錢賺不到吃,我這裡需要人,你來我這裡。」當時李鳴鵰正開始跟日本三菱(Mitsubishi)做生意,他希望廖名雁去日本受訓,回來幫他。
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廖名雁,日語說得比國語好。我看「臺灣傑出攝影家紀錄片—李鳴鵰」,聽著這個未曾謀面的五叔公說話,他說的是國語,但聽得出那個口音,平常應該是說台語。他講話講一講,有時會說,「那個國語怎麼講……」五叔公說話的聲音、速度、氣質,都跟外公好像。那個年代受日本師範教育的人,是不是都有一種溫儒的氣質?
「後來我就跟我哥哥在一起,從那裡開始到現在,就是這個緣分還在。」廖名雁說「在一起」時,我覺得這個詞好美。有多少人能跟自己的兄弟或姊妹一直在一起呢?長大後分開是自然,更有的是相敬如冰互不往來。而廖名雁從李鳴鵰做照相沖印器材生意開始,當時兩人都還不滿三十歲,一直在李鳴鵰公司直到退休,再到在紀錄片中回憶哥哥。
每次小廖和阿美提起廖名雁,都會說,你五叔公人真的很好。這個好比起三叔公李鳴鵰更立體。我問小廖,三叔公教過你什麼?結果小廖每次講,最後都在講廖名雁,「五叔教我切相紙、放大、改色,教我沖片,我會的都是五叔教的。」問到阿美也是一樣,「廖名雁是總經理,公司是他在管事。我好像很少看到你三叔公。」「你五叔公個性就是很溫和啊,跟外公很像。我沒有看過他兇員工。」
李鳴鵰派廖名雁去日本京都受訓,實習三個月,學習彩色沖印原理、沖洗照片,「回來就買機器,後來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我哥工作都交給我,所有工作都交給我,他有閒啦,常常相機帶了就出去拍照。」廖名雁提到他哥時,呵呵呵地笑。
有張照片,擔任總經理的廖名雁和兩個公司職員打著領帶,他穿著卡其色制服外套,在菱天大樓大門前,站得很正,看起來拘謹又老派。
小廖成淵中學畢業後,考上北市高工機械科,也就是現在的大安高工,在復興南路上。「我不喜歡讀書啊,不像我們學校對面的附中。」「畢業後五叔說他缺人,我就去那邊當學徒。」那時是一九六九年,小廖十九歲。
「你剛開始學彩色沖印時,感覺是什麼?你有覺得這很新奇、很有趣嗎?」我問小廖。小廖想了一下,說,都很順。我說不是要問順不順啦,是想知道你心裡的感覺,比如會覺得很難嗎?或是,你喜歡這個工作嗎?
小廖說喜歡啊。「喜歡什麼?」我問。
「因為那時候也只能做這個啊。」小廖說。過了一會又說,因為很驕傲,非常驕傲。「那時候的國小老師,一個月薪水只有兩千八,我一個小師傅就有一萬。」
一九六八年的台灣,基本月薪六百元,而小廖在一九六九年當學徒時,月薪一千元,當時他才十九歲。一九七四年小廖當兵退伍,回菱天上班,正職員工薪水調至三千元,過沒多久又加薪至三千五百元。之後菱天與高雄的照相器材行合夥成立沖印公司,派小廖下去擔任手工組組長,月薪一萬元。而台灣的基本薪資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調至二千四百元。就算不以基本薪資來看,而是看平均薪資:一九七四年的國民平均所得,一個月是二千六百八十三元,小廖的薪水幾乎是當時平均月薪的四倍,那時他才二十四歲。
小廖的回答令我感覺微妙。一開始他說,那時候只能做這個啊,好像沒有什麼好選,遇到了就做,就要喜歡。接著他似乎想起這份工作高薪所帶來的成就感,有一種―雖然我學歷不怎麼樣,但薪水待遇可不輸老師喔,這樣的感覺,「我覺得有一技之長很好,而且在當時是很新的技術。」小廖說。
我感覺到小廖的樂天,但並不明白他真正的感受。小廖不太會講,他不太會說自己。但阿美會講。阿美說,起初她沒有那麼喜歡這份工作,「剛進公司時,被安排在技術部門,但學技術沒那麼簡單,要學怎麼在暗房裝紙,還有藥水什麼的,我覺得很難。」阿美喜歡做行政,行政工作她可以做得很好,而技術部門要學的東西很多,承擔的責任也比較大,「可是我的個性不會去表達我不喜歡,既然被安排進技術部門,我就認命好好學好好做。」
但阿美說,還好當初有學這些,「這樣後來才可以跟你老爸一起開店。」
曾經採訪維修相機的師傅,我問他為什麼做這行呢?他聽到時愣了一下,那反應像是「這是什麼問題?」「這要怎麼回答?」師傅想了一下說,那時候出路沒有很多啊,「要不工廠工作,不然就當學徒,除非你念書念得很好,或是家境不錯可以培養。」「我是跟我大哥學,我大哥是跟一個 Canon 的師傅學。」一副理所當然,哪有什麼為什麼。
(未完待續)
問媽媽寫到她,要叫她什麼呢?阿美好了,「阿bí。」台語發音。阿美,一九五三年生,「小時候大家都叫我阿美。」家裡有五個小孩,她是中間那一個,「連我弟都叫我阿美。」阿美出生在宜蘭羅東,小時習舞,獲獎無數,這是後來我看照片才知道的,如果沒有照片,我大概不會相信媽媽以前跳舞。
「我跳舞很認真啊,常常跳主角。」阿美說。認真就可以跳到主角?我還以為跳舞比較看天分。我看著媽媽跳舞時的裝扮,「這是跳民俗舞蹈嗎?」「可以這樣講吧。」阿美說。
家裡的阿美相本,有小時候的,上台北讀書工作的。小時照片都是黑白照,尺寸不一,不像後來彩色沖印時期都是三乘五或四乘六那樣整齊。阿美真的很會整理東西,想想她小時住羅東,大學上台北,後來跟我爸結婚,搬到高雄,生我時回台北,沒多久去羅東,之後又下高雄工作,再跟著我爸去台南種菇,最後搬回高雄。這樣前前後後奔奔波波,她小時候的照片都還留得好好的,不僅還在,且全數整理到精裝大相本裡。
而小廖幾乎沒有小時照片。我爸說可以叫他「小廖」,「我們家四個男生嘛,我最小,大家就叫我小廖。」小廖,一九五○年生,老家在台北西門町,近今日紅樓。原本以為小廖有個開設照相材料行的三叔李鳴鵰,洗照片容易也便宜,他的照片應該不少,但並沒有。
從前對小廖的想像是:因為喜歡拍照,所以走上沖洗照片這途。結果小廖說,他去三叔的公司上班之前,沒有拿過相機,他是先學會了沖洗照片,才開始拍照。原來小廖跟李鳴鵰一樣,李鳴鵰是先學會了修片,開始賺錢存到錢之後,才為自己買了台雙眼相機。
「以前相機很貴啊。」小廖說他第一台相機也是雙眼,一台三千多,牌子忘了。一九七○年代的三千多,大約是小廖一個月的薪水。單眼相機就更貴了,他的第一台單眼是奇農(Chinon),一台要一萬多塊錢。
不是因為喜歡拍照,才去學沖洗,而是先學會了沖洗,對拍照有了一點興趣,有經濟能力後才買相機來拍。但也不是接觸沖洗這行的人,都會對拍照感興趣。像阿美,印象中沒看過她拍照,阿美雖然洗了一輩子的照片,但她會使用單眼相機嗎?我以為阿美不會,結果一問,阿美說,有學過,但不熟練。我太小看阿美了,畢竟阿美年輕時還沒有傻瓜相機,想拍照只能用單眼。既然都在沖印公司工作了,就算平常沒拿相機,但對相機的基本概念還是有的,我怎麼會覺得阿美不會用單眼相機呢?
阿美去沖印公司上班前,打過許多工。她大學讀夜間部,白天工作,晚上讀書。阿美跟同鄉的國中同學在外租屋,房間很小,是房間裡的房間,要爬木梯子上去,「我才一百五十五公分,但上去之後也只能彎腰,不然會頂到天花板。」阿美說的時候,一種媽媽以前好辛苦你知道嗎的感覺,學費生活費都要自己來,只能住在連腰都站不直的閣樓。
一九七二年,政府推動「客廳即工廠」政策,阿美和幾個蘭陽女中畢業的同學,也做過這種家庭代工,「做清潔液分裝,大家在業主的一間空房,把一大桶成品分裝成小瓶小瓶。工作很單調,但一起打工聊天很有趣。」後來外公幫忙牽線,阿美到貿易公司當小妹,可是主管會毛手毛腳,阿美又不敢講,「做了一陣子之後,我說做不習慣,你阿公就再幫我問別的工作,最後到菱天上班。」
菱天,就是三叔公李鳴鵰的沖印公司。安排媽媽到菱天上班的,是五叔公廖名雁。五叔公跟外公是師專同學。
廖名雁,一九二六年生。師專畢業後當小學老師,兩年後被派到台北市教育局做教育行政。過沒多久,李鳴鵰對廖名雁說,「你做公務員賺不到錢啦,賺不到錢賺不到吃,我這裡需要人,你來我這裡。」當時李鳴鵰正開始跟日本三菱(Mitsubishi)做生意,他希望廖名雁去日本受訓,回來幫他。
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廖名雁,日語說得比國語好。我看「臺灣傑出攝影家紀錄片—李鳴鵰」,聽著這個未曾謀面的五叔公說話,他說的是國語,但聽得出那個口音,平常應該是說台語。他講話講一講,有時會說,「那個國語怎麼講……」五叔公說話的聲音、速度、氣質,都跟外公好像。那個年代受日本師範教育的人,是不是都有一種溫儒的氣質?
「後來我就跟我哥哥在一起,從那裡開始到現在,就是這個緣分還在。」廖名雁說「在一起」時,我覺得這個詞好美。有多少人能跟自己的兄弟或姊妹一直在一起呢?長大後分開是自然,更有的是相敬如冰互不往來。而廖名雁從李鳴鵰做照相沖印器材生意開始,當時兩人都還不滿三十歲,一直在李鳴鵰公司直到退休,再到在紀錄片中回憶哥哥。
每次小廖和阿美提起廖名雁,都會說,你五叔公人真的很好。這個好比起三叔公李鳴鵰更立體。我問小廖,三叔公教過你什麼?結果小廖每次講,最後都在講廖名雁,「五叔教我切相紙、放大、改色,教我沖片,我會的都是五叔教的。」問到阿美也是一樣,「廖名雁是總經理,公司是他在管事。我好像很少看到你三叔公。」「你五叔公個性就是很溫和啊,跟外公很像。我沒有看過他兇員工。」
李鳴鵰派廖名雁去日本京都受訓,實習三個月,學習彩色沖印原理、沖洗照片,「回來就買機器,後來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我哥工作都交給我,所有工作都交給我,他有閒啦,常常相機帶了就出去拍照。」廖名雁提到他哥時,呵呵呵地笑。
有張照片,擔任總經理的廖名雁和兩個公司職員打著領帶,他穿著卡其色制服外套,在菱天大樓大門前,站得很正,看起來拘謹又老派。
小廖成淵中學畢業後,考上北市高工機械科,也就是現在的大安高工,在復興南路上。「我不喜歡讀書啊,不像我們學校對面的附中。」「畢業後五叔說他缺人,我就去那邊當學徒。」那時是一九六九年,小廖十九歲。
「你剛開始學彩色沖印時,感覺是什麼?你有覺得這很新奇、很有趣嗎?」我問小廖。小廖想了一下,說,都很順。我說不是要問順不順啦,是想知道你心裡的感覺,比如會覺得很難嗎?或是,你喜歡這個工作嗎?
小廖說喜歡啊。「喜歡什麼?」我問。
「因為那時候也只能做這個啊。」小廖說。過了一會又說,因為很驕傲,非常驕傲。「那時候的國小老師,一個月薪水只有兩千八,我一個小師傅就有一萬。」
一九六八年的台灣,基本月薪六百元,而小廖在一九六九年當學徒時,月薪一千元,當時他才十九歲。一九七四年小廖當兵退伍,回菱天上班,正職員工薪水調至三千元,過沒多久又加薪至三千五百元。之後菱天與高雄的照相器材行合夥成立沖印公司,派小廖下去擔任手工組組長,月薪一萬元。而台灣的基本薪資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調至二千四百元。就算不以基本薪資來看,而是看平均薪資:一九七四年的國民平均所得,一個月是二千六百八十三元,小廖的薪水幾乎是當時平均月薪的四倍,那時他才二十四歲。
小廖的回答令我感覺微妙。一開始他說,那時候只能做這個啊,好像沒有什麼好選,遇到了就做,就要喜歡。接著他似乎想起這份工作高薪所帶來的成就感,有一種―雖然我學歷不怎麼樣,但薪水待遇可不輸老師喔,這樣的感覺,「我覺得有一技之長很好,而且在當時是很新的技術。」小廖說。
我感覺到小廖的樂天,但並不明白他真正的感受。小廖不太會講,他不太會說自己。但阿美會講。阿美說,起初她沒有那麼喜歡這份工作,「剛進公司時,被安排在技術部門,但學技術沒那麼簡單,要學怎麼在暗房裝紙,還有藥水什麼的,我覺得很難。」阿美喜歡做行政,行政工作她可以做得很好,而技術部門要學的東西很多,承擔的責任也比較大,「可是我的個性不會去表達我不喜歡,既然被安排進技術部門,我就認命好好學好好做。」
但阿美說,還好當初有學這些,「這樣後來才可以跟你老爸一起開店。」
曾經採訪維修相機的師傅,我問他為什麼做這行呢?他聽到時愣了一下,那反應像是「這是什麼問題?」「這要怎麼回答?」師傅想了一下說,那時候出路沒有很多啊,「要不工廠工作,不然就當學徒,除非你念書念得很好,或是家境不錯可以培養。」「我是跟我大哥學,我大哥是跟一個 Canon 的師傅學。」一副理所當然,哪有什麼為什麼。
(未完待續)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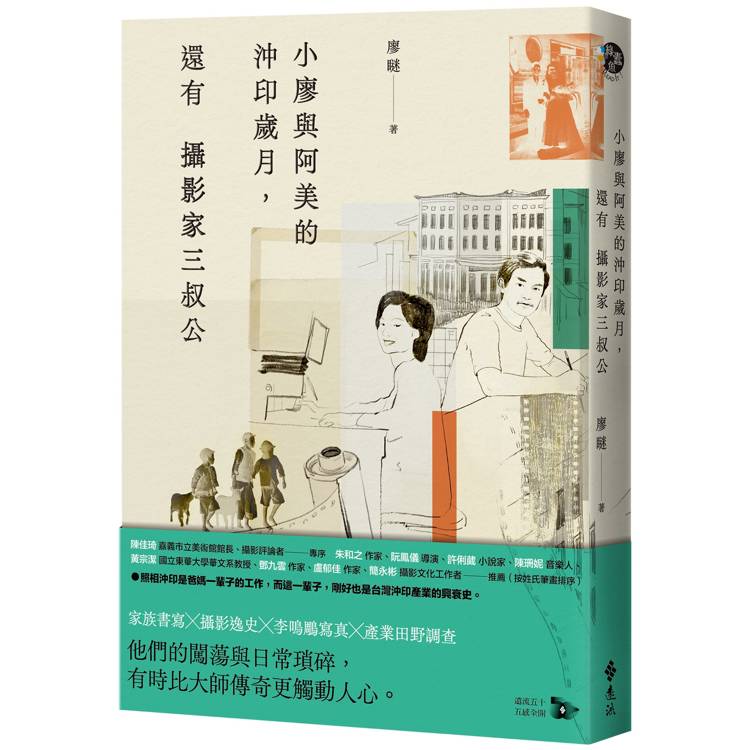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