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聲(經典版):台語二二八小說集【台華對照】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德國柏林文學學會駐村首度入選台文作家★
★2025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推薦作家★
台語二二八小說的時代之作
胡長松《槍聲》出版二十週年紀念
二○二五年經典版.深刻永傳──
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但在國民政府繼來的腐敗、歧視與威權統治下,於一九四七年爆發延燒全島的二二八事件與清鄉,堪稱近代台灣史上死傷最嚴重的衝突。然而,經歷數個世代的禁忌與壓抑,二二八的真相與正義依舊未能伸張,至今仍是台灣人難以言說的苦難與創傷。
矢志投身台語文學,追索台灣歷史,呼喚台灣人經驗,小說家胡長松於二○○五年首度出版的《槍聲》,以八篇小說再現家鄉高雄的二二八事件,不但是台語二二八小說的里程碑,也是解嚴後二二八文學作品中,史實考究最為嚴謹的寫實之作。
高雄是二二八事件傷亡最慘重的地區之一,胡長松藉由詳實的研究報告與口述歷史,細膩刻劃高雄二二八的受難者及其遺族,包括知識分子、反抗者,以及那些不為艱困生活低頭,卻仍遭暴政碾壓的市井小民們,以文學的關懷和母語的發聲,描寫在檔案和數字背後,不為人知的真切掙扎與心聲。讓二二八在持續的訴說中獲得解放,讓台灣人在命運中得以覺醒。
◎本作榮獲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書寫高雄出版獎助
★2025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推薦作家★
台語二二八小說的時代之作
胡長松《槍聲》出版二十週年紀念
二○二五年經典版.深刻永傳──
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但在國民政府繼來的腐敗、歧視與威權統治下,於一九四七年爆發延燒全島的二二八事件與清鄉,堪稱近代台灣史上死傷最嚴重的衝突。然而,經歷數個世代的禁忌與壓抑,二二八的真相與正義依舊未能伸張,至今仍是台灣人難以言說的苦難與創傷。
矢志投身台語文學,追索台灣歷史,呼喚台灣人經驗,小說家胡長松於二○○五年首度出版的《槍聲》,以八篇小說再現家鄉高雄的二二八事件,不但是台語二二八小說的里程碑,也是解嚴後二二八文學作品中,史實考究最為嚴謹的寫實之作。
高雄是二二八事件傷亡最慘重的地區之一,胡長松藉由詳實的研究報告與口述歷史,細膩刻劃高雄二二八的受難者及其遺族,包括知識分子、反抗者,以及那些不為艱困生活低頭,卻仍遭暴政碾壓的市井小民們,以文學的關懷和母語的發聲,描寫在檔案和數字背後,不為人知的真切掙扎與心聲。讓二二八在持續的訴說中獲得解放,讓台灣人在命運中得以覺醒。
◎本作榮獲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書寫高雄出版獎助
目錄
《槍聲》新版序
槍聲
金舖血案
死亡證明
只要放伊出來
阿貓不孝的故事
請問,阮阿爸……
人力車伕
總司令最後的春天
槍聲
金舖血案
死亡證明
只要放伊出來
阿貓不孝的故事
請問,阮阿爸……
人力車伕
總司令最後的春天
序/導讀
《槍聲》新版序
兼論當前的台語二二八文學
胡長松
前言
我的二二八小說集《槍聲》初版至今已歷二十年,出版社告知已無庫存,且初版當時的台語習慣用字,至今已有大幅變化,所以我們決定重新出版,我也同時做了極少量的校對。
《槍聲》裡面的篇章於二○○二年開始寫作,陸續發表後,我也對當前台灣的二二八文學做過一些基本的觀察,也和各界的專家有過多場的請教和討論,並在二○一四年發表論文〈台語二二八文學裡的台灣人面貌〉,一轉眼,距離這篇論文的發表也有十年過去了。回首《槍聲》初版至今,我對二二八及二二八文學的看法,大致就在這篇論文裡,並無時效問題,因此,我就將此論文的核心觀點摘寫修訂,放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二二八文學裡的轉型正義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國人如何面對、理解並從該事件記取教訓,是當前政治、社會、歷史、文學、文化、法律、語言等各面向的重大課題,其中的文學面向和近代西方轉型正義價值所強調的「公佈真相」、「保存記憶」等行動緊密相關。
所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民主國家對過去政府違法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具有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賠償等面向。簡而言之,通常由政府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戰爭罪行所引發的各種違反國際法或人權保障之行為,追究加害者犯罪行為,並取回犯罪行為所得之財產權利。此外,亦考慮「制度性犯罪」的價值判斷與法律評價,目的為鞏固和保障基本人權之普世價值,以督促政府停止、調查、懲處、矯正和預防未來政府對人權的侵犯。
歐洲轉型正義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遭遇過納粹政權的德國,旅德歷史學者胡昌智描述:「德國在二戰後對納粹的過去有深刻的自我批判。不少納粹集中營被保存成為紀念及教育場所。歷史博物館的設立,也與一般其他國家的目的不同,它不為宣揚民族光榮,正好相反,它是檢討自己過去的機構。漢堡社會學研究所策劃的兩次〈國防軍展〉(Wehrmachtausstellung), 第一次自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九年,第二次由二○○一年到二○○四年。展覽由聯邦文化部長揭幕,在全國三十四個城市博物館展出,展出國防軍─德國的國軍─在二戰中對俄國的罪行,以及國防軍如何參與屠殺猶太人的行動。兩次的四年展都各有將近一百萬人次的參觀者。展覽在各城市引起激烈的爭議,反對者,包括全國性的軍人協會、右派組織、被驅離故鄉人協會、部份軍事史家都發表抗議文字及遊行。但是社會大眾能夠、也願意接受這些有損國防軍清白形象的歷史事實。德國對納粹過去的自我批判,從〈國防軍展〉的事件看來,它似乎是沒有底線的。」
奧地利的例子亦可供參考。東尼.賈德在《歐洲戰後六十年》中,針對戰後奧地利的轉型正義作法有如下描述:「奧地利要恢復正常生活,得先讓當地法西斯份子和納粹合作者受到懲罰。在這個不到七百萬人口的國家裡,曾有七十萬納粹黨員……戰時有一百二十萬奧地利人在德軍服役。在納粹黨衛軍和集中營管理單位裡,奧地利人佔的比例特別高。奧地利的公眾領域和上層社會圈,充斥著納粹支持者──維也納愛樂一百一十七名成員,有四十五人是納粹黨員……在這樣的情況下,奧地利卻得到『從輕發落』……十三萬奧地利人受到戰爭罪行調查,其中兩萬三千人受審,一萬三千六百人判刑,四十三人判死刑,『只有』三十人遭處決。約七萬名公務員遭撤職。一九四六年秋,佔領奧地利的同盟國四國同意讓奧地利此後自行處理本國的罪犯,自行去納粹化。受污染特別嚴重的教育體系,順利去納粹化:兩千九百四十三名小學教師、四百七十七名中學教師遭撤職,大學教師遭撤職者『只有』二十七名──雖然許多資深大學教授支持納粹是人盡皆知。」
從前述略舉德國和奧地利的例子,可以輕易察覺台灣當局行動與社會認知,對於二二八的轉型正義的覺知是十分薄弱的:雖然對被害人展開賠償並開始建立紀念碑,但碑文的爭議反應出「只有被害人而沒有加害人」的荒謬狀況,遲遲未能解決,而且真相解密的工作進展仍不足(例如諸多加害者、劊子手與告密者之書信與日記等相關文件之缺乏),這種種,對於台灣當前的民主化工程可謂阻礙。尤其當我們發覺二二八事件後無政府官員及施暴集團成員因此事件受到究責,無任何獨裁支持者受到檢討、調查及撤職,甚至繼續佔據上層政治、經濟、社會圈高位,相較之下,讀到前述西方史家在論及奧地利之處置納粹支持者(在台灣人看來想必已是十分嚴厲了),卻屢屢以「從輕發落」、「只有」之字眼評論,則台灣對於暴行加害者的處置已遠遠非「從輕發落」可以形容。
許多台灣作家投入二二八(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書寫,無非要導正人權正義價值在此事件後處於嚴重失落的頹勢,就此「人權價值導正」與實質進行還原真相的努力而言,二二八文學是台灣民間自力於轉型正義之補救工作的一環。
(略)
目前為止,各受害族群當然都有二二八悲劇書寫的作品,而另一方面,各受害族母語在殖民統治中,因為教育與媒體政策向官方華語傾斜而出現流失加劇的慘況,則可視為台灣重大的「語言的悲劇」。筆者認為,既然語言是各族群文化重要的載體,故各受害族群以族語來進行二二八書寫,就更具語言文化轉型正義的迫切性。
關於轉型正義的書寫與母語的關係, 策蘭(Paul Celan,1921-1970)獨特的生命創作歷程可供吾輩借鏡。
策蘭是猶太裔德語詩人,經歷過悲慘的希特勒屠殺,父母都死於集中營,但戰後仍不得不用德語寫詩,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內傷,時刻展現在他的詩裡。例如在他的名作〈狼豆〉,有如下驚心動魄的詩句:
很遠,在米哈伊洛夫卡,在
烏克蘭那地方,
他們殺死了我父母:什麼
曾經在那裡開花,什麼
還在開花?什麼樣的
花,媽媽,
曾經使妳痛苦
以它的名字?
策蘭質問,在母親被殺害的地方,是什麼還在開花呢?他在原詩中寫著:
Mutter, dir,
Die du Wolfsbohne sagtest, nicht:
Lupine.
媽媽,妳,
妳說那是狼豆(Wolfsbohne),不對:
羽扇豆(Lupine)。
Wolfsbohne 和Lupine 是同一種花(即譯文所稱之「狼豆」)在不同語言的說法。Wolfsbohne 是德語的說法,但策蘭在詩裡斷然否定了這個德語詞彙。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隱喻,隱喻策蘭對於德語詞彙作為「劊子手的話語」的強大厭惡。他緊接著在詩行裡如此開展:
昨天他們來了一個人
害死了妳
又一次,在
我的詩裡。
媽媽。
媽媽,誰的
手,我曾握過,
當我攜妳的
言語去往
德國?
在烏斯季,妳總是說,在
易北河畔的
烏斯季,
在
逃亡中。
媽媽,哪裡就住著
劊子手。
……
媽媽,人們沉默。
媽媽,他們容忍
卑鄙者毀謗我。
媽媽,沒有一個人
出來打斷劊子手的話語。
媽媽,他們寫詩
喔
媽媽,多少
陌生的土地結出妳的果實!
結出果實並養活
那些吃人者!
……
透過這首詩的片段,我們就可理解一九四六年策蘭寫給《行動報》總編輯李希納的信中提到:「我要告訴您,一個猶太人用德語寫詩是多麼地沉重。我的詩發表後,也會傳到德國─允許我跟您講這麼一個可怕的事情──那隻打開我的書的手,也許曾經與殺害我母親的劊子手握過手……但我的命運已經註定了:用德語寫詩。」
戰後歐洲像策蘭這樣的傷痕書寫其實很多,很近似台灣的二二八書寫,而策蘭特殊的地方在於他察覺出無法以自身母語寫作而不得不用「劊子手的話語」寫作的痛苦,因為,這些話語和劊子手的族群連結在一起,讓他時刻無從擺脫。
而台灣的現象又是如何呢?從文學來看,目前我們尚很少在當前以華語進行的傷痕書寫裡,發現類似策蘭詩作所呈現出的語言內省,原因很難斷言。不過,我們或也可稱有比策蘭幸運之處,乃在於:我們的母語雖已苟延殘喘,但在我們的手上仍未至完全被毀棄!當我們要擺脫「劊子手的話語」的連結,我們只要單純透過母語書寫行動,回歸到母親大地的懷抱就可以!
借鏡策蘭,我們似也可以說,母語的二二八文學書寫,正是作家們針對「語言的悲劇」現狀作出反抗和突破的努力,而用母語來進行創作,也是最有力道的自我回歸。
兼論當前的台語二二八文學
胡長松
前言
我的二二八小說集《槍聲》初版至今已歷二十年,出版社告知已無庫存,且初版當時的台語習慣用字,至今已有大幅變化,所以我們決定重新出版,我也同時做了極少量的校對。
《槍聲》裡面的篇章於二○○二年開始寫作,陸續發表後,我也對當前台灣的二二八文學做過一些基本的觀察,也和各界的專家有過多場的請教和討論,並在二○一四年發表論文〈台語二二八文學裡的台灣人面貌〉,一轉眼,距離這篇論文的發表也有十年過去了。回首《槍聲》初版至今,我對二二八及二二八文學的看法,大致就在這篇論文裡,並無時效問題,因此,我就將此論文的核心觀點摘寫修訂,放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二二八文學裡的轉型正義
二二八是台灣歷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國人如何面對、理解並從該事件記取教訓,是當前政治、社會、歷史、文學、文化、法律、語言等各面向的重大課題,其中的文學面向和近代西方轉型正義價值所強調的「公佈真相」、「保存記憶」等行動緊密相關。
所謂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是民主國家對過去政府違法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具有司法、歷史、行政、憲法、賠償等面向。簡而言之,通常由政府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戰爭罪行所引發的各種違反國際法或人權保障之行為,追究加害者犯罪行為,並取回犯罪行為所得之財產權利。此外,亦考慮「制度性犯罪」的價值判斷與法律評價,目的為鞏固和保障基本人權之普世價值,以督促政府停止、調查、懲處、矯正和預防未來政府對人權的侵犯。
歐洲轉型正義最顯著的例子就是遭遇過納粹政權的德國,旅德歷史學者胡昌智描述:「德國在二戰後對納粹的過去有深刻的自我批判。不少納粹集中營被保存成為紀念及教育場所。歷史博物館的設立,也與一般其他國家的目的不同,它不為宣揚民族光榮,正好相反,它是檢討自己過去的機構。漢堡社會學研究所策劃的兩次〈國防軍展〉(Wehrmachtausstellung), 第一次自一九九五年到一九九九年,第二次由二○○一年到二○○四年。展覽由聯邦文化部長揭幕,在全國三十四個城市博物館展出,展出國防軍─德國的國軍─在二戰中對俄國的罪行,以及國防軍如何參與屠殺猶太人的行動。兩次的四年展都各有將近一百萬人次的參觀者。展覽在各城市引起激烈的爭議,反對者,包括全國性的軍人協會、右派組織、被驅離故鄉人協會、部份軍事史家都發表抗議文字及遊行。但是社會大眾能夠、也願意接受這些有損國防軍清白形象的歷史事實。德國對納粹過去的自我批判,從〈國防軍展〉的事件看來,它似乎是沒有底線的。」
奧地利的例子亦可供參考。東尼.賈德在《歐洲戰後六十年》中,針對戰後奧地利的轉型正義作法有如下描述:「奧地利要恢復正常生活,得先讓當地法西斯份子和納粹合作者受到懲罰。在這個不到七百萬人口的國家裡,曾有七十萬納粹黨員……戰時有一百二十萬奧地利人在德軍服役。在納粹黨衛軍和集中營管理單位裡,奧地利人佔的比例特別高。奧地利的公眾領域和上層社會圈,充斥著納粹支持者──維也納愛樂一百一十七名成員,有四十五人是納粹黨員……在這樣的情況下,奧地利卻得到『從輕發落』……十三萬奧地利人受到戰爭罪行調查,其中兩萬三千人受審,一萬三千六百人判刑,四十三人判死刑,『只有』三十人遭處決。約七萬名公務員遭撤職。一九四六年秋,佔領奧地利的同盟國四國同意讓奧地利此後自行處理本國的罪犯,自行去納粹化。受污染特別嚴重的教育體系,順利去納粹化:兩千九百四十三名小學教師、四百七十七名中學教師遭撤職,大學教師遭撤職者『只有』二十七名──雖然許多資深大學教授支持納粹是人盡皆知。」
從前述略舉德國和奧地利的例子,可以輕易察覺台灣當局行動與社會認知,對於二二八的轉型正義的覺知是十分薄弱的:雖然對被害人展開賠償並開始建立紀念碑,但碑文的爭議反應出「只有被害人而沒有加害人」的荒謬狀況,遲遲未能解決,而且真相解密的工作進展仍不足(例如諸多加害者、劊子手與告密者之書信與日記等相關文件之缺乏),這種種,對於台灣當前的民主化工程可謂阻礙。尤其當我們發覺二二八事件後無政府官員及施暴集團成員因此事件受到究責,無任何獨裁支持者受到檢討、調查及撤職,甚至繼續佔據上層政治、經濟、社會圈高位,相較之下,讀到前述西方史家在論及奧地利之處置納粹支持者(在台灣人看來想必已是十分嚴厲了),卻屢屢以「從輕發落」、「只有」之字眼評論,則台灣對於暴行加害者的處置已遠遠非「從輕發落」可以形容。
許多台灣作家投入二二八(以及其後的白色恐怖)書寫,無非要導正人權正義價值在此事件後處於嚴重失落的頹勢,就此「人權價值導正」與實質進行還原真相的努力而言,二二八文學是台灣民間自力於轉型正義之補救工作的一環。
(略)
目前為止,各受害族群當然都有二二八悲劇書寫的作品,而另一方面,各受害族母語在殖民統治中,因為教育與媒體政策向官方華語傾斜而出現流失加劇的慘況,則可視為台灣重大的「語言的悲劇」。筆者認為,既然語言是各族群文化重要的載體,故各受害族群以族語來進行二二八書寫,就更具語言文化轉型正義的迫切性。
關於轉型正義的書寫與母語的關係, 策蘭(Paul Celan,1921-1970)獨特的生命創作歷程可供吾輩借鏡。
策蘭是猶太裔德語詩人,經歷過悲慘的希特勒屠殺,父母都死於集中營,但戰後仍不得不用德語寫詩,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內傷,時刻展現在他的詩裡。例如在他的名作〈狼豆〉,有如下驚心動魄的詩句:
很遠,在米哈伊洛夫卡,在
烏克蘭那地方,
他們殺死了我父母:什麼
曾經在那裡開花,什麼
還在開花?什麼樣的
花,媽媽,
曾經使妳痛苦
以它的名字?
策蘭質問,在母親被殺害的地方,是什麼還在開花呢?他在原詩中寫著:
Mutter, dir,
Die du Wolfsbohne sagtest, nicht:
Lupine.
媽媽,妳,
妳說那是狼豆(Wolfsbohne),不對:
羽扇豆(Lupine)。
Wolfsbohne 和Lupine 是同一種花(即譯文所稱之「狼豆」)在不同語言的說法。Wolfsbohne 是德語的說法,但策蘭在詩裡斷然否定了這個德語詞彙。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隱喻,隱喻策蘭對於德語詞彙作為「劊子手的話語」的強大厭惡。他緊接著在詩行裡如此開展:
昨天他們來了一個人
害死了妳
又一次,在
我的詩裡。
媽媽。
媽媽,誰的
手,我曾握過,
當我攜妳的
言語去往
德國?
在烏斯季,妳總是說,在
易北河畔的
烏斯季,
在
逃亡中。
媽媽,哪裡就住著
劊子手。
……
媽媽,人們沉默。
媽媽,他們容忍
卑鄙者毀謗我。
媽媽,沒有一個人
出來打斷劊子手的話語。
媽媽,他們寫詩
喔
媽媽,多少
陌生的土地結出妳的果實!
結出果實並養活
那些吃人者!
……
透過這首詩的片段,我們就可理解一九四六年策蘭寫給《行動報》總編輯李希納的信中提到:「我要告訴您,一個猶太人用德語寫詩是多麼地沉重。我的詩發表後,也會傳到德國─允許我跟您講這麼一個可怕的事情──那隻打開我的書的手,也許曾經與殺害我母親的劊子手握過手……但我的命運已經註定了:用德語寫詩。」
戰後歐洲像策蘭這樣的傷痕書寫其實很多,很近似台灣的二二八書寫,而策蘭特殊的地方在於他察覺出無法以自身母語寫作而不得不用「劊子手的話語」寫作的痛苦,因為,這些話語和劊子手的族群連結在一起,讓他時刻無從擺脫。
而台灣的現象又是如何呢?從文學來看,目前我們尚很少在當前以華語進行的傷痕書寫裡,發現類似策蘭詩作所呈現出的語言內省,原因很難斷言。不過,我們或也可稱有比策蘭幸運之處,乃在於:我們的母語雖已苟延殘喘,但在我們的手上仍未至完全被毀棄!當我們要擺脫「劊子手的話語」的連結,我們只要單純透過母語書寫行動,回歸到母親大地的懷抱就可以!
借鏡策蘭,我們似也可以說,母語的二二八文學書寫,正是作家們針對「語言的悲劇」現狀作出反抗和突破的努力,而用母語來進行創作,也是最有力道的自我回歸。
試閱
槍聲
1
冷鋒面過境的春寒時天,早起拄落過雨,雖然雨已經停,不過氣溫猶誠低。壽山跤的看守所是一棟抹紅毛土的氆色建築物,四周圍箍一輾懸懸安鐵枝仔的圍牆。圍牆內底這面停一台軍用的吉普仔車,有一个查甫人徛佇車門邊。伊穿西米羅,手骨綁一塊有赤十字記號的布條,生狂著急的眼神投向看守所的大門。無外久,彼道門嘎一聲拍開,一个青年褪赤跤位內面行出來。穿西米羅的查甫人斟酌看,雄雄頓蹬一下。青年真虛弱,衫褲破糊糊,袂輸乞食模樣,行路小可跛跛,跤底親像拖萬斤的重量。不過,彼確實就是伊咧等的人。
「正雄君,真正是你,正雄君!」穿西米羅的查甫人大聲喝。
青年譴頭。
「院長!院長!想袂到,啊!」
這兩个人真激動,怹一下攬做伙,目屎流規面。
這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初九的代誌,彼日位看守所行出來的青年,名叫許正雄,二十五歲,日本久米留大學醫科博士,戰後轉來台灣,擔任高雄市立病院的齒科主任;另外彼个,就是市立病院的院長蘇山景。
當然,若看眼前的模樣,無人認會出許正雄是一位醫師。
「我三日前就應該愛死……就應該愛死矣啦……」
其實拄才,兵仔開門喝名的時,許正雄已經覺悟。因為彼幾日以來,有幾落擺,伊佇過度枵餓的半昏迷之中看著兵仔入來將人喊出去,過無偌久,就有槍聲位山壁的方向傳過來;逐擺佇這个時陣,牢房內就是一片寂靜。每一个人攏將目睭瞌起來,是紀念,嘛是佇心肝頭將死者的背景閣唸一遍。「咱互相鬥相共,誰若會使活咧出去,就負責去向咱厝裡的人通報。」這是怹的約束。伊佮二十幾个人關佇一間小小的牢房,因為牢房傷擠,人疊人,伊傷久無振動,規身軀麻痛。正雄聽著兵仔喝伊的名的時,強強peh 袂起來。「許桑!」坐佇伊邊仔的李阿順斡頭講:「請你會記,佇苓仔寮,我的阿娘……」李阿順的目墘澹澹。正雄向伊頕頭:「會,我會去,假使……」伊無閣講。小小窗仔縫滲入來的窗光,親像是伊生命最後的一束光線,宣布伊的死期到位……
伊喙唇咬咧,恬恬綴佇兵仔後面行,去到玄關一塊柴桌仔頭前。一个外省軍官叫伊簽名。外省軍官講:「簽完名,你就可以滾了。」伊起先毋敢相信,想講是家己聽無啥有北京話,聽毋著去,所以tshāi直直毋敢振動。「叫你滾,你沒聽見嗎?」邊仔的兵仔夯跤共踢,手指門口的方向,叫伊走。按呢,伊才真正清醒過來。
──完全想袂到,伊,竟然是夆放出來的人。
「正雄君,你敢知影?許參議員伊……」蘇院長講。
「是,我知……」
一時間重生的歡喜之情,即刻位許正雄的面消退。伊頭佒低,目屎輾落來。
──「正雄郎!」佇彼陣槍聲之後,多桑是按呢共喊的。紲落……
正雄干焦想欲緊離開這个所在。
蘇院長講,有重要的病人下晡會到,愛緊轉去。「我先送你轉去厝換衫,來,咱就去病院。」
蘇院長請正雄坐入車底。正雄的面一時躊躇。毋知啥物時陣,一个兵仔已經坐入去佇軍車的駕駛座,將車發動。
「放心啦!」蘇院長講。
怹鑽入車後斗。
軍車駛出看守所圍牆的鐵門的時,正雄斡頭看,拄落雨了的薄霧罩佇壽山山坪的相思林。山頂的烏雲必一巡,有微微光線射落來。
正雄鼻著家己一身軀焦去的血佮屎尿濫濫做伙的味,一陣反腹。
「我想,你知影是誰。」蘇院長講。
正雄頕頭。
無外久,車駛入鹽埕埔。經過市政府門口的時,伊的面貼佇窗仔邊。市政府頭前的廣場,這馬是一列一列的棺柴,排列佇四个角落的衛兵的槍空下。正雄位嚨喉底輕輕仔喝一聲:多桑……
2
蘇院長佮正雄轉到病院的時,已經是下晡一點。怹一落車,彼台吉普仔就踅頭離開。
市立病院佇小圓環北爿三百外米遠的路邊,是日本人佇戰爭尾聲起的。當初時,院裡的現代設備攏直接位日本配送過來。病院是一棟隘腹深間,二層樓懸的白色紅毛土建築物,大門向西,有遮日夯雨的白色門廊伸向硿紅毛土的頭前埕。彼時埕前的路猶是石頭仔路,路的對面佮遠遠的高雄川閣有鐵枝路之間,是一片稻田。三月,稻仔拄播好,青色的稻仔栽,佇田中央排列甲整齊整齊。水田映出壽山的山影,有幾隻白鴒鷥歇佇田墘。
病院的門口埕較早攏停四五台三輾車等欲載人,不過,彼日只賰七八个外省兵,圍佇角落的鳳凰樹跤,搦十八搏徼。怹phih-pheh叫,喝甲大細聲。
「啊!」正雄聽著怹的喝聲,心肝頭雄雄搐一下,親像猶有驚嚇。
「正雄,閣有佗位無爽快?」
「呃……無,無要緊。」
許正雄一个人坐佇二樓診療室的辦公桌,思考這幾工到底發生啥物代誌。佇一場熱情之後,這个城市雄雄冷靜落來,敢若之中存在一个巨大的斷層,予伊經過這三工監牢的烏暗了後,遂完全袂認得。敢毋是仝款?親像這塊桌仔、這條椅仔、抑是伊桌頂的紙筆佮墨水。一本烏皮燙金字的齒科辭典囥佇桌頂,彼日伊離開進前,拄好掀開佇某一頁;彼頁插圖有一齒喙齒,深深釘入齒岸,插圖畫出神經佮血管的分佈。正雄將冊閡起來。字典邊仔囥一枝鋼筆,是伊去日本留學進前,多桑位堀江買來送伊的,烏色的筆身用日本話刻一逝金字「正雄郎金榜留念」,字已經褪色。這枝鋼筆一直紮佇伊的身軀邊。
──「烏尼桑,咱敢欲轉去?」正雄想起戰爭拄結束的時,佮伊作夥佇日本的小弟世雄按呢問伊。「哪會使無轉去,多桑佮卡將攏佇台灣,哪會使無轉去。而且,啊!這是祖國的勝利啊!」正雄想起怹佮幾个台灣學生,提紙、提筆、提尺,佇無人看見的房間偷偷仔學畫青天白日旗的光景。
正雄行到窗邊,病院向南這爿,有幾間日本式的烏瓦厝,閣較遠的所在,半烏陰的市街路,寂靜中有肅殺之氣。伊聽會著外省兵的皮鞋聲,khiak-khiak 叫,有時猶有一聲兩聲槍聲,遠遠位某一个方向傳過來。除了夯槍的兵仔,路裡無啥物人,更加看無一个少年家,怹敢若是綴前幾日的雨水做伙消失去。
「主任,這是彭老夫人的病歷。」護士小姐佇伊背後講。
「嗯!先囥咧!」
「院長講,伊隨時會到。」
「嗯!我知。」
正雄行轉來坐落佇椅仔。
──「正雄郎!」
多桑的面容又閣出現。排山倒海的血跡佮悲傷位伊眼前嵌落來。
3
可能是因為傷過頭忝,無外久,正雄的目睭隨就瞌去。
茫茫中,伊親像聽著有人喝伊的名。醒過來的時,彭老夫人佮伊的新婦已經入來佇診療室。怹佮平常時仝款,攏穿旗袍。
「啊,真失禮。」正雄目睭擂擂咧,用生疏的北京語講。
「哪的話,沒干係。」彭老夫人講:「虧你回來了,要不然,我這牙,今晚上可有得受了。」
正雄請伊坐上診療椅。彭老夫人將一个珍珠皮包仔交予新婦,坐起去。邊仔的護士過將椅仔放予䖙落來。
「還是,那一顆嗎?」
「大概吧。這牙啊,痛起來可玄,一整張嘴痛得,要說哪一顆也說不準。」
正雄看護士。護士用台語共這句話閣講一擺。彼个護士是大港埔在地人,戰後捌參加過黨部婦女會辦的國語講習班,聽較有。
「喔!」正雄講:「這個,很平常。」伊將椅仔頂面的診視燈拍灼。
正雄看著伊頂排第一齒後齻蛀甲愈深落去,齒岸紅閣腫。伊提出一支鐵鋏佇下排對應的後齻頂面輕輕敲兩下。
「唔!痛!就是這兒。」彭老夫人講。
「很痛嗎?」正雄閣敲二下。
「很痛。」
「其實,我敲的這一顆好好的。這是說,您上排的那一顆蛀得很嚴重,所以才牽動底下的大神經。」
「哇!啥麼神經?那可怎麼辦?要拔掉嗎?」坐佇邊仔的彭司令夫人真緊張按呢問。
正雄閣詳細檢查一下,講:「嗯!不過,要先麻醉。」
伊拜託護士準備麻射,請彭老夫人先漉喙。
「不會痛吧?」彭司令夫人問。
正雄斡頭看彭夫人。
彭夫人的目睭閃開:「我是問你,痛是不痛?」
正雄無講話,親像咧想啥。
護士共手裡的麻射交予正雄,正雄將射針提到目睭的懸度,輕輕仔捒一下射筒。彼射針閣幼閣長,藥滴滲出一滴兩滴。紲落,伊將面向佇彭老夫人開開的喙頂懸。
無外久,正雄閣來到窗邊,伊請彭老夫人小歇睏,等麻射降。伊看著烏雲當咧貼低,敢若閣欲落雨;拄才載伊轉來的彼台吉普仔,這馬停佇病院的門口埕。
「許醫師,令尊的事……我們……我們聽說了,我們很遺憾。可是,無論如何你要記得,你的命可是老夫人救的,這可是救命之恩啊!」彭司令夫人雄雄按呢講。正雄斡過來看怹。伊對怹深深一曲躬。
1
冷鋒面過境的春寒時天,早起拄落過雨,雖然雨已經停,不過氣溫猶誠低。壽山跤的看守所是一棟抹紅毛土的氆色建築物,四周圍箍一輾懸懸安鐵枝仔的圍牆。圍牆內底這面停一台軍用的吉普仔車,有一个查甫人徛佇車門邊。伊穿西米羅,手骨綁一塊有赤十字記號的布條,生狂著急的眼神投向看守所的大門。無外久,彼道門嘎一聲拍開,一个青年褪赤跤位內面行出來。穿西米羅的查甫人斟酌看,雄雄頓蹬一下。青年真虛弱,衫褲破糊糊,袂輸乞食模樣,行路小可跛跛,跤底親像拖萬斤的重量。不過,彼確實就是伊咧等的人。
「正雄君,真正是你,正雄君!」穿西米羅的查甫人大聲喝。
青年譴頭。
「院長!院長!想袂到,啊!」
這兩个人真激動,怹一下攬做伙,目屎流規面。
這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初九的代誌,彼日位看守所行出來的青年,名叫許正雄,二十五歲,日本久米留大學醫科博士,戰後轉來台灣,擔任高雄市立病院的齒科主任;另外彼个,就是市立病院的院長蘇山景。
當然,若看眼前的模樣,無人認會出許正雄是一位醫師。
「我三日前就應該愛死……就應該愛死矣啦……」
其實拄才,兵仔開門喝名的時,許正雄已經覺悟。因為彼幾日以來,有幾落擺,伊佇過度枵餓的半昏迷之中看著兵仔入來將人喊出去,過無偌久,就有槍聲位山壁的方向傳過來;逐擺佇這个時陣,牢房內就是一片寂靜。每一个人攏將目睭瞌起來,是紀念,嘛是佇心肝頭將死者的背景閣唸一遍。「咱互相鬥相共,誰若會使活咧出去,就負責去向咱厝裡的人通報。」這是怹的約束。伊佮二十幾个人關佇一間小小的牢房,因為牢房傷擠,人疊人,伊傷久無振動,規身軀麻痛。正雄聽著兵仔喝伊的名的時,強強peh 袂起來。「許桑!」坐佇伊邊仔的李阿順斡頭講:「請你會記,佇苓仔寮,我的阿娘……」李阿順的目墘澹澹。正雄向伊頕頭:「會,我會去,假使……」伊無閣講。小小窗仔縫滲入來的窗光,親像是伊生命最後的一束光線,宣布伊的死期到位……
伊喙唇咬咧,恬恬綴佇兵仔後面行,去到玄關一塊柴桌仔頭前。一个外省軍官叫伊簽名。外省軍官講:「簽完名,你就可以滾了。」伊起先毋敢相信,想講是家己聽無啥有北京話,聽毋著去,所以tshāi直直毋敢振動。「叫你滾,你沒聽見嗎?」邊仔的兵仔夯跤共踢,手指門口的方向,叫伊走。按呢,伊才真正清醒過來。
──完全想袂到,伊,竟然是夆放出來的人。
「正雄君,你敢知影?許參議員伊……」蘇院長講。
「是,我知……」
一時間重生的歡喜之情,即刻位許正雄的面消退。伊頭佒低,目屎輾落來。
──「正雄郎!」佇彼陣槍聲之後,多桑是按呢共喊的。紲落……
正雄干焦想欲緊離開這个所在。
蘇院長講,有重要的病人下晡會到,愛緊轉去。「我先送你轉去厝換衫,來,咱就去病院。」
蘇院長請正雄坐入車底。正雄的面一時躊躇。毋知啥物時陣,一个兵仔已經坐入去佇軍車的駕駛座,將車發動。
「放心啦!」蘇院長講。
怹鑽入車後斗。
軍車駛出看守所圍牆的鐵門的時,正雄斡頭看,拄落雨了的薄霧罩佇壽山山坪的相思林。山頂的烏雲必一巡,有微微光線射落來。
正雄鼻著家己一身軀焦去的血佮屎尿濫濫做伙的味,一陣反腹。
「我想,你知影是誰。」蘇院長講。
正雄頕頭。
無外久,車駛入鹽埕埔。經過市政府門口的時,伊的面貼佇窗仔邊。市政府頭前的廣場,這馬是一列一列的棺柴,排列佇四个角落的衛兵的槍空下。正雄位嚨喉底輕輕仔喝一聲:多桑……
2
蘇院長佮正雄轉到病院的時,已經是下晡一點。怹一落車,彼台吉普仔就踅頭離開。
市立病院佇小圓環北爿三百外米遠的路邊,是日本人佇戰爭尾聲起的。當初時,院裡的現代設備攏直接位日本配送過來。病院是一棟隘腹深間,二層樓懸的白色紅毛土建築物,大門向西,有遮日夯雨的白色門廊伸向硿紅毛土的頭前埕。彼時埕前的路猶是石頭仔路,路的對面佮遠遠的高雄川閣有鐵枝路之間,是一片稻田。三月,稻仔拄播好,青色的稻仔栽,佇田中央排列甲整齊整齊。水田映出壽山的山影,有幾隻白鴒鷥歇佇田墘。
病院的門口埕較早攏停四五台三輾車等欲載人,不過,彼日只賰七八个外省兵,圍佇角落的鳳凰樹跤,搦十八搏徼。怹phih-pheh叫,喝甲大細聲。
「啊!」正雄聽著怹的喝聲,心肝頭雄雄搐一下,親像猶有驚嚇。
「正雄,閣有佗位無爽快?」
「呃……無,無要緊。」
許正雄一个人坐佇二樓診療室的辦公桌,思考這幾工到底發生啥物代誌。佇一場熱情之後,這个城市雄雄冷靜落來,敢若之中存在一个巨大的斷層,予伊經過這三工監牢的烏暗了後,遂完全袂認得。敢毋是仝款?親像這塊桌仔、這條椅仔、抑是伊桌頂的紙筆佮墨水。一本烏皮燙金字的齒科辭典囥佇桌頂,彼日伊離開進前,拄好掀開佇某一頁;彼頁插圖有一齒喙齒,深深釘入齒岸,插圖畫出神經佮血管的分佈。正雄將冊閡起來。字典邊仔囥一枝鋼筆,是伊去日本留學進前,多桑位堀江買來送伊的,烏色的筆身用日本話刻一逝金字「正雄郎金榜留念」,字已經褪色。這枝鋼筆一直紮佇伊的身軀邊。
──「烏尼桑,咱敢欲轉去?」正雄想起戰爭拄結束的時,佮伊作夥佇日本的小弟世雄按呢問伊。「哪會使無轉去,多桑佮卡將攏佇台灣,哪會使無轉去。而且,啊!這是祖國的勝利啊!」正雄想起怹佮幾个台灣學生,提紙、提筆、提尺,佇無人看見的房間偷偷仔學畫青天白日旗的光景。
正雄行到窗邊,病院向南這爿,有幾間日本式的烏瓦厝,閣較遠的所在,半烏陰的市街路,寂靜中有肅殺之氣。伊聽會著外省兵的皮鞋聲,khiak-khiak 叫,有時猶有一聲兩聲槍聲,遠遠位某一个方向傳過來。除了夯槍的兵仔,路裡無啥物人,更加看無一个少年家,怹敢若是綴前幾日的雨水做伙消失去。
「主任,這是彭老夫人的病歷。」護士小姐佇伊背後講。
「嗯!先囥咧!」
「院長講,伊隨時會到。」
「嗯!我知。」
正雄行轉來坐落佇椅仔。
──「正雄郎!」
多桑的面容又閣出現。排山倒海的血跡佮悲傷位伊眼前嵌落來。
3
可能是因為傷過頭忝,無外久,正雄的目睭隨就瞌去。
茫茫中,伊親像聽著有人喝伊的名。醒過來的時,彭老夫人佮伊的新婦已經入來佇診療室。怹佮平常時仝款,攏穿旗袍。
「啊,真失禮。」正雄目睭擂擂咧,用生疏的北京語講。
「哪的話,沒干係。」彭老夫人講:「虧你回來了,要不然,我這牙,今晚上可有得受了。」
正雄請伊坐上診療椅。彭老夫人將一个珍珠皮包仔交予新婦,坐起去。邊仔的護士過將椅仔放予䖙落來。
「還是,那一顆嗎?」
「大概吧。這牙啊,痛起來可玄,一整張嘴痛得,要說哪一顆也說不準。」
正雄看護士。護士用台語共這句話閣講一擺。彼个護士是大港埔在地人,戰後捌參加過黨部婦女會辦的國語講習班,聽較有。
「喔!」正雄講:「這個,很平常。」伊將椅仔頂面的診視燈拍灼。
正雄看著伊頂排第一齒後齻蛀甲愈深落去,齒岸紅閣腫。伊提出一支鐵鋏佇下排對應的後齻頂面輕輕敲兩下。
「唔!痛!就是這兒。」彭老夫人講。
「很痛嗎?」正雄閣敲二下。
「很痛。」
「其實,我敲的這一顆好好的。這是說,您上排的那一顆蛀得很嚴重,所以才牽動底下的大神經。」
「哇!啥麼神經?那可怎麼辦?要拔掉嗎?」坐佇邊仔的彭司令夫人真緊張按呢問。
正雄閣詳細檢查一下,講:「嗯!不過,要先麻醉。」
伊拜託護士準備麻射,請彭老夫人先漉喙。
「不會痛吧?」彭司令夫人問。
正雄斡頭看彭夫人。
彭夫人的目睭閃開:「我是問你,痛是不痛?」
正雄無講話,親像咧想啥。
護士共手裡的麻射交予正雄,正雄將射針提到目睭的懸度,輕輕仔捒一下射筒。彼射針閣幼閣長,藥滴滲出一滴兩滴。紲落,伊將面向佇彭老夫人開開的喙頂懸。
無外久,正雄閣來到窗邊,伊請彭老夫人小歇睏,等麻射降。伊看著烏雲當咧貼低,敢若閣欲落雨;拄才載伊轉來的彼台吉普仔,這馬停佇病院的門口埕。
「許醫師,令尊的事……我們……我們聽說了,我們很遺憾。可是,無論如何你要記得,你的命可是老夫人救的,這可是救命之恩啊!」彭司令夫人雄雄按呢講。正雄斡過來看怹。伊對怹深深一曲躬。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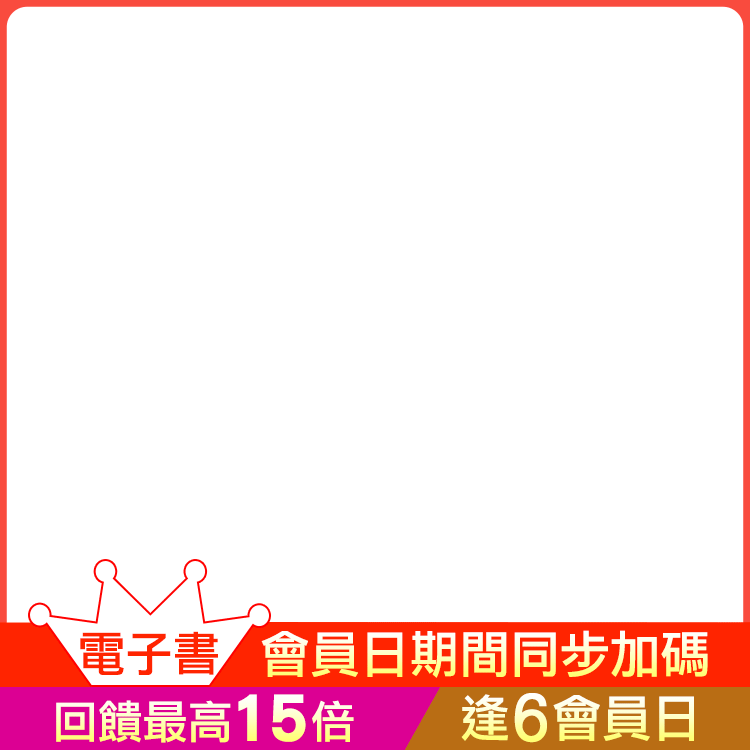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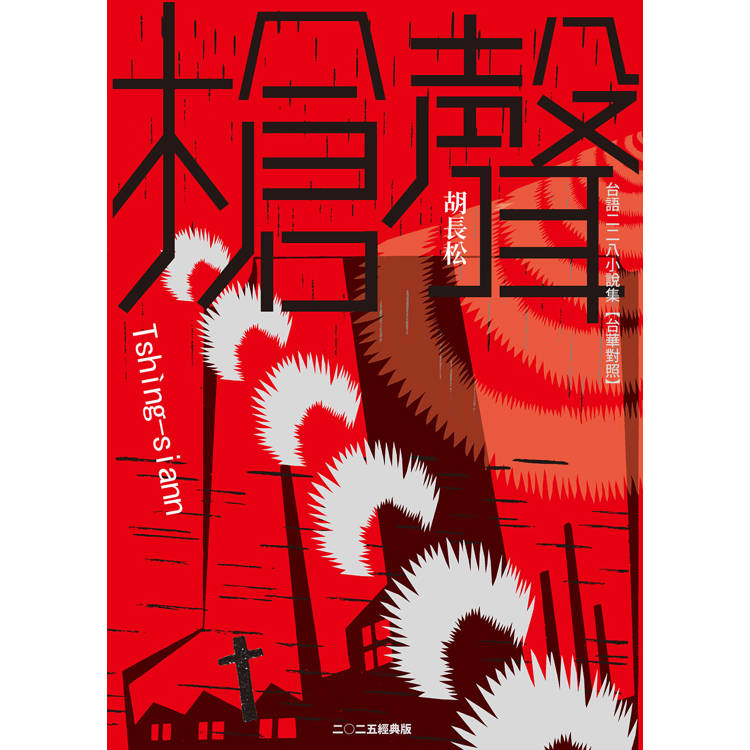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