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Collecting Blue【首刷限量贈品版】 2019-2024 詩與日誌
《流離之書》金其琪人生劇場之「後臺」,剝除外殼,袒露自我之作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小寫全新書系:寫日記
安撫、療癒自我的修復之旅
*旅英香港作家鍾耀華、精神科醫師、醫療人類學家吳易澄專文推薦
*香港藝術家、獨立音樂唱作人曾永曦插畫
*《流離之書》作者金其琪人生劇場之「後臺」,剝除外殼,袒露自我之作。
在多年的籌備後,小寫推出全新書系:寫日記,首發由《流離之書》作者金其琪於2019-2024之間所記下的日記與詩,名為《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日記作為紀錄的形式,一向具有私人史的歷史意義,在近代人文社科與心理學之中逐漸受到重視;而「寫日記」本身,具有拆解、拼貼、拾起、聚攏,將看似連續的日常切割成碎片,復又將碎片聚合成具有意義的片段之意。透過日記,個人得以召喚經驗主體,並與之對話。
在本書寫作的五年中,金其琪透過不間斷的創作日誌、詩歌和散文,從未停止與內在的自我對話,往文字深處去,為的是為痛楚、痛苦、受苦、憂鬱、創傷等等經歷與情緒,尋找一個更適切的名字,更貼近真實的說法。如書中所說,放置它們唯一的方式就是寫下來。寫下來,如同船舶在大洋中下錨,錨的鉤子深入海底,漂泊無定和隨波逐流的人,才暫時找到自己在世界的位置。
本書推薦人吳易澄引用伊朗裔人類學家奧基德.布勞珊(Orkideh Behrouzan)在民族誌《百憂解日誌》(Prozak Diaries)裡頭的一段話:「有時,我們會採用那些能夠撫慰我們、並幫助我們理解經歷的語言(例如精神醫學的語言),這些語詞能減輕不確定與羞恥的重擔,而某些語調也最能投射我們的渴望。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語言、語調與沉默,會逐漸改變我們理解我們的故事、包括我們自己,以及這個世界如何持續運行的方式。」這是語言和文字的力量,也是書寫和敘事的力量。
目錄
推薦序 如果有的話,在哪裏?/鍾耀華
推薦序 養貓、煮飯與寫字:序寫金其琪的憂鬱紀事/吳易澄
2019-2020 永劫不死的方法
2021-2022 不可能的家
2023 靈魂的碎片
2024 一個擁抱撐起的世界
後記
序/導讀
推薦序/鍾耀華
如果有的話,在哪裏?
——在生生死死明明滅滅的動蕩時代保有記憶的碎片,帶著意識直面恐懼,創造回家的歸途。
降生於這個星球,面對環境變遷生命流徙,靈魂被囚禁,在有形的肉身軀殼,在抽象的思想矩陣。清晨的陽光灑落,穿透露水折射輝煌,映照在我們的臉上,我們渴望,我們期待,想要離開的念頭又反覆搖晃,仿彿時間錯位,人類形體外框的背後裂生出過去的自我——來自前世的、今生的,透過母體與家族,從過去的、現在的延展到未來。不充分的,挫傷的,地方的,人際的,無法與之和解的。於是停滯,遲緩,斷裂,於是愛無能,身上有這麼多能量,仇恨與憤怒卻占據了身心靈。我們不甘,瘋狂想要做些甚麼,欲望滋長,強劇地體驗,希望身體被狂暴的悲哀與喜樂振動,確認內在脈搏仍舊跳動,證明自我仍然活著。
我認識金其琪於二〇一五年創辦的端傳媒,當時我們共處一個辦公室,屬不同組別,基本上沒甚麼交疊。直至後來,我離職了,她離開了;她到中國,又去臺灣,而我在香港,又到臺灣,最後抵達英國,我們不算深交,聯絡都少。
但每次見到她,我都從她的眼裏,看到和自己相似的哀愁與痛,想像死亡與逃離的渴求,和某種生之努力。仿彿某種精神在隱微處,某組密碼對上連繫,某個空間擴展了。
我從沒告訴她這種感覺。
這本書寫下她的內在狀態,那些起伏,無解的自傷與掙扎,關於知識與人生,關於愛,關於記憶,寫的是香港,是中國,是臺灣,是疫情,是家庭,是貓咪,是情欲。每個人無非是經歷一些事故,事件,持續拉扯與糾纏,生命被拖進無底的沼澤,但從中可以生出力量,一點一滴地理解自己,拾回自己,理解他人,理解社區,理解世界。用其琪的說法,不過是「珍惜生命在給定的秩序外溢出的窸窸窣窣」。
很高興她出版這本小書,她說Love is still there,其實愛是絞不碎的。我說愛從未止息。她說也許自己就是要靠近風暴眼,才可以離開風暴。我說我們與自己的故道有時差,曾撒下一列如水的凱歌或悲嗚,全然的臨在引領我們穿越如河流的時間觀念之障,看見曾經的經驗與行腳被時光照出不同的影子,有深淺有長闊有高低,貌似統合於一身的記憶幻化為雜蕪的荒地,當光照轉動,所有又遙遙如霧散不復再。又唯有如此不斷往返,我們明白活著的不必如此,不追求於盛放,不執傷於凋零,重新發現道之為道。
閱讀她的日記文字,那些日常的呢喃絮語,就像邀請自己回到那輕柔又易傷的內裏,那個如初生對一切好奇又期待被愛的嬰孩,請求愛護,請求他人的關懷,請求大家多和自己說話。我們都是如此長大,我們仍然可以創造,不也因為別人愛的饋贈嗎?愛就在周邊,收獲這份珍藏,將愛輻射開去,就是最好的報答。
「想要感到自己活著」,是因為裡面還有生之渴望,有些栽種了是不會死的。仍然活著本身就是奇蹟,是以肉身形態活在現世裏,最美麗的豐收。本書書名叫《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我問她想傳遞的是關於死亡嗎?她說重點是藍色,是blue是憂鬱,至於憂鬱了要不要去死,那是不一定的。她說她想傳遞的可能是一個人如何憂鬱又活下來吧,但是並不保證能活多久的那種。豐收過後仍然能夠收成嗎?我們都不知道也無法肯定,但至少先感謝成就當下的全部,享受慶典。至少我在她的文字裏,找到某種堅持自己的微小力量。謝謝她邀請我作序。
個人即整體,並非只有你,只有我,只有她,只有他想要家,想要有理解,想要有陪伴,「你看,我們就像珊瑚礁一樣,每一顆都不一樣。海洋和島嶼的生活智慧早就告訴我們,不一定每個人都要被打磨成方方整整的一模一樣,也可以彼此疊在一起,鑄成一堵牆。」每個看來不夠認真不夠嚴肅不夠普遍的幽微重覆的獨白,都不必如是,穿過迷霧障眼,我們持續寫作,繼續表達,依然相信,將得見山海,看到彼此在遠山大海裏,在為相同的夢編織。
「和所有的創造一樣,物質需要浸潤在精神之河,由此誕生生動的靈魂,散發著意識的輝光;當意識黯淡,創造性也會隨之消失。只有從無時無刻不在試圖侵蝕我們的陰影——『非存在』那裡汲取,持續地創造,才能保有我們對外的掌握權。因此,光是『看』這個行為,比如看山,滿懷滲透性的愛去看,就能在非存在的浩瀚空間裡拓寬存有,而這正是人類存在的唯一理由。」——《山之生》(The Living Mountain),娜恩.雪柏德(Nan Shepherd),管嘯塵譯,新經典文化出版。
是為推薦序,在英國布里斯托。
2025.07.06
耀華
鍾耀華|
寫作者,在現世尋找生之意義。
推薦序/吳易澄
養貓、煮飯與寫字:序寫金其琪的憂鬱紀事
起初注意到金其琪的作品,是在端傳媒上的阿美族祭師的報導,說的是學者巴奈.母路的身分轉變,從學術世界走入部落文化實踐的故事。而後再次吸引我注意到的是在她的非虛構書寫著作《流離之書》裡的一篇〈中國醫護疫情後心理創傷調查〉,正巧對應了我在COVID-19疫情期間進行的研究,於是我邀請其琪組成了一個議題小組,至韓國大邱參與亞洲研究會議,針對疫情間的創傷議題進行報告。會議期間我才知道,其琪另外安排了一個採訪行程,到首爾採訪了李滄東,那位時時叩問著韓國底層小人物的人性、認同與存在的導演。從這些書寫的路徑來看,金其琪看似有種雜食性的知識攝取與生產,然而也不難看出她所凝視之處,無不是受壓迫者、流浪者、邊緣者在世間掙扎的角落。
出身於中國浙江溫州,然後至香港讀書,輾轉來到臺灣求學,這個移動過程並非是一個尋常的軌跡。其琪在離開記者工作之後(其實也沒有真的離開),轉而投入了人類學的領域學習,她持續關注的是香港人的離散與創傷,並且持續參與在某種集體創傷的重構與創作過程中。曾經在香港求學的其琪,必然也見證了那段國安法實施前後香港社會的轉變與痛楚。這本冊子所記錄那些身體的、心理的痛苦,既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有時候,那些文句採取的是極為直白的語言,有時候,卻採取了隱晦的詩句。這種風格上的不穩定,究竟應如何理解?
我想起多年在大學參加詩社的往事。那是一個名為「阿米巴」的詩社,在加入詩社時便明白那不只是一個文學社團,社友們紛紛參與臺灣社會追求民主的各種抗爭。大一的社課是吳晟老師的兒子吳賢寧帶領的,他介紹兩位臺灣現代文學的標竿人物,一位是賴和,另一位是楊熾昌。賴和是臺灣新文學的先驅之一,他的詩與散文以白話文書寫,善用小說與雜文來揭露殖民暴力與階級壓迫,使文學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楊熾昌的筆名是水蔭萍,可以說是臺灣文學現代主義的濫觴。為了逃避日警的思想審查,水蔭萍選擇以「去政治化」的超現實主義作為創作姿態。他的創作帶著某種疏離的、外來者的凝視,仿彿以「異鄉人」之眼觀看自己的土地,語言與視角皆透露出殖民知識的痕跡。
從其琪的書寫中,往往能感受她身為「異鄉人」的身分,反而能養成一種精確地「看見他鄉」的能力;但是「異鄉人」的身分,也有可能是痛苦的源頭,這似乎是上個世紀以來創傷文學的共同特色。文學作為一種見證、抵抗權力與療癒創傷的形式,這點不令人陌生。在納粹發動猶太人大屠殺所造成的歷史創傷之後,無數生還者在沉默與遺忘之間掙扎——有些人選擇噤聲,有些人則仿彿將那段歷史封存在無人可及的內在角落。比方說費修珊與勞德瑞所著《見證的危機》所提出的,是一種對這段「無法言說的過去」進行見證的另類敘事方式:透過破碎語言、或冗長而細緻的敘述,試圖召喚那些被壓抑、否認的經驗。這不僅是歷史的重現,更是一場為受難者發聲、為沉默創傷找到表達形式的倫理實踐。《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Collecting Blue》顯然也是一種見證。但和讀者較為熟悉的報導作品相較之下,這本冊子的文類顯然難以歸類定義。其琪一反過去向外凝視的非虛構書寫,反而採取了向內透視的日誌,以破除既有文字框架的體裁,將自身移動的經驗、夢境,乃至於內心那些脆弱受傷之處都昭揭於世。
即使書以「收集憂鬱」為名,其琪想說的話甚至比病症本身還多。她想要尋找比憂鬱還貼近自己的說法,也想為那些受苦找到更精準的歸因。書的一開始即提起社會學朋友提到的詞neoliberal subjectivity,用來給香港九龍城街上出現的大洞一個註解,同時能解釋自己如何「漂浮不定」,甚至「憂愁、焦慮、搖擺不定、認不清自己」。其琪似乎在為所謂的「創傷」尋找更適切的名字,我則對她提到的一種「例外狀態」印象特別深刻。在二〇二〇年三月那段期間她寫道「我過得忘了日期和星期幾,好像是故意的。我發覺自己在製造一種假象,把這段日子視為一個蟲洞或是什麼,而不讓它屬於原本的生命、時間。」移動本身就是一種生命的巨大斷裂,而當這個過程又突然被拋擲在疫情之中,時間、人、空間的種種錯置,人必須尋找一種活下去的方法。這個狀態不也像是人類學者Arnold Van Gennep在討論通過儀式時所提到的「閾限」(Liminality)概念嗎?在這個過度時空中,人仿彿失去所有的歸屬,從而思考一切事物的本質,重新發現自己能夠生存或甚至去愛的能力。
正如其琪所言「我用盡全力去把一日過得像三日一樣intense,見最多的人,看最多的海,聽最多的音樂,就好像每天都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天」這是用盡全力去擁抱並且對抗生命的冊子。在各種失落中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以及與萬物的關係。在那個閾限時空中,貓咪馬桶蓋是其琪最親密的家人,煮飯與書寫是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無論是養貓還是煮飯,讀者一定覺得作者實在「想太多」。在與親人相隔兩地時,其琪與貓建立了一種特殊的牽絆。這簡直像是宮崎駿的動畫電影《魔女宅急便》,魔女琪琪(Kiki,跟其琪綽號一樣那麼剛好)與她的黑貓吉吉(Jiji)之間的關係。他們之間不僅是主僕或寵物與主人,更像是內心與自我對話的化身。Kiki(無論是其琪或琪琪)與貓的對話,似是反映著她們對變動的世界所感受的不安。而煮飯亦是,無論是準備食材,或與人吃飯,都會讓作者想到身邊的人的處境。
讀這本書時,我不知為何常常想起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永遠的一天》的場景。年邁詩人亞歷山大,在生命的最後一天,回顧自己的人生與失落的愛情,並在偶然中遇見一位非法移民男孩。原本孤獨且準備迎接死亡的他,決定陪伴這名男孩展開一段短暫旅程,試圖在記憶與現實之間找回人性與詩的溫度。《我死後,也想變成藍色 Collecting Blue》像是安哲羅普洛斯的電影一樣,不但色調相似,敘事的節奏也是穿插過去與現在,夢境與現實,藉由緩慢長鏡頭與詩意場景,思索死亡、記憶、語言與救贖的可能。這是一部關於時間、告別與存在意義的靜謐詩篇。當人們經歷痛苦,一方面或許需要為痛苦命名,但也需要讓這些痛苦本身有自己說話的空間。
最後,我想引用伊朗裔人類學家奧基德.布勞珊(Orkideh Behrouzan)的民族誌《百憂解日誌》(Prozak Diaries)裡頭的一段話:「有時,我們會採用那些能夠撫慰我們、並幫助我們理解經歷的語言(例如精神醫學的語言),這些語詞能減輕不確定與羞恥的重擔,而某些語調也最能投射我們的渴望。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語言、語調與沉默,會逐漸改變我們理解我們的故事、包括我們自己,以及這個世界如何持續運行方式。」這也正是我閱讀這本書時的態度,即使這本日誌大量揭露自身的憂愁,我看到的不是病症本身,卻是一個人如何包容、肯認自己的創傷,透過認真的感受、記錄,同時對抗又接受這一切。其琪透過養貓、煮飯與寫字來度過她的「例外狀態」;這三件事,都是奮力求生的行動。書末那句「我就是一邊哭一邊把飯吃完的人。所以我活下來了。」短短一行字,如此安靜祥和,又如雷般的震撼。
吳易澄|
精神科醫師,醫療人類學家,同時也是養貓人與慢跑者。目前任職於新竹馬偕紀念醫院與馬偕醫學大學。學生時期陸續在文學雜誌上發表詩作,曾著有散文集《詩所教我的事》。現在則專注在臨床工作、學術研究與教學任務中。
後記
2025年5月底,當我重讀過去5年的這些日記片段,發現自己讀到第16頁就已經全身發燙、心跳加速,坐在咖啡店伴著重金屬音樂流淚。我在書中多次提到「活下來」這件事,此刻我也真實的活下來了,但是說實話,我對於一個人如何在經歷許多痛苦後活下來,成為自己人生的倖存者,仍然是沒有頭緒。
「我終究活著回來了,什麼都沒殺死我。」這是2020年9月24日,我在結束14天的隔離之後,寫的句子。那時我因為回鄉過年和陪母親過生日,而在溫州遭遇 covid-19 的第一波侵襲,而有9個月無法回到臺灣。我想那之後的幾年,包括現在,我都仍處在一個漫長的復原期中,從那9個月,還有從2019年及後香港的動盪中復原。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覺得生什麼病都不奇怪了,因為吞下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倖存是有代價的。
在這些日記中,直到2024年3月,我才發現那些非常接近死亡的時刻背後的意涵。那一天我寫:「我想,有時候我們想著去死,其實只是想逃。」往前一年的夏天,我去韓國訪問李滄東,他問我在《生命之詩》的結局裡看到什麼,女主角自殺了還是沒有呢?從我的回答裡,他輕易的發現了我對人生的筋疲力盡。2025年的現在,我更確信了面對這種筋疲力盡,我想要的是逃逸,是自由,而絕非死亡與痛苦。
2022年,我因為出版《流離之書》而去了各地做分享。那本書講的全是他人的生命,如果比喻成劇場,那本書的故事是我多年來寫作的「前景」(front stage),但敏銳的出版社編輯讀了我的自序後,很希望我能多寫一點劇場的「後臺」(back stage),也就是我藏在他人生命之後的東西。我拒絕了。三年後的這本書,此刻我在寫的,就是人生劇場的「後臺」,把外殼都剝掉,像蝦子一樣。
在那時的新書發表去到澎湖時,我剛剛重看了阿巴斯1999年的電影The Wind Will Carry Us。澎湖的風好大,我捨棄了書中的章節內容,轉而只講了島嶼和風。阿巴斯在電影中引用了伊朗女詩人 Forough Farrokhzad 的詩,”The Wind Will Carry Us”。 其中有幾句我特別喜歡:
My night so brief is filled with devastating anguish
Hark! Do you hear the whisper of the shadows?
This happiness feels foreign to me.
I am accustomed to despair.
Forough 在32歲死於車禍,比我年輕。我雖然無法知道她在1934年到1967年的時代,因為什麼而習慣和適應了絕望,但卻覺得深有同感。在奇士勞斯基的Bleu中,絕望等於藍色。我很喜歡藍色,但我不喜歡絕望,我只能像Forough一樣說,I am accustomed to this blue. 我幾乎快要習慣和適應了,這像硫酸銅一樣的憂鬱,像天空一樣的陰影,像宇宙漂浮粒子一樣的藍色。
在思考書名的時候,我問幫我寫推薦序的朋友Eason有何建議。他問我,我想傳遞的是關於死亡和憂鬱的事嗎?我回答,我覺得我想傳遞的是一個人如何在憂鬱中活下來的事,所以那個accustomed to就像是說「我適應了這種憂鬱」,我接受這個世界的動盪是常態了,我們必須適應它,我不是很完美的生活著,但我還是生存了。
感謝小小書房和小寫出版的沙貓貓,接受我任性的出版提議。感謝明知閱讀的會是痛苦,還是答應幫我寫推薦序的兩位朋友吳易澄和鍾耀華。感謝小貓咪馬桶蓋,今年是我們在一起的七周年,世上沒有什麼可以把我們分開。感謝寧緯,他是一個擁抱撐起的世界。
一個人不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氣才能出版自己的日記,真正需要勇氣的是,過去、此刻、未來的歲月中,我們決定寫下日記的每一刻。
熱愛重金屬音樂的咖啡店就開在臺灣文學基地隔壁,我去年駐村的時候常去。上禮拜,我走進店裡告訴老闆,我一年沒有來了。他笑著說,那這一年過得還好嗎?有什麼變化嗎?我說,我結婚了。他沒有像常人一樣說:「恭喜。」
他問我:「那有更了解自己了嗎?」
你呢?寫日記的你,更了解自己了嗎?
2025年5月31日 臺北
試閱
2020.03.13
今天我打算逼令自己,真的接受現下的生活狀態,不是一種短期的例外狀況,而將會是持續很久的日常。我不能再逃避這件事,我需要冷靜下來面對它、接受它,然後想一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該怎麼辦。
寒假開始沒幾天,我就忙著籌備政大USR計畫和公共人類學課程合辦的寫作營。現在回想起來,那忙碌的兩天就像一場夢,我們整日和夥伴坐在一起,看喜歡的人講好聽的話,然後討論、寫作。那時我才剛剛搬到臺北的第三個家不久,結束了長達一年在指南山上獨居的日子(澄清:不是去指南宮做道姑)。那一年的日子唯有貓咪與我常伴,而我去了好多的地方,和老師請假回了兩次香港,心裡好亂。我想要有夥伴的生活,重新回到親密的人群之中,所以我搬家了。搬完家的那天晚上,我在新家的廚房親手做了四菜一湯,請我依賴和信任的人來吃。Food and love. Safety, intimacy.
但是很快,我逃避已久的農曆新年就來了。父母變幻著各種方法催我回家。我本來一直拖著,想著能拖就拖,在家的時間越短越好。這當中的原因除了慣常已有的代際矛盾與政治鴻溝之外,也有安全考量。那時肺炎疫情只不過是一個很minor的考慮因素,朋友勸我不要回家時,拿那時只在武漢有零星確診數據的肺炎出來講,是排得很後的。什麼SARS禽流感豬流感,聽得多了,但是這座城市,從來也沒有怎樣。這座城市最大的醜聞除了貪汙的前市長,就是翻掉的動車,都與疾病無關。拖著拖著,寫作營開始的前一天,媽媽說希望我回去陪她過生日。我不是狠心的人。雖然不情願,但我就回去。
後來的事就是,在短短一個星期內,瘟疫像滾雪球一樣來到我的身邊。距離最近時,樓上有一戶疑似病例,隔壁樓有兩戶接觸者,街對面的社區有確診。然而在這些隔離和封鎖接近我之前,在武漢封城當天,我就已經第二次改簽了機票,把回臺灣的時間提早到了大年初二。此前我還改簽過一次,是回家後三四天,我受不了與父母和親戚相處,覺得快要瘋了,於是把14天的回家之旅改成了10天。第二次改,我改成了7天。武漢封城時,我所在的城市還遠遠沒有成為浙江第一,可是看著武漢封城,那天我對朋友說,我怕疫情擴散會影響我回臺灣。那時我還不知道,原來這兩座看似遙遠的城市,有這麼大量的商貿往來。連義大利和法國多溫州人我都是知道的,但就是不知道武漢多溫州人。自然那些人都會回鄉過年,帶著病毒回來,自知的或不自知的。大年初二的機票,不夠早,我不夠心狠。當日中午臺灣封關。如果我改到大年初一飛,一切就不同了,然而那是大年初一,回來過年哪可能不過完大年初一。我不夠心狠。
那天是1月26日。我的行李箱在那天合上又打開,到今日沒有再移動過位置,始終在書桌下,好像我隨時要走的樣子。各種出逃我都打算過,但都不能成行。我所痛恨的投胎所決定的國籍,凌駕一切也決定一切,所有學術討論和網路論戰對改變當下的命運都毫無意義,我開始相信,這是命數。我設想自己若還在香港,那麼已經是連續居留的第幾年,距離香港護照還剩幾年。我設想自己若仍在工作沒有讀書,假期也不會允許我有寒假回家14天的行程安排。但其實,我應該設想投胎,那才釜底抽薪。怨怒和自戕的願望不斷上升,恨,恨一切。整個2月,直到3月的第一個星期,我都這樣度過。
然後我好轉了。這座城市的疫情也好轉了。我可以買到百香果、芒果乾和無糖的養樂多。漸漸地,連口罩和酒精也能買到了。但我仍舊不出門,厭惡出門。這城市沒有我的氣息,我在這裡水土不服,沒有朋友,沒有聲音,無處可去,無處想去。所以我想,不可以死在這裡。要死在讓我感到自由的地方,死在喜歡的地方,例如海邊,然後想想,是鯨魚還是鯊魚,會慢慢吃了我。
父母已經不太敢對我提出什麼要求,當然,這也是因為我不再與他們爭吵、發難。我累了,也無計可施了。我不再說要出走,因為瘟疫已經蔓延全球。我不再辯駁,任由他們去相信新聞聯播,相信中國是世上最安全的國家,from now and forever。我們達成了一種表面的相安無事,把生活空間區隔成三塊,各自生活著,只是一起吃飯。在這個長年沒有我氣息的房子裡,我徵用了一間儲物室來作為我的書房。然而最讓我感到安全的房間,還是臥室。最自由的時空是在夢裡,昨夜我夢見一個很好的人,我們在臺北重逢,他驚訝地看著我走出房間,走向忠孝復興那條滿是小吃店的街。
我過得忘了日期和星期幾,好像是故意的。我發覺自己在製造一種假象,把這段日子視為一個蟲洞或是什麼,而不讓它屬於原本的生命、時間。或是,不承認它屬於原本的生命和時間。我在一種漫長的例外狀態裡醒了又睡,睡了又醒,雖然仍舊活著,仍在進食、上遠距課程、做作業、洗澡、睡覺,然而那好像是另一個我。從原本的我之中,生生地拔起,丟到一個躲避了十年的地方和家庭,然後困在這裡。
不少人寫文章數算,歷史上曾有什麼瘟疫滅掉了帝國。我卻覺得這場瘟疫,實在是帝國的最大助力。帝國不方便做的事,它全做了。帝國不方便殺的人,它全殺了。多麼省力。到頭來,帝國還可以站出來教全世界要怎麼用數字極權和全方位的人身管控,來進行這唯一正確而古老的隔離,並為之大做文宣,搖身一變為救世主。帝國用瘟疫來提醒我,一首老歌,「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這種例外狀態,可以持續一個月、兩個月而不拖垮我原本就搖搖欲墜的精神,但如果是三個月、四個月、五個月、半年、一年呢?我必須承認這種例外,將成為我新的日常了。
不去想疫情何時能真正受控,不去想歸期,什麼都不想,這樣的日子怕是到頭了。我不能再不去想了。我真的可以在這個地方,這個時空,這個房間,這個城市,這個家庭,如此生活下去嗎?到夏天,到秋天,到冬天?起初我會擔心人們遺忘了我。但也許,最後是我遺忘了人們。我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類呢?我可以自洽地活下去嗎?
所以,請與我說說話。請多與我說說話。不要問我怎麼了,只提醒我,我曾經是怎樣的人類,是怎樣的愛人,怎樣的朋友,怎樣的姐姐和妹妹,怎樣的學生,怎樣的同事,怎樣的貓咪飼主,怎樣的寫作者。然後怎麼辦?我要怎麼辦?不知道。
2020.04.10
這是上一次搬家的時候,被洗衣袋騙進籠子,一臉擔心的馬桶蓋。想到可能跟貓咪分離的許多可能,覺得對不起她,自己也無法平靜。昨晚有厲害的會寵物溝通的姐姐去看馬桶蓋,馬桶蓋說她很想我,害怕我的味道越來越少,也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會等我回去跟她睡覺。時代的野種是人類,是我,誤以為世界和人生可以安定的人是我,可是貓咪是無辜的。馬桶蓋是無辜的,我愛她,我愛小貓咪,但我沒想過,有一天我的愛可能會傷害她。
有一位越南戰爭中流離顛沛的報導人,我叫他威哥。他會說法語英語越南語和中文,會彈吉他。十幾歲的時候,他舉家逃難,姐姐帶著兩隻秋田犬,想一起走,可是沒有辦法。狗狗就這樣失散了。今天我總想起這個故事。越南戰爭也不過是幾十年前的事。更何況當今的世界,也依然充滿戰爭。小貓咪,秋田犬,愛。我憑什麼覺得這些離我很遠呢?
或許人生中最好的年頭,都已經過去。本世紀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以後的每一年我們都會渴望回到前一年。
2020.05.17
瘟疫要將我們推向何方呢?如果不是死亡,那麼是家庭的困獸鬥,是粉紅狂潮和瘋狂資本的國,是離散,是滯留?是一個人類學者的「馬林諾斯基時刻」,還是一場無邊無際的、痛苦的,生活的田野?
2020.09.30
昨天出門的時候,馬桶蓋站在客廳門口靜靜地看著我,眼神純真而疑惑。我習慣性地對她說:「馬桶蓋,姐姐出門咯。很快就回來喔!」說完我才意識到,1月16日,那天我離開的時候,也是這樣對她說的。她也是這樣看著我,目不轉睛地看著,不回答,好像相信了我。真的很對不起。真的很對不起啊馬桶蓋。我以後再也不騙你了。
2020.10.06
清晨醒來,又在想,到底未來該去往何方。想要安心在一個地方生活,究竟有什麼方法?買那裡的房子嗎?考那裡的駕照嗎?在那裡開一間小店,安靜地生活嗎?找到那裡的愛人,然後結婚嗎?錢,護照,總要有一樣。如果什麼都沒有,那怎麼辦?因為你是這世界的alien,是被故土追殺,而離散的人。
2021.12.23
2021年12月23日凌晨,豎立在香港大學校園24年的「國殤之柱」雕塑被清拆。
香港歷史人類學家蕭鳳霞近年用 place-making來分析跨越海陸的亞洲。一個空間和城市的意義,不是被主流歷史觀定義的,當地人在歷史的關鍵節點和進程中,用自己的方式為space賦予生命力,所以space成為place,被記憶。政治外力的介入,經濟與科技的變化,帝國的殖民與傾覆,會一再改變這個空間,但自下而上的實踐也不會停息,歷史在拉扯中前進。國殤之柱曾經豎立在這裡,即使清拆,夷為平地,那塊空地也已經與其他空地不同。那是「國殤之柱曾經豎立的地方」,我們仍然可以說,「我們約在國殤之柱那裡見」,有記憶的人都會知道那是哪裡。你拆得走一件雕塑,拆不走那塊土地,拆不走歷史和記憶。你們的暴力能做到的事,是有限的。
2022.01.04
2022的密度太高,每一天有一個城邦垮掉,每一天有千萬人在面前跌倒,每一天像歷史上的一百年。還有地震、瘟疫接踵而來,只能祈求它不要再奪走任何人。
昨天去醫院處理自己的健康問題,所幸並無大礙,打了一針類固醇之後,好像鬆了一口氣般,睡了十二個小時。醒來,讓人擔心的事又是沒有停過。這麼長的睡眠,很久都沒有過了,中途醒來一次好像夢遊,回一些訊息,又睡去。夢中去了一個遙遠的屋邨,在巴士尾站,我坐在第一排,像螺旋般滑落隧道,才到站。原來那是一個朋友的家。又去一個小島,島上悶熱,有小女孩給我看地上刻的字,是關於香港的某句英文口號,我說不,現在他們都用廣東話拼音來寫這句了。然後我對小女孩說,我要去寄信了,再見。
訂購的貓砂送來了,於是我醒了,發現父母家中有被防疫措施波及的危險,想起昨天我才寄去的藥不知何時會送到。叮囑他們囤積糧食,給車子加油,然後也不再多話。昨晚地震的時候,媽媽說家裡的燈也晃了起來。我們其實這麼近啊。
馬桶蓋睡得很好,又是該買乾糧的時候了。照顧小貓咪也是照顧生活的一部分。記憶和現實交疊,已經離開這麼久的我,也感覺像再離開了一次。我可以留住一點什麼嗎?哪怕是⋯⋯任何一點?因為我是你們的風箏,你們的線永不會斷的。你們拉扯,我就顫抖和疼痛,這是命中註定的事。要做的事還有那麼多,那麼多,除非我也變成馬桶蓋貓咪,否則以後也不可以再睡那麼久了。
2022.02.24
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廈崩塌
保衛她的生活
直到大廈崩塌
最近和一個受訪者聊到,這土地的人們在微小之處,其實生活得十分幸福。但在外人看來,小島像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各種戰爭發生的沙盤推演不斷進行,但也不阻香菜日和貓咪日的到來。於是我向他提起這首歌。
保衛她的生活,需要很多努力,但大廈崩塌只需要幾日。從烏克蘭逃往波蘭的路,也讓人想起在阿富汗機場爬牆的母親。
午餐和兩位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吃飯,戰爭發生時,他們似乎必須參戰,但我只想著逃亡。逃,逃,逃,逃到更安全的地方去,護照、簽證、居留權。幾年前已有一位老師對我說,我總想著避秦,然後又覺得暴政會擴散到全世界,要尋找更安全、最安全的棲身之所,以這樣的推演為底色去想像這個人生與世界⋯⋯他沒有說我應該怎樣,他只覺得我不能總這樣。
昨天,久違地和一位在英國十年的大學同學聊天。因為瘟疫不能剪頭髮,他現在有一根清朝人的小辮子,像某種搶主唱風頭的鼓手。我告訴他我想要的是什麼,我想要自由地去往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但要有一個可以隨時回去的安全的地方。他叫我別想了。通話到一半,他家熱水器壞了,來修的人是土耳其裔,那個社區的常見移民。我們身處的世界本來就是如此,為生存而流散並不是什麼新鮮的事。
最近也去學校辦一些行政事務,順便確認出入境隔離手續的安排。我擔憂著情況會否變得比兩年前更壞,對方說不會的,防疫政策正在放寬,但是,除非打仗,那就沒有辦法了。我說,世界大概無法同時承受兩場戰爭,你也看了烏克蘭的新聞嗎?這個安坐在方形格子辦公座位裡的人,這一刻突然好像離我很近,比從前帶著親切笑容關心我的學業、身體健康(醫療保險)的那些時刻都要近。戰爭,是啊,我們還要考慮的是戰爭。
我的受訪者常常是些有大智慧的人,開頭提到的那一位曾推薦我看佛洛姆的《逃避自由》,今天我終於到圖書館借了書。他推薦的時候,給我講了佛洛姆的某一任妻子在逃避納粹德國途中,在西班牙目睹班雅明自殺,而後雖然逃亡,但最後也自殺的故事。那又是二戰時期知識分子流亡的一個歷史切片。今天的世界距離一百年前又有多遠呢?
我帶著書,買了麵包回家,依然看見貓咪在地毯上等我。我們的生活今天仍然和平,貓咪有溫暖的毯子,眼前沒有血。有人說,烏克蘭的戰爭是某種更糟糕的新世界的開始。是嗎?我也問小貓咪,是嗎?
2023.01.05
日記是幫助人記憶的嗎?
還是讓人從審美上疏離地看向過去的自己?
這個真實,這個要花力氣去看到的縫隙,都讓我太累了。
坐公車回家的時候,我想到一個句子。「每個人都傷痕累累,舔不動彼此的傷口。」我又想起,在SY撿到的那個人。我知道我看得到和捕捉得到,sense得到創傷,是因為我自己也傷得很重。我的傷口是一個泥潭,沼澤地,有許多沾黏,癡在一起。我的人生也可能是一個泥灘,像桃園草漯海邊一樣,有白沙,也有泥潭,裡面有積年的濁水,死去的蚵仔。但是在太陽底下,也變得晶瑩。
2023.07.17
最近幾日,放了一張椅子在馬桶蓋的碗盤旁,每天坐著陪她吃飯20分鐘。有時會把下巴靠在她的腳上,有時把臉埋進她的肚子,摸摸她的頭,跟她說,認真吃飯的小貓咪最棒了。
2024.04.09
高粱釀的血
眼前是磚石砌的牢
腳下是高粱釀的血
頭頂是彈殼無眼
手中是抗命無魂
風馬牛不相及之血緣
天海山不相忘之國族
霧,南風帶來的
雨,東方落下的
酒,鮮紅收割的
「那個被槍決的人,我記得。」
(於金門)
2024.06 臺灣文學基地駐村創作
11 2046
2046之後,我才知道時間是沒有意義的
過去不曾到來
未來反覆重演
無數場大雨從不落下
擊穿那把傘的 只是一場場噩夢
2024.12.15
我就是一邊哭一邊把飯吃完的人。所以我活下來了。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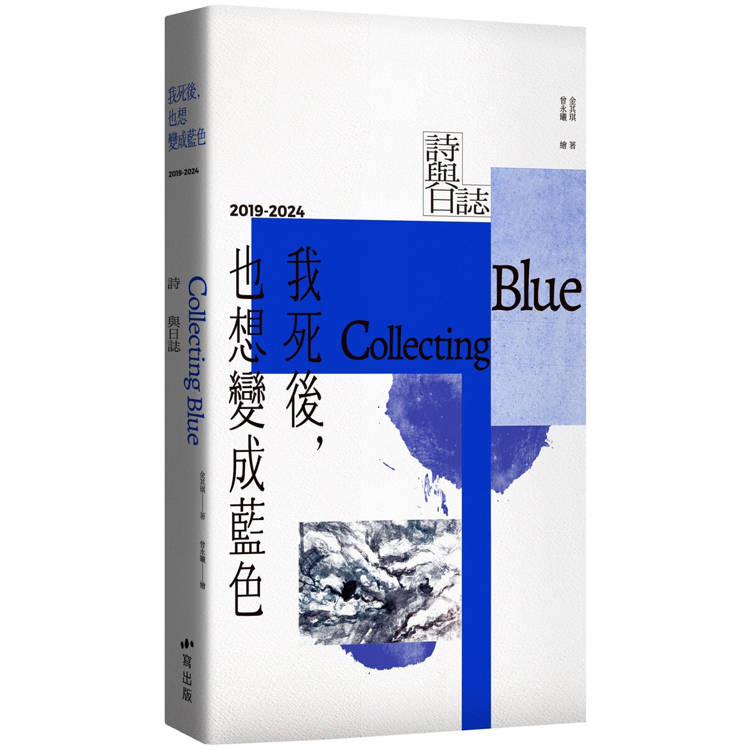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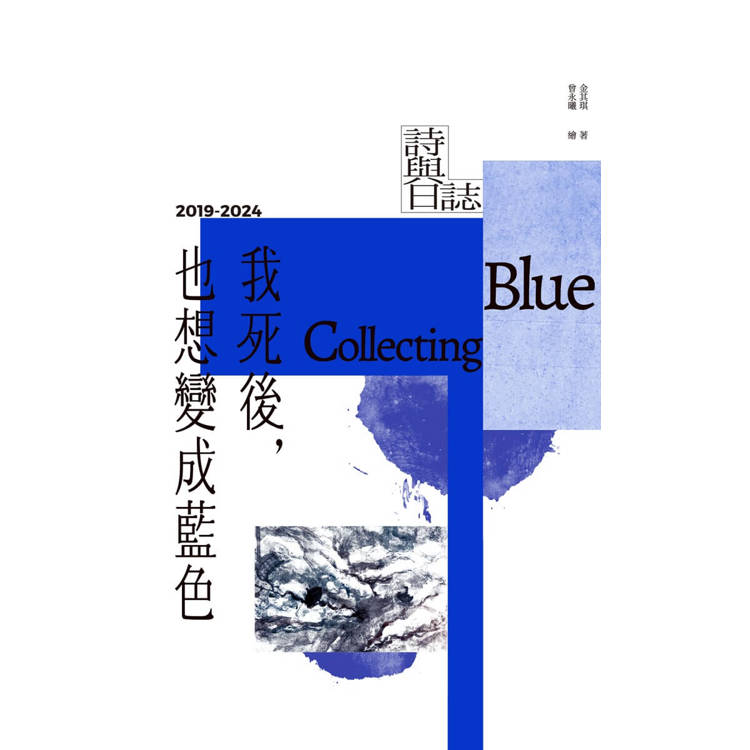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