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謀殺的城市
The City and The City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2009英國科幻協會獎
2010雨果獎
2010亞瑟.克拉克獎
2010世界奇幻獎
2010軌跡獎
2010紅色觸手通俗文藝獎
2011德國庫特拉思維茲文學獎
《洛杉磯時報》、《西雅圖時報》、《出版人週刊》2010年度小說
Amazon.com 2009 上半年嚴選十大好書
犯罪小說前所未見新體驗,有些罪行,比謀殺更殘酷!
洛杉磯時報盛譽:如果菲利普.狄克和雷蒙.錢德勒摯愛的孩子是由卡夫卡扶養長大,那孩子寫出來的作品可能就會像《被謀殺的城市》!
這一區很安靜,但街上充斥著「另一邊」的人、事、物──
我曾對他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嗅而不覺……
這樁案子走到末路了。
泰亞鐸.柏魯,極重案組探員,接獲線報指出一名女子陳屍街頭,凶器下落不明。女屍身分成謎,被藏匿在骯髒的床墊底下,濺滿鮮血的年輕軀體上,一道傷口從下巴撕裂至胸口。辛苦尋獲的廂型車曾經運過女人的屍體,現在則載滿線索。然而訊息們一條條將柏魯拖進死路,直到來自「另一邊」的電話觸發真相,引爆被掩埋的重大罪行──違規跨界。
位於東歐未知角落的雙子城,「貝澤爾」與「烏廓瑪」,如此接近,卻又如此遙遠,長久以來刻意漠視彼此,放任冷漠與罪惡滋生。無論視線交錯,或是身體碰觸,任何跨界接觸在這裡都是「違規跨界」,將喚起凌駕雙子城之上的神祕勢力。然而,女子生前如一抹幽魂,大膽遊走兩城之間,刺探底下不可告人的祕密。
她是誰?不畏犯罪也想完成的事是什麼?有人說她是特務,激進派分子,或滿腦子瘋狂妄想的考古學研究生,種種猜測讓案件陷入一層層謎團,違規跨界也令情治單位避之惟恐不及。僅剩的線索是話筒中顫抖的聲音,柏魯無路可退,獨自追上女人留下的痕跡,深深掘入城市底層,卻發現自己將觸犯的不只是禁忌──
他為真相奮不顧身,但女人捨身的信念究竟為何?畢竟真相並不甜美,無人對此抱持感激;真相像一條惡犬緊咬著人不放,直至撥雲見日,或一同粉絲碎骨。
2010雨果獎
2010亞瑟.克拉克獎
2010世界奇幻獎
2010軌跡獎
2010紅色觸手通俗文藝獎
2011德國庫特拉思維茲文學獎
《洛杉磯時報》、《西雅圖時報》、《出版人週刊》2010年度小說
Amazon.com 2009 上半年嚴選十大好書
犯罪小說前所未見新體驗,有些罪行,比謀殺更殘酷!
洛杉磯時報盛譽:如果菲利普.狄克和雷蒙.錢德勒摯愛的孩子是由卡夫卡扶養長大,那孩子寫出來的作品可能就會像《被謀殺的城市》!
這一區很安靜,但街上充斥著「另一邊」的人、事、物──
我曾對他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嗅而不覺……
這樁案子走到末路了。
泰亞鐸.柏魯,極重案組探員,接獲線報指出一名女子陳屍街頭,凶器下落不明。女屍身分成謎,被藏匿在骯髒的床墊底下,濺滿鮮血的年輕軀體上,一道傷口從下巴撕裂至胸口。辛苦尋獲的廂型車曾經運過女人的屍體,現在則載滿線索。然而訊息們一條條將柏魯拖進死路,直到來自「另一邊」的電話觸發真相,引爆被掩埋的重大罪行──違規跨界。
位於東歐未知角落的雙子城,「貝澤爾」與「烏廓瑪」,如此接近,卻又如此遙遠,長久以來刻意漠視彼此,放任冷漠與罪惡滋生。無論視線交錯,或是身體碰觸,任何跨界接觸在這裡都是「違規跨界」,將喚起凌駕雙子城之上的神祕勢力。然而,女子生前如一抹幽魂,大膽遊走兩城之間,刺探底下不可告人的祕密。
她是誰?不畏犯罪也想完成的事是什麼?有人說她是特務,激進派分子,或滿腦子瘋狂妄想的考古學研究生,種種猜測讓案件陷入一層層謎團,違規跨界也令情治單位避之惟恐不及。僅剩的線索是話筒中顫抖的聲音,柏魯無路可退,獨自追上女人留下的痕跡,深深掘入城市底層,卻發現自己將觸犯的不只是禁忌──
他為真相奮不顧身,但女人捨身的信念究竟為何?畢竟真相並不甜美,無人對此抱持感激;真相像一條惡犬緊咬著人不放,直至撥雲見日,或一同粉絲碎骨。
名人推薦
林斯諺(推理作家)、寵物先生(推理作家)、曲辰(推理小說研究者)、冬陽(推理評論者)、臥斧(文字工作者)、黃羅(推理評論人)、陳國偉(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所助理教授)、伊格言(小說家)、政大推理小說研究社、臺灣大學推理研究社──跨界但不違法推薦!
各界好評
城市是沒有邊界的,每一秒舊的邊界都在崩解,新的邊界都在重建;城市裡無處不是死亡,每一個角落都隨時死去一點點,又重生一點點。柴納以他超乎常人的感性,將城市的內面翻轉過來,抽取出荒謬卻充滿奇想的奇幻絲線,編織出一個偵探行走於都市中的真實圖景。柴納用死亡,標記了城市邊界,也標記了現代人的我們的生存困境與無數的可能。│曲辰 推理小說研究者
一個空間,兩座城市,居民卻彼此視而不見。彷彿近在眼前,卻又天涯咫尺。極為特殊的設定,使得謀殺有了不同的涵義,也讓這本帶有奇幻色彩的推理小說,從解開謎團的固有層次,提昇到反芻人性的另類城市小說。│黃羅 推理評論人
推理小說需要衝突,本作無疑提供了相當好的衝突──一對分屬異國,「彼此糾結卻又若即若離」的雙子城,外來者的闖入,對第三都市的好奇……作者運用架空卻又彷彿貼合現實的國際情勢,出色地塑造謎團,刻劃犯罪,以及其背後的陰謀。精采萬分。│寵物先生 推理作家
柴納的細緻描繪,營造出充滿魅力的謎團:兇手、動機不明的的殺人棄屍案,傳說中的第三城市,以及兩城間的神祕組織。讓人在翻開書的那一刻,不由自主隨著主角的腳步走進這虛擬的城市。│政大推理小說研究社
暢銷作家柴納.米耶維的《被謀殺的城市》幾乎不見奇幻色彩,是一部傑出的警察程序推理小說;以誇張的方式暗喻種族隔離,巧妙地揭開自溺的美好社會假像。│《出版人週刊》星級評論
警察程序推理和都會奇幻的完美融合,喜歡推理和奇幻的讀者千萬別錯過。│《書單》雜誌星級評論
奇詭、複雜,偏執狂般的情節,值回票價!│科克斯書評 星級評論
在這個描述兩座城市的故事中,米耶維營造出既奇幻,看起來又熟悉得讓人不安的世界;謀殺案雖然終將水落石出,謎題卻永遠存在。│Amazon.com
打破類型界線,令人大開眼界。稍微有點特別的故事總會讓人聯想起卡夫卡和歐威爾,但以《被謀殺的城市》來說,這樣的對照絕對名副其實。│《泰晤士報》
米耶維獲獎無數,早已打破類型界線而聞名;在《被謀殺的城市》中,他又成功涉足警察程序推理推理,而且成果輝煌,此書非凡脫俗、魅力十足!│《聖彼得堡時報》
各界好評
城市是沒有邊界的,每一秒舊的邊界都在崩解,新的邊界都在重建;城市裡無處不是死亡,每一個角落都隨時死去一點點,又重生一點點。柴納以他超乎常人的感性,將城市的內面翻轉過來,抽取出荒謬卻充滿奇想的奇幻絲線,編織出一個偵探行走於都市中的真實圖景。柴納用死亡,標記了城市邊界,也標記了現代人的我們的生存困境與無數的可能。│曲辰 推理小說研究者
一個空間,兩座城市,居民卻彼此視而不見。彷彿近在眼前,卻又天涯咫尺。極為特殊的設定,使得謀殺有了不同的涵義,也讓這本帶有奇幻色彩的推理小說,從解開謎團的固有層次,提昇到反芻人性的另類城市小說。│黃羅 推理評論人
推理小說需要衝突,本作無疑提供了相當好的衝突──一對分屬異國,「彼此糾結卻又若即若離」的雙子城,外來者的闖入,對第三都市的好奇……作者運用架空卻又彷彿貼合現實的國際情勢,出色地塑造謎團,刻劃犯罪,以及其背後的陰謀。精采萬分。│寵物先生 推理作家
柴納的細緻描繪,營造出充滿魅力的謎團:兇手、動機不明的的殺人棄屍案,傳說中的第三城市,以及兩城間的神祕組織。讓人在翻開書的那一刻,不由自主隨著主角的腳步走進這虛擬的城市。│政大推理小說研究社
暢銷作家柴納.米耶維的《被謀殺的城市》幾乎不見奇幻色彩,是一部傑出的警察程序推理小說;以誇張的方式暗喻種族隔離,巧妙地揭開自溺的美好社會假像。│《出版人週刊》星級評論
警察程序推理和都會奇幻的完美融合,喜歡推理和奇幻的讀者千萬別錯過。│《書單》雜誌星級評論
奇詭、複雜,偏執狂般的情節,值回票價!│科克斯書評 星級評論
在這個描述兩座城市的故事中,米耶維營造出既奇幻,看起來又熟悉得讓人不安的世界;謀殺案雖然終將水落石出,謎題卻永遠存在。│Amazon.com
打破類型界線,令人大開眼界。稍微有點特別的故事總會讓人聯想起卡夫卡和歐威爾,但以《被謀殺的城市》來說,這樣的對照絕對名副其實。│《泰晤士報》
米耶維獲獎無數,早已打破類型界線而聞名;在《被謀殺的城市》中,他又成功涉足警察程序推理推理,而且成果輝煌,此書非凡脫俗、魅力十足!│《聖彼得堡時報》
編輯推薦
「看見」說起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現在盯著螢幕,看著文字隨著我劈啪敲打鍵盤一個接一個冒出來,同時我也「看見」以我為圓心前方約一百八十度半圓內的所有東西,像是桌上的雜物、盆栽,還有左邊窗外的天空。但畢竟我是個盡責的好員工,自然而然地,最後面那些東西雖然「看見」了,實則「視而不見」。
當然也有非必要但刻意的視而不見,像是有個討厭的傢伙迎面走來時。而在《被謀殺的城市》中,柴納‧米耶維彷彿正是把這種狀況極度放大,創造出一個時時刻刻都必須「用力」對某些人、事、物視而不見的世界。
那是在東歐的某個角落,貝澤爾和烏廓瑪這兩座城市明明在物理上有許多重疊的地方,但因為種種歷史與政治上的因素,兩邊人民必須從小接受訓練,在第一時間先分辨出哪些東西屬於隔壁城,並立刻予以忽略。原本自然的視覺現象,在刻意強調之後,形成一種扭曲但也倒相安無事的生活方式。
這時候偏偏出現一具足跡穿梭兩城的無名女屍,負責查案的柏魯督察不得不進入隔壁城;看見的和視而不見的徹底切換,活像把腦袋內外翻轉。
柴納一向擅長建構城市,這次他不浪費時間在所謂的視而不見到底有多少嘴硬成分糾纏,直接把邊界、政治等議題無聲無息融進情節中,讓讀者跟著柏魯督察的腳步,一邊揭開前所未見的謀殺疑雲,一邊體驗刺激的心靈翻轉之旅。(文/繆思出版編輯郭湘吟)
當然也有非必要但刻意的視而不見,像是有個討厭的傢伙迎面走來時。而在《被謀殺的城市》中,柴納‧米耶維彷彿正是把這種狀況極度放大,創造出一個時時刻刻都必須「用力」對某些人、事、物視而不見的世界。
那是在東歐的某個角落,貝澤爾和烏廓瑪這兩座城市明明在物理上有許多重疊的地方,但因為種種歷史與政治上的因素,兩邊人民必須從小接受訓練,在第一時間先分辨出哪些東西屬於隔壁城,並立刻予以忽略。原本自然的視覺現象,在刻意強調之後,形成一種扭曲但也倒相安無事的生活方式。
這時候偏偏出現一具足跡穿梭兩城的無名女屍,負責查案的柏魯督察不得不進入隔壁城;看見的和視而不見的徹底切換,活像把腦袋內外翻轉。
柴納一向擅長建構城市,這次他不浪費時間在所謂的視而不見到底有多少嘴硬成分糾纏,直接把邊界、政治等議題無聲無息融進情節中,讓讀者跟著柏魯督察的腳步,一邊揭開前所未見的謀殺疑雲,一邊體驗刺激的心靈翻轉之旅。(文/繆思出版編輯郭湘吟)
序/導讀
導讀
城&城之「夕中卜」文
林翰昌
米耶維完整形塑出以往可能只會在波赫士或卡夫卡短篇中概略提及闡述的實驗性地理(建築)結構,添加當代時空背景血肉敷陳後,真正把形色人物擺在裡頭走跳討生活;令人難以置信的基本前提,也就因此具備了隨時可能躍上報紙國際版面,更難保不會有哪家新聞臺採訪小組前往製作專題的真實感受。
雙城之間的「無視」絕對是閱讀本書必經的「概念突破」。局外人讀者跟隨柏魯督察在貝澤爾跑過幾章之後,恐怕也會陪同暗譙受害者父母白目的誤闖行徑。偏偏到了故事中段,柏魯因任務需要來到烏廓瑪,原本好不容易建構完成的城市認知體系又得完全翻轉,變成不可視的對象。連自己家園都得無視的片段,不啻帶給讀者最強烈的心理衝擊。直到最後傳說中的跨界監察出動介入,在實質意義上終於回歸「全視」觀點的讀者,竟也需要花上幾個章節重新調適。整個「實驗」歷程,足以讓我們一方面反思自己多麼容易受到外在框架所支使左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文化背景所構築的框架,其影響力是多麼無遠弗屆。
城&城之「夕中卜」文
林翰昌
米耶維完整形塑出以往可能只會在波赫士或卡夫卡短篇中概略提及闡述的實驗性地理(建築)結構,添加當代時空背景血肉敷陳後,真正把形色人物擺在裡頭走跳討生活;令人難以置信的基本前提,也就因此具備了隨時可能躍上報紙國際版面,更難保不會有哪家新聞臺採訪小組前往製作專題的真實感受。
雙城之間的「無視」絕對是閱讀本書必經的「概念突破」。局外人讀者跟隨柏魯督察在貝澤爾跑過幾章之後,恐怕也會陪同暗譙受害者父母白目的誤闖行徑。偏偏到了故事中段,柏魯因任務需要來到烏廓瑪,原本好不容易建構完成的城市認知體系又得完全翻轉,變成不可視的對象。連自己家園都得無視的片段,不啻帶給讀者最強烈的心理衝擊。直到最後傳說中的跨界監察出動介入,在實質意義上終於回歸「全視」觀點的讀者,竟也需要花上幾個章節重新調適。整個「實驗」歷程,足以讓我們一方面反思自己多麼容易受到外在框架所支使左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文化背景所構築的框架,其影響力是多麼無遠弗屆。
試閱
發現屍體後的那個星期一,我接到一通電話。
「柏魯。」停頓很久後,我又報了一次名字,電話那頭覆述了一次。
「柏魯督察。」
「能為你效勞嗎?」
「我不曉得你能幫我什麼。我幾天前本來還指望你能幫我,所以一直試圖聯絡你。但我應該比較幫得上忙。」說話的男子操外國口音。
「什麼?很抱歉,請大聲一點──線路收訊很糟。」
男子的聲音受到靜電干擾,聽起來像是正在用古老機器錄音一樣。我無法確定聲音延遲是因為線路的關係,還是他需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回應我說的話。他一口流利但古怪的貝澤爾語,帶著老派的抑揚頓挫。我說:「你是誰?有何貴幹?」
「我有消息要告訴你。」
「你打過我們的服務專線嗎?」
「我不能打去那裡。」他是從國外打來的。貝澤爾落後的電話轉接服務傳送的回饋信號很有特色。
「癥結就在這兒。」
「你怎麼知道我的號碼?」
「柏魯,閉嘴。」我再次希望電話能有來電顯示功能。我坐直身子。「Google來的。報上有你的名字,那女孩的調查由你負責。要透過助理拿到你的號碼並不難。你到底要不要我幫忙?」
我還真的環視了四周,卻沒看到半個人。「你從哪裡打來的?」我掀開百葉窗的葉片,想看街上是不是有人在監視我。結果當然沒有。
「少來,柏魯。你知道我從哪裡打給你的。」
我做著筆記,這種腔調我認得。
他是從烏廓瑪打來的。
「既然知道我人所在的位置,請勿詢問我的名字。」
「跟我通話並不犯法。」
「你不知道我要跟你說什麼才會這麼說。你不知道我要跟你說的是什麼。事情是──」他突然打住。我聽到他手摀住話筒,喃喃自語了一會兒。「聽著,柏魯,我不知道你對這種事情採取怎樣的立場,但我認為從另一個國家打電話$給你,根本就是瘋狂的行為,也是一種侮辱。」
「我不談政治的。聽著,如果你想說……」我最後一句話是用的是烏廓瑪的伊利坦語。
「好吧。」他用帶有舊式伊利坦語字尾變化的貝澤爾語打斷我。「反正表面上都是同一種該死的語言。」我記下他說了這句話。「現在閉嘴。想聽我的消息嗎?」
「當然。」我站著,伸手翻找,設法找出追蹤這通電話的方法。
我的電話沒有裝設追蹤裝置,而就算我能在跟他通話的同時也聯絡上電信局,透過貝澤爾電信局追蹤也可能得花上好幾個小時。
「那個女人,就你們正在……她死了,對吧?她一定死了。我認識她。」
「很遺憾……」他沉默了幾秒,我只能吐出這句話。
「我已經認識她……很久以前認識她的。柏魯,我想幫你,但並不是因為你是條子。上天明鑑,我不承認你的權力。但是如果瑪爾雅是被……如果是他殺的話,我在乎的人可能就有危險了,當然也包括我最在乎的人,也就是我自己。而且應該有人替她……好吧,我知道的一切是這樣的──
「她說自己叫做瑪爾雅,我是在這裡認識她的,烏廓爾這裡。我會盡可能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但我知道的一向不多,因為不關我的事。她是外國人。我因為政治活動和她撘上線,她非常狂熱,懂嗎?她所狂熱的跟我一開始猜想的不一樣。她學識豐富,屬於不浪費時間的那種人。」
「聽著。」我說。
「我能說的都告訴你了。她住在這裡。」
「但是她人在貝澤爾。」
「拜託,」他很生氣,「拜託,沒有官方許可。她不能拿到許可。她就算跑到了對面,我們也得堅持她人在這邊。去問問牢裡那些激進分子,會有人認識她的。她什麼地方都去過,所有的地下組織,兩邊一定都去過。上窮碧落下黃泉只為了全盤皆知。而她也真的做到了。以上。」
「你怎麼知道她被殺了?」我聽到他發出噓聲。
發現屍體後的那個星期一,我接到一通電話。
「柏魯。」停頓很久後,我又報了一次名字,電話那頭覆述了一次。
「柏魯督察。」
「能為你效勞嗎?」
「我不曉得你能幫我什麼。我幾天前本來還指望你能幫我,所以一直試圖聯絡你。但我應該比較幫得上忙。」說話的男子操外國口音。
「什麼?很抱歉,請大聲一點──線路收訊很糟。」
男子的聲音受到靜電干擾,聽起來像是正在用古老機器錄音一樣。我無法確定聲音延遲是因為線路的關係,還是他需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回應我說的話。他一口流利但古怪的貝澤爾語,帶著老派的抑揚頓挫。我說:「你是誰?有何貴幹?」
「我有消息要告訴你。」
「你打過我們的服務專線嗎?」
「我不能打去那裡。」他是從國外打來的。貝澤爾落後的電話轉接服務傳送的回饋信號很有特色。
「癥結就在這兒。」
「你怎麼知道我的號碼?」
「柏魯,閉嘴。」我再次希望電話能有來電顯示功能。我坐直身子。「Google來的。報上有你的名字,那女孩的調查由你負責。要透過助理拿到你的號碼並不難。你到底要不要我幫忙?」
我還真的環視了四周,卻沒看到半個人。「你從哪裡打來的?」我掀開百葉窗的葉片,想看街上是不是有人在監視我。結果當然沒有。
「少來,柏魯。你知道我從哪裡打給你的。」
我做著筆記,這種腔調我認得。
他是從烏廓瑪打來的。
「既然知道我人所在的位置,請勿詢問我的名字。」
「跟我通話並不犯法。」
「你不知道我要跟你說什麼才會這麼說。你不知道我要跟你說的是什麼。事情是──」他突然打住。我聽到他手摀住話筒,喃喃自語了一會兒。「聽著,柏魯,我不知道你對這種事情採取怎樣的立場,但我認為從另一個國家打電話$給你,根本就是瘋狂的行為,也是一種侮辱。」
「我不談政治的。聽著,如果你想說……」我最後一句話是用的是烏廓瑪的伊利坦語。
「好吧。」他用帶有舊式伊利坦語字尾變化的貝澤爾語打斷我。「反正表面上都是同一種該死的語言。」我記下他說了這句話。「現在閉嘴。想聽我的消息嗎?」
「當然。」我站著,伸手翻找,設法找出追蹤這通電話的方法。
我的電話沒有裝設追蹤裝置,而就算我能在跟他通話的同時也聯絡上電信局,透過貝澤爾電信局追蹤也可能得花上好幾個小時。
「那個女人,就你們正在……她死了,對吧?她一定死了。我認識她。」
「很遺憾……」他沉默了幾秒,我只能吐出這句話。
「我已經認識她……很久以前認識她的。柏魯,我想幫你,但並不是因為你是條子。上天明鑑,我不承認你的權力。但是如果瑪爾雅是被……如果是他殺的話,我在乎的人可能就有危險了,當然也包括我最在乎的人,也就是我自己。而且應該有人替她……好吧,我知道的一切是這樣的──
「她說自己叫做瑪爾雅,我是在這裡認識她的,烏廓爾這裡。我會盡可能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但我知道的一向不多,因為不關我的事。她是外國人。我因為政治活動和她撘上線,她非常狂熱,懂嗎?她所狂熱的跟我一開始猜想的不一樣。她學識豐富,屬於不浪費時間的那種人。」
「聽著。」我說。
「我能說的都告訴你了。她住在這裡。」
「但是她人在貝澤爾。」
「拜託,」他很生氣,「拜託,沒有官方許可。她不能拿到許可。她就算跑到了對面,我們也得堅持她人在這邊。去問問牢裡那些激進分子,會有人認識她的。她什麼地方都去過,所有的地下組織,兩邊一定都去過。上窮碧落下黃泉只為了全盤皆知。而她也真的做到了。以上。」
「你怎麼知道她被殺了?」我聽到他發出噓聲。(待續)「柏魯,會這麼問就代表你是個笨蛋,而我根本在浪費時間。我是看到照片認出她的,柏魯。如果我覺得這通電話沒有必要又不重要,我還會打嗎?你認為我是怎麼知道的?當然是因為我看到那張該死的海報啊。」(註:為找尋女子身分,警局發出懸賞海報。)
他逕自掛了電話。我的話筒還貼在耳邊沒有放下,心想他還會打來。
我看到海報。我低頭看著記事本,除了他提供的資料,我只寫下胡扯、胡扯、胡扯。
我沒在辦公室多做停留。「泰亞鐸,還好嗎?」蓋德能說道。「你看起來……」我知道自己的臉色一定很糟。我在人行道上的咖啡攤喝了一杯濃咖啡,aj Tyrko,土耳其口味,這是個錯誤的決定,因為反而更焦慮。
那天回家途中很難奉行邊界,也很難只看該看的,不該看的則視而不見,對於這樣的一天來說或許也沒什麼好意外的。圍繞在我身邊的都不是貝澤爾人,我 緩緩走過人潮擁擠,在貝澤爾卻沒什麼人的地區。我只專心看著屬於我這邊的石砌建築──大教堂、酒吧、原本是學校的磚造裝飾──這裡是我生長的地方。其他一 律視而不見,或是努力不去看。
我那天晚上撥了電話給歷史學者莎芮思卡。她不僅床上功夫了得,有時也會就我辦的案子提出討論,見解精闢。我撥了兩次電話,兩次都在接通之前掛斷。不想把她拖下水的原因有二,偵察期間不得洩漏案情是其一,其二就是不想讓她成為違規越界的共犯。
我又回到記事本上的胡扯、胡扯、胡扯。最後買了兩瓶酒回家慢慢喝──也吃了一點晚餐墊胃,像是橄欖、起司、香腸等──直到喝完為止。我做了很多沒 用的筆記,還畫了晦澀難解的圖表佯裝有找到解決方法的可能,但是情況暨謎題本身其實很清楚。我或許不幸碰上無意義又硬拗的惡作劇,但看來又不太可能。打電 話來的男子說的比較可能是實話。
這個案子裡,有人給了我關鍵的線索,幫助我掌握和芙拉娜─瑪爾雅密切相關的消息。有人告訴我該去哪追蹤誰以獲得進一步的消息。接下來就是我的工 作。但要是被發現我的消息從哪來,那就定不了罪了。更麻煩的是,我追查這個案子本身就已經犯法;而比犯法更糟的是我不僅會違反貝澤爾的法律,還很有可能違 規跨界。
提供消息給我的人根本不該看到海報才對,因為海報並未出現在他的國家。他也根本不該告訴我,讓我淪為共犯。他提供的消息在貝澤爾是恐怖的過敏原 ──只是在我腦中放進這個消息,就已經造成創傷。我是共犯。木已成舟。(或許是因為喝醉了,我並沒想到他根本沒必要告訴我他如何得知此消息,也沒考慮到他 這麼做必有箇中緣由。)
我沒這麼做;但誰不想把那次通話的筆記燒掉或放入碎紙機銷毀?我還是沒這麼做。我在廚房餐桌前坐到很晚,面對著攤開的記事本,時不時毫無建設性地 重複寫著:胡扯、胡扯。我放了音樂:一張名為《小小火車小姐》的合唱專輯,收錄范?莫理森在一九八七年巡迴演唱時與可莎?雅科夫同臺合唱的曲子,後者素有 貝澤爾鄔恩?考兒蓀的美譽。我又多喝了幾杯,把瑪爾雅?芙拉娜?無名女屍?外國人?笛泰兒?違規跨界者的照片放在筆記旁邊。
沒有人認識她。老天若有眼,她或許根本是非法進入貝澤爾,即使波科斯特村完全屬於貝澤爾所有。她可能是被拖去那裡的。發現屍體的孩子、整個調查過 程都可能已經違規跨界。我不該為了查案而讓自己遭到牽連。或許我該做的就是不再參與調查,任她的屍身腐爛。假裝自己會這麼做讓我得以暫時逃避現實,但是到 頭來我還是會盡忠職守,儘管辦這個案子意味著觸犯一條法規──一個存在於兩邊的協議;比起他們付錢請我執行的所有法律,那個協議還更根本多了。 (待續)「柏魯,會這麼問就代表你是個笨蛋,而我根本在浪費時間。我是看到照片認出她的,柏魯。如果我覺得這通電話沒有必要又不重要,我還會打嗎?你認為我是怎麼知道的?當然是因為我看到那張該死的海報啊。」(註:為找尋女子身分,警局發出懸賞海報。)
他逕自掛了電話。我的話筒還貼在耳邊沒有放下,心想他還會打來。
我看到海報。我低頭看著記事本,除了他提供的資料,我只寫下胡扯、胡扯、胡扯。
我沒在辦公室多做停留。「泰亞鐸,還好嗎?」蓋德能說道。「你看起來……」我知道自己的臉色一定很糟。我在人行道上的咖啡攤喝了一杯濃咖啡,aj Tyrko,土耳其口味,這是個錯誤的決定,因為反而更焦慮。
那天回家途中很難奉行邊界,也很難只看該看的,不該看的則視而不見,對於這樣的一天來說或許也沒什麼好意外的。圍繞在我身邊的都不是貝澤爾人,我 緩緩走過人潮擁擠,在貝澤爾卻沒什麼人的地區。我只專心看著屬於我這邊的石砌建築──大教堂、酒吧、原本是學校的磚造裝飾──這裡是我生長的地方。其他一 律視而不見,或是努力不去看。
我那天晚上撥了電話給歷史學者莎芮思卡。她不僅床上功夫了得,有時也會就我辦的案子提出討論,見解精闢。我撥了兩次電話,兩次都在接通之前掛斷。不想把她拖下水的原因有二,偵察期間不得洩漏案情是其一,其二就是不想讓她成為違規越界的共犯。
我又回到記事本上的胡扯、胡扯、胡扯。最後買了兩瓶酒回家慢慢喝──也吃了一點晚餐墊胃,像是橄欖、起司、香腸等──直到喝完為止。我做了很多沒 用的筆記,還畫了晦澀難解的圖表佯裝有找到解決方法的可能,但是情況暨謎題本身其實很清楚。我或許不幸碰上無意義又硬拗的惡作劇,但看來又不太可能。打電 話來的男子說的比較可能是實話。
這個案子裡,有人給了我關鍵的線索,幫助我掌握和芙拉娜─瑪爾雅密切相關的消息。有人告訴我該去哪追蹤誰以獲得進一步的消息。接下來就是我的工 作。但要是被發現我的消息從哪來,那就定不了罪了。更麻煩的是,我追查這個案子本身就已經犯法;而比犯法更糟的是我不僅會違反貝澤爾的法律,還很有可能違 規跨界。
提供消息給我的人根本不該看到海報才對,因為海報並未出現在他的國家。他也根本不該告訴我,讓我淪為共犯。他提供的消息在貝澤爾是恐怖的過敏原 ──只是在我腦中放進這個消息,就已經造成創傷。我是共犯。木已成舟。(或許是因為喝醉了,我並沒想到他根本沒必要告訴我他如何得知此消息,也沒考慮到他 這麼做必有箇中緣由。)
我沒這麼做;但誰不想把那次通話的筆記燒掉或放入碎紙機銷毀?我還是沒這麼做。我在廚房餐桌前坐到很晚,面對著攤開的記事本,時不時毫無建設性地 重複寫著:胡扯、胡扯。我放了音樂:一張名為《小小火車小姐》的合唱專輯,收錄范?莫理森在一九八七年巡迴演唱時與可莎?雅科夫同臺合唱的曲子,後者素有 貝澤爾鄔恩?考兒蓀的美譽。我又多喝了幾杯,把瑪爾雅?芙拉娜?無名女屍?外國人?笛泰兒?違規跨界者的照片放在筆記旁邊。
沒有人認識她。老天若有眼,她或許根本是非法進入貝澤爾,即使波科斯特村完全屬於貝澤爾所有。她可能是被拖去那裡的。發現屍體的孩子、整個調查過 程都可能已經違規跨界。我不該為了查案而讓自己遭到牽連。或許我該做的就是不再參與調查,任她的屍身腐爛。假裝自己會這麼做讓我得以暫時逃避現實,但是到 頭來我還是會盡忠職守,儘管辦這個案子意味著觸犯一條法規──一個存在於兩邊的協議;比起他們付錢請我執行的所有法律,那個協議還更根本多了。
我們小時候都玩過「我是跨界監察局大人」這個遊戲。我從沒愛玩過,但輪到我玩的時候還是會偷偷跨過粉筆畫的界線,然後朋友就會張牙舞爪地來追我。 如果換成我執法的話,我也會去追別人。小孩常玩的遊戲,除了「我是跨界監察局大人」,以及把從土裡挖出來的樹枝和卵石當作貝澤爾魔法錢幣以外,還有一種融 合捉人和捉迷藏的遊戲,叫做「揪出躲在城與城之間的神祕客」[注4:神祕客在本書專指曾經犯過違規跨界卻能成功避開跨界監察局的追捕,隱身在城與城之間的 人]。
沒有一種宗教理論會極端到讓人找不到。貝澤爾有一派人信奉跨界監察局。考慮到牽涉其中的多方勢力,這種宗教雖然不像話卻也不出人意表。沒有法律可以制裁這派信眾,儘管此宗教的本質會讓所有人焦躁不安。性好腥羶色的電視節目也一直以此為主題大談特談。
凌晨三點,我醉了卻非常清醒,細看著貝澤爾的街道(更多時候看的是──交錯重疊區)。我聽得到狗吠聲和一匹流浪狼嚎叫了一兩聲。桌上滿是報紙──充斥著像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兩派意見。玻璃酒杯的環形光圈映在瑪爾雅的臉上,也投射在寫滿胡扯、胡扯、胡扯的違法筆記之上。
睡不著對我來說稀鬆平常。莎芮思卡和碧薩雅睡到一半出臥房到浴室上廁所時,都很習慣看到我坐在廚房餐桌前看書,猛嚼口香糖的,嚼到舌頭都要長出水 泡了(我不會重拾香菸)。要不然就是看到我凝視著這個城市以及另一座城市的夜景(無可避免的,嘴上說視而不見,卻又深受其燈火感動)。
莎芮思卡曾笑過我。「看看你這副模樣,」她並非全然不帶感情地說道:「像隻貓頭鷹坐在那兒,也像一臉憂鬱的石像鬼,你這過度感傷的傢伙。你根本什 麼都沒有參透,只單純因為現在是晚上,有些建築物開了燈而已。」她可不是特地起床來尋我開心的。任何想法我都來者不拒,就算是假的也好,所以我往窗外望 去。
我們小時候都玩過「我是跨界監察局大人」這個遊戲。我從沒愛玩過,但輪到我玩的時候還是會偷偷跨過粉筆畫的界線,然後朋友就會張牙舞爪地來追我。 如果換成我執法的話,我也會去追別人。小孩常玩的遊戲,除了「我是跨界監察局大人」,以及把從土裡挖出來的樹枝和卵石當作貝澤爾魔法錢幣以外,還有一種融 合捉人和捉迷藏的遊戲,叫做「揪出躲在城與城之間的神祕客」[注4:神祕客在本書專指曾經犯過違規跨界卻能成功避開跨界監察局的追捕,隱身在城與城之間的 人]。
沒有一種宗教理論會極端到讓人找不到。貝澤爾有一派人信奉跨界監察局。考慮到牽涉其中的多方勢力,這種宗教雖然不像話卻也不出人意表。沒有法律可以制裁這派信眾,儘管此宗教的本質會讓所有人焦躁不安。性好腥羶色的電視節目也一直以此為主題大談特談。
凌晨三點,我醉了卻非常清醒,細看著貝澤爾的街道(更多時候看的是──交錯重疊區)。我聽得到狗吠聲和一匹流浪狼嚎叫了一兩聲。桌上滿是報紙──充斥著像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兩派意見。玻璃酒杯的環形光圈映在瑪爾雅的臉上,也投射在寫滿胡扯、胡扯、胡扯的違法筆記之上。
睡不著對我來說稀鬆平常。莎芮思卡和碧薩雅睡到一半出臥房到浴室上廁所時,都很習慣看到我坐在廚房餐桌前看書,猛嚼口香糖的,嚼到舌頭都要長出水 泡了(我不會重拾香菸)。要不然就是看到我凝視著這個城市以及另一座城市的夜景(無可避免的,嘴上說視而不見,卻又深受其燈火感動)。
莎芮思卡曾笑過我。「看看你這副模樣,」她並非全然不帶感情地說道:「像隻貓頭鷹坐在那兒,也像一臉憂鬱的石像鬼,你這過度感傷的傢伙。你根本什 麼都沒有參透,只單純因為現在是晚上,有些建築物開了燈而已。」她可不是特地起床來尋我開心的。任何想法我都來者不拒,就算是假的也好,所以我往窗外望去。
飛機飛過雲層上方。摩天大樓的玻璃帷幕外牆,映照出大教堂塔尖的鮮明倒影。邊界另一端的建築物狀似新月向後彎曲,可見霓虹燈此起彼落閃爍。我試著把電腦連上網路好查些資料,但只有撥接連線可用,實在令人洩氣,所以我放棄了。
「細節容後稟述。」我想我確實大聲說出了這句話。我記下更多筆記。結果最後還是打了寇葳的分機留言給她。
「莉茲拜,我有個想法。」每次我說謊就會本能地說得太多也太快。我盡量逼自己像沒事一樣地跟她說話,但她可不笨。
「時間不早了。我有件事要交代妳,因為我明天可能不會進來。謹守轄區一直都沒有進展,我們原本以為有人會指認出她的想法顯然錯了。我們已經把照片 分發到各轄區,所以如果她只是個離開自家警察轄區的街頭妓女,我們也許還算幸運,但是我希望繼續查案的同時也能朝其他幾個方向調查。
「聽著,我想她並不在她所屬的區域,情況古怪,我們又不能引起注意。我跟一個反對黨分隊的友人談過,他說他監視的人都行事隱密,全是納粹、左派分 子、統派分子之類的。總之,這勾起我的好奇心,想知道什麼樣的人會隱藏身分;我想在時間允許的狀況下追一下這條線索。我想──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記的…… 好,就從統派分子開始好了。
「找奇人異事組談一談,看看透過住址、分會能查到什麼──這方面我所知不多。去沈瓦的辦公室找他,跟他說妳在幫我辦一個案子。盡可能過濾每一個 人,帶照片去,看有沒有人認得她。不用我說,妳也應該清楚那些人的態度肯定會很怪──他們不會希望跟妳有所接觸。盡力就好。我的手機不會關機,隨時保持聯 繫。如我剛才所說,我今天不進辦公室。明天再通電話吧。就這樣,再見。」
「真糟。」我想我這句話也說得很大聲。
說完之後,我打電話留言給行政部的塔絲金?希若許。之前請她協助過三、四個案子繁瑣的行政程序;我特別記下她的分機,也一直跟她保持聯繫。她的工作表現沒話說。
「塔絲金,我是泰亞鐸?柏魯。請妳明天或是有空的時候打手機給我,我想知道如果我想把一個案子交給監督委員會審理,有什麼必要的程序。又假設我想 把案子交給Breach審的話呢?」我畏縮了一下,笑出聲。「塔絲,先別張揚,好嗎?謝啦。讓我知道我應該做什麼,妳有甚麼方便的圈內人竅門也請跟我說。 謝了。」
那個提供線索、態度惡劣的男子所說的話並沒有多大問題。我照抄並標出一些重點詞彙:
語言相同
是否承認我們的主權──否
城市兩邊
這一切都說得通了,包括他為什麼選擇打給我、為什麼是這件案子,還有他看到了什麼,以及他居然看得到。雖然風險極高卻還是阻止不了他打這通電話。 他會出此下策主要是出於恐懼,害怕瑪爾雅?芙拉娜的死可能會對他帶來任何潛在的影響。他說他在貝澤爾的同夥很有可能見過瑪爾雅,以及她當時可能就不會奉行 界線了。如果真的有貝澤爾的麻煩分子共謀犯下那種罪、不顧那種禁忌,一定是打電話給我的男子與他的同夥。他們顯然都是統派分子。
我轉頭回顧夜晚燈火通明的城市時,莎芮思卡在我的心裡挖苦著我,這次我朝著鄰城看去。就算違法我還是看了。誰不會偶爾這樣做呢?那邊有著我不該看 到的加油站、懸掛骨狀鐵框廣告招牌的律師事務所。街上至少有一個行人不是貝澤爾人──從穿著、膚色、走路方式就看得出來,而我看著他。
我把視線轉向窗外幾公尺遠的鐵道並等候著,因為我知道最後會有一班晚班車進站。我看著它快速通過,車窗閃閃發亮,也與幾名乘客四目相接,只有極少 數人回望我,而且嚇到了。但是他們的蹤影旋即消失在連綿的屋簷上:這只是小小犯了規,不是他們的錯。他們或許不會內疚太久,也可能不會記得這次的凝望。我 一直都想住在可以看到外地列車的地方。 飛機飛過雲層上方。摩天大樓的玻璃帷幕外牆,映照出大教堂塔尖的鮮明倒影。邊界另一端的建築物狀似新月向後彎曲,可見霓虹燈此起彼落閃爍。我試著把電腦連上網路好查些資料,但只有撥接連線可用,實在令人洩氣,所以我放棄了。
「細節容後稟述。」我想我確實大聲說出了這句話。我記下更多筆記。結果最後還是打了寇葳的分機留言給她。
「莉茲拜,我有個想法。」每次我說謊就會本能地說得太多也太快。我盡量逼自己像沒事一樣地跟她說話,但她可不笨。
「時間不早了。我有件事要交代妳,因為我明天可能不會進來。謹守轄區一直都沒有進展,我們原本以為有人會指認出她的想法顯然錯了。我們已經把照片 分發到各轄區,所以如果她只是個離開自家警察轄區的街頭妓女,我們也許還算幸運,但是我希望繼續查案的同時也能朝其他幾個方向調查。
「聽著,我想她並不在她所屬的區域,情況古怪,我們又不能引起注意。我跟一個反對黨分隊的友人談過,他說他監視的人都行事隱密,全是納粹、左派分 子、統派分子之類的。總之,這勾起我的好奇心,想知道什麼樣的人會隱藏身分;我想在時間允許的狀況下追一下這條線索。我想──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記的…… 好,就從統派分子開始好了。
「找奇人異事組談一談,看看透過住址、分會能查到什麼──這方面我所知不多。去沈瓦的辦公室找他,跟他說妳在幫我辦一個案子。盡可能過濾每一個 人,帶照片去,看有沒有人認得她。不用我說,妳也應該清楚那些人的態度肯定會很怪──他們不會希望跟妳有所接觸。盡力就好。我的手機不會關機,隨時保持聯 繫。如我剛才所說,我今天不進辦公室。明天再通電話吧。就這樣,再見。」
「真糟。」我想我這句話也說得很大聲。
說完之後,我打電話留言給行政部的塔絲金?希若許。之前請她協助過三、四個案子繁瑣的行政程序;我特別記下她的分機,也一直跟她保持聯繫。她的工作表現沒話說。
「塔絲金,我是泰亞鐸?柏魯。請妳明天或是有空的時候打手機給我,我想知道如果我想把一個案子交給監督委員會審理,有什麼必要的程序。又假設我想 把案子交給Breach審的話呢?」我畏縮了一下,笑出聲。「塔絲,先別張揚,好嗎?謝啦。讓我知道我應該做什麼,妳有甚麼方便的圈內人竅門也請跟我說。 謝了。」
那個提供線索、態度惡劣的男子所說的話並沒有多大問題。我照抄並標出一些重點詞彙:
語言相同
是否承認我們的主權──否
城市兩邊
這一切都說得通了,包括他為什麼選擇打給我、為什麼是這件案子,還有他看到了什麼,以及他居然看得到。雖然風險極高卻還是阻止不了他打這通電話。 他會出此下策主要是出於恐懼,害怕瑪爾雅?芙拉娜的死可能會對他帶來任何潛在的影響。他說他在貝澤爾的同夥很有可能見過瑪爾雅,以及她當時可能就不會奉行 界線了。如果真的有貝澤爾的麻煩分子共謀犯下那種罪、不顧那種禁忌,一定是打電話給我的男子與他的同夥。他們顯然都是統派分子。
我轉頭回顧夜晚燈火通明的城市時,莎芮思卡在我的心裡挖苦著我,這次我朝著鄰城看去。就算違法我還是看了。誰不會偶爾這樣做呢?那邊有著我不該看 到的加油站、懸掛骨狀鐵框廣告招牌的律師事務所。街上至少有一個行人不是貝澤爾人──從穿著、膚色、走路方式就看得出來,而我看著他。
我把視線轉向窗外幾公尺遠的鐵道並等候著,因為我知道最後會有一班晚班車進站。我看著它快速通過,車窗閃閃發亮,也與幾名乘客四目相接,只有極少 數人回望我,而且嚇到了。但是他們的蹤影旋即消失在連綿的屋簷上:這只是小小犯了規,不是他們的錯。他們或許不會內疚太久,也可能不會記得這次的凝望。我 一直都想住在可以看到外地列車的地方。
「柏魯。」停頓很久後,我又報了一次名字,電話那頭覆述了一次。
「柏魯督察。」
「能為你效勞嗎?」
「我不曉得你能幫我什麼。我幾天前本來還指望你能幫我,所以一直試圖聯絡你。但我應該比較幫得上忙。」說話的男子操外國口音。
「什麼?很抱歉,請大聲一點──線路收訊很糟。」
男子的聲音受到靜電干擾,聽起來像是正在用古老機器錄音一樣。我無法確定聲音延遲是因為線路的關係,還是他需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回應我說的話。他一口流利但古怪的貝澤爾語,帶著老派的抑揚頓挫。我說:「你是誰?有何貴幹?」
「我有消息要告訴你。」
「你打過我們的服務專線嗎?」
「我不能打去那裡。」他是從國外打來的。貝澤爾落後的電話轉接服務傳送的回饋信號很有特色。
「癥結就在這兒。」
「你怎麼知道我的號碼?」
「柏魯,閉嘴。」我再次希望電話能有來電顯示功能。我坐直身子。「Google來的。報上有你的名字,那女孩的調查由你負責。要透過助理拿到你的號碼並不難。你到底要不要我幫忙?」
我還真的環視了四周,卻沒看到半個人。「你從哪裡打來的?」我掀開百葉窗的葉片,想看街上是不是有人在監視我。結果當然沒有。
「少來,柏魯。你知道我從哪裡打給你的。」
我做著筆記,這種腔調我認得。
他是從烏廓瑪打來的。
「既然知道我人所在的位置,請勿詢問我的名字。」
「跟我通話並不犯法。」
「你不知道我要跟你說什麼才會這麼說。你不知道我要跟你說的是什麼。事情是──」他突然打住。我聽到他手摀住話筒,喃喃自語了一會兒。「聽著,柏魯,我不知道你對這種事情採取怎樣的立場,但我認為從另一個國家打電話$給你,根本就是瘋狂的行為,也是一種侮辱。」
「我不談政治的。聽著,如果你想說……」我最後一句話是用的是烏廓瑪的伊利坦語。
「好吧。」他用帶有舊式伊利坦語字尾變化的貝澤爾語打斷我。「反正表面上都是同一種該死的語言。」我記下他說了這句話。「現在閉嘴。想聽我的消息嗎?」
「當然。」我站著,伸手翻找,設法找出追蹤這通電話的方法。
我的電話沒有裝設追蹤裝置,而就算我能在跟他通話的同時也聯絡上電信局,透過貝澤爾電信局追蹤也可能得花上好幾個小時。
「那個女人,就你們正在……她死了,對吧?她一定死了。我認識她。」
「很遺憾……」他沉默了幾秒,我只能吐出這句話。
「我已經認識她……很久以前認識她的。柏魯,我想幫你,但並不是因為你是條子。上天明鑑,我不承認你的權力。但是如果瑪爾雅是被……如果是他殺的話,我在乎的人可能就有危險了,當然也包括我最在乎的人,也就是我自己。而且應該有人替她……好吧,我知道的一切是這樣的──
「她說自己叫做瑪爾雅,我是在這裡認識她的,烏廓爾這裡。我會盡可能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但我知道的一向不多,因為不關我的事。她是外國人。我因為政治活動和她撘上線,她非常狂熱,懂嗎?她所狂熱的跟我一開始猜想的不一樣。她學識豐富,屬於不浪費時間的那種人。」
「聽著。」我說。
「我能說的都告訴你了。她住在這裡。」
「但是她人在貝澤爾。」
「拜託,」他很生氣,「拜託,沒有官方許可。她不能拿到許可。她就算跑到了對面,我們也得堅持她人在這邊。去問問牢裡那些激進分子,會有人認識她的。她什麼地方都去過,所有的地下組織,兩邊一定都去過。上窮碧落下黃泉只為了全盤皆知。而她也真的做到了。以上。」
「你怎麼知道她被殺了?」我聽到他發出噓聲。
發現屍體後的那個星期一,我接到一通電話。
「柏魯。」停頓很久後,我又報了一次名字,電話那頭覆述了一次。
「柏魯督察。」
「能為你效勞嗎?」
「我不曉得你能幫我什麼。我幾天前本來還指望你能幫我,所以一直試圖聯絡你。但我應該比較幫得上忙。」說話的男子操外國口音。
「什麼?很抱歉,請大聲一點──線路收訊很糟。」
男子的聲音受到靜電干擾,聽起來像是正在用古老機器錄音一樣。我無法確定聲音延遲是因為線路的關係,還是他需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回應我說的話。他一口流利但古怪的貝澤爾語,帶著老派的抑揚頓挫。我說:「你是誰?有何貴幹?」
「我有消息要告訴你。」
「你打過我們的服務專線嗎?」
「我不能打去那裡。」他是從國外打來的。貝澤爾落後的電話轉接服務傳送的回饋信號很有特色。
「癥結就在這兒。」
「你怎麼知道我的號碼?」
「柏魯,閉嘴。」我再次希望電話能有來電顯示功能。我坐直身子。「Google來的。報上有你的名字,那女孩的調查由你負責。要透過助理拿到你的號碼並不難。你到底要不要我幫忙?」
我還真的環視了四周,卻沒看到半個人。「你從哪裡打來的?」我掀開百葉窗的葉片,想看街上是不是有人在監視我。結果當然沒有。
「少來,柏魯。你知道我從哪裡打給你的。」
我做著筆記,這種腔調我認得。
他是從烏廓瑪打來的。
「既然知道我人所在的位置,請勿詢問我的名字。」
「跟我通話並不犯法。」
「你不知道我要跟你說什麼才會這麼說。你不知道我要跟你說的是什麼。事情是──」他突然打住。我聽到他手摀住話筒,喃喃自語了一會兒。「聽著,柏魯,我不知道你對這種事情採取怎樣的立場,但我認為從另一個國家打電話$給你,根本就是瘋狂的行為,也是一種侮辱。」
「我不談政治的。聽著,如果你想說……」我最後一句話是用的是烏廓瑪的伊利坦語。
「好吧。」他用帶有舊式伊利坦語字尾變化的貝澤爾語打斷我。「反正表面上都是同一種該死的語言。」我記下他說了這句話。「現在閉嘴。想聽我的消息嗎?」
「當然。」我站著,伸手翻找,設法找出追蹤這通電話的方法。
我的電話沒有裝設追蹤裝置,而就算我能在跟他通話的同時也聯絡上電信局,透過貝澤爾電信局追蹤也可能得花上好幾個小時。
「那個女人,就你們正在……她死了,對吧?她一定死了。我認識她。」
「很遺憾……」他沉默了幾秒,我只能吐出這句話。
「我已經認識她……很久以前認識她的。柏魯,我想幫你,但並不是因為你是條子。上天明鑑,我不承認你的權力。但是如果瑪爾雅是被……如果是他殺的話,我在乎的人可能就有危險了,當然也包括我最在乎的人,也就是我自己。而且應該有人替她……好吧,我知道的一切是這樣的──
「她說自己叫做瑪爾雅,我是在這裡認識她的,烏廓爾這裡。我會盡可能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你,但我知道的一向不多,因為不關我的事。她是外國人。我因為政治活動和她撘上線,她非常狂熱,懂嗎?她所狂熱的跟我一開始猜想的不一樣。她學識豐富,屬於不浪費時間的那種人。」
「聽著。」我說。
「我能說的都告訴你了。她住在這裡。」
「但是她人在貝澤爾。」
「拜託,」他很生氣,「拜託,沒有官方許可。她不能拿到許可。她就算跑到了對面,我們也得堅持她人在這邊。去問問牢裡那些激進分子,會有人認識她的。她什麼地方都去過,所有的地下組織,兩邊一定都去過。上窮碧落下黃泉只為了全盤皆知。而她也真的做到了。以上。」
「你怎麼知道她被殺了?」我聽到他發出噓聲。(待續)「柏魯,會這麼問就代表你是個笨蛋,而我根本在浪費時間。我是看到照片認出她的,柏魯。如果我覺得這通電話沒有必要又不重要,我還會打嗎?你認為我是怎麼知道的?當然是因為我看到那張該死的海報啊。」(註:為找尋女子身分,警局發出懸賞海報。)
他逕自掛了電話。我的話筒還貼在耳邊沒有放下,心想他還會打來。
我看到海報。我低頭看著記事本,除了他提供的資料,我只寫下胡扯、胡扯、胡扯。
我沒在辦公室多做停留。「泰亞鐸,還好嗎?」蓋德能說道。「你看起來……」我知道自己的臉色一定很糟。我在人行道上的咖啡攤喝了一杯濃咖啡,aj Tyrko,土耳其口味,這是個錯誤的決定,因為反而更焦慮。
那天回家途中很難奉行邊界,也很難只看該看的,不該看的則視而不見,對於這樣的一天來說或許也沒什麼好意外的。圍繞在我身邊的都不是貝澤爾人,我 緩緩走過人潮擁擠,在貝澤爾卻沒什麼人的地區。我只專心看著屬於我這邊的石砌建築──大教堂、酒吧、原本是學校的磚造裝飾──這裡是我生長的地方。其他一 律視而不見,或是努力不去看。
我那天晚上撥了電話給歷史學者莎芮思卡。她不僅床上功夫了得,有時也會就我辦的案子提出討論,見解精闢。我撥了兩次電話,兩次都在接通之前掛斷。不想把她拖下水的原因有二,偵察期間不得洩漏案情是其一,其二就是不想讓她成為違規越界的共犯。
我又回到記事本上的胡扯、胡扯、胡扯。最後買了兩瓶酒回家慢慢喝──也吃了一點晚餐墊胃,像是橄欖、起司、香腸等──直到喝完為止。我做了很多沒 用的筆記,還畫了晦澀難解的圖表佯裝有找到解決方法的可能,但是情況暨謎題本身其實很清楚。我或許不幸碰上無意義又硬拗的惡作劇,但看來又不太可能。打電 話來的男子說的比較可能是實話。
這個案子裡,有人給了我關鍵的線索,幫助我掌握和芙拉娜─瑪爾雅密切相關的消息。有人告訴我該去哪追蹤誰以獲得進一步的消息。接下來就是我的工 作。但要是被發現我的消息從哪來,那就定不了罪了。更麻煩的是,我追查這個案子本身就已經犯法;而比犯法更糟的是我不僅會違反貝澤爾的法律,還很有可能違 規跨界。
提供消息給我的人根本不該看到海報才對,因為海報並未出現在他的國家。他也根本不該告訴我,讓我淪為共犯。他提供的消息在貝澤爾是恐怖的過敏原 ──只是在我腦中放進這個消息,就已經造成創傷。我是共犯。木已成舟。(或許是因為喝醉了,我並沒想到他根本沒必要告訴我他如何得知此消息,也沒考慮到他 這麼做必有箇中緣由。)
我沒這麼做;但誰不想把那次通話的筆記燒掉或放入碎紙機銷毀?我還是沒這麼做。我在廚房餐桌前坐到很晚,面對著攤開的記事本,時不時毫無建設性地 重複寫著:胡扯、胡扯。我放了音樂:一張名為《小小火車小姐》的合唱專輯,收錄范?莫理森在一九八七年巡迴演唱時與可莎?雅科夫同臺合唱的曲子,後者素有 貝澤爾鄔恩?考兒蓀的美譽。我又多喝了幾杯,把瑪爾雅?芙拉娜?無名女屍?外國人?笛泰兒?違規跨界者的照片放在筆記旁邊。
沒有人認識她。老天若有眼,她或許根本是非法進入貝澤爾,即使波科斯特村完全屬於貝澤爾所有。她可能是被拖去那裡的。發現屍體的孩子、整個調查過 程都可能已經違規跨界。我不該為了查案而讓自己遭到牽連。或許我該做的就是不再參與調查,任她的屍身腐爛。假裝自己會這麼做讓我得以暫時逃避現實,但是到 頭來我還是會盡忠職守,儘管辦這個案子意味著觸犯一條法規──一個存在於兩邊的協議;比起他們付錢請我執行的所有法律,那個協議還更根本多了。 (待續)「柏魯,會這麼問就代表你是個笨蛋,而我根本在浪費時間。我是看到照片認出她的,柏魯。如果我覺得這通電話沒有必要又不重要,我還會打嗎?你認為我是怎麼知道的?當然是因為我看到那張該死的海報啊。」(註:為找尋女子身分,警局發出懸賞海報。)
他逕自掛了電話。我的話筒還貼在耳邊沒有放下,心想他還會打來。
我看到海報。我低頭看著記事本,除了他提供的資料,我只寫下胡扯、胡扯、胡扯。
我沒在辦公室多做停留。「泰亞鐸,還好嗎?」蓋德能說道。「你看起來……」我知道自己的臉色一定很糟。我在人行道上的咖啡攤喝了一杯濃咖啡,aj Tyrko,土耳其口味,這是個錯誤的決定,因為反而更焦慮。
那天回家途中很難奉行邊界,也很難只看該看的,不該看的則視而不見,對於這樣的一天來說或許也沒什麼好意外的。圍繞在我身邊的都不是貝澤爾人,我 緩緩走過人潮擁擠,在貝澤爾卻沒什麼人的地區。我只專心看著屬於我這邊的石砌建築──大教堂、酒吧、原本是學校的磚造裝飾──這裡是我生長的地方。其他一 律視而不見,或是努力不去看。
我那天晚上撥了電話給歷史學者莎芮思卡。她不僅床上功夫了得,有時也會就我辦的案子提出討論,見解精闢。我撥了兩次電話,兩次都在接通之前掛斷。不想把她拖下水的原因有二,偵察期間不得洩漏案情是其一,其二就是不想讓她成為違規越界的共犯。
我又回到記事本上的胡扯、胡扯、胡扯。最後買了兩瓶酒回家慢慢喝──也吃了一點晚餐墊胃,像是橄欖、起司、香腸等──直到喝完為止。我做了很多沒 用的筆記,還畫了晦澀難解的圖表佯裝有找到解決方法的可能,但是情況暨謎題本身其實很清楚。我或許不幸碰上無意義又硬拗的惡作劇,但看來又不太可能。打電 話來的男子說的比較可能是實話。
這個案子裡,有人給了我關鍵的線索,幫助我掌握和芙拉娜─瑪爾雅密切相關的消息。有人告訴我該去哪追蹤誰以獲得進一步的消息。接下來就是我的工 作。但要是被發現我的消息從哪來,那就定不了罪了。更麻煩的是,我追查這個案子本身就已經犯法;而比犯法更糟的是我不僅會違反貝澤爾的法律,還很有可能違 規跨界。
提供消息給我的人根本不該看到海報才對,因為海報並未出現在他的國家。他也根本不該告訴我,讓我淪為共犯。他提供的消息在貝澤爾是恐怖的過敏原 ──只是在我腦中放進這個消息,就已經造成創傷。我是共犯。木已成舟。(或許是因為喝醉了,我並沒想到他根本沒必要告訴我他如何得知此消息,也沒考慮到他 這麼做必有箇中緣由。)
我沒這麼做;但誰不想把那次通話的筆記燒掉或放入碎紙機銷毀?我還是沒這麼做。我在廚房餐桌前坐到很晚,面對著攤開的記事本,時不時毫無建設性地 重複寫著:胡扯、胡扯。我放了音樂:一張名為《小小火車小姐》的合唱專輯,收錄范?莫理森在一九八七年巡迴演唱時與可莎?雅科夫同臺合唱的曲子,後者素有 貝澤爾鄔恩?考兒蓀的美譽。我又多喝了幾杯,把瑪爾雅?芙拉娜?無名女屍?外國人?笛泰兒?違規跨界者的照片放在筆記旁邊。
沒有人認識她。老天若有眼,她或許根本是非法進入貝澤爾,即使波科斯特村完全屬於貝澤爾所有。她可能是被拖去那裡的。發現屍體的孩子、整個調查過 程都可能已經違規跨界。我不該為了查案而讓自己遭到牽連。或許我該做的就是不再參與調查,任她的屍身腐爛。假裝自己會這麼做讓我得以暫時逃避現實,但是到 頭來我還是會盡忠職守,儘管辦這個案子意味著觸犯一條法規──一個存在於兩邊的協議;比起他們付錢請我執行的所有法律,那個協議還更根本多了。
我們小時候都玩過「我是跨界監察局大人」這個遊戲。我從沒愛玩過,但輪到我玩的時候還是會偷偷跨過粉筆畫的界線,然後朋友就會張牙舞爪地來追我。 如果換成我執法的話,我也會去追別人。小孩常玩的遊戲,除了「我是跨界監察局大人」,以及把從土裡挖出來的樹枝和卵石當作貝澤爾魔法錢幣以外,還有一種融 合捉人和捉迷藏的遊戲,叫做「揪出躲在城與城之間的神祕客」[注4:神祕客在本書專指曾經犯過違規跨界卻能成功避開跨界監察局的追捕,隱身在城與城之間的 人]。
沒有一種宗教理論會極端到讓人找不到。貝澤爾有一派人信奉跨界監察局。考慮到牽涉其中的多方勢力,這種宗教雖然不像話卻也不出人意表。沒有法律可以制裁這派信眾,儘管此宗教的本質會讓所有人焦躁不安。性好腥羶色的電視節目也一直以此為主題大談特談。
凌晨三點,我醉了卻非常清醒,細看著貝澤爾的街道(更多時候看的是──交錯重疊區)。我聽得到狗吠聲和一匹流浪狼嚎叫了一兩聲。桌上滿是報紙──充斥著像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兩派意見。玻璃酒杯的環形光圈映在瑪爾雅的臉上,也投射在寫滿胡扯、胡扯、胡扯的違法筆記之上。
睡不著對我來說稀鬆平常。莎芮思卡和碧薩雅睡到一半出臥房到浴室上廁所時,都很習慣看到我坐在廚房餐桌前看書,猛嚼口香糖的,嚼到舌頭都要長出水 泡了(我不會重拾香菸)。要不然就是看到我凝視著這個城市以及另一座城市的夜景(無可避免的,嘴上說視而不見,卻又深受其燈火感動)。
莎芮思卡曾笑過我。「看看你這副模樣,」她並非全然不帶感情地說道:「像隻貓頭鷹坐在那兒,也像一臉憂鬱的石像鬼,你這過度感傷的傢伙。你根本什 麼都沒有參透,只單純因為現在是晚上,有些建築物開了燈而已。」她可不是特地起床來尋我開心的。任何想法我都來者不拒,就算是假的也好,所以我往窗外望 去。
我們小時候都玩過「我是跨界監察局大人」這個遊戲。我從沒愛玩過,但輪到我玩的時候還是會偷偷跨過粉筆畫的界線,然後朋友就會張牙舞爪地來追我。 如果換成我執法的話,我也會去追別人。小孩常玩的遊戲,除了「我是跨界監察局大人」,以及把從土裡挖出來的樹枝和卵石當作貝澤爾魔法錢幣以外,還有一種融 合捉人和捉迷藏的遊戲,叫做「揪出躲在城與城之間的神祕客」[注4:神祕客在本書專指曾經犯過違規跨界卻能成功避開跨界監察局的追捕,隱身在城與城之間的 人]。
沒有一種宗教理論會極端到讓人找不到。貝澤爾有一派人信奉跨界監察局。考慮到牽涉其中的多方勢力,這種宗教雖然不像話卻也不出人意表。沒有法律可以制裁這派信眾,儘管此宗教的本質會讓所有人焦躁不安。性好腥羶色的電視節目也一直以此為主題大談特談。
凌晨三點,我醉了卻非常清醒,細看著貝澤爾的街道(更多時候看的是──交錯重疊區)。我聽得到狗吠聲和一匹流浪狼嚎叫了一兩聲。桌上滿是報紙──充斥著像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兩派意見。玻璃酒杯的環形光圈映在瑪爾雅的臉上,也投射在寫滿胡扯、胡扯、胡扯的違法筆記之上。
睡不著對我來說稀鬆平常。莎芮思卡和碧薩雅睡到一半出臥房到浴室上廁所時,都很習慣看到我坐在廚房餐桌前看書,猛嚼口香糖的,嚼到舌頭都要長出水 泡了(我不會重拾香菸)。要不然就是看到我凝視著這個城市以及另一座城市的夜景(無可避免的,嘴上說視而不見,卻又深受其燈火感動)。
莎芮思卡曾笑過我。「看看你這副模樣,」她並非全然不帶感情地說道:「像隻貓頭鷹坐在那兒,也像一臉憂鬱的石像鬼,你這過度感傷的傢伙。你根本什 麼都沒有參透,只單純因為現在是晚上,有些建築物開了燈而已。」她可不是特地起床來尋我開心的。任何想法我都來者不拒,就算是假的也好,所以我往窗外望去。
飛機飛過雲層上方。摩天大樓的玻璃帷幕外牆,映照出大教堂塔尖的鮮明倒影。邊界另一端的建築物狀似新月向後彎曲,可見霓虹燈此起彼落閃爍。我試著把電腦連上網路好查些資料,但只有撥接連線可用,實在令人洩氣,所以我放棄了。
「細節容後稟述。」我想我確實大聲說出了這句話。我記下更多筆記。結果最後還是打了寇葳的分機留言給她。
「莉茲拜,我有個想法。」每次我說謊就會本能地說得太多也太快。我盡量逼自己像沒事一樣地跟她說話,但她可不笨。
「時間不早了。我有件事要交代妳,因為我明天可能不會進來。謹守轄區一直都沒有進展,我們原本以為有人會指認出她的想法顯然錯了。我們已經把照片 分發到各轄區,所以如果她只是個離開自家警察轄區的街頭妓女,我們也許還算幸運,但是我希望繼續查案的同時也能朝其他幾個方向調查。
「聽著,我想她並不在她所屬的區域,情況古怪,我們又不能引起注意。我跟一個反對黨分隊的友人談過,他說他監視的人都行事隱密,全是納粹、左派分 子、統派分子之類的。總之,這勾起我的好奇心,想知道什麼樣的人會隱藏身分;我想在時間允許的狀況下追一下這條線索。我想──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記的…… 好,就從統派分子開始好了。
「找奇人異事組談一談,看看透過住址、分會能查到什麼──這方面我所知不多。去沈瓦的辦公室找他,跟他說妳在幫我辦一個案子。盡可能過濾每一個 人,帶照片去,看有沒有人認得她。不用我說,妳也應該清楚那些人的態度肯定會很怪──他們不會希望跟妳有所接觸。盡力就好。我的手機不會關機,隨時保持聯 繫。如我剛才所說,我今天不進辦公室。明天再通電話吧。就這樣,再見。」
「真糟。」我想我這句話也說得很大聲。
說完之後,我打電話留言給行政部的塔絲金?希若許。之前請她協助過三、四個案子繁瑣的行政程序;我特別記下她的分機,也一直跟她保持聯繫。她的工作表現沒話說。
「塔絲金,我是泰亞鐸?柏魯。請妳明天或是有空的時候打手機給我,我想知道如果我想把一個案子交給監督委員會審理,有什麼必要的程序。又假設我想 把案子交給Breach審的話呢?」我畏縮了一下,笑出聲。「塔絲,先別張揚,好嗎?謝啦。讓我知道我應該做什麼,妳有甚麼方便的圈內人竅門也請跟我說。 謝了。」
那個提供線索、態度惡劣的男子所說的話並沒有多大問題。我照抄並標出一些重點詞彙:
語言相同
是否承認我們的主權──否
城市兩邊
這一切都說得通了,包括他為什麼選擇打給我、為什麼是這件案子,還有他看到了什麼,以及他居然看得到。雖然風險極高卻還是阻止不了他打這通電話。 他會出此下策主要是出於恐懼,害怕瑪爾雅?芙拉娜的死可能會對他帶來任何潛在的影響。他說他在貝澤爾的同夥很有可能見過瑪爾雅,以及她當時可能就不會奉行 界線了。如果真的有貝澤爾的麻煩分子共謀犯下那種罪、不顧那種禁忌,一定是打電話給我的男子與他的同夥。他們顯然都是統派分子。
我轉頭回顧夜晚燈火通明的城市時,莎芮思卡在我的心裡挖苦著我,這次我朝著鄰城看去。就算違法我還是看了。誰不會偶爾這樣做呢?那邊有著我不該看 到的加油站、懸掛骨狀鐵框廣告招牌的律師事務所。街上至少有一個行人不是貝澤爾人──從穿著、膚色、走路方式就看得出來,而我看著他。
我把視線轉向窗外幾公尺遠的鐵道並等候著,因為我知道最後會有一班晚班車進站。我看著它快速通過,車窗閃閃發亮,也與幾名乘客四目相接,只有極少 數人回望我,而且嚇到了。但是他們的蹤影旋即消失在連綿的屋簷上:這只是小小犯了規,不是他們的錯。他們或許不會內疚太久,也可能不會記得這次的凝望。我 一直都想住在可以看到外地列車的地方。 飛機飛過雲層上方。摩天大樓的玻璃帷幕外牆,映照出大教堂塔尖的鮮明倒影。邊界另一端的建築物狀似新月向後彎曲,可見霓虹燈此起彼落閃爍。我試著把電腦連上網路好查些資料,但只有撥接連線可用,實在令人洩氣,所以我放棄了。
「細節容後稟述。」我想我確實大聲說出了這句話。我記下更多筆記。結果最後還是打了寇葳的分機留言給她。
「莉茲拜,我有個想法。」每次我說謊就會本能地說得太多也太快。我盡量逼自己像沒事一樣地跟她說話,但她可不笨。
「時間不早了。我有件事要交代妳,因為我明天可能不會進來。謹守轄區一直都沒有進展,我們原本以為有人會指認出她的想法顯然錯了。我們已經把照片 分發到各轄區,所以如果她只是個離開自家警察轄區的街頭妓女,我們也許還算幸運,但是我希望繼續查案的同時也能朝其他幾個方向調查。
「聽著,我想她並不在她所屬的區域,情況古怪,我們又不能引起注意。我跟一個反對黨分隊的友人談過,他說他監視的人都行事隱密,全是納粹、左派分 子、統派分子之類的。總之,這勾起我的好奇心,想知道什麼樣的人會隱藏身分;我想在時間允許的狀況下追一下這條線索。我想──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記的…… 好,就從統派分子開始好了。
「找奇人異事組談一談,看看透過住址、分會能查到什麼──這方面我所知不多。去沈瓦的辦公室找他,跟他說妳在幫我辦一個案子。盡可能過濾每一個 人,帶照片去,看有沒有人認得她。不用我說,妳也應該清楚那些人的態度肯定會很怪──他們不會希望跟妳有所接觸。盡力就好。我的手機不會關機,隨時保持聯 繫。如我剛才所說,我今天不進辦公室。明天再通電話吧。就這樣,再見。」
「真糟。」我想我這句話也說得很大聲。
說完之後,我打電話留言給行政部的塔絲金?希若許。之前請她協助過三、四個案子繁瑣的行政程序;我特別記下她的分機,也一直跟她保持聯繫。她的工作表現沒話說。
「塔絲金,我是泰亞鐸?柏魯。請妳明天或是有空的時候打手機給我,我想知道如果我想把一個案子交給監督委員會審理,有什麼必要的程序。又假設我想 把案子交給Breach審的話呢?」我畏縮了一下,笑出聲。「塔絲,先別張揚,好嗎?謝啦。讓我知道我應該做什麼,妳有甚麼方便的圈內人竅門也請跟我說。 謝了。」
那個提供線索、態度惡劣的男子所說的話並沒有多大問題。我照抄並標出一些重點詞彙:
語言相同
是否承認我們的主權──否
城市兩邊
這一切都說得通了,包括他為什麼選擇打給我、為什麼是這件案子,還有他看到了什麼,以及他居然看得到。雖然風險極高卻還是阻止不了他打這通電話。 他會出此下策主要是出於恐懼,害怕瑪爾雅?芙拉娜的死可能會對他帶來任何潛在的影響。他說他在貝澤爾的同夥很有可能見過瑪爾雅,以及她當時可能就不會奉行 界線了。如果真的有貝澤爾的麻煩分子共謀犯下那種罪、不顧那種禁忌,一定是打電話給我的男子與他的同夥。他們顯然都是統派分子。
我轉頭回顧夜晚燈火通明的城市時,莎芮思卡在我的心裡挖苦著我,這次我朝著鄰城看去。就算違法我還是看了。誰不會偶爾這樣做呢?那邊有著我不該看 到的加油站、懸掛骨狀鐵框廣告招牌的律師事務所。街上至少有一個行人不是貝澤爾人──從穿著、膚色、走路方式就看得出來,而我看著他。
我把視線轉向窗外幾公尺遠的鐵道並等候著,因為我知道最後會有一班晚班車進站。我看著它快速通過,車窗閃閃發亮,也與幾名乘客四目相接,只有極少 數人回望我,而且嚇到了。但是他們的蹤影旋即消失在連綿的屋簷上:這只是小小犯了規,不是他們的錯。他們或許不會內疚太久,也可能不會記得這次的凝望。我 一直都想住在可以看到外地列車的地方。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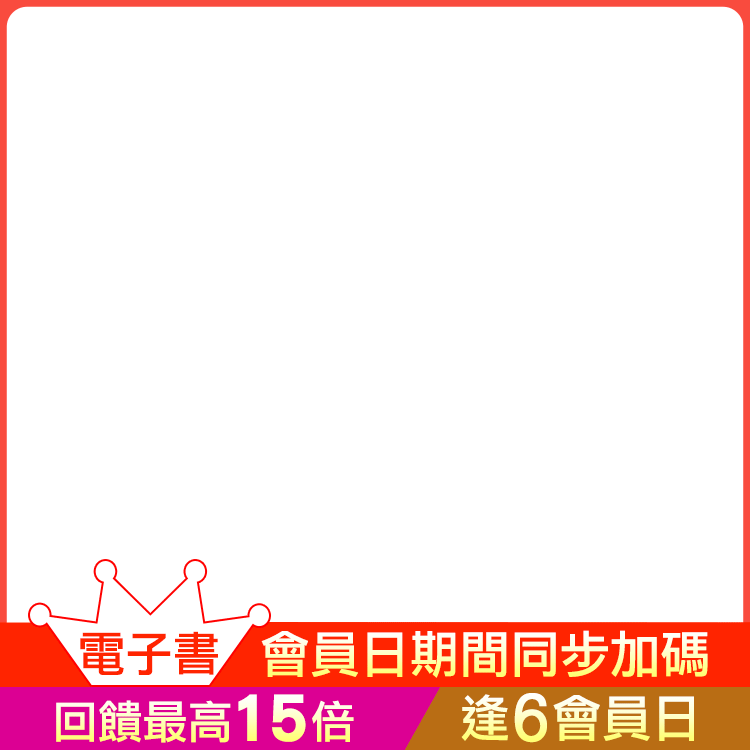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