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子戰爭
The Looking Glass War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鏡子,不會告訴你背後的東西。等你發現,一切已成定局。
史邁利:「你永遠也不會告訴我,對不對?」
一個本來不該出外勤的軍情科快遞;一場意外,一具不算無辜的屍體。
一本被吊銷的護照;可疑的投誠與更可疑的武器情資;
一個隨著戰爭失勢的軍情科,翻身一搏的最後機會……
老總:「我親愛的喬治……你想說什麼?格調太差了吧。有誰會做那麼下流的事?」
單純配合軍情科的訓練演習。提供無線電器材。配合製作假護照、人員訓練——
已經獲得老總的許可。老總很急著要幫忙。老總配合得令人眼睛一亮。
雷科勒克:「對他們來說,撒謊是第二天性。他們當中一半的人,已經搞不清楚什麼時候應該講實話了……不過我們不是圓場,約翰:我們不那樣做事。」
德國人在搞鬼,還是俄國人?既然空拍圖的底片拿不到,他們只有一個機會:找回他們戰時最厲害的老手、重新訓練他——瞞著圓場,不讓那些人搶功——然後潛入敵方,拍回照片。一切看來順利得不可思議……
但你要怎麼確認,自己出手擊中的是敵人,還是會害你曝光的鏡子?
你要怎麼確認,自己是真的看到了,還是別人想讓你看到的?
重要書評
「本書文力萬鈞,至為罕見」──《金融時報》
「摒除虛華型間諜的迷思,記錄了人性化間諜之事跡,震垮人心﹐讀來悲哀。」──《紐約前鋒論壇報》
「文筆鋒利淒苦,登峰造極。」──《出版家週刊》
名人推薦
詹宏志、唐諾、羅智成、韓良露
專文導讀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理事、台大推研社顧問 路那
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 心戒
試閱
白雪覆蓋著小機場。
白雪降自北方,在迷霧中受到夜風吹動,帶有海水的氣息。機場上的白雪將會停留整個冬季,在灰色土地上一片襤褸寒愴,是層冰冷而刺骨的粉塵,既不融化,也不凍結,而是維持靜態,彷彿一年無四季之分。不停變幻的霧氣宛如戰事的煙硝,逗留在雪地上,倏而吞噬機棚,倏而吞噬雷達中心,倏而吞噬機身。隨後才逐步釋放,色澤褪盡,成了白色沙漠中的黑色腐屍。
這幅景象沒有縱深,沒有縮凹,沒有陰影;大地與蒼穹合而為一,人影與建築物冰封於寒風中,有如浮冰裡的屍首。
小機場更遠處則空無一物,沒有民房,沒有山丘,沒有道路,連圍牆、樹木也付之闕如,僅有壓在雪堆之上的天空,和從波羅的海泥岸升入空中的滾滾濃霧。往內陸方向望去,可見群山。
一群兒童頭戴小帽,聚集在長長的觀景窗前,以德文嘰喳談天。有幾位學童身穿滑雪裝。泰勒戴著手套,手握杯子,雙目無神地凝視他們前方。一名男童轉身看著他,臉紅起來,悄聲對其他學童說話,孩子們安靜下來。
他動作很大地伸出手看錶,一方面是為了拉開外套袖子,另一方面是個人風格使然。他希望給人留下一個印象:軍人、訓練精實、隸屬高級的俱樂部。見識過大戰風浪。
還差十分四點。飛機已誤點一小時。機場不久後必將透過擴音器宣布誤點原因。他納悶的是,機場會宣布出什麼理由。大概是受濃霧影響吧,所以起飛時受到延誤。機場人員大概也一頭霧水──而且當然不會願意承認──這班飛機往羅斯托克以南方向,脫離航道兩百英哩。他喝完酒,轉身放下空酒杯。他不得不承認,有些不入流的外國酒若在產地國飲用,喝起來滋味還不錯。由於陷入苦等的狀態,有兩、三個小時要消磨,窗外又是零下十度,的確有可能碰到一些比杜松子酒更糟糕的狀況。回國後,他會請「隱名俱樂部」進貨。這樣一定會引起不小騷動。
擴音器嗡嗡響起,然後突然大響,音量漸減後,又再度發聲,音量已調至適中。學童們滿懷期望地望向擴音器。廣播首先以芬蘭文宣布,然後是瑞典文,現在則換為英語。自杜塞爾多夫起飛的北方航空二九○客機因故延誤,敬請原諒,延誤時間與原因不明。航空公司大概自己也不清楚。
然而泰勒是知道的。玻璃亭裡坐著精神抖擻的地勤人員,假設他從容地走過去告知原因,不知道對方會有何反應。二九○還要過一陣子才會到,小姐,那是因為在波羅的海上空被強烈北風吹離航道,搞亂了所有方位。但小妞當然不會相信,反而會認為他是在搞鬼。要到事後她才會恍然大悟,明白眼前這人非比尋常,他的來歷相當特別。
外面天色已開始轉暗。如今地面比天空更亮;在雪地襯托下,清理過的跑道有如疏洪道般醒目,沾染了琥珀色的標示黃光。在最靠近的飛機棚裡,日光燈管照得人與飛機皆顯得疲憊慘白;他前方的地面閃現管制塔臺的光束,似乎短暫地甦活過來。左邊的修理場駛出一輛消防車,加入已停在中央跑道附近的三輛救護車,四車同時打亮旋轉的藍燈,閃著警示訊號靜候。學童紛紛指向車陣,聒噪不休,興奮不已。
地勤小姐的嗓音再度透過擴音器響起,距上一次廣播可能僅隔數分鐘。學童再次噤口傾聽。第二九○號客機抵達時間將延誤至少一小時,本站若獲得進一步消息,將會立即廣播。小姐的聲音不大對勁,傳達出一種介於驚訝與焦慮之間的感覺,有六、七名坐在候機室另一邊的人似乎也感受到。一名老婦人對丈夫說了一句話後站起身,拎起手提包過去與學童同坐。她凝望著落日餘暉良久,神情呆滯,無奈無法從中獲得慰藉,因此便轉向泰勒,以英文發問。「杜塞爾多夫的飛機究竟是怎麼了?」她的嗓音帶有荷蘭女人的濃濃喉音,語調憤慨而急促。泰勒搖搖頭。「可能下大雪吧!」他回答。他個性乾脆,這樣的回答符合他的軍人作風。
泰勒推開旋轉門,下樓到接待廳。在靠近大門處,他認出北方航空的黃色三角旗。坐在櫃檯前的女地勤人員頗具姿色。
「杜塞爾多夫的客機發生什麼事了?」他的態度能讓人想把心裡的話講出來;據說他對小女孩很有一套。她微微一笑,聳聳肩。
「我認為是因為大雪。班機延誤在秋季很常見。」
「為何不問一下上司?」他建議,同時對著她面前的電話點頭示意。
「一有最新消息,」她說:「就會用廣播宣布。」
「小姐,是誰駕駛的?」
「什麼?」
「飛機是誰駕駛的,機長是誰?」
「藍森機長。」
「他技術好不好呢?」
這位小姐似乎大為震驚。「藍森機長的經驗非常豐富。」
泰勒看了她一眼,露齒一笑,說:「小姐啊,他頂多算是個運氣不錯的飛行員。」據他們說,泰勒的確懂得不少。而所謂的他們,便是週五晚上在隱名俱樂部齊聚一堂的人。
藍森。聽別人這樣道出姓氏,感覺詭異。在單位裡,他們絕不會指名道姓。他們偏好拐彎抹角,喜歡用臥底的姓名,只要不碰真名,什麼稱呼皆可:亞契小子、我們的飛行員朋友、我們來自北方的朋友、負責拍照的老兄;他們甚至會以文件上的字母加數字的代碼作為一種委婉的稱呼。在任何情況下,絕不指名道姓。
藍森。在倫敦時,雷科勒克曾讓他看過相片。藍森現年三十五,略帶孩子氣;金髮,外表俊美。他打賭空服員肯定愛他愛得半死。空服員的功能本來就只是讓機長得以消遣,反正其他人也看不見。泰勒右手快速伸進大衣外的口袋,只想確定信封仍在裡頭。他以前從未帶過這種錢。飛一趟五千美元,一千七百英鎊,免稅,只要在波羅的海上空稍微迷個路。請注意,這種事藍森不是天天做。雷科勒克說過,這趟任務比較特殊。他心想,假如自己倚在櫃檯上向女孩透露身分,她會有何種反應。不如讓她瞧瞧信封裡的鈔票。他從沒跟這樣的女孩交往過――真正的女孩,高䠷,而且年輕。
他再度上樓走進酒吧,酒保對他越來越熟了。泰勒指著擺在酒架中上的杜松子酒瓶說:「請再給我一杯,就是那個,你正後方的那瓶。這可是你們本地的穿腸毒藥。」
「這是德國酒啊!」酒保說。
他翻開皮夾,取出一張鈔票。膠膜後面夾著小女孩的相片,九歲左右,戴著眼鏡,抱著洋娃娃。「我女兒。」他向酒保解釋,酒保則以微笑應付。
他的語調變化多端,說起話來如同相當習慣出差的上班族。在與同階級的人對話時,他虛假的尾音會拖得更誇張,為了要強調一種根本不存在的優越感,又或是像現在,在他緊張的時候。
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確有些心虛。以他的歷練與年齡,從例行的快遞工作跨足情報領域,狀況確實有些弔詭。這種工作應該交給情報局那些豬玀來辦,根本不該落在自己的單位。他的單位負責的是他習以為常的普通例行公事,與這項任務有著天壤之別,也因此令他進退維谷,不得不置身異國荒郊。怎麼會在這種地方蓋機場呢?他怎麼也想不透。說到出差海外,他一般而言都很樂意,例如到漢堡與老吉米‧哥頓接洽,或是到馬德里花天酒地一夜。能離開瓊妮一下對他是有好處的。他跑過土耳其兩、三趟,只不過中東人不太合他胃口。但即使是土耳其,跟這一趟比起來仍顯得易如反掌。出差土耳其時,他搭的是頭等艙,行李擺在身旁的座位上,口袋裡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通行證;他有身分、有地位;視同外交人員――或幾乎算得上外交人員。但這趟不同,他不太喜歡。
雷科勒克說過,這一趟非同小可,泰勒也相信了他。上頭幫他偽造護照,把姓改成Malherbe,他們說正確發音是馬勒比。而這個姓到底是誰選的?只有老天知道。這個姓泰勒連拼都拼不出來,今早住進旅館填寫姓名時,就出了一點洋相。津貼的數字當然很理想,行動開支一天十五英鎊,而且不必出示收據。他聽說情報局給過十七英鎊。這錢可善加利用,買點東西送瓊妮。但她大概比較喜歡現金。
這事他當然有告訴過她。其實他不該透露,但雷科勒克並不認識瓊妮。他點起一支菸,吸了一口,捧在手心,就像哨兵值勤時抽菸的模樣。大老遠跑到北歐,怎麼可能不告訴老婆?
學童緊貼窗戶。他們究竟在看什麼呢?他不禁納悶。這些孩子應付外語頗有一套,實在令人驚訝。他又看了一下手錶,幾乎沒有注意時間。又忍不住碰碰口袋裡的信封。最好別再喝了,腦子必須保持清醒。他盡量讓自己去猜瓊妮現在正在做什麼――大概正坐著喝琴酒吧。整天上班也難為她了。
他突然發現周遭安靜了下來。酒保靜靜站著聆聽。圍坐餐桌的老年人也在聽著,好幾張傻呼呼的臉轉向觀景窗。隨後,他清楚聽見飛機的聲響。仍在遠方,卻逐漸靠近小機場。他趕緊走向窗戶。走了一半,擴音器就響起,才以德文廣播了幾個字,學童就宛如一群鴿子那樣紛紛飛向接待廳。圍坐餐桌的那群人也站起來,女人伸手拿手套,男人拿起外套與公事包。最後,英文廣播傳來:藍森準備降落。
泰勒望著夜色。沒有飛機的跡象。他等著,焦慮之情逐步升高。他心想,簡直像世界末日。外面簡直就像該死的世界末日――萬一藍森墜機……萬一照相機被他們找到……他寧可由其他人負責這項任務,比如伍德夫。伍德夫幹嘛不接手?或是派那個聰明的大學畢業生艾佛瑞過來?風勢轉強了。他敢發誓,風勢比剛才強許多,強風吹攪雪地,將雪塊颳上跑道,他憑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強風同時也扯著照明燈,在地平線上掃起條條白柱,然後再猛然吹開,彷彿痛恨著自己的創作。一股陣風忽然打在他眼前的窗戶,打得他向後縮,隨之而來的是雪花的沙沙聲,以及木框又急又短的呻吟。泰勒再次看錶。他已經看成習慣了。知道時間似乎有助心情安穩。
風雪這麼大,藍森不可能安全降落。絕不可能。
他的心跳像是暫停了。他聽到汽車喇叭聲。起初輕柔,隨後急升轉為嗚咽,然後四輛車齊聲在景況悽慘的小機場上呻吟,彷彿飢餓的動物正嗥叫著。失火。飛機一定著火了。飛機失火,他盡全力降落……泰勒越來越慌亂,急著找人問清楚。
酒保站在他身邊擦拭杯子,望向窗外。
「怎麼回事?」泰勒大喊。「為什麼警笛在響?」
「天氣惡劣的時候都會響警笛的。」他回答。「法律規定。」
「天氣不好,為什麼讓他降落?」泰勒追問。「讓他往南一點降落不就好了?這地方太小了,幹嘛不改到比較大的機場?」
酒保漠不關心地搖搖頭。「情況又不算太差,」他邊說邊指著小機場。「何況他誤點太久。可能汽油用光了。」
他們看見飛機出現在小機場上方不遠處,燈光在照明燈上方交替閃耀,機上的大燈掃瞄著跑道。飛機落下了,安全降落。推進器呼吼的聲音傳來,開始進行漫長的滑行,朝抵達站前進。
酒吧客人已走光,只剩泰勒一人。他點了一杯酒。交代事項他都熟記在心。雷科勒克吩咐過,要待在酒吧裡,藍森會自己前來,但他會稍微多花一點時間,因為他必須先處理飛航文件,取出照相機內的底片。泰勒聽見學童在樓下高歌,由一位女士帶領――四周淨是婦孺,這是成何體統?他進行的不是男人的任務嗎?口袋裡不是裝了五千美元與一本假護照嗎?
「今天的班機起降到此為止,」酒保說:「現在開始禁止任何起降。」
泰勒點頭。「我知道。外面情況很嚇人,真的很嚇人。」
酒保收起酒瓶。「不會有危險的啦,」他以安慰的口吻接著說:「藍森機長是個非常優秀的機長。」他遲疑了一下,不知是否該收起杜松子酒。
「當然不會有危險,」泰勒口氣很衝。「誰說會有危險的?」
「再來一杯?」酒保說。
「不用了,你自己喝。喝啊,給你自己倒一杯。」
酒保不情願地替自己斟酒,然後將酒瓶鎖進酒櫃。
「話說回來,他們是怎麼辦到的?」泰勒說。他的口氣帶有一點求和的意味,想繼續跟酒保聊天。「天氣這麼糟,什麼也看不見。」他若有所思地微笑。「坐在機頭,再怎麼拚命看、專心看,一整天也看不到東西,不如閉上眼睛算了。這種情況我看多了。」泰勒接著說。他雙手略呈杯狀,放在前方,彷彿正在操作飛機。「我很清楚,要是真的出了什麼差錯,倒楣的是那些飛行員。」他搖搖頭。「他們可以把錢留著,」他高聲說:「他們掙的每一分錢都有權力留著用。特別是像這種尺寸的風箏啊――這種東西全是用細繩子串起來的。細繩子。」
酒吧以冷淡的態度點頭,喝乾剩下的酒,洗洗酒杯,擦乾,放在櫃檯下的架上。他解開白色夾克。
泰勒不動聲色。
「嗯,」酒保皮笑肉不笑。「我們得回家了。」
「我們?什麼意思?」泰勒眼睛睜得很大,頭向後仰。「你什麼意思?」現在他已經準備要跟人吵架――誰都可以。藍森已經降落了。
「我得打烊了。」
「回家個頭。再幫我們倒一杯,快倒呀!你想回家的話請便。我家可是在倫敦喔。」他的語氣有挑釁意味,半屬玩笑性質,半屬憎惡。他的音量越來越大。「明天早上以前,你們的航空公司要是沒辦法送我回倫敦,我也到不了其他鬼地方。你居然叫我回家,是不是糊塗了啊?老兄?」他仍保持微笑,卻笑得短促且憤怒,是那種緊張的人快要發脾氣時的笑容。「下一次,當我請你喝一杯的時候,麻煩你有禮貌一點……」
門打開,藍森走進來。
原本預設的情況並非如此。這完全不符合雷科勒克描述的情況。雷科勒克說過,待在酒吧裡,坐在靠角落的那張桌子喝酒,帽子和外套放在另一張椅子上,擺出正在等人的姿態。藍森進來時,總會點啤酒喝。藍森個人偏好公眾交誼廳。因為那裡人來人往。雷科勒克如是說。這種機場雖小,周遭的大小事卻少不了。他會四處看,假裝要找地方坐下――動作光明正大――然後走過來,問你這邊有沒有人坐。你會說,原本是為朋友而留,結果朋友放你鴿子。藍森會問,那可以坐下嗎?他會點啤酒,然後說道:「是等男性朋友還是女性朋友?」你會對他說,這問題問得未免也太粗線條了吧,然後兩人大笑一陣,開始聊天。要問兩個問題:高度與航速。研究處非知道高度與航速不可。接著把錢留在大衣口袋裡。他會拿起你的大衣,掛在自己的衣服旁,不動聲色拿走信封,把底片放進你大衣的口袋。你喝完酒,和對方握手,一切順利。隔天上午,你搭機回家。雷科勒克就是這麼說的。過程簡單無比。
藍森漫步走過空盪的酒吧,朝他走來。他身穿藍色防水衣,頭戴小帽,身材高壯。他短暫地看了泰勒一眼,然後對著泰勒背後的酒保說:「彥斯,我要啤酒。」他轉頭問泰勒。「你喝什麼?」
泰勒淡淡一笑。「你們本地的東西。」
「隨便他想喝什麼。都多加一份。」
酒保迅速扣上夾克鈕釦,打開酒櫃的鎖,倒了一大杯杜松子酒。他從冰箱取出啤酒給藍森。
「是雷科勒克派你來的?」藍森問得唐突。若有旁人,一定都聽得見。
「對。」他無精打采地接上,但接得太遲。「倫敦的雷科勒克公司。」
藍森端起啤酒,走到最近的桌子。端酒的手在抖。兩人坐下。
「那你告訴我好了,」他口氣十分嚴厲。「是哪個混帳下的命令?」
「我不知道。」泰勒大吃一驚。「我連命令是什麼都不清楚。又不是我的錯。我只是奉命來這裡拿底片。這種任務又不是由我負責的。我負責的是一些檯面上的工作──比如快遞。」
藍森傾身向前,一手放在泰勒手臂上。泰勒感覺得到他在顫抖。「我本來也是負責檯面上的工作,在今天以前都是。我飛機上有孩子啊。一共二十五個等著過寒假的德國小學生。整架飛機都是。」
「是。」泰勒勉強一笑。「是,剛剛在接機室裡有歡迎團。」
藍森動了火氣。「到底是要找什麼鬼東西?我實在搞不懂。羅斯托克究竟有些什麼東西?」
「不是跟你說過了,我跟這事情無關。」接著他說出前後矛盾的話。「雷科勒克說不是在羅斯托克,而是在羅斯托克南邊。」
「南方三角區:卡許達特、蘭朵恩、沃肯。你不說我也知道。」
泰勒看著酒保,神情焦慮。
「我們好像不應該這麼大聲,」他說:「那傢伙有點喜歡跟人作對。」他喝下一點杜松子酒。
藍森做出一個好像在撥開面前東西的手勢。「不幹了,」他說:「我再也不幹了。不幹就是不幹。如果按照航道飛,拍拍下頭的東西,是沒關係。不過這趟太過分了。你知道嗎?簡直是太過分了。」他的口音濃厚笨拙,宛如患上語言障礙。
白雪降自北方,在迷霧中受到夜風吹動,帶有海水的氣息。機場上的白雪將會停留整個冬季,在灰色土地上一片襤褸寒愴,是層冰冷而刺骨的粉塵,既不融化,也不凍結,而是維持靜態,彷彿一年無四季之分。不停變幻的霧氣宛如戰事的煙硝,逗留在雪地上,倏而吞噬機棚,倏而吞噬雷達中心,倏而吞噬機身。隨後才逐步釋放,色澤褪盡,成了白色沙漠中的黑色腐屍。
這幅景象沒有縱深,沒有縮凹,沒有陰影;大地與蒼穹合而為一,人影與建築物冰封於寒風中,有如浮冰裡的屍首。
小機場更遠處則空無一物,沒有民房,沒有山丘,沒有道路,連圍牆、樹木也付之闕如,僅有壓在雪堆之上的天空,和從波羅的海泥岸升入空中的滾滾濃霧。往內陸方向望去,可見群山。
一群兒童頭戴小帽,聚集在長長的觀景窗前,以德文嘰喳談天。有幾位學童身穿滑雪裝。泰勒戴著手套,手握杯子,雙目無神地凝視他們前方。一名男童轉身看著他,臉紅起來,悄聲對其他學童說話,孩子們安靜下來。
他動作很大地伸出手看錶,一方面是為了拉開外套袖子,另一方面是個人風格使然。他希望給人留下一個印象:軍人、訓練精實、隸屬高級的俱樂部。見識過大戰風浪。
還差十分四點。飛機已誤點一小時。機場不久後必將透過擴音器宣布誤點原因。他納悶的是,機場會宣布出什麼理由。大概是受濃霧影響吧,所以起飛時受到延誤。機場人員大概也一頭霧水──而且當然不會願意承認──這班飛機往羅斯托克以南方向,脫離航道兩百英哩。他喝完酒,轉身放下空酒杯。他不得不承認,有些不入流的外國酒若在產地國飲用,喝起來滋味還不錯。由於陷入苦等的狀態,有兩、三個小時要消磨,窗外又是零下十度,的確有可能碰到一些比杜松子酒更糟糕的狀況。回國後,他會請「隱名俱樂部」進貨。這樣一定會引起不小騷動。
擴音器嗡嗡響起,然後突然大響,音量漸減後,又再度發聲,音量已調至適中。學童們滿懷期望地望向擴音器。廣播首先以芬蘭文宣布,然後是瑞典文,現在則換為英語。自杜塞爾多夫起飛的北方航空二九○客機因故延誤,敬請原諒,延誤時間與原因不明。航空公司大概自己也不清楚。
然而泰勒是知道的。玻璃亭裡坐著精神抖擻的地勤人員,假設他從容地走過去告知原因,不知道對方會有何反應。二九○還要過一陣子才會到,小姐,那是因為在波羅的海上空被強烈北風吹離航道,搞亂了所有方位。但小妞當然不會相信,反而會認為他是在搞鬼。要到事後她才會恍然大悟,明白眼前這人非比尋常,他的來歷相當特別。
外面天色已開始轉暗。如今地面比天空更亮;在雪地襯托下,清理過的跑道有如疏洪道般醒目,沾染了琥珀色的標示黃光。在最靠近的飛機棚裡,日光燈管照得人與飛機皆顯得疲憊慘白;他前方的地面閃現管制塔臺的光束,似乎短暫地甦活過來。左邊的修理場駛出一輛消防車,加入已停在中央跑道附近的三輛救護車,四車同時打亮旋轉的藍燈,閃著警示訊號靜候。學童紛紛指向車陣,聒噪不休,興奮不已。
地勤小姐的嗓音再度透過擴音器響起,距上一次廣播可能僅隔數分鐘。學童再次噤口傾聽。第二九○號客機抵達時間將延誤至少一小時,本站若獲得進一步消息,將會立即廣播。小姐的聲音不大對勁,傳達出一種介於驚訝與焦慮之間的感覺,有六、七名坐在候機室另一邊的人似乎也感受到。一名老婦人對丈夫說了一句話後站起身,拎起手提包過去與學童同坐。她凝望著落日餘暉良久,神情呆滯,無奈無法從中獲得慰藉,因此便轉向泰勒,以英文發問。「杜塞爾多夫的飛機究竟是怎麼了?」她的嗓音帶有荷蘭女人的濃濃喉音,語調憤慨而急促。泰勒搖搖頭。「可能下大雪吧!」他回答。他個性乾脆,這樣的回答符合他的軍人作風。
泰勒推開旋轉門,下樓到接待廳。在靠近大門處,他認出北方航空的黃色三角旗。坐在櫃檯前的女地勤人員頗具姿色。
「杜塞爾多夫的客機發生什麼事了?」他的態度能讓人想把心裡的話講出來;據說他對小女孩很有一套。她微微一笑,聳聳肩。
「我認為是因為大雪。班機延誤在秋季很常見。」
「為何不問一下上司?」他建議,同時對著她面前的電話點頭示意。
「一有最新消息,」她說:「就會用廣播宣布。」
「小姐,是誰駕駛的?」
「什麼?」
「飛機是誰駕駛的,機長是誰?」
「藍森機長。」
「他技術好不好呢?」
這位小姐似乎大為震驚。「藍森機長的經驗非常豐富。」
泰勒看了她一眼,露齒一笑,說:「小姐啊,他頂多算是個運氣不錯的飛行員。」據他們說,泰勒的確懂得不少。而所謂的他們,便是週五晚上在隱名俱樂部齊聚一堂的人。
藍森。聽別人這樣道出姓氏,感覺詭異。在單位裡,他們絕不會指名道姓。他們偏好拐彎抹角,喜歡用臥底的姓名,只要不碰真名,什麼稱呼皆可:亞契小子、我們的飛行員朋友、我們來自北方的朋友、負責拍照的老兄;他們甚至會以文件上的字母加數字的代碼作為一種委婉的稱呼。在任何情況下,絕不指名道姓。
藍森。在倫敦時,雷科勒克曾讓他看過相片。藍森現年三十五,略帶孩子氣;金髮,外表俊美。他打賭空服員肯定愛他愛得半死。空服員的功能本來就只是讓機長得以消遣,反正其他人也看不見。泰勒右手快速伸進大衣外的口袋,只想確定信封仍在裡頭。他以前從未帶過這種錢。飛一趟五千美元,一千七百英鎊,免稅,只要在波羅的海上空稍微迷個路。請注意,這種事藍森不是天天做。雷科勒克說過,這趟任務比較特殊。他心想,假如自己倚在櫃檯上向女孩透露身分,她會有何種反應。不如讓她瞧瞧信封裡的鈔票。他從沒跟這樣的女孩交往過――真正的女孩,高䠷,而且年輕。
他再度上樓走進酒吧,酒保對他越來越熟了。泰勒指著擺在酒架中上的杜松子酒瓶說:「請再給我一杯,就是那個,你正後方的那瓶。這可是你們本地的穿腸毒藥。」
「這是德國酒啊!」酒保說。
他翻開皮夾,取出一張鈔票。膠膜後面夾著小女孩的相片,九歲左右,戴著眼鏡,抱著洋娃娃。「我女兒。」他向酒保解釋,酒保則以微笑應付。
他的語調變化多端,說起話來如同相當習慣出差的上班族。在與同階級的人對話時,他虛假的尾音會拖得更誇張,為了要強調一種根本不存在的優越感,又或是像現在,在他緊張的時候。
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確有些心虛。以他的歷練與年齡,從例行的快遞工作跨足情報領域,狀況確實有些弔詭。這種工作應該交給情報局那些豬玀來辦,根本不該落在自己的單位。他的單位負責的是他習以為常的普通例行公事,與這項任務有著天壤之別,也因此令他進退維谷,不得不置身異國荒郊。怎麼會在這種地方蓋機場呢?他怎麼也想不透。說到出差海外,他一般而言都很樂意,例如到漢堡與老吉米‧哥頓接洽,或是到馬德里花天酒地一夜。能離開瓊妮一下對他是有好處的。他跑過土耳其兩、三趟,只不過中東人不太合他胃口。但即使是土耳其,跟這一趟比起來仍顯得易如反掌。出差土耳其時,他搭的是頭等艙,行李擺在身旁的座位上,口袋裡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通行證;他有身分、有地位;視同外交人員――或幾乎算得上外交人員。但這趟不同,他不太喜歡。
雷科勒克說過,這一趟非同小可,泰勒也相信了他。上頭幫他偽造護照,把姓改成Malherbe,他們說正確發音是馬勒比。而這個姓到底是誰選的?只有老天知道。這個姓泰勒連拼都拼不出來,今早住進旅館填寫姓名時,就出了一點洋相。津貼的數字當然很理想,行動開支一天十五英鎊,而且不必出示收據。他聽說情報局給過十七英鎊。這錢可善加利用,買點東西送瓊妮。但她大概比較喜歡現金。
這事他當然有告訴過她。其實他不該透露,但雷科勒克並不認識瓊妮。他點起一支菸,吸了一口,捧在手心,就像哨兵值勤時抽菸的模樣。大老遠跑到北歐,怎麼可能不告訴老婆?
學童緊貼窗戶。他們究竟在看什麼呢?他不禁納悶。這些孩子應付外語頗有一套,實在令人驚訝。他又看了一下手錶,幾乎沒有注意時間。又忍不住碰碰口袋裡的信封。最好別再喝了,腦子必須保持清醒。他盡量讓自己去猜瓊妮現在正在做什麼――大概正坐著喝琴酒吧。整天上班也難為她了。
他突然發現周遭安靜了下來。酒保靜靜站著聆聽。圍坐餐桌的老年人也在聽著,好幾張傻呼呼的臉轉向觀景窗。隨後,他清楚聽見飛機的聲響。仍在遠方,卻逐漸靠近小機場。他趕緊走向窗戶。走了一半,擴音器就響起,才以德文廣播了幾個字,學童就宛如一群鴿子那樣紛紛飛向接待廳。圍坐餐桌的那群人也站起來,女人伸手拿手套,男人拿起外套與公事包。最後,英文廣播傳來:藍森準備降落。
泰勒望著夜色。沒有飛機的跡象。他等著,焦慮之情逐步升高。他心想,簡直像世界末日。外面簡直就像該死的世界末日――萬一藍森墜機……萬一照相機被他們找到……他寧可由其他人負責這項任務,比如伍德夫。伍德夫幹嘛不接手?或是派那個聰明的大學畢業生艾佛瑞過來?風勢轉強了。他敢發誓,風勢比剛才強許多,強風吹攪雪地,將雪塊颳上跑道,他憑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強風同時也扯著照明燈,在地平線上掃起條條白柱,然後再猛然吹開,彷彿痛恨著自己的創作。一股陣風忽然打在他眼前的窗戶,打得他向後縮,隨之而來的是雪花的沙沙聲,以及木框又急又短的呻吟。泰勒再次看錶。他已經看成習慣了。知道時間似乎有助心情安穩。
風雪這麼大,藍森不可能安全降落。絕不可能。
他的心跳像是暫停了。他聽到汽車喇叭聲。起初輕柔,隨後急升轉為嗚咽,然後四輛車齊聲在景況悽慘的小機場上呻吟,彷彿飢餓的動物正嗥叫著。失火。飛機一定著火了。飛機失火,他盡全力降落……泰勒越來越慌亂,急著找人問清楚。
酒保站在他身邊擦拭杯子,望向窗外。
「怎麼回事?」泰勒大喊。「為什麼警笛在響?」
「天氣惡劣的時候都會響警笛的。」他回答。「法律規定。」
「天氣不好,為什麼讓他降落?」泰勒追問。「讓他往南一點降落不就好了?這地方太小了,幹嘛不改到比較大的機場?」
酒保漠不關心地搖搖頭。「情況又不算太差,」他邊說邊指著小機場。「何況他誤點太久。可能汽油用光了。」
他們看見飛機出現在小機場上方不遠處,燈光在照明燈上方交替閃耀,機上的大燈掃瞄著跑道。飛機落下了,安全降落。推進器呼吼的聲音傳來,開始進行漫長的滑行,朝抵達站前進。
酒吧客人已走光,只剩泰勒一人。他點了一杯酒。交代事項他都熟記在心。雷科勒克吩咐過,要待在酒吧裡,藍森會自己前來,但他會稍微多花一點時間,因為他必須先處理飛航文件,取出照相機內的底片。泰勒聽見學童在樓下高歌,由一位女士帶領――四周淨是婦孺,這是成何體統?他進行的不是男人的任務嗎?口袋裡不是裝了五千美元與一本假護照嗎?
「今天的班機起降到此為止,」酒保說:「現在開始禁止任何起降。」
泰勒點頭。「我知道。外面情況很嚇人,真的很嚇人。」
酒保收起酒瓶。「不會有危險的啦,」他以安慰的口吻接著說:「藍森機長是個非常優秀的機長。」他遲疑了一下,不知是否該收起杜松子酒。
「當然不會有危險,」泰勒口氣很衝。「誰說會有危險的?」
「再來一杯?」酒保說。
「不用了,你自己喝。喝啊,給你自己倒一杯。」
酒保不情願地替自己斟酒,然後將酒瓶鎖進酒櫃。
「話說回來,他們是怎麼辦到的?」泰勒說。他的口氣帶有一點求和的意味,想繼續跟酒保聊天。「天氣這麼糟,什麼也看不見。」他若有所思地微笑。「坐在機頭,再怎麼拚命看、專心看,一整天也看不到東西,不如閉上眼睛算了。這種情況我看多了。」泰勒接著說。他雙手略呈杯狀,放在前方,彷彿正在操作飛機。「我很清楚,要是真的出了什麼差錯,倒楣的是那些飛行員。」他搖搖頭。「他們可以把錢留著,」他高聲說:「他們掙的每一分錢都有權力留著用。特別是像這種尺寸的風箏啊――這種東西全是用細繩子串起來的。細繩子。」
酒吧以冷淡的態度點頭,喝乾剩下的酒,洗洗酒杯,擦乾,放在櫃檯下的架上。他解開白色夾克。
泰勒不動聲色。
「嗯,」酒保皮笑肉不笑。「我們得回家了。」
「我們?什麼意思?」泰勒眼睛睜得很大,頭向後仰。「你什麼意思?」現在他已經準備要跟人吵架――誰都可以。藍森已經降落了。
「我得打烊了。」
「回家個頭。再幫我們倒一杯,快倒呀!你想回家的話請便。我家可是在倫敦喔。」他的語氣有挑釁意味,半屬玩笑性質,半屬憎惡。他的音量越來越大。「明天早上以前,你們的航空公司要是沒辦法送我回倫敦,我也到不了其他鬼地方。你居然叫我回家,是不是糊塗了啊?老兄?」他仍保持微笑,卻笑得短促且憤怒,是那種緊張的人快要發脾氣時的笑容。「下一次,當我請你喝一杯的時候,麻煩你有禮貌一點……」
門打開,藍森走進來。
原本預設的情況並非如此。這完全不符合雷科勒克描述的情況。雷科勒克說過,待在酒吧裡,坐在靠角落的那張桌子喝酒,帽子和外套放在另一張椅子上,擺出正在等人的姿態。藍森進來時,總會點啤酒喝。藍森個人偏好公眾交誼廳。因為那裡人來人往。雷科勒克如是說。這種機場雖小,周遭的大小事卻少不了。他會四處看,假裝要找地方坐下――動作光明正大――然後走過來,問你這邊有沒有人坐。你會說,原本是為朋友而留,結果朋友放你鴿子。藍森會問,那可以坐下嗎?他會點啤酒,然後說道:「是等男性朋友還是女性朋友?」你會對他說,這問題問得未免也太粗線條了吧,然後兩人大笑一陣,開始聊天。要問兩個問題:高度與航速。研究處非知道高度與航速不可。接著把錢留在大衣口袋裡。他會拿起你的大衣,掛在自己的衣服旁,不動聲色拿走信封,把底片放進你大衣的口袋。你喝完酒,和對方握手,一切順利。隔天上午,你搭機回家。雷科勒克就是這麼說的。過程簡單無比。
藍森漫步走過空盪的酒吧,朝他走來。他身穿藍色防水衣,頭戴小帽,身材高壯。他短暫地看了泰勒一眼,然後對著泰勒背後的酒保說:「彥斯,我要啤酒。」他轉頭問泰勒。「你喝什麼?」
泰勒淡淡一笑。「你們本地的東西。」
「隨便他想喝什麼。都多加一份。」
酒保迅速扣上夾克鈕釦,打開酒櫃的鎖,倒了一大杯杜松子酒。他從冰箱取出啤酒給藍森。
「是雷科勒克派你來的?」藍森問得唐突。若有旁人,一定都聽得見。
「對。」他無精打采地接上,但接得太遲。「倫敦的雷科勒克公司。」
藍森端起啤酒,走到最近的桌子。端酒的手在抖。兩人坐下。
「那你告訴我好了,」他口氣十分嚴厲。「是哪個混帳下的命令?」
「我不知道。」泰勒大吃一驚。「我連命令是什麼都不清楚。又不是我的錯。我只是奉命來這裡拿底片。這種任務又不是由我負責的。我負責的是一些檯面上的工作──比如快遞。」
藍森傾身向前,一手放在泰勒手臂上。泰勒感覺得到他在顫抖。「我本來也是負責檯面上的工作,在今天以前都是。我飛機上有孩子啊。一共二十五個等著過寒假的德國小學生。整架飛機都是。」
「是。」泰勒勉強一笑。「是,剛剛在接機室裡有歡迎團。」
藍森動了火氣。「到底是要找什麼鬼東西?我實在搞不懂。羅斯托克究竟有些什麼東西?」
「不是跟你說過了,我跟這事情無關。」接著他說出前後矛盾的話。「雷科勒克說不是在羅斯托克,而是在羅斯托克南邊。」
「南方三角區:卡許達特、蘭朵恩、沃肯。你不說我也知道。」
泰勒看著酒保,神情焦慮。
「我們好像不應該這麼大聲,」他說:「那傢伙有點喜歡跟人作對。」他喝下一點杜松子酒。
藍森做出一個好像在撥開面前東西的手勢。「不幹了,」他說:「我再也不幹了。不幹就是不幹。如果按照航道飛,拍拍下頭的東西,是沒關係。不過這趟太過分了。你知道嗎?簡直是太過分了。」他的口音濃厚笨拙,宛如患上語言障礙。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脆弱的真相
9折
特價306元
貨到通知
死亡預約
9折
特價198元
貨到通知
上流謀殺
9折
特價198元
貨到通知
冷戰諜魂
9折
特價234元
貨到通知
鏡子戰爭
9折
特價270元
貨到通知
德國小鎮
9折
特價324元
加入購物車
頭號要犯(電影諜報風雲原著小說)
9折
特價324元
貨到通知
天真善感的愛人
9折
特價432元
加入購物車
榮譽學生
9折
特價450元
貨到通知
史邁利人馬
9折
特價351元
貨到通知
女鼓手
9折
特價450元
貨到通知
使命曲
9折
特價315元
貨到通知
完美的間諜
9折
特價450元
貨到通知
我輩叛徒
9折
特價324元
貨到通知
蘇聯司
9折
特價432元
貨到通知
二十世紀諜報小說大師 約翰.勒卡雷典藏套書上(共八冊)
9折
特價2457元
貨到通知
冷戰諜魂:約翰‧勒卡雷系列03
9折
特價306元
加入購物車
間諜身後:約翰‧勒卡雷系列09
9折
特價315元
加入購物車
鍋匠裁縫士兵間諜
9折
特價405元
加入購物車
此生如鴿: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的38個人生片羽
9折
特價378元
加入購物車
摯友
9折
特價405元
加入購物車
看更多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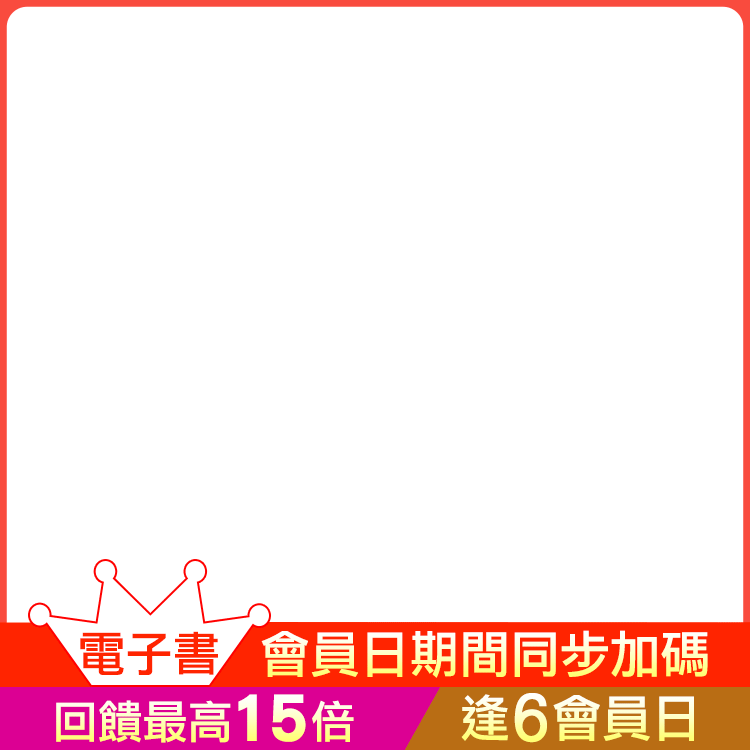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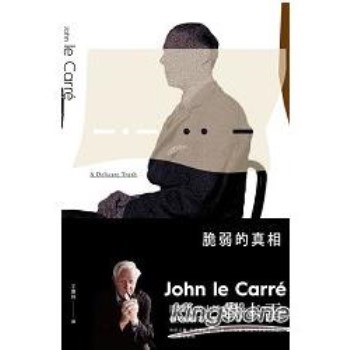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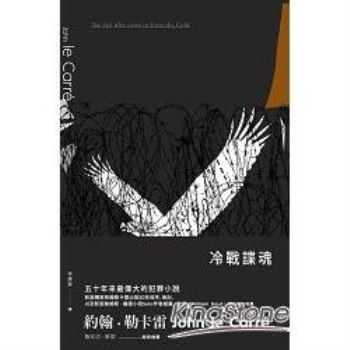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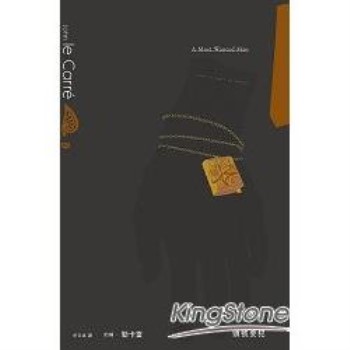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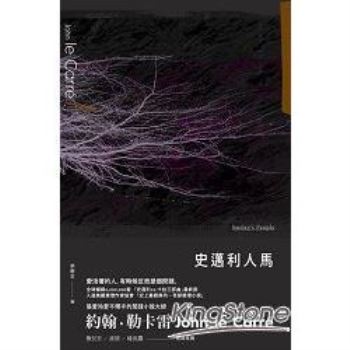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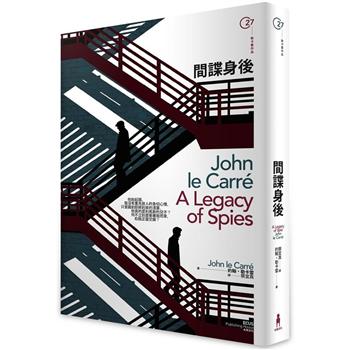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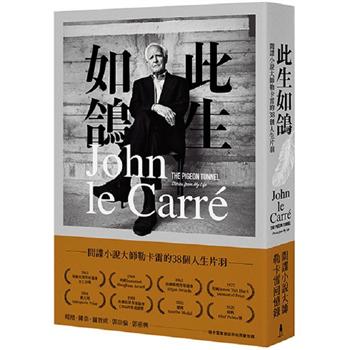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