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金的故事販賣機【電影書腰版】:收錄《史蒂芬金之猴子》電影原著小說!
超值合購
優惠活動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收錄《史蒂芬金之猴子》電影原著小說
\\\隨書限量附贈早場票價優惠券///
(詳見書腰底說明)
《分歧者》席歐.詹姆斯主演、
《厲陰宅》溫子仁製作、
《長腿》奧茲古.柏金斯導演.編劇,
2/27驚駭上映!
如果你來不及看史蒂芬.金的眾多代表作,
這一本絕對是最佳入門!
故事之王創作精華大集合,
史上最強,包君滿意!
不管你是吃重鹹還是輕辣,
這部故事販賣機有各種口味,任君選擇!
★ ☆ ★ ☆ ★
遇見史蒂芬.金,開始在最日常的世界裡窺見無限驚險!
小哈爾在衣櫥裡找到了一隻會敲鈸的玩具猴子,如果幫它上了發條,它還會露齒微笑。可是哈爾卻發現,只要它的鈸一響,恐怖的事情就會跟著出現……
每年夏天陶德太太都會來城堡岩避暑,但是某一天,喜歡開快車抄捷徑的她卻離奇失蹤了。陶德太太的園丁荷馬只能猜測,她可能找到了一條「短於直線距離」的捷徑……
拜訪史蒂芬.金,領略超乎想像的愛.恨.情.仇!
理查收到了姪子送給他的拼裝電腦,這台神奇的電腦能夠實現指令,並改變現實世界的事物。正在為惡妻孽子傷腦筋的他,忍不住按下了「刪除鍵」……
在回城堡岩的路上,他遇見了美麗的娜娜。為了表達愛意,他不惜和娜娜一同殺害冒犯她的路人和警察,但是,法庭上所有的目擊證人卻說犯案的只有他一人……
本書共收錄故事大師史蒂芬.金二十二則短篇小說代表作,從他十八歲發表的〈收割者的影像〉,一直到一九八三年的〈變形子彈之歌〉,還有由《刺激1995》名導演法蘭克.戴瑞邦改編拍成電影的〈迷霧驚魂〉,不論是奇幻、驚悚,或推理、恐怖,史蒂芬.金將日常生活經驗化成豐沛的創作靈感,巧妙地呈現了一針見血的人性鋪陳和出人意表的情節轉折,完全顛覆了讀者的閱讀想像!
【來自世界的最高讚譽】
對喜愛閱讀小說的人而言,故事本身即是最讓人著迷不已的重要環節,而《史蒂芬.金的故事販賣機》也正藉由了短篇小說的特質,巧妙讓我們再度感受到那種單純的閱讀享受。我想,如同床邊故事般每晚閱讀一篇,或許正是閱讀本書最好的方式,也是讓我們再度溫習短篇小說樂趣的最佳方式!――城堡岩小鎮家族創立人/劉韋廷
極度精采、天才之作!史蒂芬.金又一傑作!――紐約每日新聞:
讀這本書時千萬別回頭!――紐約時報書評特刊
史蒂芬.金再創巔峰!――丹佛郵報
充滿狂野想像、殘酷而歡欣!史蒂芬.金再次證明自己是個頂尖說書人!――美聯社
【各界名家一致盛讚】
【城堡岩小鎮家族創立人】劉韋廷 專文導讀
【名作家】水泉
【漢聲電台主持人】宋銘
【中時副總編輯】張慧英
一致熱血狂推!
(依姓名筆劃序排列)
影音介紹
試閱
娜娜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即使事到如今。我還是無法告訴你,為何我會這麼做。在審判時我也說不出口。這裡也有很多人問我。有個心理醫生問我。可是我默然不語,雙唇緊閉。除了在我這牢房裡,我在這裡就不沉默了。我會尖叫著醒來。
在夢裡,我看見她走向我。她穿著一件幾乎透明的白袍,表情混合著慾望與勝利。她在一個有石地板的黑暗房間裡走向我,而我可以聞到乾枯的十月玫瑰。她張開雙臂,我也張開雙臂迎向她,想要擁她入懷。
這時她開始變化,變得乾枯。她的頭髮變得粗糙,光澤褪盡,由烏黑褪為醜陋的灰棕色,披散在她雪白的兩頰旁。那雙眼睛縮小變得像珠子,眼白消失了,接著她用那像兩點烏玉般的小眼睛怒視著我。那小嘴變成血盆大口,還有兩排暴突的黃牙。
我想叫,我想醒來。我不斷地尖叫。我又被抓住了。我總是被抓住。
他們認為是我們一起做的那些事讓我瘋狂。但我的神志就某方面來說是清醒的,而且我從未停止尋找答案。我還是想知道為什麼,是什麼。
他們給我紙筆。我會把這一切寫下來。也許我會回答他們一些問題,也許我在寫下時會回答自己一些問題。但等我寫完後,還有另一件事。他們不知道我有一樣東西,那我是偷拿的,現在藏在床墊下,一把從監獄餐廳裡偷來的餐刀。
我得從奧古斯塔開始說起。
當我寫著這些事情時已經入夜,八月美好的一夜,天上繁星閃爍。透過鐵窗,我能看到星星。我的鐵窗能俯瞰運動場,和一小片用兩隻手指就能遮住的天空。這房間悶熱得很,不過我打赤膊、只穿內褲。我可以聽見蛙鳴和蟋蟀的唧唧聲,這些屬於夏季的聲音。但只要閉上眼,我就能把冬天帶回。那晚嚙人的寒冷、黑暗,以及那不再屬於我的城市的,赤裸而不友善的燈光。那天是二月十四日。
瞧,我什麼都記得。
看我的手臂──全是汗水,凝成了雞皮疙瘩。
奧古斯塔……
我到奧古斯塔時,已經差不多快凍死了。我特別挑了個晴朗的日子告別大學校區,準備搭便車到西部去。不過看起來,我還沒出本州就會先凍死了。
有個警察把我從州際公路旁踢了下來,並威脅我說,要是他又逮到我在高速公路上豎拇指想搭便車,他就會逮捕我。我差點就想回嘴要他直接逮捕我。州際公路平坦的四線道很像機場跑道,風呼呼作響,吹著水泥路面上的雪花向前滾。對坐在擋風玻璃後的人來說,黑夜中每個站在公路旁招手的人都像強暴犯或殺人兇手,假如他還有一頭長髮,你更可把他當成同性戀或有戀童癖的人。
我在路上試了一會兒,可是沒用。大約七點四十五分時,我意識到要是再不快點到個溫暖的地方,我就要被凍死了。
我走了一哩半的路,才在二○二號公路旁找到一家兼營餐館的加油站,霓虹招牌寫著「喬伊小吃」。碎石停車場上停了三輛大卡車和一輛新轎車。餐館門上掛了個沒拿下的聖誕花圈,門邊有個溫度計,顯示當時氣溫是零下五度。我的耳朵除了頭髮外,沒有任何遮蔽,而我的羊皮手套又有點裂開了,指尖就像木頭一樣,沒什麼感覺。
我開門進去。我最先感覺到的是暖氣,又暖又舒服。其次我聽到自動點唱機播著梅爾‧海格(Merle Haggard)的一首民謠:「我們不像舊金山的嬉皮,留著又髒又亂的長髮。」
我第三件感覺到的是「眼光」。那種一旦你讓頭髮長過耳垂,就會感受到的眼光。那時人們一望就知道你不是獅子會、麋鹿會(Elks,北美地區的慈善俱樂部)或海外退伍軍人協會的會員。你知道這種眼光,但永遠習慣不了。
那時給我這種眼光的,是四個坐在卡座裡的卡車司機,櫃台還有兩個司機,再加上兩個穿著廉價皮大衣的老太太,站在吧台後的廚子,跟個手上沾滿肥皂泡的瘦高小子。有個女孩坐在吧台遠端,但她只看著她的咖啡杯。
她是我察覺到的第四件事物。
我的年紀已經夠大,知道沒有一見鍾情這回事,那不過是流行歌詞作者為了配合月亮與六月的韻腳而想出來的。那是為了讓少男少女在舞會裡牽手用的,對吧?
可是看到她時,卻讓我有了這種感覺。你大可笑我,但要是換成你看到她,也一樣笑不出來。她美得逼人。我毫無疑問地知道,那家餐館裡的其他人和我也都有同感。就如我知道的,在我進來前,她也已接受過了注目禮。她的頭髮烏黑,黑得在日光燈下幾乎轉藍,自然地披在她茶色舊大衣的肩上。她的肌膚雪白,微微透著點血色──她先前一定也被凍僵了。長而黑的睫毛、清亮的眼睛,眼角微微上翹。在挺直貴氣的鼻梁下是飽滿迷人的雙唇。我看不出她身材如何。我不在乎,我想你也不會。她只需要那張臉、那頭黑髮、那副神情。她優雅絕倫。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個形容詞。
娜娜。(待續)
我挑了和她相隔兩張凳子的座位坐下,廚子立刻走過來望著我。「要什麼?」
「黑咖啡,謝謝。」
廚子把我的咖啡端來,用力一放,有些咖啡濺到我手上。同時有人拉拉我的衣袖。我轉過頭,看見了她──她已經移到我旁邊的空凳上。近看之下,那張臉幾乎可說炫目,我又灑了些咖啡出來。
「我──」她話說到一半,顯得很茫然。我突然意識到她很害怕。我對她的第一個反應再度湧了上來──保護她、照顧她,讓她不再害怕。「我需要有人載我一程。」她急促地把話說完。「我不敢問他們任何一個。」她微微指了一下卡座裡的司機。
我要如何才能讓你了解,我願付出任何代價,只要能告訴她:當然!把妳的咖啡喝完吧,我的車就在外面。看看她,就像看著復活的蒙娜麗莎,或愛神維納斯。但還有另一種感覺。彷彿在我迷惘而黑暗的心靈中,突然出現一道強光。我只知道,她需要的東西我沒有,而這個事實讓我心碎。
「我沿途搭便車來的。」我告訴她:「有個警察把我踢下州際公路,我是為了避寒才到這兒來的。真抱歉。」
「你是大學生嗎?」
「曾經是。在他們開除我之前,我主動退學了。」
「你要回家去嗎?」
「無家可歸。我受州政府監護。我上大學是因為有獎學金,現在我搞砸了,不知該上哪兒去。」只要五個句子,就能說完我一生的故事,這真讓人氣餒。
她笑了──她的笑聲讓我一陣熱一陣冷。「那我們算是一個袋子裡跳出來的貓──同病相憐了。」
我正想好好和她搭訕──說句「是嗎?」之類的──時,一隻手落到我肩上。
我轉過頭。是剛才坐在卡座裡的其中一個司機。他的下巴有金色鬍碴,嘴裡咬著根火柴,他全身都是機油味。
「我想你喝完咖啡了。」他說著,嘴唇一撇,露出獰笑。「你把這地方弄臭了,小子。你是個小子吧?有點看不出來。」
「我看你也不是什麼玫瑰花。」我說:「你用什麼刮鬍水,帥哥?曲軸箱潤滑油嗎?」
他用力甩了我一巴掌,打得我滿眼金星。
「別在這裡打架。」廚子說:「想揍他的話,到外面去。」
「來呀,你這該死的小子。」那卡車司機說。
該是那女孩出面說話的時候了。說句「放開他」或「你這個壞蛋」之類的。但她什麼也沒說。她只專注地望著我們兩個。那真有點可怕。我想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眼睛有多大。
「你要我再賞你一巴掌嗎?」
「不用。走吧,豬頭。」我不知道那句話是怎麼跳出來的。我不喜歡打架,我不是打架高手,罵人更不在行。但我當時實在氣不過,那句話自然地就冒了出來,而且我想殺他。也許那話正擊中了他的弱點,因為有一剎那,他臉上閃過猶豫的神色,不自覺地想著自己會不會挑錯嬉皮來修理了。但那絲猶豫一閃即逝,他絕對不會向個用國旗擦屁股的長髮臭嬉皮屈服──至少不能在同伴面前,尤其像他那麼一個虎背熊腰的卡車司機。
我們走向門口,那個卡車司機的同伴爭先恐後地起身準備看笑話。
娜娜?我想到她,但這時有點心不在焉。我知道娜娜會在那裡。娜娜會照顧我。我知道,正如我知道外頭會很冷。覺得自己了解一個五分鐘前才遇上的女孩,是件很奇怪的事。奇怪,但我直到後來才想起這點。我的心被憤怒盤據──不,該說是盤據,而是遮蔽。我很想殺人。
那凍人的冷分外清明,感覺就像我們的身子如利刃般劃過它。停車場結霜的碎石子路在他的靴子和我的鞋子下刺耳地吱喳作響。我們短促的呼氣在空中化成霧氣。那個卡車司機轉向我,戴著手套的手掄起拳頭。
我全身好像腫脹了起來。在麻木感中,我微微意識到體內有股從未察覺過的力量,那將會侵蝕我的理智。這感覺十分駭人──但同時我也很歡迎它、期望它、渴求它。
他對我揮出拳頭,我躲過他的右拳,毫無感覺地用臉接下他的左拳,接著便一腳踢向他的小腹。他喘了一大口氣,在空中化為一團白霧。他抱著肚子咳嗽,想要退開。
我跑到他身後,仍然笑得像某個農夫的吠月之犬,在他轉身前狠狠揍了他三拳,他亂揮亂舞的手刷過我的鼻子。我怒不可遏,再次踢他,腳抬得又高又用力,他對著夜空尖叫,我聽到一聲肋骨斷裂聲。他痛得彎下身子,我立刻撲跳上去。
後來在審判中,一名卡車司機作證說我當時像頭野獸。
我決定殺了他。我要踢到他死為止,然後再把其他人也統統殺掉──除了娜娜。我又踢他,這回他一翻身,仰面躺著,茫然地望向我。他啞著聲說:「我叫你叔叔。求你,求你──」(待續)
我在他身旁跪下,低聲說:「你叔叔在這裡。」我伸手掐住他的脖子。
三個人一起跳向我,將我從他身上拉開。我站起來時依然獰笑著朝他們逼進。他們齊步後退,三個大男人全嚇得臉色發青。
這時,我的怒氣消退了。
就這樣,所有怒火都熄了,我又變回了自己,氣喘吁吁的站在喬伊餐館的停車場上,覺得噁心而驚恐。
我轉身望向餐館。那女孩還在那裡,美麗的臉龐煥發著勝利的光采。她一手舉拳,與肩膀同高,就像那些黑人在那次奧運會上的動作,向我致敬。
我又回頭注視躺在地上的那個男人,他仍然試著爬開。當我走近他時,他的眼球恐懼地轉動。我迷惑地望著。「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傷得他那麼重。讓我幫忙──」
「你滾吧,這就是你該做的。」廚子說。他站在娜娜前面,門前的台階下方,手裡抓了根木匙。「我要叫警察了。」
我把我的羊皮手套留在餐館裡了,但走進去拿似乎不是什麼好主意。我兩手插進褲袋,邁步往高速公路入口走去。我估計在警察逮捕我之前,我搭上便車的機率大概是一成。我的耳朵快凍僵了,而且胃部陣陣作嘔,真是多事的一夜。
「等等!嘿,等一下!」我回過頭。是她,跑著向我追來,黑髮在腦後翻飛。
「你真棒!」她說:「真棒!」
「我傷得他很重。」我說:「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傷過人。」
「我倒希望你殺了他。」
我在昏暗的光線中對她眨眨眼。
「你該聽聽在你進來前,他們都對我說些什麼。下流、噁心的大笑──呵呵,看那小女孩,晚上一個人坐在那。妳要上哪兒去,甜心?要搭便車嗎?我可以讓妳上車,只要妳也讓我上。下流!」
她憤怒地回過頭,彷彿想從那雙黑色眼中打出一道閃電,把他們全都電死。接著她的目光轉向我,我的心似乎再次打開探照燈。「我叫娜娜,我要跟你一起走。」
「走去哪裡?去監獄嗎?」我用雙手拉拉頭髮。「有這頭長髮,第一個讓我們搭便車的人很可能會是警察。那個廚師說要報警不是唬人的。」
「我來找車,你站在我後面。他們會為我停車的。他們看到女孩會停車的,只要她夠漂亮。」
這點我無法和她爭辯,也不想和她爭辯。一見鍾情?也許不是。但那是種感覺。你了解那種震動嗎?
「拿著。」她說:「你忘了這個。」她把我的手套遞給我。
她沒有回餐館去。那表示她一直拿著我的手套。她早就知道會跟我一起走。這讓我有點悚然。我戴上手套,和她一起走向公路。
關於搭便車,她說的沒錯。第一輛開過的車便為她停了下來。
我們在等待時,一句話都沒說,但感覺卻像說了很多話。我不會說是什麼心電感應之類的狗屎,你知道我的意思。只要你曾經與某人極度親密,你一定也有過同樣的感覺。談話是多餘的,交流似乎是以一種高頻率的情感電波進行。只要手指的一個動作就夠了。我們對彼此完全陌生。我只知道她的名字,而此刻我回想起來,我根本還沒把名字告訴她。但我們仍在沉默中交流。那並不是愛。我真痛恨得一直重複這點,可是我覺得非說不可。我不願以我們當時的感受污染那個字──直到我們做了那些事,直到回到城堡岩,直到作了那些夢以後。
有輛車的燈光爬上了彎道。
我照她說的站在她身後。她把頭髮往後梳,抬起那張美麗的臉。娜娜豎起拇指。那輛車,一輛雪佛蘭從我們身邊駛過,想不到它的煞車燈開始閃爍,娜娜立刻抓住我的手。「走吧,我們找到便車了!」
那男人很熱心地探身越過乘客座為她開門。車內的頂燈亮起時,我看見了他──一個身材頗高大的男人,穿著一件名貴的駝毛外套,帽子下露出漸灰的頭髮,清晰的五官因為多年的美食而顯得線條柔和。一個生意人或是推銷員,單獨一人。他看到我時吃了一驚,卻已來不及將車子換檔開走。這許這樣對他也好,以後他可以騙自己說是看到我們兩個,他是真的好心想幫一對年輕人。
娜娜坐進他旁邊,我跟在她後面上車時,那人說:「今晚好冷。」
「的確是。」娜娜甜甜地說:「謝謝你!」
「是的。」我說:「謝謝。」
「不客氣。」於是我們離開,把救護車、卡車司機、和喬伊餐館拋在身後。
我在七點半時被踢下高速公路。這時不過八點半。一個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做或可能遭遇的事,實在是很驚人。
我們正往奧古斯塔收費站的黃色閃光標誌駛近。
「你們要到多遠呢?」那駕駛人問道。
我們倆一時都沒開口。我原本希望可以搭便車到吉特里,去找個在那裡教書的熟人。想來這是個很好的答案,我正想這樣答覆時,娜娜卻說:「我們要到城堡岩,那是南邊一個小鎮,就在路易斯敦西邊。」
城堡岩。那讓我覺得怪怪的。我曾是城堡岩的常客,直到艾斯‧馬瑞爾把我的生活搞爛為止。(待續)
那人停下車,取了付費票根,然後我們又上路了。
「我只到加德納鎮。」他扯謊:「就在下個出口,不過這對你們也算有點幫助。」
「是的。」娜娜仍舊甜甜地說:「真謝謝你在這麼冷的夜裡停車。」她說話時,我可以從那情緒的高波段聽出她的怒意:赤裸而惡毒,讓我不寒而慄,就像包裹中傳出嘀嗒聲一般嚇人。
「我姓布蘭奇。」那男人說:「諾曼‧布蘭奇。」他對我們伸出手。
「我叫雪柔‧葛雷。」娜娜泰然自若地說。
我明白了她的暗示,也報了個假名。「幸會。」我喃喃說了一句。
他的手又厚又軟,像個手掌型的熱水壺。這感覺讓我覺得噁心。想到我們不得不求這自以為施恩的男人載上一程,而他原以為自己有機會載到一個獨自搭便車的漂亮女孩,她可能會同意和他睡一晚,以回報為她省下的巴士車費,這想法讓我噁心。我想到,如果我單獨一人,這個此時對我伸出胖手的男人就會直駛而去,根本不會停車,我覺得噁心。想到他會在加德納鎮出口拋下我們,又直接駛回高速公路,看也不看我們一眼地往前衝,暗自慶幸圓滿地解除了一個令他困擾的局面,這讓我覺得噁心。他所有的一切都讓我噁心。他的雙下巴,他那向後梳齊的頭髮,他的古龍水香味。
而他有什麼權利?什麼權利?
噁心的感覺開始凝固,怒火又逐漸增長。雪佛蘭車燈平順地衝過黑夜,我的怒火急於發洩,勒殺與他有關的一切。就在這時,娜娜把一把指甲銼刀塞進我手裡。
我三歲時得了重感冒,被送進醫院。我三歲時,父親在床上抽菸時睡著,於是整個家被燒毀,我父母和哥哥德瑞都葬身火窟。我沒有親戚可以投靠,因此我成了州政府的被監護人。我的「養父母」姓霍利,住在哈洛鎮,和城堡岩隔著一條河。他們有棟三層樓的農舍,一共十四個房間。廚房裡的煤炭熱氣可以勉強傳到樓上。霍利太太很胖、霍利先生瘦巴巴的。我有三個「兄弟」,全是被監護人。我們只是點頭之交,就像一起參加三天巴士旅遊的遊客。
我在學校裡功課很好,高中時我還參加了棒球隊。霍利夫婦一直要我退出,但我堅持參加,直到艾斯事件發生為止。從那以後,我就哪裡也不想去,因為我的臉腫了起來,全身是傷,更不用說貝西還到處跟人亂說。因此我退出球隊,霍利夫婦立刻為我找到一份工作,在一家雜貨店搬汽水。
我高三那年二月,參加了學力測驗,用我偷藏在床墊裡的十二美元支付測驗費。緬因大學接受了我,並給我一小筆獎學金和一份在圖書館的工讀。當我把獎學金文件拿給霍利夫婦看時,他們臉上的表情是我一生最佳的回憶。
我離家前,霍利太太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可以的話就寄點什麼回來給我們吧。」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他們。我大一時成績很好,那年夏天並在圖書館全天工作。第一年我寄了張聖誕卡給他們,但就那麼一張。
我在大二上學期戀愛了。那是當時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她漂亮嗎?她漂亮到能讓你倒退兩步。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她看中我哪一點,我甚至不知道她愛不愛我。我跟她睡過兩次,兩次都不是為了愛。接著她從感恩節假期返校後,說她愛上一個住在同一個小鎮的兄弟會男孩。我試著讓她回心轉意,有一次還差點成功,可是她已經有了以前沒有的──遠景。
不管我從家人葬身火窟後的這些年來成就了什麼,但她的胸前別著那傢伙的別針時,這一切全都崩潰了。
從那以後,我跟三、四個願意和我睡覺的女孩冷一陣、熱一陣。我開始有點害怕女孩,而且能撩撥起我性慾的比無法撩撥我的更讓我害怕。我不在時她在幹什麼?她是怎麼想我的?或者還有,她有多了解我?她有多不了解我?一旦我開始想這些事,我就無時不刻都在想著。
我開始酗酒,成績跟著一落千丈。寒假前我接到一封信,說如果我的成績在六個星期內沒有進步,下學期我的獎學金支票就會被扣。我的成績沒什麼進步。二月九日,文理學院的院長寄來一封信,說我當掉了三分之二的主修學分。二月十三日,我接到那女孩一封有點遲疑的信。她計畫和兄弟會男孩結婚,她希望我們之間的事不傷感情。十四日,情人節那天,我決定該是另謀發展的時候了。接下來出現了娜娜,這你們已經曉得了。
我無法填補這個漏洞。我指的不是那女孩說再見時留下的洞,我不願讓她覺得有深重的罪惡感──而是一個一直存在的洞,這個黑暗、困惑的漩渦,在我心裡轉動不休。娜娜填補了這個洞。她讓我採取行動。
她讓我變得高貴。(待續)
從奧古斯塔的高速公路入口彎道到加德納鎮有八哩路,我們在短短幾分鐘內就下手了。我木然地將那把銼刀握在身邊,望著窗外在夜色中眨眼的綠色反光標誌──十四號出口靠右行。「可惜我只到這裡。」布蘭奇說。
「沒關係。」娜娜溫和地說。我能感覺到她的怒意滋長,像電鑽般鑽進我的腦殼。「只要在彎道上讓我們下車就行了。」
他開上出口,謹慎的在彎道上將時速減為三十哩。彎道上有盞頂燈,我看得見左邊加德納鎮的燈火,背景襯著濃濃的烏雲。右邊,什麼也沒有,只有一片漆黑。在出入口的公路上兩方都無來車。
我下了車。娜娜滑出座位,給諾曼‧布蘭奇最後一個甜美的笑容。我並不擔心。她是在指揮這齣戲。
布蘭奇露出令人冒火的蠢笑,因為擺脫了我們而感到放鬆。「呃,再──」
「哦,我的皮包!我的皮包在車裡!」
「我去拿。」我告訴她。我彎身探進車裡。布蘭奇看見我拿在手上的東西,臉上的蠢笑僵住了。坡上有車燈照過來,但現在要停已經太遲了,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止我。我左手拿起娜娜的錢包,右手用那把指甲銼刀刺向布蘭奇的喉嚨。他大叫一聲。
完事之後,我抬起頭來看見娜娜站在雪佛蘭和貨車交錯的燈光中,臉上交織著愛、恨、勝利與喜悅的表情。她對我伸開雙臂,我立刻投入她的懷抱。我們接吻。她的嘴唇冰冷,舌頭卻又暖又熱。我兩手插入她的髮間,風在我們四周呼嘯。
「現在趁別人來之前,」她說:「快點處理好。」
我處理了。我坐進貨車,坐上駕駛座,將它轉向高速公路的入口。她坐在我身邊,身體沒有接觸,但靠得很近。當她移動時,她的頭髮有時會掠過我的脖子,那就像觸電一樣。我們往南方行駛。
這輛車沒裝雪鍊,因此在我們到達路易斯敦的出口前,我已經開始在新下的雪上打滑。才二十二哩路,我們卻開了四十五分鐘。
路上沒幾輛車。風讓人保持清醒,雪下得更大了。在哈洛鎮另一頭,我們經過一輛滑到路旁的大型別克車。就在這時,從我們駛出加德納鎮的出口後,娜娜第一次開口說話。
「後面沒有警察在追你。」
「他是不是──?」
「不是。他的警示燈熄了。」
但是那讓我緊張,也許是因為樣才出了事。一三六號公路在哈洛鎮這邊的河岸有個九十度的急轉彎,然後才筆直過橋進入城堡岩。我轉過第一個彎,但城堡岩那邊的路面上卻結了冰。
「該死──」
貨車後頭飛了起來,在我來得及掌穩方向盤之前,它已經撞上了一根巨大的鋼製橋柱。我們一路滑行,接下來我看到的就是從後方投射過來的警車車頭燈。他踩著煞車──我可以從飄雪中的紅色反光看出來──但他照樣在冰上打滑並直撞向我們。接著一切都停止了。現在那個警察打開車頂的警用燈,照在哈洛鎮與城堡岩間的鐵橋與貨車的車頂上,製造出轉個不停的藍色陰影。警察打開車門走出來時,車內的頂燈亮了。
如果他沒跟在我們後面,我們的貨車就不會出事。這想法不斷在我腦際浮現,有如唱針卡在有點瑕疵的唱片凹痕裡。我在黑暗中咧嘴而笑,並彎身在貨車地板上摸索可以敲擊他的工具。
貨車上有個打開的工具箱。我摸出一把螺絲扳手,放在娜娜和我之間。警祭彎身探進車窗,一張臉在警車的閃光燈映照下,像魔鬼般不停的變幻。
「這種天氣,你開得快了點吧,小夥子?」
「你跟得也太近了點吧?」我問道:「在這種狀況下?」
他大概臉紅了,只是在閃動的燈光中實在看不清楚。「你在要嘴皮嗎,小子?「讓我看看你的駕照和行照。」
我掏出皮夾,把駕照拿給他。他用嚴厲的眼光瞪著想嚇我。當他看到嚇不倒我時,他把眼光轉向娜娜。他的眼神讓我很想當場把他的眼珠挖掉。「妳叫什麼名字?」
「雪柔‧葛雷,警官。」
他走到卡車後面去看車牌,並記下車牌號碼。他走回來時,我的身子仍舊探在車外,因而上半身在他的車頭燈照射下一覽無遺。「我要……你身上沾了什麼呀,小子?」
我不用低頭看也知道我全身上下沾了什麼。我以前總會想,當時我那樣把身子探出車外,實在是太不小心,但在我寫下這件事時,卻改變了想法。我想我完全不是不小心。我想,我是故意要他看見的。我的手上緊握著那根螺絲扳手。
「你說什麼?」
他上前兩步。「你受傷了──像是割傷了。最好──」
我對他揮出扳手。剛才撞車時,他的帽子掉了,因此他頭上什麼都沒有。我對準他額頭上方揮出致命一擊。我永遠忘不了那聲悶響,就像一磅牛油掉在硬木地板上一樣。娜娜說:「快點!」
我用雙手抱起他,走到橋邊。我看不見下游的瀑布,而上游的鐵路支架只是一團很像絞刑台的影子。那晚風聲蕭蕭,雪不斷打在我臉上。有一會兒,我像抱著新生嬰兒一樣把那警察抱在胸前,接下來,我想起了他的真實面貌,於是將他扔下橋,讓他落入黑暗中。(待續)
我們走回貨車,先後上了車,可是車子卻不肯發動。我拚命轉動鑰匙,直到一股汽油味傳來,才不得不停止。
「走吧。」我說。
我們走向警車。前座上散放著罰單存根、文件、和兩塊寫字板。儀表板下的短波對講機喀嚓作響,接著便吐出話來。
「四號,回答。四號,你聽見了嗎?」我伸手把它關掉。車子雖然有撞痕,但起他部分完好無傷。由於車子裝有雪鍊,因此駛過結冰的橋面時一路順暢。
我們進入城堡岩。我們在西南彎道上看到一個停車標誌,舞會的回憶使我莫名興奮。我開始發抖。她望著我,黑眼中透著一抹笑意。「現在?」
我無法回答,因為我抖得太厲害了,她代替我緩緩點頭。我把車開向七號公路的一條支路。我熄掉車頭燈,一片片雪花開始無聲地在擋風玻璃上聚集。
「你愛嗎?」她低柔的問。
我不斷發出某種聲音。我想那大概就像有隻兔子落入陷阱時會發出的聲音。那是一次銷魂的體驗。
我們駛回主要道路。我感覺得出她的興奮,高昂、熱烈、燃燒。我停車用手臂清掉擋風玻璃上的雪,然後我們又上了路。
我們駛過城堡岩西區。剷雪車還沒開到這裡,但有輛車已經在我們之前駛過,車胎印清晰地劃過無瑕但飄動不止的雪地。
只剩一哩,接下來不到一哩。她的渴望和迫切感染了我,讓我也迫不及待。我們繞過一個彎道,看見那輛電力公司的卡車,鮮明的橘紅色車身和血色的警告燈,它擋在路上。
你無法想像她的憤怒──應該說是,我們的憤怒。因為,在發生過那一切之後,我們已合而為一。那種你無法想像的嚴重妄想症引發的感覺,讓你深信現在每一隻手都在對抗我們。
他們有兩個人,一個在前方的黑暗中是彎腰的黑影,另一個握著手電筒。他朝我們走來,手電筒的光上下飄動,有如一隻可怕的眼睛。他引發的不只是憎恨,還有恐懼──怕他會在最後一刻將我們的一切奪走。
他在大吼,因此我把頭探出窗外。「你們不能從這裡走!走鮑溫路回去!這裡有段電線脫落了!你們不能──」
我下了車,舉起獵槍給了他兩槍。他往後退,倒向橘紅色卡車上,我踉蹌地後退靠向警車。他一吋吋往下溜,難以置信地瞪著我,隨即倒在雪地上。
「還有子彈嗎?」我問娜娜。
「有。」她把彈匣遞給我。我打開獵槍,把空彈殼拉出後裝進新的。
那人的夥伴已挺起腰,正無法置信地看著。他對我吼著,但聲音被風蓋過了。聽起來像是在問問題,但那並不重要。我要殺了他。我走向他,而他只是楞在原地瞪著我。甚至當我舉起獵槍時,他還是沒動。我想他根本猜不透發生了什麼事。我想他以為這一切只是一場夢。
我的第一槍打低了,使得地上的雪向四處飛濺,落在他身上。這時他發出一聲駭人的尖叫,開始逃跑,跳過掉在地上的電線。我又開了一槍,還是沒打中。接著他已跑進黑夜中,我只好算了。反正他已經不擋路了。我走回警車。
「我想我們得用走的。」我說。
我們走過倒在雪地上的屍體,跨過在地上閃著火花的電線,又走上公路,跟著那個逃跑的人留下的足跡。有些地方積雪高過她的膝蓋,可是她總是領頭走在我前面。我們兩人都在喘息。
我們過了一個山丘,滑下坡地。坡地另一邊有間傾斜的小草屋,荒棄無人,窗上也沒有玻璃。她停下腳步伸手抓住我的手臂。
「那裡。」她說著,伸手指向另一邊。她抓得非常用力,使我就算隔著外套也覺得痛。她的臉上燃燒著美豔而勝利的光彩。「那裡!那裡!」
那是一片墓地。(待續)
我們滑下坡,蹣跚地走向墓園,爬過一道覆雪的石牆。我也到過這裡,當然。我的親生母親就是城堡岩人,她和我父親雖然從未在這鎮上住過,但他們的墓地都在這裡。這是我外公外婆給我母親的禮物,他們都在城堡岩成長、去世。即使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和他們很接近,覺得十分安慰。
我腳一滑,在雪地上摔了一跤,扭傷了腳踝。我爬起來繼續走,用獵槍當枴杖。雪不停地下,堆在墓碑和十字架上,掩埋了一切,只有退伍軍人紀念日時才掛上國旗的旗竿還露出一截。這裡的寂靜有種讓人無法喘息的壓迫感。這是我第一次感到害怕。
她帶著我走向墓園後方建在小山丘上的一棟石屋──藏骸所。雪白的墳墓。她有鑰匙。我知道她會有鑰匙,她也真的有。
她把雪從門邊吹開,找到鎖孔。轉動制栓的嘎嘎聲在黑暗中回響。她往門上一靠,門就向內打開。迎面撲來的氣息涼如秋季,涼如霍利的冷藏地窖。我只能看到前方一點去路。石板地上有乾枯的葉子。她走進去後停下腳步,回頭看我。
「不。」我說。
「你愛嗎?」她問我,然後大笑。
我站在黑暗中,覺得所有事都交織在一起──過去,現在,未來。我想跑,邊叫邊跑,飛快逃跑以收回我所做的一切。
娜娜站在那裡看著我,世上最美的女孩,唯一一樣曾經屬於我的東西。她用手在身上比了個姿勢。我不告訴你那是什麼姿勢。你看了就知道。
我進去了。她關上門。
藏骸所裡黑漆漆的,但我的視線卻很清楚。一盞緩緩飄動的綠火照亮了這地方。那火飄過牆面,潛過鋪著落葉的地板。房間中央放了一副空的棺架,上面撒滿枯萎的玫瑰花辦,有如古代新娘的獻禮。她向我招手,指指後方的小門。一扇不明顯的小門。我開始感到驚恐。我想當時我意會過來了。她利用我、嘲笑我,現在她要毀了我。
但我無法停止,我走向那扇門,因為我必須這麼做。在一種難言的心情下,我感到可怖而瘋狂的喜悅和勝利。我的手發著抖伸向那扇,門上全是綠色的火焰。
我打開門,看見放在門裡的東西。
那是個女孩,我的女孩。她的眼睛空洞地瞪著那間十月的藏骸所,瞪向我的眼睛。她的氣味有如偷來的吻。她全身赤裸,白皙的喉嚨到大腿分岔處都被割開,整個身體變成了一個子宮,而且裡面似乎住了某種東西。老鼠。我看不見牠們,但我能聽見牠們在她身體內搔抓的聲音。那一剎那,我知道她乾癟的嘴會張開,她會問我愛嗎?我向後退,全身麻木,腦子飄在一朵烏雲上。
我轉向娜娜。她在笑,對我張開雙臂。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最後的試驗。最後最後的。我已經通過,我自由了!
我轉向門口,當然那裡什麼都沒有,只有空的棺架和地板上的枯葉。
我奔向娜娜,奔向我的生命。
她雙手攀住我的頸項,我將她拉近。就在這時她開始變化,如軟蠟般起伏、流動。那雙黑色的大眼變得小而凸出,黑髮變得粗糙,淡成棕色。鼻子變短了,鼻孔擴大。她的身體癱軟無力,向我靠來。
我被一隻老鼠抱住。
「你愛嗎?」那老鼠吱吱問道:「你愛嗎?你愛嗎?」
她那無唇的嘴向上仰,搜尋我的唇。我沒有叫,我已沒有聲音可叫,我懷疑這輩子自己是否還能尖叫。
我寫得夠多了,這枝筆的筆尖變得軟糊糊的。但我已經寫完了。我對許多事情的看法改變了,和原先完全不同了。
你知不知道,有一陣子他們幾乎讓我相信,那些可怕的事全是我一個人做的?那些卡車司機,他們說我只有一個人。他們找到我時,我是只有一個人。在墓園裡,刻有我父親、母親和哥哥德瑞的那些墓碑旁,差點沒凍死。但那只表示她離開了,你們要明白,任何傻子都明白。不過我很高興她離開了,我真的很高興。只是你一定要了解,在那一路上的每一個步驟,她都和我在一起。
現在我要自殺了,這樣會好得多。我已經對愧疚、痛苦和噩夢感到厭倦,而且我不喜歡牆壁裡的那些聲音,那裡面可能藏有任何人或任何聲音。
我沒瘋!我知道,我相信你也知道。他們說,如果一個人說自己沒瘋,那就表示他瘋了。但我已經超越這些小把戲。她曾和我在一起,她是真實的。我愛她。真愛永遠不死。我在寫給貝西的那些信上,末尾總會附上這麼一句。那些被我撕掉的信。
可是我真正愛過的,只有娜娜一個。
這裡真熱得要命,而且我不喜歡牆壁裡的聲音。
你愛嗎?
是的,我愛。
而真愛永遠不死。(2009/07/14出版)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絕筆:史蒂芬.金到目前為止最好的小說!完美集大成!進化版的《終極追殺令》!
後來
燃燒的凝視【新譯本】:電影《燃火的女孩》經典原著小說
如果它流血:故事之王史蒂芬.金寫給疫情時代的完美傑作
機構
CIA洗腦計畫:解密美國史上最暗黑的心智操控實驗
大競走
四季:故事之王史蒂芬.金寫作生涯最經典的代表作《四季奇譚》全新譯本
飄浮
安眠醫生【全景飯店回歸版】
牠【電影書衣驚駭版】
我們還沒玩完
死亡禁地
復活
有時候,他們會回來:史蒂芬‧金最膾炙人口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
鬼店 (電影原著小說)
魔符(上下冊不分售)
史蒂芬.金的故事販賣機【電影書腰版】:收錄《史蒂芬金之猴子》電影原著小說!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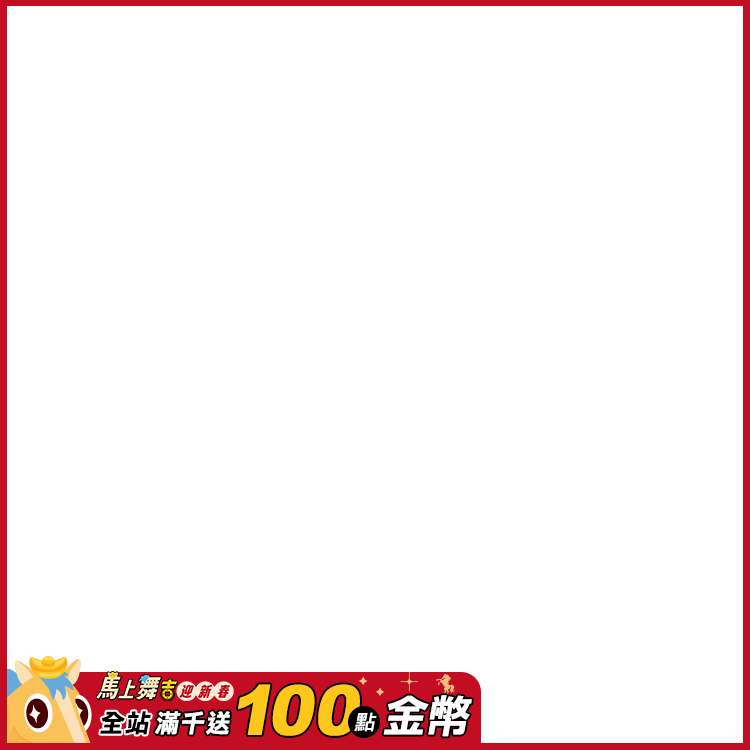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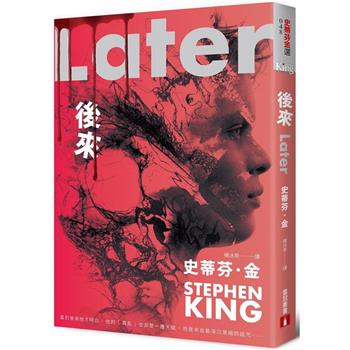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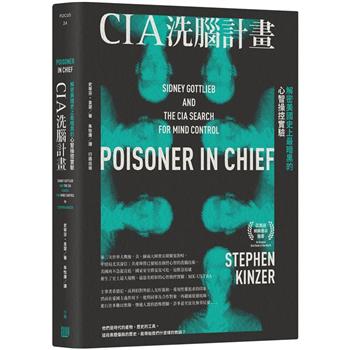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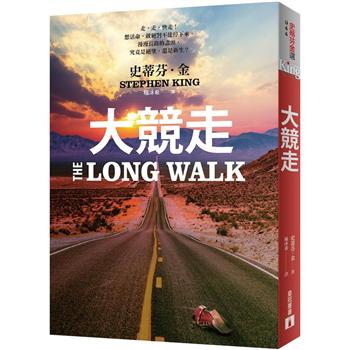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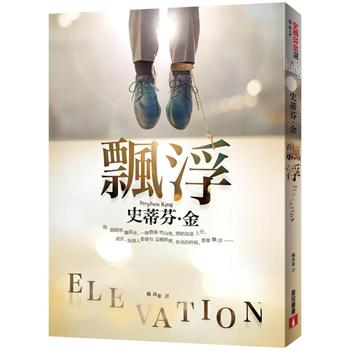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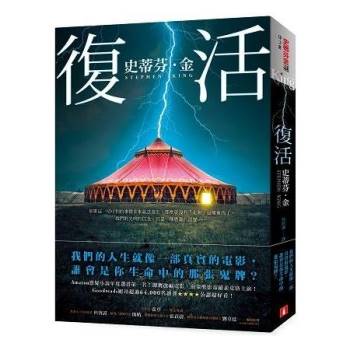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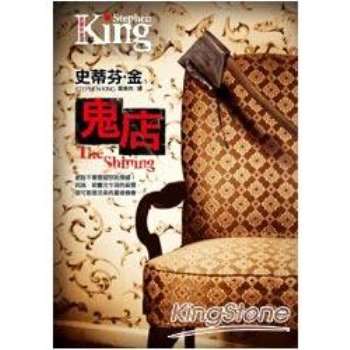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