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中祕族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入圍美國筆會2014年度最佳小說處女作
一九五○年,叫諾頓‧佩利納的年輕醫師參加了一趟人類學研究之旅,前往密克羅尼西亞地區的某座島嶼,任務是尋找一個傳說中的神祕部落。科學家們達成了任務,不但找到神祕部落,還發現一群被他們稱為「夢遊者」的森林居民,這些島民的壽命很長,但心智退化的問題愈來愈嚴重。佩利納懷疑那些人會如此長壽,是因為吃了一種稀有的海龜;他殺了一隻海龜,把部分龜肉走私帶回美國。他設法證明自己的論點,成為舉世聞名的科學家,還獲頒諾貝爾獎,但他很快就發現,海龜肉雖有神奇效用,也會讓人付出可怕的代價。情勢很快就失控了,他內心的惡魔開始占上風,毀了他的人生。
《林中祕族》講的是諾頓‧佩利納的一生,從充滿孤獨與失落的童年,到他轟動全世界的發現,以及之後的墮落。這本「回憶錄」寫於獄中,由他的研究助理編輯、作註。日裔美籍小說家柳原漢雅出身夏威夷,這部處女作摧毀神話、現實、超現實之間的界線,向上一世紀的兩位大師致敬──納博科夫與康拉德。
名人推薦
目錄
序/導讀
知名科學家面臨性侵指控
馬里蘭州貝塞斯達鎮報導──知名免疫學家、退休前曾於馬里蘭州貝塞斯達鎮國家衛生研究院擔任免疫學與病毒學中心主任的亞伯拉罕.諾頓.佩利納醫生,昨天被控性侵遭逮捕。
七十一歲的佩利納醫生面臨的指控,包括三項強暴罪、三項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兩項性侵罪及兩項危及未成年人的罪行。提出指控的人是佩利納醫生的養子們。
「那些指控都是假的。」佩利納的律師道格拉斯.辛德利昨天聲明:「佩利納醫生在科學界的聲譽卓著,備受尊崇,他非常希望盡快釐清現況,讓他回歸工作與家庭。」佩利納醫生曾於一九七四年獲頒諾貝爾醫學獎,理由是他發現一種延緩老化的病症,也就是「瑟莉妮症候群」。密克羅尼西亞群島有個名為烏伊伏的島國,在該國三島之一的伊伏伊伏島上,他發現歐帕伊伏艾克族的族人罹患此一病症,儘管他們的心智退化了,身體仍維持在很年輕的狀態。他們之所以不老,是因為吃了歐帕伊伏艾克海龜,於是佩利納醫生用海龜名來為該族命名。他發現這種海龜肉能夠抑制端粒──端粒這種天然酵素有分解端粒的功能,進而限制每個細胞分化的次數。受到瑟莉妮症候群(瑟莉妮是希臘神話裡永遠不死與青春永駐的月之女神)影響的病人,能活好幾個世紀。佩利納醫生初次前往烏伊伏國是在一九五○年,年輕的他隨同知名人類學家保羅.塔倫特,在當地各島做了多年的田野研究。此外,他也在那裡領養了四十三名小孩,其中多人是孤兒,或是歐帕伊伏艾克族窮困族人的兒女。其中一部分小孩目前正由佩利納照顧。
「諾頓是模範父親,也是天才。」長期於佩利納的實驗室裡擔任研究員,同時是其摯友的隆納德.庫波德拉醫生說:「我深信這些荒謬的指控一定會被撤銷。」
(美聯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九日)
知名科學家暨諾貝爾獎得主被判刑入獄
馬里蘭州貝塞斯達鎮報導──亞伯拉罕.諾頓.佩利納醫生於今天被判二十四個月徒刑,執行地點為費德列克懲教機構。
佩利納醫生曾於一九七四年獲頒諾貝爾醫學獎,理由是他證明一種原產於密克羅尼西亞群島烏伊伏國、如今滅絕的海龜肉,能抑制端粒,限制每個人類細胞的分裂次數。他發現,這種被稱為瑟莉妮症候群的病症,可移轉到包括人類在內的多種哺乳類動物身上。
獲准自由進出那些遙遠神祕島嶼的西方人寥寥無幾,佩利納是其中一位,從一九六八年開始,他陸續在該國收養了四十三名小孩,全都安置在他位於貝塞斯達鎮的住家。兩年前,佩利納被控強暴其中一個孩子,威脅其安危;指控他的人是他收養的某個孩子。
「這真是一樁悲劇。」路易斯.雅特舒爾醫生在佩利納醫生服務多年的國家衛生研究院擔任院長,他表示:「諾頓是個思想家與天才,我衷心希望他能夠獲得他所需要的治療與幫助。」
佩利納與他的律師目前都處於失聯狀態,無法評論此事。
(路透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
編者序
我是隆納德.庫波德拉,但那只是我在學術期刊上的名字,大家都叫我隆恩。沒錯,如果你曾在報章雜誌上看到隆納德.庫波德拉醫生這個名字,那肯定就是我。但新聞報導的內容並非全都屬實──當然真實的成分很少。
就我的例子而言,最重要的那些報導都是真的,而且我為那些事感到自豪。例如,我與諾頓有所關聯(別忘了,若是在僅僅十八個月前,我根本不用提這件事),事實上我們相識已久,從一九七○年起,我就在他位於馬里蘭州貝塞斯達鎮、隸屬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實驗室工作了。當時,諾頓還沒拿到諾貝爾獎,但是他的研究早已在醫界掀起一陣革命,自此改變學者對於病毒學、免疫學,還有醫學人類學的看法。讓我自豪的另一點是,與他成為同事之後,我們也變成好朋友;事實上,我覺得我倆建立了一種最有意義的關係。不過最重要的是,歷經了過去兩年的風風雨雨,我很自豪我們兩人仍是朋友。當然,我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有機會就能與諾頓講話或溝通,無疑地,他也不行。他不在身邊,讓我有一種奇怪而寂寞的感覺。大概十六個月前,我才遷居此地(也就是諾頓被判刑的一個月後),但在那之前,我未曾想過在自然的狀況下,我們居然會分開超過兩天以上。也許連一天都沒有想過。(當然,所謂自然的狀況是排除某些特例,像是偶爾和當時還是我妻子的前妻去度假,或者我們各自去參加葬禮、婚禮等活動。即便不在一起,我還是設法每天與他保持聯絡,不管是透過電話或者傳真。)重點是,與諾頓談話、工作或只是在一起,已經變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有人每天都得看電視、看報紙一樣:儘管是瑣事,卻不會忘記去做,藉此確保生活按照常軌運作。但是,當這種節奏突然被打斷,給人的感覺比不安更糟糕,簡直是不知所措。過去一年半,我就有這種感覺。早上醒來後,我跟往常一樣把白天的時間過完,但到了晚上總是晚睡,在公寓裡閒晃,瞪著夜空發呆,心想自己是否遺漏了什麼事。茫然的我把完成的十幾件平日瑣事核對一番,心裡想著信件是否打開看過而且也回了?截稿期到的文章交了沒?門鎖了嗎?直到最後,我才帶著後悔的心情上床睡覺。每逢快要睡著,我才想起我這輩子的所有模式都改變了,接著感到一陣短暫的憂鬱。你也許會覺得此刻我已經能接受諾頓驟變的人生,而我的人生也隨之改變,但我心裡的某個角落就是抗拒著;畢竟過去將近三十年來,他已然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覺得寂寞,諾頓的生活一定遠比我寂寞。當我想到他必須待在那種地方,我真是憤怒不已:諾頓不是年輕人了,身體也欠安,用囚禁的方式懲罰他既不適當也不合理。
我知道只有少數人跟我的想法相同。我常常試著向朋友、同事與記者(還有法官、陪審團與律師)解釋,諾頓是個有同情心、聰明而且了不起的人,次數多到我自己都忘了。事實上,過去十六個月來,我屢屢想起諾頓的許多朋友曾宣稱愛他也尊敬他,卻選擇背叛,並且這麼快就忘記他、遺棄他。有些朋友,諾頓認識且共事了幾十年,在他被起訴時就立刻消失。更糟糕的是,那些在他被判有罪後便離開他的人。當時我才發現一般人有多麼不忠不義、滿嘴謊言。
不過,我離題了。牢獄生活讓諾頓感到最難過的一件事,應該是他必須勉強自己去適應單調的生活。我必須承認我有點訝異,他入獄不到一個月就開始抱怨生活無聊到令人難過。過去,諾頓跟許多累過頭的能人志士一樣,滿心夢想著在一個溫暖的地方住上一個月或一年,完全不用投入任何事情。不用演講,不用編輯或撰寫文章,不用教學,不用顧小孩,不用做研究;只有用不完的空閒時間,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過去,諾頓總是說時間就像一片大海,一面無邊無際的空白鏡子,而這個他稱為「大海時間」的美夢已經變成一則笑話,短短幾個字,代表著他目前沒時間做、但有朝一日希望投入的事。所以,他總是信誓旦旦地說,如果有大海時間,他會用來種植熱帶蕨類植物。如果有大海時間,他會讀一些傳記。如果有大海時間,他會寫自己的回憶錄。不曾有人認為諾頓真會擁有所謂的大海時間,他自己尤其如此;但是如今他有的是時間,只是沒有溫暖的地方,沒有那種努力一輩子過後應得的安逸感,讓人覺得快樂而慵懶。不幸的是,諾頓有可能天生就是勞碌命;這陣子以來,他深受折磨(雖然如此,我得承認他會這麼想,很大一部分必須歸因於他是在不幸的情況下獲得這種悠閒時光)。在最近的一封信裡面,他寫道:
這裡能做的事不多,而且在某個時間點過後,能夠思考的事情甚至更少。我不曾想過自己會落到這一步田地,筋疲力盡,而且被放空了,不是放血,而是腦袋一片空洞。窮極無聊──事實上,過去我總以為如果有一段長時間的閒暇,我一定會好好珍惜,很容易把時間排滿。但此刻我已經瞭解,時間不是由一段段長時間的空檔組成:我們常說時間管理,其實剛好相反──我們只能用一件件忙碌的小事來填滿生活,這是我們唯一能做的。
這似乎是充滿智慧的洞見。
儘管諾頓明顯看出自己的處境嚴峻,還是有些魯莽的人表示他應該感激自己受
試閱
摘自「第一部 溪流」
I.
一九二四年,我生於印第安那州,故鄉林登鎮是那種毫不起眼的中西部鄉間小鎮,它緩緩地持續成長,距我出生之前大約二十年,人口才開始把自己「複製出來」。我的意思是,印象中小鎮唯一的特色就是它沒有值得一提的特色。鎮上有筒倉,有紅色穀倉(大多數居民都是農民),還有雜貨店與教堂,也有神職人員、醫生、老師、男人女人與小孩:它具有美國典型社會的雛形,但是欠缺任何花邊與裝飾,也沒有附屬品。鎮上有幾個酒鬼、一個瘋子,還有貓狗,也會與西邊幾哩處的蝗蟲鎮一起舉辦鄉間市集(如今蝗蟲鎮已經併入鄰近城鎮,不復存在)。鎮上一共有一千八百位居民,每個人出生後都走上同樣的路:上學、做家事、當農夫、與其他鎮民結婚,共組自己的家庭。在街上碰到別人時,大家會彼此點頭打招呼,男人則是稍稍將帽緣往下拉。隨著一年四季的更替,當地人種植菸草與玉米,然後收割。這就是林登鎮。
我們家一共有四個人:爸媽、歐文和我。我們住在一個一百英畝大的農場上,破破爛爛的住家唯一的特色,就是中央有一道曾經非常華麗的寬大階梯,但因為一代又一代的白蟻蛀蝕,早已只剩殘骸。
我們家後面大概一哩遠的地方有一條蜿蜒小溪,又小又慢,行徑詭譎多變,讓人無法幫它取一個比較恰當的名字。每年三、四月融雪之後,它就會水位暴漲,晉升成一條河,融雪與春雨讓水的流量又大又急。那幾個月,小溪的面貌丕變,變得如此無情而果決,河岸邊許多如繁星點點的血根草花與野生百里香會被連根捲入河裡,到了下游一處不知誰蓋起來的老舊水堤才被攔下,卡在灌木叢裡。溪流中一年到頭都有小魚,牠們奮力往上游游過去,淪為波臣。每年春季,它不再是一條無聲的小溪:洶湧的河水轟隆隆作響,劇力萬鈞,通常連平靜無比的平凡支流也會在那幾個月變得可怕難測,爸媽都叫我們要遠離它。
但是每年到了酷熱的夏天,那條小溪(溪流源頭不在我家土地上,而在東邊大約五哩處的穆勒家)會再度乾枯,變成涓涓細流,膽怯地從我家農場慢慢流過。小溪上方的空中飛著許多蚊蚋蜻蜓,嗡嗡作響,溪底污泥裡則攀附著許多水蛭。過去,我們會去溪釣與游泳,然後沿著低緩坡面爬回矮丘上的住家,在手臂腿部上被蚊子叮咬的地方猛抓,抓得皮膚變粗滲血。
我父親不曾往下走到丘邊的小溪,但母親喜歡坐在草地上,看著溪水潺潺流過她的腳踝。小時候,我們會對她大叫:「看我們這邊!」她總是抬起頭,一臉作夢的表情,揮揮手──不過我們總是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在對我們,還是對附近的一棵橡樹苗揮手。(母親的視力沒問題,只不過舉止常常看起來像個盲人;她平日四處晃蕩的樣子彷彿在夢遊。)等到我跟歐文大概七、八歲時(總之,就是年紀還小,對她還未幻滅的時候),我們常常作弄可憐的她。我們會對她揮手,坐在河岸上的她雙臂抱住膝蓋下方,等到她也對我們揮手(她揮動的不只是手掌,而是整隻手臂,像一大片在水底擺動的水草),我們就會轉身背對她,大聲交談,假裝沒看見她。之後,到了晚餐時間,她會問起我們在溪邊的行徑,我們兩個會裝出一副震驚困惑的模樣。在溪邊?但是我們沒有去溪邊啊!我們一整天都在農場上玩。「但我看見你們在那裡。」她總是這麼說。我們倆會口徑一致地回答說沒有,還一起搖搖頭。那一定是另外兩個男孩,兩個看起來就像我們倆的男孩。
「但是——」她欲言又止,一臉困惑,然後又恢復正常表情。「一定是別人。」她會用猶豫的口氣說,並且低頭看餐盤。
每個月,這種對話會出現幾次。這對我們來講是一種遊戲,但也令我們不安。母親也跟我們一起玩遊戲嗎?但是她臉上那種擔憂害怕的神情不太對勁,就像當年我們說的那樣:她好像真的無法相信自己親眼看到的景象,還有自己的記憶,那表情實在太過真實而自然了。我們選擇相信她是裝出來的──否則她不就是瘋子或笨蛋了嗎?這實在讓人感到害怕而不願去深究。稍後,回到房間裡,歐文和我會模仿她(「但──但──但是那明明就是你們!」),並且笑個不停,但笑完之後,我們會靜靜地躺在床上,想到那遊戲讓我們意識到的一件事,又憂慮了起來。儘管年紀幼小,我們(透過讀書,透過同儕)都知道母親的職責是責罵、指導、教誨孩子,必要時還要訓示,但我們也知道母親無法勝任那些事。我們心想,在那種女人的教養之下,長大後我們會變成哪一種人?為什麼她那麼無能?我們對待她的方式就像一般男孩玩弄小動物一樣:每當高興與寬容時就對她好一點,否則就殘酷以待。知道我們有辦法讓她肩膀放鬆下來,讓她的嘴角露出猶豫的微笑,也有辦法讓她低下頭,在不高興或困惑時用手掌快速摩擦腿部,實在令我們欣喜若狂。儘管我們擔憂,卻未曾說出口;我們只會用嘲弄或厭惡的口吻談論她。擔憂之情讓我倆變得更親近,也更大膽及惹人厭。我們心想,我們一定可以把她掩藏起來的大人模樣給逼出來。跟大多數孩童一樣,我們以為每個大人天生就知道怎樣恫嚇別人,展現權威。
她除了腦袋不靈光之外,還有一些小地方顯示她也許是個失敗的母親。她煮菜總是馬馬虎虎(她的水煮青花菜吃起來像橡皮,菜裡藏著許多微小的甲蟲蟲殼,眼睛看不見,但吃起來嘎吱嘎吱,而她的烤雞烤出來時滋滋作響,還帶著血),只會偶爾做家事──父親買了一台吸塵器給她,但被她遺忘在掛大衣的衣櫥裡,直到有一天被我跟歐文拿來解體。她似乎也沒有任何嗜好。我們不曾看她讀書寫字作畫,或者拈花惹草,總之她沒做過任何我們當時認為有價值或有趣的休閒活動。夏天的下午,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她坐在客廳裡,小腿像個小女孩一樣收在大腿下面,臉上掛著蠢蠢的微笑,用茫然的雙眼死盯著被陽光照得清清楚楚的一大片塵埃。
有一次,我看到她在禱告。某天下午放學後,我走進客廳裡,發現她跪在地上,雙掌握在一起,把頭抬起來。她的嘴唇動來動去,但我聽不見她說些什麼。她看起來荒謬無比,像是對著空蕩蕩的戲院演戲的女演員,連我都為她覺得好尷尬。「妳在做什麼?」我問她,她嚇了一跳,抬頭說:「沒什麼。」看起來一副受驚的樣子。但我知道她在做什麼,也知道她說謊。
我還能說什麼呢?只能說她令人費解,四處遊蕩,甚或是個笨女人。但在此我也必須說,她對我而言始終是個謎,能夠有她那種表現的人應該不多。我還記得其他關於她的事,像是她長得很高,面貌優雅,儘管我已經想不起她具體的形貌,但我知道她還挺漂亮的。歐文的辦公室掛了一張老舊模糊的深褐色照片,可以印證這一點。如果她活在這個時代,可能會被當成大美女,因為必須要用超越她那個時代的審美觀才能好好欣賞她──她的臉又長又白,總是一副擔驚受怕的樣子:那是一張兼具知性美、神祕感與深度的臉。現在的人會說她美麗動人。我父親一定也覺得她很美,否則我實在想不出他為什麼會娶她。如果父親會和女性說話,一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不過他不覺得那種女性性感。我想這是因為聰明的女人會讓他想起西碧兒姑姑,她是羅徹斯特鎮的一個女醫生,深受父親景仰。所以,他只能娶漂亮的女人。等到我長成青少年,發現父親只是為了母親的美貌而娶她時,我很失望。到了後來,我才發現父母在許多方面都令我們失望,最好不要對他們有任何期待,以免落空。
不過大致上,我對她可說是一無所知。我甚至不知道她的故鄉到底在哪裡(我想是內布拉斯加州的某地),但我知道她出身窮困,相對來講,父親比較有錢,要求也不高,是父親救了她。奇怪的是,儘管她家很窮,她卻不像幹過粗活,看起來沒做過苦工,或過過苦日子。她給人的印象反而像是父親的掌上明珠,上過禮儀學校後,就直接被送進丈夫懷裡。(在歐文的相片裡,她散發著光芒,因為她早早就悄然離世,再加上那些像夢遊般的緩慢動作,都讓她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充滿光澤、備受呵護寵愛的形象,但我知道實際上並非那麼一回事。)就我所知,她沒受過教育(在念我們的成績單給父親聽的時候,她連「模範」兩個字都不知道怎麼發音,她先蹩腳地念念看,接著歐文或我就忍不住大聲念出來。我們一方面沾沾自喜,一方面感到不耐,也認為她丟了我們的臉),死時年紀尚輕。但是她在各方面的表現也都很年輕。記憶中,她做的事與外表總是那麼孩子氣。無論什麼場合,她那鬈鬈的長髮總是放下來,在她背上交纏成螺旋狀。即便當時我還小,她的髮型連我都看不慣;我覺得髮型再次證明,她仍徹底維持女孩的模樣,儘管非常不恰當──不管是她的長髮、她那冷淡而茫然的微笑,還有任誰跟她講話都會亂飄的眼神,這些特質都讓她無法成為受人敬重的母親。
如今我把母親畢生的一些細節寫出來,讓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對她的瞭解居然那麼少,而且對她也不感好奇。我以為每個孩子都渴望瞭解爸媽,但我不曾認為她是有趣而值得多去瞭解的人。(或者我該倒過來想,就是因為無趣才應該多去瞭解她?)但是話說回來,我向來不認為我們該美化過去:這對我有何好處?沒想到,後來歐文卻變得對母親很感興趣,大學時期甚至想要研究她的家族史,並為她完成一篇非正式傳記。不過,才著手幾個月,他就放棄了,每當有人問起那項計畫,他總是充滿戒心,所以我假設他順利找到母親娘家那邊的親戚,發現他們全是鄉巴佬,厭惡之餘,便放棄了整個計畫(他從很年輕時就培養出一種根深柢固的菁英主義態度,因此這的確是他的作風)。令我不解的是,就某方面來講,母親對他總是那麼重要。話說回來,歐文是個詩人,我想他應該是認為那些細節無論再怎麼平庸或終究令人失望,在未來都是可用的創作題材。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相關商品
前往天堂樂園【上、下冊】
渺小一生(上、下冊)
林中祕族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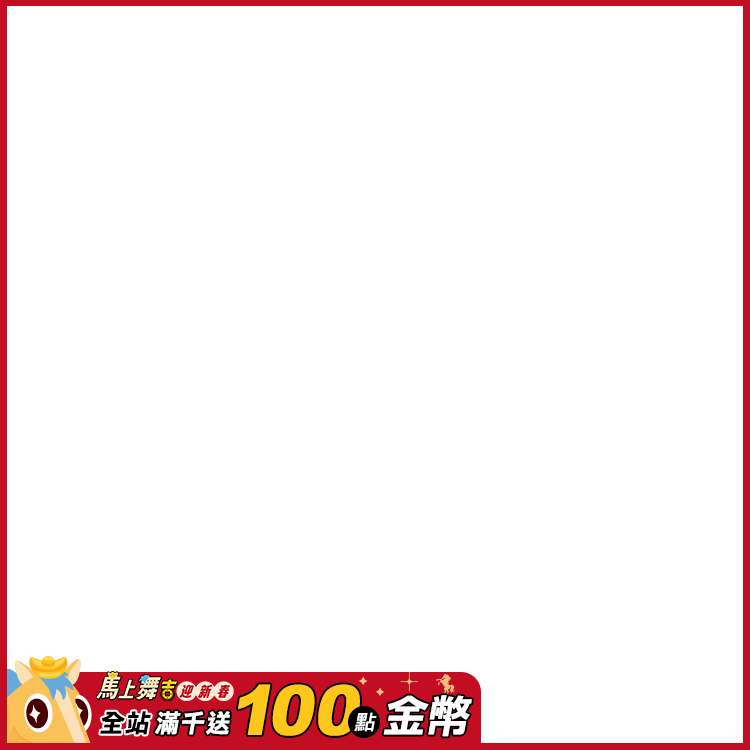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