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連環殺手正在剿滅連環殺手!
當FBI的「怪胎」遇上專殺連環殺人犯的「上帝」
誰才是真正的怪物?
「如果喜歡《夢魘殺魔》、《重返犯罪現場》,你一定會喜歡這部!」
曲辰(大眾文學評論家)、林運鴻(文字工作者)、提子墨(台灣、英國與加拿大犯罪作家協會會員)、龍貓大王(影評)──驚聲讚嘆
德州阿許藍,某處破舊的平房裡,一具被燒焦的屍體橫陳地板。
指紋鑑定結果震驚眾人——死者竟是七年前已被判定死亡的殺人魔羅斯.提農。他死狀悽慘──腹部被人剖開,全身血液幾乎流光,胸口還被刻上「5–0」數字。
隔天,新墨西哥州又出現第二具屍體。死者貝瑞.費雪是九○年代犯下多起謀殺案,才剛出獄的凶手。其器官被完整切割、真空包裝、貼上標籤,整齊排列在冰箱裡。
再接下來,一名正在接受審判、罪證確鑿的連環殺手直接在洛杉磯的聯邦調查局安全屋遇害。
短短數小時內,連續幾名罪大惡極的殺手被屠殺。
PAR,「模式辨識小組」。他們是FBI的祕密武器,也是局內的笑柄:數學怪咖、神射手、老派探員、新加入的菜鳥,再加上一個擁有天才頭腦、卻無法理解人心的男人——嘉德納.坎登。
他們被稱為「怪胎小組」,冷靜、聰明、難以親近,但當案件進入瘋狂與無解的境地,FBI最後的希望,總是他們。
這一次,他們面對的,不是普通的連環殺手,而是一名專門獵殺其他連環殺手的「上帝」。
這是一場理性與瘋狂的對決。加德納與PAR小組努力破案,卻一步步走進殺手設下的模式之中——這次,獵物是壞人,也是他們自己。
如果你喜歡《心理追兇》的心理張力,《七宗罪》的連環殺手遊戲,或《無間警探》的黑暗職場對峙,那麼《懸案對策室》將令你屏息以待!
當FBI的「怪胎」遇上專殺連環殺人犯的「上帝」
誰才是真正的怪物?
「如果喜歡《夢魘殺魔》、《重返犯罪現場》,你一定會喜歡這部!」
曲辰(大眾文學評論家)、林運鴻(文字工作者)、提子墨(台灣、英國與加拿大犯罪作家協會會員)、龍貓大王(影評)──驚聲讚嘆
德州阿許藍,某處破舊的平房裡,一具被燒焦的屍體橫陳地板。
指紋鑑定結果震驚眾人——死者竟是七年前已被判定死亡的殺人魔羅斯.提農。他死狀悽慘──腹部被人剖開,全身血液幾乎流光,胸口還被刻上「5–0」數字。
隔天,新墨西哥州又出現第二具屍體。死者貝瑞.費雪是九○年代犯下多起謀殺案,才剛出獄的凶手。其器官被完整切割、真空包裝、貼上標籤,整齊排列在冰箱裡。
再接下來,一名正在接受審判、罪證確鑿的連環殺手直接在洛杉磯的聯邦調查局安全屋遇害。
短短數小時內,連續幾名罪大惡極的殺手被屠殺。
PAR,「模式辨識小組」。他們是FBI的祕密武器,也是局內的笑柄:數學怪咖、神射手、老派探員、新加入的菜鳥,再加上一個擁有天才頭腦、卻無法理解人心的男人——嘉德納.坎登。
他們被稱為「怪胎小組」,冷靜、聰明、難以親近,但當案件進入瘋狂與無解的境地,FBI最後的希望,總是他們。
這一次,他們面對的,不是普通的連環殺手,而是一名專門獵殺其他連環殺手的「上帝」。
這是一場理性與瘋狂的對決。加德納與PAR小組努力破案,卻一步步走進殺手設下的模式之中——這次,獵物是壞人,也是他們自己。
如果你喜歡《心理追兇》的心理張力,《七宗罪》的連環殺手遊戲,或《無間警探》的黑暗職場對峙,那麼《懸案對策室》將令你屏息以待!
試閱
第一章
我的專長是謎團,亦即,當我沒在鑽研模式或破解密碼,可能會有人說我除了解決謎團之外一無是處。也因為如此,位於傑克森維爾的FBI辦公室就不適合讓我把時間或天賦用在與真人互動上。對此我完全同意。
我站在租來的Toyota Avalon旁邊盯著那棟一層樓的黃色農舍。
「幹這怎麼可能啦。」我身後傳來一個聲音。
我望向我的搭檔。
凱西.帕多身材嬌小,只有五呎三吋,卻彷彿蘊含了一千個太陽的積極能量,而且滿口都是十九歲小孩的行話。
「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我說。
凱西闔上牛皮紙檔案夾。打從我們離開達拉斯機場她就一直在埋頭研究。開到這裡的路上,她不斷在推算我們看到場景的發生機率,也許百萬分之一……或兩百萬分之一。
有個警長走來,目測四十多歲,小麥色頭髮硬往上梳,蓋住禿頭,凸出的喉結從咽喉算起簡直有十四毫米高。
「萊恩.霍林斯。」他伸出一手。
我看著那隻手。我們每平方英吋的手掌上大概繁衍了超過兩百種細菌。「嘉德納.坎登。」我邊說邊跟他握手。我沒有強迫症,只是正好對此略懂。
我指著黃色房子。「你那位受害者,」我說:「是怎麼被發現的?」
「阿許藍天然氣公司有個員工去抄表,」霍林斯說:「從推拉窗看了一眼,見到血,就打給我們。」
凱西往嘴裡扔了一塊口香糖。她二十九歲,黑西裝外套底下穿了件灰色休閒褲。「然後你查了那人的指紋,」她說:「結果看見坎登探員的名字?」
霍林斯點點頭,我們跟著他走過草坪。「等待的時候我google了你們,」他說:「發現你們就是在索諾拉的洞穴找到那個六歲小孩的人。那在我們德州這兒可是大新聞。」
他說的是大概一年一個月前解決的那起案子,主導查案的是凱西和我。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那有多扯,」霍林斯繼續說:「我們搞了個電話聯絡中心,又進行了地毯式搜索。結果你們一來就咻的一下――」
「他父親鞋子上有無水碳酸鹽的痕跡。」我說。
霍林斯皺起臉。
「就是那個從洞穴被救出來的孩子。」凱西說明。
「美國只有九個地方能開採出這種礦物質,」我說:「只有一個位於德州。」
「媽的就是這樣啦,」霍林斯搖搖頭,「我就是這個意思。」
警長有著低沉的嗓音,而我腦中出現一本書:《頸部喉結之研究》,第五十二頁,右側,一張喉結圖,外加與男中音相關的統計數字。
我們來到前門,凱西拿出兩副紫色橡膠手套,啪的往橄欖膚色的手上戴,重新將棕髮緊緊綁成一個馬尾。
「沒有別人進去過?」她邊問邊把另一副手套遞給我。
「只有我和醫療人員。」霍林斯說。
他用堅硬的靴尖推開紗門,而我仔細研究此人。他比我矮兩吋,身材結實,我比較運動員體格,六呎一,外加棕色鬈髮和藍色眼睛。
凱西指著打開的門粲然一笑。「敬老尊賢。」
我對此尋思再三,然後往裡面走了剛剛好五呎後停步。
這裡屬於開放式格局,中央有個中島,結合廚房與客廳;後方則流了滿地的鮮血。
那裡蹲了一個人,寬闊身軀上套了件拋棄式現場防護衣,「你倆一定是聯邦探員,」他說。此人目測約兩百八十磅,站起來時先用雙手撐了膝蓋,然後屁股。「我是泰瑞.沃德。」
「沃德醫生?」凱西用詢問語氣確認眼前這位是醫學檢驗官沒錯。
「正是在下。」
凱西發問時醫生眨了下眼,我立刻望向他放在廚房流理臺上的檢驗工具箱。箱中整齊俐落,看起來與釣魚時用的釣具箱無異,裡面塞了一副彎成某種角度的鉗子,握把部分只有一個圓環。
我又看了看沃德指節周圍皺巴巴的皮膚;他大約六十五至七十歲。
「阿許藍沒有全職醫學檢驗官嗎?」我問。
沃德瞇起眼睛,凱西看向了我。
「子宮頸組織取樣鉗,」我示意他的工具組,「我想您應該是婦產科醫生。」
「觀察入微,」沃德說:「我退休了,來這裡只是興趣使然。」
「非常感謝您的貢獻,」凱西說:「我們向來十分感激當地人員的合作,坎登探員你說是不是?」
我和凱西對上眼神,「是,」然後對沃德說:「一點也沒錯。」
我在距離屍體約一呎處蹲下;他正趴在磁磚地面上。我無須接觸屍體就能看出他在昨天深夜就達到屍僵,現已進入下一階段――肌肉變軟,也就是所謂的二次軟化。
但凱西注意到的是其他東西。
受害者的衣服在身側折成一堆,感覺前面釦子沒扣。凱西掀起衣服邊邊,見到他的左邊袖子滴血的路徑是一路往上而非往下,徹底違反地心引力。
「你把屍體翻過來了嗎?」她問。
「非翻不可,」沃德回答,「我得確認他死了沒。」
男人雙腿底下的血跡形成一個歪扭的橢圓,一路延伸到冰箱底下。我研究著那灘深色液體。標準成人體內總共會有五夸脫的血,地上至少有四夸脫。
「但我有把他放回去,」沃德說:「按照一開始看到的模樣。」
「謝謝您。」凱西回答,棕眼與我對看,揚起嘴脣。
我也回以一笑。沃德把屍體翻過來檢查再讓他躺回去,讓他泡回自己的血裡。
我一手放在受害者肩上,另一手擺在他腰部位置使勁推,直到讓他身體側立起來,彷彿架上的一本書,然後注視著這張我熟悉到不行的臉。
羅斯.提農。
我多年前追捕的人。之所以不再追下去是因為……他幾年前死了。
紗門喀拉一下,霍林斯兩大步走了進來。「所以你認識這傢伙?」他問:「這個死掉的傢伙和你們有一段過去?」
我腦中湧上各種統計數字:羅斯.提農二○一三年三月殺的三個女人、他的刀刺入她們體內的確切深度。
「我們採他指紋時電腦跑出他的名字,」霍林斯繼續說:「這讓我們很疑惑,因為他已經登記死亡了。」
疑惑不是正確的形容詞。
「七年前,」凱西說:「羅斯.提農是佛羅里達三起謀殺的主嫌,接著他家就發生了火災。」
我腦中出現一個畫面:羅斯.提農的妻子貝芙莉從烈焰中被救出,臉上滿是煙灰,金色鬈髮燒焦成黑炭色,但她丈夫似乎沒有這麼幸運。我還記得,那時我是直接在把羅斯.提農的焦屍運到法醫車的擔架上對他進行檢驗的。
「我沒搞懂,」沃德醫生說:「你的嫌犯――在那場大火中?」
我回想放著提農屍體的那張擔架。「人的身體遭受灼燒時會做出一個姿勢,」我對沃德說:「肌肉會收縮,雙手會像要出拳的拳擊手一樣往內收攏,法醫用詞是『拳擊手姿勢』,但這種表達有點浮誇。之所以會做出這個姿勢,單純是因為身體在遭遇兩百度以上焚燒時肌肉會出現收縮。」
我邊說沃德邊皺起額頭;先是困惑,然後是嫌惡。
「你本來以為這個提農已經死了嗎?」醫生說。
這讓我立刻想到一個問題。如果羅斯.提農昨天在德州遭到殺害,我們七年前在佛羅里達大火之中找到的屍體又是什麼人?
凱西拿出iPad。「你訊問過鄰居了嗎?」她問霍林斯。
「那邊的屋主是個房地產經紀人。」他指向一條死胡同。「他說受害者兩年前搬進來,不叫羅斯.提農,對鄰居來說他是巴伯.布肯里奇。」
提農弄了個假身分,在這裡買下房子,低調生活。
於是這引發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要殺一個已被認定死亡的人?
「有看到金髮的女人嗎?」我問:「近七十歲?提農的妻子?」
霍林斯搖頭。「沒有,這傢伙獨居。」
我低頭看。受害者的西裝襯衫沒扣釦子,大大敞開,露出血跡源頭:他的胸骨劍突到腰部之間位置被挖開了一個大窟窿。
我的目光往上挪到提農的胸膛。
那裡有個記號,刻在剖開處往上約六吋。但是當沃德醫生將屍體翻過來,提農的軀幹便因此沾滿了血。
「警長拍過照了,」沃德順著我的目光,「在我把他翻過去之前。我們想那應該是你們來這裡的原因。」
我們來這裡的原因是凱西收到了老闆的簡訊。法蘭克.羅伯茲,凌晨五點○三分。
幫妳和嘉德納訂了七點三十分傑克森維爾飛達拉斯的機票。
法蘭克只不過收到德州一具屍體上驗出提農指紋的消息,別無其他。就是因為這樣,凱西才會在開車過來的路上推算我們會看到的畫面;她在計算兩個不同的人擁有相同指紋的機率。
但不是那樣的,這就是同一個人,是我二○一三的嫌犯。
我朝門走去。霍林斯警長只進來兩步,彷彿只要和那灘橢圓血跡隔開距離就能抵禦邪惡。
死亡是有氣味的,我想。
不只是臭掉雞蛋的那種刺激氣味,或是鮮血和尿液離開原本盛裝它們的身體容器發出的惡臭。那種氣味是看不見的,是來自在旁觀看的人;來自法醫、律師和警察;來自看見這樣的屍體後不分男女產生的想像,他們腦中會浮現一個念頭:如果這種事發生在他身上,就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我不理解那種想法。小的時候,母親告訴我我的腦子「運作方式和其他人不同」。我的情感只是「比普通人慢一點」。這可能是件好事,因為在其他人可能會產生反應、感到畏懼或憤怒時,我反而能保持頭腦清晰。
但是還是有一些別的影響。
一些我母親沒說出口的,一些不得不度過的難關。
在辦公室的最後一週,兩名探員進洗手間洗手時,我正在其中一個隔間裡。「他辦案的時候――」第一個人說:「真的超級驚人,我認真的。但在人際關係上……好吧,我們可能不該再說什麼低什麼能那種話了你說是不?」
「確實啦,」第二個人說:「不過你要說的是低能對不對?」他笑著說:「唉呀,不小心說出來了。」
我從隔間出來時看見了那兩個探員的表情,很確定他們是在說我。
我走向霍林斯警長。十分鐘前,他見到我們還樂得要命。「像是追星族。」凱西大概會這麼說。可是現在他臉都青了。
我記得母親多年前教過我的一個祕訣:在開始對話之前,先給甜頭,表現得討人喜歡一點,情緒多一點。
「我很遺憾這裡發生了這種事,」我說:「阿許藍是如此風光明媚。」
霍林斯感激地點點頭。「謝謝你。」
「你在沃德醫生把屍體翻過來前先拍照了嗎?」我問。
警察從後口袋拿出手機,給我看廚房的廣角照片及羅斯.提農的仰躺特寫。
「我需要一塊海綿。」我轉向醫生。
沃德在工具箱中翻找,遞給我一個顯然是建築用泡棉的全新玩意兒。黃色長方形,三英吋厚,在最近的家得寶賣場賣三塊八九。
我拿到水槽弄溼,然後在屍體上方俯身,用泡棉角角慢慢清理提農的胸部上半。
他皮膚上刻著數字5和0,高約兩吋,中間相隔一吋,位於他兩個乳頭之間。
「你對數字『50』有什麼概念嗎?」沃德問。
我在腦中耙梳羅斯.提農二○一三被控犯下的三起謀殺的細節。他受害者的年紀分別是二十六、二十九和三十二;三人都被打昏;從傷口刺入胸壁的深度分別是四點二、五點三和六點一公分。
我在心中重複循環著五、六個不同的變數。
數字50……沒有任何意義。
我的專長是謎團,亦即,當我沒在鑽研模式或破解密碼,可能會有人說我除了解決謎團之外一無是處。也因為如此,位於傑克森維爾的FBI辦公室就不適合讓我把時間或天賦用在與真人互動上。對此我完全同意。
我站在租來的Toyota Avalon旁邊盯著那棟一層樓的黃色農舍。
「幹這怎麼可能啦。」我身後傳來一個聲音。
我望向我的搭檔。
凱西.帕多身材嬌小,只有五呎三吋,卻彷彿蘊含了一千個太陽的積極能量,而且滿口都是十九歲小孩的行話。
「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我說。
凱西闔上牛皮紙檔案夾。打從我們離開達拉斯機場她就一直在埋頭研究。開到這裡的路上,她不斷在推算我們看到場景的發生機率,也許百萬分之一……或兩百萬分之一。
有個警長走來,目測四十多歲,小麥色頭髮硬往上梳,蓋住禿頭,凸出的喉結從咽喉算起簡直有十四毫米高。
「萊恩.霍林斯。」他伸出一手。
我看著那隻手。我們每平方英吋的手掌上大概繁衍了超過兩百種細菌。「嘉德納.坎登。」我邊說邊跟他握手。我沒有強迫症,只是正好對此略懂。
我指著黃色房子。「你那位受害者,」我說:「是怎麼被發現的?」
「阿許藍天然氣公司有個員工去抄表,」霍林斯說:「從推拉窗看了一眼,見到血,就打給我們。」
凱西往嘴裡扔了一塊口香糖。她二十九歲,黑西裝外套底下穿了件灰色休閒褲。「然後你查了那人的指紋,」她說:「結果看見坎登探員的名字?」
霍林斯點點頭,我們跟著他走過草坪。「等待的時候我google了你們,」他說:「發現你們就是在索諾拉的洞穴找到那個六歲小孩的人。那在我們德州這兒可是大新聞。」
他說的是大概一年一個月前解決的那起案子,主導查案的是凱西和我。
「我不知道你還記不記得那有多扯,」霍林斯繼續說:「我們搞了個電話聯絡中心,又進行了地毯式搜索。結果你們一來就咻的一下――」
「他父親鞋子上有無水碳酸鹽的痕跡。」我說。
霍林斯皺起臉。
「就是那個從洞穴被救出來的孩子。」凱西說明。
「美國只有九個地方能開採出這種礦物質,」我說:「只有一個位於德州。」
「媽的就是這樣啦,」霍林斯搖搖頭,「我就是這個意思。」
警長有著低沉的嗓音,而我腦中出現一本書:《頸部喉結之研究》,第五十二頁,右側,一張喉結圖,外加與男中音相關的統計數字。
我們來到前門,凱西拿出兩副紫色橡膠手套,啪的往橄欖膚色的手上戴,重新將棕髮緊緊綁成一個馬尾。
「沒有別人進去過?」她邊問邊把另一副手套遞給我。
「只有我和醫療人員。」霍林斯說。
他用堅硬的靴尖推開紗門,而我仔細研究此人。他比我矮兩吋,身材結實,我比較運動員體格,六呎一,外加棕色鬈髮和藍色眼睛。
凱西指著打開的門粲然一笑。「敬老尊賢。」
我對此尋思再三,然後往裡面走了剛剛好五呎後停步。
這裡屬於開放式格局,中央有個中島,結合廚房與客廳;後方則流了滿地的鮮血。
那裡蹲了一個人,寬闊身軀上套了件拋棄式現場防護衣,「你倆一定是聯邦探員,」他說。此人目測約兩百八十磅,站起來時先用雙手撐了膝蓋,然後屁股。「我是泰瑞.沃德。」
「沃德醫生?」凱西用詢問語氣確認眼前這位是醫學檢驗官沒錯。
「正是在下。」
凱西發問時醫生眨了下眼,我立刻望向他放在廚房流理臺上的檢驗工具箱。箱中整齊俐落,看起來與釣魚時用的釣具箱無異,裡面塞了一副彎成某種角度的鉗子,握把部分只有一個圓環。
我又看了看沃德指節周圍皺巴巴的皮膚;他大約六十五至七十歲。
「阿許藍沒有全職醫學檢驗官嗎?」我問。
沃德瞇起眼睛,凱西看向了我。
「子宮頸組織取樣鉗,」我示意他的工具組,「我想您應該是婦產科醫生。」
「觀察入微,」沃德說:「我退休了,來這裡只是興趣使然。」
「非常感謝您的貢獻,」凱西說:「我們向來十分感激當地人員的合作,坎登探員你說是不是?」
我和凱西對上眼神,「是,」然後對沃德說:「一點也沒錯。」
我在距離屍體約一呎處蹲下;他正趴在磁磚地面上。我無須接觸屍體就能看出他在昨天深夜就達到屍僵,現已進入下一階段――肌肉變軟,也就是所謂的二次軟化。
但凱西注意到的是其他東西。
受害者的衣服在身側折成一堆,感覺前面釦子沒扣。凱西掀起衣服邊邊,見到他的左邊袖子滴血的路徑是一路往上而非往下,徹底違反地心引力。
「你把屍體翻過來了嗎?」她問。
「非翻不可,」沃德回答,「我得確認他死了沒。」
男人雙腿底下的血跡形成一個歪扭的橢圓,一路延伸到冰箱底下。我研究著那灘深色液體。標準成人體內總共會有五夸脫的血,地上至少有四夸脫。
「但我有把他放回去,」沃德說:「按照一開始看到的模樣。」
「謝謝您。」凱西回答,棕眼與我對看,揚起嘴脣。
我也回以一笑。沃德把屍體翻過來檢查再讓他躺回去,讓他泡回自己的血裡。
我一手放在受害者肩上,另一手擺在他腰部位置使勁推,直到讓他身體側立起來,彷彿架上的一本書,然後注視著這張我熟悉到不行的臉。
羅斯.提農。
我多年前追捕的人。之所以不再追下去是因為……他幾年前死了。
紗門喀拉一下,霍林斯兩大步走了進來。「所以你認識這傢伙?」他問:「這個死掉的傢伙和你們有一段過去?」
我腦中湧上各種統計數字:羅斯.提農二○一三年三月殺的三個女人、他的刀刺入她們體內的確切深度。
「我們採他指紋時電腦跑出他的名字,」霍林斯繼續說:「這讓我們很疑惑,因為他已經登記死亡了。」
疑惑不是正確的形容詞。
「七年前,」凱西說:「羅斯.提農是佛羅里達三起謀殺的主嫌,接著他家就發生了火災。」
我腦中出現一個畫面:羅斯.提農的妻子貝芙莉從烈焰中被救出,臉上滿是煙灰,金色鬈髮燒焦成黑炭色,但她丈夫似乎沒有這麼幸運。我還記得,那時我是直接在把羅斯.提農的焦屍運到法醫車的擔架上對他進行檢驗的。
「我沒搞懂,」沃德醫生說:「你的嫌犯――在那場大火中?」
我回想放著提農屍體的那張擔架。「人的身體遭受灼燒時會做出一個姿勢,」我對沃德說:「肌肉會收縮,雙手會像要出拳的拳擊手一樣往內收攏,法醫用詞是『拳擊手姿勢』,但這種表達有點浮誇。之所以會做出這個姿勢,單純是因為身體在遭遇兩百度以上焚燒時肌肉會出現收縮。」
我邊說沃德邊皺起額頭;先是困惑,然後是嫌惡。
「你本來以為這個提農已經死了嗎?」醫生說。
這讓我立刻想到一個問題。如果羅斯.提農昨天在德州遭到殺害,我們七年前在佛羅里達大火之中找到的屍體又是什麼人?
凱西拿出iPad。「你訊問過鄰居了嗎?」她問霍林斯。
「那邊的屋主是個房地產經紀人。」他指向一條死胡同。「他說受害者兩年前搬進來,不叫羅斯.提農,對鄰居來說他是巴伯.布肯里奇。」
提農弄了個假身分,在這裡買下房子,低調生活。
於是這引發第二個問題:為什麼要殺一個已被認定死亡的人?
「有看到金髮的女人嗎?」我問:「近七十歲?提農的妻子?」
霍林斯搖頭。「沒有,這傢伙獨居。」
我低頭看。受害者的西裝襯衫沒扣釦子,大大敞開,露出血跡源頭:他的胸骨劍突到腰部之間位置被挖開了一個大窟窿。
我的目光往上挪到提農的胸膛。
那裡有個記號,刻在剖開處往上約六吋。但是當沃德醫生將屍體翻過來,提農的軀幹便因此沾滿了血。
「警長拍過照了,」沃德順著我的目光,「在我把他翻過去之前。我們想那應該是你們來這裡的原因。」
我們來這裡的原因是凱西收到了老闆的簡訊。法蘭克.羅伯茲,凌晨五點○三分。
幫妳和嘉德納訂了七點三十分傑克森維爾飛達拉斯的機票。
法蘭克只不過收到德州一具屍體上驗出提農指紋的消息,別無其他。就是因為這樣,凱西才會在開車過來的路上推算我們會看到的畫面;她在計算兩個不同的人擁有相同指紋的機率。
但不是那樣的,這就是同一個人,是我二○一三的嫌犯。
我朝門走去。霍林斯警長只進來兩步,彷彿只要和那灘橢圓血跡隔開距離就能抵禦邪惡。
死亡是有氣味的,我想。
不只是臭掉雞蛋的那種刺激氣味,或是鮮血和尿液離開原本盛裝它們的身體容器發出的惡臭。那種氣味是看不見的,是來自在旁觀看的人;來自法醫、律師和警察;來自看見這樣的屍體後不分男女產生的想像,他們腦中會浮現一個念頭:如果這種事發生在他身上,就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我不理解那種想法。小的時候,母親告訴我我的腦子「運作方式和其他人不同」。我的情感只是「比普通人慢一點」。這可能是件好事,因為在其他人可能會產生反應、感到畏懼或憤怒時,我反而能保持頭腦清晰。
但是還是有一些別的影響。
一些我母親沒說出口的,一些不得不度過的難關。
在辦公室的最後一週,兩名探員進洗手間洗手時,我正在其中一個隔間裡。「他辦案的時候――」第一個人說:「真的超級驚人,我認真的。但在人際關係上……好吧,我們可能不該再說什麼低什麼能那種話了你說是不?」
「確實啦,」第二個人說:「不過你要說的是低能對不對?」他笑著說:「唉呀,不小心說出來了。」
我從隔間出來時看見了那兩個探員的表情,很確定他們是在說我。
我走向霍林斯警長。十分鐘前,他見到我們還樂得要命。「像是追星族。」凱西大概會這麼說。可是現在他臉都青了。
我記得母親多年前教過我的一個祕訣:在開始對話之前,先給甜頭,表現得討人喜歡一點,情緒多一點。
「我很遺憾這裡發生了這種事,」我說:「阿許藍是如此風光明媚。」
霍林斯感激地點點頭。「謝謝你。」
「你在沃德醫生把屍體翻過來前先拍照了嗎?」我問。
警察從後口袋拿出手機,給我看廚房的廣角照片及羅斯.提農的仰躺特寫。
「我需要一塊海綿。」我轉向醫生。
沃德在工具箱中翻找,遞給我一個顯然是建築用泡棉的全新玩意兒。黃色長方形,三英吋厚,在最近的家得寶賣場賣三塊八九。
我拿到水槽弄溼,然後在屍體上方俯身,用泡棉角角慢慢清理提農的胸部上半。
他皮膚上刻著數字5和0,高約兩吋,中間相隔一吋,位於他兩個乳頭之間。
「你對數字『50』有什麼概念嗎?」沃德問。
我在腦中耙梳羅斯.提農二○一三被控犯下的三起謀殺的細節。他受害者的年紀分別是二十六、二十九和三十二;三人都被打昏;從傷口刺入胸壁的深度分別是四點二、五點三和六點一公分。
我在心中重複循環著五、六個不同的變數。
數字50……沒有任何意義。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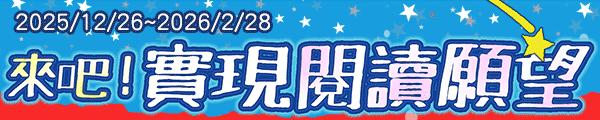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