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並留下永遠難以與之共存的傷口,
而我們之間大部分的人,我們所想要的,
不過就是活著而已。
越不痛苦越好。
● 榮獲2007年高中生龔固爾文學獎(Prix Goncourt des lyceens 2007)
● 入圍2007年龔固爾文學獎最後決選
●售出包括英美在內二十三國語文版權
從邊境過來的路上,已經很久沒有人出現過,也從沒有人想再走過這條只會帶來不幸與悲劇的路。
但在五月的某一天,一個外地人帶著家當突然出現。他的打扮特異,口音不同,但舉止文雅,彬彬有禮,常常一個人在村裡散步、畫畫。在他短暫居留的期間,這個偏僻小村的平靜生活幾乎完全被攪亂了。
波戴克要寫的報告,就是關於這個外地人被村民集體私謀殺害的事件。因為他是村裡唯一受過教育的人,知道該如何正確用文字書寫表達;也因為他是唯一未參與謀殺案的人。所以村裡所有的人都希望由他來執筆撰寫報告,並且寄望透過他的文字來證明村民的清白。
但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波戴克逐漸發現,這些要求他來撰寫報告的村民,並非完全都是無辜的。相反地,他們一個個都牽涉其中。同時波戴克也開始對圍繞在他周遭的村民有更多的認識,特別是村民所不希望被他發現的諸多秘密,包括他為什麼會被圍捕送到集中營,以及他離家的這段時間,他的妻子發生了什麼事。
波戴克並不冀望能夠為自己所發現的一切伸張正義,只是希望將真相公諸於世。而最終波戴克也讓自己成為了真正的外地人。
本書特色
透過波戴克的報告,會看到封閉的小村因為恐慌、對陌生人的敵意而釀成的悲劇,以及人性的醜陋面並非只在戰爭時才會顯露,而是隨時隨地都可能被你我遇上......
名人推薦
王秀文 / 文藻外語學院法文系助理教授
讀完這個力道十足、震撼人心的故事,任何讀者都別想全身而退。闔上書頁的許久之後,故事中的文字仍將如影隨形,長存於腦海中,並精準道出了我們心中的疑問和恐懼。法國Lire閱讀雜誌
克婁代在本書中探討他向來著迷的主題——人性的「恨」與其所伴隨的邪惡。他的文字不憐憫或同情任何角色,筆觸更達到極高的藝術之境,而字裡行間透露的人性關懷,最是動人。這個故事必定會烙印在你心上。法國快訊雜誌
簡練、清晰的創作,完美的架構,《波戴克報告》是一部崇高的巨著。世界報
這本書無疑是克婁代的創作顛峰,完全展現了他說故事的功力,以及將文字化為一幕幕影像的天賦。Elle雜誌
在克婁代簡鍊優美的文筆下,一個可怖的世界出現在讀者眼前,在那裡,「犯罪」是理所當然的生存之道……Le Magazine-Litteraire
對人性做出反思,道出了對外來者的憎恨、對異者的抗拒心理、群眾的盲從和愚昧、集體的懦弱……克婁代再次直指人心的黑暗核心,故事中藏著壓抑的憤怒與深思後的人性……這正是上乘的文學作品。法國巴黎人報
作者的文字故事與他執導的電影一樣光彩奪目,給人一種「真希望我們早點認識他」的驚喜。他大膽處理一個看似老生常談的題材,卻能提出極為新鮮的觀點;並用惡夢般的筆觸精準勾勒出一種人類基本的、無法逃避的「毀滅他人」衝動。紐約時報
小說背景設在無名的歐洲山區小村裡,探討的是人類的集體罪惡,藉著村民回想戰爭時期的艱苦而揭開最黑暗的祕密。雖然故事裡沒有一個人是乾淨的,但到了最後卻有幾人已開始慢慢邁出腳步,朝著人性的方向踏出不太確定的腳步。作者的筆法具有高度視覺化、想像力,作品有如格林童話般令人驚駭,卻能帶出美感與奇蹟。出版人週刊
「不確定性」正是克婁代作品的主題。這個故事既像虛構的寓言,又似寫實的紀錄片,道出了人性的冷漠和偏狹。英國衛報
克婁代的故事深邃而睿智,捕捉了人性心理複雜而幽微的面向。它把人性善與惡的兩極完全鋪陳在讀者眼前。英國電訊報
高度原創、成就非凡、卻又深深扎進 人心的小說;克婁代是法國傳統下的概念小說家,長於熟練處理抽象觀念與人物原型。泰唔士報
在卡夫卡、卡謬和(猶太裔科學家) 普利摩.李維的作品中都有陰暗的黑影,但是克婁代的文筆卻喚醒了生命的美好——縱使他量測的是邪惡與刻毒的深度。金融時報
一趟直探人性核心的旅程,深切詮釋了身為「人」、並致力尋求「真相」的意義。直指人性的關鍵問題:當我們的生命本為「虛無」,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泰唔士報評論
一本超凡的小說,如卡夫卡的作品般捕捉了身為人的迷惘狀態。英國週日郵報
本書的獨到之處在於,雖然刻畫的是「人對人」的不人道對待、殘酷的愚昧行徑、恐懼,終至向邪惡屈服,但克婁代卻在這片黑暗中捕捉到一線希望。蘇格蘭人報
試閱
我得說出來。得讓所有人都知道。
我啊,我什麼也沒做,沒參與;而且事情發生後,當我得知事情的經過時,我本來打算永遠也不要再提起這事。我本來打算綑綁起我的記憶,將它牢牢裹在繩索中,好讓它安穩的像一隻困在鐵網裡的貂那樣。
但是其他人強迫我:「你呢,你會寫啊,」他們對我說:「你讀過書的。」我回說讀那點書不算什麼,何況我甚至沒有完成學業,而且我對讀過的東西也沒啥印象了。他們才不想理解這些呢:「你會寫東西,認得很多字,知道怎麼用字,也知道怎麼用文字來說一些事情。這樣就夠了。咱們呢,咱不懂得這些。咱們會講得亂七八糟的,可是你啊,你會說話,然後這樣他們就會相信你。再加上你又有那台打字機。」
那台打字機,老舊得很,好幾個按鍵都壞了,也我沒有任何可以用來修理的工具。這機器任性得很。疲憊不堪的機器。有幾次它就這麼卡住,沒給我任何警告,彷彿它在反叛似的。不過所有這些情況我都沒說,因為我不想最後落得安德雷——那個「外人」——同樣的下場。
不要問我他的真名,我們從來都不知道他的真字。他才幾乎剛到這裡,人們便用徹頭徹尾捏造出來的方言詞彙稱呼他,我翻譯一下:「禿眼仔」──因為他的眼神好像有點快從他臉上跳出來的緣故;「喃喃人」── 因為他話說的很少,而且總是用我們覺得好像在呼氣一般的小小音量說話;「月亮來的」──因為他看起來雖然人在我們這卻是心不在焉;「從那裡來的人」。
不過對我來說,他一直都是「外人」,也許是因為除了他是從不知道哪裡冒出來的之外,他還與眾不同。關於這點,我很清楚:甚至有時候我得承認,我覺得他,好像有點就是我。
他的真名,我們之中從來沒有人曾經問過他;或許村長有問過一次,不過我想他並沒有得到答案。現在,我們再也不會知道任何事了。一切都太遲了。然而這樣很可能還比較好。真相,可是會斬斷雙手,並且留下深深的傷痕,讓人永遠難以與之共存的傷口。而我們之間大部分的人,我們所想要的,不過就是活著而已。越不痛苦越好。這就是人性吧。我很確定你會跟我們一樣,要是你們瞭解戰爭,瞭解戰爭把這裡變成什麼樣子,特別是那些隨著戰爭而來的事情,那好幾個星期,好幾個月。尤其是最近這段時間,那個男人來到了我們的村子,然後就住了下來,就這樣,很突然地。為什麼選上了我們的村子?山腳下有這麼多個村子,座落在林子裡,就好像安置在巢裡的蛋一樣,而且很多都與我們村子並無二致。為什麼偏偏就是選了我們這個離什麼都遠、如此的偏僻村子?
他們說他們想要我來寫這個報告的那個時刻,是在許洛斯客棧裡發生的,大約是在三個月以前。就在之後…… ,就在那之後……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們就說是那個事件之後吧,或者說慘劇,或著說事故發生之後吧。除非我用「那件事」來稱呼。這是一個很詭異的詞,滿是煙霧,鬼魅般的字眼,它的意思差不多是「發生了的那件事」。從方言裡找一個字來說明這些,也許還比較好,那是一種不是語言的語言,卻與住在這裡人們的處境、氣息與靈魂,如此完美地契合。用「那件事」來形容無法形容的事情。好吧,我就說「那件事」吧。
所以說當時那件事才剛剛發生。除了兩三個足不出戶的老人,大概還加上裴貝神父,他當時應該在他那座有著像展翅老鷹般大牆的小教堂內某處,喝李子酒喝得醉醺醺的,除了他們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場,在像個有點昏暗的大山洞似的客棧裡,菸草與壁爐的煙把大家悶得快要窒息。剛剛發生的那件事讓大家變得遲頓,嚇得呆滯,然而同時,該怎麼說呢,又感到心頭寬了,因為事情一定得做個了結,不管是用這個方法還是別的法子。我們再也承受不了了,您要知道。(待續)
每個人都退縮在自己的沉默中,即便我們幾乎有四十個人在客棧裡,擠得像是一捆柴裡的柳樹枝,擠到快要透不過氣來,擠到聞得到別人身上的味道,他們的口氣、他們的腳味、他們的汗,與潮濕舊羊毛或呢絨衣服上的嗆人霉味,他們的衣服上沾抹著塵土、樹林、肥料、麥桿兒、葡萄酒與啤酒,尤其是葡萄酒。不過倒不是說因為大家喝醉了,完全不是,拿酒醉作為藉口實在是太方便了。這樣會一下子抹去所有的凶殘暴行。太簡單了。太過於簡單了。我會努力不要去淡化那些十分艱苦而且複雜的事情。我會盡力。我不敢保證我一定做得到。
請大家搞清楚我的立場,我再說一次,我啊,我大可閉嘴沉默,但是他們要求我來敘述,而且當他們要求我做這件事的時候,大部分的人拳頭都握著,要不就是把手放在口袋裡,我想像他們的手緊緊的握著刀柄,就是這些人剛剛才用來……
我最好不要講得太快,不過挺困難的,因為現在我覺得在我背後有東西,有動作,有聲音,有人在看。幾天下來,我自問:自己是不是一點一點變成了獵物,有一大群獵人在追逐我,還帶著狗嗅來嗅去。我覺得自己被窺伺、被圍捕、被監視,就好像以前每次有人在我背後想要抓住我最細微的一舉一動,並且解讀我腦子裡的想法時的那種感覺。
我再回到那件用了刀子解決的事情上頭。我不得不回到這件事上頭來。我剛才想說的是,在那種很特殊的情緒裡,大家滿腦子都還是野蠻與血腥的想法,想要拒絕大家對我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很危險的。所以我才接受了,儘管心理不願意。我只是單純地出現在那個客棧裡,在不對的時刻,就在「那件事」發生的幾分鐘後,在這個令人驚愕的片刻,同時也是搖擺不定、躊躇未決的片刻,人們會拼命抓住第一個開門進來的人,不管是要把他當成救星,還是要把他砍成碎片。
許洛斯客棧是我們村裡最大的咖啡店,村子裡另外還有五家咖啡館和一間郵局、一間服飾縫紉用品店、一家五金行、一間肉店、一間雜貨店、一間專賣肝胗等的下水鋪、一所學校,還有一間附屬於S城公證人辦事處的支處,髒得跟個馬廄似的,而負責這個職務的,是戴著老朽夾鼻眼鏡的席格菲.克諾普,我們叫他公證人大人,即使他只是個辦事員而已。另外還有楊金斯的小辦公室,他當年擔任警察的職位,不過他戰爭的時候死了。我記得楊金斯出發去打仗時的情景,他是頭一個去的,平常從來不笑的他,那天笑著跟所有的人握手,彷彿要去參加的是自己的婚禮似的,旁人都認不出他來了。當他在莫貝史旺的鋸木場旁轉彎的時候,他大動作地揮手,並把帽子拋向空中,做個歡樂的道別。人們從此再也沒見過他,也從來沒有人來接替他的位子。他那間小辦公室的遮陽窗板是關上的。些許苔藓從此封住了門檻。門用鑰匙鎖上了,我不知道這把鑰匙在誰那裡。我從來沒問過。我學會了不去問太多問題。我還學會了把自己裝扮成牆壁、街道上塵埃的色調。那一點也不難。我跟什麼都不相像。
許洛斯客棧有時候有點算是雜貨店,因為寡婦貝納赫開的那家雜貨店,一旦太陽下山就會拉下鐵捲門。許洛斯客棧也是大家最常去的一家咖啡館。它有兩間廳堂:大的那間在前面,牆壁是變黑了的木頭,地板上鋪著木屑,而且當人們走進去的時候,幾乎都差點要跌倒,因為要走下兩級直接在砂岩上鑿出來的陡峭台階,而台階中間的部分,已經被魚貫而過的、好幾千名酒客的鞋底給磨出了凹陷。再來是那間小廳,在後面,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小廳由一扇優雅的落葉松木門與前廳隔開了,門上刻著一個年份,一八一二。小廳是保留給幾位客人專用的,他們每週在此聚會,每個星期二晚上,他們在此喝酒,用菸嘴刻花的陶瓷煙斗抽他們自己田裡種的菸草,也抽不知哪裡做的劣等雪茄。他們甚至還給自己取了個名字,叫做「覺醒會」。對一個古怪的社團而言,這仍是個古怪的名字。人們既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時候成立的,也不知道成立這個社團的目的是什麼,又不知道要怎麼樣才能入會,更不知道成員有誰,應該是些重要的農莊主吧,也許有克諾普大人、許洛斯本人,想當然爾還有村長漢司.歐許維,他是這裡擁有最多產業的人。人們也不知道他們在這個小廳裡搞些什麼,也不知道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談些什麼。有些人說重要的決定都是在這裡訂下的,說他們訂下了古怪的盟約、承諾。其他人則懷疑他們只是在那裡大口大口的猛灌燒酒,玩玩跳棋或是紙牌,一邊抽抽煙、說說笑話。也有人宣稱他們聽見過門下傳出音樂聲。也許小學老師迪歐登知道真相,他以前總是到處翻找搜尋,不管是在紙張文件堆裡,還是在人們的腦袋裡,而且他對於探求事情的正反兩面是那樣的饑渴。不過,唉,這個可憐的人不在了,往後再也不能對這事說些什麼了。(待續)
許洛斯客棧,我幾乎是從來不去的,因為,我應該承認這點,狄業特.許洛斯那鼴鼠般陰鬱的眼神,他那粉紅通透、沒有頭髮的腦袋下,總是汗涔涔的額頭,他那聞起來像骯髒敷料的褐色牙齒,讓我覺得渾身不自在。然後,還有另一個理由,就是自從我從戰地歸來之後,我便不求與人為伍。我習慣了自己的孤獨。
「那件事」發生的那一晚,老費朵琳差我去客棧買家裡缺的奶油。她那天想要做奶油小酥餅。通常是她去採買食物必需品,但在那個不祥的晚上,我的小普雪發著可怕的高燒不能下床,費朵琳在她的床頭跟她講著《可憐裁縫畢立希》的童話故事,而我太太艾梅莉亞則挨著她們,極為輕柔地哼著她的歌兒。
自那天起,我想了很多,關於這奶油,食物櫃裡缺少的這小小一塊奶油。我們永遠也沒辦法太清楚地理解,人生的路程竟可以像那樣取決於一些不重要的事物:一塊奶油、我們為了他途而放棄的某條道路、我們追隨或逃避的一個影子、我們決定用幾顆鉛彈射殺或是饒牠性命的一隻烏鴉。
小普雪張著太過明亮的美麗雙眸,聆聽著那個蒼老的聲音,那是我自己從前也曾經聆聽的,發自於同一張嘴,當時比較沒這麼老的這同一張嘴,可是在那時就已經沒有牙齒了。小普雪用她那被高燒加溫的小小黑色瞳仁望著我。她的雙頰是越橘的顏色。她對我微笑,向我伸出雙手,在空中拍打,同時像隻小鴨子似的牙牙呢喃道:「爸爸,回來我的爸爸,回來!」
我出門的時候,耳朵裡帶著我孩子的樂音,還有費朵琳低聲述說的話語:「畢立希在他茅屋的門口看到了三個騎士,披著被歲月洗白的盔甲。三位都持著一根紅棕色的長槍與一塊銀色的盾牌。我們看不到他們的臉,甚至連他們的眼睛也看不到。在天色太晚的時候,往往都是這樣的。」
2.
夜晚將它的大衣覆蓋在村子上,就像馬車夫拿斗篷掩蓋旅途中所生營火的餘燼。一家家的房舍緩緩吐著青煙,屋頂如鱗片般的長長松木條,讓人聯想到化石紀元的動物那凹凸不平的背部。寒氣開始降臨,還只是一種單薄的冷,然而我們卻沒法再習以為常,因為在九月的最後這幾天,白晝裡天熱得跟麵包師的烤爐似的。我記得我望了望天空,然後看著滿天的星星這麼樣彼此擠在一起,樣子就像因害怕而找著伴兒的雛鳥。我心想我們馬上就會一下子跳進冬季。冬天在我們這兒,可漫長得有如串在一把長劍上的好幾世紀一樣;而在冬季期間,我們村子擠在樹林裡,而周圍山谷的遼闊無盡就彷彿像個奇特的監獄。
當我走進客棧的時候,他們就在那兒了,我們全村的男人幾乎都在,他們的眼神是那麼的陰沉,像石頭一樣呆滯而沒有表情,我立刻就猜到發生了什麼事。歐許維在我背後關上了門,隨即向我走來。他有點兒顫抖,用他那對藍色的大眼直勾勾盯著我的雙眼,彷彿他是第一次見到我似的。
我的腸胃開始翻攪,我以為它們就要吞沒我的心臟了。於是我問了,非常虛弱地,一面望著天花板,為了想要用眼睛穿透它,為了試著想像安德雷的房間,為了試著想像他。安德雷,他這個人,留著頰髯,細細的小鬍子,稀少的捲髮自他兩鬢邊伸向空中;他那屬於胖子的、和善且圓滾滾的大頭。然後我說了:「你們該不會是幹下了那件事吧……?」那幾乎不算是個問題。比較像是一句沒有徵求我允許便自我口中脫出的控訴。
歐許維用他那像騾子蹄般碩大的雙手,抓住我的肩膀。他的表情比平常更粗暴,而在他那長著痲子的鼻樑上,一粒細小而閃亮的汗珠,宛若一粒晶石,以極緩慢的速度滑落。他依然顫抖著,而且因為他那樣地抓著我,讓我也顫抖了起來。「波戴克…… 波戴克……」他能夠跟我說的就只有這樣。然後他便退後,再度走入全部都望著我的人群中,與他們融為一體。(待續)
我覺得自己像是一隻細瘦蝌蚪,迷失在春天的巨大水漥中。我的腦袋嗡嗡作響,而且很詭異地,我想到了我來這兒要買的奶油。我轉身走向站在櫃檯後面的狄業特.許洛斯,對他說:「我來這兒只是要買點奶油,一點奶油,就這樣而已……」他聳了聳他那瘦弱的肩膀,一面調整了一下梨型肚子上的法蘭绒腰帶,然後我想就是在這一刻,威廉.弗滕候,一個長著一張兔子臉的農夫,擁有從史黛努森林到漢奈克高原之間的所有土地,他向前走了幾步,對我說:「你要多少奶油都給你,波戴克,可是你要寫下事件的始末,你要當抄寫人。」我大大地翻著白眼,心想弗滕候是打從哪裡找來「抄寫人」這個說法──他連這個詞的發音都扭曲了。這人愚笨的很,這輩子應該從來沒翻開過一本書。
說故事可是一項專業,但卻非我的才能。我所做的只是針對植被、樹木、不同的季節與獵物、思托比河的枯水期、雪量及雨量的狀態,寫下一些簡短的概述報告。對我所屬的單位而言,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工作,而且不管怎樣,這個單位遙遠得很,要旅行上好幾天才到得了,而且他們一點也不把這工作放在眼裡。我都不太清楚我的報告是否還能夠送達目的地,甚至連這些報告是否有人會讀都不知道。
自從打戰以來,郵政通訊就運作得挺糟,而且我想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郵務才能重新建立起來。我幾乎都沒有再收到錢了。我覺得自己被遺忘了,或者他們以為我死了,要不就是他們再也不需要我了。
有時候,艾弗德.伍茲維勒,那個郵務員,他會兩周一次徒步來回走一趟,一直走到S城──也只有他能去,因為他有許可證,可以交換郵件。他讓我明白他替我帶回了一張匯票,並且給我幾張鈔票。我要求他解釋清楚一點。結果他大動作地比劃著手勢,我看不懂是什麼意思,只有斷斷續續、破碎的聲音,好像絞肉似的,從他被嚴重的兔唇弄得皺成一團的嘴裡跑出來,也是些我無法理解的聲音。我收下那張字跡難以辨認、皺巴巴,上面被他重重打了三個戳印的紙片,和與之而來的少許金錢。我們就是靠這些錢度日。
「我們又沒有要你寫一本小說。」說這句話的人是魯迪.勾特,馬蹄鐵匠。儘管他的醜陋──一匹馬的蹄子踩碎了他整個鼻子,且讓他的左臉頰凹陷了下去──,他卻娶了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芳名叫做潔爾德,她總是在鍛鐵爐前擺著姿勢,彷彿永遠在等待畫家給她畫肖像。「你就把事情說一說,就這樣而已。就好像是你平常那些報告的其中一篇。」勾特的右手緊緊抓著他那把大槌子,他赤條條的肩膀裸露在皮圍裙外頭。他離壁爐很近。爐火炙烤著他的面孔,而他那把工具的鋼面閃閃發亮,好像一把仔細鍍了錫的鐮刀刀鋒。「好吧,」我說道:「我來說,我試試,我答應你們我會試試看,我會用『我』來說,就好像我報告裡寫的那樣,因為我不會別的敘述方式。不過我要先告訴你們,那意思是說所有人,所有人,你們給我聽好了。我會說『我』,但我指的是整個村子、周圍的小村莊,我們全部啊,好嗎?」
一陣譁然,有如拉車的牛馬畜生,只要車轅綁得鬆了一點,便咕噥抱怨要更舒服一點的那種躁動聲。然後他說了:「一言為定,就這麼做吧,不過,要小心,什麼都別改,你得說出一切。必須要確實把一切說出來,好讓讀報告的人能夠理解,並且原諒。」
我不知道誰會讀這報告,我心想。要他理解,也許可以,但是要他原諒,那可是另一回事。這點我不敢說出來,我是在自己內心最深處想到的。當我說好的時候,客棧裡到處一片喧嘩,像是鬆了一口氣,拳頭鬆開了,口袋裡的手伸了出來。我覺得好像所有的雕像又再度變回了人類。而我,我很用力地喘著氣。我非常驚險地避免了某件事的發生。我甚至寧可不要知道是什麼事。(待續)
那是在去年的初秋。當時戰事停息已經有一年了。在防禦工事上,長出了淡紫色的秋水仙,而初雪往往會在晨間落下,落在圍繞著我們這座背斜谷東邊的那座龐佐尼山脈的花崗岩山峰上。粉末狀白皙清新的積雪,在太陽升到高峰的時刻就會融化殆盡。當時安德雷才來我們這裡剛滿三個月,幾乎是不多不少整整三個月,他來的時候帶著幾口大箱子,穿著刺繡的衣服,一身神秘,還有他那隻棗紅色的馬兒和一頭驢子──「他名字叫做蘇格拉底先生,」他指著驢子說道,「然後這位是茱莉小姐,我請您跟大家打招呼啊,茱莉小姐,」然後那隻美麗的馬兒接連低了兩次頭,讓在場的那三個女人驚訝得倒退了一步,並比劃著十字。他那細細的聲音我猶仍在耳,他跟我們介紹他那兩隻動物,彷彿牠們是人類似的,使我們全都驚奇不已。
許洛斯拿出了玻璃杯、酒杯、碗、茶杯給所有的人,還倒上了酒。我也必須要喝。就好像是在宣誓一樣。我驚駭地想著安德雷的面容,想著他住的那個房間,一間我有點認識的房間,因為我去過,在他的邀請之下去過三次,交換幾句神秘的話語,一面喝著一種黑色、很奇怪的茶,是我從來沒喝過的。那兒有書名很複雜的厚重書本,有些還是跟我們語言的寫法完全不同的外國文,唸起來應該會像敲打碎石子般鏗鏘作響,還有封面飾了燙金的精裝書籍,或是截然相反,像一堆破布的軟趴趴舊書。有一套中國瓷器的餐具,被他保存在飾著釘子的皮箱子裡。大皮箱子裡收著一套用獸骨與烏木做成的棋子、一根手杖,杖柄是琢磨過的水晶,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他的臉上總是堆滿笑容,一種常常取代了話語的笑容,因為他是個省話的人。他的眼睛很圓,是玉器的那種美麗綠色,而且有點從他的臉上突出來,這讓他的目光更具有穿透力。他話說得很少,反而常聆聽。
我想到所有這些我認識多年的人剛剛幹下的事情。他們不是兇殘的人,而是些農夫、工匠、農場雇員、守林員、小公務員。總之就是些和您我一樣的人。我放下我的杯子。我接過了狄業特.許洛斯遞給我的奶油,厚厚一大塊,包在玻璃紙中,紙張發出斑鳩震動翅膀那樣的聲響。我走出了客棧,然後一路跑回我家。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跑得這麼快過。
從來沒有。
3
我回到家的時候,小普雪已經睡著了,費朵林半睡半醒,待在她旁邊,嘴巴微微張開,露出那三顆僅存的牙齒。艾梅莉亞停止了低聲歌唱,反而抬起眼睛望向我。她笑了。我沒有什麼好跟她說的。我速速爬上通往我們臥房的樓梯,鑽進被單裡,像人們潛入遺忘中那樣。我因此覺得好像經歷了一場無邊無際的墜落。
這一夜我睡得很少,而且還睡得很不好。我圍繞著「火山口」打轉又打轉。「火山口」的由來是因為戰爭:將近有兩年的漫長時間,我是在離我們村子很遠的地方度過的。他們把我帶走,就像那好幾千人被帶走一樣,只因為我們的姓氏、面孔或是信仰與其他人的姓氏、面孔、信仰不同。他們把我關在很遠的地方,那是一個所有的人性都被抽離了的所在,留下的只有披著人類外皮、沒有良知的獸。(待續)
那兩年真的是充滿了晦暗。我想要說的是,在我的人生中,我感覺到有一種非常黑暗、非常深沉的空虛,就是因為如此,我把這兩年命名為「火山口」,我夜裡還常常會冒險到火山口的邊緣去。
老費朵琳從來不離開廚房。那是她的偉大王國,夜晚時分她都在她的椅子上度過。她不睡覺。她說她已經過了睡覺的年紀。我從來都不知道她確切的歲數到底是多少,她自己都說她不記得了,還說反正這樣沒有妨礙她出生,也不會阻擋她死亡。她還說她不睡覺,是因為她不想被死亡出奇不意地碰上,而她想要的是在死亡來臨之際,好好地正面看著死亡。她閉著眼睛低聲唱歌,補綴著故事與回憶,用嚴重磨損的夢境來編織幃幔。她的手放在她跟前的膝蓋上,而她這雙手,她乾燥的雙手,銘刻著扭曲的血管,與像刀鋒般直條條的皺紋。在這雙手裡,我們可以閱讀她的人生。
我跟費朵琳講述過我遠離我們世界的那兩年歲月。我回來後,負責照料我的人就是她,當時艾梅莉亞還太過虛弱。費朵琳像在我還小的時候那樣照顧我。她重新尋回了那些照顧的動作,用湯匙餵我那張支離破碎的嘴,包紮我的傷口,一點一點地讓我那些外露的骨頭長出些筋肉。在我發燒發得太過劇烈、顫抖得有如浸泡在冰川裡且神志錯亂的時候,是她看護著我。幾個星期便這樣過去。她沒有提問題。她等待著話語自己跑出來。然後她傾聽,久久地傾聽。
她什麼都知道。或者說幾乎是如此。
她知道那個總是會回到我夢中的黑暗空虛。知道我在「火山口」邊緣的靜止漫遊。我常常覺得她應該也有類似的夢境,她應該也有糾纏著她、煩擾著她的一大片空白。我們每個人都有。
我不知道費朵琳是否曾經識得青春。我見過的她一直都是彎著腰、駝著背,且長著斑點,像是一粒被人遺忘在食物貯藏室裡放了三季的枇杷。甚至在我還是個孩子、當她收容我的時候,她就已經長得像個坑坑疤疤的巫婆了。她那沒有奶水的乳房垂在灰色的罩衫下。她來自非常遠的地方,時間上很久遠,地理上也很遙遠。她從歐洲腐敗的肚子裡逃了出來。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站在一間傾圮了、還冒著煙的屋子前。也許那是我父親、我母親的屋子?我應該也曾經擁有一個家庭。那次是在另一場戰爭的初期,當時我獨自一人,年屆四歲,玩著被火吞噬掉一半的木圈圈殘骸。費朵琳拖著她的手拉車經過。她看到了我。她停了下來,搜索著她的背包,取出一粒光鮮紅亮的漂亮蘋果。她把蘋果遞給我。我像個餓死鬼似地吃掉了蘋果。費朵琳跟我說話,對我說了些我不懂的字眼,也問了一些我不會回答的問題,她摸了摸我的額頭和頭髮。(待續)
我跟著這個有蘋果的老女人,彷彿她是個吹奏魔笛的人。她把我舉起來放在手拉車上,把我穩穩地安置在一些袋子、三只平底鍋和一包牧草之間。車上還有一隻兔子,長著漂亮的棕色眼睛和黃褐色的毛,牠的肚子軟軟的,而且非常暖和。我記得我撫摸了牠,而牠也任我撫摸。我也記得費朵琳在生長著染料木的轉彎處停了下來,然後她用我的語言詢問我的名字,也告訴我她的名字 ──「費朵琳」──,並且要我往回看看我村子的殘留廢墟。「看清楚啊,小波戴克,你是從那裡來的,而且你再也不會回去了,因為這個村子很快就會什麼也不剩了。睜大你的眼睛看啊!」
於是我用盡全力看了那些肚子腫脹的動物屍體、四面透風的穀倉、崩塌的牆壁。村子的街道上也有很多躺著、手臂攤開呈十字或是身軀捲成球狀的傀儡。很大的傀儡,不過因為距離的緣故,在我看來顯得極為細小。然後當我從正面盯著看的時候,太陽在我眼裡放入了滾燙的金子,並且讓我村子的景象消失了蹤跡。
我在床上翻來覆去。我清楚地感覺到艾梅莉亞也不比我睡的更沉。我一閉上眼,就看見安德雷的臉,他那棕色的眼睛,他那飽滿、像是用雞冠花塗抹過的顴骨,他那些微微捲曲的稀疏頭髮。我聞到他的紫羅蘭香水。
艾梅莉亞動了一下。我感覺到她的呼吸挨著我的臉頰,也吹撫著我的唇。我睜開眼睛。她的眼皮是闔上的,顯得十分平靜。她是那麼的美麗,讓我常常問我自己到底做了什麼,才讓她有一天注意到了我。多虧了她,在那時候我才沒有陷入絕境;當時我每一分鐘想的都是她,當我在集中營的時候。
看管我們、毆打我們的那些人總是反覆的說我們不過就是些屎,比老鼠大便還不如。我們不可以看他們的臉,我們得一直保持著頭朝向地面,並且要不吭一聲地挨打。每天傍晚,他們會把湯倒入他們那些看門狗的碗裡,長著蜜色被毛、嘴巴翹翹的看門犬,眼睛常常垂著有點兒紅紅的淚水。我們必須像狗一樣,四肢著地,去吃我們的食物,像狗一樣,只能用我們的嘴。
大部分跟我一起被關的人都拒絕這麼做。他們都死了。我呢,我像狗一樣的吃東西,四肢著地並且用我的嘴吃東西。所以我活著。
有時候,衛兵喝醉酒或是無所事事之際,會拿我來尋開心,給我套上頸圈和狗鍊。我得要這麼行走,戴著頸圈和狗鍊。我得要裝腔作勢,學狗用後腿站立,自己兜著圈子轉;我得汪汪叫,我得伸舌頭,我得舔他們的靴子。衛兵從此再也不叫我波戴克,而是叫我「波戴克犬」,然後他們更加起勁的大笑。大部分跟我一起的人都拒絕學狗,於是他們死了:不是餓死的,就是被衛兵反覆毆打到死。
其他的囚犯很久都沒有人肯跟我說話了。「你比看守我們的傢伙還要糟,你是個畜生,你是一坨屎啊,波戴克!」像那些衛兵一樣,他們反覆說我不是人。結果呢,他們死了。全都死了。我呢,我還活著。也許他們沒有任何生存下去的理由?也許在他們內心深處或是在他們村子裡,沒有任何愛人?是啊,也許他們沒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
持續好幾夜,衛兵最後都把我綁在一根木樁子上,離狗窩很近。我就地睡下,在塵土中,在狗的皮毛、呼吸和狗尿的氣味裡。在我的上方,有天空。遠一點的地方,有瞭望台、有哨兵。然後更遠之處,有田野。我們白天看得到那些麥田,在風的吹撫之下,以一種不真實的肆無忌憚,讓麥穗呈波浪之態起伏擺動;還有樺樹叢的樹冠,還有附近那條大河的銀色河水流動的聲響。
但我呢,其實,我離這個地方非常遙遠。我並沒有被綁在一個木樁子上。我沒有戴著皮項圈。我沒有半裸的躺在狗旁。我是在我們家裡,躺在我們床上,緊靠著艾梅莉亞溫熱的身軀。我再也不是躺在塵土中了。我很溫暖,而且我感覺到她的心貼著我的心跳動。我聽見她的聲音對我訴說著所有愛的字眼,那些她最清楚在我們房間暗處哪裡可以找到的字眼。就為了這一切,我回來了。
「波戴克犬」回到了他的家,活著,而且與期待他歸來的、他的艾梅莉亞重逢了。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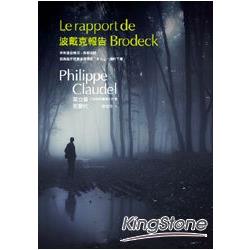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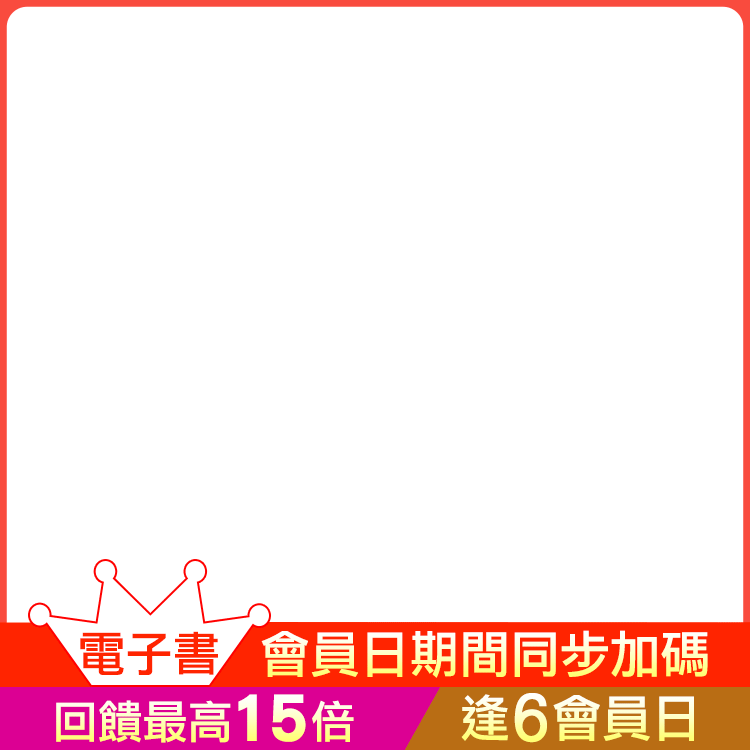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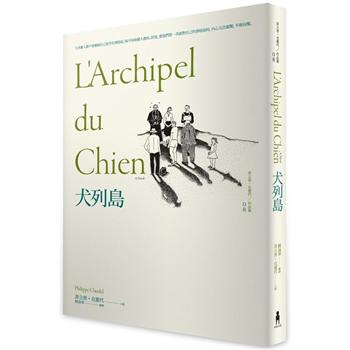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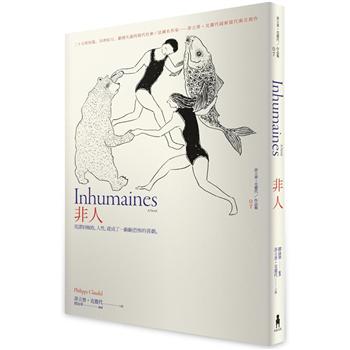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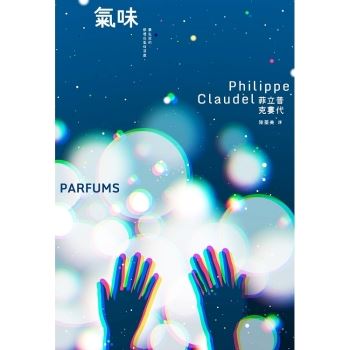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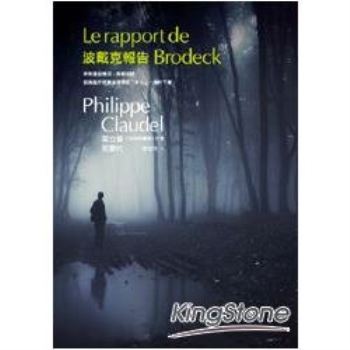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