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姆斯:創作,到真實之路
全球最經典設計雙人組 伊姆斯Eames 唯一傳記故事及設計哲學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也改變了我們坐下來時所看到的景象
英國設計教父 Terence Conran 與法國設計大師Philippe Starck 齊聲推薦
伊姆斯事務所主持人、伊姆斯夫婦外孫 伊姆斯.迪米崔歐斯 執筆
全球最經典設計雙人組 伊姆斯Eames 唯一傳記故事及設計哲學
Terence Conran:「對我這一代設計師來說,查爾斯與蕾.伊姆斯是英雄人物。對於任何創意領域的學習者來說,這本書讀起來肯定愛不釋手。」
Philip Starck:「伊姆斯並非創作美與智慧,只不過是傳達出了本然而已,輕輕鬆鬆、渾然天成。」
◆伊姆斯夫婦(Charles & Ray Eames)堪稱20世紀全球最傑出設計雙人組,其設計的家具及建築作品,成為世紀流傳的經典。
◆伊姆斯躺椅Eames Lounge、雲朵椅La Chaise、休閒木椅LCW,及被大量仿製的暢銷系列伊姆斯玻璃纖維椅……知名經典作品歷時不衰,至今仍保有時尚流行尖端地位。
◆領導當代家具界的國際品牌Herman Miller及Vitra,伊姆斯即為其中最具影響力及重要性的設計師。
◆全球著名Vitra Museum所典藏100張全球經典設計椅中,伊姆斯座椅即佔了十多張。
◆包括MoMA、龐畢度中心在內的全球多家美術館都有伊姆斯作品的永久典藏。
◎伊姆斯,永遠的「時尚經典」
當代建築圈流傳一件事:當贏得建築生涯第一件重要委託案之後,對自己最大的犒賞,就是買一張「伊姆斯躺椅」!這故事真實地傳達了伊姆斯在建築設計師心中的重要地位;而向來強調「創新是最後手段」的伊姆斯,卻是以其多樣卓越創新的產品設計,擄獲了時尚份子乃至大眾的心;也許還有很多人未曾聽聞「伊姆斯」的名字,但一定看過甚至坐過至少一張「伊姆斯椅」!即使歷經了數十年後的今天,只要看看幾乎每一個強調時尚及設計感的空間,一定都不缺一張伊姆斯的設計椅即可得證!
◎伊姆斯,用「創作」,讓這個世界更完整
雖然是以家具設計奠定了這對夫妻檔設計師查爾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 1907~1978)及蕾.伊姆斯(Ray Eames, 1912~1988),在大眾心中的地位,但除了身為建築師及設計師的伊姆斯,他們其實還同時是影片導演、策展人、攝影師、藝術家……等全方位創作人,創作遍及家具座椅、展覽策劃(一些展覽成為永久展,或目前仍在進行中)、影片(多銀幕影片及幻燈影片)、攝影照片、繪畫、建築等。
曾以單件創作在拍賣市場創下36萬美元(約合台幣一千萬元以上)的伊姆斯作品,在伊姆斯夫婦兩人均過世後,家族將其主要收藏品、近百萬件的照片、幻燈片、繪圖、手稿,捐贈予美國國會圖書館(許多作品是伊姆斯生前便承諾要贈予該館);而家具作品的原型則贈予德國威爾的Vitra維特拉設計博物館,讓後代學者、學子及所有有興趣的朋友,仍有機會親炙伊姆斯的畢生智慧泉源,讓創作的種子持續萌芽下去。
◎《伊姆斯:創作,到真實之路》伊姆斯唯一傳記故事及設計哲學
伊姆斯的豐碩創作之所以能跨越時空,一項關鍵原因可能在於,他們除了受到傳統藝術的吸引(許多二十世紀的創造者都是如此),還更進一步探索設計的方式,以回應他們尊敬的傳統所採用的質樸設計流程。伊姆斯常常舉傳統印度圓壺為例來說明設計過程,剛認識伊姆斯作品的人可能會問,這個演變已久的印度圓壺和當代家具經典有何關係?或許關聯性不在產品本身,而是要回頭追溯伊姆斯作品背後的演變過程,以及伊姆斯夫婦兩人的創作、思考及生活歷程。
然而雖然伊姆斯的作品已在全球掀起風潮,但一直沒有像本書一樣的傳記,充分地連接起這些傳奇作品背後的理念與哲學、嘗試聯繫起完整的故事,以闡述伊姆斯作品最重要、且史無前例特色:在哲學與琳瑯滿目的個別成果之間,具有深層與完整的連續性,像是「創新是最後手段」、「賓主關係」、「從做中學」等實踐的信條。這正是本書將要與讀者分享的重要層面。
身為伊姆斯基金會執行長、伊姆斯夫婦外孫的本書作者伊姆斯.迪米崔歐斯,與查爾斯和蕾的關係親密,從獨特的角度,探索伊姆斯夫婦世界的豐富力量。他分享了個人趣事、以往未曾曝光的照片,並廣為訪談伊姆斯夫婦的友人與同事,將他們足具影響力的哲學與廣獲推崇的作品連繫起來。這些設計流程背後的故事,對於不熟悉這兩名設計師的讀者來說,不僅能增長知識,讀起來也相當有趣、深獲啟發;而對於已熟知伊姆斯夫妻檔的讀者來說,則能更深入理解其設計流程。他們的作品從建築、家具,延伸到展覽設計與電影製作,在這些龐大的作品中,他們的核心哲學隨處可見。這是第一本書,說明這些緊密交織的聯繫。
◎伊姆斯改變了二十世紀坐的方式,也改變了坐下時所看到的景象
《華盛頓郵報》指出,查爾斯與蕾改變了「二十世紀坐的方式」,但他們其實也改變了我們坐下來時所看到的景象。他們改變了我們房間裡的東西,及我們在房間裡安裝的螢幕上所顯示的東西。重要的不光是他們做了什麼,更是他們預見了什麼。他們的作品暗示著一條道路,在此藝術與科技並不衝突,而傳統也可以代表著改變。將概念傳達給外行人,不表示要在他們面前花言巧語。製作一張便宜的椅子,不代表可以粗製濫造,而是依據需求而來的合理設計限制。
隨著新世紀開始,設計更講究時尚,但過程卻不必然有著全面的理解。然而對查爾斯與蕾來說,設計不是展現風格,而是傳達「目的」。草圖或模型不是目的,而是即將展開一個全方位過程。人們有意無意間感受到和伊姆斯作品的連結,反應的就是這個願景——設計必須「進入形式內裡」。
對於伊姆斯來說,設計不是一項專業能力,而是生活能力;「伊姆斯住宅」是一項里程碑,也向來一直是個家;伊姆斯椅子是圖像,也總是舒適;《十的次方》是哲學宣言,也總是最能讓人感到興奮。認識與喜愛查爾斯與蕾的人,或許最想念的,是再度與他們談天的機會。
本書的目的,就是在將伊姆斯的思想拼圖整合在一起,協助讀者看出伊姆斯作品之間綿密的聯繫。在讀者展開自己的設計創作旅程之時,本書提供一些方式,讓每個人更具體地體驗查爾斯與蕾的作品。希望讀者進入伊姆斯夫婦精彩的故事、認識他們所創造的美麗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期盼讀者能把在書中所遇見的觀念,應用到自己的生活與工作上。
目錄
序言
Chapter 1 查爾斯與蕾.伊姆斯的世界
Chapter 2 牛頓紙牌
Chapter 3 印度圓壺
Chapter 4 伊姆斯椅:三十年瞬間(一)
Chapter 5 優秀的學習者
Chapter 6 最廣義的繪畫
Chapter 7 從墨西哥到葛蘭布魯克
Chapter 8 查爾斯與蕾.伊姆斯
Chapter 9 三十年瞬間(二)
Chapter 10 認真看待樂趣
Chapter 11 個案研究第八號
Chapter 12 以影片寫散文
Chapter 13 賓主關係
Chapter 14 限制
Chapter 15 「數學」
Chapter 16 九○一文化
Chapter 17 模型製作
Chapter 18 「如果事務所是座島嶼」
Chapter 19 畫面可以是想法
Chapter 20 提案、初樣與《十的次方》
Chapter 21 十年分離
後記
序/導讀
能為我的著作《伊姆斯》(An Eames Primer)特別撰寫繁體中文版序言,我感到無比榮幸。自從本書英文版出版之後,我曾在華文世界各地的大學演講、舉辦展覽,包括香港、台北、廣州、北京、上海等等。我曾在那些地方分享本書中的部分想法,但總盼望著某一天,能與我所遇見的熱情群眾,分享書中所有的故事。
十分感激商周出版費心製作本書,無論是照片或插圖皆依照我最初的理想安排,呈現給繁體中文版的讀者。當然我感到自豪的原因,除了《伊姆斯》能以另一種語言出版之外,真正的理由在於:雖然伊姆斯的作品在全球掀起風潮,但沒有一本像本書一樣的傳記,充分地連接起這些傳奇作品背後的理念與哲學。能與讀者分享本書的這一層面,令我振奮不已。希望讀者喜歡伊姆斯夫婦精彩的故事,認識他們所創造的美麗作品,而更重要的是,期盼讀者能把在書中所遇見的觀念,應用到自己的生活與工作上。
從設計方面來看,當初會撰寫這本書,是因為我體認到了一種需求。回顧與伊姆斯夫婦作品相關的文獻,無論是在他們生前或逝世後撰寫,我發現了許多圖文書,也有幾本學術著作,當然還包括蕾.伊姆斯本人撰寫的書——這本書有點類似分類目錄,並未在她有生之年完成。雖然完成該書的人寫作目的或許與蕾不同,但大致而言,蕾所提供的基本內容相當完整。
然而,這些書籍卻未曾嘗試聯繫起完整的故事,以闡述伊姆斯作品最重要、且史無前例特色:在哲學與琳瑯滿目的個別成果之間,具有深層與完整的連續性。正是這項思想與行動之間的關聯,促使我撰寫讀者即將閱讀的這本書。不僅如此,雖然過去十年,伊姆斯書籍所涵蓋的範圍固然擴大了,並帶來許多用處(有些也在龐大的參考書目中提到),但《伊姆斯》依然是唯一試著聯繫起查爾斯與蕾的生活、工作與思想,將之視為整體的一本書。這一點令我自豪。能寫出一本可當作「故事書」來閱讀的設計書,我感到相當得意。無論你在捷運上、在家或在飛機上,都可以閱讀這本書。
能以繁體中文與讀者分享這完整的連結,對於我及今天伊姆斯家族的每個人來說,意義相當重大,因為這是一股動力,讓我們大家以各自的方式,照料我們家族的作品。但還有另一項原因令我高興:無論我走到哪裡,都看到這世界渴望好設計的證據。我的意思並不是指「風格」,而是在最深刻的意義上,對設計的投入。
我想在此提出幾點說明。這份說明,尤其適用於設計師——無論是身經百戰的老手,或是才剛開始理解到設計將在生命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年輕學子:
從我當初撰寫本書以來,全球各地的人已見識到意料之外的變遷、悲劇與機會在眼前展開。華文世界的人也不例外,事實上更可說是清楚的例證。無論是天災、社會巨變或環境破壞,和經濟機會、生活水準及對國際的理解提高是共同存在的。每個國家各有自我的挑戰,從我所在的美國,到太平洋上的小島國無一例外。
那麼,設計該在何處找到最佳立足點?答案是:正如查爾斯與蕾的實踐方式,設計可在任何地方立足。設計不是特定的產品或可看見的外觀,而是一種「過程」。我相信設計是一種投身於這趟旅程的意願,而沒有人比查爾斯與蕾的實踐方式更豐富、更通用。
讓我舉出你將在書中看到的例子:「賓主關係」。查爾斯曾說,設計師的角色,基本上是做個能預期賓客需求的好主人。換言之,當你坐在真正的「伊姆斯椅」上,你就是查爾斯與蕾的賓客。當你在觀賞伊姆斯影片《十的次方》,你也是他們的賓客。而你將會知道,他們以各種方式,闡述這個觀念。
我們必須體認到,這是普世皆然的觀念。賓主關係並非和現代主義或今天的生活一樣新穎。在希臘最古老的神殿、阿拉伯半島的傳統漁船,及中國運用了數個世紀的農地配置規劃,皆反映著賓主關係。原因在於,賓主關係是屬於「人性」的一部分。截至目前,我已在三十五個國家談論過設計與我自己的作品,我敢說,每個地方都會負起主人照料賓客的人情責任。或許「賓客為神」這句梵文諺語,把賓主關係的觀念,表達得最簡潔扼要。
對於查爾斯和蕾來說,要把這個概念放在其作品的中心,就是重視人性勝於意識形態、設計勝於風格。容我說得更清楚些:美與美學絕對可能成為擔任好主人的一部分。
為什麼我要在序言中提出這項觀念?因為這本書對於設計師與學生的重要性,不只是告訴你過去有哪些優秀的作品,更要告訴你這些作品背後的思想。本書出版之後最重要的成果,可能是「你」如何把這些概念,應用到「你」自己的作品中。
正如查爾斯.伊姆斯曾說:「一切終將有所連結。」我在此邀請讀者,讓自己能在查爾斯與蕾的作品之間,做出雙向的連結。
獻上至深的期盼與感激
伊姆斯.迪米崔歐斯
(Eames Demetrios)
2011.2.28 於 加州洛杉磯
原文序
我十四歲時,曾在舊金山的斯坦哈特水族館(Steinhart Aquarium)擔任志工,經過一串繁複的過程後,我很幸運地獲選參加一趟南太平洋的旅程,跟在長達三十呎(約九公尺)的鯨鯊後頭游泳。出發前一夜,外公查爾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竟出現在我家門口,沒人料到他會來。他帶著一台相機,那是一九七○年代中期上市、一款35mm的陽春機種,讓我帶去旅行。查爾斯告訴我,這是他能找到最便宜的一台,因此就算遺失或泡水都無妨。他說,他和我的外婆蕾(Ray)知道,如果我借了父母的尼康(Nikon)相機,肯定不敢把它泡到海裡,隨便想怎麼拍,說不定連帶出門都不敢,所以找了這台給我。真佩服他們,怎麼知道我當時正擔心,要是弄壞了父母昂貴的相機怎麼辦?查爾斯帶給我的禮物真是恰到好處。我後來照了好些鯨鯊的照片,部分還收進我最早的出版品中。
這則小故事,又和我心裡的另一則小故事連在一起。我的母親露西亞.伊姆斯(Lucia Eames)曾說,她小時候和父親查爾斯一同在戶外畫畫。對她來說,「跟父親共用顏料和畫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後來,她聽到旁人對於查爾斯竟讓一個五歲的小女孩碰昂貴的貂毛畫筆,甚至還能整天使用,感到驚訝不已。查爾斯有他自己的看法。一般人會覺得,這麼貴的畫筆「給孩子用只是浪費」,但是查爾斯卻主張,讓小女孩這麼做,是在幫他自己「確認露西亞從小就知道,如何適當地尊重畫筆和顏料,並小心使用。」與其養成壞習慣,好的作法(例如顧好自己的工具)可從小灌輸。
若單獨來看,其中一則故事講的是節儉,另一則卻是奢侈。誰都可以輕鬆想出相反的故事:祖父母幫出發探險的孫子找來最炫的相機,或者父親買最便宜的畫筆給五歲的孩子。但其實這兩則故事都顯示出價格與價值之間的差異。重要的不是故事中的行為,而是背後的想法,如此一來,才能把這些故事裡真正的觀念連繫起來。無論是相機,還是畫筆的故事,最終都展現何謂「適切」。
查爾斯會把這個概念稱作「需求」,例如設計流程的關鍵是在體認「需求」。我開始寫這本書、做了些研究之後,現在回顧起這些往事,發現許多其他例子都回應著相同的想法。我知道,似不相干的伊姆斯案件之間有何關聯,必須退後一步、探究更深層的聯繫才能明白。我想起他們的攝影,及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伊姆斯館藏的八十萬張照片。我想起外祖父母的「水族館」(Aquarium)設計案。我想起他們的朋友。我想起我的姊姊卡拉(Carla)要出遠門,登上飛機前,蕾設法把最完美的小禮物送到登機門前,給她一個驚喜。我想起了「本該如此」(way-it-should-be-ness)。我想起查爾斯似乎總和最高層的人合作,無論對方是來自哪個組織。我想著蕾的畫作及查爾斯較不知名的繪畫,以及兩個這樣的藝術家有何共通之處。我想起聖路易(St. Louis),想著查爾斯和蕾兩人都在這個曾經是重要核心的城市中長大,這裡是十九世紀鐵路幹線的樞紐,但到了二十世紀中期,終究失去了地位。我想著查爾斯與蕾多麼了解商標的意義、甚至是它的價值,卻從不認為那是萬能的。
這本入門書的目的,是讓讀者了解查爾斯與蕾.伊姆斯的重要作品、主旨及想法,以及他們生活與工作的軌跡。我會討論他們作品如何完成、為何有這些作品。我不會牽強地把他們的生活與作品連繫起來,而是描述伊姆斯夫婦作品與設計手法的主要概念。最重要的是,我想傳達他們的設計哲學。本書書名《伊姆斯入門書》(An Eames Primer),是源自自他們創作的影片《通訊入門》(A Communications Primer),但或許這本書的作法,是在回應《十的次方:關於宇宙萬物的相對大小的影片提案初樣》(Powers of Ten: Rough Sketch for a Proposed Film on the Relative Size of Things in the Universe),影片《十的次方》是查爾斯與蕾.伊姆斯在1977年共同攝製的一部科普影片,展現宇宙間當時已知的最大與最小組成型態)這本書的第二版版本(共有三個版本)。本書是以主題式傳記的形式,淺談他們作品的入門書。
本書中談到的,不光是我年輕時候的事情,還包括近年來經營伊姆斯事務所(Eames Office),負責查爾斯與蕾作品的宣傳、保存與延續的工作生涯。我在這份工作中身兼數職,但最美好的部分,應是與查爾斯和蕾的親友、同事進行許多對話,或閱讀舊書信、看他們的影片、上圖書館、處理未解的問題、理出頭緒、端詳那些座椅、研究伊姆斯住宅的光線、尋找畫作、檢視幻燈片、聆聽錄音……等等。我要謝謝這段時間以來,和我討論查爾斯與蕾的人,因為這是持續進行的對談。查爾斯在
試閱
曾有人問查爾斯:「你是在一瞬間,就構想出『伊姆斯椅』?」他回答:「是呀,差不多在三十年的瞬間。」說話的當時,距離一九四○年和艾羅.沙利南一同獲得紐約當代藝術館(MoMA)舉辦的「有機家具」比賽首獎,已經有三十年了。
若追溯到最早為阿肯薩斯州海蓮娜市的教堂,設計出有著彎曲扶手的長椅,時間就更長了。但是查爾斯的話,顯然透露出比這些細節還重要的訊息。他的基本信念是:設計是個過程,而非單一的成果,這個過程從未真正結束。伊姆斯事務所最後所進行的其中一項案件,是關於「創造」的時程,並舉辦展覽,但是這個案子隨著查爾斯的辭世而擱置。只不過,即便查爾斯活得更久,這項案件也可能會被捨棄,因為他對這案子感到灰心。他認為,越是探索知名的創造發明(如攝影或電腦),就越會發現,要確定這個發明是在哪個時刻發生,無異緣木求魚。伊姆斯夫婦「三十年的瞬間」,就是一項好例子。在《設計問答》(Design Q &A, 1969)這部影片中,有人問查爾斯:「設計是個人的創作嗎?」他回答:「不是。如果要講求實際,就必須肯定前人的努力。」有趣的是,隨著時間過去,查爾斯和蕾發展出的創作方式,使他們自己也成為這些曾付出努力的「前人」。
這三十年的瞬間,可追溯至一九三九年,查爾斯為水牛城克蘭漢斯音樂廳(Kleinhans Music Hall)設計座椅。到了一九五○年代初期,查爾斯和蕾設計出「玻璃纖維椅」時,椅子的概念已臻完整。然而一直到一九七○年代初期,伊姆斯仍在探索相關概念,例如「兩件式祕書椅」(Two Pieces Secretarial Chair,這項案件使他們的設計過程綿延了三十年)。這樣的演進過程,最能說明伊姆斯事務所的設計運作過程:他們不是靠著一時興起的靈感,而是持續不斷地解決一個接一個問題,並從做中學,直到找出解決方案。而這項解決方案,又成為下一段旅程的起點。查爾斯與蕾在一件件案子中實踐這哲學;由此觀之,思考他們職業生涯的寬度與廣度時,就是在追溯設計過程能如何合理地應用到生活方式。這一瞬間或可說是象徵著查爾斯與蕾的設計手法。假如這是他們的工作方式,那麼,最早的果實就是以家具呈現。
一九三九年,查爾斯三十二歲,擔任底特律附近葛蘭布魯克藝術學院的設計系主任。他已經在這裡待了一年左右,而過去十年,多半在聖路易從事建築行業。他與艾利爾.沙利南建築師事務所的年輕合夥人、也是老沙利南的兒子艾羅.沙利南結為好友。查爾斯不時參與沙利南事務所的案件。當時擔任葛蘭布魯克藝術學院校長的老沙利南,正在紐約州水牛城設計克蘭漢斯音樂廳。老沙利南擔任該棟建物的建築師,查爾斯和艾羅則負責設計座椅。
他們設計出許多不同的座椅,他們先是用一堆插銷做草模,模擬找出符合人的臀形、坐起來最舒適的曲線,而決定出座椅個別惹人注目的曲線。雖然這些椅子並未大量生產賣給一般消費者,但從設計仍能看出量產的潛力。「克蘭漢斯椅」(Kleinhans Chair)在查爾斯的設計生涯中,佔有重要地位,因為這是他首度傳達出這項概念:從單一塊材料上絞盡心汁找出了「一體成型椅」(single-shell chair)的解決方案。然而從材料的觀點來看,這張椅子基本上仍只是彎曲的木板,並沒有複雜的曲線,比較傾向於芬蘭建築設計師阿瓦爾.奧圖(Alvar Aalto)的椅子類型。
這款座椅安裝後獲得好評。雖然椅子數量不算多,但因為也是小批量產,因此可以說是客製商品的量產。而查爾斯與艾羅一定也開始思考他們所面臨的限制與可能性。一九四○年,MoMA宣布舉辦「有機家具設計」(Organic Designs in Home Furnishings)比賽時,查爾斯和艾羅知道機不可失。競賽由MoMA設計部門總監諾耶斯所籌辦,他認為隨著社會上出現種種變化,設計也該隨之有機演化。他在簡報時這樣表示:「隨著新的生活方式發展,我們需要新穎的方式處理設計難題,也需要新的設計語彙。在居家家具領域裡,近年來並未發展出傑出的設計。能充分考量現今社會、經濟、科技與美學趨勢的解決方案,仍嫌不足。」諾耶斯繼續指出,能提出解決方式的年輕設計師,面臨著相當不利的環境:「他們沒有機會接觸到製造商,來生產所設計出的產品。」
「有機家具設計」比賽旨在以一種不尋常的方式,處理這項難題。許多製造商同意生產獲獎產品,而一批零售業者也同意販售。(最初僅由紐約的布魯明戴爾百貨公司﹝Bloomingdale’s﹞帶頭。)換言之,比賽獲勝的設計師可以確保有通路。值得注意的是,今天要舉辦由博物館與廠商合作的競賽會很困難,原因是擔心利益衝突。然而,這種生產方式絕對是「有機家具設計」比賽能成功的關鍵因素。
比賽吸引全國有志之士參與,共有五百八十五件作品參賽,最熱切回應的莫過於葛蘭布魯克藝術學院。實用性與現代造型的結合,對學院的幾乎每個人而言,當然是有很大的吸引力。該校至少組成了五組團隊,參與這項競賽。這所學院受到「美術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的影響,普遍認為量產與優質作品可以共存。而對喜愛比賽的查爾斯與艾羅而言,藉由參賽作品來延續理想,是很自然的發展。查爾斯曾為他在聖路易的住宅案件設計過家具,並從這些經驗中,學到在設計一張實體座椅時,需要哪些努力。「有機家具設計」競賽是處理這些問題的好機會,還能獲得椅子生產的實際經驗。
查爾斯與艾羅的設計,比起「克蘭漢斯椅」又躍進一大步。這次作品已不是一道簡單的弧線在座椅骨架上,柔順地保持著平衡,而是運用了多重曲線。椅墊可以隱藏木作上的任何瑕疵,讓造型顯得流暢,也讓獨特的接合方式更搶眼。設計師這次則希望椅身的多重曲線盡可能保持連貫,而且是木材材料本身就創造出這種均衡,不必再用布料來遮掩。如果有幸贏得這項競賽,這些問題肯定能在生產階段中解決。
秋季班進入尾聲時,蕾.凱瑟(Ray Kaiser,不久後嫁給查爾斯,改姓伊姆斯)正好也在葛蘭布魯克藝術學院,旁聽編織的課程。許多設計本身已差不多完成,蕾則協助參賽者製作最後的一些展示用圖。蕾說自己「像個幫手」,和學校裡許多人一樣,熱情地投入製作過程。大約在這段期間,她和查爾斯發展出私人情誼。若從日後的發展來看,能親眼觀察設計流程,對蕾來說是極其寶貴的經驗,因為到頭來這支設計團隊及特別是這樣的設計手法,成了查爾斯與蕾他們兩人自己的實驗起點。另一名參與的學生是唐.奧賓森(Don Albinson),他後來加入伊姆斯事務所,負責製作伊姆斯家具很重要的原型設計。他還記得查爾斯大聲吆喝著問,有沒有人要來試坐這張椅子。查爾斯會很仔細地觀察,看看使用者對這張椅子的反應與體驗。最後,查爾斯和艾羅選定五張椅子、兩張休閒沙發、兩張桌子和幾件收納櫃參賽。
參賽作品(包括圖面資料與小比例模型照片)總算寄到紐約去了,留下精疲力竭的參賽者。葛蘭布魯克藝術學院的生活恢復正常,蕾返回紐約,和查爾斯一同思考他們的未來。一九四一年一月底,比賽結果公佈,查爾斯和艾羅贏得兩個項目:椅子和收納櫃。「有機椅」(Organic Chair)的造型搶眼,對量產可說帶來了挑戰,但評審還提及了另一項創新之舉:裝設彈性椅腳,因此有彈簧的感覺。然而,真正的冒險才要展開:短短八個月後,得獎作品就要在MoMA展出,還得投入生產。這會兒,伊姆斯與沙利南的團隊得交出真正的椅子,但目前他們手上只有平面圖和幾個模型。即便如此,他們的模型和查爾斯的照片實在太有說服力了,因此別人會問,椅子成品是不是已經做出來了——這當然還言之過早。
一開始,他們請奧賓森製作其中一張椅子的原寸石膏模型。事實上奧賓森和另一名學生吉兒.米契爾(Jill Mitchell),後來都成了查爾斯的員工。爾後多年,兩人也對於率先成為查爾斯員工的這事說出了自己的看法。雖然聖路易還有其他選擇,但一開始選擇從葛蘭布魯克藝術學院起步,絕對是明智之舉。奧賓森回憶起,查爾斯和艾羅一開始先用一種原本只是運用在木盤細部上的專利技術,但若要應用在較大型的家具上(例如椅子),則有相當困難。他們測試了另一種作法,也就是用「循環焊接」(cycle weld)這種汽車工業用技術,將椅腳的鋼材和椅身接合在一起。查爾斯將試作用的木料與鋼材用這種方式結合後,放進爐裡。然而,木材縮成了木炭(對爐子也會造成損害),這種手法還是有其侷限性:木材和金屬不能同時間、以同一種方式加熱。
椅子原型費時比預期為久,而桌子和收納櫃的問題則較少。桌子與收納櫃在一九四一年四月簽下合約,最後交由賓州的紅獅家具公司(Red Lion Furniture Company)生產。但椅子可沒這麼順利。同年四月,第一個木製椅身總算完成,可是沒有人滿意。廠商開始焦急了。七月份,海伍魏克菲家具公司的保羅.波瑟(Paul Posser)說:「我們這麼做,只是想幫商店和博物館一個忙。」當時查爾斯和蕾已結了婚、搬到加州,而艾羅則因為忙於其他案件(例如「軍用住宅」﹝Defense Housing﹞)而分身乏術。洩氣的查爾斯寫信給諾耶斯:「我想艾羅已告訴您,我們總算搞定鑄鐵模具。一想到幾個月前沒堅持試作,我就懊惱不已。」他的意思是,要製作出實際生產的模具困難多得多。的確,每張椅身都需要在各方面下很大的功夫。木材經過鑄模成型的流程之後會裂開,因此須以布料掩飾,這是他們不想要見到的。換言之,「有機椅」雖然旨在表現出量產的潛能,但是正如蕾日後所言,終究還是「成為手工品」。
從諾耶斯寫給MoMA館長阿弗列德.巴爾(Alfred Barr)的一封信裡,或許對於生產與成本的問題給出了最好的結論:「以扶手椅和躺椅來說,」他寫道:「椅背曲線非常複雜,目前還找不到方法做到充份修邊,讓木料能完全外露。因此背面都只好以布料包覆,只有小餐椅例外……目前,中產階級還無福享受坐上這些椅子的喜悅,畢竟這些椅子價格實在高得嚇人。」事實上,布魯明戴爾百貨公司在這則故事中成了英雄,因為該公司利潤通常為百分之百,但這回卻願意縮減到百分之十。即便如此,還是無法創造出「中產階級的享受」,光是一個椅身的成本,就要六至七美元。
一九四一年九月,「有機家具」展於MoMA揭幕。在查爾斯、艾羅、美術館與廠商的共同努力下,數量不多的椅子總算是生產出來了。由於經費拮据,查爾斯與蕾無法參加「激起了大片聲浪」——查爾斯曾在一封信中這樣表示──的開幕。對於這個計畫的各種意見大致上是正面的:一方面創造出好作品、發掘好設計師、也給予廠商有用的經驗;但是另一方面,伊姆斯與沙利南一體成型的椅身,卻未能在實質上達到大量生產的目的。這次展覽本身還有有趣的象徵。諾耶斯在展場擺放一張傳統的安樂椅,這張椅子像是金剛一樣被關在牢籠中,後面還貼著「巨人」海報,上面的標籤模仿動物園或自然歷史博物館的作法,寫著:「巨椅,美洲屬(Cathedra Gargantua, Genus Americanus)。成熟時體重為六十磅,棲息地:美國住家。嗜食小孩、鉛筆、自來水筆、手環、夾子、耳環、剪刀、髮夾與其他居家叢林的小型動植物。快速絕跡中。」
如果傳統家具即將絕跡,原因絕非展場裡的那些現代椅子,還是得靠著後繼的椅子不斷出現。查爾斯清楚地學到,若要做出能大量生產的設計,就得弄懂如何自己製作模具,而不光是做出最終成品。如此深刻的領悟,正是來自他實際動手做設計和工程方面的天分。不僅如此,查爾斯肯定理解到,為量產而設計是一種新的型態。這些椅子成品無法令他滿意,是因為他和艾羅當時在設計椅子時,並不了解製程的限制。後來查爾斯回憶道:「這麼說吧,我們一開始想朝著萊特(Frank Lloyd Wright)的理論前進(至少是我心中的萊特),後來卻可能看起來像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而不是萊特;但無論如何,仍是個人詮釋。」
他繼續說:「這場有機展覽更像是在主張一種原則。」從設計觀點來看,他們主要的概念突破,是將「克蘭漢斯椅」採用的奧圖式(Aaltoesque)板材中的合板材料,轉變成「一體成型座椅」的概念。現在查爾斯和蕾得為這樣子的材料找條出路,以做出複雜的曲線。查爾斯之後曾在這一條家具設計的路途上表示:「我們希望以最少的材料,為最多人做出最好的設計。現在聽起來或許有點自負了,但在當時絕對是最合理的處理方式。」如果有機展覽本質上變成了原則的宣示,那麼查爾斯與蕾花了五年,才提出生產上的實用主張,也耗費整整十年,才使之完整。
距離家具競賽結果揭曉不到一年的時間,珍珠港事變爆發了,一個月後的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諾耶斯沮喪地寫信給查爾斯:「在以戰爭為優先的壓力下,整個計畫的成果似乎一點一滴消失,最後什麼都不剩;沒有橡膠、沒有合板。」諾耶斯說的沒錯,有機計畫在戰火下無疾而終,不僅如此,查爾斯與蕾也無法繼續試作,學到正確的教訓。查爾斯和艾羅的合作,因為艾羅必須投入手邊急待處理的案件而就此畫下句點。然而兩人是在友善的情況下單飛,且雙方日後於公於私,都還有更多的探險待展開。查爾斯與接手任務的新婚妻子蕾,繼續朝著這方向前進。
查爾斯和蕾遷居洛杉磯,不僅代表來到新城市、過新生活,也代表著以新方式來理解設計與創作。這一次,查爾斯會學到在決定外觀之前,先考慮如何製作。換言之,伊姆斯椅子不再只是為了「純粹」造型上的表現;而是更經淬鍊的東西:設計的表現是在於做出判斷以滿足材料、生產與舒適度方面的特定需求,這樣子的成果。設計採用何種造型,是取決於這個過程。
洛杉磯西林區(Westwood)、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不遠處,現代主義建築師理查.努特拉(Richard Neutra)設計的一棟複合公寓裡,查爾斯與蕾在此潛心研究。蕾這麼說:「問題顯而易見,有機椅若要進入量產,就無法用原本以為的方式製造……所以我們的想法很單純:設法找出讓有機椅量產的方式。」換言之,他們需要學習如何量產出有複合曲線的模壓成型合板(molded plywood),以做出一體成型的椅身。椅子的造型得從這個過程誕生。
在這棟公寓的空房裡,夫婦倆著手建造一座稱為「喀嚓機」(Kazam!Machine)的裝置。之所以如此命名,並非因為它會發出怪聲,而是可傳達出魔法感,就像查爾斯先前為女兒露西亞設計的神奇盒子一樣。這台機器可以讓他們自行將合板模壓成型。機器裝設了曲線型石膏模,再繞上很耗電的線圈。查爾斯當年為了要讓機器有足夠的電力運作,得爬上公寓旁的電線杆,從變電箱偷接電,越爬越深信自己會被電死,恐怖的經驗令他永生難忘。所幸,他毫髮無傷、全身而退。透過模壓過程他們製作出了自己的合板:首先在模具上鋪一層單板(薄薄的木板,也就是膠合板裡的板層),再抹上一層膠,這個過程要重複大約五至十一次。(在製作「有機椅」時,是將一條條細長的單板鋪進想要的模具中做出木板,而不是置入一整片的單板。)「喀嚓機」密閉夾緊之後,接著以腳踏車打氣筒,為機器裡的橡膠氣球充氣,把木板推向模子,壓製成型。
在開發「喀嚓機」時,查爾斯與蕾也開始探索這台機器能做些什麼。他們早期做過的實驗還包括一組模壓成型合板的雕塑,這些雕塑既是在做技術的測試,也是美麗的藝術品,藝術與科技並不衝突。技術測試可同時成為具有美麗形式的雕塑,而雕塑就是一項測試。多年後,蕾談到藝術教育的理念時曾說,社會應該前進到「不需要再用到藝術這個字眼的時代。」他們以許多方式實踐這項理想,而值得注意的是,這項哲學在他們開始工作之初、在西林區小小事務所只有他們兩人時便已顯現。(他們得悄悄地把設備與材料搬進來;蕾說,要是讓房東們﹝包括努特拉的岳父母﹞看見,準會「心臟病發」。)
比較長的雕塑中,目前還留了兩模,當初應該做了更多個。這些是細微但重要的線索,訴說著雕塑在生產過程的測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這些雕塑多半被歸功於是蕾的作品,其實是兩人合作,就像許多後來的家具,也不該只歸功於查爾斯。他們還做了許多不同的一體成型椅身,測試技術與材料的極限。有些椅身出現了裂痕,有些則有伊姆斯切割的縫隙與孔洞。這些裂縫無論是刻意切出,或自然產生,都是為了釋放一體成型的複合曲線椅身在成型過程中所產生的壓力。
查爾斯與蕾持續地以「誠實」、或說非特意的自然方式來運用材料,此理念也成為日後他們設計流程的重要基石。換言之,如果椅子是以模壓合板製作,就該展現出模壓的合板,不應試圖隱藏,反而該去彰顯合板的本質特性。這個概念從某種程度來說,很類似「形隨機能」的信條,而使用「誠實」這個字眼,不僅賦予道德色彩,更是認可人性與主體的意義,意味著要做出特定的設計選擇,方式不只一種。查爾斯與蕾在尋求合板的誠實使用方式時,也對抗了原本不容置疑的經驗(說那是「事實」可就不對了):合板不行成為一體成型的椅身。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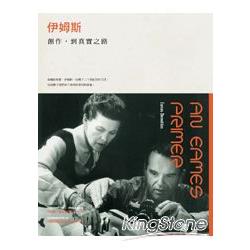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