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與文化冷戰:美國外交與亞洲電影網絡的起源
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 US 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
內容簡介
《電影與文化冷戰》探索了在冷戰政治高峰時期,新興獨立國家和殖民國家之間的跨國合作和競爭,如何形塑了二戰後的亞洲電影。李順真在對亞洲電影文化和產業的分析中,同時採用了全球和區域取向的研究方法。亞洲地區的新經濟格局和早期電影創業家間共通的戰後經驗,受到冷戰政治、美國文化外交,以及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間更加旺盛的文化流動所影響。作者詳細審視此混亂時期的文化現實,並根據冷戰時期因「不結盟」運動的影不斷擴大而形成、破裂和重建的國際關係,在此脈絡下全面重建亞洲電影史。
作者闡述了當時東亞和東南亞電影界高層、創意人員、政策制定者及學者力求將他們受好萊塢啟發的體系產業化,進而擴大市場,並提高其文化產品的競爭力。為此,他們成立了亞洲電影製片人聯盟,共同主辦亞太影展,並聯合製作電影。《電影與文化冷戰》闡明,亞洲戰後最初密集形成的電影製片人網絡體系,很大程度上是冷戰文化政治的結果和美國霸權的產物。在東京、新加坡、香港、吉隆坡等眾多城市舉辦的亞太影展,是冷戰期間電影人才一年一度的展示場合,而中央情報局也藉此機會,建立並維持美國與亞洲之間在文化、政治和制度各方面的聯繫。《電影與文化冷戰》以躍然紙上的筆觸,高度還原了這段幾乎被遺忘的亞洲劇院和電影產業史。
作者闡述了當時東亞和東南亞電影界高層、創意人員、政策制定者及學者力求將他們受好萊塢啟發的體系產業化,進而擴大市場,並提高其文化產品的競爭力。為此,他們成立了亞洲電影製片人聯盟,共同主辦亞太影展,並聯合製作電影。《電影與文化冷戰》闡明,亞洲戰後最初密集形成的電影製片人網絡體系,很大程度上是冷戰文化政治的結果和美國霸權的產物。在東京、新加坡、香港、吉隆坡等眾多城市舉辦的亞太影展,是冷戰期間電影人才一年一度的展示場合,而中央情報局也藉此機會,建立並維持美國與亞洲之間在文化、政治和制度各方面的聯繫。《電影與文化冷戰》以躍然紙上的筆觸,高度還原了這段幾乎被遺忘的亞洲劇院和電影產業史。
名人推薦
學界推薦(依中文姓氏筆畫排序)
王萬睿|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副教授
王潔瑩(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施茗懷(Evelyn Shih)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助理教授
孫松榮|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陳柏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謝欣芩|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王萬睿|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副教授
王潔瑩(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施茗懷(Evelyn Shih)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助理教授
孫松榮|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陳柏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謝欣芩|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目錄
導讀|地緣政治的微觀與感官/楊子樵
《電影與文化冷戰》中文版作者序
致謝
縮寫詞
前言|文化冷戰與亞洲電影網絡的誕生
第一部分:第一個網絡
第一章∣亞洲基金會的電影計畫
第二章∣FPA、美國宣傳和戰後日本電影
第三章∣奧斯卡光臨亞洲!
第四章∣建立反共製片人聯盟
第五章∣將亞洲電影推向世界
第二部分:第二個網絡
第六章∣發展型國家製片廠的興衰
第七章∣香港、好萊塢與網絡的終結
結 語|從亞洲到亞太
附錄一|延伸閱讀推薦書目
附錄二|參考書目
《電影與文化冷戰》中文版作者序
致謝
縮寫詞
前言|文化冷戰與亞洲電影網絡的誕生
第一部分:第一個網絡
第一章∣亞洲基金會的電影計畫
第二章∣FPA、美國宣傳和戰後日本電影
第三章∣奧斯卡光臨亞洲!
第四章∣建立反共製片人聯盟
第五章∣將亞洲電影推向世界
第二部分:第二個網絡
第六章∣發展型國家製片廠的興衰
第七章∣香港、好萊塢與網絡的終結
結 語|從亞洲到亞太
附錄一|延伸閱讀推薦書目
附錄二|參考書目
序/導讀
《電影與文化冷戰》中文版作者序
《電影與文化冷戰》(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是2020年10月當疫情將一切喊停時,於美國首次出版。那時我無法離開新加坡,只能坐在研究室裡透過Zoom,與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義大利、澳洲、香港和台灣,對我的工作成果感到興趣的各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學者和學生們會面。在這些新書分享中,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尤其來自博士班學生,是我當初如何想出要寫這樣一本書。我的研究綜合了電影研究、美國研究、冷戰歷史研究與區域研究等方法,於是相較於這些學門傳統定義下的學術訓練,我的研究顯得較為獨特。另外,如何在許多不同國家、多個圖書館間處理大量檔案素材,也是常被問到的問題。因而當台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請我為中文版書寫序言時,我想台灣讀者或許也會有類似疑問,便藉此機會將這個過程整理給讀者們。
這本書前後花費了十三年,開始於香港並擴展至六個城市,包括紐約、安娜堡、首爾、新加坡與坎培拉。這一切起自我因攻讀紐約大學博士班而待在香港的那六個月,當時我計劃書寫1950至1970年間香港與南韓之間合作製片的歷史。這個題目的靈感來自2004 年釜山影展的特殊回顧單元──「南韓香港聯合製作的年代」(The Age of Korean-Hong Kong Coproduction)。被南韓電影與香港華語電影產業之間獨特的電影交流歷史深深吸引的我,於2007 年夏天抵達香港。那是香港移交後的第十週年,一個混雜了各種期待與焦慮的時期。我待在香港島東面的西灣河──香港電影資料館所在地。我每天去那裡看片,並且在老電影雜誌、政府文件與各種檔案素材裡掘考資料。當時香港電影資料館是一個充滿生氣的地方,香港電影學者們包括已逝的黃愛玲(Wong Ain-ling)、何思穎(Sam Ho)、羅卡(Law Kar)、張建德(Stephen Teo)與高思雅(Roger Garcia),都積極書寫乃至重寫香港電影跨越亞洲、歐美多國的產業網絡歷史,組織學術活動、出版各式書籍與專刊。在他們的慷慨支持下,我有幸能面見並訪談諸多退休導演、製片與影星,讓我博士論文的研究能順利進展。
某次至香港大學圖書館特殊典藏閱覽時,我發現一本古舊的影展手冊,那是1956 年於香港舉辦的第三屆東南亞影展(Southeast Asian Film Festival)。我當時不知道這個影展,它從未在亞洲電影文獻中被提及討論,而我同時也很驚訝,在那個年代,一個亞洲的國際影展竟可以累積出將近百頁的英文報告。我試著收集更多該影展相關資料,但僅找到寥寥數行,只有大部分由香港電影學者寫的簡短評論以及趣聞筆記,除此之外,就沒有關於該影展更有價值的文字了。然而,這個影展集結了來自八個亞洲國家的一百多位導演,包括南韓、日本、香港、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台灣,他們齊聚一堂放映各自的電影作品,也會舉辦論壇,討論區域聯合製片的展望,和分享在學習現代電影拍攝技術上所遭遇到的困境。同時最新的攝影機、錄音設備,和其他各樣拍攝器材,也都在電影設備展中被展出。
更讓我訝異的是,影展主席是由曾被控戰爭罪的日本大映映畫總裁永田雅一(Nagata Masaichi)擔任,好萊塢當時也有派代表與會,除此之外,美國電影協會(MPAA)主席艾瑞克.強斯頓(Eric Johnston)亦曾向影展致上問候並表示為無法出席感到遺憾。1956 年,這一距離太平洋戰爭結束十一年、韓戰停火甚至僅過三年的時刻,我們就看到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南韓、台灣與日本導演們與日本影業代表一起構築反共戰線、討論如何聯合製片,讓人不禁感到困惑。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這件事?以及首先,何為「亞洲電影製片人聯盟」(Federation of 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in Asia)?作為影展籌組組織,他們的資金如何籌措又從何而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沒有人確實清楚這個影展與亞洲電影製片人聯盟。我於是將它放入我電腦的一個檔案夾裡,決定先專心完成博士論文。
2012 年,五年後,我才再度回到對亞洲影展的研究,那時我剛取得博士學位,受聘為密西根大學助理教授。我前往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尋找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的資料,這一基金會我曾於博士論文中簡短提及,是一個總部位於舊金山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待在檔案館的那三天,我很快速地翻閱著關鍵檔案,本不預期能有收穫。結果發現,中情局當時提供了非官方支持,並以「自由」亞洲名義與學者、記者、藝術家結盟,試圖強化美國影響力創造一個反文化(counterculture)。在這之下亞洲基金會於焉形成,可謂為文化冷戰(Cultural Cold War)的產物。當我明白亞洲電影製片人聯盟原來是在永田雅一的協助下由亞洲基金會資金挹注,而亞洲基金會早期活動的主要焦點之一便是電影產業,突然間一切都明朗了起來。亞洲各國電影導演、學者、政治家們在這場精微的拔河中入列,聯手打造一個出於各自需求與利益的聯盟,並最終成為戰後亞洲地區第一個電影產業網絡─這與美國政府為建立霸權與最大化自身利益去串連自由亞洲的意圖,展現出赤裸裸的對照。
2012 至2018 年間,為尋找線索完成研究,我旅行了許多國家與城市,包括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與密西根大學的特殊典藏、香港電影資料館、香港大學圖書館、新加坡國家圖書檔案館、亞洲影片資料館、韓國映像資料院、韓國國家紀錄院、澳洲國家影音資料庫與雪梨國家圖書館。全書完成後最終於2020 年10 月由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列為「世界中的美國」(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系列叢書。韓文版則在2023 年7 月出版。
我很高興我的研究可以來到台灣的學生、研究者以及對亞洲電影文化產業與冷戰歷史感興趣的讀者面前。我從沒想過這本書能被翻譯為中文,因著台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和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願意出版並翻譯此書,它能更深地走入世界與更多台灣讀者相遇。為此我要特別感謝楊子樵博士相信這本書的潛力,啟動翻譯航程將它帶入中文世界。
《電影與文化冷戰》(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是2020年10月當疫情將一切喊停時,於美國首次出版。那時我無法離開新加坡,只能坐在研究室裡透過Zoom,與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義大利、澳洲、香港和台灣,對我的工作成果感到興趣的各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學者和學生們會面。在這些新書分享中,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尤其來自博士班學生,是我當初如何想出要寫這樣一本書。我的研究綜合了電影研究、美國研究、冷戰歷史研究與區域研究等方法,於是相較於這些學門傳統定義下的學術訓練,我的研究顯得較為獨特。另外,如何在許多不同國家、多個圖書館間處理大量檔案素材,也是常被問到的問題。因而當台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請我為中文版書寫序言時,我想台灣讀者或許也會有類似疑問,便藉此機會將這個過程整理給讀者們。
這本書前後花費了十三年,開始於香港並擴展至六個城市,包括紐約、安娜堡、首爾、新加坡與坎培拉。這一切起自我因攻讀紐約大學博士班而待在香港的那六個月,當時我計劃書寫1950至1970年間香港與南韓之間合作製片的歷史。這個題目的靈感來自2004 年釜山影展的特殊回顧單元──「南韓香港聯合製作的年代」(The Age of Korean-Hong Kong Coproduction)。被南韓電影與香港華語電影產業之間獨特的電影交流歷史深深吸引的我,於2007 年夏天抵達香港。那是香港移交後的第十週年,一個混雜了各種期待與焦慮的時期。我待在香港島東面的西灣河──香港電影資料館所在地。我每天去那裡看片,並且在老電影雜誌、政府文件與各種檔案素材裡掘考資料。當時香港電影資料館是一個充滿生氣的地方,香港電影學者們包括已逝的黃愛玲(Wong Ain-ling)、何思穎(Sam Ho)、羅卡(Law Kar)、張建德(Stephen Teo)與高思雅(Roger Garcia),都積極書寫乃至重寫香港電影跨越亞洲、歐美多國的產業網絡歷史,組織學術活動、出版各式書籍與專刊。在他們的慷慨支持下,我有幸能面見並訪談諸多退休導演、製片與影星,讓我博士論文的研究能順利進展。
某次至香港大學圖書館特殊典藏閱覽時,我發現一本古舊的影展手冊,那是1956 年於香港舉辦的第三屆東南亞影展(Southeast Asian Film Festival)。我當時不知道這個影展,它從未在亞洲電影文獻中被提及討論,而我同時也很驚訝,在那個年代,一個亞洲的國際影展竟可以累積出將近百頁的英文報告。我試著收集更多該影展相關資料,但僅找到寥寥數行,只有大部分由香港電影學者寫的簡短評論以及趣聞筆記,除此之外,就沒有關於該影展更有價值的文字了。然而,這個影展集結了來自八個亞洲國家的一百多位導演,包括南韓、日本、香港、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與台灣,他們齊聚一堂放映各自的電影作品,也會舉辦論壇,討論區域聯合製片的展望,和分享在學習現代電影拍攝技術上所遭遇到的困境。同時最新的攝影機、錄音設備,和其他各樣拍攝器材,也都在電影設備展中被展出。
更讓我訝異的是,影展主席是由曾被控戰爭罪的日本大映映畫總裁永田雅一(Nagata Masaichi)擔任,好萊塢當時也有派代表與會,除此之外,美國電影協會(MPAA)主席艾瑞克.強斯頓(Eric Johnston)亦曾向影展致上問候並表示為無法出席感到遺憾。1956 年,這一距離太平洋戰爭結束十一年、韓戰停火甚至僅過三年的時刻,我們就看到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南韓、台灣與日本導演們與日本影業代表一起構築反共戰線、討論如何聯合製片,讓人不禁感到困惑。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這件事?以及首先,何為「亞洲電影製片人聯盟」(Federation of Motion Picture Producers in Asia)?作為影展籌組組織,他們的資金如何籌措又從何而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沒有人確實清楚這個影展與亞洲電影製片人聯盟。我於是將它放入我電腦的一個檔案夾裡,決定先專心完成博士論文。
2012 年,五年後,我才再度回到對亞洲影展的研究,那時我剛取得博士學位,受聘為密西根大學助理教授。我前往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尋找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的資料,這一基金會我曾於博士論文中簡短提及,是一個總部位於舊金山的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待在檔案館的那三天,我很快速地翻閱著關鍵檔案,本不預期能有收穫。結果發現,中情局當時提供了非官方支持,並以「自由」亞洲名義與學者、記者、藝術家結盟,試圖強化美國影響力創造一個反文化(counterculture)。在這之下亞洲基金會於焉形成,可謂為文化冷戰(Cultural Cold War)的產物。當我明白亞洲電影製片人聯盟原來是在永田雅一的協助下由亞洲基金會資金挹注,而亞洲基金會早期活動的主要焦點之一便是電影產業,突然間一切都明朗了起來。亞洲各國電影導演、學者、政治家們在這場精微的拔河中入列,聯手打造一個出於各自需求與利益的聯盟,並最終成為戰後亞洲地區第一個電影產業網絡─這與美國政府為建立霸權與最大化自身利益去串連自由亞洲的意圖,展現出赤裸裸的對照。
2012 至2018 年間,為尋找線索完成研究,我旅行了許多國家與城市,包括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與密西根大學的特殊典藏、香港電影資料館、香港大學圖書館、新加坡國家圖書檔案館、亞洲影片資料館、韓國映像資料院、韓國國家紀錄院、澳洲國家影音資料庫與雪梨國家圖書館。全書完成後最終於2020 年10 月由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列為「世界中的美國」(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系列叢書。韓文版則在2023 年7 月出版。
我很高興我的研究可以來到台灣的學生、研究者以及對亞洲電影文化產業與冷戰歷史感興趣的讀者面前。我從沒想過這本書能被翻譯為中文,因著台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和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願意出版並翻譯此書,它能更深地走入世界與更多台灣讀者相遇。為此我要特別感謝楊子樵博士相信這本書的潛力,啟動翻譯航程將它帶入中文世界。
試閱
導讀
地緣政治的微觀與感官/楊子樵
初次接觸到尚埈一系列關於冷戰亞洲電影的研究,可追溯至2017 年前後。當時我還在柏克萊大學撰寫博士論文,嘗試結合歷史檔案與影像文本分析,重建國民黨冷戰時期宣傳影像的跨媒介環境。為了找資料,我經常開車或搭火車到同樣位於舊金山灣區,距離柏克萊約一小時車程的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也就是尚埈這本著作所倚賴的檔案史料重要館藏地之一。跟尚埈一樣,我經常在安靜的胡佛檔案館內,調閱一箱箱紙本檔案,也開始注意到,當時自己研究的台港冷戰文化宣傳品(小說、電影、畫報、雜誌等)經常跟「福特基金會」、「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等角色曖昧的非政府組織掛上關係。在這段時間,我首次注意到諸如布魯姆(Robert Blum)這類冷戰時期活躍於官方外交、學術界與文化產業界的「亞洲通」,以及隱藏在電影幕後的龐大人流、物流、金流。同時,我讀到了尚埈刊登在《電影史》(Film History)期刊上一篇談「亞洲基金會電影計畫」的論文。這篇論文讓我首次見到英語學界有人試圖處理這個隱蔽的政治與文化網絡,也讓我意識到過往偏重於國族、類型與形式的電影研究大大限制了我們對冷戰期間電影文化生產的理解與想像。
當時英語學界所熟知的「文化冷戰」研究通常偏向以歐美出發的觀點與歷史素材,經常被引用的相關研究不外乎幾位知名著作,如法蘭西絲.桑德斯(Frances Saunders)於2000 年開風氣之先的《文化冷戰》(The Cultural Cold War),研究美國中情局(CIA)如何資助雜誌、音樂表演、藝術展覽等「文化武器」;或是東尼.蕭(Tony Shaw)於2007年的《好萊塢冷戰》(Hollywood’s Cold War),探討政府、影業人員與電影檢查之間的複雜關係。然而,這些開拓領域之作泰半聚焦美國國內政策或面向歐洲的文化宣傳戰場,對於1945 年之後亞洲新興國家之間錯綜複雜的網絡及他們夾在美蘇兩大陣營間的競逐合作卻鮮少著墨。這樣的研究侷限,隨著近幾年各國冷戰檔案解密及國際學術單位合作交流而開始出現了轉機。尤其是,2017 年美國中情局在公眾多年呼籲下,在線上圖書館公開了大約93 萬份庫存機密文件,內容涵蓋了20 世紀40 年代至90 年代,涉及冷戰、韓戰、越戰等事件。此後幾年間,我們開始看到以亞洲觀點出發的冷戰文化史以及電影史書寫。例如,長期耕耘電影史的傅葆石(Poshek Fu)在2019 年與葉曼丰(Man-Fung Yip)合編了英文論文集《冷戰與亞洲電影》(The Cold War and AsianCinemas),書中多位中生代與新生代學者以單篇、個案研究處理亞洲各國冷戰期間的電影產業交流與新興類型。在星、港華語出版界,許維賢的《重繪華語語系版圖:冷戰前後新馬華語電影的文化生產》(2018)以及麥欣恩的《香港電影與新加坡:冷戰時代星港文化連繫1950-1965》(2019)分別透過東南亞華語電影視角,串連起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在1960 年代以前,依循著冷戰邊界所產生電影產業與敘事,兩書集中討論港英殖民地與馬來世界的流通與連帶,對於美國扮演的角色以及台、韓、日等東北亞網絡並無太多探討。一股重探文化冷戰的熱潮似乎在華語學術圈與出版界方興未艾。
在台灣,長期耕耘冷戰報刊文化與文學傳播與翻譯的陳建忠、王梅香、單德興等重要學者在過往幾年內則從「美援文藝體制」的角度探討美新處所支持的現代主義文藝出版,其研究積累豐碩,開拓了冷戰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研究路向。單德興於2022 年出版的《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是此一方向的代表性專書。然而,台灣在美援文藝體制方面的研究,一直以來還是集中火力處理報刊雜誌、翻譯以及文學網絡的問題,對於紙本之外的媒介載體研究相對缺乏。對於生產機制與傳播路徑更加複雜、預算也更加高昂的電影產業,台灣本地研究者目前尚無太多具體研究成果。綜觀以上,學界依然缺乏一部從全球冷戰脈絡出發,直接處理「美國因素」對亞洲電影產業影響的專著。這樣的研究視野與企圖,一直要到2020 年尚埈的《電影與文化冷戰》(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US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在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才真正得到解答與實踐。
尚埈這本企圖與規模都相當宏大的著作,其重點不在於揭露美國文化宣傳組織在戰後東亞如何建立合作或是討論強權如何驅動各國在地協力者,而在於細膩地呈現出冷戰時期反共陣營內部各方勢力合縱連橫的角力過程。本書前半部「第一個網絡」相當精彩地展示1950 年代美國介入亞洲電影產業初期,即便同屬一個陣營的各方也充滿著極大內部衝突與利益矛盾,其運作完全不如外界所想像的平穩順利。例如,美國對亞洲的文化宣傳組織「自由亞洲協會」(CFA),其首任主席艾倫.瓦倫泰(Alan Valentine)的任命過程即充滿來自美方內部的各種雜音與挑戰,而其繼任者布魯姆這類富有亞洲經驗的學者(柏克萊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曾任教於耶魯大學)及他領導改組後的「亞洲基金會」(TAF)則象徵著一批更具亞洲經驗與文化敏感度的區域研究專家在組織內的崛起。組織內的衝突不但可見於內部人士的安排上,也在亞洲國家之間各帶愛恨情仇、甚至懷鬼胎的權力角力上。例如,身為戰敗國的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竟成為戰後主導「東南亞電影製片人聯盟」(FPA)以及「東南亞影展」(亞洲影展的前身)的領導者。其「重返東南亞」的過程也讓其他曾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印尼、馬來西亞、中華民國等會員對其領導正當性產生懷疑,甚至擔心太平洋戰爭時期的「南洋電影協會」與「大東亞電影圈」在戰後借屍還魂。而印尼更在FPA 的成立過程中發難,質疑FPA 對「東南亞」的定義及其排除中國、北韓、緬甸、越南、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家的政治決定。這類重現反共陣營內部人事變動與鬥爭細節的「深描」在本書中俯拾即是,為讀者展示了一幅與大眾印象迥然不同的複雜權力圖景,耐人尋味。
然而本書真正讓我驚豔的,卻是書後半部討論的「第二個網絡」,也就是從1960 年代初期至1970 年代中後期,當美方認定透過影展組織反共勢力效能不佳,逐步淡出的關鍵時期。乍看之下,這似乎代表著美國文化宣傳機構在亞洲的撤退。然而,尚埈在本書中指出,恰恰是在亞洲基金會電影計畫逐漸走下坡時,一個由東亞各國影人為行動主體的新網絡,才得以在前期所建立的「基礎設施」之上發生。李尚埈在此提出了「發展型國家製片廠」(The Developmental State Studio)此一分析觀念,用以詮釋南韓、香港、台灣在1960 年代崛起的電影產業領導人階層─包含了香港的邵逸夫(邵氏)、新加坡的陸運濤(電懋)、南韓的申相玉(申氏)還有台灣的李翰祥(國聯)和龔弘(中影),以及他們透過亞洲影展逐漸形成的橫向連結與合作默契。這一新世代的文化官僚與影業人員,多半由國家單位扶持,但在決策上保有一定自主性,對亞洲市場也具有敏銳判斷與拓展企圖。書中最精彩的例子,當屬南韓申氏影業。申氏一方面利用朴正熙政權的文化保護政策,稱霸韓國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又與香港邵氏形成國際上的技術、產銷合作,並同時賺取進口外語片至韓國的配額。這一獨特的「出口轉內銷」模式與後來韓國影視產業的崛起,恰可形成一有趣的歷史參照。
過往在研究如中影、龔弘以及1960 年代健康寫實主義等官方主導電影時,中文學界重點通常放在政治宣傳與國族身分建構,而缺少跨域比較的視野。本書中對於「第二個網絡」的案例討論,尤其是關於韓國申氏與香港政商影業網絡的深入爬梳,提供中文讀者一個嶄新的視角與參照點。在此作基礎上,作者更進一步提出「亞際文化勞力的分工」(inter-Asian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此一觀察,探討1960、1970年代港產功夫片與李小龍風潮席捲全球,邵氏、嘉禾等影業全力實踐大規模片廠制度,搭配上國際外包與跨國合作模式,大量產製武打、喜劇、警匪等迎合國際市場的電影類型。這彷彿也見證尼克森訪中後冷戰政治的降溫,以及跨境商業產業鏈的大行其道。作者對於1970年代,「亞洲電影網」潰散過程的觀察,也不禁讓人深思所謂地緣政治、市場與影業人員之間的關係,對於目前各國試圖透過Netflix 等OTT平台以「內容產業」擴張影響力的當下,猶有啟發。
本書對於冷戰文化史研究以及電影媒體史提出重大史料發現與原創見解。作者擺脫了過往區域研究常見的框架─以語言種類或是電影美學或類型為系譜的分析框架,改聚焦於以美國反共宣傳、亞洲基金會、亞洲影展以及各國影業人員為核心的宏觀系統性視角。習慣以作者論或影像為分析主體的讀者,一開始或許會不習慣本書所涵蓋的的巨大資訊量與歷史背景。但若能掌握本書基本歷史架構,花點時間熟悉書中所提到幾個關鍵機構與人物,本書將能帶領讀者重返一個又一個精彩歷史現場,或許也能對於當今數位平台當道的影視產業走向,多一份具有歷史縱深的思考。而尚埈本人遊走在韓國、美國、新加坡、香港四地的學術軌跡,除了本書的冷戰影史研究外,目前更兼及對韓國流行影視產業以及港、韓跨國影視交流史。他這十年來的研究軌跡,其實導向的是一個規模宏大的亞際媒介史書寫。過往,學界探討所謂的「亞際連結」或「亞洲連帶」時,習慣性以「左翼跨國主義」作為歷史案例,卻忽略了同樣時空內所謂「右翼陣營」內一樣充滿複雜多元的角力與溢出政治宣傳的創造動能。本書最大的啟發,在於鼓舞我們重新檢視過去有意忽略的檔案資料,並正視其對於當下地緣政治與文化處境的歷史關聯。
2020年我返國加入國立陽明交通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以及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隔年隨即邀請尚埈為師生舉辦以本書為內容的線上講座,引起不少迴響,並牽起我們合作向中文世界介紹本書的念頭。在尚埈與我本人皆投入部分研究經費,加上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深耕經費的慷慨挹注,本書經過多位翻譯、研究助理、出版編輯的大力協助終於完成。而本書的出版,除了呼應陽明交大發展中的冷戰研究群出版計畫,也祈望能為冷戰研究與媒介史研究帶來嶄新的參考視角與研究動能。
地緣政治的微觀與感官/楊子樵
初次接觸到尚埈一系列關於冷戰亞洲電影的研究,可追溯至2017 年前後。當時我還在柏克萊大學撰寫博士論文,嘗試結合歷史檔案與影像文本分析,重建國民黨冷戰時期宣傳影像的跨媒介環境。為了找資料,我經常開車或搭火車到同樣位於舊金山灣區,距離柏克萊約一小時車程的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也就是尚埈這本著作所倚賴的檔案史料重要館藏地之一。跟尚埈一樣,我經常在安靜的胡佛檔案館內,調閱一箱箱紙本檔案,也開始注意到,當時自己研究的台港冷戰文化宣傳品(小說、電影、畫報、雜誌等)經常跟「福特基金會」、「自由亞洲協會」、「亞洲基金會」等角色曖昧的非政府組織掛上關係。在這段時間,我首次注意到諸如布魯姆(Robert Blum)這類冷戰時期活躍於官方外交、學術界與文化產業界的「亞洲通」,以及隱藏在電影幕後的龐大人流、物流、金流。同時,我讀到了尚埈刊登在《電影史》(Film History)期刊上一篇談「亞洲基金會電影計畫」的論文。這篇論文讓我首次見到英語學界有人試圖處理這個隱蔽的政治與文化網絡,也讓我意識到過往偏重於國族、類型與形式的電影研究大大限制了我們對冷戰期間電影文化生產的理解與想像。
當時英語學界所熟知的「文化冷戰」研究通常偏向以歐美出發的觀點與歷史素材,經常被引用的相關研究不外乎幾位知名著作,如法蘭西絲.桑德斯(Frances Saunders)於2000 年開風氣之先的《文化冷戰》(The Cultural Cold War),研究美國中情局(CIA)如何資助雜誌、音樂表演、藝術展覽等「文化武器」;或是東尼.蕭(Tony Shaw)於2007年的《好萊塢冷戰》(Hollywood’s Cold War),探討政府、影業人員與電影檢查之間的複雜關係。然而,這些開拓領域之作泰半聚焦美國國內政策或面向歐洲的文化宣傳戰場,對於1945 年之後亞洲新興國家之間錯綜複雜的網絡及他們夾在美蘇兩大陣營間的競逐合作卻鮮少著墨。這樣的研究侷限,隨著近幾年各國冷戰檔案解密及國際學術單位合作交流而開始出現了轉機。尤其是,2017 年美國中情局在公眾多年呼籲下,在線上圖書館公開了大約93 萬份庫存機密文件,內容涵蓋了20 世紀40 年代至90 年代,涉及冷戰、韓戰、越戰等事件。此後幾年間,我們開始看到以亞洲觀點出發的冷戰文化史以及電影史書寫。例如,長期耕耘電影史的傅葆石(Poshek Fu)在2019 年與葉曼丰(Man-Fung Yip)合編了英文論文集《冷戰與亞洲電影》(The Cold War and AsianCinemas),書中多位中生代與新生代學者以單篇、個案研究處理亞洲各國冷戰期間的電影產業交流與新興類型。在星、港華語出版界,許維賢的《重繪華語語系版圖:冷戰前後新馬華語電影的文化生產》(2018)以及麥欣恩的《香港電影與新加坡:冷戰時代星港文化連繫1950-1965》(2019)分別透過東南亞華語電影視角,串連起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在1960 年代以前,依循著冷戰邊界所產生電影產業與敘事,兩書集中討論港英殖民地與馬來世界的流通與連帶,對於美國扮演的角色以及台、韓、日等東北亞網絡並無太多探討。一股重探文化冷戰的熱潮似乎在華語學術圈與出版界方興未艾。
在台灣,長期耕耘冷戰報刊文化與文學傳播與翻譯的陳建忠、王梅香、單德興等重要學者在過往幾年內則從「美援文藝體制」的角度探討美新處所支持的現代主義文藝出版,其研究積累豐碩,開拓了冷戰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研究路向。單德興於2022 年出版的《從文化冷戰到冷戰文化:《今日世界》的文學傳播與文化政治》是此一方向的代表性專書。然而,台灣在美援文藝體制方面的研究,一直以來還是集中火力處理報刊雜誌、翻譯以及文學網絡的問題,對於紙本之外的媒介載體研究相對缺乏。對於生產機制與傳播路徑更加複雜、預算也更加高昂的電影產業,台灣本地研究者目前尚無太多具體研究成果。綜觀以上,學界依然缺乏一部從全球冷戰脈絡出發,直接處理「美國因素」對亞洲電影產業影響的專著。這樣的研究視野與企圖,一直要到2020 年尚埈的《電影與文化冷戰》(Cinem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USDiploma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Cinema Network)在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才真正得到解答與實踐。
尚埈這本企圖與規模都相當宏大的著作,其重點不在於揭露美國文化宣傳組織在戰後東亞如何建立合作或是討論強權如何驅動各國在地協力者,而在於細膩地呈現出冷戰時期反共陣營內部各方勢力合縱連橫的角力過程。本書前半部「第一個網絡」相當精彩地展示1950 年代美國介入亞洲電影產業初期,即便同屬一個陣營的各方也充滿著極大內部衝突與利益矛盾,其運作完全不如外界所想像的平穩順利。例如,美國對亞洲的文化宣傳組織「自由亞洲協會」(CFA),其首任主席艾倫.瓦倫泰(Alan Valentine)的任命過程即充滿來自美方內部的各種雜音與挑戰,而其繼任者布魯姆這類富有亞洲經驗的學者(柏克萊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曾任教於耶魯大學)及他領導改組後的「亞洲基金會」(TAF)則象徵著一批更具亞洲經驗與文化敏感度的區域研究專家在組織內的崛起。組織內的衝突不但可見於內部人士的安排上,也在亞洲國家之間各帶愛恨情仇、甚至懷鬼胎的權力角力上。例如,身為戰敗國的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竟成為戰後主導「東南亞電影製片人聯盟」(FPA)以及「東南亞影展」(亞洲影展的前身)的領導者。其「重返東南亞」的過程也讓其他曾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印尼、馬來西亞、中華民國等會員對其領導正當性產生懷疑,甚至擔心太平洋戰爭時期的「南洋電影協會」與「大東亞電影圈」在戰後借屍還魂。而印尼更在FPA 的成立過程中發難,質疑FPA 對「東南亞」的定義及其排除中國、北韓、緬甸、越南、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家的政治決定。這類重現反共陣營內部人事變動與鬥爭細節的「深描」在本書中俯拾即是,為讀者展示了一幅與大眾印象迥然不同的複雜權力圖景,耐人尋味。
然而本書真正讓我驚豔的,卻是書後半部討論的「第二個網絡」,也就是從1960 年代初期至1970 年代中後期,當美方認定透過影展組織反共勢力效能不佳,逐步淡出的關鍵時期。乍看之下,這似乎代表著美國文化宣傳機構在亞洲的撤退。然而,尚埈在本書中指出,恰恰是在亞洲基金會電影計畫逐漸走下坡時,一個由東亞各國影人為行動主體的新網絡,才得以在前期所建立的「基礎設施」之上發生。李尚埈在此提出了「發展型國家製片廠」(The Developmental State Studio)此一分析觀念,用以詮釋南韓、香港、台灣在1960 年代崛起的電影產業領導人階層─包含了香港的邵逸夫(邵氏)、新加坡的陸運濤(電懋)、南韓的申相玉(申氏)還有台灣的李翰祥(國聯)和龔弘(中影),以及他們透過亞洲影展逐漸形成的橫向連結與合作默契。這一新世代的文化官僚與影業人員,多半由國家單位扶持,但在決策上保有一定自主性,對亞洲市場也具有敏銳判斷與拓展企圖。書中最精彩的例子,當屬南韓申氏影業。申氏一方面利用朴正熙政權的文化保護政策,稱霸韓國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又與香港邵氏形成國際上的技術、產銷合作,並同時賺取進口外語片至韓國的配額。這一獨特的「出口轉內銷」模式與後來韓國影視產業的崛起,恰可形成一有趣的歷史參照。
過往在研究如中影、龔弘以及1960 年代健康寫實主義等官方主導電影時,中文學界重點通常放在政治宣傳與國族身分建構,而缺少跨域比較的視野。本書中對於「第二個網絡」的案例討論,尤其是關於韓國申氏與香港政商影業網絡的深入爬梳,提供中文讀者一個嶄新的視角與參照點。在此作基礎上,作者更進一步提出「亞際文化勞力的分工」(inter-Asian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r)此一觀察,探討1960、1970年代港產功夫片與李小龍風潮席捲全球,邵氏、嘉禾等影業全力實踐大規模片廠制度,搭配上國際外包與跨國合作模式,大量產製武打、喜劇、警匪等迎合國際市場的電影類型。這彷彿也見證尼克森訪中後冷戰政治的降溫,以及跨境商業產業鏈的大行其道。作者對於1970年代,「亞洲電影網」潰散過程的觀察,也不禁讓人深思所謂地緣政治、市場與影業人員之間的關係,對於目前各國試圖透過Netflix 等OTT平台以「內容產業」擴張影響力的當下,猶有啟發。
本書對於冷戰文化史研究以及電影媒體史提出重大史料發現與原創見解。作者擺脫了過往區域研究常見的框架─以語言種類或是電影美學或類型為系譜的分析框架,改聚焦於以美國反共宣傳、亞洲基金會、亞洲影展以及各國影業人員為核心的宏觀系統性視角。習慣以作者論或影像為分析主體的讀者,一開始或許會不習慣本書所涵蓋的的巨大資訊量與歷史背景。但若能掌握本書基本歷史架構,花點時間熟悉書中所提到幾個關鍵機構與人物,本書將能帶領讀者重返一個又一個精彩歷史現場,或許也能對於當今數位平台當道的影視產業走向,多一份具有歷史縱深的思考。而尚埈本人遊走在韓國、美國、新加坡、香港四地的學術軌跡,除了本書的冷戰影史研究外,目前更兼及對韓國流行影視產業以及港、韓跨國影視交流史。他這十年來的研究軌跡,其實導向的是一個規模宏大的亞際媒介史書寫。過往,學界探討所謂的「亞際連結」或「亞洲連帶」時,習慣性以「左翼跨國主義」作為歷史案例,卻忽略了同樣時空內所謂「右翼陣營」內一樣充滿複雜多元的角力與溢出政治宣傳的創造動能。本書最大的啟發,在於鼓舞我們重新檢視過去有意忽略的檔案資料,並正視其對於當下地緣政治與文化處境的歷史關聯。
2020年我返國加入國立陽明交通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以及文化研究國際中心,隔年隨即邀請尚埈為師生舉辦以本書為內容的線上講座,引起不少迴響,並牽起我們合作向中文世界介紹本書的念頭。在尚埈與我本人皆投入部分研究經費,加上文化研究國際中心深耕經費的慷慨挹注,本書經過多位翻譯、研究助理、出版編輯的大力協助終於完成。而本書的出版,除了呼應陽明交大發展中的冷戰研究群出版計畫,也祈望能為冷戰研究與媒介史研究帶來嶄新的參考視角與研究動能。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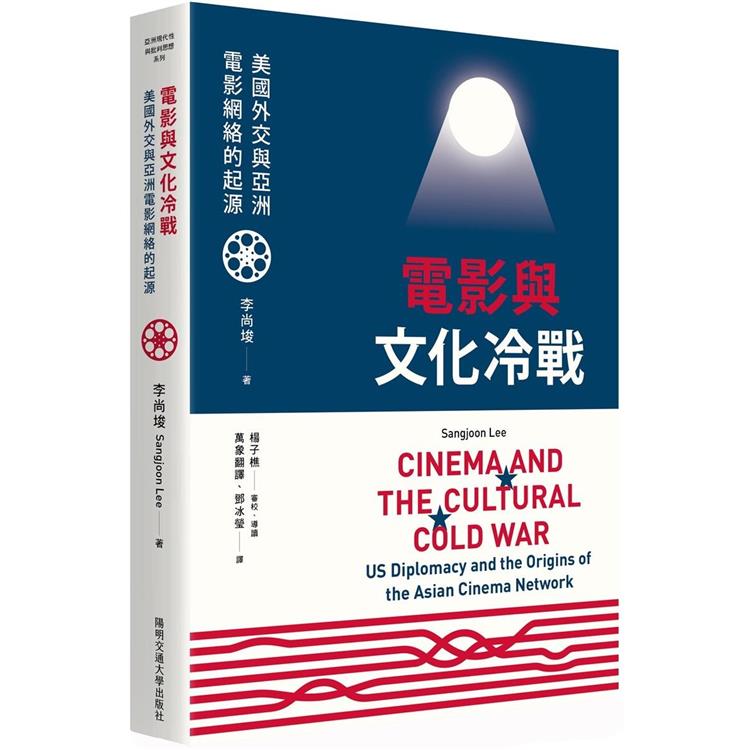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