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成長小說」以少年啟蒙的過程為書寫的主題,在中國古典便能找到,如賈寶玉親眼目睹烏托邦「大觀園」一步步的崩毀;也有將「少年」視為新生命勃發的意象,賦予改革的意義,特別是自晚清以來的「發現少年」與「想像中國」息息相關。
編選《臺灣成長小說選》是以理想的幻滅、成長的代價為主調,少年從帶有夢幻幸福氣質的青春陡然進入生硬的現實,可能懂了一些什麼,也可能增添更多迷惑,放棄了什麼,也明瞭了自我的無能為力。這是觀察「臺灣成長小說史」,與回到生活現場,觀察本地青年「轉大人」的完整構圖。
本書特色
觀察「臺灣成長小說史」
回到生活現場,觀察本地青年「轉大人」的完整構圖。
編選《臺灣成長小說選》是以理想的幻滅、成長的代價為主調,少年從帶有夢幻幸福氣質的青春陡然進入生硬的現實,可能懂了一些什麼,也可能增添更多迷惑,放棄了什麼,也明瞭了自我的無能為力。這是觀察「臺灣成長小說史」,與回到生活現場,觀察本地青年「轉大人」的完整構圖。
本書特色
觀察「臺灣成長小說史」
回到生活現場,觀察本地青年「轉大人」的完整構圖。
目錄
楊佳嫻 序論
楊逵 種地瓜
葉石濤 玉皇大帝的生日
郭松棻 雪盲
王文興 命運的跡線
李渝 菩提樹
夏烈 白門再見
李昂 花季
吳錦發 春秋茶室
朱天文 小畢的故事
郭箏 彈子王
袁哲生 西北雨
駱以軍 ㄩ∕川端
張惠菁 哭渦
許榮哲 那年夏天,美濃
伊格言 鬼甕
曹麗娟 童女之舞
胡淑雯 奸細
楊逵 種地瓜
葉石濤 玉皇大帝的生日
郭松棻 雪盲
王文興 命運的跡線
李渝 菩提樹
夏烈 白門再見
李昂 花季
吳錦發 春秋茶室
朱天文 小畢的故事
郭箏 彈子王
袁哲生 西北雨
駱以軍 ㄩ∕川端
張惠菁 哭渦
許榮哲 那年夏天,美濃
伊格言 鬼甕
曹麗娟 童女之舞
胡淑雯 奸細
序/導讀
序論
主編 楊佳嫻
壹、
〈春秋茶室〉中使少年發仔和讀者同感震撼的,是被輾轉賣為娼妓的原住民少女林美麗所說的一句話:「我已經認命了。」作者吳錦發描寫了這句話是如何地使愛慕與悲憐著林美麗的少年,終於窺見了所謂命運,不可解的現實世界和成人的醜陋;小說最後彷彿變得雲淡風清,然而發仔早已經不是那個愛鬧的逃學孩子了,他心中已存在著記憶與悲哀的種子。
廣義的「成長小說」以少年啟蒙過程為書寫主題,在中國古典便能找到,讀者最熟悉的大抵是賈寶玉如何目睹青春烏托邦「大觀園」一步步的崩毀,乃至體歷人間劫難,覺悟真假,向佛道尋求脫解--著重的不是發展,而是覺悟,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地認識世界、發見時間與現實之本質的悲劇性。論述現代「成長小說」或「啟蒙小說」時,往往會追溯到兩個歷史點,一是十八世紀康德在〈何謂啟蒙〉中揭示的,所謂啟蒙,便是走出無他人之教養監護便無法使用一己之思索能力的未成年狀態,當然,同時也必須具備使用這種自我思維能力的自由;另一則是十九世紀歌德創作的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創造了德文中所說Bildungsroman的小說類型,主要呈現的是少年人格的成長、世界觀的定型,尤重於文化教養、自我教育的義涵,屬於狹義的「成長小說」--歌德與康德筆下,無論文學或思想,皆涵藏著發展的、向上的、正面的意義。
拿「少年」當作新生命勃發的意象,且賦予改革變化、救亡圖存的意義,「發現少年」與「想像中國」息息相關,自晚清以來可見端倪[1]﹔然而,當「少年」進入現代小說創作,特別是在台灣文學的範疇中,持續和國族寓言糾纏不已,更進而在「台灣」抑或「中國」的矛盾中徘徊[2],複雜化了成長小說可能帶來的被詮釋面向﹔其中可能是白先勇《孽子》中對於那群來自失去父親的家庭、血緣上涵蓋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日本人等的「青春鳥」在融合與茁壯上的期許,讓他們勇敢地一一踏上追尋父親/自我的路途,也可能是張大春筆下逃家逃學的大頭春,通過週記形式,透過一個未成年的孩子的眼光去窺看現實世界的傾斜處,在胡說八道的自以為是中,包含著純真和世故。
本書選文的過程中,採取廣義的角度;但是,早有識者追蹤台灣成長小說寫作情況時,即指出當中含有強烈的悲劇傾向,樂觀的、以人文的正向發展為主旨的,少之又少。本書最後擇定的篇章,包括同意入選與不同意入選的,歸納起來發現,絕大多數都以人間的悲哀、理想的幻滅作為成長的代價,且強烈地以感性作為小說驅動的力量,少年在淚水中成長,放棄了一些什麼,懂得了一些什麼,明瞭了某些事務上自我的無能為力,對於自我和現實的認識,乃是在於發現裂縫,而非與群體社會達到更好的接合。
由於期望能在選本能呈現各個不同世代小說家在成長小說書寫上的同質與異質,因為兼顧戰後日治時代出生到所謂「六年級」的一代;選本本就具有經典意義建立的意味,選擇篇章上也往往優先考慮藝術歷程與成就較為成熟的作家,本書自不例外,卻也同時希望納入較多的年輕作者;再者,以成長為主題的台灣小說不少,篇章的擇定中自然在各種客觀考量之下,不免還透露著選者的主觀品味與愛好,但仍力求在主客觀之間平衡。因此,選本最後呈現的,便是自楊逵、葉石濤、王文興等早已備受肯定的老作家,到張惠菁、許榮哲、伊格言等近年來崛起的年輕小說家;除了因私人理由不同意被選入的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童偉格〈我〉之外,楊青矗〈在室男〉鮮活動人,勇敢的酒家姑娘「大目仔」令人印象深刻,以篇幅太長而割愛,我更感遺憾的是以去世的顧肇森〈張偉〉一篇,此篇完成於八十年代,是白先勇《孽子》之外較早的明確以男同志生活與心境成長為主題的小說,筆觸俐落,在論述上卻較少受到注意,近來雖有陳雨航先生策劃選書,將刊有〈張偉〉的《貓臉的歲月》一書重新出版,仍希望能在選本中鄭重提出,惟因為聯絡顧肇森家人不易,故而作罷。另外,如白先勇的諸篇作品,不少皆集中於成長的議題,尤其《孽子》透過城市地景、父子關係來描述邊緣族群,亦有較為積極正面的自我成長意義,只是白先勇的作品流布極廣,閱者已眾,此處不再添花。
以下分成兩個小節,概述本書所選各家特色與其對於成長、啟蒙議題的發揮,書內另附有各家小傳與簡評,簡評中已提及處,這裡不再贅述。
貳、
選本從日治時代作家開始,自然是希望不拘泥於「戰後」「日治」的普遍文學史分期,而以與成長主題有關的現代小說一脈貫串,同時彰顯作家特色與主要關懷。楊逵作品為日治時代完成,〈種地瓜〉表現出兒子立定意志、體會父親心情而願意挑起生活擔子﹔比他晚二十年出生、經歷日治時代後半期的葉石濤,自十六歲發表第一篇小說以來,除了羈獄前後幾年,均持續發表創作,小說與評論皆豐[3],尤其對於塑造本土文學意識與價值、藉著書寫勾勒台灣五十年代風貌,具有貢獻,〈玉皇大帝的生日〉也有這種味道。這兩位作家的文筆較為質樸,而由於所處時代與文學發展的關係,葉石濤在文學技巧上又較楊逵前進。
王文興以苦行緩慢的書寫與形式的執著著稱於台灣文學史,一部前後長達二十餘年才完成的《背海的人》,以及符號、形式的曲折,被年輕一代文藝工作者稱為「文學史的驕傲,排版工人的惡夢」[4]。在眾所關注的《家變》、《背海的人》之外,集結了大學時代作品的《十五篇小說》或許較不為一般讀者熟悉,但這些即是王文興發表過的僅十五個短篇小說,且有不少可就成長、啟蒙角度切入討論者。本書選取〈命運的跡線〉,講一名憂慮自身康健的少年,如何在同儕流行的算命話題中加倍地感覺受到傷害,陷入強大的憂鬱,而以刀片劃傷手掌,意欲延伸過短的壽命線,而幾乎真正地縮減了性命--孱弱敏感的少年,王文興另一篇〈玩具手槍〉亦曾塑造過一個年紀較長的類似角色,他們都極為在意身體健康與其帶來的自卑,也往往陷入同儕的嘲笑中,擴大了那些嘲笑的效應,在內心迴響成更大的威脅,逼迫少年作出極端的行為。〈命運的跡線〉中的少年以未來的詩人自命,期許自我能以文字闖出一番事業,可是那醜陋孩子的算命結果,卻宣布他只能活三十歲,則所有的努力或將成為枉然罷,則再多的努力與想像都敵不過宿命,過份的執著造成偏激的行徑,傷口痊癒後留下了疤痕,「看來就跟那真的壽命線一模一樣」,像一條銘刻在身上的,永恆的反諷。
以〈春秋茶室〉聞名的吳錦發,在這篇得獎小說中,以山花陳美麗、少年阿發仔以及家裡開茶室的好友富林為主角,透過發仔的眼睛,描述少年之間歡樂的友誼、對成年人的不屑和懼怕、情竇初開的心境;遭遇悲慘的原住民少女陳美麗從富林口中描述出的形象,到實際窺看得的形貌,深植發仔腦中,逐漸成為夢中女神般的存在,而在現實中女神卻是被迫風塵的。和愛情與欲望同時萌發的,是發仔同時揣度著富林營救、看顧林美麗的心情,遠遠地看著成人如何施展心理與行動上的壓力,如何因為一股年少意氣與自己未必真正懂得的愛欲的驅使,而挺身對抗現實的橫暴;這驅使的力量,可以說是非理性的,而是出自於本善與感性,彷彿完成了營救,便不枉青春,對得起友情與愛情。然而,陳美麗對於雷雨夜的懼怕、藏匿時的飢餓寒暖、車錢等等,是可以解決的,社會大環境卻不是兩個少年能轉動乾坤的,陳美麗被抓回茶室了,失去了和命運奮鬥的激情,小說主角透過失望與無力感而成長--
……我的年齡還無法明白什麼叫做「命」,她,陳美麗和我一樣小,她一定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命」吧?
「我已經認命了﹗」
但她為什麼要這麼說呢?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心裡在想些什麼?她這句話是從哪裡學來的呢?小說嗎?廣播劇嗎?
「我已經認命了!」
她一定不知道,她這句話不但擊敗了她自己,連帶的,也擊敗了我年輕的愛、夢及公義之心……。
李永平曾如此評論:「在體裁上倒是很強有力的三結合……少年的初戀,非常美麗浪漫的故事,然後一個小鎮的生活,然後社會問題,現實社會問題,販賣人口的問題……。」[5]清楚說明了〈春秋茶室〉故事魅力的來源,雖然,九十年代以來這樣的故事情節可能在小說、電視電影與某些戲劇性的新聞報導中被熟化了,年輕一代讀者所受到的衝擊會小一些。不可否認的是,〈春秋茶室〉不以嚴肅的面孔探討社會問題,而以少年情感的生發與挫折做為主軸,大幅增添了小說動人的力量。吳錦發也在序中表表示:「〈春秋茶室〉寫的是我年少時候的激情,我的心理成長歷程」,並明確地自我定義為「成長小說」,乃是主角「在性心理、生理成長過程中所碰到的『事件』,使『我』逐漸省悟到:『我』在生命中的『位格』在哪裡,以及『我』在整個生存的大社會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是什麼……。」[6]
「成長小說」既然寫的是成長歷程,不免摻入作者個人經驗,特別是台灣的「成長小說」都帶有相當強的情感取向和悲劇性,描摹少年困厄、惆悵心境時,相較其他類型的作品,更多地借鏡於自我是書寫過程之必然。
〈春秋茶室〉末了,發仔跑到茶室送客出門的陳美麗面前,以自我傷害表達稚幼的愛情,這個動作可和王文興〈命運的跡線〉並觀,證明愛情,或延長人壽,其實為的都是落實自我生命的重量。然而,〈命運的跡線〉著力描繪的,屬於少年內心隱微的糾結,那自我認知的歧錯,卻是〈春秋茶室〉沒有的﹔王文興往心理描寫發展,同時也涉及了「家」所不能解決與滿足的個人的裂縫,吳錦發則把視野延伸到現實面,各有所優。〈春秋茶室〉的帶血腥氣的愛情啟發,若跟夏烈〈白門再見〉相較,則傳說中的「白門」與成長中的少年們的關係還是稍微含有喜劇成分的,「白門」是女神,也是友情的聯繫、青春的證明,成年後那出其不意卻又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隱隱可以想見的結尾,不禁使得曾經經歷輕狂歲月的讀者們都泛出微笑來﹔和李昂〈花季〉相較,
主編 楊佳嫻
壹、
〈春秋茶室〉中使少年發仔和讀者同感震撼的,是被輾轉賣為娼妓的原住民少女林美麗所說的一句話:「我已經認命了。」作者吳錦發描寫了這句話是如何地使愛慕與悲憐著林美麗的少年,終於窺見了所謂命運,不可解的現實世界和成人的醜陋;小說最後彷彿變得雲淡風清,然而發仔早已經不是那個愛鬧的逃學孩子了,他心中已存在著記憶與悲哀的種子。
廣義的「成長小說」以少年啟蒙過程為書寫主題,在中國古典便能找到,讀者最熟悉的大抵是賈寶玉如何目睹青春烏托邦「大觀園」一步步的崩毀,乃至體歷人間劫難,覺悟真假,向佛道尋求脫解--著重的不是發展,而是覺悟,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地認識世界、發見時間與現實之本質的悲劇性。論述現代「成長小說」或「啟蒙小說」時,往往會追溯到兩個歷史點,一是十八世紀康德在〈何謂啟蒙〉中揭示的,所謂啟蒙,便是走出無他人之教養監護便無法使用一己之思索能力的未成年狀態,當然,同時也必須具備使用這種自我思維能力的自由;另一則是十九世紀歌德創作的小說《威廉˙邁斯特的學習年代》,創造了德文中所說Bildungsroman的小說類型,主要呈現的是少年人格的成長、世界觀的定型,尤重於文化教養、自我教育的義涵,屬於狹義的「成長小說」--歌德與康德筆下,無論文學或思想,皆涵藏著發展的、向上的、正面的意義。
拿「少年」當作新生命勃發的意象,且賦予改革變化、救亡圖存的意義,「發現少年」與「想像中國」息息相關,自晚清以來可見端倪[1]﹔然而,當「少年」進入現代小說創作,特別是在台灣文學的範疇中,持續和國族寓言糾纏不已,更進而在「台灣」抑或「中國」的矛盾中徘徊[2],複雜化了成長小說可能帶來的被詮釋面向﹔其中可能是白先勇《孽子》中對於那群來自失去父親的家庭、血緣上涵蓋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日本人等的「青春鳥」在融合與茁壯上的期許,讓他們勇敢地一一踏上追尋父親/自我的路途,也可能是張大春筆下逃家逃學的大頭春,通過週記形式,透過一個未成年的孩子的眼光去窺看現實世界的傾斜處,在胡說八道的自以為是中,包含著純真和世故。
本書選文的過程中,採取廣義的角度;但是,早有識者追蹤台灣成長小說寫作情況時,即指出當中含有強烈的悲劇傾向,樂觀的、以人文的正向發展為主旨的,少之又少。本書最後擇定的篇章,包括同意入選與不同意入選的,歸納起來發現,絕大多數都以人間的悲哀、理想的幻滅作為成長的代價,且強烈地以感性作為小說驅動的力量,少年在淚水中成長,放棄了一些什麼,懂得了一些什麼,明瞭了某些事務上自我的無能為力,對於自我和現實的認識,乃是在於發現裂縫,而非與群體社會達到更好的接合。
由於期望能在選本能呈現各個不同世代小說家在成長小說書寫上的同質與異質,因為兼顧戰後日治時代出生到所謂「六年級」的一代;選本本就具有經典意義建立的意味,選擇篇章上也往往優先考慮藝術歷程與成就較為成熟的作家,本書自不例外,卻也同時希望納入較多的年輕作者;再者,以成長為主題的台灣小說不少,篇章的擇定中自然在各種客觀考量之下,不免還透露著選者的主觀品味與愛好,但仍力求在主客觀之間平衡。因此,選本最後呈現的,便是自楊逵、葉石濤、王文興等早已備受肯定的老作家,到張惠菁、許榮哲、伊格言等近年來崛起的年輕小說家;除了因私人理由不同意被選入的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童偉格〈我〉之外,楊青矗〈在室男〉鮮活動人,勇敢的酒家姑娘「大目仔」令人印象深刻,以篇幅太長而割愛,我更感遺憾的是以去世的顧肇森〈張偉〉一篇,此篇完成於八十年代,是白先勇《孽子》之外較早的明確以男同志生活與心境成長為主題的小說,筆觸俐落,在論述上卻較少受到注意,近來雖有陳雨航先生策劃選書,將刊有〈張偉〉的《貓臉的歲月》一書重新出版,仍希望能在選本中鄭重提出,惟因為聯絡顧肇森家人不易,故而作罷。另外,如白先勇的諸篇作品,不少皆集中於成長的議題,尤其《孽子》透過城市地景、父子關係來描述邊緣族群,亦有較為積極正面的自我成長意義,只是白先勇的作品流布極廣,閱者已眾,此處不再添花。
以下分成兩個小節,概述本書所選各家特色與其對於成長、啟蒙議題的發揮,書內另附有各家小傳與簡評,簡評中已提及處,這裡不再贅述。
貳、
選本從日治時代作家開始,自然是希望不拘泥於「戰後」「日治」的普遍文學史分期,而以與成長主題有關的現代小說一脈貫串,同時彰顯作家特色與主要關懷。楊逵作品為日治時代完成,〈種地瓜〉表現出兒子立定意志、體會父親心情而願意挑起生活擔子﹔比他晚二十年出生、經歷日治時代後半期的葉石濤,自十六歲發表第一篇小說以來,除了羈獄前後幾年,均持續發表創作,小說與評論皆豐[3],尤其對於塑造本土文學意識與價值、藉著書寫勾勒台灣五十年代風貌,具有貢獻,〈玉皇大帝的生日〉也有這種味道。這兩位作家的文筆較為質樸,而由於所處時代與文學發展的關係,葉石濤在文學技巧上又較楊逵前進。
王文興以苦行緩慢的書寫與形式的執著著稱於台灣文學史,一部前後長達二十餘年才完成的《背海的人》,以及符號、形式的曲折,被年輕一代文藝工作者稱為「文學史的驕傲,排版工人的惡夢」[4]。在眾所關注的《家變》、《背海的人》之外,集結了大學時代作品的《十五篇小說》或許較不為一般讀者熟悉,但這些即是王文興發表過的僅十五個短篇小說,且有不少可就成長、啟蒙角度切入討論者。本書選取〈命運的跡線〉,講一名憂慮自身康健的少年,如何在同儕流行的算命話題中加倍地感覺受到傷害,陷入強大的憂鬱,而以刀片劃傷手掌,意欲延伸過短的壽命線,而幾乎真正地縮減了性命--孱弱敏感的少年,王文興另一篇〈玩具手槍〉亦曾塑造過一個年紀較長的類似角色,他們都極為在意身體健康與其帶來的自卑,也往往陷入同儕的嘲笑中,擴大了那些嘲笑的效應,在內心迴響成更大的威脅,逼迫少年作出極端的行為。〈命運的跡線〉中的少年以未來的詩人自命,期許自我能以文字闖出一番事業,可是那醜陋孩子的算命結果,卻宣布他只能活三十歲,則所有的努力或將成為枉然罷,則再多的努力與想像都敵不過宿命,過份的執著造成偏激的行徑,傷口痊癒後留下了疤痕,「看來就跟那真的壽命線一模一樣」,像一條銘刻在身上的,永恆的反諷。
以〈春秋茶室〉聞名的吳錦發,在這篇得獎小說中,以山花陳美麗、少年阿發仔以及家裡開茶室的好友富林為主角,透過發仔的眼睛,描述少年之間歡樂的友誼、對成年人的不屑和懼怕、情竇初開的心境;遭遇悲慘的原住民少女陳美麗從富林口中描述出的形象,到實際窺看得的形貌,深植發仔腦中,逐漸成為夢中女神般的存在,而在現實中女神卻是被迫風塵的。和愛情與欲望同時萌發的,是發仔同時揣度著富林營救、看顧林美麗的心情,遠遠地看著成人如何施展心理與行動上的壓力,如何因為一股年少意氣與自己未必真正懂得的愛欲的驅使,而挺身對抗現實的橫暴;這驅使的力量,可以說是非理性的,而是出自於本善與感性,彷彿完成了營救,便不枉青春,對得起友情與愛情。然而,陳美麗對於雷雨夜的懼怕、藏匿時的飢餓寒暖、車錢等等,是可以解決的,社會大環境卻不是兩個少年能轉動乾坤的,陳美麗被抓回茶室了,失去了和命運奮鬥的激情,小說主角透過失望與無力感而成長--
……我的年齡還無法明白什麼叫做「命」,她,陳美麗和我一樣小,她一定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命」吧?
「我已經認命了﹗」
但她為什麼要這麼說呢?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心裡在想些什麼?她這句話是從哪裡學來的呢?小說嗎?廣播劇嗎?
「我已經認命了!」
她一定不知道,她這句話不但擊敗了她自己,連帶的,也擊敗了我年輕的愛、夢及公義之心……。
李永平曾如此評論:「在體裁上倒是很強有力的三結合……少年的初戀,非常美麗浪漫的故事,然後一個小鎮的生活,然後社會問題,現實社會問題,販賣人口的問題……。」[5]清楚說明了〈春秋茶室〉故事魅力的來源,雖然,九十年代以來這樣的故事情節可能在小說、電視電影與某些戲劇性的新聞報導中被熟化了,年輕一代讀者所受到的衝擊會小一些。不可否認的是,〈春秋茶室〉不以嚴肅的面孔探討社會問題,而以少年情感的生發與挫折做為主軸,大幅增添了小說動人的力量。吳錦發也在序中表表示:「〈春秋茶室〉寫的是我年少時候的激情,我的心理成長歷程」,並明確地自我定義為「成長小說」,乃是主角「在性心理、生理成長過程中所碰到的『事件』,使『我』逐漸省悟到:『我』在生命中的『位格』在哪裡,以及『我』在整個生存的大社會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是什麼……。」[6]
「成長小說」既然寫的是成長歷程,不免摻入作者個人經驗,特別是台灣的「成長小說」都帶有相當強的情感取向和悲劇性,描摹少年困厄、惆悵心境時,相較其他類型的作品,更多地借鏡於自我是書寫過程之必然。
〈春秋茶室〉末了,發仔跑到茶室送客出門的陳美麗面前,以自我傷害表達稚幼的愛情,這個動作可和王文興〈命運的跡線〉並觀,證明愛情,或延長人壽,其實為的都是落實自我生命的重量。然而,〈命運的跡線〉著力描繪的,屬於少年內心隱微的糾結,那自我認知的歧錯,卻是〈春秋茶室〉沒有的﹔王文興往心理描寫發展,同時也涉及了「家」所不能解決與滿足的個人的裂縫,吳錦發則把視野延伸到現實面,各有所優。〈春秋茶室〉的帶血腥氣的愛情啟發,若跟夏烈〈白門再見〉相較,則傳說中的「白門」與成長中的少年們的關係還是稍微含有喜劇成分的,「白門」是女神,也是友情的聯繫、青春的證明,成年後那出其不意卻又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隱隱可以想見的結尾,不禁使得曾經經歷輕狂歲月的讀者們都泛出微笑來﹔和李昂〈花季〉相較,
訂購/退換貨須知
購買須知:
使用金石堂電子書服務即為同意金石堂電子書服務條款。
電子書分為「金石堂(線上閱讀+APP)」及「Readmoo(兌換碼)」兩種:
- 請至會員中心→電子書服務「我的e書櫃」領取複製『兌換碼』至電子書服務商Readmoo進行兌換。
退換貨須知:
- 因版權保護,您在金石堂所購買的電子書僅能以金石堂專屬的閱讀軟體開啟閱讀,無法以其他閱讀器或直接下載檔案。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不受「網購服務需提供七日鑑賞期」的限制。為維護您的權益,建議您先使用「試閱」功能後再付款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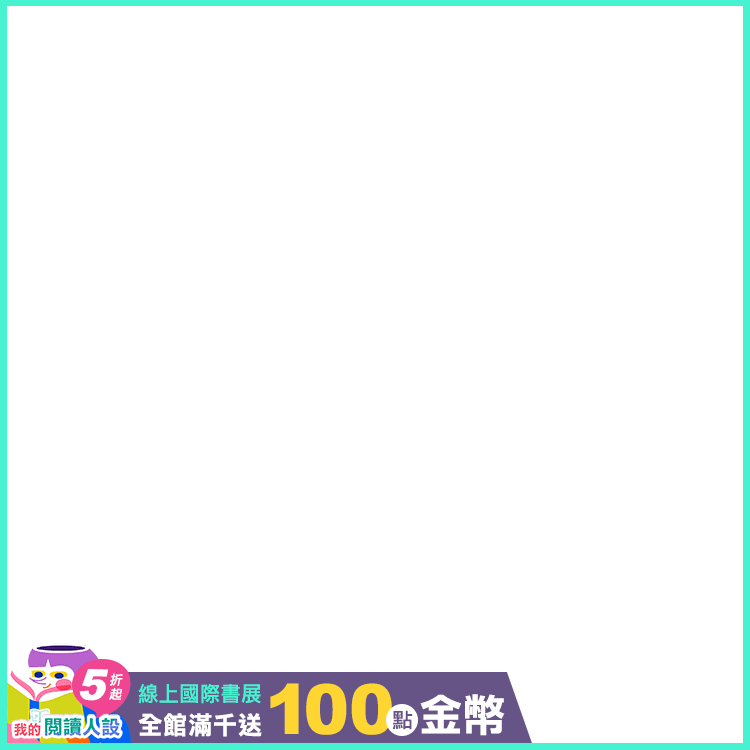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