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先自己自己,再一起一起
內容簡介
一位太魯閣族人寫給每一位臺灣人的邀請信
讓知識從自己的文化裡長出來,
不斷地回到歷史與生活裡去看,不斷地去對話……
一個太魯閣族女兒「回家」的故事。回到自己的經驗去尋找,回到家族裡的故事去尋找,把會呼吸的歷史找回來。
「媽,為什麼我是太魯閣族?」當時十七歲的我哭著問。
「我不要當太魯閣族,把我的血抽掉!」我說。
「妳就是太魯閣族呀。」媽媽把手放在我手上,這麼回我。
Yabung.Haning 是一九八〇年代出生的太魯閣族女性,在接受現代高等教育後,也接受了許多外來對於自己族群的詮釋及標籤,使得她覺得書讀得越高卻離部落越遠。
為了打破困境,她透過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父母親、祖父母輩及家族成員所經歷的遷移與勞動史,以家族口述出發,並與太魯閣族青年社群彼此的家庭故事對話,交織詮釋出當代太魯閣族家庭的樣貌,希望為臺灣社會提供理解太魯閣族社會的方式。
原來,要能看懂自身族群議題及標籤,是無法透過國外的知識研究、臺灣社會的學術理論,而是得從自身家庭及個人情緒來讀懂族群面臨的問題。重要的是必須由我們自己長出的聲音來詮釋自己。無論你是不是原住民族,都可以用這種最庶民的方式來理解自己。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專文推薦
Ciwang Teyra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Liglav A-wu /作家
余桂榕/延平鄉立圖書館館長
官大偉/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益仁/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浦忠成/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程廷Apyang Imiq /作家
賀照緹/導演
廉兮/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博班副教授暨多元文化教育中心主任
羅素玫/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一起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序)
太魯閣語很常使用pusu,語譯為「根」,物理形體的pusu qhuni指的是「樹根」,抽象邏輯的pusu kari是「語言的本意」,還有pusu gaya表示「文化的真諦」。
Yabung嘗試探討的 pusu kingal ruwan sapah就是「一個家庭裡面的根」。
Yabung像一個挖土的payi,往自己家裡挖,文字愈挖愈坦露,明明私人,卻帶來令人振奮的太魯閣族青年「共感」,私密卻又集體。
最終只想知道,我們究竟為什麼長成這個樣子?
──程廷Apyang Imiq/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得獎作家
看到雅雯的勇氣,一個人遁入非原民的婚姻家庭世界,一個人投入太魯閣族人的現代議題,再帶著一群人互為激盪與實踐,絕對是因為寛容的愛及對族群的愛,鍥而不捨地希望尋找與社會對話的出口。而她的勇氣發聲將讓此愛永不止息。有幸看到本書的出版,讓更多原住民世界的議題,漫漫現形。
──余桂榕/延平鄉立圖書館館長
Yabung.Haning,一個花蓮秀林鄉太魯閣族優秀的女孩,她與她的家族的成長歷程就是一部臺灣原住民族被殖民的歷史創傷圖鑑……這本書記錄著一位成功進入主流社會的原住民女孩,嘗試回到部落自己的根,尋找屬於原住民社會工作者自己的知識生成之路。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讓知識從自己的文化裡長出來,
不斷地回到歷史與生活裡去看,不斷地去對話……
一個太魯閣族女兒「回家」的故事。回到自己的經驗去尋找,回到家族裡的故事去尋找,把會呼吸的歷史找回來。
「媽,為什麼我是太魯閣族?」當時十七歲的我哭著問。
「我不要當太魯閣族,把我的血抽掉!」我說。
「妳就是太魯閣族呀。」媽媽把手放在我手上,這麼回我。
Yabung.Haning 是一九八〇年代出生的太魯閣族女性,在接受現代高等教育後,也接受了許多外來對於自己族群的詮釋及標籤,使得她覺得書讀得越高卻離部落越遠。
為了打破困境,她透過回顧自己的成長經歷,父母親、祖父母輩及家族成員所經歷的遷移與勞動史,以家族口述出發,並與太魯閣族青年社群彼此的家庭故事對話,交織詮釋出當代太魯閣族家庭的樣貌,希望為臺灣社會提供理解太魯閣族社會的方式。
原來,要能看懂自身族群議題及標籤,是無法透過國外的知識研究、臺灣社會的學術理論,而是得從自身家庭及個人情緒來讀懂族群面臨的問題。重要的是必須由我們自己長出的聲音來詮釋自己。無論你是不是原住民族,都可以用這種最庶民的方式來理解自己。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專文推薦
Ciwang Teyra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Liglav A-wu /作家
余桂榕/延平鄉立圖書館館長
官大偉/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益仁/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浦忠成/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程廷Apyang Imiq /作家
賀照緹/導演
廉兮/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博班副教授暨多元文化教育中心主任
羅素玫/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一起推薦(依姓名筆畫排序)
太魯閣語很常使用pusu,語譯為「根」,物理形體的pusu qhuni指的是「樹根」,抽象邏輯的pusu kari是「語言的本意」,還有pusu gaya表示「文化的真諦」。
Yabung嘗試探討的 pusu kingal ruwan sapah就是「一個家庭裡面的根」。
Yabung像一個挖土的payi,往自己家裡挖,文字愈挖愈坦露,明明私人,卻帶來令人振奮的太魯閣族青年「共感」,私密卻又集體。
最終只想知道,我們究竟為什麼長成這個樣子?
──程廷Apyang Imiq/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得獎作家
看到雅雯的勇氣,一個人遁入非原民的婚姻家庭世界,一個人投入太魯閣族人的現代議題,再帶著一群人互為激盪與實踐,絕對是因為寛容的愛及對族群的愛,鍥而不捨地希望尋找與社會對話的出口。而她的勇氣發聲將讓此愛永不止息。有幸看到本書的出版,讓更多原住民世界的議題,漫漫現形。
──余桂榕/延平鄉立圖書館館長
Yabung.Haning,一個花蓮秀林鄉太魯閣族優秀的女孩,她與她的家族的成長歷程就是一部臺灣原住民族被殖民的歷史創傷圖鑑……這本書記錄著一位成功進入主流社會的原住民女孩,嘗試回到部落自己的根,尋找屬於原住民社會工作者自己的知識生成之路。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目錄
推薦序 讓說故事再度成為原住民族知識生產的起點/王增勇
楔子
第一章 我是誰
第二章 我的成長與情緒
第三章 我族群文化的養成與矛盾
第四章 我的爸爸
第五章 我的媽媽
第六章 視框移動
第七章 看懂
第八章 一個人的故事與一群人的故事
第九章 談知識
第十章 持續對話
參考書目
楔子
第一章 我是誰
第二章 我的成長與情緒
第三章 我族群文化的養成與矛盾
第四章 我的爸爸
第五章 我的媽媽
第六章 視框移動
第七章 看懂
第八章 一個人的故事與一群人的故事
第九章 談知識
第十章 持續對話
參考書目
序/導讀
【推薦序】
讓說故事再度成為原住民族知識生產的起點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雅崩(Yabung.Haning)是我的指導學生,但我從她身上學到很多,尤其她幫助我看到自己的學術訓練如何成為文化殖民原住民族的工具,這讓我對自以為傲的學術訓練學會謙虛。
認識雅崩,是在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的聚會上,她是個充滿熱情與活力的女孩。那時我知道她曾是慈濟社工所的碩士生,但遲遲沒完成論文。有一次她分享來到原照盟進行原住民長照倡議的由來,她說:「我一方面透過太魯閣學青會投入族群工作;另一方面,我在研究所進行長照研究。但我從來沒有把原住民跟長照連結起來,原來我可以從原住民的觀點分析長照!」
口直心快的雅崩很幽默地說出她作為原住民的生命經驗與她作為研究生的學術研究,彼此之間涇渭分明的區隔,但背後卻深刻地反應出當前的學術知識體制排除原住民族的世界觀,以致於原住民學生無法在學習過程中看見自己族群的身影。
這也成為雅崩後來的論文對社工教育的批判與反思:當下的社工專業教育中,讓原住民學生看不見原住民,也因此無法成為真正的助人者。原住民社工需要另一種知識路徑:說故事!
帶著這個反省,雅崩進到政大社工所,再度成為學術殿堂上的社工研究生,成為我的指導學生。我告訴自己:「這次一定要讓雅崩畢業!不能讓優秀的原住民在學術領域中跌倒!」我用自己被培養的方式訓練雅崩,透過修課,帶領她進入研究團隊,練習資料分析與書寫,希望培養她成為一個學術工作者。
當她選擇用自我敘事作為研究方法,我非常支持,因為我知道這是研究者尋回主體性的重要方法。於是,雅崩開始書寫自己的故事。一開始,她寫得很停滯,但是她在臉書上,卻揮灑自如,文筆流暢,故事一瀉千里。我知道她對寫論文有心理的魔障。於是,我跟她說:「就像妳寫臉書一樣,寫自我敘事就是跟自己對話,好好貼近自己。」
於是,她的故事開始出土。閱讀後,我鼓勵她帶入一些她曾經接觸過的理論觀點,希望讓她的論文具有理論的參照與對話。結果,雅崩因此卡住了很久……
原來,她的故事容不進一點雜質,理論就像一粒塵土,讓雅崩的思緒因此中斷。我急忙告訴雅崩,放下理論,就用自己的語言盡情敘說。這讓我意識到,理論對於故事的侵入性,原來這麼深,理論的進入可能改變敘事的基調。
之後,我對雅崩的論文回應,就以第三隻眼的上帝視角,以生命碰觸生命的方式,回饋雅崩給我的感動,而我發現這才是雅崩聽得懂的方式。
過程中,我學著放下我對理論的執著,學著把空間讓給學生,讓原住民族傳統口述歷史的知識典範充分展現在雅崩的論文之中。
這份文化謙虛,跟二○一七年我在雪梨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經驗有關。有一天有一隻導盲犬闖進我的辦公室,跟我玩了起來,於是我認識了牠的主人昔拉格.丹尼爾斯-梅耶斯(Sheelagh Daniels-Mayes)教授。
昔拉格是澳洲原住民金米拉萊族(Kamilaroi)婦女,她從小是個盲人,被棄養在孤兒院,由於她的視覺障礙讓她的學習受阻,她一直被當成智能障礙的孩子對待。但她卻很清楚自己要逃離這個孤兒院,她選擇了在澳洲總理訪問孤兒院時,赤身露體地衝上講臺。這件事讓她被孤兒院驅離,從此她獲得自由之身。
當她念博士時,她告訴指導教授:「我的文獻回顧會以原住民的聲音為主、以批判族群理論為主,那些西方白人學者的理論,我最多只給他們三頁的篇幅,因為我的論文是原住民發聲的空間,這裡沒有他們的位置!」她的故事震撼了我,我想起雅崩,想起我曾經帶過的原住民學生,我自忖著:「我一定要給原住民學生屬於他們的空間。」雅崩的論文之所可以長成今天的樣貌,與昔拉格.丹尼爾斯-梅耶斯教授的分享,有著間接的關連。
原住民族過去四百年殖民歷史經歷不同形式的殖民,社會工作是福利殖民的主要執行者,原住民進入社工專業的視野,多半是需要被幫助的受助者或是社會問題需要矯正的偏差者。
雅崩,一個花蓮秀林鄉太魯閣族優秀的女孩,她與她的家族的成長歷程就是一部臺灣原住民族被殖民的歷史創傷圖鑑,她的論文起點來自於她越進入主流社會(念研究所),就越遺忘自己的原住民記憶的斷裂。她進入社工專業教育的過程中,沒有被教導理解她身上所背負的經驗,反而把主流社會的標籤與框架貼在自己與族人身上。
她對社會工作專業的批判因此來自她抵抗既有學術的框架,回到自身經驗的書寫,寫自己、寫父母,當她把自己跟族群的創傷經驗寫通透,她才能作社工,成為有能力抵抗殖民的助人者。這本論文記錄著一位成功進入主流社會的原住民女孩,嘗試回到部落自己的根,尋找屬於原住民社會工作者自己的知識生成的路。
雅崩的論文精彩之處不只在論文本身,更在於她完成論文後的行動。雅崩完成論文後,她開始集結太魯閣族年輕社工一起到部落說自己的論文。她的知識下鄉行動讓許多完成論文的太魯閣族社工進一步將學院知識帶回部落,開啟對話,開啟另一種對社工專業的寧靜革命。
雅崩的論文現在改寫成書,將會號召更多的讀者。這個作品最重要的意義於,她的論文始於生命,用於召喚原住民的集體故事,對處於福利/文化殖民的社工專業提出最具抵/解殖的具體行動。
【自序】
楔子
你知道你自己是誰嗎?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也是很難的問題。
當我們要介紹自己是誰的時候,你會怎麼介紹你自己?
我先生A是河洛人,我們剛認識時,我刻意帶他到新竹尖石鄉泰雅族領域找我的朋友亞弼,她的爸爸是一個很有智慧的長者,也在原住民族運動裡走得很前面。我帶著那時還只是朋友的A去見他們,許多泰雅族的朋友見到A便問他:「你是誰?」
A想著除了說名字和成長地之外,因為面對不同族群就必須要介紹自己的族群,一般閩南人會稱自己是「逮丸郎」(臺灣人),但他想了想,原住民也是臺灣人,他怎麼能介紹自己是「臺灣人」呢?而過去又鮮少說自己是河洛人,除此之外還可以怎麼再更深地介紹自己的族群文化背景呢?他回程時跟我分享著,以他以往的經歷,他從來沒有機會好好去思考這個關於「我是誰」的問題。
我叫Yabung,是在花蓮縣秀林鄉加灣部落長大的太魯閣族女孩。我是一名社工員、居家照顧服務員、族群工作者及日文口譯員。目前嫁到板橋,還在練習做第一代遷移的都市原住民部落婦女。我曾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太魯閣族族群委員(二○二○— 二○二三)、臺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協會祕書長(二○一四— 二○二○)、撒固兒部落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二○一八—二○一九)、臺灣原住民族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理事/理事長(二○一五—)等。
由上述介紹可以知道我在族群事務、長期照顧以及社會工作領域上面耕耘了有段時間,我有一群很親近的夥伴,大部分是太魯閣族,每個人在不同的位置持續努力實踐族群的文化與生活。
我們總是會面對很多的疑問與挑戰,在當代社會與傳統價值之間,在不同且多層次的面向中,比如知識、記憶、歷史、經濟與生活等,總是可以有很多的發現與反思。我總在想「我是怎麼變成現在的我」?這是我仍持續在整理的問題。現階段我尚可以說,就是因為在二十幾歲的某一天,我意識到父親的某一面,那個正值意氣風發,卻又太早進入到承擔家庭的重擔,在承擔與不甘心之間的那個好像「長不大的父親」;僅是那種「視角翻轉」的瞬間,我就好像可以開始理解某些對於父親不明白的種種,也許就是從那時刻開啟了更多深刻的感知,尋找「為什麼」與「我是誰」的旅程。若哪一天我明白了,就可以分享這個過程,讓更多人也可以成為我的夥伴。
回想起過去是何時開始有了族群意識?那大概是從很小的時候接觸非原住民族的那一刻起,我在國小一年級時因為父母親在西部工作,曾就讀桃園的小學半學期,那時候就不斷被其他人提醒我是「番仔子」,雖然也沒有人欺負我,但就意識到自己好像某個地方跟別人不太一樣,且是持續不斷被暴露的狀態,被迫意識群體和我之間的關係。
後來,我乘著這個「不一樣」的身分經過一段自我認同的崩潰與重新定位,然後投入族群事務的工作,現在仍在生活日常的種種大小事情當中,持續不斷地推延拉扯族群文化的認同版圖。
為什麼說是認同版圖呢?臺灣原住民族占臺灣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二,其實有非常多人對於當代原住民族了解不多,其中有更多人可能也沒有興趣想要了解,畢竟跟自身的生活交集不多,也就是因為不了解而產生許多想像。不過,確實也有不少非原民的朋友是支持且陪伴原住民族一起實現轉型正義的工作,在我的生命裡就有不少這樣的夥伴。
偏見是每個人本來就都有的,只是有沒有意識到、並嘗試去確認的差別而已。
我想起我剛入社會,在XX社會企業做有機蔬菜的行銷工作,當時的老闆心胸非常開闊,也很願意給我機會,放手讓非行銷背景的小女孩負責部落的有機蔬菜行銷,那時他以從事部落有機蔬菜的資本買賣背景下,提出了一個理論,他認為:「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終有一天會消失。」這是以人口趨勢、大環境的教育背景及資本社會得出的「真理」。而我卻不疑有他地全部接收了這個「真理」,甚至還在當時某一場分享會中,引用了這句話,告訴更年輕的莘莘學子們:「原住民族的文化終有一天會消失。」這是比悲傷還更悲傷的故事。
當時的我不經掙扎抵抗地直接宣告放棄,放棄去證實結果是否真如他所說的那樣,而事實上,世界上並沒有任何人知道真正的結果會是什麼。特別是現在地球生態環境的議題開始有了新的風向,想要了解有關於原住民族與大自然相處的知識作為現代科技知識的反省;不只服裝會流行復古,就連知識也會,所以誰能走到最後又有誰會知道?
這也成為我不斷自我警惕的經驗,我依舊記得工作中的美好畫面,那些在高山上部落穿梭的每一天,凌晨起來採摘的高麗菜,高山上的農田邊,我們圍在一起邊吃自己種植的蔬菜、邊聊天,這在交易買賣視角上看不到的關係建立,那是人跟人、人跟土地,還有人跟靈之間的關係,我想我還在那個關係建立的過程中學習,而我始終感受得到──靈的呼喚。
為了打破偏見,所以我想先把我的故事說給大家聽,才有了這本書的產生。
讓說故事再度成為原住民族知識生產的起點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雅崩(Yabung.Haning)是我的指導學生,但我從她身上學到很多,尤其她幫助我看到自己的學術訓練如何成為文化殖民原住民族的工具,這讓我對自以為傲的學術訓練學會謙虛。
認識雅崩,是在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的聚會上,她是個充滿熱情與活力的女孩。那時我知道她曾是慈濟社工所的碩士生,但遲遲沒完成論文。有一次她分享來到原照盟進行原住民長照倡議的由來,她說:「我一方面透過太魯閣學青會投入族群工作;另一方面,我在研究所進行長照研究。但我從來沒有把原住民跟長照連結起來,原來我可以從原住民的觀點分析長照!」
口直心快的雅崩很幽默地說出她作為原住民的生命經驗與她作為研究生的學術研究,彼此之間涇渭分明的區隔,但背後卻深刻地反應出當前的學術知識體制排除原住民族的世界觀,以致於原住民學生無法在學習過程中看見自己族群的身影。
這也成為雅崩後來的論文對社工教育的批判與反思:當下的社工專業教育中,讓原住民學生看不見原住民,也因此無法成為真正的助人者。原住民社工需要另一種知識路徑:說故事!
帶著這個反省,雅崩進到政大社工所,再度成為學術殿堂上的社工研究生,成為我的指導學生。我告訴自己:「這次一定要讓雅崩畢業!不能讓優秀的原住民在學術領域中跌倒!」我用自己被培養的方式訓練雅崩,透過修課,帶領她進入研究團隊,練習資料分析與書寫,希望培養她成為一個學術工作者。
當她選擇用自我敘事作為研究方法,我非常支持,因為我知道這是研究者尋回主體性的重要方法。於是,雅崩開始書寫自己的故事。一開始,她寫得很停滯,但是她在臉書上,卻揮灑自如,文筆流暢,故事一瀉千里。我知道她對寫論文有心理的魔障。於是,我跟她說:「就像妳寫臉書一樣,寫自我敘事就是跟自己對話,好好貼近自己。」
於是,她的故事開始出土。閱讀後,我鼓勵她帶入一些她曾經接觸過的理論觀點,希望讓她的論文具有理論的參照與對話。結果,雅崩因此卡住了很久……
原來,她的故事容不進一點雜質,理論就像一粒塵土,讓雅崩的思緒因此中斷。我急忙告訴雅崩,放下理論,就用自己的語言盡情敘說。這讓我意識到,理論對於故事的侵入性,原來這麼深,理論的進入可能改變敘事的基調。
之後,我對雅崩的論文回應,就以第三隻眼的上帝視角,以生命碰觸生命的方式,回饋雅崩給我的感動,而我發現這才是雅崩聽得懂的方式。
過程中,我學著放下我對理論的執著,學著把空間讓給學生,讓原住民族傳統口述歷史的知識典範充分展現在雅崩的論文之中。
這份文化謙虛,跟二○一七年我在雪梨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的經驗有關。有一天有一隻導盲犬闖進我的辦公室,跟我玩了起來,於是我認識了牠的主人昔拉格.丹尼爾斯-梅耶斯(Sheelagh Daniels-Mayes)教授。
昔拉格是澳洲原住民金米拉萊族(Kamilaroi)婦女,她從小是個盲人,被棄養在孤兒院,由於她的視覺障礙讓她的學習受阻,她一直被當成智能障礙的孩子對待。但她卻很清楚自己要逃離這個孤兒院,她選擇了在澳洲總理訪問孤兒院時,赤身露體地衝上講臺。這件事讓她被孤兒院驅離,從此她獲得自由之身。
當她念博士時,她告訴指導教授:「我的文獻回顧會以原住民的聲音為主、以批判族群理論為主,那些西方白人學者的理論,我最多只給他們三頁的篇幅,因為我的論文是原住民發聲的空間,這裡沒有他們的位置!」她的故事震撼了我,我想起雅崩,想起我曾經帶過的原住民學生,我自忖著:「我一定要給原住民學生屬於他們的空間。」雅崩的論文之所可以長成今天的樣貌,與昔拉格.丹尼爾斯-梅耶斯教授的分享,有著間接的關連。
原住民族過去四百年殖民歷史經歷不同形式的殖民,社會工作是福利殖民的主要執行者,原住民進入社工專業的視野,多半是需要被幫助的受助者或是社會問題需要矯正的偏差者。
雅崩,一個花蓮秀林鄉太魯閣族優秀的女孩,她與她的家族的成長歷程就是一部臺灣原住民族被殖民的歷史創傷圖鑑,她的論文起點來自於她越進入主流社會(念研究所),就越遺忘自己的原住民記憶的斷裂。她進入社工專業教育的過程中,沒有被教導理解她身上所背負的經驗,反而把主流社會的標籤與框架貼在自己與族人身上。
她對社會工作專業的批判因此來自她抵抗既有學術的框架,回到自身經驗的書寫,寫自己、寫父母,當她把自己跟族群的創傷經驗寫通透,她才能作社工,成為有能力抵抗殖民的助人者。這本論文記錄著一位成功進入主流社會的原住民女孩,嘗試回到部落自己的根,尋找屬於原住民社會工作者自己的知識生成的路。
雅崩的論文精彩之處不只在論文本身,更在於她完成論文後的行動。雅崩完成論文後,她開始集結太魯閣族年輕社工一起到部落說自己的論文。她的知識下鄉行動讓許多完成論文的太魯閣族社工進一步將學院知識帶回部落,開啟對話,開啟另一種對社工專業的寧靜革命。
雅崩的論文現在改寫成書,將會號召更多的讀者。這個作品最重要的意義於,她的論文始於生命,用於召喚原住民的集體故事,對處於福利/文化殖民的社工專業提出最具抵/解殖的具體行動。
【自序】
楔子
你知道你自己是誰嗎?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也是很難的問題。
當我們要介紹自己是誰的時候,你會怎麼介紹你自己?
我先生A是河洛人,我們剛認識時,我刻意帶他到新竹尖石鄉泰雅族領域找我的朋友亞弼,她的爸爸是一個很有智慧的長者,也在原住民族運動裡走得很前面。我帶著那時還只是朋友的A去見他們,許多泰雅族的朋友見到A便問他:「你是誰?」
A想著除了說名字和成長地之外,因為面對不同族群就必須要介紹自己的族群,一般閩南人會稱自己是「逮丸郎」(臺灣人),但他想了想,原住民也是臺灣人,他怎麼能介紹自己是「臺灣人」呢?而過去又鮮少說自己是河洛人,除此之外還可以怎麼再更深地介紹自己的族群文化背景呢?他回程時跟我分享著,以他以往的經歷,他從來沒有機會好好去思考這個關於「我是誰」的問題。
我叫Yabung,是在花蓮縣秀林鄉加灣部落長大的太魯閣族女孩。我是一名社工員、居家照顧服務員、族群工作者及日文口譯員。目前嫁到板橋,還在練習做第一代遷移的都市原住民部落婦女。我曾擔任原住民族委員會太魯閣族族群委員(二○二○— 二○二三)、臺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協會祕書長(二○一四— 二○二○)、撒固兒部落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二○一八—二○一九)、臺灣原住民族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理事/理事長(二○一五—)等。
由上述介紹可以知道我在族群事務、長期照顧以及社會工作領域上面耕耘了有段時間,我有一群很親近的夥伴,大部分是太魯閣族,每個人在不同的位置持續努力實踐族群的文化與生活。
我們總是會面對很多的疑問與挑戰,在當代社會與傳統價值之間,在不同且多層次的面向中,比如知識、記憶、歷史、經濟與生活等,總是可以有很多的發現與反思。我總在想「我是怎麼變成現在的我」?這是我仍持續在整理的問題。現階段我尚可以說,就是因為在二十幾歲的某一天,我意識到父親的某一面,那個正值意氣風發,卻又太早進入到承擔家庭的重擔,在承擔與不甘心之間的那個好像「長不大的父親」;僅是那種「視角翻轉」的瞬間,我就好像可以開始理解某些對於父親不明白的種種,也許就是從那時刻開啟了更多深刻的感知,尋找「為什麼」與「我是誰」的旅程。若哪一天我明白了,就可以分享這個過程,讓更多人也可以成為我的夥伴。
回想起過去是何時開始有了族群意識?那大概是從很小的時候接觸非原住民族的那一刻起,我在國小一年級時因為父母親在西部工作,曾就讀桃園的小學半學期,那時候就不斷被其他人提醒我是「番仔子」,雖然也沒有人欺負我,但就意識到自己好像某個地方跟別人不太一樣,且是持續不斷被暴露的狀態,被迫意識群體和我之間的關係。
後來,我乘著這個「不一樣」的身分經過一段自我認同的崩潰與重新定位,然後投入族群事務的工作,現在仍在生活日常的種種大小事情當中,持續不斷地推延拉扯族群文化的認同版圖。
為什麼說是認同版圖呢?臺灣原住民族占臺灣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二,其實有非常多人對於當代原住民族了解不多,其中有更多人可能也沒有興趣想要了解,畢竟跟自身的生活交集不多,也就是因為不了解而產生許多想像。不過,確實也有不少非原民的朋友是支持且陪伴原住民族一起實現轉型正義的工作,在我的生命裡就有不少這樣的夥伴。
偏見是每個人本來就都有的,只是有沒有意識到、並嘗試去確認的差別而已。
我想起我剛入社會,在XX社會企業做有機蔬菜的行銷工作,當時的老闆心胸非常開闊,也很願意給我機會,放手讓非行銷背景的小女孩負責部落的有機蔬菜行銷,那時他以從事部落有機蔬菜的資本買賣背景下,提出了一個理論,他認為:「原住民族的文化發展,終有一天會消失。」這是以人口趨勢、大環境的教育背景及資本社會得出的「真理」。而我卻不疑有他地全部接收了這個「真理」,甚至還在當時某一場分享會中,引用了這句話,告訴更年輕的莘莘學子們:「原住民族的文化終有一天會消失。」這是比悲傷還更悲傷的故事。
當時的我不經掙扎抵抗地直接宣告放棄,放棄去證實結果是否真如他所說的那樣,而事實上,世界上並沒有任何人知道真正的結果會是什麼。特別是現在地球生態環境的議題開始有了新的風向,想要了解有關於原住民族與大自然相處的知識作為現代科技知識的反省;不只服裝會流行復古,就連知識也會,所以誰能走到最後又有誰會知道?
這也成為我不斷自我警惕的經驗,我依舊記得工作中的美好畫面,那些在高山上部落穿梭的每一天,凌晨起來採摘的高麗菜,高山上的農田邊,我們圍在一起邊吃自己種植的蔬菜、邊聊天,這在交易買賣視角上看不到的關係建立,那是人跟人、人跟土地,還有人跟靈之間的關係,我想我還在那個關係建立的過程中學習,而我始終感受得到──靈的呼喚。
為了打破偏見,所以我想先把我的故事說給大家聽,才有了這本書的產生。
試閱
第二章
我的成長與情緒
我是一九八七年在花蓮縣秀林鄉加灣部落出生,族名Yabung.Haning。太魯閣族是父子連名,Yabung 是我的名字,Haning 則是我爸的名字。
太魯閣族人叫人名時,總是會加上一些形象特徵或是故事方便記憶,簡單來說就是很愛幫人家取外號,我小時候總被隔壁部落的叔叔叫Yabung.Tuba,Tuba是太魯閣族語「魚藤」的意思,在溪裡抓魚時把藤汁搗出來放水裡,可以暫時麻痺附近的魚。聽說我出生時的加灣部落有個名字同樣也叫Yabung 的婦女試圖吃魚藤自殺而出名,所以隔壁部落的叔叔總是叫我加灣來的Yabung.Tuba。
我的阿公叫Jiru,大家都叫我阿公Jiru.Honda,因為他是我們部落第一個買下Honda(本田)摩托車的人。阿公阿嬤認真務農,以前家裡的客廳還有農會頒發的木製匾額,是阿公擔任農會代表時所贈。而聽說我出生時,阿公抱我沒有多久就去世了,爸爸總說那時候我剛出生,阿公第一次抱我,我叫了三聲阿公之後,他就因農藥中毒而死在田裡。
當時加灣部落主要經濟來源是種稻米,在沒有保護遮蔽的狀態下灑農藥,導致不少人因為農藥中毒或是肝臟方面的疾病而去世,我阿公Jiru就是肝病去世。
有關族人因肝病而去世這件事,不知道為什麼在我長大之後,總是被人說「原住民得肝病就是因為愛喝酒」的關係,而讓我一度以為會得肝病的原因只有喝酒,一直到我接觸長期照顧服務的工作才知道,原來會得肝病的原因有很多種,有喝酒、農藥及過勞等。
加灣部落的太魯閣族名叫Alang Qowgan, Qowgan 是一種大竹子的名字,祖先遷移至此看見許多這種竹子因此命名,而後來的加灣山相繼因為各種法律的規定,諸如獵人狩獵被抓、禁止游耕燒墾、禁伐補償的政策以及部落生活經濟的改變,導致缺乏族人上山整理而逐漸荒廢,竹林樹木被覆蓋著滿滿的小花蔓澤蘭。這種外來藤本植物會攀著植物往上爬,只要有陽光空隙它便會填滿,植物會因為缺乏光合作用而死亡,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很少找到長者所說的Qowgan 這種竹子了。
鄰近我家後面的是一座陡直約六百五十公尺高的加灣山,我依稀記得小時候跟著阿嬤沿著景美國小旁邊的小路上山,在阿嬤刻意栽種的箭筍細竹間用繩子與帆布搭建的簡易工寮,並放置鍋碗瓢盆、寶特瓶水,阿嬤在那裡生火煮湯麵,我則會在放完火燒墾後的山坡,坐在紙箱上找地方滑下去,當然最後少不了被修理一頓。也記得小時候常常看到我們家後面的山頂上有人招手,或者將要製作竹筒飯的節慶日,往山的方向看去會有「竹子雨」──山上有人把竹子用投射的方式往下丟擲,聚集在某處,或者順著竹子的路往山下拖拉,那些往下移動的竹子就好像下雨一樣。
「部落很多規矩妳不知道!」
我的童年,常常聽到有人在部落的路上打架爭執,甚至刀光劍影、拿著電鋸在路上跑都不是奇怪的畫面。
只要半夜有人叫囂,部落的族人就會前去阻止、拉扯,就如同我爸和部落的叔叔在飲酒過後有些言論產生不愉快,就會扭打起來,甚至拿刀出來,好像很有默契地把手上的刀打在對方的刀上,鏗鏘產生火花,但不至於出人命,頂多扭到腳或是不小心劃到耳朵流血包紮,隔天腳一跛一跛地再到對方家道歉。我總不覺得在部落看到幾個男人打架是令人害怕的事情,某個部分還覺得有種湊熱鬧的興奮感,這是跟新聞上面播放的槍擊殺戮社會案件不一樣的情境。
在太魯閣族社群裡的衝突事件,有個潛規則,就是不太能叫警察,族人間可以打架,其他人會協助勸架阻止,但其中一方如果有人報警來處理,或是訴訟上法院,會被譴責說那樣做太超過了。我爸媽就指責過隔壁鄰居兄弟鬩牆鬧上警局,但他們譴責最多的不是打架行為本身,而是報警處理的這件事。
我又想起大學時期年輕氣盛做的蠢事。部落一個阿姨為人霸道,多數族人盡量不跟她有交集,我媽透過關係在部落買了一隻貴賓狗,那隻狗是那個阿姨的狗配種後的小孩。我媽養了一陣子很是喜愛,有一天那位阿姨就衝進我家直接把那隻狗給帶走說那是她的狗,我氣不過就跑去警察局準備要報案。
我媽得知後氣沖沖地衝去警察局當著大家的面把我給拖走,她嘴裡對我罵著:「部落很多規矩妳都不知道,妳以為妳讀書讀得高就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嗎?妳還早得很!部落的人是我每天都會見面的,妳這樣子一搞我要怎麼在部落裡生活?」
當時的我並不明白,為什麼部落的人寧願自己吃虧,也不要找警察處理。
彎彎曲曲的歷史殖民痕跡與我的小姆指
我就讀部落裡一間私立天主教安德幼稚園,那時候園長是一個外國人,園區的角落有個小教堂,幽幽靜靜,我們小孩總是說那裡有吸血鬼,不乖的話會被園長抓去裡面吃掉。
園內的孩子都是加灣部落的太魯閣族,因為私立的關係學費本來就很貴,但是安德幼稚園可以接受分期付款,或是同意以先欠費的方式照顧小孩,甚至付不出學費的家庭,園長也還是會收,依靠募款等方式來維持營運。我們家都有分期付款和欠費的情況,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事情。
即便是在太魯閣族部落裡的幼稚園,學生也都是太魯閣族,但園內並沒有讓我有任何學習太魯閣族文化、語言的印象,當然那時的年代忙著生存都來不及,更不可能談到族群文化,秉著慈愛與收容幫助我們偏鄉兒童的議題就很偉大了,所以我依稀記得幼稚園的畢業表演是跳著阿美族舞蹈和蚌殼精。
我是看著迪士尼和格林童話的卡通長大,小姑姑還送我《十萬個為什麼》的動畫卡帶給我,小姑姑很喜歡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她房間都是他的海報和音樂,當時部落甚至還有許多小朋友相繼模仿麥可.傑克森的月球漫步舞步。
每到星期日,就是要去加灣基督長老教會聽《聖經》故事,然後吃糖果,阿嬤通常給我二十元的奉獻金,我都會投十元給教會,剩下十元我會拿來買糖果。我最喜歡在星期日中午,部落十字路口中間,會有棉花糖阿伯,下午會有糖葫蘆阿伯,甚至有行動剪髮的阿伯在部落走動。那些阿伯們都是漢人,在固定的時間出現在部落固定的位置,持續至少有二十年以上,直到可能行動不便無法來為止。
每當到了夏天,我會和鄰居小朋友去景美國小的水圳游泳,摘水圳上母構樹的種子當糖果來吃,水圳是在臺美建交時期為了部落種植灌溉水稻時建設的。我們在半山腰有個祕密基地,我依稀記得是藤蔓圍繞著樹形成的天然樹洞,我們也不曾害怕會有蛇或是蟲之類的,自以為地把寶物藏在那裡。
部落正中間有個叫做「高山青」的廢棄酒店,它是我們部落孩子冒險的鬼屋,我們會在高山青前空地集合,拿著手電筒去闖,闖過了可怕幽暗的大廳,到二樓會看見破碎的玻璃落地窗,然後就是樓梯下樓直達酒店後的花園池塘。花園池畔上有一個一個小小的獨立小房子,很像蘑菇長在花園上。傍晚我跟鄰居的小朋友都在部落的馬路上賽跑。
部落的大人們都在忙,我們小孩每天在部落也忙著玩,但玩的時候切記不能讓自己受傷,或是遺失東西。比方今天手被割到了,自己很痛就算了,回去被大人發現受傷了,就是先一陣挨打;或是鞋子掉了一隻後,又是一陣挨打;被發現去了大人警告不能去的地方,比方溪河、水圳、海邊後,又會一陣挨打。
對這些處罰的因應方式就是,不要讓自己受傷,或是想辦法不被發現,我的右手小拇指彎彎的,因為小時候玩耍時折到,回家默默地藏起來不講,就是怕被打的關係,但也就這樣彎彎曲曲地長大了。
分離寄宿的國小生活
要上國小時,爸媽到雲林麥寮及桃園等地工作,我們跟著很多同樣是太魯閣族叔叔阿姨們一起同居生活。當時我一年級就讀桃園的國小,我的同學幾乎都是閩南人,我到同學家玩時第一次聽到他們家長說出「番仔」的稱呼,不懂這意思的我們還是玩在一起。
讀了半個學期,爸媽因為接工程常常要轉移陣地,不方便帶著我一起,於是我被送回花蓮給阿嬤照顧。我還記得當爸媽準備要騎車離去時,我手抱著我媽媽,然後阿嬤抓住我的腳,我騰空在半空中聲嘶竭力地哭喊著:「我不要!我要一起去!」
當然最後,我還是留在花蓮。但沒有多久,不太會中文的阿嬤因為不知道要怎麼教我,小學課本都是她看不懂的中文和注音,所以又把我交給隔壁佳民部落的大姑姑照顧,使我就讀佳民部落的國小。
佳民國小一個年級只有一班,每班大約只有十到十五位學生,我一進去期中考直接考第一名,因此被全班排擠過。全校學生都是太魯閣族,但任教的老師沒有一個是太魯閣族,印象中幾乎都是外省籍老師,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們講過閩南語。
國小在學校除了學習中文、數學、自然等主科之外,老師還教我們打響板數來寶、做紙雕、念順口溜,以及唱童謠(童謠都是閩南語或是中文的歌謠)。
我常常會被推去比賽國語朗讀、演講、注音寫字與書法。老師為了要「糾正」我的口音,要求我每天上臺朗讀《國語日報》,教我拿著筆、順著注音的四聲畫在空中調整我的抑揚頓挫,所以我的中文咬字很標準,這也導致我在後來接觸自己的文化時,有一段時間總被誤認為「不在部落長大的孩子」。
由於我臺風很穩,便被加灣部落提倡母語推廣的田老師相中,要我去比賽母語演講。大約是在我三、四年級時,常常要到田老師家受訓,她先教我如何認羅馬拼音,再教我咬字發音,然後要我用中文寫一篇〈我的家〉,她翻譯成母語,再要求我背下來。我就以這篇〈Alang mu〉(我的家)拿下了全國第一名的母語演講冠軍,成為家喻戶曉的全國太魯閣族語冠軍的Yabung。
那時的我懵懵懂懂,只知道把背下來的音與手勢演繹出來,但其實對於母語並沒有很熟知。因為那時太魯閣族還沒有正名,使得我報名參加的族群名也總是在變化,一下子是泰雅族東賽德克族語、或是泰雅亞族德魯固族語,而年幼無知的我對於族別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我在比賽母語演講。
而田老師鋼鐵般的教導,總讓我很害怕去她家學母語。我曾看過她在我面前打了跟我同年紀的小男孩耳光,只因為他一直念錯,巨大的壓力之下,我向阿嬤哭訴說不想再去比賽了,所以阿嬤就幫我擋下了田老師的比賽要求。也許是因為說母語的經驗讓我有陰影,自此之後我就再也不去碰母語了,即便在部落總是聽到長輩們都用母語交談。
我的成長與情緒
我是一九八七年在花蓮縣秀林鄉加灣部落出生,族名Yabung.Haning。太魯閣族是父子連名,Yabung 是我的名字,Haning 則是我爸的名字。
太魯閣族人叫人名時,總是會加上一些形象特徵或是故事方便記憶,簡單來說就是很愛幫人家取外號,我小時候總被隔壁部落的叔叔叫Yabung.Tuba,Tuba是太魯閣族語「魚藤」的意思,在溪裡抓魚時把藤汁搗出來放水裡,可以暫時麻痺附近的魚。聽說我出生時的加灣部落有個名字同樣也叫Yabung 的婦女試圖吃魚藤自殺而出名,所以隔壁部落的叔叔總是叫我加灣來的Yabung.Tuba。
我的阿公叫Jiru,大家都叫我阿公Jiru.Honda,因為他是我們部落第一個買下Honda(本田)摩托車的人。阿公阿嬤認真務農,以前家裡的客廳還有農會頒發的木製匾額,是阿公擔任農會代表時所贈。而聽說我出生時,阿公抱我沒有多久就去世了,爸爸總說那時候我剛出生,阿公第一次抱我,我叫了三聲阿公之後,他就因農藥中毒而死在田裡。
當時加灣部落主要經濟來源是種稻米,在沒有保護遮蔽的狀態下灑農藥,導致不少人因為農藥中毒或是肝臟方面的疾病而去世,我阿公Jiru就是肝病去世。
有關族人因肝病而去世這件事,不知道為什麼在我長大之後,總是被人說「原住民得肝病就是因為愛喝酒」的關係,而讓我一度以為會得肝病的原因只有喝酒,一直到我接觸長期照顧服務的工作才知道,原來會得肝病的原因有很多種,有喝酒、農藥及過勞等。
加灣部落的太魯閣族名叫Alang Qowgan, Qowgan 是一種大竹子的名字,祖先遷移至此看見許多這種竹子因此命名,而後來的加灣山相繼因為各種法律的規定,諸如獵人狩獵被抓、禁止游耕燒墾、禁伐補償的政策以及部落生活經濟的改變,導致缺乏族人上山整理而逐漸荒廢,竹林樹木被覆蓋著滿滿的小花蔓澤蘭。這種外來藤本植物會攀著植物往上爬,只要有陽光空隙它便會填滿,植物會因為缺乏光合作用而死亡,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很少找到長者所說的Qowgan 這種竹子了。
鄰近我家後面的是一座陡直約六百五十公尺高的加灣山,我依稀記得小時候跟著阿嬤沿著景美國小旁邊的小路上山,在阿嬤刻意栽種的箭筍細竹間用繩子與帆布搭建的簡易工寮,並放置鍋碗瓢盆、寶特瓶水,阿嬤在那裡生火煮湯麵,我則會在放完火燒墾後的山坡,坐在紙箱上找地方滑下去,當然最後少不了被修理一頓。也記得小時候常常看到我們家後面的山頂上有人招手,或者將要製作竹筒飯的節慶日,往山的方向看去會有「竹子雨」──山上有人把竹子用投射的方式往下丟擲,聚集在某處,或者順著竹子的路往山下拖拉,那些往下移動的竹子就好像下雨一樣。
「部落很多規矩妳不知道!」
我的童年,常常聽到有人在部落的路上打架爭執,甚至刀光劍影、拿著電鋸在路上跑都不是奇怪的畫面。
只要半夜有人叫囂,部落的族人就會前去阻止、拉扯,就如同我爸和部落的叔叔在飲酒過後有些言論產生不愉快,就會扭打起來,甚至拿刀出來,好像很有默契地把手上的刀打在對方的刀上,鏗鏘產生火花,但不至於出人命,頂多扭到腳或是不小心劃到耳朵流血包紮,隔天腳一跛一跛地再到對方家道歉。我總不覺得在部落看到幾個男人打架是令人害怕的事情,某個部分還覺得有種湊熱鬧的興奮感,這是跟新聞上面播放的槍擊殺戮社會案件不一樣的情境。
在太魯閣族社群裡的衝突事件,有個潛規則,就是不太能叫警察,族人間可以打架,其他人會協助勸架阻止,但其中一方如果有人報警來處理,或是訴訟上法院,會被譴責說那樣做太超過了。我爸媽就指責過隔壁鄰居兄弟鬩牆鬧上警局,但他們譴責最多的不是打架行為本身,而是報警處理的這件事。
我又想起大學時期年輕氣盛做的蠢事。部落一個阿姨為人霸道,多數族人盡量不跟她有交集,我媽透過關係在部落買了一隻貴賓狗,那隻狗是那個阿姨的狗配種後的小孩。我媽養了一陣子很是喜愛,有一天那位阿姨就衝進我家直接把那隻狗給帶走說那是她的狗,我氣不過就跑去警察局準備要報案。
我媽得知後氣沖沖地衝去警察局當著大家的面把我給拖走,她嘴裡對我罵著:「部落很多規矩妳都不知道,妳以為妳讀書讀得高就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嗎?妳還早得很!部落的人是我每天都會見面的,妳這樣子一搞我要怎麼在部落裡生活?」
當時的我並不明白,為什麼部落的人寧願自己吃虧,也不要找警察處理。
彎彎曲曲的歷史殖民痕跡與我的小姆指
我就讀部落裡一間私立天主教安德幼稚園,那時候園長是一個外國人,園區的角落有個小教堂,幽幽靜靜,我們小孩總是說那裡有吸血鬼,不乖的話會被園長抓去裡面吃掉。
園內的孩子都是加灣部落的太魯閣族,因為私立的關係學費本來就很貴,但是安德幼稚園可以接受分期付款,或是同意以先欠費的方式照顧小孩,甚至付不出學費的家庭,園長也還是會收,依靠募款等方式來維持營運。我們家都有分期付款和欠費的情況,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事情。
即便是在太魯閣族部落裡的幼稚園,學生也都是太魯閣族,但園內並沒有讓我有任何學習太魯閣族文化、語言的印象,當然那時的年代忙著生存都來不及,更不可能談到族群文化,秉著慈愛與收容幫助我們偏鄉兒童的議題就很偉大了,所以我依稀記得幼稚園的畢業表演是跳著阿美族舞蹈和蚌殼精。
我是看著迪士尼和格林童話的卡通長大,小姑姑還送我《十萬個為什麼》的動畫卡帶給我,小姑姑很喜歡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她房間都是他的海報和音樂,當時部落甚至還有許多小朋友相繼模仿麥可.傑克森的月球漫步舞步。
每到星期日,就是要去加灣基督長老教會聽《聖經》故事,然後吃糖果,阿嬤通常給我二十元的奉獻金,我都會投十元給教會,剩下十元我會拿來買糖果。我最喜歡在星期日中午,部落十字路口中間,會有棉花糖阿伯,下午會有糖葫蘆阿伯,甚至有行動剪髮的阿伯在部落走動。那些阿伯們都是漢人,在固定的時間出現在部落固定的位置,持續至少有二十年以上,直到可能行動不便無法來為止。
每當到了夏天,我會和鄰居小朋友去景美國小的水圳游泳,摘水圳上母構樹的種子當糖果來吃,水圳是在臺美建交時期為了部落種植灌溉水稻時建設的。我們在半山腰有個祕密基地,我依稀記得是藤蔓圍繞著樹形成的天然樹洞,我們也不曾害怕會有蛇或是蟲之類的,自以為地把寶物藏在那裡。
部落正中間有個叫做「高山青」的廢棄酒店,它是我們部落孩子冒險的鬼屋,我們會在高山青前空地集合,拿著手電筒去闖,闖過了可怕幽暗的大廳,到二樓會看見破碎的玻璃落地窗,然後就是樓梯下樓直達酒店後的花園池塘。花園池畔上有一個一個小小的獨立小房子,很像蘑菇長在花園上。傍晚我跟鄰居的小朋友都在部落的馬路上賽跑。
部落的大人們都在忙,我們小孩每天在部落也忙著玩,但玩的時候切記不能讓自己受傷,或是遺失東西。比方今天手被割到了,自己很痛就算了,回去被大人發現受傷了,就是先一陣挨打;或是鞋子掉了一隻後,又是一陣挨打;被發現去了大人警告不能去的地方,比方溪河、水圳、海邊後,又會一陣挨打。
對這些處罰的因應方式就是,不要讓自己受傷,或是想辦法不被發現,我的右手小拇指彎彎的,因為小時候玩耍時折到,回家默默地藏起來不講,就是怕被打的關係,但也就這樣彎彎曲曲地長大了。
分離寄宿的國小生活
要上國小時,爸媽到雲林麥寮及桃園等地工作,我們跟著很多同樣是太魯閣族叔叔阿姨們一起同居生活。當時我一年級就讀桃園的國小,我的同學幾乎都是閩南人,我到同學家玩時第一次聽到他們家長說出「番仔」的稱呼,不懂這意思的我們還是玩在一起。
讀了半個學期,爸媽因為接工程常常要轉移陣地,不方便帶著我一起,於是我被送回花蓮給阿嬤照顧。我還記得當爸媽準備要騎車離去時,我手抱著我媽媽,然後阿嬤抓住我的腳,我騰空在半空中聲嘶竭力地哭喊著:「我不要!我要一起去!」
當然最後,我還是留在花蓮。但沒有多久,不太會中文的阿嬤因為不知道要怎麼教我,小學課本都是她看不懂的中文和注音,所以又把我交給隔壁佳民部落的大姑姑照顧,使我就讀佳民部落的國小。
佳民國小一個年級只有一班,每班大約只有十到十五位學生,我一進去期中考直接考第一名,因此被全班排擠過。全校學生都是太魯閣族,但任教的老師沒有一個是太魯閣族,印象中幾乎都是外省籍老師,因為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們講過閩南語。
國小在學校除了學習中文、數學、自然等主科之外,老師還教我們打響板數來寶、做紙雕、念順口溜,以及唱童謠(童謠都是閩南語或是中文的歌謠)。
我常常會被推去比賽國語朗讀、演講、注音寫字與書法。老師為了要「糾正」我的口音,要求我每天上臺朗讀《國語日報》,教我拿著筆、順著注音的四聲畫在空中調整我的抑揚頓挫,所以我的中文咬字很標準,這也導致我在後來接觸自己的文化時,有一段時間總被誤認為「不在部落長大的孩子」。
由於我臺風很穩,便被加灣部落提倡母語推廣的田老師相中,要我去比賽母語演講。大約是在我三、四年級時,常常要到田老師家受訓,她先教我如何認羅馬拼音,再教我咬字發音,然後要我用中文寫一篇〈我的家〉,她翻譯成母語,再要求我背下來。我就以這篇〈Alang mu〉(我的家)拿下了全國第一名的母語演講冠軍,成為家喻戶曉的全國太魯閣族語冠軍的Yabung。
那時的我懵懵懂懂,只知道把背下來的音與手勢演繹出來,但其實對於母語並沒有很熟知。因為那時太魯閣族還沒有正名,使得我報名參加的族群名也總是在變化,一下子是泰雅族東賽德克族語、或是泰雅亞族德魯固族語,而年幼無知的我對於族別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我在比賽母語演講。
而田老師鋼鐵般的教導,總讓我很害怕去她家學母語。我曾看過她在我面前打了跟我同年紀的小男孩耳光,只因為他一直念錯,巨大的壓力之下,我向阿嬤哭訴說不想再去比賽了,所以阿嬤就幫我擋下了田老師的比賽要求。也許是因為說母語的經驗讓我有陰影,自此之後我就再也不去碰母語了,即便在部落總是聽到長輩們都用母語交談。
訂購/退換貨須知
購買須知:
使用金石堂電子書服務即為同意金石堂電子書服務條款。
電子書分為「金石堂(線上閱讀+APP)」及「Readmoo(兌換碼)」兩種:
- 請至會員中心→電子書服務「我的e書櫃」領取複製『兌換碼』至電子書服務商Readmoo進行兌換。
退換貨須知:
- 因版權保護,您在金石堂所購買的電子書僅能以金石堂專屬的閱讀軟體開啟閱讀,無法以其他閱讀器或直接下載檔案。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不受「網購服務需提供七日鑑賞期」的限制。為維護您的權益,建議您先使用「試閱」功能後再付款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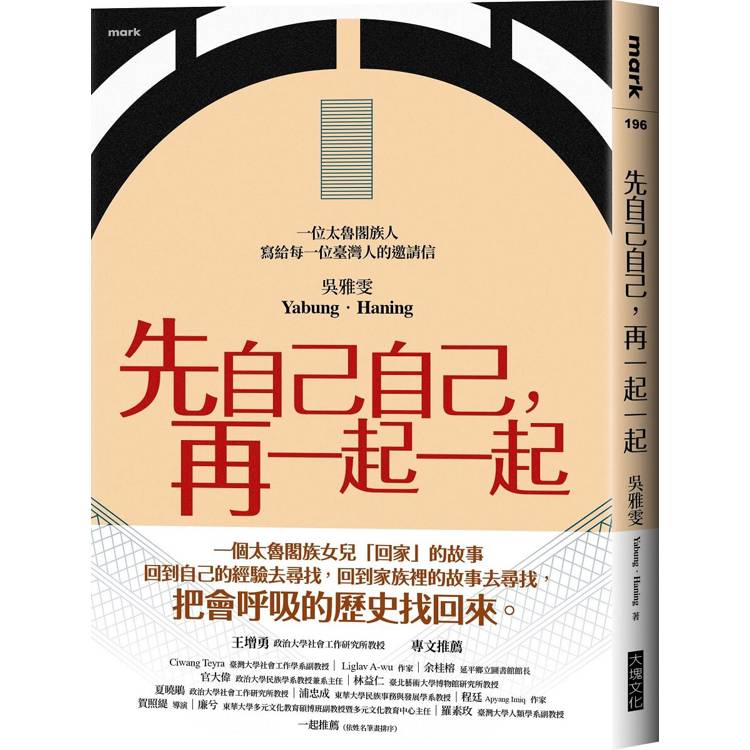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