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
內容簡介
1917-2017 現代文學革命的百年對話!
尋索漢語詩現代與古典的鏈接,
自語音分節到姿態節奏,
重現詩國革命的轉向與蛻變!
台大中文系教授──鄭毓瑜全新論文集
自晚清民初的知識割裂、語言西化衝擊,
論至漢語文化在句讀、文法上的種種演變。
不僅回應了一九一七年胡適、陳獨秀力倡的文學革命,
更完整呈現古典和現代質地的激盪碰撞!
什麼是詩?何謂詩國?革命是否仍有其必要?鄭毓瑜教授探勘古典資源,重新為白話詩歌作出定義,並擬想詩學未來。她以「姿」與「言」為準,所提倡的「抒情傳統」本身就不妨是推翻前人的嘗試。誠如她的自許,她的志之所之不僅是「新詩」學,更是「新」詩學。──王德威(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鄭毓瑜教授有感於當「漢語詩」逐漸演變成為「現代詩」,其中的「現代質地」更必須回到漢語脈絡來討論。她解析了晚清民初以來,漢語文化系統面對新語詞、新學科、英語文法等外來衝擊的種種回應,以及不斷內省「如何向新世界開口發聲?」、「如何重建與世界的新關係?」不論是新詞,或是原來已經使用的舊詞,作者坦言當語言成為思考對象或者翻新意旨,都足以作為考察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思想、感知及語文表現種種變遷的軌跡。因此鄭毓瑜教授詳實地從語法學、音韻學、修辭學、心理學等不同領域,研究探討漢語新思維的轉身與蛻變。
本書重新探索「文法」與「句讀」相迎應的動態過程,勾勒自詩界革命以來的漢語詩論述,如何在技術體系、工業文明的惘惘憂懼中,引生從語音分節到姿態節奏、從語序連斷到活軟肌理的種種說法;其中由足之進止來往,模擬往復力動的心聲意態,並同步體現由物我「相與(相感)」至於「相對」的意象旋轉與存有變動,一個不能被當代語言學所設定,而必須由身體自我來進行重設的語言現象,其實早已經在二十世紀初期宣告了漢語詩自己的「現代」轉向!
目錄
革命自有後來人:序《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王德威
導論 「情境」:晚清民初
博覽會與現代視線
第一章 博物連類與博覽會
第二章 「定解/多義」與「文法/句讀」的拉鋸
語音構義與姿態節奏
第三章 聲音與意義
第四章 姿態節奏
意象、肌理與現代詩形
第五章 文法、修辭與意義
第六章 意象與肌理
後記
參考書目
序/導讀
序
革命自有後來人
◎王德威(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新青年》雜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項文學之道: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祛除陳腔濫調,不用典,不對仗,不避俗字俗語。《新青年》主編、北大教授陳獨秀旋即在二月發表〈文學革命論〉以為聲援。陳認為中國社會的黑暗不能僅以革命改造,而必須仰賴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的革新。他推動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三大主義,並視白話文為最重要的利器。
〈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引起知識界廣大迴響,成為兩年後五四運動的先聲。晚清黃遵憲已經提倡「我手寫我口」,及至梁啟超登高一呼「詩界革命」(一八九 九)。但胡適、陳獨秀帶來真正的轉折。轉折的關鍵在於文學與語言關係的全面評估,而爭議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是以白話新詩作為文學革命的指標。
早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前,胡適即已思考「詩國革命」的必要。他在〈戲和叔永再贈詩,卻寄綺城諸友〉寫道,「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如作白話文。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談新詩〉,稱當時出現的白話詩為「新詩」,取其與「舊詩」相對的意思。隨後,胡適以白話文翻譯美國詩人蒂絲黛兒 (Sara Teasdale)的詩作〈關不住了〉(Over The Roofs),聲稱這是「新詩成立的新紀元」。一九二○年胡適出版《嘗試集》,是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第一本白話新詩集。
這場奉革命之名的新舊詩之爭由此為引線的新舊文學、文化之爭。「革命」是二十世紀初的時髦話語,所蘊含的強烈政治隱喻自不待言。據此文學史多以決然二分的修辭描述:舊詩被視為傳統糟粕,從對偶押韻到比興風雅無不陳陳相因。新詩以白話是尚,力求形式題材推陳出新,成為現代性表徵。兩相比較,進步和落伍、前衛和保守不言自明。但這樣的論述近年開始鬆動。學者已經指出現代舊詩未嘗沒有新意,新詩也不曾完全擺脫傳統。而新舊詩之別的焦點不應僅限於形式、內容和語言的比較而已,更牽涉一代文人知識份子如何看待「文學」,以及蘊含其中的世界觀。但如何進一步思考兩者的有機關係,卻少見突破。
在這樣的背景下,鄭毓瑜教授新著《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尤其顯得難能可貴。鄭教授專治中古詩歌,近年鑽研傳統詩學的現代意涵,尤其對「抒情傳統」的探討頗有所獲。在新著裡,鄭教授將焦點置於民國時期新舊文人對何謂「詩歌」的爭議上,以及詩歌如何現代化的理論可能。她的對話對象首先就是倡導「詩國革命」的胡適。而談論詩歌,首先必須回到語言文字問題。
如上所述,胡適一輩視白話文為啟蒙最重要的工具。〈文學改良芻議〉所列八項建議(一九一八年衍化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八不主義)明白表示文學革新首在推動通俗易曉、文法清晰的文字。而新詩發展的目標正是言文合一,「我手寫我口」。相對於文言的詰屈聱牙,隱晦多義,白話不但是語音語法的「自然」呈現,也是思想觀念的「自由」表徵。
胡適的白話文學觀當然早已受到質疑,但絕大部分的批評都僅止於分殊白話作為書寫和言說形式的古典淵源,或質疑白話(文)與方言口語的差距。鄭教授的研究則另闢蹊徑。她指出晚清民國之際,語言、文字、文法、文學的辯論遠較此複雜。小學學者如黃人、黃侃等強調「文字者,文學之單位細胞也」,而章太炎則更追本溯源,聲稱「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他們雖站在胡適對立面,但也在認真思考言、文之間的「自然關係」。他們的立論也許為新派文人所不取,鄭教授卻提醒我們,由復古而開新,未嘗不是「被壓抑的現代性」的一端。
一八九七年《馬氏文通》問世,以西洋文法規範為中文排列語序,分析結構,帶來典範式轉變。自此中文「文法」儼然成為日後語文的規範。彷彿透過了井然有序的文法羅列, 「中文」即可豁然開朗。然而這套文法觀念承襲彼時西方語言學的觀點與實踐,未必能照顧中文言說讀寫的方方面面。誠如黃侃所言,西洋文法專注「目治」,忽略傳統章句之學強調句讀節奏,「因聲求義」的「耳治」。這裡所牽涉的中國語言書寫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體系,不能由西方以字母為基礎的文法學所概括。更何況在此之上,中國傳統的「文」學的觀念與實踐有其獨到之處:「文」是符號言辭,也是氣質體性、文化情境,乃至天地萬物的表徵,和西方遠有不同。一九○四年清廷設立「文學科」,沿用西法,視文學為學院教程,其實簡化了傳統「文」學觀念。
由是觀之,胡適的「詩國革命」在五四前夕先聲奪人,正因為他直搗傳統文學的根本──詩歌,及其深遠的知識價值體系。「詩國」一詞既向文明傳統致意,也饒富現代國家民族主義的啟示。弔詭的是,胡適的「詩國革命」始終未能克竟全功,也因為他低估了詩歌文明盤根錯節的脈絡,以及感時、觀物、應世一脈相承的理路。胡適呼應《馬氏文通》式的文法學,樂觀相信只要避免無病呻吟、對仗用典、講求文法,新文學必能脫穎而出,新詩也就必能新意盎然。鄭教授卻強調,在唯新是尚的時代裡,傳統詩歌詩學儘管漸行漸遠,其實卻以各種形式滲入新詩世界。《姿與言》所致力的是,我們應當如何抽絲剝繭、「溫故而知新」?
鄭教授書中所提出的兩個關鍵詞,「姿」與「言」,極富論辯意義。先說「言」。「言」和詩歌的關聯性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四世紀的《書經》:「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首二句後來成為《樂論》的核心。言從舌,是言說,也是言辭,既是生理發聲表白的管道,也是心志抒情釋意的標記。作為身體與世界,內與外溝通的行為,言以其抑揚頓挫,一方面體現生命喜怒悲歡的情態,一方面體認為草木蟲魚、人倫天地命名的意義,正所謂「心生,言立,文明。」(《文心雕龍》)。這也就是黃侃以「文以載言」取代「文以載道」的理由。在看似瑣碎的研究裡,小學家們切切要發現「太初有言」的奧祕:一切意義「盡在言中」。
高友工教授在另一脈絡裡,曾指出中國語言的傳統「並不只是『文言』和『白話』的問題,而是『文字語言』和『聲傳語言』」對立的問題(〈中國語言對詩歌文字的影響〉)。近代「言文一致」運動循西方的民族國家/語言論述而起,其實不能解釋中國語言現代化的過程。高先生特別強調中文「聲語」和「文語」交相為用現象,前者所擬想的是聲音、文字之間的置換關係,而後者所著重的是聲音、文字之間的聯屬關係。就此鄭教授繼續發揮,強調語言、文字表達過程中情態與情境的重要性,不論是擬聲諧韻還是會意象形都指涉我者與他者之間綿密互動的關係。如是迴旋往復,節奏興起,韻律衍生,詩乃成為可能。
這就引領到鄭教授對﹁姿﹂的詮釋。姿原有姿態、姿勢、次序之意。推而廣之,又與「志」、「思」、「辭」、「次」等古韻相通互訓,因此引發聯想。鄭教授的靈感來自陳世驤教授。一九四八年陳出版陸機〈文賦〉英譯時,注意到「姿」與肢體、聲音、語言的密切關聯,並在推論至「之」義,即遠古先民根據象足前後停動所形成的節奏衍生出詩歌意象。陳日後並有專文論「姿」與西方文化中的「gesture」之關聯。鄭教授特別強調「姿」的審美、律動面向。在靜與動、重複與興發之間,姿是亮相,是間奏;是悠然暫止的狀態,也是蓄勢待發的可能。鄭教授更發現在「姿」和時間之流的辯證關係。屈原的發憤抒情,六朝詩人的感時傷逝,莫不與時間的久暫、物象的流變、以及詩人主體隨之而來的感應相通,由此興起的喜怒悲歡,都化作吟哦比興的「姿」。
或有識者指出,《姿與言》如此看待現代文學的發生,似乎未必照顧到現代情境所帶來的全面衝擊;新詩與舊詩的鴻溝畢竟歷歷在目。鄭教授對這樣的質疑有備而來。關於新詩「中國性」如何的爭論一個世紀以來眾說紛紜。在種種形式、題材、立場的分殊之外,鄭教授的建議是,眼前無路想回頭:作為「詩」的最新一種呈現,新詩是否仍然能「言」之有「物」?鍾「情」而多「姿」?只有在中國詩歌知識譜系學層次繼續做出探討,新詩的論辯才能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鄭教授的立論與其說是回到過去,不如說是回到未來──一種對中國詩歌「物種源起」的投射,一種烏托邦未來的興發。在她的調度下,中國現代和古典詩學呈現少見的對話密度,而她所提出的問題與觀察在在值得後之來者的追蹤。以下僅志個人所得,聊供作為討論起點。
貫穿《姿與言》全書的重要命題是「抒情傳統」的重新檢討。「抒情傳統」的研究是近半世紀臺灣中文學界的重要貢獻──或發明。在陳世驤、高友工等先生的引領下,早已形成可觀的隊伍,而鄭教授正是中堅一輩的佼佼者。她曾將抒情連鎖到知識論和倫理學層面(《引譬連類》),也思考抒情和身體生理、病理、物理的關係(《文本風景》)。《姿與言》則更進一步,探問「抒情傳統」與現代文學的關聯為何?在鄭教授的研究下,民國以來保守派聲韻學者、小學家從黃侃到唐鉞、胡樸安浮出歷史地表;他們對聲氣節奏,吟哦詠嘆的專注提醒我們詩歌啟動的不僅是語言文字的琢磨推敲,也是感官與世界的來往復沓。所謂聲隨意轉,辭以情發,舊詩如此,新詩亦復如此。另一方面,新詩學者詩人從朱光潛、朱自清到卞之琳、陳世驤飽受西學啟迪,卻終能在研究呂恰慈(I.A. Richards),
試閱
◎王德威(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新青年》雜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項文學之道: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祛除陳腔濫調,不用典,不對仗,不避俗字俗語。《新青年》主編、北大教授陳獨秀旋即在二月發表〈文學革命論〉以為聲援。陳認為中國社會的黑暗不能僅以革命改造,而必須仰賴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的革新。他推動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三大主義,並視白話文為最重要的利器。
〈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引起知識界廣大迴響,成為兩年後五四運動的先聲。晚清黃遵憲已經提倡「我手寫我口」,及至梁啟超登高一呼「詩界革命」(一八九 九)。但胡適、陳獨秀帶來真正的轉折。轉折的關鍵在於文學與語言關係的全面評估,而爭議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是以白話新詩作為文學革命的指標。
早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前,胡適即已思考「詩國革命」的必要。他在〈戲和叔永再贈詩,卻寄綺城諸友〉寫道,「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如作白話文。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談新詩〉,稱當時出現的白話詩為「新詩」,取其與「舊詩」相對的意思。隨後,胡適以白話文翻譯美國詩人蒂絲黛兒 (Sara Teasdale)的詩作〈關不住了〉(Over The Roofs),聲稱這是「新詩成立的新紀元」。一九二○年胡適出版《嘗試集》,是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第一本白話新詩集。
這場奉革命之名的新舊詩之爭由此為引線的新舊文學、文化之爭。「革命」是二十世紀初的時髦話語,所蘊含的強烈政治隱喻自不待言。據此文學史多以決然二分的修辭描述:舊詩被視為傳統糟粕,從對偶押韻到比興風雅無不陳陳相因。新詩以白話是尚,力求形式題材推陳出新,成為現代性表徵。兩相比較,進步和落伍、前衛和保守不言自明。但這樣的論述近年開始鬆動。學者已經指出現代舊詩未嘗沒有新意,新詩也不曾完全擺脫傳統。而新舊詩之別的焦點不應僅限於形式、內容和語言的比較而已,更牽涉一代文人知識份子如何看待「文學」,以及蘊含其中的世界觀。但如何進一步思考兩者的有機關係,卻少見突破。
在這樣的背景下,鄭毓瑜教授新著《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尤其顯得難能可貴。鄭教授專治中古詩歌,近年鑽研傳統詩學的現代意涵,尤其對「抒情傳統」的探討頗有所獲。在新著裡,鄭教授將焦點置於民國時期新舊文人對何謂「詩歌」的爭議上,以及詩歌如何現代化的理論可能。她的對話對象首先就是倡導「詩國革命」的胡適。而談論詩歌,首先必須回到語言文字問題。
如上所述,胡適一輩視白話文為啟蒙最重要的工具。〈文學改良芻議〉所列八項建議(一九一八年衍化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八不主義)明白表示文學革新首在推動通俗易曉、文法清晰的文字。而新詩發展的目標正是言文合一,「我手寫我口」。相對於文言的詰屈聱牙,隱晦多義,白話不但是語音語法的「自然」呈現,也是思想觀念的「自由」表徵。
胡適的白話文學觀當然早已受到質疑,但絕大部分的批評都僅止於分殊白話作為書寫和言說形式的古典淵源,或質疑白話(文)與方言口語的差距。鄭教授的研究則另闢蹊徑。她指出晚清民國之際,語言、文字、文法、文學的辯論遠較此複雜。小學學者如黃人、黃侃等強調「文字者,文學之單位細胞也」,而章太炎則更追本溯源,聲稱「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他們雖站在胡適對立面,但也在認真思考言、文之間的「自然關係」。他們的立論也許為新派文人所不取,鄭教授卻提醒我們,由復古而開新,未嘗不是「被壓抑的現代性」的一端。
一八九七年《馬氏文通》問世,以西洋文法規範為中文排列語序,分析結構,帶來典範式轉變。自此中文「文法」儼然成為日後語文的規範。彷彿透過了井然有序的文法羅列, 「中文」即可豁然開朗。然而這套文法觀念承襲彼時西方語言學的觀點與實踐,未必能照顧中文言說讀寫的方方面面。誠如黃侃所言,西洋文法專注「目治」,忽略傳統章句之學強調句讀節奏,「因聲求義」的「耳治」。這裡所牽涉的中國語言書寫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體系,不能由西方以字母為基礎的文法學所概括。更何況在此之上,中國傳統的「文」學的觀念與實踐有其獨到之處:「文」是符號言辭,也是氣質體性、文化情境,乃至天地萬物的表徵,和西方遠有不同。一九○四年清廷設立「文學科」,沿用西法,視文學為學院教程,其實簡化了傳統「文」學觀念。
由是觀之,胡適的「詩國革命」在五四前夕先聲奪人,正因為他直搗傳統文學的根本──詩歌,及其深遠的知識價值體系。「詩國」一詞既向文明傳統致意,也饒富現代國家民族主義的啟示。弔詭的是,胡適的「詩國革命」始終未能克竟全功,也因為他低估了詩歌文明盤根錯節的脈絡,以及感時、觀物、應世一脈相承的理路。胡適呼應《馬氏文通》式的文法學,樂觀相信只要避免無病呻吟、對仗用典、講求文法,新文學必能脫穎而出,新詩也就必能新意盎然。鄭教授卻強調,在唯新是尚的時代裡,傳統詩歌詩學儘管漸行漸遠,其實卻以各種形式滲入新詩世界。《姿與言》所致力的是,我們應當如何抽絲剝繭、「溫故而知新」?
鄭教授書中所提出的兩個關鍵詞,「姿」與「言」,極富論辯意義。先說「言」。「言」和詩歌的關聯性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四世紀的《書經》:「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首二句後來成為《樂論》的核心。言從舌,是言說,也是言辭,既是生理發聲表白的管道,也是心志抒情釋意的標記。作為身體與世界,內與外溝通的行為,言以其抑揚頓挫,一方面體現生命喜怒悲歡的情態,一方面體認為草木蟲魚、人倫天地命名的意義,正所謂「心生,言立,文明。」(《文心雕龍》)。這也就是黃侃以「文以載言」取代「文以載道」的理由。在看似瑣碎的研究裡,小學家們切切要發現「太初有言」的奧祕:一切意義「盡在言中」。
高友工教授在另一脈絡裡,曾指出中國語言的傳統「並不只是『文言』和『白話』的問題,而是『文字語言』和『聲傳語言』」對立的問題(〈中國語言對詩歌文字的影響〉)。近代「言文一致」運動循西方的民族國家/語言論述而起,其實不能解釋中國語言現代化的過程。高先生特別強調中文「聲語」和「文語」交相為用現象,前者所擬想的是聲音、文字之間的置換關係,而後者所著重的是聲音、文字之間的聯屬關係。就此鄭教授繼續發揮,強調語言、文字表達過程中情態與情境的重要性,不論是擬聲諧韻還是會意象形都指涉我者與他者之間綿密互動的關係。如是迴旋往復,節奏興起,韻律衍生,詩乃成為可能。
這就引領到鄭教授對﹁姿﹂的詮釋。姿原有姿態、姿勢、次序之意。推而廣之,又與「志」、「思」、「辭」、「次」等古韻相通互訓,因此引發聯想。鄭教授的靈感來自陳世驤教授。一九四八年陳出版陸機〈文賦〉英譯時,注意到「姿」與肢體、聲音、語言的密切關聯,並在推論至「之」義,即遠古先民根據象足前後停動所形成的節奏衍生出詩歌意象。陳日後並有專文論「姿」與西方文化中的「gesture」之關聯。鄭教授特別強調「姿」的審美、律動面向。在靜與動、重複與興發之間,姿是亮相,是間奏;是悠然暫止的狀態,也是蓄勢待發的可能。鄭教授更發現在「姿」和時間之流的辯證關係。屈原的發憤抒情,六朝詩人的感時傷逝,莫不與時間的久暫、物象的流變、以及詩人主體隨之而來的感應相通,由此興起的喜怒悲歡,都化作吟哦比興的「姿」。
訂購/退換貨須知
購買須知:
使用金石堂電子書服務即為同意金石堂電子書服務條款。
電子書分為「金石堂(線上閱讀+APP)」及「Readmoo(兌換碼)」兩種:
- 請至會員中心→電子書服務「我的e書櫃」領取複製『兌換碼』至電子書服務商Readmoo進行兌換。
退換貨須知:
- 因版權保護,您在金石堂所購買的電子書僅能以金石堂專屬的閱讀軟體開啟閱讀,無法以其他閱讀器或直接下載檔案。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不受「網購服務需提供七日鑑賞期」的限制。為維護您的權益,建議您先使用「試閱」功能後再付款購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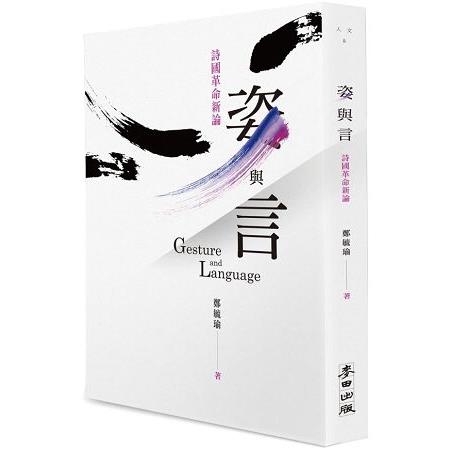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