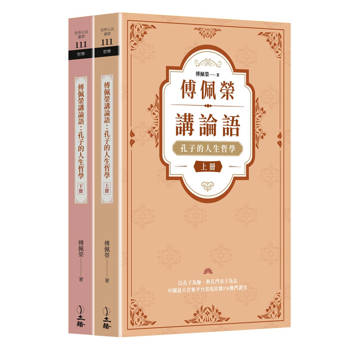1〈學而篇 1.1〉
做個悅樂的君子
《論語.學而篇》的第一章,原文是這樣的。
1.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ㄩㄝˋ)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ㄩㄣˋ),不亦君子乎?」
【譯文】
孔子說:「學了做人處事的道理,並在適當的時候去實踐,不也覺得高興嗎?志趣相近的朋友從遠方來聚會,不也感到快樂嗎?別人不了解你,而你並不生氣,不也是君子的風度嗎?」
在本章,孔子連續說了三句話都以「問句」結束。孔子不知道答案嗎?不是的,他是要學生想一想,情況是不是如此。所以這裡反映了孔子對學生的期許,希望他們可以成為「悅樂的君子」。
我們依序來看。
第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關於「學」這個字,我們想到三點:學什麼?如何學?為何學?
首先,學什麼?就是學習的內容。歷史學家錢穆有一個簡單的分法可以參考。他說:「中國文化五千年,孔子之前2500年;孔子之後到今天2500年。」所以在孔子的時代,如果問學什麼,前面有古人豐富的知識與技能,如五經與六藝。
五經是《詩》、《書》、《易》、《禮》、《樂》,包括了古代的文學、歷史、哲學、社會規範、音樂藝術。在技能方面主要是指六藝:禮、樂、射箭、駕車、書寫、計算。「禮」與「樂」兩邊都有,代表它們有知識的部分也有技能的部分,所以學起來就特別不容易了。
其次,如何學?就是學習的方法。孔子特別指出:要配合「思考」,「學」與「思」並重。孔子認為:學習而不思考,則將毫無領悟;思考而不學習,就會陷於迷惑。(〈為政2.15〉)
譬如,你專心學習,把《論語》背誦下來,但不去思考:這句話什麼意思?為什麼這樣說?他說的對嗎?對我今天有什麼啟發?你不做這樣的思考,永遠是只能背書,很容易就忘記了。但是,也不能全靠思考,全靠思考而不去向老師請教、向書本學習,那麼只能想著每天發生的事、各種八卦消息,想了半天只會覺得迷惑:為什麼善惡沒有報應?為什麼有些人得意?有些人失意?如此難免陷於迷惑了。這是談到學習的方法。
然後,為何學?這就涉及學習的目的了。學習的目的很多,包括前面說的,學會知識與技能。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有一次,魯國國君問孔子說:「你教這麼多學生,有哪幾位是好學的?」孔子說:「只有一位,顏回。」接著,孔子用六個字肯定顏回的好學。他說的不是考試第一,升學順利。他說的是「不遷怒,不貳過」。顏回不把怒氣發洩在不相干的人身上,也從不重複犯同樣的過錯。(〈雍也6.3〉)
由此可知,「好學」與「修德」是一體之兩面,有如「知」與「行」應該合一。所以整體來看,孔子所謂的「學」,包括了所有做人處事的道理。
那麼,「學」了之後呢?後面出現「習」字。「習」是指實踐。要身體力行,也包括由練習而熟能生巧,讓自己成為能知能行的人才。接著,學而時習之的「時」是什麼意思?我們以前對孔子的誤會往往來自這裡,以為孔子要學生時常復習功課。
問題在於:「時」是指「時常」嗎?在《論語》中,「時」字出現11次,其中3次與時間有關,所指的是季節,譬如四時(〈陽貨17.19〉);或配合天時的曆法,像夏朝的曆法(〈衛靈公15.11〉);或人生的階段,如少年之時(〈季氏16.7〉)。另外,有 7 次與「適當的時候」有關,譬如孔子談到在「適當的時候」說話,別人不討厭你的說話(〈憲問14.13〉);命令百姓服勞役,要選在「適當的時候」(〈學而1.5〉);喜歡做事而屢次錯過「適當的時候」(〈陽貨17.1〉)等。
換言之,「時」字在《論語》沒有用作「時常」來講的。因此,學而時習之的「時」字,應該是指「適當的時候」。譬如你學了孝順,要在與父母相處的時候去實踐;學了守信,要在與朋友往來的時候去實踐;學了射箭或駕車,要在運動場上的時候去練習。
事實上,做任何事都有適當的時候,而對「時」的判斷,已經成為孔子的標誌了。後來,孟子推崇孔子為「聖之時者」,就是聖人之中最重視時宜的(《孟子.萬章下》)。因此,這裡孔子的意思是:「學了做人處事的道理,並在適當的時候去實踐,不也覺得高興嗎?」你如果照孔子所說的去做,在知識、能力、德行方面,都會有更深的心得、體悟與提升,如此內心自然會覺得充實而喜悅高興了。
接著看第二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第一句說的「悅」,是自己心裡高興;這一句說的「樂」,就表現出來了,眉開眼笑、氣氛歡樂。那麼,「有朋自遠方來」是什麼情況呢?
我們現在習慣說「朋友」二字,《論語》也已經這麼用了,「朋友」二字出現8次。如果分開使用的話,古代有一種說法: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但是,不論是同門的「朋」或同志的「友」,都是指在思想上接近,並在志趣上相投的人。然後要問:為什麼從遠方來的朋友會讓你特別快樂呢?因為他在遠方,處於不同的甚至外國的社會人群中。如果他還能保持與我相似的思想與志趣,那就代表我們所肯定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是正確的。我們可以繼續依此在人生正路上攜手並進。朋友之間有心靈的共鳴,又能互相印證及分享人生的體悟,豈不是一大樂事?所以,孔子這裡說的是:「志趣相近的朋友從遠方來聚會,不也感到快樂嗎?」
最後,再看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一個人學習有了心得,具備基本的知識、能力與德行,成為有用的人才。他又能與遠方來的朋友相互切磋、彼此肯定,產生更大的自信,這時當然希望實至名歸,得到人們的了解與讚賞,進而有機會從政服務百姓。但是,在主觀期許與客觀現實之間有了差距,難免會覺得委屈與無奈,所以孔子提醒學生:別人不了解你,而你並不生氣,不也是君子的風度嗎?
這裡要問的是:君子何所指?「君子」一詞,原意是「君之子」,指古代統治階級的子弟。後來,用來指稱在德行方面可以做為表率的傑出人物。在《論語》中,「君子」一詞出現107次,是孔子所肯定的人格典型,也是他鼓勵弟子們去追求的修養目標。
那麼,為什麼「人不知而不慍」可以代表君子的風度呢?因為君子所要求的是自己,所實踐的是道義。如果時運不濟或天下無道,那就更加努力修養自己,何必為此而有情緒上的波動呢?我們從本章學到了什麼?學到了孔子對弟子的教導。他期許大家互相勉勵,努力做一個悅樂的君子。
2〈學而篇1.2〉
做人以孝弟為本
《論語.學而篇》第二章,原文如下:
1.2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ㄊㄧˋ),而好(ㄏㄠˋ)犯上者,鮮(ㄒㄧㄢˇ)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ㄩˊ)!」
【譯文】
有子說:「一個人能做到孝順父母與尊敬兄長,卻喜歡冒犯上司的,那是很少有的;不喜歡冒犯上司,卻喜歡造反作亂的,那是不曾有過的。君子要在根基上努力,根基穩固了,人生正途就會隨之展現開來。孝順父母與尊敬兄長,就是一個人做人的根基啊!」
讀完本章,首先要說明的是:有子是誰?他是孔子的學生,原名有若,字子有,魯國人,小孔子三十三歲。有若既然字子有,為何在這裡稱有子呢?這一點,我們在引言第二集已經說過了,那是因為編輯《論語》的是孔子的第二代弟子,主要是有若與曾參的學生。學生在提到自己的老師時,必須尊稱為有子與曾子。
排在《論語》開頭〈學而篇〉的一共16章,其中8章直接記載孔子的話。然後,另外八章怎麼分配?有子占3章,曾子占2章,子貢占2章,子夏占1章。如果深入分析這麼分配的理由,可以說,有子與曾子是因為他們的學生在編輯,所以不但二人稱「子」,並且可以搶先上場排進第一篇。
至於子貢,則他是孔子三大弟子僅存的一位。而子夏呢?他後來成為著名的老師。孔子三大弟子中,另外兩位是他最親近、最器重的顏回與子路,沒有排上,那是因為他們比孔子還早過世,所以到了第二篇〈為政篇〉才有機會排上場。像這些背景資料,大致知道即可。
比較重要的,是我們在「引言第二集」提過的,念《論語》要分辨一章的重要性,可以分為四個層次。排在第四個層次的是:孔門弟子自己表述的話。弟子的話代表他們各自的心得,所說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與孔子的話相提並論。
為什麼要作這樣的區分呢?因為孔子的核心觀念「仁」在這一章結束時出現了。事實上,我們將一再看到,孔門弟子連最傑出的顏回在內,沒有一位可以說完全理解「仁」字,並作出清楚的論述。有子也不例外。因此仔細閱讀本章,就會看到最後出現的「仁」字,其實是開頭所說的人類的「人」字。
現在就來仔細閱讀吧!
有子的話可以分兩段來看:第一段是根據經驗而作的推論,第二段是簡單的結論。第一段在說什麼呢?他說:「一個人能做到孝順父母與尊敬兄長,卻喜歡冒犯上司,那是很少有的;不喜歡冒犯上司,卻喜歡造反作亂的,那是不曾有過的。」
在春秋時代晚期,天下動盪不安、諸侯征戰不休,像造反作亂的事,早已司空見慣了。但那畢竟是百姓所害怕及厭惡的,怎麼辦呢?有子採用推溯原因的方法。要避免出現造反作亂的事,就要讓人們不要冒犯上司。因為哪裡有人從不冒犯上司卻去造反作亂的呢?這顯然不合常理。
接著,如何讓人們不去冒犯上司呢?再往源頭推溯,答案就是:要教導人們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在這裡,有子說的是「鮮」字,就是很少。這個「鮮」字用得好,「很少」並不是沒有。譬如有人既「孝」且「弟」,但在亂世中遇到壞的上司,怎麼辦呢?他如果冒犯這樣的上司,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就算太平盛世也有可能遇到不講理的、作惡的上司。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必多舉了。但無論如何,教導人們孝順父母與尊敬兄長,至少可以減少「犯上作亂」的事。
接著,再看有子的第二段話,他說:「君子要在根基上好好努力,根基穩固了,人生正途就會隨之展現出來。孝順父母與尊敬兄長,就是一個人做人的根基啊!」
這裡提到了君子,孔門弟子都知道「君子」是孔子所立下的人格典型,是人們效法的目標。我們在理解的時候,最好把君子理解成「立志成為君子的人」。它不只是一個名詞,更是一個動名詞,是正在進行式,也就是正在成為君子的人,而不是已經成為君子的人。正是因為把「君子」理解為「立志成為君子的人」,才需要接著強調「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等。我們在《論語》後續各章看到「君子」一詞,大都可以這樣理解。
有子這裡說的有道理:「君子要務本」,就是在根基上好好努力,然後「本立而道生」。怎麼說呢?這裡出現了「道」字,是指人生正途。「道」的原意是「路」,儒家關心人的社會,社會有其應循之路,所循合乎此路是有道,不然就是無道。像天下有道或無道,國君有道或無道等說法。因此,「道」字最好理解為正途或正路,而不只是單純的路。
這裡說的「本立而道生」,在邏輯上可以再分析一下。有子說的是:「若根本確立,則正途展現。」我們由此可以推論:一個人沒有找到或未能走上人生正路,那是因為他沒有確立根本。這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在人生經驗中也同樣正確。再從正面來看,「本立而道生」是說:一個人確立了根本,則人生正途展現出來。「道生」是正途展現出來,但展現出來並不等於已經走完了,中間還有漫長的努力過程。
最後的結論是「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在《論語》原文,這裡寫的是「仁」字。怎麼這裡忽然出現這個字呢?是不是寫錯了呢?古代很多學者認為仁義的「仁」與人類的「人」,這兩者(仁、人)可以通用。這一點可以參考。
但是對照本章第一句,「其為人也孝弟」,再看最後一句「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兩相對照就知道,最後這個「仁」字,應該是人類的「人」字。我們也不用去懷疑是不是寫錯了,有子如果講的是從前面人類的「人」,到最後講仁義的「仁」的話,就變成偷換概念了,因為全章裡面,沒有理由提到「仁」這個字。
有關孔子的學生對「仁」的理解,將來提出問題的很多,但沒有能夠說清楚的。所以,有子說的話代表他個人的心得,不能等同於孔子的思想。他的話前後對照,所說的是:要以「孝弟」為做人的根本,前面所說的「人」字,與後面所用的「仁」字,是同一個字或至少是同一個意思,統統指的是人類的「人」。
這樣一來,本篇的意思就比較清楚了。
做個悅樂的君子
《論語.學而篇》的第一章,原文是這樣的。
1.1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ㄩㄝˋ)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ㄩㄣˋ),不亦君子乎?」
【譯文】
孔子說:「學了做人處事的道理,並在適當的時候去實踐,不也覺得高興嗎?志趣相近的朋友從遠方來聚會,不也感到快樂嗎?別人不了解你,而你並不生氣,不也是君子的風度嗎?」
在本章,孔子連續說了三句話都以「問句」結束。孔子不知道答案嗎?不是的,他是要學生想一想,情況是不是如此。所以這裡反映了孔子對學生的期許,希望他們可以成為「悅樂的君子」。
我們依序來看。
第一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關於「學」這個字,我們想到三點:學什麼?如何學?為何學?
首先,學什麼?就是學習的內容。歷史學家錢穆有一個簡單的分法可以參考。他說:「中國文化五千年,孔子之前2500年;孔子之後到今天2500年。」所以在孔子的時代,如果問學什麼,前面有古人豐富的知識與技能,如五經與六藝。
五經是《詩》、《書》、《易》、《禮》、《樂》,包括了古代的文學、歷史、哲學、社會規範、音樂藝術。在技能方面主要是指六藝:禮、樂、射箭、駕車、書寫、計算。「禮」與「樂」兩邊都有,代表它們有知識的部分也有技能的部分,所以學起來就特別不容易了。
其次,如何學?就是學習的方法。孔子特別指出:要配合「思考」,「學」與「思」並重。孔子認為:學習而不思考,則將毫無領悟;思考而不學習,就會陷於迷惑。(〈為政2.15〉)
譬如,你專心學習,把《論語》背誦下來,但不去思考:這句話什麼意思?為什麼這樣說?他說的對嗎?對我今天有什麼啟發?你不做這樣的思考,永遠是只能背書,很容易就忘記了。但是,也不能全靠思考,全靠思考而不去向老師請教、向書本學習,那麼只能想著每天發生的事、各種八卦消息,想了半天只會覺得迷惑:為什麼善惡沒有報應?為什麼有些人得意?有些人失意?如此難免陷於迷惑了。這是談到學習的方法。
然後,為何學?這就涉及學習的目的了。學習的目的很多,包括前面說的,學會知識與技能。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有一次,魯國國君問孔子說:「你教這麼多學生,有哪幾位是好學的?」孔子說:「只有一位,顏回。」接著,孔子用六個字肯定顏回的好學。他說的不是考試第一,升學順利。他說的是「不遷怒,不貳過」。顏回不把怒氣發洩在不相干的人身上,也從不重複犯同樣的過錯。(〈雍也6.3〉)
由此可知,「好學」與「修德」是一體之兩面,有如「知」與「行」應該合一。所以整體來看,孔子所謂的「學」,包括了所有做人處事的道理。
那麼,「學」了之後呢?後面出現「習」字。「習」是指實踐。要身體力行,也包括由練習而熟能生巧,讓自己成為能知能行的人才。接著,學而時習之的「時」是什麼意思?我們以前對孔子的誤會往往來自這裡,以為孔子要學生時常復習功課。
問題在於:「時」是指「時常」嗎?在《論語》中,「時」字出現11次,其中3次與時間有關,所指的是季節,譬如四時(〈陽貨17.19〉);或配合天時的曆法,像夏朝的曆法(〈衛靈公15.11〉);或人生的階段,如少年之時(〈季氏16.7〉)。另外,有 7 次與「適當的時候」有關,譬如孔子談到在「適當的時候」說話,別人不討厭你的說話(〈憲問14.13〉);命令百姓服勞役,要選在「適當的時候」(〈學而1.5〉);喜歡做事而屢次錯過「適當的時候」(〈陽貨17.1〉)等。
換言之,「時」字在《論語》沒有用作「時常」來講的。因此,學而時習之的「時」字,應該是指「適當的時候」。譬如你學了孝順,要在與父母相處的時候去實踐;學了守信,要在與朋友往來的時候去實踐;學了射箭或駕車,要在運動場上的時候去練習。
事實上,做任何事都有適當的時候,而對「時」的判斷,已經成為孔子的標誌了。後來,孟子推崇孔子為「聖之時者」,就是聖人之中最重視時宜的(《孟子.萬章下》)。因此,這裡孔子的意思是:「學了做人處事的道理,並在適當的時候去實踐,不也覺得高興嗎?」你如果照孔子所說的去做,在知識、能力、德行方面,都會有更深的心得、體悟與提升,如此內心自然會覺得充實而喜悅高興了。
接著看第二句,「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第一句說的「悅」,是自己心裡高興;這一句說的「樂」,就表現出來了,眉開眼笑、氣氛歡樂。那麼,「有朋自遠方來」是什麼情況呢?
我們現在習慣說「朋友」二字,《論語》也已經這麼用了,「朋友」二字出現8次。如果分開使用的話,古代有一種說法: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但是,不論是同門的「朋」或同志的「友」,都是指在思想上接近,並在志趣上相投的人。然後要問:為什麼從遠方來的朋友會讓你特別快樂呢?因為他在遠方,處於不同的甚至外國的社會人群中。如果他還能保持與我相似的思想與志趣,那就代表我們所肯定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是正確的。我們可以繼續依此在人生正路上攜手並進。朋友之間有心靈的共鳴,又能互相印證及分享人生的體悟,豈不是一大樂事?所以,孔子這裡說的是:「志趣相近的朋友從遠方來聚會,不也感到快樂嗎?」
最後,再看第三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一個人學習有了心得,具備基本的知識、能力與德行,成為有用的人才。他又能與遠方來的朋友相互切磋、彼此肯定,產生更大的自信,這時當然希望實至名歸,得到人們的了解與讚賞,進而有機會從政服務百姓。但是,在主觀期許與客觀現實之間有了差距,難免會覺得委屈與無奈,所以孔子提醒學生:別人不了解你,而你並不生氣,不也是君子的風度嗎?
這裡要問的是:君子何所指?「君子」一詞,原意是「君之子」,指古代統治階級的子弟。後來,用來指稱在德行方面可以做為表率的傑出人物。在《論語》中,「君子」一詞出現107次,是孔子所肯定的人格典型,也是他鼓勵弟子們去追求的修養目標。
那麼,為什麼「人不知而不慍」可以代表君子的風度呢?因為君子所要求的是自己,所實踐的是道義。如果時運不濟或天下無道,那就更加努力修養自己,何必為此而有情緒上的波動呢?我們從本章學到了什麼?學到了孔子對弟子的教導。他期許大家互相勉勵,努力做一個悅樂的君子。
2〈學而篇1.2〉
做人以孝弟為本
《論語.學而篇》第二章,原文如下:
1.2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ㄊㄧˋ),而好(ㄏㄠˋ)犯上者,鮮(ㄒㄧㄢˇ)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ㄩˊ)!」
【譯文】
有子說:「一個人能做到孝順父母與尊敬兄長,卻喜歡冒犯上司的,那是很少有的;不喜歡冒犯上司,卻喜歡造反作亂的,那是不曾有過的。君子要在根基上努力,根基穩固了,人生正途就會隨之展現開來。孝順父母與尊敬兄長,就是一個人做人的根基啊!」
讀完本章,首先要說明的是:有子是誰?他是孔子的學生,原名有若,字子有,魯國人,小孔子三十三歲。有若既然字子有,為何在這裡稱有子呢?這一點,我們在引言第二集已經說過了,那是因為編輯《論語》的是孔子的第二代弟子,主要是有若與曾參的學生。學生在提到自己的老師時,必須尊稱為有子與曾子。
排在《論語》開頭〈學而篇〉的一共16章,其中8章直接記載孔子的話。然後,另外八章怎麼分配?有子占3章,曾子占2章,子貢占2章,子夏占1章。如果深入分析這麼分配的理由,可以說,有子與曾子是因為他們的學生在編輯,所以不但二人稱「子」,並且可以搶先上場排進第一篇。
至於子貢,則他是孔子三大弟子僅存的一位。而子夏呢?他後來成為著名的老師。孔子三大弟子中,另外兩位是他最親近、最器重的顏回與子路,沒有排上,那是因為他們比孔子還早過世,所以到了第二篇〈為政篇〉才有機會排上場。像這些背景資料,大致知道即可。
比較重要的,是我們在「引言第二集」提過的,念《論語》要分辨一章的重要性,可以分為四個層次。排在第四個層次的是:孔門弟子自己表述的話。弟子的話代表他們各自的心得,所說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與孔子的話相提並論。
為什麼要作這樣的區分呢?因為孔子的核心觀念「仁」在這一章結束時出現了。事實上,我們將一再看到,孔門弟子連最傑出的顏回在內,沒有一位可以說完全理解「仁」字,並作出清楚的論述。有子也不例外。因此仔細閱讀本章,就會看到最後出現的「仁」字,其實是開頭所說的人類的「人」字。
現在就來仔細閱讀吧!
有子的話可以分兩段來看:第一段是根據經驗而作的推論,第二段是簡單的結論。第一段在說什麼呢?他說:「一個人能做到孝順父母與尊敬兄長,卻喜歡冒犯上司,那是很少有的;不喜歡冒犯上司,卻喜歡造反作亂的,那是不曾有過的。」
在春秋時代晚期,天下動盪不安、諸侯征戰不休,像造反作亂的事,早已司空見慣了。但那畢竟是百姓所害怕及厭惡的,怎麼辦呢?有子採用推溯原因的方法。要避免出現造反作亂的事,就要讓人們不要冒犯上司。因為哪裡有人從不冒犯上司卻去造反作亂的呢?這顯然不合常理。
接著,如何讓人們不去冒犯上司呢?再往源頭推溯,答案就是:要教導人們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在這裡,有子說的是「鮮」字,就是很少。這個「鮮」字用得好,「很少」並不是沒有。譬如有人既「孝」且「弟」,但在亂世中遇到壞的上司,怎麼辦呢?他如果冒犯這樣的上司,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就算太平盛世也有可能遇到不講理的、作惡的上司。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必多舉了。但無論如何,教導人們孝順父母與尊敬兄長,至少可以減少「犯上作亂」的事。
接著,再看有子的第二段話,他說:「君子要在根基上好好努力,根基穩固了,人生正途就會隨之展現出來。孝順父母與尊敬兄長,就是一個人做人的根基啊!」
這裡提到了君子,孔門弟子都知道「君子」是孔子所立下的人格典型,是人們效法的目標。我們在理解的時候,最好把君子理解成「立志成為君子的人」。它不只是一個名詞,更是一個動名詞,是正在進行式,也就是正在成為君子的人,而不是已經成為君子的人。正是因為把「君子」理解為「立志成為君子的人」,才需要接著強調「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等。我們在《論語》後續各章看到「君子」一詞,大都可以這樣理解。
有子這裡說的有道理:「君子要務本」,就是在根基上好好努力,然後「本立而道生」。怎麼說呢?這裡出現了「道」字,是指人生正途。「道」的原意是「路」,儒家關心人的社會,社會有其應循之路,所循合乎此路是有道,不然就是無道。像天下有道或無道,國君有道或無道等說法。因此,「道」字最好理解為正途或正路,而不只是單純的路。
這裡說的「本立而道生」,在邏輯上可以再分析一下。有子說的是:「若根本確立,則正途展現。」我們由此可以推論:一個人沒有找到或未能走上人生正路,那是因為他沒有確立根本。這在邏輯上是正確的,在人生經驗中也同樣正確。再從正面來看,「本立而道生」是說:一個人確立了根本,則人生正途展現出來。「道生」是正途展現出來,但展現出來並不等於已經走完了,中間還有漫長的努力過程。
最後的結論是「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在《論語》原文,這裡寫的是「仁」字。怎麼這裡忽然出現這個字呢?是不是寫錯了呢?古代很多學者認為仁義的「仁」與人類的「人」,這兩者(仁、人)可以通用。這一點可以參考。
但是對照本章第一句,「其為人也孝弟」,再看最後一句「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兩相對照就知道,最後這個「仁」字,應該是人類的「人」字。我們也不用去懷疑是不是寫錯了,有子如果講的是從前面人類的「人」,到最後講仁義的「仁」的話,就變成偷換概念了,因為全章裡面,沒有理由提到「仁」這個字。
有關孔子的學生對「仁」的理解,將來提出問題的很多,但沒有能夠說清楚的。所以,有子說的話代表他個人的心得,不能等同於孔子的思想。他的話前後對照,所說的是:要以「孝弟」為做人的根本,前面所說的「人」字,與後面所用的「仁」字,是同一個字或至少是同一個意思,統統指的是人類的「人」。
這樣一來,本篇的意思就比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