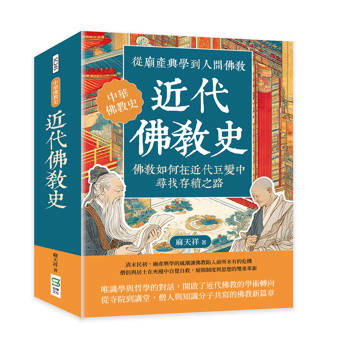一、學佛的思想基礎和社會根源
西元1814年,當龔自珍22歲的時候,天理教農民起義軍裡應外合,進襲皇宮,後雖失敗,但嘉慶皇帝卻為之驚恐不已。龔自珍針對當時百孔千瘡、行將就木的官僚政治,開始撰寫〈明良論〉,筆鋒直指封建君主專制與陳陳相因的科舉制度和「用人論資格之大略」,鋒芒畢露地抨擊時政。他說,京師之中「一日不再食者甚眾」,而「內外大小之臣,俱思全軀保室家,不復有所作為」。他們「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正是這些人,「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盡奄然而無有生氣」,活脫脫刻劃了士大夫飽食終日、庸碌無能、寡廉鮮恥、怠忽職守的形象。他還指出,由於這些人安富尊榮,不思進取,且不肯自行引退,致使「英才未盡之士,亦卒不得相代」,「賢智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一切都在無聲無息地腐爛,一切都在走向不可挽回的崩潰。他斷然指出:「當今之弊,抑或出於此。」他認為「一祖之法無不蔽,千夫之議無不靡」,因此要變。變則通,通則久,這就是結論。龔自珍以天下為己任,大聲疾呼改革時弊,修訂封建禮儀,廢除跪拜,由君臣坐而論道,共商國是;只有任人以才,不論資排輩,不以四書八股文章取士,才能打破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儘管這種願望僅僅是對舊制度的補綴和改良,但是已經隱隱地傳出了叛逆之音,展現了他的社會批判的思想畫面,也表露出他那「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忤」的怪傑、狂士的性格。也正是在這一年,其外祖父,著名的文字學家段玉裁,專門致書勸勉龔自珍「勿讀無益之書,勿作無用之文」,並指出有用之文是經,是史,要求他「博聞強記,多識蓄德,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翌年,段玉裁又以讚賞的口吻,評論〈明良論〉說:「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髦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他稱龔自珍為英俊之士,欣然之情溢於言表。但是,或許由於他已從龔的文章中嗅出桀驁不馴的氣味,隱約感到一種離經叛道的不祥之兆;或許是經驗之談,諄諄告誡外孫要側身仕途,博取高官,做一代名臣;要麼就潛心學問,為人師表;切莫效阮籍倡狂,承柳永之遺風,做玩世不恭的名士。然而歷史恰恰與他的願望相反,龔自珍不幸「浮堪郎署」,為俗務所累,後又動觸時忌,辭官南歸,既沒有當上轟轟烈烈、大刀闊斧改革時弊的名官,也沒有做聚徒講學、樹宗立說的一代宗師。他挾「非常可怪之論」,言滿天下,傷時罵世;或者「朝借一經覆以簦,暮還一經龕已燈」,在佛卷中不倦地漫遊,一變而為「正人君子」側目而視的呆子和狂士,終以名士了其一生。孔繡山在題《己亥雜詩》中,不無調侃地說:「戒詩以後詩還富,哀樂中年感倍增。值得江湖狂士笑,不攜名妓即名僧。」確實如段氏所望,龔自珍致力於名吏名師,卻以寄跡江湖的名士為歸宿,歷史向他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也啟示我們進行必要的思考──是佛教極樂淨土的信仰,還是釋氏說理縝密與龔氏文化心理的趨合?是社會環境的逼迫,還是名士的心理召感?
西元1814年,當龔自珍22歲的時候,天理教農民起義軍裡應外合,進襲皇宮,後雖失敗,但嘉慶皇帝卻為之驚恐不已。龔自珍針對當時百孔千瘡、行將就木的官僚政治,開始撰寫〈明良論〉,筆鋒直指封建君主專制與陳陳相因的科舉制度和「用人論資格之大略」,鋒芒畢露地抨擊時政。他說,京師之中「一日不再食者甚眾」,而「內外大小之臣,俱思全軀保室家,不復有所作為」。他們「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益近,則媚亦益工」。正是這些人,「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盡奄然而無有生氣」,活脫脫刻劃了士大夫飽食終日、庸碌無能、寡廉鮮恥、怠忽職守的形象。他還指出,由於這些人安富尊榮,不思進取,且不肯自行引退,致使「英才未盡之士,亦卒不得相代」,「賢智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一切都在無聲無息地腐爛,一切都在走向不可挽回的崩潰。他斷然指出:「當今之弊,抑或出於此。」他認為「一祖之法無不蔽,千夫之議無不靡」,因此要變。變則通,通則久,這就是結論。龔自珍以天下為己任,大聲疾呼改革時弊,修訂封建禮儀,廢除跪拜,由君臣坐而論道,共商國是;只有任人以才,不論資排輩,不以四書八股文章取士,才能打破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儘管這種願望僅僅是對舊制度的補綴和改良,但是已經隱隱地傳出了叛逆之音,展現了他的社會批判的思想畫面,也表露出他那「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忤」的怪傑、狂士的性格。也正是在這一年,其外祖父,著名的文字學家段玉裁,專門致書勸勉龔自珍「勿讀無益之書,勿作無用之文」,並指出有用之文是經,是史,要求他「博聞強記,多識蓄德,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翌年,段玉裁又以讚賞的口吻,評論〈明良論〉說:「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髦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他稱龔自珍為英俊之士,欣然之情溢於言表。但是,或許由於他已從龔的文章中嗅出桀驁不馴的氣味,隱約感到一種離經叛道的不祥之兆;或許是經驗之談,諄諄告誡外孫要側身仕途,博取高官,做一代名臣;要麼就潛心學問,為人師表;切莫效阮籍倡狂,承柳永之遺風,做玩世不恭的名士。然而歷史恰恰與他的願望相反,龔自珍不幸「浮堪郎署」,為俗務所累,後又動觸時忌,辭官南歸,既沒有當上轟轟烈烈、大刀闊斧改革時弊的名官,也沒有做聚徒講學、樹宗立說的一代宗師。他挾「非常可怪之論」,言滿天下,傷時罵世;或者「朝借一經覆以簦,暮還一經龕已燈」,在佛卷中不倦地漫遊,一變而為「正人君子」側目而視的呆子和狂士,終以名士了其一生。孔繡山在題《己亥雜詩》中,不無調侃地說:「戒詩以後詩還富,哀樂中年感倍增。值得江湖狂士笑,不攜名妓即名僧。」確實如段氏所望,龔自珍致力於名吏名師,卻以寄跡江湖的名士為歸宿,歷史向他們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也啟示我們進行必要的思考──是佛教極樂淨土的信仰,還是釋氏說理縝密與龔氏文化心理的趨合?是社會環境的逼迫,還是名士的心理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