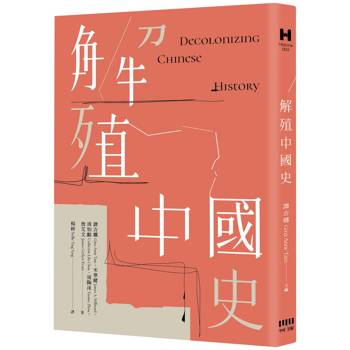第四章
多向度的離散:在全球種族清算時代書寫中國移民史
周陶沫 Taomo Zhou
解殖範式及其不滿
在On not speaking Chinese一書中,文化研究學者洪宜安(Ien Ang)將移民學者視為「戰術性的介入者」。他們通常並不提出反霸權的宏大主張,而是在那些被給定的「真理」之中點出矛盾與暴力。 本著這種精神,我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善加結合我在中國成長的生活經驗以及英文學術界的資源。正如詹姆斯.埃文斯的文章所言,「解殖」中國歷史研究是個雙重任務:既要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傳的敘事霸權,也要挑戰全球北方對知識生產的壟斷。若沒有中國學者的參與,當前的「解殖」運動只會像殖民主義一樣,再次成為一場西方的工程。
研討會中其他學者們的論文非漢族國家、臺灣、香港、以及毛派組織在印度和秘魯等地的歷史敘事,並解構了它們的中國中心視角。但英語世界高度壟學術聲望仍是個待處理的課題,這造成那些接受中文學術訓練、並用中文寫作、教學的學者,始終受到全球學術網絡的邊緣化。正如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所言,「每個人的發聲位置都取決於全球權力分布」。作為一位在美國受訓、現於新加坡工作的學者,我深知我受到體制的充分保護,因此沒有資格為那些在高壓政治與畸形化的知識生產下保持深刻反思韌性的中國知識分子代言,但我希望能藉此機會邀請大家關注我們所面對的複雜現實。
我們這番對中國歷史的討論,很大程度上受到北美社會正義運動的啟發。「解殖」的本義是「使殖民地成為在政治與經濟上能自我主導的自治實體」,但這個詞的內涵在過去幾年間已經超出了原指。在教育與文化語境下,「解殖」通常泛指透過質疑歐洲中心的知識生產為被邊緣化的群體賦能。為了避免歧義,我將這個擴展過的概念稱為「解殖範式」。
在華人移民研究中,文學學者史書美率先用「殖民主義」描述中共對「中國認同」的整肅,指的是中共用一種對「中國」的單一想像覆寫全球各地多樣化的中國認同。她在二○一一年便寫道:「中國境內外有不少被邊緣化的作家與藝術家,都曾對中國中心主義與中國的霸權呼聲提出批判。他們認為這是那些掌握身分決定權的人們強加的殖民暴行。」
和其他許多學者一樣,史書美有充分理由對中國在經濟與地緣政治上的崛起、及其對海外華人日益積極的動員感到警惕。在習近平政府的官方話語中,無論海外華人在中國境外開枝散葉了幾代,他們永遠承擔著「共同的中華民族之根、共同的中華文化之魂,以及共同的中華民族復興之夢」。
既然解殖範式在歐美語境中如此流行,我們這些英文世界的中國歷史學者是否也該用它來批判中國呢?更具體地說,解殖範式是否能幫助我們撼動血緣、世系本位的中國文明論述?它是否能幫助我們對抗一個認為同種必然同文、並強迫對單一祖國輸誠的中國政府?
在本文中,我主張當代西方公共論述對「解殖」一詞的濫用已稀釋了它的解釋效力,將它從原生語境移植到迥異的社會脈絡未必有助於分析。在這點上,我與奧盧費米.泰伊沃、伊芙.塔克與韋恩.楊等學者及社會活動家觀點一致。我們都認為「太隨易地吸收、轉用」這個術語,只是在「粗疏地描述完客觀事件」後,冠上解殖範式這個「包山包海的修辭」。如果中國政府對「族群歸屬」本質主義式的粗暴理解是我們批判的對象,那麼一套同樣肆意簡化歷史的思維框架很難成為有用的批判工具。
更重要的是,解殖範式創造出一種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假性二元對立,例如一個位居中心的專制中國對立於香港、臺灣等邊陲的進步政權,或是單一化的「中國大陸人」對照於多采多姿的海外華人社群。解殖範式可能適得其反地將中共的本質主義史觀替換成另一種「威權中國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相提並論」的本質主義。從冷戰時期到可以稱為「冷戰二‧○」的今日,無論是北京當局對美國境內反亞裔仇恨罪的譴責,或是西方對中國大規模監禁少數民族的批判,雙邊民族主義者都經常以種族作為交火的彈藥。這種政治修辭被人權律師滕彪稱為「比爛主義」(whataboutism),它的思路就是「把美國(或任何其它西方國家)與中國發生的事描述為各自獨立的兩碼事,最後在等式兩邊互相抵銷」。
我們將在後文中看到,率先對「中國性」的民族主義敘事發難的,是英文世界的華人移民研究者。或許,我們不必停留在將海外華人與中國做概念上的區隔。身為用英文研究華人移民的學者,我們更可以利用自身的特殊位置,幫助歐美公眾將中國與海外華人理解為一個「動態的、持續變化的過程」。為此,也許我們不該全然放棄那個備受爭議的術語「離散」(diaspora)。畢竟,東南亞的解殖過程本身就創造了某些促使華人向中國離散的複雜歷史條件;而今日,那些「回到」中國的東南亞華人也善用其多重身分,靈活經營與多個祖國的關係。正如我將在下文討論的,中國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政策並非單線敘事,海外華人的遷徙路徑也並不總是單向輸出。而海外華人的政治認同,更未必總是一條從遠距離民族主義走向同化的線性旅程。
從「是否離散?」到「如何離散?」
怎麼定義自己研究的對象,一直是華人移民學者爭論不休的課題。此一領域的權威學者王賡武就認為「離散」(diaspora)一詞無條件地假設「中國」是所有具華人血統者的家園,忽視了華人在多元地緣條件下建構新身分、形成新社群的能動性,因此避免使用這個詞彙。隨意使用「離散中國人」一詞是危險的,因為它暗示了中共與全球華人之間存在某種政治紐帶。正如歷史學家許慧玲(Madeline Hsu)所言:「這種危險可能來自將海外華人培養成國家發展資源的中國政府,也可能來自擔心這種狀況、因此將華人移民視為潛在威脅的其他族裔。」史書美更進一步指出,「離散」是對華人昔日定居殖民的委婉說詞,也是中國政府當下動員海外華人的修辭工具。
出於對這種離散的抗衡,史書美提出了「華語語系」(Sinophone)這個反霸權的文化空間概念,指的是「位於中國及『中國性』邊緣的華語文化與社群」。這個概念的核心在於拒絕對中共的認同,轉而強調在地歸屬。史書美寫道,華語語系文化在任何民族國家「都是該國多元文化與多語社會的一部分」,比方說「美國華語語系文化就是美國文化」。她的理論對歷史學界有重大影響。例如,瑞秋.羅(Rachael Leow)與蔡秀敏(Sai Siew Min)的近期研究就從性別角度出發,批判了華人父權體制如何延續宗族源自祖籍、從未中斷的世系神話。
中國在全球政經格局中的角色,也持續影響英語學界的海外華人研究。在北美,海外華人歷史最初被視為中國研究的延伸。東南亞的反共與排華暴力、美國民權運動等都促成了研究模式迭代,使海外華人的經歷逐漸被視為所在國歷史一部分。美國長期擔心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勝利後,東南亞華人社群將集體成為北京的「第五縱隊」,而上述的史學轉向及對在地歸屬的強調,正與這種骨牌效應邏輯相抗衡。鄧小平改革開放後,跨越民族國家疆界的華人身分與網絡,在史學界的「跨國轉向」下成為爆炸性成長的研究焦點。華語語系研究大力推動中國性與中國的脫鉤,也預示了當前美國與中國之間正在發生的脫鉤。隨著千禧時代全球化高峰期的樂觀情緒消退,不確定性與危機感使得許多海外華人更傾向將自己定位為已融入所在國的少數群體,而不願在政治上與中國強行綁定。
華語語系固然豐富了我們對全球華人社群多樣性與駁雜性的討論,史書美的「排除式取徑」卻可能失於偏頗,也可能限制我們探索跨國連結的可能性。當我們歌頌海外華人的多樣性、適應力與應變能力,中國大陸漢人卻可能被描繪為面目單一的國家順民。不同於史書美提出的「與中國脫鉤」,文學學者王德威主張一種更為寬泛、容得下中國大陸作家的華語語系研究。同樣地,歷史學家龔建文也勾勒出了一個範圍更宏大、從臺灣延及菲律賓的「華語語系歷史」。
或許我們可以將贊成或反對離散的是非題轉換為「如果離散」和「如何離散」的申論題。洪宜安曾寫道:「血統讓我無可避免地生為中國人,但我只在某些時刻才自願成為中國人。至於何時成為、如何成為,則是個政治問題。」什麼因素、哪些情況會讓中國政府選擇承認或否認海外華人的中國身分?反過來說,又是怎樣的動機、怎樣的歷史情境,會驅使個人選擇親附中國或保持距離?
(全文未完)
多向度的離散:在全球種族清算時代書寫中國移民史
周陶沫 Taomo Zhou
解殖範式及其不滿
在On not speaking Chinese一書中,文化研究學者洪宜安(Ien Ang)將移民學者視為「戰術性的介入者」。他們通常並不提出反霸權的宏大主張,而是在那些被給定的「真理」之中點出矛盾與暴力。 本著這種精神,我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善加結合我在中國成長的生活經驗以及英文學術界的資源。正如詹姆斯.埃文斯的文章所言,「解殖」中國歷史研究是個雙重任務:既要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傳的敘事霸權,也要挑戰全球北方對知識生產的壟斷。若沒有中國學者的參與,當前的「解殖」運動只會像殖民主義一樣,再次成為一場西方的工程。
研討會中其他學者們的論文非漢族國家、臺灣、香港、以及毛派組織在印度和秘魯等地的歷史敘事,並解構了它們的中國中心視角。但英語世界高度壟學術聲望仍是個待處理的課題,這造成那些接受中文學術訓練、並用中文寫作、教學的學者,始終受到全球學術網絡的邊緣化。正如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所言,「每個人的發聲位置都取決於全球權力分布」。作為一位在美國受訓、現於新加坡工作的學者,我深知我受到體制的充分保護,因此沒有資格為那些在高壓政治與畸形化的知識生產下保持深刻反思韌性的中國知識分子代言,但我希望能藉此機會邀請大家關注我們所面對的複雜現實。
我們這番對中國歷史的討論,很大程度上受到北美社會正義運動的啟發。「解殖」的本義是「使殖民地成為在政治與經濟上能自我主導的自治實體」,但這個詞的內涵在過去幾年間已經超出了原指。在教育與文化語境下,「解殖」通常泛指透過質疑歐洲中心的知識生產為被邊緣化的群體賦能。為了避免歧義,我將這個擴展過的概念稱為「解殖範式」。
在華人移民研究中,文學學者史書美率先用「殖民主義」描述中共對「中國認同」的整肅,指的是中共用一種對「中國」的單一想像覆寫全球各地多樣化的中國認同。她在二○一一年便寫道:「中國境內外有不少被邊緣化的作家與藝術家,都曾對中國中心主義與中國的霸權呼聲提出批判。他們認為這是那些掌握身分決定權的人們強加的殖民暴行。」
和其他許多學者一樣,史書美有充分理由對中國在經濟與地緣政治上的崛起、及其對海外華人日益積極的動員感到警惕。在習近平政府的官方話語中,無論海外華人在中國境外開枝散葉了幾代,他們永遠承擔著「共同的中華民族之根、共同的中華文化之魂,以及共同的中華民族復興之夢」。
既然解殖範式在歐美語境中如此流行,我們這些英文世界的中國歷史學者是否也該用它來批判中國呢?更具體地說,解殖範式是否能幫助我們撼動血緣、世系本位的中國文明論述?它是否能幫助我們對抗一個認為同種必然同文、並強迫對單一祖國輸誠的中國政府?
在本文中,我主張當代西方公共論述對「解殖」一詞的濫用已稀釋了它的解釋效力,將它從原生語境移植到迥異的社會脈絡未必有助於分析。在這點上,我與奧盧費米.泰伊沃、伊芙.塔克與韋恩.楊等學者及社會活動家觀點一致。我們都認為「太隨易地吸收、轉用」這個術語,只是在「粗疏地描述完客觀事件」後,冠上解殖範式這個「包山包海的修辭」。如果中國政府對「族群歸屬」本質主義式的粗暴理解是我們批判的對象,那麼一套同樣肆意簡化歷史的思維框架很難成為有用的批判工具。
更重要的是,解殖範式創造出一種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假性二元對立,例如一個位居中心的專制中國對立於香港、臺灣等邊陲的進步政權,或是單一化的「中國大陸人」對照於多采多姿的海外華人社群。解殖範式可能適得其反地將中共的本質主義史觀替換成另一種「威權中國不能與自由民主國家相提並論」的本質主義。從冷戰時期到可以稱為「冷戰二‧○」的今日,無論是北京當局對美國境內反亞裔仇恨罪的譴責,或是西方對中國大規模監禁少數民族的批判,雙邊民族主義者都經常以種族作為交火的彈藥。這種政治修辭被人權律師滕彪稱為「比爛主義」(whataboutism),它的思路就是「把美國(或任何其它西方國家)與中國發生的事描述為各自獨立的兩碼事,最後在等式兩邊互相抵銷」。
我們將在後文中看到,率先對「中國性」的民族主義敘事發難的,是英文世界的華人移民研究者。或許,我們不必停留在將海外華人與中國做概念上的區隔。身為用英文研究華人移民的學者,我們更可以利用自身的特殊位置,幫助歐美公眾將中國與海外華人理解為一個「動態的、持續變化的過程」。為此,也許我們不該全然放棄那個備受爭議的術語「離散」(diaspora)。畢竟,東南亞的解殖過程本身就創造了某些促使華人向中國離散的複雜歷史條件;而今日,那些「回到」中國的東南亞華人也善用其多重身分,靈活經營與多個祖國的關係。正如我將在下文討論的,中國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政策並非單線敘事,海外華人的遷徙路徑也並不總是單向輸出。而海外華人的政治認同,更未必總是一條從遠距離民族主義走向同化的線性旅程。
從「是否離散?」到「如何離散?」
怎麼定義自己研究的對象,一直是華人移民學者爭論不休的課題。此一領域的權威學者王賡武就認為「離散」(diaspora)一詞無條件地假設「中國」是所有具華人血統者的家園,忽視了華人在多元地緣條件下建構新身分、形成新社群的能動性,因此避免使用這個詞彙。隨意使用「離散中國人」一詞是危險的,因為它暗示了中共與全球華人之間存在某種政治紐帶。正如歷史學家許慧玲(Madeline Hsu)所言:「這種危險可能來自將海外華人培養成國家發展資源的中國政府,也可能來自擔心這種狀況、因此將華人移民視為潛在威脅的其他族裔。」史書美更進一步指出,「離散」是對華人昔日定居殖民的委婉說詞,也是中國政府當下動員海外華人的修辭工具。
出於對這種離散的抗衡,史書美提出了「華語語系」(Sinophone)這個反霸權的文化空間概念,指的是「位於中國及『中國性』邊緣的華語文化與社群」。這個概念的核心在於拒絕對中共的認同,轉而強調在地歸屬。史書美寫道,華語語系文化在任何民族國家「都是該國多元文化與多語社會的一部分」,比方說「美國華語語系文化就是美國文化」。她的理論對歷史學界有重大影響。例如,瑞秋.羅(Rachael Leow)與蔡秀敏(Sai Siew Min)的近期研究就從性別角度出發,批判了華人父權體制如何延續宗族源自祖籍、從未中斷的世系神話。
中國在全球政經格局中的角色,也持續影響英語學界的海外華人研究。在北美,海外華人歷史最初被視為中國研究的延伸。東南亞的反共與排華暴力、美國民權運動等都促成了研究模式迭代,使海外華人的經歷逐漸被視為所在國歷史一部分。美國長期擔心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勝利後,東南亞華人社群將集體成為北京的「第五縱隊」,而上述的史學轉向及對在地歸屬的強調,正與這種骨牌效應邏輯相抗衡。鄧小平改革開放後,跨越民族國家疆界的華人身分與網絡,在史學界的「跨國轉向」下成為爆炸性成長的研究焦點。華語語系研究大力推動中國性與中國的脫鉤,也預示了當前美國與中國之間正在發生的脫鉤。隨著千禧時代全球化高峰期的樂觀情緒消退,不確定性與危機感使得許多海外華人更傾向將自己定位為已融入所在國的少數群體,而不願在政治上與中國強行綁定。
華語語系固然豐富了我們對全球華人社群多樣性與駁雜性的討論,史書美的「排除式取徑」卻可能失於偏頗,也可能限制我們探索跨國連結的可能性。當我們歌頌海外華人的多樣性、適應力與應變能力,中國大陸漢人卻可能被描繪為面目單一的國家順民。不同於史書美提出的「與中國脫鉤」,文學學者王德威主張一種更為寬泛、容得下中國大陸作家的華語語系研究。同樣地,歷史學家龔建文也勾勒出了一個範圍更宏大、從臺灣延及菲律賓的「華語語系歷史」。
或許我們可以將贊成或反對離散的是非題轉換為「如果離散」和「如何離散」的申論題。洪宜安曾寫道:「血統讓我無可避免地生為中國人,但我只在某些時刻才自願成為中國人。至於何時成為、如何成為,則是個政治問題。」什麼因素、哪些情況會讓中國政府選擇承認或否認海外華人的中國身分?反過來說,又是怎樣的動機、怎樣的歷史情境,會驅使個人選擇親附中國或保持距離?
(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