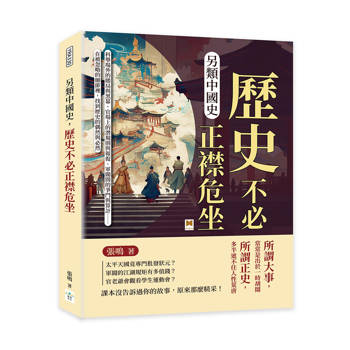不規矩的歷史
有個說法是宗教改革跟文藝復興,是擺脫封建桎梏,導致資本主義興起的一大因素。由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因此也成為了進步的象徵。因此,在我們的意識中,文藝復興形成的人文主義思潮,是和新教倫理相輔相成的,而信仰新教的地區,都應該是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的。新教是進步的,作為對立面,天主教則是保守的。
可惜,歷史從來不按歷史學家的規矩行事。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興起,實際上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場道德革新運動。他們反對羅馬教廷的腐敗和奢華,順便反對了跟這種腐敗奢華相伴而生的文藝復興。非宗教的人文主義精神,強調人欲的人學,跟新教格格不入。在最為嚴厲的喀爾文教派中,這樣的思想和行為,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如果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和喬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生活在喀爾文統治的日內瓦,命運只有一個,就是被活活燒死。那時的日內瓦,所有人都必須過一種令人窒息的禁慾生活,所有能引起人們感官愉悅的色彩和音樂,都被加以嚴格的限制,如果人們被發現有一點點出格的娛樂活動,就很容易被人告發,而遭到嚴厲懲處,直至火刑。路德教派雖然相對比喀爾文教派寬容一點,但生活的禁慾和刻板,也是一樣的。唯一的反例,是新教允許神職人員(新教稱牧師)結婚。但是,新教牧師婚姻,無非是給人們一個模範,目的是讓所有人都按牧師的標準生活。現在看當年新教初興時期的繪畫,裡面的男男女女,從頭到腳,都包裹得嚴嚴實實,衣服鞋帽無作黑白兩色,人人表情嚴肅呆板。真的沒辦法想像,這些人當年是怎樣做愛的。
相反,最早的文藝復興,背後的支持者,既有義大利的城邦,也有羅馬教廷。現在留下的那麼多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傑作,不有很多都是為教廷做的壁畫和雕塑嗎?教廷所屬的神職人員,雖然不能結婚,卻從不缺乏情人。在男女之事方面,當年的羅馬教廷和後來的天主教,絕對要比新教開放不知多少倍。人的欲望不能得到肯定,資本主義多半是沒戲的。就算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說得對,新教倫理那種上帝選民的概念,啟用了人們爭做選民進行世俗的努力,從而發奮工作。如果社會中所有的人都像清教徒這樣生活,消費怎麼能提升呢?消費上不去,東西生產了,要賣給誰呢?別說歐洲的手工業產品沒人買,地理大發現帶來的各種奢侈的消費,東方的絲綢、茶葉、香料、瓷器以及金銀器,誰肯買呢?說到底,工商業的下面,基礎就是人欲,人的欲望被壓抑了,工商業怎麼可能發展呢?
所以,新教崛起之後,工商業發達的地區,未必就一定信仰新教,而信仰「保守的」天主教的,也有商業繁盛的都市,比如巴黎。路德教派在經濟停滯的北日耳曼聯邦地區,傳播得相當順利。傳統的農業地區像蘇格蘭、波蘭和匈牙利,也有不少的喀爾文教派信徒。宗教改革後的天主教,成立了宗教異端裁判所,做了很多令人髮指的事。但他們未必是想阻止科學技術的進步,更在意的倒是宗教體系的完整。他們做的事,新教徒也會做。發現了血液循環的科學家米格爾.塞爾韋特(Michael Servetus),不也是被喀爾文送上了火刑柱嗎?至少,羅馬的宗教裁判所,還沒有燒死伽利略.伽利萊(Galileo Galilei)。在後人眼裡屬於十分保守的耶穌會士,也不是一點好事沒做。在中國,最早把西方近代文化、幾何學、地理發現和火藥製作技術傳入的傳教士,都是耶穌會士。
近代中國,新教給人的印象更為開放和進步,多半是因為新教人士熱衷於跟中國士大夫接觸,在士大夫中的口碑比較好。其實,天主教在傳播西方文化、發展教育方面,也一樣有積極性。在中小學層面上,天主教辦的學校顯然要更多。
宗教跟歷史進步的關係,相當複雜,沒辦法按照某種規則的框框來描繪。刻板地將某一部分人劃為保守勢力,另一部分人劃為進步勢力,讓他們互相打架,然後把歷史描繪成進步戰勝落後、先進戰勝保守的過程,理解起來固然方便,但有時往往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歷史是人創造出來的,人是複雜的,歷史也是複雜的。沒辦法,它就那麼不規矩。
有個說法是宗教改革跟文藝復興,是擺脫封建桎梏,導致資本主義興起的一大因素。由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因此也成為了進步的象徵。因此,在我們的意識中,文藝復興形成的人文主義思潮,是和新教倫理相輔相成的,而信仰新教的地區,都應該是資本主義工商業比較發達的。新教是進步的,作為對立面,天主教則是保守的。
可惜,歷史從來不按歷史學家的規矩行事。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興起,實際上是基督教世界的一場道德革新運動。他們反對羅馬教廷的腐敗和奢華,順便反對了跟這種腐敗奢華相伴而生的文藝復興。非宗教的人文主義精神,強調人欲的人學,跟新教格格不入。在最為嚴厲的喀爾文教派中,這樣的思想和行為,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如果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和喬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生活在喀爾文統治的日內瓦,命運只有一個,就是被活活燒死。那時的日內瓦,所有人都必須過一種令人窒息的禁慾生活,所有能引起人們感官愉悅的色彩和音樂,都被加以嚴格的限制,如果人們被發現有一點點出格的娛樂活動,就很容易被人告發,而遭到嚴厲懲處,直至火刑。路德教派雖然相對比喀爾文教派寬容一點,但生活的禁慾和刻板,也是一樣的。唯一的反例,是新教允許神職人員(新教稱牧師)結婚。但是,新教牧師婚姻,無非是給人們一個模範,目的是讓所有人都按牧師的標準生活。現在看當年新教初興時期的繪畫,裡面的男男女女,從頭到腳,都包裹得嚴嚴實實,衣服鞋帽無作黑白兩色,人人表情嚴肅呆板。真的沒辦法想像,這些人當年是怎樣做愛的。
相反,最早的文藝復興,背後的支持者,既有義大利的城邦,也有羅馬教廷。現在留下的那麼多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傑作,不有很多都是為教廷做的壁畫和雕塑嗎?教廷所屬的神職人員,雖然不能結婚,卻從不缺乏情人。在男女之事方面,當年的羅馬教廷和後來的天主教,絕對要比新教開放不知多少倍。人的欲望不能得到肯定,資本主義多半是沒戲的。就算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說得對,新教倫理那種上帝選民的概念,啟用了人們爭做選民進行世俗的努力,從而發奮工作。如果社會中所有的人都像清教徒這樣生活,消費怎麼能提升呢?消費上不去,東西生產了,要賣給誰呢?別說歐洲的手工業產品沒人買,地理大發現帶來的各種奢侈的消費,東方的絲綢、茶葉、香料、瓷器以及金銀器,誰肯買呢?說到底,工商業的下面,基礎就是人欲,人的欲望被壓抑了,工商業怎麼可能發展呢?
所以,新教崛起之後,工商業發達的地區,未必就一定信仰新教,而信仰「保守的」天主教的,也有商業繁盛的都市,比如巴黎。路德教派在經濟停滯的北日耳曼聯邦地區,傳播得相當順利。傳統的農業地區像蘇格蘭、波蘭和匈牙利,也有不少的喀爾文教派信徒。宗教改革後的天主教,成立了宗教異端裁判所,做了很多令人髮指的事。但他們未必是想阻止科學技術的進步,更在意的倒是宗教體系的完整。他們做的事,新教徒也會做。發現了血液循環的科學家米格爾.塞爾韋特(Michael Servetus),不也是被喀爾文送上了火刑柱嗎?至少,羅馬的宗教裁判所,還沒有燒死伽利略.伽利萊(Galileo Galilei)。在後人眼裡屬於十分保守的耶穌會士,也不是一點好事沒做。在中國,最早把西方近代文化、幾何學、地理發現和火藥製作技術傳入的傳教士,都是耶穌會士。
近代中國,新教給人的印象更為開放和進步,多半是因為新教人士熱衷於跟中國士大夫接觸,在士大夫中的口碑比較好。其實,天主教在傳播西方文化、發展教育方面,也一樣有積極性。在中小學層面上,天主教辦的學校顯然要更多。
宗教跟歷史進步的關係,相當複雜,沒辦法按照某種規則的框框來描繪。刻板地將某一部分人劃為保守勢力,另一部分人劃為進步勢力,讓他們互相打架,然後把歷史描繪成進步戰勝落後、先進戰勝保守的過程,理解起來固然方便,但有時往往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歷史是人創造出來的,人是複雜的,歷史也是複雜的。沒辦法,它就那麼不規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