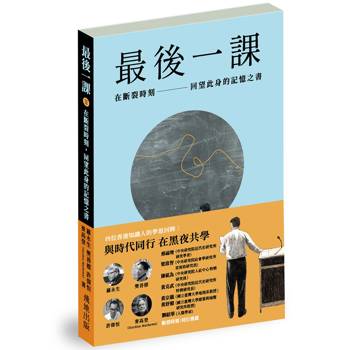編輯序:此處曾有光
◉ 張潔平(飛地出版總編輯)
如果整個課堂,和它所存在的社會處境、整段時光,都消失不見,為什麼還要執著於「最後一課」?
當編輯台收到一篇篇文章時,我們常常在想這問題。他們中的許多人,並沒有機會在講堂上完成自己的「最後一課」。生命裡親歷的驚心動魄,與歷史浪潮中的觀念起伏,他們只得在文章裡娓娓道來。這樣「最後一課」裡的老師,和平時不太一樣。
書寫這一課的老師們,知道自己正在做出選擇。他們不只是被動地保存過去,也是站在此刻的抵抗 —— 抵抗遺憾,抵抗遺忘,抵抗被取消。
而這抵抗的核心,正是通過記憶,直指未來。
為什麼記住?記憶是身份的土壤,是意義的錨點。當一段歷史、一種精神被連根拔起,記憶成為我們重建連結的唯一線索。教學者的「最後一課」,不只是他們個人的告別,也是一整代香港知識人集體經歷的突然斷章。如果我們遺忘,斷裂的不僅是某個人的教學生涯,也是一整個時代的精神譜系——那種在課堂上與社會中同時踐行理念的方式,那種師生並肩面對歷史的勇氣。
記憶賦予「曾經存在」以尊嚴。但它並非懷舊的感傷。
留下「最後一課」,並不是懷念美好舊時光。它記錄的恰恰是那些無法被美化、正在思辨的掙扎,與行動在疼痛中的突然中止。它要讓那些被迫提前退場的人,不被簡化、不被扭曲地留在集體意識中,誠實面對歷史的複雜檢視。它不必被供奉,也不提供慰藉,而是要求承擔。
留下最後一課,是希望留下一把拒絕讓我們安於現狀的鑰匙,一個叩問當下的尖銳問題。那些在課堂中被中斷的對話,在我們當下的閱讀與思考中,因此得以延續。
這也是記憶正義的一部分——它要求我們不只是「記得」,而是以怎樣的方式記得。
記憶於未來是有用的。當一個時代被系統性遺忘,未來的人們將失去理解自身處境的歷史坐標,他們遭遇不公時,會以為那是前所未有的創痛,或命中註定的常態。他們將失去描述現實的語言和想像另一種可能的詞彙——正如我們曾經失去過的。
因此,記憶正是為未來保存一份至關重要的「認知底稿」與「可能性檔案」。當未來的某一天,有人再度追問「為什麼我們不能有另一種活法」時,這些被保存的記憶將作出回應:曾經有人如此生活、如此思考、如此相信過。這份記憶本身,就否定了「當下即永恆」的謊言,為未來的改變提供了歷史的依據與勇氣。
如此,我們今日埋下的記憶,便不是墓碑,而是路標。它或許不能指明一條確定的坦途,但它堅定地告訴走在未來暗夜裡的人們:你們此刻站立的地方,曾經有光。而光,來過一次,就可以再來。
願我們不只是記得。願我們在記憶中辨認出正義的尺度,在耕種時明白種子來自何方。
◉ 張潔平(飛地出版總編輯)
如果整個課堂,和它所存在的社會處境、整段時光,都消失不見,為什麼還要執著於「最後一課」?
當編輯台收到一篇篇文章時,我們常常在想這問題。他們中的許多人,並沒有機會在講堂上完成自己的「最後一課」。生命裡親歷的驚心動魄,與歷史浪潮中的觀念起伏,他們只得在文章裡娓娓道來。這樣「最後一課」裡的老師,和平時不太一樣。
書寫這一課的老師們,知道自己正在做出選擇。他們不只是被動地保存過去,也是站在此刻的抵抗 —— 抵抗遺憾,抵抗遺忘,抵抗被取消。
而這抵抗的核心,正是通過記憶,直指未來。
為什麼記住?記憶是身份的土壤,是意義的錨點。當一段歷史、一種精神被連根拔起,記憶成為我們重建連結的唯一線索。教學者的「最後一課」,不只是他們個人的告別,也是一整代香港知識人集體經歷的突然斷章。如果我們遺忘,斷裂的不僅是某個人的教學生涯,也是一整個時代的精神譜系——那種在課堂上與社會中同時踐行理念的方式,那種師生並肩面對歷史的勇氣。
記憶賦予「曾經存在」以尊嚴。但它並非懷舊的感傷。
留下「最後一課」,並不是懷念美好舊時光。它記錄的恰恰是那些無法被美化、正在思辨的掙扎,與行動在疼痛中的突然中止。它要讓那些被迫提前退場的人,不被簡化、不被扭曲地留在集體意識中,誠實面對歷史的複雜檢視。它不必被供奉,也不提供慰藉,而是要求承擔。
留下最後一課,是希望留下一把拒絕讓我們安於現狀的鑰匙,一個叩問當下的尖銳問題。那些在課堂中被中斷的對話,在我們當下的閱讀與思考中,因此得以延續。
這也是記憶正義的一部分——它要求我們不只是「記得」,而是以怎樣的方式記得。
記憶於未來是有用的。當一個時代被系統性遺忘,未來的人們將失去理解自身處境的歷史坐標,他們遭遇不公時,會以為那是前所未有的創痛,或命中註定的常態。他們將失去描述現實的語言和想像另一種可能的詞彙——正如我們曾經失去過的。
因此,記憶正是為未來保存一份至關重要的「認知底稿」與「可能性檔案」。當未來的某一天,有人再度追問「為什麼我們不能有另一種活法」時,這些被保存的記憶將作出回應:曾經有人如此生活、如此思考、如此相信過。這份記憶本身,就否定了「當下即永恆」的謊言,為未來的改變提供了歷史的依據與勇氣。
如此,我們今日埋下的記憶,便不是墓碑,而是路標。它或許不能指明一條確定的坦途,但它堅定地告訴走在未來暗夜裡的人們:你們此刻站立的地方,曾經有光。而光,來過一次,就可以再來。
願我們不只是記得。願我們在記憶中辨認出正義的尺度,在耕種時明白種子來自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