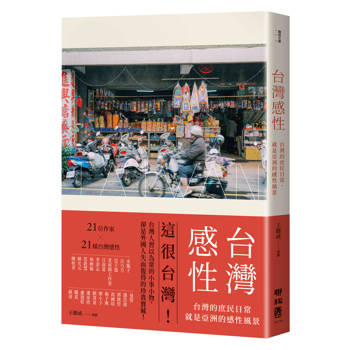【助人感性】穿上雨鞋,前往善的方向──花蓮光復救災小記 盛浩偉
這種內建想要「助人」的心情又是從何而來?
為什麼每每發生重大災難,台灣人都如此熱心,願意奉獻呢?
「明天要去花蓮光復。想起我們以前『八八風災』去台南。」我這樣回覆了友人Y在社群媒體上,一則標記了我的限時動態。限時動態本身跟我回覆的內容沒有什麼關係,純粹是因為看到那則限動標記通知的時間點,正巧在我購買好前往光復的車票並訂完住宿之後。
那是十月的第一個週末,也是「樺加沙颱風」侵襲後隔一週的連假。風災的雨量導致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潰壩溢出,滾滾洪流挾帶大量泥沙奔向下游,沖毀橋墩堤防,淹沒花蓮光復鄉一帶。危急的片段不斷在新聞及社群媒體上播送,空拍畫面裡,建築、房舍、農地、車輛、人,全覆沒在一片灰黑淤泥之下,像災難電影那樣誇張,真實到令人感覺不真實。
▎未竟的遺憾,以行動補足
幾天之內,電腦和手機的視窗被災難景象占據,看見這些,腦海閃過的念頭是「我能做些什麼?」迅速檢視過一遍自己的狀態、能力,還有手邊的工作及行程安排,發現自己不太有幫忙的餘裕,於是點開衛生福利部的捐款專案捐了一筆,可心頭仍有種難以言喻的未完之感。
已經算是盡一份力了,但不知為何,仍感覺遠遠不夠。
又過了一兩天,網路上開始看到不少志願者前往光復協助災後重建,也有熱心人士整理出幾個「如何當志工」的懶人包,無論是加入專業的救災、慈善團體或者自行前往,皆有明確的步驟指引,此外還有現場即時狀況、地理環境分析、裝備如何準備、具體協助方式有哪些,甚至交通或住宿等相關資訊,這些都清清楚楚,一應俱全。不斷更新的即時資訊大大降低了門檻,讓人更容易在其中找到自己施得上力的地方,也就更激起人們前往擔任志工的意願;至少我,就是因為更能掌握當地狀況而下定決心,要趁著連假前往光復。
說是連假,共有三天,但因為首日白天已有安排,且假期結束後手邊還有繁瑣的工作需先準備,再加上前往當地的車程頗長,零零總總計算下來,能專心投注在災區的時間反倒所剩不多。我一邊查著火車車次,一邊苦惱行程安排,最終才決定,在連假第一天的當晚先搭夜車直驅花蓮,深夜在市區簡便過夜,隔日一早再搭區間車前往光復。如此一來,至少能在光復待上一個整日,將協助時間最大化,到傍晚收工後返抵花蓮,再慢慢搭車回台北。這樣連假的最後一天還能在家休息恢復精力,準備隔日開工。心中計劃擬定,遂馬上開始執行,確保了車票及住宿,接著,就是Y在限動上標記我,傳來的通知。
很快Y就回覆了我。「我也想去,但還沒有車票。」他說:「還是我們一起?」
真是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回答。
我與Y從高中一年級就結識,如今Y位居公司要職,事務既繁且重,假日也經常不得閒,平時想見上一面都不容易,居然,就這麼碰巧有共同的空檔。然而,在送出訊息的當下,其實我就隱約預感了Y的反應。畢竟十六年前的八八風災也是這樣,大學時還住同寢室的我們看到新聞,頗有默契地都想要出一臂之力,簡單交換了點想法,隔日就憑著一股衝勁動身南下。
時移事往,許多細節早已模糊,印象裡,八八風災受創嚴重的地區同樣滿目瘡痍,只是當年的志工行,最終僅僅被分配到某個學校的禮堂,搬運各界盛情捐贈的乾糧零食礦泉水。沒看見破損的屋舍,沒看見災區的生活景象與人的模樣,甚至好像幫忙一整天,連一點日光都沒有曝晒到,記得的只有磨石子地板的泥濘與雜沓的腳印。這次前往光復,會有種特別期許自己能真的幫上些什麼的心情,或許,多少也是出於過往這段經驗的緣故吧。
▎在日常添購雨鞋的異樣感
我把行程計劃告訴Y,他還需要點時間確認,我則趁著這空檔出門添購必要裝備。其實據網路資訊,光復當地——更準確地說,是光復車站前廣場的救災志工集散處——救災物資並不匱乏,除了飲食之外,鏟子、手套、護目鏡、口罩、毛巾、清涼貼布等也都非常充足,甚至連雨鞋都有前人遺留。想當志工者只要準備髒了不心疼的衣褲,以及極少量的個人必需品即可。只是網路資訊也特別提醒,當地淤泥深厚,難保泥底藏有銳物,故建議鞋底務必夠厚,最好還要再加內墊保護腳底,避免意外穿刺受傷;然而如此一來雨鞋更加密不透氣,整天穿著勢必悶出大量汗濕,沾滿個人分泌氣味,所以介意二手雨鞋者,最好還是自備。
這倒令我遲疑了。也才意識到,雨鞋竟是這麼微妙的東西:它絕非陌生之物,平常卻又幾乎不曾穿上。只因我早就被都市生活寵壞,日常行住坐臥已過度可控,雨日單靠現今鞋款常見的防潑水就已足夠,並沒有什麼非得涉足大水或行過沼窪的機會。這樣,要為了救災特地買一雙,似乎稍嫌浪費又不環保。然而,確實又如網路資訊提醒,雨鞋在這種狀況下已經可算是私人衛生用品,自備一雙亦不為過。苦苦考量之下,最終還是傾向了後者。到了社區鄰近的生活用品百貨,向櫃檯詢問雨鞋在哪,老闆立刻反問:「要去救災?」我點點頭。老闆又說:「那要買有束帶的,水才不會從鞋筒倒灌。」接著補上一句:「這種只剩一雙。」聽到這句話,忽然有種沒來由的結伴感。明明無法確知雨鞋是否都是被像我這樣想要前往光復的人買走,心裡卻還是這樣擅自認定了。
備齊必需品,Y也傳來訊息確定同行,還邀了另一位朋友作伴,但搭的是比我更晚的末班車。交換完資訊,相互檢查彼此準備的東西有無缺漏,對過行程,我差不多也該整理行李,準備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