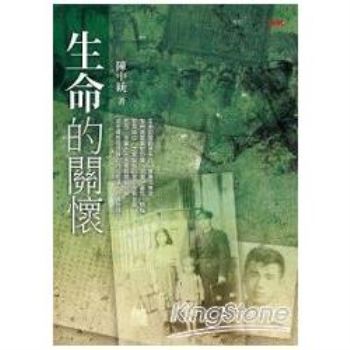第十章 死囚的槍決輓歌
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 警總景美看守所
靜!靜!靜!每一個夜晚,除了偶爾傳來衛兵在長廊如貓一般的走動聲,便是「難友」們入睡的鼾聲,偶爾,也會突然的有大吼的喊叫聲,可能是某位難友從噩夢中突然的驚叫吧?那時,我會從安寧的睡眠中半睡,也會聽到衛兵急速的跑步聲,隨即聽到他在傳來吼叫聲的囚房急匆匆的問語:
「是誰?是誰在大吼大叫?」當然,得不到回答,一切又回復到靜寂狀態。雖然,曾有難友告訴我,假使被判了極刑的人,大部分拉出去、架出去、拖去的時刻,都是在凌晨的四、五點時刻,將會聽到死囚面對死亡的哀號,以及腳鐐的撞擊聲。而那恐懼的淒厲嚎哭與喊叫,在長廊裡逐漸遠去,使所有囚房的囚徒不得不驚醒而惶恐,尤其對那死刑已確定的人,更是沉重的一擊。我轉押到景美看守所,尚未見識到這種淒慘的情景,雖然同房的藍振基已是……。
今天,晨曦還未升起吧?因為,從高高的小鐵窗,根本看不到晨曦到黎明的到來。什麼時間?我無法知道,只是一陣沉重的皮靴聲,遠遠的傳來,那不是平時聽到只有一名衛兵的急速步履,而是幾名士兵的皮靴聲,由遠而近,竟然在我們三十四號房停住了,接著鐵門被打開,走進三名班長,帶頭的是一名士官,我們被驚醒了,劉班長以「溫婉」的聲音唱名:
「藍振基!」這一唱名不打緊,藍老師在一角知道了這是自己最後的命運到了,整個人便顫抖癱瘓下來,哭喊著說:「我不是匪諜、我不是匪諜,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你們殘害忠良!」儘管如此,兩名班長已一個箭步走到他面前,如同老鷹抓小雞一般,一左一右將藍老師的手臂架起來,半拖半拉的帶出牢門!班長在後面,又對我們說:
「不要亂動,與你們無關。」我們當然無能為力,只能聽到藍老師拚命的哭喊:
「我不是匪諜、我不是匪諜,我是冤枉的……」淒厲悲切豪哭、夾雜著沉重的皮靴走在長廊的腳步,又混淆了藍老師腳鐐撞擊,如同一曲悲慘的交響樂,由高而低、由近而遠,逐漸在長廊的盡頭消失。聽說,到長廊盡頭,劉班長會以濕毛巾掩住死囚的嘴巴,而在長廊中任憑死囚哭嚎,具有「殺雞儆猴」的作用。
我們面面相覷,透過鐵窗外暗的燈光,我們再也不能入睡了!也不能相互交談,每個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默然祈禱,有的口念阿彌陀佛,有的向看不見的上帝祈禱:「生命來自塵土、也歸於塵土。」我呢?雖不是任何宗教信仰者,但也習慣性的默念著:「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算是為藍老師的訣別祈禱!
在我轉押到景美看守所時,藍振基雖不是和我們一般的「樂觀」「高興」,因為他已被戴上了一頂「紅帽子」的罪名,第一審已被判決死刑,覆判只是形式,否則也不會戴上腳鐐,和我們共處一室。在這期間,他曾與我交談,並且與我下車馬炮暗棋,消磨度日如年的囚徒生涯。因為下象棋,明棋要費腦力,暗棋一翻兩瞪眼,全靠運氣。當然,相處幾個月,他的情況、我的遭遇,彼此都有些了解。他「忠黨愛國」,曾是國民黨部隊的軍人,當初被共產黨俘虜,如果不「忠黨愛國」,他又何必冒著危險,從廈門游泳逃回到故鄉金門,又從金門來到台灣求學,派到彰化縣某國小擔任老師,結了婚,還有稚齡的兒女。只因上課之時,向小朋友說了幾句不該說的話,偶爾與同事談一談時局,便給安全的人事部門,打了小報告,說他為匪宣傳是匪諜,加上警總情治人員到他家逮捕、搜索時,又查收到他有三十年代某些大陸文藝作家的「禁書」,於是以第二條第一項起訴,落實了他的罪名。
今天,他終於走上「斷頭台」;面對無辜的罪名,我不禁在想,他真的犯下滔天大罪嗎?瘦小的他,能推翻這個軍、情、特龐大組織的國民黨政權嗎?國民黨不是以自由、民主自誇自大嗎?國民黨不是講萬惡的共匪,只會殺害老百姓,剝奪人民財產生命嗎?可是國民黨統治之下,像藍老師這樣的人,只說了幾句話、看了幾本「禁書」,就被剝奪了生命,剝奪了生存權,這又是什麼自由和民主?豈不是和共產政權一丘之貉嗎?藍老師走了,死不瞑目,他的妻子、兒女,將如何生活下去?是否又將被他人歧視,是否被稱為「匪諜」的妻子?「匪諜」的兒女?政治!政治!這就是國民黨口口聲聲的民主政治?或許國民黨還認為寬大慈悲呢?沒有滅九族,沒有將連保人一併收押治罪,已是實施「德政」的民主國呢!
藍老師被架走了,早餐之後,老士官進來收拾藍老師的遺物,其實關在牢中的死囚,有什麼遺物可收拾呢?只是一些換洗的內衣、內褲,以及什麼起訴書、判決書、上訴書狀之類的文件和盥洗的用具而已。這些雜物,老士官以一床軍毯,包在一起,我們靜靜的看著,誰也不敢問一聲,只見老士官包好,搖搖頭,似乎是對我們說,也似乎自言自語:
「唉!真夠慘了!挨了七、八槍,才斷了氣,何苦呢?看什麼共匪的書。」
我們不曉得在藍老師一堆遺物中有沒有遺書,在他臨終的一瞬間,他的腦海裡,想起的將是他的妻兒吧?和他共處一室幾個月,自然有同病相憐的感情,一旦少了他,我們油然地感覺到失落了什麼,他永遠不會再回來了!他的妻子稚子能不能看到他最後一面,因為我們知道很多被槍斃的人,是埋骨於亂葬坑中,家屬連收屍的權利也沒有,人間的慘事,莫過於此。
還有一種傳說,槍斃匪諜的劊子手,十有八九是憲兵擔任,這群憲兵被稱為「領袖的鐵衛隊」,他們的腦筋極多數是僵化的,被灌輸了黨即是國、國即是蔣介石,誰反對蔣介石,便是反對黨、反對國。因此,對匪諜視之如外國的仇敵,槍斃他們理所當然。他們槍斃了一名匪諜,如同在前線殺死一名敵人,聽說還有紅包可拿。這些「合法」槍殺自己同胞的劊子手,他們經過特殊訓練,也並不是每一個憲兵都是合格的「槍手」。據說,憲兵司令部的調查組,也是情治機構之一,與調查局、運事情報局、驚總保安處的情治人員,並駕齊驅,是抓「紅帽子」、「獨帽子」的核心。
自從藍老師走了之後,同樣被腳鐐住的郭子猷老師,最為鬱卒,因為他也是 「紅帽子」一頂,眼見藍老師走了,他內心的悲哀,從他的臉上就看出來了。我們無法勸慰他,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只有互相傳遞老鼠尾巴,吸它兩口菸來消除心中的愁悶。
第十一章 調服外役
一九七○年一月十三日 警總景美看守所
我在去年七月遭警總軍法處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叛亂罪」起訴,不到一個月軍事法庭即判決有期徒刑十五年。而後,阿爸聘請的兩位律師代我向國防部軍法局上訴,軍法是一次覆判確定,即不能再行上訴。我深切知道,上訴只是一種形式,是沒有希望中的希望。連替我辯護的律師,竟不敢在軍事法庭上為辯護無罪,只說一些什麼被告年輕啦!不知國家在戡亂時期青年應為黨國盡忠的教條道理,一時誤入歧途,懇請庭上憐憫,減輕其刑;更以我在服官役時,曾被選拔為「模範軍醫」,酌予減刑……。尤其那位鮑律師,一口浙江鄉音,說不到五分鐘,就坐下來了。這種辯護律師,只可說是「等因奉此」,如同公設辯護人一樣,不知道阿爸付出多少律師費了,白花花鈔票等於丟在水裡一樣。
軍法審判速審速決,真是快煞人也。只是未起訴之前,那漫長的偵訊,才會使我忐忑不安。當年十一月,國防部軍法局的覆判判決書,主文很簡單只有四個字:「聲請駁回」。換句話說,維持原判決十五年刑期,理由倒是洋洋灑灑一大篇。換句話說,沒有判我唯一死刑,已是「皇恩浩蕩」、「再生父母」了。
這個覆判早在預料之中,沒有加重我的罪刑,已是上帝保佑。大部分一審判決再聲請覆判的,以判亂罪名判決的被告,十有八九維持原判,很少減刑,一如我前面所說未加重罪刑,已是好命、好運。
解除禁見,每週四都有親友來面會,阿爸與憲子當然是每次都來的,而後岳父、岳母以及其他的親友,都抽空來見我,隔著窗子為我打氣,要我安心。我深知十五年的歲月是漫長的,曾透過岳母希望憲子申請與我離婚,岳母老人家對我說:
「這是你們年輕人的事,再說憲子嫁到陳家,就是陳家的媳婦,我們蔡家不管。」岳母這樣說,真使我感動,眼眶含著淚水,只能慚愧和內疚。憲子來時,我也曾當面提起離婚的事,她斷然拒絕。在景美看守所關著的有同學陳永善、初中同學吳耀忠。永善被判十年,在警總看守所住了不到一年,將他轉監到台東的泰源監獄去。我呢?仍然在景美看守所,只是隔一段時間,便換一間牢房。刑期確定後,黃輔導長曾召見我,和我談及調服外役的事,他很客氣的說:
「陳中統,我知道你是學醫的,家學淵源,又在日本岡山大學專攻血液學。所裡的醫務室,編制上只有兩名醫官,而所裡同學又這麼多,兩名醫官忙不過來,現在有名同學李吉村,也是學醫的、刑期將滿出獄,我想調你去服外役。不知道你……」我明白外役,多多少少有一些自由,尤其調到醫務室服外役,更是自由得多,要比關在牢房裡數那十四年的饅頭好多了。因此,我對黃輔導長說;
「能夠有這個機會,我樂意為同學服務。」
「只是你一定要遵守規定,不能出樓子,否則我無法向長官交代。」
「輔導長放心,我不會落跑,我還有家。」
「當然,服外役還要辦理保證手續。」黃輔導長如此熱心幫助我,我怎能不知好歹。
警總為了實施感化教育,在土城設立台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簡稱「生教所」後改仁愛教育實驗所簡稱「仁教所」,尤其對政治犯更要加強心理教育,依據我們的罪犯教育程度分為初級、中級、高級、研究四個班級,因此,我們在牢房裡互相稱難友,可是所方卻稱我們為同學。而感化教育的教材,當然是三民主義啦!蘇俄在中國!總統嘉言錄!要我們「研讀」,撰寫讀後心得,甚至開討論會,大罵萬惡的共匪、反攻大陸解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
景美看所守關押了不少名望很高的政治犯,例如郭衣洞(柏楊)、李敖、謝聰敏、魏廷朝、崔小萍、余登發、林火泉、陳永善……等,而且在國際媒體如《時代周刊》(Time)都有報導。我雖然是藉藉無名的陳中統,由於日本岡山大學校長及醫學部教授發動日本首相岸信介等政要聯名陳情,加上妹妹陳瑞麗及妹婿張子清在美國的奔走,因而美、日兩國的媒體,對我的逮捕、起訴、判決,也有了詳盡報導,雖不是轟動的焦點,卻使我在看守所裡有點分量,算是需注意的人犯。
判刑確定,唯一希望便是先能調服外役、而後再坐若干年囚牢,予以假釋(後來才知道政治犯不能假釋)。在景美看守所,調服外役的有不少人,視各人的刑責、教育程度以及在所裡的「表現」,方可調服外役,最重要的自然是在外面的關係了,否則只有坐滿刑期。小小景美看守所,設立了壓榨「囚徒」勞力的工程隊、洗衣工廠、縫衣工廠,以及其他人事部門、會計部門、廚房等;給予象徵性的工資,表示寬厚仁慈。除了醫務室之外,另外有一個圖書室。有一陣子,柏楊調到圖書室服外役。所謂圖書室,除了一些反共八股教條的書籍,其他的書籍,一概欠缺。連當天的報紙,也經過選擇,《中央日報》之外,便是中華、新生、《青年戰士報》(現改名為《青年日報》),連那民營的《中國時報》、《聯合報》一律不准擺在圖書室。可以看的也經剪洞開天窗。
一月二十七日,我開始到醫務室「見習」,原先調外役的醫師李吉村,刑期將滿出獄,為了協助孫治華、馮帝邦兩位醫官。李吉村是什麼案子,在看守所裡大家都是難友,不問也知道?李吉村難友告訴了我一些服外役應注意的事項,兩位醫官也很客氣,說明我主要的治療對象是所裡的同學。
服外役確實「自由」多了,不必大多數時間待在牢房中無所重心,只是與難友瞎擺龍門陣,而且時間久了,各人的案情,都耳熟能詳,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對我來說,無須在菸癮來的時候,只吸老鼠尾巴,而是堂而皇之,一支一支的吸那長命百歲的長壽菸;酒癮來的時候,也可以利用用餐時刻,喝上幾杯。有時,孫上尉或是馮上尉會派我到洗衣工廠、縫衣工廠去「出診」一番。
自從服外役後,不知道什麼緣故,除了替難友治療疾病,也替所裡及軍法處編制內的軍官、士兵,甚至軍眷治病。有時候還能到府出診,記得軍法處的周處長、劉副處長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有時患有小毛病,也會打電話給所長,指名陳中統出診。最初,還有兩名憲兵穿著便衣陪著我去,時間久了,知道我不會落跑,就讓我和一位班長一同出去。這可是我得其所哉的好時光,便利用空檔,約憲子出來見面,或是回家相聚。
在這期間,有幾件事是我「永銘」記憶,關在所裡絕大多數是良心犯,是對國民黨政權的專制極權表達合理的、文明的抗議,都是手無縛雞之力,又無武器、暴力傾向的接受相當高等教育的人士,只因提供國名黨政權應徹底實施民主政治的意見,被警總關押了進來,內心自然難免不平、口不服。在我服外役醫師那段期間;柏揚曾經一度以絕食抗議,三餐不吃一菜一飯,只喝些白開水。所長一見茲事體大,因為柏楊被關,已是「世界性」新聞,還有留美學人孫觀漢博士,甘冒大不諱,「上書」蔣介石請他無罪釋放柏楊,蔣介石當然不理,認為柏楊案件是法律問題,不是政治事件。更由他的愛子蔣經國透過新聞局表明,台灣沒有政治犯、思想犯,只有刑事犯。這種掩耳盜鈴的說詞,可說是自欺欺人。
柏楊絕食,康所長十個頭九個大,醫務室有孫、馮兩位醫官,無法以言詞說服柏揚,便要我這個外役醫師擔綱。憑良心講,我對心理學、精神醫學只可言一知半解,要以言詞打動柏揚使他不絕食,實在難堪大任。不過,我在成功中學高中部念書時,柏揚那時候在救國團擔任組長,應是蔣經國身邊的「紅人」,且在成功中學教國文,所教的班級比我高一、兩班。有了這關係層次,我心中有了主意,不妨以學生身分向老師勸言吧?不管他有沒有教過我,喊他一聲老師,相信柏揚對我這個外役醫師,不會嗤之以鼻,我便答應了康所長,和柏揚溝通去也。
柏楊的大名,我早在十多年前,他在《自立晚報》撰寫「倚夢閒話」時,就如雷貫耳,他的「醬缸學」,曾使我心有戚戚,惟我的性向只懂「欣賞」文學作品,如要自己拿起筆來寫一篇兩千字的文字則比斧頭還要重。
我第一次去看柏楊,尊稱他老師,他當然知道我是陳中統,是戴「獨帽」的,他是戴「紅帽」的。我對他介紹自己是成功高中畢業,這一聊,柏楊對我這個後生小子,自有另番情意,談興一濃,便無所不言。我便單刀直入:
「老師!聽說你絕食抗議?」
「是的!」他是河南人,鄉音並不重,倒是有些東北腔,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在東北大學讀歷史,本名郭衣洞。
「老師!何必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中統!你要曉得,蔣家早要抓我了,在四十七、八年時,我在《自立晚報》寫「倚夢閒話」,視我如眼中釘,除之而後快。現在以一幅無人島上的漫畫,因我加上了一句說白,藉此加上匪諜罪名,怎能使我……」柏楊越說越激昂。
「老師!絕食正符合他們心意,餓死,豈不更冤枉,國民黨會給你一個罪名『畏罪自殺』……」我不知道這樣說法是否妥當。經過幾次的個別溝通,柏楊總算給我這個學生一個面子,拍拍我的肩膀說:
「中統老弟,聽你的,不絕食,沉冤總有大白的一天。只要活著,總能使世人看清國民黨……」
我的任務達成,康所長非常高興,還給了我兩次特別面會的獎勵,和阿爸、憲子、岳父、岳母……能在接見室面對面交談,不是隔著一層厚玻璃,手拿聽筒說話。
一九六九年七月五日 警總景美看守所
靜!靜!靜!每一個夜晚,除了偶爾傳來衛兵在長廊如貓一般的走動聲,便是「難友」們入睡的鼾聲,偶爾,也會突然的有大吼的喊叫聲,可能是某位難友從噩夢中突然的驚叫吧?那時,我會從安寧的睡眠中半睡,也會聽到衛兵急速的跑步聲,隨即聽到他在傳來吼叫聲的囚房急匆匆的問語:
「是誰?是誰在大吼大叫?」當然,得不到回答,一切又回復到靜寂狀態。雖然,曾有難友告訴我,假使被判了極刑的人,大部分拉出去、架出去、拖去的時刻,都是在凌晨的四、五點時刻,將會聽到死囚面對死亡的哀號,以及腳鐐的撞擊聲。而那恐懼的淒厲嚎哭與喊叫,在長廊裡逐漸遠去,使所有囚房的囚徒不得不驚醒而惶恐,尤其對那死刑已確定的人,更是沉重的一擊。我轉押到景美看守所,尚未見識到這種淒慘的情景,雖然同房的藍振基已是……。
今天,晨曦還未升起吧?因為,從高高的小鐵窗,根本看不到晨曦到黎明的到來。什麼時間?我無法知道,只是一陣沉重的皮靴聲,遠遠的傳來,那不是平時聽到只有一名衛兵的急速步履,而是幾名士兵的皮靴聲,由遠而近,竟然在我們三十四號房停住了,接著鐵門被打開,走進三名班長,帶頭的是一名士官,我們被驚醒了,劉班長以「溫婉」的聲音唱名:
「藍振基!」這一唱名不打緊,藍老師在一角知道了這是自己最後的命運到了,整個人便顫抖癱瘓下來,哭喊著說:「我不是匪諜、我不是匪諜,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你們殘害忠良!」儘管如此,兩名班長已一個箭步走到他面前,如同老鷹抓小雞一般,一左一右將藍老師的手臂架起來,半拖半拉的帶出牢門!班長在後面,又對我們說:
「不要亂動,與你們無關。」我們當然無能為力,只能聽到藍老師拚命的哭喊:
「我不是匪諜、我不是匪諜,我是冤枉的……」淒厲悲切豪哭、夾雜著沉重的皮靴走在長廊的腳步,又混淆了藍老師腳鐐撞擊,如同一曲悲慘的交響樂,由高而低、由近而遠,逐漸在長廊的盡頭消失。聽說,到長廊盡頭,劉班長會以濕毛巾掩住死囚的嘴巴,而在長廊中任憑死囚哭嚎,具有「殺雞儆猴」的作用。
我們面面相覷,透過鐵窗外暗的燈光,我們再也不能入睡了!也不能相互交談,每個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默然祈禱,有的口念阿彌陀佛,有的向看不見的上帝祈禱:「生命來自塵土、也歸於塵土。」我呢?雖不是任何宗教信仰者,但也習慣性的默念著:「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算是為藍老師的訣別祈禱!
在我轉押到景美看守所時,藍振基雖不是和我們一般的「樂觀」「高興」,因為他已被戴上了一頂「紅帽子」的罪名,第一審已被判決死刑,覆判只是形式,否則也不會戴上腳鐐,和我們共處一室。在這期間,他曾與我交談,並且與我下車馬炮暗棋,消磨度日如年的囚徒生涯。因為下象棋,明棋要費腦力,暗棋一翻兩瞪眼,全靠運氣。當然,相處幾個月,他的情況、我的遭遇,彼此都有些了解。他「忠黨愛國」,曾是國民黨部隊的軍人,當初被共產黨俘虜,如果不「忠黨愛國」,他又何必冒著危險,從廈門游泳逃回到故鄉金門,又從金門來到台灣求學,派到彰化縣某國小擔任老師,結了婚,還有稚齡的兒女。只因上課之時,向小朋友說了幾句不該說的話,偶爾與同事談一談時局,便給安全的人事部門,打了小報告,說他為匪宣傳是匪諜,加上警總情治人員到他家逮捕、搜索時,又查收到他有三十年代某些大陸文藝作家的「禁書」,於是以第二條第一項起訴,落實了他的罪名。
今天,他終於走上「斷頭台」;面對無辜的罪名,我不禁在想,他真的犯下滔天大罪嗎?瘦小的他,能推翻這個軍、情、特龐大組織的國民黨政權嗎?國民黨不是以自由、民主自誇自大嗎?國民黨不是講萬惡的共匪,只會殺害老百姓,剝奪人民財產生命嗎?可是國民黨統治之下,像藍老師這樣的人,只說了幾句話、看了幾本「禁書」,就被剝奪了生命,剝奪了生存權,這又是什麼自由和民主?豈不是和共產政權一丘之貉嗎?藍老師走了,死不瞑目,他的妻子、兒女,將如何生活下去?是否又將被他人歧視,是否被稱為「匪諜」的妻子?「匪諜」的兒女?政治!政治!這就是國民黨口口聲聲的民主政治?或許國民黨還認為寬大慈悲呢?沒有滅九族,沒有將連保人一併收押治罪,已是實施「德政」的民主國呢!
藍老師被架走了,早餐之後,老士官進來收拾藍老師的遺物,其實關在牢中的死囚,有什麼遺物可收拾呢?只是一些換洗的內衣、內褲,以及什麼起訴書、判決書、上訴書狀之類的文件和盥洗的用具而已。這些雜物,老士官以一床軍毯,包在一起,我們靜靜的看著,誰也不敢問一聲,只見老士官包好,搖搖頭,似乎是對我們說,也似乎自言自語:
「唉!真夠慘了!挨了七、八槍,才斷了氣,何苦呢?看什麼共匪的書。」
我們不曉得在藍老師一堆遺物中有沒有遺書,在他臨終的一瞬間,他的腦海裡,想起的將是他的妻兒吧?和他共處一室幾個月,自然有同病相憐的感情,一旦少了他,我們油然地感覺到失落了什麼,他永遠不會再回來了!他的妻子稚子能不能看到他最後一面,因為我們知道很多被槍斃的人,是埋骨於亂葬坑中,家屬連收屍的權利也沒有,人間的慘事,莫過於此。
還有一種傳說,槍斃匪諜的劊子手,十有八九是憲兵擔任,這群憲兵被稱為「領袖的鐵衛隊」,他們的腦筋極多數是僵化的,被灌輸了黨即是國、國即是蔣介石,誰反對蔣介石,便是反對黨、反對國。因此,對匪諜視之如外國的仇敵,槍斃他們理所當然。他們槍斃了一名匪諜,如同在前線殺死一名敵人,聽說還有紅包可拿。這些「合法」槍殺自己同胞的劊子手,他們經過特殊訓練,也並不是每一個憲兵都是合格的「槍手」。據說,憲兵司令部的調查組,也是情治機構之一,與調查局、運事情報局、驚總保安處的情治人員,並駕齊驅,是抓「紅帽子」、「獨帽子」的核心。
自從藍老師走了之後,同樣被腳鐐住的郭子猷老師,最為鬱卒,因為他也是 「紅帽子」一頂,眼見藍老師走了,他內心的悲哀,從他的臉上就看出來了。我們無法勸慰他,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只有互相傳遞老鼠尾巴,吸它兩口菸來消除心中的愁悶。
第十一章 調服外役
一九七○年一月十三日 警總景美看守所
我在去年七月遭警總軍法處以「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叛亂罪」起訴,不到一個月軍事法庭即判決有期徒刑十五年。而後,阿爸聘請的兩位律師代我向國防部軍法局上訴,軍法是一次覆判確定,即不能再行上訴。我深切知道,上訴只是一種形式,是沒有希望中的希望。連替我辯護的律師,竟不敢在軍事法庭上為辯護無罪,只說一些什麼被告年輕啦!不知國家在戡亂時期青年應為黨國盡忠的教條道理,一時誤入歧途,懇請庭上憐憫,減輕其刑;更以我在服官役時,曾被選拔為「模範軍醫」,酌予減刑……。尤其那位鮑律師,一口浙江鄉音,說不到五分鐘,就坐下來了。這種辯護律師,只可說是「等因奉此」,如同公設辯護人一樣,不知道阿爸付出多少律師費了,白花花鈔票等於丟在水裡一樣。
軍法審判速審速決,真是快煞人也。只是未起訴之前,那漫長的偵訊,才會使我忐忑不安。當年十一月,國防部軍法局的覆判判決書,主文很簡單只有四個字:「聲請駁回」。換句話說,維持原判決十五年刑期,理由倒是洋洋灑灑一大篇。換句話說,沒有判我唯一死刑,已是「皇恩浩蕩」、「再生父母」了。
這個覆判早在預料之中,沒有加重我的罪刑,已是上帝保佑。大部分一審判決再聲請覆判的,以判亂罪名判決的被告,十有八九維持原判,很少減刑,一如我前面所說未加重罪刑,已是好命、好運。
解除禁見,每週四都有親友來面會,阿爸與憲子當然是每次都來的,而後岳父、岳母以及其他的親友,都抽空來見我,隔著窗子為我打氣,要我安心。我深知十五年的歲月是漫長的,曾透過岳母希望憲子申請與我離婚,岳母老人家對我說:
「這是你們年輕人的事,再說憲子嫁到陳家,就是陳家的媳婦,我們蔡家不管。」岳母這樣說,真使我感動,眼眶含著淚水,只能慚愧和內疚。憲子來時,我也曾當面提起離婚的事,她斷然拒絕。在景美看守所關著的有同學陳永善、初中同學吳耀忠。永善被判十年,在警總看守所住了不到一年,將他轉監到台東的泰源監獄去。我呢?仍然在景美看守所,只是隔一段時間,便換一間牢房。刑期確定後,黃輔導長曾召見我,和我談及調服外役的事,他很客氣的說:
「陳中統,我知道你是學醫的,家學淵源,又在日本岡山大學專攻血液學。所裡的醫務室,編制上只有兩名醫官,而所裡同學又這麼多,兩名醫官忙不過來,現在有名同學李吉村,也是學醫的、刑期將滿出獄,我想調你去服外役。不知道你……」我明白外役,多多少少有一些自由,尤其調到醫務室服外役,更是自由得多,要比關在牢房裡數那十四年的饅頭好多了。因此,我對黃輔導長說;
「能夠有這個機會,我樂意為同學服務。」
「只是你一定要遵守規定,不能出樓子,否則我無法向長官交代。」
「輔導長放心,我不會落跑,我還有家。」
「當然,服外役還要辦理保證手續。」黃輔導長如此熱心幫助我,我怎能不知好歹。
警總為了實施感化教育,在土城設立台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簡稱「生教所」後改仁愛教育實驗所簡稱「仁教所」,尤其對政治犯更要加強心理教育,依據我們的罪犯教育程度分為初級、中級、高級、研究四個班級,因此,我們在牢房裡互相稱難友,可是所方卻稱我們為同學。而感化教育的教材,當然是三民主義啦!蘇俄在中國!總統嘉言錄!要我們「研讀」,撰寫讀後心得,甚至開討論會,大罵萬惡的共匪、反攻大陸解救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
景美看所守關押了不少名望很高的政治犯,例如郭衣洞(柏楊)、李敖、謝聰敏、魏廷朝、崔小萍、余登發、林火泉、陳永善……等,而且在國際媒體如《時代周刊》(Time)都有報導。我雖然是藉藉無名的陳中統,由於日本岡山大學校長及醫學部教授發動日本首相岸信介等政要聯名陳情,加上妹妹陳瑞麗及妹婿張子清在美國的奔走,因而美、日兩國的媒體,對我的逮捕、起訴、判決,也有了詳盡報導,雖不是轟動的焦點,卻使我在看守所裡有點分量,算是需注意的人犯。
判刑確定,唯一希望便是先能調服外役、而後再坐若干年囚牢,予以假釋(後來才知道政治犯不能假釋)。在景美看守所,調服外役的有不少人,視各人的刑責、教育程度以及在所裡的「表現」,方可調服外役,最重要的自然是在外面的關係了,否則只有坐滿刑期。小小景美看守所,設立了壓榨「囚徒」勞力的工程隊、洗衣工廠、縫衣工廠,以及其他人事部門、會計部門、廚房等;給予象徵性的工資,表示寬厚仁慈。除了醫務室之外,另外有一個圖書室。有一陣子,柏楊調到圖書室服外役。所謂圖書室,除了一些反共八股教條的書籍,其他的書籍,一概欠缺。連當天的報紙,也經過選擇,《中央日報》之外,便是中華、新生、《青年戰士報》(現改名為《青年日報》),連那民營的《中國時報》、《聯合報》一律不准擺在圖書室。可以看的也經剪洞開天窗。
一月二十七日,我開始到醫務室「見習」,原先調外役的醫師李吉村,刑期將滿出獄,為了協助孫治華、馮帝邦兩位醫官。李吉村是什麼案子,在看守所裡大家都是難友,不問也知道?李吉村難友告訴了我一些服外役應注意的事項,兩位醫官也很客氣,說明我主要的治療對象是所裡的同學。
服外役確實「自由」多了,不必大多數時間待在牢房中無所重心,只是與難友瞎擺龍門陣,而且時間久了,各人的案情,都耳熟能詳,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對我來說,無須在菸癮來的時候,只吸老鼠尾巴,而是堂而皇之,一支一支的吸那長命百歲的長壽菸;酒癮來的時候,也可以利用用餐時刻,喝上幾杯。有時,孫上尉或是馮上尉會派我到洗衣工廠、縫衣工廠去「出診」一番。
自從服外役後,不知道什麼緣故,除了替難友治療疾病,也替所裡及軍法處編制內的軍官、士兵,甚至軍眷治病。有時候還能到府出診,記得軍法處的周處長、劉副處長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有時患有小毛病,也會打電話給所長,指名陳中統出診。最初,還有兩名憲兵穿著便衣陪著我去,時間久了,知道我不會落跑,就讓我和一位班長一同出去。這可是我得其所哉的好時光,便利用空檔,約憲子出來見面,或是回家相聚。
在這期間,有幾件事是我「永銘」記憶,關在所裡絕大多數是良心犯,是對國民黨政權的專制極權表達合理的、文明的抗議,都是手無縛雞之力,又無武器、暴力傾向的接受相當高等教育的人士,只因提供國名黨政權應徹底實施民主政治的意見,被警總關押了進來,內心自然難免不平、口不服。在我服外役醫師那段期間;柏揚曾經一度以絕食抗議,三餐不吃一菜一飯,只喝些白開水。所長一見茲事體大,因為柏楊被關,已是「世界性」新聞,還有留美學人孫觀漢博士,甘冒大不諱,「上書」蔣介石請他無罪釋放柏楊,蔣介石當然不理,認為柏楊案件是法律問題,不是政治事件。更由他的愛子蔣經國透過新聞局表明,台灣沒有政治犯、思想犯,只有刑事犯。這種掩耳盜鈴的說詞,可說是自欺欺人。
柏楊絕食,康所長十個頭九個大,醫務室有孫、馮兩位醫官,無法以言詞說服柏揚,便要我這個外役醫師擔綱。憑良心講,我對心理學、精神醫學只可言一知半解,要以言詞打動柏揚使他不絕食,實在難堪大任。不過,我在成功中學高中部念書時,柏揚那時候在救國團擔任組長,應是蔣經國身邊的「紅人」,且在成功中學教國文,所教的班級比我高一、兩班。有了這關係層次,我心中有了主意,不妨以學生身分向老師勸言吧?不管他有沒有教過我,喊他一聲老師,相信柏揚對我這個外役醫師,不會嗤之以鼻,我便答應了康所長,和柏揚溝通去也。
柏楊的大名,我早在十多年前,他在《自立晚報》撰寫「倚夢閒話」時,就如雷貫耳,他的「醬缸學」,曾使我心有戚戚,惟我的性向只懂「欣賞」文學作品,如要自己拿起筆來寫一篇兩千字的文字則比斧頭還要重。
我第一次去看柏楊,尊稱他老師,他當然知道我是陳中統,是戴「獨帽」的,他是戴「紅帽」的。我對他介紹自己是成功高中畢業,這一聊,柏楊對我這個後生小子,自有另番情意,談興一濃,便無所不言。我便單刀直入:
「老師!聽說你絕食抗議?」
「是的!」他是河南人,鄉音並不重,倒是有些東北腔,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在東北大學讀歷史,本名郭衣洞。
「老師!何必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中統!你要曉得,蔣家早要抓我了,在四十七、八年時,我在《自立晚報》寫「倚夢閒話」,視我如眼中釘,除之而後快。現在以一幅無人島上的漫畫,因我加上了一句說白,藉此加上匪諜罪名,怎能使我……」柏楊越說越激昂。
「老師!絕食正符合他們心意,餓死,豈不更冤枉,國民黨會給你一個罪名『畏罪自殺』……」我不知道這樣說法是否妥當。經過幾次的個別溝通,柏楊總算給我這個學生一個面子,拍拍我的肩膀說:
「中統老弟,聽你的,不絕食,沉冤總有大白的一天。只要活著,總能使世人看清國民黨……」
我的任務達成,康所長非常高興,還給了我兩次特別面會的獎勵,和阿爸、憲子、岳父、岳母……能在接見室面對面交談,不是隔著一層厚玻璃,手拿聽筒說話。